三、广州城港与海上丝路的关系
| 内容出处: | 《丝绸之路与文明的对话》 图书 |
| 唯一号: | 320920020210005816 |
| 颗粒名称: | 三、广州城港与海上丝路的关系 |
| 分类号: | K928.6 |
| 页数: | 4 |
| 页码: | 273-276 |
| 摘要: | 广州对外贸易的繁荣与海上交通密不可分。广州“州城三重”,“紫绯满城,邑居逼侧”③,城港相连。“海边时有鬼市,半夜而合,鸡鸣而散,人从之,多得异物”④,民间外贸活动十分频繁。城南濒临珠江(亦称海),上述主管对外贸易的海阳馆即因在海的北面而得名。由于招待蕃商有“阅货之宴”和送行之宴,“货通师子国,乐奏武王台”①,多在海阳馆设宴。域外的“鲛人”、“蕃客”成为广州城内外一道亮丽的风景。海阳馆、粤王台之外,广江驿亦成为款待客商、达官贵人的津亭,李群玉有《中秋广江驿示韦益》⑤、《广江驿饯筵留别》,后者有“别筵欲尽秋,一醉海西楼”⑥。 |
| 关键词: | 阿克苏 广州城港 海上丝路 |
内容
广州对外贸易的繁荣与海上交通密不可分。广州港在广州城南,不仅可利用珠江与广大腹地相连,而且海潮还可直入港内,“向郡海潮迎”①,“春城海水边”②,兼有河港与海港之利。“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广州“州城三重”,“紫绯满城,邑居逼侧”③,城港相连。“海边时有鬼市,半夜而合,鸡鸣而散,人从之,多得异物”④,民间外贸活动十分频繁。“海郡雄蛮落,津亭壮越台。城隅百雉映,水曲万家开。里树桄榔出,时禽翡翠来”⑤,广州城水环曲绕,内地与海外物品皆汇聚于此,“大抵珠江、玳瑁之所聚”⑥。城南濒临珠江(亦称海),上述主管对外贸易的海阳馆即因在海的北面而得名。“岁贡随重译,年芳遍四时”⑦,“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⑧,“常闻岛夷俗,犀象满城邑”⑨。如此琳琅满目,价值连城的宝货,“人来皆望珠玑去”⑩;“此乡多宝玉”⑪,豪侈重商之风尤盛,“厥俗多豪侈,古来难致礼”⑫。由于招待蕃商有“阅货之宴”和送行之宴,“货通师子国,乐奏武王台”①,多在海阳馆设宴。“江上粤王台”②,今越秀山上,亦应是登高宴请场所,真可谓“楼台重蜃气,邑里杂鲛人”③;“波心涌楼阁,规外布星辰”。域外的“鲛人”、“蕃客”成为广州城内外一道亮丽的风景。“冠冕中华客,梯航异域臣,”“贡兼蛟女绢,俗重语儿巾。舶主腰藏宝,黄家砦起臣”④。海阳馆、粤王台之外,广江驿亦成为款待客商、达官贵人的津亭,李群玉有《中秋广江驿示韦益》⑤、《广江驿饯筵留别》,后者有“别筵欲尽秋,一醉海西楼”⑥。广江驿应在广州城偏西,不然何以称其楼为“海西楼”?不过,此驿多为官员来往送别场所,“楼台笼海色”⑦,沿海楼台亭榭不绝于岸,这与商贸活动和政客的往来有关。
新近考古发现也证明了唐代广州城对外贸易的发达。在今广州中山四路儿童公园的南越宫署遗址之上的唐地层中,出土了一批高级手工艺的原料和成品,有水晶、玻璃、象牙等,其中一件象牙印章,通高2.8厘米,印钮为外国人头像,曲发后梳,眼帘微垂,鼻梁宽挺,嘴唇厚实,实为唐时来自西域的胡人形象⑧。而唐代珠江边还在今广州市内文明路附近。而就在今广州文明路与北京路交汇处的丽都酒店的建筑工地,以及德政路担杆巷宿舍工地,分别发现了唐代的码头。而在今广州市一宫门前建人行天桥,钻柱孔时又发现了护岸的大木桩和木板⑨。因此,今广州文明路、德政路担杆巷一带,唐时为对外贸易港口所在,“当令输贡赋,不使外夷骄”⑩,贡舶贸易发达。
早在元和之前的贞元十四年(798年)王虔休任岭南节度使时,对原来建于广州城南、珠江滨畔的海阳馆作进一步修整,“近得海阳旧馆,前临广江,大槛飞轩,高明式叙,崇其栋宇。辨其名物,陆海珍藏,徇公忘私,俾其戴天捧日,见圣人一家之为贵;穷祥极瑞,知天子万方之司存。”面貌焕然一新。海阳馆不仅是“百宝丛货”汇聚、“天子万方之司存”的宝库之所①,而且因临珠江,交通便利,“始至有阅货之宴”②,归有送别之宴,招款外国使节、客商的客馆,亦称“岭南王馆”,此为市舶使代表中央行使对外贸易之所,也号“市舶使院”。岑仲勉先生以朱彧《萍洲可谈》、王象之《舆地纪胜》、黄佐嘉靖《广东通志》认为:“(宋)海山楼或即(唐)贞元时代临江之‘海阳旧馆’,宋盖承唐制而建设也。其地可能在今邮政总局至十三行附近,此处正对五洲,即今河南之鳌洲,‘鳌’‘五’双声,方音之转变也”③,当为正确。唐市舶使院的地理位置,为以后宋元海山楼及明市舶提举司署、清十三行等外贸商馆、办事机构皆设在城南沿江一带打下基础。虽然贞元、元和时,外贸发达,市舶使院一派繁荣景象,但官方祭祀南海神因夏季珠江风大浪急,加之台风时常发生,故广州刺史祭祀南海神多令副使代之,从元和后期孔戮任广州刺史始,以改往日副使祭祀之惯例,亲至南海神庙祭祀,为后代刺史仿效的榜样。民间祭祀因史料缺乏,难穷究竟,但不能说“海客”(域外客商)、当地商人和渔民,就没有祭祀南海神之举。从一般常理来说,保佑海上交通平安,期求商贸正常进行,应是南海神神职庇护范围之内,因此,唐代中后期,南海神亦随着商贸活动的发展,对外贸易的兴盛,官吏和渔商士民应继续崇祀这一神灵,不断修整和扩建,前引韩愈《南海神(广利王)庙碑》对南海神庙的扩建即是例证。
就在港口与广州城西南部一带,唐时外商多居住于此,时称“蕃坊”。蕃坊设立“蕃长”、“蕃酋”①,处理蕃商内部事务。蕃坊范围大体在今广州中山路以南、人民路以东、大德路以北、解放路以西一带,中心在今光塔街及其附近②。唐开成以前,广州“土人与蛮僚杂居,婚娶相通”。开成时,岭南节度使卢钧立法,“俾华蛮异处,婚聚不通,蛮人不得立田宅”③,加强蕃商管理。
值得一提的是,外国商舶的到来和回航,唐政府设宴款待,“牙樯迎海舶,铜鼓赛江神”④,沿江(海)有诸如龙舟的竞赛活动。海商平安到达与龙舟竞渡,都应以祭祀南海神为要。唐时这种风气已经形成。“瓦樽留海客,铜鼓赛江神”⑤,白居易、许浑皆有诗为证。皮日休“铜鼓夜敲溪上月,布帆晴照海边霞”⑥,亦应是岭南的写照。当然,岭南“岛夷徐市种,庙觋赵佗神”⑦,“北与南殊俗,身将货孰亲”⑧,“事事皆殊异”⑨,重鬼信巫风俗相沿,加之,“吾闻近南海,乃是魑魅乡”⑩,“水庙蛟龙集”⑪,“鲸吞洗钵水,犀触点灯船”⑫,赛神与对外贸易交通、岭南民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新近考古发现也证明了唐代广州城对外贸易的发达。在今广州中山四路儿童公园的南越宫署遗址之上的唐地层中,出土了一批高级手工艺的原料和成品,有水晶、玻璃、象牙等,其中一件象牙印章,通高2.8厘米,印钮为外国人头像,曲发后梳,眼帘微垂,鼻梁宽挺,嘴唇厚实,实为唐时来自西域的胡人形象⑧。而唐代珠江边还在今广州市内文明路附近。而就在今广州文明路与北京路交汇处的丽都酒店的建筑工地,以及德政路担杆巷宿舍工地,分别发现了唐代的码头。而在今广州市一宫门前建人行天桥,钻柱孔时又发现了护岸的大木桩和木板⑨。因此,今广州文明路、德政路担杆巷一带,唐时为对外贸易港口所在,“当令输贡赋,不使外夷骄”⑩,贡舶贸易发达。
早在元和之前的贞元十四年(798年)王虔休任岭南节度使时,对原来建于广州城南、珠江滨畔的海阳馆作进一步修整,“近得海阳旧馆,前临广江,大槛飞轩,高明式叙,崇其栋宇。辨其名物,陆海珍藏,徇公忘私,俾其戴天捧日,见圣人一家之为贵;穷祥极瑞,知天子万方之司存。”面貌焕然一新。海阳馆不仅是“百宝丛货”汇聚、“天子万方之司存”的宝库之所①,而且因临珠江,交通便利,“始至有阅货之宴”②,归有送别之宴,招款外国使节、客商的客馆,亦称“岭南王馆”,此为市舶使代表中央行使对外贸易之所,也号“市舶使院”。岑仲勉先生以朱彧《萍洲可谈》、王象之《舆地纪胜》、黄佐嘉靖《广东通志》认为:“(宋)海山楼或即(唐)贞元时代临江之‘海阳旧馆’,宋盖承唐制而建设也。其地可能在今邮政总局至十三行附近,此处正对五洲,即今河南之鳌洲,‘鳌’‘五’双声,方音之转变也”③,当为正确。唐市舶使院的地理位置,为以后宋元海山楼及明市舶提举司署、清十三行等外贸商馆、办事机构皆设在城南沿江一带打下基础。虽然贞元、元和时,外贸发达,市舶使院一派繁荣景象,但官方祭祀南海神因夏季珠江风大浪急,加之台风时常发生,故广州刺史祭祀南海神多令副使代之,从元和后期孔戮任广州刺史始,以改往日副使祭祀之惯例,亲至南海神庙祭祀,为后代刺史仿效的榜样。民间祭祀因史料缺乏,难穷究竟,但不能说“海客”(域外客商)、当地商人和渔民,就没有祭祀南海神之举。从一般常理来说,保佑海上交通平安,期求商贸正常进行,应是南海神神职庇护范围之内,因此,唐代中后期,南海神亦随着商贸活动的发展,对外贸易的兴盛,官吏和渔商士民应继续崇祀这一神灵,不断修整和扩建,前引韩愈《南海神(广利王)庙碑》对南海神庙的扩建即是例证。
就在港口与广州城西南部一带,唐时外商多居住于此,时称“蕃坊”。蕃坊设立“蕃长”、“蕃酋”①,处理蕃商内部事务。蕃坊范围大体在今广州中山路以南、人民路以东、大德路以北、解放路以西一带,中心在今光塔街及其附近②。唐开成以前,广州“土人与蛮僚杂居,婚娶相通”。开成时,岭南节度使卢钧立法,“俾华蛮异处,婚聚不通,蛮人不得立田宅”③,加强蕃商管理。
值得一提的是,外国商舶的到来和回航,唐政府设宴款待,“牙樯迎海舶,铜鼓赛江神”④,沿江(海)有诸如龙舟的竞赛活动。海商平安到达与龙舟竞渡,都应以祭祀南海神为要。唐时这种风气已经形成。“瓦樽留海客,铜鼓赛江神”⑤,白居易、许浑皆有诗为证。皮日休“铜鼓夜敲溪上月,布帆晴照海边霞”⑥,亦应是岭南的写照。当然,岭南“岛夷徐市种,庙觋赵佗神”⑦,“北与南殊俗,身将货孰亲”⑧,“事事皆殊异”⑨,重鬼信巫风俗相沿,加之,“吾闻近南海,乃是魑魅乡”⑩,“水庙蛟龙集”⑪,“鲸吞洗钵水,犀触点灯船”⑫,赛神与对外贸易交通、岭南民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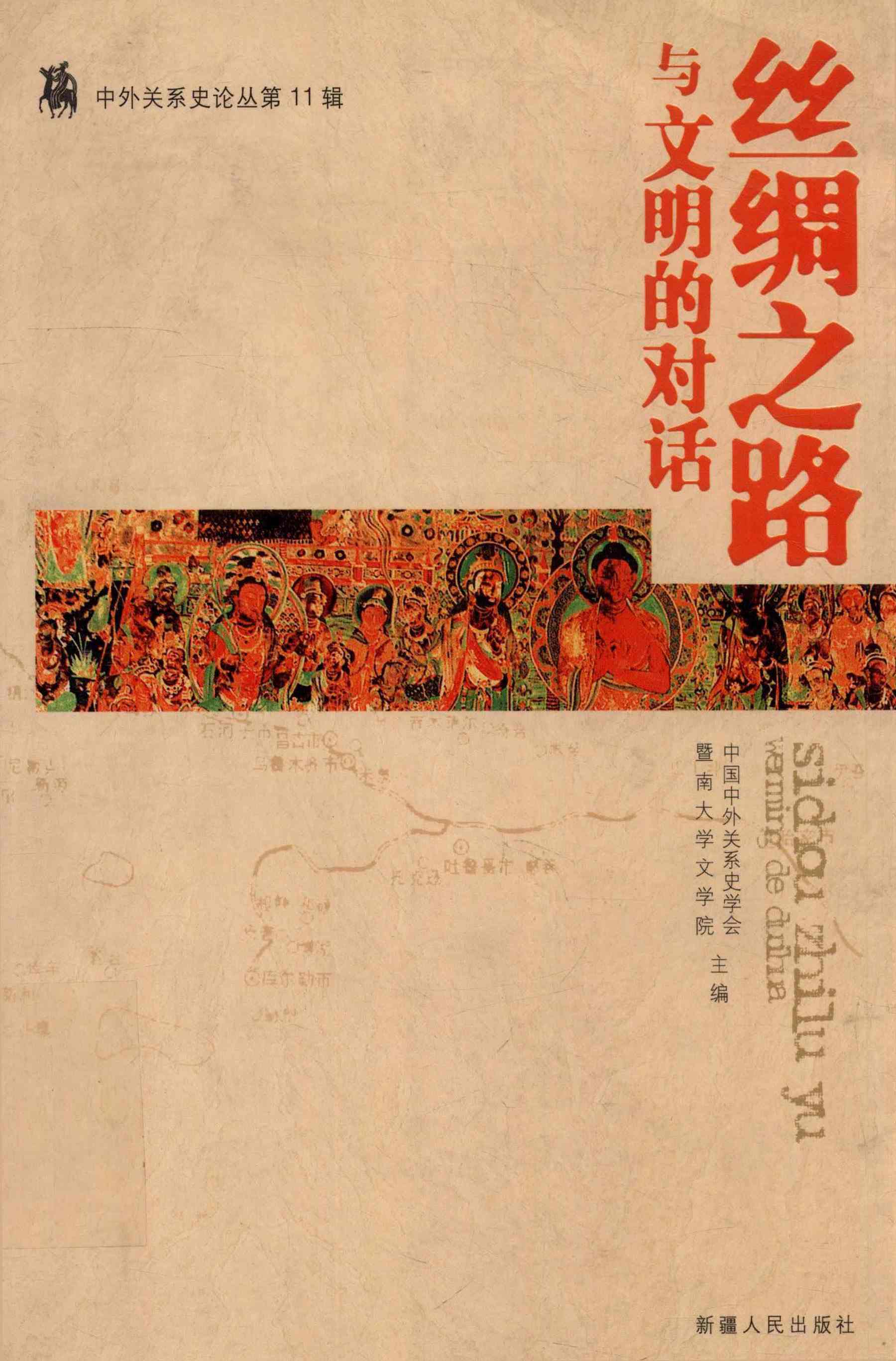
《丝绸之路与文明的对话》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本书收录了《丝绸之路在中亚北部地区的发展与作用》、《丝绸之路上的新和》、《古代新疆与阿拉伯文化》、《巴蜀古代文明与南方丝绸之路》、《21世纪中印关系史研究概述》、《喀什“香妃墓”辨误》、《19世纪西方国家对新疆的认知渠道》、《丝绸之路上的英国驻新疆领事馆考述》、《20世纪中印关系史研究概述》、《从丝绸文化传播看丝绸之路上的文化回流》等二十余篇文章。
阅读
相关人物
王元林
责任者
相关地名
阿克苏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