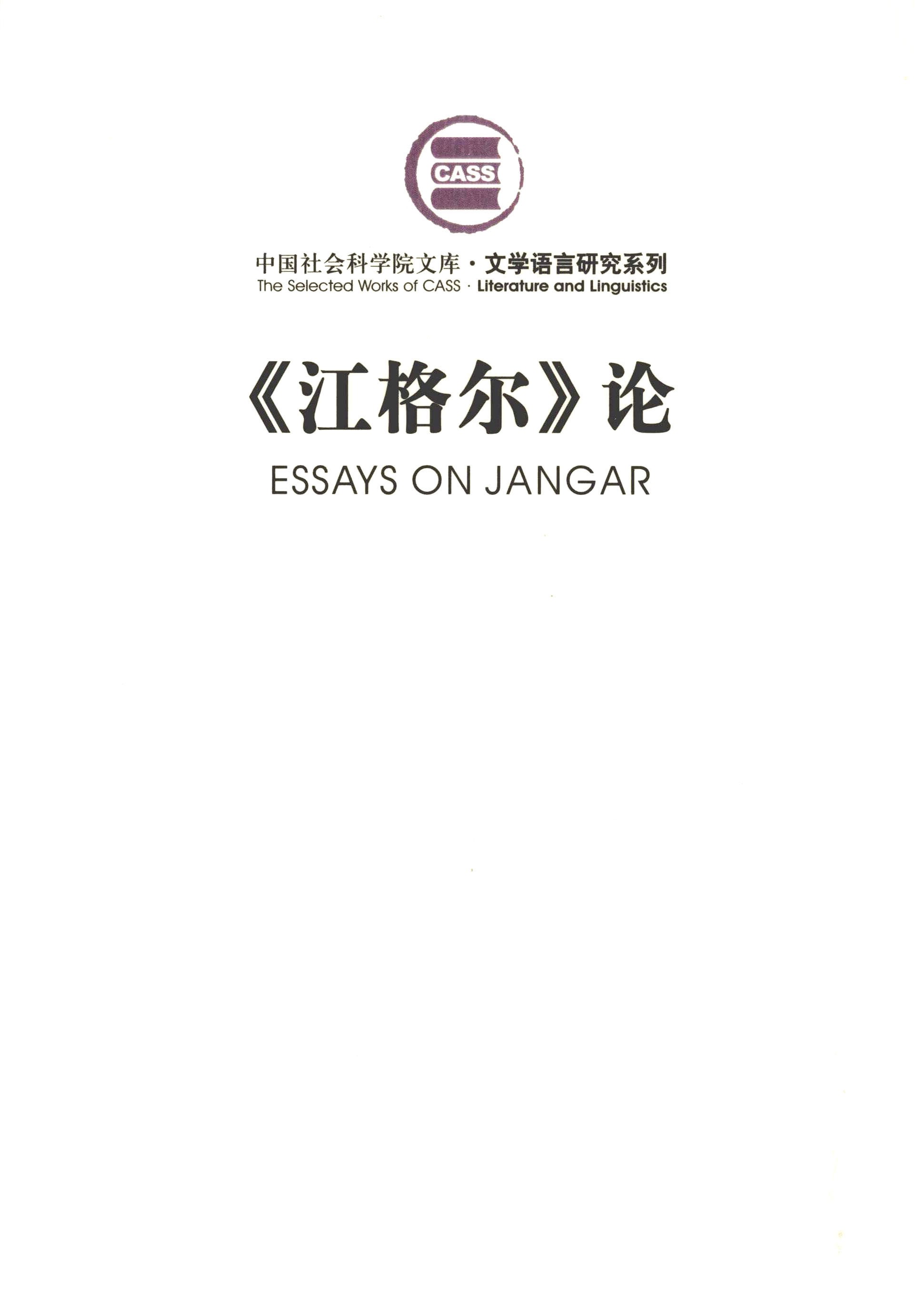四 长篇史诗的形成时代
| 内容出处: | 《《江格尔》论》 图书 |
| 唯一号: | 320020020210069770 |
| 颗粒名称: | 四 长篇史诗的形成时代 |
| 分类号: | I207;G633;G634 |
| 页数: | 10 |
| 页码: | 161-170 |
| 摘要: | 现有《江格尔》是一部并列复合型长篇英雄史诗。在它形成为长篇英雄史诗之前,是否存在过以江格尔为主人公的传说和小型英雄史诗,这是有待于考证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在它之前有过各种小型英雄史诗,《江格尔》继承和吸收了它们的现成的素材,其各章节(或诗篇)是以它们作为框架而形成的。因此,笔者不准备谈《江格尔》的最初产生时代,而只探讨它形成为长篇英雄史诗的时代。 |
| 关键词: | 江格尔 噶尔丹 萨满教 英雄史诗 卫拉特 |
内容
现有《江格尔》是一部并列复合型长篇英雄史诗。在它形成为长篇英雄史诗之前,是否存在过以江格尔为主人公的传说和小型英雄史诗,这是有待于考证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在它之前有过各种小型英雄史诗,《江格尔》继承和吸收了它们的现成的素材,其各章节(或诗篇)是以它们作为框架而形成的。因此,笔者不准备谈《江格尔》的最初产生时代,而只探讨它形成为长篇英雄史诗的时代。
1.根据文化渊源看,《江格尔》主要是在蒙古族本身的文化土壤上形成和发展的长篇英雄史诗。在本书前一部分中,笔者曾指出《江格尔》具有多层次文化结构,其中:既有古代文化,又有近代文化;既有蒙古文化,又有北方民族和汉族文化;既有早期神话、萨满文化因素,又有后来的佛教和印度、西藏文化因素;既有新疆各民族文化影响,又有波斯、阿拉伯文化影响。但其中有主要与次要之别,对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的产生起决定作用的是本民族口头文学作品,外来文化在使它丰富和多样化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蒙古口头文学对《江格尔》的形成起的主要作用如下:
(1)长篇英雄史诗是口头文学的一种巨型体裁,其中包括口头文学的各种小型样式。《江格尔》运用和吸收了蒙古古老的祝词、赞词、歌谣、谚语、咒语、神话、传说、故事和小型英雄史诗等样式的形式和艺术成就;
(2)《江格尔》借用了蒙古原始小型英雄史诗的现成素材,即利用了单篇型史诗和串联复合型史诗的题材、主题、情节、结构、母题、人物和艺术手法等方面的一些因素;
(3)《江格尔》的各个诗篇(各章节)是以蒙古小型史诗的基本情节作为框架而形成的。
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不是蒙古族第一部英雄史诗,更不是北方民族最早期的英雄史诗,不仅在它之前有过各种体裁的蒙古口头创作,而且也有过作为它艺术框架的数以百计的蒙古小型英雄史诗,如果不存在蒙古口头创作和小型英雄史诗,《江格尔》就缺乏产生的文化前提和艺术土壤。无疑,《江格尔》是在蒙古小型英雄史诗基础上形成的。它的形成晚于小型英雄史诗,这是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
那么,蒙古小型英雄史诗体裁是在什么时代产生的呢?
许多蒙古史学家认为,到公元11~12世纪蒙古氏族社会尚未结束,还处于部落战争和族外婚阶段。我们可以从《蒙古秘史》里清楚地看到这种现象。当然,史诗产生的那种“英雄时代”早已开始,但到11~12世纪还没有完全结束。因此,研究蒙古英雄史诗的一批学者认为,蒙古原始小型英雄史诗产生于11~12世纪。另有一批学者则认为,它的产生比这个时代还要早,可能最初产生于8~9世纪。同时,外国著名学者一致认为,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的产生晚于13世纪。研究突厥英雄史诗的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学者指出,突厥史诗共性的发生可能是属于突厥汗国时代(公元552~744年),个别人说《乌古斯》产生于公元4世纪,但没有进行考证。外国许多学者把蒙古史诗与突厥史诗进行比较,指出了它们在主要方面存在的共同性,并且探讨了这些共同性出现的原因,不少学者认为蒙古英雄史诗和突厥英雄史诗具有共同起源。笔者也曾发表过类似意见。众所周知,蒙古民族及其国家的形成是在13世纪。可是,蒙古原始小型英雄史诗,包括单篇型史诗和串联复合型史诗体裁的产生远远早于民族和国家的形成。笔者同意一些学者的看法,即蒙古史诗和突厥史诗产生在蒙古—突厥各部落共同居住于中央亚细亚和南西伯利亚时期。笔者认为,在这一大地区可能出现过一个大的共同的英雄史诗发生带,其中有过许多史诗发生点,在这个大的史诗发生带内,史诗点与史诗点之间有密切联系,它们相互影响,共同发展,因而逐渐形成了蒙古—突厥英雄史诗的共同性和相似现象。①随着蒙古—突厥各部落的迁徙和各个民族的形成,原有的那些史诗点变成为各个民族史诗和各个部族史诗,出现了蒙古—突厥英雄史诗的民族特征和地域特征。
在上述共同的史诗带内产生的是原始小型英雄史诗。后来,在各民族逐渐形成以后,原有的小型史诗进一步发展成为具有民族特点的长达万行或数万诗行的中篇和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和《玛纳斯》不属于原始史诗,也不是在上述共同的史诗发生带内产生的作品。而是柯尔克孜和卫拉特由西伯利亚西迁到中亚和新疆阿尔泰山一带之后,在封建时代为了表现当时的民族斗争和民族内部斗争,在原有小型英雄史诗的基础上,创作了长篇英雄史诗《玛纳斯》和《江格尔》。因此,在这两部长篇英雄史诗中,存在着一些古老的阿尔泰语系人民的史诗传统,同时,它们有了完全不同的内容和形式。拿卫拉特(斡亦剌惕)人来说,他们离开故乡安加拉河一带迁移到了阿尔泰山和额尔齐斯河一带游牧,并且同土尔扈特等部一起建立了早期四卫拉特联盟以后,约于15世纪开始为了反映四卫拉特的内讧和外战,运用原有小型英雄史诗的现成素材,把它加以修改和再创作,改变成并列复合型长篇史诗《江格尔》。因此,它是15世纪以后形成的长篇英雄史诗。
2.《江格尔》的社会原型是蒙古—卫拉特封建割据时代的现实生活。这部长篇英雄史诗的内容很广,其中对原始社会以来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上发生的事物和现象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这是由民间口头创作的特殊发展规律所决定的。口头创作有传承性和变异性,后期形成的作品不会不继承早期作品的传统。如前所述,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继承和借用了早期神话、传说、小型史诗、祝词、赞词、谚语和咒语等各种体裁的民间口头创作的一些内容和形式,因此,其中存在着匈奴时代以来的一些古老因素,甚至还有一些母系社会的因素。但我们必须注意一个问题,任何社会现象都有它的起点和终点,也就是说,各种社会现象都有它产生时间和消失时间。有的现象产生的很早,但它消失的也较早。可是,有的则不同,既产生的很早,又存在的时间很长,甚至有些原始社会产生的现象,至今还在民间有一定的遗迹。如萨满教一些习俗就是如此。有的地区萨满教还存在着,有的地区没有萨满了,可是萨满教的一些现象变成为民间风俗继续存在着。因此,不能只根据在一部长篇英雄史诗在民间口头创造中出现的个别古老现象和原始母题的产生时代,判断那部作品的产生时代。因为二者的产生时代不同。另一方面,对那些古老现象和原始母题而言,不但要知道它的产生时代,而且还需要了解它继续存在到什么时候,也就是要区别它的起点和终点。不能以它开始产生的时间代替它存在到最后一个时期的时间。在《江格尔》研究中存在着这种现象:根据一些古老现象,甚至把封建时代的现象也当做原始时代的现象去谈这部史诗的产生时代,这是不科学的。
因为,民间口头创作有变异性,《江格尔》在形成后的口头流传过程中打上了后期社会的烙印,其中出现了不少近几百年的内容。我们也不能根据那些后期增加的表面上的因素,去判断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形成的时代。
在《江格尔》中确实有一些原始社会的现象和近几百年的内容,但它们都是次要的因素,不是史诗的核心内容。笔者在前边“社会原型”中考证了作为史诗框架的核心内容,并指出,《江格尔》描绘的各汗国的社会状况、战争的性质和目的、社会军事政治制度、社会各阶层的结构以及人们的思想愿望同明代蒙古族封建割据时期西蒙古卫拉特地区社会现实相符。
这部史诗除总的内容与卫拉特社会现实相符之外,在一批诗篇中还有一些具体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反映。在前一个部分里,我们已经提到了阿拉奇汗的问题。
最值得注意的是在《江格尔》里多处提到了“四卫拉特”和准噶尔汗国的噶尔丹博硕克图汗的名字。噶尔丹(1644—1697)是准噶尔汗国的政治活动家和宗教活动家。早年他曾“投达赖喇嘛,习沙门法”。他曾得到了西藏僧俗上层实权人物的支持,打着达赖喇嘛的旗号,于1671年返回准噶尔,掌握了卫拉特的政教权,后来成为博硕克图汗。他从事禁止萨满教和传播黄教的活动,曾在特克斯河岸和伊犁河岸上修建了几座金顶、银顶大庙,让大批卫拉特儿童上寺庙当喇嘛,并向寺院划分所属百姓,称为“沙弥那尔”。因此,在《江格尔》中出现了崇拜达赖喇嘛和噶尔丹喇嘛的现象。如在《征服库尔勒·额尔德尼蟒古思之部》和《征服残暴的沙尔·古尔格汗之部》等长诗中说:勇士们“来到了噶尔丹·沙尔喇嘛庙,不声不响徒步走,将那嘎兴金殿绕行七千周,虔诚地徒步走,将那嘎兴金殿绕行八千回,走到了噶尔丹喇嘛面前,接受了他的摩顶”。①因噶尔丹是黄教徒,史诗称他为“沙尔喇嘛”。也许有人不会相信,“噶尔丹·沙尔喇嘛”就是指历史人物噶尔丹汗。可是在《江格尔》的一些诗篇中明确提到了“噶尔丹汗”。如在《征服乌图·查干蟒古思之部》中几处说:“一位贫穷的孤儿,骑着两岁小马,远离勇士江格尔的国土,在他乡异地漂流,去噶尔丹汗国途中,他看到了敌人,把雄狮洪古尔拖走。”②这里所说的“噶尔丹汗国”,不会不是历史人物噶尔丹博硕克图汗的准噶尔汗国。演唱者将江格尔的宝木巴地方与噶尔丹的准噶尔汗国分开,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有的人看来《江格尔》不是历史,宝木巴地方不是具体存在过的国家。有关噶尔丹的诗篇和情节的产生时代,不可能早于17世纪后半叶噶尔丹汗统治四卫拉特时期。
此外,在《江格尔》里存在着“四卫拉特”这一名称。科津院士曾正确指出了这个问题。有的地方说“土仁·杜尔本·汗”(统治国家的四位可汗)和“哈日·杜尔本·奥冉”(外部四个地区),有时则明确说“哈日·杜尔本·卫拉特”(外部四卫拉特),其中都包含着“四卫拉特”这个意思。卫拉特人看来,他们不是蒙古成吉思汗后裔大汗统治区内部的人,而是“哈日”(外部)四卫拉特人。史诗里不但有“四卫拉特”这一名称,有时还把江格尔和洪古尔也看做卫拉特人,如有一次雄狮洪古尔将单枪匹马出征时,江格尔劝他说,不能一个人去,应当与6012名勇士一同去消灭敌人。可是,洪古尔则不同意,说:“这样做会有损于哈日·杜尔本·卫拉特的英名,人家会笑话,说洪古尔惧怕外来敌人的使者,出征迎战还拉上了江格尔汗!”①有的地方说“我们卫拉特的乌兰·洪古尔”,当然,这里指的也是四卫拉特。②“四卫拉特”这个名称的出现,说明了《江格尔》的形成时代晚于13世纪,甚至晚于15世纪早期四卫拉特联盟的建立。
总之,据《江格尔》的社会内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部族名称看,它反映了蒙古族封建割据时代四卫拉特地区的内讧和外战,即描写了卫拉特与周围地区和民族的混战,其中包括卫拉特与东蒙古一些地区的斗争,也有与察合台汗后裔诸汗统治的蒙兀儿斯坦国的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乌兹别克人、诺盖人、维吾尔人之间进行的连绵不断的战争。根据史诗反映的这种社会内容看,《江格尔》初具长篇英雄史诗(或并列复合型史诗)规模的时代,是在从早期四卫拉特联盟的建立到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率部西迁之前(15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上半叶)这200年之间。当然,在这部史诗中也难免出现一些这个时代之前和之后的内容。
3.《江格尔》里用的词汇和地名,说明它是土尔扈特西迁以前在阿尔泰山和额尔齐斯河一带形成的。科津把江格尔与成吉思汗等同起来是错误的,但在他的研究中有不少合理的因素。他分析了史诗的词汇和地名,这不能不说明问题。科津对自己俄译《江格尔》的4部长诗进行分析后,得出如下结论:
在伏尔加河流域居住的卡尔梅克人的口语中有许多借用的俄语词汇,可是在上述4部中只发现了5个词:ura、knes、basmag、beder和sabla。这是晚期借用的几个词,若它在伏尔加河卡尔梅克人中产生的话,借用的俄语词汇比现在多得多。
史诗中多处出现了金、银、钢、陶瓷、丝绸和檀香等词,在这些词前边运用了各种古老的形容词,可是伏尔加河卡尔梅克人早已不熟悉这些形容词。在准噶尔的时候,卫拉特人生活在丝绸之路上。那些与草原商品有关的古老词汇,可能是在准噶尔时代出现的。
他分析的作品中约有60个地名,其中四分之三与山有关,而且这些山名的三分之一又同阿尔泰山联系在一起。此外,还有额尔齐斯河、科布多以及青藏地区的昭、锡莱依高勒等地名,同时,尚未发现伏尔加河一带的任何一个地名。这些现实说明了《江格尔》英雄们活动的范围在阿尔泰山南北、额尔齐斯河流域、科布多地区和青藏高原地带。①这就是卡尔梅克人西迁以前的故乡,它说明了这部史诗的形成时代。
近十多年来,中国学者巴达玛、贾木措(原来汉译为贾木查,后来自己改为贾木措,是同一人)、哈萨格拜等人又从中发现了一些新疆一带的地名。金峰考证了史诗里出现的各汗国的地理位置,认为阿鲁·宝木巴地方处于额尔齐斯河流域,在它的东方有东蒙古(四十万世界)、在西方有察合台汗国(八千世界),那尔图是天山以南库车、喀什噶尔到苏联七河一带地区。
众所周知,在17世纪20年代卡尔梅克人的祖先和鄂尔勒克率土尔扈特部游牧到伏尔加河一带去生活。科津研究的《江格尔》的4部长诗是19世纪中叶在伏尔加河一带卡尔梅克人中间记录的。远离故乡200余年的伏尔加河卡尔梅克人演唱的史诗里没有出现当地地名,反而有大量的阿尔泰山、额尔齐斯河、科布多、青海和西藏的地名以及中世纪准噶尔人的古老词汇,这不能不说是《江格尔》顽强地保留着它的形成地域和部族特征。史诗这种特征说明了它早在1630年土尔扈特西迁以前已在新疆一带形成。
4.如前所述,加·巴图那生等人在新疆搜集到了17世纪上半叶土尔扈特西迁到伏尔加河以前,在和鄂尔勒克的家乡有一位叫作土尔巴雅尔的江格尔奇能演唱《江格尔》的70部长诗的传说。这个传说与别尔克曼在伏尔加河下游的卡尔梅克人中所听到的历史人物策伯克多尔挤诺谚的事迹有密切联系。它们从侧面证明了英雄史诗《江格尔》早在17世纪上半叶已在新疆形成和发展。
5.卫拉特人的迁徙史和《江格尔》的流传情况也可以说明这一史诗的形成时代。卫拉特人的历史很复杂,他们经历了几次大迁徙,也经过了几次部落大融合阶段,现在的卫拉特人不是由有血缘关系的部落所组成的,但总体而言,他们还是属于古卫拉特人的后裔。蒙元时期史书称他们为“斡亦剌惕”,明代称“瓦剌”、“额鲁特”,清代以后写成“卫拉特”。在13世纪成吉思汗时代,斡亦刺惕人民居住在贝加尔湖西北安加拉河一带的八河流域,他们属于森林部落,故称“斡亦剌惕”(森林之民)。从成吉思汗时代起,他们向南迁徙,约于14~15世纪到新疆阿尔泰山一带游牧。后来约于15世纪30年代起与客列亦惕部出身的土尔扈特等部落联合形成了四卫拉特联盟,建立了卫拉特汗国,并曾经一度统一了东蒙古和西蒙古。17世纪初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率部众5万户,由新疆阿尔泰山一带游牧到了伏尔加河流域。过了100多年后,于1771年渥巴锡汗率部分土尔扈特人经过艰难困苦斗争终于回归新疆。留在伏尔加河西岸的就是俄国卡尔梅克人。这样卫拉特人的历史就有几个明显的阶段,这有利于我们断定《江格尔》的形成时代。
那么,《江格尔》到底是哪一时期形成的长篇史诗呢?
根据《江格尔》的流传情况看,它是于15世纪以后在新疆一带形成的。目前蒙古语族人民分散居住在东起大兴安岭,西至欧洲的伏尔加河西岸,南到长城,北至贝加尔湖周围广大地区的各民族人民之中。如前所述,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蒙古语族人民中存在着史诗流传的七大中心,它们是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巴尔虎—布里亚特地区,哲里木盟的扎鲁特—科尔沁地区,新疆一带的卫拉特地区,蒙古国的喀尔喀地区和西蒙古卫拉特地区,俄国伏尔加河西岸的卡尔梅克地区和贝加尔湖一带的布里亚特地区。在这七大中心中有些地区之间相隔数千公里,而且几百年来没有相互联系。可是单篇型史诗和串联复合型史诗在这些中心里普遍流传,这些史诗还在主要方面都有一些相似性。因此,笔者认为,单篇型史诗和串联复合型史诗是古代各蒙古部落的共同创作,它们产生于民族形成和国家形成以前各个蒙古部落共同聚居在南西伯利亚和中央亚细亚时期。可是,《江格尔》的流传则不同,它主要是广泛流传于新疆的卫拉特人和伏尔加河下游的卡尔梅克人中。在其他各中心里,《江格尔》很少流传,流传的部分也是在卫拉特人的影响下出现的。这种分布情况说明,《江格尔》不可能是各蒙古部落共同聚居时期的作品。它可能是卫拉特人脱离贝加尔湖一带的巴尔虎、布里亚特等蒙古部落,到新疆阿尔泰山一带去同土尔扈特等部一起建立了四卫拉特联盟以后形成的长篇英雄史诗。因此它形成时代的上限,应当在15世纪以后。
6.《江格尔》里的宗教形态也对断定其形成时代方面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国内外一批研究者曾注意过这个问题。
这部史诗的宗教形态有以下特点:
(1)萨满教因素和佛教因素同时并存,也就是说在史诗里,既有萨满教因素,又有佛教因素。
(2)萨满教因素和佛教因素,往往在一处对同一事物和现象的描写上融合在一起。
(3)萨满教处于衰弱状态,佛教处于上升状态之中。
这些现象反映了《江格尔》形成的时代特征。在蒙古—卫拉特历史上,曾出现过宗教处于上述状态的历史时期,而且这一时期的界限较分明。蒙古人有悠久的佛教文化传统,从13世纪中叶起,他们接触到了西藏佛教,尤其是由忽必烈时代起元朝宫廷和统治阶层接受了藏传佛教。但在这一时期,草原上的广大牧民群众尚未受到佛教的影响,在他们中间萨满教仍然占最重要地位。佛教第二次传入蒙古地方是从16世纪中叶开始,到16世纪末17世纪上半叶到了高速发展时期,土默特阿勒坦汗是最早在蒙古地方传播喇嘛教和禁止萨满教的重要人物。他于1573年邀请西藏黄教徒索南嘉错(后来被奉为三世达赖喇嘛)赴蒙古地方传教,但索南嘉错到1576年才前往会见了阿勒坦汗。从此以后,阿勒坦汗制定了新法律,以便保证传播喇嘛教,禁止萨满教,使呼和浩特成为喇嘛教中心,其附近修建了许多喇嘛庙。因为他弘扬佛法,得到了西藏喇嘛教首领的信任,三世达赖于1587年圆寂之后,从阿勒坦汗家族中发现了四世达赖喇嘛允丹嘉错(1588—1617),接着东蒙古也接受了喇嘛教。喀尔喀部阿巴岱汗曾拜见过达赖喇嘛,他于1586年为达赖喇嘛送给他的佛像修建了额尔德尼昭寺,又颁布了禁萨满教令。西蒙古四卫拉特地区也是从16世纪末起接受了喇嘛教。在卫拉特地区兴佛灭萨满教的主要人物是大喇嘛内济托音(1557—1653)和热迥巴·咱雅班智达(1599—1662)。土尔扈特部贵族出身的内济托音前往呼和浩特当喇嘛,他翻译了一批佛经。他从16世纪末起镇压卫拉特萨满,接着于1629~1653年间去内蒙古东部区传播黄教,同时,破坏了那里的萨满教活动。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于17世纪20年代帮助达赖喇嘛,在西藏战胜了噶举巴派。17世纪初西蒙古杜尔伯特、绰罗斯、和硕特,还有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在内的各部贵族都选送一个儿子去西藏当了喇嘛。在那些孩子中出现了卫拉特文化名人热迥巴·咱雅班智达。他于1617~1639年去西藏深造,回卫拉特地区后,按着西藏黄教领袖的旨意进行佛教活动,发布了禁萨满教令。他于1648年创造了适应卫拉特地方方言的托忒蒙古文,并于1650~1662年间用此文字翻译了《甘珠尔》等大量佛教典籍。在此以前,于1628~1629年察哈尔部林丹汗组织35名学者将《甘珠尔》译成了蒙古文。后来在乾隆时代的1742~1749年间蒙译出版了《丹珠尔》。此外,在卫拉特地区,传播黄教的一个重要人物是噶尔丹大喇嘛,他曾去西藏深造,于1671年赶回卫拉特地区参加了政权斗争。在1677年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错任命他弟子噶尔丹为卫拉特汗,让他掌握卫拉特政教权,进行政治活动和黄教活动。因此《江格尔》里多处称他为“噶尔丹·沙尔喇嘛”。
上述历史事件说明,从16世纪末始,不论在东蒙古地区,还是在西蒙古卫拉特地区,传播喇嘛教活动同迫害和禁止萨满教活动,几乎都是同步进行的。因此可以肯定《江格尔》所反映的佛教现象的上限,只能在这一时期以后,甚至有的更晚些,如历史人物噶尔丹·沙尔喇嘛的出现是17世纪下半叶的事情。颁布禁萨满教令之后,当然萨满不敢在公开场所活动了,但不能认为,有了禁令,萨满教的一切现象都不存在了。在民众头脑中,在他们的风俗习惯中,萨满教观念和习俗还长期存在着,而且后来佛教和萨满教调和了。正如瓦·海希西教授所说“在蒙古人中,喇嘛教可能最早与因兴奋而狂舞的萨满教调和了”,又说“鉴于喇嘛教在16~17世纪间长期地坚持迫害萨满教,后者被迫自我掩饰起来,并采纳了喇嘛教的历史和喇嘛教万神殿中的神祇,而且还使用了喇嘛教祈祷中的词句”。①因此,由16世纪末以后,在一段历史时期内,在蒙古人中间,出现了佛教因素和萨满教因素同时并存及相互交叉的现象。在这个时期,也就是萨满教走向了衰弱阶段,喇嘛教进入了强盛时期。《江格尔》反映了这个时代的蒙古族卫拉特地区的宗教现实。
根据以上种种事实看,《江格尔》形成为长篇英雄史诗的上限是15世纪30年代早期四卫拉特联盟建立以后,下限是17世纪20年代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率部众西迁以前,在这200年内《江格尔》的主要部分业已形成。
1.根据文化渊源看,《江格尔》主要是在蒙古族本身的文化土壤上形成和发展的长篇英雄史诗。在本书前一部分中,笔者曾指出《江格尔》具有多层次文化结构,其中:既有古代文化,又有近代文化;既有蒙古文化,又有北方民族和汉族文化;既有早期神话、萨满文化因素,又有后来的佛教和印度、西藏文化因素;既有新疆各民族文化影响,又有波斯、阿拉伯文化影响。但其中有主要与次要之别,对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的产生起决定作用的是本民族口头文学作品,外来文化在使它丰富和多样化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蒙古口头文学对《江格尔》的形成起的主要作用如下:
(1)长篇英雄史诗是口头文学的一种巨型体裁,其中包括口头文学的各种小型样式。《江格尔》运用和吸收了蒙古古老的祝词、赞词、歌谣、谚语、咒语、神话、传说、故事和小型英雄史诗等样式的形式和艺术成就;
(2)《江格尔》借用了蒙古原始小型英雄史诗的现成素材,即利用了单篇型史诗和串联复合型史诗的题材、主题、情节、结构、母题、人物和艺术手法等方面的一些因素;
(3)《江格尔》的各个诗篇(各章节)是以蒙古小型史诗的基本情节作为框架而形成的。
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不是蒙古族第一部英雄史诗,更不是北方民族最早期的英雄史诗,不仅在它之前有过各种体裁的蒙古口头创作,而且也有过作为它艺术框架的数以百计的蒙古小型英雄史诗,如果不存在蒙古口头创作和小型英雄史诗,《江格尔》就缺乏产生的文化前提和艺术土壤。无疑,《江格尔》是在蒙古小型英雄史诗基础上形成的。它的形成晚于小型英雄史诗,这是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
那么,蒙古小型英雄史诗体裁是在什么时代产生的呢?
许多蒙古史学家认为,到公元11~12世纪蒙古氏族社会尚未结束,还处于部落战争和族外婚阶段。我们可以从《蒙古秘史》里清楚地看到这种现象。当然,史诗产生的那种“英雄时代”早已开始,但到11~12世纪还没有完全结束。因此,研究蒙古英雄史诗的一批学者认为,蒙古原始小型英雄史诗产生于11~12世纪。另有一批学者则认为,它的产生比这个时代还要早,可能最初产生于8~9世纪。同时,外国著名学者一致认为,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的产生晚于13世纪。研究突厥英雄史诗的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学者指出,突厥史诗共性的发生可能是属于突厥汗国时代(公元552~744年),个别人说《乌古斯》产生于公元4世纪,但没有进行考证。外国许多学者把蒙古史诗与突厥史诗进行比较,指出了它们在主要方面存在的共同性,并且探讨了这些共同性出现的原因,不少学者认为蒙古英雄史诗和突厥英雄史诗具有共同起源。笔者也曾发表过类似意见。众所周知,蒙古民族及其国家的形成是在13世纪。可是,蒙古原始小型英雄史诗,包括单篇型史诗和串联复合型史诗体裁的产生远远早于民族和国家的形成。笔者同意一些学者的看法,即蒙古史诗和突厥史诗产生在蒙古—突厥各部落共同居住于中央亚细亚和南西伯利亚时期。笔者认为,在这一大地区可能出现过一个大的共同的英雄史诗发生带,其中有过许多史诗发生点,在这个大的史诗发生带内,史诗点与史诗点之间有密切联系,它们相互影响,共同发展,因而逐渐形成了蒙古—突厥英雄史诗的共同性和相似现象。①随着蒙古—突厥各部落的迁徙和各个民族的形成,原有的那些史诗点变成为各个民族史诗和各个部族史诗,出现了蒙古—突厥英雄史诗的民族特征和地域特征。
在上述共同的史诗带内产生的是原始小型英雄史诗。后来,在各民族逐渐形成以后,原有的小型史诗进一步发展成为具有民族特点的长达万行或数万诗行的中篇和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和《玛纳斯》不属于原始史诗,也不是在上述共同的史诗发生带内产生的作品。而是柯尔克孜和卫拉特由西伯利亚西迁到中亚和新疆阿尔泰山一带之后,在封建时代为了表现当时的民族斗争和民族内部斗争,在原有小型英雄史诗的基础上,创作了长篇英雄史诗《玛纳斯》和《江格尔》。因此,在这两部长篇英雄史诗中,存在着一些古老的阿尔泰语系人民的史诗传统,同时,它们有了完全不同的内容和形式。拿卫拉特(斡亦剌惕)人来说,他们离开故乡安加拉河一带迁移到了阿尔泰山和额尔齐斯河一带游牧,并且同土尔扈特等部一起建立了早期四卫拉特联盟以后,约于15世纪开始为了反映四卫拉特的内讧和外战,运用原有小型英雄史诗的现成素材,把它加以修改和再创作,改变成并列复合型长篇史诗《江格尔》。因此,它是15世纪以后形成的长篇英雄史诗。
2.《江格尔》的社会原型是蒙古—卫拉特封建割据时代的现实生活。这部长篇英雄史诗的内容很广,其中对原始社会以来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上发生的事物和现象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这是由民间口头创作的特殊发展规律所决定的。口头创作有传承性和变异性,后期形成的作品不会不继承早期作品的传统。如前所述,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继承和借用了早期神话、传说、小型史诗、祝词、赞词、谚语和咒语等各种体裁的民间口头创作的一些内容和形式,因此,其中存在着匈奴时代以来的一些古老因素,甚至还有一些母系社会的因素。但我们必须注意一个问题,任何社会现象都有它的起点和终点,也就是说,各种社会现象都有它产生时间和消失时间。有的现象产生的很早,但它消失的也较早。可是,有的则不同,既产生的很早,又存在的时间很长,甚至有些原始社会产生的现象,至今还在民间有一定的遗迹。如萨满教一些习俗就是如此。有的地区萨满教还存在着,有的地区没有萨满了,可是萨满教的一些现象变成为民间风俗继续存在着。因此,不能只根据在一部长篇英雄史诗在民间口头创造中出现的个别古老现象和原始母题的产生时代,判断那部作品的产生时代。因为二者的产生时代不同。另一方面,对那些古老现象和原始母题而言,不但要知道它的产生时代,而且还需要了解它继续存在到什么时候,也就是要区别它的起点和终点。不能以它开始产生的时间代替它存在到最后一个时期的时间。在《江格尔》研究中存在着这种现象:根据一些古老现象,甚至把封建时代的现象也当做原始时代的现象去谈这部史诗的产生时代,这是不科学的。
因为,民间口头创作有变异性,《江格尔》在形成后的口头流传过程中打上了后期社会的烙印,其中出现了不少近几百年的内容。我们也不能根据那些后期增加的表面上的因素,去判断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形成的时代。
在《江格尔》中确实有一些原始社会的现象和近几百年的内容,但它们都是次要的因素,不是史诗的核心内容。笔者在前边“社会原型”中考证了作为史诗框架的核心内容,并指出,《江格尔》描绘的各汗国的社会状况、战争的性质和目的、社会军事政治制度、社会各阶层的结构以及人们的思想愿望同明代蒙古族封建割据时期西蒙古卫拉特地区社会现实相符。
这部史诗除总的内容与卫拉特社会现实相符之外,在一批诗篇中还有一些具体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反映。在前一个部分里,我们已经提到了阿拉奇汗的问题。
最值得注意的是在《江格尔》里多处提到了“四卫拉特”和准噶尔汗国的噶尔丹博硕克图汗的名字。噶尔丹(1644—1697)是准噶尔汗国的政治活动家和宗教活动家。早年他曾“投达赖喇嘛,习沙门法”。他曾得到了西藏僧俗上层实权人物的支持,打着达赖喇嘛的旗号,于1671年返回准噶尔,掌握了卫拉特的政教权,后来成为博硕克图汗。他从事禁止萨满教和传播黄教的活动,曾在特克斯河岸和伊犁河岸上修建了几座金顶、银顶大庙,让大批卫拉特儿童上寺庙当喇嘛,并向寺院划分所属百姓,称为“沙弥那尔”。因此,在《江格尔》中出现了崇拜达赖喇嘛和噶尔丹喇嘛的现象。如在《征服库尔勒·额尔德尼蟒古思之部》和《征服残暴的沙尔·古尔格汗之部》等长诗中说:勇士们“来到了噶尔丹·沙尔喇嘛庙,不声不响徒步走,将那嘎兴金殿绕行七千周,虔诚地徒步走,将那嘎兴金殿绕行八千回,走到了噶尔丹喇嘛面前,接受了他的摩顶”。①因噶尔丹是黄教徒,史诗称他为“沙尔喇嘛”。也许有人不会相信,“噶尔丹·沙尔喇嘛”就是指历史人物噶尔丹汗。可是在《江格尔》的一些诗篇中明确提到了“噶尔丹汗”。如在《征服乌图·查干蟒古思之部》中几处说:“一位贫穷的孤儿,骑着两岁小马,远离勇士江格尔的国土,在他乡异地漂流,去噶尔丹汗国途中,他看到了敌人,把雄狮洪古尔拖走。”②这里所说的“噶尔丹汗国”,不会不是历史人物噶尔丹博硕克图汗的准噶尔汗国。演唱者将江格尔的宝木巴地方与噶尔丹的准噶尔汗国分开,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有的人看来《江格尔》不是历史,宝木巴地方不是具体存在过的国家。有关噶尔丹的诗篇和情节的产生时代,不可能早于17世纪后半叶噶尔丹汗统治四卫拉特时期。
此外,在《江格尔》里存在着“四卫拉特”这一名称。科津院士曾正确指出了这个问题。有的地方说“土仁·杜尔本·汗”(统治国家的四位可汗)和“哈日·杜尔本·奥冉”(外部四个地区),有时则明确说“哈日·杜尔本·卫拉特”(外部四卫拉特),其中都包含着“四卫拉特”这个意思。卫拉特人看来,他们不是蒙古成吉思汗后裔大汗统治区内部的人,而是“哈日”(外部)四卫拉特人。史诗里不但有“四卫拉特”这一名称,有时还把江格尔和洪古尔也看做卫拉特人,如有一次雄狮洪古尔将单枪匹马出征时,江格尔劝他说,不能一个人去,应当与6012名勇士一同去消灭敌人。可是,洪古尔则不同意,说:“这样做会有损于哈日·杜尔本·卫拉特的英名,人家会笑话,说洪古尔惧怕外来敌人的使者,出征迎战还拉上了江格尔汗!”①有的地方说“我们卫拉特的乌兰·洪古尔”,当然,这里指的也是四卫拉特。②“四卫拉特”这个名称的出现,说明了《江格尔》的形成时代晚于13世纪,甚至晚于15世纪早期四卫拉特联盟的建立。
总之,据《江格尔》的社会内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部族名称看,它反映了蒙古族封建割据时代四卫拉特地区的内讧和外战,即描写了卫拉特与周围地区和民族的混战,其中包括卫拉特与东蒙古一些地区的斗争,也有与察合台汗后裔诸汗统治的蒙兀儿斯坦国的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乌兹别克人、诺盖人、维吾尔人之间进行的连绵不断的战争。根据史诗反映的这种社会内容看,《江格尔》初具长篇英雄史诗(或并列复合型史诗)规模的时代,是在从早期四卫拉特联盟的建立到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率部西迁之前(15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上半叶)这200年之间。当然,在这部史诗中也难免出现一些这个时代之前和之后的内容。
3.《江格尔》里用的词汇和地名,说明它是土尔扈特西迁以前在阿尔泰山和额尔齐斯河一带形成的。科津把江格尔与成吉思汗等同起来是错误的,但在他的研究中有不少合理的因素。他分析了史诗的词汇和地名,这不能不说明问题。科津对自己俄译《江格尔》的4部长诗进行分析后,得出如下结论:
在伏尔加河流域居住的卡尔梅克人的口语中有许多借用的俄语词汇,可是在上述4部中只发现了5个词:ura、knes、basmag、beder和sabla。这是晚期借用的几个词,若它在伏尔加河卡尔梅克人中产生的话,借用的俄语词汇比现在多得多。
史诗中多处出现了金、银、钢、陶瓷、丝绸和檀香等词,在这些词前边运用了各种古老的形容词,可是伏尔加河卡尔梅克人早已不熟悉这些形容词。在准噶尔的时候,卫拉特人生活在丝绸之路上。那些与草原商品有关的古老词汇,可能是在准噶尔时代出现的。
他分析的作品中约有60个地名,其中四分之三与山有关,而且这些山名的三分之一又同阿尔泰山联系在一起。此外,还有额尔齐斯河、科布多以及青藏地区的昭、锡莱依高勒等地名,同时,尚未发现伏尔加河一带的任何一个地名。这些现实说明了《江格尔》英雄们活动的范围在阿尔泰山南北、额尔齐斯河流域、科布多地区和青藏高原地带。①这就是卡尔梅克人西迁以前的故乡,它说明了这部史诗的形成时代。
近十多年来,中国学者巴达玛、贾木措(原来汉译为贾木查,后来自己改为贾木措,是同一人)、哈萨格拜等人又从中发现了一些新疆一带的地名。金峰考证了史诗里出现的各汗国的地理位置,认为阿鲁·宝木巴地方处于额尔齐斯河流域,在它的东方有东蒙古(四十万世界)、在西方有察合台汗国(八千世界),那尔图是天山以南库车、喀什噶尔到苏联七河一带地区。
众所周知,在17世纪20年代卡尔梅克人的祖先和鄂尔勒克率土尔扈特部游牧到伏尔加河一带去生活。科津研究的《江格尔》的4部长诗是19世纪中叶在伏尔加河一带卡尔梅克人中间记录的。远离故乡200余年的伏尔加河卡尔梅克人演唱的史诗里没有出现当地地名,反而有大量的阿尔泰山、额尔齐斯河、科布多、青海和西藏的地名以及中世纪准噶尔人的古老词汇,这不能不说是《江格尔》顽强地保留着它的形成地域和部族特征。史诗这种特征说明了它早在1630年土尔扈特西迁以前已在新疆一带形成。
4.如前所述,加·巴图那生等人在新疆搜集到了17世纪上半叶土尔扈特西迁到伏尔加河以前,在和鄂尔勒克的家乡有一位叫作土尔巴雅尔的江格尔奇能演唱《江格尔》的70部长诗的传说。这个传说与别尔克曼在伏尔加河下游的卡尔梅克人中所听到的历史人物策伯克多尔挤诺谚的事迹有密切联系。它们从侧面证明了英雄史诗《江格尔》早在17世纪上半叶已在新疆形成和发展。
5.卫拉特人的迁徙史和《江格尔》的流传情况也可以说明这一史诗的形成时代。卫拉特人的历史很复杂,他们经历了几次大迁徙,也经过了几次部落大融合阶段,现在的卫拉特人不是由有血缘关系的部落所组成的,但总体而言,他们还是属于古卫拉特人的后裔。蒙元时期史书称他们为“斡亦剌惕”,明代称“瓦剌”、“额鲁特”,清代以后写成“卫拉特”。在13世纪成吉思汗时代,斡亦刺惕人民居住在贝加尔湖西北安加拉河一带的八河流域,他们属于森林部落,故称“斡亦剌惕”(森林之民)。从成吉思汗时代起,他们向南迁徙,约于14~15世纪到新疆阿尔泰山一带游牧。后来约于15世纪30年代起与客列亦惕部出身的土尔扈特等部落联合形成了四卫拉特联盟,建立了卫拉特汗国,并曾经一度统一了东蒙古和西蒙古。17世纪初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率部众5万户,由新疆阿尔泰山一带游牧到了伏尔加河流域。过了100多年后,于1771年渥巴锡汗率部分土尔扈特人经过艰难困苦斗争终于回归新疆。留在伏尔加河西岸的就是俄国卡尔梅克人。这样卫拉特人的历史就有几个明显的阶段,这有利于我们断定《江格尔》的形成时代。
那么,《江格尔》到底是哪一时期形成的长篇史诗呢?
根据《江格尔》的流传情况看,它是于15世纪以后在新疆一带形成的。目前蒙古语族人民分散居住在东起大兴安岭,西至欧洲的伏尔加河西岸,南到长城,北至贝加尔湖周围广大地区的各民族人民之中。如前所述,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蒙古语族人民中存在着史诗流传的七大中心,它们是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巴尔虎—布里亚特地区,哲里木盟的扎鲁特—科尔沁地区,新疆一带的卫拉特地区,蒙古国的喀尔喀地区和西蒙古卫拉特地区,俄国伏尔加河西岸的卡尔梅克地区和贝加尔湖一带的布里亚特地区。在这七大中心中有些地区之间相隔数千公里,而且几百年来没有相互联系。可是单篇型史诗和串联复合型史诗在这些中心里普遍流传,这些史诗还在主要方面都有一些相似性。因此,笔者认为,单篇型史诗和串联复合型史诗是古代各蒙古部落的共同创作,它们产生于民族形成和国家形成以前各个蒙古部落共同聚居在南西伯利亚和中央亚细亚时期。可是,《江格尔》的流传则不同,它主要是广泛流传于新疆的卫拉特人和伏尔加河下游的卡尔梅克人中。在其他各中心里,《江格尔》很少流传,流传的部分也是在卫拉特人的影响下出现的。这种分布情况说明,《江格尔》不可能是各蒙古部落共同聚居时期的作品。它可能是卫拉特人脱离贝加尔湖一带的巴尔虎、布里亚特等蒙古部落,到新疆阿尔泰山一带去同土尔扈特等部一起建立了四卫拉特联盟以后形成的长篇英雄史诗。因此它形成时代的上限,应当在15世纪以后。
6.《江格尔》里的宗教形态也对断定其形成时代方面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国内外一批研究者曾注意过这个问题。
这部史诗的宗教形态有以下特点:
(1)萨满教因素和佛教因素同时并存,也就是说在史诗里,既有萨满教因素,又有佛教因素。
(2)萨满教因素和佛教因素,往往在一处对同一事物和现象的描写上融合在一起。
(3)萨满教处于衰弱状态,佛教处于上升状态之中。
这些现象反映了《江格尔》形成的时代特征。在蒙古—卫拉特历史上,曾出现过宗教处于上述状态的历史时期,而且这一时期的界限较分明。蒙古人有悠久的佛教文化传统,从13世纪中叶起,他们接触到了西藏佛教,尤其是由忽必烈时代起元朝宫廷和统治阶层接受了藏传佛教。但在这一时期,草原上的广大牧民群众尚未受到佛教的影响,在他们中间萨满教仍然占最重要地位。佛教第二次传入蒙古地方是从16世纪中叶开始,到16世纪末17世纪上半叶到了高速发展时期,土默特阿勒坦汗是最早在蒙古地方传播喇嘛教和禁止萨满教的重要人物。他于1573年邀请西藏黄教徒索南嘉错(后来被奉为三世达赖喇嘛)赴蒙古地方传教,但索南嘉错到1576年才前往会见了阿勒坦汗。从此以后,阿勒坦汗制定了新法律,以便保证传播喇嘛教,禁止萨满教,使呼和浩特成为喇嘛教中心,其附近修建了许多喇嘛庙。因为他弘扬佛法,得到了西藏喇嘛教首领的信任,三世达赖于1587年圆寂之后,从阿勒坦汗家族中发现了四世达赖喇嘛允丹嘉错(1588—1617),接着东蒙古也接受了喇嘛教。喀尔喀部阿巴岱汗曾拜见过达赖喇嘛,他于1586年为达赖喇嘛送给他的佛像修建了额尔德尼昭寺,又颁布了禁萨满教令。西蒙古四卫拉特地区也是从16世纪末起接受了喇嘛教。在卫拉特地区兴佛灭萨满教的主要人物是大喇嘛内济托音(1557—1653)和热迥巴·咱雅班智达(1599—1662)。土尔扈特部贵族出身的内济托音前往呼和浩特当喇嘛,他翻译了一批佛经。他从16世纪末起镇压卫拉特萨满,接着于1629~1653年间去内蒙古东部区传播黄教,同时,破坏了那里的萨满教活动。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于17世纪20年代帮助达赖喇嘛,在西藏战胜了噶举巴派。17世纪初西蒙古杜尔伯特、绰罗斯、和硕特,还有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在内的各部贵族都选送一个儿子去西藏当了喇嘛。在那些孩子中出现了卫拉特文化名人热迥巴·咱雅班智达。他于1617~1639年去西藏深造,回卫拉特地区后,按着西藏黄教领袖的旨意进行佛教活动,发布了禁萨满教令。他于1648年创造了适应卫拉特地方方言的托忒蒙古文,并于1650~1662年间用此文字翻译了《甘珠尔》等大量佛教典籍。在此以前,于1628~1629年察哈尔部林丹汗组织35名学者将《甘珠尔》译成了蒙古文。后来在乾隆时代的1742~1749年间蒙译出版了《丹珠尔》。此外,在卫拉特地区,传播黄教的一个重要人物是噶尔丹大喇嘛,他曾去西藏深造,于1671年赶回卫拉特地区参加了政权斗争。在1677年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错任命他弟子噶尔丹为卫拉特汗,让他掌握卫拉特政教权,进行政治活动和黄教活动。因此《江格尔》里多处称他为“噶尔丹·沙尔喇嘛”。
上述历史事件说明,从16世纪末始,不论在东蒙古地区,还是在西蒙古卫拉特地区,传播喇嘛教活动同迫害和禁止萨满教活动,几乎都是同步进行的。因此可以肯定《江格尔》所反映的佛教现象的上限,只能在这一时期以后,甚至有的更晚些,如历史人物噶尔丹·沙尔喇嘛的出现是17世纪下半叶的事情。颁布禁萨满教令之后,当然萨满不敢在公开场所活动了,但不能认为,有了禁令,萨满教的一切现象都不存在了。在民众头脑中,在他们的风俗习惯中,萨满教观念和习俗还长期存在着,而且后来佛教和萨满教调和了。正如瓦·海希西教授所说“在蒙古人中,喇嘛教可能最早与因兴奋而狂舞的萨满教调和了”,又说“鉴于喇嘛教在16~17世纪间长期地坚持迫害萨满教,后者被迫自我掩饰起来,并采纳了喇嘛教的历史和喇嘛教万神殿中的神祇,而且还使用了喇嘛教祈祷中的词句”。①因此,由16世纪末以后,在一段历史时期内,在蒙古人中间,出现了佛教因素和萨满教因素同时并存及相互交叉的现象。在这个时期,也就是萨满教走向了衰弱阶段,喇嘛教进入了强盛时期。《江格尔》反映了这个时代的蒙古族卫拉特地区的宗教现实。
根据以上种种事实看,《江格尔》形成为长篇英雄史诗的上限是15世纪30年代早期四卫拉特联盟建立以后,下限是17世纪20年代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率部众西迁以前,在这200年内《江格尔》的主要部分业已形成。
附注
仁钦道尔吉:《蒙古英雄史诗发祥地考》,《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1985年第4期,第54~74页。; 《江格尔——卡尔梅克英雄史诗》第一卷(25章),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8年,第105、137、215页。; 《江格尔——卡尔梅克英雄史诗》第一卷,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8年,第76、77页。; 《江格尔——卡尔梅克英雄史诗》第一卷(25章),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8年,第250页;又见《江格尔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71页。; 《江格尔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05页。; 斯·阿·科津:《江格尔传》,莫斯科—列宁格勒,1940年,第70~76页。; 图齐、海希西著,耿升译,王尧校订:《西藏和蒙古的宗教》,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54~3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