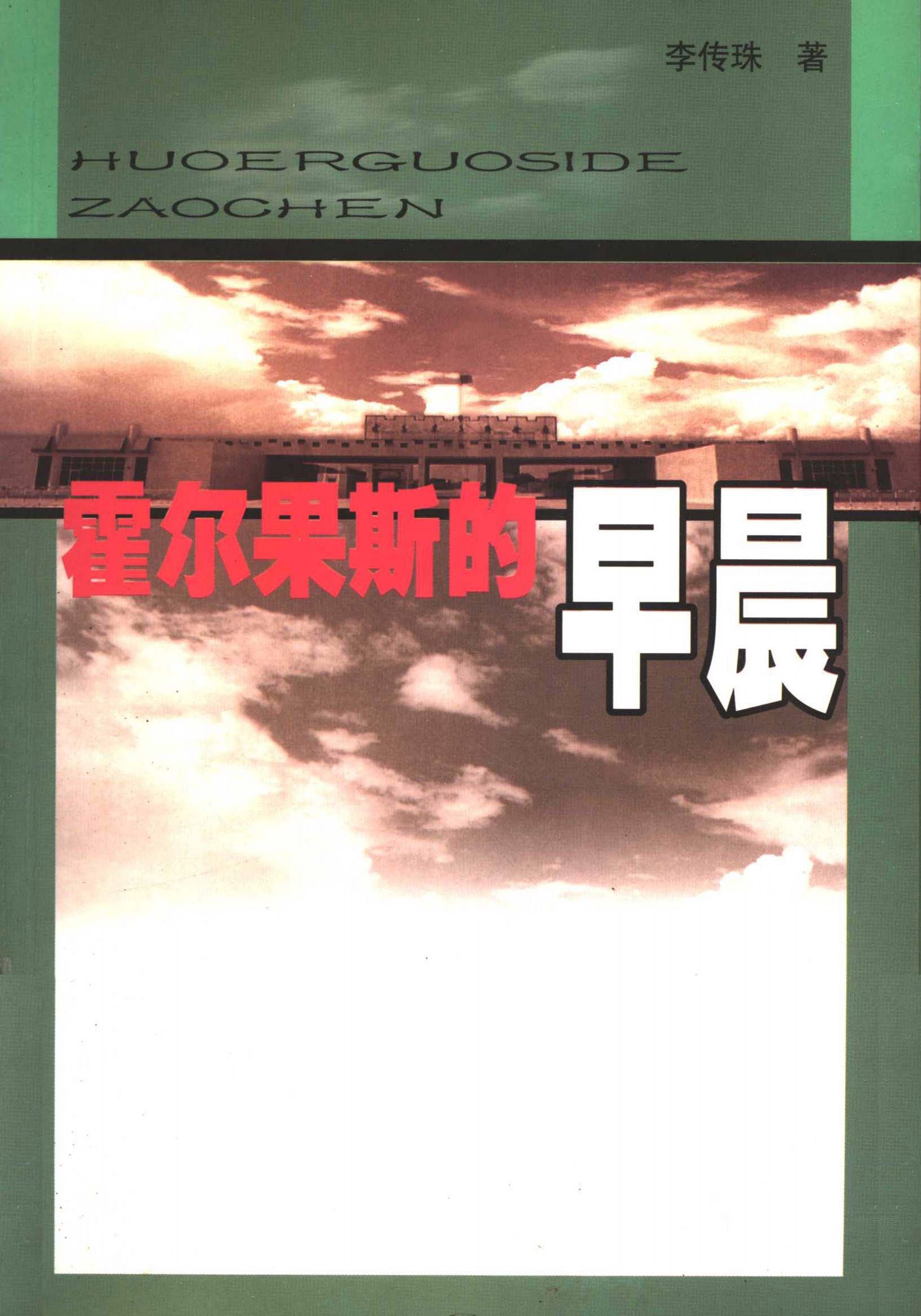阿力麻里行思
| 内容出处: | 《霍尔果斯的早晨》 图书 |
| 唯一号: | 320020020210062575 |
| 颗粒名称: | 阿力麻里行思 |
| 分类号: | F426;I267;G624 |
| 页数: | 6 |
| 页码: | 1-6 |
| 摘要: | 阿力麻里,距古“丝绸之路”之驿站霍尔果斯口岸30公里,坐落在北边的塔尔奇山中。它曾是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领地——察合台国的首都,是当时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是中亚的名城。透过口岸瞭望塔40倍望远镜向它打量:它幽居在霍尔果斯河发源地的山垭中,低处绿葱葱,山腰雾蒙蒙,山顶雪皑皑,看不到它的身姿,寻不到它的倩影。惟一望到的是影影绰绰的守卫着它的19世纪50年代修建的军事瞭望塔,在望远镜中只有模模糊糊的一小点,它幽居得愈深,对人们愈具神奇的诱惑力。 |
| 关键词: | 察合台 瞭望塔 霍尔果斯 阿力麻里 霍尔果斯口岸 |
内容
阿力麻里,距古“丝绸之路”之驿站霍尔果斯口岸30公里,坐落在北边的塔尔奇山中。它曾是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领地——察合台国的首都,是当时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是中亚的名城。透过口岸瞭望塔40倍望远镜向它打量:它幽居在霍尔果斯河发源地的山垭中,低处绿葱葱,山腰雾蒙蒙,山顶雪皑皑,看不到它的身姿,寻不到它的倩影。惟一望到的是影影绰绰的守卫着它的19世纪50年代修建的军事瞭望塔,在望远镜中只有模模糊糊的一小点,它幽居得愈深,对人们愈具神奇的诱惑力。
1988年9月10日下午,我以口岸管委会工作人员的身份陪同国家煤炭部部长、伊犁地区雷以亮副专员一行参观完口岸,顺着蜿蜒的中苏界河——霍尔果斯河东岸的巡逻公路,乘车向阿力麻里驰去。
穿过柳树丛丛,一个个小水电站列队欢迎的9公里柏油公路,拐过驻扎在清朝哨卡旧址上的红卡子连的哨楼,跨上了戈壁路。车缓缓而行,逆水而上,绮丽的霍尔果斯河又闯入我的眼帘。
宽阔的河面,碧波粼粼;硕大的卵石突出水面,时而撞起朵朵浪花。河道中心线上,划了一道看不见的、不可逾越的国际界线,左边是苏联的,右边是中国的。水的两边,虽在不同国度,却都镶着一条宝石似的很宽的卵石带,卵石有红的、白的、褐的、黄的、灰的、花的,五颜六色,耀人眼目。再往外,便是护卫它的两道连绵巍峨葱绿的山脉;右边山脚下,是座宏伟的红卡子一级水电站。霍尔果斯河像一条缀满珠宝的白练,在霍尔果斯口岸腰间耀眼生辉。
“前面那房子是谁的?建造得真漂亮!”煤炭部杨江有秘书赞赏地问道。我向他笑笑,说:“这是苏联基洛夫集体农庄的东方作业组。”
作业组在河对岸。一律独立方形铁皮尖顶别墅式的房子,光亮的油漆顶或红或灰,在太阳照射下,熠熠生辉。房子门前花墙内,有苏联人晒着衣服,不时走动,说话的声音隐隐传来。房屋傍着河岸,布局有致。房区宽300余米,长2公里多。高大成行的白杨,把一幢幢房子掩在林间。
我们这边是柳树的王国。遍地的柳树,有的干粗而直,形成一个庞大的蘑菇状树冠;有的斜长着,树冠扫着地面,活像放在地上撑开晾着的一把雨伞;有的不成树木,却成丛丛灌柳,给人一种自然之美。离河岸不远,靠路两三米,与马路平行地生长着7棵合抱粗的柳树,残留着两个合抱粗的50多厘米高的柳树桩,这就是传说的周恩来总理关心的9棵树。他老人家一再指示要保护好这9棵树。如今,9棵树老朽了两棵。老朽的树根还在,根部生发出繁茂的枝条。牛羊成群地在林边吃草,有的在树阴下静卧反刍。一位穿花裙子的哈萨克族中年妇女从河边挑水归来,向毡房走去。安定和平的气氛笼罩在霍尔果斯河的上空。同饮一河水的两国边民,隔河相望,说话都能听见,相互来往却不能。我想:口岸的重新开放,贸易“互市”即在眼前,边民交往,实现互通有无的时候,将会不远了。
车子猛烈颠簸了一下,身子一闪,庄园、柳林不见了。车子拐上了盘山路。这段路,路面狭窄,右面靠山,左临悬崖,往下一瞧,惊心动魄。但是我们的老司机,手把方向盘,面不改色,左转右拐,并不减速。技术如此娴熟,真叫人佩服。正当我感叹之时,从前方不远的高山迎面飞来一个刀劈似的断崖。偌大的断层,像挂在天宫的一个屏幕。远望,宽300米,高近百米,一片青灰色;近看,线条笔直,高低有致,像个巨大雕刻作品。整个画面素雅清晰,立体逼真。
“停下!停下!”杨秘书叫了起来,分水桥到了。
分水桥为游客称道,并不是因为它是什么雄伟建筑,它只不过是一座长70米、宽1.5米的钢丝吊桥。人们称道的是它沟通了两国边民的心,造福于六七万人民,是两国边民友谊的纽带。
这桥本来叫贸易桥,因霍尔果斯口岸开辟100多年来在此出口活牲畜得名。1968年将原腐朽的木桥拆除改修为今日的钢丝吊桥,改称分水桥。
吊桥上铺着刷了绿漆的木板,两边的铁栏杆也是绿的。人们下了车,踏上了分水桥中国的一半,瞧瞧苏联的会晤厅,沿石级而上102个台阶,建在山坡上;厅的正面上方塑着镰刀斧头国徽,两边各塑6面旗子,是苏联由多个共和国组成的象征。内设餐厅、会晤厅、娱乐厅。望望中国的会晤厅,顺桥平伸百米,建在山脚下;餐厅、会晤厅、娱乐厅呈凹形摆开。中苏两厅对称典雅,造型优美,各具特色。看着桥下奔涌的哗哗流水,水清如晶,偶尔泛起乳白色的水花,使人觉得流的不是水,而是乳汁,是玉液。几个人经不住这清水的诱惑,跑下桥去,拥水畅饮,噎得上气不接下气,连声地赞叹道:“真甜!真甜!”
我告诉客人,以前这水任其流向两国的土地,哺育着两国的边民。1965年4月30日成立了中苏联合分配使用霍尔果斯河水委员会,双方相继签订了协议、议定书,制定了工作程序,规定每年4月5日至10月25日逢5例行测水分水;如一方发生问题,还可全面测水,被邀一方必须在24小时内赶到。会晤地点,这次在这边,下次在那边。几十年来,尽管风云变幻,两国分水人员相处得十分融洽。
“鱼!鱼!好大的鱼!游那边去了,又游过来了!”人们惊喜地叫道。但是,由此也引起人们的沉思:鱼,一个小动物尚且能够自由地游来游去,人却给自己脖子上套个枷锁,一水之隔,却互不往来!这个历史过程何时是头呢?
我们又上了路。阿力麻里就在眼前。顺利通过了泥石流,一条小河挡住了去路。司机加大油门,呜地一声冲到了对岸。
后边的车子不见了,我们只好到阿力麻里等候。
爬上两个坡,便到了海拔1600米高的阿力麻里。这是一个比较开阔的山顶,高高低低大约有几平方公里。三面是更高的山脉。絮云挂山腰,山巅在云上。一条絮云分明地把山分成了两个世界、两个季节。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曾经置疑,察合台为什么把首都建在这里呢?驻扎在这里的边防连指导员领我观看了城墙遗址。城墙是土垒的,高3米,厚2米,长百多米。墙上生满了厚厚的青苔和几撮秃子头上黄毛似的细草。我想:把城池建在这里,可能是军事上的缘故吧。后来伊犁地区文管所所长赵德荣给我介绍说,阿力麻里建于西辽时期,分为东、西阿力麻里。西阿力麻里在苏联哈萨克共和国阿拉木图郊区,毁于战争。东阿力麻里出土的青花瓷碗、高脚杯成为国家的一级保护文物。成吉思汗的高参邱处机在回忆文中说,阿力麻里方圆50里。阿力麻里列入了西亚研究的内容。为解此谜,许多国家来我国参观,但此时伊犁未开放。我才知道,阿力麻里是个大的概念。我陪同部长一行的游览原来没出阿力麻里呀。目前这里是解放军的一个哨卡。据说,《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一首歌,就是根据这里战士在黑板上写的一首诗创作的。我们在阿力麻里等不到部长,正要返回,却见部长几个人步行往山上爬来,还边走边照相。一问,原来车子在河里抛锚了。部长在山上观看了阿力麻里遗址和这里的风光,在瞭望塔上与执勤战士合了影。我逗趣地说:“部长,这次山没白爬吧?”
部长哈哈笑着说:“没白爬,没白爬。我来到祖国的西天边,看了古人的遗址。这里的风光太美了,真是太美了!”
是的,这里的风光太美了。我们该怎样珍惜呢?
(发表于《绿洲》1989年第5期)
1988年9月10日下午,我以口岸管委会工作人员的身份陪同国家煤炭部部长、伊犁地区雷以亮副专员一行参观完口岸,顺着蜿蜒的中苏界河——霍尔果斯河东岸的巡逻公路,乘车向阿力麻里驰去。
穿过柳树丛丛,一个个小水电站列队欢迎的9公里柏油公路,拐过驻扎在清朝哨卡旧址上的红卡子连的哨楼,跨上了戈壁路。车缓缓而行,逆水而上,绮丽的霍尔果斯河又闯入我的眼帘。
宽阔的河面,碧波粼粼;硕大的卵石突出水面,时而撞起朵朵浪花。河道中心线上,划了一道看不见的、不可逾越的国际界线,左边是苏联的,右边是中国的。水的两边,虽在不同国度,却都镶着一条宝石似的很宽的卵石带,卵石有红的、白的、褐的、黄的、灰的、花的,五颜六色,耀人眼目。再往外,便是护卫它的两道连绵巍峨葱绿的山脉;右边山脚下,是座宏伟的红卡子一级水电站。霍尔果斯河像一条缀满珠宝的白练,在霍尔果斯口岸腰间耀眼生辉。
“前面那房子是谁的?建造得真漂亮!”煤炭部杨江有秘书赞赏地问道。我向他笑笑,说:“这是苏联基洛夫集体农庄的东方作业组。”
作业组在河对岸。一律独立方形铁皮尖顶别墅式的房子,光亮的油漆顶或红或灰,在太阳照射下,熠熠生辉。房子门前花墙内,有苏联人晒着衣服,不时走动,说话的声音隐隐传来。房屋傍着河岸,布局有致。房区宽300余米,长2公里多。高大成行的白杨,把一幢幢房子掩在林间。
我们这边是柳树的王国。遍地的柳树,有的干粗而直,形成一个庞大的蘑菇状树冠;有的斜长着,树冠扫着地面,活像放在地上撑开晾着的一把雨伞;有的不成树木,却成丛丛灌柳,给人一种自然之美。离河岸不远,靠路两三米,与马路平行地生长着7棵合抱粗的柳树,残留着两个合抱粗的50多厘米高的柳树桩,这就是传说的周恩来总理关心的9棵树。他老人家一再指示要保护好这9棵树。如今,9棵树老朽了两棵。老朽的树根还在,根部生发出繁茂的枝条。牛羊成群地在林边吃草,有的在树阴下静卧反刍。一位穿花裙子的哈萨克族中年妇女从河边挑水归来,向毡房走去。安定和平的气氛笼罩在霍尔果斯河的上空。同饮一河水的两国边民,隔河相望,说话都能听见,相互来往却不能。我想:口岸的重新开放,贸易“互市”即在眼前,边民交往,实现互通有无的时候,将会不远了。
车子猛烈颠簸了一下,身子一闪,庄园、柳林不见了。车子拐上了盘山路。这段路,路面狭窄,右面靠山,左临悬崖,往下一瞧,惊心动魄。但是我们的老司机,手把方向盘,面不改色,左转右拐,并不减速。技术如此娴熟,真叫人佩服。正当我感叹之时,从前方不远的高山迎面飞来一个刀劈似的断崖。偌大的断层,像挂在天宫的一个屏幕。远望,宽300米,高近百米,一片青灰色;近看,线条笔直,高低有致,像个巨大雕刻作品。整个画面素雅清晰,立体逼真。
“停下!停下!”杨秘书叫了起来,分水桥到了。
分水桥为游客称道,并不是因为它是什么雄伟建筑,它只不过是一座长70米、宽1.5米的钢丝吊桥。人们称道的是它沟通了两国边民的心,造福于六七万人民,是两国边民友谊的纽带。
这桥本来叫贸易桥,因霍尔果斯口岸开辟100多年来在此出口活牲畜得名。1968年将原腐朽的木桥拆除改修为今日的钢丝吊桥,改称分水桥。
吊桥上铺着刷了绿漆的木板,两边的铁栏杆也是绿的。人们下了车,踏上了分水桥中国的一半,瞧瞧苏联的会晤厅,沿石级而上102个台阶,建在山坡上;厅的正面上方塑着镰刀斧头国徽,两边各塑6面旗子,是苏联由多个共和国组成的象征。内设餐厅、会晤厅、娱乐厅。望望中国的会晤厅,顺桥平伸百米,建在山脚下;餐厅、会晤厅、娱乐厅呈凹形摆开。中苏两厅对称典雅,造型优美,各具特色。看着桥下奔涌的哗哗流水,水清如晶,偶尔泛起乳白色的水花,使人觉得流的不是水,而是乳汁,是玉液。几个人经不住这清水的诱惑,跑下桥去,拥水畅饮,噎得上气不接下气,连声地赞叹道:“真甜!真甜!”
我告诉客人,以前这水任其流向两国的土地,哺育着两国的边民。1965年4月30日成立了中苏联合分配使用霍尔果斯河水委员会,双方相继签订了协议、议定书,制定了工作程序,规定每年4月5日至10月25日逢5例行测水分水;如一方发生问题,还可全面测水,被邀一方必须在24小时内赶到。会晤地点,这次在这边,下次在那边。几十年来,尽管风云变幻,两国分水人员相处得十分融洽。
“鱼!鱼!好大的鱼!游那边去了,又游过来了!”人们惊喜地叫道。但是,由此也引起人们的沉思:鱼,一个小动物尚且能够自由地游来游去,人却给自己脖子上套个枷锁,一水之隔,却互不往来!这个历史过程何时是头呢?
我们又上了路。阿力麻里就在眼前。顺利通过了泥石流,一条小河挡住了去路。司机加大油门,呜地一声冲到了对岸。
后边的车子不见了,我们只好到阿力麻里等候。
爬上两个坡,便到了海拔1600米高的阿力麻里。这是一个比较开阔的山顶,高高低低大约有几平方公里。三面是更高的山脉。絮云挂山腰,山巅在云上。一条絮云分明地把山分成了两个世界、两个季节。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曾经置疑,察合台为什么把首都建在这里呢?驻扎在这里的边防连指导员领我观看了城墙遗址。城墙是土垒的,高3米,厚2米,长百多米。墙上生满了厚厚的青苔和几撮秃子头上黄毛似的细草。我想:把城池建在这里,可能是军事上的缘故吧。后来伊犁地区文管所所长赵德荣给我介绍说,阿力麻里建于西辽时期,分为东、西阿力麻里。西阿力麻里在苏联哈萨克共和国阿拉木图郊区,毁于战争。东阿力麻里出土的青花瓷碗、高脚杯成为国家的一级保护文物。成吉思汗的高参邱处机在回忆文中说,阿力麻里方圆50里。阿力麻里列入了西亚研究的内容。为解此谜,许多国家来我国参观,但此时伊犁未开放。我才知道,阿力麻里是个大的概念。我陪同部长一行的游览原来没出阿力麻里呀。目前这里是解放军的一个哨卡。据说,《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一首歌,就是根据这里战士在黑板上写的一首诗创作的。我们在阿力麻里等不到部长,正要返回,却见部长几个人步行往山上爬来,还边走边照相。一问,原来车子在河里抛锚了。部长在山上观看了阿力麻里遗址和这里的风光,在瞭望塔上与执勤战士合了影。我逗趣地说:“部长,这次山没白爬吧?”
部长哈哈笑着说:“没白爬,没白爬。我来到祖国的西天边,看了古人的遗址。这里的风光太美了,真是太美了!”
是的,这里的风光太美了。我们该怎样珍惜呢?
(发表于《绿洲》198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