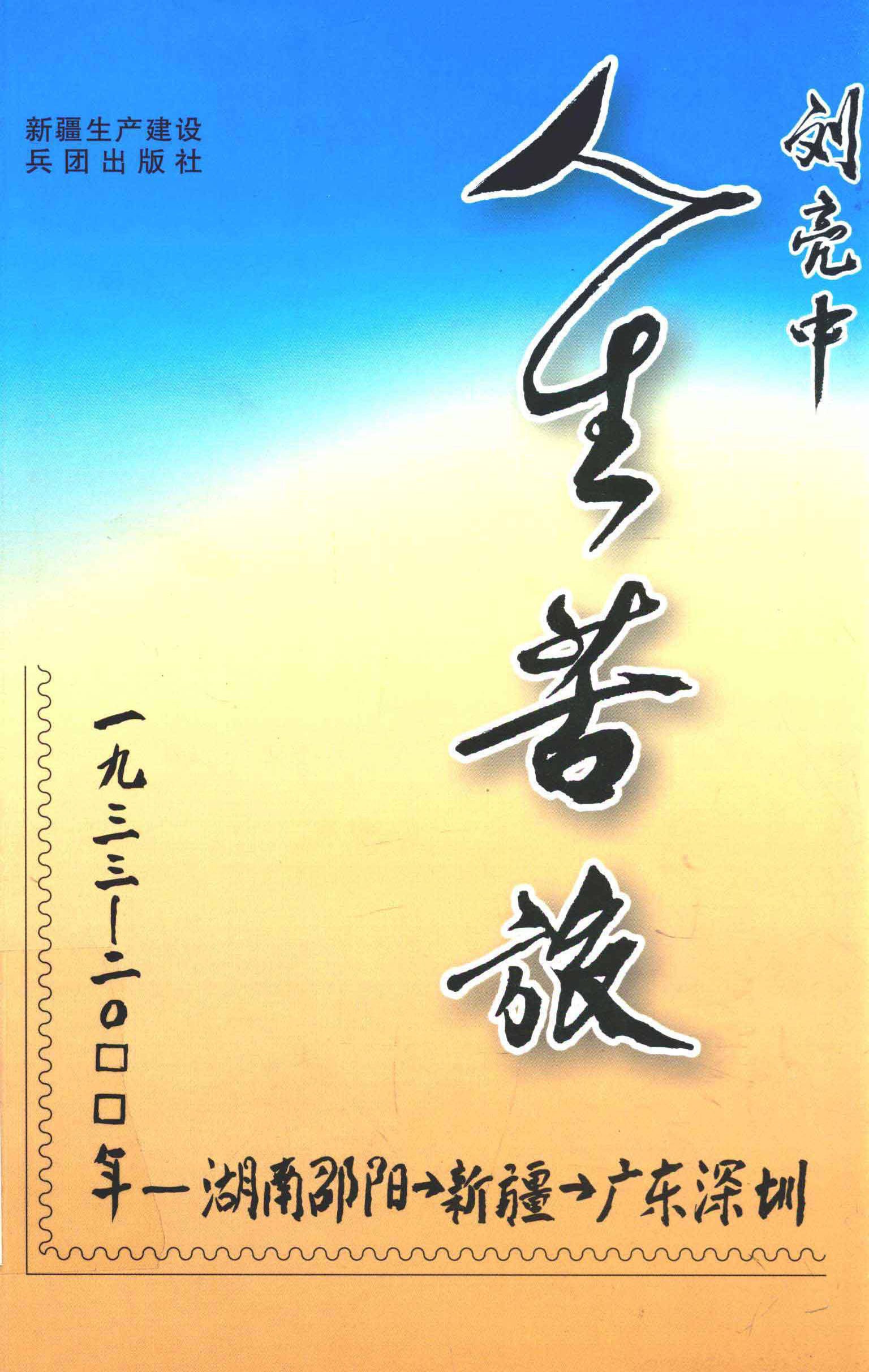内容
乙丑仲秋。
中原大地,列车奔驰。
在69次特别快车的3号硬席卧铺车厢里,我对面的下铺空着。午后,车到郑州站稍停。我下车散步回来时,见一个打扮入时的青年妇女坐在对座靠窗处,身边偎着一个约莫五六岁的女孩。一位老人把几个大包在行李架上放稳当,提起身旁盖着毛巾的麦枯篮,塞到青年妇女的铺位底下,而后在过道窗下的折叠椅上落坐。
列车徐徐开动了。新来的青年妇女从手提包中取出一个带尼龙罩的玻璃杯,提起桌下暖水瓶,倒满一杯,让小女孩递给老人,又给我的杯里添满水。
“谢谢”!我欠身致意,“你们一家子从那儿来?刚上车的?”
“不,在北京上车的,从山东老家来。你呢?”青年妇女说话不紧不慢,嗓音清亮甜润。
我告诉她:“回新疆去,家住石城,在乌市工作。”她像见到乡亲似地高兴,说:“我也回新疆,家也住石城,也在乌市工作”。这连声三个“也”,在心境上缩短了我同她的距离,似乎也感染了注视着我们的老人。老人从铺下拉出提篮,掀开毛巾,露出一篮鲜桃。他拣出几个,分给座上乘客。青年妇女接过老人递来的桃,对我们说:“我爸爸是哑巴,头一回离开山东。这桃是他从山东老家带来的。我说新疆也有桃,可他硬要带。”
秋令时节,午后七时便近黄昏了。还没到洛阳,车厢就亮起灯来。挤坐下铺聊天的乘客们开始各就各位。兴许是前几天东奔西忙欠觉太多的缘故,我今晚睡得特别“死”,一觉醒来,窗外大亮,车到宝鸡站了。人群的上上下下,用具的磕磕碰碰,搅动了凝聚一夜的夹酸带臭的厢内空气。车窗的玻璃提起了,清新的空气进厢了,全车厢顿时活跃起来。直到乘客们陆陆续续漱洗完毕,吃过早点,之后,车厢复归平静。乘客们用各自喜欢的方式消磨时间。此刻,哑巴老人依旧坐在过道一侧的折叠椅上,凝望窗外陇南的层层山峦。这陇南山区铁路线,隧道一个接一个。车厢里忽明忽暗,既不便看书,也玩不成扑克。我同对座的“石城老乡”,在互通姓名之后,聊起天来。
她名叫艾莉。我们一开始交谈,哑巴老人便把目光从窗外移过来。艾莉说话时,他目不转睛地瞅着她;艾莉笑时,他紧锁的眉毛也舒展开来。
“你爸爸上新疆,妈妈呢?”“妈妈在新疆,她进疆多年了。”“你妈妈同爸爸分居两地,怎么回事呢?”艾莉见我这个“石城老乡”打破砂锅问到底,转过头瞧一眼老人,长长地叹一口气,好一会儿,呷口开水,轻声道:“我妈妈同爸爸的事,说来话长”。艾莉打开了话匣——
我爸爸是鲁西一户地主的儿子,是地主家一个丫环生的,从小聋哑。哑巴不到16岁就成了亲。媳妇是被人拖进洞房的,双手反绑着,嘴巴用毛巾堵着。这媳妇就是我妈。
我妈出生在河南伏牛山下穷人家。伏牛山下盛产桃。因洪水毁了家园,妈妈跟随姥姥,提着一篮山桃出走。母女俩逃荒北上,路过鲁西这个地主家。老地主见大人虽衣衫褴褛,但个高脸俊,小孩虽骨瘦如柴,却看似机灵,便收留下来。老地主得知她来自伏牛山区会种桃,而且篮子里还装着好些桃核,于是,白天叫她到果园干活,黑天叫她进内室服侍起居。才过几月,姥姥种在园里的桃没发芽,却惨死在这个地主家的园里。
泡桐在碱地里长成,妈妈在苦水里泡大,长到14岁,便出落成一个高挑、俊俏的姑娘。一天夜里,她进地主卧室整理被褥,老地主逼她上床。她眼前浮现出亲人吊死桃园的惨状,旧仇新恨涌上心头,在拼命挣扎中,把老色鬼的鼻头咬掉一块。妈妈被拉进桃园,绑在树上。地主婆本要撵她走,老地主却把她留下来许给哑巴儿子。妈妈儿次以死抗婚,可是,上吊被哑巴发现解脱,投水被哑巴捞出救活。
父亲虽是地主的儿子,可同他的其他兄弟待遇大不一样,他跟长工一起下地干活。每天干完活,吃过饭,他便回到自己的小天地,把床铺收拾好,等候着妈妈。他待妈妈很温顺,从没跟她红过脸。可是,他对他父亲没有好脸色,特别是遇见那个老色鬼趁他不在闯进卧室的时候,他会挥舞拳头,冲他吼叫。
妈妈同哑巴父亲生活的第三年,也就是咱们老家土改那年,生下了我这个唯一的女儿。土改过后,乡、村干部三番五次劝妈妈同哑巴少爷离婚。妈妈不忍抛开这个并没过过少爷生活的少爷,伏在爸爸胸前啜泣。不过,妈妈这个正在申请入党的村妇女干部,终究同父亲分手了。
离婚以后,父亲被他的在泉城郊区园艺场工作的弟弟接走了。不久,妈妈便带着我参加了“支援新疆建设妇女大队”。妇女大队集中到泉城等火车。在临上车的前一天,妈妈悄悄来到市郊园艺场,在场部大门前徘徊。他,近在咫尺。她想见他一面,然而,她没有跨进大门,只是望着门口一树桃花发呆。第二天,“支援新疆建设妇女大队”登上了西去的列车。同车的姐妹们在车厢里叽叽喳喳地说长道短,我妈妈却一言不发。
列车穿山绕岭,跨河过镇,从黄土高原落入祁连山下。车轮单调的咣当声千万次地重复着,车头载着一千多个生命不倦地前行,时光随着窗外的气流分分秒秒地逝去。我们进入河西走廊的时候,又是一个白昼了。
“从那年进疆到如今,三十几年过去了,我们孤儿寡母走过这三十几年可真不易哪”!艾莉双掌合成V形,支撑着下巴,沉浸在“这三十几年”的回忆中。
我做为老宣传工作者,对于艾莉妈妈当年参加的“支援新疆建设妇女大队”的内情知道一点。那时,驻疆部队的许多老同志,单身入伍,戒马半生,如今功成国兴,是该聚妻成家了。这批山东妇女的进疆,为解决这些老同志的婚姻问题创造了条件。对此,进疆的妇女多半心中有数,也心甘情愿。不出半年,建设大队只剩下几个不肯轻易再嫁的倔女人了。
“我妈就是个倔女人”。自谓当过语文教师的艾莉,接着娓娓道来——
当时,在建设大队,数我妈年轻,长得也俊。建设大队进石城农场不到一月,有人把她介绍给主管大队工作的一位场领导。偏偏我妈执意不从。同伴说她傻,她却缄口低眉,并不解释。半年后,建设大队解散,剩下几个人要分到生产连队去。当领导问她想上哪个连队时,她豪不犹豫地回答:园林队。
当时,园林队没有桃园,只有苹果园。果园班里,多数是女的,除了我妈,都是场部干部家属。她们家务繁重,出勤率低。我妈没有这个负担,又是党员,所以领导要她当果园班长。
园林队有个老技术员,解放前在内地一所农学院毕业后,在国民党政府一个农业机构干过几年。我妈领导的果园班扩大后,老技术员带领她们除了管苹果园外,还开辟了个小桃园。他常同妈妈在一起干活,尤其爱听她讲伏牛山下种桃的故事。收工时,他同妈妈常走在最后,待走到连队生活区,妈妈越过栅栏拐进家门时,他还在路口呆立着。要是哪天他在办公室忙业务,妈妈收工回家,准能发现路口有一个熟悉的身影,他在傻等着她。可那时,老技术员的痴情,打不开她的关闭的心扉。她愿意同他交朋友,但没有想过嫁给他。
然而,生活中常常会出现令人意想不到的契机。在五十年代中期刮起的一场政治旋风,波及园林队。那一年,老技术员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我妈因同“历史反革命分子”划不清界限而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可是,人们没料到,这个警告反而引发了我妈这个倔女人的爱情火焰。她不但不跟他划清界限,而且把他请到家里。在家门口,他俩一起栽下一棵桃树。第二年,结成了共同生活的伴侣。
列车驶出河西走廊,过嘉峪关,转入一望无际的干涸沙原。窗外的景致是一派单调的灰色,可车厢内艾莉的叙说却展示出一幅幅光怪陆离的生活画卷——
1958年暮春一日,妈妈到队上食堂打饭,见墙上贴着一张批判我继父的大字报,标题文绉绉的:“敢笑东风者戒”。大字报在高喊“红旗舞东风……”之后,作为批判靶子,引用了职工揭发继父在桃园吟过的一首唐诗:
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东风。(原诗为“春风”,大字报有误)
大字报作者披露出惊人的“发现”:不种向日葵而种桃,不颂向日葵而颂桃,而且,“借桃讽今”,公然耻笑伟大领袖颂扬过的象征社会主义的“东风”,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现行活动,是其老婆“地主少奶奶”颓废没落的精神寄托,也是“两个阶级敌人”臭味相投的铁证。
不久,妈妈和继父合种的那棵桃树被砍掉了;妈妈以“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少奶奶”的罪名被监督劳动,我继父因“反革命罪”被判刑劳改,1960年死在劳改队里了。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后来,我们家庭院里又出现一棵新桃树。原来,1962年,我那在泉城园艺场工作的叔叔,给妈妈寄来一包桃种。叔叔附信告诉妈妈:这是他的哑巴哥哥亲手栽种的桃树结下的。妈妈拉上我,一起把它种在庭院一角。桃种出苗后,我妈变得越发的沉默寡言。白天,妈上班管理公家的果园;回到家,除了招呼我吃、穿、上学外,便一门心思扑在她的桃苗上,施肥、浇水、剪枝,忙个不停。活忙完,搬条小板凳,坐在桃树边,凝视着它。
这棵桃树和我这个女孩子,在妈妈的悉心抚育下,熬过了一场又一场风风雨雨,终于成长起来。到1966年,我成了高中学生,桃树也挂满果实了。
然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一次掀翻了我们孤儿寡母的生活之舟。我顶着“黑崽子”帽被分到垦区最边远的单位劳动;妈妈以带病之躯,白天下地干活,晚间被队里的造反派拉去批斗。这伙人横扫院中的桃,挖出它的老根,而后批判妈妈“颂固坚持地主少奶奶的立场,不爱别的果树,偏爱地主家带来的桃”。
十年荒唐的闹剧终于结束了。1978年,妈妈虽已年近半百,双鬓斑白,但依然步履稳健,精神矍铄。她把我从“接受再教育”的边远连队接回家,要我专心复习功课,准备高考。她把希望寄托于我。第二年高考,我舍弃报考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志愿,按照妈妈的意思考入了农业大学园艺系。毕业后,我成了家。爱人和我是同班同学,分在乌市同一个科研部门工作。结婚时,我俩一道回到石城园林队妈妈家。妈妈是队上桃园的“园长”。她叫我和我爱人当桃园的技术指导,还让我们跟在泉城园艺场当技术顾问的叔叔取得联系,同他交流种桃经验。年过半百的妈妈焕发了青春。她带领桃园班的几个年轻人,一心扑在桃树上,汗水浇在桃园里。从前年起,队上的果园,妈妈的庭院,一棵棵桃树便陆续开花结果了。
这几年,我和我爱人每年都要回石城妈妈家好几次。特别是桃花盛开的春天,我们总要带上孩子丝丝回家看花。妈妈拉着小丝丝,坐在桃树下,桃花映照着这一老一幼的红润的脸。微风吹来,几瓣桃花落在丝丝头上,落入妈妈怀里。
看来颇有文才的艾莉的充满诗情画意的叙说,使我在精神上完全摆脱了车厢外茫茫戈壁的灰色圈,脑海浮现一幅五彩缤纷的新生活的画图,浮现一个感情深沉的“倔女人”的形象。我不由得问艾莉:“你和你爱人都在乌市工作,你妈妈怎么没迁来?”
妈妈已经退休,户口已经迁到乌市,可她就是不到乌市定居。她说在园林队的土房住惯了,觉得挺好,不愿离开它。每年,除了冬天,大部分时间住在园林队。队里挺照顾她,房子没有收回,房前房后的菜地、桃园也给她留着。她带过的果园班的姑娘常去和她作伴。他也爱同她们一起给桃树浇水、施肥。无论是院里的树,院外的园,她都认认真真地管。每年摘下的桃,除了留少量的家用,大都交给队里。队里给她发劳务补助费,她一个子儿也不要。为了发展种桃业,她常常给我们出这样那样的题目,要我们解答,要我们试验。
桃子不比别的水果,容易烂。妈妈常向我们叨叨这个问题,要我们设法解决桃子保鲜问题。她劝我们同在泉城园艺场的叔叔联合起来办这件事。其实,桃子保鲜课题早已列入我们单位的科研计划中,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干起来。经妈妈一再催促,在上级有关方面的支持下,我们俩同叔叔,当然还有乌市、泉城两单位的其他同事,联合开展了桃子贮藏保鲜的研究试验工作。这项研究试验搞了两三年了。这次我爸爸从山东带来的这篮鲜桃,算是这项联合攻关的科研成果。丝丝她爸爸和我出差到北京,便是为这项科研课题去的。
这次出差前,我对妈妈说,办完公事,我带丝丝回趟山东,到泉城把哑巴父亲接来住几年吧。她低头不语,半响才说:“你当女儿的要接父亲来住我不反对。只是你得告诉我他来新疆的日期。我要在他到来之前回石城去。我不见他,你也别把他带石城去,别让他知道我住的地方。”我注意到,妈妈讲这番话的时候,声音发颤,泪水盈眶。
我理解她老人家的心。我从她常常独自望着庭院桃花出神的目光中感觉到,她思念家乡的亲人,也思念他,忘不掉他。但是,她宁愿一辈子在心灵深处保留婚后相爱的那短暂的一幕场景,而不愿让离异半生后、晚年重逢时产生的情感冲击波搅乱它。何况,她恨他出身的封建地主家庭。这个家庭毁了姥姥,伤了妈妈。她不愿再见到这个家庭的成员,因为,一旦见到他们,便会勾起早已沉入心底的不堪回首的住事。平素,看电视电影,凡是再现旧社会苦难特别是妇女苦难的,她要我们去看,可自己从不去看。
列车在茫茫戈壁又穿行了一昼夜,进入鄯善县境。列车员开始收拾铺位上的卧具,性急的旅客着手整理自己的东西。车过盐湖站后,在女儿的示意下,哑巴老人取下货架上的行包,把桌面的杂物装进网兜里,把铺下的麦秸篮拖出来,抖去盖布上的灰尘,重新拉平盖严。我注意到,他在做这些事的时候,粗糙的手微微地颤抖。特别是,他掀开篮子的盖布,暗红包的鲜桃跳入眼帘时,缓缓移动的目光戛然而止。此刻,他那轻轻抚摸着桃面的手指,抖得更厉害了。
列车徐徐进站了。
“姥姥会来接我们吗?”小丝丝抬眼问妈妈。
“姥姥不会来。”妈妈抚摸着她桃红的小圆脸,轻声回答。
(1987年春,为思念友人,根据“乙丑(1985年)仲秋”日记改写)
中原大地,列车奔驰。
在69次特别快车的3号硬席卧铺车厢里,我对面的下铺空着。午后,车到郑州站稍停。我下车散步回来时,见一个打扮入时的青年妇女坐在对座靠窗处,身边偎着一个约莫五六岁的女孩。一位老人把几个大包在行李架上放稳当,提起身旁盖着毛巾的麦枯篮,塞到青年妇女的铺位底下,而后在过道窗下的折叠椅上落坐。
列车徐徐开动了。新来的青年妇女从手提包中取出一个带尼龙罩的玻璃杯,提起桌下暖水瓶,倒满一杯,让小女孩递给老人,又给我的杯里添满水。
“谢谢”!我欠身致意,“你们一家子从那儿来?刚上车的?”
“不,在北京上车的,从山东老家来。你呢?”青年妇女说话不紧不慢,嗓音清亮甜润。
我告诉她:“回新疆去,家住石城,在乌市工作。”她像见到乡亲似地高兴,说:“我也回新疆,家也住石城,也在乌市工作”。这连声三个“也”,在心境上缩短了我同她的距离,似乎也感染了注视着我们的老人。老人从铺下拉出提篮,掀开毛巾,露出一篮鲜桃。他拣出几个,分给座上乘客。青年妇女接过老人递来的桃,对我们说:“我爸爸是哑巴,头一回离开山东。这桃是他从山东老家带来的。我说新疆也有桃,可他硬要带。”
秋令时节,午后七时便近黄昏了。还没到洛阳,车厢就亮起灯来。挤坐下铺聊天的乘客们开始各就各位。兴许是前几天东奔西忙欠觉太多的缘故,我今晚睡得特别“死”,一觉醒来,窗外大亮,车到宝鸡站了。人群的上上下下,用具的磕磕碰碰,搅动了凝聚一夜的夹酸带臭的厢内空气。车窗的玻璃提起了,清新的空气进厢了,全车厢顿时活跃起来。直到乘客们陆陆续续漱洗完毕,吃过早点,之后,车厢复归平静。乘客们用各自喜欢的方式消磨时间。此刻,哑巴老人依旧坐在过道一侧的折叠椅上,凝望窗外陇南的层层山峦。这陇南山区铁路线,隧道一个接一个。车厢里忽明忽暗,既不便看书,也玩不成扑克。我同对座的“石城老乡”,在互通姓名之后,聊起天来。
她名叫艾莉。我们一开始交谈,哑巴老人便把目光从窗外移过来。艾莉说话时,他目不转睛地瞅着她;艾莉笑时,他紧锁的眉毛也舒展开来。
“你爸爸上新疆,妈妈呢?”“妈妈在新疆,她进疆多年了。”“你妈妈同爸爸分居两地,怎么回事呢?”艾莉见我这个“石城老乡”打破砂锅问到底,转过头瞧一眼老人,长长地叹一口气,好一会儿,呷口开水,轻声道:“我妈妈同爸爸的事,说来话长”。艾莉打开了话匣——
我爸爸是鲁西一户地主的儿子,是地主家一个丫环生的,从小聋哑。哑巴不到16岁就成了亲。媳妇是被人拖进洞房的,双手反绑着,嘴巴用毛巾堵着。这媳妇就是我妈。
我妈出生在河南伏牛山下穷人家。伏牛山下盛产桃。因洪水毁了家园,妈妈跟随姥姥,提着一篮山桃出走。母女俩逃荒北上,路过鲁西这个地主家。老地主见大人虽衣衫褴褛,但个高脸俊,小孩虽骨瘦如柴,却看似机灵,便收留下来。老地主得知她来自伏牛山区会种桃,而且篮子里还装着好些桃核,于是,白天叫她到果园干活,黑天叫她进内室服侍起居。才过几月,姥姥种在园里的桃没发芽,却惨死在这个地主家的园里。
泡桐在碱地里长成,妈妈在苦水里泡大,长到14岁,便出落成一个高挑、俊俏的姑娘。一天夜里,她进地主卧室整理被褥,老地主逼她上床。她眼前浮现出亲人吊死桃园的惨状,旧仇新恨涌上心头,在拼命挣扎中,把老色鬼的鼻头咬掉一块。妈妈被拉进桃园,绑在树上。地主婆本要撵她走,老地主却把她留下来许给哑巴儿子。妈妈儿次以死抗婚,可是,上吊被哑巴发现解脱,投水被哑巴捞出救活。
父亲虽是地主的儿子,可同他的其他兄弟待遇大不一样,他跟长工一起下地干活。每天干完活,吃过饭,他便回到自己的小天地,把床铺收拾好,等候着妈妈。他待妈妈很温顺,从没跟她红过脸。可是,他对他父亲没有好脸色,特别是遇见那个老色鬼趁他不在闯进卧室的时候,他会挥舞拳头,冲他吼叫。
妈妈同哑巴父亲生活的第三年,也就是咱们老家土改那年,生下了我这个唯一的女儿。土改过后,乡、村干部三番五次劝妈妈同哑巴少爷离婚。妈妈不忍抛开这个并没过过少爷生活的少爷,伏在爸爸胸前啜泣。不过,妈妈这个正在申请入党的村妇女干部,终究同父亲分手了。
离婚以后,父亲被他的在泉城郊区园艺场工作的弟弟接走了。不久,妈妈便带着我参加了“支援新疆建设妇女大队”。妇女大队集中到泉城等火车。在临上车的前一天,妈妈悄悄来到市郊园艺场,在场部大门前徘徊。他,近在咫尺。她想见他一面,然而,她没有跨进大门,只是望着门口一树桃花发呆。第二天,“支援新疆建设妇女大队”登上了西去的列车。同车的姐妹们在车厢里叽叽喳喳地说长道短,我妈妈却一言不发。
列车穿山绕岭,跨河过镇,从黄土高原落入祁连山下。车轮单调的咣当声千万次地重复着,车头载着一千多个生命不倦地前行,时光随着窗外的气流分分秒秒地逝去。我们进入河西走廊的时候,又是一个白昼了。
“从那年进疆到如今,三十几年过去了,我们孤儿寡母走过这三十几年可真不易哪”!艾莉双掌合成V形,支撑着下巴,沉浸在“这三十几年”的回忆中。
我做为老宣传工作者,对于艾莉妈妈当年参加的“支援新疆建设妇女大队”的内情知道一点。那时,驻疆部队的许多老同志,单身入伍,戒马半生,如今功成国兴,是该聚妻成家了。这批山东妇女的进疆,为解决这些老同志的婚姻问题创造了条件。对此,进疆的妇女多半心中有数,也心甘情愿。不出半年,建设大队只剩下几个不肯轻易再嫁的倔女人了。
“我妈就是个倔女人”。自谓当过语文教师的艾莉,接着娓娓道来——
当时,在建设大队,数我妈年轻,长得也俊。建设大队进石城农场不到一月,有人把她介绍给主管大队工作的一位场领导。偏偏我妈执意不从。同伴说她傻,她却缄口低眉,并不解释。半年后,建设大队解散,剩下几个人要分到生产连队去。当领导问她想上哪个连队时,她豪不犹豫地回答:园林队。
当时,园林队没有桃园,只有苹果园。果园班里,多数是女的,除了我妈,都是场部干部家属。她们家务繁重,出勤率低。我妈没有这个负担,又是党员,所以领导要她当果园班长。
园林队有个老技术员,解放前在内地一所农学院毕业后,在国民党政府一个农业机构干过几年。我妈领导的果园班扩大后,老技术员带领她们除了管苹果园外,还开辟了个小桃园。他常同妈妈在一起干活,尤其爱听她讲伏牛山下种桃的故事。收工时,他同妈妈常走在最后,待走到连队生活区,妈妈越过栅栏拐进家门时,他还在路口呆立着。要是哪天他在办公室忙业务,妈妈收工回家,准能发现路口有一个熟悉的身影,他在傻等着她。可那时,老技术员的痴情,打不开她的关闭的心扉。她愿意同他交朋友,但没有想过嫁给他。
然而,生活中常常会出现令人意想不到的契机。在五十年代中期刮起的一场政治旋风,波及园林队。那一年,老技术员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我妈因同“历史反革命分子”划不清界限而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可是,人们没料到,这个警告反而引发了我妈这个倔女人的爱情火焰。她不但不跟他划清界限,而且把他请到家里。在家门口,他俩一起栽下一棵桃树。第二年,结成了共同生活的伴侣。
列车驶出河西走廊,过嘉峪关,转入一望无际的干涸沙原。窗外的景致是一派单调的灰色,可车厢内艾莉的叙说却展示出一幅幅光怪陆离的生活画卷——
1958年暮春一日,妈妈到队上食堂打饭,见墙上贴着一张批判我继父的大字报,标题文绉绉的:“敢笑东风者戒”。大字报在高喊“红旗舞东风……”之后,作为批判靶子,引用了职工揭发继父在桃园吟过的一首唐诗:
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东风。(原诗为“春风”,大字报有误)
大字报作者披露出惊人的“发现”:不种向日葵而种桃,不颂向日葵而颂桃,而且,“借桃讽今”,公然耻笑伟大领袖颂扬过的象征社会主义的“东风”,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现行活动,是其老婆“地主少奶奶”颓废没落的精神寄托,也是“两个阶级敌人”臭味相投的铁证。
不久,妈妈和继父合种的那棵桃树被砍掉了;妈妈以“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少奶奶”的罪名被监督劳动,我继父因“反革命罪”被判刑劳改,1960年死在劳改队里了。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后来,我们家庭院里又出现一棵新桃树。原来,1962年,我那在泉城园艺场工作的叔叔,给妈妈寄来一包桃种。叔叔附信告诉妈妈:这是他的哑巴哥哥亲手栽种的桃树结下的。妈妈拉上我,一起把它种在庭院一角。桃种出苗后,我妈变得越发的沉默寡言。白天,妈上班管理公家的果园;回到家,除了招呼我吃、穿、上学外,便一门心思扑在她的桃苗上,施肥、浇水、剪枝,忙个不停。活忙完,搬条小板凳,坐在桃树边,凝视着它。
这棵桃树和我这个女孩子,在妈妈的悉心抚育下,熬过了一场又一场风风雨雨,终于成长起来。到1966年,我成了高中学生,桃树也挂满果实了。
然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一次掀翻了我们孤儿寡母的生活之舟。我顶着“黑崽子”帽被分到垦区最边远的单位劳动;妈妈以带病之躯,白天下地干活,晚间被队里的造反派拉去批斗。这伙人横扫院中的桃,挖出它的老根,而后批判妈妈“颂固坚持地主少奶奶的立场,不爱别的果树,偏爱地主家带来的桃”。
十年荒唐的闹剧终于结束了。1978年,妈妈虽已年近半百,双鬓斑白,但依然步履稳健,精神矍铄。她把我从“接受再教育”的边远连队接回家,要我专心复习功课,准备高考。她把希望寄托于我。第二年高考,我舍弃报考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志愿,按照妈妈的意思考入了农业大学园艺系。毕业后,我成了家。爱人和我是同班同学,分在乌市同一个科研部门工作。结婚时,我俩一道回到石城园林队妈妈家。妈妈是队上桃园的“园长”。她叫我和我爱人当桃园的技术指导,还让我们跟在泉城园艺场当技术顾问的叔叔取得联系,同他交流种桃经验。年过半百的妈妈焕发了青春。她带领桃园班的几个年轻人,一心扑在桃树上,汗水浇在桃园里。从前年起,队上的果园,妈妈的庭院,一棵棵桃树便陆续开花结果了。
这几年,我和我爱人每年都要回石城妈妈家好几次。特别是桃花盛开的春天,我们总要带上孩子丝丝回家看花。妈妈拉着小丝丝,坐在桃树下,桃花映照着这一老一幼的红润的脸。微风吹来,几瓣桃花落在丝丝头上,落入妈妈怀里。
看来颇有文才的艾莉的充满诗情画意的叙说,使我在精神上完全摆脱了车厢外茫茫戈壁的灰色圈,脑海浮现一幅五彩缤纷的新生活的画图,浮现一个感情深沉的“倔女人”的形象。我不由得问艾莉:“你和你爱人都在乌市工作,你妈妈怎么没迁来?”
妈妈已经退休,户口已经迁到乌市,可她就是不到乌市定居。她说在园林队的土房住惯了,觉得挺好,不愿离开它。每年,除了冬天,大部分时间住在园林队。队里挺照顾她,房子没有收回,房前房后的菜地、桃园也给她留着。她带过的果园班的姑娘常去和她作伴。他也爱同她们一起给桃树浇水、施肥。无论是院里的树,院外的园,她都认认真真地管。每年摘下的桃,除了留少量的家用,大都交给队里。队里给她发劳务补助费,她一个子儿也不要。为了发展种桃业,她常常给我们出这样那样的题目,要我们解答,要我们试验。
桃子不比别的水果,容易烂。妈妈常向我们叨叨这个问题,要我们设法解决桃子保鲜问题。她劝我们同在泉城园艺场的叔叔联合起来办这件事。其实,桃子保鲜课题早已列入我们单位的科研计划中,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干起来。经妈妈一再催促,在上级有关方面的支持下,我们俩同叔叔,当然还有乌市、泉城两单位的其他同事,联合开展了桃子贮藏保鲜的研究试验工作。这项研究试验搞了两三年了。这次我爸爸从山东带来的这篮鲜桃,算是这项联合攻关的科研成果。丝丝她爸爸和我出差到北京,便是为这项科研课题去的。
这次出差前,我对妈妈说,办完公事,我带丝丝回趟山东,到泉城把哑巴父亲接来住几年吧。她低头不语,半响才说:“你当女儿的要接父亲来住我不反对。只是你得告诉我他来新疆的日期。我要在他到来之前回石城去。我不见他,你也别把他带石城去,别让他知道我住的地方。”我注意到,妈妈讲这番话的时候,声音发颤,泪水盈眶。
我理解她老人家的心。我从她常常独自望着庭院桃花出神的目光中感觉到,她思念家乡的亲人,也思念他,忘不掉他。但是,她宁愿一辈子在心灵深处保留婚后相爱的那短暂的一幕场景,而不愿让离异半生后、晚年重逢时产生的情感冲击波搅乱它。何况,她恨他出身的封建地主家庭。这个家庭毁了姥姥,伤了妈妈。她不愿再见到这个家庭的成员,因为,一旦见到他们,便会勾起早已沉入心底的不堪回首的住事。平素,看电视电影,凡是再现旧社会苦难特别是妇女苦难的,她要我们去看,可自己从不去看。
列车在茫茫戈壁又穿行了一昼夜,进入鄯善县境。列车员开始收拾铺位上的卧具,性急的旅客着手整理自己的东西。车过盐湖站后,在女儿的示意下,哑巴老人取下货架上的行包,把桌面的杂物装进网兜里,把铺下的麦秸篮拖出来,抖去盖布上的灰尘,重新拉平盖严。我注意到,他在做这些事的时候,粗糙的手微微地颤抖。特别是,他掀开篮子的盖布,暗红包的鲜桃跳入眼帘时,缓缓移动的目光戛然而止。此刻,他那轻轻抚摸着桃面的手指,抖得更厉害了。
列车徐徐进站了。
“姥姥会来接我们吗?”小丝丝抬眼问妈妈。
“姥姥不会来。”妈妈抚摸着她桃红的小圆脸,轻声回答。
(1987年春,为思念友人,根据“乙丑(1985年)仲秋”日记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