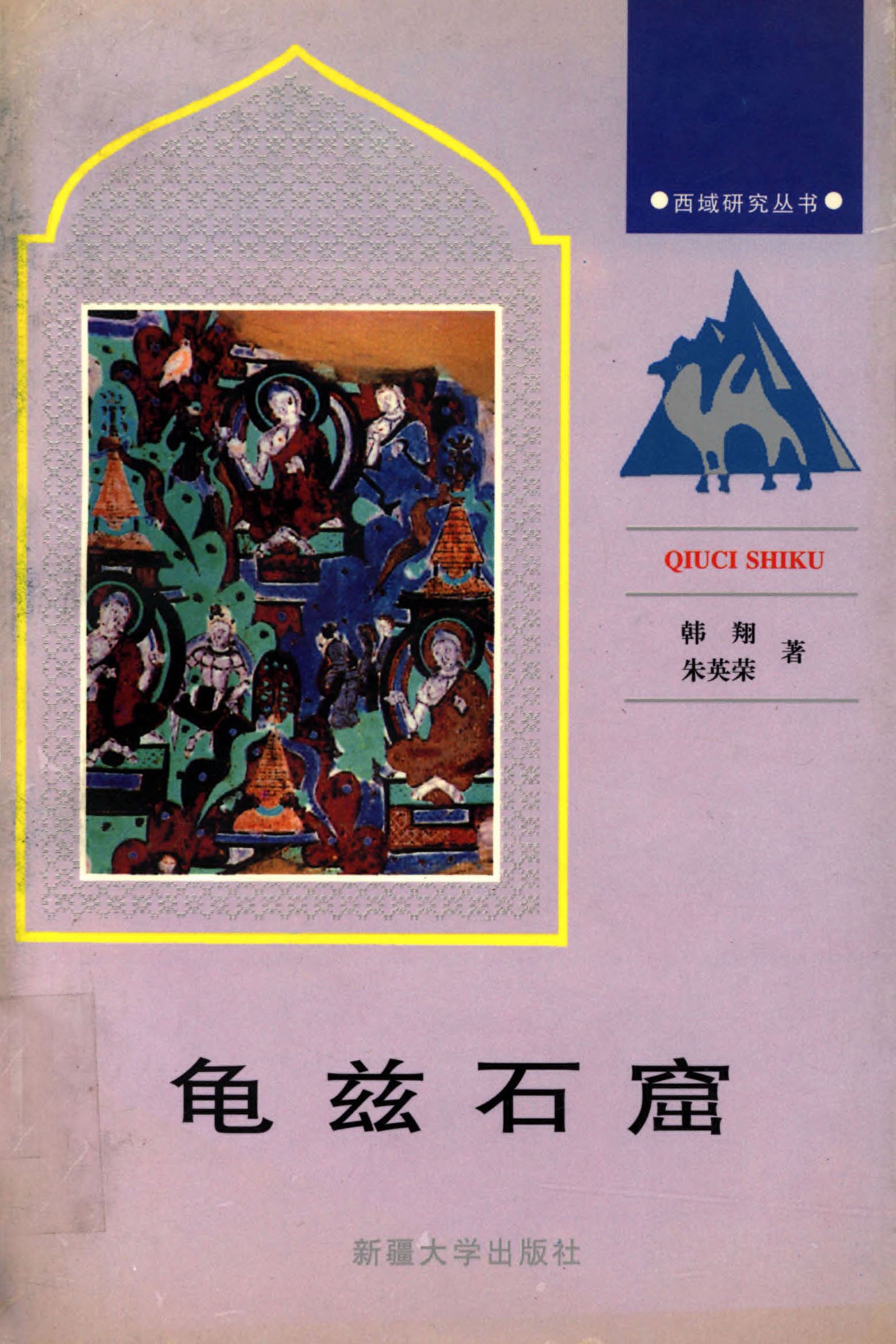一、龟兹文题记
| 内容出处: | 《龟兹石窟》 图书 |
| 唯一号: | 320020020210026008 |
| 颗粒名称: | 一、龟兹文题记 |
| 分类号: | P618;C55;I267 |
| 页数: | 6 |
| 页码: | 111-116 |
| 摘要: | 龟兹文为古代龟兹的通用文字。据《大唐西域记》的记载,龟兹“文字取则印度,粗有改变”。可见,当时的龟兹文是从印度传入的一种文字。但是,龟兹文到底记录了什么样的语言,是用什么字母书写的呢?从《大唐西域记》中是找不到答案的。在19世纪末叶以前,人们也几乎是毫无所知。1890年,美国人鲍威尔在库车附近获得贝叶形桦皮记载的古写本,1892年英国传教师威伯也在库车附近获得此类纸写本断片,它们都用婆罗迷文写成(即中亚婆罗迷文斜体)。 |
| 关键词: | 塔里木盆地 拉丁语 大唐西域记 希腊语 西域传 |
内容
龟兹文为古代龟兹的通用文字。据《大唐西域记》的记载,龟兹“文字取则印度,粗有改变”。可见,当时的龟兹文是从印度传入的一种文字。但是,龟兹文到底记录了什么样的语言,是用什么字母书写的呢?从《大唐西域记》中是找不到答案的。在19世纪末叶以前,人们也几乎是毫无所知。1890年,美国人鲍威尔在库车附近获得贝叶形桦皮记载的古写本,1892年英国传教师威伯也在库车附近获得此类纸写本断片,它们都用婆罗迷文写成(即中亚婆罗迷文斜体)。德国两位学者西格和西格林研究了这种语言的文献。他们在其1908年发表的《吐火罗语——印度斯基泰人的语言》一文中指出:这种语言分为两种很不相同的方言。他们称之为甲、乙两种方言(A和B),其间的关系尚弄不清楚。他们两人通过对这种语言的语法形式和词汇进一步研究,认为它是一种印欧语,但与亚洲的其他印欧语,即印度——伊兰语很不一样,而与西欧语言——希腊、拉丁、凯尔特、日耳曼语接近。如数词“八”叫Okadh(A)、okdh(B)等于希腊语okto,拉丁语octookadh(但梵语为astau);“二十”叫wiki(A)、ikan(B),等于希腊语vi—kati,拉丁语viginti;“一百”叫kandh(A)、kante(B),等于希腊语hekatou,拉丁语centum(读成kentum),但印度—伊兰语为satam;“马”叫yakwe(A)、yuk(B)等于拉丁语eguus,(但梵语为ava-s);“狗”叫ku(B),等于希腊语kuon,kyon(梵语则为va,svan);“别的”叫alyek,等于拉丁语alius。但这种语言在其整个外部形态上与上述古代欧洲语言有很大的不同,一下子很难看出它们之间有什么亲属关系的存在。他们在此基础上再作进一步研究发现:甲种方言残卷发现的地点几乎只限于焉耆,而乙种方言发现的地点主要是在库车。到了1913年,法国学者列维主张把乙种方言改称为龟兹语。1907年,法国人伯希和在库车西北约16公里的夏德郎峡口古垒中盗去一批木简,简上有婆罗迷字写的文字。列维考证了这批木简的一枚,其中一个国王名叫swarnate所签发的商队通行证。假如能从其他文献中找出这个名字,那么就可以确定这木简的年代以及使用这种语言的地区。他发现《旧唐书》卷一四八《龟兹传》有一个国王名苏伐叠,和唐太宗同时。苏伐叠显然就是swarnate的音译。swarnate相当梵文suvarnadeva,意译“金天”。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屈支条”说“闻诸先志曰:近代有王号金华”。“金华”的梵文就是suvarnapuspa。两个名字里都有suvarna(金)这个字,可见是有血缘关系。这都证明这个木简上写的国王就是龟兹(库车)的国王,而这种语言就是本地的语言。
列维还发现,甲种方言的写本文书只流行于焉耆、吐鲁番一带,在库车则无之,而乙种方言的写本不仅库车有,焉耆、吐鲁番一带也有。甲种方言是焉耆用于官方和佛教方面的语言,与古代焉耆居民的口头语言可能没有多大关系,但乙种方言除大量采用梵语之外,还保留了一些古代龟兹居民的口头语言。如梵文之“pravrajyā”义为前进,而汉译作“出家”,即龟兹语ost memlalne;梵文之“mithyā-drsti”义为谬见,而汉译作“外道”,即龟兹语Parna—nne,义为“外”;梵文之“sama,santi”义为“和”,而汉译作“灭”,即龟兹语kes,义为“息”。这里的Parnanne、kes等字,不是来自梵文,只能说是古代龟兹居民的土语。龟兹居民因与来自北方的突厥种民族接触,故在突厥语里也保存了一些龟兹语,如突厥语taman,来自龟兹语的tamane、tmane。
据周连宽先生在《在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中说:“斯坦因在敦煌西边汉长城废址的屯戍站附近盗去一批古物,其中有木简和丝织物。据说有一段残绢,是属于西汉末年的遗物,上面用汉文和印度文写着绢的原来尺寸,证明从西汉末起,已有印度商人把印度婆罗谜文字带到塔里木盆地。又佛教经典之东传,初期多由月氏人转介,据《高僧传》所载,最早为月氏僧支谦,于汉灵帝时(公元168—189年)来到洛阳,并传译《般若》、《道行般舟》、《首楞严》等三经。故黄文弼说:‘吾人知道佛教初入塔里木盆地,是由大月氏王伽腻色迦二世之介绍,而伽腻色迦王传播佛教,是以犍陀罗为中心,向西方传播,势力及于塔里木盆地当在纪元后2世纪,发蒙滋长当在3世纪以后’。黄氏此说,似较符合实际。三国魏甘露三年(公元258年)有龟兹沙门白延在洛阳白马寺译出大乘方等部中之《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二卷及小乘部中之《除灾患经》二卷。又晋简文帝咸安三年(公元371年)有月氏国人支施仑诵习《须赖经》、《首楞严》、《上金光首经》等,当时任翻译者名帛延,亦龟兹国人。4世纪时名僧鸠摩罗什,原籍虽属天竺,但生长于龟兹,于后秦弘始三年(公元401年)至长安,此后30年中凡译经98部。据伯希和说:有一佛经(《南条目录》402号)曾在龟兹金光寺中从梵文译为龟兹语,后于公元394年又从龟兹语译为汉文。《宋高僧传》记载,6世纪下半叶名僧彦琮曰‘如天竺经律传到龟兹,龟兹不解天竺语,呼天竺为印特伽国者,因而译之。若易解者,犹存梵语。如此胡梵俱有者是。’根椐以上的史料,我们不妨作如下的假定:龟兹在4世纪以前,原无文字,公元1世纪,印度商人把婆罗谜文字带来塔里木盆地,公元2世纪时印度僧人带来了梵文佛经,公元3世纪以后,龟兹佛教日益盛行,因而龟兹僧徒学习梵文者愈众。正如4世纪末法显经过鄯善国时所记的那样‘诸国俗人及沙门尽行天竺法,但有精粗。从此西行所经诸国类皆如是。唯国国胡语不同,然出家人皆习天竺书、天竺语。’从两汉至南北朝,龟兹官府文书和民间契约都用汉文,但从4世纪起,龟兹人民已经开始借用婆罗谜字,以表达本地的语言,于是逐渐形成了所谓‘乙种方言’(‘龟兹语’)的文字,4世纪末已有僧徒用这种文字翻译佛经。此后不仅僧徒用以译经,民间亦渐流行,至6世纪后,官府文书和民间契约,亦采用之,与汉文并行。”〔16〕
周连宽先生把龟兹文的产生时间定在公元4世纪,是有相当根椐的。又椐东初先生之说法:“法国pelliot于库车附近发现龟兹语记写的通行证,且其卷中,有玄奘来游此国时国王名字swapnate,据此可知龟兹语,在西历7世纪中叶,尚属通用的语言。”〔17〕那么,一直到公元7世纪中叶,龟兹文仍是很流行的。
目前,已经发现的龟兹文文献甚多,有《Dharamapāda》(《法句经》),《Mahāpa rinivāna》(《大般涅经》),《Nagaropama》(《古城比喻经》),《Karunā—pundarika》(《悲华经》),《Var nanarhavayauana》(《佛德赞叹偈》),《Pratimoksa》(《十诵比丘戒本》),《Paytai》(《波夜提》第七十一至第八十五),《Prayayascitika》(《十诵律波逸提》第八十九、第九十),《Pnalidesaniya》(《波罗提提舍尼》第一、第二),《Pratityasa mutpada—sastra》(《第十二因缘论》),《Smtyupasthana》(《念处》)的断片,《Maitreyasamitinataka》(关于弥勒的剧本),《Nandacaritanataka》(关于难陀的剧本)……。季羡林先生曾经说过:“最早的汉文里的印度文借字都不是直接从梵文译过来的,而是经过中亚古代语言……”“最早译过来的佛经不是直接根椐梵文或巴利文,而是经过中亚和新疆一带今天已经不存在的许多古代语言转译过来的,比如焉耆语和龟兹语等等都是。”〔18〕因此,在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龟兹文作出过重大的贡献。
古龟兹存在的时间很长。在我国的古文献中,《汉书·西域传》即有关于龟兹的记载,其后《晋书·四夷传》、《魏书·西域传》、《隋书·西域传》、《新唐书·西域传》、《旧唐书·西戎传》中都有关于龟兹的记载,而从东汉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西域长史班超立龟兹之侍子白霸为王起,一直到《悟空入竺记》中所记的龟兹王白环为止。龟兹的白氏王朝延续了近700年。唐德宗贞元六年(公元790年),吐蕃攻陷龟兹。9世纪中叶,住在蒙古草原上的回鹘人在内忧外患的逼迫下四处流散,其中的主要部分占据了古高昌国即唐西州地区,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辖境西至库车、东抵哈密东境,北越天山、南接于阗。龟兹从此并入高昌回鹘王国版图之内,白氏王朝也随之而消失。
在白氏王朝统治的700年内,龟兹经济发达,国势强盛,成为西域的一个大国。《新唐书·西域传》记载:“龟兹……横千里,纵六百里。”《大唐西域记》记载:“屈支国(旧曰龟兹),东西千余里,南北六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七八里。”
因此,在白氏王朝强大的经济基础上,龟兹的文化十分发达,突出地表现在佛教文化上,使这里出现了如鸠摩罗什这样的佛教大师。大量的佛经从梵文译成龟兹文,再通过龟兹高僧、居士译成汉文,为我国古代佛教文化的昌盛奠定了基础,羽田亨在《西域文化史》中说:“三世纪中叶有龟兹人白延来魏从事佛典的汉译工作,北魏朱士行到于阗求大乘佛典以及汉译最古佛典中有龟兹语音译或义译的词”,凡此等等,说明了龟兹文不仅为龟兹的文化,也为中国的文化作出过特殊的贡献。
目前,在龟兹石窟中被保存下来的龟兹文可分成两类:一类是古代龟兹人在石窟内的题名或题记,如库木吐拉石窟69号窟为三重套窟,前室为支提窟,中室为昆诃罗窟,后室为禅窟。在中室正壁、右壁刻有大量龟兹文题记和题名,还有汉文题名如“戒香”、“还源”、“定铨”、“惠亲”等(图版23)。一类则写在一幅幅壁画的上面,用来说明壁画的内容。如库木吐拉石窟50号窟是一个中心柱形支提窟,窟的左右壁用白条划成8行,每行用不同颜色分成10个方格,每个方格中画出一幅供养故事画,上面的白条中则写着龟兹文,是说明下面这些供养故事画的内容的(图版24)。今天,这些龟兹文已经成为我们研究古代龟兹的文字和语言的不可缺少的第一手资料了。
列维还发现,甲种方言的写本文书只流行于焉耆、吐鲁番一带,在库车则无之,而乙种方言的写本不仅库车有,焉耆、吐鲁番一带也有。甲种方言是焉耆用于官方和佛教方面的语言,与古代焉耆居民的口头语言可能没有多大关系,但乙种方言除大量采用梵语之外,还保留了一些古代龟兹居民的口头语言。如梵文之“pravrajyā”义为前进,而汉译作“出家”,即龟兹语ost memlalne;梵文之“mithyā-drsti”义为谬见,而汉译作“外道”,即龟兹语Parna—nne,义为“外”;梵文之“sama,santi”义为“和”,而汉译作“灭”,即龟兹语kes,义为“息”。这里的Parnanne、kes等字,不是来自梵文,只能说是古代龟兹居民的土语。龟兹居民因与来自北方的突厥种民族接触,故在突厥语里也保存了一些龟兹语,如突厥语taman,来自龟兹语的tamane、tmane。
据周连宽先生在《在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中说:“斯坦因在敦煌西边汉长城废址的屯戍站附近盗去一批古物,其中有木简和丝织物。据说有一段残绢,是属于西汉末年的遗物,上面用汉文和印度文写着绢的原来尺寸,证明从西汉末起,已有印度商人把印度婆罗谜文字带到塔里木盆地。又佛教经典之东传,初期多由月氏人转介,据《高僧传》所载,最早为月氏僧支谦,于汉灵帝时(公元168—189年)来到洛阳,并传译《般若》、《道行般舟》、《首楞严》等三经。故黄文弼说:‘吾人知道佛教初入塔里木盆地,是由大月氏王伽腻色迦二世之介绍,而伽腻色迦王传播佛教,是以犍陀罗为中心,向西方传播,势力及于塔里木盆地当在纪元后2世纪,发蒙滋长当在3世纪以后’。黄氏此说,似较符合实际。三国魏甘露三年(公元258年)有龟兹沙门白延在洛阳白马寺译出大乘方等部中之《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二卷及小乘部中之《除灾患经》二卷。又晋简文帝咸安三年(公元371年)有月氏国人支施仑诵习《须赖经》、《首楞严》、《上金光首经》等,当时任翻译者名帛延,亦龟兹国人。4世纪时名僧鸠摩罗什,原籍虽属天竺,但生长于龟兹,于后秦弘始三年(公元401年)至长安,此后30年中凡译经98部。据伯希和说:有一佛经(《南条目录》402号)曾在龟兹金光寺中从梵文译为龟兹语,后于公元394年又从龟兹语译为汉文。《宋高僧传》记载,6世纪下半叶名僧彦琮曰‘如天竺经律传到龟兹,龟兹不解天竺语,呼天竺为印特伽国者,因而译之。若易解者,犹存梵语。如此胡梵俱有者是。’根椐以上的史料,我们不妨作如下的假定:龟兹在4世纪以前,原无文字,公元1世纪,印度商人把婆罗谜文字带来塔里木盆地,公元2世纪时印度僧人带来了梵文佛经,公元3世纪以后,龟兹佛教日益盛行,因而龟兹僧徒学习梵文者愈众。正如4世纪末法显经过鄯善国时所记的那样‘诸国俗人及沙门尽行天竺法,但有精粗。从此西行所经诸国类皆如是。唯国国胡语不同,然出家人皆习天竺书、天竺语。’从两汉至南北朝,龟兹官府文书和民间契约都用汉文,但从4世纪起,龟兹人民已经开始借用婆罗谜字,以表达本地的语言,于是逐渐形成了所谓‘乙种方言’(‘龟兹语’)的文字,4世纪末已有僧徒用这种文字翻译佛经。此后不仅僧徒用以译经,民间亦渐流行,至6世纪后,官府文书和民间契约,亦采用之,与汉文并行。”〔16〕
周连宽先生把龟兹文的产生时间定在公元4世纪,是有相当根椐的。又椐东初先生之说法:“法国pelliot于库车附近发现龟兹语记写的通行证,且其卷中,有玄奘来游此国时国王名字swapnate,据此可知龟兹语,在西历7世纪中叶,尚属通用的语言。”〔17〕那么,一直到公元7世纪中叶,龟兹文仍是很流行的。
目前,已经发现的龟兹文文献甚多,有《Dharamapāda》(《法句经》),《Mahāpa rinivāna》(《大般涅经》),《Nagaropama》(《古城比喻经》),《Karunā—pundarika》(《悲华经》),《Var nanarhavayauana》(《佛德赞叹偈》),《Pratimoksa》(《十诵比丘戒本》),《Paytai》(《波夜提》第七十一至第八十五),《Prayayascitika》(《十诵律波逸提》第八十九、第九十),《Pnalidesaniya》(《波罗提提舍尼》第一、第二),《Pratityasa mutpada—sastra》(《第十二因缘论》),《Smtyupasthana》(《念处》)的断片,《Maitreyasamitinataka》(关于弥勒的剧本),《Nandacaritanataka》(关于难陀的剧本)……。季羡林先生曾经说过:“最早的汉文里的印度文借字都不是直接从梵文译过来的,而是经过中亚古代语言……”“最早译过来的佛经不是直接根椐梵文或巴利文,而是经过中亚和新疆一带今天已经不存在的许多古代语言转译过来的,比如焉耆语和龟兹语等等都是。”〔18〕因此,在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龟兹文作出过重大的贡献。
古龟兹存在的时间很长。在我国的古文献中,《汉书·西域传》即有关于龟兹的记载,其后《晋书·四夷传》、《魏书·西域传》、《隋书·西域传》、《新唐书·西域传》、《旧唐书·西戎传》中都有关于龟兹的记载,而从东汉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西域长史班超立龟兹之侍子白霸为王起,一直到《悟空入竺记》中所记的龟兹王白环为止。龟兹的白氏王朝延续了近700年。唐德宗贞元六年(公元790年),吐蕃攻陷龟兹。9世纪中叶,住在蒙古草原上的回鹘人在内忧外患的逼迫下四处流散,其中的主要部分占据了古高昌国即唐西州地区,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辖境西至库车、东抵哈密东境,北越天山、南接于阗。龟兹从此并入高昌回鹘王国版图之内,白氏王朝也随之而消失。
在白氏王朝统治的700年内,龟兹经济发达,国势强盛,成为西域的一个大国。《新唐书·西域传》记载:“龟兹……横千里,纵六百里。”《大唐西域记》记载:“屈支国(旧曰龟兹),东西千余里,南北六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七八里。”
因此,在白氏王朝强大的经济基础上,龟兹的文化十分发达,突出地表现在佛教文化上,使这里出现了如鸠摩罗什这样的佛教大师。大量的佛经从梵文译成龟兹文,再通过龟兹高僧、居士译成汉文,为我国古代佛教文化的昌盛奠定了基础,羽田亨在《西域文化史》中说:“三世纪中叶有龟兹人白延来魏从事佛典的汉译工作,北魏朱士行到于阗求大乘佛典以及汉译最古佛典中有龟兹语音译或义译的词”,凡此等等,说明了龟兹文不仅为龟兹的文化,也为中国的文化作出过特殊的贡献。
目前,在龟兹石窟中被保存下来的龟兹文可分成两类:一类是古代龟兹人在石窟内的题名或题记,如库木吐拉石窟69号窟为三重套窟,前室为支提窟,中室为昆诃罗窟,后室为禅窟。在中室正壁、右壁刻有大量龟兹文题记和题名,还有汉文题名如“戒香”、“还源”、“定铨”、“惠亲”等(图版23)。一类则写在一幅幅壁画的上面,用来说明壁画的内容。如库木吐拉石窟50号窟是一个中心柱形支提窟,窟的左右壁用白条划成8行,每行用不同颜色分成10个方格,每个方格中画出一幅供养故事画,上面的白条中则写着龟兹文,是说明下面这些供养故事画的内容的(图版24)。今天,这些龟兹文已经成为我们研究古代龟兹的文字和语言的不可缺少的第一手资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