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世纪上半俄国商人在新疆的无约贸易
| 内容出处: | 《新疆对苏(俄)贸易史 1660—1990》 图书 |
| 唯一号: | 320020020210017868 |
| 颗粒名称: | 一、19世纪上半俄国商人在新疆的无约贸易 |
| 分类号: | F127;F426;F124 |
| 页数: | 10 |
| 页码: | 42-51 |
| 摘要: | 19世纪初,随着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俄国力图进一步扩大对华贸易。1801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继位。在他执政之始,就十分重视西伯利亚的经济发展和俄国在远东及北美的利益,同时着手扩展中俄两国的通商。1801年俄国在恰克图制定了新的对华贸易章程。1803年,由俄国政府资助的克鲁逊什特恩舰队开始作环球航行,以便寻求开辟对华海上贸易。1805年1月,俄国商务大臣鲁缅采夫上奏沙皇,要求俄国正式照会清政府,准两国商人在布赫塔尔明斯克以至整个额尔齐斯河一带通商贸易①。 |
| 关键词: | 明斯克 哈萨克 塔尔巴哈台 恰克图 清政府 |
内容
19世纪初,随着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俄国力图进一步扩大对华贸易。1801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继位。在他执政之始,就十分重视西伯利亚的经济发展和俄国在远东及北美的利益,同时着手扩展中俄两国的通商。1801年俄国在恰克图制定了新的对华贸易章程。1803年,由俄国政府资助的克鲁逊什特恩舰队开始作环球航行,以便寻求开辟对华海上贸易。1805年1月,俄国商务大臣鲁缅采夫上奏沙皇,要求俄国正式照会清政府,准两国商人在布赫塔尔明斯克以至整个额尔齐斯河一带通商贸易①。同年7月,俄国政府派出以戈洛夫金伯爵为首的使团前往北京与清政府谈判通商。俄方的要求是:开放整个中俄边境的通商贸易,东北方面每年至少准许一定数量的俄国船只通航阿穆尔河(即中国黑龙江),如果大船实在不能在该河上通行,即准在河口建立一处贸易屯货栈;西北方面要求清政府开放俄国商人在伊犁与塔尔巴哈台的贸易。同时对俄国商船开放广州,向北京、广东和阿穆尔河口派遣商务代表。①1805年10月,戈洛夫金使团到达恰克图,清政府为迎接使团作了准备。但终因礼仪等问题,俄国使团自张家口返回,出使未获结果。与此同时,俄国单方面采取了扩大对华贸易的行动。1805年12月,由克鲁逊什特恩率领的环球船队的两艘商船“希望”号和“涅瓦”号抵达广州城,要求入城贸易。两广总督那彦成拒绝接纳,俄商船便通过英商疏通了粤海关监督延丰,得开仓贸易许可。清政府闻报,以“擅准进浦卸货”罪将延丰革职,并晓喻俄商:向例只准在恰克图地方通市贸易,本有一定界限。嗣后遇有俄国商船来粤贸易,惟当严行驳回。②杜绝了俄方要求开放广东海上贸易的企图。
恢复新疆对俄直接贸易,是19世纪初俄国政府对华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是与俄国加紧对中亚哈萨克部的兼并相一致的。1805年,俄国在西西伯利亚地方当局支持商人涅尔平在靠近中国卡伦的列姆巴科夫斯克镇建立了固定贸易点,以吸引新疆商人前往贸易。西西伯利亚地方当局还试图开辟谢米巴拉金斯克至新疆阿克苏城的贸易。
18世纪末,清政府禁止在新疆开放对俄贸易的政策虽然没有改变,但已有所松动。1797年,清理藩院声明:“俄罗斯除恰克图贸易外,其霍尼迈拉呼卡伦(又称辉迈拉虎卡伦,位于斋桑湖北额尔齐斯河左岸,与俄布赫塔尔明斯克相对)俱不准通商,若由萨纳特衙门(Ceнaт,枢密院)行文,即将原文报明本院,听候办理”。③这项谕令表明,清政府对中国西部俄商违约贸易日益扩大的状况十分清楚,一方面仍通令禁止,同时也不排除在俄国官方正式提出西部中俄通商问题时与之谈判的可能。这是面对现实的务实态度。因为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俄商在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的贸易已相当普遍,随着当地出现越来越多的做俄国商品生意的商人,地方当局渐习以为常了。因此带有哈萨克王公通商证明或信件的必要性便自行消失了。19世纪初,新疆与俄国贸易额已相当可观,双方交易已为两国沿边地区所接受,并对两国上述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补充。即使是在伊犁、塔尔巴哈台的清地方官员中,也有人希望实现俄国与新疆贸易的合法化。①进入19世纪后,清政府再未发出有关禁止新疆中俄通商的指令,俄国对新疆贸易的性质已由18世纪后半的违禁走私贸易转变为半公开的无约贸易。
1807年,第一支由500匹驼马组成的俄国商队在商人穆尔塔金的带领下,冒充中亚商人之名,自谢米巴拉金斯克进入塔城,开辟了近代西部中俄商队贸易的历史。1809年,商人涅尔平自布赫塔尔明斯克派出另一支商队到达塔城,运来价值5000卢布的俄国商品,交易后返回。1810年,涅尔平的另一支商队由官方译员普蒂姆来地率领,带往塔城价值10000卢布的货物。西部中俄商队贸易迅速发展,1811年,经布赫塔尔明斯克一地输往新疆的俄国货物价值约15万卢布。②西部中俄贸易的发展引起俄国西西伯利亚地方当局的重视,他们曾说服两个从塔什干和喀山来的著名穆斯林商人,装备了一支商队进入阿克苏,以调查在该地扩大俄国贸易的可能性。1813年,西西伯利亚地方当局派遣了一支由译员巴宾洛夫陪同前往的俄国官方商队。这个商队携带着价值32.1万卢布的货物,自谢米巴拉金斯克出发,穿过柯尔克孜(布鲁特)领地,到达阿克苏和喀什噶尔。次年,这支商队带着价值100万卢布的茶叶、大黄、织品、锦锻等货物返回。俄国官方第一次直接经营对新疆的贸易,即获利相当可观。随着贸易的扩大,新疆商人也开始带着货物或银两,前往布赫塔尔明斯克与俄商易货。①据这一时期俄方的调查,输入新疆的俄国呢料子和皮革等货物大部分卖给当地清驻军,一部份货物向中国商人换取中国货或银锭。除布赫塔尔明斯克外,谢米巴拉金斯克这时成为俄商对新疆贸易的另一中心。根据当地税册记载,1803年至1813年10年之间,谢米巴拉金斯克同伊犁、塔尔巴哈台和阿克苏的交易额增长了一倍多;自1814至1824年则增长了2倍。其中1803年俄商经谢米巴拉金斯克出口价值约69606银卢布的俄国货物,1812年出口额为112547银卢布,1821年当地出口俄国货物的价值已达141817银卢布。②
进入19世纪以后,俄国加紧兼并被他们称之为“通向亚洲各国地方的关键和大门”的中亚哈萨克草原。1822年,俄国颁布了《关于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标志着对中亚哈萨克部的兼并基本完成。俄国的势力推进到中亚锡尔河一线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中国西部边境,穿越哈萨克草原直接到达新疆的道路畅通了。此外,进入19世纪后,俄国中、西部工业产品在对新疆贸易中的比重增长。由于这些因素,谢米巴拉金斯克和彼得巴甫洛夫斯克在俄国对新疆贸易中的意义日益重要,先前西部中俄贸易集散地布赫塔尔明斯克的作用大大降低了。
19世纪上半,清政府对西向贸易的管理更趋严格。按《哈萨克贸易章程》规定,凡西向贸易商人到达管理卡伦后,必须交验证明书(牌禀),查明人、货及所带牲畜等与证明书相符,方准入卡;贸易期间,商人在贸易亭附近专门设立的土堡内居住,清官兵在堡门堆房稽查出入,平日不得私自进城;因事必须进城者,报明贸易亭管理官员,请领执照,限以时刻返回,呈缴执照;贸易后如有剩余货物,令自行带回,不得借货未换完滞留;遇有犯事,由清地方官员审理。①俄商管理照此章程执行。据1845年到过伊犁和塔尔巴哈台的H.N.柳比莫夫记载,“所有商人到塔城后,就被安置在一个不大的住宅内,院子围以土墙,货物堆放进中国关卡,在关卡里,有专门的仓库。白天,商人空闲,可以外出,同来他们那里的中国商人接触,…….但是,进中国城和去见中国商人洽谈贸易,必须得到地方官员的允许,在关卡职员的陪同下前往。晚上,住宅的院门关闭。在院内除了居住的人员外,还有商队的牲畜,几百匹骆驼、马、绵羊等”。②
俄商运入新疆的货物主要有皮革、呢子、棉纺织品、毛织品、毛皮、铜铁制品及日用杂品。新疆输出的主要货物是绸缎、茶叶、大布及杂品。茶叶输出额在19世纪30年代以后迅速增长,1842年输出总值为5.96万卢布,1851年增加到57.98万卢布,几乎增长了9倍。同一时期红茶输出由2.12万卢布增加到48.42万卢布,增长了22倍。
俄国经伊犁、塔尔巴哈台输入谢米巴拉金斯克中国茶叶数量统计
19世纪上半俄国在对新疆贸易中处于出超,每年有相当数量的白银流入俄国。
俄国对经布赫塔玛尔明斯克和谢米巴拉金斯克流入俄国白银数额统计
40年代以后,新疆对俄输出的各类茶叶骤增,使双方贸易差额缩小,新疆流入俄国白银量递减。这一时期,俄国对新疆的贸易已过渡到以规模较大的商队贸易为主,贸易额有明显增长。19世纪上半,新疆对俄贸易额已相当于中俄在恰克图口岸贸易总额的3%—4%,到40年代末,俄国对新疆贸易额达到中俄恰克图贸易总额的6%。
1840年至1850年俄国对新疆贸易统计
1842年和1850年俄国对新疆输出货物统计
1842年和1850年新疆对俄国输出货物统计
十九世纪上半叶,俄国商人萨姆索诺夫和伊布拉吉·阿米洛夫在对新疆的商队贸易中起着重要作用。萨姆索诺夫是俄商中第一个在伊犁作生意的人。他主要从事谢米巴拉金斯克至伊犁的商队贸易,1845年交易额为20000银卢布。伊布拉吉·阿米洛夫每年自谢米巴位金斯克向塔城输入15000卢布的俄国货物。
随着双边贸易的发展,新疆天山以南各主要城镇市场也渐为俄国商品占据。早在1823年,俄国便与浩罕汗国之间存在一个协议,根据此协议规定,浩罕将提供“安全护送队”,保护穿越浩罕领地到新疆的俄国商队。俄商通常由俄境出发,穿过中亚哈萨克草原及浩罕领地,向东一直深入到库车、阿克苏、喀什噶尔。阿克苏在19世纪30年代已成了中俄商品交易的大市场。俄国的海豹皮、兽皮、绿色天鹅绒、金银锈花线、博勒克罕皮革、铁铲、锄头、洋苏木、塔糖、海狸皮、阿斯特拉罕羔皮、大幅面厚黑呢等远销和田市场。为了谋取厚利,新疆中国商人也开始避开清军的稽查,私自越界进入俄境易货,一些胆大的商人甚至到了俄国国内市场中心之一——下诺夫哥罗德集市参加贸易。①
恢复新疆对俄直接贸易,是19世纪初俄国政府对华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是与俄国加紧对中亚哈萨克部的兼并相一致的。1805年,俄国在西西伯利亚地方当局支持商人涅尔平在靠近中国卡伦的列姆巴科夫斯克镇建立了固定贸易点,以吸引新疆商人前往贸易。西西伯利亚地方当局还试图开辟谢米巴拉金斯克至新疆阿克苏城的贸易。
18世纪末,清政府禁止在新疆开放对俄贸易的政策虽然没有改变,但已有所松动。1797年,清理藩院声明:“俄罗斯除恰克图贸易外,其霍尼迈拉呼卡伦(又称辉迈拉虎卡伦,位于斋桑湖北额尔齐斯河左岸,与俄布赫塔尔明斯克相对)俱不准通商,若由萨纳特衙门(Ceнaт,枢密院)行文,即将原文报明本院,听候办理”。③这项谕令表明,清政府对中国西部俄商违约贸易日益扩大的状况十分清楚,一方面仍通令禁止,同时也不排除在俄国官方正式提出西部中俄通商问题时与之谈判的可能。这是面对现实的务实态度。因为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俄商在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的贸易已相当普遍,随着当地出现越来越多的做俄国商品生意的商人,地方当局渐习以为常了。因此带有哈萨克王公通商证明或信件的必要性便自行消失了。19世纪初,新疆与俄国贸易额已相当可观,双方交易已为两国沿边地区所接受,并对两国上述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补充。即使是在伊犁、塔尔巴哈台的清地方官员中,也有人希望实现俄国与新疆贸易的合法化。①进入19世纪后,清政府再未发出有关禁止新疆中俄通商的指令,俄国对新疆贸易的性质已由18世纪后半的违禁走私贸易转变为半公开的无约贸易。
1807年,第一支由500匹驼马组成的俄国商队在商人穆尔塔金的带领下,冒充中亚商人之名,自谢米巴拉金斯克进入塔城,开辟了近代西部中俄商队贸易的历史。1809年,商人涅尔平自布赫塔尔明斯克派出另一支商队到达塔城,运来价值5000卢布的俄国商品,交易后返回。1810年,涅尔平的另一支商队由官方译员普蒂姆来地率领,带往塔城价值10000卢布的货物。西部中俄商队贸易迅速发展,1811年,经布赫塔尔明斯克一地输往新疆的俄国货物价值约15万卢布。②西部中俄贸易的发展引起俄国西西伯利亚地方当局的重视,他们曾说服两个从塔什干和喀山来的著名穆斯林商人,装备了一支商队进入阿克苏,以调查在该地扩大俄国贸易的可能性。1813年,西西伯利亚地方当局派遣了一支由译员巴宾洛夫陪同前往的俄国官方商队。这个商队携带着价值32.1万卢布的货物,自谢米巴拉金斯克出发,穿过柯尔克孜(布鲁特)领地,到达阿克苏和喀什噶尔。次年,这支商队带着价值100万卢布的茶叶、大黄、织品、锦锻等货物返回。俄国官方第一次直接经营对新疆的贸易,即获利相当可观。随着贸易的扩大,新疆商人也开始带着货物或银两,前往布赫塔尔明斯克与俄商易货。①据这一时期俄方的调查,输入新疆的俄国呢料子和皮革等货物大部分卖给当地清驻军,一部份货物向中国商人换取中国货或银锭。除布赫塔尔明斯克外,谢米巴拉金斯克这时成为俄商对新疆贸易的另一中心。根据当地税册记载,1803年至1813年10年之间,谢米巴拉金斯克同伊犁、塔尔巴哈台和阿克苏的交易额增长了一倍多;自1814至1824年则增长了2倍。其中1803年俄商经谢米巴拉金斯克出口价值约69606银卢布的俄国货物,1812年出口额为112547银卢布,1821年当地出口俄国货物的价值已达141817银卢布。②
进入19世纪以后,俄国加紧兼并被他们称之为“通向亚洲各国地方的关键和大门”的中亚哈萨克草原。1822年,俄国颁布了《关于西伯利亚吉尔吉斯人条例》,标志着对中亚哈萨克部的兼并基本完成。俄国的势力推进到中亚锡尔河一线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中国西部边境,穿越哈萨克草原直接到达新疆的道路畅通了。此外,进入19世纪后,俄国中、西部工业产品在对新疆贸易中的比重增长。由于这些因素,谢米巴拉金斯克和彼得巴甫洛夫斯克在俄国对新疆贸易中的意义日益重要,先前西部中俄贸易集散地布赫塔尔明斯克的作用大大降低了。
19世纪上半,清政府对西向贸易的管理更趋严格。按《哈萨克贸易章程》规定,凡西向贸易商人到达管理卡伦后,必须交验证明书(牌禀),查明人、货及所带牲畜等与证明书相符,方准入卡;贸易期间,商人在贸易亭附近专门设立的土堡内居住,清官兵在堡门堆房稽查出入,平日不得私自进城;因事必须进城者,报明贸易亭管理官员,请领执照,限以时刻返回,呈缴执照;贸易后如有剩余货物,令自行带回,不得借货未换完滞留;遇有犯事,由清地方官员审理。①俄商管理照此章程执行。据1845年到过伊犁和塔尔巴哈台的H.N.柳比莫夫记载,“所有商人到塔城后,就被安置在一个不大的住宅内,院子围以土墙,货物堆放进中国关卡,在关卡里,有专门的仓库。白天,商人空闲,可以外出,同来他们那里的中国商人接触,…….但是,进中国城和去见中国商人洽谈贸易,必须得到地方官员的允许,在关卡职员的陪同下前往。晚上,住宅的院门关闭。在院内除了居住的人员外,还有商队的牲畜,几百匹骆驼、马、绵羊等”。②
俄商运入新疆的货物主要有皮革、呢子、棉纺织品、毛织品、毛皮、铜铁制品及日用杂品。新疆输出的主要货物是绸缎、茶叶、大布及杂品。茶叶输出额在19世纪30年代以后迅速增长,1842年输出总值为5.96万卢布,1851年增加到57.98万卢布,几乎增长了9倍。同一时期红茶输出由2.12万卢布增加到48.42万卢布,增长了22倍。
俄国经伊犁、塔尔巴哈台输入谢米巴拉金斯克中国茶叶数量统计
19世纪上半俄国在对新疆贸易中处于出超,每年有相当数量的白银流入俄国。
俄国对经布赫塔玛尔明斯克和谢米巴拉金斯克流入俄国白银数额统计
40年代以后,新疆对俄输出的各类茶叶骤增,使双方贸易差额缩小,新疆流入俄国白银量递减。这一时期,俄国对新疆的贸易已过渡到以规模较大的商队贸易为主,贸易额有明显增长。19世纪上半,新疆对俄贸易额已相当于中俄在恰克图口岸贸易总额的3%—4%,到40年代末,俄国对新疆贸易额达到中俄恰克图贸易总额的6%。
1840年至1850年俄国对新疆贸易统计
1842年和1850年俄国对新疆输出货物统计
1842年和1850年新疆对俄国输出货物统计
十九世纪上半叶,俄国商人萨姆索诺夫和伊布拉吉·阿米洛夫在对新疆的商队贸易中起着重要作用。萨姆索诺夫是俄商中第一个在伊犁作生意的人。他主要从事谢米巴拉金斯克至伊犁的商队贸易,1845年交易额为20000银卢布。伊布拉吉·阿米洛夫每年自谢米巴位金斯克向塔城输入15000卢布的俄国货物。
随着双边贸易的发展,新疆天山以南各主要城镇市场也渐为俄国商品占据。早在1823年,俄国便与浩罕汗国之间存在一个协议,根据此协议规定,浩罕将提供“安全护送队”,保护穿越浩罕领地到新疆的俄国商队。俄商通常由俄境出发,穿过中亚哈萨克草原及浩罕领地,向东一直深入到库车、阿克苏、喀什噶尔。阿克苏在19世纪30年代已成了中俄商品交易的大市场。俄国的海豹皮、兽皮、绿色天鹅绒、金银锈花线、博勒克罕皮革、铁铲、锄头、洋苏木、塔糖、海狸皮、阿斯特拉罕羔皮、大幅面厚黑呢等远销和田市场。为了谋取厚利,新疆中国商人也开始避开清军的稽查,私自越界进入俄境易货,一些胆大的商人甚至到了俄国国内市场中心之一——下诺夫哥罗德集市参加贸易。①
附注
(苏)《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俄国对外政策(俄国外交部文件集)》,1961年莫斯科版,第一集,第二卷,第297页、301页。转引自《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二期166页。; (苏)Ц.И.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中译本,1983年哈尔滨版第55—56页。; 《清仁宗实录》卷156,第25—26页。; 《朔方备乘》卷47.; (美)约瑟夫.费莱彻《剑桥中国史》第10卷,第七章。转引自《西北历史资料》,1980年第3期。; 斯拉德科夫斯基《俄中贸易和经济关系》第211页。; 《剑侨中国史》第10卷,第七章。; (苏)A.H.霍赫洛夫《18世纪9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中国的对外贸易》。;《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一,第3—4页。; H.维谢洛夫斯基《H.И.柳比莫夫乔装成商人霍罗舍夫去塔城和伊梨的游记》圣彼得堡1909年版。转引自许淑明《伊犁、塔尔巴哈台开埠记》。;《剑桥中国史》第10卷,第7章。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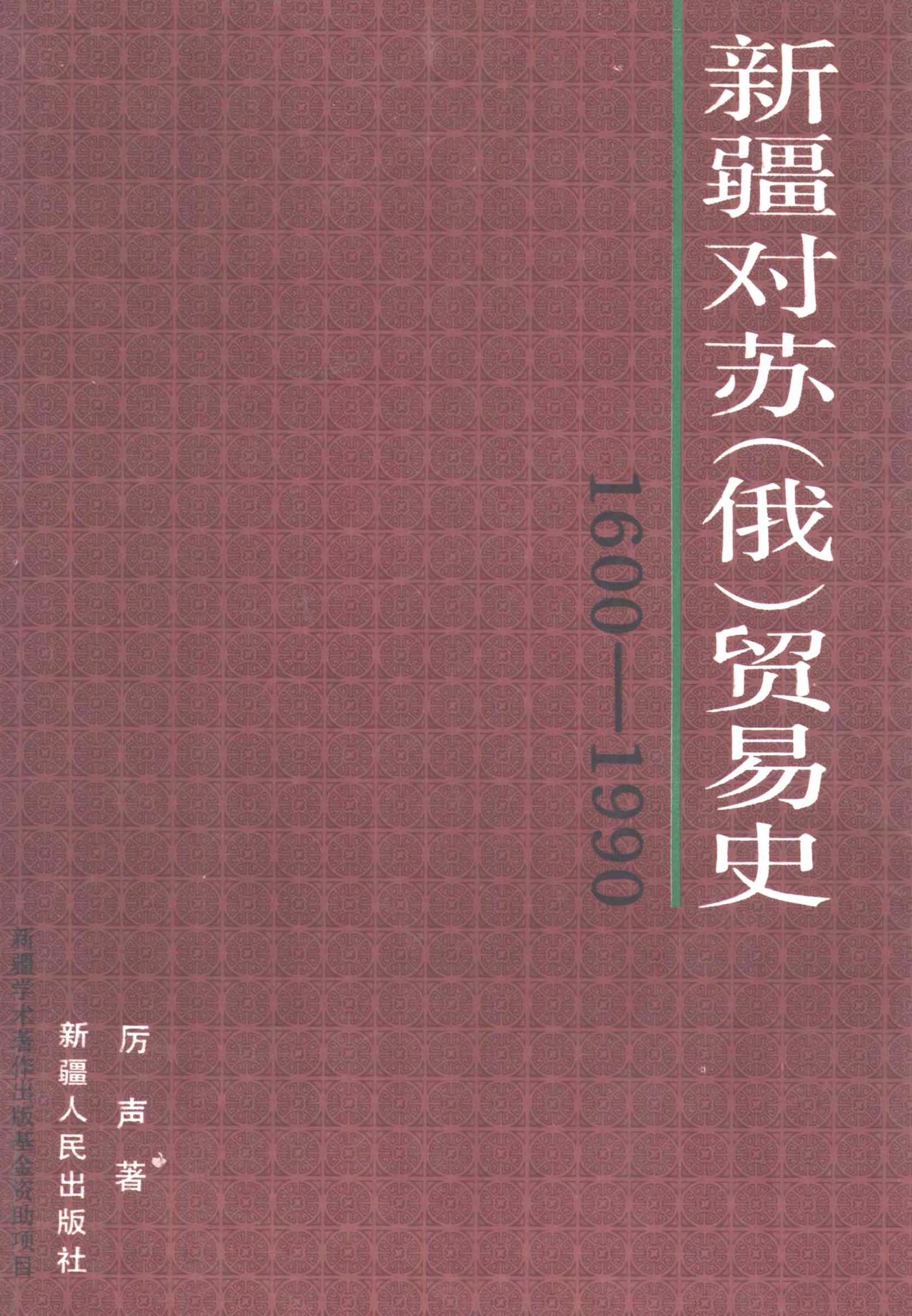
《新疆对苏(俄)贸易史 1660—1990》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出版地:1993
《新疆对苏(俄)贸易史(1600—1990)》一书是一部有关新疆对外经济关系史的力作。全书依清代、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通过丰富、翔实的史料,对17世纪初以来长达近四百年的新疆对苏(俄)贸易历史作了较为系统的综述。既从宏观上叙述了双边贸易的发展和变化,又以具体史实为依据,认真地探讨和论证了不同历史时期新疆对苏(俄)贸易的性质和特点;既是一部有学术价值的新疆历史研究著述,又在当今新疆对前苏联各国贸易中有重要参考意义,同时也填补了国内外对新疆与苏(俄)贸易缺乏系统研究的空白。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