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清统一新疆后对哈萨克贸易的开辟及俄商在新疆的违约贸易
| 内容出处: | 《新疆对苏(俄)贸易史 1660—1990》 图书 |
| 唯一号: | 320020020210017866 |
| 颗粒名称: | 二、清统一新疆后对哈萨克贸易的开辟及俄商在新疆的违约贸易 |
| 分类号: | F426;F127;F752 |
| 页数: | 12 |
| 页码: | 30-41 |
| 摘要: | 1757年清平定阿睦尔撤纳叛乱,统一天山以北。1759年复平定南疆大、小和卓之乱,统一天山以南。在统一新疆的过程中,清军为解决军饷,在各驻兵重镇实行了屯田,为新疆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新疆统一后,关内人民纷纷应召携眷出塞,前往各城镇屯田实边。领种土地,报垦升科。清政府又迁南疆维吾尔族人往伊犁开荒屯种,一时各类屯田开辟兴办,新疆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
| 关键词: | 哈萨克 塔尔巴哈台 恰克图 清政府 哈萨克人 |
内容
1757年清平定阿睦尔撤纳叛乱,统一天山以北。1759年复平定南疆大、小和卓之乱,统一天山以南。在统一新疆的过程中,清军为解决军饷,在各驻兵重镇实行了屯田,为新疆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新疆统一后,关内人民纷纷应召携眷出塞,前往各城镇屯田实边。领种土地,报垦升科。清政府又迁南疆维吾尔族人往伊犁开荒屯种,一时各类屯田开辟兴办,新疆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762年10月,清在伊犁惠远城设立了军政合一的地方机构——伊犁将军府,统一治理南北疆各地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伊犁将军府初辖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阿克苏、库车、喀喇沙尔、吐鲁番、哈密、乌鲁木齐、库尔喀喇乌苏、古城、巴里坤15个区划)。伊犁将军的设置标志着新疆社会和经济进入了稳定发展时期。随着生产的发展,经济交流日益繁荣。早在清军统一新疆时,东向关内商业贸易已经恢复。史称大军西征时,内地商人馈粮千里,转谷百万。师行所至,则有随营商人奔走前后,军中牛酒之犒、筐篚之颁、声色百伎之娱乐一切取供于商。无行斋居送之烦,国不耗而饷足,民不劳而军赡。①伊犁将军设置后,伊犁、乌鲁木齐成为关内客商聚集地,1762年底,乌鲁木齐内地贸易人等开设市肆达500余间。②
清统一新疆后,鉴于中俄已在蒙古恰克图及东北额尔古纳河畔祖鲁海图开辟了贸易市场,同时又有俄国官方大型商队定期进北京贸易,清政府决定不再对俄国开放西部通商,并将在伊犁等地的各类俄国人员皆查明送还出境,③俄国与中国西部的贸易关系遂告中断。1762年,俄方撤销了闲置的谢米巴拉金斯克和亚梅什海关。④对俄国贸易的中断,并未影响新疆西向通商的发展,前来贸易的主要是哈萨克人。
18世纪中期,占据中亚草原的哈萨克人分为三部,称为三个“玉兹”。1757年,清军在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中进入中玉兹,阿布赍汗上表臣服了清王朝。表称:臣阿布赍愿率哈萨克全部,归于鸿化,永为中国臣仆,伏惟中国大皇帝睿鉴。谨遣头目7人及随役共11人,。赍捧表文,恭请万安,并敬备马匹进献。⑤同年秋,哈萨克大玉兹部也臣服于清王朝,与新疆为邻的大、中玉兹哈萨克部成为奉清为宗主的藩部。清准哈萨克人在新疆通商,是将其视为归附藩属,与对东向关内客商前来贸易等同看待,并非对外商开埠。惟为便于管理,将对哈萨克贸易纳为官营,同时又给予了免税等多种优惠。
1757年秋,阿布赍汗请于乌陇古地方(今福海县南)通商,以马匹易换货物。清政府以该地道远,商贩不便,约定于次年在额林哈毕尔噶(今乌苏县、玛纳斯县以南)和乌鲁木齐等处贸易。1758年9月,第一支哈萨克商队赶着300匹马至乌鲁木齐易货,乌鲁木齐成为清统一新疆后西向贸易的第一个市场。为了方便哈萨克人通商,1760年在伊犁开放了第二个西向贸易市场;1763年,又向哈萨克人开放了塔尔巴哈台。此后,哈萨克在新疆的贸易主要集中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两地。清政府规定新疆与哈萨克部的贸易主要限于交换马匹,若哈萨克带来驼、牛、羊只亦系军营需用,应一体收买。至疲瘦牲只、一切杂货,虽不应交易,但念携带远来,作减价收留,以示节制。①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羊只也成为主要交换物之一。新疆输出大宗为绸、绢、土布、茶叶、瓷器。史书记载:哈萨克最喜中国之瓷器、茶叶、杂色梭布及金倭缎等,得之宝贵,绸缎绫绢更是爱不释手。②新疆与哈萨克的贸易为地方当局官办,交易货物由清政府筹备,绸缎续绢自关内江南、陕甘等地调入;土布部分自关内调入,部分来向南疆赋税所得;茶叶由陕甘官茶局发运;瓷器则多收购于关内客商。与哈萨克所易换的各类畜只均归入清官马厂放养滋生,马匹供军用及屯田生产役用,羊只供应驻防军及当地户民食用。③1761年伊犁将军阿桂奏称:内地一牛值哈萨克四匹马价,一驴值哈萨克二匹马价,请停办关内购置牛、驴,在新疆推广马匹为主要役畜。④新疆西向贸易的开辟,又为清政府节省了大笔从陕甘、喀尔喀蒙古调解马匹和羊只供应军需的费用。自1762年起,廉价的哈萨克马匹开始东向调往内地肃州、安西一带补充军用。新疆与哈萨克贸易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日益扩大。
哈萨克西部及北部与俄国相接壤,清统一新疆以前,俄国已经在这些地区开辟了通商贸易,为哥萨克殖民军购置军马。1734年俄国政府派出以基芮洛夫为首的使团前往哈萨克部,主要任务之一是要求与哈萨克部建立商队贸易关系。1735年,俄国在昔日与哈萨克交易地奥尔河口建立了奥伦堡城,这里很快成为俄国同哈萨克人通商贸易的主要集市。按照游牧民族交易的特点,贸易最活跃的时期是从6月中旬到11月初,在这牲畜最肥壮的季节,奥伦堡市场上每天前来贸易的哈萨克人等达几百人至上千人。①1758年新疆与哈萨克西向贸易开通后,哈萨克商人利用地处中国西部与俄国之间的地理条件,很快成为西部中俄贸易的中间人。他们往来于新疆与奥伦堡及俄国西西伯利亚诸城,专门从事中介转手贸易。将新疆输出的绸绢、布匹、茶叶等运往俄国集市销售,或与哈萨克小玉兹人民交易,回程带来的是俄国“布勒噶尔哦噔绸”及杂货等。清王朝在中亚的藩属布鲁特部(今柯尔克孜族人)商人及中亚浩罕等国商人与哈萨克商人一起从事着俄国与中国西部之间的中介贸易,他们主要是向俄国贩运茶叶及大黄。
对于哈萨克人、柯尔克孜人等中亚商人在新疆与俄国之间的中介往来贸易及长途贩运,清政府并不禁阻,“即与俄罗斯往来,亦所不校”。②1764年至1768年清关闭恰克图集市期间,经中介贸易流入新疆的俄国货物增多。清廷谕令:“现我于恰克图地方已与俄方停止贸易,哈萨克人等由俄方交换所得之货物,我方尚可买取。倘俄罗斯人携带货物与我方贸易,无论于何地均不可也”。③后清廷顾虑流入的俄国货物影响恰克图闭关,对哈萨克人携带俄货贸易晓谕禁止。1768年8月谕称:
“嗣后哈萨克人等倘携带马畜前来贸易,除照例贸易外,倘有携带俄方货物前来贸易者,即便价廉,且商货亦少于前次,亦不准贸易。惟因不准交换此等货物一事,尚未晓谕哈萨克人等,倘于此间伊等不知此来而有少许携带俄方货物者,则可照旧准其贸易,然尚应晓谕哈萨克等;嗣后仅准携带马牲前来,不准携带俄方货物,此次尔等既已带来,即如此办理,我等晓谕后,倘仍携带俄方货物前来贸易,则我等既断不允准,并责令尔等带回”。①
禁令尚未实施,恰克图贸易恢复,遂通融驰禁。谕令:“现已照旧与俄罗斯通商,尔等不必如此过甚严禁。”②复又谕称:“既然(恰克图)现已开商,理应听其自便”。③
18世纪末,新疆社会经济处于稳定繁荣时期。农业屯田取得显著成果,1782年,仅伊犁各仓内储粮即达50多万石,因存粮过多,不得不暂时将兵屯数量减少五分之二。社会经济的发展促使更多的关内人民举家迁入新疆,边疆人口增长,城镇商业贸易进一步繁荣。时乌鲁木齐为“四达之区,字号店铺鳞次栉比,市衢宽广,人民辐辏。茶寮酒肆、优伶歌童、工艺技巧之人无一不备,繁华富庶,甲于关外。”④伊犁城内“商民阛阓,民乐田畴。轮蹄懋迁,货殖平准。村落毗接,鸡犬相闻。昔年荒服之区,今悉无殊内地矣。”⑤社会经济的发展、城镇商业的繁荣为新疆西向贸易的进一步扩大奠定了基础。
俄国国内经济在18世纪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8世纪上半,彼得大帝在俄国实行了政治、经济改革,在改革俄国工业,财政、商业贸易的基础上鼓励和支持私人资本和私人工商业的发展,彼得大帝时期(1689年一1725年),俄国新开办了约178家大型工业企业。经济改革很快收到效果,18世纪中期,俄国国内生铁产量已居于世界前列,并大量输往英国。至18世纪末,俄国的工业企业比彼得大帝时期增长了2倍,大工业机器生产的基础已经形成,一些工业部门(如纺织业、制糖业)已彻底摆脱了手工工场生产,铁路运输开始兴办,城镇经济繁荣。城市居民在1796年达到130.1万(1724年为32.8万)。随着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俄国国内外市场已基本连成一体,对国外市场的需求大大增加了。彼得大帝实行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振兴俄国,把俄国置于与欧洲大国等同的地位。因此,当18世纪下半叶改革取得成效时,俄国发动了一系列的对外扩张战争。1768年至1774年和1787年至1791年发动了两次对土耳其的战争;1788年至1790年对瑞典的战争;1763年、1793年、1795年三次瓜分波兰的战争等等。扩张战争使俄国军队的人数在叶卡捷林娜二世统治末期(1796年叶卡捷林娜去世)达到50万人,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用于军费开支,扩大财源成为俄国经济的紧迫需要。
1729年开始的中俄恰克图贸易,在18世纪后半时无论是在俄国国外市场需求上,还是在俄国财政收入上都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时期恰克图对华贸易占俄国常年对外贸易的7%—9%,占俄国在亚洲贸易的67.6%。(1807年上升到70%),年贸易额在百万卢布以上,1775年俄国对华贸易关税收入占俄国关税总收入的38.5%。至18世纪末,俄国在恰克图的对华贸易和关税收入又有增长,见下表:
俄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拮据的状况需要进一步扩大获利丰厚的对华贸易,在发展恰克图贸易的同时,力图开辟中国西部新疆市场。
18世纪后半叶,中亚哈萨克部在俄国的兼并扩张下日益衰落。1781年,中玉兹阿布赍汗去世,由俄国扶持的继任者瓦里汗采取了亲俄政策,不久即投向俄国,引起内部争权夺利,政局混乱;大玉兹受到来自中亚乌兹别克人的进攻;臣服于俄国的小玉兹与俄关系也十分紧张,双方相互劫掠人口、牲畜,并多次发生冲突战争。18世纪末,俄国完成了沿锡尔河和额尔齐斯河的两条殖民堡垒线,形成对哈萨克部的三面包围,兼并之势已成。整个哈萨克部开始走向衰亡,哈萨克部与新疆的贸易锐减。他们已无力承当俄国对中国西部贸易的中介人,不断向哈萨克腹地推进的俄国殖民城镇却具备了与新疆直接贸易的条件。一些俄国商人从这里出发,在哈萨克王公处索取了通商证明或信件,以哈萨克商人的名义进入伊犁,塔尔巴哈台。尽管运入新疆市场上的商品是俄国制造的,但以哈萨克商人的名义进行贸易,可以在表面上维护清政府禁止在新疆开辟中俄通商的政策。另一些俄商干脆以走私方式潜入伊犁,塔城附近进行交易,这些冒名或走私贸易,成为清统一新疆后西部中俄直接通商的先声。
18世纪后半。清政府加强了对哈萨克贸易的管理。1768年,规定哈萨克商人至伊犁、塔尔巴哈台贸易,“只准贩马,不准携带俄罗斯物件,如违,从重治罪。”①俄商前来新疆贸易更在禁止之列。因此,在18世纪后半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俄国与新疆之间的贸易往来只是偶然性的,贸易额和贸易品种都很有限。俄国私商对这一地区的通商没有长远打算,甚至对坚持长期贸易没有信心。他们运送的货物中途没有条约保证,经常遭到游牧民族的抢劫,致使他们失去原先指望过的盈利,有时甚至使他们完全破产。按照俄国人的说法:“只有那些坚强果敢、勇于进取的人,才敢冒险把自已的劳动和资本投入这一可能完全亏本的生意中去”②1785年至1792年,清政府关闭了恰克图通商口岸,俄商在新疆的违禁贸易明显增长。清诏令称:“自恰克图停止贸易以来,因大黄为俄罗期必需之物,屡经严禁,乃商人等冀图厚利,知新疆伊犁、喀什噶尔等处与哈萨克、布鲁特、安集延(指中亚浩罕地区)较近,此等之人常在俄罗斯地方贸易往来。将大黄带往新疆,转售与俄罗斯,不惟可得重利,且将俄罗斯之布勒噶尔哦噔绸等物换来,又卖与伊犁、喀什噶尔等处。所关紧要,已降旨禁止。……果有贪利违禁者,一经发觉,从重治罪,以示惩儆。”③1790年,清政府再次通令新疆各地:“俄罗斯所产物件,禁止不准入卡,大黄等物,不准出境”。①当年查获新疆商民张子敬等一次走私俄国灰鼠、水獭、海龙、香龟、貂等细皮21200余张。②可见俄商在新疆的违禁贸易已初具规模,甚至在新疆腹地乌鲁木齐有“万昌号”等数家经营俄商走私货物的铺面。这些违禁贸易为18世纪后半俄国在中亚哈萨克草原的殖民扩张提供了各类必要的物资,俄国地方当局对此采取了支持和任其发展的策略,这使走私俄商有持无恐,违禁贸易禁而不止。到18世纪末,往来于新疆的各类俄商已相当普遍。
18世纪后半俄商往来于新疆的路线,仍然是沿额尔齐斯河岸这条厄鲁特时期通商的旧道。1763年,俄国在向额尔齐斯河的扩张中,于河右岸、铿格尔图喇东南建立了布赫塔尔明斯克寨堡(今孜里亚诺夫斯克),这里成为俄国的殖民前哨,俄商多从此地沿额尔齐斯河进入新疆。布赫塔尔明斯克距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分别为784公里和478公里(731俄里和446俄里),有道路直通伊、塔两地,俄商将此地作为对新疆开展贸易的货物集散地。1797年,俄国政府单方面颁布了经布赫塔尔明斯克前往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两地贸易的《通商条例》,次年,在这里设立了通商关卡,管理前往新疆的俄国私商。1803年,又设立了海关,征收俄商出口货物税。此时,布赫塔尔明斯克已成为俄国对新疆开展违禁贸易的中心。
考察18世纪后半俄国对新疆的违约贸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中俄两国政府对这一时期新疆双边贸易的态度截然相反。清统一新疆后,采取了各种措施尽快恢复和发展边疆社会经济。此时,新疆经济发展类型相对比较单一,主要集中于农业屯垦经济、官营牧场及土布、毛织业等有限的手工业生产。凡生产及日常生活所需,大都仰靠关内贸易供应和西向与藩属哈萨克部的贸易来补充。从新疆当地经济形势讲,并不需要任何国外市场。清政府对新疆的一系列政策主要是从政治角度出发,建设一个巩固和安定的边疆。鉴于已经对俄国开放了恰克图市场和北京的商队贸易,在18世纪后半,清政府一直禁止新疆与俄国的通商。
由于国内经济、财政等方面的原因及在中亚哈萨克草原殖民扩张的需要,俄国不顾清政府的禁令,在18世纪后半一直放任和支持俄商对新疆的走私贸易,形成这一时期俄国与新疆贸易的不正常局面,其性质由前期对厄鲁特蒙古的自发互惠贸易变为违约走私贸易。
2、接待俄商贸易场所的性质发生了变化。17世纪初至18世纪上半叶,厄鲁特(准噶尔)境内虽然没有明确对外商开埠,但接待俄商贸易的一些城镇市场,如前期的亚梅什湖及后来的伊犁、乌鲁木齐等地已具有对俄商开放的外贸商埠性质。清统一新疆后,关闭了新疆的对外商贸易,只在境内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开辟了对归附藩部的交易市场,用以接待藩属哈萨克、柯尔克孜(布鲁特)、浩罕等部的易货贸易。各交易市场货物流通的大致情况是:经新疆西向输出的商品以关内东向输入新疆的商品为大宗,除土布一项新疆可自产部分外,西向输出的绸绢、茶叶、瓷器、大黄等大宗商品皆由关内运入;而西向输入新疆的牲畜,畜产品等,除部分供应沿边需求外,大多流入了关内市场。此时,新疆的各交易市场属于国内商品流通市场,是清王朝内部关内商品与藩属货物的交易场所,已经失去了昔日对外商埠的性质。即使俄商通过哈萨克等的中介贸易,或以各种名目对新疆的走私贸易,也都是以清藩属对内贸易的形式进行的。
3、新疆输出商品结构发生了变化。17世纪初至18世纪上半,厄鲁特(准噶尔)蒙古对国俄贸易中主要输出的商品是牲畜和畜产品。清统一新疆后,游牧于中亚草原的哈萨克人成为中俄双方牲畜和畜产品的供应者,新疆反成为牲畜和畜产品的输入地区。而西向输出货物,主要以绸绢,土布、茶叶、瓷器、大黄等为大宗。西向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一方面是清统一新疆后原天山以北的蒙古游牧经济迅速地向农业屯田经济过渡、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是新疆已处于国内贸易的大流通中,西向贸易所反映出的主要是中原农业经济与哈萨克等藩属游牧经济的交换关系。
4、西向与哈萨克、柯尔克孜(布鲁特)、浩罕等诸藩属的贸易管理严格,官为代办。西向贸易开通后,出于对边疆稳定和控制交易价格的考虑,清政府将哈萨克贸易定为官办。制定了《哈萨克贸易章程》,并分别在伊犁惠远城外和塔尔巴哈台绥靖城外建立了专门用于交易的市场——贸易亭。《哈萨克贸易章程》内容如下:
①固定交易时间。与哈萨克交易定于每年牲畜最肥壮的夏秋之交举行。
②指定商队(人)行走路线。规定哈萨克贸易自沁达兰卡伦或匡俄尔俄鸾卡伦行走。
③入卡稽查。哈萨克贸易人抵固定卡伦后,由卡伦待卫稽查人货之数,先行具报主管部门。
④官兵接护。贸易主管部门派出官兵自卡伦接入,带至城外贸易亭附近搭帐居住,等候安排交易。
⑤官方代理贸易。交易由贸易主管部门安排后,在规定时间由绿营官员或废员内派员扮作商人,与哈萨克人等在贸易亭相交易。货价计值平论。另有官员带兵丁在贸易亭监督。
⑥禁止私人交易。“其贸易之日,昼夜巡查,禁止兵民不得私换,犯者重惩之”。凡商人贸易皆在官方交易完毕后,委托交易官员代为办理。
⑦贸易完毕,由官兵护送返回出境。①
官方与哈萨克交易所用绸绢,大布、茶叶、大黄、瓷器等,或由清政府直接调入,或关内客商运抵后官方收购,储于官库备用。交易所得各类牲畜等交驼马处入官。商人所得自便贩运。因清对哈萨克贸易管理严格,一切官为经理,任何私商不得直接参加交易,故贸易亭又有“官市”之称。凡前来贸易的清各藩属和以各种名义进入新疆的俄国商人,均照《哈萨克贸易章程》管理。俄国商人进入伊犁、塔尔巴哈台后,将货物放置在贸易亭,商人们居住在贸易亭外指定地点等待批准贸易。经官方许可后交易开始,先由清官员带数名随从,与俄国商人选出的代表在贸易亭洽谈买卖,清官员观看货物,秉公制定价格,俄国代表同意后,缴纳3%贸易税,即为交易完毕。清官员将货物运入城内,在需要购买俄国货物的中国商人中分配出售。俄国商人则去官库中提取换得的中国货。商队货物由清军护送出卡。
5、中俄双方对这一时期俄国对新疆的违约走私贸易没有任何统计资料,如果要对此作一个大概的估计,18世纪末,年度交易额约20万卢布左右(1811年俄国经布赫塔尔明斯克向新疆输出了价植约15万卢布的货物,①年交易额超过了30万卢布。)
6、清统一新疆后,随即着手开展西向与哈萨克等诸内附藩属的通商贸易,其中有很强的政治意义,“非利其所有而欲溅值以取之也”。这一贸易关系的建立,一方面繁荣了边疆的经济,更重要的是通过经济交流更牢固地维系了清与诸藩属的相互关系,“俾遐荒咸知天朝柔远之经”;稳定了边疆社会,“俾得懋迁有无,稍资生计”,②各安游牧。所以,新疆西向与哈萨克等诸归附藩属贸易关系的开辟和发展,是清政府在边疆实行的一项重要治边理藩政策,对稳定边疆政局、维护祖国边防和边疆统一起了重要作用。
清统一新疆后,鉴于中俄已在蒙古恰克图及东北额尔古纳河畔祖鲁海图开辟了贸易市场,同时又有俄国官方大型商队定期进北京贸易,清政府决定不再对俄国开放西部通商,并将在伊犁等地的各类俄国人员皆查明送还出境,③俄国与中国西部的贸易关系遂告中断。1762年,俄方撤销了闲置的谢米巴拉金斯克和亚梅什海关。④对俄国贸易的中断,并未影响新疆西向通商的发展,前来贸易的主要是哈萨克人。
18世纪中期,占据中亚草原的哈萨克人分为三部,称为三个“玉兹”。1757年,清军在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中进入中玉兹,阿布赍汗上表臣服了清王朝。表称:臣阿布赍愿率哈萨克全部,归于鸿化,永为中国臣仆,伏惟中国大皇帝睿鉴。谨遣头目7人及随役共11人,。赍捧表文,恭请万安,并敬备马匹进献。⑤同年秋,哈萨克大玉兹部也臣服于清王朝,与新疆为邻的大、中玉兹哈萨克部成为奉清为宗主的藩部。清准哈萨克人在新疆通商,是将其视为归附藩属,与对东向关内客商前来贸易等同看待,并非对外商开埠。惟为便于管理,将对哈萨克贸易纳为官营,同时又给予了免税等多种优惠。
1757年秋,阿布赍汗请于乌陇古地方(今福海县南)通商,以马匹易换货物。清政府以该地道远,商贩不便,约定于次年在额林哈毕尔噶(今乌苏县、玛纳斯县以南)和乌鲁木齐等处贸易。1758年9月,第一支哈萨克商队赶着300匹马至乌鲁木齐易货,乌鲁木齐成为清统一新疆后西向贸易的第一个市场。为了方便哈萨克人通商,1760年在伊犁开放了第二个西向贸易市场;1763年,又向哈萨克人开放了塔尔巴哈台。此后,哈萨克在新疆的贸易主要集中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两地。清政府规定新疆与哈萨克部的贸易主要限于交换马匹,若哈萨克带来驼、牛、羊只亦系军营需用,应一体收买。至疲瘦牲只、一切杂货,虽不应交易,但念携带远来,作减价收留,以示节制。①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羊只也成为主要交换物之一。新疆输出大宗为绸、绢、土布、茶叶、瓷器。史书记载:哈萨克最喜中国之瓷器、茶叶、杂色梭布及金倭缎等,得之宝贵,绸缎绫绢更是爱不释手。②新疆与哈萨克的贸易为地方当局官办,交易货物由清政府筹备,绸缎续绢自关内江南、陕甘等地调入;土布部分自关内调入,部分来向南疆赋税所得;茶叶由陕甘官茶局发运;瓷器则多收购于关内客商。与哈萨克所易换的各类畜只均归入清官马厂放养滋生,马匹供军用及屯田生产役用,羊只供应驻防军及当地户民食用。③1761年伊犁将军阿桂奏称:内地一牛值哈萨克四匹马价,一驴值哈萨克二匹马价,请停办关内购置牛、驴,在新疆推广马匹为主要役畜。④新疆西向贸易的开辟,又为清政府节省了大笔从陕甘、喀尔喀蒙古调解马匹和羊只供应军需的费用。自1762年起,廉价的哈萨克马匹开始东向调往内地肃州、安西一带补充军用。新疆与哈萨克贸易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日益扩大。
哈萨克西部及北部与俄国相接壤,清统一新疆以前,俄国已经在这些地区开辟了通商贸易,为哥萨克殖民军购置军马。1734年俄国政府派出以基芮洛夫为首的使团前往哈萨克部,主要任务之一是要求与哈萨克部建立商队贸易关系。1735年,俄国在昔日与哈萨克交易地奥尔河口建立了奥伦堡城,这里很快成为俄国同哈萨克人通商贸易的主要集市。按照游牧民族交易的特点,贸易最活跃的时期是从6月中旬到11月初,在这牲畜最肥壮的季节,奥伦堡市场上每天前来贸易的哈萨克人等达几百人至上千人。①1758年新疆与哈萨克西向贸易开通后,哈萨克商人利用地处中国西部与俄国之间的地理条件,很快成为西部中俄贸易的中间人。他们往来于新疆与奥伦堡及俄国西西伯利亚诸城,专门从事中介转手贸易。将新疆输出的绸绢、布匹、茶叶等运往俄国集市销售,或与哈萨克小玉兹人民交易,回程带来的是俄国“布勒噶尔哦噔绸”及杂货等。清王朝在中亚的藩属布鲁特部(今柯尔克孜族人)商人及中亚浩罕等国商人与哈萨克商人一起从事着俄国与中国西部之间的中介贸易,他们主要是向俄国贩运茶叶及大黄。
对于哈萨克人、柯尔克孜人等中亚商人在新疆与俄国之间的中介往来贸易及长途贩运,清政府并不禁阻,“即与俄罗斯往来,亦所不校”。②1764年至1768年清关闭恰克图集市期间,经中介贸易流入新疆的俄国货物增多。清廷谕令:“现我于恰克图地方已与俄方停止贸易,哈萨克人等由俄方交换所得之货物,我方尚可买取。倘俄罗斯人携带货物与我方贸易,无论于何地均不可也”。③后清廷顾虑流入的俄国货物影响恰克图闭关,对哈萨克人携带俄货贸易晓谕禁止。1768年8月谕称:
“嗣后哈萨克人等倘携带马畜前来贸易,除照例贸易外,倘有携带俄方货物前来贸易者,即便价廉,且商货亦少于前次,亦不准贸易。惟因不准交换此等货物一事,尚未晓谕哈萨克人等,倘于此间伊等不知此来而有少许携带俄方货物者,则可照旧准其贸易,然尚应晓谕哈萨克等;嗣后仅准携带马牲前来,不准携带俄方货物,此次尔等既已带来,即如此办理,我等晓谕后,倘仍携带俄方货物前来贸易,则我等既断不允准,并责令尔等带回”。①
禁令尚未实施,恰克图贸易恢复,遂通融驰禁。谕令:“现已照旧与俄罗斯通商,尔等不必如此过甚严禁。”②复又谕称:“既然(恰克图)现已开商,理应听其自便”。③
18世纪末,新疆社会经济处于稳定繁荣时期。农业屯田取得显著成果,1782年,仅伊犁各仓内储粮即达50多万石,因存粮过多,不得不暂时将兵屯数量减少五分之二。社会经济的发展促使更多的关内人民举家迁入新疆,边疆人口增长,城镇商业贸易进一步繁荣。时乌鲁木齐为“四达之区,字号店铺鳞次栉比,市衢宽广,人民辐辏。茶寮酒肆、优伶歌童、工艺技巧之人无一不备,繁华富庶,甲于关外。”④伊犁城内“商民阛阓,民乐田畴。轮蹄懋迁,货殖平准。村落毗接,鸡犬相闻。昔年荒服之区,今悉无殊内地矣。”⑤社会经济的发展、城镇商业的繁荣为新疆西向贸易的进一步扩大奠定了基础。
俄国国内经济在18世纪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8世纪上半,彼得大帝在俄国实行了政治、经济改革,在改革俄国工业,财政、商业贸易的基础上鼓励和支持私人资本和私人工商业的发展,彼得大帝时期(1689年一1725年),俄国新开办了约178家大型工业企业。经济改革很快收到效果,18世纪中期,俄国国内生铁产量已居于世界前列,并大量输往英国。至18世纪末,俄国的工业企业比彼得大帝时期增长了2倍,大工业机器生产的基础已经形成,一些工业部门(如纺织业、制糖业)已彻底摆脱了手工工场生产,铁路运输开始兴办,城镇经济繁荣。城市居民在1796年达到130.1万(1724年为32.8万)。随着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俄国国内外市场已基本连成一体,对国外市场的需求大大增加了。彼得大帝实行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振兴俄国,把俄国置于与欧洲大国等同的地位。因此,当18世纪下半叶改革取得成效时,俄国发动了一系列的对外扩张战争。1768年至1774年和1787年至1791年发动了两次对土耳其的战争;1788年至1790年对瑞典的战争;1763年、1793年、1795年三次瓜分波兰的战争等等。扩张战争使俄国军队的人数在叶卡捷林娜二世统治末期(1796年叶卡捷林娜去世)达到50万人,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用于军费开支,扩大财源成为俄国经济的紧迫需要。
1729年开始的中俄恰克图贸易,在18世纪后半时无论是在俄国国外市场需求上,还是在俄国财政收入上都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时期恰克图对华贸易占俄国常年对外贸易的7%—9%,占俄国在亚洲贸易的67.6%。(1807年上升到70%),年贸易额在百万卢布以上,1775年俄国对华贸易关税收入占俄国关税总收入的38.5%。至18世纪末,俄国在恰克图的对华贸易和关税收入又有增长,见下表:
俄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拮据的状况需要进一步扩大获利丰厚的对华贸易,在发展恰克图贸易的同时,力图开辟中国西部新疆市场。
18世纪后半叶,中亚哈萨克部在俄国的兼并扩张下日益衰落。1781年,中玉兹阿布赍汗去世,由俄国扶持的继任者瓦里汗采取了亲俄政策,不久即投向俄国,引起内部争权夺利,政局混乱;大玉兹受到来自中亚乌兹别克人的进攻;臣服于俄国的小玉兹与俄关系也十分紧张,双方相互劫掠人口、牲畜,并多次发生冲突战争。18世纪末,俄国完成了沿锡尔河和额尔齐斯河的两条殖民堡垒线,形成对哈萨克部的三面包围,兼并之势已成。整个哈萨克部开始走向衰亡,哈萨克部与新疆的贸易锐减。他们已无力承当俄国对中国西部贸易的中介人,不断向哈萨克腹地推进的俄国殖民城镇却具备了与新疆直接贸易的条件。一些俄国商人从这里出发,在哈萨克王公处索取了通商证明或信件,以哈萨克商人的名义进入伊犁,塔尔巴哈台。尽管运入新疆市场上的商品是俄国制造的,但以哈萨克商人的名义进行贸易,可以在表面上维护清政府禁止在新疆开辟中俄通商的政策。另一些俄商干脆以走私方式潜入伊犁,塔城附近进行交易,这些冒名或走私贸易,成为清统一新疆后西部中俄直接通商的先声。
18世纪后半。清政府加强了对哈萨克贸易的管理。1768年,规定哈萨克商人至伊犁、塔尔巴哈台贸易,“只准贩马,不准携带俄罗斯物件,如违,从重治罪。”①俄商前来新疆贸易更在禁止之列。因此,在18世纪后半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俄国与新疆之间的贸易往来只是偶然性的,贸易额和贸易品种都很有限。俄国私商对这一地区的通商没有长远打算,甚至对坚持长期贸易没有信心。他们运送的货物中途没有条约保证,经常遭到游牧民族的抢劫,致使他们失去原先指望过的盈利,有时甚至使他们完全破产。按照俄国人的说法:“只有那些坚强果敢、勇于进取的人,才敢冒险把自已的劳动和资本投入这一可能完全亏本的生意中去”②1785年至1792年,清政府关闭了恰克图通商口岸,俄商在新疆的违禁贸易明显增长。清诏令称:“自恰克图停止贸易以来,因大黄为俄罗期必需之物,屡经严禁,乃商人等冀图厚利,知新疆伊犁、喀什噶尔等处与哈萨克、布鲁特、安集延(指中亚浩罕地区)较近,此等之人常在俄罗斯地方贸易往来。将大黄带往新疆,转售与俄罗斯,不惟可得重利,且将俄罗斯之布勒噶尔哦噔绸等物换来,又卖与伊犁、喀什噶尔等处。所关紧要,已降旨禁止。……果有贪利违禁者,一经发觉,从重治罪,以示惩儆。”③1790年,清政府再次通令新疆各地:“俄罗斯所产物件,禁止不准入卡,大黄等物,不准出境”。①当年查获新疆商民张子敬等一次走私俄国灰鼠、水獭、海龙、香龟、貂等细皮21200余张。②可见俄商在新疆的违禁贸易已初具规模,甚至在新疆腹地乌鲁木齐有“万昌号”等数家经营俄商走私货物的铺面。这些违禁贸易为18世纪后半俄国在中亚哈萨克草原的殖民扩张提供了各类必要的物资,俄国地方当局对此采取了支持和任其发展的策略,这使走私俄商有持无恐,违禁贸易禁而不止。到18世纪末,往来于新疆的各类俄商已相当普遍。
18世纪后半俄商往来于新疆的路线,仍然是沿额尔齐斯河岸这条厄鲁特时期通商的旧道。1763年,俄国在向额尔齐斯河的扩张中,于河右岸、铿格尔图喇东南建立了布赫塔尔明斯克寨堡(今孜里亚诺夫斯克),这里成为俄国的殖民前哨,俄商多从此地沿额尔齐斯河进入新疆。布赫塔尔明斯克距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分别为784公里和478公里(731俄里和446俄里),有道路直通伊、塔两地,俄商将此地作为对新疆开展贸易的货物集散地。1797年,俄国政府单方面颁布了经布赫塔尔明斯克前往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两地贸易的《通商条例》,次年,在这里设立了通商关卡,管理前往新疆的俄国私商。1803年,又设立了海关,征收俄商出口货物税。此时,布赫塔尔明斯克已成为俄国对新疆开展违禁贸易的中心。
考察18世纪后半俄国对新疆的违约贸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中俄两国政府对这一时期新疆双边贸易的态度截然相反。清统一新疆后,采取了各种措施尽快恢复和发展边疆社会经济。此时,新疆经济发展类型相对比较单一,主要集中于农业屯垦经济、官营牧场及土布、毛织业等有限的手工业生产。凡生产及日常生活所需,大都仰靠关内贸易供应和西向与藩属哈萨克部的贸易来补充。从新疆当地经济形势讲,并不需要任何国外市场。清政府对新疆的一系列政策主要是从政治角度出发,建设一个巩固和安定的边疆。鉴于已经对俄国开放了恰克图市场和北京的商队贸易,在18世纪后半,清政府一直禁止新疆与俄国的通商。
由于国内经济、财政等方面的原因及在中亚哈萨克草原殖民扩张的需要,俄国不顾清政府的禁令,在18世纪后半一直放任和支持俄商对新疆的走私贸易,形成这一时期俄国与新疆贸易的不正常局面,其性质由前期对厄鲁特蒙古的自发互惠贸易变为违约走私贸易。
2、接待俄商贸易场所的性质发生了变化。17世纪初至18世纪上半叶,厄鲁特(准噶尔)境内虽然没有明确对外商开埠,但接待俄商贸易的一些城镇市场,如前期的亚梅什湖及后来的伊犁、乌鲁木齐等地已具有对俄商开放的外贸商埠性质。清统一新疆后,关闭了新疆的对外商贸易,只在境内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开辟了对归附藩部的交易市场,用以接待藩属哈萨克、柯尔克孜(布鲁特)、浩罕等部的易货贸易。各交易市场货物流通的大致情况是:经新疆西向输出的商品以关内东向输入新疆的商品为大宗,除土布一项新疆可自产部分外,西向输出的绸绢、茶叶、瓷器、大黄等大宗商品皆由关内运入;而西向输入新疆的牲畜,畜产品等,除部分供应沿边需求外,大多流入了关内市场。此时,新疆的各交易市场属于国内商品流通市场,是清王朝内部关内商品与藩属货物的交易场所,已经失去了昔日对外商埠的性质。即使俄商通过哈萨克等的中介贸易,或以各种名目对新疆的走私贸易,也都是以清藩属对内贸易的形式进行的。
3、新疆输出商品结构发生了变化。17世纪初至18世纪上半,厄鲁特(准噶尔)蒙古对国俄贸易中主要输出的商品是牲畜和畜产品。清统一新疆后,游牧于中亚草原的哈萨克人成为中俄双方牲畜和畜产品的供应者,新疆反成为牲畜和畜产品的输入地区。而西向输出货物,主要以绸绢,土布、茶叶、瓷器、大黄等为大宗。西向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一方面是清统一新疆后原天山以北的蒙古游牧经济迅速地向农业屯田经济过渡、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是新疆已处于国内贸易的大流通中,西向贸易所反映出的主要是中原农业经济与哈萨克等藩属游牧经济的交换关系。
4、西向与哈萨克、柯尔克孜(布鲁特)、浩罕等诸藩属的贸易管理严格,官为代办。西向贸易开通后,出于对边疆稳定和控制交易价格的考虑,清政府将哈萨克贸易定为官办。制定了《哈萨克贸易章程》,并分别在伊犁惠远城外和塔尔巴哈台绥靖城外建立了专门用于交易的市场——贸易亭。《哈萨克贸易章程》内容如下:
①固定交易时间。与哈萨克交易定于每年牲畜最肥壮的夏秋之交举行。
②指定商队(人)行走路线。规定哈萨克贸易自沁达兰卡伦或匡俄尔俄鸾卡伦行走。
③入卡稽查。哈萨克贸易人抵固定卡伦后,由卡伦待卫稽查人货之数,先行具报主管部门。
④官兵接护。贸易主管部门派出官兵自卡伦接入,带至城外贸易亭附近搭帐居住,等候安排交易。
⑤官方代理贸易。交易由贸易主管部门安排后,在规定时间由绿营官员或废员内派员扮作商人,与哈萨克人等在贸易亭相交易。货价计值平论。另有官员带兵丁在贸易亭监督。
⑥禁止私人交易。“其贸易之日,昼夜巡查,禁止兵民不得私换,犯者重惩之”。凡商人贸易皆在官方交易完毕后,委托交易官员代为办理。
⑦贸易完毕,由官兵护送返回出境。①
官方与哈萨克交易所用绸绢,大布、茶叶、大黄、瓷器等,或由清政府直接调入,或关内客商运抵后官方收购,储于官库备用。交易所得各类牲畜等交驼马处入官。商人所得自便贩运。因清对哈萨克贸易管理严格,一切官为经理,任何私商不得直接参加交易,故贸易亭又有“官市”之称。凡前来贸易的清各藩属和以各种名义进入新疆的俄国商人,均照《哈萨克贸易章程》管理。俄国商人进入伊犁、塔尔巴哈台后,将货物放置在贸易亭,商人们居住在贸易亭外指定地点等待批准贸易。经官方许可后交易开始,先由清官员带数名随从,与俄国商人选出的代表在贸易亭洽谈买卖,清官员观看货物,秉公制定价格,俄国代表同意后,缴纳3%贸易税,即为交易完毕。清官员将货物运入城内,在需要购买俄国货物的中国商人中分配出售。俄国商人则去官库中提取换得的中国货。商队货物由清军护送出卡。
5、中俄双方对这一时期俄国对新疆的违约走私贸易没有任何统计资料,如果要对此作一个大概的估计,18世纪末,年度交易额约20万卢布左右(1811年俄国经布赫塔尔明斯克向新疆输出了价植约15万卢布的货物,①年交易额超过了30万卢布。)
6、清统一新疆后,随即着手开展西向与哈萨克等诸内附藩属的通商贸易,其中有很强的政治意义,“非利其所有而欲溅值以取之也”。这一贸易关系的建立,一方面繁荣了边疆的经济,更重要的是通过经济交流更牢固地维系了清与诸藩属的相互关系,“俾遐荒咸知天朝柔远之经”;稳定了边疆社会,“俾得懋迁有无,稍资生计”,②各安游牧。所以,新疆西向与哈萨克等诸归附藩属贸易关系的开辟和发展,是清政府在边疆实行的一项重要治边理藩政策,对稳定边疆政局、维护祖国边防和边疆统一起了重要作用。
附注
《新疆图志》卷二十九,实业二,第14页。;《清高宗实录》卷674,第17页。; 何秋涛编撰:《朔方备乘》卷48。;(苏)H·安东诺夫:《论1851年签订俄中伊犁条约的经过》; 傅恒等编:《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4。;《清高宗实录》卷550,第11页。;(清)椿园:《西域闻见录》卷3《外藩列传·哈萨克》。; 例载:满州、索伦等兵丁月支羊3只,绿旗兵丁月支羊2只。伊犁将军设置后,仅伊犁满营、索伦营等额定兵丁即9169人,月支羊27507只。;《清高宗实录》卷663,第14—15页。; А·Д·列夫申:《吉尔吉斯—哈萨克帐及各草原的叙述》巴黎1840年版,第423页。;《清高宗实录》卷580,第20页。; 乾隆三十三年八月十三日《伊犁将军伊勒图为钦遵上谕事折》。; 乾隆三十三年七月《满文月折档》。; 乾隆三十三年八月二十日朱批。; 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八日朱批。; (清)椿园:《西域记》卷一,第6页。; (清)格琫额:《伊江汇览》第37页。;《清高宗实录》卷814,第2页。;《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第177页。;《清高宗实录》卷1321,第13页。;《清高宗实录》卷1361,第36页。; 同上,卷1366,第8—9页。;《伊江汇览》第100—101页。;(苏)斯拉德科夫斯基:《俄中贸易和经济关系史》1974年莫斯科版,第211页。; 《清高宗实录》卷550,第13页。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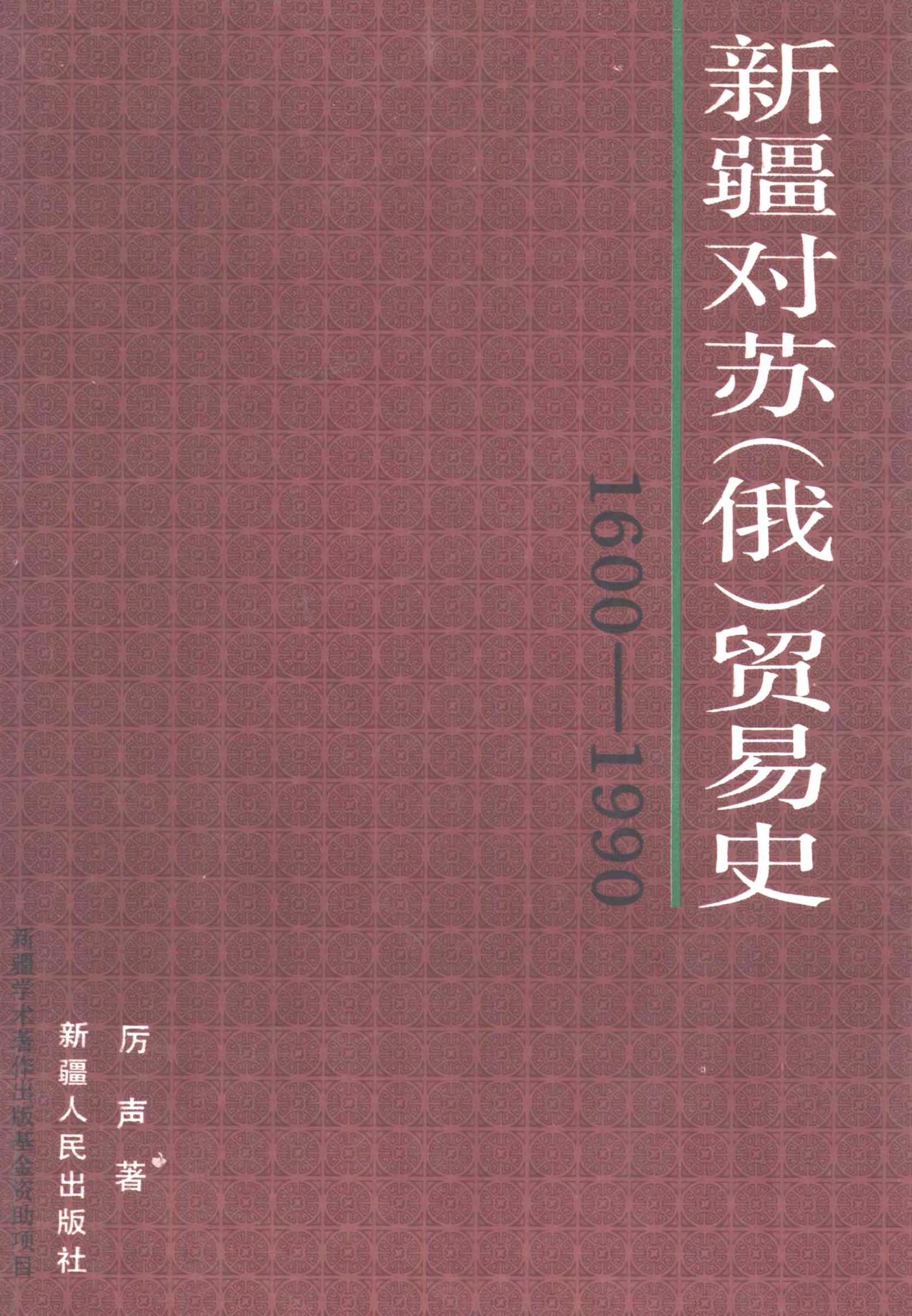
《新疆对苏(俄)贸易史 1660—1990》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出版地:1993
《新疆对苏(俄)贸易史(1600—1990)》一书是一部有关新疆对外经济关系史的力作。全书依清代、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通过丰富、翔实的史料,对17世纪初以来长达近四百年的新疆对苏(俄)贸易历史作了较为系统的综述。既从宏观上叙述了双边贸易的发展和变化,又以具体史实为依据,认真地探讨和论证了不同历史时期新疆对苏(俄)贸易的性质和特点;既是一部有学术价值的新疆历史研究著述,又在当今新疆对前苏联各国贸易中有重要参考意义,同时也填补了国内外对新疆与苏(俄)贸易缺乏系统研究的空白。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