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西部厄鲁特(准噶尔)蒙古与俄国的贸易关系
| 内容出处: | 《新疆对苏(俄)贸易史 1660—1990》 图书 |
| 唯一号: | 320020020210017865 |
| 颗粒名称: | 一、中国西部厄鲁特(准噶尔)蒙古与俄国的贸易关系 |
| 分类号: | F426;F752;F127 |
| 页数: | 13 |
| 页码: | 17-29 |
| 摘要: | 厄鲁特蒙古是中国蒙古族中的一支,明代称瓦喇,游牧于蒙古大漠西部。16世纪末西迁额尔齐斯河和鄂毕河中上游、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及准噶尔盆地一带。其内部分为准噶尔,杜尔伯特、和硕特、土尔扈特四大部,统称为厄鲁特蒙古(又译为额鲁特或卫拉特,中亚突厥语系各族称之为喀尔木克人或卡尔梅克人)。在俄国人到来之前,厄鲁特蒙古人即保持着原有与中国内地的贸易,同时与锡尔河沿岸中亚诸城之间建立了通商关系。 |
| 关键词: | 厄鲁特 厄鲁特蒙古 托木斯克 准噶尔 托博尔斯克 |
内容
厄鲁特蒙古是中国蒙古族中的一支,明代称瓦喇,游牧于蒙古大漠西部。16世纪末西迁额尔齐斯河和鄂毕河中上游、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及准噶尔盆地一带。其内部分为准噶尔,杜尔伯特、和硕特、土尔扈特四大部,统称为厄鲁特蒙古(又译为额鲁特或卫拉特,中亚突厥语系各族称之为喀尔木克人或卡尔梅克人)。在俄国人到来之前,厄鲁特蒙古人即保持着原有与中国内地的贸易,同时与锡尔河沿岸中亚诸城之间建立了通商关系。与中国内地的贸易走陆路,多经明朝西北重镇肃州(今甘肃酒泉)往来贸易;与中亚诸城之间的贸易主要由“不花剌”(即布哈拉)商人承担①,往来货物多经水路贩运。先由额尔齐斯河上溯至托博尔河口,再沿托博尔河上行往南至中亚诸城。在托博尔河与额尔齐斯河汇流处,形成长途贩运或从事航运贸易的“不花刺”商人聚居地。
俄国向东方进入亚洲的殖民活动始于16世纪后半。1581年,以叶尔马克为首的一群哥萨克人越过乌拉尔山,开始了对西伯利亚的征服。1586年,在一个小镇的废墟上建立了秋明城堡,这是俄国人在乌拉尔山以东建立的第一个殖民据点。1587年,在托博尔河与额尔齐斯河的汇流处构筑了托博尔斯克城堡。随后俄国人沿额尔齐斯河上溯,于1594年在该河中游建立了塔拉城堡。1604年,俄国人在鄂毕河上游支流托木河畔修筑了托木斯克城堡,在这里他们与游牧于鄂毕河中上游的厄鲁特蒙古人发生了接触。此后,俄国人与厄鲁特蒙古人的活动主要集中在额尔齐斯河流域,双方的关系不断发展。这种关系是多方面的:在政治上,侵略与反侵略、殖民与反殖民、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与正常的往来并存;在经济上,一方面存在着掠夺与反掠夺的斗争,同时厄鲁特牧民与俄国人民在西西伯利亚各定居殖民城堡之间的经济交往相应发展起来。厄鲁特蒙古王公也像当年要求同中国内地明王朝开市一样,希望在俄国城镇出售牲畜和畜产品。他们开始赶着成群的马匹前往托博尔斯克或托木斯克,用以交换俄国人的商品。“如像软革、铜锅、黄铜环、铁和水獭皮(他们认为水獭皮比其它皮好)”。①由于地理因素及厄鲁特蒙古周边形势的变化,东向与中国内地的贸易呈现出时断时续的不景气状况,对俄国贸易的重要性却日益明显。此外,当俄国人占有托博尔河口这个往日中亚“不花刺”商人的聚集地后,相当一部分厄鲁特人西向与中亚诸城的贸易实际转入了俄国商人手中。
塔拉城堡是俄国人在额尔齐斯河中游建立的前沿据点,1597年,这里已成为俄国与厄鲁特蒙古部之间的贸易中心。1607年,当厄鲁特人的使团前往塔拉城时,一支商队随使团进入塔拉城,商队“赶着550匹马来出售,换取衣服、金钱和书写纸。塔拉当局免去了这笔交易的税收”。①此后,双边贸易相互免税成为一条不成文的通例。不久,托博尔斯克和托木斯克也成为厄鲁特商队时常光顾的地区。
俄国商人则沿额尔齐斯河深入厄鲁特领地进行贸易,易货集中在亚梅什湖(位于额尔齐斯河中游左岸,中方称之为达布逊淖尔。蒙语,意为盐池。)周围地区。这里长期以来就是厄鲁特蒙古牧民的贸易中心,每年都定期举行历时20多天的大规模民间集市贸易,来自周围各部的蒙古牧民、中亚“不花剌”商人、天山以南的维吾尔商人等会聚一处,相互通商交易。后来的俄国商人加入了亚梅什湖集市,与当地居民易货。有时俄商还深入周围蒙古族部民中去兜售商品,牧民则向他们出售牲畜及畜产品;王公们在出售牲畜的同时,还以从中国内地贩运来的大黄、烟草、麝香等与俄商交易。厄鲁特蒙古王公有时也遨请俄国官方派商队前来贸易,如1609年,王公们向俄方建议,请塔拉将军本人带领俄国商人到厄鲁特所属的额尔齐斯河上游地区来通商贸易。
俄国档案文献是研究17世纪俄国与中国西部厄鲁特蒙古相互关系的主要资料来源,M·N·戈利曼与C·N·斯列萨尔丘克在《17世纪30—50年代俄国与蒙古相互关系的俄国档案资料》(载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简讯》1965年第76期)中指出:在这一时期俄文档案文献中,内容最多的是记载厄鲁特人与俄国的贸易情况。由于厄鲁特人每年春、夏两季三次前往俄国西伯利亚贸易,俄方公文和报告中有关厄鲁特商人前来经商的指示很多。其中有不少关于马匹的价格和厄鲁特商人在西伯利亚城市以马匹换回商品的情况。1618年3月,厄鲁特蒙古的代表对俄方谈到双边贸易时说,在以往13年中,“他们曾不断来到俄国城市,赶着牛、马和各种牲畜各两三百头,几乎遍城皆是。”俄国政府则表示欢迎厄鲁特人“赶着马群和各种牲畜、携带卡尔梅克汗国(批厄鲁特蒙古部)出产的商品来西伯利亚各城市,来托博尔斯克和我们的其它城布,吩咐其属民不必有任何顾虑。……对你们的商人做到关怀备至,使之丝毫不受任何人的欺凌。”①随着贸易的扩大,俄属西西伯利亚各城堡都辟出专门地点接待厄鲁特商人。双方政治交往中互赠礼物或回赠的赏赐往往是相互贸易的另一种形式。礼物与赏赐的项目与商人间贸易品种大致相同,且数额较大,价值一般对等。这种贸易方式主要是满足了厄鲁特封建王公的需要,在赏赐或回赠礼物前双方要协商或讨价还价,甚至可以指名要求回赠某物或拒绝接受礼物中某些不需要的项目。
17世纪上半叶,俄国当局在贸易方面对厄鲁特蒙古人给予了相当优惠的待遇,但这是以“要求厄鲁特人转入俄国国籍、履行始终不渝地服务于俄国沙皇的义务”为条件的。俄国有自已的企图,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借助这些措施,不使用武力就可以在这一地区巩固和扩大自已的领地”。②尽管如此,贸易本身还是在双方需求的基础上发展着。这种贸易关系的发展和东向与中国内地的贸易互为补充,这一点可以从厄鲁特对从两个方向贸易输入的不同商品类别上反映出来:对俄国贸易输入的商品主要为马具、呢绒、服装、武器、纸张及小五金。东向与中国内地贸易的主要输入品为绸绢、布匹、茶叶、铁器及食品、大黄、烟草等。在厄鲁特与俄国的贸易中,中亚商人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相当一部分厄鲁特与俄国的贸易是通过中亚商人的中介来完成的。这些中亚商人组成商队,向厄鲁特封建王公运送货物(奢侈品在其中占多数),换取的牲畜和畜产品又被商队运到俄属西西伯利亚各城出售。
巴图尔浑台吉执政时期(1635年至1653年),厄鲁特经济进一步发展。农业种植业经济已兴起,并在一些城镇周围初具规模。与俄国之间的通商贸易也更趋繁荣。1638年,厄鲁特人曾自豪地宣称:我们“供给各城市大量牛、马和其它牲畜,这使你们西伯利亚各城市肉食富足,我们还运来各种皮货进行贸易,这些东西都能使沙皇受益。”①1640年,巴图尔浑台吉亲自邀请俄国商人前来厄鲁特领地发展通商贸易。1645年底,俄国当局向巴图尔浑台吉递交信函,重申允许厄鲁特商人在俄国境内“免税进行自由贸易。”居住在西西伯利亚的俄国军役人员和居民也期望不断扩大这种贸易关系,秋明城堡事件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1646年6月,俄国西伯利亚衙门发出了一项通告,规定今后对厄鲁特部的贸易只限于在边境地区的托博尔斯克、塔拉、托木斯克三处进行,其余各地禁止开展贸易活动。1647年7月,一支厄鲁特商队赶着马匹和牛、羊前来到秋明,当地俄国官员按规定拒绝商队进城,并建议去托博尔斯克贸易。厄鲁特商队以俄国当局准在西伯利亚自由通商为由,拒绝离去,双方相持不下。秋明城中各阶层人民闻知此事,纷纷向地方当局递交呈文,请求准许从卡尔梅克兀鲁思(指厄鲁特部)来的贸易使者进入秋明,并请求准予打破惯例,同卡尔梅克人自由贸易。呈文中称:“彼等军役人员为陛下效劳,络绎不绝踏上征途,奔赴城镇。远行之卫兵在许多地方设防镇守,农民为陛下耕种俄国之田地。然陛下不施恩典于彼等,不准与卡尔梅克人通商,彼等为沙皇陛下效劳军役人员,终将为此丧命,农民亦将荒芜田地。”于是,地方当局不得不允许厄鲁特商队进入秋明城堡。①半年后,俄国政府对厄鲁特商队增加开放了秋明。
巴图尔浑台吉执政时期,厄鲁特对外征战相应增加。在这一时期的对俄贸易中,武器的输入占了相当部分(中国内地禁止向厄鲁特部输出兵器。)。1644年,厄鲁特与哈萨克部开战时,巴图尔浑台吉派出代表到俄国库兹涅茨克县,有组织地大批收购武器和军事装备;向俄属居民和军役人员购买库亚克(一种锁子甲)、头盔、弓箭、矛及各种铁器。②散见于厄鲁特与俄国贸易主要地点托木斯克、塔拉、托博尔斯克的俄文海关资料,反映了这一时期双边贸易的一个侧面。
“据第305号海关税册记载,1649年,托木斯克的军役人员和商人向厄鲁特人采购的主要是黑貂皮、狐皮、貂皮和海狸皮。在这一年12月,军役人在卡尔梅克人那里购买了106张黑貂皮、76张狐皮、3张海狸皮。同年,俄国人去过厄鲁特乌鲁斯,并运回了许多黑貂皮、狐皮和貂皮。1650年5月,托木斯克人向外来的厄鲁特人购买了398张黑貂皮、125条貂尾、187张狐皮、44张貂皮、8张海狸皮等等。”
“据托木斯克海关税册资料,在1652年,厄鲁特人来托木斯克五次,时间分别在1、3、5、6月和12月,他们同时赶来了马群和角畜,运来了羊皮袄、黑貂皮、狐皮、貂皮、海狸皮,6月,准噶人(即厄鲁特人)卖出了41匹马和各种毛皮。12月,他们运来了28捆零4张黑貂皮、130个黑貂脐、10张残次黑貂皮、671条貂尾、686张狐皮、92张貂皮、2张残次貂皮、2只狼獾、47张海狸皮。在1652年的托木斯克,还以30卢布的价格,卖出了二普特大黄。”
“塔拉海关登记册记载,1637—1688年卖出了各种毛皮和61匹马;1645—1646年卖了52匹、29头牛、164只羊;1648—1649年卖出20张羊羔皮、4件羊皮袄、各种卡尔梅克货物。1653—1654年出售的有大黄、30头家畜、2峰骆驼;1657—1659年出售了45张狐皮、220张羊羔皮、20件皮袄、20条毡子和大黄、皮货。”
“1639—1640年在托博尔斯克海关税册上注册的有:各种卡尔梅克毛皮、500多只绵羊和山羊、31匹马、67头角畜;1644—1645年有140只绵羊和山羊、毛皮;1650年有29匹马、毛皮;1653年,从卡尔梅克运来了大黄根和大黄茎;1654—1658运来了85匹马、60头牲口、528张羊羔皮、888张狐皮和其他各种毛皮、大黄、各种中国货(织物、茶叶)。和托木斯克一样,托博尔斯克与厄鲁特人的贸易也是在一个专门为贸易划定的地方进行,这个地方被称为鞑靼区。俄国商人从这里把厄鲁特货物运往莫斯科,阿尔汉格尔斯克,一部分货物还转卖给来自欧洲的商人。”①
1653年,巴图尔浑台吉去世,厄鲁特内部发生混战,对俄关系中断,双边贸易受到严重影响。1664年,僧格执政,希望尽快恢复对俄贸易,派出以伊尔卡切庆亚扎为首的代表团前往托木斯克,要求恢复鲁厄鲁特蒙古人在托木斯克的自由贸易权。1667年,僧格再次向俄国托木斯克地方官员的代表声明:“对于陛下的不同阶层的人携带商品前来我的领地或(俄)大君主派人去中国(内地)贸易,我都表示欢迎。……同样,我也愿意派自已的人去托木斯克和托博尔斯克通商。”①但这一时期由于僧格拒绝归顺俄国和俄方拒不交还非法进入托木斯克的厄鲁特属民,双方关系相当紧张,俄国方面拒绝恢复与厄鲁特的贸易关系。即使厄鲁特的使团,也禁止在托木斯克出售或购买物品。②1670年,托博尔斯克地方当局颁布了一道通令,规定对厄鲁特使团成员随带的商品必须查验,并向购买厄鲁特代表携带商品的俄国商人征收关税,“每个卢布收10戈比,一匹马和一头牛各收10戈比,每只羊收5戈比。”③
俄国当局在减少对厄鲁特贸易的同时,却在努力开辟经厄鲁特前往中国北京的通道。早在俄国进入西伯利亚之前,聚居在托博尔河口的中亚“不花剌”商人即从事着往来中国甘肃肃州(今酒泉)的易货贸易。长期以来肃州一直是中国中原王朝接纳西部各地方贸易的重要货物集散地和交易场所,而且也是前往中国内地通商的主要关口。俄国在与厄鲁特蒙古开展贸易的同时,即力图将贸易向肃州延伸,以便同中国首府北京直接通商。1642年,俄属塔拉城堡的哥萨克骑兵叶麦利扬·维尔申宁等三人曾大胆地随同厄鲁特土尔扈特部岱青台吉的商队,深入到中国甘肃西宁城(今青海省西宁市)。
1652年,厄鲁特和硕特部的一支“使团”到达莫斯科。在与俄国方面的会谈中,使臣表示愿意协助俄国商队前往中国内地。同年,一支“不花剌”商队将中国货物运到了莫斯科,由此进一步引发了俄国政府直接开展对华贸易的兴头。是年11月,俄国开始筹划经厄鲁特部与中国内地的通商。定居托博尔斯克的“不花剌”商人谢·阿勃林和叶·谢伊托夫奉诏至莫斯科,向俄国政府财务衙门(相当于财政部)报告了他们以往同中国内地通商的各种有关情况。1653年,俄国财务衙门正式委派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带领若干名税收人员和五万卢布国库款,①前往托博尔斯克建立与中亚、厄鲁特部和中国内地直接通商的基地。托博尔斯克地方当局奉命为此筹建货栈、仓库等设施,一俟各方面准备就绪,即向中国内地派遣大型商队。1654年2月,巴伊科夫作为俄国使节自托博尔斯克出发,经厄鲁特部出使北京,寻求同中国建立直接通商是其最重要的目的。由于俄国入侵中国黑龙江流域的行径和礼仪等方面的问题,巴伊科夫出使未得任何结果,但使团经厄鲁特领地进入中国内地的路线却为日后中俄两国商队贸易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1663年3月,俄国在托博尔斯克组建了第一支赴北京的大型商队。1668年7月,商队委托商人阿勃林和库尔提·买买提率领,自托博尔斯克出发,沿额尔齐斯河上溯进入厄鲁特领地,在额尔齐斯河河源处越阿尔泰山,经外蒙古、内蒙古、张家口进入北京贸易。1671年10月,商队经原路返回托博尔斯克。据商队帐目计算,商队带往中国的货物估值为4540卢布,从中国运回的货物在莫斯科售价为18752卢布。②此后很长一个时期,托博尔斯克至北京的路线是中俄贸易的主要通道。俄国商队在往来途经厄鲁特部时,常常于各人口聚集区停驻数日,开展易货贸易。所以西路中俄贸易通道的开辟和两国商务的发展,对厄鲁特部与俄国人的贸易发展有相当的促进作用。
此时,厄鲁特人又为俄国方面对当地贸易的冷落不满,他们以中断俄方人员的食盐供应来要求恢复先前的对俄贸易。按惯例,俄方采盐团每年可定期进入厄鲁特所属的亚梅什湖采盐,供应西西伯利亚诸城。1672年8月,俄方又来采盐,被早已等候的厄鲁特人围住,他们占据通路,不让俄方人员采盐,“不想给盐而要求(俄国人)跟他们贸易,并按他们的价格购买他们的各种商品”。俄方采盐团负责人不得不宣布“……在亚梅什湖取完盐后,就跟他们自由贸易,并照规定的价格买他们的商品”。厄鲁特人这才允许采盐团进入亚梅什湖,并于采盐后与俄方进行了交易。①史料未能证明俄国大型商队经厄鲁特领地至北京贸易与厄鲁特人在亚梅什湖的行动是否有直接联系,但亚梅什湖发生的事件至少反映了厄鲁特人希望与俄国恢复贸易关系的愿望。
1671年噶尔丹执政,准噶尔(即前厄鲁特)与俄国的贸易关系有所缓和,1678年,噶尔丹向托博尔斯克派出了自已的商队。随着双方政治上的接近,俄国对准噶尔蒙古人的通商要求大多给以了满足,但在以后十多年中,噶尔丹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对东部喀尔喀蒙古人的争斗上。1688年,噶尔丹向喀尔喀蒙古大举进犯,战争连年不断,准噶尔的社会经济发展受到严重损害,对俄贸易趋于停顿。
18世纪初,俄国利用准噶尔在征战中削弱的时机,在托博尔河与额尔齐斯河中上游地区向准噶尔领地蚕食推进。1716年建立了鄂木斯克城堡,1717年修筑了热列金斯克寨堡,1718年建立了谢米巴拉金斯克城堡,1720年深入到斋桑湖北建立了乌斯季卡缅诺哥尔斯克城堡(清代文献称铿格尔图喇。)俄国沿额尔齐斯河的殖民扩张活动受到准噶尔人民的武装反抗,双方接连发生几次冲突战争,关系日益恶化,贸易再次受到影响。在其后与俄国的谈判中,准噶尔方面曾要求俄国撤出被占领的准噶尔领地;提出双方友好相处、和平贸易等项建议,被俄国拒绝。18世纪20年代,俄国在西西伯利亚的殖民扩张活动进入巩固时期,扩大与周边地区的经济联系,成为俄国巩固当地殖民经济的重要内容。
1721年,沙皇彼得一世向俄国枢密院下了一道诏令,一方面要求加强对已侵占地区亚梅什湖要塞的防务,同时命令与准噶尔蒙古人“媾和通商”,派遣商队深入准噶尔以至西宁,大坝和拉萨等地区。诏令特别强调指出:派出这些商队“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派出一批干练的人员随商人一起活动,以便探明何地出产黄金,产量如何;有哪些道路可以通,能否达到并占领该地”。①从18世纪20年代起,准噶尔与俄国的通商关系逐渐恢复,准噶尔商队成了“西伯利亚市场、伊尔比茨克集市、甚至这些市场、集市以外的显著因素。”托博尔斯克和俄国新占领的亚梅什湖周围成为这一时期准噶尔商人的贸易集中地。为了管理贸易,俄国在亚梅什要塞和谢米巴拉金斯克城堡设立了海关,当地的进出口贸易开始有了较为准确的统计。
1724年一1728年俄国亚梅什、谢米巴拉金斯克海关对准噶尔贸易统计:
上表中的数字并未包括准噶尔与俄国贸易的全部数额,但这些数字说明双方贸易已经具有相当规模了。一些实力雄厚的俄国商队深入到乌鲁木齐,这里是准噶尔部最大的、也是最富有的城镇之一。由于双方贸易额的增长,俄国当局认为对等自由免税通商对准噶尔商人比对俄国商人更为有利,便开始向准噶尔商人征收货物进口关税。但其内部对此认识并不一致,西伯利亚总督加加林向准噶尔商人征收了进口税,而他的继任者切尔卡斯基则根据双方的自由免税贸易协议,把收来的进口税退还给了准噶尔商人。1733年,俄国政府派出以乌格里莫夫少校为首的代表团前往准噶尔,俄方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能缔结一个特别通商条约。在双方谈判中,乌格里莫夫提出了俄国方面的草案:准噶尔商人有权在亚梅什和谢米巴拉金斯克贸易,在这些地方他们的商品可以不受海关检查,不收关税。他们也有权把商品运到俄国其它城市,但这时就要课收规定的关税。俄国商人在亚梅什和谢米巴拉金斯克贸易也豁免关税,当俄国商人来准噶尔部时,准噶尔当局可酌情向他们征收适当的赋税。这实际上是希望把对准噶尔的免税贸易限制在个别边境开放城市。准噶尔代表坚持保留原有的自由免税贸易协议,双方未能就俄方提案取得一致意见。18世纪上半,俄国商人在准噶尔领地内贸易活动的范围扩大了,伊犁、塔尔巴哈台都不时地有俄国商队到来,一些商队则把乌鲁木齐作为交易地点。1729年8月,中国与俄国在蒙古边境恰克图开辟了贸易市场。进入40年代,恰克图年均贸易额已达50—60万卢布。一些西西伯利亚城镇的富商便前往恰克图,从事更为有利可图的对中国内地的贸易,与准噶尔之间的贸易明显地减少了。
1745年噶尔丹策凌去世,准噶尔蒙古处于内乱中。1755年清军出兵统一西域,至1757年平定反叛的阿睦尔撤纳,结束了准噶尔政权在西域的统治。
17世纪初开始的厄鲁特(准噶尔)与俄国的贸易,是中国与俄国之间最早的地区性贸易。从中国方面讲,厄鲁特(准噶尔)与俄国的贸易具有游牧经济与周边经济交往的一般性质,即与俄国的贸易补充了厄鲁特(准噶尔)单一游牧经济的不足。厄鲁特(准噶尔)牧民以牲畜和畜产品换取生活必需品,封建王公贵族则通过对俄贸易得到奢侈品或武器。俄国与近邻厄鲁特(准噶尔)部贸易关系的建立,是同其对厄鲁特(准噶尔)所属额尔齐斯河流域的武装殖民活动紧密相联的。俄国一方面向厄鲁特(准噶尔)实行蚕食,同时又与他们建立起对自已颇为有利的贸易关系。“随着军人的开进,商人也开进去了。这些商人以哥萨克人的村镇为基地,继续把贸易向南和向东推进。”①因此,从俄国方面讲,与近邻厄鲁特(准噶尔)部的贸易对其巩固西西伯利亚的殖民经济有着重要的意义。厄鲁特(准噶尔)的蒙古马匹是俄属各殖民城镇军马和役畜的主要来源,牛、羊和畜产品则供应了城镇的肉食和生活需要。18世纪20年代俄国在这一地区的海关建立之前,基本上没有什么有关双边贸易额的统计资料,双方贸易采取游牧民族惯用的以货易货方式进行,互不征税,基本是处于自由发展中。由于贸易在厄鲁特(准噶尔)游牧经济与俄国殖民经济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双方的贸易关系与政治关系往往同步开展,与之相适应的是双方贸易关系往往受政治关系变化的影响或制约,反之贸易交往又是双方在制定政策时优先考虑的因素。17世纪初至18世纪中期,中国西部与俄国西西伯利亚边区之间的地区贸易,首先是双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贸易关系具有互惠的性质。
俄国向东方进入亚洲的殖民活动始于16世纪后半。1581年,以叶尔马克为首的一群哥萨克人越过乌拉尔山,开始了对西伯利亚的征服。1586年,在一个小镇的废墟上建立了秋明城堡,这是俄国人在乌拉尔山以东建立的第一个殖民据点。1587年,在托博尔河与额尔齐斯河的汇流处构筑了托博尔斯克城堡。随后俄国人沿额尔齐斯河上溯,于1594年在该河中游建立了塔拉城堡。1604年,俄国人在鄂毕河上游支流托木河畔修筑了托木斯克城堡,在这里他们与游牧于鄂毕河中上游的厄鲁特蒙古人发生了接触。此后,俄国人与厄鲁特蒙古人的活动主要集中在额尔齐斯河流域,双方的关系不断发展。这种关系是多方面的:在政治上,侵略与反侵略、殖民与反殖民、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与正常的往来并存;在经济上,一方面存在着掠夺与反掠夺的斗争,同时厄鲁特牧民与俄国人民在西西伯利亚各定居殖民城堡之间的经济交往相应发展起来。厄鲁特蒙古王公也像当年要求同中国内地明王朝开市一样,希望在俄国城镇出售牲畜和畜产品。他们开始赶着成群的马匹前往托博尔斯克或托木斯克,用以交换俄国人的商品。“如像软革、铜锅、黄铜环、铁和水獭皮(他们认为水獭皮比其它皮好)”。①由于地理因素及厄鲁特蒙古周边形势的变化,东向与中国内地的贸易呈现出时断时续的不景气状况,对俄国贸易的重要性却日益明显。此外,当俄国人占有托博尔河口这个往日中亚“不花刺”商人的聚集地后,相当一部分厄鲁特人西向与中亚诸城的贸易实际转入了俄国商人手中。
塔拉城堡是俄国人在额尔齐斯河中游建立的前沿据点,1597年,这里已成为俄国与厄鲁特蒙古部之间的贸易中心。1607年,当厄鲁特人的使团前往塔拉城时,一支商队随使团进入塔拉城,商队“赶着550匹马来出售,换取衣服、金钱和书写纸。塔拉当局免去了这笔交易的税收”。①此后,双边贸易相互免税成为一条不成文的通例。不久,托博尔斯克和托木斯克也成为厄鲁特商队时常光顾的地区。
俄国商人则沿额尔齐斯河深入厄鲁特领地进行贸易,易货集中在亚梅什湖(位于额尔齐斯河中游左岸,中方称之为达布逊淖尔。蒙语,意为盐池。)周围地区。这里长期以来就是厄鲁特蒙古牧民的贸易中心,每年都定期举行历时20多天的大规模民间集市贸易,来自周围各部的蒙古牧民、中亚“不花剌”商人、天山以南的维吾尔商人等会聚一处,相互通商交易。后来的俄国商人加入了亚梅什湖集市,与当地居民易货。有时俄商还深入周围蒙古族部民中去兜售商品,牧民则向他们出售牲畜及畜产品;王公们在出售牲畜的同时,还以从中国内地贩运来的大黄、烟草、麝香等与俄商交易。厄鲁特蒙古王公有时也遨请俄国官方派商队前来贸易,如1609年,王公们向俄方建议,请塔拉将军本人带领俄国商人到厄鲁特所属的额尔齐斯河上游地区来通商贸易。
俄国档案文献是研究17世纪俄国与中国西部厄鲁特蒙古相互关系的主要资料来源,M·N·戈利曼与C·N·斯列萨尔丘克在《17世纪30—50年代俄国与蒙古相互关系的俄国档案资料》(载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简讯》1965年第76期)中指出:在这一时期俄文档案文献中,内容最多的是记载厄鲁特人与俄国的贸易情况。由于厄鲁特人每年春、夏两季三次前往俄国西伯利亚贸易,俄方公文和报告中有关厄鲁特商人前来经商的指示很多。其中有不少关于马匹的价格和厄鲁特商人在西伯利亚城市以马匹换回商品的情况。1618年3月,厄鲁特蒙古的代表对俄方谈到双边贸易时说,在以往13年中,“他们曾不断来到俄国城市,赶着牛、马和各种牲畜各两三百头,几乎遍城皆是。”俄国政府则表示欢迎厄鲁特人“赶着马群和各种牲畜、携带卡尔梅克汗国(批厄鲁特蒙古部)出产的商品来西伯利亚各城市,来托博尔斯克和我们的其它城布,吩咐其属民不必有任何顾虑。……对你们的商人做到关怀备至,使之丝毫不受任何人的欺凌。”①随着贸易的扩大,俄属西西伯利亚各城堡都辟出专门地点接待厄鲁特商人。双方政治交往中互赠礼物或回赠的赏赐往往是相互贸易的另一种形式。礼物与赏赐的项目与商人间贸易品种大致相同,且数额较大,价值一般对等。这种贸易方式主要是满足了厄鲁特封建王公的需要,在赏赐或回赠礼物前双方要协商或讨价还价,甚至可以指名要求回赠某物或拒绝接受礼物中某些不需要的项目。
17世纪上半叶,俄国当局在贸易方面对厄鲁特蒙古人给予了相当优惠的待遇,但这是以“要求厄鲁特人转入俄国国籍、履行始终不渝地服务于俄国沙皇的义务”为条件的。俄国有自已的企图,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借助这些措施,不使用武力就可以在这一地区巩固和扩大自已的领地”。②尽管如此,贸易本身还是在双方需求的基础上发展着。这种贸易关系的发展和东向与中国内地的贸易互为补充,这一点可以从厄鲁特对从两个方向贸易输入的不同商品类别上反映出来:对俄国贸易输入的商品主要为马具、呢绒、服装、武器、纸张及小五金。东向与中国内地贸易的主要输入品为绸绢、布匹、茶叶、铁器及食品、大黄、烟草等。在厄鲁特与俄国的贸易中,中亚商人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相当一部分厄鲁特与俄国的贸易是通过中亚商人的中介来完成的。这些中亚商人组成商队,向厄鲁特封建王公运送货物(奢侈品在其中占多数),换取的牲畜和畜产品又被商队运到俄属西西伯利亚各城出售。
巴图尔浑台吉执政时期(1635年至1653年),厄鲁特经济进一步发展。农业种植业经济已兴起,并在一些城镇周围初具规模。与俄国之间的通商贸易也更趋繁荣。1638年,厄鲁特人曾自豪地宣称:我们“供给各城市大量牛、马和其它牲畜,这使你们西伯利亚各城市肉食富足,我们还运来各种皮货进行贸易,这些东西都能使沙皇受益。”①1640年,巴图尔浑台吉亲自邀请俄国商人前来厄鲁特领地发展通商贸易。1645年底,俄国当局向巴图尔浑台吉递交信函,重申允许厄鲁特商人在俄国境内“免税进行自由贸易。”居住在西西伯利亚的俄国军役人员和居民也期望不断扩大这种贸易关系,秋明城堡事件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1646年6月,俄国西伯利亚衙门发出了一项通告,规定今后对厄鲁特部的贸易只限于在边境地区的托博尔斯克、塔拉、托木斯克三处进行,其余各地禁止开展贸易活动。1647年7月,一支厄鲁特商队赶着马匹和牛、羊前来到秋明,当地俄国官员按规定拒绝商队进城,并建议去托博尔斯克贸易。厄鲁特商队以俄国当局准在西伯利亚自由通商为由,拒绝离去,双方相持不下。秋明城中各阶层人民闻知此事,纷纷向地方当局递交呈文,请求准许从卡尔梅克兀鲁思(指厄鲁特部)来的贸易使者进入秋明,并请求准予打破惯例,同卡尔梅克人自由贸易。呈文中称:“彼等军役人员为陛下效劳,络绎不绝踏上征途,奔赴城镇。远行之卫兵在许多地方设防镇守,农民为陛下耕种俄国之田地。然陛下不施恩典于彼等,不准与卡尔梅克人通商,彼等为沙皇陛下效劳军役人员,终将为此丧命,农民亦将荒芜田地。”于是,地方当局不得不允许厄鲁特商队进入秋明城堡。①半年后,俄国政府对厄鲁特商队增加开放了秋明。
巴图尔浑台吉执政时期,厄鲁特对外征战相应增加。在这一时期的对俄贸易中,武器的输入占了相当部分(中国内地禁止向厄鲁特部输出兵器。)。1644年,厄鲁特与哈萨克部开战时,巴图尔浑台吉派出代表到俄国库兹涅茨克县,有组织地大批收购武器和军事装备;向俄属居民和军役人员购买库亚克(一种锁子甲)、头盔、弓箭、矛及各种铁器。②散见于厄鲁特与俄国贸易主要地点托木斯克、塔拉、托博尔斯克的俄文海关资料,反映了这一时期双边贸易的一个侧面。
“据第305号海关税册记载,1649年,托木斯克的军役人员和商人向厄鲁特人采购的主要是黑貂皮、狐皮、貂皮和海狸皮。在这一年12月,军役人在卡尔梅克人那里购买了106张黑貂皮、76张狐皮、3张海狸皮。同年,俄国人去过厄鲁特乌鲁斯,并运回了许多黑貂皮、狐皮和貂皮。1650年5月,托木斯克人向外来的厄鲁特人购买了398张黑貂皮、125条貂尾、187张狐皮、44张貂皮、8张海狸皮等等。”
“据托木斯克海关税册资料,在1652年,厄鲁特人来托木斯克五次,时间分别在1、3、5、6月和12月,他们同时赶来了马群和角畜,运来了羊皮袄、黑貂皮、狐皮、貂皮、海狸皮,6月,准噶人(即厄鲁特人)卖出了41匹马和各种毛皮。12月,他们运来了28捆零4张黑貂皮、130个黑貂脐、10张残次黑貂皮、671条貂尾、686张狐皮、92张貂皮、2张残次貂皮、2只狼獾、47张海狸皮。在1652年的托木斯克,还以30卢布的价格,卖出了二普特大黄。”
“塔拉海关登记册记载,1637—1688年卖出了各种毛皮和61匹马;1645—1646年卖了52匹、29头牛、164只羊;1648—1649年卖出20张羊羔皮、4件羊皮袄、各种卡尔梅克货物。1653—1654年出售的有大黄、30头家畜、2峰骆驼;1657—1659年出售了45张狐皮、220张羊羔皮、20件皮袄、20条毡子和大黄、皮货。”
“1639—1640年在托博尔斯克海关税册上注册的有:各种卡尔梅克毛皮、500多只绵羊和山羊、31匹马、67头角畜;1644—1645年有140只绵羊和山羊、毛皮;1650年有29匹马、毛皮;1653年,从卡尔梅克运来了大黄根和大黄茎;1654—1658运来了85匹马、60头牲口、528张羊羔皮、888张狐皮和其他各种毛皮、大黄、各种中国货(织物、茶叶)。和托木斯克一样,托博尔斯克与厄鲁特人的贸易也是在一个专门为贸易划定的地方进行,这个地方被称为鞑靼区。俄国商人从这里把厄鲁特货物运往莫斯科,阿尔汉格尔斯克,一部分货物还转卖给来自欧洲的商人。”①
1653年,巴图尔浑台吉去世,厄鲁特内部发生混战,对俄关系中断,双边贸易受到严重影响。1664年,僧格执政,希望尽快恢复对俄贸易,派出以伊尔卡切庆亚扎为首的代表团前往托木斯克,要求恢复鲁厄鲁特蒙古人在托木斯克的自由贸易权。1667年,僧格再次向俄国托木斯克地方官员的代表声明:“对于陛下的不同阶层的人携带商品前来我的领地或(俄)大君主派人去中国(内地)贸易,我都表示欢迎。……同样,我也愿意派自已的人去托木斯克和托博尔斯克通商。”①但这一时期由于僧格拒绝归顺俄国和俄方拒不交还非法进入托木斯克的厄鲁特属民,双方关系相当紧张,俄国方面拒绝恢复与厄鲁特的贸易关系。即使厄鲁特的使团,也禁止在托木斯克出售或购买物品。②1670年,托博尔斯克地方当局颁布了一道通令,规定对厄鲁特使团成员随带的商品必须查验,并向购买厄鲁特代表携带商品的俄国商人征收关税,“每个卢布收10戈比,一匹马和一头牛各收10戈比,每只羊收5戈比。”③
俄国当局在减少对厄鲁特贸易的同时,却在努力开辟经厄鲁特前往中国北京的通道。早在俄国进入西伯利亚之前,聚居在托博尔河口的中亚“不花剌”商人即从事着往来中国甘肃肃州(今酒泉)的易货贸易。长期以来肃州一直是中国中原王朝接纳西部各地方贸易的重要货物集散地和交易场所,而且也是前往中国内地通商的主要关口。俄国在与厄鲁特蒙古开展贸易的同时,即力图将贸易向肃州延伸,以便同中国首府北京直接通商。1642年,俄属塔拉城堡的哥萨克骑兵叶麦利扬·维尔申宁等三人曾大胆地随同厄鲁特土尔扈特部岱青台吉的商队,深入到中国甘肃西宁城(今青海省西宁市)。
1652年,厄鲁特和硕特部的一支“使团”到达莫斯科。在与俄国方面的会谈中,使臣表示愿意协助俄国商队前往中国内地。同年,一支“不花剌”商队将中国货物运到了莫斯科,由此进一步引发了俄国政府直接开展对华贸易的兴头。是年11月,俄国开始筹划经厄鲁特部与中国内地的通商。定居托博尔斯克的“不花剌”商人谢·阿勃林和叶·谢伊托夫奉诏至莫斯科,向俄国政府财务衙门(相当于财政部)报告了他们以往同中国内地通商的各种有关情况。1653年,俄国财务衙门正式委派费奥多尔·伊萨科维奇·巴伊科夫带领若干名税收人员和五万卢布国库款,①前往托博尔斯克建立与中亚、厄鲁特部和中国内地直接通商的基地。托博尔斯克地方当局奉命为此筹建货栈、仓库等设施,一俟各方面准备就绪,即向中国内地派遣大型商队。1654年2月,巴伊科夫作为俄国使节自托博尔斯克出发,经厄鲁特部出使北京,寻求同中国建立直接通商是其最重要的目的。由于俄国入侵中国黑龙江流域的行径和礼仪等方面的问题,巴伊科夫出使未得任何结果,但使团经厄鲁特领地进入中国内地的路线却为日后中俄两国商队贸易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1663年3月,俄国在托博尔斯克组建了第一支赴北京的大型商队。1668年7月,商队委托商人阿勃林和库尔提·买买提率领,自托博尔斯克出发,沿额尔齐斯河上溯进入厄鲁特领地,在额尔齐斯河河源处越阿尔泰山,经外蒙古、内蒙古、张家口进入北京贸易。1671年10月,商队经原路返回托博尔斯克。据商队帐目计算,商队带往中国的货物估值为4540卢布,从中国运回的货物在莫斯科售价为18752卢布。②此后很长一个时期,托博尔斯克至北京的路线是中俄贸易的主要通道。俄国商队在往来途经厄鲁特部时,常常于各人口聚集区停驻数日,开展易货贸易。所以西路中俄贸易通道的开辟和两国商务的发展,对厄鲁特部与俄国人的贸易发展有相当的促进作用。
此时,厄鲁特人又为俄国方面对当地贸易的冷落不满,他们以中断俄方人员的食盐供应来要求恢复先前的对俄贸易。按惯例,俄方采盐团每年可定期进入厄鲁特所属的亚梅什湖采盐,供应西西伯利亚诸城。1672年8月,俄方又来采盐,被早已等候的厄鲁特人围住,他们占据通路,不让俄方人员采盐,“不想给盐而要求(俄国人)跟他们贸易,并按他们的价格购买他们的各种商品”。俄方采盐团负责人不得不宣布“……在亚梅什湖取完盐后,就跟他们自由贸易,并照规定的价格买他们的商品”。厄鲁特人这才允许采盐团进入亚梅什湖,并于采盐后与俄方进行了交易。①史料未能证明俄国大型商队经厄鲁特领地至北京贸易与厄鲁特人在亚梅什湖的行动是否有直接联系,但亚梅什湖发生的事件至少反映了厄鲁特人希望与俄国恢复贸易关系的愿望。
1671年噶尔丹执政,准噶尔(即前厄鲁特)与俄国的贸易关系有所缓和,1678年,噶尔丹向托博尔斯克派出了自已的商队。随着双方政治上的接近,俄国对准噶尔蒙古人的通商要求大多给以了满足,但在以后十多年中,噶尔丹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对东部喀尔喀蒙古人的争斗上。1688年,噶尔丹向喀尔喀蒙古大举进犯,战争连年不断,准噶尔的社会经济发展受到严重损害,对俄贸易趋于停顿。
18世纪初,俄国利用准噶尔在征战中削弱的时机,在托博尔河与额尔齐斯河中上游地区向准噶尔领地蚕食推进。1716年建立了鄂木斯克城堡,1717年修筑了热列金斯克寨堡,1718年建立了谢米巴拉金斯克城堡,1720年深入到斋桑湖北建立了乌斯季卡缅诺哥尔斯克城堡(清代文献称铿格尔图喇。)俄国沿额尔齐斯河的殖民扩张活动受到准噶尔人民的武装反抗,双方接连发生几次冲突战争,关系日益恶化,贸易再次受到影响。在其后与俄国的谈判中,准噶尔方面曾要求俄国撤出被占领的准噶尔领地;提出双方友好相处、和平贸易等项建议,被俄国拒绝。18世纪20年代,俄国在西西伯利亚的殖民扩张活动进入巩固时期,扩大与周边地区的经济联系,成为俄国巩固当地殖民经济的重要内容。
1721年,沙皇彼得一世向俄国枢密院下了一道诏令,一方面要求加强对已侵占地区亚梅什湖要塞的防务,同时命令与准噶尔蒙古人“媾和通商”,派遣商队深入准噶尔以至西宁,大坝和拉萨等地区。诏令特别强调指出:派出这些商队“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派出一批干练的人员随商人一起活动,以便探明何地出产黄金,产量如何;有哪些道路可以通,能否达到并占领该地”。①从18世纪20年代起,准噶尔与俄国的通商关系逐渐恢复,准噶尔商队成了“西伯利亚市场、伊尔比茨克集市、甚至这些市场、集市以外的显著因素。”托博尔斯克和俄国新占领的亚梅什湖周围成为这一时期准噶尔商人的贸易集中地。为了管理贸易,俄国在亚梅什要塞和谢米巴拉金斯克城堡设立了海关,当地的进出口贸易开始有了较为准确的统计。
1724年一1728年俄国亚梅什、谢米巴拉金斯克海关对准噶尔贸易统计:
上表中的数字并未包括准噶尔与俄国贸易的全部数额,但这些数字说明双方贸易已经具有相当规模了。一些实力雄厚的俄国商队深入到乌鲁木齐,这里是准噶尔部最大的、也是最富有的城镇之一。由于双方贸易额的增长,俄国当局认为对等自由免税通商对准噶尔商人比对俄国商人更为有利,便开始向准噶尔商人征收货物进口关税。但其内部对此认识并不一致,西伯利亚总督加加林向准噶尔商人征收了进口税,而他的继任者切尔卡斯基则根据双方的自由免税贸易协议,把收来的进口税退还给了准噶尔商人。1733年,俄国政府派出以乌格里莫夫少校为首的代表团前往准噶尔,俄方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能缔结一个特别通商条约。在双方谈判中,乌格里莫夫提出了俄国方面的草案:准噶尔商人有权在亚梅什和谢米巴拉金斯克贸易,在这些地方他们的商品可以不受海关检查,不收关税。他们也有权把商品运到俄国其它城市,但这时就要课收规定的关税。俄国商人在亚梅什和谢米巴拉金斯克贸易也豁免关税,当俄国商人来准噶尔部时,准噶尔当局可酌情向他们征收适当的赋税。这实际上是希望把对准噶尔的免税贸易限制在个别边境开放城市。准噶尔代表坚持保留原有的自由免税贸易协议,双方未能就俄方提案取得一致意见。18世纪上半,俄国商人在准噶尔领地内贸易活动的范围扩大了,伊犁、塔尔巴哈台都不时地有俄国商队到来,一些商队则把乌鲁木齐作为交易地点。1729年8月,中国与俄国在蒙古边境恰克图开辟了贸易市场。进入40年代,恰克图年均贸易额已达50—60万卢布。一些西西伯利亚城镇的富商便前往恰克图,从事更为有利可图的对中国内地的贸易,与准噶尔之间的贸易明显地减少了。
1745年噶尔丹策凌去世,准噶尔蒙古处于内乱中。1755年清军出兵统一西域,至1757年平定反叛的阿睦尔撤纳,结束了准噶尔政权在西域的统治。
17世纪初开始的厄鲁特(准噶尔)与俄国的贸易,是中国与俄国之间最早的地区性贸易。从中国方面讲,厄鲁特(准噶尔)与俄国的贸易具有游牧经济与周边经济交往的一般性质,即与俄国的贸易补充了厄鲁特(准噶尔)单一游牧经济的不足。厄鲁特(准噶尔)牧民以牲畜和畜产品换取生活必需品,封建王公贵族则通过对俄贸易得到奢侈品或武器。俄国与近邻厄鲁特(准噶尔)部贸易关系的建立,是同其对厄鲁特(准噶尔)所属额尔齐斯河流域的武装殖民活动紧密相联的。俄国一方面向厄鲁特(准噶尔)实行蚕食,同时又与他们建立起对自已颇为有利的贸易关系。“随着军人的开进,商人也开进去了。这些商人以哥萨克人的村镇为基地,继续把贸易向南和向东推进。”①因此,从俄国方面讲,与近邻厄鲁特(准噶尔)部的贸易对其巩固西西伯利亚的殖民经济有着重要的意义。厄鲁特(准噶尔)的蒙古马匹是俄属各殖民城镇军马和役畜的主要来源,牛、羊和畜产品则供应了城镇的肉食和生活需要。18世纪20年代俄国在这一地区的海关建立之前,基本上没有什么有关双边贸易额的统计资料,双方贸易采取游牧民族惯用的以货易货方式进行,互不征税,基本是处于自由发展中。由于贸易在厄鲁特(准噶尔)游牧经济与俄国殖民经济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双方的贸易关系与政治关系往往同步开展,与之相适应的是双方贸易关系往往受政治关系变化的影响或制约,反之贸易交往又是双方在制定政策时优先考虑的因素。17世纪初至18世纪中期,中国西部与俄国西西伯利亚边区之间的地区贸易,首先是双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贸易关系具有互惠的性质。
附注
不花刺即布哈拉汗国。16世纪初布哈拉汗昔班尼建立汗国,16世纪中期布哈拉汗国进入鼎盛时期,首府布哈拉成为中亚最繁荣的商业城镇。在每年秋季定期的贸易市集上,来自周围各国的商人云集布哈拉,易货交易通常要持续到第二年初春。繁盛的国际贸易使布哈拉名扬四方,以致当时人们往往将包括撒玛尔罕、希瓦等在内的中亚商人统称为不花刺(布哈拉)商人。;(苏)、伊、亚、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1635—1758)》中译本,1980年商务印书馆,第110页。; 《准噶尔汗国史》,中译本,第130页。;(苏)伊·亚·兹拉特金主编:《俄蒙关系文件汇集(1607—1636)》,1959年莫斯科出版,第72、76页。;《准噶尔汗国史》中译本,第165页。;《准噶尔汗国史》中译本,第187页。;(苏)M·N·戈利曼Г·N·斯列萨尔丘克:《17世纪30—50年代俄国与蒙古相互关系的俄国档案资料(概述)》载《文件在反驳,反对伪造俄中关系史》1982年莫斯科版。;《准噶尔汗国史》,中译本,第201页。;(苏)Ш·Б·奇米特多尔日耶夫:《17—18世纪蒙俄关系》1978年莫斯科出版第44—46页。;(英)约·弗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中译本1981年商务印书馆版,第1225页。; 同上,第1227页。;《准噶尔汗国史》中译本,第247页。; 17世纪下半与20世纪初的卢布比值约为1:8。见(俄)克卢琴切夫斯基:《文集》第一集,第171页。;(苏)M·N·斯拉德科夫斯基:《俄国各族人民与中国经济贸易关系史》1974年,莫斯科版,第94页。;《准噶尔汗国史》,中译本,第223页。;这道诏令原载《1649年以来俄罗斯帝国诏令大全》,1830年帝国秘书厅刊本,第6卷,第313页。转引自《沙俄侵华史》,1981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卷,第96页。;(俄)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中译本,1980年,商务印书馆版,第176页。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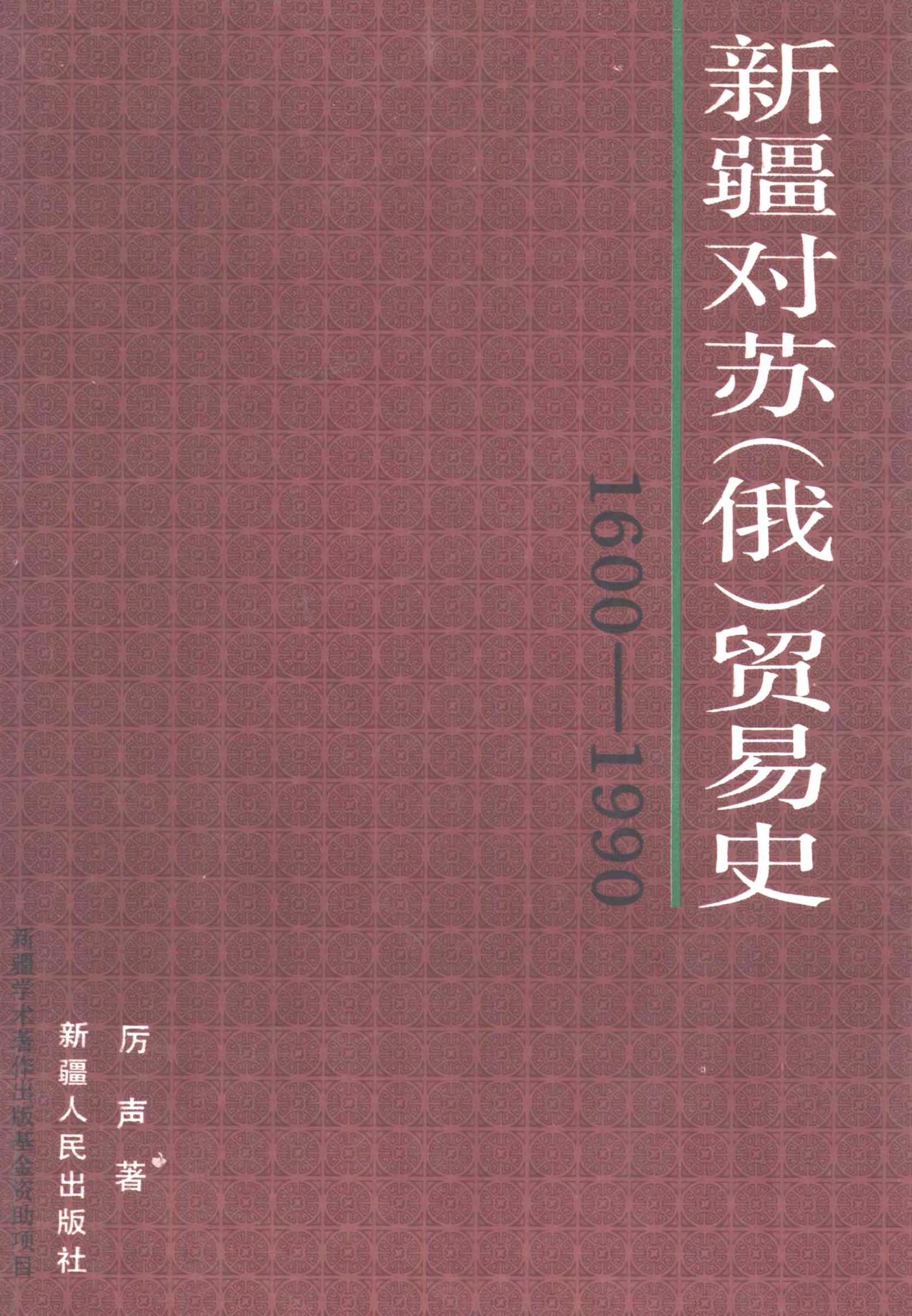
《新疆对苏(俄)贸易史 1660—1990》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出版地:1993
《新疆对苏(俄)贸易史(1600—1990)》一书是一部有关新疆对外经济关系史的力作。全书依清代、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通过丰富、翔实的史料,对17世纪初以来长达近四百年的新疆对苏(俄)贸易历史作了较为系统的综述。既从宏观上叙述了双边贸易的发展和变化,又以具体史实为依据,认真地探讨和论证了不同历史时期新疆对苏(俄)贸易的性质和特点;既是一部有学术价值的新疆历史研究著述,又在当今新疆对前苏联各国贸易中有重要参考意义,同时也填补了国内外对新疆与苏(俄)贸易缺乏系统研究的空白。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