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上述姓名按照姓名结构可以划分为几类。这些姓名种类在表12中进行列举。
A类型的姓名有着藏文类型的姓名结构,即氏族(rus,骨系)、论或尚(头衔)和姓名(mkhan与mying)的结合。有着姓名A类型的人员,多数是吐蕃政府的吐蕃官吏。那些有着部落名称“末”或“康”的人员,不是吐蕃人而是苏毗人。然而在契约中,他们并不是以当地居民而是以统治者吐蕃官吏出现。然而也有例外:论拉藏奴子,有着姓名A的结构;但是他的名字(mying)“do-tse”很有可能是汉名“奴子”的音译;他可能是唐人出身,后来成为吐蕃统治时期的一名官吏。②在契约中,这些官吏的角色是会议召集者、证人,或者是债务方的主人;他们很少担任债务方、债权方或担保人,只是相关人员。①
另一方面,B类型的姓名有着汉文类型的姓名结构:即汉姓+名字。B类型的姓是汉姓的音译;它们能够绝大多数回复到对应的汉字。表13列出古藏文契约中主要的汉姓。妇女方面有些变化,藏文za“氏”附加到姓后:如bam-za(汜氏)或“来自汜家的妻子”(文本25A);她的名是shibsam-nyang“十三娘”。
种类B可以按照名字的形式继续划分为三个种类:种类B-1:汉文姓名;种类B-2:藏文姓名;种类B-3:藏汉混合姓名。那些有着种类B-1的姓名(汉姓和汉名),最有可能是唐人。事实上,被列举的他们大多数生活在敦煌汉族居民的三个千户:悉董萨部落(stong-sar gyi sde),阿骨萨部落(rgod-sar gyi sde)和悉宁宗部落(snying-tsoms gyi sde)中①,虽然其他人属于吐谷浑、苏毗和通颊千户,一些有如“安”、“康”和“史”的姓,可能是粟特族裔。②简单说,他们都是当地唐人和其他有着汉文姓名的当地居民。
种类B-2和B-3(一个汉姓与一个藏文或藏文混合名字)的情况如何呢?我发现如此姓名的居民,与姓名种类B-1居民有着相同的族群背景。这一点可以从以下情形看出:a)他们属于同一汉人千户、吐谷浑、苏毗或通颊;b)某些情况下,卖方或借贷者是父子关系,父亲有种类B-1的姓名,但儿子有种类B-2或B-3的姓名③,也就是说,这些汉族居民最初有着纯粹的汉文姓名,但是在长期的吐蕃统治下,他们的后代开始拥有吐蕃或吐蕃混合的姓名。相应地,拥有姓名种类B-2和B-3内容的文本,写成于吐蕃控制敦煌的后期。
所以,有着种类B姓名的人员是汉族居民,包括其他吐蕃统治河西时期汉化的居民。他们在契约中数量最多,并且以债务方、债权方、担保人和证人出现;也就是说,他们的角色是契约当事方。
种类C的姓名是僧人姓名。种类C-1是藏文,但种类C-2是汉文。有着汉文僧人姓名的人员(种类C-2)显然是唐人,但是有着藏文僧人姓名(种类C-1)的并不一定是吐蕃人:如堪布土登(thub-brtan)[文本no.33-35]和僧人帕央(dpal-dbyang)[文本no.4,28]应是吐蕃人,但是文本no.6中的江确扎西(byang-cub bkra-shis)却出自汉族。这表明当汉族在吐蕃统治时期成为僧人,他们有时会接受藏文的僧名。有意思的是有些人,特别是僧人会使用种类B-1和B-2两种姓名,即一个最初的汉姓和一个藏文的音译或意译的名字,著名的译经僧吴法成(vgo chos-grub),就是其中之一。④
种类D的姓名,是非藏文非汉文的姓(或族群名称)和一个藏文或藏化名字的结合。族群名称或小邦名称如突厥(dru-gu),李(li,于阗),弥药(mi-nyag,党项)和多弥(da-myi或nam-pa?),以代替族群名称使用①。鞑靼(khe-rgad,一个蒙古部落)②可能也属于这一种类。朗(rlang),康(kam),折(tre),萨迦(skya氏族的后代)和羌若(vgreng-ro),都是苏毗部族的名字。确(skyo)属于通颊人。其他姓名如:诺(gno),尼(gnyi),洛(gnyos),金(gshen),墨革(mo-lgo),古折(sgub-tse),吴塘(vu-tang)和育冈(yogang),还不能完全确定,但是他们可能是生活在河西和塔里木盆地南缘之间地区的居民。
他们的名字在一些情形下完全是藏文的(如突厥拉春),在其他情形中或多或少是藏化的形式。例如,其中两个于阗人姓名,李萨宗(li bsargzhong)和李阿色(li ar-sel),他们的名是根据其最初的于阗人名字(sudãrrjãm和Arsäli),用藏文音译过来的。但是,萨宗(bsar-gzhong)在形式上由于添加了前缀b,③从而更加吐蕃化。
种类D的名字事实上十分接近于种类B。例如,于阗人姓名李萨宗(种类D)与汉文姓名李康子(种类B-1)和李玉勒(种类B-2)接近。在这种情形中,于阗人的族姓li同样接近于汉姓李。种类B和种类D有着非藏文的族名并添加一个名字的结构。种类B-1的名字是汉文名字的音译,种类B-2和B-3是B-1的修正。看来种类D的姓名的产生,主要指称汉族以外的非吐蕃人,它的形式借鉴了种类B的姓名。当时,族群名称用来代替部落名称,以防止没有合适的部落名称。所以,种类B和种类D的名字是与种类A相对的非吐蕃人的藏文姓名,而种类A是吐蕃人的最初姓名形式。
所以,那些有着种类D姓名的人群来自于河西、藏东北和塔里木盆地南部,包括苏毗、突厥、多弥、鞑靼、党项和于阗。在契约中,他们的角色是债务方、债权方、担保方和证人。
种类E包含了其余因文本损害,姓名结构不太清楚的名字。因为它们大多数包含有藏文字词,它们可能是藏文姓名的一部分,或者是藏文的不规则形式,或者是非吐蕃居民使用的藏化姓名。如果这些姓名的内容在将来能够得到较清楚地辨认,这一种类中的许多姓名可能会归入种类A至种类D中。
A类型的姓名有着藏文类型的姓名结构,即氏族(rus,骨系)、论或尚(头衔)和姓名(mkhan与mying)的结合。有着姓名A类型的人员,多数是吐蕃政府的吐蕃官吏。那些有着部落名称“末”或“康”的人员,不是吐蕃人而是苏毗人。然而在契约中,他们并不是以当地居民而是以统治者吐蕃官吏出现。然而也有例外:论拉藏奴子,有着姓名A的结构;但是他的名字(mying)“do-tse”很有可能是汉名“奴子”的音译;他可能是唐人出身,后来成为吐蕃统治时期的一名官吏。②在契约中,这些官吏的角色是会议召集者、证人,或者是债务方的主人;他们很少担任债务方、债权方或担保人,只是相关人员。①
另一方面,B类型的姓名有着汉文类型的姓名结构:即汉姓+名字。B类型的姓是汉姓的音译;它们能够绝大多数回复到对应的汉字。表13列出古藏文契约中主要的汉姓。妇女方面有些变化,藏文za“氏”附加到姓后:如bam-za(汜氏)或“来自汜家的妻子”(文本25A);她的名是shibsam-nyang“十三娘”。
种类B可以按照名字的形式继续划分为三个种类:种类B-1:汉文姓名;种类B-2:藏文姓名;种类B-3:藏汉混合姓名。那些有着种类B-1的姓名(汉姓和汉名),最有可能是唐人。事实上,被列举的他们大多数生活在敦煌汉族居民的三个千户:悉董萨部落(stong-sar gyi sde),阿骨萨部落(rgod-sar gyi sde)和悉宁宗部落(snying-tsoms gyi sde)中①,虽然其他人属于吐谷浑、苏毗和通颊千户,一些有如“安”、“康”和“史”的姓,可能是粟特族裔。②简单说,他们都是当地唐人和其他有着汉文姓名的当地居民。
种类B-2和B-3(一个汉姓与一个藏文或藏文混合名字)的情况如何呢?我发现如此姓名的居民,与姓名种类B-1居民有着相同的族群背景。这一点可以从以下情形看出:a)他们属于同一汉人千户、吐谷浑、苏毗或通颊;b)某些情况下,卖方或借贷者是父子关系,父亲有种类B-1的姓名,但儿子有种类B-2或B-3的姓名③,也就是说,这些汉族居民最初有着纯粹的汉文姓名,但是在长期的吐蕃统治下,他们的后代开始拥有吐蕃或吐蕃混合的姓名。相应地,拥有姓名种类B-2和B-3内容的文本,写成于吐蕃控制敦煌的后期。
所以,有着种类B姓名的人员是汉族居民,包括其他吐蕃统治河西时期汉化的居民。他们在契约中数量最多,并且以债务方、债权方、担保人和证人出现;也就是说,他们的角色是契约当事方。
种类C的姓名是僧人姓名。种类C-1是藏文,但种类C-2是汉文。有着汉文僧人姓名的人员(种类C-2)显然是唐人,但是有着藏文僧人姓名(种类C-1)的并不一定是吐蕃人:如堪布土登(thub-brtan)[文本no.33-35]和僧人帕央(dpal-dbyang)[文本no.4,28]应是吐蕃人,但是文本no.6中的江确扎西(byang-cub bkra-shis)却出自汉族。这表明当汉族在吐蕃统治时期成为僧人,他们有时会接受藏文的僧名。有意思的是有些人,特别是僧人会使用种类B-1和B-2两种姓名,即一个最初的汉姓和一个藏文的音译或意译的名字,著名的译经僧吴法成(vgo chos-grub),就是其中之一。④
种类D的姓名,是非藏文非汉文的姓(或族群名称)和一个藏文或藏化名字的结合。族群名称或小邦名称如突厥(dru-gu),李(li,于阗),弥药(mi-nyag,党项)和多弥(da-myi或nam-pa?),以代替族群名称使用①。鞑靼(khe-rgad,一个蒙古部落)②可能也属于这一种类。朗(rlang),康(kam),折(tre),萨迦(skya氏族的后代)和羌若(vgreng-ro),都是苏毗部族的名字。确(skyo)属于通颊人。其他姓名如:诺(gno),尼(gnyi),洛(gnyos),金(gshen),墨革(mo-lgo),古折(sgub-tse),吴塘(vu-tang)和育冈(yogang),还不能完全确定,但是他们可能是生活在河西和塔里木盆地南缘之间地区的居民。
他们的名字在一些情形下完全是藏文的(如突厥拉春),在其他情形中或多或少是藏化的形式。例如,其中两个于阗人姓名,李萨宗(li bsargzhong)和李阿色(li ar-sel),他们的名是根据其最初的于阗人名字(sudãrrjãm和Arsäli),用藏文音译过来的。但是,萨宗(bsar-gzhong)在形式上由于添加了前缀b,③从而更加吐蕃化。
种类D的名字事实上十分接近于种类B。例如,于阗人姓名李萨宗(种类D)与汉文姓名李康子(种类B-1)和李玉勒(种类B-2)接近。在这种情形中,于阗人的族姓li同样接近于汉姓李。种类B和种类D有着非藏文的族名并添加一个名字的结构。种类B-1的名字是汉文名字的音译,种类B-2和B-3是B-1的修正。看来种类D的姓名的产生,主要指称汉族以外的非吐蕃人,它的形式借鉴了种类B的姓名。当时,族群名称用来代替部落名称,以防止没有合适的部落名称。所以,种类B和种类D的名字是与种类A相对的非吐蕃人的藏文姓名,而种类A是吐蕃人的最初姓名形式。
所以,那些有着种类D姓名的人群来自于河西、藏东北和塔里木盆地南部,包括苏毗、突厥、多弥、鞑靼、党项和于阗。在契约中,他们的角色是债务方、债权方、担保方和证人。
种类E包含了其余因文本损害,姓名结构不太清楚的名字。因为它们大多数包含有藏文字词,它们可能是藏文姓名的一部分,或者是藏文的不规则形式,或者是非吐蕃居民使用的藏化姓名。如果这些姓名的内容在将来能够得到较清楚地辨认,这一种类中的许多姓名可能会归入种类A至种类D中。
附注
另一个这种姓名类型的事例可见于一封信件内容(Ch.86.II=vol.70,fol.40),其中的收信人姓名为论刘显子路顿。他的官职是论,但是他的族名刘和名显子是汉文(刘显子?)。他的姓名结构是:论+族源(rus汉文)+姓(mkhan汉文)+名(mying藏文)。他应也是汉族身份。;除了文本no.27和28,他们在其中是粮食借贷者,为欢迎都护论悉诺昔(blon stag-zigs)借粮酿酒。;参见如斯坦因文本Ch.73ⅹ.ⅴ.(5武内绍人《将》:849-851),和台湾保存的一份敦煌文本,敦煌卷子125v。;关于汉化的粟特人姓名,参见桑原骘藏(1926:239)和蒲立本(1952)。;如文本no.18中契约债务方有着姓名类型B-1(hva dze-dze华折折),但是他的儿子作为担保人,有着姓名类型B-2(hva khrom-legs华冲勒)。;这反而再次证明vgo chos-grub的汉族身份。;这种族群名称dru gu=突厥,也同样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一份汉文文献(TTD3:文献300)中,被作为人名使用。;关于khe-rgad,参见森安孝夫(1977:22-25)。;这些姓名可能并不是直接从于阗语转译而来,而是通过于阗语的汉文形式转译的。这些于阗人在汉族统治时期担任地方官吏(790年前),他们必须以汉文来书写姓名(KT4:178);通过这种方法,他们使用汉姓“李”和汉名的音译,在吐蕃征服于阗后,他们造出吐蕃名的形式,以便在藏文文书(如我们所讨论的契约)中使用。当时,他们遵循唐人取吐蕃名的方式,即姓名种类B,将他们的汉名转为吐蕃名。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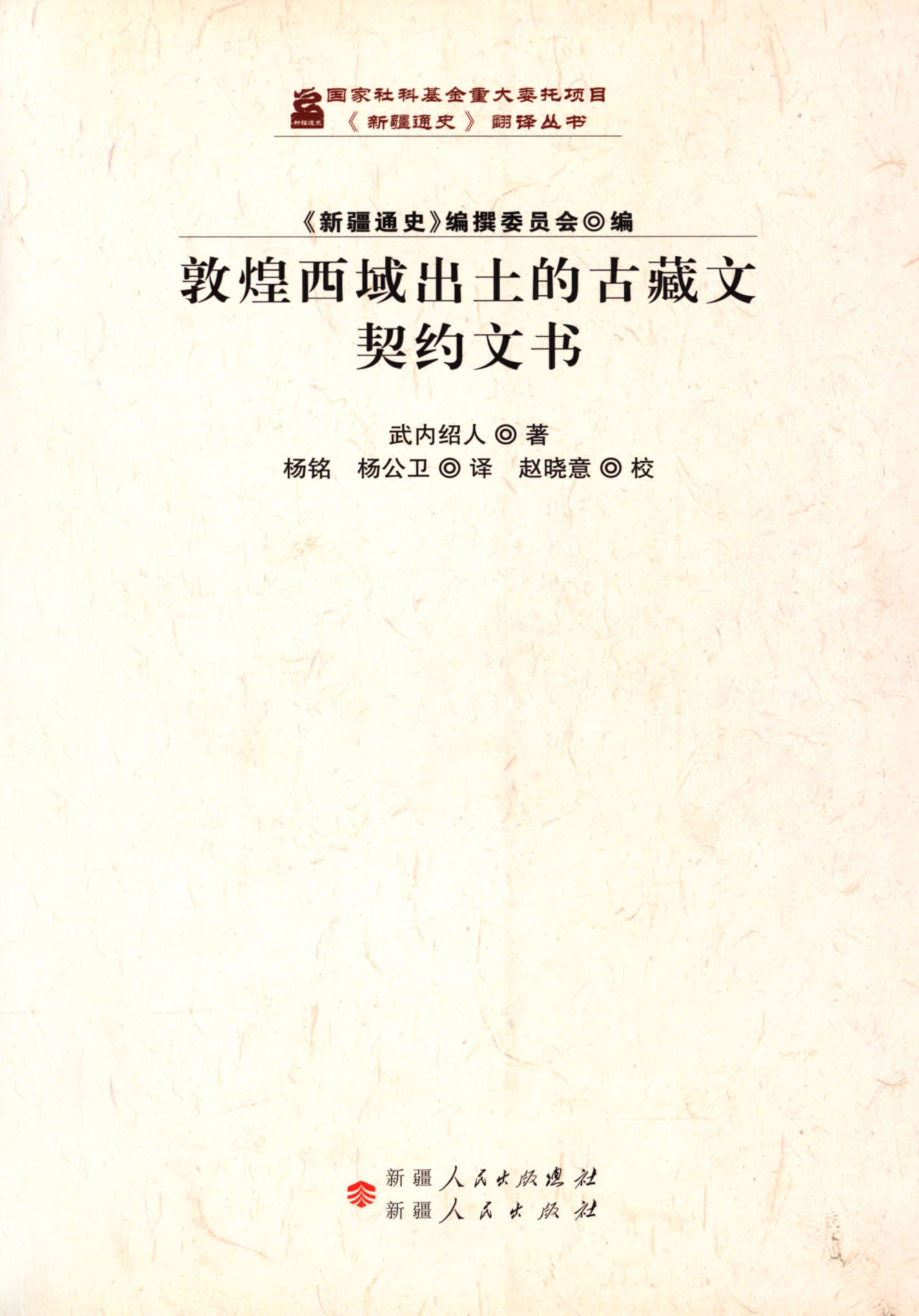
《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约文书》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出版地:2016
本书稿是《新疆通史》辅助项目:翻译丛书之一种。书稿是一部全面汇集敦煌、新疆出土的古藏文契约文书,并加以细致转写和考释的著作。对于全面认识吐蕃统治丝绸之路,尤其是西域地区各民族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状况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书稿译者杨明,长期从事敦煌、西域出土的古代吐蕃文书的解读与研究工作,在吐蕃文献的研究方面造诣深厚。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