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口述:杜文慧□访录:李丹莉张竹新整理:王丽①
一天,编辑部接到一个电话,明亮清脆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我看到了你们的征稿函,我想咨询你们要求从哪些方面写?”我们一下子兴奋起来,因为这是我们访谈中遇到的第一位女科学家。几经交流,她说开始动笔了。两周后,电话又来了,她说已经写好了,马上要去海南过冬,走之前配合我们作现场访谈。我们赶紧带上相关资料匆匆赶往她家采访。一进门,看见一位优雅端庄的老太太站在我们面前,她把照片和资料摆在餐桌上,言谈中透着高贵的气息,我们一边看照片,一边聆听当年奋斗在新疆医疗战线上的那些人、那些事……
1935—1945年,是中国的多事之秋,我也因此几度濒临失学的边缘,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自我国东北扩大入侵版图,危及华北乃至全中国。1941年12月又偷袭珍珠港。在天津,日本侵略军进入英租界,学校门口都驻扎了日本兵,进校门还得给他们行礼,往日校园中欢娱快乐的气氛消失殆尽。课程中消减了英语课,增加了日语课,音乐课改唱日语歌,一些原有的课余活动如歌咏、文体等活动减少或取消了,经常“勤劳奉仕”(即为日本侵略军的需要停课出去劳动)。所以在日本占领期间学生的资质,比以前的高中毕业生有所下降。在校期间,令我终生难忘的是爱国志士——我们的校长赵君达先生被日寇暗杀的事件。在纪念他的庄严肃穆的追悼会上,全体师生莫不失声痛哭。赵校长的刚正不阿、忠于祖国、不屈服于日寇淫威的爱国主义精神,深深地触动了我们幼小的心灵,对媚日求荣的汉奸深恶痛绝,那时的我不满12岁。
1945年,我考入了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在开学前日本已经投降了。从广播里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时莫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并热烈欢迎国军归来。没想到的是我们成了“伪学生”,还需甄审,接着1946年北京又发生了“沈崇事件”。目睹所谓国军的倒行逆施,物价飞涨,国民党政府又印金圆券搜刮民财。我们的老师带来的盒饭里装的是玉米面窝头,那时我虽幼稚但有正义感,是地下党员的同学引领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48年秋去了解放区,学习了我党的城市政策,为解放天津做准备。解放天津的战争打得非常艰苦,当我们行军进驻天津时,入城的路上不止一次听到地雷爆炸声,大家马上趴在地上,感觉土及碎石块落下来,知道自己没死,就站起来继续前进。经常见拉着解放军尸体的马车迎面而来,在城内马路上国民党伤员也随处可见,我感到战争太残酷了,体会到解放战争的胜利来之不易,此时已经开始考虑今后我怎样工作才能对得起这些牺牲的战士。入城后,我们被分配在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卫生接管处工作,时间不长,卫生部又统一安排这批同学继续回校学习,那时我已离开学校半年(1948年10月至1949年4月)。
1951年,我在北大医学院学习了6年终于毕业了(当时是6年制),那时是毕业大学生全国统一分配的第一年。当时分配的原则是党员要吃苦在先,30%的党团员分配去边远地区,70%的群众留在天津地区。我和同班同学共4名,其中党员2名,团员1名,群众1名被分配到新疆,翻开了新生活的一页。
1951年,国家卫生部在北京召开了少数民族卫生工作会议,作为将去新疆工作的医学毕业生,我们参加了此次会议。会后,在卫生部人事部门负责同志的介绍中,我们了解到当时新疆只有16名医生,但无一人毕业于正式的医学院,中央对我们将去新疆参加医疗卫生工作的4名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生寄予厚望。数日后,我们准备了很多生活用品,如肥皂、牙膏、草纸等,做了充分吃苦的思想准备,和卫生防疫大队人员一起跟随当时新疆的人事干部何世禄同志、新疆莎车县卫生科长伊沙克江同志,奔赴西北边城——迪化市(乌鲁木齐市)。伊沙克江同志是我见到的第一个维吾尔族同志,途中每到一站我们这些年轻人不是聊天就是逛街,而他总在进行翻译工作(汉语译维吾尔语),他的勤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自西安开始转乘敞篷汽车,途经天水、兰州、武威、张掖、酒泉、星星峡、哈密、吐鲁番等地,历时22天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迪化市。当时的迪化只有8万人口,仅有的一条柏油马路就是现在的解放路,记得当时空气清新,马路上的积雪白得耀眼,马路两旁都有树和小渠沟,马路上跑着“六根棍”马车,这就是西北边陲重镇迪化市给我的第一印象。除了“盛督办衙门”和人民银行是两层的楼房外,其他都是平房,只有市中心区有些商店门面似二层楼房,但一刮风,窗子被吹开,就看到天了,原来只有门面墙修了窗户,好像二楼一样。记得在一次会议上,饶正锡市长的讲话中提到:今后一定要把这些“布景式”的房子一律变成楼房,当时市长雷厉风行,一年左右这样的房子基本都加上了一层。
当日,省医院食堂的张师傅驾着“六根棍”把我们连人带行李接到新疆省医院一部(即解放前省立第一医院,俗称北门医院),我们开始正式工作了。当时的省医院内、儿科还不分,如果儿科患者需要住院,也住在内科病房里。1951年秋季,儿科有了独立的病房,当时医院小儿科才成为门诊、病房都有的科室,病房安置在一个大庙内,大庙中间为办公室,两旁摆放病床各3张。那时没有自来水,吃水靠车拉,护士除了医疗护理外,还要挑水,非常辛苦。由于人民群众的需要和医院领导的支持,两年间儿科病床就发展到30张,病房也搬入人民医院大门右侧的小土楼内。这时医生也有了3名:裴元龙、王获和我。裴大夫固定在门诊,我和王获医生在病房。当时结核病人非常多,病人最多时,儿科病房30张床,结核性脑膜炎的患者竟占了18位。当时的检验科只做血、尿、便三大常规,脑脊液常规尚未开展。一次遇到一名怀疑脑膜炎的病儿需要做腰穿,全院却找不到一个腰穿针,只得赶紧到当时的“官药房”(医药公司)买到一支BD腰穿针(美国进口),这说明不是没有相关的工具,而是无“人”使用。那时的抗痨药物仅有链霉素、PAS,由于上述药物不能通过血脑屏障,初来的患儿天天都需要做腰穿,鞘内注射链霉素。而且当时链霉素都是双氢链霉素,对耳蜗神经毒性大,所以那时的听力障碍后遗症非常多见,我对此印象异常深刻。1954年开始有了可以通过血脑屏障的药物异烟肼,停止了鞘注链霉素的治疗。到了50年代后期,开始合理应用激素辅助治疗结核性脑膜炎,疗效明显提高。我们在长期的工作中探索出结核性脑膜炎的临床分期和激素使用的最佳剂量,及时抢救、治疗,使结核性脑膜炎愈后情况大为改观,甚至在基层因不规范治疗而出现后遗症的患儿转入我院治疗后都能完全康复。
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我院相应地改为自治区人民医院。1956年,自治区人民医院迁入新院址,即位于乌鲁木齐市山西巷的原省立第二医院,在该院旧址上盖了600张床位的自治区医院。小儿科床位又逐渐扩展为60张、80张、100张,成为乌鲁木齐市最大的儿科。1958年冬季最忙时,床位扩张至140张(曾借用了妇产科一个病组的病房)。
在新疆医学院第一批大学毕业生(1961年)来院前,我院儿科医生主要来自省外大学,当时有重庆、成都、沈阳、哈尔滨等地毕业的医生,真是五湖四海,而且有很多男医生。那时可谓儿科临床的鼎盛时期。儿科工作以临床管理严格、学术气氛浓厚著称于乌鲁木齐市,科室长期坚持对进修和实习医生进行教学查房及讲课,临床实习严格要求,使学生在实习期就养成努力认真的工作态度,对病人负责的医疗风范。在儿科医生中实行24小时负责制、总住院师制,使年轻医生得到正规的培养,不仅增强了责任心,而且也锻炼了他们处理问题的能力。
20世纪60年代,自治区人民政府还没有监护仪器,但在自治区儿科,对患儿的抢救工作已形成制度化,制定了一系列抢救常规制度,凡小儿危重患者均有专职医护小组守护,科主任也经常参加守护直至病人转危为安,当时还积极引进和采用先进的抢救理念和方法,使中毒性痢疾等感染性休克的死亡率大幅度下降,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要求儿科医生对危重患儿要守护在床前,便于及时发现患儿病情变化,做好预测,使险情在第一时间就能得到预防和处理。我记得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抢救一个叫毛毛的孩子——一个中毒性痢疾患儿。我和医护人员轮班,几乎24小时守候在患者身边,给毛毛降温、止惊,5分钟量一次血压,记录毛毛的排尿量,测尿量比重,仔细观察毛毛的生命体征,了解微小变化情况,直到毛毛病情完全稳定后,大家才松了一口气。毛毛的家长说了很多感谢的话,但我认为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因为面对一个生命的时候你的责任使你必须那么去做。毛毛出院后,他的家长写了一篇文章,详细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当年的《新疆日报》用一个版面全文予以刊登,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一切从病人的利益出发,不计个人得失的工作作风一直延续到现在。那时还成立了医疗差错监督小组。在实践中制订了医生工作40条,加强了对医生的常规临床监督工作,此制度后来被医院推广到内科。由于浓厚的学术氛围和良好的医德医风,儿科培养了众多德才兼备的医生,加之严格的管理,儿科工作在各个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儿科曾被评为自治区“三八红旗集体”。
“文化大革命”期间,儿科正常的工作曾一度受到影响。“文革”结束后,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逐渐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秩序。在院领导的支持下,给儿科添置了当时乌鲁木齐儿科的先进设备——新生儿血压监护仪、心电图呼吸监护仪等。同时儿科恢复了进行大便培养及痰涂片,由医生亲自观察细菌变化的结果,作为选用抗生素治疗腹泻的初步参考。儿科在当时虽无名义上的实验室,但已开展了很多检验科尚未开展的部分血液及免疫学试验。由于对检验工作的重视,提高了医生诊治水平,也孕育了儿科研究所的诞生。
进入七八十年代,由于计划生育工作的落实和儿童保健工作的加强,儿科病人比以前大大减少了,儿科的病种也改变了。传染性、细菌感染性疾病减少了,慢性病增多了。结合儿科的临床实际培养人才,在原有的呼吸及血液专病基础上,儿科又相继开展了小儿肾脏、小儿神经、儿童心理、小儿内分泌等专业。在乌鲁木齐市儿科率先开展了肾脏穿刺,明确了病理诊断,使病人得到合理治疗。小儿神经医生均经专业培训,技术全面。儿童心理门诊是乌鲁木齐市唯一的诊断治疗儿童行为异常的专病门诊,解决了很多既常见又疑难的问题。
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结核性脑膜炎的治疗有了新的进展。“结脑”临床病程一般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根据“结脑”病理变化的临床病情进展及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提出在病程的中、晚期之间应设中偏晚期分期。我觉得这一病程属于抢救期,如抢救及时,病人可治愈,如错过这个抢救时期,病人即会陷于昏迷,不仅增加了治疗难度,也易导致患儿死亡,即便治愈也往往留有后遗症。通过对大量临床治疗事例进行总结、对比,发现教科书里记载的有关治疗“结脑”的激素使用剂量偏小,为此我们撰写了与此有关的论文,在第七届全国教科书会议呼吸专业会上宣读,受到儿科学术界的重视。《实用儿科学》再版时,治疗“结脑”的激素使用剂量做了相应修改。激素治疗剂量的调整,明显地提高了“结脑”的治愈率,降低了它的后遗症率和死亡率。
1981年开始进行临床病毒学研究,在深入研究巨细胞病毒感染的过程中,国产医学有关TORCH感染的研究,是临床研究的前沿课题。1984年自儿科孕育产生儿科研究室,1986年在院领导的支持下筹建了新疆第一个自治区儿科研究所,1988年又申请并中标卫生部科研基金资助课题。终于完成了TORCH感染对围产母婴影响的综合研究,写出了《乌鲁木齐地区TORCH各感染因素的流行病学的调查及对围产母婴危害》的研究报告,共发表相关文章10篇,这个科研项目是国内最早完成的TORCH感染自流行病学以及母婴传播的研究项目。研究所成立15年来,独自承担科研课题共6项,其中卫生部科研课题1项,卫生部委托卫生厅科研课题3项,协作课题6项,与院内协作课题4项,自选题10项。研究所长期与预防医学院及中国医科院协作,因此在国内享有一定的知名度。并先后获得自治区和卫生部的科研经费支持各1项。在此过程中,除了儿科研究所全体同志辛勤劳动外,和我们协作的产科、儿科都做了大量工作。获自治区二等奖的2个科研课题都是在自选课题的基础上逐渐深入研究而取得的成果。我们还协助医院其他科室如神经科、心脏内科进行了课题研究,获得了自治区科技成果奖。
多年来,儿科鼓励医护人员努力钻研业务,重视临床实践和理论研究,大力培养人才。儿科一共考取了11个硕士研究生,2个博士生,6个出国研修生,并为全院培养、输送了数名护士长。
目前儿科已发展为104张床位,86名医护人员,儿研所有5名科研人员。
我相信,在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的医院党委领导的支持和指导下,在儿科全体临床及科研人员的努力下,儿科及儿科研究所将会迎来更加辉煌的明天。
一天,编辑部接到一个电话,明亮清脆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我看到了你们的征稿函,我想咨询你们要求从哪些方面写?”我们一下子兴奋起来,因为这是我们访谈中遇到的第一位女科学家。几经交流,她说开始动笔了。两周后,电话又来了,她说已经写好了,马上要去海南过冬,走之前配合我们作现场访谈。我们赶紧带上相关资料匆匆赶往她家采访。一进门,看见一位优雅端庄的老太太站在我们面前,她把照片和资料摆在餐桌上,言谈中透着高贵的气息,我们一边看照片,一边聆听当年奋斗在新疆医疗战线上的那些人、那些事……
1935—1945年,是中国的多事之秋,我也因此几度濒临失学的边缘,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自我国东北扩大入侵版图,危及华北乃至全中国。1941年12月又偷袭珍珠港。在天津,日本侵略军进入英租界,学校门口都驻扎了日本兵,进校门还得给他们行礼,往日校园中欢娱快乐的气氛消失殆尽。课程中消减了英语课,增加了日语课,音乐课改唱日语歌,一些原有的课余活动如歌咏、文体等活动减少或取消了,经常“勤劳奉仕”(即为日本侵略军的需要停课出去劳动)。所以在日本占领期间学生的资质,比以前的高中毕业生有所下降。在校期间,令我终生难忘的是爱国志士——我们的校长赵君达先生被日寇暗杀的事件。在纪念他的庄严肃穆的追悼会上,全体师生莫不失声痛哭。赵校长的刚正不阿、忠于祖国、不屈服于日寇淫威的爱国主义精神,深深地触动了我们幼小的心灵,对媚日求荣的汉奸深恶痛绝,那时的我不满12岁。
1945年,我考入了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在开学前日本已经投降了。从广播里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时莫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并热烈欢迎国军归来。没想到的是我们成了“伪学生”,还需甄审,接着1946年北京又发生了“沈崇事件”。目睹所谓国军的倒行逆施,物价飞涨,国民党政府又印金圆券搜刮民财。我们的老师带来的盒饭里装的是玉米面窝头,那时我虽幼稚但有正义感,是地下党员的同学引领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48年秋去了解放区,学习了我党的城市政策,为解放天津做准备。解放天津的战争打得非常艰苦,当我们行军进驻天津时,入城的路上不止一次听到地雷爆炸声,大家马上趴在地上,感觉土及碎石块落下来,知道自己没死,就站起来继续前进。经常见拉着解放军尸体的马车迎面而来,在城内马路上国民党伤员也随处可见,我感到战争太残酷了,体会到解放战争的胜利来之不易,此时已经开始考虑今后我怎样工作才能对得起这些牺牲的战士。入城后,我们被分配在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卫生接管处工作,时间不长,卫生部又统一安排这批同学继续回校学习,那时我已离开学校半年(1948年10月至1949年4月)。
1951年,我在北大医学院学习了6年终于毕业了(当时是6年制),那时是毕业大学生全国统一分配的第一年。当时分配的原则是党员要吃苦在先,30%的党团员分配去边远地区,70%的群众留在天津地区。我和同班同学共4名,其中党员2名,团员1名,群众1名被分配到新疆,翻开了新生活的一页。
1951年,国家卫生部在北京召开了少数民族卫生工作会议,作为将去新疆工作的医学毕业生,我们参加了此次会议。会后,在卫生部人事部门负责同志的介绍中,我们了解到当时新疆只有16名医生,但无一人毕业于正式的医学院,中央对我们将去新疆参加医疗卫生工作的4名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生寄予厚望。数日后,我们准备了很多生活用品,如肥皂、牙膏、草纸等,做了充分吃苦的思想准备,和卫生防疫大队人员一起跟随当时新疆的人事干部何世禄同志、新疆莎车县卫生科长伊沙克江同志,奔赴西北边城——迪化市(乌鲁木齐市)。伊沙克江同志是我见到的第一个维吾尔族同志,途中每到一站我们这些年轻人不是聊天就是逛街,而他总在进行翻译工作(汉语译维吾尔语),他的勤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自西安开始转乘敞篷汽车,途经天水、兰州、武威、张掖、酒泉、星星峡、哈密、吐鲁番等地,历时22天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迪化市。当时的迪化只有8万人口,仅有的一条柏油马路就是现在的解放路,记得当时空气清新,马路上的积雪白得耀眼,马路两旁都有树和小渠沟,马路上跑着“六根棍”马车,这就是西北边陲重镇迪化市给我的第一印象。除了“盛督办衙门”和人民银行是两层的楼房外,其他都是平房,只有市中心区有些商店门面似二层楼房,但一刮风,窗子被吹开,就看到天了,原来只有门面墙修了窗户,好像二楼一样。记得在一次会议上,饶正锡市长的讲话中提到:今后一定要把这些“布景式”的房子一律变成楼房,当时市长雷厉风行,一年左右这样的房子基本都加上了一层。
当日,省医院食堂的张师傅驾着“六根棍”把我们连人带行李接到新疆省医院一部(即解放前省立第一医院,俗称北门医院),我们开始正式工作了。当时的省医院内、儿科还不分,如果儿科患者需要住院,也住在内科病房里。1951年秋季,儿科有了独立的病房,当时医院小儿科才成为门诊、病房都有的科室,病房安置在一个大庙内,大庙中间为办公室,两旁摆放病床各3张。那时没有自来水,吃水靠车拉,护士除了医疗护理外,还要挑水,非常辛苦。由于人民群众的需要和医院领导的支持,两年间儿科病床就发展到30张,病房也搬入人民医院大门右侧的小土楼内。这时医生也有了3名:裴元龙、王获和我。裴大夫固定在门诊,我和王获医生在病房。当时结核病人非常多,病人最多时,儿科病房30张床,结核性脑膜炎的患者竟占了18位。当时的检验科只做血、尿、便三大常规,脑脊液常规尚未开展。一次遇到一名怀疑脑膜炎的病儿需要做腰穿,全院却找不到一个腰穿针,只得赶紧到当时的“官药房”(医药公司)买到一支BD腰穿针(美国进口),这说明不是没有相关的工具,而是无“人”使用。那时的抗痨药物仅有链霉素、PAS,由于上述药物不能通过血脑屏障,初来的患儿天天都需要做腰穿,鞘内注射链霉素。而且当时链霉素都是双氢链霉素,对耳蜗神经毒性大,所以那时的听力障碍后遗症非常多见,我对此印象异常深刻。1954年开始有了可以通过血脑屏障的药物异烟肼,停止了鞘注链霉素的治疗。到了50年代后期,开始合理应用激素辅助治疗结核性脑膜炎,疗效明显提高。我们在长期的工作中探索出结核性脑膜炎的临床分期和激素使用的最佳剂量,及时抢救、治疗,使结核性脑膜炎愈后情况大为改观,甚至在基层因不规范治疗而出现后遗症的患儿转入我院治疗后都能完全康复。
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我院相应地改为自治区人民医院。1956年,自治区人民医院迁入新院址,即位于乌鲁木齐市山西巷的原省立第二医院,在该院旧址上盖了600张床位的自治区医院。小儿科床位又逐渐扩展为60张、80张、100张,成为乌鲁木齐市最大的儿科。1958年冬季最忙时,床位扩张至140张(曾借用了妇产科一个病组的病房)。
在新疆医学院第一批大学毕业生(1961年)来院前,我院儿科医生主要来自省外大学,当时有重庆、成都、沈阳、哈尔滨等地毕业的医生,真是五湖四海,而且有很多男医生。那时可谓儿科临床的鼎盛时期。儿科工作以临床管理严格、学术气氛浓厚著称于乌鲁木齐市,科室长期坚持对进修和实习医生进行教学查房及讲课,临床实习严格要求,使学生在实习期就养成努力认真的工作态度,对病人负责的医疗风范。在儿科医生中实行24小时负责制、总住院师制,使年轻医生得到正规的培养,不仅增强了责任心,而且也锻炼了他们处理问题的能力。
20世纪60年代,自治区人民政府还没有监护仪器,但在自治区儿科,对患儿的抢救工作已形成制度化,制定了一系列抢救常规制度,凡小儿危重患者均有专职医护小组守护,科主任也经常参加守护直至病人转危为安,当时还积极引进和采用先进的抢救理念和方法,使中毒性痢疾等感染性休克的死亡率大幅度下降,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要求儿科医生对危重患儿要守护在床前,便于及时发现患儿病情变化,做好预测,使险情在第一时间就能得到预防和处理。我记得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抢救一个叫毛毛的孩子——一个中毒性痢疾患儿。我和医护人员轮班,几乎24小时守候在患者身边,给毛毛降温、止惊,5分钟量一次血压,记录毛毛的排尿量,测尿量比重,仔细观察毛毛的生命体征,了解微小变化情况,直到毛毛病情完全稳定后,大家才松了一口气。毛毛的家长说了很多感谢的话,但我认为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因为面对一个生命的时候你的责任使你必须那么去做。毛毛出院后,他的家长写了一篇文章,详细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当年的《新疆日报》用一个版面全文予以刊登,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一切从病人的利益出发,不计个人得失的工作作风一直延续到现在。那时还成立了医疗差错监督小组。在实践中制订了医生工作40条,加强了对医生的常规临床监督工作,此制度后来被医院推广到内科。由于浓厚的学术氛围和良好的医德医风,儿科培养了众多德才兼备的医生,加之严格的管理,儿科工作在各个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儿科曾被评为自治区“三八红旗集体”。
“文化大革命”期间,儿科正常的工作曾一度受到影响。“文革”结束后,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逐渐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秩序。在院领导的支持下,给儿科添置了当时乌鲁木齐儿科的先进设备——新生儿血压监护仪、心电图呼吸监护仪等。同时儿科恢复了进行大便培养及痰涂片,由医生亲自观察细菌变化的结果,作为选用抗生素治疗腹泻的初步参考。儿科在当时虽无名义上的实验室,但已开展了很多检验科尚未开展的部分血液及免疫学试验。由于对检验工作的重视,提高了医生诊治水平,也孕育了儿科研究所的诞生。
进入七八十年代,由于计划生育工作的落实和儿童保健工作的加强,儿科病人比以前大大减少了,儿科的病种也改变了。传染性、细菌感染性疾病减少了,慢性病增多了。结合儿科的临床实际培养人才,在原有的呼吸及血液专病基础上,儿科又相继开展了小儿肾脏、小儿神经、儿童心理、小儿内分泌等专业。在乌鲁木齐市儿科率先开展了肾脏穿刺,明确了病理诊断,使病人得到合理治疗。小儿神经医生均经专业培训,技术全面。儿童心理门诊是乌鲁木齐市唯一的诊断治疗儿童行为异常的专病门诊,解决了很多既常见又疑难的问题。
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结核性脑膜炎的治疗有了新的进展。“结脑”临床病程一般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根据“结脑”病理变化的临床病情进展及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提出在病程的中、晚期之间应设中偏晚期分期。我觉得这一病程属于抢救期,如抢救及时,病人可治愈,如错过这个抢救时期,病人即会陷于昏迷,不仅增加了治疗难度,也易导致患儿死亡,即便治愈也往往留有后遗症。通过对大量临床治疗事例进行总结、对比,发现教科书里记载的有关治疗“结脑”的激素使用剂量偏小,为此我们撰写了与此有关的论文,在第七届全国教科书会议呼吸专业会上宣读,受到儿科学术界的重视。《实用儿科学》再版时,治疗“结脑”的激素使用剂量做了相应修改。激素治疗剂量的调整,明显地提高了“结脑”的治愈率,降低了它的后遗症率和死亡率。
1981年开始进行临床病毒学研究,在深入研究巨细胞病毒感染的过程中,国产医学有关TORCH感染的研究,是临床研究的前沿课题。1984年自儿科孕育产生儿科研究室,1986年在院领导的支持下筹建了新疆第一个自治区儿科研究所,1988年又申请并中标卫生部科研基金资助课题。终于完成了TORCH感染对围产母婴影响的综合研究,写出了《乌鲁木齐地区TORCH各感染因素的流行病学的调查及对围产母婴危害》的研究报告,共发表相关文章10篇,这个科研项目是国内最早完成的TORCH感染自流行病学以及母婴传播的研究项目。研究所成立15年来,独自承担科研课题共6项,其中卫生部科研课题1项,卫生部委托卫生厅科研课题3项,协作课题6项,与院内协作课题4项,自选题10项。研究所长期与预防医学院及中国医科院协作,因此在国内享有一定的知名度。并先后获得自治区和卫生部的科研经费支持各1项。在此过程中,除了儿科研究所全体同志辛勤劳动外,和我们协作的产科、儿科都做了大量工作。获自治区二等奖的2个科研课题都是在自选课题的基础上逐渐深入研究而取得的成果。我们还协助医院其他科室如神经科、心脏内科进行了课题研究,获得了自治区科技成果奖。
多年来,儿科鼓励医护人员努力钻研业务,重视临床实践和理论研究,大力培养人才。儿科一共考取了11个硕士研究生,2个博士生,6个出国研修生,并为全院培养、输送了数名护士长。
目前儿科已发展为104张床位,86名医护人员,儿研所有5名科研人员。
我相信,在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的医院党委领导的支持和指导下,在儿科全体临床及科研人员的努力下,儿科及儿科研究所将会迎来更加辉煌的明天。
附注
王丽:新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发展与教育心理学2011级研究生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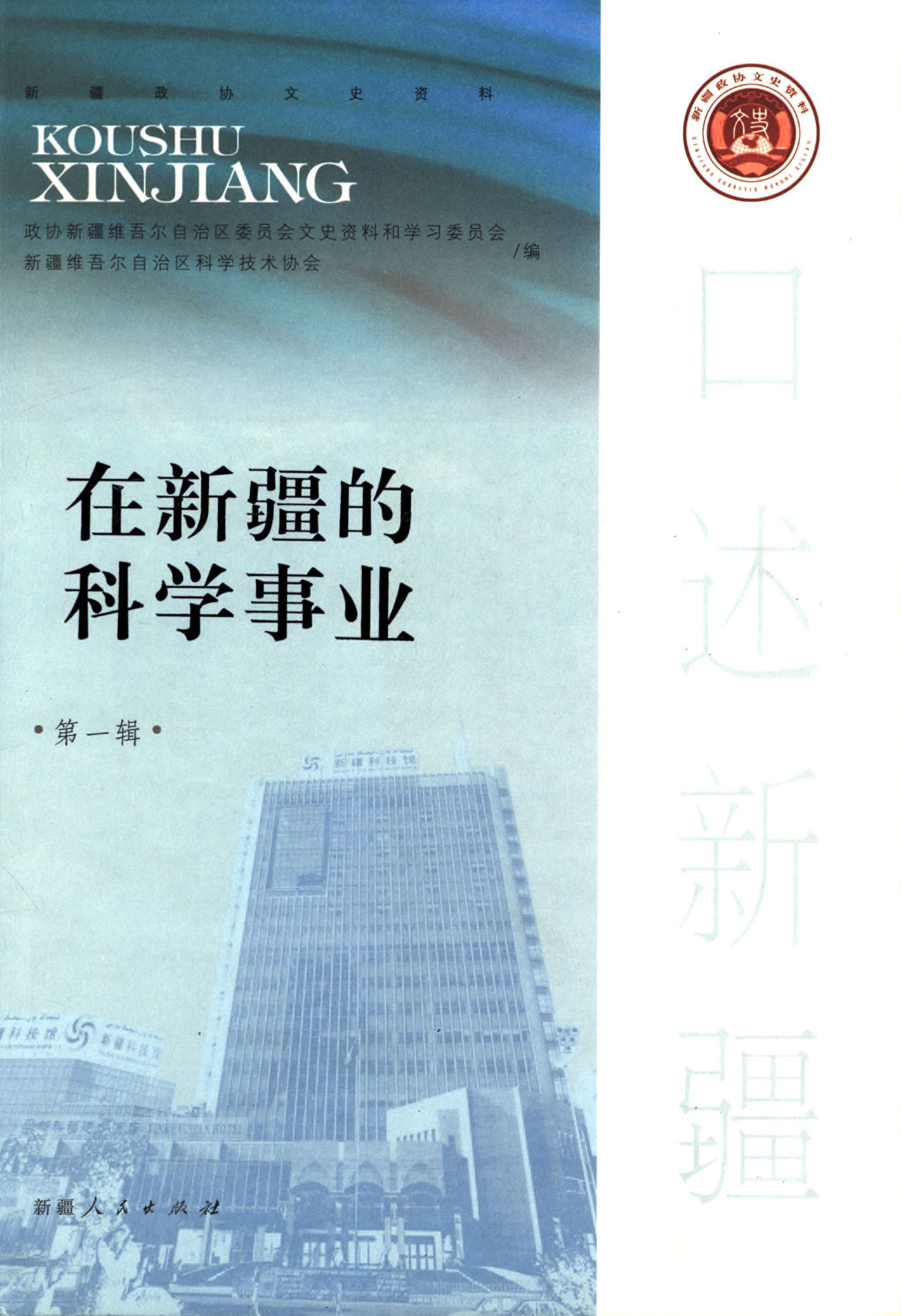
《在新疆的科学事业 第一辑》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出版地:2012
本书主要讲述在新疆工作和生活的多位科学家的奋斗历程和取得的成就,以口述、自述为主,科学家们从不同角度、不同专业,叙述了当年来到新疆、投身新疆科学事业的人生经历。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