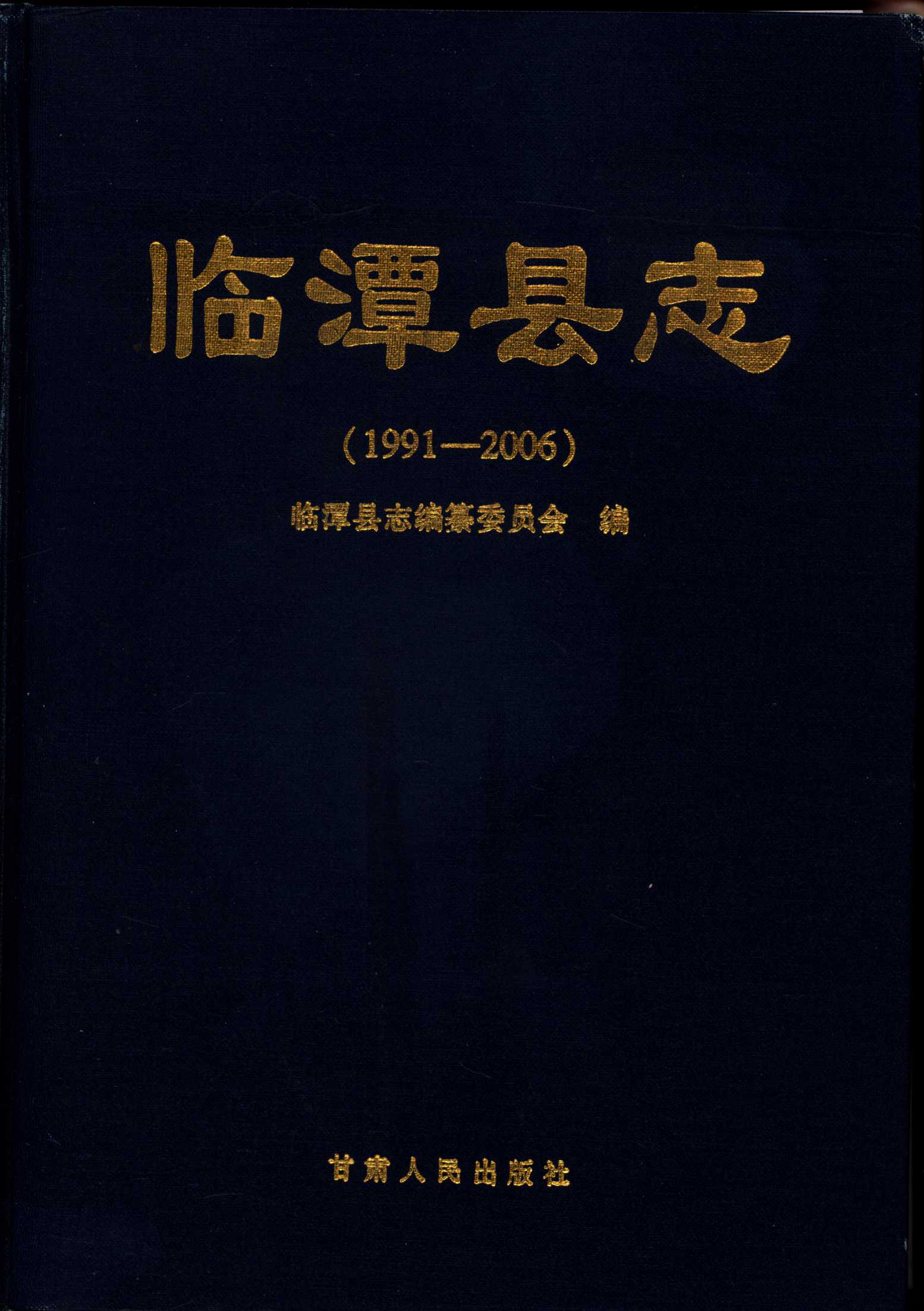第二节 民国时期的洮商
内容
黄叶菜,黄又黄,洮州地方天气凉。三月四月穿皮袄,六月不见庄稼黄。老百姓全靠做生意,耕田务农莫指望。一年到头走番地,十月、六月两会场;张三赶来一群马,李二赶来牛一帮,土拉保驮来十捆皮,麻目沙赶到五百羊,马又大来羊又肥,一天到晚卖了个光。
——李安宅、于式玉《黑错、临潭卓尼一带旅行日记•洮州歌一》清末民国初,由于皮毛交易的兴盛,临潭市场又一次繁盛起来,外地客商云集,本地商人也向外地及全国各大城市扩展。临潭出产的名贵药材麝香、鹿茸、洮马、皮货、木材吸引河南、陕西、四川、临洮、甘谷等地的商人流入,遂将丝绸、棉布、纸张、盐、粮食等商品运人临潭。民国初至民国十八年(1929)在临潭县设立商号的外省客商有京帮、陕帮、豫帮、鄂帮等商帮,外县商号数十家,本地商号数十家,共有资金银元230余万元。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1937年《西北考察日记》中记载:“又论旧城商号,谓兰州、狄道两帮木客每年到此买木材十万元,加运费为二十万元,运至兰州便值五十万元;生皮毛走张家口,以其制皮之术工也;熟羊皮销四川。其他骡马走陕西,猪毛走汉口,羊肠走天津,麝香发河南,药材发陕西,牛售岷县、渭源一带。故旧城商务,东至陕西,更沿江而达津、沪,西赴青海,南抵川、康;北及内外蒙,当民国十七年未破坏前,其繁荣可想也。”
外地商号陕西的“万镒恒”、“恒顺昌”经营百货业;河南的“杜盛兴”、“复生荣”、“永隆全”专门经营药材,收购鹿茸、牛黄、麝香、洮贝等名贵药材;其他的“皋记商行”、“乾元商行”、“强华商行”经营皮毛生意。1917年旧城成立了商会,据统计民国三十年(1941)旧城一地有商业资金银洋647000元,当地资本在3000元以上的商号47家。“万盛西”、“义心公”、“福顺通”、“复有公”、“永泰和”、“天兴隆”、“全盛敏”等商号经营日用百货、贩运牛马、名贵药材等,是当时临潭享有盛名的商业大户,在川、青、藏、汉口等地设有分号商店。新城天成隆等十户商号有资金34500元,只占旧城商业资金的3.8%。此一时期还出现了面行、斗行、秤行、山货行管理市场,收取牙金(中介费)。客栈旅店有集成店、德泰店、义泰行、长胜店、福兴店等,以及名目繁多的饮食业如宏泰馆、元顺馆等。
民国时期的洮商经商形式分为坐商和行商。
坐商,如上述的商号,设商行,开铺面旅店摆摊等。贸易网达西安、北京、张家口、汉口、成都、松潘、西宁、兰州、西康等20个省市,从事商业物资的输入输出。据1941年统计全年输入布匹、粮食、面粉、日用百货39万余银元。1947年仅羊皮输出152000多张、毛褐1000多匹,猪鬃、牛皮等贸易额达银洋300余万元。以西道堂为例:民国十八年(1929)十五个坐商固定、流动资金银洋达到20多万元。截至1949年仅旧城铺面达61间、旅店2处。坐商天兴隆分号遍及四川、青海、陕西、宁夏、甘肃、碌曲拉仁关,岷县、夏河建有贸易集散地。在成都、松潘、兰州、西安、张家口、北京、天津、上海、内蒙古设有商行。在汉口、江西、广州、河南、新疆、西藏等地有商业网点,经营皮张、鹿茸、麝香等物资交易。仅1930-1932年夏河网点与英商普伦洋行三次交易野牲皮张,收入白银达34300余两、银元15390元。
1949年前临潭新旧城著名商号一览表行商,俗称“牛马商贩”,往来于甘、青、川、藏区,将藏区所需物资运入,又将藏区所产物资运出。行商中又有商队和“单马客”(一人一马一枪)之分。商队的形式主要有:
(一)牛马贸易商队。临潭向藏区运进日用百货等,从藏区购买或以物资交换牛、马、羊等牲畜,赶往旧城出售。牛马主要来源于青海玉树、果洛,四川阿坝、若尔盖,甘肃碌曲、玛曲、夏河等地,骡马交易会上的牲畜交易约达5000多头(匹只),据1941年的不完全统计,旧城交易马3000多匹、牛2000多头、羊4000多只,全年总输出牲畜额价值银元330多万元,牛马主要贩往陕西、岷县、西和、礼县等地。
(二)从事皮毛贩运的牛马驮队。清末民初皮毛交易兴盛,外国洋行向西北腹地深入,光绪二十六年(1900)甘南地区的羊毛生意被英商垄断,拉卜楞的“丛拉”(市场)建起了英国普伦洋行,直接收购羊毛,先在甘加、麦西、桑科、欧拉、黑错等地集中,然后统一运到拉卜楞,交洋行验收过秤。“以天兴隆为例,光绪三十年(1904)一月即洋行到河州开设分行的第四年,西道堂教民丁重明捐银一万两,以此为资金,西道堂'天兴隆’商行正式开业……次年12月,丁重明再捐银1000两;在新城建'天兴亨'商号……。临潭地处藏区,西北靠近著名的拉卜楞寺院,南连上下迭部,西达双岔、毛日、西仓,全是以牧业经济为主的藏族聚居区,'天兴隆’商行从事的皮毛收购业中的行商活动范围包括甘肃和青海玉树、果洛海北等……行商队在经理们的带领下到草原腹地收购羊毛,销售藏族生活日用品。民国二十一年(1932)时天兴隆流动资金达银元16万余两……西道堂加强与外省的商业交流,扩充骆驼60峰,派经理马仁山专往归绥、包头等处经商。”(袁纣卫《包头回族皮毛贸易(1879-1945)》载宁夏社科院《回族研究》2007,第三期。)民国二十一年(1932)西道堂行商共计20个商队,计驮牛1700多头、骑马200余匹、流动资金16万余元,贸易来往于内蒙、四川等地。当时洮州著名文人吕芳规《看贩子出口》一诗,形象描绘了皮毛商队的盛况:
番帽番衣番样穿,腰悬利刃背生烟。弩马识途能致远,驮牛负重各争先。笠天席地何辞苦,暑寒夏冬不计年。皮毛满载归来日,猎犬狺狺犹带膻。
(三)盐帮驮队,是从青海驮运食盐的驮牛商队。民国时期临潭旧城有盐帮驮队70多家,驮牛15000多头。年贩运盐约50万公斤。从明中叶开始,以回族为主的洮商就自发组织盐帮到青海省的茶卡盐湖驮盐,到1953年为止持续了400多年。
盐帮的组织形式:盐帮的最高层由2~4名大“郭哇”(藏语意为头人)组成。他们是从全体盐帮成员中民主选举产生的。只在驮盐的路途中起组织领导作用。盐帮的基层组织叫“锅子”,每个“锅子”由6至10人自愿结合而成。他们在驮盐途中住在一起,食在一锅,故名“锅子”。每个“锅子”产生1名领导,叫“尕郭哇”。组成“锅子”的条件是每人都必须有1匹乘马,每个锅子枪不少于1支,凶猛的藏獒不少于2—3只。通常情况下盐帮由20—30“锅子”组成。驮牛最少时约为1万头左右。最多达3万头。供骑的乘马约为200-600匹左右。藏獒100只左右。盐帮们个个体魄健壮,精通藏语,马术娴熟,枪法精良。驮牛均为强壮的犏牛。这一时期最大的盐帮当为西道堂驮队和以苏温西为大郭哇的驮队。
盐帮的驮运时间和路线:盐帮驮盐的时间一年两次,每年的6月初,上一年的“大郭哇”,在旧城召集各“锅子”的“尕郭哇”开会,商讨驮盐的启程日期和路线,开始启程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夏季:从夏历的六月十五启程到八月底返回。路线是旧城→沙冒→多花儿→博拉扎沙→桑科保安西面的那哈差纳哈→贵德浮桥→红柳沟→上嫄台→青海湖→茶卡盐湖。返回路线仍按原路返回。
冬季:盐帮从夏历的十月初出发到次年的正月十五返回。路线是:旧城→斜藏沟→沙冒→博拉寺院→阿木去乎寺院→达采寺院→科采寺院→胡儿地苍→漏苍→塔尔秀贡巴→东加达苍→个儿马阳群(从此处过黄河冰桥)→阿苏乎云→尕务路小寺院→青海湖→茶卡盐湖。返回时仍按原路返洮。
盐帮的行军、宿营方式和路途纪律:在“郭哇”庄严下达起程的命令后,牛群徐徐起身,驮队逶迤长达30-40华里,这支队伍不为战争行军,却似远征将士,英勇威武地肃然前进。
一天后,驮队离开旧城,进入草原地带,宿营后,由上一任大“郭哇”组织召开全体盐客会议,民主选举本次途程中的新“郭哇”,这些新选的大、小“郭哇”再详细地编排各“锅子”行走的次序,大家依然绝对地服从这些新“郭哇”的领导。
行进的盐客每天在黎明时分就生火熬茶,只喝少量的“豆码”(藏语意为稀糌耙,因为驮驮子时吃的过饱会有损身体健康)。然后每两人为一组,快速利落地驮好30-40头牛的盐驮子,在“郭哇”下达动身的命令后,徐徐启行。每天的行进序列都按“蛇落皮”的方式排列,即头天排在第一位的“锅子”在第二天是最后动身,头天排在第二位的“锅子”在当天变为先行,在行进中,每“锅子”抽1-2名枪法好、骑术精的人组成盐帮的“前卫”和“后卫”。当行至险要地段时,“前卫”即策马占据有利地形,直到驮队全部通过,才将阵地交给后卫殿后。大约走50—60华里路,到达预定的宿营地时,将近中午先拴好藏獒,以防咬伤行人。然后两人一组,快速卸下盐驮,让牛去自由觅食吃草,这时盐客们才生火做饭,饭后再将盐袋每六只为一垛码放起来,在其三面扯起“档绳”准备晚上拴牛。宿营地点,均选在开阔地带,从不在山根崖坎下宿营,以防晚上盗贼从高处滚石头惊乱牛群。
宿营时各个“锅子”的马匹、帐篷、驮牛、盐垛和藏獒都按下图位置排列,不得紊乱。而整个盐帮的宿营地是一支军旅的圆形大营盘,每个“锅子”的帐篷门一致背离圆心向外,形成一个大圆,叫做“场子”。
休息时,烧红烙铁,将牛背压伤的肿块烙治消肿。盐队每走四五天要大休息一天,这一天就是盐客们的节日,有的人比赛枪法,他们大多数人枪法百发百中;有的人抱盐袋比赛力量,要求双腿盘起来坐在地上,再怀抱盐袋站立起来;有些人则去探望附近的蒙、藏朋友,拿的礼物有哈达、布匹、红枣、核桃、柿饼、油炸果等,朋友家除盛情款待外,临走还送酥油、曲拉、活羊、蕨麻、醍等东西给盐客们;大“郭哇”们则去拜访当地的头人、活佛,拉关系搞交易。
临近黄昏,全部要返回宿营地,晚饭前把牛拴到“档绳”上,马一律套上“铁绊”,拴在帐篷的前两侧,藏獒全部放开,盐客们围坐在篝火旁,一面品尝着酥油茶,一面讲故事,说笑话,有的还放开喉咙唱起了家乡的“花儿”。而大小的“郭哇”们每天晚饭前要在“场子”中央召开一次例行会议,讨论第二天的行进路线、宿营地点,研究决定在第二天可能经过的地方,给头人、土官或寺院送礼的具体事宜,处理当天盐客中违犯盐帮纪律的事。会议结束后,小“郭哇”们回到各自的帐篷传达会议内容,指派晚上前后夜的岗哨后,各自安歇。而大“郭哇”们还不定期地检査值勤放哨的情况,如有人在守夜放哨时睡觉,属于严重失职,必须罚牛一头。由于盐帮有严明的纪律,加之队伍庞大,枪械快利,内部团结,所以很少发生意外事件。
在路途中,盐帮有相当严明的纪律,如经过村庄和寺院时,不得打马狂奔,不得和其他兄弟民族寻衅闹事,骑在马上不能打瞌睡,不允许马缰绳掉落在地,服装穿戴不齐整要批评,睡姿和坐姿都有规定,如坐下时臀部落在盘起的双脚上不能落在地面上(这种坐姿能快速起立),睡姿呈“弓形”,绝不允许四仰八叉的大睡。如有违犯上述纪律者,处以一定的罚金(一头牛、一只羊或五块银元),由于有严明的纪律,所以所到之处和各族群众关系相当融洽,出现了盐帮到时“全家喜迎,去时洒泪而别”的感人场面,盐客们个个都能自觉遵守纪律,极少有违犯者。
驮盐的经济效益
每年夏历的六月初。洮州地区的农作物全部耕种完毕。大量的耕畜需要草料,仅靠当地的产草量是无法解决的,一年两次的驮盐,使耕畜在外的时间长达7个月之久,几乎全年一半以上的草料在驮盐的路途中解决了,去时沿草原地带行进,到达茶卡湖边时牛马已膘肥体壮。这样安排时间既不耽误农活,又能使耕畜身体得到恢复,是很科学的。
另外,洮州气候寒冷,农业收入微薄,驮盐可以增加经济收入。据老盐客们回忆,在清末民初时期,用帽缨子、粗织布等物从湖边蒙古族群众处换取食盐,用一顶帽缨子可以换一驮盐(200市斤左右)。在1931-1941年间,茶卡湖由马步芳的“厘金局”管理,每驮盐交“厘金”2块银元,只数驮子,不过秤。从1941年到解放初,开始过秤计值,每100市斤盐付给厘金局8—12元的国民政府纸币。驮到洮州旧城,扣除各项费用,每驮盐(200市斤)纯利约30块银元。
这样,洮州盐帮无形中使旧城变成了一个很大的食盐集散地,每年运到的盐至少在100万斤以上,这些盐除满足洮州附近数县群众的需求外,还有相当数量的盐由“脚户骡子”客和舟曲、文县、礼县一带的“背子手”们再贩运到岷县、宕昌、武都、礼县、舟曲、文县等,有些还运到陕西等地,上述客商又从四川运回布匹、线、竹器、颜料,从武都运回铧,从陕西运回了“杠铃”(老牛车所用的铁铃或系在牛项的铁铃)、马镫等,既丰富了洮州市场的货物品种,满足了当地各族群众对生产、生活必需品的需求, 也促进了洮州旧城市场的大发展。
盐帮生活艰苦,旅途艰辛。驮盐一趟往返需要3个多月,而且旅途时常有不测的事件发生,劳累、疾病、贼盗伴随着他们。冬天,从黄河岸边到茶卡湖的路程基本上是沙磧地带,人畜逆风而行,牛、马踏起的滚滚沙尘,似黄龙舞动,晚上风停以后才能生火做饭。每天驮卸百来斤的盐袋60余袋,衣服前胸全被擦破,一趟盐驮回来胸部肌肉结了老茧。更苦的是从湖水里捞盐,双腿浸泡在冰冷咸涩的湖中,双腿、手、脚都要脱一层皮。不少盐客的生命就抛却在这条漫长的不归之路上。因此盐帮们在动身之前,亲朋好友们会前来送行,纷纷送上“干粮”(点心、各类糖果、柿饼、红枣、核桃等)。各家盐客都请阿訇念《古兰经》,祈求真主的襄助。在动身的当天清晨,整个洮州旧城是倾城沸腾,场面十分壮观。盐客们身着藏服,跨马背枪、精神抖擞地用藏语吆喝牛群,藏獒们欢欣跳跃,在驮队的两侧奔跑追逐,护卫着这支浩浩荡荡的大军远行,送行的场面显得庄严热闹。盐帮驮队回来时又全城出动,亲戚、朋友、邻居前往迎接探望。
盐帮驮牛队轶事
1.盐帮的忠实卫士——藏獒
藏獒是出产在四川和甘南草原地区的一种猛犬,身躯高大,耐寒灵敏,当盐客们在茫茫草原上行走,沉沉黑夜中宿营时藏獒都能忠实地履行护卫任务,和盐客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民国二十九年(1940)的夏天,盐帮离开茶卡盐湖在红柳沟宿营时,有盗贼乘黑来劫,被藏獒发觉,近百只藏獒群起进攻,贼人仓皇逃窜,其中一人未来及上马,被藏獒穷追不舍,他急中生智爬到一棵大树上,藏獒将树围了一夜,直到第二天盐客发现,驱散藏獒,那贼才从树上溜下来,但已被吓得半死。
2.盐帮的扶困济危精神
事情发生在民国二十九年(1940),四川松潘舍儿哇地区的藏民,从茶卡湖往西宁驮盐返回的途中,200多头牛、20余匹马,被一伙盗贼抢劫。哭诉到洮州盐帮的苏温西大“郭哇”处,苏立即下达了追击贼盗的命令,盐客一天的强行军,追上了被盗牛群。起初,这些贼人不肯退赃,盐帮中的神枪手骑在马上把贼匪远处几头驮牛项下的铃铛弹无虚发地击落,贼匪受到震慑,原数退还所劫东西,这些“舍儿哇”藏民赶着3头肥牛前来答谢,盐帮均未接受,他们流着感激的泪水离去,并和盐帮结成了 “主人家” (朋友)。
3.盐帮的技能为马步芳所钦佩
有一年马步芳会同青海湖周边的蒙藏王公、头人、活佛,在青海湖边“祭海”,恰逢洮州的盐帮路过该地,马步芳派人传话给盐帮:“听说你们洮州人驮牛跟的好,我想看一下。”经大小“郭哇”们商量后,给马步芳送了2包大茶、六桶蜂蜜(2市斤/桶),接下来表演驮驮子、支帐篷、生火做饭等,马步芳评价:“驮盐确实很苦,你们洮州人驮牛跟的好,纪律好,牛马的装备齐整。”并赏给盐帮3000驮盐(约60万斤)、炒面2000斤,猎获的黄羊6只,将盐帮送的蜂蜜转赠给在场的头人、王公、活佛,并嘱咐道:“这些洮州的盐客很苦,以后请你们多照看的哈。”
(四)“单马客”,是在抗战及其后的解放战争时期,由于藏区大量种植罂粟(鸦片),旧城成为鸦片集散地之后大量产生的。他们一人一枪一马,从迭部等藏区往返倒运鸦片。其中亦有大批“单马客”是从藏区往来贩卖日用品和羊毛皮张的。
(五)在清末民国初至民国中期,临潭洮商中还兴起了做马鸡翎子的生意,每百根蓝马鸡翎售价银洋30元,销往北京作满清官员官帽饰品,民国初期远销欧美,以法国销路最好,年销售额约银洋20万元以上,临潭群众家家养马鸡,户户有鸡舍。
(资料来源:除注明出处者外,文中资料均来自于《临潭县志》,李英俊《临潭简史》,《西道堂史料辑》,敏生华《古洮州的回族盐帮》)。
——李安宅、于式玉《黑错、临潭卓尼一带旅行日记•洮州歌一》清末民国初,由于皮毛交易的兴盛,临潭市场又一次繁盛起来,外地客商云集,本地商人也向外地及全国各大城市扩展。临潭出产的名贵药材麝香、鹿茸、洮马、皮货、木材吸引河南、陕西、四川、临洮、甘谷等地的商人流入,遂将丝绸、棉布、纸张、盐、粮食等商品运人临潭。民国初至民国十八年(1929)在临潭县设立商号的外省客商有京帮、陕帮、豫帮、鄂帮等商帮,外县商号数十家,本地商号数十家,共有资金银元230余万元。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1937年《西北考察日记》中记载:“又论旧城商号,谓兰州、狄道两帮木客每年到此买木材十万元,加运费为二十万元,运至兰州便值五十万元;生皮毛走张家口,以其制皮之术工也;熟羊皮销四川。其他骡马走陕西,猪毛走汉口,羊肠走天津,麝香发河南,药材发陕西,牛售岷县、渭源一带。故旧城商务,东至陕西,更沿江而达津、沪,西赴青海,南抵川、康;北及内外蒙,当民国十七年未破坏前,其繁荣可想也。”
外地商号陕西的“万镒恒”、“恒顺昌”经营百货业;河南的“杜盛兴”、“复生荣”、“永隆全”专门经营药材,收购鹿茸、牛黄、麝香、洮贝等名贵药材;其他的“皋记商行”、“乾元商行”、“强华商行”经营皮毛生意。1917年旧城成立了商会,据统计民国三十年(1941)旧城一地有商业资金银洋647000元,当地资本在3000元以上的商号47家。“万盛西”、“义心公”、“福顺通”、“复有公”、“永泰和”、“天兴隆”、“全盛敏”等商号经营日用百货、贩运牛马、名贵药材等,是当时临潭享有盛名的商业大户,在川、青、藏、汉口等地设有分号商店。新城天成隆等十户商号有资金34500元,只占旧城商业资金的3.8%。此一时期还出现了面行、斗行、秤行、山货行管理市场,收取牙金(中介费)。客栈旅店有集成店、德泰店、义泰行、长胜店、福兴店等,以及名目繁多的饮食业如宏泰馆、元顺馆等。
民国时期的洮商经商形式分为坐商和行商。
坐商,如上述的商号,设商行,开铺面旅店摆摊等。贸易网达西安、北京、张家口、汉口、成都、松潘、西宁、兰州、西康等20个省市,从事商业物资的输入输出。据1941年统计全年输入布匹、粮食、面粉、日用百货39万余银元。1947年仅羊皮输出152000多张、毛褐1000多匹,猪鬃、牛皮等贸易额达银洋300余万元。以西道堂为例:民国十八年(1929)十五个坐商固定、流动资金银洋达到20多万元。截至1949年仅旧城铺面达61间、旅店2处。坐商天兴隆分号遍及四川、青海、陕西、宁夏、甘肃、碌曲拉仁关,岷县、夏河建有贸易集散地。在成都、松潘、兰州、西安、张家口、北京、天津、上海、内蒙古设有商行。在汉口、江西、广州、河南、新疆、西藏等地有商业网点,经营皮张、鹿茸、麝香等物资交易。仅1930-1932年夏河网点与英商普伦洋行三次交易野牲皮张,收入白银达34300余两、银元15390元。
1949年前临潭新旧城著名商号一览表行商,俗称“牛马商贩”,往来于甘、青、川、藏区,将藏区所需物资运入,又将藏区所产物资运出。行商中又有商队和“单马客”(一人一马一枪)之分。商队的形式主要有:
(一)牛马贸易商队。临潭向藏区运进日用百货等,从藏区购买或以物资交换牛、马、羊等牲畜,赶往旧城出售。牛马主要来源于青海玉树、果洛,四川阿坝、若尔盖,甘肃碌曲、玛曲、夏河等地,骡马交易会上的牲畜交易约达5000多头(匹只),据1941年的不完全统计,旧城交易马3000多匹、牛2000多头、羊4000多只,全年总输出牲畜额价值银元330多万元,牛马主要贩往陕西、岷县、西和、礼县等地。
(二)从事皮毛贩运的牛马驮队。清末民初皮毛交易兴盛,外国洋行向西北腹地深入,光绪二十六年(1900)甘南地区的羊毛生意被英商垄断,拉卜楞的“丛拉”(市场)建起了英国普伦洋行,直接收购羊毛,先在甘加、麦西、桑科、欧拉、黑错等地集中,然后统一运到拉卜楞,交洋行验收过秤。“以天兴隆为例,光绪三十年(1904)一月即洋行到河州开设分行的第四年,西道堂教民丁重明捐银一万两,以此为资金,西道堂'天兴隆’商行正式开业……次年12月,丁重明再捐银1000两;在新城建'天兴亨'商号……。临潭地处藏区,西北靠近著名的拉卜楞寺院,南连上下迭部,西达双岔、毛日、西仓,全是以牧业经济为主的藏族聚居区,'天兴隆’商行从事的皮毛收购业中的行商活动范围包括甘肃和青海玉树、果洛海北等……行商队在经理们的带领下到草原腹地收购羊毛,销售藏族生活日用品。民国二十一年(1932)时天兴隆流动资金达银元16万余两……西道堂加强与外省的商业交流,扩充骆驼60峰,派经理马仁山专往归绥、包头等处经商。”(袁纣卫《包头回族皮毛贸易(1879-1945)》载宁夏社科院《回族研究》2007,第三期。)民国二十一年(1932)西道堂行商共计20个商队,计驮牛1700多头、骑马200余匹、流动资金16万余元,贸易来往于内蒙、四川等地。当时洮州著名文人吕芳规《看贩子出口》一诗,形象描绘了皮毛商队的盛况:
番帽番衣番样穿,腰悬利刃背生烟。弩马识途能致远,驮牛负重各争先。笠天席地何辞苦,暑寒夏冬不计年。皮毛满载归来日,猎犬狺狺犹带膻。
(三)盐帮驮队,是从青海驮运食盐的驮牛商队。民国时期临潭旧城有盐帮驮队70多家,驮牛15000多头。年贩运盐约50万公斤。从明中叶开始,以回族为主的洮商就自发组织盐帮到青海省的茶卡盐湖驮盐,到1953年为止持续了400多年。
盐帮的组织形式:盐帮的最高层由2~4名大“郭哇”(藏语意为头人)组成。他们是从全体盐帮成员中民主选举产生的。只在驮盐的路途中起组织领导作用。盐帮的基层组织叫“锅子”,每个“锅子”由6至10人自愿结合而成。他们在驮盐途中住在一起,食在一锅,故名“锅子”。每个“锅子”产生1名领导,叫“尕郭哇”。组成“锅子”的条件是每人都必须有1匹乘马,每个锅子枪不少于1支,凶猛的藏獒不少于2—3只。通常情况下盐帮由20—30“锅子”组成。驮牛最少时约为1万头左右。最多达3万头。供骑的乘马约为200-600匹左右。藏獒100只左右。盐帮们个个体魄健壮,精通藏语,马术娴熟,枪法精良。驮牛均为强壮的犏牛。这一时期最大的盐帮当为西道堂驮队和以苏温西为大郭哇的驮队。
盐帮的驮运时间和路线:盐帮驮盐的时间一年两次,每年的6月初,上一年的“大郭哇”,在旧城召集各“锅子”的“尕郭哇”开会,商讨驮盐的启程日期和路线,开始启程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夏季:从夏历的六月十五启程到八月底返回。路线是旧城→沙冒→多花儿→博拉扎沙→桑科保安西面的那哈差纳哈→贵德浮桥→红柳沟→上嫄台→青海湖→茶卡盐湖。返回路线仍按原路返回。
冬季:盐帮从夏历的十月初出发到次年的正月十五返回。路线是:旧城→斜藏沟→沙冒→博拉寺院→阿木去乎寺院→达采寺院→科采寺院→胡儿地苍→漏苍→塔尔秀贡巴→东加达苍→个儿马阳群(从此处过黄河冰桥)→阿苏乎云→尕务路小寺院→青海湖→茶卡盐湖。返回时仍按原路返洮。
盐帮的行军、宿营方式和路途纪律:在“郭哇”庄严下达起程的命令后,牛群徐徐起身,驮队逶迤长达30-40华里,这支队伍不为战争行军,却似远征将士,英勇威武地肃然前进。
一天后,驮队离开旧城,进入草原地带,宿营后,由上一任大“郭哇”组织召开全体盐客会议,民主选举本次途程中的新“郭哇”,这些新选的大、小“郭哇”再详细地编排各“锅子”行走的次序,大家依然绝对地服从这些新“郭哇”的领导。
行进的盐客每天在黎明时分就生火熬茶,只喝少量的“豆码”(藏语意为稀糌耙,因为驮驮子时吃的过饱会有损身体健康)。然后每两人为一组,快速利落地驮好30-40头牛的盐驮子,在“郭哇”下达动身的命令后,徐徐启行。每天的行进序列都按“蛇落皮”的方式排列,即头天排在第一位的“锅子”在第二天是最后动身,头天排在第二位的“锅子”在当天变为先行,在行进中,每“锅子”抽1-2名枪法好、骑术精的人组成盐帮的“前卫”和“后卫”。当行至险要地段时,“前卫”即策马占据有利地形,直到驮队全部通过,才将阵地交给后卫殿后。大约走50—60华里路,到达预定的宿营地时,将近中午先拴好藏獒,以防咬伤行人。然后两人一组,快速卸下盐驮,让牛去自由觅食吃草,这时盐客们才生火做饭,饭后再将盐袋每六只为一垛码放起来,在其三面扯起“档绳”准备晚上拴牛。宿营地点,均选在开阔地带,从不在山根崖坎下宿营,以防晚上盗贼从高处滚石头惊乱牛群。
宿营时各个“锅子”的马匹、帐篷、驮牛、盐垛和藏獒都按下图位置排列,不得紊乱。而整个盐帮的宿营地是一支军旅的圆形大营盘,每个“锅子”的帐篷门一致背离圆心向外,形成一个大圆,叫做“场子”。
休息时,烧红烙铁,将牛背压伤的肿块烙治消肿。盐队每走四五天要大休息一天,这一天就是盐客们的节日,有的人比赛枪法,他们大多数人枪法百发百中;有的人抱盐袋比赛力量,要求双腿盘起来坐在地上,再怀抱盐袋站立起来;有些人则去探望附近的蒙、藏朋友,拿的礼物有哈达、布匹、红枣、核桃、柿饼、油炸果等,朋友家除盛情款待外,临走还送酥油、曲拉、活羊、蕨麻、醍等东西给盐客们;大“郭哇”们则去拜访当地的头人、活佛,拉关系搞交易。
临近黄昏,全部要返回宿营地,晚饭前把牛拴到“档绳”上,马一律套上“铁绊”,拴在帐篷的前两侧,藏獒全部放开,盐客们围坐在篝火旁,一面品尝着酥油茶,一面讲故事,说笑话,有的还放开喉咙唱起了家乡的“花儿”。而大小的“郭哇”们每天晚饭前要在“场子”中央召开一次例行会议,讨论第二天的行进路线、宿营地点,研究决定在第二天可能经过的地方,给头人、土官或寺院送礼的具体事宜,处理当天盐客中违犯盐帮纪律的事。会议结束后,小“郭哇”们回到各自的帐篷传达会议内容,指派晚上前后夜的岗哨后,各自安歇。而大“郭哇”们还不定期地检査值勤放哨的情况,如有人在守夜放哨时睡觉,属于严重失职,必须罚牛一头。由于盐帮有严明的纪律,加之队伍庞大,枪械快利,内部团结,所以很少发生意外事件。
在路途中,盐帮有相当严明的纪律,如经过村庄和寺院时,不得打马狂奔,不得和其他兄弟民族寻衅闹事,骑在马上不能打瞌睡,不允许马缰绳掉落在地,服装穿戴不齐整要批评,睡姿和坐姿都有规定,如坐下时臀部落在盘起的双脚上不能落在地面上(这种坐姿能快速起立),睡姿呈“弓形”,绝不允许四仰八叉的大睡。如有违犯上述纪律者,处以一定的罚金(一头牛、一只羊或五块银元),由于有严明的纪律,所以所到之处和各族群众关系相当融洽,出现了盐帮到时“全家喜迎,去时洒泪而别”的感人场面,盐客们个个都能自觉遵守纪律,极少有违犯者。
驮盐的经济效益
每年夏历的六月初。洮州地区的农作物全部耕种完毕。大量的耕畜需要草料,仅靠当地的产草量是无法解决的,一年两次的驮盐,使耕畜在外的时间长达7个月之久,几乎全年一半以上的草料在驮盐的路途中解决了,去时沿草原地带行进,到达茶卡湖边时牛马已膘肥体壮。这样安排时间既不耽误农活,又能使耕畜身体得到恢复,是很科学的。
另外,洮州气候寒冷,农业收入微薄,驮盐可以增加经济收入。据老盐客们回忆,在清末民初时期,用帽缨子、粗织布等物从湖边蒙古族群众处换取食盐,用一顶帽缨子可以换一驮盐(200市斤左右)。在1931-1941年间,茶卡湖由马步芳的“厘金局”管理,每驮盐交“厘金”2块银元,只数驮子,不过秤。从1941年到解放初,开始过秤计值,每100市斤盐付给厘金局8—12元的国民政府纸币。驮到洮州旧城,扣除各项费用,每驮盐(200市斤)纯利约30块银元。
这样,洮州盐帮无形中使旧城变成了一个很大的食盐集散地,每年运到的盐至少在100万斤以上,这些盐除满足洮州附近数县群众的需求外,还有相当数量的盐由“脚户骡子”客和舟曲、文县、礼县一带的“背子手”们再贩运到岷县、宕昌、武都、礼县、舟曲、文县等,有些还运到陕西等地,上述客商又从四川运回布匹、线、竹器、颜料,从武都运回铧,从陕西运回了“杠铃”(老牛车所用的铁铃或系在牛项的铁铃)、马镫等,既丰富了洮州市场的货物品种,满足了当地各族群众对生产、生活必需品的需求, 也促进了洮州旧城市场的大发展。
盐帮生活艰苦,旅途艰辛。驮盐一趟往返需要3个多月,而且旅途时常有不测的事件发生,劳累、疾病、贼盗伴随着他们。冬天,从黄河岸边到茶卡湖的路程基本上是沙磧地带,人畜逆风而行,牛、马踏起的滚滚沙尘,似黄龙舞动,晚上风停以后才能生火做饭。每天驮卸百来斤的盐袋60余袋,衣服前胸全被擦破,一趟盐驮回来胸部肌肉结了老茧。更苦的是从湖水里捞盐,双腿浸泡在冰冷咸涩的湖中,双腿、手、脚都要脱一层皮。不少盐客的生命就抛却在这条漫长的不归之路上。因此盐帮们在动身之前,亲朋好友们会前来送行,纷纷送上“干粮”(点心、各类糖果、柿饼、红枣、核桃等)。各家盐客都请阿訇念《古兰经》,祈求真主的襄助。在动身的当天清晨,整个洮州旧城是倾城沸腾,场面十分壮观。盐客们身着藏服,跨马背枪、精神抖擞地用藏语吆喝牛群,藏獒们欢欣跳跃,在驮队的两侧奔跑追逐,护卫着这支浩浩荡荡的大军远行,送行的场面显得庄严热闹。盐帮驮队回来时又全城出动,亲戚、朋友、邻居前往迎接探望。
盐帮驮牛队轶事
1.盐帮的忠实卫士——藏獒
藏獒是出产在四川和甘南草原地区的一种猛犬,身躯高大,耐寒灵敏,当盐客们在茫茫草原上行走,沉沉黑夜中宿营时藏獒都能忠实地履行护卫任务,和盐客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民国二十九年(1940)的夏天,盐帮离开茶卡盐湖在红柳沟宿营时,有盗贼乘黑来劫,被藏獒发觉,近百只藏獒群起进攻,贼人仓皇逃窜,其中一人未来及上马,被藏獒穷追不舍,他急中生智爬到一棵大树上,藏獒将树围了一夜,直到第二天盐客发现,驱散藏獒,那贼才从树上溜下来,但已被吓得半死。
2.盐帮的扶困济危精神
事情发生在民国二十九年(1940),四川松潘舍儿哇地区的藏民,从茶卡湖往西宁驮盐返回的途中,200多头牛、20余匹马,被一伙盗贼抢劫。哭诉到洮州盐帮的苏温西大“郭哇”处,苏立即下达了追击贼盗的命令,盐客一天的强行军,追上了被盗牛群。起初,这些贼人不肯退赃,盐帮中的神枪手骑在马上把贼匪远处几头驮牛项下的铃铛弹无虚发地击落,贼匪受到震慑,原数退还所劫东西,这些“舍儿哇”藏民赶着3头肥牛前来答谢,盐帮均未接受,他们流着感激的泪水离去,并和盐帮结成了 “主人家” (朋友)。
3.盐帮的技能为马步芳所钦佩
有一年马步芳会同青海湖周边的蒙藏王公、头人、活佛,在青海湖边“祭海”,恰逢洮州的盐帮路过该地,马步芳派人传话给盐帮:“听说你们洮州人驮牛跟的好,我想看一下。”经大小“郭哇”们商量后,给马步芳送了2包大茶、六桶蜂蜜(2市斤/桶),接下来表演驮驮子、支帐篷、生火做饭等,马步芳评价:“驮盐确实很苦,你们洮州人驮牛跟的好,纪律好,牛马的装备齐整。”并赏给盐帮3000驮盐(约60万斤)、炒面2000斤,猎获的黄羊6只,将盐帮送的蜂蜜转赠给在场的头人、王公、活佛,并嘱咐道:“这些洮州的盐客很苦,以后请你们多照看的哈。”
(四)“单马客”,是在抗战及其后的解放战争时期,由于藏区大量种植罂粟(鸦片),旧城成为鸦片集散地之后大量产生的。他们一人一枪一马,从迭部等藏区往返倒运鸦片。其中亦有大批“单马客”是从藏区往来贩卖日用品和羊毛皮张的。
(五)在清末民国初至民国中期,临潭洮商中还兴起了做马鸡翎子的生意,每百根蓝马鸡翎售价银洋30元,销往北京作满清官员官帽饰品,民国初期远销欧美,以法国销路最好,年销售额约银洋20万元以上,临潭群众家家养马鸡,户户有鸡舍。
(资料来源:除注明出处者外,文中资料均来自于《临潭县志》,李英俊《临潭简史》,《西道堂史料辑》,敏生华《古洮州的回族盐帮》)。
相关地名
临潭县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