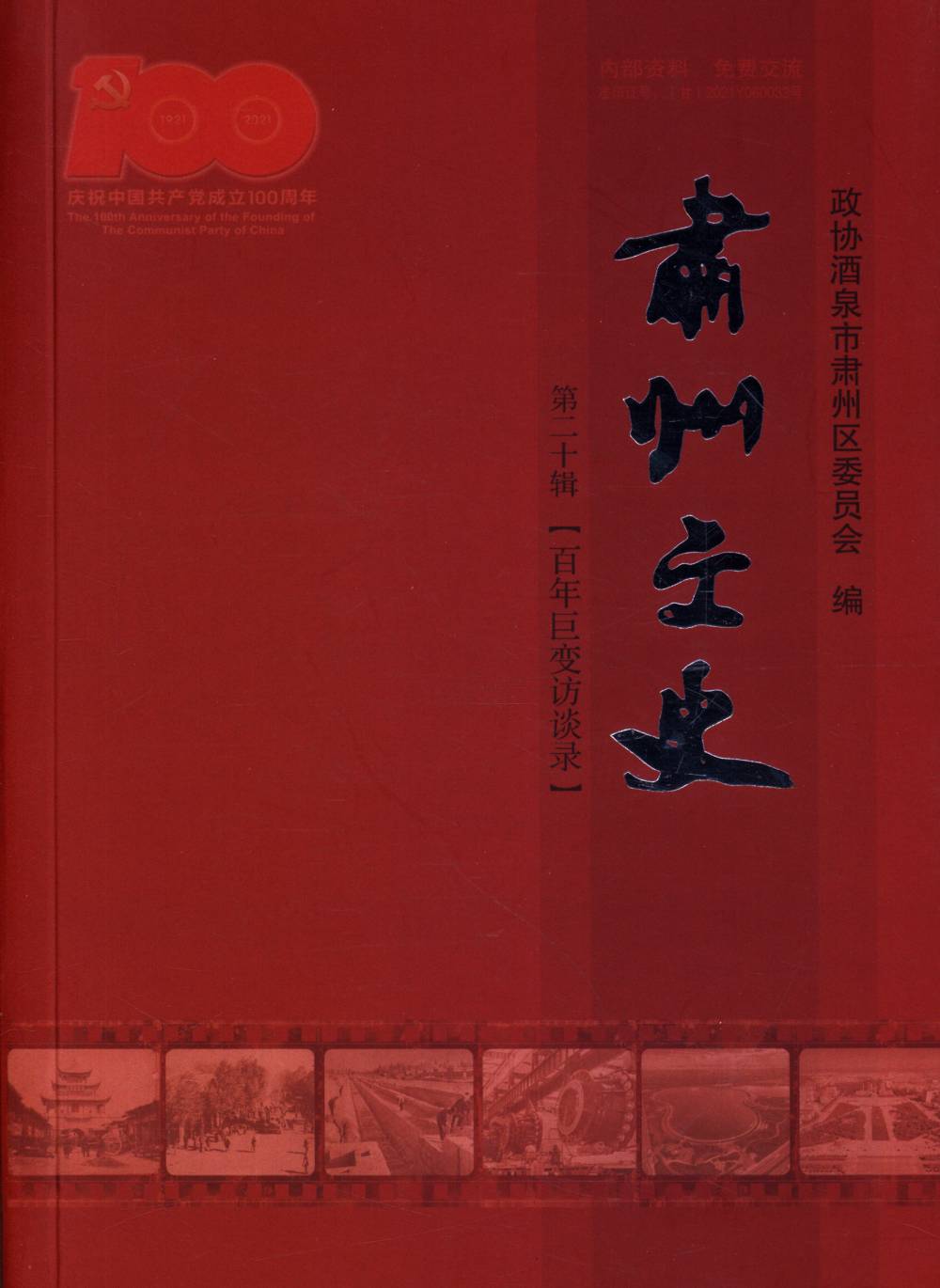罗世银
| 知识出处: | 《肃州文史·百年巨变访谈录》 |
| 唯一号: | 292230020220001507 |
| 人物姓名: | 罗世银 |
| 文件路径: | 2922/01/object/PDF/291010020220000023/001 |
| 起始页: | 0437.pdf |
| 籍贯: | 黄泥堡裕固族乡 |
传略
罗世银,四十年代出生在黄泥堡裕固族乡新湖村,社教后当生产队会计,1983年当乡干部直至退休。
罗世银:我小时候吃水艰难得很,庄子南里有个淌水浇地的官沟,水一淌下来,人就吃沟里的水,水淌过就吃沟里汪下的死水渗水,渗水羊啊牛啊也吃,水里面牛羊杷上粪了人也得撇得吃,不吃没办法,渗水吃完沟里没水了,就得去远处驮水吃。新湖南面有个索家井,用柳斗打地吃,再一个就是黄泥堡二队西头子有个杜家井,就吃这两口井里的水。
罗世银:驴驮的呢。每家都有一对驮水的大木桶,桶上有两个耳子,穿上担子,驴的脊背上备着鞍子,两个木桶用担子穿起来搭在鞍子上,一边一个桶,驮一次能吃一两天,费些每天驮一次,省着些用隔一天驮一次。木桶上有盖子封顶,边边上有个斜拐拐,开着个三角子尖尖,就像茶壶的嘴嘴,水打上从嘴子里倒进去,一边倒一柳斗,循环几次,直到两个木桶盛满,把口子用木头塞子塞住。驮水时间长了,驴也习惯了,塞子塞上不用下令就自己走开了。
罗世艮:大约六十年代,杜家井、索家井枯竭,我们没处驮水了,就到新湖二队妥家门上驮水,妥家门上有口苦水井,不吃也没办法。后来,大约到了七十年代,新湖学校门口打了口机井,井水还可以,不苦,是个探井,打开打算要封掉,结果没封,打井的人就走了。探井不停地冒水,水冒得半人高,冒了好几年,我们就从这个井上驮水。冒了几年水越来越小了,最后不冒了,这时各生产队开始打机井了,一个生产队打了一眼,吃水就近便多了,水质也好。吃水的过程就是这样,从外村驮水,到本村驮水,再到本队挑水,又到自己家里提水,直至水到锅头夹道,水 质也由苦涩变得纯净。
知识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