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天津人的回忆
| 内容出处: | 《肃州文史·百年巨变访谈录》 图书 |
| 唯一号: | 292220020220006489 |
| 颗粒名称: | 一个天津人的回忆 |
| 分类号: | K294.23 |
| 页数: | 9 |
| 页码: | 143-151 |
| 摘要: | 何景秀回忆从天津去酒泉支援边疆的经历。 |
| 关键词: | 肃州 酒泉 文史资料 |
内容
一个天津人的回忆
采访对象:何景秀,生于1938年,天津人。曾任原酒泉县饮食服务公司经理、酒泉地区服装公司和煤炭公司经理。1998年退休,现居酒泉。
采访人:刘永丰
采访时间:2019年9月2日
采访地点:阳光小区
采访人:您是在什么情况下来到酒泉的?当时的酒泉城是个什么样子?
何景秀:1955年甘肃省委派专人到天津市招录干部,这批干部属于支援边疆的干部,一共有一千多人。来人首先动员各个中学的学生报名,然后组织笔试,一周后张榜公布考试结果。我们这些中学生突然间变身为干部,最大的十八岁,最小的十六岁,出门坐公车,大家像出窝的家雀一样兴高采烈。那个时候,天津的情况也不怎么好,我家最大的问题是人多,天天吃的是棒子面,也还是经常吃不饱,当了国家干部,吃饭就不成问题了。
当时我们乘坐的是老式火车,到兰州市停了一个多小时,下了一部分人,然后就一直到达武威。大伙儿都是第一次离家远行到西北来,好多人以前连火车都没有坐过。到武威后,晚上安排我们睡的是土坯房,房子的隔墙中间留有方孔,里面是若明若暗的清油灯。突然,屋外有人喊:“土匪来了!”女学生都吓哭了。带队干部吩咐我们不要出去,防止发生意外。第二天天还没亮,我们同屋的三个人就结伴去上街,远远看见街道旁有个火苗一窜一窜的,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个老汉在那里拉着风箱卖鸡蛋醪糟,他的醪糟三分钱一碗,每碗打一个鸡蛋,我们要了三碗,凑到鼻子跟前一闻,一股酒味扑面而来,都喝不惯。转回来时,又遇见一个卖卤鸡的,一分钱一个卤鸡蛋,我们都有点馋,又花了一毛钱,每人三个卤鸡蛋,一问一只鸡腿才五分钱,我们每人又吃了一个鸡腿,这才解了馋。中午武威地委请我们吃饭,这顿饭摆的是席,席间,武威地委书记和大家见了面。第三天早晨,我们一起乘坐汽车继续西行,这些汽车有的有棚,有的没棚,车后扬起弥天的尘土随风飞向茫茫戈壁,路边的景象异常荒凉。这时候,有的女生就哭开了,紧接着乂有更多的人哭了。到张掖后,张掖地委也招待了我们,吃完饭每人又发了一个馒头,接着就上车赶路。到太阳偏西,大约是下午五六点钟,才到酒泉。我们从南门进城,城里的道路坑坑洼洼,我们的十几辆大汽车在前面慢慢行进,一群孩子追着车跑,因为他们感到好奇。我们这批到酒泉的一共是256人,留到酒泉县的有九十多人。到了第三天,我被分到了花纱部。
当时正值春季,酒泉这个小城风沙很大,全城除了鼓楼和儿处庙宇,满城都是东倒西歪的土坯房,马路两边的门面也都是破破烂烂的。民间都说酒泉是“风吹石头跑,十八的丫头不洗澡。”在农村,多数小孩都是光屁股,好多十五六岁的姑娘没有裤子穿。记得1956年冬天在西店下乡时,老百姓家里烧着火盆,屋子里边烟雾缭绕,什么都看不清。带队干部告诉我,进老乡家门时先要看腿,如果地上能看见人的腿脚就进去,因为许多老百姓家条件都很差,有的家里就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炕上坐的人可能都不穿裤子,遇到了会尴尬。当时,城里卫生最好的地方是现在东大街医药公司旁边的利民商店,每天都扫地洒水,门面显得比较干净,其他地方都很脏,马路旁边的很多老杨树上都栓着牲口。白天,大街上的马车和大车古辘车一辆接着一辆,大车古辘车比人高,直接从鼓楼洞子钻过去。街上的马粪牛粪有人在拾,也有人在铲。那时候,饭馆里卖的早点一般是糊锅、素面筋,前面的人吃罢,把碗放到污浊的洗碗水里一蘸,后面的接着吃,大师傅用的抹布散发着难闻的馒味。
采访人:请您谈谈在花纱部工作期间的情况。
何景秀:1955年至1957年我在花纱部工作。花纱部在仓门街东口对面,现在的大明步行街,是商业局的下属单位,商业局就在隔壁。对面有个老人巷,几乎天天都有死人从单位门前拉过,这里住的居民都认为不吉利,后来就改成了吉祥巷。我们当中有6个人分到了花纱部,单位是一个土院子,院子里有一口水井,一共五间房子,我在大办公室工作,属于计划科,主管棉花的统购统销。单位大门外面有个土厕所,围墙很矮,一点隐蔽性也没有,过路的人和本单位的人都在那里上厕所,夏天臭气熏天,招得苍蝇到处乱飞。单位的房子很紧张,晚上睡觉,7个小伙子挤在一个宿舍里,点一盏煤油灯。人事科有个同事要结婚,自己没房子,单位给他腾了半间房子,他又借了一张床板,算是安了家,两口子都是广东人,他爱人对这里的条件很不满意,刚结婚几天就回广东了。当时,我的工资是每月32.08元,发了工资先必须给家里寄15元,每月最低要吃1。元的伙食。
花纱部供应的布匹有华达呢、白布、红布、平布等四种,最好的是华达呢,还有棉花、布线等。当时,城市居民每人每年领取布票8尺,肉票每月4两,此外,还有粮票、糖票、油票等。买布时先看布票后看钱,遇上结婚等大事,全家的布票做不出一床被子,必须向亲戚朋友借。计划科的人每天晚上都要从各个门市部收布票,每个月烧一次布票,足有厚厚的七八摞,都是用细麻绳捆扎,销毁时必须有计划科和商务局的三个人监烧签字。当时计划科有个管布票的因为少了一丈多布票,被定为贪污犯。因为我出身贫困,上班第二天,人事科通知我去搞运动,当时我不知道什么是运动,就跟着一位年长的同志学。我的工作主要是批斗反革命时通知人,准备会场。1956年公私合营时期,我参与了对旧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邮电街口一直到北市街是商贩和门店最集中的地方,我们管辖范围内一共有36家卖布的商店,大多数经营惨淡,只有利民商店姓鲁的老板经营良好。花纱部有十几个党员,大部分是从部队转业的。我1958年入党是我们全家最荣耀的事,天津那边,我的父母和舅舅舅妈逢人就讲这件事,都觉得我给他们长了光。1958年反右派,一开始不知道谁是右派,先是互相揭发,其中有个年轻人搞对象时对周围一些女青年评头论足,引起了别人的反感,就被划成右派,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改造。
采访人:你们天津一同到酒泉的256人最后为什么只留下了19人?何景秀:这里面有很多情况,绝大多数是嫌酒泉的工作生活条件不好,自愿放弃干部身份,有家人帮助托人找关系返回原籍的。有一批人因为家里老人孩子无人照顾,熬到七十年代初,终于等来了返津政策。有的是自己犯了错误,被开除公职,或者因为害怕被抓,偷偷返回原籍,做了一个黑人黑户。比如有一个发小分配到了县广播局,因为平时说话不忌口,加上家庭出身不好,被打成右派,押送到山丹煤矿背煤三年,后来落户到山丹农垦兵团,在那里娶妻生子,成了一名农工。有的是来酒泉时已经结婚生子,离家太远,无法照顾家人,想回去又没有门路,只好放弃工作,辞职回家。比如有一个人在酒泉是税务局的干部,因为家里没人管就回去了,在天津也没有工作,变成了拉板车的人力车夫。
采访人:请您谈谈饮食服务公司的组建和三年困难时期的食堂经营情况。
何景秀:1959年,组织上让我负责组建饮食服务公司,任书记和工会主席,又派了一名当过兵会做饭的同志任经理,外加其他同志一共8人,单位在邮电街邮局家属院对面,就是后来的饮食服务公司家属院。先前,顾客都在饭馆门前露天的地方吃饭,既不卫生,也不雅观。经过公私合营,酒泉县城的食堂合并成了8个食堂,即一、二、三、五、九食堂,两个清真食堂,外加东街的一个高价食堂,六、七、八食堂是公私合营的,包括7个旅社,2个照相馆、3个理发店、1个澡堂子、1个镶牙的,大大小小一共25家,职工160多人。当时,最大的旅社是三旅社。大跃进以后,人们的生活渐渐变好,到高价食堂开洋荤的人也逐渐多起来,一段时间门庭若市。三年困难时期粮油很紧缺,很多人为了活命,就想方设法涌进食堂吃饭。1961年吃饭的人数达到高峰时,到食堂吃饭先要带单位的介绍信,一开始由饮食服务公司凭介绍信批条子,安排他们到各个食堂买饭吃,目的一方面是控制吃饭人数,另一方面是平衡各食堂粮油肉供应,防止因为缺粮关门。有时候,排队批条子的人一直从办公室排到大院,又从大院排到大街上。当时,我每天都要批好几百个人,工作量很大,中午和下午都不能正常下班。连续批条子过了大约两个多月,因为工作量太大,就改成由食堂经理批条子。到了这一年年底,粮油供应紧张的情况有所好转,又恢复到以前的凭粮票和现金买饭。
采访人:请您谈谈酒泉饭店大楼的起建过程。
何景秀:原来的酒泉四大街没有一座高楼,最早起建的是酒泉饭店大楼,位于南大街。1963年底,商业局局长高怀孝通知说,高文斗副市长要到局里召集会议,说要盖酒泉饭店大楼,是个面积3000多平方米的四层楼。当年年底成立了酒泉饭店大楼筹建领导小组,由商务局局长孝茂权任组长,我负责施工。当时,我对建筑工程一窍不通,心里没底,就跟着高市长到84701部队去找刘勇副师长。刘副师长问我都需要什么,我说需要人、材料、设备,因为我们饮食服务公司都是些做饭、洗衣服、剃头的,让我们凭空建一座楼对我们来说什么都缺。刘副师长很爽快,说我给你一个工程连,吃住不用你管,你只要每个礼拜发一双手套一条毛巾就行,工程用的搅拌机、卷扬机等都由部队自带。酒泉建安公司负责工程图纸设计,图纸经过市上修改审批,最终选址就在原饮食服务公司第九食堂的基址上。部队的一个加强连进驻工地后,正是隆冬季节,室外滴水成冰,战士们每天早晨都唱着革命歌曲迈着整齐的步伐来到工地,晚上又迈着整齐的步伐回到营地。后来因为人不够,刘副师长又派来一名副营长,并增加了二十几个战士。那年冬天特别冷,我们的工人都无法在外面干活,我们担心水泥无法搅拌,但部队的工作并没有受到影响,一天24小时倒班上岗。这座楼修了一年半时间。1964年7月正值工程紧张推进当中,天津传来电报说我父亲病危,老人家手里拿着我的照片,嘴里喊着我的小名,就是不闭眼,让我赶快回去。这时,大楼即将封顶,天津那边每天两份电报催我回去,说老父饮食服务公司酒泉旅社亲非要见我最后一面,这边领导又不给请假,说大楼封顶的事情得我管。高市长批给我150元,让我寄到家去,等大楼完工再回去,我因此没能见上老父亲最后一面,到现在都感到心里过意不去。8月份,大楼主体工程基本完工,这时,财政上批给我们10万元,领导让我出去购买饭店的设备,我亲自到景德镇订购了一批陶瓷餐具,上面都印着“酒泉饭店”字样。这座大楼包括食堂、旅社、澡堂子、百货店安置职工近60人,一楼二楼吃饭,三楼四楼住宿。一楼二楼的饭店大厅可一次性容纳200多人。
采访人:请您谈谈后来的情况和您的感想。
何景秀:改革开放以后,我先后在地区服装公司和地区煤炭公司工作,直到1998年从煤炭公司退休。地区服装公司组建于1982年,主管各县市的被服厂和鞋厂,一开始在东关二校对面,后来搬到西大街综合楼。地区煤炭公司组建于1984年,在北门小什字东边办公。当时,各县市用煤量逐年加大,进煤炭的渠道不同,价格也不同,市场比较混乱。为了加强煤炭统购统销,我们把各县市经销煤炭的人员和公章都收到总公司。这个单位属省煤炭厅直管,一年后下放到地区。
我就这样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没有给子孙留下存款和房产,就留下了一个“模范共产党员”的称号,但我很知足。
采访对象:何景秀,生于1938年,天津人。曾任原酒泉县饮食服务公司经理、酒泉地区服装公司和煤炭公司经理。1998年退休,现居酒泉。
采访人:刘永丰
采访时间:2019年9月2日
采访地点:阳光小区
采访人:您是在什么情况下来到酒泉的?当时的酒泉城是个什么样子?
何景秀:1955年甘肃省委派专人到天津市招录干部,这批干部属于支援边疆的干部,一共有一千多人。来人首先动员各个中学的学生报名,然后组织笔试,一周后张榜公布考试结果。我们这些中学生突然间变身为干部,最大的十八岁,最小的十六岁,出门坐公车,大家像出窝的家雀一样兴高采烈。那个时候,天津的情况也不怎么好,我家最大的问题是人多,天天吃的是棒子面,也还是经常吃不饱,当了国家干部,吃饭就不成问题了。
当时我们乘坐的是老式火车,到兰州市停了一个多小时,下了一部分人,然后就一直到达武威。大伙儿都是第一次离家远行到西北来,好多人以前连火车都没有坐过。到武威后,晚上安排我们睡的是土坯房,房子的隔墙中间留有方孔,里面是若明若暗的清油灯。突然,屋外有人喊:“土匪来了!”女学生都吓哭了。带队干部吩咐我们不要出去,防止发生意外。第二天天还没亮,我们同屋的三个人就结伴去上街,远远看见街道旁有个火苗一窜一窜的,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个老汉在那里拉着风箱卖鸡蛋醪糟,他的醪糟三分钱一碗,每碗打一个鸡蛋,我们要了三碗,凑到鼻子跟前一闻,一股酒味扑面而来,都喝不惯。转回来时,又遇见一个卖卤鸡的,一分钱一个卤鸡蛋,我们都有点馋,又花了一毛钱,每人三个卤鸡蛋,一问一只鸡腿才五分钱,我们每人又吃了一个鸡腿,这才解了馋。中午武威地委请我们吃饭,这顿饭摆的是席,席间,武威地委书记和大家见了面。第三天早晨,我们一起乘坐汽车继续西行,这些汽车有的有棚,有的没棚,车后扬起弥天的尘土随风飞向茫茫戈壁,路边的景象异常荒凉。这时候,有的女生就哭开了,紧接着乂有更多的人哭了。到张掖后,张掖地委也招待了我们,吃完饭每人又发了一个馒头,接着就上车赶路。到太阳偏西,大约是下午五六点钟,才到酒泉。我们从南门进城,城里的道路坑坑洼洼,我们的十几辆大汽车在前面慢慢行进,一群孩子追着车跑,因为他们感到好奇。我们这批到酒泉的一共是256人,留到酒泉县的有九十多人。到了第三天,我被分到了花纱部。
当时正值春季,酒泉这个小城风沙很大,全城除了鼓楼和儿处庙宇,满城都是东倒西歪的土坯房,马路两边的门面也都是破破烂烂的。民间都说酒泉是“风吹石头跑,十八的丫头不洗澡。”在农村,多数小孩都是光屁股,好多十五六岁的姑娘没有裤子穿。记得1956年冬天在西店下乡时,老百姓家里烧着火盆,屋子里边烟雾缭绕,什么都看不清。带队干部告诉我,进老乡家门时先要看腿,如果地上能看见人的腿脚就进去,因为许多老百姓家条件都很差,有的家里就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炕上坐的人可能都不穿裤子,遇到了会尴尬。当时,城里卫生最好的地方是现在东大街医药公司旁边的利民商店,每天都扫地洒水,门面显得比较干净,其他地方都很脏,马路旁边的很多老杨树上都栓着牲口。白天,大街上的马车和大车古辘车一辆接着一辆,大车古辘车比人高,直接从鼓楼洞子钻过去。街上的马粪牛粪有人在拾,也有人在铲。那时候,饭馆里卖的早点一般是糊锅、素面筋,前面的人吃罢,把碗放到污浊的洗碗水里一蘸,后面的接着吃,大师傅用的抹布散发着难闻的馒味。
采访人:请您谈谈在花纱部工作期间的情况。
何景秀:1955年至1957年我在花纱部工作。花纱部在仓门街东口对面,现在的大明步行街,是商业局的下属单位,商业局就在隔壁。对面有个老人巷,几乎天天都有死人从单位门前拉过,这里住的居民都认为不吉利,后来就改成了吉祥巷。我们当中有6个人分到了花纱部,单位是一个土院子,院子里有一口水井,一共五间房子,我在大办公室工作,属于计划科,主管棉花的统购统销。单位大门外面有个土厕所,围墙很矮,一点隐蔽性也没有,过路的人和本单位的人都在那里上厕所,夏天臭气熏天,招得苍蝇到处乱飞。单位的房子很紧张,晚上睡觉,7个小伙子挤在一个宿舍里,点一盏煤油灯。人事科有个同事要结婚,自己没房子,单位给他腾了半间房子,他又借了一张床板,算是安了家,两口子都是广东人,他爱人对这里的条件很不满意,刚结婚几天就回广东了。当时,我的工资是每月32.08元,发了工资先必须给家里寄15元,每月最低要吃1。元的伙食。
花纱部供应的布匹有华达呢、白布、红布、平布等四种,最好的是华达呢,还有棉花、布线等。当时,城市居民每人每年领取布票8尺,肉票每月4两,此外,还有粮票、糖票、油票等。买布时先看布票后看钱,遇上结婚等大事,全家的布票做不出一床被子,必须向亲戚朋友借。计划科的人每天晚上都要从各个门市部收布票,每个月烧一次布票,足有厚厚的七八摞,都是用细麻绳捆扎,销毁时必须有计划科和商务局的三个人监烧签字。当时计划科有个管布票的因为少了一丈多布票,被定为贪污犯。因为我出身贫困,上班第二天,人事科通知我去搞运动,当时我不知道什么是运动,就跟着一位年长的同志学。我的工作主要是批斗反革命时通知人,准备会场。1956年公私合营时期,我参与了对旧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邮电街口一直到北市街是商贩和门店最集中的地方,我们管辖范围内一共有36家卖布的商店,大多数经营惨淡,只有利民商店姓鲁的老板经营良好。花纱部有十几个党员,大部分是从部队转业的。我1958年入党是我们全家最荣耀的事,天津那边,我的父母和舅舅舅妈逢人就讲这件事,都觉得我给他们长了光。1958年反右派,一开始不知道谁是右派,先是互相揭发,其中有个年轻人搞对象时对周围一些女青年评头论足,引起了别人的反感,就被划成右派,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改造。
采访人:你们天津一同到酒泉的256人最后为什么只留下了19人?何景秀:这里面有很多情况,绝大多数是嫌酒泉的工作生活条件不好,自愿放弃干部身份,有家人帮助托人找关系返回原籍的。有一批人因为家里老人孩子无人照顾,熬到七十年代初,终于等来了返津政策。有的是自己犯了错误,被开除公职,或者因为害怕被抓,偷偷返回原籍,做了一个黑人黑户。比如有一个发小分配到了县广播局,因为平时说话不忌口,加上家庭出身不好,被打成右派,押送到山丹煤矿背煤三年,后来落户到山丹农垦兵团,在那里娶妻生子,成了一名农工。有的是来酒泉时已经结婚生子,离家太远,无法照顾家人,想回去又没有门路,只好放弃工作,辞职回家。比如有一个人在酒泉是税务局的干部,因为家里没人管就回去了,在天津也没有工作,变成了拉板车的人力车夫。
采访人:请您谈谈饮食服务公司的组建和三年困难时期的食堂经营情况。
何景秀:1959年,组织上让我负责组建饮食服务公司,任书记和工会主席,又派了一名当过兵会做饭的同志任经理,外加其他同志一共8人,单位在邮电街邮局家属院对面,就是后来的饮食服务公司家属院。先前,顾客都在饭馆门前露天的地方吃饭,既不卫生,也不雅观。经过公私合营,酒泉县城的食堂合并成了8个食堂,即一、二、三、五、九食堂,两个清真食堂,外加东街的一个高价食堂,六、七、八食堂是公私合营的,包括7个旅社,2个照相馆、3个理发店、1个澡堂子、1个镶牙的,大大小小一共25家,职工160多人。当时,最大的旅社是三旅社。大跃进以后,人们的生活渐渐变好,到高价食堂开洋荤的人也逐渐多起来,一段时间门庭若市。三年困难时期粮油很紧缺,很多人为了活命,就想方设法涌进食堂吃饭。1961年吃饭的人数达到高峰时,到食堂吃饭先要带单位的介绍信,一开始由饮食服务公司凭介绍信批条子,安排他们到各个食堂买饭吃,目的一方面是控制吃饭人数,另一方面是平衡各食堂粮油肉供应,防止因为缺粮关门。有时候,排队批条子的人一直从办公室排到大院,又从大院排到大街上。当时,我每天都要批好几百个人,工作量很大,中午和下午都不能正常下班。连续批条子过了大约两个多月,因为工作量太大,就改成由食堂经理批条子。到了这一年年底,粮油供应紧张的情况有所好转,又恢复到以前的凭粮票和现金买饭。
采访人:请您谈谈酒泉饭店大楼的起建过程。
何景秀:原来的酒泉四大街没有一座高楼,最早起建的是酒泉饭店大楼,位于南大街。1963年底,商业局局长高怀孝通知说,高文斗副市长要到局里召集会议,说要盖酒泉饭店大楼,是个面积3000多平方米的四层楼。当年年底成立了酒泉饭店大楼筹建领导小组,由商务局局长孝茂权任组长,我负责施工。当时,我对建筑工程一窍不通,心里没底,就跟着高市长到84701部队去找刘勇副师长。刘副师长问我都需要什么,我说需要人、材料、设备,因为我们饮食服务公司都是些做饭、洗衣服、剃头的,让我们凭空建一座楼对我们来说什么都缺。刘副师长很爽快,说我给你一个工程连,吃住不用你管,你只要每个礼拜发一双手套一条毛巾就行,工程用的搅拌机、卷扬机等都由部队自带。酒泉建安公司负责工程图纸设计,图纸经过市上修改审批,最终选址就在原饮食服务公司第九食堂的基址上。部队的一个加强连进驻工地后,正是隆冬季节,室外滴水成冰,战士们每天早晨都唱着革命歌曲迈着整齐的步伐来到工地,晚上又迈着整齐的步伐回到营地。后来因为人不够,刘副师长又派来一名副营长,并增加了二十几个战士。那年冬天特别冷,我们的工人都无法在外面干活,我们担心水泥无法搅拌,但部队的工作并没有受到影响,一天24小时倒班上岗。这座楼修了一年半时间。1964年7月正值工程紧张推进当中,天津传来电报说我父亲病危,老人家手里拿着我的照片,嘴里喊着我的小名,就是不闭眼,让我赶快回去。这时,大楼即将封顶,天津那边每天两份电报催我回去,说老父饮食服务公司酒泉旅社亲非要见我最后一面,这边领导又不给请假,说大楼封顶的事情得我管。高市长批给我150元,让我寄到家去,等大楼完工再回去,我因此没能见上老父亲最后一面,到现在都感到心里过意不去。8月份,大楼主体工程基本完工,这时,财政上批给我们10万元,领导让我出去购买饭店的设备,我亲自到景德镇订购了一批陶瓷餐具,上面都印着“酒泉饭店”字样。这座大楼包括食堂、旅社、澡堂子、百货店安置职工近60人,一楼二楼吃饭,三楼四楼住宿。一楼二楼的饭店大厅可一次性容纳200多人。
采访人:请您谈谈后来的情况和您的感想。
何景秀:改革开放以后,我先后在地区服装公司和地区煤炭公司工作,直到1998年从煤炭公司退休。地区服装公司组建于1982年,主管各县市的被服厂和鞋厂,一开始在东关二校对面,后来搬到西大街综合楼。地区煤炭公司组建于1984年,在北门小什字东边办公。当时,各县市用煤量逐年加大,进煤炭的渠道不同,价格也不同,市场比较混乱。为了加强煤炭统购统销,我们把各县市经销煤炭的人员和公章都收到总公司。这个单位属省煤炭厅直管,一年后下放到地区。
我就这样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没有给子孙留下存款和房产,就留下了一个“模范共产党员”的称号,但我很知足。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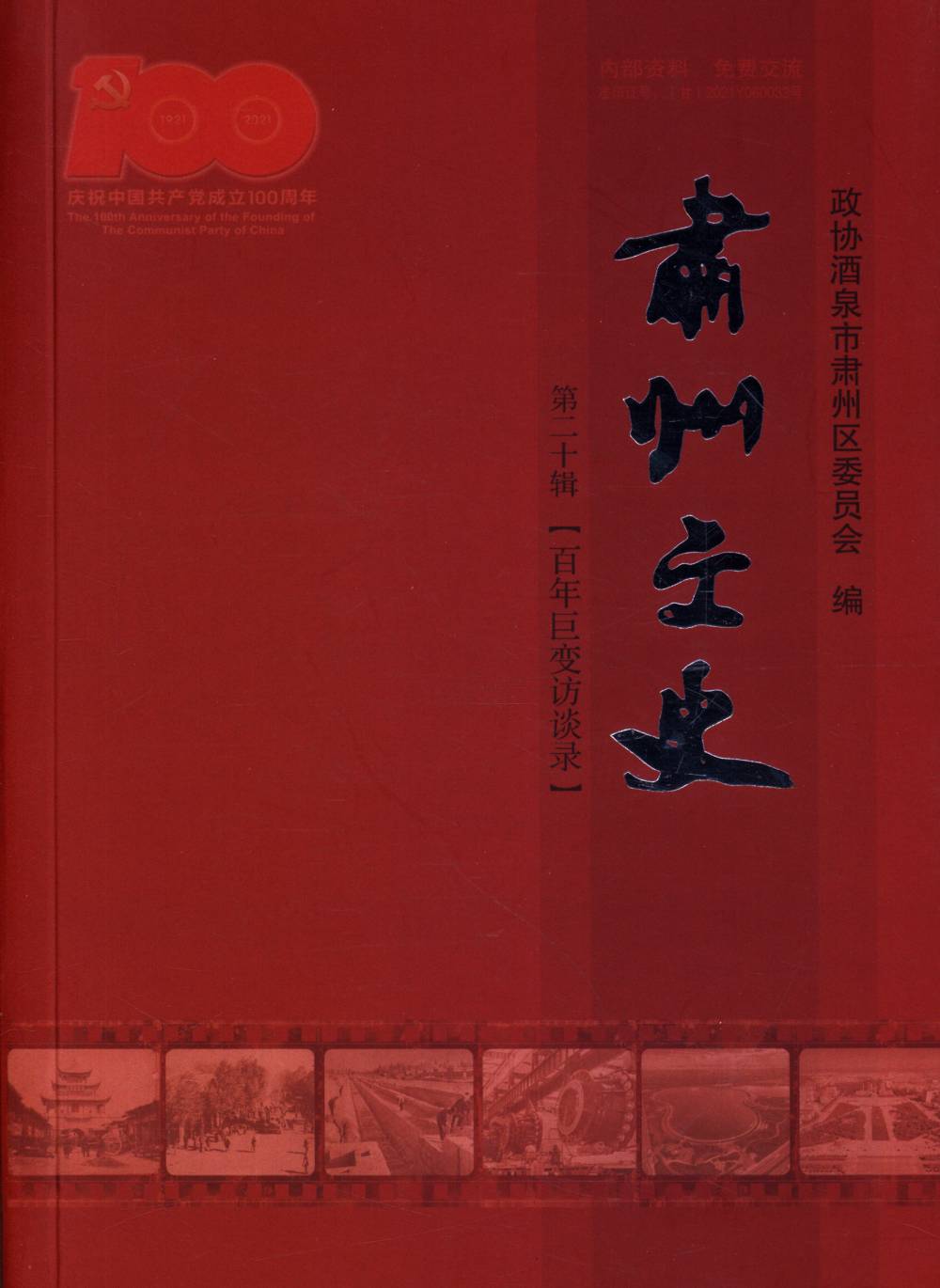
相关人物
刘永丰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