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陇东工作的一些回忆
| 内容出处: |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二辑》 图书 |
| 唯一号: | 290120020210004801 |
| 颗粒名称: | 我在陇东工作的一些回忆 |
| 分类号: | K250.6 |
| 页数: | 8 |
| 页码: | 22-29 |
| 摘要: | 陇东地区,早在一九三二、三三年间,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就曾领导、组织过游击队,创立过苏维埃区。当时活动地区主要是毗邻关中淳、宜、耀的合水、正宁、宁县一带。因为关中及陇东山区,自一九二八年“渭华暴动”失败后,革命的种子已撒播各县,特别是陇东山区,交通不便,地处偏僻,国民党统治力量比较薄弱,人民革命斗争此起彼伏,从未停止。 |
| 关键词: | 近代史 文史资料 中国 |
内容
陇东地区,早在一九三二、三三年间,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就曾领导、组织过游击队,创立过苏维埃区。当时活动地区主要是毗邻关中淳、宜、耀的合水、正宁、宁县一带。因为关中及陇东山区,自一九二八年“渭华暴动”失败后,革命的种子已撒播各县,特别是陇东山区,交通不便,地处偏僻,国民党统治力量比较薄弱,人民革命斗争此起彼伏,从未停止。
一九三六年六月,中央红军为迎接二、四方面军,组织西征,部队经过战斗,解放了环县、曲子镇等地,局面逐渐打开。 但此时驻在这一带的张学良的东北军,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投降政策下,被迫向红军进攻。我方为了保卫环县、曲子镇等地,准备迎接二、四方面军和一方面军会师,同时为了分散就粮,我红军大学第三科开到陇东。当时红军大学共分三个科,第一科学员完全是高级干部,第二科是中上级干部,第三科是连排干部。我在三科二营任政委。红大三科开进陇东后,即进驻环县以南的木钵镇。当时这一带为新辟地区,开展工作比较困难,加上部队又多,地广人稀,吃粮很困难。为此,由科长周昆、政委袁国平带头,组织学员去外地背粮。红大的学习内容主要是军事和政治,此外,还加一门“新文字”的学习。
“双十二”事变前,张学良的东北军在国民党蒋介石的逼迫驱使下,进攻红军,红大三科奉命自卫,参加了保卫环县、曲子镇的战斗。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在曲子镇五里桥与东北军打了一仗,这是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末期我们在这个地区和国民党的最后一仗。当时陇东各县人民对我们热情支持,但由于土地瘠薄,生产落后,军民生活都十分困难,又值隆冬季节,天寒地冻,我们的部队、学员衣衫单薄,特别是刚由南方到北方的同志,更是十分难耐。“双十二”事变发生,活捉蒋介石的消息传来,人心振奋,军民欢腾。但不久又传达了党中央和毛主席主张释放蒋介石,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迫蒋联合抗日的指示。起初大家对此都很不理解,经过认真学习讨论,联系国内形势的变化,民族矛盾突出,全民团结一致抗日已成为当时最迫切的要求,大家一致拥护党中央毛主席这一英明决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原驻陇东一些地区的东北军撤走了。红大三科(对外称为红军教导师)进驻庆阳城,在进行军政训练、培养干部的同时,在地方上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并建立地方党的组织。当时东北军官兵爱国心切,抗日热情高,同我军接触较多。但他们部队纪律差,军民关系紧张,对待老百姓态度野蛮,说什么“三句好话不如一马棒”,“打粳米,骂白,不打不骂小米饭”。当时东北军骑兵第七团驻扎在泾川、隆德一带,团长陈大章要求红军教导师派干部到他们部队去做政治工作。师政委袁国平同志指派我和许兴同志前去,先到泾川,任命我们为团军事教导队政治教官。一九三七年春节前,我和许兴同志到隆德县第七团团部找陈大章,陈和隆德县县长(姓名忘记,也是东北军派的)待我们很热情,一见如故,往往深谈至半夜。有一次陈团长看到团政训处工作人员 (双十二事变后换成的平津大学生)提着石灰桶在写大标语,他接过笔写了一条:“只有红军胜利,穷人才永远有饭吃”。政训处的人告我说:“如果国民党特务知道了,对陈不利。”当我对陈转告此种意见之后,陈很快接受把标语涂掉。在这个期间,我对他们着重讲说红军的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这一段工作比较顺利,直到一九三七年三月,国民党的中央军接替了东北军之后,我才回到庆阳教导师,任教导师一团政治主任教员。一团政委张平化同志调走后,我接替了他的职务。
“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西北红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教导师学员毕业,分赴抗日前线。此时,师长兼政委袁国平同志奉中央指示组建陇东特委,并指定他任特委书记,由教导师留了一批干部,在特委和所属各县担任负责工作。我因病亦留特委工作。当时有两个很不习惯的改变——是我们的红军改变为国民革命军;二是自己由红军干部改变为地方工作人员。前一个改变在思想上、感情上经过了一个很大的转弯;后一个改变是因工作的需要,由不习惯逐渐习惯,心情才逐渐安定下来。
一九三七年秋,陇东特委派我到国民党第三区专员公署所在地西峰镇,任八路军驻西峰镇办事处主任,党内职务是西峰县工委书记,任务是做国民党专署官员和地方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同时还要建立和发展我党地下组织,因为当时西峰镇还是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的专员公署、县政府和县党部都设在那里。我在西峰镇工作不到两年时间,国民党的专员就换过三任。第一任是罗人骥,湖南省衡阳人,此人官僚气习十足,除了在例行公文上划行签名外,无所作为。他对袁国平同志十分敬重,甘拜下风。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七日,罗人骥去合水“巡视”,正遇上群众开大会,群众冲着他喊口号,其中有一句是“拥护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祖国苏联”。他大为生气,回来后找我质问,说什么“你们是中国人还是苏联人”?我据理和他进行了一场辩论,驳斥得他无言对答。当时国民党口头上也说是抗战,但是他们强调一个领袖、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他们害怕群众,无视群众的力量,认为只要在中央政府领导下抗战,不需要发动群众,因此反对我党所进行的群众工作。他们不赞成实行民主,不同意实行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他们宣扬的民族、民权、民生,完全是空有其名的假三民主义。我们不仅主张要动员群众进行全民抗战,而且要实行民主,关心人民疾苦,改善人民生活。我们工作中贯彻了党的主张,充分发动群众,组织工会、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和抗日自卫队,以及各级抗敌后援会,实行减租减息,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我们的工作深入群众。于是他千方百计进行破坏,利用保甲长和联保主任下乡收税催粮镇压人民。还由兰州派来经过特工训练的“黄衣队”(因为他们一律身穿黄衣,群众叫黄衣队),下乡破坏群众组织,镇压群众抗日活动。
罗人骥走后,国民党派钟竟成为庆阳专员。钟是河北省怀柔县人,是反共摩擦专家,自从他到庆阳后,国共斗争就更趋尖锐复杂了。钟竟成走后,又派贺其燊接替,贺是江西省永新县人。 贺到任不久,我也调离西峰镇去庆阳,任陇东特委统战部长,孙君一同志接替我为八路军驻西峰镇办事处主任。我到庆阳不久, 陇东特委和庆环分区合并改称陇东地委,仍驻曲子镇,惟地委统战部仍以“陕甘宁边区政府驻庆阳办事处”的名义,驻在庆阳城。
这段时间,党在陇东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和群众抗日救亡活动蓬勃发展,但国共两党斗争日益激烈,直至发展到国民党三次反共高潮。由于党内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对国民党无原则的迁就,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结果把党所领导的抗日群众组织如工会、农会、青救会、抗日自卫队等,全被统到国民党官办的“抗敌后援会”去了。这等于解散了真正的抗日群众组织,完全放弃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和独立自主方针,因而群众情绪一落千丈,当地干部特别象西峰近郊和镇原县一带的干部和积极分子,横遭国民党特务的打击和逮捕,个别甚至被杀害,我们培养的一个当地区长名叫顾登西,就被国民党特务抓到西峰镇杀害了。在我们内部,也有个别人在国民党反共政策的威逼利诱下, 经不起严峻的考验,背叛革命,投奔敌人。经验和教训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毛主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方针的无比正确,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给党的事业带来的严重危害。后来我们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方针,才打退了国民党的反共高潮,把庆阳、合水、驿马关、镇原北三镇的国民党县长、区长“护送”出境,建立起人民的抗日民主政权,各种群众抗日组织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中共陇东地委和专署随即由曲子镇移驻庆阳城内,大灭了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威风,大长了边区人民的志气。
为了坚持持久抗战,克服困难,巩固边区,党中央于一九四〇年制定并实施了著名的十大政策,这就是:加强对敌斗争;建立“三三”制政权;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实行精兵简政;开展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群众运动;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开展生产运动;整顿党的作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等。建立“三三”制政权,是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基本原则,即在政权机构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占三分之一,吸收党外进步人士和开明士绅参加政府工作。陇东地区在一九四〇年春召开了参议会,民主选举民主人士刘仲邠为议长,我当选为副议长。各县也先后召开了县参议会,并选出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了人民法院,普遍推广了当时行政专员马锡五同志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审判方法。评剧《刘巧儿》的故事就是取材于马锡五同志判案中的一个案例。
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到一九四〇年三月,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后,即开始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并早已停发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薪饷,给边区军民生活造成困难。毛主席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边区军民热烈响应,各地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主要是开垦荒地,多打粮食,逐步发展植棉、种油料、蔬菜等经济作物,搞手工业生产,发展畜牧业。地方党政军干部和家属纺棉花、捻毛线,整个边区掀起了热气腾腾的大生产高潮。初期开荒时,群众认识不足,加之有些基层干部强迫命令,群众不愿接受,恰好这年风调雨顺,年景不错,边区政府又规定新开荒地头三年免征公粮,群众生产积极性大为高涨,争着圈地开荒。只用了短短两年时间,基本上实现了丰衣足食和保障供给。军民生活改善,不愁穿衣吃饭,从而促进了人民文化生活的发展,群众自办的业余剧团和秧歌队到处兴起,自编自演革命文娱节目,县县办起了文化教育馆,农村冬学也发展很快,当时陇东地区的最高学府、一所新型的中学——陇东中学,也于一九四〇年九月成立。边区军民大生产的胜利,带来了文化教育事业的欣欣向荣。
一九四一年六月在西吉、海原、固原一带,爆发了回族人民反抗国民党的武装暴动。暴动失败后,这支回民群众武装撤退到陇东地区,驻在庆阳三十里铺,我们当时欢迎他们参加革命,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对党的政策还有怀疑,我们表示愿去愿留悉听自便,去后再来仍然欢迎。马思义是这支群众武装的首领,他急于出去报仇,结果又遭到失败,退回边区,人员减少了许多。这时,马思义同志对党才有了认识,参加了革命,部队改编为回民支队,马思义同志任队长,西北局派杨静仁同志到这支部队工作。 这支部队后来在解放战争中发展壮大,屡立战功,许多指战员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成为共产党员和我军优秀的干部。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开展了整风运动,接着就是审干运动。整风运动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运动,提出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是十分正确的。在审干运动中,清查出少数特务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纯洁了干部队伍,也是必要的。但是,在审干过程中受到“左”的严重干扰,这就是康生搞的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尽管时间很短,由于采取逼供信造成许多冤假错案,把大批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党员和青年知识分子打成国民党特务,把许多地方的共产党地下组织诬陷为“红旗党”,甘肃地下党也不例外。党中央和毛主席发现后, 及时起草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提出“首长负责;自己动手;调查研究;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九条方针,并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才使错误没有继续发展。这次错误在陇东地区也有影响,我当时也执行了上面的错误指示,是有一定责任的,因为这时马文瑞同志已调西北局组织部工作,由、我代理地委书记。在这次运动中,华池县县长第五汉杰在审查中被迫致死便是一例。就当时的客观情况来看,敌情是十分严重和复杂的。由于土匪、反动民团的骚扰,边区人民身受其害,例如当时环县甜水堡有个土匪头子赵老五,经常带领匪徒骚扰边区,奸淫掳掠无所不为,群众无不切齿痛恨。我环县保安大队在大队长刘懋功同志率领下,多次击退他们的进犯,最后消灭了这股匪徒。另一方面,国民党也不断派遣特务潜入边区,刺探我方情况,伺机捣乱破坏,有的甚至已打入我内部充当坐探,敌我斗争是十分尖锐复杂的。也有少数敌人潜入边区后,在人民群众的威力震慑下和党的政策的感召下,主动坦白自首,改恶从善,个别人还参加革命戴罪图功,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经受了“考验,为革命事业做了一定的贡献。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我当选为代表,去延安参加“七大”,由李合邦同志接替了我的工作。此后,我再未回陇东。我在陇东工作阶段,正是抗日战争时期,这是党的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关头,也是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军事上达到完全成熟的重要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正确解决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依靠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克服了重重困难,壮大了革命力量, 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击退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三次反共高潮,使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陷于极大的孤立。当时,我们党已成为一个拥有一百二十万党员全国范围的、有广大群众性的党,这就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解放全中国奠定了思想、政治、组织和军事等方面的坚实基础。
—九八一年八月十九日于青岛海军疗养院
一九三六年六月,中央红军为迎接二、四方面军,组织西征,部队经过战斗,解放了环县、曲子镇等地,局面逐渐打开。 但此时驻在这一带的张学良的东北军,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投降政策下,被迫向红军进攻。我方为了保卫环县、曲子镇等地,准备迎接二、四方面军和一方面军会师,同时为了分散就粮,我红军大学第三科开到陇东。当时红军大学共分三个科,第一科学员完全是高级干部,第二科是中上级干部,第三科是连排干部。我在三科二营任政委。红大三科开进陇东后,即进驻环县以南的木钵镇。当时这一带为新辟地区,开展工作比较困难,加上部队又多,地广人稀,吃粮很困难。为此,由科长周昆、政委袁国平带头,组织学员去外地背粮。红大的学习内容主要是军事和政治,此外,还加一门“新文字”的学习。
“双十二”事变前,张学良的东北军在国民党蒋介石的逼迫驱使下,进攻红军,红大三科奉命自卫,参加了保卫环县、曲子镇的战斗。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在曲子镇五里桥与东北军打了一仗,这是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末期我们在这个地区和国民党的最后一仗。当时陇东各县人民对我们热情支持,但由于土地瘠薄,生产落后,军民生活都十分困难,又值隆冬季节,天寒地冻,我们的部队、学员衣衫单薄,特别是刚由南方到北方的同志,更是十分难耐。“双十二”事变发生,活捉蒋介石的消息传来,人心振奋,军民欢腾。但不久又传达了党中央和毛主席主张释放蒋介石,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迫蒋联合抗日的指示。起初大家对此都很不理解,经过认真学习讨论,联系国内形势的变化,民族矛盾突出,全民团结一致抗日已成为当时最迫切的要求,大家一致拥护党中央毛主席这一英明决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原驻陇东一些地区的东北军撤走了。红大三科(对外称为红军教导师)进驻庆阳城,在进行军政训练、培养干部的同时,在地方上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并建立地方党的组织。当时东北军官兵爱国心切,抗日热情高,同我军接触较多。但他们部队纪律差,军民关系紧张,对待老百姓态度野蛮,说什么“三句好话不如一马棒”,“打粳米,骂白,不打不骂小米饭”。当时东北军骑兵第七团驻扎在泾川、隆德一带,团长陈大章要求红军教导师派干部到他们部队去做政治工作。师政委袁国平同志指派我和许兴同志前去,先到泾川,任命我们为团军事教导队政治教官。一九三七年春节前,我和许兴同志到隆德县第七团团部找陈大章,陈和隆德县县长(姓名忘记,也是东北军派的)待我们很热情,一见如故,往往深谈至半夜。有一次陈团长看到团政训处工作人员 (双十二事变后换成的平津大学生)提着石灰桶在写大标语,他接过笔写了一条:“只有红军胜利,穷人才永远有饭吃”。政训处的人告我说:“如果国民党特务知道了,对陈不利。”当我对陈转告此种意见之后,陈很快接受把标语涂掉。在这个期间,我对他们着重讲说红军的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这一段工作比较顺利,直到一九三七年三月,国民党的中央军接替了东北军之后,我才回到庆阳教导师,任教导师一团政治主任教员。一团政委张平化同志调走后,我接替了他的职务。
“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西北红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教导师学员毕业,分赴抗日前线。此时,师长兼政委袁国平同志奉中央指示组建陇东特委,并指定他任特委书记,由教导师留了一批干部,在特委和所属各县担任负责工作。我因病亦留特委工作。当时有两个很不习惯的改变——是我们的红军改变为国民革命军;二是自己由红军干部改变为地方工作人员。前一个改变在思想上、感情上经过了一个很大的转弯;后一个改变是因工作的需要,由不习惯逐渐习惯,心情才逐渐安定下来。
一九三七年秋,陇东特委派我到国民党第三区专员公署所在地西峰镇,任八路军驻西峰镇办事处主任,党内职务是西峰县工委书记,任务是做国民党专署官员和地方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同时还要建立和发展我党地下组织,因为当时西峰镇还是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的专员公署、县政府和县党部都设在那里。我在西峰镇工作不到两年时间,国民党的专员就换过三任。第一任是罗人骥,湖南省衡阳人,此人官僚气习十足,除了在例行公文上划行签名外,无所作为。他对袁国平同志十分敬重,甘拜下风。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七日,罗人骥去合水“巡视”,正遇上群众开大会,群众冲着他喊口号,其中有一句是“拥护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祖国苏联”。他大为生气,回来后找我质问,说什么“你们是中国人还是苏联人”?我据理和他进行了一场辩论,驳斥得他无言对答。当时国民党口头上也说是抗战,但是他们强调一个领袖、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他们害怕群众,无视群众的力量,认为只要在中央政府领导下抗战,不需要发动群众,因此反对我党所进行的群众工作。他们不赞成实行民主,不同意实行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他们宣扬的民族、民权、民生,完全是空有其名的假三民主义。我们不仅主张要动员群众进行全民抗战,而且要实行民主,关心人民疾苦,改善人民生活。我们工作中贯彻了党的主张,充分发动群众,组织工会、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和抗日自卫队,以及各级抗敌后援会,实行减租减息,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我们的工作深入群众。于是他千方百计进行破坏,利用保甲长和联保主任下乡收税催粮镇压人民。还由兰州派来经过特工训练的“黄衣队”(因为他们一律身穿黄衣,群众叫黄衣队),下乡破坏群众组织,镇压群众抗日活动。
罗人骥走后,国民党派钟竟成为庆阳专员。钟是河北省怀柔县人,是反共摩擦专家,自从他到庆阳后,国共斗争就更趋尖锐复杂了。钟竟成走后,又派贺其燊接替,贺是江西省永新县人。 贺到任不久,我也调离西峰镇去庆阳,任陇东特委统战部长,孙君一同志接替我为八路军驻西峰镇办事处主任。我到庆阳不久, 陇东特委和庆环分区合并改称陇东地委,仍驻曲子镇,惟地委统战部仍以“陕甘宁边区政府驻庆阳办事处”的名义,驻在庆阳城。
这段时间,党在陇东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和群众抗日救亡活动蓬勃发展,但国共两党斗争日益激烈,直至发展到国民党三次反共高潮。由于党内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对国民党无原则的迁就,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结果把党所领导的抗日群众组织如工会、农会、青救会、抗日自卫队等,全被统到国民党官办的“抗敌后援会”去了。这等于解散了真正的抗日群众组织,完全放弃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和独立自主方针,因而群众情绪一落千丈,当地干部特别象西峰近郊和镇原县一带的干部和积极分子,横遭国民党特务的打击和逮捕,个别甚至被杀害,我们培养的一个当地区长名叫顾登西,就被国民党特务抓到西峰镇杀害了。在我们内部,也有个别人在国民党反共政策的威逼利诱下, 经不起严峻的考验,背叛革命,投奔敌人。经验和教训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毛主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方针的无比正确,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给党的事业带来的严重危害。后来我们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方针,才打退了国民党的反共高潮,把庆阳、合水、驿马关、镇原北三镇的国民党县长、区长“护送”出境,建立起人民的抗日民主政权,各种群众抗日组织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中共陇东地委和专署随即由曲子镇移驻庆阳城内,大灭了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威风,大长了边区人民的志气。
为了坚持持久抗战,克服困难,巩固边区,党中央于一九四〇年制定并实施了著名的十大政策,这就是:加强对敌斗争;建立“三三”制政权;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实行精兵简政;开展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群众运动;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开展生产运动;整顿党的作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等。建立“三三”制政权,是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基本原则,即在政权机构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占三分之一,吸收党外进步人士和开明士绅参加政府工作。陇东地区在一九四〇年春召开了参议会,民主选举民主人士刘仲邠为议长,我当选为副议长。各县也先后召开了县参议会,并选出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了人民法院,普遍推广了当时行政专员马锡五同志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审判方法。评剧《刘巧儿》的故事就是取材于马锡五同志判案中的一个案例。
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到一九四〇年三月,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后,即开始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并早已停发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薪饷,给边区军民生活造成困难。毛主席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边区军民热烈响应,各地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主要是开垦荒地,多打粮食,逐步发展植棉、种油料、蔬菜等经济作物,搞手工业生产,发展畜牧业。地方党政军干部和家属纺棉花、捻毛线,整个边区掀起了热气腾腾的大生产高潮。初期开荒时,群众认识不足,加之有些基层干部强迫命令,群众不愿接受,恰好这年风调雨顺,年景不错,边区政府又规定新开荒地头三年免征公粮,群众生产积极性大为高涨,争着圈地开荒。只用了短短两年时间,基本上实现了丰衣足食和保障供给。军民生活改善,不愁穿衣吃饭,从而促进了人民文化生活的发展,群众自办的业余剧团和秧歌队到处兴起,自编自演革命文娱节目,县县办起了文化教育馆,农村冬学也发展很快,当时陇东地区的最高学府、一所新型的中学——陇东中学,也于一九四〇年九月成立。边区军民大生产的胜利,带来了文化教育事业的欣欣向荣。
一九四一年六月在西吉、海原、固原一带,爆发了回族人民反抗国民党的武装暴动。暴动失败后,这支回民群众武装撤退到陇东地区,驻在庆阳三十里铺,我们当时欢迎他们参加革命,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对党的政策还有怀疑,我们表示愿去愿留悉听自便,去后再来仍然欢迎。马思义是这支群众武装的首领,他急于出去报仇,结果又遭到失败,退回边区,人员减少了许多。这时,马思义同志对党才有了认识,参加了革命,部队改编为回民支队,马思义同志任队长,西北局派杨静仁同志到这支部队工作。 这支部队后来在解放战争中发展壮大,屡立战功,许多指战员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成为共产党员和我军优秀的干部。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开展了整风运动,接着就是审干运动。整风运动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运动,提出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是十分正确的。在审干运动中,清查出少数特务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纯洁了干部队伍,也是必要的。但是,在审干过程中受到“左”的严重干扰,这就是康生搞的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尽管时间很短,由于采取逼供信造成许多冤假错案,把大批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党员和青年知识分子打成国民党特务,把许多地方的共产党地下组织诬陷为“红旗党”,甘肃地下党也不例外。党中央和毛主席发现后, 及时起草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提出“首长负责;自己动手;调查研究;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九条方针,并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才使错误没有继续发展。这次错误在陇东地区也有影响,我当时也执行了上面的错误指示,是有一定责任的,因为这时马文瑞同志已调西北局组织部工作,由、我代理地委书记。在这次运动中,华池县县长第五汉杰在审查中被迫致死便是一例。就当时的客观情况来看,敌情是十分严重和复杂的。由于土匪、反动民团的骚扰,边区人民身受其害,例如当时环县甜水堡有个土匪头子赵老五,经常带领匪徒骚扰边区,奸淫掳掠无所不为,群众无不切齿痛恨。我环县保安大队在大队长刘懋功同志率领下,多次击退他们的进犯,最后消灭了这股匪徒。另一方面,国民党也不断派遣特务潜入边区,刺探我方情况,伺机捣乱破坏,有的甚至已打入我内部充当坐探,敌我斗争是十分尖锐复杂的。也有少数敌人潜入边区后,在人民群众的威力震慑下和党的政策的感召下,主动坦白自首,改恶从善,个别人还参加革命戴罪图功,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经受了“考验,为革命事业做了一定的贡献。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我当选为代表,去延安参加“七大”,由李合邦同志接替了我的工作。此后,我再未回陇东。我在陇东工作阶段,正是抗日战争时期,这是党的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关头,也是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军事上达到完全成熟的重要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正确解决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依靠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克服了重重困难,壮大了革命力量, 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击退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三次反共高潮,使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陷于极大的孤立。当时,我们党已成为一个拥有一百二十万党员全国范围的、有广大群众性的党,这就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解放全中国奠定了思想、政治、组织和军事等方面的坚实基础。
—九八一年八月十九日于青岛海军疗养院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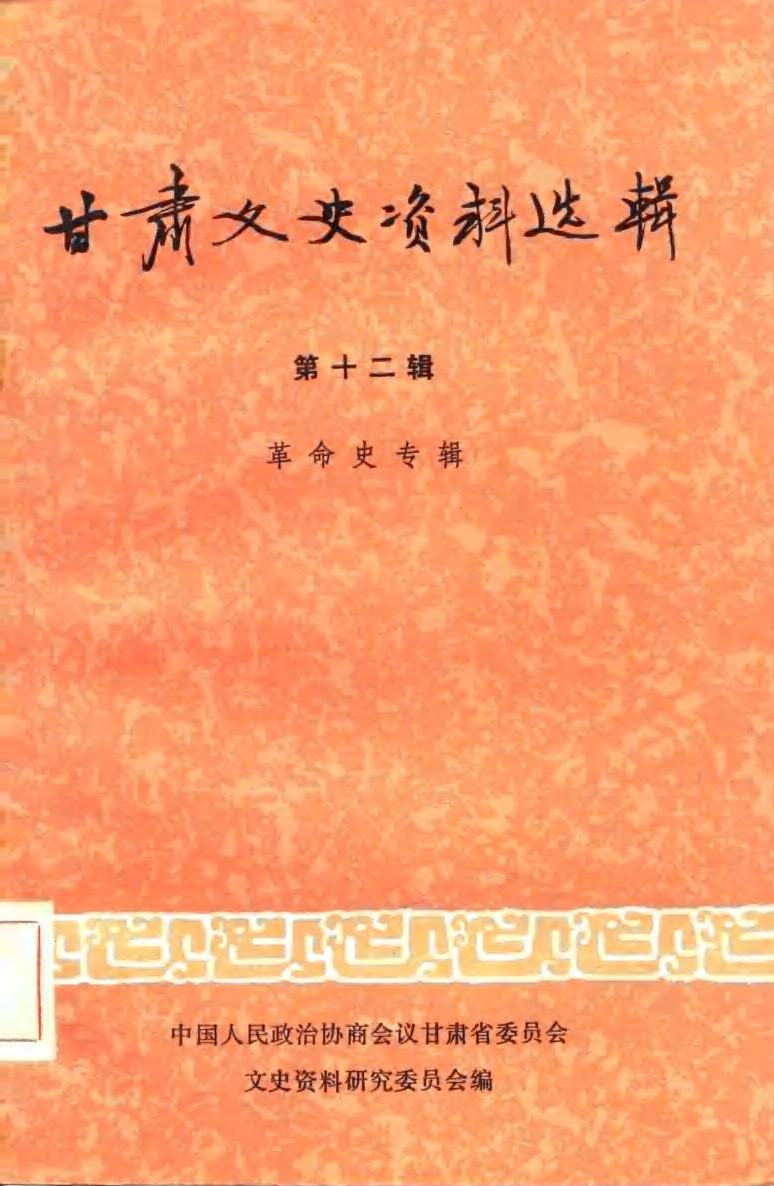
相关人物
段德彰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