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鄂尔多斯式青铜艺术的区系类型、种类和演化
| 内容出处: | 《丝绸之路草原民族文化》 图书 |
| 唯一号: | 290120020210004548 |
| 颗粒名称: | 二、鄂尔多斯式青铜艺术的区系类型、种类和演化 |
| 分类号: | K28 |
| 页数: | 32 |
| 页码: | 379-410 |
| 摘要: | 在我国北方,东从大兴安岭,西至新疆,自古迄今,一直是茫茫的草原。这个草原是欧亚北大陆草原的一部分。古往今来,是猎牧民族活动的苑囿,自商周以来,活动于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的古代民族,大都过着游牧或半游牧的生活,他们不仅创造过在当时堪称先进的经济文化,而且还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草原艺术。其中从商周到两汉的北方系青铜艺术品,是古代北方草原艺术的奇葩,在艺术人类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
| 关键词: | 民族文化 民族历史 |
内容
在我国北方,东从大兴安岭,西至新疆,自古迄今,一直是茫茫的草原。这个草原是欧亚北大陆草原的一部分。古往今来,是猎牧民族活动的苑囿,自商周以来,活动于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的古代民族,大都过着游牧或半游牧的生活,他们不仅创造过在当时堪称先进的经济文化,而且还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草原艺术。其中从商周到两汉的北方系青铜艺术品,是古代北方草原艺术的奇葩,在艺术人类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北方系青铜艺术品,由于最早多数出土于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故被人称做“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又由于鄂尔多斯高原,原属“绥远省”管辖,故又称做“绥远式青铜器”。
近几十年来,由于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带,越来越多的考古新发现,证实这类青铜器的分布范围,远远超过原绥远省地区,更远远超过鄂尔多斯高原,同时在文化内涵上殊为丰富多采,远非“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所能概括,故在我国的考古学界又出现了“北方系青铜器”等称谓。自然,这种称谓,比“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要好些,它所包涵的范畴要大得多。然而,北方系青铜器,从时空来看,它所包涵的内容又嫌过分庞杂,因此很难于准确地表述这种艺术的内容和实质。因此,很有必要将“北方系青铜器”这个无所不包的艺术综合体加以划分,区分为若干区系类型,以便更加准确地显示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化艺术面貌,这将有助于古代北方民族史、文化史和艺术史的研究,有助于对各个民族的艺术界定及其相互关系的探索。
尽管由于这个草原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经济文化的相近,反映在艺术上很相似,但我们观察问题,不仅应看到异中之同,更应分辨出同中之异,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囊括一切的“北方系青铜器”艺术的区系类型区分出来。
按照青铜器艺术品的题材内容、构图技法和艺术风格,从东至西,大约可以区分为以下几个区系类型:东胡系、山戎系、匈奴系和西戎系等四个青铜器艺术类型。当然这个划分是很粗略的,不一定都是准确的,随着考古新资料的不断被发现和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还会有新的类型被识别出来,同时会将划分不准确的地方纠正过来。
东胡系青铜艺术。分布于昔日东胡人分布的范围内。夏家店上层文化即东胡人的遗迹,这几乎是我国考古学界的共识,如果这个认定不误的话,那末夏家店上层文化分布的区域即为东胡系青铜艺术所分布的范围。大致包括今日内蒙古的赤峰地区、哲里木盟及辽宁省的朝阳地区、河北省的承德地区。发现青铜动物纹的主要遗址有宁城县南山根石椁墓、小黑石沟上层墓、敖汉旗周家地墓地等地。①共发现带有动物纹饰的器物近千件。其时代自西周晚期至春秋。
东胡系青铜艺术,若与匈奴、山戎、西戎、塞克人青铜艺术相比,具有许多明显的特点。
首先,从题材内容上看,似乎鸟禽纹出现较多,并极富特色。在兽类纹中,以马、牛、羊、犬等四种家畜最多。野生动物中,以虎纹最多,鹿纹偶见。这与匈奴系青铜艺术中喜欢表现鹿有明显区别。铜带扣虽也不乏其例,但比匈奴人少得多,而且其上的纹饰简单得多。
其次,在构图上,单个动物纹较常见,有些虽然是由多个动物纹所组成,但都是同一种动物的上下或左右有序的排列。给予观者的印象是构图简单而变化较少。
在艺术风格上,以写实为主,追求形似,抽象和变态者罕见,即便是有意变态的动物纹,也很容易地找到艺术的源头,即原来所凭借的对象。以鸟禽纹为例,在艺术处理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表现动态,刻画鸟禽平展双翅飞翔;一种是刻画鸟禽侧立。兽类纹的艺术处理,均以完整的形态出现,或以同一形态有规律排列组合。在对动物的刻画上;虽采用写实的手法,但这种写实,不是对动物外形的抄袭,而是力求在准确地描绘形态中去表现出动物的神韵。比如奔兔、飞鸟、立马,无不形神兼备,栩栩如生。在描绘静卧动物时,既显示了动物的静态,又不失于呆滞无神。在动物纹中,也存在着对表现对象的简化和变形,具有一些写意的意味,比如以人字纹表现鸟禽的羽毛,用圆圈象征动物的眼睛,用重圈表示关节等等。
动物纹给予人的印象是温顺的、和善的,甚至是可亲的,充满了畜牧社会的牧民对动物的喜爱之情,与匈奴艺术中,充满了动物间的厮斗意味,泾渭有别。
在技法上,虽也有透雕、浮雕和圆雕之分,但圆雕一般多限于刀剑柄端的动物,形体较小,立体感也不强,刀环和竿头上的动物,虽立体感极强,但数量甚少。浮雕的方法,或将动物整体凸出;或以凸线表现动物;或用铸出的阴线表现动物。这些都与其他各系青铜艺术品有较大差异。
东胡后来分裂为乌桓与鲜卑。《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说:“乌桓者,本东胡也。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因以为号焉。”乌桓艺术是东胡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乌桓是东胡的后裔,乌桓艺术是东胡的继承和发展,但由于乌桓艺术的时代较东胡晚得多,是汉代的作品,因此乌桓艺术虽与东胡人艺术有某些近似,但也有鲜明的自身特点。
乌桓人的艺术品发现较少,截至目前,比较可以肯定的乌桓人墓群只有辽宁省西丰县西岔沟一处,因此欲说明乌桓艺术,只好举西岔沟乌桓墓群出土品为例。
正如前面“辽宁出土的乌桓青铜艺术”一节所提到的,西岔沟青铜艺术品,出土过二十余面铜饰牌,从这些饰牌中,乌桓人的艺术似有以下几个特点: 在题材内容上,虽仍以表现动物为主,但从动物的种类和习性看,多数以家畜为表现的对象,如马、牛、羊、犬等。各种家畜多为温静安谧之态,显示了进入畜牧社会之后,由于动物早已驯化为家畜,在艺术上所起的巨大变化。
在艺术手法上,技艺娴熟,能用浮雕或透雕表现手法,去灵活多变地塑造对象。喜欢用双双对对的动物,去描绘谐和温顺的家畜。已能用复杂的画面,去描写人对家畜的役使和人与动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行为。
从艺术风格上讲,虽以写实为主,但也不乏抽象的艺术作品,有时故意使物象变态,去追求特殊的韵味和格调,使目睹者产生意想不到的风趣,从而加深艺术的感染力。
鲜卑人的墓群,分布范围广,延续时间长,到目前为止,在昔日鲜卑人的故土上,发现了许多自汉代至北朝的鲜卑墓群,并发掘出土过大批骨、铜、金、陶质的艺术品,这就为我们探索鲜卑艺术的特点和演变提供了可能。
鲜卑人的早期艺术,与乌桓艺术有很大一致性,到了它的后期,由于鲜卑居于原匈奴人的地域内,受匈奴艺术和域外艺术的影响较深,在艺术题材和风格上有一定变化。
大约在汉代,鲜卑人的青铜艺术品与乌桓的青铜艺术品是比较相近的,但在构图方面,也受到匈奴青铜艺术品的影响。比如,匈奴和鲜卑腰带上带扣的形状和纹饰就比较接近。纹饰的题材以鹿和马为主。还出现了几何形饰牌,有的可能是对牲畜圈栅栏的模仿形象。
到了西晋、北朝时期,东部鲜卑与西部的拓跋鲜卑,在青铜艺术方面有较大不同。东部鲜卑,大约还承袭着东胡和山戎的艺术传统,青铜艺术的题材以马为最常见,作蹲踞偃卧之状。比如内蒙古科左中旗六家子鲜卑墓出土的金马饰牌便是一例。而西部的拓跋鲜卑便大异其趣。比如凉城县小坝子滩出土的西晋时期的金银器,其上的动物纹,以众多的动物组成的图案为特征,动物的形象十分抽象。和林格尔县另皮窑村和土默特左旗讨合气村两处北魏鲜卑墓出土的带扣上的纹饰,因受波斯等地金银工艺品的影响,在题材上多以野猪纹为饰,并多镶嵌宝石和珠玉。同时关于鲜卑祖先兴起时的神话题材,仍有保留,比如土默特左旗讨合气村北魏鲜卑墓出土的带扣上的神兽纹便是一例。
西晋至北朝鲜卑人的艺术,不仅以金属为载体,还反映在陶器纹饰方面,形形色色的纹饰多达近20种,陶纹中的马、鹿纹,是鲜卑陶器一大特色。
这一时期,鲜卑人的墓室壁画内容,还受到汉族文化的深刻影响。
综观汉代至北朝鲜卑的青铜艺术,似可得出如下的结论:它的早期,以北方游牧民族传统的艺术为主旋律;到了它的后期,则在传统艺术的基础上,融溶了波斯和中原汉民族的艺术因子。
山戎系的青铜艺术,既不同于东胡系,又相异于匈奴系,它是具有自身特点的。它是具有特定的地域范围、时代界限和具有艺术特色的一种特有艺术。
从分布地域讲,山戎青铜艺术,分布于山戎昔日活动的区域内:大致包括今日的河北省北部、北京北部、辽宁省朝阳地区和内蒙古赤峰地区,这不仅从古文献记载中可以大致推知,也能从考古发现中得到证实。
从发掘出土的山戎遗物看,其时代大致相当于东周,即上限可早到春秋,下限不会晚于战国早期。
从山戎的艺术特色讲,山戎的青铜艺术十分富有特点。题材内容,多表现马、虎和青蛙。马、虎的造型特点是:身躯狭长,背部下凹,垂首,缚尾,腿短而粗,双腿向前,匍匐而卧,呈静态的伏卧式。在工艺技法上,遍体镶嵌多少不一的珠玉之类的饰物。凭借着这些特征,就可以把山戎的青铜器艺术品从整个北方系青铜器综合体中划分出来。
匈奴系青铜艺术,产生早、延续时间长,是我国北方系青铜艺术的主要构成部分之一。匈奴系青铜器,是匈奴人及先匈奴的北狄、猃狁、荤粥、楼烦、林胡等部族制作的。主要分布于:内蒙古西南、陕西北部、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部分地区。
匈奴系的青铜艺术,从制作技术上讲,有浮雕、透雕和圆雕之别,匈奴系和西戎系的青铜制品,其表面锡含量较高,与合金基体之间有明显的分界,多数锡含量大于40%,比一般基体中含锡6%—16%高出许多。表面富锡层的厚度不同,“对取样样品表面富锡层的组织及成分鉴定可知,富锡层内部不是单层,内又分2—3层,每分层的组织及成分有差异,各分层之间互相交错,界限不规则,内层与中层分界处有较多的孔洞,内层包纳基体组织中的铅、夹杂物,渗入基体组织的界限有的也不规则”。①表面富锡的青铜饰品,是将青铜器浸入熔化的锡液中,或者是把液态的锡涂覆在青铜器表面而成的。不过青铜器表面的锡层,有的是一层纯锡,有的则是铅锡合金。若制品单面镀层,多用热擦工艺进行,若双面有镀层,多是用热浸工艺,前法镀层比后法镀层薄。将金属制品浸入熔融的纯锡或铅锡合金中,以获得金属镀层的工艺,称为热浸镀,这是一种古老的传统工艺方法,一直流传至今。由于锡在铜中的可溶性,在纯铜上或青铜上镀锡都比较容易。纯锡熔点为232℃,高出50—100℃熔化时,对被镀制品的性能不致于影响太大。在热浸镀时,熔融状态金属与基体金属之间相互扩散,互相熔解,形成一层金属间化合物组成的合金层。镀层与基体金属是冶金结合,故相互粘黏力较强,镀层不起皮,也不脱落。在合金层外,还会存在一层纯锡或铅锡合金。
在进行热镀前,制品需经过仔细的镀前准备,包括除油、除锈和一定程度的表面光洁度的获取等工序。据oddy等记述的热镀锡的方法是:“在已完成镀前准备的铜或青铜制品表面上,放少许松香,制品在炭火中加热,松香熔化后布满制品表面形成熔剂层,以防止当温度增加时,基体金属进一步氧化。将锡球或锡箔放在制品表面上,制品加热到比纯锡熔点高50—100℃,纯锡完全熔化,将金属制品反复倾斜,使熔化的纯锡在制品表面覆盖完全。制品移出加热源,在锡尚未凝固时,用一块皮革或旧布擦拭制品表面,除去多余的纯锡,从而获得平滑均匀的薄层镀锡膜。”②应用此法,可得到单面镀锡表面层,但镀层厚薄较难控制。
“Tylecote进行镀锡的模拟实验是用含锡16%—18%青铜作样品。Zncl作熔剂,将样品(20℃)插入熔化的锡液中,锡液放在熔罐中,并保持一定温度(234、259、271及320℃),控制样品插入锡液的时间(2、10、15秒),得到镀锡层的厚度为4—50微米。应用这种热浸镀锡方法,得到的是双面镀锡表面层,镀层厚度可由插入锡液的时间进行控制。”①铅锡合金也可以用来作为镀层合金使用。Tylecote用熔化铅锡合金进行了热浸镀模拟实验,得到的镀层较用纯锡作镀层金属时的厚度略薄。
在埋葬环境中存在着电解腐蚀,纯锡相对于铜和低锡青铜是阳极,故锡层易穿孔。若表面层由高锡合金构成,相对于基体金属则是阴极,将能较好地阻止正常电解腐蚀。因此,高锡合金镀层的抗腐蚀能力比纯锡镀层更强,且能保持银白色的光泽。故西戎系和匈奴系制品表面具有高锡合金镀层者比纯锡镀层者更稳定。
西戎系和匈奴系青铜饰品,经过镀锡表面处理后,能较好地保持银白色光泽,不易生锈,又比使用银便宜,同时还可以减缓铜制品的进一步腐蚀,有助于延长制品的寿命。这些优点已由发掘出土的较多镀锡制品所证实。古代青铜制品表面镀锡处理的目的,不管当初是否为了外观美丽、实用和耐蚀,但达到了此种功效,那倒是事实。
表面镀锡制品的大量出现,不仅从艺术上,而且从制作技术上来说,无疑是一种进步,可以认为这是西戎系和匈奴系青铜制品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公元前6—4世纪,我国西北和内蒙古西南地区的西戎和匈奴系的游牧民族部落,已用镀锡的青铜制品。而在同一时期,东胡系和山戎系墓葬中,至今没有发现镀锡的青铜制品。这是草原东西部生产技术发展不平衡,抑或青铜艺术品的地域性和民族性所造成,目前尚难遽断。但应该指出的是,自新石器时代开始,草原东、西地区便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这种不同是可以理解的。
匈奴系青铜艺术。大约从东周至两汉,分布范围十分辽阔。匈奴文化是由不同的氏族部落融合而成的,反映在艺术上,各地不同的部族间是不尽相同的。但共性是主要的,我们从宏观上归纳区分北方系青铜艺术的区系类型时,可以不必去考虑这些细节问题。
匈奴系青铜器的动物形象,早期(东周)多虎、豹、狼等野生形象,造型生动,野性十足,以野生动物间的撕咬、搏斗和肉食动物对草食动物的吞噬为主要特征。晚期多马、牛、羊、犬、驼等家畜形象,动物的形象是温顺和驯服的,多表现人对动物的役使,动物与动物和人与动物的关系显得和谐温馨,全无敌意。这是猎人转变为牧民、狩猎社会转变为畜牧社会在艺术上的反映。
西戎系青铜艺术。西戎包括緜诸、绲戎、翟?、義渠、大荔、乌氏、朐衍等多种戎人。大约自青铜时代至东周,西戎长期居住于甘肃、宁夏南部和青海省东部一带。但西戎系青铜器,截至目前为止,仅见出土于宁夏南部的固原地区和甘肃的庆阳地区。
从总体上讲,西戎系与匈奴系的青铜艺术品比较接近。在制作技术上,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甘肃庆阳、宁夏固原地区、内蒙古凉城等地出土的西戎、匈奴系的青铜艺术品,其表面锡含量较高,与合金基体之间有明显的分界,多数锡含量大于40%。制作手法,都有浮雕、透雕和圆雕之别。西戎系青铜艺术品的纹饰,多表现肉食动物对草食动物的吞噬,尤其喜欢表现虎和虎对鹿的吞食。此外,还有龙和蟠虺等形象。在艺术风格上,虽然以写实为主,但也不乏抽象化的作品,比如固原和西吉出土的鸟形饰,皆作双鸟合体之形,十分抽象化和几何纹样化。固原出土的“涡纹饰”铜饰件,是鸟形饰的高度抽象的结果。固原西戎墓出土的圆形、三角、菱形等形状的铜饰牌,是对现实存在物图案化的结果。
总之,由于我国北方草原的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经济生活、以及各民族心理基质的相近,反映在文化艺术上,尤其是在青铜艺术上,各民族青铜艺术的大同总是问题的主流。但是,又由于各游牧民族的文化传统的不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与之相关的技术水平和文化水平的差异性,各民族的青铜艺术,不仅每个民族由于时代的不同而有变异,各民族在同一历史时期青铜艺术在题材内容、制作方法和艺术风格上的差别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就为我们区别出各自不同的区系类型提供了可能,而对北方各游牧民族青铜艺术区系类型的划分和确定,对研究各游牧民族的历史、文化和艺术有重要意义,这样可以把笼统的、无所不包的、含混的、不确切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这一称谓逐渐分解开来。
青铜器艺术品,多数出土于游牧民族的墓葬之中。其种类有仪仗用的铜竿头、身饰、服饰、佩物饰、器物饰和明器等。
第一类是仪仗用的铜竿头。竿头下有一个圆筒形或方形的铜柲,其上有马、鹿、刺猬、羚羊、虎、狼、鹤、盘羊形圆雕动物形,銎口呈圆形或方形,原来安插着木柄,供举行各种仪式时执用。过去的研究者,每每称之为“竿头”①或“车饰”②,但前一种称谓,并没有说清楚它的功能,后一种说法也未能说明是车上哪一个部位的装饰。这些说法都是没有说服力的。随着匈奴考古的新发现,为研究匈奴的历史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资料,并为探索“铜竿头”的功能成为可能。
到目前为止,出土铜竿头的地方有内蒙古伊克昭盟准格尔旗速机沟、玉隆太、瓦尔吐沟、西沟畔等地和陕西省神木县纳林高免等地,即从陕西北部到伊克昭盟地区,在黄河呈“n”形的河套之内,那里适当匈奴的故土。出土铜竿头的匈奴墓的时代,约从战国至西汉时期,这时正值匈奴鼎盛之时。
由以上出土情况似可推知,在匈奴故土上出土的铜竿头是匈奴举行礼仪仪式的用具。缅怀当年的匈奴人,一定在定期举行祭祀仪式的地方,在部落大人的率领下,手里高高擏起铜竿头,嘴里喃喃地念着祷词,在神像面前一圈一圈地舞动。匈奴人迷信至深。《史记·匈奴列传》谓:“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祭地先、天地、鬼神”,又谓:“而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举事而候星月,常随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可惜这里没有把举行祭祀仪式的全部细节描绘出来,由于铜竿头的出土,为我们想象和重构匈奴的祭祀仪式提供了可靠依据。
匈奴举行祭祀仪式,并不是随便找个场所举办一下了事,而是有一定的时间和场地,因为在匈奴人看来祭祀是一件神圣的事情,前面提到的“单于庭”和“茏城”便是两例,而且是专指由“诸长”所组成的国家级的祭祀仪式。上有好者,下必效之,匈奴普通民众亦必有自己传统的习惯的祭祀仪式方法。当时匈奴民众的祭奠仪式虽因古文献没有记载不得而知,但考古上的新发现,却为探索这些问题露出了蛛丝马迹。比如,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宁夏、江苏等地,发现了大批刻在石面上的面具岩画,少则一两个,多则数十个,这些由面具所体现的祖先、天神地祗和鬼神,便是当时祭祀的对象。
除了定时定地举行祭祀外,人死后,尤其是首领和特殊身份的人(如巫觋)死后,便要举行盛大规模的祭祀仪式,铜竿头的被发现,便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在准格尔旗速机沟,当地农民千四板定在那里挖窖时出土了一批铜竿头,计有鹤羊形、羊形、狻猊形、屈肢马形、长喙鹤头形、狼头形等六种鸟兽形动物,还有大小铜铃各二件。值得注意的是,与铜竿头一同出土的还有二件单系圆盘。奇怪的是,就是没有发现人骨。可见它并不是一座匈奴墓,也不是一座寻常的什么窖藏文物,而应当是匈奴的祭祀坑。
无独有偶,在其他地方和民族也有类似的祭祀坑。比如四川广汉三星堆巴蜀文化中的1、2号祭祀坑,便与之类似。1号坑内出土有:金杖、面具(包括金面罩和青铜人头像)、青铜酒器、青铜兵器、玉石礼器,以及十余根象牙和3立方米左右的烧骨碎渣。那是举行一次盛大的宗教礼仪之后而埋入的。①2号祭祀坑,首先投放的是海贝、玉石礼器、青铜兽面具、凤鸟、小型青铜杂件和青铜树枝、树干等。这些遗物在清理时,大部分都杂在灰烬的炭屑里,并留下了明显的烟熏火烧痕迹。其后再投入大型的酒器(青铜容器)和立着的巫师长(青铜立人像)、面具(包括头像和面具)、树座。最后投放象牙。根据遗物的火烧痕迹,结合文献记载,有理由相信,当时的祭祀,应有“燔尞”祭天,“〓埋”祭地,“悬庪”祭山等形式,2号坑正是一次重大综合祭祀活动的遗存。②类似三星堆的1、2号祀坑在陕西汉中地区也发现过。③ 可见见于准格尔旗速机沟的匈奴祭祀坑并非历史上的偶然现象,而是在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分布很广的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令人遗憾的是速机沟匈奴祭祀坑是农民挖开的,没有经过科学发掘,致使许多文化现象没有弄清楚。
其他如玉隆太、瓦尔吐沟、西沟畔和神木县纳林高兔等地古墓中出土的铜竿头,也是祭祀用器具,即仪仗顶端的饰物。但并非所有匈奴人死后都以这类仪仗埋入。考古发现证实,以仪仗葬入墓内的并不占多数,只是一些具有特殊身份的人,才在墓中发现有仪仗(因木柄已腐烂,只能看到仗顶的动物饰件)。
埋有仪仗头的匈奴墓,死者的身份估计有两种可能:其一,死者生前的身份是巫觋,葬入的仪仗,是死者生前参加祭祀仪式时常用之物,这些仪仗,不仅是死者生前喜爱之物,而且简直可以视作神圣之物,死后将它作为随葬品而埋入墓中,应是情理中的事情;其二,是氏族部落中的头面人物,因此,当人死后,要在墓地举行祭奠仪式,待丧礼过后,即将举行仪式时用过的仪仗投入墓中,作为随葬品,这应视作氏族部落的首领,死后享有他人无以伦比的殊荣的一种表现。看来第一种可能性要比第二种大些,因为匈奴社会中巫风炽烈,巫觋是社会上一种不可小视的社会力量,他们的人数多,巫师作法和祭奠活动也是很频繁的。这在《史记·匈奴列传》和《汉书·匈奴传》等古文献中多有见及,现举数例予以证实。
匈奴人迷信甚深,这些迷信活动,通常是由巫觋来实现的。比如汉贰师将军李广利投降匈奴后,丁灵王卫律妒忌他得宠,乃串通胡巫陷害贰师,假托已死的“先单于”降言要用贰师作牺牲,血祭胡社。于是单于逮捕贰师,贰师骂曰:“我死,必灭匈奴。”会连续雨雪数月,牲畜死亡,人民疫病,谷稼不熟,单于恐惧,为贰师设立祠室。①《汉书·西域传》下说:匈奴使巫埋牛羊于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赠给汉帝的马、裘,常先使巫祝之。可见巫对于匈奴的军事和政治影响都很大。胡巫所用的法术通常是咒语,降汉的匈奴人遒侯隆强之子和容成侯唯徐卢之孙,都曾因为使用胡巫祝诅汉帝而被削爵。②汉武帝征和时,汉军追击匈奴兵,至漠北的范夫人城,这个范氏是个能“胡诅”的女人,可见城主范夫人原先也是个胡巫。③ 这种胡巫,后来由于匈奴人的不断附汉而流入中原地区。汉安定郡所属的朝那郡(今甘肃平凉县西北)有端旬祠15所,祠内有胡巫祝诅。①汉朝宫廷中也有不少胡巫,比如《汉书·江充传》和《汉书·戾太子传》就记有江充串通胡巫陷害戾太子的事件。
匈奴人祭祠的地点和仪式,除了上述的单于庭之外,还有茏城和蹀林。“蹛:者,绕林木而祭也”②。上文提到的匈奴人以贰师血祭“胡社”,可知那里也是祭奠之处。
由以上胡巫的职司和行为看,他们生前有仪仗之类的法器,死后埋入墓中是完全可能的。由于匈奴仪仗用的铜竿头的发现,及其功能的被认定,为了解匈奴人的原始信仰又找到了新证据。
第二类是服饰。死者身着的葬服虽已腐烂,然而缀连于衣服上的饰物却依然存在。主要包括有冠饰、纽扣、腰带扣和带钩等。这些衣服上的附着物,从服饰的角度,展现了古代游牧人审美观念的一个侧面。
截至目前,已发现的北方游牧民族的“胡冠”有三套。其一,前面已经提到,就是杭锦旗阿鲁柴登匈奴墓出土的胡冠,它的装饰部分由冠顶、冠带两部分组成,全是金制品。冠顶上面是一个半浮雕的狼咬羊图案,浮雕于厚金片锤鍱而成的半球体表面,半球体表面从中间四等份为夹角90°的扇面形,展翅的雄鹰傲立于半球体之上。鹰的头、颈由绿松石做成,颈的上部与头相连处,有精细的金片做成的项链,头、腹是用通过颈部的金丝连结成一体的,尾部是插入的,以金丝相连结,头、颈、尾都可左右摆动,活龙活现,栩栩如生,整个冠顶,宛如一只在蓝天上翱翔的雄鹰俯视地面上狼咬羊的生动画面,而这种画面又是草原上常见的情景。冠带由三条半圆形金条围合而成,冠带前部有上下两条,冠带后边一条,并以两端的榫铆联结在一起,组成圆形的冠带。冠带左右靠近人耳处,每条两端分别浮雕伏虎、盘羊、马等动物图案。冠顶与冠带间,原应有皮制品或丝织品联结,惜已腐烂无存。
其二,是陕西神木纳林高兔出土的“胡冠”,仅残留圆雕神兽形金冠顶上的饰物,原来胡冠的形制虽已难测知,但其雄姿犹存。这两顶冠饰都十分讲究,是匈奴首领在特定场合才戴的胡冠上的装饰。冠饰制作精工,在取材上富有浓郁的草原气息。
其三,是准格尔旗西沟畔4号墓出土的头巾饰。出土时已凌乱,但大体可复原:上部中间,有椭圆形包金贝壳饰,左右排列有云纹金饰片,稍下有圭形包金花边的贝壳饰左右成行排列;下部有三排云纹长条形金饰片,下垂一道道熠熠发光的菱形金属珠。从组成头饰的金饰片上的钉孔和贝壳饰上的纽孔推测,这些头饰构件原来是缝缀在头巾之上的。
这件头巾上的饰物,是中外经济交往、文化交流的产物,类似的巾饰或冠饰在西方多次发现过。比如在第聂伯河沿岸捷尔特穆里克斯基泰王墓中,发现过顶部饰有12个狮子的冠饰①。又在顿河下游诺沃切卡斯克萨尔马特王墓中,出土过呈带状的金冠,其上缘是鹿嘴衔轮状物在林中奔跑的图案,并有两只似鹅的禽鸟;中部镶嵌有水晶、宝石、玉髓、戴冠的妇女胸像和猛禽;下缘垂挂有两个把手的壶形物②。有人认为,此冠是戴在头巾或面纱上的③,这与西沟畔四号墓出土的头巾饰很近似。而捷尔特穆里克王墓出土的冠饰,又与阿鲁柴登和纳林高兔匈奴墓胡冠上的饰物接近。
纽扣,普遍出土于各地的游牧民族的墓葬之中,形制各式各样,多数加以装饰,使之既有使用价值,又有观赏价值。观之,使人赏心悦目,产生美的娱乐。现将各个墓地出土的纽扣列表于下:从上表看,纽扣散见于古代北方各游牧民族的古墓之中,同时大都是在衣服之上的。但它并不限于衣服上,比如凉城毛庆沟楼烦墓中的纽扣,除衣服上之外,还有在腰带上、手套上和剑鞘之上的。看来它的功能有二:其一,是衣服上的扣子;其二,是装饰在各种物件上的装饰品。应当指出的是:过去被人称做“铜泡”的东西,实际上是纽扣。首先,它的大小正有扣子那么大;其次,出土的位置在衣服上;其三,其背后有纽,可以缝缀在衣物上。还有过去被称做“铜泡饰”的东西,也应是扣类,因其边缘有小圆孔,可缝连在衣物上,其大小、样式也与纽扣一样。纽扣不仅有使用价值,它的观赏价值也是望而可知的。
带扣,是先秦至晋代北方游牧民族衣服上重要的金属括结具。带扣又称带卡、扣绊、带铰或带鐍。古人对带扣很讲究,十分注重它的精美。带扣的质料有铜、金、银、玉等,也有在铜带扣外面包金或鎏金者。历来从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古墓中出土的带扣,品种多样,形状繁复。由于带扣的品类繁多,研究者对带扣的分类问题每感困惑。近年来,孙机先生根据国内外出土的大量带扣资料,对带扣进行了分型分式工作,从而使对带扣的认识有了新的突破。①根据孙先生的意见,带扣可分做三种类型:I型,无扣舌;Ⅱ型,装固定扣舌;Ⅲ型,装活动扣舌。
以无扣舌为特征的I型带扣又可分为两式:I型1式,既无扣舌又无穿孔;1型2式,是在一条腰带中的2枚带扣中,其中1枚的一侧有穿孔。I型2式带扣是由I型1式发展而来的。
1型1式,即上文提到的既无扣舌又无穿孔的带扣。在我国,此式带扣约出现于春秋时。内蒙古凉城毛庆沟5号春秋晚期的北狄墓,有2件大小一致的虎纹带扣左右对称地摆在死者腹部前面(即腰部),看来原装于腰带会合处两侧,其前部和后部各有圆孔,以便缝在腰带上。这两件带扣均无括结装置。带扣的使用方法,只能像斯基泰人那样,他们遍装“饰牌”的腰带,其长度大致为腰围相等,两端在腰前会合对齐,各端再接续出一段窄带,用此窄带打结扣系。②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另皮窑与土默特左旗讨合气出土的铁芯包金之猪纹与神兽纹带具中,各有二枚成对的马蹄形带扣,既无穿孔也无明确的扣舌,无疑应属于I型1式。两地带扣各有2枚接近椭圆形的带环,形制与老河深所出土者相同,可以确认是腰带上的装饰。讨合气出土4枚长条形带銙,也是腰带上的装饰,束腰时用两带扣之间的窄带相系结。
I型1式的带扣还有许多,如杭锦旗阿鲁柴登发现的匈奴金银器中,有12枚铸成头生多枝长盘角的虎状怪兽的金带具,原来是装在一条腰带上的。准格尔旗西沟畔2号战国匈奴墓出土的金饰片等,都属此种类型的带扣。与毛庆沟带扣时代相近的哈萨克斯坦伊细克(lssik,在阿拉木图附近)塞种王墓中,死者腰带中部也装有左右对称的此种式样的金带具,并依次向后排列。带具呈鹰喙鹿身、头生多枝长盘角的神兽形。此带具与阿鲁柴登发现的匈奴金带扣,在形制上尤为相似。在塞种迤西的斯基泰人那里,也能见到I型1式带扣,乌克兰切尔卡萨州Berestnya3i村之前5世纪的斯基泰古墓中所出青铜带具,以八枚为一副,腰前二枚呈侧视的狮头形,体积较大,显得特别突出,两边则装有较小的兽面形饰牌。①这些情况表明,此时生活于欧亚草原上的北狄、匈奴、塞种、斯基泰等游牧民族的带具形制是比较接近的。
至西汉时,I型1式带扣得以广泛传布,北自蒙古草原,南抵广东,到处都出土过。比如,南西伯利亚出土有双龙纹金带扣②,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出土有蟠龙双龟纹鎏金铜带扣,而在西安三店村西汉墓及江苏扬州西汉“妾莫书”墓中,也发现过同类之物。
I型2式带扣,是在腰带两端相接处的两个左右相对的带扣中,其中一枚的一侧有穿孔,这样便可只用一条窄带来系结,腰带一端的窄带可以通过另一枚带扣之穿孔,绕回来再系结。它是由I型1式发展而来的。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同心倒墩子19号西汉匈奴墓出土的双马纹1型2式鎏金铜带扣,所开穿孔使马嘴部的图案受损。杭锦旗阿鲁柴登发现的战国匈奴遗物中有此式的金带扣,铸出浮雕式的四狼噬牛纹,带穿孔的那一枚在牛鼻上硬凿开一个洞,以致图案又受到破坏。
I型2式带扣,在匈奴遗物中多见之,除上举两例外,诸如准格尔旗西沟畔2号战国墓和同心倒墩子5号西汉墓中都有发现。内地亦有此式之精品出土,如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出土过十余枚此式带扣。① I型带扣,颇似班固《与窦将军笺》所称的“犀毗金头带”之金头,因为I式金属带扣装在腰带两头,具有明显的装饰作用。至于所称的“犀毗”,颜师古在《汉书·匈奴传》中解释说:“犀毗,胡带之钩也;亦曰鲜卑,亦谓师比,总一物也,语有轻重耳。”又《楚辞·大招》以“小腰细颈,若鲜卑只”的句子来形容“腰支细少,颈锐秀长”的“好女之状”,由此观之,“犀毗”似指带钩而言。但据上海博物馆所藏“庚午”(371年)玉带扣上的“御府造白玉衮带鲜卑头”之铭文②,则鲜卑应指带扣。二者仿佛存在着矛盾。实际上,无论带钩还是带扣,凡属胡带用的括结具,大约均可称做犀毗或鲜卑。
Ⅱ型带扣,既有系结用的穿孔,又有固定的扣舌。在我国北方匈奴、鲜卑等草原民族中广为流行,除宁夏、内蒙古屡有出土外,在匈奴居住过的南西伯利亚地区也多有出土。从外形轮廓看,有圆形、长方形、马蹄形与不规则形等。按使用情况,Ⅱ型带扣可分作二式:Ⅱ型1式,一条腰带只装1枚带扣,是单独使用;Ⅱ型2式,一条腰带上装2枚带扣,成双使用。
Ⅱ型1式中的圆形带扣,在春秋时期至战国早期的杭锦旗桃红巴拉1、2号墓中已经发现。关于它的来源,“其直接的借鉴应得自内地马具中之扣具”③。关于这一点,可从陕西凤翔马家庄1号春秋中晚期建筑群遗址之车马坑内出土的金质和铜质“圆策”得到启迪,都在圆环上装有向外伸出的固定扣舌,其形状与内蒙古博物馆所藏Ⅱ型1式圆形铜带扣的构造基本一致。将马用扣具上的固定括舌巧妙地改用于腰带带扣上来,使带扣的括结功能大为改进和加强,这是我国古代北方草原民族在吸收基础上的一种创造。
Ⅱ型2式带扣,其形状有马蹄形、长方形和不规则形三种。满洲里市扎赉诺尔和吉林榆树县老河深两地之鲜卑墓所出土的马蹄形带扣,它们皆为铜质鎏金并饰以鲜卑神兽纹,是Ⅱ型2式带扣中的有代表性的作品。此外,南西伯利亚出土的时代约属战国的不规则形怪兽噬马纹金带扣,其上之后身极度扭曲的马,在斯基泰和塞种金饰上出现,也在宁夏固原红庄出土的战国西戎金带具上见过。①可见Ⅱ型2式带扣,广泛地见于鲜卑、匈奴、斯基泰和塞种等多种游牧民之中。
在此型带扣中,起括结作用的是铸出固扣舌的那一枚,而对称的另一枚,则只起装饰作用。本来一枚已敷用,而还要在对面增加一枚,看来是受I式带扣的格局影响所致。Ⅱ式带扣的括结法,在内蒙古凉城毛庆沟59号楼烦墓及完工鲜卑墓中均由残存的革带反映出来,那是将其一端的窄带自下而上通过对面的带扣之穿孔, 再折回来用扣舌勾住,则腰带便可束紧,估计多余部分则在当中垂下。
Ⅱ型带扣,大约相当于古籍中所称之带鐍。《说文·角部》谓: “鐍,觼或从金、矞,”“觼,环之有舌者”。段玉裁注:“环中有横者以固系”则鐍是有“固系”之舌的括结具,与此型带扣的性状大体是相合的。
Ⅲ型带扣装有活动的扣舌。按照使用情况,也可分作两式:Ⅲ 型1式,单独使用;Ⅲ型2式,成对使用。Ⅲ型带扣,也是受马具用扣具的影响而制作的。始皇陵2号兵马俑坑T12出土的陶鞍马腹带上所见之扣具,已装有活动扣舌。①Ⅲ型1式带扣最早见于西汉,比如云南晋宁石寨山7号西汉墓出土的银带扣,其形制与平壤贞柏洞37号乐浪墓所出虎纹银带扣极为肖似。②这2枚带扣的穿孔呈弧形,位于扣体前部,扣舌较短,其他汉代金、玉带扣亦无不如此。新疆焉耆博格达沁古城黑圪垯与平壤石岩里9号乐浪墓所出形制相近的龙纹金带扣,均长约10厘米,锤鍱成型,作群龙戏水图案,龙体上满缀大小金珠,工艺精湛。这种富丽华美的金带扣,直至西晋,仍可在湖南安乡刘弘墓出土的龙纹带扣中见到。
Ⅲ型2式带扣,多见于晋代。比如辽宁朝阳袁台子东晋墓、江苏宜兴元康七年(297年)周处墓均曾成对出土。
Ⅲ型1式和2式的括结方法,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根据孙机先生的研究,宜兴周处墓所出Ⅲ型2式带扣及同出之带具,其系结方法与老河深105号墓出土带具相同。③ 虽然这里的窄带贯穿的是装活动扣舌的带扣,却依然要折返回来将多余的部分于腰腹中部打结下垂。Ⅲ型2式带扣的括结法应与周处墓出土带具使用方式基本一致,只不过仅用1枚带扣而已。
进入南北朝以后,我国带具的形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时装活动扣舌的小带扣已在腰带上广泛使用,扣身只以简单的横轴支撑扣舌,腰带也变成前后等宽的一整条,并迅速向鞢〓带过渡。革带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带扣的类型略如上述,我们再看腰带上的装饰。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对腰带的装饰十分重视,根据饰物在腰带上的位置及其功能约可分作三种:其一,它是一种纯装饰性质的,其高度与腰带的宽度正同,竖着固定于腰带上。带饰形状各有不同:或呈长方形,或呈联珠形,或呈卷曲的双鸟纹。
其二,呈半悬挂式,饰件的上端固着在腰带的下缘。
其三,是悬挂在腰带的垂饰物,其中有铜环、联珠、鸟兽纹饰牌、扣饰、管状饰、棒形饰、饰针、动物形垂饰等。
上述情况,是仅就一般情况而言的,事物往往是很复杂的,同一种装饰品常常装饰于不同的部位。以联珠状铜饰为例:凉城毛庆沟3号墓出土的Ⅵ式联珠状铜饰,均装饰在腰带之上,《内蒙古·长城地带》一书的作者,根据围场东家营子的发现,也认为它装饰于革带上。宁城县南山根夏家店上层文化墓中发现的此种饰件,服饰在衣服前衿上,赤峰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中发现的,整齐地排列于头部。杭锦旗桃红巴拉发现的,多数散落在足部。看来有些饰物的装饰位置是有随意性的。
带钩与带扣都是腰带头供系结之物,本是中原地区普遍流行之物,在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地区,它常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共出,与青铜带扣配合使用或交替使用。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出土数量较多,仅凉城县毛庆沟楼烦墓地就出土有16件,其中铜带钩13件,铁带钩三件。北京延庆军都山东周山戎部落墓地也有出土。根据目前的发现,至少在春秋早期就出现了带钩,最早的带钩仿自飞禽走兽,后来逐渐发展成鸟头形、琵琶形、棒形、竹节形,最后铁带钩又代替了铜带钩。带钩在我国北方草原,流行时间很长,大约从春秋早期,经战国直至汉代。
带钩是将使用功能与审美功能巧妙结合的生动体现,一方面它是腰带上的构件,起着括结腰带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又是制作者审美观念的外化形式,内中蕴寓着美的意味和对美的追求,使目睹者产生美的愉悦。
第三类是身饰。包括有头饰、耳饰、项饰和手饰。饰于头部和颈部的珠饰,在北方游牧民族中十分普遍,是古代北方草原民族古墓中常见的出土物。比如杭锦旗桃红巴拉狄人古墓群出土石串珠349枚,凉城县毛庆沟狄人、楼烦古墓出土各类料珠200枚。其他如乌拉特中旗呼鲁斯太匈奴墓、西丰县西岔沟乌桓墓群、敖汉旗周家地东胡墓地、榆树县老河深鲜卑墓、怀来北辛堡山戎墓、宁城县南山根102号东胡墓、张家口市宣化县小白阳地山戎墓、北京延庆军都山东周山戎部落墓地等游牧民族墓地,都出土了许多珠饰之类的装饰品。各地出土的珠饰,种类繁多,形状各异,大小不一,主要有骨珠、石珠、玛瑙珠、水晶珠、绿松石、琉璃、琥珀、料珠、海贝、珊瑚珠、珊瑚枝饰等。其形状有:柱状、棱柱状、扁圆形、长方扁平、圆管形、菱形、方柱状、球形、梯形等。出土的部位,在头部、项部或胸部。它应是头饰、项饰和额饰。
头饰,一般是冠帽或头巾上的饰物,前文提到的准格尔旗西沟畔汉代匈奴墓地4号墓出土的头巾上的装饰品便是典型一例。此外,凉城毛庆沟3号墓和5号墓死者头颅周围的料珠,看来原来也是死者的头饰。
项饰,一般只出土于比较讲究的墓葬中,看来比较富有的人才戴项饰。项饰的种类颇多,见于古墓的古代游牧民族的项饰,有金项圈、银项圈,和由各种串珠组成的项链等。
金项圈共出土三件,其中阿鲁柴登出土2件(其中1件残),西沟畔2号匈奴墓出土一件。西沟畔匈奴墓出土者,是用金条围成的,长1.42米,重达502.5克,绕周圈套于颈部,非常豪华壮观。一般说来,金项圈、金冠或头饰成套共出,看来是达官贵人的墓葬。
银项圈,用银条围圈而成,仅在准格尔旗玉隆太和瓦尔吐沟出土过。其中瓦尔吐沟出土的银项圈的一端饰有虎咬羊动物纹,富有浓郁的草原风味。
串珠组成的项链。在已发掘的古代游牧人的墓葬中,多数墓出土有各种质料制成的串珠。比如敖汉旗周家地东胡墓群45号墓,在死者胸上,有排列十分整齐的箕形蚌项饰①。榆树县老河深1号鲜卑墓群环绕颈部为一件颈饰,这串颈饰由266颗玛瑙珠和六只金管组成。玛瑙珠为圆形,大小不一,桔红色。金管呈圆筒状,相隔穿于玛瑙珠之间。56号墓,出土一件玛瑙串珠链组成的项链,有玛瑙珠78颗,其形多为圆形与椭圆形,也有六棱或七棱,珠孔为一面钻或两面对钻,颜色有红、桔红、桔黄、黄色等。58号墓出土项饰一串,由玛瑙珠串连而成,现有玛瑙珠39颗,形状为六棱形和圆鼓形,珠孔对钻,颜色红色和桔红色。杭锦旗桃红巴拉和公苏壕七座墓均出土有串珠。凉城毛庆沟有31座墓发现有串珠。准格尔旗西沟畔汉代匈奴12座墓,只有4号墓出了串珠。各墓项饰串珠大同小异,比如毛庆沟65号墓的项链,由绿松石、骨珠、铜铃形饰组成。毛庆沟5号墓出土项链,由玛瑙、绿松石、水晶珠等组成。桃红巴拉狄人墓出土的项链,则由水晶、绿松石、玛瑙、骨珠组成。西沟畔4号汉代匈奴墓串珠项链,据出土时观察,由两套组成:一套由大型水晶和玛瑙组成;另一套由小型的水晶、琉璃和琥珀组成。各种串珠色彩斑斓,五光十色,十分美观。北京延庆军都山东周山戎墓群发掘证实:这里男女老少都有佩戴项链者,由各种质料制成的项练多佩于死者胸前。相当一部分男性死者和少数儿童及婴儿,以及个别女性死者,在颈下佩戴各种动物形铜牌饰,少数身份高贵的男性死者佩戴金璜饰或金虎牌饰。河北宣化县小白阳山戎墓地出土的项链,质料有玛瑙绿松石和铜珠。
由串珠组成的项链,盛行于春秋战国,到汉代便逐渐减少,它既反映时代特征,又体现了死者的身份差别。考古发掘资料显示了如下的事实:相当于春秋晚期或战国早中期墓,串珠组成的项链,普遍出土于中小型墓;战国晚期以后,小型墓仍出土由各种料珠组成的项链,而大型墓则出现了银项圈和金项圈。
额饰较少见,仅在西沟畔4号墓,在死者额部有菱形垂珠。
耳饰较多,有耳环和耳坠等。形制各异,兹列表说明如下。
成的项链,而大型墓则出现了银项圈和金项圈。
额饰较少见,仅在西沟畔4号墓,在死者额部有菱形垂珠。
耳饰较多,有耳环和耳坠等。形制各异,兹列表说明如下。
桑变迁,戒指的样式也起了变化。凉城县小坝子滩拓跋鲜卑墓出土的金戒指十分名贵,在金光灿灿的戒指上,饰以兽头形。
死者的身饰,是其生前身饰的反映,而服饰又是身饰的扩大。身饰与服饰,在颇大程度上反映了死者所处时代的审美观念和对美的追求。
第四类是佩饰物,包括刀饰、剑饰、锥饰、针饰及其他各种人身佩饰物。这些佩饰物都与身饰和服饰密切相关。
上文提到的腰带饰物,实际上是佩饰物的一部分,但它以腰带为附着体,便将其放到腰带中一并加以介绍,现将更大范围的与人身有关的佩物上纹饰予以介绍,以期对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游牧人的审美观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作为死者佩带物的短剑和铜刀,又从兵器和工具的角度,展现了这一历史阶段北方草原游牧人的审美意识。
当时的青铜剑是一种短剑,它广泛地出土于今内蒙古和东北地区,以及内蒙古与河北、山西、陕西的交界地带。向西南,至宁夏南部、甘肃庆阳地区。向北可至俄国的南西伯利亚、外贝加尔地区。我国北方青铜短剑,约可分做内蒙古长城沿浅的直刃剑系和东北地区的曲刃剑系两个类型。
由青铜短剑所反映的审美意识,集中反映在剑柄上,即由剑首到剑格这一段的样式、纹饰变化上。为了解各个历史阶段剑柄的特征及其变化规律,特将我国北方青铜短剑的剑首情况列表于下:从上表各式短剑的首、柄、格的特征,结合其时代,大体可以看出鄂尔多斯式青铜短剑的演变规律:剑首由铃首或者兽首→蕈首(瘤状首,蘑菇首)→“触角式”首→“变形触角式”首→环首(包括双环首)发展;剑格由一字形格→舌状突起形格→多变的椭圆形格→翼状格发展;剑柄发展的总趋势,则是由装饰复杂向简朴无华演变。短剑在首、柄、格方面的变化,说明了短剑制作者审美观念的演化。
死者另一种佩饰物是青铜刀。短剑和铜刀这两种器物的造型,在同一时期内,风格大体是一致的。根据青铜刀的首、柄、栏的造型约可分作5式。
1式:是鄂尔多斯式青铜刀的最早样式,柄首有孔,铃首或兽首,首下有环扣,刀栏与1式剑格造型风格相似。时代为商代。
2式:是鄂尔多斯式青铜刀的多变期,它是从1式发展而来的,但1式刀的重要特征有减弱趋势。刀首变化较快,并以兽首→蕈首→环首的次第发展着。本式时代约在西周。 .3式:是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繁盛期,种类多,而且器物制作精致,装饰花纹繁缛。反映在青铜刀上,自西周以来的蕈首(瘤状首)还继续存在,首按照蕈首→不规则孔首→环首→三角孔形首的次第发展。时代约从春秋至战国早期。
5式:这一时期铁刀代替了铜刀,但铜刀继续存在。铁刀的样式与鄂尔多斯式晚期铜刀相似。刀首有:环首和有孔首。时代约从战国时期至西汉早期。
6式:为木柄铁刀。这时木柄铁刀颇为流行。时代约从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
综观上述铜刀的发展序列,铜刀遵循的变化规律是兽首→蕈首(瘤状首)→有孔首→环首。
短剑和铜刀的装饰花纹,一般限于早期。剑、刀的装饰纹样,约可分作四类:蛇(龙)纹;鸟纹;动物纹;几何纹。
饰于龙首匕上的晚商蛇(龙)纹,属于蛇纹的写实形象:张嘴、圆睛、蘑菇柱状角,龙身以长方点示之。到西周,龙首简化,蛇纹变成了叶脉纹或网状纹。
鸟纹多见于剑首和铜刀柄部。开始鸟头纹喙部较短,后来鸟喙变长,呈内勾状,最后鸟的造型趋向图案化,鸟头的形象逐渐消失。
其他动物纹有:羊头纹、鹿头纹、伫立山羊纹、群马纹、双鹿纹、卧羊纹、身体反转的鹿纹、弯曲鹿纹、双兽头纹等。
几何纹有:三角纹、三角折线纹、云形纹、圆点纹、绕线纹等。
蛇(龙)纹,多饰于2式铜刀和曲柄短剑;鸟纹多饰于早期短剑和铜刀;其他动物纹和几何纹仍以早期的剑、刀为多。
从上述各式剑、刀的演变,似可对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游牧人的审美演变规律得出如下推论: 其一,短剑的装饰,是由具象到抽象,即由写实到写意。
其二,审美重点由外观到内涵,即由表层到深层。
其三,审美功能与实用功能始终是统一的,而且和合为一。短剑上的鸟兽之形及各种纹饰,既有审美意味,又都是实用的。
第五类是明器。明器是专门为死者随葬而制作的器物。《盐铁论·散不足》说“明器”是“有形无实之器”,即不能实用的器物。在汉族地区,明器的种类,除仿制各种生活器具外,还有房屋、田地、车船、仓、井、灶、猪圈和家具等模型。而在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北方草原上的游牧人则与之不同,他们的随葬品多数是死者生前生活上的实用品,但也有为随葬而特意制作的明器。其中艺术品之中最明显的例子是准格尔旗玉隆太、速机沟、瓦尔吐沟等地区墓葬中出土的伫立或蹲踞形铜鹿,瓦尔吐沟古墓中出土的蹲踞形盘角羊,以及土默特右旗水涧沟门古墓出土的铜鹿等。它在墓中的功能,既与身饰、服饰无关,又与仪仗、佩物无涉。它在墓中,只是死者生前曾占有众多马牛羊的象征,希冀在彼岸世界继续有无数的牲畜,以便死后继续享用。因为在牧业世界,牲畜是财富的象征,人们食其肉、饮其酪、衣其皮,骨头、筋是制作物品的原料,连粪便都是烧火用的燃料。这也如同以农业为生的汉族地区以房屋、田地、车船、仓、井、灶、猪圈等模型,充作财富的象征一样,都是须臾不可离开之物。这种现象,不是内蒙古草原所独有,在同一时间,几乎欧亚大草原的游牧民族,都是以牲畜为墓中的明器。比如俄罗斯库班科斯特罗马村就出土过这种造型的金鹿。①类似的鹿,在米努辛斯克盆地中也有发现。② 明器中的动物,多取圆雕形,并以逼肖对象为艺术追求的目标。存在的形式有,伫立和偃卧两种,而以偃息者居多。伫立者前后两脚往往相连,以示立于地面,但亦有不连者。偃息者,或前后腿折而向前,或前后蹄相接,或前后腿相叠,或前蹄向上、后蹄往下,姿态各异。不管伫立还是偃卧,以昂首居多,腿作远眺状。也有低首闭目者。动物的角,往往因姿态不同而相异:伫立者角多高扬,偃卧者角多后背。早期的鹿角接近自然状态,晚期的鹿角愈加夸张华丽,并故意使角变态,使其规范化、艺术化、抽象化,有的后背至尾。对于尾部的表现,也往往符合动物的自然状态,比如伫立的马,尾巴自然下垂,卧着的马,尾巴回弯至身侧。总之明器中的动物,个个活龙活现,栩栩如生。身体各个部位的比例,也恰到好处。生动地展现了当年我国北方草原各种动物富有充沛的生命力那种绚丽画卷。
古代游牧民族的明器艺术品,除圆雕动物之外,还有青铜铸成的鎏金铜马,仅西沟畔汉代匈奴墓4号墓就出土49件之多。西沟畔4号墓中的石佩饰,有46件之多,上刻形形色色的各种图案,其中有舞人纹、双龙纹、螭虎纹、龙虎纹等,技艺娴熟,异常精致,堪称佳作。
北方系青铜艺术品,由于最早多数出土于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故被人称做“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又由于鄂尔多斯高原,原属“绥远省”管辖,故又称做“绥远式青铜器”。
近几十年来,由于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带,越来越多的考古新发现,证实这类青铜器的分布范围,远远超过原绥远省地区,更远远超过鄂尔多斯高原,同时在文化内涵上殊为丰富多采,远非“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所能概括,故在我国的考古学界又出现了“北方系青铜器”等称谓。自然,这种称谓,比“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要好些,它所包涵的范畴要大得多。然而,北方系青铜器,从时空来看,它所包涵的内容又嫌过分庞杂,因此很难于准确地表述这种艺术的内容和实质。因此,很有必要将“北方系青铜器”这个无所不包的艺术综合体加以划分,区分为若干区系类型,以便更加准确地显示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化艺术面貌,这将有助于古代北方民族史、文化史和艺术史的研究,有助于对各个民族的艺术界定及其相互关系的探索。
尽管由于这个草原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经济文化的相近,反映在艺术上很相似,但我们观察问题,不仅应看到异中之同,更应分辨出同中之异,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囊括一切的“北方系青铜器”艺术的区系类型区分出来。
按照青铜器艺术品的题材内容、构图技法和艺术风格,从东至西,大约可以区分为以下几个区系类型:东胡系、山戎系、匈奴系和西戎系等四个青铜器艺术类型。当然这个划分是很粗略的,不一定都是准确的,随着考古新资料的不断被发现和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还会有新的类型被识别出来,同时会将划分不准确的地方纠正过来。
东胡系青铜艺术。分布于昔日东胡人分布的范围内。夏家店上层文化即东胡人的遗迹,这几乎是我国考古学界的共识,如果这个认定不误的话,那末夏家店上层文化分布的区域即为东胡系青铜艺术所分布的范围。大致包括今日内蒙古的赤峰地区、哲里木盟及辽宁省的朝阳地区、河北省的承德地区。发现青铜动物纹的主要遗址有宁城县南山根石椁墓、小黑石沟上层墓、敖汉旗周家地墓地等地。①共发现带有动物纹饰的器物近千件。其时代自西周晚期至春秋。
东胡系青铜艺术,若与匈奴、山戎、西戎、塞克人青铜艺术相比,具有许多明显的特点。
首先,从题材内容上看,似乎鸟禽纹出现较多,并极富特色。在兽类纹中,以马、牛、羊、犬等四种家畜最多。野生动物中,以虎纹最多,鹿纹偶见。这与匈奴系青铜艺术中喜欢表现鹿有明显区别。铜带扣虽也不乏其例,但比匈奴人少得多,而且其上的纹饰简单得多。
其次,在构图上,单个动物纹较常见,有些虽然是由多个动物纹所组成,但都是同一种动物的上下或左右有序的排列。给予观者的印象是构图简单而变化较少。
在艺术风格上,以写实为主,追求形似,抽象和变态者罕见,即便是有意变态的动物纹,也很容易地找到艺术的源头,即原来所凭借的对象。以鸟禽纹为例,在艺术处理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表现动态,刻画鸟禽平展双翅飞翔;一种是刻画鸟禽侧立。兽类纹的艺术处理,均以完整的形态出现,或以同一形态有规律排列组合。在对动物的刻画上;虽采用写实的手法,但这种写实,不是对动物外形的抄袭,而是力求在准确地描绘形态中去表现出动物的神韵。比如奔兔、飞鸟、立马,无不形神兼备,栩栩如生。在描绘静卧动物时,既显示了动物的静态,又不失于呆滞无神。在动物纹中,也存在着对表现对象的简化和变形,具有一些写意的意味,比如以人字纹表现鸟禽的羽毛,用圆圈象征动物的眼睛,用重圈表示关节等等。
动物纹给予人的印象是温顺的、和善的,甚至是可亲的,充满了畜牧社会的牧民对动物的喜爱之情,与匈奴艺术中,充满了动物间的厮斗意味,泾渭有别。
在技法上,虽也有透雕、浮雕和圆雕之分,但圆雕一般多限于刀剑柄端的动物,形体较小,立体感也不强,刀环和竿头上的动物,虽立体感极强,但数量甚少。浮雕的方法,或将动物整体凸出;或以凸线表现动物;或用铸出的阴线表现动物。这些都与其他各系青铜艺术品有较大差异。
东胡后来分裂为乌桓与鲜卑。《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说:“乌桓者,本东胡也。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因以为号焉。”乌桓艺术是东胡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乌桓是东胡的后裔,乌桓艺术是东胡的继承和发展,但由于乌桓艺术的时代较东胡晚得多,是汉代的作品,因此乌桓艺术虽与东胡人艺术有某些近似,但也有鲜明的自身特点。
乌桓人的艺术品发现较少,截至目前,比较可以肯定的乌桓人墓群只有辽宁省西丰县西岔沟一处,因此欲说明乌桓艺术,只好举西岔沟乌桓墓群出土品为例。
正如前面“辽宁出土的乌桓青铜艺术”一节所提到的,西岔沟青铜艺术品,出土过二十余面铜饰牌,从这些饰牌中,乌桓人的艺术似有以下几个特点: 在题材内容上,虽仍以表现动物为主,但从动物的种类和习性看,多数以家畜为表现的对象,如马、牛、羊、犬等。各种家畜多为温静安谧之态,显示了进入畜牧社会之后,由于动物早已驯化为家畜,在艺术上所起的巨大变化。
在艺术手法上,技艺娴熟,能用浮雕或透雕表现手法,去灵活多变地塑造对象。喜欢用双双对对的动物,去描绘谐和温顺的家畜。已能用复杂的画面,去描写人对家畜的役使和人与动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行为。
从艺术风格上讲,虽以写实为主,但也不乏抽象的艺术作品,有时故意使物象变态,去追求特殊的韵味和格调,使目睹者产生意想不到的风趣,从而加深艺术的感染力。
鲜卑人的墓群,分布范围广,延续时间长,到目前为止,在昔日鲜卑人的故土上,发现了许多自汉代至北朝的鲜卑墓群,并发掘出土过大批骨、铜、金、陶质的艺术品,这就为我们探索鲜卑艺术的特点和演变提供了可能。
鲜卑人的早期艺术,与乌桓艺术有很大一致性,到了它的后期,由于鲜卑居于原匈奴人的地域内,受匈奴艺术和域外艺术的影响较深,在艺术题材和风格上有一定变化。
大约在汉代,鲜卑人的青铜艺术品与乌桓的青铜艺术品是比较相近的,但在构图方面,也受到匈奴青铜艺术品的影响。比如,匈奴和鲜卑腰带上带扣的形状和纹饰就比较接近。纹饰的题材以鹿和马为主。还出现了几何形饰牌,有的可能是对牲畜圈栅栏的模仿形象。
到了西晋、北朝时期,东部鲜卑与西部的拓跋鲜卑,在青铜艺术方面有较大不同。东部鲜卑,大约还承袭着东胡和山戎的艺术传统,青铜艺术的题材以马为最常见,作蹲踞偃卧之状。比如内蒙古科左中旗六家子鲜卑墓出土的金马饰牌便是一例。而西部的拓跋鲜卑便大异其趣。比如凉城县小坝子滩出土的西晋时期的金银器,其上的动物纹,以众多的动物组成的图案为特征,动物的形象十分抽象。和林格尔县另皮窑村和土默特左旗讨合气村两处北魏鲜卑墓出土的带扣上的纹饰,因受波斯等地金银工艺品的影响,在题材上多以野猪纹为饰,并多镶嵌宝石和珠玉。同时关于鲜卑祖先兴起时的神话题材,仍有保留,比如土默特左旗讨合气村北魏鲜卑墓出土的带扣上的神兽纹便是一例。
西晋至北朝鲜卑人的艺术,不仅以金属为载体,还反映在陶器纹饰方面,形形色色的纹饰多达近20种,陶纹中的马、鹿纹,是鲜卑陶器一大特色。
这一时期,鲜卑人的墓室壁画内容,还受到汉族文化的深刻影响。
综观汉代至北朝鲜卑的青铜艺术,似可得出如下的结论:它的早期,以北方游牧民族传统的艺术为主旋律;到了它的后期,则在传统艺术的基础上,融溶了波斯和中原汉民族的艺术因子。
山戎系的青铜艺术,既不同于东胡系,又相异于匈奴系,它是具有自身特点的。它是具有特定的地域范围、时代界限和具有艺术特色的一种特有艺术。
从分布地域讲,山戎青铜艺术,分布于山戎昔日活动的区域内:大致包括今日的河北省北部、北京北部、辽宁省朝阳地区和内蒙古赤峰地区,这不仅从古文献记载中可以大致推知,也能从考古发现中得到证实。
从发掘出土的山戎遗物看,其时代大致相当于东周,即上限可早到春秋,下限不会晚于战国早期。
从山戎的艺术特色讲,山戎的青铜艺术十分富有特点。题材内容,多表现马、虎和青蛙。马、虎的造型特点是:身躯狭长,背部下凹,垂首,缚尾,腿短而粗,双腿向前,匍匐而卧,呈静态的伏卧式。在工艺技法上,遍体镶嵌多少不一的珠玉之类的饰物。凭借着这些特征,就可以把山戎的青铜器艺术品从整个北方系青铜器综合体中划分出来。
匈奴系青铜艺术,产生早、延续时间长,是我国北方系青铜艺术的主要构成部分之一。匈奴系青铜器,是匈奴人及先匈奴的北狄、猃狁、荤粥、楼烦、林胡等部族制作的。主要分布于:内蒙古西南、陕西北部、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部分地区。
匈奴系的青铜艺术,从制作技术上讲,有浮雕、透雕和圆雕之别,匈奴系和西戎系的青铜制品,其表面锡含量较高,与合金基体之间有明显的分界,多数锡含量大于40%,比一般基体中含锡6%—16%高出许多。表面富锡层的厚度不同,“对取样样品表面富锡层的组织及成分鉴定可知,富锡层内部不是单层,内又分2—3层,每分层的组织及成分有差异,各分层之间互相交错,界限不规则,内层与中层分界处有较多的孔洞,内层包纳基体组织中的铅、夹杂物,渗入基体组织的界限有的也不规则”。①表面富锡的青铜饰品,是将青铜器浸入熔化的锡液中,或者是把液态的锡涂覆在青铜器表面而成的。不过青铜器表面的锡层,有的是一层纯锡,有的则是铅锡合金。若制品单面镀层,多用热擦工艺进行,若双面有镀层,多是用热浸工艺,前法镀层比后法镀层薄。将金属制品浸入熔融的纯锡或铅锡合金中,以获得金属镀层的工艺,称为热浸镀,这是一种古老的传统工艺方法,一直流传至今。由于锡在铜中的可溶性,在纯铜上或青铜上镀锡都比较容易。纯锡熔点为232℃,高出50—100℃熔化时,对被镀制品的性能不致于影响太大。在热浸镀时,熔融状态金属与基体金属之间相互扩散,互相熔解,形成一层金属间化合物组成的合金层。镀层与基体金属是冶金结合,故相互粘黏力较强,镀层不起皮,也不脱落。在合金层外,还会存在一层纯锡或铅锡合金。
在进行热镀前,制品需经过仔细的镀前准备,包括除油、除锈和一定程度的表面光洁度的获取等工序。据oddy等记述的热镀锡的方法是:“在已完成镀前准备的铜或青铜制品表面上,放少许松香,制品在炭火中加热,松香熔化后布满制品表面形成熔剂层,以防止当温度增加时,基体金属进一步氧化。将锡球或锡箔放在制品表面上,制品加热到比纯锡熔点高50—100℃,纯锡完全熔化,将金属制品反复倾斜,使熔化的纯锡在制品表面覆盖完全。制品移出加热源,在锡尚未凝固时,用一块皮革或旧布擦拭制品表面,除去多余的纯锡,从而获得平滑均匀的薄层镀锡膜。”②应用此法,可得到单面镀锡表面层,但镀层厚薄较难控制。
“Tylecote进行镀锡的模拟实验是用含锡16%—18%青铜作样品。Zncl作熔剂,将样品(20℃)插入熔化的锡液中,锡液放在熔罐中,并保持一定温度(234、259、271及320℃),控制样品插入锡液的时间(2、10、15秒),得到镀锡层的厚度为4—50微米。应用这种热浸镀锡方法,得到的是双面镀锡表面层,镀层厚度可由插入锡液的时间进行控制。”①铅锡合金也可以用来作为镀层合金使用。Tylecote用熔化铅锡合金进行了热浸镀模拟实验,得到的镀层较用纯锡作镀层金属时的厚度略薄。
在埋葬环境中存在着电解腐蚀,纯锡相对于铜和低锡青铜是阳极,故锡层易穿孔。若表面层由高锡合金构成,相对于基体金属则是阴极,将能较好地阻止正常电解腐蚀。因此,高锡合金镀层的抗腐蚀能力比纯锡镀层更强,且能保持银白色的光泽。故西戎系和匈奴系制品表面具有高锡合金镀层者比纯锡镀层者更稳定。
西戎系和匈奴系青铜饰品,经过镀锡表面处理后,能较好地保持银白色光泽,不易生锈,又比使用银便宜,同时还可以减缓铜制品的进一步腐蚀,有助于延长制品的寿命。这些优点已由发掘出土的较多镀锡制品所证实。古代青铜制品表面镀锡处理的目的,不管当初是否为了外观美丽、实用和耐蚀,但达到了此种功效,那倒是事实。
表面镀锡制品的大量出现,不仅从艺术上,而且从制作技术上来说,无疑是一种进步,可以认为这是西戎系和匈奴系青铜制品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公元前6—4世纪,我国西北和内蒙古西南地区的西戎和匈奴系的游牧民族部落,已用镀锡的青铜制品。而在同一时期,东胡系和山戎系墓葬中,至今没有发现镀锡的青铜制品。这是草原东西部生产技术发展不平衡,抑或青铜艺术品的地域性和民族性所造成,目前尚难遽断。但应该指出的是,自新石器时代开始,草原东、西地区便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这种不同是可以理解的。
匈奴系青铜艺术。大约从东周至两汉,分布范围十分辽阔。匈奴文化是由不同的氏族部落融合而成的,反映在艺术上,各地不同的部族间是不尽相同的。但共性是主要的,我们从宏观上归纳区分北方系青铜艺术的区系类型时,可以不必去考虑这些细节问题。
匈奴系青铜器的动物形象,早期(东周)多虎、豹、狼等野生形象,造型生动,野性十足,以野生动物间的撕咬、搏斗和肉食动物对草食动物的吞噬为主要特征。晚期多马、牛、羊、犬、驼等家畜形象,动物的形象是温顺和驯服的,多表现人对动物的役使,动物与动物和人与动物的关系显得和谐温馨,全无敌意。这是猎人转变为牧民、狩猎社会转变为畜牧社会在艺术上的反映。
西戎系青铜艺术。西戎包括緜诸、绲戎、翟?、義渠、大荔、乌氏、朐衍等多种戎人。大约自青铜时代至东周,西戎长期居住于甘肃、宁夏南部和青海省东部一带。但西戎系青铜器,截至目前为止,仅见出土于宁夏南部的固原地区和甘肃的庆阳地区。
从总体上讲,西戎系与匈奴系的青铜艺术品比较接近。在制作技术上,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甘肃庆阳、宁夏固原地区、内蒙古凉城等地出土的西戎、匈奴系的青铜艺术品,其表面锡含量较高,与合金基体之间有明显的分界,多数锡含量大于40%。制作手法,都有浮雕、透雕和圆雕之别。西戎系青铜艺术品的纹饰,多表现肉食动物对草食动物的吞噬,尤其喜欢表现虎和虎对鹿的吞食。此外,还有龙和蟠虺等形象。在艺术风格上,虽然以写实为主,但也不乏抽象化的作品,比如固原和西吉出土的鸟形饰,皆作双鸟合体之形,十分抽象化和几何纹样化。固原出土的“涡纹饰”铜饰件,是鸟形饰的高度抽象的结果。固原西戎墓出土的圆形、三角、菱形等形状的铜饰牌,是对现实存在物图案化的结果。
总之,由于我国北方草原的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经济生活、以及各民族心理基质的相近,反映在文化艺术上,尤其是在青铜艺术上,各民族青铜艺术的大同总是问题的主流。但是,又由于各游牧民族的文化传统的不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与之相关的技术水平和文化水平的差异性,各民族的青铜艺术,不仅每个民族由于时代的不同而有变异,各民族在同一历史时期青铜艺术在题材内容、制作方法和艺术风格上的差别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就为我们区别出各自不同的区系类型提供了可能,而对北方各游牧民族青铜艺术区系类型的划分和确定,对研究各游牧民族的历史、文化和艺术有重要意义,这样可以把笼统的、无所不包的、含混的、不确切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这一称谓逐渐分解开来。
青铜器艺术品,多数出土于游牧民族的墓葬之中。其种类有仪仗用的铜竿头、身饰、服饰、佩物饰、器物饰和明器等。
第一类是仪仗用的铜竿头。竿头下有一个圆筒形或方形的铜柲,其上有马、鹿、刺猬、羚羊、虎、狼、鹤、盘羊形圆雕动物形,銎口呈圆形或方形,原来安插着木柄,供举行各种仪式时执用。过去的研究者,每每称之为“竿头”①或“车饰”②,但前一种称谓,并没有说清楚它的功能,后一种说法也未能说明是车上哪一个部位的装饰。这些说法都是没有说服力的。随着匈奴考古的新发现,为研究匈奴的历史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资料,并为探索“铜竿头”的功能成为可能。
到目前为止,出土铜竿头的地方有内蒙古伊克昭盟准格尔旗速机沟、玉隆太、瓦尔吐沟、西沟畔等地和陕西省神木县纳林高免等地,即从陕西北部到伊克昭盟地区,在黄河呈“n”形的河套之内,那里适当匈奴的故土。出土铜竿头的匈奴墓的时代,约从战国至西汉时期,这时正值匈奴鼎盛之时。
由以上出土情况似可推知,在匈奴故土上出土的铜竿头是匈奴举行礼仪仪式的用具。缅怀当年的匈奴人,一定在定期举行祭祀仪式的地方,在部落大人的率领下,手里高高擏起铜竿头,嘴里喃喃地念着祷词,在神像面前一圈一圈地舞动。匈奴人迷信至深。《史记·匈奴列传》谓:“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祭地先、天地、鬼神”,又谓:“而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举事而候星月,常随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可惜这里没有把举行祭祀仪式的全部细节描绘出来,由于铜竿头的出土,为我们想象和重构匈奴的祭祀仪式提供了可靠依据。
匈奴举行祭祀仪式,并不是随便找个场所举办一下了事,而是有一定的时间和场地,因为在匈奴人看来祭祀是一件神圣的事情,前面提到的“单于庭”和“茏城”便是两例,而且是专指由“诸长”所组成的国家级的祭祀仪式。上有好者,下必效之,匈奴普通民众亦必有自己传统的习惯的祭祀仪式方法。当时匈奴民众的祭奠仪式虽因古文献没有记载不得而知,但考古上的新发现,却为探索这些问题露出了蛛丝马迹。比如,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宁夏、江苏等地,发现了大批刻在石面上的面具岩画,少则一两个,多则数十个,这些由面具所体现的祖先、天神地祗和鬼神,便是当时祭祀的对象。
除了定时定地举行祭祀外,人死后,尤其是首领和特殊身份的人(如巫觋)死后,便要举行盛大规模的祭祀仪式,铜竿头的被发现,便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在准格尔旗速机沟,当地农民千四板定在那里挖窖时出土了一批铜竿头,计有鹤羊形、羊形、狻猊形、屈肢马形、长喙鹤头形、狼头形等六种鸟兽形动物,还有大小铜铃各二件。值得注意的是,与铜竿头一同出土的还有二件单系圆盘。奇怪的是,就是没有发现人骨。可见它并不是一座匈奴墓,也不是一座寻常的什么窖藏文物,而应当是匈奴的祭祀坑。
无独有偶,在其他地方和民族也有类似的祭祀坑。比如四川广汉三星堆巴蜀文化中的1、2号祭祀坑,便与之类似。1号坑内出土有:金杖、面具(包括金面罩和青铜人头像)、青铜酒器、青铜兵器、玉石礼器,以及十余根象牙和3立方米左右的烧骨碎渣。那是举行一次盛大的宗教礼仪之后而埋入的。①2号祭祀坑,首先投放的是海贝、玉石礼器、青铜兽面具、凤鸟、小型青铜杂件和青铜树枝、树干等。这些遗物在清理时,大部分都杂在灰烬的炭屑里,并留下了明显的烟熏火烧痕迹。其后再投入大型的酒器(青铜容器)和立着的巫师长(青铜立人像)、面具(包括头像和面具)、树座。最后投放象牙。根据遗物的火烧痕迹,结合文献记载,有理由相信,当时的祭祀,应有“燔尞”祭天,“〓埋”祭地,“悬庪”祭山等形式,2号坑正是一次重大综合祭祀活动的遗存。②类似三星堆的1、2号祀坑在陕西汉中地区也发现过。③ 可见见于准格尔旗速机沟的匈奴祭祀坑并非历史上的偶然现象,而是在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分布很广的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令人遗憾的是速机沟匈奴祭祀坑是农民挖开的,没有经过科学发掘,致使许多文化现象没有弄清楚。
其他如玉隆太、瓦尔吐沟、西沟畔和神木县纳林高兔等地古墓中出土的铜竿头,也是祭祀用器具,即仪仗顶端的饰物。但并非所有匈奴人死后都以这类仪仗埋入。考古发现证实,以仪仗葬入墓内的并不占多数,只是一些具有特殊身份的人,才在墓中发现有仪仗(因木柄已腐烂,只能看到仗顶的动物饰件)。
埋有仪仗头的匈奴墓,死者的身份估计有两种可能:其一,死者生前的身份是巫觋,葬入的仪仗,是死者生前参加祭祀仪式时常用之物,这些仪仗,不仅是死者生前喜爱之物,而且简直可以视作神圣之物,死后将它作为随葬品而埋入墓中,应是情理中的事情;其二,是氏族部落中的头面人物,因此,当人死后,要在墓地举行祭奠仪式,待丧礼过后,即将举行仪式时用过的仪仗投入墓中,作为随葬品,这应视作氏族部落的首领,死后享有他人无以伦比的殊荣的一种表现。看来第一种可能性要比第二种大些,因为匈奴社会中巫风炽烈,巫觋是社会上一种不可小视的社会力量,他们的人数多,巫师作法和祭奠活动也是很频繁的。这在《史记·匈奴列传》和《汉书·匈奴传》等古文献中多有见及,现举数例予以证实。
匈奴人迷信甚深,这些迷信活动,通常是由巫觋来实现的。比如汉贰师将军李广利投降匈奴后,丁灵王卫律妒忌他得宠,乃串通胡巫陷害贰师,假托已死的“先单于”降言要用贰师作牺牲,血祭胡社。于是单于逮捕贰师,贰师骂曰:“我死,必灭匈奴。”会连续雨雪数月,牲畜死亡,人民疫病,谷稼不熟,单于恐惧,为贰师设立祠室。①《汉书·西域传》下说:匈奴使巫埋牛羊于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赠给汉帝的马、裘,常先使巫祝之。可见巫对于匈奴的军事和政治影响都很大。胡巫所用的法术通常是咒语,降汉的匈奴人遒侯隆强之子和容成侯唯徐卢之孙,都曾因为使用胡巫祝诅汉帝而被削爵。②汉武帝征和时,汉军追击匈奴兵,至漠北的范夫人城,这个范氏是个能“胡诅”的女人,可见城主范夫人原先也是个胡巫。③ 这种胡巫,后来由于匈奴人的不断附汉而流入中原地区。汉安定郡所属的朝那郡(今甘肃平凉县西北)有端旬祠15所,祠内有胡巫祝诅。①汉朝宫廷中也有不少胡巫,比如《汉书·江充传》和《汉书·戾太子传》就记有江充串通胡巫陷害戾太子的事件。
匈奴人祭祠的地点和仪式,除了上述的单于庭之外,还有茏城和蹀林。“蹛:者,绕林木而祭也”②。上文提到的匈奴人以贰师血祭“胡社”,可知那里也是祭奠之处。
由以上胡巫的职司和行为看,他们生前有仪仗之类的法器,死后埋入墓中是完全可能的。由于匈奴仪仗用的铜竿头的发现,及其功能的被认定,为了解匈奴人的原始信仰又找到了新证据。
第二类是服饰。死者身着的葬服虽已腐烂,然而缀连于衣服上的饰物却依然存在。主要包括有冠饰、纽扣、腰带扣和带钩等。这些衣服上的附着物,从服饰的角度,展现了古代游牧人审美观念的一个侧面。
截至目前,已发现的北方游牧民族的“胡冠”有三套。其一,前面已经提到,就是杭锦旗阿鲁柴登匈奴墓出土的胡冠,它的装饰部分由冠顶、冠带两部分组成,全是金制品。冠顶上面是一个半浮雕的狼咬羊图案,浮雕于厚金片锤鍱而成的半球体表面,半球体表面从中间四等份为夹角90°的扇面形,展翅的雄鹰傲立于半球体之上。鹰的头、颈由绿松石做成,颈的上部与头相连处,有精细的金片做成的项链,头、腹是用通过颈部的金丝连结成一体的,尾部是插入的,以金丝相连结,头、颈、尾都可左右摆动,活龙活现,栩栩如生,整个冠顶,宛如一只在蓝天上翱翔的雄鹰俯视地面上狼咬羊的生动画面,而这种画面又是草原上常见的情景。冠带由三条半圆形金条围合而成,冠带前部有上下两条,冠带后边一条,并以两端的榫铆联结在一起,组成圆形的冠带。冠带左右靠近人耳处,每条两端分别浮雕伏虎、盘羊、马等动物图案。冠顶与冠带间,原应有皮制品或丝织品联结,惜已腐烂无存。
其二,是陕西神木纳林高兔出土的“胡冠”,仅残留圆雕神兽形金冠顶上的饰物,原来胡冠的形制虽已难测知,但其雄姿犹存。这两顶冠饰都十分讲究,是匈奴首领在特定场合才戴的胡冠上的装饰。冠饰制作精工,在取材上富有浓郁的草原气息。
其三,是准格尔旗西沟畔4号墓出土的头巾饰。出土时已凌乱,但大体可复原:上部中间,有椭圆形包金贝壳饰,左右排列有云纹金饰片,稍下有圭形包金花边的贝壳饰左右成行排列;下部有三排云纹长条形金饰片,下垂一道道熠熠发光的菱形金属珠。从组成头饰的金饰片上的钉孔和贝壳饰上的纽孔推测,这些头饰构件原来是缝缀在头巾之上的。
这件头巾上的饰物,是中外经济交往、文化交流的产物,类似的巾饰或冠饰在西方多次发现过。比如在第聂伯河沿岸捷尔特穆里克斯基泰王墓中,发现过顶部饰有12个狮子的冠饰①。又在顿河下游诺沃切卡斯克萨尔马特王墓中,出土过呈带状的金冠,其上缘是鹿嘴衔轮状物在林中奔跑的图案,并有两只似鹅的禽鸟;中部镶嵌有水晶、宝石、玉髓、戴冠的妇女胸像和猛禽;下缘垂挂有两个把手的壶形物②。有人认为,此冠是戴在头巾或面纱上的③,这与西沟畔四号墓出土的头巾饰很近似。而捷尔特穆里克王墓出土的冠饰,又与阿鲁柴登和纳林高兔匈奴墓胡冠上的饰物接近。
纽扣,普遍出土于各地的游牧民族的墓葬之中,形制各式各样,多数加以装饰,使之既有使用价值,又有观赏价值。观之,使人赏心悦目,产生美的娱乐。现将各个墓地出土的纽扣列表于下:从上表看,纽扣散见于古代北方各游牧民族的古墓之中,同时大都是在衣服之上的。但它并不限于衣服上,比如凉城毛庆沟楼烦墓中的纽扣,除衣服上之外,还有在腰带上、手套上和剑鞘之上的。看来它的功能有二:其一,是衣服上的扣子;其二,是装饰在各种物件上的装饰品。应当指出的是:过去被人称做“铜泡”的东西,实际上是纽扣。首先,它的大小正有扣子那么大;其次,出土的位置在衣服上;其三,其背后有纽,可以缝缀在衣物上。还有过去被称做“铜泡饰”的东西,也应是扣类,因其边缘有小圆孔,可缝连在衣物上,其大小、样式也与纽扣一样。纽扣不仅有使用价值,它的观赏价值也是望而可知的。
带扣,是先秦至晋代北方游牧民族衣服上重要的金属括结具。带扣又称带卡、扣绊、带铰或带鐍。古人对带扣很讲究,十分注重它的精美。带扣的质料有铜、金、银、玉等,也有在铜带扣外面包金或鎏金者。历来从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古墓中出土的带扣,品种多样,形状繁复。由于带扣的品类繁多,研究者对带扣的分类问题每感困惑。近年来,孙机先生根据国内外出土的大量带扣资料,对带扣进行了分型分式工作,从而使对带扣的认识有了新的突破。①根据孙先生的意见,带扣可分做三种类型:I型,无扣舌;Ⅱ型,装固定扣舌;Ⅲ型,装活动扣舌。
以无扣舌为特征的I型带扣又可分为两式:I型1式,既无扣舌又无穿孔;1型2式,是在一条腰带中的2枚带扣中,其中1枚的一侧有穿孔。I型2式带扣是由I型1式发展而来的。
1型1式,即上文提到的既无扣舌又无穿孔的带扣。在我国,此式带扣约出现于春秋时。内蒙古凉城毛庆沟5号春秋晚期的北狄墓,有2件大小一致的虎纹带扣左右对称地摆在死者腹部前面(即腰部),看来原装于腰带会合处两侧,其前部和后部各有圆孔,以便缝在腰带上。这两件带扣均无括结装置。带扣的使用方法,只能像斯基泰人那样,他们遍装“饰牌”的腰带,其长度大致为腰围相等,两端在腰前会合对齐,各端再接续出一段窄带,用此窄带打结扣系。②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另皮窑与土默特左旗讨合气出土的铁芯包金之猪纹与神兽纹带具中,各有二枚成对的马蹄形带扣,既无穿孔也无明确的扣舌,无疑应属于I型1式。两地带扣各有2枚接近椭圆形的带环,形制与老河深所出土者相同,可以确认是腰带上的装饰。讨合气出土4枚长条形带銙,也是腰带上的装饰,束腰时用两带扣之间的窄带相系结。
I型1式的带扣还有许多,如杭锦旗阿鲁柴登发现的匈奴金银器中,有12枚铸成头生多枝长盘角的虎状怪兽的金带具,原来是装在一条腰带上的。准格尔旗西沟畔2号战国匈奴墓出土的金饰片等,都属此种类型的带扣。与毛庆沟带扣时代相近的哈萨克斯坦伊细克(lssik,在阿拉木图附近)塞种王墓中,死者腰带中部也装有左右对称的此种式样的金带具,并依次向后排列。带具呈鹰喙鹿身、头生多枝长盘角的神兽形。此带具与阿鲁柴登发现的匈奴金带扣,在形制上尤为相似。在塞种迤西的斯基泰人那里,也能见到I型1式带扣,乌克兰切尔卡萨州Berestnya3i村之前5世纪的斯基泰古墓中所出青铜带具,以八枚为一副,腰前二枚呈侧视的狮头形,体积较大,显得特别突出,两边则装有较小的兽面形饰牌。①这些情况表明,此时生活于欧亚草原上的北狄、匈奴、塞种、斯基泰等游牧民族的带具形制是比较接近的。
至西汉时,I型1式带扣得以广泛传布,北自蒙古草原,南抵广东,到处都出土过。比如,南西伯利亚出土有双龙纹金带扣②,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出土有蟠龙双龟纹鎏金铜带扣,而在西安三店村西汉墓及江苏扬州西汉“妾莫书”墓中,也发现过同类之物。
I型2式带扣,是在腰带两端相接处的两个左右相对的带扣中,其中一枚的一侧有穿孔,这样便可只用一条窄带来系结,腰带一端的窄带可以通过另一枚带扣之穿孔,绕回来再系结。它是由I型1式发展而来的。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同心倒墩子19号西汉匈奴墓出土的双马纹1型2式鎏金铜带扣,所开穿孔使马嘴部的图案受损。杭锦旗阿鲁柴登发现的战国匈奴遗物中有此式的金带扣,铸出浮雕式的四狼噬牛纹,带穿孔的那一枚在牛鼻上硬凿开一个洞,以致图案又受到破坏。
I型2式带扣,在匈奴遗物中多见之,除上举两例外,诸如准格尔旗西沟畔2号战国墓和同心倒墩子5号西汉墓中都有发现。内地亦有此式之精品出土,如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出土过十余枚此式带扣。① I型带扣,颇似班固《与窦将军笺》所称的“犀毗金头带”之金头,因为I式金属带扣装在腰带两头,具有明显的装饰作用。至于所称的“犀毗”,颜师古在《汉书·匈奴传》中解释说:“犀毗,胡带之钩也;亦曰鲜卑,亦谓师比,总一物也,语有轻重耳。”又《楚辞·大招》以“小腰细颈,若鲜卑只”的句子来形容“腰支细少,颈锐秀长”的“好女之状”,由此观之,“犀毗”似指带钩而言。但据上海博物馆所藏“庚午”(371年)玉带扣上的“御府造白玉衮带鲜卑头”之铭文②,则鲜卑应指带扣。二者仿佛存在着矛盾。实际上,无论带钩还是带扣,凡属胡带用的括结具,大约均可称做犀毗或鲜卑。
Ⅱ型带扣,既有系结用的穿孔,又有固定的扣舌。在我国北方匈奴、鲜卑等草原民族中广为流行,除宁夏、内蒙古屡有出土外,在匈奴居住过的南西伯利亚地区也多有出土。从外形轮廓看,有圆形、长方形、马蹄形与不规则形等。按使用情况,Ⅱ型带扣可分作二式:Ⅱ型1式,一条腰带只装1枚带扣,是单独使用;Ⅱ型2式,一条腰带上装2枚带扣,成双使用。
Ⅱ型1式中的圆形带扣,在春秋时期至战国早期的杭锦旗桃红巴拉1、2号墓中已经发现。关于它的来源,“其直接的借鉴应得自内地马具中之扣具”③。关于这一点,可从陕西凤翔马家庄1号春秋中晚期建筑群遗址之车马坑内出土的金质和铜质“圆策”得到启迪,都在圆环上装有向外伸出的固定扣舌,其形状与内蒙古博物馆所藏Ⅱ型1式圆形铜带扣的构造基本一致。将马用扣具上的固定括舌巧妙地改用于腰带带扣上来,使带扣的括结功能大为改进和加强,这是我国古代北方草原民族在吸收基础上的一种创造。
Ⅱ型2式带扣,其形状有马蹄形、长方形和不规则形三种。满洲里市扎赉诺尔和吉林榆树县老河深两地之鲜卑墓所出土的马蹄形带扣,它们皆为铜质鎏金并饰以鲜卑神兽纹,是Ⅱ型2式带扣中的有代表性的作品。此外,南西伯利亚出土的时代约属战国的不规则形怪兽噬马纹金带扣,其上之后身极度扭曲的马,在斯基泰和塞种金饰上出现,也在宁夏固原红庄出土的战国西戎金带具上见过。①可见Ⅱ型2式带扣,广泛地见于鲜卑、匈奴、斯基泰和塞种等多种游牧民之中。
在此型带扣中,起括结作用的是铸出固扣舌的那一枚,而对称的另一枚,则只起装饰作用。本来一枚已敷用,而还要在对面增加一枚,看来是受I式带扣的格局影响所致。Ⅱ式带扣的括结法,在内蒙古凉城毛庆沟59号楼烦墓及完工鲜卑墓中均由残存的革带反映出来,那是将其一端的窄带自下而上通过对面的带扣之穿孔, 再折回来用扣舌勾住,则腰带便可束紧,估计多余部分则在当中垂下。
Ⅱ型带扣,大约相当于古籍中所称之带鐍。《说文·角部》谓: “鐍,觼或从金、矞,”“觼,环之有舌者”。段玉裁注:“环中有横者以固系”则鐍是有“固系”之舌的括结具,与此型带扣的性状大体是相合的。
Ⅲ型带扣装有活动的扣舌。按照使用情况,也可分作两式:Ⅲ 型1式,单独使用;Ⅲ型2式,成对使用。Ⅲ型带扣,也是受马具用扣具的影响而制作的。始皇陵2号兵马俑坑T12出土的陶鞍马腹带上所见之扣具,已装有活动扣舌。①Ⅲ型1式带扣最早见于西汉,比如云南晋宁石寨山7号西汉墓出土的银带扣,其形制与平壤贞柏洞37号乐浪墓所出虎纹银带扣极为肖似。②这2枚带扣的穿孔呈弧形,位于扣体前部,扣舌较短,其他汉代金、玉带扣亦无不如此。新疆焉耆博格达沁古城黑圪垯与平壤石岩里9号乐浪墓所出形制相近的龙纹金带扣,均长约10厘米,锤鍱成型,作群龙戏水图案,龙体上满缀大小金珠,工艺精湛。这种富丽华美的金带扣,直至西晋,仍可在湖南安乡刘弘墓出土的龙纹带扣中见到。
Ⅲ型2式带扣,多见于晋代。比如辽宁朝阳袁台子东晋墓、江苏宜兴元康七年(297年)周处墓均曾成对出土。
Ⅲ型1式和2式的括结方法,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根据孙机先生的研究,宜兴周处墓所出Ⅲ型2式带扣及同出之带具,其系结方法与老河深105号墓出土带具相同。③ 虽然这里的窄带贯穿的是装活动扣舌的带扣,却依然要折返回来将多余的部分于腰腹中部打结下垂。Ⅲ型2式带扣的括结法应与周处墓出土带具使用方式基本一致,只不过仅用1枚带扣而已。
进入南北朝以后,我国带具的形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时装活动扣舌的小带扣已在腰带上广泛使用,扣身只以简单的横轴支撑扣舌,腰带也变成前后等宽的一整条,并迅速向鞢〓带过渡。革带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带扣的类型略如上述,我们再看腰带上的装饰。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对腰带的装饰十分重视,根据饰物在腰带上的位置及其功能约可分作三种:其一,它是一种纯装饰性质的,其高度与腰带的宽度正同,竖着固定于腰带上。带饰形状各有不同:或呈长方形,或呈联珠形,或呈卷曲的双鸟纹。
其二,呈半悬挂式,饰件的上端固着在腰带的下缘。
其三,是悬挂在腰带的垂饰物,其中有铜环、联珠、鸟兽纹饰牌、扣饰、管状饰、棒形饰、饰针、动物形垂饰等。
上述情况,是仅就一般情况而言的,事物往往是很复杂的,同一种装饰品常常装饰于不同的部位。以联珠状铜饰为例:凉城毛庆沟3号墓出土的Ⅵ式联珠状铜饰,均装饰在腰带之上,《内蒙古·长城地带》一书的作者,根据围场东家营子的发现,也认为它装饰于革带上。宁城县南山根夏家店上层文化墓中发现的此种饰件,服饰在衣服前衿上,赤峰夏家店上层文化墓葬中发现的,整齐地排列于头部。杭锦旗桃红巴拉发现的,多数散落在足部。看来有些饰物的装饰位置是有随意性的。
带钩与带扣都是腰带头供系结之物,本是中原地区普遍流行之物,在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地区,它常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共出,与青铜带扣配合使用或交替使用。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出土数量较多,仅凉城县毛庆沟楼烦墓地就出土有16件,其中铜带钩13件,铁带钩三件。北京延庆军都山东周山戎部落墓地也有出土。根据目前的发现,至少在春秋早期就出现了带钩,最早的带钩仿自飞禽走兽,后来逐渐发展成鸟头形、琵琶形、棒形、竹节形,最后铁带钩又代替了铜带钩。带钩在我国北方草原,流行时间很长,大约从春秋早期,经战国直至汉代。
带钩是将使用功能与审美功能巧妙结合的生动体现,一方面它是腰带上的构件,起着括结腰带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又是制作者审美观念的外化形式,内中蕴寓着美的意味和对美的追求,使目睹者产生美的愉悦。
第三类是身饰。包括有头饰、耳饰、项饰和手饰。饰于头部和颈部的珠饰,在北方游牧民族中十分普遍,是古代北方草原民族古墓中常见的出土物。比如杭锦旗桃红巴拉狄人古墓群出土石串珠349枚,凉城县毛庆沟狄人、楼烦古墓出土各类料珠200枚。其他如乌拉特中旗呼鲁斯太匈奴墓、西丰县西岔沟乌桓墓群、敖汉旗周家地东胡墓地、榆树县老河深鲜卑墓、怀来北辛堡山戎墓、宁城县南山根102号东胡墓、张家口市宣化县小白阳地山戎墓、北京延庆军都山东周山戎部落墓地等游牧民族墓地,都出土了许多珠饰之类的装饰品。各地出土的珠饰,种类繁多,形状各异,大小不一,主要有骨珠、石珠、玛瑙珠、水晶珠、绿松石、琉璃、琥珀、料珠、海贝、珊瑚珠、珊瑚枝饰等。其形状有:柱状、棱柱状、扁圆形、长方扁平、圆管形、菱形、方柱状、球形、梯形等。出土的部位,在头部、项部或胸部。它应是头饰、项饰和额饰。
头饰,一般是冠帽或头巾上的饰物,前文提到的准格尔旗西沟畔汉代匈奴墓地4号墓出土的头巾上的装饰品便是典型一例。此外,凉城毛庆沟3号墓和5号墓死者头颅周围的料珠,看来原来也是死者的头饰。
项饰,一般只出土于比较讲究的墓葬中,看来比较富有的人才戴项饰。项饰的种类颇多,见于古墓的古代游牧民族的项饰,有金项圈、银项圈,和由各种串珠组成的项链等。
金项圈共出土三件,其中阿鲁柴登出土2件(其中1件残),西沟畔2号匈奴墓出土一件。西沟畔匈奴墓出土者,是用金条围成的,长1.42米,重达502.5克,绕周圈套于颈部,非常豪华壮观。一般说来,金项圈、金冠或头饰成套共出,看来是达官贵人的墓葬。
银项圈,用银条围圈而成,仅在准格尔旗玉隆太和瓦尔吐沟出土过。其中瓦尔吐沟出土的银项圈的一端饰有虎咬羊动物纹,富有浓郁的草原风味。
串珠组成的项链。在已发掘的古代游牧人的墓葬中,多数墓出土有各种质料制成的串珠。比如敖汉旗周家地东胡墓群45号墓,在死者胸上,有排列十分整齐的箕形蚌项饰①。榆树县老河深1号鲜卑墓群环绕颈部为一件颈饰,这串颈饰由266颗玛瑙珠和六只金管组成。玛瑙珠为圆形,大小不一,桔红色。金管呈圆筒状,相隔穿于玛瑙珠之间。56号墓,出土一件玛瑙串珠链组成的项链,有玛瑙珠78颗,其形多为圆形与椭圆形,也有六棱或七棱,珠孔为一面钻或两面对钻,颜色有红、桔红、桔黄、黄色等。58号墓出土项饰一串,由玛瑙珠串连而成,现有玛瑙珠39颗,形状为六棱形和圆鼓形,珠孔对钻,颜色红色和桔红色。杭锦旗桃红巴拉和公苏壕七座墓均出土有串珠。凉城毛庆沟有31座墓发现有串珠。准格尔旗西沟畔汉代匈奴12座墓,只有4号墓出了串珠。各墓项饰串珠大同小异,比如毛庆沟65号墓的项链,由绿松石、骨珠、铜铃形饰组成。毛庆沟5号墓出土项链,由玛瑙、绿松石、水晶珠等组成。桃红巴拉狄人墓出土的项链,则由水晶、绿松石、玛瑙、骨珠组成。西沟畔4号汉代匈奴墓串珠项链,据出土时观察,由两套组成:一套由大型水晶和玛瑙组成;另一套由小型的水晶、琉璃和琥珀组成。各种串珠色彩斑斓,五光十色,十分美观。北京延庆军都山东周山戎墓群发掘证实:这里男女老少都有佩戴项链者,由各种质料制成的项练多佩于死者胸前。相当一部分男性死者和少数儿童及婴儿,以及个别女性死者,在颈下佩戴各种动物形铜牌饰,少数身份高贵的男性死者佩戴金璜饰或金虎牌饰。河北宣化县小白阳山戎墓地出土的项链,质料有玛瑙绿松石和铜珠。
由串珠组成的项链,盛行于春秋战国,到汉代便逐渐减少,它既反映时代特征,又体现了死者的身份差别。考古发掘资料显示了如下的事实:相当于春秋晚期或战国早中期墓,串珠组成的项链,普遍出土于中小型墓;战国晚期以后,小型墓仍出土由各种料珠组成的项链,而大型墓则出现了银项圈和金项圈。
额饰较少见,仅在西沟畔4号墓,在死者额部有菱形垂珠。
耳饰较多,有耳环和耳坠等。形制各异,兹列表说明如下。
成的项链,而大型墓则出现了银项圈和金项圈。
额饰较少见,仅在西沟畔4号墓,在死者额部有菱形垂珠。
耳饰较多,有耳环和耳坠等。形制各异,兹列表说明如下。
桑变迁,戒指的样式也起了变化。凉城县小坝子滩拓跋鲜卑墓出土的金戒指十分名贵,在金光灿灿的戒指上,饰以兽头形。
死者的身饰,是其生前身饰的反映,而服饰又是身饰的扩大。身饰与服饰,在颇大程度上反映了死者所处时代的审美观念和对美的追求。
第四类是佩饰物,包括刀饰、剑饰、锥饰、针饰及其他各种人身佩饰物。这些佩饰物都与身饰和服饰密切相关。
上文提到的腰带饰物,实际上是佩饰物的一部分,但它以腰带为附着体,便将其放到腰带中一并加以介绍,现将更大范围的与人身有关的佩物上纹饰予以介绍,以期对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游牧人的审美观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作为死者佩带物的短剑和铜刀,又从兵器和工具的角度,展现了这一历史阶段北方草原游牧人的审美意识。
当时的青铜剑是一种短剑,它广泛地出土于今内蒙古和东北地区,以及内蒙古与河北、山西、陕西的交界地带。向西南,至宁夏南部、甘肃庆阳地区。向北可至俄国的南西伯利亚、外贝加尔地区。我国北方青铜短剑,约可分做内蒙古长城沿浅的直刃剑系和东北地区的曲刃剑系两个类型。
由青铜短剑所反映的审美意识,集中反映在剑柄上,即由剑首到剑格这一段的样式、纹饰变化上。为了解各个历史阶段剑柄的特征及其变化规律,特将我国北方青铜短剑的剑首情况列表于下:从上表各式短剑的首、柄、格的特征,结合其时代,大体可以看出鄂尔多斯式青铜短剑的演变规律:剑首由铃首或者兽首→蕈首(瘤状首,蘑菇首)→“触角式”首→“变形触角式”首→环首(包括双环首)发展;剑格由一字形格→舌状突起形格→多变的椭圆形格→翼状格发展;剑柄发展的总趋势,则是由装饰复杂向简朴无华演变。短剑在首、柄、格方面的变化,说明了短剑制作者审美观念的演化。
死者另一种佩饰物是青铜刀。短剑和铜刀这两种器物的造型,在同一时期内,风格大体是一致的。根据青铜刀的首、柄、栏的造型约可分作5式。
1式:是鄂尔多斯式青铜刀的最早样式,柄首有孔,铃首或兽首,首下有环扣,刀栏与1式剑格造型风格相似。时代为商代。
2式:是鄂尔多斯式青铜刀的多变期,它是从1式发展而来的,但1式刀的重要特征有减弱趋势。刀首变化较快,并以兽首→蕈首→环首的次第发展着。本式时代约在西周。 .3式:是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繁盛期,种类多,而且器物制作精致,装饰花纹繁缛。反映在青铜刀上,自西周以来的蕈首(瘤状首)还继续存在,首按照蕈首→不规则孔首→环首→三角孔形首的次第发展。时代约从春秋至战国早期。
5式:这一时期铁刀代替了铜刀,但铜刀继续存在。铁刀的样式与鄂尔多斯式晚期铜刀相似。刀首有:环首和有孔首。时代约从战国时期至西汉早期。
6式:为木柄铁刀。这时木柄铁刀颇为流行。时代约从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
综观上述铜刀的发展序列,铜刀遵循的变化规律是兽首→蕈首(瘤状首)→有孔首→环首。
短剑和铜刀的装饰花纹,一般限于早期。剑、刀的装饰纹样,约可分作四类:蛇(龙)纹;鸟纹;动物纹;几何纹。
饰于龙首匕上的晚商蛇(龙)纹,属于蛇纹的写实形象:张嘴、圆睛、蘑菇柱状角,龙身以长方点示之。到西周,龙首简化,蛇纹变成了叶脉纹或网状纹。
鸟纹多见于剑首和铜刀柄部。开始鸟头纹喙部较短,后来鸟喙变长,呈内勾状,最后鸟的造型趋向图案化,鸟头的形象逐渐消失。
其他动物纹有:羊头纹、鹿头纹、伫立山羊纹、群马纹、双鹿纹、卧羊纹、身体反转的鹿纹、弯曲鹿纹、双兽头纹等。
几何纹有:三角纹、三角折线纹、云形纹、圆点纹、绕线纹等。
蛇(龙)纹,多饰于2式铜刀和曲柄短剑;鸟纹多饰于早期短剑和铜刀;其他动物纹和几何纹仍以早期的剑、刀为多。
从上述各式剑、刀的演变,似可对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游牧人的审美演变规律得出如下推论: 其一,短剑的装饰,是由具象到抽象,即由写实到写意。
其二,审美重点由外观到内涵,即由表层到深层。
其三,审美功能与实用功能始终是统一的,而且和合为一。短剑上的鸟兽之形及各种纹饰,既有审美意味,又都是实用的。
第五类是明器。明器是专门为死者随葬而制作的器物。《盐铁论·散不足》说“明器”是“有形无实之器”,即不能实用的器物。在汉族地区,明器的种类,除仿制各种生活器具外,还有房屋、田地、车船、仓、井、灶、猪圈和家具等模型。而在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北方草原上的游牧人则与之不同,他们的随葬品多数是死者生前生活上的实用品,但也有为随葬而特意制作的明器。其中艺术品之中最明显的例子是准格尔旗玉隆太、速机沟、瓦尔吐沟等地区墓葬中出土的伫立或蹲踞形铜鹿,瓦尔吐沟古墓中出土的蹲踞形盘角羊,以及土默特右旗水涧沟门古墓出土的铜鹿等。它在墓中的功能,既与身饰、服饰无关,又与仪仗、佩物无涉。它在墓中,只是死者生前曾占有众多马牛羊的象征,希冀在彼岸世界继续有无数的牲畜,以便死后继续享用。因为在牧业世界,牲畜是财富的象征,人们食其肉、饮其酪、衣其皮,骨头、筋是制作物品的原料,连粪便都是烧火用的燃料。这也如同以农业为生的汉族地区以房屋、田地、车船、仓、井、灶、猪圈等模型,充作财富的象征一样,都是须臾不可离开之物。这种现象,不是内蒙古草原所独有,在同一时间,几乎欧亚大草原的游牧民族,都是以牲畜为墓中的明器。比如俄罗斯库班科斯特罗马村就出土过这种造型的金鹿。①类似的鹿,在米努辛斯克盆地中也有发现。② 明器中的动物,多取圆雕形,并以逼肖对象为艺术追求的目标。存在的形式有,伫立和偃卧两种,而以偃息者居多。伫立者前后两脚往往相连,以示立于地面,但亦有不连者。偃息者,或前后腿折而向前,或前后蹄相接,或前后腿相叠,或前蹄向上、后蹄往下,姿态各异。不管伫立还是偃卧,以昂首居多,腿作远眺状。也有低首闭目者。动物的角,往往因姿态不同而相异:伫立者角多高扬,偃卧者角多后背。早期的鹿角接近自然状态,晚期的鹿角愈加夸张华丽,并故意使角变态,使其规范化、艺术化、抽象化,有的后背至尾。对于尾部的表现,也往往符合动物的自然状态,比如伫立的马,尾巴自然下垂,卧着的马,尾巴回弯至身侧。总之明器中的动物,个个活龙活现,栩栩如生。身体各个部位的比例,也恰到好处。生动地展现了当年我国北方草原各种动物富有充沛的生命力那种绚丽画卷。
古代游牧民族的明器艺术品,除圆雕动物之外,还有青铜铸成的鎏金铜马,仅西沟畔汉代匈奴墓4号墓就出土49件之多。西沟畔4号墓中的石佩饰,有46件之多,上刻形形色色的各种图案,其中有舞人纹、双龙纹、螭虎纹、龙虎纹等,技艺娴熟,异常精致,堪称佳作。
附注
①刘冰:《夏家店上层文化动物纹饰的研究》,《北方民族文化》1991年增刊。
①② 韩汝玢(北京科技大学)、埃玛·邦克(美国丹佛艺术博物馆):《表面富锡的鄂尔多斯青铜饰品的研究》,《文物》1993年第9期。
①韩汝玢(北京科技大学)、埃玛·邦克(美国丹佛艺术博物馆):《表面富锡的鄂尔多斯青铜饰品的研究》,《文物》1993年第9期。
①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5期。
②唐金裕:《陕西省城固县出土殷商铜器整理简报》,《考古》1980年第3期。
①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0期。
②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5期。
③唐金裕:《陕西省城固县出土殷商铜器整理简报》,《考古》1980年第3期。
①《汉书·匈奴传》上。
②《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
③《汉书·匈奴传》。
①《汉书·地理志》下。
②见《汉书·匈奴传》上颜师古注。
①②A·B·阿尔茨霍夫斯基:《考古学通论》,科学出版社,1950年。
③E·D·菲利普斯:《草原の骑马民族国家》,胜藤猛译(日文)。
①孙机:《先秦、汉、晋腰带用金银带扣》,《文物》1994年第1期。
②《スキ夕イ黄金美术展》,日本放送协会,1992年。
①《スキ夕イ黄金美术展》图37。日本放送协会,1 992年。
② с·и·рyд eиo,cиИlpcкaя кoдиeкцlя пeTpa.l тa68,9. Mоcквa—дeпппrpaд,1962年。
①见《西汉南越王墓》上,第212页。
②《上海博物馆》图版155。文物出版社、讲谈社,1985年。
③孙机:《先秦、汉、晋腰带用金银带扣》,《文物》1994年第1期。
①钟侃、韩孔乐:《宁夏南部春秋战国的青铜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3年。
①孙机:《我国古代的革带》,《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②朝鲜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田野工作队:《考古学资料集》5,平壤,1978年。
③孙机:《先秦、汉、晋腰带用金银带扣》,《文物》1994年第1期。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周家地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5期。
①吉林省文物工作队等:《吉林榆树县老河深鲜卑墓群部分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2期。
①A·B·阿尔茨霍夫斯基:《考古学通论》,科学出版社(中译本),1956年。
②H·д·奇列诺娃:《蒙古考古论文集·关于蒙古和西伯利亚的鹿石》,苏联科学院出版社,莫斯科,1962年。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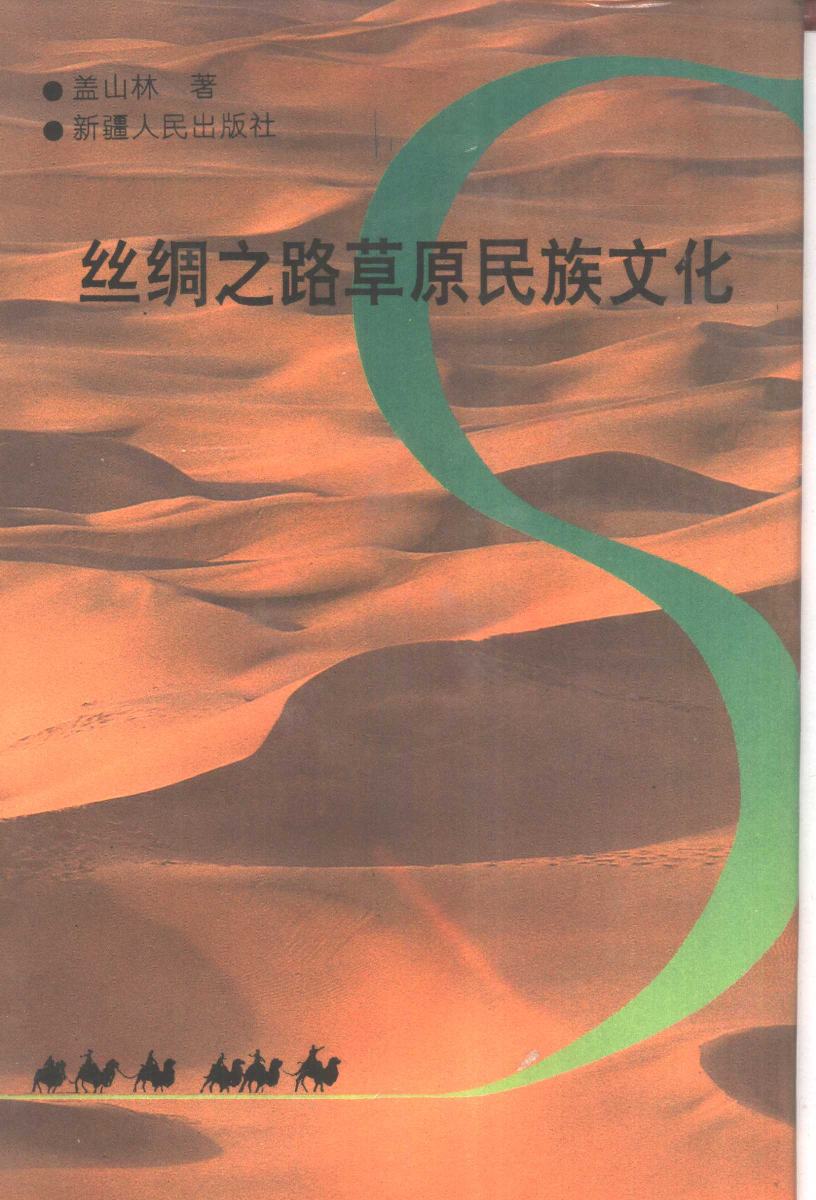
《丝绸之路草原民族文化》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出版地:1996.11
本书内容包括:石器时代草原文化艺术、青铜器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草原文化艺术、北朝至唐代的草原文化艺术、辽代至清代的草原文化艺术、当代草原文化艺术等。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