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草原丝绸之路
| 内容出处: | 《丝绸之路草原石人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290120020210003465 |
| 颗粒名称: | 第二节 草原丝绸之路 |
| 分类号: | K92 |
| 页数: | 11 |
| 页码: | 5-15 |
| 摘要: | 本文描述了一、亚欧草原通道寻踪,二艰辛的草原通道,三、黄金之路,四、张骞通西域后的草原丝路。 |
| 关键词: | 经济交流 “草原丝绸之路” 草原通道 |
内容
在广阔的亚欧大陆上,曾经有几条东西走向的道路,因以丝绸贸易而得名,人们称这些道路为“丝绸之路”。丝绸固然是沟通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是几千年来连接东方和西方商业往来的纽带。然而,中西方交通的开凿并非始自公元前二世纪,西汉时期的丝绸贸易,也并非唯独通行于绿洲农业地区。同样,草原通道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也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道路之一。人们将这条道路称作草原丝绸之路,又称作草原大通道,从而拓宽了丝绸之路的含义。
一、亚欧草原通道寻踪所谓草原通道,顾名思义,它是开辟于亚欧草原上的一条道路,通过草原地区连结东方农业居民与西方农业居民,以及草原居民与农业居民之间的往来,促进城市文明的发展。有人认为,最初的草原道是无形的,居民或追逐野兽随居而安,或“随畜逐水草”而行,骑马自由行进于草原,无路可寻。也有人认为,草原的道路就是牧羊道,草原通道就是牧道。牧民随季节性草场的迁移,年复一年地在草原踩出无数条道路,将它们串通起来就是亚欧草原之路。草原通道早期或许是在无形中形成的,然而仅仅通过居民的一般生活活动,是无法打通亚欧草原通道的,它必须是大规模的活动,才能够直接引起东西方居民的接触和相互了解东西方的差异,从而激发了开通和维护这条道路的共识。
亚欧草原通道的形成,部族或民族的迁移是其重要因素之一。
草原居民的自然迁移历来是非常频繁的,这是草原自然经济发展的必然,或因生活和生产的需要,或因自然灾害引起的被迫性转移。另外,就是战争引起的部族或民族活动。其中大规模的活动,能够成功地开辟草原的一些道路,为商贸活动打下一定的基础。
大约在距今三千年的时候,亚洲北部草原曾出现大面积的干旱,沙漠化非常地严重,迫使游牧部落大规模的南迁西移,从而踏开了东起西伯利亚的额尔古纳河流域,西至中亚、西亚和东欧的亚欧大陆草原交通大道。②类似的现象在历史文献中也有记载,比如:商周时期的鬼方北迁,开通了中原至西伯利亚贝加尔地区的通道,将中原进步的青铜工艺带到了这些地区产公元前2世纪,大月氏人的西迁,引起了塞人的南移;又随着乌孙人的西迁,而引起月氏人的南移。这些游牧民族的迁移活动,对开发河西走廊至伊犁地区,以及伊犁地区至帕米尔一带的草原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公元91年的北匈奴迁移,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汉朝与匈奴的战争有关系,然而漠北连年的严重天灾,也不能说不是原因之一。匈奴西迁进入新疆、中亚一直到了欧洲,对开通蒙古草原至伏尔加河沿黑海北岸交通起到重要作用。公元6世纪柔然汗国被突厥所灭,余部也西迁到了欧洲。另外,匈奴连年侵扰中原,掠夺缯絮、粮食,构成了中原文化与匈奴文化的接触,同时也发展了草原通向农业地区的道路。
公元六世纪,突厥人建立汗国并以武力兼并了蒙古高原、新疆和中亚的广大地区,控制和利用着草原通道,蒙古帝国的扩张更是众所周知的,他们的活动虽然存在很大的破坏性,但是,在这一时期,即“从13世纪中叶至14世纪中叶一百多年光景,欧洲和远东之间的接触的频繁,前所未有,也可能超过了快近19世纪止的任何时期”。④公元前7—1世纪生活和游牧在黑海、里海一带的斯基泰人,经常攻击四邻的部族或民族,将掠夺品和征收品从事交换活动,他们占据着黑海北岸的希腊殖民市场,输入希腊制品,⑤并且输出及革和奴隶。他们也到东方来进行贸易活动,成为东方和希腊文化传播的中间民族。
部族或民族的迁徙和战争打开了亚欧草原通道,居民的行商往来则巩固和发展了草原通道。居民的行商往往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比如,汉朝与匈奴的“和亲”形成了定期的“关市”贸易,增强了草原丝路居民的经济文化交流。这种交易往往是以物换物,各取所需。不过,这样的活动在草原并不是能持久的,草原游牧经济的难以稳定,以及受到天然灾害较多的影响,贸易总是阶段性的。尽管如此,贸易断断续续地发展着,交流的一些物资是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包括铁铜器、木漆器及丝织品等,都需要从汉地运往草原。所以,草原和农业居民的商贸关系紧紧地将他们联结在一起,这也是草原通道历久不衰的原因所在。
亚欧草原通道,显然并不像绿洲丝绸之路那样能够划分的很清楚,不过,通过一些迹象使我们能够寻觅到他们的轨迹。开发最早的草原通道是“古北道”,⑥这也是名符其实的草原丝绸之路。它是由漠北经过阿尔泰山向西的一条路线,在阿尔泰山东面自然地分出南北两条道路,南路沿阿尔泰山南麓西行,经过斋桑泊通过乌拉尔山南部草原,进入里海、黑海北沿岸的南俄草原。北路是沿阿尔泰山北行,经过今俄罗斯阿尔泰地区,而后南下与南路汇合,这条草原通道的两端各连结着ー个古文明地区,东面是与黄河流域商周文明的中国中原相连,由中国中原出发经河套地区至漠北或进入阿尔泰东部地区;西面与地中海北岸的古希腊文明连结起来,进入黑海地区。构成这一条通道存在的媒介,显然不可能仅仅是丝绸(对于严寒地带的居民来说,毛皮制品也是重要的商品),而应该是黄金。黄金是游牧民非常喜好的装饰品原料,可以打制首饰,装饰任何物品。同样,黄金也受到农业和城市居艮的偏爱。从一些资料反映出,亚欧许多地区的黄金来自于阿尔泰山,阿尔泰山金子发现的早,开采的也很早,大概公元前8—7世纪东西方的居民已知道阿尔泰黄金了,所以,亚欧草原大通道又被称作“黄金之路”。⑦草原通道是复杂的,这和草原游牧经济形态而造成的居民分散状况相联系,所以,在主线之外自然还有许多的支线。无论是主线还是支线,它都有一个使用上的变迁过程,新的路线开发必然要冷落某些旧路线,又因一些特殊情况而使某些一度冷落的旧路又得以重新利用。总之,草原通道不是僵死、固定不变的。
二、艰辛的草原通道草原通道路程非常艰险,许多地方只能是夏季才能通行,冬天一般都被风雪封山,无法通行。冬季最寒冷的日子,有的地方气温降到零下40度,许多野生动物都被冻死・经常还能听到冰雪成灾造成人畜死亡的消息,所以,气候的恶劣增加了开通草原通道的难度。另外,行走草原通道要翻越许多的山林,这些地方时有野兽出没,常常会发生野兽袭击人畜的事故,其危险程度显而易见,它的艰险不下于绿洲路。
亚欧草原通道的形成,曾经历过一个漫长的时间,它的出现与人类的活动是不可分割的。追溯草原居民的过去,考察文化发展的情况,就会发现草原通道的历程是艰苦的。
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就已进入了亚欧草原地带,由于中亚北部地区和欧洲草原之间受冰河以及里海海浸的影响,⑧形成了天然屏障,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造成地域性文化分隔的独特现象,形成了东欧平原、西伯利亚——蒙古高原、中亚三大晚旧石器文化系统(新疆草原目前还没有发现旧石器遗址),其中,中亚南部没有受冰川作用的直接影响。人们由南向北的迁移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以及对恶劣自然条件的适应能力,伴着对新地区的开发,或者说是尾随着狩猎的野生动物来到了辽阔的北方大草原的。
蒙古考古工作者曾将蒙古境内出土的旧石器与西伯利亚的作过比较,认为旧石器时代的蒙古和西伯利亚与中亚居民有过接触,⑨并且指出,蒙古旧石器与欧洲的有区别,表现在石核的形制及石器的制作方法上。亚洲草原和欧洲草原的隔绝保持了很长的时间,不仅在整个旧石器时代居民之间没有接触,而且到了中石器时代双方的文化传统仍有着显著的差异,同是狩猎经济而在石器加工的方法上则大相径庭。研究过里海周围地区中石器文化的学者认为,里海的中石器文化可能源于扎兹安,⑩与伊朗西北方和里海南岸的中石器文化群体相联系。作为这一地区的中石器文化总是伴随着传统的几何形细石器。而在中亚地区的细石器遗址中却出现了几何形和非几何形细石器共存的现象,说明东方文化传统与西方文化的接触主要还是在中亚地区。细石器似乎也可以划分为几个时期来考虑。这一划分不仅适合于新疆,而且也利于对周边文化的研究。细石器物在一定范围内延续的时间比较长,不仅在青铜时代,而且至铁器时代早期也能见到这种遗物,这在新疆境内的考古文化中表现的尤为明显。然而,这并不能否认它作为阶段性典型器物的存在,应该说对它的情况还需要作进一步研究。新疆中石器文化来自于东方,而细石器则形成了几个地方类型。⑪新疆草原带发现了不少的细石器遗址,在阿尔泰山前的额尔齐斯河流域,准噶尔盆地周缘的一些地方都有所发现。这些细石器传统主要是非几何形的,至今还没有发现典型的几何形石器。
从目前的考古资料可以看出,旧石器时代亚洲草原居民与欧洲草原居民没有发生过直接的接触,而在中石器时代或者说细石器出现后才有了接触,接触地点主要在中亚南部。这一时期的遗址分布情况表明,居民分布已非常广泛,并出现了相互移动的情况。
欧洲人向东移动,而东方人也开始向西活动,形成了亚欧草原居民布局的基本格局。
亚欧草原游牧居民的形成,应该是经过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半狩猎半农业向半农业半畜牧业的转化过程。农业的出现才使得有可能发展牲畜,草原适宜于畜牧业迅速的发展,迫使居民废弃了农业。蒙古、西伯利亚、中亚、里海和黑海锄耕农业工具的发现,说明了亚欧草原居民的游牧是在农业生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青铜时代是亚欧草原游牧业的发展时期,能够反映这一情况的考古发现,在亚洲草原上主要有安德罗诺沃文化、卡拉索克文化和鄂尔多斯式早期青铜文化。蒙古草原出土了类似卡拉索克文化的陶器、青铜刀、青铜斧,以及装饰品等,说明蒙古青铜时代文化与南西伯利亚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新疆也发现了与南西伯利亚青铜文化相类似的陶器和青铜器等,其铜镰刀,铜斧在奇台县七戽、吉木萨尔县、⑫阜康县、塔城市、⑬托里县、伊宁市、巩留县、⑭特克斯县等地都有出土。另外,类似的青铜器物在哈萨克斯坦大部分地区也有发现。这一文化西起乌拉尔,东迄鄂尔浑河,在花剌子模与塔札巴基阿布文化相混合。⑮东欧草原地带的青铜文化经过了三个时期,⑯都是以典型墓葬形制为代表的文化分期:竖井期、横穴期和木椁期。竖井期属于铜石并用时代;横穴期的青铜器已经相当地多了,但缺少大型铜器,常见的大型青铜器是宽刃斧;木椁文化起源于伏尔加河,随之代替了横穴文化传播到了顿河、徳聂伯河流域。一般认为,东欧的青铜器较西欧和西伯利亚为少,其中的銎管孔斧头,在西欧几乎没有,而东欧则常见,巴比伦特别多。如果说銎管孔斧可作为一种文化传统的特点,它在亚洲出现的比较早,不能排斥欧洲草原銎管孔斧是受亚洲草原青铜斧的影响而发展的地方类型。
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是亚洲草原文化与欧洲草原文化接触频繁的时期,主要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一是动物纹样装饰的青铜器的出现;二是出现了鹿石和墓地石人;三是青铜鍑在亚欧草原的分布。当然,还有其它的一些文化现象,比如前面提到的銎管孔斧。这几种文化现象,从目前的资料看都是首先出现于亚洲草原,此后到了欧洲草原,并且迅速地发展为地方类型。同时也存在文化上的反馈现象。这些都说明,青铜时代曾发生过亚欧草原居民的迁移的现象,迁移是相互的,而时间上有差异。到了早期铁器时代则存在着相对的稳定时期,地方性类型的文化特点也逐渐形成了。
青铜时代草原居民显得非常活跃,给人们一种印象是有的文化现象分布的非常广,甚至很难构成地方类型。亳无疑问,其中存在着大的部族或民族迁移,原因可能是天灾,正如前面谈到,三千年前亚洲北部草原出现的干旱、沙化,迫使游牧部族的大规模南迁西移。迁移造成了亚欧草原文化的传播,打通了亚欧草原大通道,随之牧民骑上了马背,奔驰于辽阔的草原,穿越漠北高原到达黄河流域;或横越阿尔泰山,经中亚进入南俄草原。总之,虽然亚欧草原青铜文明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发达的农耕文化影响,但发展的相当快,在打通亚欧草原通道上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东西方文明首先就是通过亚欧草原而得以了解的。到了早期铁器时代由于游牧民的强盛,亚欧草原通道オ出现了新的情况。
三、黄金之路虽然在青铜时代游牧民已经能够生产许多的乳制品、肉类,而且有兽皮、羊毛,及随着原料增加而日益增长的毛织品,这为游牧民与农业居民的最初的正常交换带来了可能⑰但是,这只能作为邻近地区的贸易活动。还要指出的是,这些物品是亚欧草原的游牧民共有的生产物品,不可能成为他们之间的贸易抢手商品,更不可能是沟通亚欧草原商贸的媒介。
亚欧草原传说中的古国名,常常出现在东西方的史料中,其中的“一目国”和“穷发”国,目前被认为是见于史籍的北方草原古老国家。“穷发”国见于《庄子》⑱,是一个极北的国家,在阿尔泰山一带。“穷发”即秃头之意。西方史料中也有类似的记载,称作“秃头”人,⑲指的也是亚洲北方草原的古老居民。如果从考古的发现来考察这两个国家,也能够追踪到他们的蛛丝马迹,据记载,秃头人“是一个长着狮子鼻和巨大下顎的民族”,显然具有蒙古人种特征。⑳新疆阿勒泰地区目前发现一种年代较早的墓地石人,没有雕刻发饰,眼睛一般呈圆形,显得外鼓,鼻子几乎呈三角形,翼部特别地宽大,嘴雕刻的很宽,呈特大嘴形,嘴与圆形的下颌构成了巨大的下顎,明显具有秃头人“狮子鼻和巨大下顎''的特点。从墓地石人的报导资料来看,哈萨克斯坦斋桑泊一带还没有发现这样的石人,新疆境内其它地区也没有见到,说明其分布仅限于阿尔泰山地。
在南西伯利亚米努辛斯克盆地发现的拟人形塔兹明石人,石人头顶和脸面两侧雕刻出了或竖立或横直的发饰及须髯,并且有动物式的耳朵,额部常常刻一只眼睛,呈圆形,用两条弧线将其与两侧的眼睛相隔。很明显,石人表现的是戴有假面具人物。我国对“一目国”的记载,最早见于《山海经》,说该国人皆一目,“中其面而居”。西方史料有关“独目人”的记载是,前额当中有一目,毛发毵疑,狗耳,对于这样的民族面貌特征的描述,也只能以游牧居民的民俗来考虑,仅仅作为一种伪装,或者说是面具,事情也就容易理解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独目人”的情况与南西伯利亚拟人形石人是多么的相似。
以上阐述的无论是“秃头”人,还是“独目人”,在希罗多德的记述中都与黄金交易有联系,他们不仅仅是黄金的采掘者,而且也是黄金的贩运者,黄金的产地就在阿尔泰山。⑳这一点,从希罗多德叙述的黄金贸易路线中就会看得更加清楚。
希罗多德著录的路线是公元前七至六世纪阿利斯铁阿斯《独目人》中提到的东行路线,基本路线是由顿河口出发,渡河来到了萨尔马特人的地区,而后经过布迪尼人境、沙漠带、杜萨格特伊人和玉尔卡依人地区、分离出来的斯基泰人和秃头人地区,最后到达伊塞顿人的地区。其中提到的布迪尼人的住地大概在今萨拉托夫州市附近,分离出来的斯基泰人在今切利诺格勒一带,而秃头人便活动在阿尔泰山地区。独目人则居住在黄金产地,斯基泰人主要是从秃头人手中获取金子,秃头人居住地就是黄金交易的地方。
阿尔泰金子对黑海北岸的斯基泰人是很有吸引力的,他们发展了黄金手工艺,制作人身饰物,装饰马具、武器以及各种器物,创造了辉煌的黄金艺术。阿尔泰黄金对黄河流域居民也是有吸引力的,目前考古出土部分先秦金器被推测可能是阿尔泰金的制品。另外,中亚和新疆其它地区出土的一些金器,也不排斥为阿尔泰金制品的可能。
阿尔泰山地自古以来就是盛产黄金的地方,史称“金微山”、“金山”,《新疆图志》记载,“阿尔泰向以产金著称”,“山之阳分东山、西山,绵亘三数百里,山沟矿沙中处产金,惟矿脉之广狭及产额丰歉不同”。根据勘探资料,阿勒泰黄金主要是砂金,有的河沟砂金含纯金达95%以上,㉑而且容易开采。所以,在开采工具十分落后的古代,这里的黄金就已能够成为亚欧草原贸易的主要商品,起到了沟通亚欧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在构筑、沟通亚欧草原的“黄金之路”中,阿尔泰这个黄金产地也是功不可没的。
四、张骞通西域后的草原丝路自张骞第一次通西域,随之公元前60年汉朝政府在新疆乌垒设西域都护府始,连结东西方文化的丝绸之路的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汉长安为丝绸之路起点的意义非常明确,将丝绸源源不断地运到了罗马。此时绿洲道的作用日趋明显,但是,草原道也是其重要路段,被人们称为“草原丝绸之路”。作为“古北道”的草原通道情况我们了解的并不多,此时主要涉及的草原丝路在新疆境内是沿天山北麓而行走的道路。《后汉书•西域传》车师条记载,“后部通乌孙”,也就是说“北新道西行,至东且弥国、西且弥国、单桓国、毕陆国、乌贪国,皆属车师后部王……转西北则乌孙、康居”,这条道也称作北道,属草原丝路。
从漠北进入新疆天山北麓,至中亚、乌拉尔南部地区、顿河的草原道,由匈奴西迁的情况中得到了证明。突厥进入新疆以至中亚,走的也应该是草原道。通过一个很长时间的草原居民活动,草原通道已经比较明确,它的畅通与否经常与政治形势联系在一起。
《新唐书•地理志》四:''自庭州西延城西六十里有沙钵城守捉,又有冯洛守捉,又本八十里有耶勒城守捉,又八十里有俱六城守捉,又百里至轮台县,又百五十里有张堡城守捉,又渡里移德建河,七十里有乌宰守捉,又渡白杨河,七十里有清镇军城,又渡叶叶河,七十里有叶河守捉,又渡黑水,七十里有黑水守捉,又七十里有东林守捉,又七十里有西林守捉,又经黄草泊、大漠、小磧、渡石漆河,逾车岭,至弓月城”。这条路又称作碎叶路,《元和郡县志》卷四十“庭州"条载”沙缽镇在州西五十里,当碎叶路"• “俱六镇在州西二百四十里,当〓叶路”,另外,八世纪时,由庭州进入漠北的路叫回鹘道,见于《元和郡县志》所载,从庭州至回鹘衙帐三千里,经赤遮镇,盐泉镇,特罗堡子等。
新疆境内的草原道还包括准噶尔盆地西缘的道路,由青河沿阿尔泰山南麓西行至福海地界南下,再顺准噶尔盆地西缘行,至博尔塔拉与北道汇合,这条路被称作“大北道”。㉒总之•草原通道历史悠长,从遥远的中石器时代,经过元、明、清代至今都在利用,起到联系中西文化的作用。从亚欧草原居民的活动情况考察,居民的大规模迁移对开拓草原通道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阿尔泰黄金的发现开采和加工成许多金制品,对众多草原居民的吸引力,无疑也是促进亚欧草原通道繁荣畅通的重要原因。
一、亚欧草原通道寻踪所谓草原通道,顾名思义,它是开辟于亚欧草原上的一条道路,通过草原地区连结东方农业居民与西方农业居民,以及草原居民与农业居民之间的往来,促进城市文明的发展。有人认为,最初的草原道是无形的,居民或追逐野兽随居而安,或“随畜逐水草”而行,骑马自由行进于草原,无路可寻。也有人认为,草原的道路就是牧羊道,草原通道就是牧道。牧民随季节性草场的迁移,年复一年地在草原踩出无数条道路,将它们串通起来就是亚欧草原之路。草原通道早期或许是在无形中形成的,然而仅仅通过居民的一般生活活动,是无法打通亚欧草原通道的,它必须是大规模的活动,才能够直接引起东西方居民的接触和相互了解东西方的差异,从而激发了开通和维护这条道路的共识。
亚欧草原通道的形成,部族或民族的迁移是其重要因素之一。
草原居民的自然迁移历来是非常频繁的,这是草原自然经济发展的必然,或因生活和生产的需要,或因自然灾害引起的被迫性转移。另外,就是战争引起的部族或民族活动。其中大规模的活动,能够成功地开辟草原的一些道路,为商贸活动打下一定的基础。
大约在距今三千年的时候,亚洲北部草原曾出现大面积的干旱,沙漠化非常地严重,迫使游牧部落大规模的南迁西移,从而踏开了东起西伯利亚的额尔古纳河流域,西至中亚、西亚和东欧的亚欧大陆草原交通大道。②类似的现象在历史文献中也有记载,比如:商周时期的鬼方北迁,开通了中原至西伯利亚贝加尔地区的通道,将中原进步的青铜工艺带到了这些地区产公元前2世纪,大月氏人的西迁,引起了塞人的南移;又随着乌孙人的西迁,而引起月氏人的南移。这些游牧民族的迁移活动,对开发河西走廊至伊犁地区,以及伊犁地区至帕米尔一带的草原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公元91年的北匈奴迁移,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汉朝与匈奴的战争有关系,然而漠北连年的严重天灾,也不能说不是原因之一。匈奴西迁进入新疆、中亚一直到了欧洲,对开通蒙古草原至伏尔加河沿黑海北岸交通起到重要作用。公元6世纪柔然汗国被突厥所灭,余部也西迁到了欧洲。另外,匈奴连年侵扰中原,掠夺缯絮、粮食,构成了中原文化与匈奴文化的接触,同时也发展了草原通向农业地区的道路。
公元六世纪,突厥人建立汗国并以武力兼并了蒙古高原、新疆和中亚的广大地区,控制和利用着草原通道,蒙古帝国的扩张更是众所周知的,他们的活动虽然存在很大的破坏性,但是,在这一时期,即“从13世纪中叶至14世纪中叶一百多年光景,欧洲和远东之间的接触的频繁,前所未有,也可能超过了快近19世纪止的任何时期”。④公元前7—1世纪生活和游牧在黑海、里海一带的斯基泰人,经常攻击四邻的部族或民族,将掠夺品和征收品从事交换活动,他们占据着黑海北岸的希腊殖民市场,输入希腊制品,⑤并且输出及革和奴隶。他们也到东方来进行贸易活动,成为东方和希腊文化传播的中间民族。
部族或民族的迁徙和战争打开了亚欧草原通道,居民的行商往来则巩固和发展了草原通道。居民的行商往往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比如,汉朝与匈奴的“和亲”形成了定期的“关市”贸易,增强了草原丝路居民的经济文化交流。这种交易往往是以物换物,各取所需。不过,这样的活动在草原并不是能持久的,草原游牧经济的难以稳定,以及受到天然灾害较多的影响,贸易总是阶段性的。尽管如此,贸易断断续续地发展着,交流的一些物资是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包括铁铜器、木漆器及丝织品等,都需要从汉地运往草原。所以,草原和农业居民的商贸关系紧紧地将他们联结在一起,这也是草原通道历久不衰的原因所在。
亚欧草原通道,显然并不像绿洲丝绸之路那样能够划分的很清楚,不过,通过一些迹象使我们能够寻觅到他们的轨迹。开发最早的草原通道是“古北道”,⑥这也是名符其实的草原丝绸之路。它是由漠北经过阿尔泰山向西的一条路线,在阿尔泰山东面自然地分出南北两条道路,南路沿阿尔泰山南麓西行,经过斋桑泊通过乌拉尔山南部草原,进入里海、黑海北沿岸的南俄草原。北路是沿阿尔泰山北行,经过今俄罗斯阿尔泰地区,而后南下与南路汇合,这条草原通道的两端各连结着ー个古文明地区,东面是与黄河流域商周文明的中国中原相连,由中国中原出发经河套地区至漠北或进入阿尔泰东部地区;西面与地中海北岸的古希腊文明连结起来,进入黑海地区。构成这一条通道存在的媒介,显然不可能仅仅是丝绸(对于严寒地带的居民来说,毛皮制品也是重要的商品),而应该是黄金。黄金是游牧民非常喜好的装饰品原料,可以打制首饰,装饰任何物品。同样,黄金也受到农业和城市居艮的偏爱。从一些资料反映出,亚欧许多地区的黄金来自于阿尔泰山,阿尔泰山金子发现的早,开采的也很早,大概公元前8—7世纪东西方的居民已知道阿尔泰黄金了,所以,亚欧草原大通道又被称作“黄金之路”。⑦草原通道是复杂的,这和草原游牧经济形态而造成的居民分散状况相联系,所以,在主线之外自然还有许多的支线。无论是主线还是支线,它都有一个使用上的变迁过程,新的路线开发必然要冷落某些旧路线,又因一些特殊情况而使某些一度冷落的旧路又得以重新利用。总之,草原通道不是僵死、固定不变的。
二、艰辛的草原通道草原通道路程非常艰险,许多地方只能是夏季才能通行,冬天一般都被风雪封山,无法通行。冬季最寒冷的日子,有的地方气温降到零下40度,许多野生动物都被冻死・经常还能听到冰雪成灾造成人畜死亡的消息,所以,气候的恶劣增加了开通草原通道的难度。另外,行走草原通道要翻越许多的山林,这些地方时有野兽出没,常常会发生野兽袭击人畜的事故,其危险程度显而易见,它的艰险不下于绿洲路。
亚欧草原通道的形成,曾经历过一个漫长的时间,它的出现与人类的活动是不可分割的。追溯草原居民的过去,考察文化发展的情况,就会发现草原通道的历程是艰苦的。
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就已进入了亚欧草原地带,由于中亚北部地区和欧洲草原之间受冰河以及里海海浸的影响,⑧形成了天然屏障,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造成地域性文化分隔的独特现象,形成了东欧平原、西伯利亚——蒙古高原、中亚三大晚旧石器文化系统(新疆草原目前还没有发现旧石器遗址),其中,中亚南部没有受冰川作用的直接影响。人们由南向北的迁移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以及对恶劣自然条件的适应能力,伴着对新地区的开发,或者说是尾随着狩猎的野生动物来到了辽阔的北方大草原的。
蒙古考古工作者曾将蒙古境内出土的旧石器与西伯利亚的作过比较,认为旧石器时代的蒙古和西伯利亚与中亚居民有过接触,⑨并且指出,蒙古旧石器与欧洲的有区别,表现在石核的形制及石器的制作方法上。亚洲草原和欧洲草原的隔绝保持了很长的时间,不仅在整个旧石器时代居民之间没有接触,而且到了中石器时代双方的文化传统仍有着显著的差异,同是狩猎经济而在石器加工的方法上则大相径庭。研究过里海周围地区中石器文化的学者认为,里海的中石器文化可能源于扎兹安,⑩与伊朗西北方和里海南岸的中石器文化群体相联系。作为这一地区的中石器文化总是伴随着传统的几何形细石器。而在中亚地区的细石器遗址中却出现了几何形和非几何形细石器共存的现象,说明东方文化传统与西方文化的接触主要还是在中亚地区。细石器似乎也可以划分为几个时期来考虑。这一划分不仅适合于新疆,而且也利于对周边文化的研究。细石器物在一定范围内延续的时间比较长,不仅在青铜时代,而且至铁器时代早期也能见到这种遗物,这在新疆境内的考古文化中表现的尤为明显。然而,这并不能否认它作为阶段性典型器物的存在,应该说对它的情况还需要作进一步研究。新疆中石器文化来自于东方,而细石器则形成了几个地方类型。⑪新疆草原带发现了不少的细石器遗址,在阿尔泰山前的额尔齐斯河流域,准噶尔盆地周缘的一些地方都有所发现。这些细石器传统主要是非几何形的,至今还没有发现典型的几何形石器。
从目前的考古资料可以看出,旧石器时代亚洲草原居民与欧洲草原居民没有发生过直接的接触,而在中石器时代或者说细石器出现后才有了接触,接触地点主要在中亚南部。这一时期的遗址分布情况表明,居民分布已非常广泛,并出现了相互移动的情况。
欧洲人向东移动,而东方人也开始向西活动,形成了亚欧草原居民布局的基本格局。
亚欧草原游牧居民的形成,应该是经过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半狩猎半农业向半农业半畜牧业的转化过程。农业的出现才使得有可能发展牲畜,草原适宜于畜牧业迅速的发展,迫使居民废弃了农业。蒙古、西伯利亚、中亚、里海和黑海锄耕农业工具的发现,说明了亚欧草原居民的游牧是在农业生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青铜时代是亚欧草原游牧业的发展时期,能够反映这一情况的考古发现,在亚洲草原上主要有安德罗诺沃文化、卡拉索克文化和鄂尔多斯式早期青铜文化。蒙古草原出土了类似卡拉索克文化的陶器、青铜刀、青铜斧,以及装饰品等,说明蒙古青铜时代文化与南西伯利亚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新疆也发现了与南西伯利亚青铜文化相类似的陶器和青铜器等,其铜镰刀,铜斧在奇台县七戽、吉木萨尔县、⑫阜康县、塔城市、⑬托里县、伊宁市、巩留县、⑭特克斯县等地都有出土。另外,类似的青铜器物在哈萨克斯坦大部分地区也有发现。这一文化西起乌拉尔,东迄鄂尔浑河,在花剌子模与塔札巴基阿布文化相混合。⑮东欧草原地带的青铜文化经过了三个时期,⑯都是以典型墓葬形制为代表的文化分期:竖井期、横穴期和木椁期。竖井期属于铜石并用时代;横穴期的青铜器已经相当地多了,但缺少大型铜器,常见的大型青铜器是宽刃斧;木椁文化起源于伏尔加河,随之代替了横穴文化传播到了顿河、徳聂伯河流域。一般认为,东欧的青铜器较西欧和西伯利亚为少,其中的銎管孔斧头,在西欧几乎没有,而东欧则常见,巴比伦特别多。如果说銎管孔斧可作为一种文化传统的特点,它在亚洲出现的比较早,不能排斥欧洲草原銎管孔斧是受亚洲草原青铜斧的影响而发展的地方类型。
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是亚洲草原文化与欧洲草原文化接触频繁的时期,主要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一是动物纹样装饰的青铜器的出现;二是出现了鹿石和墓地石人;三是青铜鍑在亚欧草原的分布。当然,还有其它的一些文化现象,比如前面提到的銎管孔斧。这几种文化现象,从目前的资料看都是首先出现于亚洲草原,此后到了欧洲草原,并且迅速地发展为地方类型。同时也存在文化上的反馈现象。这些都说明,青铜时代曾发生过亚欧草原居民的迁移的现象,迁移是相互的,而时间上有差异。到了早期铁器时代则存在着相对的稳定时期,地方性类型的文化特点也逐渐形成了。
青铜时代草原居民显得非常活跃,给人们一种印象是有的文化现象分布的非常广,甚至很难构成地方类型。亳无疑问,其中存在着大的部族或民族迁移,原因可能是天灾,正如前面谈到,三千年前亚洲北部草原出现的干旱、沙化,迫使游牧部族的大规模南迁西移。迁移造成了亚欧草原文化的传播,打通了亚欧草原大通道,随之牧民骑上了马背,奔驰于辽阔的草原,穿越漠北高原到达黄河流域;或横越阿尔泰山,经中亚进入南俄草原。总之,虽然亚欧草原青铜文明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发达的农耕文化影响,但发展的相当快,在打通亚欧草原通道上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东西方文明首先就是通过亚欧草原而得以了解的。到了早期铁器时代由于游牧民的强盛,亚欧草原通道オ出现了新的情况。
三、黄金之路虽然在青铜时代游牧民已经能够生产许多的乳制品、肉类,而且有兽皮、羊毛,及随着原料增加而日益增长的毛织品,这为游牧民与农业居民的最初的正常交换带来了可能⑰但是,这只能作为邻近地区的贸易活动。还要指出的是,这些物品是亚欧草原的游牧民共有的生产物品,不可能成为他们之间的贸易抢手商品,更不可能是沟通亚欧草原商贸的媒介。
亚欧草原传说中的古国名,常常出现在东西方的史料中,其中的“一目国”和“穷发”国,目前被认为是见于史籍的北方草原古老国家。“穷发”国见于《庄子》⑱,是一个极北的国家,在阿尔泰山一带。“穷发”即秃头之意。西方史料中也有类似的记载,称作“秃头”人,⑲指的也是亚洲北方草原的古老居民。如果从考古的发现来考察这两个国家,也能够追踪到他们的蛛丝马迹,据记载,秃头人“是一个长着狮子鼻和巨大下顎的民族”,显然具有蒙古人种特征。⑳新疆阿勒泰地区目前发现一种年代较早的墓地石人,没有雕刻发饰,眼睛一般呈圆形,显得外鼓,鼻子几乎呈三角形,翼部特别地宽大,嘴雕刻的很宽,呈特大嘴形,嘴与圆形的下颌构成了巨大的下顎,明显具有秃头人“狮子鼻和巨大下顎''的特点。从墓地石人的报导资料来看,哈萨克斯坦斋桑泊一带还没有发现这样的石人,新疆境内其它地区也没有见到,说明其分布仅限于阿尔泰山地。
在南西伯利亚米努辛斯克盆地发现的拟人形塔兹明石人,石人头顶和脸面两侧雕刻出了或竖立或横直的发饰及须髯,并且有动物式的耳朵,额部常常刻一只眼睛,呈圆形,用两条弧线将其与两侧的眼睛相隔。很明显,石人表现的是戴有假面具人物。我国对“一目国”的记载,最早见于《山海经》,说该国人皆一目,“中其面而居”。西方史料有关“独目人”的记载是,前额当中有一目,毛发毵疑,狗耳,对于这样的民族面貌特征的描述,也只能以游牧居民的民俗来考虑,仅仅作为一种伪装,或者说是面具,事情也就容易理解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独目人”的情况与南西伯利亚拟人形石人是多么的相似。
以上阐述的无论是“秃头”人,还是“独目人”,在希罗多德的记述中都与黄金交易有联系,他们不仅仅是黄金的采掘者,而且也是黄金的贩运者,黄金的产地就在阿尔泰山。⑳这一点,从希罗多德叙述的黄金贸易路线中就会看得更加清楚。
希罗多德著录的路线是公元前七至六世纪阿利斯铁阿斯《独目人》中提到的东行路线,基本路线是由顿河口出发,渡河来到了萨尔马特人的地区,而后经过布迪尼人境、沙漠带、杜萨格特伊人和玉尔卡依人地区、分离出来的斯基泰人和秃头人地区,最后到达伊塞顿人的地区。其中提到的布迪尼人的住地大概在今萨拉托夫州市附近,分离出来的斯基泰人在今切利诺格勒一带,而秃头人便活动在阿尔泰山地区。独目人则居住在黄金产地,斯基泰人主要是从秃头人手中获取金子,秃头人居住地就是黄金交易的地方。
阿尔泰金子对黑海北岸的斯基泰人是很有吸引力的,他们发展了黄金手工艺,制作人身饰物,装饰马具、武器以及各种器物,创造了辉煌的黄金艺术。阿尔泰黄金对黄河流域居民也是有吸引力的,目前考古出土部分先秦金器被推测可能是阿尔泰金的制品。另外,中亚和新疆其它地区出土的一些金器,也不排斥为阿尔泰金制品的可能。
阿尔泰山地自古以来就是盛产黄金的地方,史称“金微山”、“金山”,《新疆图志》记载,“阿尔泰向以产金著称”,“山之阳分东山、西山,绵亘三数百里,山沟矿沙中处产金,惟矿脉之广狭及产额丰歉不同”。根据勘探资料,阿勒泰黄金主要是砂金,有的河沟砂金含纯金达95%以上,㉑而且容易开采。所以,在开采工具十分落后的古代,这里的黄金就已能够成为亚欧草原贸易的主要商品,起到了沟通亚欧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在构筑、沟通亚欧草原的“黄金之路”中,阿尔泰这个黄金产地也是功不可没的。
四、张骞通西域后的草原丝路自张骞第一次通西域,随之公元前60年汉朝政府在新疆乌垒设西域都护府始,连结东西方文化的丝绸之路的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汉长安为丝绸之路起点的意义非常明确,将丝绸源源不断地运到了罗马。此时绿洲道的作用日趋明显,但是,草原道也是其重要路段,被人们称为“草原丝绸之路”。作为“古北道”的草原通道情况我们了解的并不多,此时主要涉及的草原丝路在新疆境内是沿天山北麓而行走的道路。《后汉书•西域传》车师条记载,“后部通乌孙”,也就是说“北新道西行,至东且弥国、西且弥国、单桓国、毕陆国、乌贪国,皆属车师后部王……转西北则乌孙、康居”,这条道也称作北道,属草原丝路。
从漠北进入新疆天山北麓,至中亚、乌拉尔南部地区、顿河的草原道,由匈奴西迁的情况中得到了证明。突厥进入新疆以至中亚,走的也应该是草原道。通过一个很长时间的草原居民活动,草原通道已经比较明确,它的畅通与否经常与政治形势联系在一起。
《新唐书•地理志》四:''自庭州西延城西六十里有沙钵城守捉,又有冯洛守捉,又本八十里有耶勒城守捉,又八十里有俱六城守捉,又百里至轮台县,又百五十里有张堡城守捉,又渡里移德建河,七十里有乌宰守捉,又渡白杨河,七十里有清镇军城,又渡叶叶河,七十里有叶河守捉,又渡黑水,七十里有黑水守捉,又七十里有东林守捉,又七十里有西林守捉,又经黄草泊、大漠、小磧、渡石漆河,逾车岭,至弓月城”。这条路又称作碎叶路,《元和郡县志》卷四十“庭州"条载”沙缽镇在州西五十里,当碎叶路"• “俱六镇在州西二百四十里,当〓叶路”,另外,八世纪时,由庭州进入漠北的路叫回鹘道,见于《元和郡县志》所载,从庭州至回鹘衙帐三千里,经赤遮镇,盐泉镇,特罗堡子等。
新疆境内的草原道还包括准噶尔盆地西缘的道路,由青河沿阿尔泰山南麓西行至福海地界南下,再顺准噶尔盆地西缘行,至博尔塔拉与北道汇合,这条路被称作“大北道”。㉒总之•草原通道历史悠长,从遥远的中石器时代,经过元、明、清代至今都在利用,起到联系中西文化的作用。从亚欧草原居民的活动情况考察,居民的大规模迁移对开拓草原通道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阿尔泰黄金的发现开采和加工成许多金制品,对众多草原居民的吸引力,无疑也是促进亚欧草原通道繁荣畅通的重要原因。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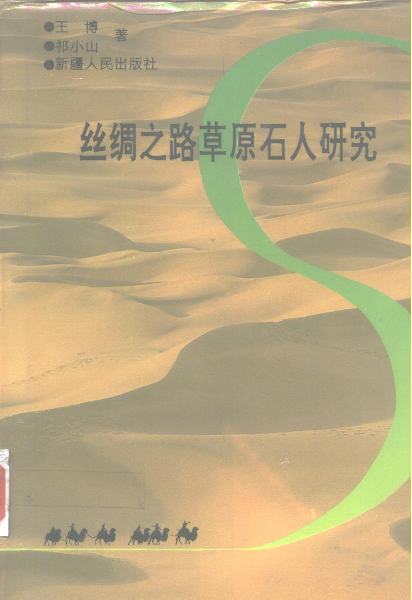
《丝绸之路草原石人研究》
出版者:新疆人民出版社
出版地:2010
本书内容包括:亚欧草原和草原丝绸之路、蒙古石人研究综述、南西伯利亚草原石人、中亚石人研究综述、新疆石人的分布及特征、亚欧草原鹿石及相关问题等。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