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丹枕与统埏
| 内容出处: | 《敦煌吐蕃统治时期石窟与藏传佛教艺术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290120020210003313 |
| 颗粒名称: | 二、丹枕与统埏 |
| 分类号: | K879.214-53 |
| 页数: | 22 |
| 页码: | 541-562 |
| 摘要: | 西藏拉萨的大昭寺创建于吐蕃时期,它的属于早期阶段的建筑,布局、形制以及装饰风格,俱与印度公元6世纪开凿的阿旃陀石窟十分相似①。 宿白先生在《西藏拉萨地区佛寺调查记》中对此已有缜密细致的分析研究。这里要讨论的是大昭寺中心佛殿第二层四周廊道壁面上发现的两幅早期壁画,其中一幅(图16),《西藏拉萨地区佛寺调查记》认为其“既有一定的印度风格,又和传世的公元12~13世纪所绘唐卡有相似处”①,因将之归人大昭寺第二阶段,即公元9世纪40年代至14世纪中期的遗存。张亚莎的《西藏美术史》也持大致相同的意见②。另一幅著录于《宝藏——中国西藏历史文物》,命为“供奉图”(图17),归之于吐蕃时期③。谢继胜的《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一书也举出此幅,并认为“大昭寺虽然经过后代多次重修,但这些早期壁画并没有重新绘制的痕迹,我们没有理由否定它们的存在”;“但是从根本上来看,这些卫藏地区的大昭寺壁画与公元1040年左右的塔波(Tabo)壁画的用线风格所展示的优雅、舒缓曲线有关系,只是没有塔波风格的厚重线条”①,则仍是从绘画风格的角度来认识它的时代。 大昭寺的这两幅早期壁画遗存究竟是否可以归属于吐蕃时期,或者还可以有另外的分析角度。这里想从一两个细节人手。且看几个可作比较的例子,如《中国藏传佛教雕塑全集》著录故宫藏吐蕃时期出自东北印度工匠的金铜佛像,即释迦牟尼坐像一尊,观音菩萨坐像一尊(图18、19)气又 《图像与风格——故宫藏传佛教造像》著录同期来自尼泊尔的一尊铜镀金嵌宝石观音菩萨坐像(图20)®。关于前两例佛坐像的坐具,《中国藏传佛教雕塑全集》图版说明曰:莲花座后是方形宝座式靠背,雕出软靠垫,靠背左右两边雕刻立起的狮子, 狮子踏象,象卧莲花上。圆形火焰头光, 顶部饰圆伞盖、双飘带,莲花座上为长方底座,两角刻卧狮,这种豪华的宝座形背光,在印度后笈多时期的佛像中已出现。 |
| 关键词: | 敦煌石窟 文集 喇嘛宗 宗教艺术 |
内容
西藏拉萨的大昭寺创建于吐蕃时期,它的属于早期阶段的建筑,布局、形制以及装饰风格,俱与印度公元6世纪开凿的阿旃陀石窟十分相似①。 宿白先生在《西藏拉萨地区佛寺调查记》中对此已有缜密细致的分析研究。这里要讨论的是大昭寺中心佛殿第二层四周廊道壁面上发现的两幅早期壁画,其中一幅(图16),《西藏拉萨地区佛寺调查记》认为其“既有一定的印度风格,又和传世的公元12~13世纪所绘唐卡有相似处”①,因将之归人大昭寺第二阶段,即公元9世纪40年代至14世纪中期的遗存。张亚莎的《西藏美术史》也持大致相同的意见②。另一幅著录于《宝藏——中国西藏历史文物》,命为“供奉图”(图17),归之于吐蕃时期③。谢继胜的《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一书也举出此幅,并认为“大昭寺虽然经过后代多次重修,但这些早期壁画并没有重新绘制的痕迹,我们没有理由否定它们的存在”;“但是从根本上来看,这些卫藏地区的大昭寺壁画与公元1040年左右的塔波(Tabo)壁画的用线风格所展示的优雅、舒缓曲线有关系,只是没有塔波风格的厚重线条”①,则仍是从绘画风格的角度来认识它的时代。
大昭寺的这两幅早期壁画遗存究竟是否可以归属于吐蕃时期,或者还可以有另外的分析角度。这里想从一两个细节人手。且看几个可作比较的例子,如《中国藏传佛教雕塑全集》著录故宫藏吐蕃时期出自东北印度工匠的金铜佛像,即释迦牟尼坐像一尊,观音菩萨坐像一尊(图18、19)气又 《图像与风格——故宫藏传佛教造像》著录同期来自尼泊尔的一尊铜镀金嵌宝石观音菩萨坐像(图20)®。关于前两例佛坐像的坐具,《中国藏传佛教雕塑全集》图版说明曰:莲花座后是方形宝座式靠背,雕出软靠垫,靠背左右两边雕刻立起的狮子, 狮子踏象,象卧莲花上。圆形火焰头光, 顶部饰圆伞盖、双飘带,莲花座上为长方底座,两角刻卧狮,这种豪华的宝座形背光,在印度后笈多时期的佛像中已出现。
观音坐像之说明曰:背靠装饰豪华图20铜镀金嵌宝石观音菩萨坐像故宫藏的宝座,雕出软靠垫,靠背两侧雕立狮、大象、莲花。……圆莲座下承长方台座,座中饰翻卷的台布,左右角两狮支撑。①讨论所欲关注的细节之一,便是坐具后面的所谓“软靠垫”,它正为大昭寺早期壁画和这里举出的金铜佛像所共有。而“软靠垫”的渊源本在印度,早期如出土于纳迦尔朱纳康达的石雕《惊悉出家》②(图21),又今藏法国吉美博物馆的石雕《难陀出家》③(图22),时代为公元3世纪的南印度伊克什瓦库王朝时期。之后的实例,有阿旃陀石窟第2、10、17窟中的雕像或壁画,时代约在公元5~6世纪(图23、24)④。稍晚的例子,可以举出埃罗拉石窟第12窟的佛雕像(图25、26),时代约在公元6~8世纪。
此所谓“软靠垫”,在佛经中名作丹枕或倚枕。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二 (释《大般涅槃经》卷一之“丹枕”)曰:“案天竺无木枕,皆以赤皮叠布为枕,贮以兜罗绵及毛,枕而且倚。丹,言其赤色也。”①又慧琳《音义》卷四“丹枕” 条(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三百九十八)曰:“天竺国风俗不用木石为枕,皆赤皮或赤色布作囊,贮以覩罗绵及以毛絮之类为枕,或用枕头,或作倚枕。丹,红赤色者用也。”又同书卷二十七:“丹枕,有释枕着仙丹可以延寿,此谓不然。案天竺无木枕,皆以赤皮叠布为枕,贮以覩罗绵及毛絮之类,枕而且倚。丹,赤色也,即同诸经朱色枕耳。头枕、倚枕,悉赤如丹。”又同书卷十三“倚枕”条(释《大宝积经》卷一百零九)曰:“案倚枕者,以锦绮缯彩作囊,盛耍物,贵人置之左右,或倚或凭,名为倚枕也。”又卷四十九 “倚枕”条(释《菩提资粮论》卷一)曰:“倚枕者,大枕也。锦绮缯彩作囊,盛轻耍物,置之左右前后,尊贵之人倚凭,名为倚枕。”叠布,即棉布;覩罗绵即木棉。所谓“耍物”“轻契物”,也当是棉花、毛絮之类。可知丹枕或倚枕, 原系印度上流社会日常生活中的习用之具。释典中的描述也是如此,如 《佛本行集经》卷十九:“呜呼我子!在于宫内,细滑床敷,柔软毡褥,或覆天衣,或复两边挟置倚枕。或卧或偃,随意自在。”前举纳迦尔朱纳康达石雕 《惊悉出家》,表现的便正是与此描写相合的宫廷生活。在阿旃陀石窟第 17窟“太子须大拏本生图”以及此窟的藻井装饰画中,都可以见到丹枕在生活中或背倚或侧凭的使用情景(图27、28 )。阿旃陀石窟第26窟涅槃石雕中的佛陀则是以丹枕枕首而卧(图29)。丹枕并且也用于印度教艺术, 如印度国家博物馆所藏一件公元5世纪的石雕湿婆像(图30、31)②。
丹枕用于佛教艺术,自然也有释典的依据如玄奘译《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九十八云:“妙香城内有诸士女,于其城中七宝台上,为法涌菩萨摩诃萨敷师子座”;“于其座上重敷裀褥,次铺绮粑,覆以白㲲,络以綩〓,宝座两边双设丹枕,垂诸帏带,散妙香花”气原是“贵人置之左右,或倚或凭”的倚枕亦即丹枕,移用于此,便又添一重尊礼之意。而丹枕之外, 这里提到的还有“綩〓”,此即本文涉及的另一个细节问题。
婉埏是汉译佛经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名词,但诸经对它的描述不尽一致。或曰以缯制成,如西晋竺法护译《佛说海龙王经》卷三中提到海龙王于大殿上化立师子之座,“敷无数百千天缯,以为綩〓”④。或曰锦绣金缕,饰以璎珞,如竺法护译《普曜经》卷一“瓔珞之饰床座婉绁”;《普曜经》卷八“吾子在宫时,茵蓐布綩綖,皆以锦绣成,柔软有光泽” ①;《长阿含经》卷三 “綩綖细软,金缕织成,布其座上”②。又曰以绮,唐地婆诃罗译《方广大庄严经》卷十二:“我子在家时,坐卧敷綩綖。皆以绮饰成,柔软而光泽。”③而隋吉藏《法华义疏》卷六云:“綩綖者,外国精绢也,名盘缩绣。富贵者重而敷之。”④可知统缍原是异域的高档织物,大略与中土绢、绮、缯等之精好者相仿佛,而以柔软光润精细华美为特色。诸经译者便只是从汉语中拣择接近经文原义的字词以释义,中土其实并无与它恰切对应之物。此所以慧琳 《一切经音义》释“綩綖”一词乃颇费踌躇,如《音义》卷十二释《大宝积经》 卷十二曰:“若依字义,与经甚乖,今并不取。经云綩綖者,乃珍妙华丽锦绣绵褥、概(音池)毡、花毯,舞筵之类也。字书并无此正字,借用也。”而唐窥基撰《妙法莲华经玄赞》则以为之译并不恰当:“重敷婉莛者,敷,陈设也,有作綩綖。统音,《字林》:一远反。《玉篇》:琬,纮也,纮冠也。今应作婉, 婉,美文章。綩綖者,席褥,应作莛字。《切韵》:綖者,冠上覆。《玉篇》:冠前后而垂者名綩綖。今取文缛、华毡之类,綩綖以为茵蓐,不知义何所从。故字应从婉莚”⑤。不过排比诸经之义,綩綖并不等同于茵褥。译经者取“缀”而不取“筵”,当是考虑其式与冕服之冠前后而垂的“纟延”约略相当,于是借用 “綩綖”在这里的垂覆之义。“琬”字则是借来以表其“文”,——或织文,或绣文' 然而慧琳所举绵褥、毡、毯,包括舞筵,其用途或者是铺展,或者是围护⑦,却皆非以轻薄柔软之状而成垂覆之式,窥基因此说“綩綖以为茵蓐, 不知义何所从”,且认为若是席褥,“字应从婉莛”。
今细绎经义,所谓“于其座上重敷裀褥,次铺绮粑,覆以白㲲,络以綩綖”,便是吉藏所云“重而敷之”“重敷蓐上”®,则綩綖当是蒙覆于坐具之表,即裀褥、绮粑、白㲲之外,更敷设綩綖而颇有装饰之用。译者特地用了一个“络”字,意在表明它的有垂穗如璎珞之类ᄆ而他经提到綩綖,也常常是茵褥、毡毯与之并举,且綩綖列在其末①,更每每强调它的“柔软”或“柔软细叠”,可据以想见其式。
按照这样的理解,在印度早期石雕中便可以找到綩綖的实例,如印度国家博物馆藏一件早期安达罗王朝石雕中坐具的敷设,石雕内容为宫廷生活(图32、33)②。綩綖在佛教艺术中的使用,前期主要见于古印度西北部犍陀罗艺术中的石雕,如白沙瓦博物馆藏佛传故事中的《占梦》(图 34)③拉合尔博物馆藏《三十三天说法》(图35 )④。后期则可以埃罗拉佛教石窟中的样式为例,即它是敷设于仰覆莲花之下的坐床上面,垂覆于两个背向坐狮之间的一具半月式敷设。精细者,其外缘以联珠纹为饰,简质者则光素无纹(图36~38)。
至于中土佛造像,自南北朝至隋唐,坐具中表现綩綖的例子,采用犍陀罗样式者,主要见于新疆地区,如克孜尔石窟原位于第206窟主室右壁的“为释迦族女说法图”(图39),第207窟“蛤闻法升天因缘图”(图40)①, 又巴楚县托库孜萨莱遗址出土的唐代石膏砖雕(图41)②。而中原地区则实例很少,所知有台湾震旦文教基金会藏北齐皇建二年(561年)比丘造佛七尊像碑(图42)③,此虽与印度石雕中的綩綖意趣相异,但与綩綖的垂覆之式大抵一致。然而在汉传佛教艺术中它终究没有形成流传之势。
如此以观前举故宫藏吐蕃时期铜坐像,所谓“圆莲座下承长方台座, 座中饰翻卷的台布”,或“莲座下是双狮垂帘式台座”,此“台布”与“垂帘”, 所表现的便是在印度传统图式中长久保持着的“綩綖”,而在边缘处作出皱褶以表现綩綖的质感。这是一种新的表现方式,以后便长久延续下来。 而同埃罗拉雕像近似者也与之并存,如同为故宫藏品的两尊吐蕃时期出自斯瓦特的铜造像坐具敷设,即图版说明称作“梯形台布”者(图43.44)④。
又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出自敦煌、时属中唐亦即吐蕃统治时期的几件擦擦,亦相似之例(图45~47 )①。
图式中尚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即莲花台下、獅子座侧成掎角之势的一对背向坐狮。獅子座本来源于印度,其造型的早期例子,可以举出马图拉博物馆藏石雕佛传故事“四天王奉体”②,又卡特拉出土贵霜时期的佛陀坐像(图48~50)③,座间狮子均为背向。前者时代约当在公元1世纪,后者约成于公元2世纪前半叶。更晚的例子不胜枚举。当然也不乏相向的一对坐狮之例,但毕竟以背向者为主流。相反,东传之后,坐具造型为两侧一对正面坐狮,或是相向蹲踞的一对狮子,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始终为主流。然而安西榆林窟第25窟东壁《八大菩萨曼荼罗经变》中卢舍那佛莲花下的獅子座,其构图却与印度的传统图式十分接近(图51)'此窟开凿于综上所述,现在可以提出这样一个意见,即吐蕃时期一种来自印度的佛造像样式,其基本构图与围绕尊像的情境安排:背屏式坐床,坐床前方两端各一对背向的坐狮。背屏装饰拏具,最简单的一种为背屏两端一对摩羯;繁复者,摩羯下方有立在大象身上的狮羊。尊像背倚丹枕,丹枕或有表现缝制痕迹的横向纹路,两端多有花朵式的束结。尊像上方的两边,通常有一对相向而舞的飞天。莲花台下的坐床上面、两个背向的坐獅之间,或垂覆“綩綖”。
大昭寺的两幅早期壁画遗存,尊像均是背屏式坐床,背倚丹枕,丹枕两端有束结,坐床下方壸门内各一对背向的坐獅,其中一幅背屏两端有一对摩羯。在坐床的细节安排上,此与吐蕃时期来自印度和尼泊尔的佛造像是一致的,只是拏具的表现形式尚比较简略。而在这之后的藏传佛教绘画中,这种样式的丹枕几乎不再出现,因此判断两幅壁画是否为吐蕃时期的作品,这是一个可以重点考虑的因素。
大昭寺的这两幅早期壁画遗存究竟是否可以归属于吐蕃时期,或者还可以有另外的分析角度。这里想从一两个细节人手。且看几个可作比较的例子,如《中国藏传佛教雕塑全集》著录故宫藏吐蕃时期出自东北印度工匠的金铜佛像,即释迦牟尼坐像一尊,观音菩萨坐像一尊(图18、19)气又 《图像与风格——故宫藏传佛教造像》著录同期来自尼泊尔的一尊铜镀金嵌宝石观音菩萨坐像(图20)®。关于前两例佛坐像的坐具,《中国藏传佛教雕塑全集》图版说明曰:莲花座后是方形宝座式靠背,雕出软靠垫,靠背左右两边雕刻立起的狮子, 狮子踏象,象卧莲花上。圆形火焰头光, 顶部饰圆伞盖、双飘带,莲花座上为长方底座,两角刻卧狮,这种豪华的宝座形背光,在印度后笈多时期的佛像中已出现。
观音坐像之说明曰:背靠装饰豪华图20铜镀金嵌宝石观音菩萨坐像故宫藏的宝座,雕出软靠垫,靠背两侧雕立狮、大象、莲花。……圆莲座下承长方台座,座中饰翻卷的台布,左右角两狮支撑。①讨论所欲关注的细节之一,便是坐具后面的所谓“软靠垫”,它正为大昭寺早期壁画和这里举出的金铜佛像所共有。而“软靠垫”的渊源本在印度,早期如出土于纳迦尔朱纳康达的石雕《惊悉出家》②(图21),又今藏法国吉美博物馆的石雕《难陀出家》③(图22),时代为公元3世纪的南印度伊克什瓦库王朝时期。之后的实例,有阿旃陀石窟第2、10、17窟中的雕像或壁画,时代约在公元5~6世纪(图23、24)④。稍晚的例子,可以举出埃罗拉石窟第12窟的佛雕像(图25、26),时代约在公元6~8世纪。
此所谓“软靠垫”,在佛经中名作丹枕或倚枕。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二 (释《大般涅槃经》卷一之“丹枕”)曰:“案天竺无木枕,皆以赤皮叠布为枕,贮以兜罗绵及毛,枕而且倚。丹,言其赤色也。”①又慧琳《音义》卷四“丹枕” 条(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三百九十八)曰:“天竺国风俗不用木石为枕,皆赤皮或赤色布作囊,贮以覩罗绵及以毛絮之类为枕,或用枕头,或作倚枕。丹,红赤色者用也。”又同书卷二十七:“丹枕,有释枕着仙丹可以延寿,此谓不然。案天竺无木枕,皆以赤皮叠布为枕,贮以覩罗绵及毛絮之类,枕而且倚。丹,赤色也,即同诸经朱色枕耳。头枕、倚枕,悉赤如丹。”又同书卷十三“倚枕”条(释《大宝积经》卷一百零九)曰:“案倚枕者,以锦绮缯彩作囊,盛耍物,贵人置之左右,或倚或凭,名为倚枕也。”又卷四十九 “倚枕”条(释《菩提资粮论》卷一)曰:“倚枕者,大枕也。锦绮缯彩作囊,盛轻耍物,置之左右前后,尊贵之人倚凭,名为倚枕。”叠布,即棉布;覩罗绵即木棉。所谓“耍物”“轻契物”,也当是棉花、毛絮之类。可知丹枕或倚枕, 原系印度上流社会日常生活中的习用之具。释典中的描述也是如此,如 《佛本行集经》卷十九:“呜呼我子!在于宫内,细滑床敷,柔软毡褥,或覆天衣,或复两边挟置倚枕。或卧或偃,随意自在。”前举纳迦尔朱纳康达石雕 《惊悉出家》,表现的便正是与此描写相合的宫廷生活。在阿旃陀石窟第 17窟“太子须大拏本生图”以及此窟的藻井装饰画中,都可以见到丹枕在生活中或背倚或侧凭的使用情景(图27、28 )。阿旃陀石窟第26窟涅槃石雕中的佛陀则是以丹枕枕首而卧(图29)。丹枕并且也用于印度教艺术, 如印度国家博物馆所藏一件公元5世纪的石雕湿婆像(图30、31)②。
丹枕用于佛教艺术,自然也有释典的依据如玄奘译《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九十八云:“妙香城内有诸士女,于其城中七宝台上,为法涌菩萨摩诃萨敷师子座”;“于其座上重敷裀褥,次铺绮粑,覆以白㲲,络以綩〓,宝座两边双设丹枕,垂诸帏带,散妙香花”气原是“贵人置之左右,或倚或凭”的倚枕亦即丹枕,移用于此,便又添一重尊礼之意。而丹枕之外, 这里提到的还有“綩〓”,此即本文涉及的另一个细节问题。
婉埏是汉译佛经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名词,但诸经对它的描述不尽一致。或曰以缯制成,如西晋竺法护译《佛说海龙王经》卷三中提到海龙王于大殿上化立师子之座,“敷无数百千天缯,以为綩〓”④。或曰锦绣金缕,饰以璎珞,如竺法护译《普曜经》卷一“瓔珞之饰床座婉绁”;《普曜经》卷八“吾子在宫时,茵蓐布綩綖,皆以锦绣成,柔软有光泽” ①;《长阿含经》卷三 “綩綖细软,金缕织成,布其座上”②。又曰以绮,唐地婆诃罗译《方广大庄严经》卷十二:“我子在家时,坐卧敷綩綖。皆以绮饰成,柔软而光泽。”③而隋吉藏《法华义疏》卷六云:“綩綖者,外国精绢也,名盘缩绣。富贵者重而敷之。”④可知统缍原是异域的高档织物,大略与中土绢、绮、缯等之精好者相仿佛,而以柔软光润精细华美为特色。诸经译者便只是从汉语中拣择接近经文原义的字词以释义,中土其实并无与它恰切对应之物。此所以慧琳 《一切经音义》释“綩綖”一词乃颇费踌躇,如《音义》卷十二释《大宝积经》 卷十二曰:“若依字义,与经甚乖,今并不取。经云綩綖者,乃珍妙华丽锦绣绵褥、概(音池)毡、花毯,舞筵之类也。字书并无此正字,借用也。”而唐窥基撰《妙法莲华经玄赞》则以为之译并不恰当:“重敷婉莛者,敷,陈设也,有作綩綖。统音,《字林》:一远反。《玉篇》:琬,纮也,纮冠也。今应作婉, 婉,美文章。綩綖者,席褥,应作莛字。《切韵》:綖者,冠上覆。《玉篇》:冠前后而垂者名綩綖。今取文缛、华毡之类,綩綖以为茵蓐,不知义何所从。故字应从婉莚”⑤。不过排比诸经之义,綩綖并不等同于茵褥。译经者取“缀”而不取“筵”,当是考虑其式与冕服之冠前后而垂的“纟延”约略相当,于是借用 “綩綖”在这里的垂覆之义。“琬”字则是借来以表其“文”,——或织文,或绣文' 然而慧琳所举绵褥、毡、毯,包括舞筵,其用途或者是铺展,或者是围护⑦,却皆非以轻薄柔软之状而成垂覆之式,窥基因此说“綩綖以为茵蓐, 不知义何所从”,且认为若是席褥,“字应从婉莛”。
今细绎经义,所谓“于其座上重敷裀褥,次铺绮粑,覆以白㲲,络以綩綖”,便是吉藏所云“重而敷之”“重敷蓐上”®,则綩綖当是蒙覆于坐具之表,即裀褥、绮粑、白㲲之外,更敷设綩綖而颇有装饰之用。译者特地用了一个“络”字,意在表明它的有垂穗如璎珞之类ᄆ而他经提到綩綖,也常常是茵褥、毡毯与之并举,且綩綖列在其末①,更每每强调它的“柔软”或“柔软细叠”,可据以想见其式。
按照这样的理解,在印度早期石雕中便可以找到綩綖的实例,如印度国家博物馆藏一件早期安达罗王朝石雕中坐具的敷设,石雕内容为宫廷生活(图32、33)②。綩綖在佛教艺术中的使用,前期主要见于古印度西北部犍陀罗艺术中的石雕,如白沙瓦博物馆藏佛传故事中的《占梦》(图 34)③拉合尔博物馆藏《三十三天说法》(图35 )④。后期则可以埃罗拉佛教石窟中的样式为例,即它是敷设于仰覆莲花之下的坐床上面,垂覆于两个背向坐狮之间的一具半月式敷设。精细者,其外缘以联珠纹为饰,简质者则光素无纹(图36~38)。
至于中土佛造像,自南北朝至隋唐,坐具中表现綩綖的例子,采用犍陀罗样式者,主要见于新疆地区,如克孜尔石窟原位于第206窟主室右壁的“为释迦族女说法图”(图39),第207窟“蛤闻法升天因缘图”(图40)①, 又巴楚县托库孜萨莱遗址出土的唐代石膏砖雕(图41)②。而中原地区则实例很少,所知有台湾震旦文教基金会藏北齐皇建二年(561年)比丘造佛七尊像碑(图42)③,此虽与印度石雕中的綩綖意趣相异,但与綩綖的垂覆之式大抵一致。然而在汉传佛教艺术中它终究没有形成流传之势。
如此以观前举故宫藏吐蕃时期铜坐像,所谓“圆莲座下承长方台座, 座中饰翻卷的台布”,或“莲座下是双狮垂帘式台座”,此“台布”与“垂帘”, 所表现的便是在印度传统图式中长久保持着的“綩綖”,而在边缘处作出皱褶以表现綩綖的质感。这是一种新的表现方式,以后便长久延续下来。 而同埃罗拉雕像近似者也与之并存,如同为故宫藏品的两尊吐蕃时期出自斯瓦特的铜造像坐具敷设,即图版说明称作“梯形台布”者(图43.44)④。
又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出自敦煌、时属中唐亦即吐蕃统治时期的几件擦擦,亦相似之例(图45~47 )①。
图式中尚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即莲花台下、獅子座侧成掎角之势的一对背向坐狮。獅子座本来源于印度,其造型的早期例子,可以举出马图拉博物馆藏石雕佛传故事“四天王奉体”②,又卡特拉出土贵霜时期的佛陀坐像(图48~50)③,座间狮子均为背向。前者时代约当在公元1世纪,后者约成于公元2世纪前半叶。更晚的例子不胜枚举。当然也不乏相向的一对坐狮之例,但毕竟以背向者为主流。相反,东传之后,坐具造型为两侧一对正面坐狮,或是相向蹲踞的一对狮子,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始终为主流。然而安西榆林窟第25窟东壁《八大菩萨曼荼罗经变》中卢舍那佛莲花下的獅子座,其构图却与印度的传统图式十分接近(图51)'此窟开凿于综上所述,现在可以提出这样一个意见,即吐蕃时期一种来自印度的佛造像样式,其基本构图与围绕尊像的情境安排:背屏式坐床,坐床前方两端各一对背向的坐狮。背屏装饰拏具,最简单的一种为背屏两端一对摩羯;繁复者,摩羯下方有立在大象身上的狮羊。尊像背倚丹枕,丹枕或有表现缝制痕迹的横向纹路,两端多有花朵式的束结。尊像上方的两边,通常有一对相向而舞的飞天。莲花台下的坐床上面、两个背向的坐獅之间,或垂覆“綩綖”。
大昭寺的两幅早期壁画遗存,尊像均是背屏式坐床,背倚丹枕,丹枕两端有束结,坐床下方壸门内各一对背向的坐獅,其中一幅背屏两端有一对摩羯。在坐床的细节安排上,此与吐蕃时期来自印度和尼泊尔的佛造像是一致的,只是拏具的表现形式尚比较简略。而在这之后的藏传佛教绘画中,这种样式的丹枕几乎不再出现,因此判断两幅壁画是否为吐蕃时期的作品,这是一个可以重点考虑的因素。
附注
①宿白在《西藏拉萨地区佛寺调查记》中云:“大昭寺与印度寺院关系密切,既可与藏文文献所记松赞干布妃泥婆罗尺尊公主创建大昭寺的传说相比较,又可和赤松德赞、 赤德松赞父子复兴佛教,遣使去印度迎请高僧和经典,建立僧伽,扩大大昭寺等一系列事迹相印证”; ”从8世纪后期赤松德赞亲政起,吐蕃迎来的印度高僧如寂护、莲花生以及曾与汉地大乘和尚诤辩并取得胜利的莲花戒等皆出身于自公元6、7世纪以来已成为北印度佛教中心之一的那烂陀寺”。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第7~10页, 文物出版社,1996年。
① 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第12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
② 张亚莎在《西藏美术史》中说:“此幅大日如来与众菩萨被认为是吐蕃时期少量遗存之一,画面已漫漶不清,正中主尊像的造像显示出早期印度波罗艺术之风,早期波罗艺术造型严谨,体态苗条,装饰性不强,显得比较朴素。”张亚莎《西藏美术史》第89 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不过张亚莎在《11世纪西藏的佛教艺术——从扎塘寺壁画研究出发》一书中,将其时代明确定为“大昭寺二期壁画”,即公元1080— Ш87年。张亚莎《 11世纪西藏的佛教艺术——从扎塘寺壁画研究出发》第212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
③ 甲央等《宝藏——中国西藏历史文物》图—〇四,朝华出版社,2000年。
① 谢继胜《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第205~206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② 两者均为黄铜。杨新等《中国藏传佛教雕塑全集》第2卷《金铜佛》(上)图11、15,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02年。
③ 故宫博物院《图像与风格——故宫藏传佛教造像》图100,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
① 两件作品也收入《图像与风格——故宫藏传佛教造像》中,图版说明曰:“莲座下是双狮垂帘式台座,双狮背向而踞。”故宫博物院《图像与风格——故宫藏传佛教造像》图 67、96,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垂帘”说又见罗文华《龙袍与袈裟:清宫藏传佛教文化考察》第288页,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
② 印度国家博物馆藏,本文照片为参观所摄。
③ 林保尧《佛像大观》第15页,艺术家出版社,1997年。
④ 阿旃陀石第2窟约开凿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不过窟内壁画为后绘。
① 同书卷六释《妙法莲华经》卷一之“丹枕”与此同。
② 照片为参观所摄(陈菊霞摄)。
③ 《大正藏》第6册,第220页。
④ 同③,第15册,第144页。
① 《大正藏》第3册,第488、535页。
② 同①第1册,第23页。
③ 同①第3册,第614页。
④ 同①第34册,第528页。
⑤ 《妙法莲华经玄赞》卷五《大正藏》第34册,第751页。
⑥ “_者,《埤苍》云:‘统者,衣绣裳也。’Щ者,席也。应作莛字。此綖字是天子覆冠曰綖。亦可通用。”湛然《止观辅行传弘决》卷七,(大正藏》第46册,第387页。
⑦ 如白居易《青毡帐二十韵》中“软煖围毡毯”,”平铺小舞筵”等。
⑧ “綩綖者,此间字书,未见其事。云是外国槃缩绣,大富家重敷蓐上也。”吉藏《法华统略》卷中,《续藏经》第27册,第479页。
① 如西晋于阗国三藏无罗叉译《放光般若经》卷十八中”譬如幻师持一镜,……于中示现若干种坐:氍氈、疑親、②……”《大正藏》第8册,第130页。
② 照片为参观时所摄,展品说明曰:Royal couple with attendants,Satavahana.③ 栗田功《ガンダ一ラ美術• П •佛陀の世界》图P1-IV,二玄社,1990年。
④ 栗田功(ガンダーラ美術.I •佛伝》(改订增补版)图414,二玄社,2003年。
① 时代为公元6-7世纪,今均藏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中国新疆壁画•龟兹》图80、120,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8年。关于龟兹石窟壁画中的坐具, 尚待更为细致的分析,本文暂不涉及。
② 喀什地区博物馆藏,本文照片为参观时所摄。
佛雕之美•北朝佛教石雕艺术》图45,(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1997年。其图版说明曰:‘‘主尊结跏趺坐于须弥座,座上覆盖华毯。”④杨新等《中国藏传佛教雕塑全集》第2卷《金铜佛》(上)图12、13,北京美术摄影出版,2002年。其图12图版说明曰:”双狮方座,前垂梯形台布,瓔珞镶边,上刻花纹。”① 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敦煌艺术品》(I )图28:1、2,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② 本文照片为参观所摄(孙毅华摄)。
③ 雕像铭文曰”菩萨”,但实为佛陀形象。王镱《印度美术》第13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本文照片为参观所摄。
④ 段文杰《敦煌石窟艺术•榆林窟第25窟、附第15窟》图8,江苏美术出版社,1993年。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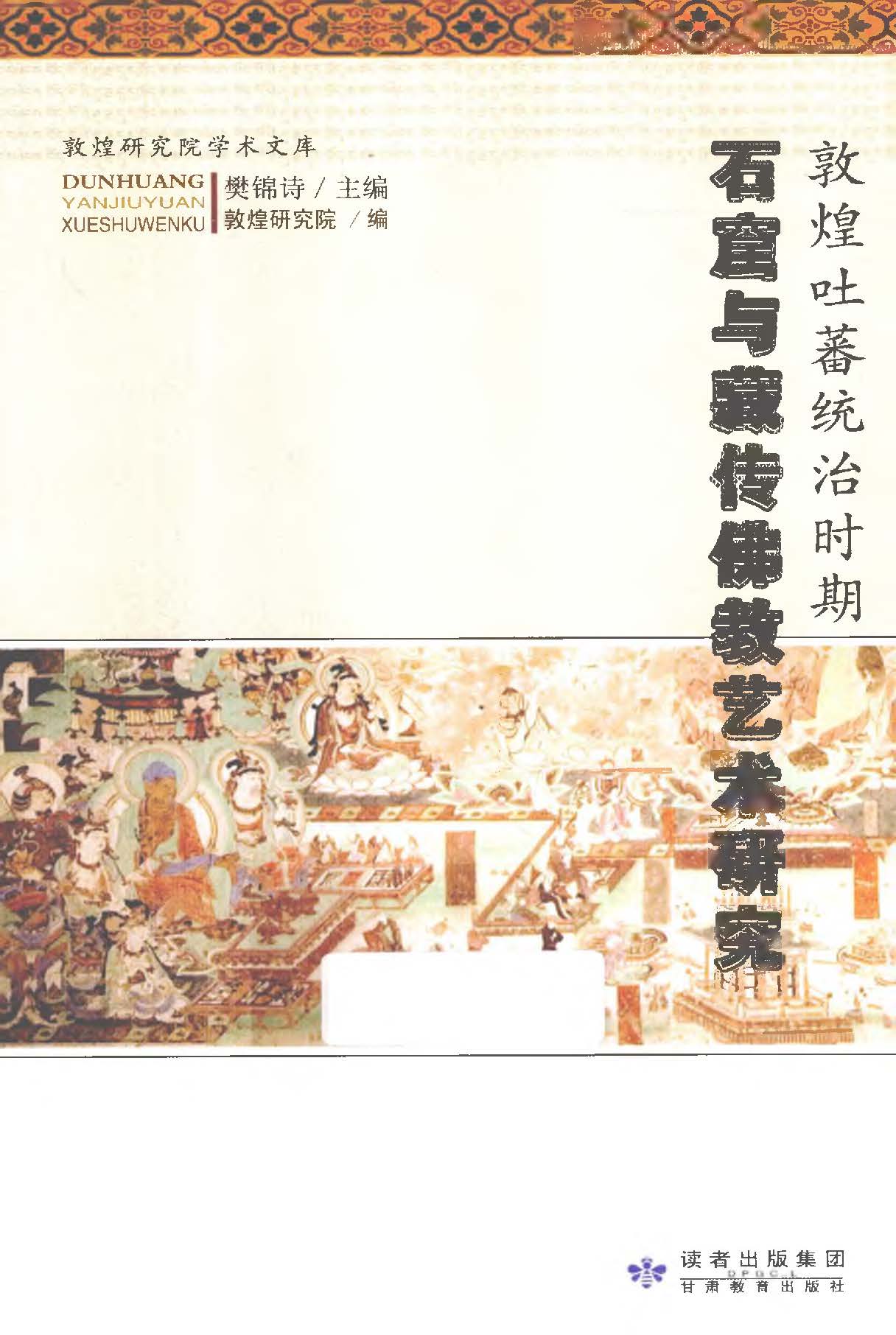
《敦煌吐蕃统治时期石窟与藏传佛教艺术研究》
出版者:甘肃教育出版社
出版地:2012.4
本书内容涉及对敦煌吐蕃石窟艺术样式的研究、社会政治背景探讨、造像思想研究、吐蕃密教文献研究、石窟经变画与图像专题研究、密教尊像研究、西藏考古与艺术研究、毗沙门天王像研究、莫高窟第465窟研究等多个领域。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