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榆林窟第25窟《弥勒经变》中的“农作图”不是寺院收获图
| 内容出处: | 《敦煌吐蕃统治时期石窟与藏传佛教艺术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290120020210003301 |
| 颗粒名称: | 1.榆林窟第25窟《弥勒经变》中的“农作图”不是寺院收获图 |
| 分类号: | K879.214-53 |
| 页数: | 7 |
| 页码: | 509-515 |
| 摘要: | 这里,先把金毓黻先生判断为“寺院收获图”的描述引录如下:本文要着重解释的是第一图。第一图分为四个部分:……(四)右上角画三人俱为男,其一人僧服趺坐于方毡之上,而前放一长方短足之案,案上置方盘二,圆形盂一,案前二人,常服巾冠,曲足而坐,似有所陈述,其傍尚绘有未割之谷,应为坐谈于谷地之上。以上四个部分未绘分界线,但不能解释为同时耕作。例如第四图即绘有分界线,可证此图是属于省略。 |
| 关键词: | 敦煌石窟 文集 喇嘛宗 宗教艺术 |
内容
这里,先把金毓黻先生判断为“寺院收获图”的描述引录如下:本文要着重解释的是第一图。第一图分为四个部分:……(四)右上角画三人俱为男,其一人僧服趺坐于方毡之上,而前放一长方短足之案,案上置方盘二,圆形盂一,案前二人,常服巾冠,曲足而坐,似有所陈述,其傍尚绘有未割之谷,应为坐谈于谷地之上。以上四个部分未绘分界线,但不能解释为同时耕作。例如第四图即绘有分界线,可证此图是属于省略。
总括第一图所显示的形象,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过程中一个时期的形象,应分为不劳而食的剥削者和自食其力而被剥削的劳动者两个方面。并由劳动者使用的生产工具的技巧,意识到生产力之不断地向前发展。图中已经清楚地表明,劳动者出其中血汗所经营的生产资料,都不属于自己,而是为封建地主组成部分之一的僧侣等所有,因此这一幅图绘,即会构成唐代寺院经济系统剥削者与劳动者两方面对立的鲜明形象。
……次说图中从剥削者和劳动者对此所显示的生产情况。
右上角部分趺坐之僧,很可能是代表寺院的庄园主或管庄者,其案前曲足而坐之二人,或者就是寺院系統中管庄奔走之人,以其不服僧服,知为依附寺院之受度而不必出家者。上文所举醴泉寺 “一届新年,寺之纲维,典产、直岁将寺中诸庄一年内之交易并诸物破用钱物向众僧申读”之例,亦可得到说明。此图如解释为,供管庄奔走之人于季节或秋收后向寺主或管庄汇报,亦应为事实所有。
但此二人既着世俗中服,亦可设想为地主阶级向寺主陈请,准其私度为僧,以遂其逃税避役之私图,其案上竹盘所盛之物, 并可释为寺主予受度者之度牒或袈裟。总之此一角落,系属于寺院庄园经济剥削者的一方面。其他三个部分,即属于被剥削的劳动者之另一方面。右下角部分为春耕、播种,左下角部分为秋收割谷,左上角部分为秋成打场。劳动者有男有女,即以表明他们为组成寺院庄园之寄托户;或者就是“非脱尘俗,畜妻养孥”之受度者;即使说他们是寺院蓄养的奴婢,亦未为不可。不用细说,他们的劳动果实,要以绝大部分贡献于寺主,而自己则过其最低级的生活。_我们必须把图中所显示的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看,才会看出这是唐代寺院经济中阶级矛盾的一种形象。①由于金毓黻先生对敦煌壁画、古代农业生产工具等方面的诸多问题不甚清楚,所以,论文中对所论及的敦煌壁画的时代、画面中出现的劳动工具的名称与用途等的考证大都存在问题。文章发表后,于豪亮先生曾专门写文章指出这些问题,敦煌文物研究所也给《考古》编辑部写了信,编辑部的(夏)作铭先生还为此加了编者按①。但是,作为这篇论文主要立论证据的所谓“寺院收获图”这个致命错误并没有人发现和提出过。
此后,这种观点沿用至今。例如,有学者说:榆林窟第25窟弥勒变中的“耕获图”与莫高窟第445窟不同,它不是地主庄园,而是一幅“寺院收获图”。在成堆的粮食面前,寺主之类的人物结跏坐在胡床上,下有“营田”之类的人物胡跪禀报收获情况。②还有学者认为:“耕获图”的右上角,一僧侣主坐蒲团上察看,前有两个戴软翅幞头的官人跪向主子禀报事情。这实是当时发展中“寺院经济”的缩写。③实际上,从金毓黻先生对画面的描述中已经明显出现了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致命伤。例如,他对僧人和下跪两人的描述,似应是室内环境,而后又说他们“其傍尚绘有未割之谷,应为坐谈于谷地之上”。主要的问题都出在对敦煌壁画的一些常识性问题的错误认识。在这里他错误地把壁画中的两枚小花(草)误解为“未割之谷”。实际上,这种穿插在画面中的小花(草),在僧人面前的案腿间、场上、扫场人、耕地人旁边等处都有, 这种小花(草)作为背景穿插在画面中起装饰、分割画面及其他方面的作用,不仅在榆林窟第25窟的这幅画面中有,而且在莫高窟第148、 445窟(盛唐),莫高窟第186、202、205窟(中唐),莫高窟第85、156 窟(晚唐),莫高窟第53窟(五代)中的10余幅《弥勒经变》中都有。同时,这种现象也出现在敦煌石窟的多种经变中。只不过花(草)的形状、大小、 数目有所不同。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在“农作图”的收割场面中,画有已经收割和没有收割的画面,这种画面与作为壁画背景的花(草)是完全不同的。就榆林窟第25 窟的这幅画面而言,这种小花(草)与持镰刀的农民所收割的“未割之谷”是完全不同的。
为了证明上坐僧人和下跪两人这个画面是“农作图”的一部分或有联系,金毓黻先生以莫高窟第61窟《弥勒经变》中的农作图(图3)作比较, 认为榆林窟第25窟的这幅只是省略了画面中的分界线。其实,这也是一种误解。据笔者对敦煌壁画中所有“农作图”的调查分析,壁画的创造者对类似“农作图”这种生活场景的设计非常灵活,穿插得很巧妙①。仅就《弥勒经变》中的“农作图”而言,有的用粗线条或其他形式把几个情节连起来组成一个整体。而大部分都不画分界标志。从画有分界标志的“农作图”来看,上坐僧人和下跪两人的这个画面正好被分割在“农作图”的分界标志之外。例如,榆林窟第 38窟(五代)西壁《弥勒经变》“农作图”的分界标志之外,绘一位高僧坐在床上,下面跪两人(图4)。
关于金毓黻先生 “次说图中从剥削者和劳动者对此所显示的生产情况”的论点, 由于其立论证据不存在,所以,观点自然很难成立。
下面以壁画事实为例进行辩解。首先,我们看看上坐僧人和下跪两人的这个画面是不是“农作图”的组成部分,在敦煌壁画中保存的80余幅 “农作图”中,只有莫高窟第445窟(盛唐)和榆林窟第25窟中的两幅被个别学者认为分别是地主庄园和寺院收获图(莫高窟第445窟笔者另文讨论)。
根据笔者的调查研究,类似的画面并非榆林窟第25窟《弥勒经变》中独有。由于莫高窟第148(盛唐),85(晚唐),53、61、72、454窟和榆林窟第 20,38窟(五代),榆林窟第25、55窟(北宋)的《弥勒经变》中保存了部分画面的榜题,通过这些榜题,对照相同的画面,我们可以搞清楚画面的内容。例如,莫高窟第148窟南壁“弥勒经变”中“农作图”的情节前面已经提到,画面榜题为“一种七收用ロロ □所获甚多”。此榜题出自后秦鸠摩罗什译《弥勒下生成佛经》中“一种七获,用功甚少,所获甚多”一句。相似的还有榆林窟第20窟“农作图”画面榜题尔时一种七获,用功甚少,所收甚多。尔时弥勒世,一种七收。”榆林窟第38窟“农作图”画面榜题为尔时弥勒世,一种七收。”而唐代义净译《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中写作“自然出香稻,美味皆充足。诸树生衣服,众彩共庄严。”莫高窟第61窟《弥勒经变》 中的“农作图”画面榜题为:“当遇慈悲尊,美味皆充足。勤苦极劳力,耕种不以工。”莫高窟第H8窟“树上生衣”画面榜题为诸树口衣服……”。莫高窟第72(五代)、55窟(北宋)的榜题都与义净译本相同。
莫高窟第148窟(盛唐)经变的左侧,绘一比丘坐椅子上,下面跪一人,双手捧物敬献,榜题不清,应是反映义净译本“或归佛法僧’恭敬常亲近,当修诸善行,来生我法中”之“供养佛法僧”。 近旁另一个画面为:比丘坐于榻上,身着俗服的两个男子跪拜,双手捧物敬献。其榜题为:“或于佛法中恭敬常亲近如是行恭敬来生我法中。”此榜题出自义净译本“或于佛法中,受持诸学处,善护无缺犯,来生我法中”,反映的是“持戒不犯”。在经变相对称的右侧,位于“农作图”左上方的是“老人人墓图”(榆林窟第25 窟“农作图”的下方是“老人入墓图”),在上方“供养佛塔”旁边绘一比丘坐于榻上,两个男子跪拜,双手捧物敬献,榜题“或于四方僧受持斋戒兼奉妙衣服”,此榜题出自义净译本“或于四方僧,施衣服饮食,并奉妙医药,来生我法中”,反映的是“供养四方僧”。近旁另一个画面为:一比丘坐于椅子上,下面二人双手捧物跪献, 榜题“恭十方僧卧具及至药受持八斋戒来生我法中”,此榜题出自义净译本“或于四方僧,施衣服饮食,并奉妙医药,来生我法中。或于四斋长,乃在神通月,受持八支戒,来生我法中”,反映的也是“供养四方僧”①。以上几个画面中下跪的人其衣帽与榆林窟第25窟下跪的两人完全相同。有学者认为:敦煌石窟中唐以后的《弥勒经变》基本依据义净译本绘制②此观点与画面情节及其榜题不符。在莫高窟第202窟(中唐),也有与莫高窟第148窟完全相同的画面(图5)。在莫高窟第186窟(中唐)的《弥勒经变》中,在“农作图” 旁,一比丘坐在上面,下面两人跪拜;在“老人人墓图”旁,一比丘坐在上面,下面两人跪拜。其衣帽与榆林窟第25窟跪拜的两人完全相同。在莫高窟第129窟(中唐),第85窟(晚唐)的《弥勒经变》中,左下角“农作图”上方一比丘端坐在椅子上,下面两人跪拜,另有一比丘坐在上面,下面三人跪拜,其中,一人持幢。在左侧中部“嫁娶图”旁边,也有相同的两个画面, 只不过下面跪拜的是两人,没有持幢之人。莫高窟第156窟(晚唐)《弥勒经变》的左边中间部分,一位比丘坐在上面,下面两人跪拜;另有一幅,下面三人跪拜。而该经变中的“农作图”与“嫁娶图”绘于经变的右边中下角部分。与左边的画面可以说是天壤一别。莫高窟第196窟《弥勒经变》中, “农作图”的上面是一座塔,在塔的上面左右两侧,各有一比丘坐在上面, 左侧下面两人跪拜;右侧下面一人跪拜。两幅比丘的服饰完全相同。还有多幅,不一一赘述。莫高窟第205窟(中唐)的“农作图”也画了分界标志, 在收割的粮捆、送饭的妇女的分界标志之外,跪着两位双手合十礼拜的妇女(图6)。
以上这几种类似的场面,虽然画面位置有所不同,但都是《弥勒经变》 中属于“供养佛塔”“供养四方僧”“供养佛法僧”“持戒不犯”等供养场面, 绝不是反映“一种七获”的内容。例如,与榆林窟第25窟“农作图”旁那位上坐的比丘完全相同的人物画面,在“农作图”的上方也有,不同的是,他是跪在方毯上,双手捧着袈裟,献给对面率领四众的弥勒佛。据经文记载, 这个场面是描绘弥勒佛于说法会后率领四众前往耆阇崛山,在山顶上见到大迦叶,接受迦叶佛献上的袈裟。而与下跪的俗人及其服饰完全相同的人物以一人出现在经变的多处。这种场面与“农作图”相差很远,其他洞窟的《弥勒经变》中也是如此。在此不一一赘述。
总括第一图所显示的形象,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过程中一个时期的形象,应分为不劳而食的剥削者和自食其力而被剥削的劳动者两个方面。并由劳动者使用的生产工具的技巧,意识到生产力之不断地向前发展。图中已经清楚地表明,劳动者出其中血汗所经营的生产资料,都不属于自己,而是为封建地主组成部分之一的僧侣等所有,因此这一幅图绘,即会构成唐代寺院经济系统剥削者与劳动者两方面对立的鲜明形象。
……次说图中从剥削者和劳动者对此所显示的生产情况。
右上角部分趺坐之僧,很可能是代表寺院的庄园主或管庄者,其案前曲足而坐之二人,或者就是寺院系統中管庄奔走之人,以其不服僧服,知为依附寺院之受度而不必出家者。上文所举醴泉寺 “一届新年,寺之纲维,典产、直岁将寺中诸庄一年内之交易并诸物破用钱物向众僧申读”之例,亦可得到说明。此图如解释为,供管庄奔走之人于季节或秋收后向寺主或管庄汇报,亦应为事实所有。
但此二人既着世俗中服,亦可设想为地主阶级向寺主陈请,准其私度为僧,以遂其逃税避役之私图,其案上竹盘所盛之物, 并可释为寺主予受度者之度牒或袈裟。总之此一角落,系属于寺院庄园经济剥削者的一方面。其他三个部分,即属于被剥削的劳动者之另一方面。右下角部分为春耕、播种,左下角部分为秋收割谷,左上角部分为秋成打场。劳动者有男有女,即以表明他们为组成寺院庄园之寄托户;或者就是“非脱尘俗,畜妻养孥”之受度者;即使说他们是寺院蓄养的奴婢,亦未为不可。不用细说,他们的劳动果实,要以绝大部分贡献于寺主,而自己则过其最低级的生活。_我们必须把图中所显示的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看,才会看出这是唐代寺院经济中阶级矛盾的一种形象。①由于金毓黻先生对敦煌壁画、古代农业生产工具等方面的诸多问题不甚清楚,所以,论文中对所论及的敦煌壁画的时代、画面中出现的劳动工具的名称与用途等的考证大都存在问题。文章发表后,于豪亮先生曾专门写文章指出这些问题,敦煌文物研究所也给《考古》编辑部写了信,编辑部的(夏)作铭先生还为此加了编者按①。但是,作为这篇论文主要立论证据的所谓“寺院收获图”这个致命错误并没有人发现和提出过。
此后,这种观点沿用至今。例如,有学者说:榆林窟第25窟弥勒变中的“耕获图”与莫高窟第445窟不同,它不是地主庄园,而是一幅“寺院收获图”。在成堆的粮食面前,寺主之类的人物结跏坐在胡床上,下有“营田”之类的人物胡跪禀报收获情况。②还有学者认为:“耕获图”的右上角,一僧侣主坐蒲团上察看,前有两个戴软翅幞头的官人跪向主子禀报事情。这实是当时发展中“寺院经济”的缩写。③实际上,从金毓黻先生对画面的描述中已经明显出现了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致命伤。例如,他对僧人和下跪两人的描述,似应是室内环境,而后又说他们“其傍尚绘有未割之谷,应为坐谈于谷地之上”。主要的问题都出在对敦煌壁画的一些常识性问题的错误认识。在这里他错误地把壁画中的两枚小花(草)误解为“未割之谷”。实际上,这种穿插在画面中的小花(草),在僧人面前的案腿间、场上、扫场人、耕地人旁边等处都有, 这种小花(草)作为背景穿插在画面中起装饰、分割画面及其他方面的作用,不仅在榆林窟第25窟的这幅画面中有,而且在莫高窟第148、 445窟(盛唐),莫高窟第186、202、205窟(中唐),莫高窟第85、156 窟(晚唐),莫高窟第53窟(五代)中的10余幅《弥勒经变》中都有。同时,这种现象也出现在敦煌石窟的多种经变中。只不过花(草)的形状、大小、 数目有所不同。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在“农作图”的收割场面中,画有已经收割和没有收割的画面,这种画面与作为壁画背景的花(草)是完全不同的。就榆林窟第25 窟的这幅画面而言,这种小花(草)与持镰刀的农民所收割的“未割之谷”是完全不同的。
为了证明上坐僧人和下跪两人这个画面是“农作图”的一部分或有联系,金毓黻先生以莫高窟第61窟《弥勒经变》中的农作图(图3)作比较, 认为榆林窟第25窟的这幅只是省略了画面中的分界线。其实,这也是一种误解。据笔者对敦煌壁画中所有“农作图”的调查分析,壁画的创造者对类似“农作图”这种生活场景的设计非常灵活,穿插得很巧妙①。仅就《弥勒经变》中的“农作图”而言,有的用粗线条或其他形式把几个情节连起来组成一个整体。而大部分都不画分界标志。从画有分界标志的“农作图”来看,上坐僧人和下跪两人的这个画面正好被分割在“农作图”的分界标志之外。例如,榆林窟第 38窟(五代)西壁《弥勒经变》“农作图”的分界标志之外,绘一位高僧坐在床上,下面跪两人(图4)。
关于金毓黻先生 “次说图中从剥削者和劳动者对此所显示的生产情况”的论点, 由于其立论证据不存在,所以,观点自然很难成立。
下面以壁画事实为例进行辩解。首先,我们看看上坐僧人和下跪两人的这个画面是不是“农作图”的组成部分,在敦煌壁画中保存的80余幅 “农作图”中,只有莫高窟第445窟(盛唐)和榆林窟第25窟中的两幅被个别学者认为分别是地主庄园和寺院收获图(莫高窟第445窟笔者另文讨论)。
根据笔者的调查研究,类似的画面并非榆林窟第25窟《弥勒经变》中独有。由于莫高窟第148(盛唐),85(晚唐),53、61、72、454窟和榆林窟第 20,38窟(五代),榆林窟第25、55窟(北宋)的《弥勒经变》中保存了部分画面的榜题,通过这些榜题,对照相同的画面,我们可以搞清楚画面的内容。例如,莫高窟第148窟南壁“弥勒经变”中“农作图”的情节前面已经提到,画面榜题为“一种七收用ロロ □所获甚多”。此榜题出自后秦鸠摩罗什译《弥勒下生成佛经》中“一种七获,用功甚少,所获甚多”一句。相似的还有榆林窟第20窟“农作图”画面榜题尔时一种七获,用功甚少,所收甚多。尔时弥勒世,一种七收。”榆林窟第38窟“农作图”画面榜题为尔时弥勒世,一种七收。”而唐代义净译《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中写作“自然出香稻,美味皆充足。诸树生衣服,众彩共庄严。”莫高窟第61窟《弥勒经变》 中的“农作图”画面榜题为:“当遇慈悲尊,美味皆充足。勤苦极劳力,耕种不以工。”莫高窟第H8窟“树上生衣”画面榜题为诸树口衣服……”。莫高窟第72(五代)、55窟(北宋)的榜题都与义净译本相同。
莫高窟第148窟(盛唐)经变的左侧,绘一比丘坐椅子上,下面跪一人,双手捧物敬献,榜题不清,应是反映义净译本“或归佛法僧’恭敬常亲近,当修诸善行,来生我法中”之“供养佛法僧”。 近旁另一个画面为:比丘坐于榻上,身着俗服的两个男子跪拜,双手捧物敬献。其榜题为:“或于佛法中恭敬常亲近如是行恭敬来生我法中。”此榜题出自义净译本“或于佛法中,受持诸学处,善护无缺犯,来生我法中”,反映的是“持戒不犯”。在经变相对称的右侧,位于“农作图”左上方的是“老人人墓图”(榆林窟第25 窟“农作图”的下方是“老人入墓图”),在上方“供养佛塔”旁边绘一比丘坐于榻上,两个男子跪拜,双手捧物敬献,榜题“或于四方僧受持斋戒兼奉妙衣服”,此榜题出自义净译本“或于四方僧,施衣服饮食,并奉妙医药,来生我法中”,反映的是“供养四方僧”。近旁另一个画面为:一比丘坐于椅子上,下面二人双手捧物跪献, 榜题“恭十方僧卧具及至药受持八斋戒来生我法中”,此榜题出自义净译本“或于四方僧,施衣服饮食,并奉妙医药,来生我法中。或于四斋长,乃在神通月,受持八支戒,来生我法中”,反映的也是“供养四方僧”①。以上几个画面中下跪的人其衣帽与榆林窟第25窟下跪的两人完全相同。有学者认为:敦煌石窟中唐以后的《弥勒经变》基本依据义净译本绘制②此观点与画面情节及其榜题不符。在莫高窟第202窟(中唐),也有与莫高窟第148窟完全相同的画面(图5)。在莫高窟第186窟(中唐)的《弥勒经变》中,在“农作图” 旁,一比丘坐在上面,下面两人跪拜;在“老人人墓图”旁,一比丘坐在上面,下面两人跪拜。其衣帽与榆林窟第25窟跪拜的两人完全相同。在莫高窟第129窟(中唐),第85窟(晚唐)的《弥勒经变》中,左下角“农作图”上方一比丘端坐在椅子上,下面两人跪拜,另有一比丘坐在上面,下面三人跪拜,其中,一人持幢。在左侧中部“嫁娶图”旁边,也有相同的两个画面, 只不过下面跪拜的是两人,没有持幢之人。莫高窟第156窟(晚唐)《弥勒经变》的左边中间部分,一位比丘坐在上面,下面两人跪拜;另有一幅,下面三人跪拜。而该经变中的“农作图”与“嫁娶图”绘于经变的右边中下角部分。与左边的画面可以说是天壤一别。莫高窟第196窟《弥勒经变》中, “农作图”的上面是一座塔,在塔的上面左右两侧,各有一比丘坐在上面, 左侧下面两人跪拜;右侧下面一人跪拜。两幅比丘的服饰完全相同。还有多幅,不一一赘述。莫高窟第205窟(中唐)的“农作图”也画了分界标志, 在收割的粮捆、送饭的妇女的分界标志之外,跪着两位双手合十礼拜的妇女(图6)。
以上这几种类似的场面,虽然画面位置有所不同,但都是《弥勒经变》 中属于“供养佛塔”“供养四方僧”“供养佛法僧”“持戒不犯”等供养场面, 绝不是反映“一种七获”的内容。例如,与榆林窟第25窟“农作图”旁那位上坐的比丘完全相同的人物画面,在“农作图”的上方也有,不同的是,他是跪在方毯上,双手捧着袈裟,献给对面率领四众的弥勒佛。据经文记载, 这个场面是描绘弥勒佛于说法会后率领四众前往耆阇崛山,在山顶上见到大迦叶,接受迦叶佛献上的袈裟。而与下跪的俗人及其服饰完全相同的人物以一人出现在经变的多处。这种场面与“农作图”相差很远,其他洞窟的《弥勒经变》中也是如此。在此不一一赘述。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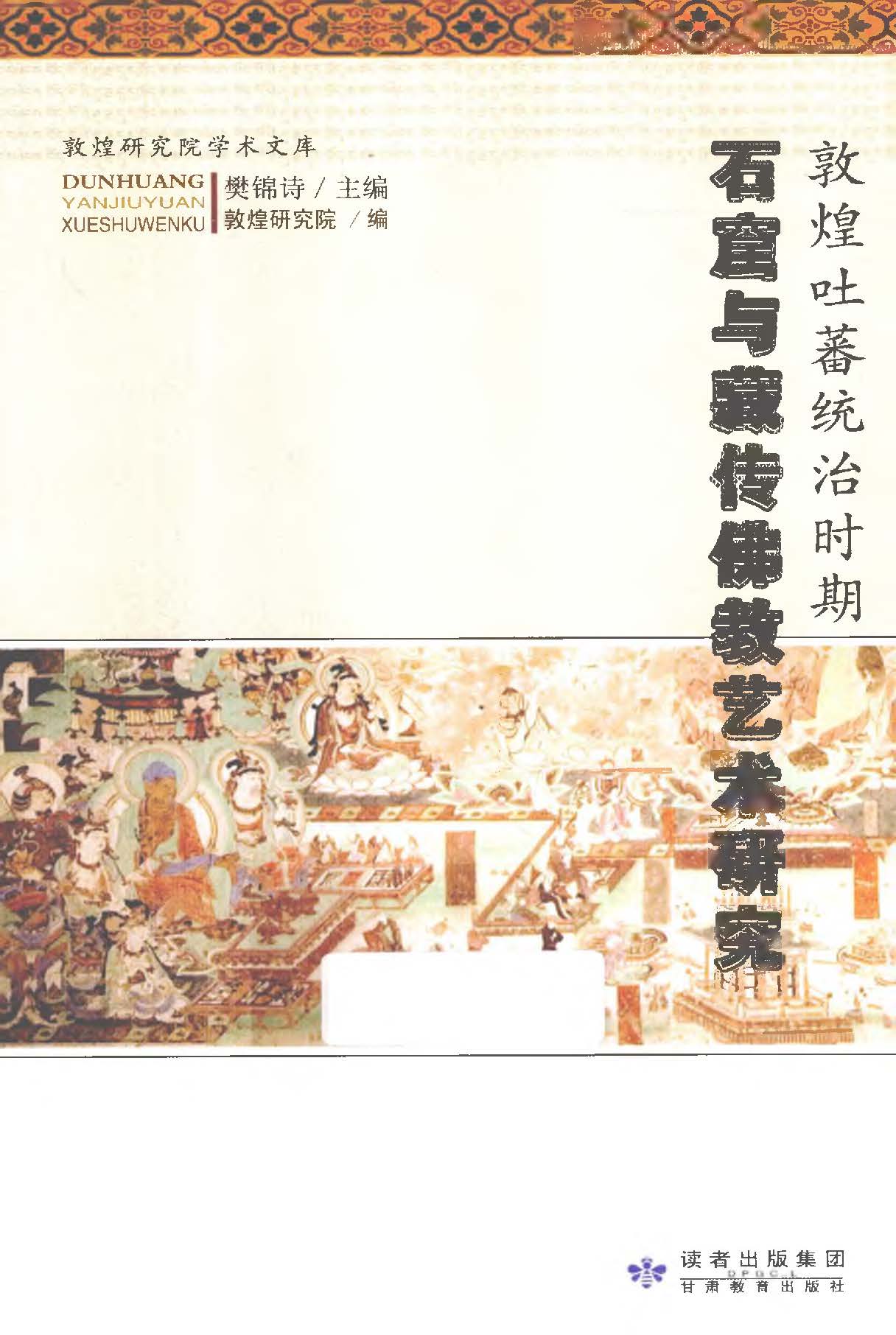
《敦煌吐蕃统治时期石窟与藏传佛教艺术研究》
出版者:甘肃教育出版社
出版地:2012.4
本书内容涉及对敦煌吐蕃石窟艺术样式的研究、社会政治背景探讨、造像思想研究、吐蕃密教文献研究、石窟经变画与图像专题研究、密教尊像研究、西藏考古与艺术研究、毗沙门天王像研究、莫高窟第465窟研究等多个领域。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