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吐蕃佛教的兴盛期
| 内容出处: | 《敦煌吐蕃统治时期石窟与藏传佛教艺术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290120020210003296 |
| 颗粒名称: | 四、吐蕃佛教的兴盛期 |
| 分类号: | K879.214-53 |
| 页数: | 4 |
| 页码: | 500-503 |
| 摘要: | 在吐蕃统治敦煌的半个多世纪里,敦煌几乎成了西域、中原、中亚一带佛教文化的交汇之地,同时也是佛教的一大圣地。而这一时期正是早期吐蕃佛教的兴盛期,我们从藏汉文史料中可以看到当时在敦煌活跃一时的汉僧都相继人藏,同时又有很多藏族的高僧们在敦煌从事译经等佛教活动。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敦煌对吐蕃文化的发展创新和融合曾起到了重大的历史作用了。而敦煌密宗艺术的大量兴起恰恰也就在这一时期。 被称为“大蕃国大德三藏法师”的著名僧人吴法成(藏文名“茄古布”),就曾翻译了相当数量的藏传密宗典籍,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有:《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经》《观世音菩萨秘密如意轮陀罗尼神咒经》《十一面神咒心经》。可见当时的敦煌已在流行这些藏传密宗经典,而大多数汉译的藏文密典也都是在藏王赞普的命令下翻译的。 |
| 关键词: | 敦煌石窟 文集 喇嘛宗 宗教艺术 |
内容
在吐蕃统治敦煌的半个多世纪里,敦煌几乎成了西域、中原、中亚一带佛教文化的交汇之地,同时也是佛教的一大圣地。而这一时期正是早期吐蕃佛教的兴盛期,我们从藏汉文史料中可以看到当时在敦煌活跃一时的汉僧都相继人藏,同时又有很多藏族的高僧们在敦煌从事译经等佛教活动。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敦煌对吐蕃文化的发展创新和融合曾起到了重大的历史作用了。而敦煌密宗艺术的大量兴起恰恰也就在这一时期。 被称为“大蕃国大德三藏法师”的著名僧人吴法成(藏文名“茄古布”),就曾翻译了相当数量的藏传密宗典籍,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有:《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经》《观世音菩萨秘密如意轮陀罗尼神咒经》《十一面神咒心经》。可见当时的敦煌已在流行这些藏传密宗经典,而大多数汉译的藏文密典也都是在藏王赞普的命令下翻译的。
从敦煌吐蕃统治时期的艺术发展来看,有以下几个方面特征。
其一,自公元8世纪左右起,敦煌壁画千手千眼观音等经变壁画的逐渐增多,都与藏传密教佛典的翻译、流行、普及等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曰本敦煌学者上山大峻在谈到敦煌密教画的出现时说:从归义军时代起,敦煌佛窟的壁画中,含有密教意味者曰渐增多,这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早在唐初时期(618—683年)所造的莫高窟第334窟石壁上,就有十一面观音像。稍后的盛唐时期(684—781年),出现了千手千眼观音图。张仪潮窟内龛顶上绘有千手观音像及其圆形光背,周围并配以曼陀罗构成的菩萨及明王等。莫高窟第130窟也就是这一时期所营造的。窟的内侧左右墙上绘有如意观音轮及不空绢索观音。随着时代的推移,这一类带有密教意味的題材渐渐增加。①这些史料都有力地证明了敦煌密宗壁画的出现与盛行和吐蕃佛教的直接关系。由于密教佛典的兴盛,敦煌壁画也随之出现了一些新的艺术表现形式,有些壁画在題材和技巧上受到了藏传佛教艺术的影响。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莫高窟第14窟北壁的“如意轮观音图”,第384窟南壁的“不空绢索观音图”等。这些壁画的构图布局都明显地流露出吐蕃艺术的美学风格。
如果我们将敦煌吐蕃统治时期的壁画与西藏大昭寺、桑耶寺、古格壁画以及早期唐卡画作一比较分析的话,就很容易找出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相似性。这种带有唐卡式的构图方式在唐末、西夏及元代的密宗壁画中都有一定的表现。以往的敦煌壁画研究,只强调了吐蕃壁画对汉画的吸收与继承,由于缺少比较研究,往往忽略了藏传佛教艺术在继承了敦煌石窟艺术的传统上,还给敦煌壁画艺术带来了密教绘画等新的艺术形式与绘画技法。
其二,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出现了新的经变画和屏式连环的佛教故事壁画。这一壁画形式的出现,大约也与吐蕃有一定的关联。敦煌学家段文杰先生在对敦煌的故事画和变经画作了前后期的比较之后,他认为中晚唐以后的变经故事画与吐蕃绘画有密切的关系:具体来说,唐代后期经变画的构图,基本上继承了前期的几种形式。吐蕃时期又出现了屏风画这一新形式。壁画下部的屏风画内,图绘故事,与上部的整铺经变紧密配合,这种布局一直延续到宋代。②从藏传佛教壁画的发展来看,以屏风故事画的形式绘制壁画,一直是藏传佛教寺院壁画的一大特色和传统。早期的布达拉宫、大昭寺、小昭寺以及赤松德赞时期的桑耶寺,特别是桑耶寺就以故事画的形式绘制了不少佛传故事和吐蕃史的演绎故事。因而吐蕃画师将这种壁画绘制方式与风格带人敦煌壁画是极有可能的。
其三,吐蕃占领敦煌初期,虽然吐蕃画师们继承了敦煌的壁画风格, 补画完成了“图素未就”的盛唐壁画,保留了盛唐壁画一壁一铺经变的传统格局。但是到了吐蕃统治中期,经变图的内容与形式都发生了新的变化。首先是出现了新的经变题材,其次是形式上,由盛唐的一壁一铺增加到一壁三四铺,大大增加了壁画的内容。例如,莫高窟第139窟有经变9 种,第231窟增加到20神。吐蕃统治时期敦煌流行的经变画题材主要有以下诸类:《观无量寿经变》26铺,《弥勒经变》20铺,《东方药师经变》20铺,《阿弥陀经变》17铺,《维摩诘经变》7铺,《法华经变》7铺,《涅槃经变》3铺, 《天请问经变》9铺,《金刚经变》7铺,《报恩经变6》補,《金刚明经变》4铺, 《华严经变》5铺,《楞伽经变》11铺,《思益梵天问经变》1铺。
这些新的经变画的出现,大大丰富了吐蕃统治中期的壁画内容,同时也使盛唐时期的经变画在艺术表现上有了创新。正如“张淮深碑”所言:四壁诸经变一十六铺,参罗万象,表化迹之多门;摄相归真,总三身而无异。方丈室内,化尽十方,一室之内,宛然三界。①在这些经变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维摩诘经变》了。此经变在吐蕃统治时期有很大的变化,除了在屏风画内增加了《弟子品》《方便品》等内容外, 颇有戏剧性的是维摩诘帐下的各国王子群臣像,刻意画成了吐蕃赞普礼佛图,这幅壁画生动地记录了吐蕃国王曾君临敦煌的历史事实。然而,有趣的是一旦张议潮收复河西后,吐蕃赞普的形象便也随之从壁画中消失。 这也说明,敦煌政权的更替对佛教艺术所产生的直接影响。
其四,吐蕃统治中期敦煌壁画中的供养人画像不断增多,导致了此时敦煌壁画供养人像大于佛像的世俗化倾向。从敦煌供养人像的演变看,吐蕃统治初期,供养人像极少,中期逐渐增多,出现了巨大的高僧像。诸如莫高窟第158窟门侧,有高近2米的僧人像4身。题记曰:“大蕃官内三学法师持钵僧宣。”又如莫高窟第359窟,供养人像绕窟一周,北壁是男像,头戴红髙冠,身着左祍袍,脚登乌靴,全着吐蕃装,旁边题记漫漶不清,不知是吐蕃人还是穿吐蕃装的汉人。南壁是女像,衫裙帔帛,全为汉装。莫高窟第225窟有吐蕃男装像,题名“王沙奴”,人物造型具有吐蕃特征。另莫高窟第220窟门道新发现的小龛西壁有供养人2身,男着吐蕃装,女着汉装。吐蕃时期僧人、供养人像的大量出现,段文杰先生认为可能与吐蕃僧侣参政、僧侶地位提髙有关。敦煌晩期的供养人像大大超过盛唐,世俗化的气息逐渐取代了早期的庄严、神圣感,一般都将供养人像绘在东壁的门上,面向正龛主尊佛像,遥相礼敬,以显示窟主的特殊身份。
随着经变画的大量增加,洞窟内部的整体布局及装饰图案尤显得重要,逐渐形成了以边饰组成窟内的框架结构,并以花边镶饰各铺经变,使其排列有序,丰富各异的莲花纹、菱形纹、石榴纹、云头纹以及生动活泼的孔雀、蹲狮、共命鸟、迦陵频伽等,编织了一幅幅佛国净土的庄严妙好,给人一种清淡、纯净、温馨的美感。在这里,菩萨和弟子、礼佛者和诸天神绕着佛像,而这些佛像及周围人物代表了佛教的一种理想佛国。因此,洞窟中的这些经变图使人们看到了超脱尘世的佛国净土。而当虔诚的人们走进洞窟时,我们似乎感到在那个火一般信仰的时代里,虔诚的僧人和艺术家们,不知疲倦地运用绚丽的线条、色彩,造型描绘着他们心中的佛国世界:如果你想到佛国,就必须纯洁自己的精神,随之,佛国也就纯洁了。
从敦煌吐蕃统治时期的艺术发展来看,有以下几个方面特征。
其一,自公元8世纪左右起,敦煌壁画千手千眼观音等经变壁画的逐渐增多,都与藏传密教佛典的翻译、流行、普及等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曰本敦煌学者上山大峻在谈到敦煌密教画的出现时说:从归义军时代起,敦煌佛窟的壁画中,含有密教意味者曰渐增多,这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早在唐初时期(618—683年)所造的莫高窟第334窟石壁上,就有十一面观音像。稍后的盛唐时期(684—781年),出现了千手千眼观音图。张仪潮窟内龛顶上绘有千手观音像及其圆形光背,周围并配以曼陀罗构成的菩萨及明王等。莫高窟第130窟也就是这一时期所营造的。窟的内侧左右墙上绘有如意观音轮及不空绢索观音。随着时代的推移,这一类带有密教意味的題材渐渐增加。①这些史料都有力地证明了敦煌密宗壁画的出现与盛行和吐蕃佛教的直接关系。由于密教佛典的兴盛,敦煌壁画也随之出现了一些新的艺术表现形式,有些壁画在題材和技巧上受到了藏传佛教艺术的影响。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莫高窟第14窟北壁的“如意轮观音图”,第384窟南壁的“不空绢索观音图”等。这些壁画的构图布局都明显地流露出吐蕃艺术的美学风格。
如果我们将敦煌吐蕃统治时期的壁画与西藏大昭寺、桑耶寺、古格壁画以及早期唐卡画作一比较分析的话,就很容易找出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相似性。这种带有唐卡式的构图方式在唐末、西夏及元代的密宗壁画中都有一定的表现。以往的敦煌壁画研究,只强调了吐蕃壁画对汉画的吸收与继承,由于缺少比较研究,往往忽略了藏传佛教艺术在继承了敦煌石窟艺术的传统上,还给敦煌壁画艺术带来了密教绘画等新的艺术形式与绘画技法。
其二,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出现了新的经变画和屏式连环的佛教故事壁画。这一壁画形式的出现,大约也与吐蕃有一定的关联。敦煌学家段文杰先生在对敦煌的故事画和变经画作了前后期的比较之后,他认为中晚唐以后的变经故事画与吐蕃绘画有密切的关系:具体来说,唐代后期经变画的构图,基本上继承了前期的几种形式。吐蕃时期又出现了屏风画这一新形式。壁画下部的屏风画内,图绘故事,与上部的整铺经变紧密配合,这种布局一直延续到宋代。②从藏传佛教壁画的发展来看,以屏风故事画的形式绘制壁画,一直是藏传佛教寺院壁画的一大特色和传统。早期的布达拉宫、大昭寺、小昭寺以及赤松德赞时期的桑耶寺,特别是桑耶寺就以故事画的形式绘制了不少佛传故事和吐蕃史的演绎故事。因而吐蕃画师将这种壁画绘制方式与风格带人敦煌壁画是极有可能的。
其三,吐蕃占领敦煌初期,虽然吐蕃画师们继承了敦煌的壁画风格, 补画完成了“图素未就”的盛唐壁画,保留了盛唐壁画一壁一铺经变的传统格局。但是到了吐蕃统治中期,经变图的内容与形式都发生了新的变化。首先是出现了新的经变题材,其次是形式上,由盛唐的一壁一铺增加到一壁三四铺,大大增加了壁画的内容。例如,莫高窟第139窟有经变9 种,第231窟增加到20神。吐蕃统治时期敦煌流行的经变画题材主要有以下诸类:《观无量寿经变》26铺,《弥勒经变》20铺,《东方药师经变》20铺,《阿弥陀经变》17铺,《维摩诘经变》7铺,《法华经变》7铺,《涅槃经变》3铺, 《天请问经变》9铺,《金刚经变》7铺,《报恩经变6》補,《金刚明经变》4铺, 《华严经变》5铺,《楞伽经变》11铺,《思益梵天问经变》1铺。
这些新的经变画的出现,大大丰富了吐蕃统治中期的壁画内容,同时也使盛唐时期的经变画在艺术表现上有了创新。正如“张淮深碑”所言:四壁诸经变一十六铺,参罗万象,表化迹之多门;摄相归真,总三身而无异。方丈室内,化尽十方,一室之内,宛然三界。①在这些经变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维摩诘经变》了。此经变在吐蕃统治时期有很大的变化,除了在屏风画内增加了《弟子品》《方便品》等内容外, 颇有戏剧性的是维摩诘帐下的各国王子群臣像,刻意画成了吐蕃赞普礼佛图,这幅壁画生动地记录了吐蕃国王曾君临敦煌的历史事实。然而,有趣的是一旦张议潮收复河西后,吐蕃赞普的形象便也随之从壁画中消失。 这也说明,敦煌政权的更替对佛教艺术所产生的直接影响。
其四,吐蕃统治中期敦煌壁画中的供养人画像不断增多,导致了此时敦煌壁画供养人像大于佛像的世俗化倾向。从敦煌供养人像的演变看,吐蕃统治初期,供养人像极少,中期逐渐增多,出现了巨大的高僧像。诸如莫高窟第158窟门侧,有高近2米的僧人像4身。题记曰:“大蕃官内三学法师持钵僧宣。”又如莫高窟第359窟,供养人像绕窟一周,北壁是男像,头戴红髙冠,身着左祍袍,脚登乌靴,全着吐蕃装,旁边题记漫漶不清,不知是吐蕃人还是穿吐蕃装的汉人。南壁是女像,衫裙帔帛,全为汉装。莫高窟第225窟有吐蕃男装像,题名“王沙奴”,人物造型具有吐蕃特征。另莫高窟第220窟门道新发现的小龛西壁有供养人2身,男着吐蕃装,女着汉装。吐蕃时期僧人、供养人像的大量出现,段文杰先生认为可能与吐蕃僧侣参政、僧侶地位提髙有关。敦煌晩期的供养人像大大超过盛唐,世俗化的气息逐渐取代了早期的庄严、神圣感,一般都将供养人像绘在东壁的门上,面向正龛主尊佛像,遥相礼敬,以显示窟主的特殊身份。
随着经变画的大量增加,洞窟内部的整体布局及装饰图案尤显得重要,逐渐形成了以边饰组成窟内的框架结构,并以花边镶饰各铺经变,使其排列有序,丰富各异的莲花纹、菱形纹、石榴纹、云头纹以及生动活泼的孔雀、蹲狮、共命鸟、迦陵频伽等,编织了一幅幅佛国净土的庄严妙好,给人一种清淡、纯净、温馨的美感。在这里,菩萨和弟子、礼佛者和诸天神绕着佛像,而这些佛像及周围人物代表了佛教的一种理想佛国。因此,洞窟中的这些经变图使人们看到了超脱尘世的佛国净土。而当虔诚的人们走进洞窟时,我们似乎感到在那个火一般信仰的时代里,虔诚的僧人和艺术家们,不知疲倦地运用绚丽的线条、色彩,造型描绘着他们心中的佛国世界:如果你想到佛国,就必须纯洁自己的精神,随之,佛国也就纯洁了。
附注
① 上山大峻《敦煌佛教的盛衰》,《丝路佛教》,华宇出版社,1985年。
② 段文杰《敦煌石窟艺术研究》第83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①段文杰《敦煌石窟艺术研究》第82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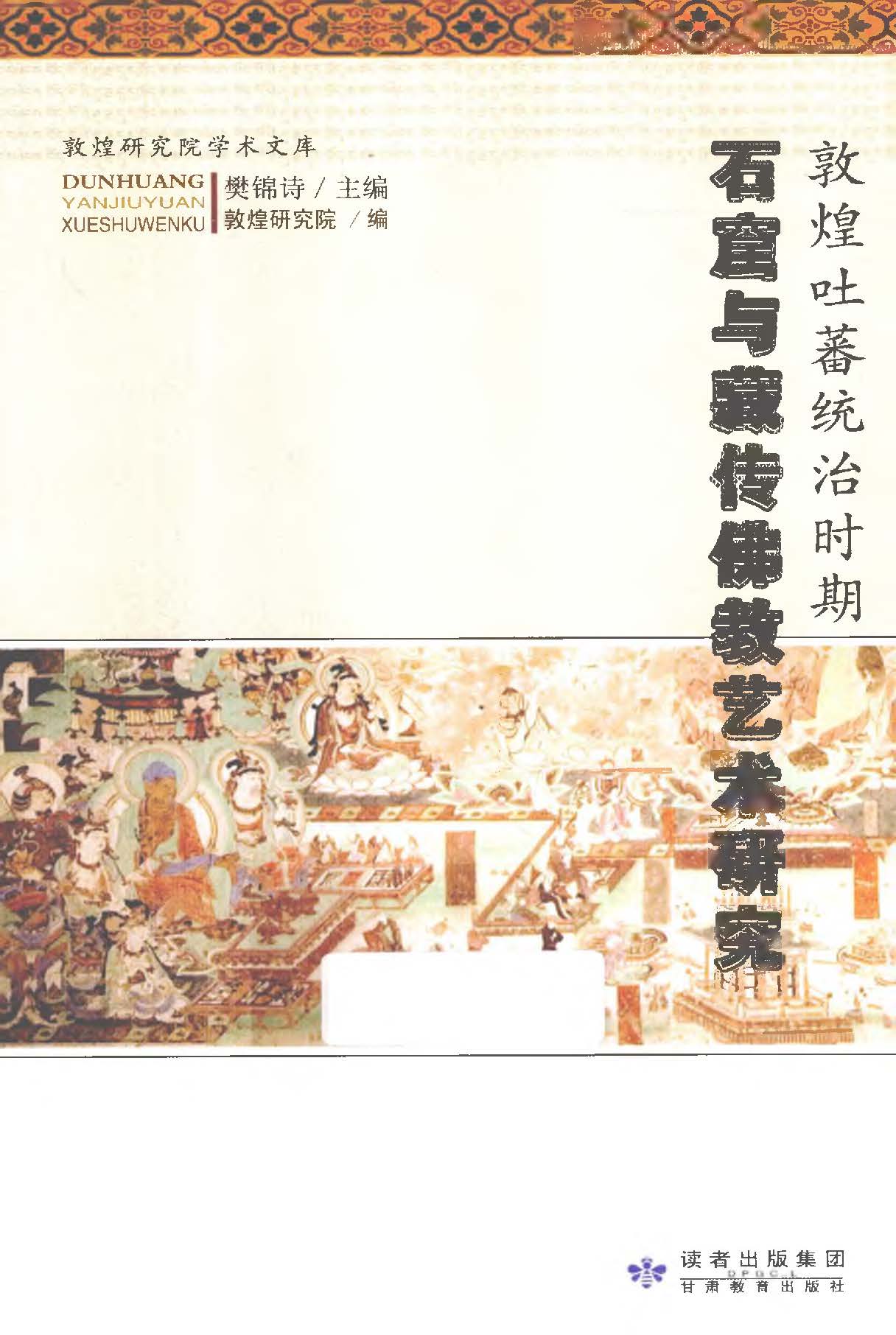
《敦煌吐蕃统治时期石窟与藏传佛教艺术研究》
出版者:甘肃教育出版社
出版地:2012.4
本书内容涉及对敦煌吐蕃石窟艺术样式的研究、社会政治背景探讨、造像思想研究、吐蕃密教文献研究、石窟经变画与图像专题研究、密教尊像研究、西藏考古与艺术研究、毗沙门天王像研究、莫高窟第465窟研究等多个领域。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