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吐蕃艺术家们对敦煌艺术所作的巨大贡献
| 内容出处: | 《敦煌吐蕃统治时期石窟与藏传佛教艺术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290120020210003295 |
| 颗粒名称: | 三、吐蕃艺术家们对敦煌艺术所作的巨大贡献 |
| 分类号: | K879.214-53 |
| 页数: | 4 |
| 页码: | 497-481 |
| 摘要: | 从《新唐书》《旧唐书》的吐蕃列传来看,吐蕃占领敦煌之前,虽有开元、天宝时期的一批洞窟,但是,“开凿有人,图素未就”,这类洞窟共有18 个。吐蕃占领敦煌之后,社会生活相对定安,这批洞窟的塑像和壁画才逐步完成。从有关史料来看,吐蕃统治时期开凿的洞窟,现存48个。若将未完成的18个洞窟算在一起,总数为66个石窟,其数量和规模都超过了盛唐时期ᄆ这是吐蕃艺术家们对敦煌艺术所作的巨大贡献。 |
| 关键词: | 敦煌石窟 文集 喇嘛宗 宗教艺术 |
内容
从《新唐书》《旧唐书》的吐蕃列传来看,吐蕃占领敦煌之前,虽有开元、天宝时期的一批洞窟,但是,“开凿有人,图素未就”,这类洞窟共有18 个。吐蕃占领敦煌之后,社会生活相对定安,这批洞窟的塑像和壁画才逐步完成。从有关史料来看,吐蕃统治时期开凿的洞窟,现存48个。若将未完成的18个洞窟算在一起,总数为66个石窟,其数量和规模都超过了盛唐时期ᄆ这是吐蕃艺术家们对敦煌艺术所作的巨大贡献。
更重要的是吐蕃佛教的介人,使敦煌艺术在内容与形式上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虽然这种变化并非根本性的变化,但却促使了敦煌艺术呈现出了吐蕃藏传佛教艺术的美学特征。前面我们曾经提到,随着吐蕃对敦煌及西域四镇的统治,藏传佛教艺术中的密宗绘画和造像大量增加。这使得敦煌艺术的题材得到了拓展,人物造型和绘画表现技法也变得更加丰富多样。在敦煌壁画宁静清迈、优美灵秀的审美气氛中,凸现出了密宗艺术特有的几分陸诞净狞、神秘恐惧的味道。显示出密宗与显宗在义理及艺术图像以及藏汉文化等审美心理方面所形成的民族文化差异性。
这一时期,所见的题材除药师佛、五方佛、观世音、大势至、地藏王等外,大部分壁画内容,人物多为不空绢索观音、如意轮观音、千手千眼观音、千手千钵文殊等密宗画艺术。在密宗造像中,还出现了藏传佛教艺术中常见的日月神像。
据敦煌研究院的调查统计,莫高窟现存的历代洞窟中,绘有《千手千眼观音经变》的洞窟多达37个,共绘40幅。最早的为盛唐,最晚的在元代。其中盛唐和中唐绘制不多,也不很流行。而晚唐以后流行千手观音,绘制的观音像也最多。从西夏至元代,敦煌一直盛行藏传密宗艺术,《千手千眼观音经变》的绘画题材大量增加,其观音菩萨像较之前表现得更为丰富和精美。
究其本源,我们以为这与吐蕃王朝信奉观音菩萨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知道,吐蕃人从接受佛教之日起,就尊信观音菩萨,藏王松赞干布被认为是观音菩萨的化身,而雪域藏地也被看成是观音菩萨教化藏人的道场。 藏族史书《王统世袭明鉴》的第五章“圣观世音菩萨发愿引领雪国众生证得解脱”中曾说:圣者观世音菩萨,为利益边地雪国众生有情,在无量光佛面前,产生大慈悲心,并发誓愿说我将引领三界六道的众生有情获得平安,尤其要引领雪国藏族众生走向安乐之道。……观世音菩萨为教化雪国众生,又示现许多化身,使所有众生都证得解脱。”①因而,在藏传佛教艺术中,观音菩萨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了解了吐蕃人的观音信仰,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敦煌壁画在中唐以后,藏传密教的《千手千眼观音经变》会逐步代替以前汉传显宗的《观音经变》,以及单一的持莲观音、杨柳观音、净瓶观音和施财观音等的原因了。
唐代晩期,密宗图像的大量出现,一改敦煌壁画前期的美学风格。这些密宗图像,造型极富于舞蹈性,特别是菩萨宝冠巍峨,璎珞绕身,舞蹈优美,神姿妙态中流溢出几分粗矿的妩媚。这种新的造型特点,显然与藏传佛教艺术是分不开的。
我们知道,藏传壁画艺术的特点之一,即是壁画人物极富于舞蹈性和音乐感。这大约是受到了古印度古典绘画美学思想以及《舞论》思想的影响,《舞论》首倡的“味”论被奉为印度美学的圭臬和一切艺术的通则,不仅适用于戏剧、舞蹈、音乐,而且也扩展到诗歌、绘画、雕刻等其他艺术形式。 在造型艺术领域,и味”与“情”经常被用于绘画、雕刻之中。
敦煌晩期出现的密宗图像,那种极富旋律性的舞蹈造型以及自然流溢出妖冶媚态,都无不含有印度美学所追求的“味”与“情”之境。在这里, 绘画之“味”是绘画的审美情感基调,绘画之“情”则是表现这种审美感情基调的具体造型手段。正如印度古代《峨湿奴往世书》的附录《毗湿奴最上法》中的《画经》所言:“绘画的知识没有《舞论》的帮助,是不可能得到的。①的确,欣赏敦煌壁画和藏传寺院壁画艺术,若缺少了舞蹈与音乐的联想及体悟,也是难以人境的。因为最美的壁画形象往往是那些仿佛戛然而止的凝固了的舞蹈造型。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壁画或多或少地都表现了这一艺术造型上的美学追求。
关于敦煌晚唐的密宗造像,我国著名的敦煌学家段文杰先生曾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他说:唐朝后期,密宗图像大量出现,初唐曾出现数幅十一面观音像,后又曾以绘塑结合的方式出现于盛唐末大历十一年(776 年)前后的莫高窟第148窟。吐蕃时期逐渐增多,张议潮统一河西之后,蔚为大观,莫高窟第161、54、14等窟绘满了唐密图像。 莫高窟第161窟的观音像,姿态妩媚,构图自由,别具一格。莫高窟第14窟排列着成铺的千手千眼观音、千手千钵文殊、如意轮观音、金刚杵观音、十一面观音等〇这些尊像都有随从眷属,上部画飞天,四角画天王及菩萨,下部有婆薮仙、功德天及忿怒明王。
观音菩萨结跏趺坐在莲座上,十一面,有慈悲相,有忿怒相。每面各于身上生四十手,每手掌中有一慈眼,手中持轮、宝、杵、斧、索、刀、剑等诸法器。莲座下为须弥山,山上悬日月,山腰下有双龙,山下碧波荡漾。画面上的各种人物神态不同,别有一种神秘境界。②虽然吐蕃统治时期的壁画充满了密宗艺术的神秘气息,但与西藏本土的密教壁画相比较,它显然少了净狞怪诞、恐怖阴森的过分张扬与表现,虽具神秘的威慑感觉,但仍表现得明快、富于理性的把握,它似乎将青藏高原原始的生命冲动有机地调和在敦煌这样一个多民族文化相融、交汇的地方,表现得宽容而又谦虚。这也如克林凯特所言:从西藏传来的密教“金刚乘”的影响,也表现在晩期艺术中。 那里面的密教神,都拿着杀人武器,如斧子和绳索,然而他们的形象并不完全像在西藏那样凶恶。
显然,克林凯特对藏传密宗艺术的看法颇有偏差,那武器并非是专门杀人的凶器,而是佛教的护法之器,是摄受和斩灭我们众生内心三毒的利器。除此之外,他对密宗艺术的风格认识和把握仍有一定的见地。显而易见,远离本土的藏传佛教艺术必定会发生新的变化,尤其是在敦煌这样一个宗教艺术的圣地也必定会吸收新的艺术成分。
的确,吐蕃统治敦煌之后,“敦煌的社会行政及文化方面都产生了种种变化,敦煌的佛教也出现了种种特色。不过,吐蕃虽然统治了敦煌多年, 照一般的情形看,并没有压迫汉人教徒或意图消灭汉传佛教的迹象,相反的,甚至有助长汉文化并加以保护的做法,其中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吐蕃原本就是个崇仰佛教的国家”日本学者上山大峻的这一观点,基本上客观反映了吐蕃统治敦煌时的政治态度与文化心理。从敦煌出土的佛教文献和吐蕃统治时期的壁画来分析,藏文《大藏经》中的不少佛典都是经由敦煌传至西藏的。
更重要的是吐蕃佛教的介人,使敦煌艺术在内容与形式上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虽然这种变化并非根本性的变化,但却促使了敦煌艺术呈现出了吐蕃藏传佛教艺术的美学特征。前面我们曾经提到,随着吐蕃对敦煌及西域四镇的统治,藏传佛教艺术中的密宗绘画和造像大量增加。这使得敦煌艺术的题材得到了拓展,人物造型和绘画表现技法也变得更加丰富多样。在敦煌壁画宁静清迈、优美灵秀的审美气氛中,凸现出了密宗艺术特有的几分陸诞净狞、神秘恐惧的味道。显示出密宗与显宗在义理及艺术图像以及藏汉文化等审美心理方面所形成的民族文化差异性。
这一时期,所见的题材除药师佛、五方佛、观世音、大势至、地藏王等外,大部分壁画内容,人物多为不空绢索观音、如意轮观音、千手千眼观音、千手千钵文殊等密宗画艺术。在密宗造像中,还出现了藏传佛教艺术中常见的日月神像。
据敦煌研究院的调查统计,莫高窟现存的历代洞窟中,绘有《千手千眼观音经变》的洞窟多达37个,共绘40幅。最早的为盛唐,最晚的在元代。其中盛唐和中唐绘制不多,也不很流行。而晚唐以后流行千手观音,绘制的观音像也最多。从西夏至元代,敦煌一直盛行藏传密宗艺术,《千手千眼观音经变》的绘画题材大量增加,其观音菩萨像较之前表现得更为丰富和精美。
究其本源,我们以为这与吐蕃王朝信奉观音菩萨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知道,吐蕃人从接受佛教之日起,就尊信观音菩萨,藏王松赞干布被认为是观音菩萨的化身,而雪域藏地也被看成是观音菩萨教化藏人的道场。 藏族史书《王统世袭明鉴》的第五章“圣观世音菩萨发愿引领雪国众生证得解脱”中曾说:圣者观世音菩萨,为利益边地雪国众生有情,在无量光佛面前,产生大慈悲心,并发誓愿说我将引领三界六道的众生有情获得平安,尤其要引领雪国藏族众生走向安乐之道。……观世音菩萨为教化雪国众生,又示现许多化身,使所有众生都证得解脱。”①因而,在藏传佛教艺术中,观音菩萨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了解了吐蕃人的观音信仰,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敦煌壁画在中唐以后,藏传密教的《千手千眼观音经变》会逐步代替以前汉传显宗的《观音经变》,以及单一的持莲观音、杨柳观音、净瓶观音和施财观音等的原因了。
唐代晩期,密宗图像的大量出现,一改敦煌壁画前期的美学风格。这些密宗图像,造型极富于舞蹈性,特别是菩萨宝冠巍峨,璎珞绕身,舞蹈优美,神姿妙态中流溢出几分粗矿的妩媚。这种新的造型特点,显然与藏传佛教艺术是分不开的。
我们知道,藏传壁画艺术的特点之一,即是壁画人物极富于舞蹈性和音乐感。这大约是受到了古印度古典绘画美学思想以及《舞论》思想的影响,《舞论》首倡的“味”论被奉为印度美学的圭臬和一切艺术的通则,不仅适用于戏剧、舞蹈、音乐,而且也扩展到诗歌、绘画、雕刻等其他艺术形式。 在造型艺术领域,и味”与“情”经常被用于绘画、雕刻之中。
敦煌晩期出现的密宗图像,那种极富旋律性的舞蹈造型以及自然流溢出妖冶媚态,都无不含有印度美学所追求的“味”与“情”之境。在这里, 绘画之“味”是绘画的审美情感基调,绘画之“情”则是表现这种审美感情基调的具体造型手段。正如印度古代《峨湿奴往世书》的附录《毗湿奴最上法》中的《画经》所言:“绘画的知识没有《舞论》的帮助,是不可能得到的。①的确,欣赏敦煌壁画和藏传寺院壁画艺术,若缺少了舞蹈与音乐的联想及体悟,也是难以人境的。因为最美的壁画形象往往是那些仿佛戛然而止的凝固了的舞蹈造型。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壁画或多或少地都表现了这一艺术造型上的美学追求。
关于敦煌晚唐的密宗造像,我国著名的敦煌学家段文杰先生曾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他说:唐朝后期,密宗图像大量出现,初唐曾出现数幅十一面观音像,后又曾以绘塑结合的方式出现于盛唐末大历十一年(776 年)前后的莫高窟第148窟。吐蕃时期逐渐增多,张议潮统一河西之后,蔚为大观,莫高窟第161、54、14等窟绘满了唐密图像。 莫高窟第161窟的观音像,姿态妩媚,构图自由,别具一格。莫高窟第14窟排列着成铺的千手千眼观音、千手千钵文殊、如意轮观音、金刚杵观音、十一面观音等〇这些尊像都有随从眷属,上部画飞天,四角画天王及菩萨,下部有婆薮仙、功德天及忿怒明王。
观音菩萨结跏趺坐在莲座上,十一面,有慈悲相,有忿怒相。每面各于身上生四十手,每手掌中有一慈眼,手中持轮、宝、杵、斧、索、刀、剑等诸法器。莲座下为须弥山,山上悬日月,山腰下有双龙,山下碧波荡漾。画面上的各种人物神态不同,别有一种神秘境界。②虽然吐蕃统治时期的壁画充满了密宗艺术的神秘气息,但与西藏本土的密教壁画相比较,它显然少了净狞怪诞、恐怖阴森的过分张扬与表现,虽具神秘的威慑感觉,但仍表现得明快、富于理性的把握,它似乎将青藏高原原始的生命冲动有机地调和在敦煌这样一个多民族文化相融、交汇的地方,表现得宽容而又谦虚。这也如克林凯特所言:从西藏传来的密教“金刚乘”的影响,也表现在晩期艺术中。 那里面的密教神,都拿着杀人武器,如斧子和绳索,然而他们的形象并不完全像在西藏那样凶恶。
显然,克林凯特对藏传密宗艺术的看法颇有偏差,那武器并非是专门杀人的凶器,而是佛教的护法之器,是摄受和斩灭我们众生内心三毒的利器。除此之外,他对密宗艺术的风格认识和把握仍有一定的见地。显而易见,远离本土的藏传佛教艺术必定会发生新的变化,尤其是在敦煌这样一个宗教艺术的圣地也必定会吸收新的艺术成分。
的确,吐蕃统治敦煌之后,“敦煌的社会行政及文化方面都产生了种种变化,敦煌的佛教也出现了种种特色。不过,吐蕃虽然统治了敦煌多年, 照一般的情形看,并没有压迫汉人教徒或意图消灭汉传佛教的迹象,相反的,甚至有助长汉文化并加以保护的做法,其中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吐蕃原本就是个崇仰佛教的国家”日本学者上山大峻的这一观点,基本上客观反映了吐蕃统治敦煌时的政治态度与文化心理。从敦煌出土的佛教文献和吐蕃统治时期的壁画来分析,藏文《大藏经》中的不少佛典都是经由敦煌传至西藏的。
附注
①索南坚赞著,陈庆英译《王统世袭明鉴》第47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① 婆罗多著,金克木译《舞论 》,《文艺理论译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57年。
② 段文杰《敦煌石窟艺术研究》第93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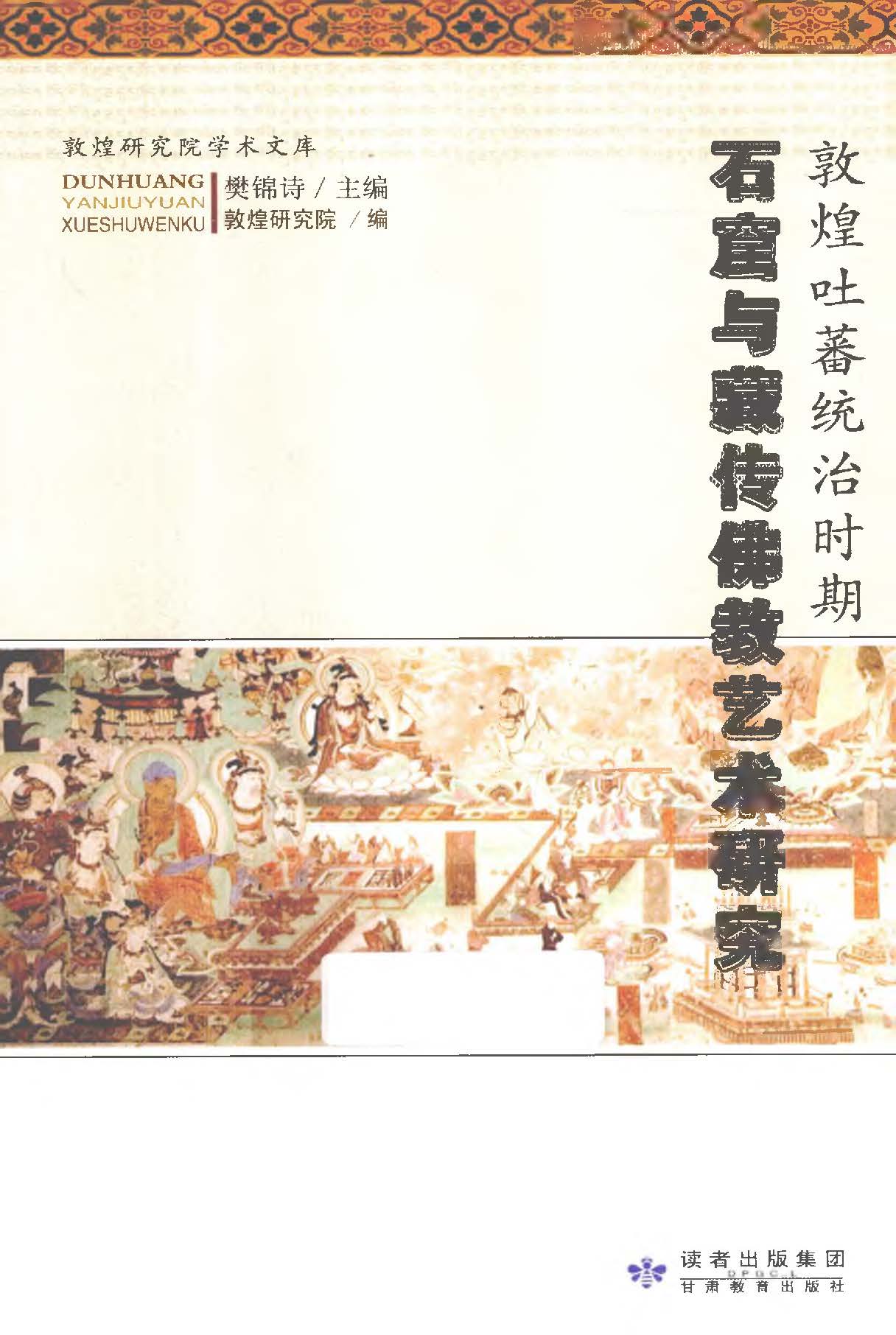
《敦煌吐蕃统治时期石窟与藏传佛教艺术研究》
出版者:甘肃教育出版社
出版地:2012.4
本书内容涉及对敦煌吐蕃石窟艺术样式的研究、社会政治背景探讨、造像思想研究、吐蕃密教文献研究、石窟经变画与图像专题研究、密教尊像研究、西藏考古与艺术研究、毗沙门天王像研究、莫高窟第465窟研究等多个领域。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