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敦煌石窟供养人题记介绍
| 内容出处: | 《敦煌吐蕃统治时期石窟与藏传佛教艺术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290120020210003294 |
| 颗粒名称: | 二、敦煌石窟供养人题记介绍 |
| 分类号: | K879.214-53 |
| 页数: | 6 |
| 页码: | 492-497 |
| 摘要: | 从《敦煌石窟供养人题记》来看,“敦煌的中唐,或者更切合实际地称 -为吐蕃占有时期,共计六十七年”,在这近70年的历史中,吐蕃人修缮完成了不少因战争而中断修建与绘画的石窟和壁画。据敦煌石窟题记提供的史料表明,现存的莫髙窟第220、365、158、231、180、185、148等窟都是吐蕃统治时期补绘完成的石窟。与此同时,吐蕃统治者还开凿了新的洞窟,壁画的内容题材得到了极大的丰富,藏传佛教生活在壁画艺术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反映。正如敦煌出土石室本《大蕃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修功德碑》题记所言:当犹莫高山为今至圣主及七代凿窟龛一所,永垂不朽,用记将来……龛内塑释迦牟尼像,并声闻、菩萨、神王等七躯。帐门两面,画文殊、贤普菩萨,并侍从。南壁画西天净土、法华、天请问、 报恩变各一铺,北墙乐师、净土、华严、弥勒、维摩变各一铺,门外护法善神。①本世纪初,伯希和与斯坦因盗取的敦煌吐蕃文书中也记载了吐蕃赞普大兴佛法、译经造像的经过。如以下几段:丑年,寅年赞普新加福田,转大般若经分付诸寺维那历。 |
| 关键词: | 敦煌石窟 文集 喇嘛宗 宗教艺术 |
内容
从《敦煌石窟供养人题记》来看,“敦煌的中唐,或者更切合实际地称 -为吐蕃占有时期,共计六十七年”,在这近70年的历史中,吐蕃人修缮完成了不少因战争而中断修建与绘画的石窟和壁画。据敦煌石窟题记提供的史料表明,现存的莫髙窟第220、365、158、231、180、185、148等窟都是吐蕃统治时期补绘完成的石窟。与此同时,吐蕃统治者还开凿了新的洞窟,壁画的内容题材得到了极大的丰富,藏传佛教生活在壁画艺术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反映。正如敦煌出土石室本《大蕃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修功德碑》题记所言:当犹莫高山为今至圣主及七代凿窟龛一所,永垂不朽,用记将来……龛内塑释迦牟尼像,并声闻、菩萨、神王等七躯。帐门两面,画文殊、贤普菩萨,并侍从。南壁画西天净土、法华、天请问、 报恩变各一铺,北墙乐师、净土、华严、弥勒、维摩变各一铺,门外护法善神。①本世纪初,伯希和与斯坦因盗取的敦煌吐蕃文书中也记载了吐蕃赞普大兴佛法、译经造像的经过。如以下几段:丑年,寅年赞普新加福田,转大般若经分付诸寺维那历。
(P.3336)吐蕃宰相尚伦藏嘘律钵有病设斋文。(P.2974、P.3395)《大乘经纂要义》一卷,题记;“任寅年之月”,大吐蕃国赞普印信,并此十善经本“流传诸州,流行读育,后八月十六日写毕记”。(S.3699)又如,Stein painting32的藏文题记,为我们记录下了吐蕃画师创作佛画的一些重要内容:龙卓、我、僧人白央为身体健康和作回向功德(利益所有众生)而创作下列组画,药师佛、普贤菩萨、妙吉祥王子、千手千目艮观世音菩萨、如意轮转王、回向转轮王等佛像。
又莫高窟第225窟东壁千佛像下南、北侧着吐蕃装男、女供养人像题记:“佛弟子王沙奴敬画千佛六百一十躯一心供养”,“女弟子优婆姨郭氏为亡男画千佛六百一十躯一心供养”。
从这些题记中,我们不难看出吐蕃在统治敦煌时期对敦煌佛教艺术发展所做的贡献。
观音菩萨像一直是藏传佛教艺术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敦煌吐蕃统治时期的壁画中也保留了不同风格的观音菩萨画像,这些绘画作品从艺术手法上吸收了汉画的传统技法,但是在人物肖像,画面的构图、着色上明显带有藏传艺术的特色,有些作品还有尼泊尔、印度、克什米尔佛画的影子。例如,莫髙窟第463窟中窟顶南披所绘的南方宝生佛,佛座前的供养菩萨像,神态端庄,秀美怡然,侧身趺坐,头戴宝冠,顶饰环佩,斜披璎珞,裸身短裙,手执芙蕖,凝视莲花,神情虔静,是一幅难得的艺术作品。在同一石窟的窟顶东方药师佛座前,还绘有手执凤箜篌,双眉下视。沉浸于天国佛曲的供养菩萨像,娟秀文静,裸体短裙、璎珞环佩,侧身于莲花座之上。双耳饰圆形大耳环,头戴高髻花冠,菩萨手掌和足心都着朱红色,这是藏传壁画绘制佛母、度母等像时惯用的绘画手法。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幅供养菩萨的高髻花冠在敦煌壁画中极为少见,但是我们却能在遥远的古格早期壁画中找到同一风格的花冠装饰。这种花冠装饰,在我们看来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克什米尔和中亚佛教艺术的影响。
在莫高窟第405窟四壁中部绘有一幅藏传密宗壁画,此窟是以供奉大日如来为主尊的罗刹神堂,除塑像外窟顶绘大日如来、四方佛,四壁绘曼陀罗11铺。东壁门上为五金刚,左右壁画绘制大威德等,其他三壁分别绘梵天、罗刹王、大黑天、龙王等。主尊像被安排在曼荼罗的中心,莲花座之上,四周是形态不一的双身和単身修行像,从构图看很接近唐卡的构图形态,但却无传统唐卡严谨有余、生动灵秀不足的艺术感觉。
表现佛陀涅槃的题材一直是佛教艺术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我们从莫高窟第158窟的壁画中,可以欣赏到吐蕃赞普在侍从的陪伴下率领众大臣、贵妇悼念佛陀大涅槃时的生动情景。赞普身后绕着背光,侍从和大臣们都着吐蕃装,人物形象明显表现出少数民族的气质特征。佛陀示寂后的寂静与超然,与有情众生的哀鸣、痛不欲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画面十分生动地传达了生命无常的苦难与矛盾。在壁画的左上方有“吐蕃赞普”等藏文题记。在同一画面中还有唐朝皇帝和其他国家来使悼念佛陀涅槃的情景,人物众多,神态各异,画面恢宏,大气镑礴,充分表达了艺术家们对佛的虔诚膜拜以及当时的政权格획情况。
莫高窟第158窟窟门北壁上还有供养沙门“大蕃管内三学法师持钵僧宜”的汉文题记。“大蕃管内”是吐蕃人的自称,“宜”字是吐蕃时代的藏人姓氏,根据这两则壁画题记,我们可以断定莫高窟第158窟壁画是由吐蕃画师所绘。
大英博物馆现收藏有不少被斯坦因劫去的吐蕃统治时期的壁画和土纸画,这些作品的艺术内容和艺术形式都具有浓郁的吐蕃风格,是吐蕃占领敦煌时期创作的精品,真实生动地展现了吐蕃的艺术风格和美学情趣。 例如Stein paiming32,其中就有绘于曼荼罗上“救度佛母”像,佛母侧身呈交脚坐式,俯视众生,双手于胸前结手印,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态。佛母身后的背光沿用了前代背光形式。不难看出吐蕃画师在创作上继承了敦煌壁画的技法与传统。另外,还有“五耆那曼荼罗”“千手观音菩萨曼荼罗”。
在大英博物馆里收藏的敦煌吐蕃统治时期的土纸画和绢本设色画中,最有艺术价值的则是笔法细腻,线条流畅,色彩饱满,画面简洁的观音菩萨画像。我们似能透过虚空藏菩萨像看到当时吐蕃赞普的影子。在敦煌藏经洞中曾出土过绘在土纸上的虚空藏菩萨像,菩萨坐在莲花之中,右手施无畏印,左手于胸前,似作威严怒目状,画家对鼻、眼眉、嘴,特别是髭须的勾勒十分传神。这幅作品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布达拉宫、大昭寺内的松赞干布塑像以及其在画像上的某种内在的关系。虚空藏菩萨背后围绕着火焰纹式的背光,左右上方绘有日轮金乌和月轮檐蜍(此类日月菩萨壁画在藏传佛教寺院中一直沿袭到今天)。在这幅画的下方有藏文题记和画家名称。有人认为此画是吐蕃时期壁画的粉本。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绢画和紙布画都是艺术水平很高的作品,例如“如意轮观音”“观音曼荼罗”“观世音菩萨”等。但它们大多流失海外,藏于大英博物馆内。
“如意轮观音像”是莫高窟第14窟东侧的壁画。洞窟开凿于吐蕃统治时期,在北南壁两侧绘有观音经变8铺,北壁东侧的如意轮观音,头戴化佛宝冠,伴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作六臂思惟状,背光是典型的吐蕃云纹, 周围布满神态各异的佛、菩萨等,整个构图好似一幅放大的唐卡,色彩绚丽,具有典型的藏式绘画风格。如意轮观音是密宗六观音之一。如意是指如意宝珠,轮指法轮,全称为如意宝珠法轮观音。此观音住如意宝珠禅定, 能如意说法救度六道众生之苦,成就一切众生之愿望,所以深受敬奉。《观自在菩萨如意轮瑜伽仪轨》中说:手持如意宝,六臂身金色,顶髻宝庄严,冠坐自在王,住于说法相。左第一手思惟,愍念有情故;第二手持如意宝,能满众愿;第三手持念珠,为度众生苦。右第一手持光明山,成就无倾动;第二手持莲,能将诸法;第三手持轮,能转无二法。六臂,体能现六道。
大部分如意轮观音壁画都是以此经轨仪绘制的。在莫高窟第14窟的供养人题记中,有两位妇女的汉文题记,其一曰“妮子阿敦悉力供养”,其二曰“妮子延美供养”。这两位供养人的汉名是由藏语转译过来的,联系北壁东侧的如意轮观音壁画风格,我们认为此画出自吐蕃画师之手。
公元8~9世纪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敦煌成为藏汉等多民族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从某种意义上讲,敦煌促成了西域诸民族文化交流、吸收与融合的发展前景。德国学者克林凯特在他的名著《丝路古道上的文化》中曾这样评说了敦煌在中国古代文明中的地位:丝绸之路东段最重要的文化中心,就是位于中国甘肃西部对中国文化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敦煌,这是进入中国的大门。…… 在绿洲城市敦煌进行着活跃的贸易往来,而佛教寺院则是生机勃勃的文化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中心。敦煌不仅反映了佛教的发展,而且也反映了直至相当于我们中世纪那个时代的中国文化史的发展。这里所创作的绘画,绝不仅仅是宗教场景,还有世俗画面,其中介绍了工业、农业、商业、建筑业、音乐,特别是佛事情况。①如果我们把敦煌文化看成是多民族文化交互影响的产物的话,那么在这个独特的文化序列中,吐蕃人一方面学习借鉴了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与此同时也为敦煌佛教艺术的发展和创新做出了积极贡献。在敦煌发现的公元9世纪的一部乡土志——《敦煌录》中曾这样写道:州南有莫高窟,去州二十五里,古寺僧舍绝多,亦有洪钟。其谷南北两头,有天王堂及神祠,壁画吐蕃赞普部从。其山西壁南北二里,并是镌凿高大沙窟,塑画师佛像。每窟动计费税百万;前设楼阁数层,有大像堂殿,其像长一百六十尺;其小龛无数,悉有虚槛通连巡礼游览之景。②这段出自公元9世纪的乡土志,真实记录了吐蕃在其统治敦煌时期对于发展佛教文化事业所采取的积极态度。诚如刘锡淦先生在《龟兹古国史》评价吐蕃佛教文化对龟兹艺术影响的那样:自公元789年至公元821年,吐蕃占领龟兹,对社会生产谈不上有何推进,但对佛教的推弘则是不遗余力的,对以后的龟兹有着极大影响,我们现在在于阗和、龟兹石窟的壁画、雕塑中以及文书、典籍里,均可见到吐蕃文化的成分。藏传佛教在龟兹佛教艺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研究龟兹佛教不可不对藏传佛教给予一定的重视。①我们认为刘锡淦先生的这一评述不但适用于龟兹、于阗,同样也适用于敦煌。正如大多数敦煌学者们公认的那样,吐蕃统治时期的吐蕃艺术家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虔诚的信仰给敦煌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审美范式。
(P.3336)吐蕃宰相尚伦藏嘘律钵有病设斋文。(P.2974、P.3395)《大乘经纂要义》一卷,题记;“任寅年之月”,大吐蕃国赞普印信,并此十善经本“流传诸州,流行读育,后八月十六日写毕记”。(S.3699)又如,Stein painting32的藏文题记,为我们记录下了吐蕃画师创作佛画的一些重要内容:龙卓、我、僧人白央为身体健康和作回向功德(利益所有众生)而创作下列组画,药师佛、普贤菩萨、妙吉祥王子、千手千目艮观世音菩萨、如意轮转王、回向转轮王等佛像。
又莫高窟第225窟东壁千佛像下南、北侧着吐蕃装男、女供养人像题记:“佛弟子王沙奴敬画千佛六百一十躯一心供养”,“女弟子优婆姨郭氏为亡男画千佛六百一十躯一心供养”。
从这些题记中,我们不难看出吐蕃在统治敦煌时期对敦煌佛教艺术发展所做的贡献。
观音菩萨像一直是藏传佛教艺术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敦煌吐蕃统治时期的壁画中也保留了不同风格的观音菩萨画像,这些绘画作品从艺术手法上吸收了汉画的传统技法,但是在人物肖像,画面的构图、着色上明显带有藏传艺术的特色,有些作品还有尼泊尔、印度、克什米尔佛画的影子。例如,莫髙窟第463窟中窟顶南披所绘的南方宝生佛,佛座前的供养菩萨像,神态端庄,秀美怡然,侧身趺坐,头戴宝冠,顶饰环佩,斜披璎珞,裸身短裙,手执芙蕖,凝视莲花,神情虔静,是一幅难得的艺术作品。在同一石窟的窟顶东方药师佛座前,还绘有手执凤箜篌,双眉下视。沉浸于天国佛曲的供养菩萨像,娟秀文静,裸体短裙、璎珞环佩,侧身于莲花座之上。双耳饰圆形大耳环,头戴高髻花冠,菩萨手掌和足心都着朱红色,这是藏传壁画绘制佛母、度母等像时惯用的绘画手法。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幅供养菩萨的高髻花冠在敦煌壁画中极为少见,但是我们却能在遥远的古格早期壁画中找到同一风格的花冠装饰。这种花冠装饰,在我们看来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克什米尔和中亚佛教艺术的影响。
在莫高窟第405窟四壁中部绘有一幅藏传密宗壁画,此窟是以供奉大日如来为主尊的罗刹神堂,除塑像外窟顶绘大日如来、四方佛,四壁绘曼陀罗11铺。东壁门上为五金刚,左右壁画绘制大威德等,其他三壁分别绘梵天、罗刹王、大黑天、龙王等。主尊像被安排在曼荼罗的中心,莲花座之上,四周是形态不一的双身和単身修行像,从构图看很接近唐卡的构图形态,但却无传统唐卡严谨有余、生动灵秀不足的艺术感觉。
表现佛陀涅槃的题材一直是佛教艺术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我们从莫高窟第158窟的壁画中,可以欣赏到吐蕃赞普在侍从的陪伴下率领众大臣、贵妇悼念佛陀大涅槃时的生动情景。赞普身后绕着背光,侍从和大臣们都着吐蕃装,人物形象明显表现出少数民族的气质特征。佛陀示寂后的寂静与超然,与有情众生的哀鸣、痛不欲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画面十分生动地传达了生命无常的苦难与矛盾。在壁画的左上方有“吐蕃赞普”等藏文题记。在同一画面中还有唐朝皇帝和其他国家来使悼念佛陀涅槃的情景,人物众多,神态各异,画面恢宏,大气镑礴,充分表达了艺术家们对佛的虔诚膜拜以及当时的政权格획情况。
莫高窟第158窟窟门北壁上还有供养沙门“大蕃管内三学法师持钵僧宜”的汉文题记。“大蕃管内”是吐蕃人的自称,“宜”字是吐蕃时代的藏人姓氏,根据这两则壁画题记,我们可以断定莫高窟第158窟壁画是由吐蕃画师所绘。
大英博物馆现收藏有不少被斯坦因劫去的吐蕃统治时期的壁画和土纸画,这些作品的艺术内容和艺术形式都具有浓郁的吐蕃风格,是吐蕃占领敦煌时期创作的精品,真实生动地展现了吐蕃的艺术风格和美学情趣。 例如Stein paiming32,其中就有绘于曼荼罗上“救度佛母”像,佛母侧身呈交脚坐式,俯视众生,双手于胸前结手印,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态。佛母身后的背光沿用了前代背光形式。不难看出吐蕃画师在创作上继承了敦煌壁画的技法与传统。另外,还有“五耆那曼荼罗”“千手观音菩萨曼荼罗”。
在大英博物馆里收藏的敦煌吐蕃统治时期的土纸画和绢本设色画中,最有艺术价值的则是笔法细腻,线条流畅,色彩饱满,画面简洁的观音菩萨画像。我们似能透过虚空藏菩萨像看到当时吐蕃赞普的影子。在敦煌藏经洞中曾出土过绘在土纸上的虚空藏菩萨像,菩萨坐在莲花之中,右手施无畏印,左手于胸前,似作威严怒目状,画家对鼻、眼眉、嘴,特别是髭须的勾勒十分传神。这幅作品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布达拉宫、大昭寺内的松赞干布塑像以及其在画像上的某种内在的关系。虚空藏菩萨背后围绕着火焰纹式的背光,左右上方绘有日轮金乌和月轮檐蜍(此类日月菩萨壁画在藏传佛教寺院中一直沿袭到今天)。在这幅画的下方有藏文题记和画家名称。有人认为此画是吐蕃时期壁画的粉本。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绢画和紙布画都是艺术水平很高的作品,例如“如意轮观音”“观音曼荼罗”“观世音菩萨”等。但它们大多流失海外,藏于大英博物馆内。
“如意轮观音像”是莫高窟第14窟东侧的壁画。洞窟开凿于吐蕃统治时期,在北南壁两侧绘有观音经变8铺,北壁东侧的如意轮观音,头戴化佛宝冠,伴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作六臂思惟状,背光是典型的吐蕃云纹, 周围布满神态各异的佛、菩萨等,整个构图好似一幅放大的唐卡,色彩绚丽,具有典型的藏式绘画风格。如意轮观音是密宗六观音之一。如意是指如意宝珠,轮指法轮,全称为如意宝珠法轮观音。此观音住如意宝珠禅定, 能如意说法救度六道众生之苦,成就一切众生之愿望,所以深受敬奉。《观自在菩萨如意轮瑜伽仪轨》中说:手持如意宝,六臂身金色,顶髻宝庄严,冠坐自在王,住于说法相。左第一手思惟,愍念有情故;第二手持如意宝,能满众愿;第三手持念珠,为度众生苦。右第一手持光明山,成就无倾动;第二手持莲,能将诸法;第三手持轮,能转无二法。六臂,体能现六道。
大部分如意轮观音壁画都是以此经轨仪绘制的。在莫高窟第14窟的供养人题记中,有两位妇女的汉文题记,其一曰“妮子阿敦悉力供养”,其二曰“妮子延美供养”。这两位供养人的汉名是由藏语转译过来的,联系北壁东侧的如意轮观音壁画风格,我们认为此画出自吐蕃画师之手。
公元8~9世纪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敦煌成为藏汉等多民族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从某种意义上讲,敦煌促成了西域诸民族文化交流、吸收与融合的发展前景。德国学者克林凯特在他的名著《丝路古道上的文化》中曾这样评说了敦煌在中国古代文明中的地位:丝绸之路东段最重要的文化中心,就是位于中国甘肃西部对中国文化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敦煌,这是进入中国的大门。…… 在绿洲城市敦煌进行着活跃的贸易往来,而佛教寺院则是生机勃勃的文化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中心。敦煌不仅反映了佛教的发展,而且也反映了直至相当于我们中世纪那个时代的中国文化史的发展。这里所创作的绘画,绝不仅仅是宗教场景,还有世俗画面,其中介绍了工业、农业、商业、建筑业、音乐,特别是佛事情况。①如果我们把敦煌文化看成是多民族文化交互影响的产物的话,那么在这个独特的文化序列中,吐蕃人一方面学习借鉴了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与此同时也为敦煌佛教艺术的发展和创新做出了积极贡献。在敦煌发现的公元9世纪的一部乡土志——《敦煌录》中曾这样写道:州南有莫高窟,去州二十五里,古寺僧舍绝多,亦有洪钟。其谷南北两头,有天王堂及神祠,壁画吐蕃赞普部从。其山西壁南北二里,并是镌凿高大沙窟,塑画师佛像。每窟动计费税百万;前设楼阁数层,有大像堂殿,其像长一百六十尺;其小龛无数,悉有虚槛通连巡礼游览之景。②这段出自公元9世纪的乡土志,真实记录了吐蕃在其统治敦煌时期对于发展佛教文化事业所采取的积极态度。诚如刘锡淦先生在《龟兹古国史》评价吐蕃佛教文化对龟兹艺术影响的那样:自公元789年至公元821年,吐蕃占领龟兹,对社会生产谈不上有何推进,但对佛教的推弘则是不遗余力的,对以后的龟兹有着极大影响,我们现在在于阗和、龟兹石窟的壁画、雕塑中以及文书、典籍里,均可见到吐蕃文化的成分。藏传佛教在龟兹佛教艺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研究龟兹佛教不可不对藏传佛教给予一定的重视。①我们认为刘锡淦先生的这一评述不但适用于龟兹、于阗,同样也适用于敦煌。正如大多数敦煌学者们公认的那样,吐蕃统治时期的吐蕃艺术家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虔诚的信仰给敦煌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审美范式。
附注
①敦煌研究院《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第56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
① 克林凯特著,赵崇明译,贾应逸审校《丝绸古道上的文化》第36页,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
② 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第 302 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 年。
①刘锡淦《龟兹古国史》第89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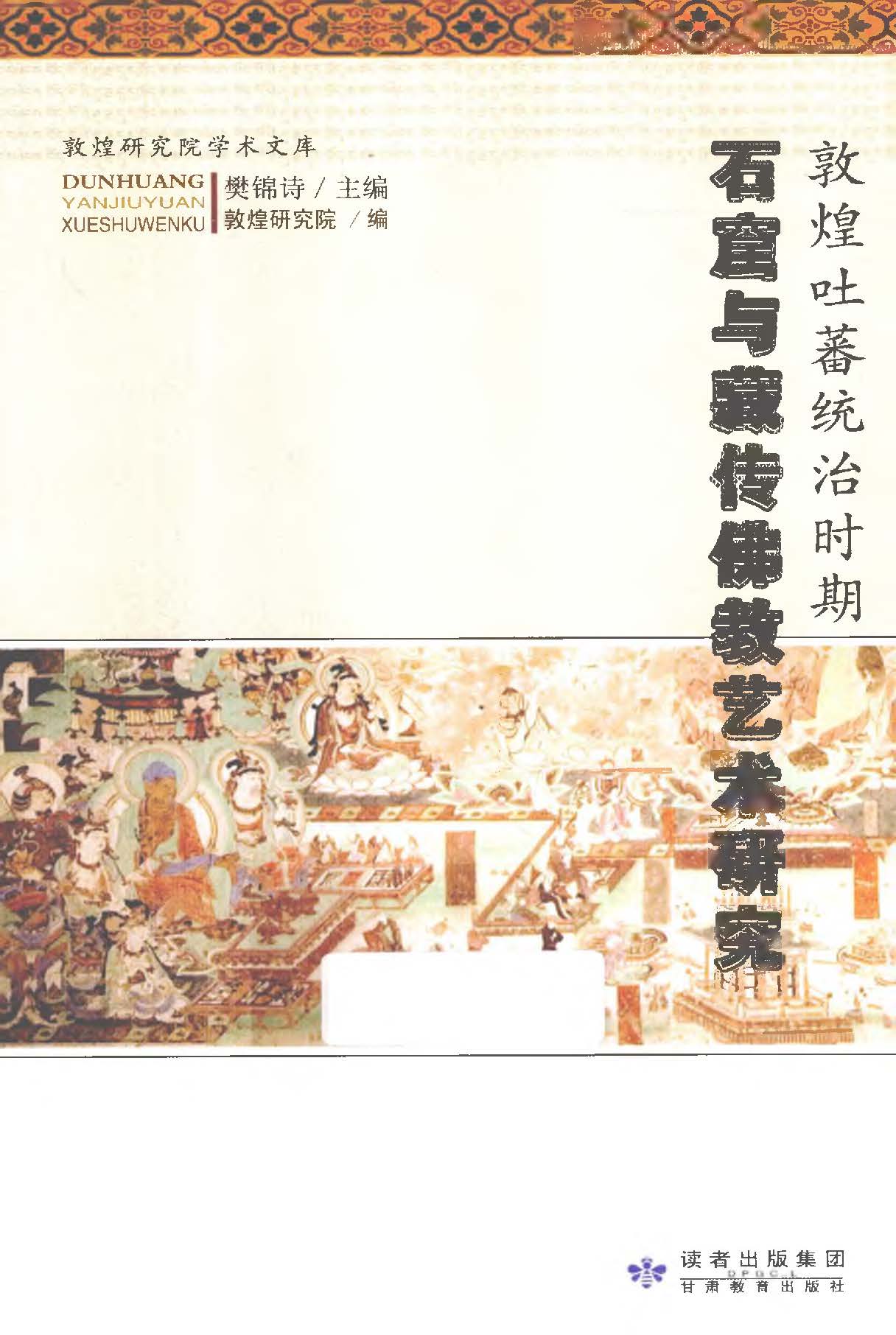
《敦煌吐蕃统治时期石窟与藏传佛教艺术研究》
出版者:甘肃教育出版社
出版地:2012.4
本书内容涉及对敦煌吐蕃石窟艺术样式的研究、社会政治背景探讨、造像思想研究、吐蕃密教文献研究、石窟经变画与图像专题研究、密教尊像研究、西藏考古与艺术研究、毗沙门天王像研究、莫高窟第465窟研究等多个领域。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