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毗沙门的组合的形象
| 内容出处: | 《敦煌吐蕃统治时期石窟与藏传佛教艺术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290120020210003228 |
| 颗粒名称: | 三、毗沙门的组合的形象 |
| 分类号: | K879.214-53 |
| 页数: | 10 |
| 页码: | 386-395 |
| 摘要: | 毗沙门的组合中,一个突出的形象就是戴虎头帽、披虎皮的形象了④这个形象多是与毗沙门天,即财神伴出的,而且其手中多持有吐宝鼠或吐宝鼠皮作的袋子。如果按佛典所记,天部组合的毗沙门天多与吉祥天女、鬼子母、最胜太子同出,那么这个形象是否即是最胜太子呢?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有一个认识基础,就是事实上,信众造像,能在多在大程度上严格按照经典的记载进行表现呢?有多少信众熟读经典和造像记呢?诸多的观音佛像、一些奇怪的组合和信众身份的不明确,说明民间造像及礼拜的随意性以及时尚对造像的影响。比如,1948年一个县的民间崇拜报告调査认为仅有19.7%的崇拜群体是由可辨认出的佛教徒组成的,并且其中有许多神也有与那些非佛教起源的神相混淆的倾向①。因此,时尚和某位有声望法师的传播,可能直接影响到一个地区一个时期的造像样式,这是理解经典(文本)与造像实物(图本)关系的前提。 也是下文讨论的基础。 |
| 关键词: | 敦煌石窟 文集 喇嘛宗 宗教艺术 |
内容
毗沙门的组合中,一个突出的形象就是戴虎头帽、披虎皮的形象了④这个形象多是与毗沙门天,即财神伴出的,而且其手中多持有吐宝鼠或吐宝鼠皮作的袋子。如果按佛典所记,天部组合的毗沙门天多与吉祥天女、鬼子母、最胜太子同出,那么这个形象是否即是最胜太子呢?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有一个认识基础,就是事实上,信众造像,能在多在大程度上严格按照经典的记载进行表现呢?有多少信众熟读经典和造像记呢?诸多的观音佛像、一些奇怪的组合和信众身份的不明确,说明民间造像及礼拜的随意性以及时尚对造像的影响。比如,1948年一个县的民间崇拜报告调査认为仅有19.7%的崇拜群体是由可辨认出的佛教徒组成的,并且其中有许多神也有与那些非佛教起源的神相混淆的倾向①。因此,时尚和某位有声望法师的传播,可能直接影响到一个地区一个时期的造像样式,这是理解经典(文本)与造像实物(图本)关系的前提。 也是下文讨论的基础。
集大英博物馆藏敦煌绘画出版的《西域美术》,对这个图像做出了说明,在其第二卷关于Ch.0069图的释名上写着“毗沙门天与乾闼婆”,有学者也认同这个组合,原因为:乾闼婆是“八部鬼众”之一,毗沙门天王是其主管神,所以乾闼婆常追随毗沙门天王左右。在与毗沙门天王的组合中,乾闽婆一般画于毗沙门天王的右侧,立姿,穿虎皮衣,一手拿金鼠,一手拿珠宝等不同器物②。
笔者认为这种辨识有些不妥,原因是此形象不是鬼相,不能代表鬼众,也无典可据。如大英博物馆藏 Ch.0018、Ch.xxxvii.002 《行道天王图》表现的追随鬼众,都是鬼相。之所以有这样认定,其原因是在大正藏图像部中,有一幅乾闼婆与诸鬼图(图15)③这个形象就是头戴一兽头帽。按典上记录, 这个神在密法中是守护胎儿及儿童之神,据日本仁和寺样,其图像是该神与十五种鬼的曼陀罗,样式描述为:乾闼婆王,形如冥宦,甲冑形。 坐石上,垂右足,台右手押膝,左手持戟,顶上有牛头。 这个描述有两点值得关注, 一是头顶上为牛头,不是虎头或狮头;二是手中持戟, 不是宝鼠、口袋或宝珠。另外要强调的一点是所谓的乾闼婆,也只是头戴一个兽首帽子,而毗沙门的伴出者着虎皮(是有头有尾的整个虎皮)。另据图像部七“天部形象”所载的乾闼婆形象(图16):怒相武士形,利牙上出如鬼,左手牵诸鬼众,右手持戟,右侧一群小儿。又据毗沙门夜叉鬼众图像看,几乎都是鬼相武士形。综上所述,可以总结三点:第一,在经典中确有一个头戴兽帽称为 “旃檀乾闼婆”的神王图样,但文字说明是顶上“牛头”,佛教辞典也说明,乾闼婆是八部众之ᅳ,是东方天王之眷属,如大牛王;第二,乾闼婆形如天王形,以上两个图像手中持物都是戟;第三,在本文涉及的与毗沙门组合图像中,该神不是持戟,而是一手持鼠或口袋,一手持宝珠,头上所戴,明确的是虎头、虎皮。因此《西域研究》中的称名还值得商確。
相传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西蕃、康居等国来寇扰唐朝的边境。 当时,唐玄宗请不空三藏祈求毗沙门天护持。作法之后,果然感得天王神兵在西方边境的云雾间鼓角喧鸣地出现,终使蕃兵溃走。这是佛教史籍所载天王帮助唐朝击溃敌兵的故事。关于毗沙门天救安西城(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龟兹城,今新疆库车)的传说,纵观文献所记,事实上,毗沙门天没有亲自出现来救城,而是其第二子,叫“独键”的领天兵而来。不空译《毗沙门仪轨》后记:头或狮头;二是手中持戟, 不是宝鼠、口袋或宝珠。另外要强调的一点是所谓的乾闼婆,也只是头戴一个兽首帽子,而毗沙门的伴出者着虎皮(是有头有尾的整个虎皮)。另据图像部七“天部形象”所载的乾闼婆形象(图16):怒相武士形,利牙上出如鬼,左手牵诸鬼众,右手持戟,右侧一群小儿。又据毗沙门夜叉鬼众图像看,几乎都是鬼相武士形。综上所述,可以总结三点:第一,在经典中确有一个头戴兽帽称为 “旃檀乾闼婆”的神王图样,但文字说明是顶上“牛头”,佛教辞典也说明,乾闼婆是八部众之ᅳ,是东方天王之眷属,如大牛王;第二,乾闼婆形如天王形,以上两个图像手中持物都是戟;第三,在本文涉及的与毗沙门组合图像中,该神不是持戟,而是一手持鼠或口袋,一手持宝珠,头上所戴,明确的是虎头、虎皮。因此《西域研究》中的称名还值得商確。
相传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西蕃、康居等国来寇扰唐朝的边境。 当时,唐玄宗请不空三藏祈求毗沙门天护持。作法之后,果然感得天王神兵在西方边境的云雾间鼓角喧鸣地出现,终使蕃兵溃走。这是佛教史籍所载天王帮助唐朝击溃敌兵的故事。关于毗沙门天救安西城(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龟兹城,今新疆库车)的传说,纵观文献所记,事实上,毗沙门天没有亲自出现来救城,而是其第二子,叫“独键”的领天兵而来。不空译《毗沙门仪轨》后记:毗沙门天王子赦儞娑,现童子形告持诵者言:汝有何事请召我父?持捅者言:我为供养三宝,受与我财宝。童子赦備娑于须臾顷还至毗沙门天王所。告父王言:持诵者求诸财宝,为供养故利益有情。毗沙门天王告童子赦倩娑言:汝日日与金钱一百乃至寿终。其童子赦儞娑,日日送金钱一百。
两部经记载了相同的内容,即有善人祈请毗沙门时,由其子给予钱财①。
但在佛经中,我们只能看到“最胜太子”的经法与形象。最胜太子,是护持佛法、守护国家之善神,与哪吒为同尊。为战争或镇定兵乱所修之法, 称为“最胜太子法”。考察其形象,为四面八臂,面相极为凶猛(图17)。也有一面二臂、头梳二髻相(图18)。另在不空译的《北方毗沙门天王随军护法仪轨》记录有太子哪吒的形象,为护持国家军队的:画一毗沙门神其孙哪吒天神七宝庄严①,左手令执口齿,右手诧腰,令执三戟稍。其神足下作一药叉女住趺坐,并作青黑色少赤加...在《大正藏》中存有唐代哪吒太子的画样为一手持宝塔相,正如《毗沙门仪轨》所云:“天王第三子哪吒太子,捧塔常随天王。”(图19)法国集美博物馆藏品中有一幅《行道天王图》(五代至北宋,MG. 17666),据说表现了毗沙门及第一和第三王子、吉祥天、毗那夜迦、猪头天、夜叉三躯②但这些都与戴虎皮帽者的形象相去甚远。
笔者认为对于这类持鼠的虎皮勇士, 一个基础认识是:此神属于毗沙门天王的眷属。理由是这种神出现的时候,通常是手持象征财富的宝鼠或提鼠皮袋子(图20),通过其持物,基本可以判断,在宗教意义上,他属于财神毗沙门天王的眷属而不是一般的武士、金刚或夜叉。另外,与一般的天王像比较,这个形象表现的可能是一个少年,身材矮小,且面部没有胡须。因此笔者在历史材料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假设,就是此像表现的可能是救安西城的毗沙门天第二子独键。
佛典中没有独键的形象,只有最胜太子或哪吒的像式,但对于独键救下西域安西城之功,西域人是不会忘记的,人们在记住毗沙门天护持的同时,对其ニ子独键更是心存感激。不空所记录的内容应是当时人们的普遍认识。独键除了救护安西城外,还常领天兵护持国家。不空记曰:“天宝元载四月二十三日,内谒者监高慧明宜天王第二子独健,常领天兵护其国界。”由于独键有这种护国的行为,因此当时有专门纪念独键的日子。在不空的记录中说每月的第十一日,为第ニ子独健辞父王巡界日。”通过这种检索可知,当时人们对独键的勇猛和护国是十分熟悉的,而以虎的形象来形容少年的英勇似乎也是合情合理的。这样理解的一个重要的线索是, 以皮饰勇者可能与吐蕃的“大虫皮”制度有关。
史书记载,吐蕃自古就有“大虫皮”制度,据《贤者喜宴》记:勇者的标志虎皮袍;贤者的标志是告身。所谓六褒贬是勇士裹以草豹与虎皮;懦夫贬以狐帽;……所谓六勇饰是虎皮褂,虎皮裙两者;缎鞯及马镫缎垫两者;项巾及虎皮袍等,共为六种。①向达在敦煌cm号洞窟发现在供养人中间的一块牌子上书写“大虫皮” 三字,另在东壁门南女供养人像第一人题名中又发现“大虫皮”字样。题记曰:“夫人蕃任瓜州都督口仓曹參军金银间告身大虫皮康公之女修行颖悟优婆姨如济(?)弟(?)一心供养。”据此,向达先生指出:“大虫皮乃是吐蕃武职官阶,或是因其身披大虫皮,故名。”②据研究,吐蕃的大虫皮制度始自公元7世纪的松赞干布,《新唐书•吐蕃传》中记:“山多柏坡,皆丘墓,旁作屋赭涂之,绘白虎,皆虏贵人有战功者,生衣其皮,死以旌勇。”在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中也有赤松德赞给功臣赐虎皮衣的记载,汉文史集中也记载有类似的信息。旧五代史记唐天成三年(928年),回鹘王仁喻来朝,吐蕃亦遣使附以来……明宗(李嗣源)赐以虎皮,人一张,皆披而拜……”③大虫皮除去授予武职官员外,在吐蕃历史上对于勇猛的士兵也授予“虎”的称号,称为“虎兵”,汉文典籍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唐代樊绰撰《蛮书》卷八“蛮夷风俗第八”曰:贵绯色紫两色,得紫后有大功则得锦。又有超等殊功者,则得全披波罗皮。其次功则胸前背后得披,而闲其袖。又以次功,则胸前得披,并阙其背。谓之大虫皮,亦曰波罗皮。
从这段记载得知,大虫皮至少有三个等级的三种款式:一种是“全皮”,这须要立特殊的功劳;次之功得到的是没有袖,只有前心后背的虫皮;更次之的是只有胸前的虫皮,并且得知大虫皮的另一名称“波罗皮”①。由于吐蕃与南诏的关系②,大虫皮制度,也直接影响到南诏国的武官制度③。回顾一下西藏的佛教图像志,着虎皮者十分常见,尤其在藏传佛教的怒相神的表现上,几乎都系有虎皮裙。综上所述,穿皮袍,戴虎头帽是源自吐蕃的一种风俗(图21、22、23)。安史之乱以后,吐蕃逐步占领了河陇西域之地,并对佛教大力扶植。因此,吐蕃的一些风俗喜好,便出现在敦煌、龟兹等地的佛教石窟造像中。其中,吐蕃的大虫皮制度也反映在敦煌、龟兹的护法和类似武士的神祇形象中(图24、25、26)。当然,在龟兹的壁画中出现的着虎皮者多为护法的金刚力士和天龙八部中的护法神。类似敦煌、榆林那种与毗沙门天共出图像还没有发现。
敦煌地区传承了西域的某些供养习惯,如大量供奉兜跋毗沙门天,但由于救安城之事,人们在供奉毗沙门天的同时,也表现了救安西城和护国勇士独键,但是独键没有图像传统。中唐和以后的敦煌石窟中,由于有吐蕃画师的参与,可能在表现独键这样的勇者时,依据吐蕃画师的习惯创造了这个形象,从而将这个着虎皮、戴虎头帽的少年与毗沙门和吉祥天一同供养在圣殿上。而在这里的着虎皮少年,便不同于一般出现在护法神中的力士,而是具有具体人物指向的图像,即勇者独键。在这种组合像中,两个主要形象,即毗沙门天与独键,都是源自吐蕃的表现传统,即兜跋毗沙门天王和着虎皮武士(图27)。这种既迎合吐蕃人审美兴味又符合西域人价值判断的毗沙门天王组合像就这样出现在中唐时期的敦煌和榆林石窟中。
集大英博物馆藏敦煌绘画出版的《西域美术》,对这个图像做出了说明,在其第二卷关于Ch.0069图的释名上写着“毗沙门天与乾闼婆”,有学者也认同这个组合,原因为:乾闼婆是“八部鬼众”之一,毗沙门天王是其主管神,所以乾闼婆常追随毗沙门天王左右。在与毗沙门天王的组合中,乾闽婆一般画于毗沙门天王的右侧,立姿,穿虎皮衣,一手拿金鼠,一手拿珠宝等不同器物②。
笔者认为这种辨识有些不妥,原因是此形象不是鬼相,不能代表鬼众,也无典可据。如大英博物馆藏 Ch.0018、Ch.xxxvii.002 《行道天王图》表现的追随鬼众,都是鬼相。之所以有这样认定,其原因是在大正藏图像部中,有一幅乾闼婆与诸鬼图(图15)③这个形象就是头戴一兽头帽。按典上记录, 这个神在密法中是守护胎儿及儿童之神,据日本仁和寺样,其图像是该神与十五种鬼的曼陀罗,样式描述为:乾闼婆王,形如冥宦,甲冑形。 坐石上,垂右足,台右手押膝,左手持戟,顶上有牛头。 这个描述有两点值得关注, 一是头顶上为牛头,不是虎头或狮头;二是手中持戟, 不是宝鼠、口袋或宝珠。另外要强调的一点是所谓的乾闼婆,也只是头戴一个兽首帽子,而毗沙门的伴出者着虎皮(是有头有尾的整个虎皮)。另据图像部七“天部形象”所载的乾闼婆形象(图16):怒相武士形,利牙上出如鬼,左手牵诸鬼众,右手持戟,右侧一群小儿。又据毗沙门夜叉鬼众图像看,几乎都是鬼相武士形。综上所述,可以总结三点:第一,在经典中确有一个头戴兽帽称为 “旃檀乾闼婆”的神王图样,但文字说明是顶上“牛头”,佛教辞典也说明,乾闼婆是八部众之ᅳ,是东方天王之眷属,如大牛王;第二,乾闼婆形如天王形,以上两个图像手中持物都是戟;第三,在本文涉及的与毗沙门组合图像中,该神不是持戟,而是一手持鼠或口袋,一手持宝珠,头上所戴,明确的是虎头、虎皮。因此《西域研究》中的称名还值得商確。
相传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西蕃、康居等国来寇扰唐朝的边境。 当时,唐玄宗请不空三藏祈求毗沙门天护持。作法之后,果然感得天王神兵在西方边境的云雾间鼓角喧鸣地出现,终使蕃兵溃走。这是佛教史籍所载天王帮助唐朝击溃敌兵的故事。关于毗沙门天救安西城(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龟兹城,今新疆库车)的传说,纵观文献所记,事实上,毗沙门天没有亲自出现来救城,而是其第二子,叫“独键”的领天兵而来。不空译《毗沙门仪轨》后记:头或狮头;二是手中持戟, 不是宝鼠、口袋或宝珠。另外要强调的一点是所谓的乾闼婆,也只是头戴一个兽首帽子,而毗沙门的伴出者着虎皮(是有头有尾的整个虎皮)。另据图像部七“天部形象”所载的乾闼婆形象(图16):怒相武士形,利牙上出如鬼,左手牵诸鬼众,右手持戟,右侧一群小儿。又据毗沙门夜叉鬼众图像看,几乎都是鬼相武士形。综上所述,可以总结三点:第一,在经典中确有一个头戴兽帽称为 “旃檀乾闼婆”的神王图样,但文字说明是顶上“牛头”,佛教辞典也说明,乾闼婆是八部众之ᅳ,是东方天王之眷属,如大牛王;第二,乾闼婆形如天王形,以上两个图像手中持物都是戟;第三,在本文涉及的与毗沙门组合图像中,该神不是持戟,而是一手持鼠或口袋,一手持宝珠,头上所戴,明确的是虎头、虎皮。因此《西域研究》中的称名还值得商確。
相传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西蕃、康居等国来寇扰唐朝的边境。 当时,唐玄宗请不空三藏祈求毗沙门天护持。作法之后,果然感得天王神兵在西方边境的云雾间鼓角喧鸣地出现,终使蕃兵溃走。这是佛教史籍所载天王帮助唐朝击溃敌兵的故事。关于毗沙门天救安西城(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龟兹城,今新疆库车)的传说,纵观文献所记,事实上,毗沙门天没有亲自出现来救城,而是其第二子,叫“独键”的领天兵而来。不空译《毗沙门仪轨》后记:毗沙门天王子赦儞娑,现童子形告持诵者言:汝有何事请召我父?持捅者言:我为供养三宝,受与我财宝。童子赦備娑于须臾顷还至毗沙门天王所。告父王言:持诵者求诸财宝,为供养故利益有情。毗沙门天王告童子赦倩娑言:汝日日与金钱一百乃至寿终。其童子赦儞娑,日日送金钱一百。
两部经记载了相同的内容,即有善人祈请毗沙门时,由其子给予钱财①。
但在佛经中,我们只能看到“最胜太子”的经法与形象。最胜太子,是护持佛法、守护国家之善神,与哪吒为同尊。为战争或镇定兵乱所修之法, 称为“最胜太子法”。考察其形象,为四面八臂,面相极为凶猛(图17)。也有一面二臂、头梳二髻相(图18)。另在不空译的《北方毗沙门天王随军护法仪轨》记录有太子哪吒的形象,为护持国家军队的:画一毗沙门神其孙哪吒天神七宝庄严①,左手令执口齿,右手诧腰,令执三戟稍。其神足下作一药叉女住趺坐,并作青黑色少赤加...在《大正藏》中存有唐代哪吒太子的画样为一手持宝塔相,正如《毗沙门仪轨》所云:“天王第三子哪吒太子,捧塔常随天王。”(图19)法国集美博物馆藏品中有一幅《行道天王图》(五代至北宋,MG. 17666),据说表现了毗沙门及第一和第三王子、吉祥天、毗那夜迦、猪头天、夜叉三躯②但这些都与戴虎皮帽者的形象相去甚远。
笔者认为对于这类持鼠的虎皮勇士, 一个基础认识是:此神属于毗沙门天王的眷属。理由是这种神出现的时候,通常是手持象征财富的宝鼠或提鼠皮袋子(图20),通过其持物,基本可以判断,在宗教意义上,他属于财神毗沙门天王的眷属而不是一般的武士、金刚或夜叉。另外,与一般的天王像比较,这个形象表现的可能是一个少年,身材矮小,且面部没有胡须。因此笔者在历史材料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假设,就是此像表现的可能是救安西城的毗沙门天第二子独键。
佛典中没有独键的形象,只有最胜太子或哪吒的像式,但对于独键救下西域安西城之功,西域人是不会忘记的,人们在记住毗沙门天护持的同时,对其ニ子独键更是心存感激。不空所记录的内容应是当时人们的普遍认识。独键除了救护安西城外,还常领天兵护持国家。不空记曰:“天宝元载四月二十三日,内谒者监高慧明宜天王第二子独健,常领天兵护其国界。”由于独键有这种护国的行为,因此当时有专门纪念独键的日子。在不空的记录中说每月的第十一日,为第ニ子独健辞父王巡界日。”通过这种检索可知,当时人们对独键的勇猛和护国是十分熟悉的,而以虎的形象来形容少年的英勇似乎也是合情合理的。这样理解的一个重要的线索是, 以皮饰勇者可能与吐蕃的“大虫皮”制度有关。
史书记载,吐蕃自古就有“大虫皮”制度,据《贤者喜宴》记:勇者的标志虎皮袍;贤者的标志是告身。所谓六褒贬是勇士裹以草豹与虎皮;懦夫贬以狐帽;……所谓六勇饰是虎皮褂,虎皮裙两者;缎鞯及马镫缎垫两者;项巾及虎皮袍等,共为六种。①向达在敦煌cm号洞窟发现在供养人中间的一块牌子上书写“大虫皮” 三字,另在东壁门南女供养人像第一人题名中又发现“大虫皮”字样。题记曰:“夫人蕃任瓜州都督口仓曹參军金银间告身大虫皮康公之女修行颖悟优婆姨如济(?)弟(?)一心供养。”据此,向达先生指出:“大虫皮乃是吐蕃武职官阶,或是因其身披大虫皮,故名。”②据研究,吐蕃的大虫皮制度始自公元7世纪的松赞干布,《新唐书•吐蕃传》中记:“山多柏坡,皆丘墓,旁作屋赭涂之,绘白虎,皆虏贵人有战功者,生衣其皮,死以旌勇。”在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中也有赤松德赞给功臣赐虎皮衣的记载,汉文史集中也记载有类似的信息。旧五代史记唐天成三年(928年),回鹘王仁喻来朝,吐蕃亦遣使附以来……明宗(李嗣源)赐以虎皮,人一张,皆披而拜……”③大虫皮除去授予武职官员外,在吐蕃历史上对于勇猛的士兵也授予“虎”的称号,称为“虎兵”,汉文典籍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唐代樊绰撰《蛮书》卷八“蛮夷风俗第八”曰:贵绯色紫两色,得紫后有大功则得锦。又有超等殊功者,则得全披波罗皮。其次功则胸前背后得披,而闲其袖。又以次功,则胸前得披,并阙其背。谓之大虫皮,亦曰波罗皮。
从这段记载得知,大虫皮至少有三个等级的三种款式:一种是“全皮”,这须要立特殊的功劳;次之功得到的是没有袖,只有前心后背的虫皮;更次之的是只有胸前的虫皮,并且得知大虫皮的另一名称“波罗皮”①。由于吐蕃与南诏的关系②,大虫皮制度,也直接影响到南诏国的武官制度③。回顾一下西藏的佛教图像志,着虎皮者十分常见,尤其在藏传佛教的怒相神的表现上,几乎都系有虎皮裙。综上所述,穿皮袍,戴虎头帽是源自吐蕃的一种风俗(图21、22、23)。安史之乱以后,吐蕃逐步占领了河陇西域之地,并对佛教大力扶植。因此,吐蕃的一些风俗喜好,便出现在敦煌、龟兹等地的佛教石窟造像中。其中,吐蕃的大虫皮制度也反映在敦煌、龟兹的护法和类似武士的神祇形象中(图24、25、26)。当然,在龟兹的壁画中出现的着虎皮者多为护法的金刚力士和天龙八部中的护法神。类似敦煌、榆林那种与毗沙门天共出图像还没有发现。
敦煌地区传承了西域的某些供养习惯,如大量供奉兜跋毗沙门天,但由于救安城之事,人们在供奉毗沙门天的同时,也表现了救安西城和护国勇士独键,但是独键没有图像传统。中唐和以后的敦煌石窟中,由于有吐蕃画师的参与,可能在表现独键这样的勇者时,依据吐蕃画师的习惯创造了这个形象,从而将这个着虎皮、戴虎头帽的少年与毗沙门和吉祥天一同供养在圣殿上。而在这里的着虎皮少年,便不同于一般出现在护法神中的力士,而是具有具体人物指向的图像,即勇者独键。在这种组合像中,两个主要形象,即毗沙门天与独键,都是源自吐蕃的表现传统,即兜跋毗沙门天王和着虎皮武士(图27)。这种既迎合吐蕃人审美兴味又符合西域人价值判断的毗沙门天王组合像就这样出现在中唐时期的敦煌和榆林石窟中。
附注
④ 对于这个形象,也有学者提到与希腊神话中大力神“海格力斯”有图像上的传承关系。本文在此主要考虑其形象所指。
① 芮沃寿著,常蕾译《中国历史中的佛教》第7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② 张永安《敦煌毗沙门天王图像及其信仰》,《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 期。
③ 见《大正蔵》图像部九“童子经法”。
①不空译《毗沙门仪轨》中记"唐天宝元年壬午岁,大石、康五国围安西城,其年二月十一曰有表请兵救援。圣人告一行禅师曰:和尚,安西被大石康□口ロロロロ国围城,有表请兵。安西去京一万二千里,兵程八个月然到其安西……一行в:陛下何不请北方毗沙门天王神兵应援。圣人云:朕如何请得?一行曰唤取胡僧大广智即请得。有勅唤得大广智到内云,圣人所唤臣僧者,岂不缘安西城被五国賊围城,圣人云是。大广智曰: 陛下执香炉入道场,与陛下请北方天王神兵救。急入道场请,真言未二七遍,圣人忽见有神人二三百人,带甲于道场前立。圣人问僧曰:此是何人?大广智日:此是北方毗沙门天王第二子独键,领天兵救援安西故来辞,圣人设食发遗。至其年四月日,安西表到云:去二月十一日已后午前,去城东北三十里,有云雾斗暗,雾中有人,身长一丈,约三五百人,尽着金甲。至酉后鼓角大鸣,声震三百里,地动山崩停住三日,五国大惧尽退军,抽兵诸营坠中,并是金鼠咬弓弩弦,及器械损断尽不堪用。有老弱去不得者,臣所管兵欲损之,空中云放去不须杀。寻声反顾城北门楼上有大光明,毗沙门天王见身于楼上,其天王神样,谨随表进上者,中华天宝十四载,于内供养僧大悲处,写得经及像,至大历五年,于集洲见内供养僧良贲法师,移住集洲开元寺,勘经像与大悲本同,昔防援国界,奉佛教勅,令第三子哪咤捧塔随天王。三藏大广智云:每月一日,天王与诸天鬼神集会日;十一日第二子独键辞父王巡界日;十五日与四天王集会日;二十一日哪吒与父王交塔日。”①关于神派使者行使神权的说法及相关文献材料,是由以色列特拉维夫孔子学院院长夏维明先生提供的信息,在此表示感谢。
① 这段文字中提到哪吒是毗沙门夫王之孙。关于哪吒是太子还是孙子的问题,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暂不论及。
② 《西域美术•ギメ美术馆ペリオ•コレクション( П ),讲谈社,1994年。
① 黄颢《<贤者喜宴》摘译 》(三),《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
②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363~36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
③ 薛居正《日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八“外国列传第二",中华书局,1976年① 唐人樊绰的记载,也得到后人的转载,如清代史梦兰《尔尔书屋诗草》卷七中就有相似的文字。
② 关于吐蕃与南诏的交通关系及联姻情况,见杨铭《敦煌藏文献所见的南诏及其与吐蕃的关系》,《敦煌研究》2008 年第 2 期。
©关于“大虫皮”制度,可见陆离《大虫皮考》,《敦煌研究》2004年第1期。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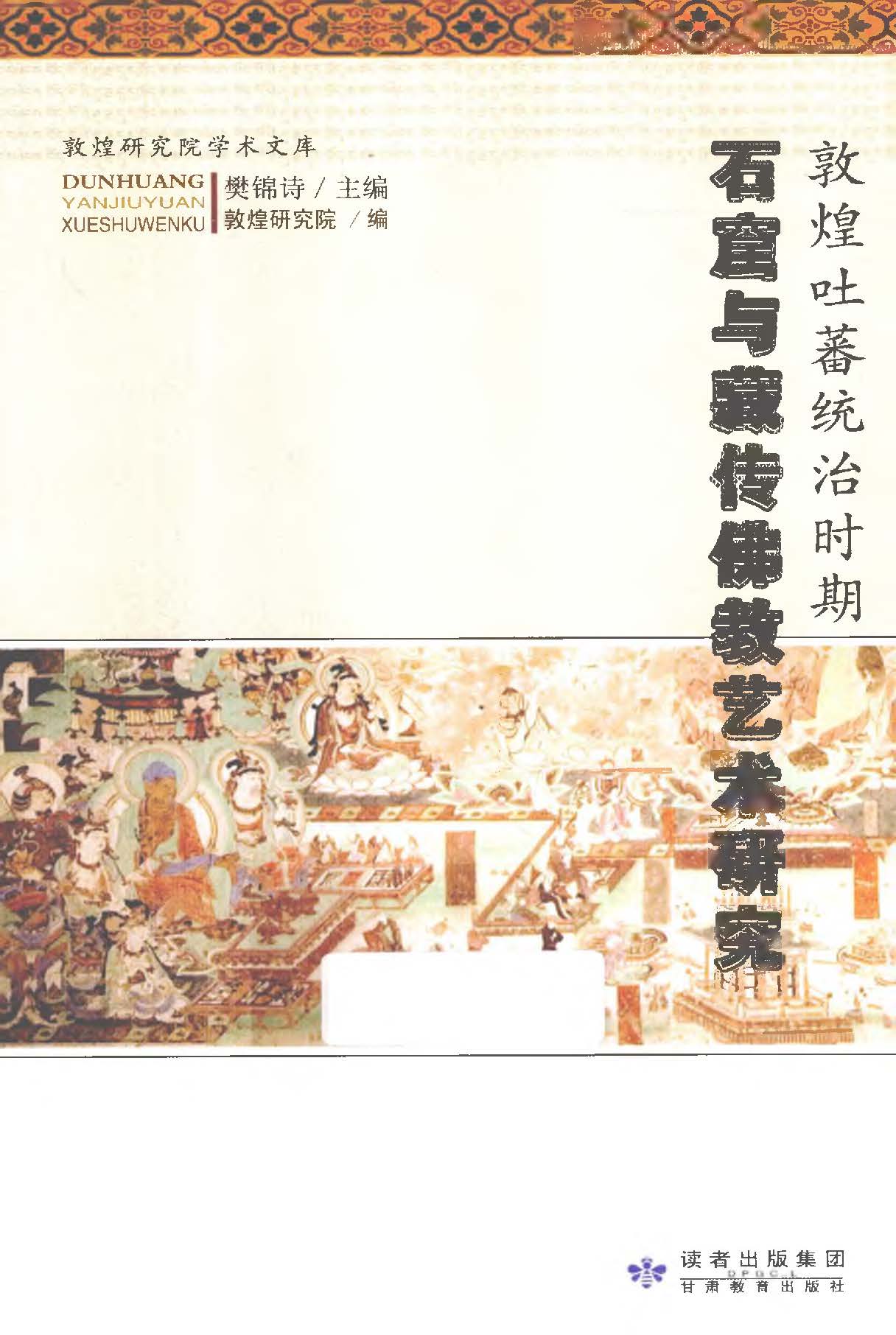
《敦煌吐蕃统治时期石窟与藏传佛教艺术研究》
出版者:甘肃教育出版社
出版地:2012.4
本书内容涉及对敦煌吐蕃石窟艺术样式的研究、社会政治背景探讨、造像思想研究、吐蕃密教文献研究、石窟经变画与图像专题研究、密教尊像研究、西藏考古与艺术研究、毗沙门天王像研究、莫高窟第465窟研究等多个领域。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