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小结
| 内容出处: | 《敦煌吐蕃统治时期石窟与藏传佛教艺术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290120020210003204 |
| 颗粒名称: | 四、小结 |
| 分类号: | K879.214-53 |
| 页数: | 3 |
| 页码: | 339-341 |
| 摘要: | 综上所述,在印度,孔雀明王像从一面二臂发展至一面四臂、三面六臂,而在敦煌,有依据汉译经典的一面四臂像,依据了汉译经典和梵文文献的一面六臂像,还有忠实于梵文文献的一面二臂像,这几种图像基本并行出现。其背景,想来应是曹元忠、曹延禄作为归义军节度使向北宋朝贡的同时,与周边各种势力维持着微妙的平衡关系,促进了贸易往来。 |
| 关键词: | 敦煌石窟 文集 喇嘛宗 宗教艺术 |
内容
综上所述,在印度,孔雀明王像从一面二臂发展至一面四臂、三面六臂,而在敦煌,有依据汉译经典的一面四臂像,依据了汉译经典和梵文文献的一面六臂像,还有忠实于梵文文献的一面二臂像,这几种图像基本并行出现。其背景,想来应是曹元忠、曹延禄作为归义军节度使向北宋朝贡的同时,与周边各种势力维持着微妙的平衡关系,促进了贸易往来。
河西地区即使在吐蕃统治结束之后,用藏文写成的公牍也不在少数②。 因此,与中原不同,敦煌很可能通过吐蕃或西域,有选择地接受了印度佛教。其次,虽说归义军节度使张氏曾控制整个西域地区,但到了经过内乱之后的曹氏时代,其所控制的领域只限于沙州、瓜州等地。从敦煌向西,龟兹、伯孜克里克、高昌为西州回鹘所统治。敦煌以东,甘州为甘州回鹘所辖,西凉府(凉州)由吐蕃支配。为了稳妥地促进贸易往来,曹氏必然要与各少数民族政权保持良好的关系③。关于曹氏的出身,有人认为他并非汉族,而是粟特人④。敦煌特异的孔雀明王图像,也正反映了少数民族与地方豪族在相互影响和关联之间形成的某种图示。
北宋后期,在都城开封,孔雀明王深受人们尊崇。
尉氏县(南去城九十里云々)兴国寺□孟禅院主宝乘和尚与照大师来坐。赐紫人也。照大师云。常念法花经、孔雀瑜伽教、十大明王真言人也云々。礼拜法花坛即买芍药花十二枚供养坛上。
花并叶似牡丹色赤。大乐金刚经七卷看了。要枢经也。①延久五年(1073年)五月二十三日,尉氏县兴国寺□孟禅院的僧侣宝乘和尚造访滞留于太平兴国寺传法院的日僧成寻,这位宝乘和尚是常念 “法华经、孔雀瑜伽教、十大明王真言”之人增记隆介先生认为此“孔雀瑜伽教”“非唐代所见,为北宋时期新译”,依据他的研究,“在开封,存在以 《法华经》为代表的显教信仰以及以孔雀明王相关经典为代表的密教信仰。另外,皇帝周围也有与此相关的造像”。这种环境应是三面六臂孔雀明王像(仁和寺藏)诞生的背景。就是说,由于北宋时期新的《孔雀经》信仰盛行,因此与一面四臂相异的孔雀明王像也就出现了。
即便如此,敦煌的一面六臂孔雀明王像比成寻的记录还是早了约 100年。有可能是在北宋后期,密教经由西域和敦煌传入中原,然而反过来由中原传入敦煌的可能性不大。
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后唐,不空译《大孔雀明王经》广泛盛行,恒安在 《续贞元释教录》(945—946年成书)中记载,有人将其部分内容广为传播。
大孔雀明王经三卷(已广流行见转读者)五十纸佛说大孔雀明王画像坛场仪轨一卷四纸与②敦煌开始出现一面四臂孔雀明王像之时,中原的孔雀明王信仰盛行, 修法方式从单纯的陀罗尼读诵发展到多样化。此修法主要依据的经典,是唐代不空译《孔雀经》和不空译《仪轨》。
几乎与此同时,成都大圣慈寺与善院,唐末画家张南本所绘“孔雀王变相”,与“大悲菩萨(千手观音)”和“八大明王”同时存在③。之后,淳熙四年(1177年)成书的范成大著《成都古寺名笔记》,只记载了兴善院田内壁画的八明王,没有提到孔雀明王。唐末至五代十国时期存在于成都的孔雀明王像,虽然图像尚不确定,大概不是基于汉译经典的一面四臂造型吧。
归义军节度使曹氏统治之下的敦煌,孔雀明王信仰在短短的100年间经历了从兴盛到衰亡的过程。图像虽有四臂、二臂、六臂之变化,但也能看到将唐代汉译密教经典作为理想的倾向。造成图像变迁的原因,来自北宋中原密教影响的可能性不大。当然,孔雀明王被信仰的根源,在印度密教初期是出于不受毒蛇侵袭的朴素愿望,这也很难适用于敦煌。然而,从图像看敦煌的孔雀明王,能够唤起人们对于印度密教的记忆,同时又有新图像的刺激,这种多层次、多角度的相互作用至少是存在的。
在今后的研究中,关于敦煌的密教美术和其制作目的、曹氏以及与曹氏有姻亲关系的西域诸民族对其有何影响,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深人考察。
附记:本篇论文为“财团法人松下幸之助纪念财团2010年度赞助研究”的一部分研究成果。笔者赴敦煌进行实地考察时,受到樊锦诗院长、刘永增所长、沙武田研究员等人的热情接待。在调查过程中,王友奎先生向笔者提出了宝贵建议。笔者在“2010敦煌论坛:吐蕃时期敦煌石窟艺术研究国际研讨会”的发言,受到金泽大学大学院人间社会环境研究科2010 年度“文化资源学领域.培育人才项目”与兵库县立历史博物馆的支持。本论文的中文翻译者为故宫博物院宫廷部张雅静。特此表示感谢!另夕卜,文中所附画图均为笔者所绘。
(翻译:张雅静)
河西地区即使在吐蕃统治结束之后,用藏文写成的公牍也不在少数②。 因此,与中原不同,敦煌很可能通过吐蕃或西域,有选择地接受了印度佛教。其次,虽说归义军节度使张氏曾控制整个西域地区,但到了经过内乱之后的曹氏时代,其所控制的领域只限于沙州、瓜州等地。从敦煌向西,龟兹、伯孜克里克、高昌为西州回鹘所统治。敦煌以东,甘州为甘州回鹘所辖,西凉府(凉州)由吐蕃支配。为了稳妥地促进贸易往来,曹氏必然要与各少数民族政权保持良好的关系③。关于曹氏的出身,有人认为他并非汉族,而是粟特人④。敦煌特异的孔雀明王图像,也正反映了少数民族与地方豪族在相互影响和关联之间形成的某种图示。
北宋后期,在都城开封,孔雀明王深受人们尊崇。
尉氏县(南去城九十里云々)兴国寺□孟禅院主宝乘和尚与照大师来坐。赐紫人也。照大师云。常念法花经、孔雀瑜伽教、十大明王真言人也云々。礼拜法花坛即买芍药花十二枚供养坛上。
花并叶似牡丹色赤。大乐金刚经七卷看了。要枢经也。①延久五年(1073年)五月二十三日,尉氏县兴国寺□孟禅院的僧侣宝乘和尚造访滞留于太平兴国寺传法院的日僧成寻,这位宝乘和尚是常念 “法华经、孔雀瑜伽教、十大明王真言”之人增记隆介先生认为此“孔雀瑜伽教”“非唐代所见,为北宋时期新译”,依据他的研究,“在开封,存在以 《法华经》为代表的显教信仰以及以孔雀明王相关经典为代表的密教信仰。另外,皇帝周围也有与此相关的造像”。这种环境应是三面六臂孔雀明王像(仁和寺藏)诞生的背景。就是说,由于北宋时期新的《孔雀经》信仰盛行,因此与一面四臂相异的孔雀明王像也就出现了。
即便如此,敦煌的一面六臂孔雀明王像比成寻的记录还是早了约 100年。有可能是在北宋后期,密教经由西域和敦煌传入中原,然而反过来由中原传入敦煌的可能性不大。
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后唐,不空译《大孔雀明王经》广泛盛行,恒安在 《续贞元释教录》(945—946年成书)中记载,有人将其部分内容广为传播。
大孔雀明王经三卷(已广流行见转读者)五十纸佛说大孔雀明王画像坛场仪轨一卷四纸与②敦煌开始出现一面四臂孔雀明王像之时,中原的孔雀明王信仰盛行, 修法方式从单纯的陀罗尼读诵发展到多样化。此修法主要依据的经典,是唐代不空译《孔雀经》和不空译《仪轨》。
几乎与此同时,成都大圣慈寺与善院,唐末画家张南本所绘“孔雀王变相”,与“大悲菩萨(千手观音)”和“八大明王”同时存在③。之后,淳熙四年(1177年)成书的范成大著《成都古寺名笔记》,只记载了兴善院田内壁画的八明王,没有提到孔雀明王。唐末至五代十国时期存在于成都的孔雀明王像,虽然图像尚不确定,大概不是基于汉译经典的一面四臂造型吧。
归义军节度使曹氏统治之下的敦煌,孔雀明王信仰在短短的100年间经历了从兴盛到衰亡的过程。图像虽有四臂、二臂、六臂之变化,但也能看到将唐代汉译密教经典作为理想的倾向。造成图像变迁的原因,来自北宋中原密教影响的可能性不大。当然,孔雀明王被信仰的根源,在印度密教初期是出于不受毒蛇侵袭的朴素愿望,这也很难适用于敦煌。然而,从图像看敦煌的孔雀明王,能够唤起人们对于印度密教的记忆,同时又有新图像的刺激,这种多层次、多角度的相互作用至少是存在的。
在今后的研究中,关于敦煌的密教美术和其制作目的、曹氏以及与曹氏有姻亲关系的西域诸民族对其有何影响,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深人考察。
附记:本篇论文为“财团法人松下幸之助纪念财团2010年度赞助研究”的一部分研究成果。笔者赴敦煌进行实地考察时,受到樊锦诗院长、刘永增所长、沙武田研究员等人的热情接待。在调查过程中,王友奎先生向笔者提出了宝贵建议。笔者在“2010敦煌论坛:吐蕃时期敦煌石窟艺术研究国际研讨会”的发言,受到金泽大学大学院人间社会环境研究科2010 年度“文化资源学领域.培育人才项目”与兵库县立历史博物馆的支持。本论文的中文翻译者为故宫博物院宫廷部张雅静。特此表示感谢!另夕卜,文中所附画图均为笔者所绘。
(翻译:张雅静)
附注
② 坂尻彰宏《帰義軍時代のチべット文牧畜関係文書》,《史学雑誌》第111号,2002年 11月;武内绍人《敦煌•トルキスタン出土チベット語手紙文書の研究序説》,◊チべ ットの仏教と社会》,春秋社,1986年。
③ 段文杰(唐代後期の莫高窟芸術),《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4),平凡社,1982年。
④ 郑炳林《唐五代敦煌粟特人与归义军政权》,《敦煌研究》1996年第4期。
① 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第七》"延久五年三月二十三日条平林文雄《参天台五台山记•校本並に研究》,风间书房,1978年。
② 《大正藏》第55册,第1050页中至第1051页下。
③ 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卷二,1004年成书;王卫明《五代における西蜀寺観壁画に関 する_考察一成都大聖慈寺の絵画史料をめぐつて-》,(京都橘女子大学研究纪要》 第26号,1999年3月。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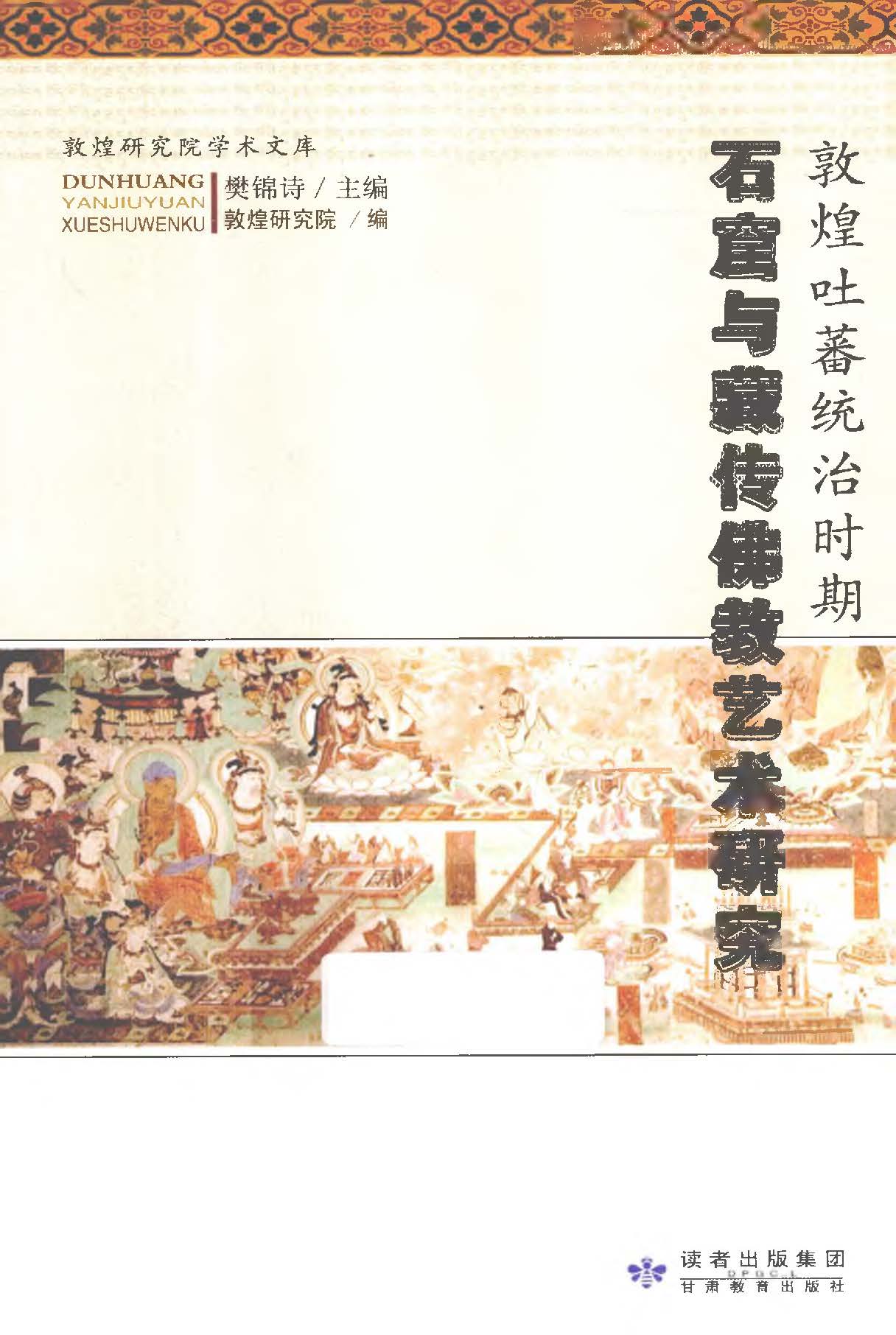
《敦煌吐蕃统治时期石窟与藏传佛教艺术研究》
出版者:甘肃教育出版社
出版地:2012.4
本书内容涉及对敦煌吐蕃石窟艺术样式的研究、社会政治背景探讨、造像思想研究、吐蕃密教文献研究、石窟经变画与图像专题研究、密教尊像研究、西藏考古与艺术研究、毗沙门天王像研究、莫高窟第465窟研究等多个领域。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