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嬗变
| 内容出处: | 《海南历史文化.特辑》 图书 |
| 唯一号: | 200120020230004812 |
| 颗粒名称: | 文化嬗变 |
| 分类号: | G127.66 |
| 页数: | 64 |
| 页码: | 61-124 |
| 摘要: | 本篇记述了海南省文化嬗变的情况,包含了海南岛文化根性的若干思考、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市场经济转化与产业化重构等。 |
| 关键词: | 海南 文化 研究 |
内容
关于海南岛文化根性的若干思考(一)
闫广林
一
从文化学的角度考察,世界上的岛屿大致有三类。除了至今仍散落在太平洋上的诸多具有原始部落和原始宗教意义的岛屿外,还有两类岛屿因为与大陆文化的关系而尤其值得关注。其一是被异化的岛屿,其二是被同化的岛屿。
克里特岛作为被异化的岛屿的典范,隶属于爱琴海文化。爱琴海上岛屿众多,其中最大的是克里特岛。克里特岛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出现了青铜文化,公元前2000年就出现了奴隶制国家,拥有丰富的文化成果,并对爱琴海周围诸岛特别是希腊半岛的文化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包括米诺斯王朝那雄伟的宫殿和卡马雷斯那精美的陶器,还有象形文字及其简化而成的以线条表示轮廓的线形文字。史称“克里特文化”或“米诺斯文化”。但是,在公元前15世纪,希腊人利用火山爆发后对克里特岛的破坏性影响,以战争和贸易的手段入侵克里特,并与当地原住民渐渐融合成新的文化形态。于是,在这征服与被征服的过程中,爱琴海文化的中心便转移到希腊本土的迈锡尼地区,而克里特文化在不自觉地转换成了对西方文化有重要意义的古希腊文化后,则逐渐为世人所遗忘。只是近代以来经过古发掘才重新为人们所认识:这个旅游胜地原来是西方文明的根!
克里特文化或米诺斯文化的历史命运,从另一角度说明:在航海业很发达的古代社会中,岛民居住的环境被海洋包围,生活空间受到很大限,只能以封闭的岛屿内陆为生活天地。不仅与外界缺乏交流,无法向大延伸,而且缺乏内在竞争,生产力水平很不发达,创造财富的能力极其限,社会文明的水平也难以持续,与大陆文化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从更般的意义上来看,岛屿文化并不具备进步发展的内在机制。诚如文化地学家葛绥成所说:“人类幼稚时代,只在岛上半岛上或海岸地方,发展化:及人智发达,大陆方面,亦渐为文化所进展……然而岛屿方面,人与自然,或人类与人类之间,少有大陆中那样的生存竞争,所以人类的达,就不免受阻碍。不过一旦从其他陆地比较发达的民族移至岛屿,或大陆方面输入种种文化,而使之发达时,那岛屿的文化,便得产生。”岛屿如不受大陆的何种刺激,而自己能开拓文化的,却未之前闻。如英、日本,虽说开拓了岛屿文化,其他所有的文化,还是由大陆输入而。英国、日本,在地形上从前为大陆的一部分,故有陆岛之称”①。故有化型岛屿的普遍存在。的确,在新历史观的概念中,没有任何一个原生岛屿国家,能够独立进化出一种高端文化,并因此“蛮荒”而不遭受诉乃至摧毁。例如日本,据《后汉书》记载,东汉光武帝刘秀年间就有又委倭王”事,日本从这时就开始正式接受汉帝国封号倭王,成为中国附属国。另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岁时来献见云。”倭字本意是丑陋的、矮小的、琐碎的意思。一个“倭”,体现了大陆文化与岛屿文化的尊卑地位及其独尊中原、鄙夷四裔的文意义。再如英国。在罗马化时期的不列颠诸岛,先住民凯尔特人是“低的”,凯尔特语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来自罗马帝国的拉丁语成了列颠的主要语言。条顿化时期,凯尔特人的地位更是每况愈下,只能逃山野树林寻求生存,结果导致土著语言凯尔特语随着凯尔特人的消亡而亡了。
其文化都根基于大陆文化的英国和日本,都是同化型的岛屿国家。历史地来看,这些岛屿文化的诞生,多以大陆军事力量的征服开始。罗马人和条顿人渡海征服不列颠群岛,大和民族征服本洲岛民(大和民族并非日本土著部落,而是从海峡过来的战争逃亡者和政治流亡者)①,均为此例。但征服者征服后便会发现,只靠军事手段无法实现征服的目的,所以随着军事优势的确认,大陆的世俗生活和价值观便开始殖民化到新领地亦即岛的文化中,并不得不从现实的角度来对土著文化和自身文化进行反思,进而形成新的岛屿文化,创造出了适合新的生存环境的文明体系。英国的既与罗马教廷保持相对独立性,又与之相承相袭的宗教革命,以及日本的神道教、情教和佛教三位一体、相互并存的意识形态,均属此类。所不同的是,由于中华文明的中和特质,加之当时移民人口有限且武备不足,这些为日本岛屿带去了冶铁、农耕、医药、纺织、养蚕、建筑等谋生方式的大陆秦汉移民,不可能像罗马帝国军队踏上不列颠群岛那样残酷杀戮先住民,到岛屿上当主宰话语权力的主人,而只能基于仁政传统,采取战国“割地自保,不争王霸”的生存方略,与原住民和平共处地生存。于是,在中国文字的基础上产生了日本文字,在中国“吴服”影响中产生了日本和服,在中国饮食的同化作用下产生了日本料理。所以日本19世纪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第九章“日本文明的来源”中说:“把我国人民从野蛮世界中拯救出来,这不能不归功于佛教和儒学。尤其是近世以来儒学逐渐昌盛,排除了世俗神佛的荒谬之说,扫除了人们的迷信,其功绩的确很大。”②“如果过去我国没有儒学,也不可能有今天”③。因此,如果说大陆文化来源于各种文化的碰撞与妥协,那么,同化型的岛屿文化则来源于大陆优秀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征服与同化。只是到了科学技术使大航海成为一种可能,岛国经济以及岛国军事的独立才得以真正出现,脱离母体的岛屿文化才成为现实,甚至强大的大陆文化也只能望洋兴叹(如率先发起工业革命的不列颠之于保守顽固的欧洲大陆)。在此之前,岛屿文化难以在狭小、封闭的环境中以普遍的社会形式成熟起来,他们的文化不仅来源于大陆,而且他们若不继续从距离最近又较为发达的大陆文明中汲取养分,其文化的根基必然无法成长。
起源于一种普遍的事实,在这普遍的事实中,海南岛文化,显然属于普遍的同化型的岛屿文化,而不是个别的异化型的岛屿文化。有研究表明,如今广西南部的勾漏山,在远古时期直延伸到海南岛五指山;如今海南岛北部和广东的雷州半岛南部还分布有同样的玄武岩层:以前海南原始居民落笔洞人的牙齿,与河南(仰韶文化)、甘肃新石器时代人以及云南现代人的差别不大,不排除人类从大陆迁入海南岛的可能性。由此可见,海南岛是一个古老而典型的“大陆型岛屿”①。这种岛屿文明的性质,使得大陆人口的移入历史相当久远和持续。具言之,早在7000~3000年前,南方“骆越人”(百越族之一)便陆续移入海南岛,成为海南岛的先住民——黎族的祖先。并且早从秦始皇时期开始,至少由于三方面的原因,大陆中原文化便侵入和浸入海南文化之中,逐渐取黎族文化而代之,成为海南文化体系的主体。首先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的政治需要。在这种需要下,秦始皇统一岭南,设南海、桂林、象郡,海南岛属象郡边缘;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伏波将军路博德和楼船将军杨仆平服南越后,在海南岛设立珠崖、儋耳两郡,隶属交趾(越南)部刺史;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九年(43年),伏波将军马援平定交趾,往来南海,抚定珠崖,调立城郭。如此等等,直至隋文帝开皇十一年(591年),冼夫人招慰诸俚僚,十余州归附大陆政权,海南岛才结束了整体性的军事冲突和完成了行政建制,政治的同化才告完成。其次是大陆移民的必然结果。从汉代辟郡建制到隋代设县并邑之间,海南即有大陆人群移入。到了唐宋之际,随着航海业的发达,福建、广东的商人开始落籍海南。尤其是中原大陆战争频繁,导致大陆北方人群南迁,而闽、粤、桂诸地区的大批南方人群则继续南迁至海南岛,海南移民开始形成规模,并到明清二代,达到高潮。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移居海南的大陆人,唐以前仅有2万多人,唐代增至7万多人,南宋时增至10万多人,元代已达17万多人,明代高达50万人,清代中叶增加到217万人。其中,闽人150多万,中原人40多万,客家人20多万,而作为先住民的黎人,仅有20多万人。这种现在在海南人的姓氏中依然可觅其踪的移民运动,为海南岛形成同化型的岛屿文化,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最后是贬官文化的必然结果。唐宋时期,大陆中央政权派系斗争激烈,被称为“蛮荒之域”和“瘴疠之区”的海南成为流放贬谪官员的地方。人数之多(唐朝70余人,宋朝80余人)、职位之高(侍郎、尚书以上的高级官员达50余人)、影响之广、对贬地文化贡献之大,乃全国之最,并为世界文化史罕见。尤其重要的是,这些“独上高楼望帝京”的贬官们,均为中华封建帝国的政治文化精英,他们流贬到海南岛后,或寄情山水,或著文销愤,或开办学堂、教书课徒……因而也就成了大陆文化的自觉的传播者,在用先进的文化同化海南岛文化方面,居功至伟。其中的杰出代表当属苏东坡。苏东坡在贬谪中和镇的三年间,开辟儋州学府,自编讲义,自讲诗书,不遗余力地推行文化教育,培养了大批如姜唐佐、王宵、黎子云等饱学之士,益及全岛,大陆文化日兴,儒道精神日盛。这些精英,为海南岛文化体系创建了重要的主流话语。
如此一来,经过军事征服、人口移入和官员流贬,到了明清之际,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中华大陆文化已在政治体制、社会基础、核心价值观诸方面,基本完成了对海南岛文化的彻底同化,以及海南文化体系的创建。其同化的力度之大、程度之深、强度之固,非其他同化型岛屿所能比。
二
海南岛是个在政治体制、社会基础和核心价值观诸多方面被中华大陆文明深深同化的岛屿。和其他同化型岛屿所遭受的命运一样,在此过程中,海南岛也曾发生过黎族先住民的顽强抵抗。早在汉代,黎族就曾反抗官府强征“广幅布”而攻破郡城,杀死珠崖太守孙幸。而此后的黎汉冲突一直都时有时无,未能终止。即使海南文化兴盛时期的明代和海南文化普及时期的清代,亦复如此。但总体来看,深受大陆农业文明和儒家文化所熏陶的历代统治者,从隋明冼夫人奉众“归附”以后,一直在探讨平黎治黎的问题,并且尽力避免使用武力最终选择了以抚定为主,以讨平为辅的“文治”路线。他们或厚赏赐官;或诰令世袭,世为峒首;或设立社学、延聘教师;或实行“土官、土舍”制度,授以黎族统首各种自治权力。更有清代制定了“抚黎”章程《十二条》,提出了“据其心腹,通其险阻,令其向化”的治黎方针,在统治方法上不断进行改进,所以同化得比较温和,王化得比较彻底。除此之外,明清政府也加大了海南的投资开发力度,架设了一些桥梁,修了一些道路,完成了一些基础建设,遂使海南岛的土地开发、农业种植、工矿企业和对外贸易全面发展,黎汉关系明显改善,黎人汉化明显加强。甚至一些地方,黎族已基本融入汉族,出现了文化交流和联姻通婚,以及“无黎”之说(如“文昌无黎”)。也有一些汉人,“因近黎土,谙晓黎俗”、“利其山水田地,创为村峒,落土藉田”,逐渐同化于黎族之中。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明清二代的海南岛文化,全面吸收了中华大陆文明,形成了“海外衣冠胜事”,出现了一批杰出的文化学者。其中,尤以书院和科举考试为最。
海南的书院始之于宋代文豪苏东坡。明清时期,在东坡书院的基础上,海南书院蔚然兴起,达六十余所,以尚友书院、蔚文书院、琼台书院、溪北书院著名,云集了众多名儒、学者,其特殊的教育方式和优雅的书院建筑,对当时海南的教育以及文化均有重要影响,使海南进入了人才辈出的时代。据文献记载,海南从宋代开始参与中华帝国的科举考试,到明清两朝,不断涌现举人或进士。其中,宋代有举人13人,进士12人;明代则有举人595人,进士62人,文渊阁大学士1人,达到高峰;清代有举人157人,进士22人,虽逊于明代,但产生了当朝探花张岳崧,并得到了皇帝的手谕——“何地无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文化传播过程,并不是岛屿文化对大陆文化的被动接受,而是一种主动吸收及精神向往。所以,其间不仅有普遍的民间响应,还有特别的精英推动,还发生了明代名臣王弘诲“奏考回琼”的故事。由于海南岛孤悬海外,距中原和京师都非常遥远,所以每当科举大考时,主考官惧怕凶险,很少到琼督考,只是驻节雷州,行文调考。海岛学子不得不长途跋涉,劈波斩浪,冒险前去赴考,死伤颇多,以致发生了嘉靖三十六年一次覆没数百人的惨案。基于此,深感“天下儒生之远而苦者,未有如琼之甚者也”的王弘诲,便上奏疏请在海南岛增设考场,由琼州兵备道台兼提学考官,并且获得诏准。其推动海南岛屿文化靠拢大陆主流文化的“形而上”之心,跃然而出。
其实,海南岛民,或者说移居到海南岛的大陆人以及受其同化的先住民,他们向往和吸收中原文化的现象,不仅仅体现在书院和科举考试方
面,而且还发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大陆中原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宗法性,而宗法性又发展为对祖先世系的记载和认知,即来源于“孔氏家谱”的叙谱传统。这种海洋文明中较为罕见而且带有传宗接代意义的叙谱传统,在海南由来已久,而且十分普遍。遍布海南的宗庙祠堂,尤其是那些显然与妈祖庙不同的祠堂,充分说明了海南岛文化体系中大陆文化因子的影响。还有海南民居,海南传统主流民居不仅与北京主次分明、方正对称的四合院非常相似,而且堂屋比其他房屋宽敞高大,在院落中显得特别突出,堂屋中供奉着祖宗神位,是家族礼制的中心。过年过节,婚丧大典或生辰忌日时,家庭成员都会在这里设条行礼,出嫁的女儿回娘家也要在这里拜见父母,鲜明地体现了大陆中原文化循规蹈矩、祖先认同、家长权威的特点。
所有这些现象都足以说明,海南岛作为一个被大陆文化同化的岛屿,始终对其文化的母体持以吸收传承的态度。
三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曾区分过三种不同的地理环境,一是干燥的高地和高地上的广阔草原和平原;二是巨大河流所经过的平原流域;三是处在与海直接相连的沿海地区。第一种地区盛行畜牧业,第二种地区盛行农业,第三种地区则盛行商业。黑格尔说,海洋和河流使人们接近,山岳使人们分离,但“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补充说:“不过海洋使人们接近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到较高的阶段上;而在生产力较低的阶段……海洋却大大阻碍了被它所隔离开来的各个部落间的关系。”①直到生产力发展水平达到可以制造出安全可靠的海上交通工具以前,海洋一直是使人类分割封闭的因素。只有当可以保证较为安全地在海上航行的轮船出现之后,欧洲才打破了氏族血缘集团以及封建主的有效控制,形成平等自由的观念和民主政体;海洋才不再使各民族分割成或大或小的生活单元,居住在地中海地带的各民族之间才得以有了更为频繁的交往,并促进了国际贸易以及资本主义的发展,才出现了反对封建专制的资产阶级革命及其民主政治的代表——英国。作为一个岛屿国家,英国近代崛起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而其中与时俱进的宪政体制(三权分立)的形成与完善,无疑是最重要的结构性和制度性支撑。近代英国正是借此而引领时代潮流,先消灭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又打败了“海上马车夫”荷兰,并在工业革命中迅速成为欧洲强国的。因此,如果说农业文化创造了专制国家,那么,近代英国岛的文化,拥有一个包括海南岛在内的所有东方岛屿文化所普遍缺乏的体制性特点,即由开放而非封闭、不确定而非确定、多元而非大统的海洋所产生的自由平等意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民主制度—宪政精神、法律制度—契约精神、私有财产制度一个人主义精神。这与自给自足,重农轻商、讲求宗法约束之下的海南岛文化,大异其趣。
但是近代英国与西方的海洋文化,尤其与古代地中海的岛屿或半岛文化之间还存在另一种历史关系。古代地中海的这些小岛和半岛,山地丘陵较多,土地也较贫瘠,适合种植葡萄树和橄榄树之类的经济作物,但不适合进行大规模的粮食作物的栽培,这意味着它不可能为文明的发育提供足够的内部资源,只有从战争和贸易中获取必需的外部资源,并建立相应的商业文化。于是,古代地中海海洋文明便在航海和贸易中早就形成了一种思维模式,只要通过武力扩张,建立海外殖民地,控制地中海沿岸,就能攫取大量财富,实现强国梦想。古希腊之于特洛伊战争,古罗马之于埃及征伐,均为此例。延续这种海洋文化的传统,不列颠岛屿文化便具有了突出的扩张主义、重商主义和物质享受主义的色彩。具言之,大不列颠岛系由诸多岛屿构成,隔海峡与欧洲大陆相望,是一个领土面积狭小的岛国。在古代历史中,地中海的罗马帝国扩张入侵过这里,欧洲大陆的条顿人扩张征服过这里,北欧“蛮夷部落”维京海盗也肆虐骚扰过这里,导致从欧洲早期移居而来的先住民凯尔特人,一个个消亡在山野丛林之中。而且,取凯尔特人而代之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在近代全球化的过程中,随着圈地运动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达与本岛资源的衰竭,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后先进的政治制度的形成,随着航海浪潮中强大的海军的创建,以及宗教改革后英国清教徒强烈的个人奋斗进取精神的张扬,又秉承着这种扩张精神,开始成立殖民公司,甚至展开殖民战争,向殖民地倾销商品,同时掠夺殖民地的廉价原料,到海外进行不平等的贸易,获得了财富的流入,获得了原料和工业品市场,一举成为著名的“日不落帝国”。由此可见,领先于欧洲近代化进程的英国岛的文化,是通过征服与开拓殖民地来实现其重商主义的。而之所以必然如此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资源的贫乏短缺。
与海洋性质的岛屿文化不同,海南岛文化显然更具有农业文化的性质。而能够如此的原因之一,也在于海南岛资源极为丰富,人口却不众多,发展空间巨大,并无地中海诸岛以及“圈地运动”后英国那种因为空间狭小或资源紧缺所产生的社会压力,或者说,没有扩张主义和重商主义基础。首先,海南岛有1830公里的海岸线,近海物产极为丰富,完全能够靠海吃海,靠水吃水;其次,岛上又有大片的热带雨林,生长着各种植物4200多种,包括椰子、胡椒、槟榔、腰果、沉香、香茅、剑麻等稀有特产,以及花梨、母生、子京、坡垒、苦梓、红椤等珍贵木材,完全能够立足本岛,靠山吃山;再次,海南岛全境34000平方公里,其中有大量的土地尚待开发,土地潜力很大,根本无须对外扩张。而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唐宋之际的海南人口不过10多万,清代中叶的人口仅仅200多万!总之,无论在移民潮之初,还是在移民潮之末,海南都是一个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的社会,是一个完全可以走农业开发道路的岛屿。事实也是如此,到了宋代,随着汉人增多、文化开化、航海发达,以槟榔、吉贝(棉布)和香料等农产品为主的海外贸易在海南甚为兴盛,其贸易对象是以广州、泉州、福州为主的大陆,兼有马来半岛。而到了明清时期,在大陆农业文明和农业技术的影响下,海南岛的开发更直接地体现在农业生产方面。或者说,海南岛作为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已臻于成熟,形成了大陆性质而非海洋性质的岛屿文化体系。
西方岛屿文化的海洋观,从其海神形象中可见一斑。在古希腊的神话体系中,脾气暴躁而贪婪成性的波塞冬是众神之王宙斯的哥哥,他与宙斯一同战胜了父亲克洛斯之后,一同分割世界,负责掌管海洋,以三叉戟主宰水域,在水上拥有无上的权威,能动摇大地,能呼唤或平息暴风雨,能轻易地令任何船只粉碎。但象征着他的圣兽海豚则又显示出海的宁静和波塞冬亲切的神性。更重要的是,波塞冬不仅神性广泛,而且野心勃勃,常与诸神交战,不满足于他所拥有的权力,具有强烈的侵略性和极大的野心。他密谋夺取宙斯天帝的宝座,但被宙斯发觉,放逐到地上受刑,帮助劳梅顿王修建特洛伊城。力量和权力以及在此基础上诞生的冒险和争霸意
识,是西方海神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唯其如此,爱琴海附近的希腊海员和渔民对他极为崇拜。他们认为,海洋的自然力非常强大,这个自然力中必有一种更强大并能够使其左右的力量,这个力量的化身就是令人崇敬的波塞冬。诚如研究者所说:“波塞冬是海洋的强者,他可以给人类制造种种灾难。从东方人的观点看,波塞冬是个恶神,但古代希腊人重视的不是善恶之辨,而是力量的比较。”①
与此不同,在以岛屿内陆为生活生产环境的海南黎族的宗教信仰中,有山神、地神、灶神、雷公神,就是没有海神;有植物崇拜、动物崇拜,就是没有海洋崇拜;有婚姻禁忌、丧葬禁忌、生育禁忌、做鬼禁忌,但却鲜有海洋禁忌。说明黎族虽然居住在海岛之上,却是一个农业民族。而在海南后来的移民文化中,虽有与海洋相关的宗教信仰,但与西方的海神精神相去甚远。其中的原因之一在于,作为其来源的中国大陆的海洋观相当保守,且具有农业文化的性质。在古代中国人看来,海洋是一个充满黑暗和恐怖的地方。“海”这个字“从水从晦”。晦便是晦暗,便是“晦昏无所睹”,即不可知。这与古代海神传说相辅相成。中国最早的四海海神包括东海海神禺虢、南海海神不廷胡余、西海海神弇兹、北海海神禺疆。他们都是珥两蛇,践两蛇,甚至人面鸟身,与蛇图腾密切相关。随着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四海龙王信仰渐取蛇图腾而代之,其神形成了大鱼或蛟龙。又由于佛教的传入,以及佛经中描述的西天来的兴云布雨、令诸众生、热恼消灭、“无边法力”的特点,无量诸大龙王自然同中国原有的龙蛇形早期海神相融合,名正言顺地取代了原始海神,享用渔民舟子的香火。从此以后,中国东西南北四海全部由四海龙王接管,其成为海中之王,水族统帅和海洋世界的最高统治者。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陆的民间传说中,人格化了的龙王既有为民造福的形象,也有与民为害的事迹。神话小说《封神榜》《西游记》,戏曲杂剧《柳毅传书》《张羽煮海》中,都有善恶不同的龙王出现。尤其是《西游记》中面对孙悟空时战战兢兢地献上金箍棒、黄金甲的龙王,更是几近于小丑。但其原型——不同于大陆龙王传说的海南海龙王则是一位护佑平安、拯救灾难的正神。说明海南先民对潮起潮落、碧波万顷以及水患无穷的南海,不能做出解释,还不具备认识海洋和征服海洋的能力,他们只能抱着一种敬畏的心理来看待海洋,祭祀海神,祈求海神。于是具有“广徕天下财利”和“广利生民”之意的南海广利王,在海南的民间便演变成海龙王和海龙王庙,成为民间崇拜对象。
更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海龙王之外,海南还从大陆引进并创造了一系列女性海神,首先就是著名的妈祖。妈祖的神形像东海女神观世音一样,慈眉善目,和蔼可亲,但又与东海女神观世音有所不同。作为东海女神,观世音是由佛教中的菩萨转化而来,妈祖则是由人死后的魂灵转化而来。妈祖姓林名默,福建莆田人。相传妈祖性情和顺,热心助人,洞晓天文气象,能够“预知休咎事”,有“神女”“龙女”之称。她羽化成仙后,传说身着红装飞翔在海上,每当风高浪险时,“涛雨济民”“挂席泛槎”“化草救商”“降伏二神”“圣泉救疫”,等等,屡屡显灵,被尊为“妈祖”,被宋元明清历代帝王先后封为“顺济夫人”“灵惠夫人”“天妃”“天后”“天上圣母”等,是历代船工、海员、旅客、商人和渔民共同信奉的神祗,影响遍及包括海南在内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妈祖崇拜在海南相当悠久。宋元之际,大量移入海南的福建船民,先是在船上设神主牌位香案各自祭拜,后来在岸上分区位集中祭拜并形成“天后庙”或“天妃庙”。据日本学者小叶田淳《海南岛史》记载,元代的海南岛即建有“天后庙”,而且发展很快。据考证,整个元代,海南岛的妈祖庙仅有5座,明清两代却增加了42座,遍布琼州府的13个州县;数量最多的是文昌县,达11座之多,其次是万宁,有7座①。海南妈祖崇拜之盛,可见一斑。属于这类女性海神的还有来自大陆佛教的观世音菩萨,来自海南本土的水尾圣娘、泰华仙妃和三江晶信夫人,等等。这些女性海神之所以能够与男性的海龙王并驾齐驱甚至备受海南岛民崇拜,在于她们个个慈眉善目,不像海龙王那样怪异狰狞,具有东方的古典美;也在于她们温和慈祥,大慈大悲,乐于拯救苦难,救渔夫于狂风巨浪之中,救岛民于生老病死之中。而且无处不在,有求必应,一呼即灵。体现着男性海神所缺乏的关怀和关爱,更为一般渔夫舟子所接受和膜拜。
总而言之,虽然海南和西方宗教中都有海神崇拜,但性质大不相同。西方海神波塞冬体现了征服、冲突的海洋文化精神,其中那充满紧张对立关系的力量与权力,吸引着人们在精神层面上信仰崇拜;而海南的“海龙王”和“妈祖”,作为正神和善神,他们体现的都是天人合一的大陆农业文化精神,其中那正义与善良,吸引人们在实践层面上祈求乃至迷信,以对付不可知的“恶”。这再次说明,海南和中国沿海地区一样,虽然有着漫长的海岸线,靠海、吃海、用海、观海,海洋文化历史悠久且内涵丰富,但受到黄河文化的深刻制约,有着明显的农业性质。如果把英国式的岛屿文化称为竞争、扩张性质的海洋商业文化,那么海南岛文化则可称为服从、保守性质的海洋农业文化。
综上比较,海南岛作为一个被中华大陆农业文化所持续而深刻同化的岛屿,其文化中既不存在去大陆化的倾向,也不存在扩张主义的传统;既没有东方岛屿文化的狭隘性,也没有西方岛屿文化的冲突性;既缺乏大河文化的宏大性(所以海南古代文学中少有重大题材的叙事文学),也缺乏海洋文化的民主性(因为在海南古代生活中更具话语霸权的不是制度而是宗法),具有自己独立而特殊的文化根性。这种根性,属于非常值得研究的“蓝色的农业文化”。①
关于海南岛文化根性的若干思考(二)
闫广林
一
从社会根性的视角来看,海南是一种多元的历史组合,黎、汉、苗、回四个民族,不同时期先后移居海南并形成了海南社会的基本结构。而从文化根性的视角来看,海南文化形成则更为复杂。这是因为:除极少数富裕的长老能够用金钱或牛马向汉族、黎族地主换得少量土地作为私有产业外,大部分苗人基本上都是租种汉族、黎族地主的山岭。苗族是一个没有文字、没有土地的佃种与游耕民族。而作为一个人数同样不多、居住又分散的族群,海南回族一直群体聚居,自然形成村落,使用自己的语言,拥有自己的宗教,属于一个迄今仍然未被同化的民族。所以,苗族文化和回族文化对于海南文化根性的形成,未能产生主体作用。对海南文化根性产生主体作用的,是先住民的黎族文化、后来者大陆文化尤其是闽南文化,以及给海南带来佛教和基督教信仰的外来文化。但海南文化与这些构成元素又有所不同。
首先是黎族文化。虽然早在宋代就有“熟黎”之说,而到了明代,在靠近汉族的黎族地区的汉化已很普遍,虽然黎族诚实守信、勤劳俭朴、敬老爱幼、团结互助、热情好客的传统,对海南文化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其深山丛林的生活环境,船型屋的居住方式,“峒”的社会组织,“合亩制”的生产方式,黎锦、文身、树皮布和盘条制陶等工艺形式,鼻箫、山歌等艺术形式,以及节日、出生、结婚、死亡、生病等仪式规则,还有100多种的一系列与鬼文化相关的禁忌辟邪法术,以及“道公”“娘母”习俗,并没有在海南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被海南社会所普遍接受,而成为地方性知识的主体。个中原因,应与地理环境导致的文化封闭有关。诚如学者司徒尚纪分析:“至岛内部,山高林密,瘴疠袭人,为少数民族所居,汉人难以进入,多数地区来往稀少,处于分割、阻绝状态。如‘秦以水德王,其数用六。今琼人行使铜钱,犹用六数,以六文为一钱,六十文为一两,六百文为一贯。又田禾以六把为半担,十二把为一担,亦用六数,皆秦旧俗也’。黎族至今传统计算方法仍然如此。鸡卜、钻木取火、文身、不落夫家、夜寮以及古越族一些自然、神灵崇拜等习俗,在大陆上已经消失或残存,但在海南却长期传承,显示海南文化少受外来文化因素冲击,一旦形成或从岛外传入,只要没有强大因素影响,即能长期保存下来。”①
其次是外来文化。海南文化与域外文化的交流始于唐宋,到了明清时期,由于生活贫困、战乱饥荒、海盗掠卖以及经商贸易等原因,移居境外的海南人逐渐增多至数百万。而且在家园情结的推动下,这些华侨、华人在寻根觅祖、回报乡里的同时,也为海南引进了佛教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对海南岛的地方性知识,尤其是建筑和饮食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海南的骑楼。作为一种外廊式的建筑,骑楼艺术历史久远,甚至可以追溯至古希腊的“帕特农神庙”。随着华侨群体的形成,闯南洋的商人将南洋的骑楼样式带入了海口以及海南岛东南沿海的各大乡镇,形成了繁华的商业群和独特的景观线,形成了既有浓厚的西方建筑风格,又有南洋装饰风格,还明显受到印度和阿拉伯文化影响的骑楼艺术。可谓多姿多彩,合而为一。但不可忽视的是,海南骑楼中的中国元素,尤其是外墙浮雕上那精美的百鸟朝凤、双龙戏珠、海棠花、蜡梅花等中国传统的雕刻艺术,以及窗楣、柱子、墙面造型、腰线、阳台、栏杆、雕饰,等等,居功至伟。这种中西合璧的复合风格表明,海南文化已经使外来的诸种文化中国化、海岛化了;同时也表明,外来文化之于海南岛,影响作用不小决定作用不大,缺少文化支配的权力。
再次,作为孤悬海外的小岛,海南岛的文化根性也与大陆文化不尽相同。当然,由移民和贬流官员传播而来的大陆文化是海南岛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构成要素。海南岛以儒为主、以道为辅,以仁为主、以自然为辅,以中和中庸为主、以天人合一为辅的文化,与大陆文化也具有同宗同源的关系。但由于大陆文化在本质上是温带文化、内陆文化和原住民文化,所以也不能取热带、海岛和移民的海南文化而代之。例如“大一统”。从秦汉开始,中国大陆的宗法统治就逐渐被中央集权式的官僚等级制所取代,形成了一套成熟而严格的“三省六部制”政治制度,以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核心价值观,还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伦理,“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道德。显然,大陆文化的这种社会控制和人身约束能力,足以让孤悬海外的海南叹为观止。海南不是广袤的大陆,不是黑格尔所说的人类文明起源的温带,而是一个小岛,一个热带岛,一个从大陆文化中移民而来的岛屿。这个岛屿上的文化如同这个岛屿上的环境一样,植物丰富多样,有的在换叶、有的在开花、有的正处在生长阶段,难以看到某种野果成片地出现,难以看到一种树木一统天下的局面,一种集权的基础。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当推闽南岭南文化。海南学者符永光认为:“五代十国至宋代是我国北方向南方大举移民的第二次高峰,其时移民的方向多从中原往东南沿海诸省大流动,尤其是福建省,以至于形成了人稠地狭的局面。于是,宋代闽人(包括落籍闽南的中原人)开始迁移广东、海南岛乃至东南亚各国。大批的有意识或松散式的移民,沿着粤东的潮汕平原南下,他们跨越珠江三角洲,经粤西、雷州半岛直至海南岛,这是沿着陆路来的移民。而自闽南沿海从水路乘船直达海南岛者,大多在岛北至岛东部的琼山、文昌至琼海一线登陆,形成了宋代闽南人向海南岛移民的第一次高潮,也是海南方言以闽南方言为母语基础的开始。”①此外,经海南学者对海南112个姓氏205位迁琼先祖的调查,表明海南各姓先祖来自于全国各地,其中有65个姓氏123位先祖来自福建,占60%;来自莆田的迁琼先祖就有90位,占44%。②因此有“琼者莆之枝叶、莆者琼之本根”之说,甚至有学者将海南与潮汕和台湾一起,列入“泛闽南文化”。③的确,海南文化中诸多元素如方言、祠堂、牌坊、舞狮、琼剧,尤其是祭祖风俗和妈祖崇拜,均与闽南文化密切相关。但尽管如此,闽南文化仍与作为地方知识的海南文化不尽相同,那宫殿式的“古大厝”建筑,那悬丝傀儡、普度仪式、南音文化,在文化移植过程中不是被改造过了就是被过滤掉了。或者说,作为热带海岛和移民社会的海南,在接受闽南文化的同时使之本岛化了。例如屋顶正脊的建筑。有专家指出,闽南岭南传统民居屋顶正脊多呈弧形曲线,向两端翘起成燕尾之型;琼北民居简化了正脊的形式,两端用脊吻以强调立体感;脊吻形式与闽南岭南的龙凤豪华造型也不一样,多用草尾、祥云图案。在山墙建造方面,闽南岭南较多用镬耳山墙,常以此来显示富贵富有,而琼北屋顶多作硬山顶,多为人字山墙,装饰也较前两者更加简约明快。“这体现了海南人谦虚、低调的生活态度和质朴的情感。”④这种谦虚、低调的特点体现在思想文化方面,就是对大陆儒家文化的不同态度。实际上,大陆儒家文化在闽南文化的发展史上,经常被草根阶层消极地抵制着,甚至出现了一个叛逆的反儒教思想家李贽。但海南却不同,他对儒家文化一直践行着一条全盘接受和全面归化的道路。甚至可以说,唐宋以来的海南文化史,就是一部儒家文化的接交史。
海南军坡节最初与岭南文化中的冼夫人崇拜有关。冼夫人的军队最先驻在新坡镇,人们在安居乐业之后,为感激冼夫人而举行模仿当年出军仪式的活动,故此得名。后来,“军坡”活动融进了更为丰富的内容,军坡节成了海南凌驾于地方道德观和其他民俗文化之上的最主要的神道节,所拜祭的对象也逐渐演变成当地曾经存在过的杰出“峒主”“境主”或者“祖先”及其生日,亦即“公期”和“婆期”。所以军坡节虽然多集中在阳春二三月,但却没有统一的日子。文昌文城镇是正月十三,海口新坡镇是二月初六,定安定城镇是二月十二,屯昌屯城镇是二月二十五,文昌东郊镇甚至每年有两期。而有些乡镇,既有共同的军坡节,各村还有各自的公期;既供奉较大的神祖“大公”,又供奉各自的神祖“小公”。多元性、多神性和不充分性的特征相当突出,说明在移民社会的公共意识里,只要具备足够的道德威望和能力,包括祖先在内的任何领袖都可以成为他们崇拜的神。所以海南人从一个地方搬家到另一个地方居住以后,就会立即放弃原来的军坡节,而改成新居住地的军坡节,原来拜祭的神也随即放弃,而改拜新居住地的神。凡此种种,均与崇尚境主的闽南文化密切相关,而与移民性质尤其是贬官色彩并不十分突出的岭南文化相去渐远。至于军坡节中颇具道教神秘色彩的各类“穿杖”节目,更与崇高性质的岭南巾帼英雄(谯国夫人、岭南圣母)大异其趣。
文化有意识形态和非意识形态之分,意识形态是想象性的“社会意识”或价值系统,是一个社会非正式约束的核心,或者说是社会中每个人的思想、信仰和行为都受其支配的准则和规范。而且,这种已经被某个群体所接受的体系性的社会意识融于生活特别是成为习惯时,就会成为集体无意识,使之自觉遵守并持之以恒。即所谓“道在伦常之中”和“日用而不知”。美国当代著名的人类学家吉尔兹认为,人类所赖以塑型的意识形态,就社会决定因素而言,存有利益论和张力论两种研究路径。在前者看来,意识形态是一种面具或武器;而对后者来说,意识形态则是病症和处方。在前一种可能性中,人们追逐权力,所以应在争取优越的斗争的背景中加以考察;而在后一种背景下,人们逃离焦虑,则应在修正社会心理失衡的漫长努力背景中来进行考察。由此可见,与更具革命性质的利益关系不同,张力关系既是一种充满对抗性的紧张关系,又是一种富有吸引力的合作关系,而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的海南文化,与其说是权力关系下的意识形态,毋宁说是蓝色的热带海岛文化和大陆的农业文化之间张力关系下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表明,受到狭小性和边缘性的地理条件的限制,古代海南不可能独立创造出自己的文化体系,只能步入一条吸收性的道路,从大陆吸收文化元素,但孤立的海岛生存又使他所吸收的诸多元素在这里汇成现世主义的文化品格。
二
同样是岛屿文化,但英伦理想国的归宿是理性,日本理想国的归宿是神道,海南理想国中的归宿是至尊至善并超越一切批判视野的祖先。祖先崇拜是海南岛的精神支柱和文化灵魂;以此为支点,海南历史不自觉地建构起了一个亲情和人情的社会。
其实,作为海南的先住民,黎族就是一个祖先信仰的民族。只不过,黎族的祖先信仰不是崇拜,而是敬畏,原始宗教性质的敬畏。原始宗教的发生原理在于,人们以集体的力量和简陋的工具与自然界做斗争时,一方面逐步认识到人们的生产活动与某些自然现象的联系;另一方面又对许多诸如风雨、雷电、日月、死亡、生育等自然现象和人类自身的现象进行万物有灵的朴素理解,认为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存在于自然之中。于是,敬畏与崇拜、恐惧与希望交织在一起,各种禁忌和巫术油然而生。黎族亦复如此。具言之,相信“灵魂不灭”的黎族人历来就认为,生命生时灵魂附于躯体,死后灵魂独立存在,或栖附于其他物体,或往来于阴阳两界间,或游离于亡者的村峒住所近处,成为鬼魂。人们只能用巫术的方式来敬畏,或请鬼公、娘母“作鬼”来驱邪,或以作法的方式来消灾避难。而且在黎族鬼魂体系中,“祖先鬼”是最大的鬼,和雷公鬼一样可怕,比其他鬼还要令人敬畏。即所谓:天上怕雷公,人间怕禁公,地下怕祖公。所以黎族便形成了诸多严厉的祖先禁忌文化,如平日禁忌提及祖先的名字,唯恐触怒祖先而招致灾难。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习俗在汉族文化的影响下,特别是在道教文化的影响下,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即从“鬼”向“神”的转变,并呈现巫道结合的特点。在这种转变中,“祖先鬼”已经淡化了对家人施以各种灾祸的能力,并有了“神”的内容和保护家人平安、牲畜繁殖、庄家丰收的“善”的意义。于是,黎族对“祖先鬼”由畏而敬,祭祀性质由恐惧而祈福,宗教目的也有了敬祖尊先、慎终追远的大陆人伦礼仪和道德情怀。
与黎族原始的祖先崇拜不同,海南汉人的祖先崇拜因移民的原因而明显呈现宗族化的特点。宗族观念是中国历史上盛行了几千年的文化观念,但对海南来说,似乎要特别突出一些。所以如此的原因在于,海南岛是个移民岛,从中原和闽粤以及广西南下驻琼的大批移民多以同姓同宗聚族而居,规模较大且人口较多的村落一村一姓,反之则一村多姓。这种宗族性质的村落组织是海南社会的基本结构,并使得社会成员产生并保持了祖先崇拜的传统,自觉和不自觉地在与祖先的关系中确定自己的位置和等级;使得他们相当重视血缘和宗姓关系,比较缺乏天下意识和终极关怀;使得他们固守于某一村落,对外部世界缺乏好奇心和交往动力,形成了保守主义的文化品格。一言以蔽之,祖先崇拜早已成为海南宗亲文化的历史起点,而宗亲文化也早已成为海南地方文化的逻辑起点。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孤悬海外,长期闭锁,远离中国政治的中心,因为较少受到大陆那样由于战争征伐、权力斗争、改朝换代等重大事件的革命性冲击,所以这种以祖先崇拜为中心的宗亲关系及其文化,在海南得到了更加纯粹的继承和更加顽强的坚守。以至于可以说,祖先崇拜已成为海南岛的文化根性之一。在这种崇拜中,所有家族成员都必须与自己的祖先建立起一种想象性关系,与社会建立起一种话语权力,并通过一系列的方式予以隐喻或实现。
首先是民居。海南主流民居是大陆四合院文化的延续,但又有自己的特色,诸如郁郁葱葱的居住环境、“龙翅”和“云公”的屋顶建筑、四面通风的结构设计、俗称“飘廊”的挡风遮雨功能,等等。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更具祖先崇拜意义的“堂屋”文化。大陆四合院的“四”字表示东南西北四面,“合”则表示围在一起的意思。也就是说,四合院是由四面的房屋或围墙圈成的一个封闭空间;只要关上大门,四合院内便形成一个独立自足的小世界,而中堂便是这世界的中心。在这个中心中敬奉着不同的神位。其中,观音位于左方,以凸显其地位,其余神明位阶不分上下并设于右方,而祖先牌位往往被安放在神位中最低的位阶,不能超越于诸神明之上。①与此相应的是,在这个中心中还会悬挂着一些书画作品,喜欢精英文化的挂诗词字画,喜欢世俗文化的挂“福、禄、寿”,官宦人家挂激励子孙的对联,而经商人家则多用吉祥如意、恭喜发财的对子。如此多元的文化元素在中堂这个小世界中构建了一个礼仪文化空间,而祖先崇拜文化仅居其一,尚未达到唯我独尊的高度。海南民居特别是民居中的“堂屋”则有所不同,虽然在这里也有其他元素存在,但却更集中地体现了祖先认同主题——“屋”。因此在选址上,“屋”只能选在自己的祖地,不能占用其他的土地;在动土之前,要请来风水先生给“屋”看风水定阴阳,定良辰吉日;在“起屋”之时,要邀请同宗同族成员,一同祭祀土地爷,祭祀祖先;在新房建好之时,还要举行“进屋”仪式,宴请前来贺喜的三亲六戚、左邻右舍。而从建筑格局来看,海南之“屋”的祖先崇拜主题更为突出。海南传统民居系由“正屋”和“横屋”两部分组成。“正屋”的主体是堂屋,堂屋的主体是客厅,客厅里设有三殿堂,供奉祖先神位和道德格训。年时节下,生辰忌日,婚丧大典,在此设祭行礼;贵客临门,在此接待;女儿回娘家在此拜见父母;甚至上年纪的老人,也会守在客厅以待归天。他们认为,如果在屋外逝世,就成了孤魂野鬼,以后必须做佛招魂,方能上得灵位,与列祖列宗一起接受在世亲人的祭拜。对于海南人来说,堂屋是家园和家族的象征,是祖先崇拜的外在表现,只有儿子或者长子才能继承。所以在海南方言中,“屋”字涵盖了“家”“室”“房”的意义,“有屋有头”就是说有产有业、有根有基,光宗耀祖。一字之中,包含着血脉相承、薪火相传的隐喻。
其次是宗祠。宗祠或称家庙、祠堂,是本姓氏奉祀祖先神位的建筑,也是血亲村落最重要的建筑,有着很强的神灵色彩和精神家园、血缘纽带的意义。中国大陆的姓氏宗祠文化很早就与郡望——门阀文化联系在一起,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政治生活。“郡”是行政区划,“望”是名门望族,“郡望”表示某一地域的名门大族。这些高门大姓一般地说由家族人物的地位、权威和声望自然造成,一旦形成则显赫无比,十分威严,并世代传承,成为所谓“门阀”,亦即门第阀阅。有时官方还做明确规定,宣称某姓为望族大姓,具体划分姓族等级,确定门阀序列以及特权。而与高门望族相比,门第较低,家世不显的家族则被称为“寒门”“庶族”。他们虽然也有一定的土地、财产,其成员也有入仕的机会,但总的说来,其社会地位无法与门阀士族相比。其结果便是士庶不同。出身于名门望族的“衣冠子弟”,即便无才无德,也能列为上品优先入仕,得授清贵之职,而出身孤寒的庶族子弟,即便才德超群,总被列为下品,即使入仕,也只可能就任士族所不屑的卑微之职,以致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甚至“士庶之别,国之章也”。
政治色彩十分显然。而海南的姓氏宗祠则与政治基本无关。具言之,海南的姓氏宗祠都源于渡琼始祖的崇拜。尽管其中有的始祖来自内陆,有的来自闽南岭南;有的属于朝廷命官,有的属于朝廷贬官;有的避乱入琼,有的经商落籍;有的是迁居入琼者,有的是宦游来琼者;有的是举人进士,有的是武将出身,还有张氏宗祠的张岳崧为海南历史上唯一的探花。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除了曾氏宗祠以及符氏宗祠的始祖,或为中国历史上圣贤以及望族的后裔外,多数宗祠的始祖之所以成为始祖,并非其“郡望”身份而是其宗法力量和海南岛的生存环境所使然。因此,人们建设宗祠这种族人群落在精神层面的公共财产,并不是要获取和维护某种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而是要在这里敬奉祖先,记载祖训,举行祭祀仪式,保存全族的派系、行辈、婚姻及其历史渊源,让族人感受到本族变迁、发展的轨迹。春节、清明、中秋、冬至等重大节庆,以及凡是家有要事,如结婚生子等,一般都要来这里“告慰”先人。由此可见,作为祖先崇拜的一种存在形式,宗祠完全属于宗族血亲的圣殿,郡望性质的政治色彩及其权力意义并不明显。
最后是家谱。如果说宗祠是与姓氏有关的物质文化,那么家谱就是与姓氏有关的非物质文化,是以记载一个血亲家族的世系与事迹为主要内容的历史文献。而且,虽然许多欧洲国家都有家谱族谱的传统,甚至像意大利的罗伦佐家族那样,记载了该家族十分重要的历史贡献,但相比之下,中国家谱文化更加源远流长和普遍化。所以自夏商以来,中国不仅王室有家谱,诸侯及一些贵族也有家谱,政府还曾设专门机构进行家谱管理。屈原官居三闾大夫,其主要职掌就是掌管楚国昭、景、屈三族的三姓事务,编制三姓的家谱。相传荀子也曾编有《春秋公子血脉谱》,“血脉”二字生动形象地揭示了家谱的本质。直到清代,中国家谱文化依然十分发达,而且愈演愈烈。所以当时的著名史学家章学诚说过“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家乘谱牍,一家一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①把家谱与国史、方志相提并论。家谱如此重要的原因,在于其中的家规族训,不仅具有规范人生和教育子弟的道德功能,而且具有维系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加强文化认同的团结功能。所不同的是,古代海南“编户之民”很少,姓氏总量偏少,多集中在王、陈、符、李、黄、林、吴几大姓中,而且家谱文化的移民主题十分突出,均记载了渡琼始祖在海南的丰功伟绩。与此移民文化相对应的是,海南各宗姓之间和睦相处,并未形成生存地位上的士族与庶族的等级关系和紧张关系。因此使得海南的家谱文化各问其祖,各寻其根,各自进行自己慎终追远性质的文化认同,以通过祖先崇拜而获得最可靠、最永久的血脉依凭。即使在多姓的村落中,也无小说《白鹿原》中白鹿两姓那种充满恩怨的权力斗争。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随着历史的发展,海南的祖先崇拜从一个血亲现象演变成了一个社会现象。以至于可以说,整个海南就是个由祖先崇拜延伸而来的恩情世界,其中的子女与父母、兄弟与姐妹、宗亲与外戚、师生与朋友甚至所有的人,都因为生命或生存与恩情构成了一种或核心或紧密或松散的情义关系亦即社会秩序,而孝与忠则是维系这情义关系的基本义务和行为准则。规范之下,每个人都不再是单独的个人,而是这个情义世界的组成部分,并和邻近的人构成另一个情义世界。每个人都要明白自己的位置,并将“孝”和“忠”奉为必须履行的最高责任和准则。因此,他可以为“孝”去牺牲幸福和生命,也可能因为不忠而成为不义之人,受到社会的谴责与惩罚。这种无私的超功利的情义精神,体现了岛屿生存的团结需要,因为古代岛民只有依靠“群”的力量才能够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和发展。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说:“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①在这方面,特殊的地理环境,使义务和责任均成为行之有效的道德律令的海南岛,颇具“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性质。
三
当然,团结的需要是人类古代社会的普遍需要。在“日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的远古社会里,人类只有通过集体协作的方式才能生产和生活,而血亲组织是集体协作的不二选择。于是,以血亲为基础,以部落为形式,以集体主义为精神,自然而然地成了原始氏族社会的一个共同属性。一直到阶级诞生以后,家族—部落式的血亲组织才逐渐被国家这一更高级的社会组织形式所取代。后来的差异在于,古希腊的“梭伦变法”一举摧毁了氏族公社制度,并经由古罗马的继承,早已使西方的“族人”关系让位给“公民”关系,血亲制度让位给民主制度。而在农业中国,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血亲制度或者说宗法制度却世代相传,甚至还以伦理纲常和政治制度的形式获得了话语霸权,以至于发展成为“家族本位”的中国“伦理法系”精神。在这种精神的支配下,家长对家庭成员管理的“规矩”就是家法,家族对国家管理的规矩就是国法,甚至成为超越法律原则的一种意识形态。伍子胥为报父仇,叛国、投敌、弑君,实属罪大恶极,但在人们心中,他仍然是正面的英雄,原因就在于“杀父之仇,不共戴天”。随后,战国时期发生在各个诸侯国的“变法”运动,对代表家族利益的“家族本位”形成重大冲击。“变法”最重要的内容是“隆君”“重法”。“隆君”抬高了君主和国家的权威,变贵族(家族)制为君主制,变“家族本位”为“国家本位”;“重法”抬高了法律和制度的权威,变“礼治”为“法治”,变众家族之“家法”为君主独裁之“王法”。从此,“朕即国家,朕即法律”便成了不可置疑的绝对真理,家家户户也成了“天然的皇权主义者”。而且从汉武帝时期起,儒家容忍代表“国家本位”的专制皇权,法家也容忍代表“家族本位”的宗法伦理,中国社会开始从强调礼法对立转变为提倡礼法合一。例如二者结合的典范——《唐律》,其“十恶”中“谋反”“谋大逆”“谋叛”“大不敬”所维护的,显然是“国家本位”的专制皇权和中央集权体制,而“恶逆”“不孝”“不睦”“内乱”四条所维护的,则显然是“家族本位”。
海南的问题在于,无论从历时性还是从共时性的角度考察,都没有完成从“家族本位”向“国家本位”的转变,以至于各种由“家族本位”所产生的地方性的“习惯法”,在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中一直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历时性地来看,汉王朝在海南设置郡县,实行“遥领”;隋王朝赐冼夫人“临振县汤沐邑一千五百户”,认可了冯冼家族在海南岛的统治;唐王朝在崖州设都督府,又设琼州都督府统管全岛;宋元王朝海南先后隶属于广南西路、湖广行省、广西行省;称海南为“南溟奇甸”的明太祖朱元璋,在登基的第三年也就是1370年,海南隶属广东,把琼州升格为府,大修府城、州城、县城,调查户口,丈量土地。从此,海南才有了统一的治理结构,才不被看作蛮荒和流放之地,即所谓:“前代珠崖郡,今日少窜臣。”由此可见,直到中国封建政治文化十分发达和严格的明代,大陆对海南的“王化”才告完成。而且在此过程中,由于统治者对这块遥远边地的轻视,中央政府对海南的控制时断时续,海南的行政区划时弱时强,海南黎族百姓的造反活动时有时无,导致王权的霸权力量远不如大陆那么强大。所以王安石变差役法为免役法后,“天下无复有邮差为吏之州,独海南四州不行焉”。于是,神宗只好下诏,仅海南岛罢免役法而仍旧令服差役。①在此“梗化”的背景下,海南的基层社会组织的“自治”作用也就更加重要了。
共时性地来看,海南的村落组织可以分为:作为山区居民地点的抱或者番,作为比较原始的氏族部落组织的峒,作为苗族游居地点的山岭苗,作为回族居住区的羊栏,还有诸多汉族居住区,如以原籍名命名的东山、东坡、东阁、蓬莱、铺前,以军事移民命名的所、亭、屯、都、堡、营、台。而且峒有峒首,村有村老,亭有亭长,以血亲家族为核心的村落组织相当牢固。例如峒首。实际上,峒首已经握有超越氏族长老所有的军事和行政权力,是一个黎区的军事长官和行政长官,甚至政治领袖。在他的领导下,峒有自己的规矩,土地共有,共耕分收,抵御外辱,保卫家园。这种移民性质和家族性质结合而成的社会结构,更支持了地方“自治”及其习惯法。
习惯法是一种源于生产生活的地方性习俗、信仰、规范,一种与条文法相对应并具有普遍性和权威性的习惯做法。法国著名的比较法学家勒内·达维德认为:“中国人解决争端首先必须考虑‘情’,其次是‘礼’,最后是‘理’,只有最后才诉诸法。”“中国人民一般是在不用法的情况下生活的。……他们处理与别人的关系以是否合乎情理为准则。他们不要求什么权利,要的只是和睦相处下和谐。”①在这乡土社会、礼治秩序、长老统治方面,由于没有完成从“家族本位”向“国家本位”的转变,海南的状况似乎更为突出。
首先,习惯法就是海南先住民黎族中普遍存在的民间法。如前所述,在社会体制方面,黎族的基层组织为“峒”;峒的地域一般以山岭、河流为界,并且立碑、砌石或栽种树木作为标志。黎族百姓称呼他们的峒领为“奥雅”亦即“老人”,说明原始氏族社会的长老观念仍存在于民众意识之中。峒内成员的行为都有一定的规范,以世代相传的传统习惯为一切行动的准则,对峒的疆界和其他成员负有保卫保护的责任;如受到外峒人欺侮时,必须为其复仇,并共同负担械斗时的费用。诸如此类的行为,主要靠习惯法来维持。在法律方面,黎族传统习惯多是民法与刑法合二为一,司法大权掌握在峒长、哨官、头家手中,一般案件由头家处理,大的案件由哨官或峒长裁决,处理不了才上报县衙,交由条文法处理。而且在黎族习惯法中,对通奸处理较轻,对盗窃处理较重,对本村人处理较轻,对外村人处理较重,对峒里人处理较轻,对外峒人处理较重。穷人少罚,富人多罚,穷人无力赔偿,家族或氏族分担赔偿的责任。除此之外还罚牛、猪、鸡、酒、谷慰劳峒长和其他长老。在财产关系方面,峒管辖的范围神圣不可侵犯。峒内的土地、森林、河流未经许可,外人不能越界砍山开荒、采藤、伐木、打猎、捕鱼和居住等。或者须经本峒许可,还要上缴一定数额的物产给峒长,这些物产由峒长和峒长所居住的村庄的奥雅享用;村与村之间也不能越界砍山开荒、采藤、伐木、打猎、捕鱼,违者峒长负责仲裁,罚款赔偿。此外,婚姻家庭关系的各种规范也是黎族传统习惯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各地区各方言都有自己的婚俗,同一方言不同地区的婚俗也有差异。一般为一夫一妻制,多在本民族本方言内择偶,但严格遵守氏族社会族外婚制,即不同血缘集团才能通婚。如此等等,表明海南黎族社会是一个由习惯法所维系的地方自治社会。
在这方面,海南汉族社会与黎族社会大有异曲同工之趣。具言之,海南汉族不仅是一个血亲的社会,还是一个与“家族本位”密切相关的习惯法的社会。因为封建王朝只能把政权机构设立到州县,而将广大的乡村权力空间让渡给地方乡绅。这类人多属乡间长老,识字识历,有财有势,协调能力较强,因而受到普遍的拥戴,成了各种纠纷的仲裁者和可以同官府打交道的头面人物,人治与礼治的具体操作者。诚如日本学者小叶田淳所说,宋代海南,“长官是知县,有通判辅佐,镇有监镇官,乡有乡户,又设有称为耆户长等等的长老,关于警察催税等等,都听从长老的指圖”①。海南崖州的“父兄”就是如此。“父兄”既不领俸禄,也不问政务,只依“乡规民约”仲裁邻里纠纷,公正分家典田,主持婚丧礼仪。其势力范围或仅及族内,或波及全村,或四野六乡,乃至可以蓄养兵丁,缉捕盗贼,处死人犯。只要不触犯官威,便可相安无事。如对盗贼的惩治:着人将盗贼按到板凳上,或反手向后吊上榕树,用扁担或竹编狠狠抽打,还让早在一旁待命的歌手歌唱,进行讽刺挖苦,教育众人不可学坏。②所不同的是,海南汉族的习惯法不仅约定俗成,而且得到了勒石刻碑,以示标志。海南的乡规民约即是如此。具言之,海南的乡规民约所体现的习惯法,一般以禁碑为载体,这些禁碑既有“官府示禁”之碑,但更多的是“奉官示禁”之碑,且多立于约亭之中。所谓“约亭”,通常是乡村文人儒士吟诗作对、联谊交友之地,同时也是乡村士绅传达官府谕示、讨论重大事务的地方。禁碑放置约亭,既体现了乡民们的高度重视,又方便乡民接近禁碑,为禁约的内容能够深入人心奠定了基础。从名称可以看出,具有禁约性质的海南乡规民约,虽属民间行为,但须官府认可。一方面,包括立约原因和奖罚标准在内的禁约条文,须根据当地生产生活的实际情况,经过乡民们的充分酝酿和商议,再署上“首事”(即倡导人)及父老的名单呈报官府。另一方面,官府同意禁约。例如文昌龙楼镇的一块奉谕示禁之碑:
近来盗贼滋甚,此非风俗之偷,实由乡禁之不显耳。遍开名都,图皆有弭盗要策,独我处此举未备。今圆得云梯岭四面,遵圣谕联保以弭盗贼之条,称家捐资生息,以资巡×(碑文不清,以×代替,下同),严赏罚务,使游懒者警,狗盗风熄,将人皆托业农,有所储士,有所储立,见风俗还淳,则乡×之中,虽赏不窃矣,敬将条规开勒于石:窃盗家财衣服耕牛捉获者,赏钱乙千六百文,窃盗罚钱演大戏三本。窃盗家器物件捉获者,赏钱五百文,窃盗罚钱演小戏三本。窃盗田园物业捉获者,赏钱乙千五百文,窃盗罚钱演小戏六本。窃盗小六畜海子棠,乱砍青叶树木各物件者,随众议罚,捉者随众议赏。窝盗者与捉盗私和者,加倍议罚,有家当为盗者,任众重罚,捉者赏亦加,接贼者同窝论。凡捉盗者,俱要连状送出方准有赏,不得凭例,呈凶过甚……①
由此可见,海南古代的乡禁虽然不是政府法律,却具有法律的作用,而且具有自我保护的乡民自治的性质。所以在保护乡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农业生产和经商活动、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管束伤风败俗的行为、倡导黎汉团结的一般内容中,在“禁刀斧不得入山砍”“禁盗砍芦林竹木”“禁不得盗割竹笋”,以及禁赌、禁抢、禁盗的习惯条文之外,更以排他性的禁约警告邻近乡村,充分体现了“自治”性质。即“遍开名都,图皆有弭盗要策,独我处此举未备”。凡此“有上述行为之徒”,或被绑起来让父老杖打,然后游村示众;或由官府“以凭拿究,决不稍微宽待”。如此看来,海南古代社会秩序并不十分安定,乡民忧虑之下,便请求恩准勒石示禁,“家族本位”的性质显而易见,而“奉官示禁”一语,则清晰表明了禁碑乃是私权与公权的结合。于是,乡规民约因官府的认可成为国家在地方的民法或习惯“法”,国家管制因乡规民约实现其“法治”化,最大限度减少了国家法律的执行阻力。可谓相得益彰。
值得关注的是,人类历史上的许多国家和许多时期,都出现过地方自治的力量和现象。如中国大陆的乡绅集团以及乡绅自治,英伦岛屿的贵族集团以及庄园自治,日本列岛的大名以及领地自治。但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大陆的乡绅集团走上了既依附于专制皇权又以施仁义道德来约束官员的儒士道路,英伦贵族集团走上了一条既与国王斗争又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底层民众基本权利的绅士道路,日本列岛大名集团走上了一条既受幕府控制又有地方武装的军事道路,而海南的长老、父兄阶层却仍然停留在家族宗族的阶段,社会化和政治化的能力尚不发达,公权与私权、条文与习惯处于弱势平衡状态;在这里从来没有形成一个大陆式的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
四
西方文化,是一种典型的“罪感文化”,相信人人有原罪,人人有罪,所以强调忏悔和赎罪,希望借此来减轻自身的罪,从而得到心灵的安慰。日本文化是“耻感文化”,“重视耻辱感远胜于罪恶感”①。日本人的耻辱感,来源于他们对名誉的高要求,来源于他们敏感的脆弱的自尊心。“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最大的区别是在对待“罪”的态度上:前者只有耻辱感,而无罪恶感,哪怕干着的是十恶不赦的大罪恶;没有忏悔和赎罪之说,即使认识到自己的确犯了罪,也是如此。而中国文化,则是一种乐感文化。李泽厚认为,中国文化精神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罪感文化的乐感文化,它立足于此岸世界而强调自强不息、乐观积极的精神状态,尽管千辛万苦,也要乐于眺望未来。具有“乐行之,忧则违之”(《周易》)的乐天知命的乐生特点,相信只要前仆后继、百折不挠,就会否极泰来、柳暗花明。所谓:“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但乐感文化也有其消极的性质:由于讲究“实用理性”,讲究变通,导致中国人整体耻辱感、罪恶感的缺乏,“内心的自我约束力”的缺乏;导致形而上的终极追问能力的缺乏。蓝色的农业文明所哺育起来的张力性的海南意识形态,就是一种乐感文化,一种以人的现世性为本的乐感文化。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中江兆民曾经说:“我们日本从古代到现在,一直没有哲学。”②海南亦复如此。
当然,海南意识形态中也有形而上的“道”的追求,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浸润下,才产生了大陆主流文化中不普遍的“牌坊”文化和并不存在的“从道不从君”的思想。牌坊起源于汉代坊墙上的坊门,门上榜书坊名以为标记,宋以后随着里坊制的瓦解,坊门的原有功能消失,但坊门仍然脱离坊墙的形式独立存在,成为象征性的门,立于大街、桥梁的显要位置。经汉代的“榜其闾里”,唐宋的“树阙门闾”,至元明清已发展为“旌表建坊”,即对政绩、及弟、长寿、守节等进行表彰,具有了“道”的意义。据史料,海口市文山村,原有明代进士举人牌坊“折桂坊”“毓秀坊”“登科坊”“文魁坊”“科甲联芳坊”等多达15座,记载着文山古村周氏家族“文士接踵,官员济济”的盛况。而海口市攀丹村原有明代进士举人牌坊“青云坊”“天衢坊”“省魁坊”“进士第坊”等也多达11座,记载了攀丹村唐氏名门“累朝衣冠蝉联,英才辈出,代不乏人”的荣耀。以至于可以说,海南岛就是一个牌坊岛。①关于“从道不从君”的思想,海南更为突出。尽管大陆主流文化中也有谏官文化,也出现过名臣魏征,但他们在侍明君的立场下,常常谏言不露,“密陈所见,潜献所闻”,难以“从道不从君”,难以坚持守道精神、产生批判意识,而海瑞之所以备受争议,“大逆不道”,或许正是因为他的这种守道思想和行动与大陆文化的差异所致。他在户部云南司主事任上,目睹了皇帝的昏庸和朝政的腐败,深为天下百姓的安危而担忧,更为大明王朝的内忧外患而心急如焚。如果上疏劝谏,必然是死路一条;如果袖手旁观,又大失忠臣之道。终于列举事实,冒死为国家和百姓,上疏抨击皇帝,以实现他一生追求的“武死战,文死谏”的道德目标,将一份措辞十分激烈的《治安疏》呈给了皇帝。“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言人所不敢言”,“触人所不欲言”,震动朝野,惊动皇帝,险些丢掉身家性命。
但是,在海南意识形态基础上所成长起来的这种伦理道德和政治道德,少有终极关怀的意义。作为哲学智慧的终极关怀,是一种超越有限追求无限,以化解生存和死亡紧张关系的终极性思考。在实践理性的引领下,中国古代圣贤一般不去进行这种务虚的精神活动。即所谓的“道可道,非常道”(老子),“不知生,焉知死”(孔子),“以有涯随无涯,殆己”(庄子)。海南牌坊文化和海瑞思想中的“道”,亦复如此,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海南古代书院与大陆古代书院的一个重要差别,就是始终处于礼仪文化的教育层面,“以诗书礼乐之教,转移其风俗,变化其心”,普遍缺乏问天、问道的哲学内容,以及天下关怀的忧患意识。推而广之,海南文化重感觉,轻抽象;重经验,轻思辨;重道德,轻忧患。其结果便是,文化建构力度不强、主体地位不高、话语权力不大,始终未能与大陆主流文化之间形成一种对话关系,其话语权力与同属于中华文化子系统的闽南文化难以相提并论。闽南颇富文化底蕴,正如泉州文庙对联所说:“圣域津梁,理学渊源开石井;海滨邹鲁,诗书弦诵遍桐城。”根基于这个文化底蕴,朱熹创建的书院及其闽学,便因其形而上的思考而曾对中国古代思想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哲学贡献。如果说,宋儒革新了汉代以来的儒家道统学说,将儒家经学传统拓展为关于政道、经史、文章的文化学术,那么,闽学则由此转向文化的心性义理,成为性理之学或宋代新儒学中的新儒学,朱熹也成了继先秦孔孟、汉代董仲舒、唐代韩愈之后最伟大的儒学大师。如此重要的理论贡献,非海南文化所能企及。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注重世俗幸福的大陆农业文化,试图消解焦虑的海岛生存,远离政治中心的地缘环境,诸如此类的因素使追寻乐感乐生的现世倾向成为海南乐感文化的主流,进而从现世主义倾向发展成为现实主义精神,支配着历代海南人的价值观。
首先是安贫乐道的人生态度。这种在海南比较普遍的人生态度似乎与贬流文化相关。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安贫乐道、快意生存素来是中国重要的人文选择。海南亦复如此。那些被贬谪的精英们身处“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交无友,冬无碳,夏无寒泉”的“蛮荒”之地,有人壮志未酬,“独上高楼望帝京”(李德裕);有人黯然神伤,“白首何归,怅余生之无几”(赵鼎);但是已经不能兼济天下的流放者们,更多地像苏东坡那样,选择了独善其身的道路,安贫乐道,快意生存。诚如斯言:“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①于是,他怀着对老庄思想的浓厚兴趣,追随陶渊明,写了大量的和陶诗,办起了“载酒堂”,在海南过了三年的隐士生活,写下了大量的诗词文赋,给海南留下了“一蓑烟雨任平生”的精神遗产。
其次是闲适优游的人生情怀。诗是一种阐述心灵的文字,“感其况而述其心,发乎情而施乎艺也。”借此心灵文字,我们可以看到:“五指山光胜九华,版图曾奏汉王家。窠中老人多遗世,被里官闲早放衙。橄榄香回茶后美,蝤蛑鲙出酒余嘉。薰风座上羲皇客,一曲雍容咏天涯。”“地极南堧萃物华,竹垣深浅里人家。儿童总解藏私货,父老无由识县衙。藜子熟时村酒酽,甜茹拙处野肴嘉。东风不负凫鷖约,白首同归醉天涯。”①在诸多的心灵文字中,我们对海南文化之闲适优游的追求也可略见一斑。司马迁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奋(愤)之所为作也。”(《史记·太史公自序》)但唐宋以来海南的古代诗歌中,却鲜有“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的忧患意味,更多的是颇具老庄精神的咏物咏怀。如邢宥的《休归咏怀》:“脱却樊笼得自由,家园万里望琼州。花看晚节添幽兴,人忆同时觅旧游。一枕黑甜山舍午,半樽白泼水亭秋。归来已定栖身地,独愧君恩未应酬。”②
最后还有乐观主义的艺术传统。千古绝唱《梁山伯与祝英台》本来与《白蛇传》《孟姜女》《牛郎织女》一样,属于那种颇为悲惨的爱情故事,但流传到海南,却被本土化成了一个具有大团圆结局的喜剧——海南岛的《威尼斯商人》:马俊逼婚,祝英台誓死不从;梁山伯考中状元,被招驸马;金銮殿上梁山伯不从君命,被定欺君之罪;祝英台及时赶到,据理力争,皇帝倍受感动,特赐梁祝天地良缘。乐感文化不言而喻。在乐感文化的引领下,传统而普遍的海南琼剧,放弃悲剧性的宏大叙事,忽视权力斗争和死亡情节,一直围绕着优美的爱情主题,积淀着乐观主义的艺术传统。
1882年美国人香便文海南岛之行日期考
辛世彪
香便文(Benjamin Couch Henry,1850~1901),美国传教士,1873年来华,为岭南大学前身格致书院(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创办人之一,曾著有《基督教与中国》(The Cross and the Dragon)和《岭南纪行》(Ling-Nam)。①
1882年10月,香便文在早一年上岛传教的美籍丹麦裔传教士冶基善(CarlC.Jeremiassen,1847~1901)②的陪同下前往海南岛考察旅行,考察经过写在《岭南纪行》一书中,成为该书的后半部分(第17~27章)。这是西方人穿越黎区的最早记录,1868年史温侯(Robert Swinhoe,1836~1877)最远只到过琼中的岭门。③不过,香便文“海南纪行”这一部分内容已于1883年分为四篇率先发表,前三篇题为“海南几瞥”(Glimpses of Hainan),发表在上海出版的《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①末篇题为“海南纪行尾声”(The close of a journey through Hainan),刊载于香港出版的《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②这四篇文章收入《岭南纪行》时,只增加了两小段文字,其他内容几乎没有改动。
香便文在书中没有说明他在海南岛旅行的具体起止日期和总天数,给我们留下了一处疑问。“海南纪行”译注完成后,我觉得有必要弄清楚这些具体时间。本文根据他在书中每日行程的记录,结合所能找到的当时其他相关文献,考订1882年香便文海南岛之行的日期和时间,以供治近代史及基督教入华史者参考。以下所引文献皆为笔者翻译,但引文末括号内所标为原书页码。
一 现有的材料和记录
有关香便文海南岛之行时间的直接记述,主要有以下3项材料。
1.香便文在《岭南纪行》第17章中说,这次旅行时间是1882年10月和11月:
直到三年前,海南岛腹地的外壳才被真正打破,对外界开放。做这事的第一人是冶基善先生,一位丹麦绅士,现在献身向岛内民众做独立的传教工作。1882年4~5月,他做了徒步环岛游,探索在岛上旅行的可行性,他走过每一个地区都未受到侵扰,并证实那里的人很友善。这次由一个岛内外国人做的大范围旅行的记录,非常详细,令人充满兴趣。在过去的一年里,他已从岛北穿到岛南,再从东穿到西,在任何地方都未遇到特别的敌意。1882年10月和11月,我有幸跟这位先生一道做了大范围旅行,穿越了这个岛的腹地,我就把这次的旅行记录续上。(p.331)
2.《教务杂志》1882年11~12月号“传教士新闻”栏中说,香便文于1882年12月7日返回广州:①
广州。12月7日,传教士香便文从海南岛旅行归来,这次穿越之旅是在冶基善先生陪同下进行的。他们在所到之处获得当地居民的极大好感,既有说海南话的汉人,也包括土著部落。冶基善先生诊治了无数的病人。书籍很容易就被买走了,处处热情好客,对待旅行的客人也如此。我们希望读到香便文先生对海南岛及岛上居民考察的记录。
3.香便文在《基督教与中国》里说,他们在海南岛内旅行共计45天:②
两年前,我在冶基善先生陪同下去过海南,做了穿越该岛的大范围旅行。我在海南岛腹地度过了45天时间,在汉人和土著人中都住过,因此我可以基于个人的观察和经历,说一说海南岛人的性情以及如何在他们中间开展工作;我可以强调说,整个海南岛——无论沿海还是腹地,无论山区还是平原——似乎都向基督教工作完全敞开了。
以上3种材料综合在一起,并非从12月7日往前数45天即可得到香便文旅行的准确日期。首先,香便文说他在海南岛旅行是10月和11月,并没有把12月包括在内。其次,香便文说得很清楚,这45天是他在海南岛内旅行的时间,而不是往返海南岛的总时间,如果把12月7日作为旅行的最后一天,那他们登岛旅行的第一天就是1882年10月23日,可是香便文收集的植物标本清楚地记着,10月24日在临高收集到某些植物,根据《岭南纪行》中的记录推算,他们到达海口以后的第7天才进入临高县境内,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因此,接下来我们要靠两种材料加以考订。一是香便文书中每天行程的记录,每天从哪儿到哪儿,住在什么地方,这是最重要的内证材料。二是当时香港的植物学家汉斯博士(Dr.Henry Fletcher Hance,1827~1886)的文章,因为香便文把他在海南岛收集到的植物标本全部赠送给汉斯做研究,汉斯将这些标本分类整理,发表于专业杂志,每一种植物都注明了香便文收集的地点、日期等,这可以作为重要的旁证。
二 香便文行程的描述
香便文在书中虽然没有说到任何一天具体是几月几日,但他提供了两种重要的时间信息。一是每天的行止,住在哪儿,在那里待了几天,我们可以据此推算出旅行的总天数;二是有两处提到在某地过星期天,这可以帮助我们推算出当天是几月几日,进而推算出该日前后的具体日期。
1.从海口到儋州南丰
1882年10月的一天,香便文从香港乘船前往海口:
我们从香港到海口的旅行,是乘坐一艘破旧的小汽船,船舱就在蒸汽锅炉上面。……傍晚时分,我们在开阔的锚地抛锚,港口的弊端立时显现。……我们乘坐其中的一只小船,到将近午夜才上岸,离我们下大船已有5个小时。在这番遭罪的航行之后,我朋友清洁、宁静、舒适的住处,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解脱。(p.332)
此次随香便文一同来海南岛的还有几个说粤语的挑夫。从香港到海口,原文说海路有290英里,不管走了几天,这一段不算在45天之内,他们的行程是从登岛开始算起的。
接下来他们考察了海口及周边环境、历史人文风貌,并做旅行前的准备,但没有注明天数。他们在岛上的旅行是走西线,从东线返回,这一路都记着当晚住哪里、住了几天,可以据此排列推算日期。书中涉及的地名笔者都做过实地调查,多数地名都已考订出来。古今地名不一致的,在叙述中注明了原书所记历史地名,并用括弧标注今地名,有些暂时无法弄清楚的,则用音译名,叙述文字中用括弧标出原文。
第1天从海口出发,当晚住海口西部的龙山(荣山):
第一天徒步旅行17英里,止于“龙山村”(Lung-shan),村边有小溪流向大海,溪上有座石桥。(p.345)
次日住澄迈县城(老城),从荣山到老城只有5英里:
城里的居民有礼而淡然地迎接我们。我们包下了整个旅店,这样就觉得相对舒服些。(p.348)
第3天住澄迈森山(福山),女店主泼辣能干,丈夫是鸦片烟鬼:
我们住在镇上最好的客栈里。据我们观察,海南所有的客栈都是女人当家,这可能是她们自立的一个迹象。(p.352)
第4天住临高船肚(皇桐),这地方离福山大约6英里:
几英里之后,我们来到一个叫“船肚”(Shun-tó)的小市镇,在这里我们住了一家上等客栈,干净舒适,又很安静,后面还有一个隐蔽的门。(p.354)
第5天住临高县城(临城),考察城内古迹,登高山岭。第6天到临高美珠(波莲),因在此地诊治病人走不开,多住一天,一百多人得到诊治:
我们本打算次日一早动身,但是散集回去的人已经把我们到来的消息传开了,我朋友的医术在远近村庄都很有名。第二天早晨,我们的门口挤满了热切而焦急的人。……于是,我们舍出一天,给他们治病,锁上里面的门,让一个人守着,一次只许进几个人。(pp.359-360)
第8~10天住临高马停(美台),在这里休息并治病,从安息日(星期六)到星期一共3天,有清楚的时间标记。
尽管他们一再请求,我们还是拒绝了所有的邀请,动身前往“马停”(Ma-ting),离此地五英里远,我们希望去那里过一个安静的安息日。(p.360)
这一段说的依然是波莲,那天应该是星期五,由于治病太累,他们希望到下一站美台过安息日(星期六),休息一下;次日就是星期日,香便文和冶基善两位牧师要做礼拜。书中又说到,星期一美台有集市,他们详细考察了市场,并且卖掉了带来的一部分书,当天也治病,治疗的人比波莲多一半;由于病人多,次日凌晨才脱身。因此他们在美台共计待了3天。
第11天住临高和舍,次日亦在和舍考察:
我们沿着缓坡下山,走了一英里半后到达“和舍”(Wo-she)镇,我们要在这里休息两天。(p.365)
第13天住儋州那大,在这里治病、卖书,考察当地多种方言:
到了那大,我们发现正是繁忙开市的日子,街上挤满了赶时间专心做买卖的人。人的数量之多,商品交换速度之快,以及整个城镇的面貌,使人感觉这里是个繁华的地方。我们急于避开拥挤的人群,步行二十英里之后也很想休息一会儿,就走进了一家客栈。(p.372)
第14天到儋州南丰,原文说因下雨滞留一周,但具体停留几天没有说明。因此从南丰开始我们重新排列日期。
终于,耽搁了一周之后,天有些放晴,我们早晨就动身,希望天黑前能到达第一个黎村。(p.402)
2.从儋州南丰到海口
从南丰开始,第1天住志文(Chi-wan),因下雨滞留3天。
已经大半天过去了,我们全身湿透,筋疲力尽,又打着冷战。这里离镇上还有六英里,考虑到天黑下来,又阴沉沉的要下雨,全身衣服也是湿的,并且还可能找不到住处,我们就在“志文”(Chi-wán)村停下来,决定在这里过夜。幸好做了这样的决定,因为雨又下起来,在三天内不可能再往前走。(p.404)
三天之后,尽管浓重的雾气依然在山间萦绕,我们还是动身往黎村走。(p.406)
第4天住什满汀(Ta-man-teen),他们的到来在黎人中引起轰动:
什满汀(Ta-mán-teen)村距南丰十二英里,位于黎区内边缘地带,在汉人辖区几英里之外。……我们要求见村里的头人,马上有人送我们到他家。头人当时不在家,但我们被毫不犹豫地请了进去,像回到家里一样。他的妹妹担当起女主人的角色,麻利地拿来水、木柴及其他必需品。(p.410)
我们一行(共十四人)的到来,在镇上引起巨大的轰动,几乎所有的人都来看我们。(p.415)
第5天住白沙县东北部的番仑,番仑是大村,他们住其中的一个小村:
几分钟后来到一个小村子里,这就是那些被称为“番仑”(Fan-lun)的第一个村庄。年轻活泼的黎人把我们带到此地最好的房子,我们进去后,按照待客的礼数,这房子和里面的一切就属于我们了。(p.422)
第6天住福马(Fung-ma):
步行三英里之后,我们又经过了两个村子,都叫“福马”(Fung-ma),我们在第二个福马村停下休息。(p.435)
第7天到黎班,因下雨耽搁2天。此地离福马不远,俱在今白沙县细水乡合口村境内,因此第7天当天也应该算上:
到了黎班,人们带我们去的房子,虽然并不像我们离开的那座房子那样整洁吸引人,但也够大够舒适。(p.440)
因为下雨,我们在黎班耽搁了两天,但这并不妨碍附近村子的人成群结队来看我们。(p.443)
第9天住快丰(Kwai-fung),次日在那里过主日(礼拜天),这是第二个清楚的时间标记:
到达“快丰”(Kwai-fung)以后我们感到极大的轻松,这里是进入山谷以后的最后一个村庄。(p.454)
星期天是在村子里过的。尽管人们对我们的宗教活动表现出极大的尊重,但是我们发现,让他们理解其中的含义是困难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不懂他们的语言。(p.457)
第11天住琼中县红毛镇西北的打寒,这里的黎语跟白沙黎语不同:
休息一小时后我们继续上路,又翻过一道岭,走了一英里半路,到达“打寒”(Ta-hán)。……这里的人属于“干脚黎”(the Kon-keuk Les)部落,所讲方言与山岭那边的截然不同,我们的黎人挑夫只好讲海南话,这样他们才能听懂。房主和其他几个常跟汉人做生意的人,包括一个刚从海口回来的人,穿着汉服,但是大多数男人穿的衣服,如果可以称之为衣服,那就更为原始。(pp.460-461)
第12天到牙寒,住在一个汉族商人家里,他们的穿越计划即被此人破坏(详见附录):
我们来到“牙寒镇”(the town of Nga-han),它位于一条较大的溪流边上。我们的老黎人挑夫是我们在山岭那边遇到的一个鸦片烟鬼,他带我们去一个汉人家里,说是为了让我们住得更舒服些,但我们相信他是为了给自己弄一点鸦片。(p.464)
第13天他们到牙寒南边一个村子的黎头家里,请他帮助物色说当地方言的挑夫,遭拒后折回,住在牙寒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此村当为红毛镇的毛西:
黎头的村里没有可住之处,我们只好折回来,三次趟过宽阔的河流,在早晨路过的一个小村里过夜。(p.467)
第14天开始返回海口,但没有走老路,而是从红毛往北走,当日住水乖(Shui-kwai):
黎族老向导好像急匆匆要赶往下个歇脚的地方,我紧随其后,天黑前一个小时,我便到达一个叫“水乖”(Shui-kwai)的村子。尽管有前面的教训,但一进村子,老向导还是把我带进一户汉人家里。(p.476)
第15天到岭门,在岭门停留2天,经历了很多事情:
就这样,我们一次次在臭气熏天的泥潭里挣扎前行,又一次次在溪流里把全身冲洗干净,终于隐约看到了我们的目的地岭门镇。……我们找了一处相对干燥的地方休息,是一个建在主房上面的小阁楼,有点像鸡舍。(p.480)
经过两天半的休整,我们继续上路,穿过这片平原,直取东部的山脉。(p.489)
第18天离开岭门向北,住屯昌县乌坡镇:
在道路崎岖的平原上走了十英里,我们来到了一个海南话叫“乌坡”(Au-pó)的市镇。一天的交易已经结束,但还是有成群的人聚集围观我们。客栈大都客满,这时候有一大群人带着稻谷和货物住在店里。在一座小房子里,我们总算找到了一个安身之所;这房子没有门,但好奇围观的人比我们更欣赏它。(p.489)
第19天从乌坡经船埠坐船,一夜漂流到琼海嘉积,次日在嘉积考察集市,卖掉剩下的书和东西:
清晨,我们发现已经到了嘉积镇外的码头。从码头步行到客栈,我们差不多走了一英里,因此我们对镇子的规模有了一些概念。……我花了一整天时间逛街,带着大约三百册书和我们余下的所有东西,不费吹灰之力就处理掉了。(p.492)
第21天住定安县居丁镇,第22天从居丁到定安县城(定城),乘船连夜返回海口:
第一天我们走了二十五英里,在“居丁”(Kü-ting)镇落脚,次日中午抵达海口河。我们在这里乘船,连夜驶往海口,清晨到岸,在我朋友的住处吃早餐。(p.494)
以上从海口到南丰共走了14天,南丰以后共22天,合计36天,这是非常清楚的。需要考订的是他们在海口住了几天,在南丰住了几天,以及每一天的具体日期。
三 具体日期推算及旁证
1.日期推算
有四个时间标记可以参考:一是此次旅行在10~11月,二是在海南岛旅行共计45天,三是在美台的3天是从星期六到星期一,四是在快丰村的那一日是星期天。
我们把最后的一天(从居丁到海口)当作第45天,以快丰的那个星期日(倒数第13天)作为起点,在11月和12月初之间进行时间排列,发现那一天正好是1882年11月19日(光绪八年十月初九)。旅行的后半段时间就是11月18日(周六)晚上到达快丰,12月1日(周五)连夜返回海口。
然后从19日往前推,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时间标记,在美台正好是周六、周日、周一,这个不会变,这样他们滞留在南丰的时间就可以推算出来。他们于1882年10月28日(周六)当天到达美台(原文说从美珠到马停有5英里),31日(周二)离开美台前往和舍,当日及次日都住和舍。11月2日住那大。11月3日(周五)到达南丰,滞留6天,11月10日离开南丰到志文,后面的日期就都接上了。
最后,他们初到海口时待的时间也就清楚了,总共3天,具体日期是1882年10月18日至20日(周三到周五)。
这样,香便文一行是在1882年10月17日(星期二)晚上到达海口港,次日凌晨上岸。他们在海南岛旅行的时间是从1882年10月18日(星期三)算起,12月1日连夜赶路也就是12月2日(星期六)清晨到海口,不计12月2日当天,共45天。具体行程及大事记见附录。
有一个问题,《教务杂志》1882年11~12月号说香便文于1882年12月7日返回广州,这怎么解释?原来,香便文因为旅途的疲惫,加上从船埠到嘉积那一夜在船上受了风寒,11月30日到达会同(今琼海塔洋)后本想取道文昌回海口,但因发高烧,不得不乘坐轿子加紧赶回海口:
我们本打算先去文昌,再从那儿返回海口,但是嘉积河上那一夜漂流的恶果,在我身上转成了严重的打摆子发高烧,这病把我放倒了。我们只好抄最近、最便捷的路赶回去。几天后,我的朋友也同样病倒了,因此这次旅行的结尾并不如开始时那么令人愉快。从会同坐上轿子,我们直奔距离海口河(the Hoi-how river)最近的地点。(p.494)
接下来的几天香便文在海口养病、恢复,整理材料,于1882年12月7日回到广州。香便文对于坐船到海口港的情形已经表现得深恶痛绝,加上身体不适,情理上不可能立即从海口坐船折腾到广州。12月初这几天在香便文书中没有任何记录,自然也不可能算在穿越海南岛的旅行当中。而且根据书中的叙述推算,也没有超过45天的行程记录。
2.旁证材料
香便文是植物学爱好者,来海南之前就曾在广东北江、连州一带收集过很多植物标本,交给当时在香港的植物学家汉斯博士①做分类研究并且发表。香便文在海南岛旅行45天,收集到200种植物样本,都带回去交给了汉斯。汉斯将这些样本整理并做了植物学分类,发表在英国的《植物学报》(Journal of Botarey:British and Foreign)上,每一种都注明了香便文收集的地点、日期等。较重要的有如下几篇。
1883年的《中国植物志拾遗(八)》,包括植物品种100个,其中有香便文1882年在海南收集的5个。②1884年的《几种中国榛木科植物》,包括植物品种10个,其中有香便文1882年在海南收集的3个。③1885年的《中国植物志拾遗(九)》,包括植物品种59个,其中有香便文1882年在海南收集的13个。①1887年的《中国植物志拾遗(十)》,包括植物品种19个,其中有香便文1882年在海南收集的2个。②1885年的一篇短文《中国的四种番樱桃属植物》,③用拉丁语写成,所说的4个品种都是香便文收集的,其中有3个品种是在海南岛收集的。
这26种在海南岛收集的植物按汉斯原文标注的收集时间排列如下所示。
1.Jasminum ( Unifoliata) microcalyx,sp.nov.-1882 年10月19日香便文在海南海口(Hoi-hau)收集。
2.Gossypii sp.—1882年10月21日香便文在海南临高(Lam-ko)收集。
3.Loranthus ( cichlanthus) notothixoides,sp.nov.——1882年10月香便文在海南临高(Lam-ko)收集。
4.Helicteres spicata Colebr.Var.hainanensis.—1882年10月24日香便文在海南临高(Lam-ko)收集。
5.Anisochilus sinense,sp.nov.—1882年10月24日香便文在海南临高(Lam-ko)收集。
6.Pteris quadriaurum Retz. Var.—1882年10月24日香便文在海南什满汀(Ta-men-tin)收集。
7.Hygrophilia phlomoides N.abE.—1882年10月31日香便文在海南临高(Lam-ko)收集。
8.Ipomoea capitellata Choisy.—1882年10月31日香便文在海南和舍(Wo-chi)收集。
9.Ipomoea pileata Roxb.—1882年10月31日香便文在海南和舍(Wo-chi)收集。
10.Engenia (syzygium)Henryi.——1882年10月31日香便文在海南和舍(Wo-chi)收集。
11.Chailletia hainanensis,sp.nov.——1882年11月1日香便文在海南和舍(Wo-shi)收集。
12.Linociera(Ceranthus)Cambodiana Hance.——1882年11月1日香便文在海南临高和舍(Wo-shi)收集。
13.Suertia (Ophelia)vacillans Hance.——1882年11月6日香便文在海南南丰(Nam-fung)收集。
14.Kleinhoriahospital L.1882年11月7日香便文在海南收集。
15.Sphenodesma unguiculata Schauer.——1882年11月14日香便文在海南黎人区什满汀(Ta-men-tin)收集。
16.Thea bohea L.1882年11月14日香便文在海南黎人区什满汀(Ta-men-tai)收集。
17.Gomph Jiostemma Chinense Oliv.——1882年11月15日香便文在海南黎人区番仑(Fan-lrn)收集。
18.Quercus (Cyclobalanus) silvicolarum,sp.nov.1882年11月16日香便文在海南黎人区收集。
19.Diosspyros eriantha Champ.——1882年11月21日香便文在海南黎人区的红毛(Hung-mo)收集。
20.Plectraqnthus(Isodon,Euisodon)veronicifolius,sp.nov.1882年11月21日香便文在海南黎人区收集。
21.Eugenia(syzygium)myrsinifolia.——1882年11月21日香便文在海南黎人区的红毛(Hung-mo)收集。
22.Quercus(Pasania)litseifolia,sp.nov.——1882年11月22日香便文在海南黎人区的红毛(Hung-mo)收集。
23.Quercus (Pasania) Naiadarum,sp.nov.1882年11月26日香便文在海南黎人区的山脚下收集。
24.Melodorum ( Eumelodorum ) verrucosum Hook.fil.& Thomas.——1882年11月28日香便文在海南黎人区的红毛(Hung-mo)收集。
25.Eugenia(Syzygium) tephrodes.——1882年11月30日香便文在海南嘉积(Ka-chik)收集。26.Myrica(Morella)adenophora,sp.nov.——1882年11月香便文在海南定安(Ting-on)境内收集。
以上26条记录中,第3条和第26条没有注明具体日期,第14条、第18条和第23条没有注明具体收集地点。第1条,第4~5条,第7~13条,第15~17条,第19~22条,第25条,共计18条都与笔者考订的时间完全相合。其中第15和第16条在同一天,地点应该都是什满汀,“Ta-men-tai”当是“Ta-men-tin”之误。
1882年10月24日香便文从澄迈森山(福山)到临高船肚(皇桐),10月31日至11月1日在临高和舍,第3条说是10月在临高收集,应该说得过去。11月4-9日香便文一行滞留在南丰(当时属临高,今属儋州),因此第14条应该也是在南丰收集。第18条笼统地说11月16日在黎区收集,他们当天在黎区的福马到黎班之间行走。11月25~26日他们在岭门,这是黎区最北端,第23条也说得过去。第26条说11月在定安收集,当时的定安县范围很大,包括现在的琼中县全境和屯昌县一部分,可以是11月20日到27日的任何一天所经过的地方。因此这5条也不一定有问题。
问题出在第2条、第6条和第24条。据我考订,10月21日是香便文一行开始穿越旅行的第一天,从海口出发到龙山(荣山)过夜,行走17英里(27公里),4天后才到临高境内,10月21日无论如何不可能在临高。怀疑是香便文手写的标签“24”或“27”因看起来像“21”,被汉斯误认作10月21日。第6个标本说是香便文10月24日在什满汀收集的,这绝无可能,10月24日应该在临高境内,从这一天到什满汀还有近20天的路程,肯定是汉斯把标签弄错了。第24条说是11月28日在红毛峒收集,这个也没有可能。他们在11月23日离开红毛,当晚住在水乖,其地在琼中北部,当在今湾岭镇境内。11月28日这一天他们已经离开黎区了,更无可能在黎区的红毛。怀疑是汉斯把香便文手写标签“23”看成“28”,因此出错。
以上26条材料中,有3条怀疑是汉斯弄错了标签上的日期或地点,5条虽然没有具体时间或地点标记,但也未必有问题,其他18条都与考订出来的日期相合。汉斯的文章可以旁证香便文1882年海南岛之行的具体日期。
结语
我们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香便文没有在书中标注这次行程的具体日期,这本是轻而易举之事,也许他这样做是为了保证可读性,避免成为流水账似的日志或报告。香便文行文的简洁、流畅和优美令人称道,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记者出身的前缅甸殖民者司各特爵士(Sir James George Scott,1851~1935)是很能写作的人,但他的《法国与东京》(Franceand Tongkin,1885)①一书中关于海南岛的描写直接大段抄录香便文的文章,对其文笔大加赞叹,可见其价值和影响力。尽管如此,香便文记下了他们在旅途中的行止等相关信息,当时的教会文献也记载了这次旅行,汉斯博士的植物分类论文中更保留了香便文采集植物样本的时间、地点等。我们从内证和外证两方面的材料加以考订,得出1882年香便文海南岛之行的具体日期,应该是比较准确的。
附录 1882年10月18日至12月1日香便文一行海南岛旅行大事记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市场经济转化与产业化重构
——以海南为例
张军军
如何发展海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其在现代文明进程中快速消逝的本土文明得到良好的保护和传承,是海南省文化与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公益性保护与市场化开发相结合,政府主导、民间资本参与的多种样式的产业化经营,旅游文化园区、文化艺术品、民族性演艺等多元化开发模式,都将带动非遗融入现代理念,走可持续的发展与传承之路。在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大背景下,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市场开发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也必须看到,国际旅游岛的建设目标与海南非遗的保护之间存在一些内在的矛盾与冲突。那么,在国际旅游岛建设的市场经济背景下,如何做到海南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和构建旅游产业化之间理性沟通,使二者能够有机融合,最大限度地做到双赢?这一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一 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市场经济转化的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反映了一个民族、族群、社区和国家对自身特性的认同和自豪感,以及被世界认可的程度,是维系一个群体或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由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人们生产、生活方式及文化生态环境的变化,原生态的传统文化正在走向衰落,或走向变异。但世代劳动人民口传心授、约定俗成的活态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民族的根脉,也是现代文化发展的不竭源泉。
海南由于其地理位置,本土文化受现代文化冲击相对较小,很多地区都还保有原生态、古朴的自然状态。如距今6000多年的黎族制陶技艺、4000年历史的树皮布制作技艺、3000年历史的黎族文身,这些活态传承的技艺,在海南仍保存完好。但由于传承方式的局限,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现状堪忧,尤其是较为单一的项目,一旦传承人离世,绝活就成了绝唱,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如手工制陶的艺人全省不足10人,懂得黎族骨簪工艺的手艺人只有3人,临高人偶戏后继乏人。再如黎族打柴舞,全省只有三亚的一个村庄还完整存在,如果这个村庄打柴舞消失了,从此这个古老的舞蹈就在世界上消失了。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归根到底是对传承制度的创新性、传承环境的承接性和传承人的保护。
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程度,离不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程度和文化政策制定执行水平。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具有产业化潜质的项目走向市场,通过这一渠道可以使传统的文化项目获得生机,促进其有效传承的同时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国内有些城市将非遗项目的旅游市场开发与保护相结合,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如甘肃省环县道情皮影几十支队伍在全国各地演出,获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庆阳香包制作产业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民族文化在市场上特别是在旅游市场因特有的地域、文化、民族等优势,已经成为重要的旅游资源,是被开发和有效利用的热点。许多原本被抛弃的文化遗产不仅随着民族旅游文化的商品化而重获新生,而且正在成为独具地方特色的文化旅游资源。
其次,把非遗适度地通过市场化的形式融入当代生活,这样在资金的组合上,除了政府常态的财政“输血”外,带来了更多的资金渠道,从而开发非遗项目的自身“造血”功能。如海南以热带旅游为主题的“呀诺达”度假公园,将部分海南“非遗”项目纳入观光旅游中,成为海南岛特色品牌景区,年接待游客百万人次,单门票一项收入可达亿元,为技艺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资金与物质保障。
此外,将本地区的文化景观、本民族传统民间文化遗产、本土个性化的文化元素整合起来,构建相应的文化产业园区,已经成为世界上很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瞩目的议题。一个地区人们世代传习的精神文化因子经过时间的沉积、岁月的锻造,有机地融入这座城市的主体命脉,构成这座城市的精神源泉。将精神文化与文化产业相融合,打造适合本地区特点的文化产业园区,既是各地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举措,也是对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激发、重塑,形成产业化模式的市场动力。此举可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培育区域经济和城市经济新的增长点,对于扩大就业、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实力具有积极意义。
二 非遗项目在市场经济转化中存在的问题
(一)以利益为目的的商业化开发将失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
本真性(Authenticity),本意是真实而非虚假的、原本的而非复制的、忠实的而非虚伪的、神圣的而非亵渎的。①20世纪60年代,“本真性”或称为“原真性”被引入遗产保护领域,逐渐在世界范围内达成理解和共识。文化遗产的本真性来自原初可以流传的一切之整体,从物质形态上的持续、文化环境的“本体真实”,到它所经历的历史发展过程的见证,这一系列本真性的存在可以提高公众对文化遗产价值的认知度,防止“伪民俗”“伪遗产”。
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市场性开发相对滞后。21世纪初期,随着全国性文化旅游热潮的兴起,海南各地曾建起以打造地方民俗文化为旗号的大大小小的民俗风情园、黎村苗寨原始风情村等众多市场化行为的伪文化园区,极大地破坏了海南特有民族黎族及其原始黎族文化的本体真实性。如在海南的陵水、保亭、五指山等海南少数民族聚居区沿线,迅速仿建了许多少数民族居住村寨、粗制微缩原始景观。这些风情园、民俗村既没有文化赋予的生命内涵,又没有因时间的沉积而透出的历史厚重,相互间的同质化又导致了恶性竞争,暴露出很多市场性问题,其命运是以金钱的损失而落幕。这种只有民俗形,没有文化魂的伪民俗、伪遗产,最终破坏的是海南宝贵的文化资源,损害的是海南人民千百年来世代相传的文化印记。
(二)盲从性复制使“非遗”的可解读性遭到破坏,无法形成保护性开发
可解读性,指的是我们能够从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上辨识、解读出它的历史年轮、演变规律,尤其是内在的精神蕴涵。①非物质文化遗产蕴涵着一个民族传统文化最深厚的根源,保留着该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心理图腾和价值观念。在挖掘、开发、保护时,自然要格外重视其精神观念,即人和文化的关系。目的是使得所继承的事物具有真正的历史文化价值,而不是表现外在的文化形式,不能解读其内容。如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从农耕时代的祭神、蜡祭,发展到汉代出现的朝廷“众吏饮宴”、民间“华服盛饰”,演变到宋代出现的传递“拜年贴”、贴“门神”,到明代出现了年画的多样性。从其长期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出,春节无论是其功能、饮食、习俗,都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直到今天仍然能够解读出其延续的历史性变迁。再如,省级“非遗”项目海南传统节日“三月三”是黎族文化最具体、最典型的表现,也是黎族生产、生活、娱乐等整体民俗风貌的集中体现,是世人了解黎族文化和历史的窗口。近年来,海南本地进行了不同形式的市场性开发,政府“搭台唱戏”,但其中的舞台性表演、群众性会演、游人的即兴参与,反而掩盖了黎族在这一节庆里原有的传统民俗、仪式、庆典、传说等及其历史发展脉络,以及其具有的原始神秘性。结果,并没有给当地带来更多的经济收入,同时也破坏了这一节庆的可解读性,更无从谈起对“非遗”的保护性。
三 国际旅游岛背景下海南非遗项目的产业化重构
(一)海南国际旅游岛开发与非遗保护之间的内在矛盾
旅游开发与非遗保护之间虽然有利益结合点,但其根本性的目标还是不同的。国际旅游岛的建设要将海南特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纳入现代性的观光产业中来,就必须对此加以改造,以适应人们猎奇式观看的需求。在这种改造的过程中,难免将现代人的思维方式纳入其中,使那些能够与旅游开发相配套的项目为适应旅游开发的需求,削足适履,变成一种表演,从而破坏了其核心的文化价值;此外,这种为了适应旅游而进行的开发,也将使一些无法被改造成为视觉体验产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淘汰出局。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本身不存在商业目标,它完全站在对人类文明、文化方式延留的立场上,对项目的评价有其独立的尺度与价值体系,以项目的独特性与不可再生性为选取标准。非物质文化是在特定的文化生态场景、语境中发生、发展的,失去了这样的场景和语境,单独把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传承人保存下来,这虽然也很重要,但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背景和基础。然而,这一套体系却难以与旅游开发的市场经济相一致。我们可以将非遗项目与旅游开发之间的关系分为三种。
第一,二者有着高度的关联性。这方面的项目得到了海南各级政府与旅游开发组织的高度重视,如前述的呀诺达等项目,由于形成了良性循环,既获得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也在客观上避免了这些项目陷于失传的危险中。
第二,二者关联性不大,未得到良好开发。如黎族的骨簪工艺。黎族的骨簪,不仅是精美的饰品,而且反映了黎族的一段历史,记录了黎族的一位英雄,但由于市场开发不善,未能成为旅游工艺品,而使传承人越来越少,目前懂得制作的只有3人。与此同时,原本具有旅游表演项目潜质的黎族传统打柴舞,由于未得到相应重视而无人开发,截至目前只在三亚的一个村庄得以保存,如果打柴舞在这个村庄消失,那么就意味着后人只能从图片上找寻这一古老舞蹈的踪迹了……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缺乏旅游开发的潜力,或者未能被开发成为旅游产品而被冷落,进而面临失传的危险。
第三,二者存在矛盾或冲突。出于旅游开发的需要,对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人为改造,使遗产失掉了原有的意义与风貌。如海口府城古老传统的“换花节”,作为民俗类项目入选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①本地政府也有意要将这一传统习俗传承下去,形成品牌的力量。近几年的换花节虽然形式仍然延续,举办模式也由民间自发变成了政府主办,活动内容也不断外延,还增添了花展、灯展、舞狮、游艺娱乐等内容,但人们对该节日的期待却有衰减之势。
旅游是“看”的经济,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存在商业目标。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建设,使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旅游的产业化虽然对非现代的文化提供了资金支持等保护,但又迫使一些传统文化因“被看”而被改造进而破坏了其文化承载。海南是国内的重要旅游地区,又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较多的地区。尤其是2010年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开发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之后,旅游开发一路走热,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申请与实施保护迎来关键时期。二者之间的关系既有一致性,又充满了矛盾,实际上体现了现代社会的内在矛盾与冲突。
(二)非遗项目与旅游产业构建之间的结合点
有学者从旅游业的角度将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划分为五种资源类型,即观赏型、参与型、体验型、深层型、辅助型。②从视觉特征吸引旅游者、行动上融入体会人文风貌、精神上享有更深层文化内涵等范畴进行了旅游资源的划分。海南现有的89项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中,涵盖了传统手工技艺、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文学、民俗、戏剧、杂技、民间美术、文化空间等,其中一半以上属于观赏型、参与型、体验型的旅游文化资源。如濒临失传的手工制陶、龙被技艺;黎族特有的织锦、树皮衣制作技艺;传统民俗节庆“三月三”、军坡节;海南传统的琼剧、临高人偶戏;极富地方特色的崖州民歌、儋州调声;传统民间舞蹈打柴舞、招龙舞;黎族古民居船型屋、干栏式建筑等,这些既是海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又是具有极强的旅游开发价值的地域文化资源。这对于正在进行的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开发与建设,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资源财富。
旅游业围绕人们本能性的心理体验,满足人们好奇与陌生化的心理体验需求。因此,发展旅游业除了自然奇观之外,很大程度上需要提供给游客与其日常感官体验不一致的“奇观”。这种奇观一方面是物质性的,另一方面则是文化性的。尤其是在今天全球的现代性生产与消费体系抹平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差异化的时代,寻找与这种现代性的日常生活方式不同的文化体验,成为旅游的一个重要目标。旅游产业根据工业化的原则,将这种异域性的文化差异转变成为可供人们观赏的奇观。这就要求对一些不符合现代社会的文化加以包装与改造,使之成为人们进行工业化观赏的消费产品。而这正是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产业的结合点。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看不到,或者正在消失的“奇观”,它本身是一种陌生化的看点,能够为现代生活中的人们提供一种体验,并使之形成旅游产业所需要的市场,这是非遗与旅游业能达成一致的原因。这种需求可以为保护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资金和保护动力。如前文提到,国内一些非遗项目将旅游与保护相结合,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一方面通过走入市场,使传统的文化项目获得生机,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以热带原生态旅游为主题的海南呀诺达度假公园,将黎族织锦、文身等纳入观光项目,为技艺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资金与物质保障。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企业将黎族织锦开发成为工艺品与旅游纪念品,逐渐形成产业化运营模式,在获得市场的同时,也使这项手工技艺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和传承。
(三)非遗保护与旅游产业之间的双赢
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台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政府行为限定为: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总政策;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主管机构;编制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奖励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机构;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鼓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工作;制定法律法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等。这一规定,明确了政府与社会团体以及旅游企业之间的关系,体现出政府的主导作用。
首先,各级政府需要分辨非遗中能与旅游文化结合的点,并按它们之间不同的关系、不同项目区别对待和处理。对于具有旅游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鼓励个人与企业进行产业化开发,从而获得更多的资金与社会资源来对它们进行保护,进而提升旅游的深度,形成良性循环。如对黎锦、花梨木雕,以及一些村镇能够与旅游结合的公期等项目,可以采取与旅游结合的方式获得更好的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借此使古老的技艺和民俗得以传承,避免因缺乏资金与积极性而失传。找到非遗能够被“看”的一面,借助现代媒体力量吸引人来看,为旅游产业服务。如对于黎族骨簪制作这样的项目,应挖掘其潜在的旅游资源,通过帮扶其扩大市场的方式使之与旅游工艺品市场相结合,引导更多的民间艺人参与进来。否则,单纯依靠政府人为保护的方式,一旦资金、保护方式出现问题,这种技艺可能就永久性失传。
与旅游经济相矛盾或者相冲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则需要以政府力量为主导进行抢救和保护。首先需要厘清哪些是无旅游价值却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然后重点投入资金进行保护。如钻木取火、一些与原始宗教相关的黎族歌舞、口头传说等既无实用价值,又暂时难以对游客产生吸引力,这就需要政府层面进行抢救式的保护,一方面需要投入资金,另一方面保留影像资料。对于无旅游市场的民间技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则采取政府专项资金保护扶持的方式给予传承人经济支持。
其次,引导社会对非主流的生存方式与价值观给予充分的尊重与理解,保护民间独立性的生活方式与生存方式的存在空间,在现代化进程中能够更好地保留文化的多元性和差异性。这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所在,也能为旅游产业的未来发展提供更加充分的后续资源,在这点上保护与提供二者是一致的。针对海南现今的情况,可以考虑通过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方式将二者结合起来。“文化生态保护区是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对历史积淀丰厚、存续状态良好、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特色和价值的文化形态进行整体性保护,以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而划定的特定区域。”①
在海南未来的发展中,正视旅游开发与非遗保护之间的矛盾,在思考中不局限于现代性的思维方式,使“看”与“被看”都以全方位的视角来进行,这才能为日后海南的社会发展留下充足的空间。在这一过程中,需鼓励的是“看”的兴趣刺激旅游产业发展,但需避免“看”的过程对“被看”物的破坏。笔者希望海南能够成为一个永远有可“看”之处的旅游岛,也希望那些“被看”的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恒久地得到保护与传承。
四 从文化溯源的视角挖掘市场经济下海南非遗的地方承载
因阿诗玛而声名远播的云南石林;因白蛇传说而重新修缮的雷峰塔;滕王阁、岳阳楼、黄鹤楼因王勃、范仲淹、崔颢的诗句而千古传世,这些都因其合理有效的发掘,重塑了承载着浓厚地域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激活了非遗这一古老的文化元素构成,从而更好地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如何在发展中拓宽文化的传承渠道,在开发中体现文化的价值,在市场化的进程中构建文化的精神内涵,是当下必须关注的问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中,首先不能丢的是文化存在的根源,非遗本身的文化溯源要始终与现实生活的需求站在同一水平线上,否则“非遗”就变得“夹生”了。
海南府城正月十五日的换花节,原为“换香节”,俗称“驳香”,是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日海口市琼山地区具有历史特色的民间节日,起源于唐代贞观元年(627年),宋元时一直盛行,距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上的元宵节,府城居民在街上“换香”,意味着香火不绝,象征真实、祥和、喜庆、友好和爱慕,除此之外,民间还有挂灯、换香摘青的风俗。这些民俗形式实际上都是由元宵节演化而来,清咸丰《琼山县志》等史书均有记载:元宵节之夜满城妇女尽到总镇衙前,折取榕叶,谓之偷青。或燃香城门祝之,以祈有子。孩儿则摩总镇衙前两旁石狮,以祈平安。好事者悬迷灯于门首,游人聚观,测中者酬以笔墨烟草。①琼山府城镇曾为琼州府官方的驻地,每年农历“元宵节”都要举行灯会。脚下穿着新履的居民纷纷出门上街赏灯,由于当时没有路灯,人们为了夜行方便,手里都拿一把点燃的香烛用以照明,路遇没有香的人便送他几枝,有时偶遇朋友,也用香烛互相交换,互相说几句祝福的话语,换完香烛后不少人感到心中的夙愿已传到佛祖那里,便开始心满意足地踏上归路。一些人兴致勃勃,还特意从路边摘些青枝绿叶带回家,寓意一种蓬勃向上、乐观豁达的精神,由此演变成了海南人民之间一种传递心中情感的特殊方式。直到1984年,琼山政府考虑到燃香的安全性以及其本身附带封建迷信色彩,于是将这一近千年的民间换香习俗改为换花,希望能以花为媒继续传递祝福、友谊和爱情。但这种改变失掉了传统民俗性,其中寓意被置换,影响了民众参与的积极性。如今,人们手中的“香”换成了“花”,而这“花”多是“玫瑰花”,不产自海南,大多从云南空运到海南。人来人往、换花如潮的大街上,已经很少有纯朴的海南人自愿相互交换手中物、互道祝福的温馨场面了。在换花节上常常看到,一些小伙子从姑娘手中野蛮抢花的镜头,换花已经缺失了海南韵味。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节日、一种海南独特民俗、一份珍贵的海南本土文化的遗产,就这样变得不伦不类了。从换花节产生发展的脉络上可知,其原本的社会功能是娱乐、交友、祝福,而随着人们生活的变化、文化需求的变迁,这些原有的功能存在空间日益变大、渠道拓宽了,民众可以在更多的时间、地点里有选择地从事类似活动,又何必要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里重复性参与这种毫无创意的活动呢?由此可见,换花节这一节日习俗的变迁有其内在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如果不解风情地在发展中一味地简单复制、盲目恢复、粗暴改造,不仅会有损节日自身的民俗内涵,而且会加速其走向相反方向,甚至用我们的双眼看着它有一天消失殆尽。如今的“换花节”,虽然仍在延续这一节庆形式,内容也在不断丰富,但人们对“换花节”的期待却大有衰减之势,究其原因不得不从文化的传承错位进行分析。
在传承与发展换花节这一问题上,笔者认为没有必要原模原样的生搬硬套,非要照葫芦画瓢空留这套“外衣”,而是要在保有其文化内涵上做文章。把这一天作为纪念海南整体民俗文化的节日来组织运作,把更多的海南民俗拓展进来,打造一个富有海南地方文化品位、民间文化特色、民族文化精髓的品牌,集娱乐、和谐、诚信、交融、互动于一体的富有参与性的民俗活动,创造新的社会功能,使之世代传承。同时,一些非遗项目为了与开发挂钩,让媒体过度宣传、对比炒作、失实夸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实中的存在,使部分地方政府、百姓错误地认为“非遗”可以变成“摇钱树”,能成为地方的“标志性景观”,导致很多非遗项目遭到人为破坏。“如果把非物质文化比为鱼的话,那么特定的生态环境就是它的生命之水。水之不存,鱼将不再,二者是无法分割的。”①
海南学者将海南划分为五大文化区域,即以海口为中心的琼北历史文化区;以五指山为中心的黎苗族历史文化区;以三亚天涯海角和崖城镇为中心的历史文化区;以文昌、万宁为中心的沿海文化区;以儋州为中心的西部历史文化区。②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所在的区域文化紧密相关,构成了有机的整体,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所在城市的文化形象内涵。在进行非遗的市场化运作时,如果单纯地为了开发而进行简单的形态语境的还原,为了市场效益而进行文化元素的复制,忽略其文化的原真性,那么将失去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的本真形态及其历史价值的可解读性,同时失去的还将是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承载。
闫广林
一
从文化学的角度考察,世界上的岛屿大致有三类。除了至今仍散落在太平洋上的诸多具有原始部落和原始宗教意义的岛屿外,还有两类岛屿因为与大陆文化的关系而尤其值得关注。其一是被异化的岛屿,其二是被同化的岛屿。
克里特岛作为被异化的岛屿的典范,隶属于爱琴海文化。爱琴海上岛屿众多,其中最大的是克里特岛。克里特岛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出现了青铜文化,公元前2000年就出现了奴隶制国家,拥有丰富的文化成果,并对爱琴海周围诸岛特别是希腊半岛的文化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包括米诺斯王朝那雄伟的宫殿和卡马雷斯那精美的陶器,还有象形文字及其简化而成的以线条表示轮廓的线形文字。史称“克里特文化”或“米诺斯文化”。但是,在公元前15世纪,希腊人利用火山爆发后对克里特岛的破坏性影响,以战争和贸易的手段入侵克里特,并与当地原住民渐渐融合成新的文化形态。于是,在这征服与被征服的过程中,爱琴海文化的中心便转移到希腊本土的迈锡尼地区,而克里特文化在不自觉地转换成了对西方文化有重要意义的古希腊文化后,则逐渐为世人所遗忘。只是近代以来经过古发掘才重新为人们所认识:这个旅游胜地原来是西方文明的根!
克里特文化或米诺斯文化的历史命运,从另一角度说明:在航海业很发达的古代社会中,岛民居住的环境被海洋包围,生活空间受到很大限,只能以封闭的岛屿内陆为生活天地。不仅与外界缺乏交流,无法向大延伸,而且缺乏内在竞争,生产力水平很不发达,创造财富的能力极其限,社会文明的水平也难以持续,与大陆文化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从更般的意义上来看,岛屿文化并不具备进步发展的内在机制。诚如文化地学家葛绥成所说:“人类幼稚时代,只在岛上半岛上或海岸地方,发展化:及人智发达,大陆方面,亦渐为文化所进展……然而岛屿方面,人与自然,或人类与人类之间,少有大陆中那样的生存竞争,所以人类的达,就不免受阻碍。不过一旦从其他陆地比较发达的民族移至岛屿,或大陆方面输入种种文化,而使之发达时,那岛屿的文化,便得产生。”岛屿如不受大陆的何种刺激,而自己能开拓文化的,却未之前闻。如英、日本,虽说开拓了岛屿文化,其他所有的文化,还是由大陆输入而。英国、日本,在地形上从前为大陆的一部分,故有陆岛之称”①。故有化型岛屿的普遍存在。的确,在新历史观的概念中,没有任何一个原生岛屿国家,能够独立进化出一种高端文化,并因此“蛮荒”而不遭受诉乃至摧毁。例如日本,据《后汉书》记载,东汉光武帝刘秀年间就有又委倭王”事,日本从这时就开始正式接受汉帝国封号倭王,成为中国附属国。另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岁时来献见云。”倭字本意是丑陋的、矮小的、琐碎的意思。一个“倭”,体现了大陆文化与岛屿文化的尊卑地位及其独尊中原、鄙夷四裔的文意义。再如英国。在罗马化时期的不列颠诸岛,先住民凯尔特人是“低的”,凯尔特语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来自罗马帝国的拉丁语成了列颠的主要语言。条顿化时期,凯尔特人的地位更是每况愈下,只能逃山野树林寻求生存,结果导致土著语言凯尔特语随着凯尔特人的消亡而亡了。
其文化都根基于大陆文化的英国和日本,都是同化型的岛屿国家。历史地来看,这些岛屿文化的诞生,多以大陆军事力量的征服开始。罗马人和条顿人渡海征服不列颠群岛,大和民族征服本洲岛民(大和民族并非日本土著部落,而是从海峡过来的战争逃亡者和政治流亡者)①,均为此例。但征服者征服后便会发现,只靠军事手段无法实现征服的目的,所以随着军事优势的确认,大陆的世俗生活和价值观便开始殖民化到新领地亦即岛的文化中,并不得不从现实的角度来对土著文化和自身文化进行反思,进而形成新的岛屿文化,创造出了适合新的生存环境的文明体系。英国的既与罗马教廷保持相对独立性,又与之相承相袭的宗教革命,以及日本的神道教、情教和佛教三位一体、相互并存的意识形态,均属此类。所不同的是,由于中华文明的中和特质,加之当时移民人口有限且武备不足,这些为日本岛屿带去了冶铁、农耕、医药、纺织、养蚕、建筑等谋生方式的大陆秦汉移民,不可能像罗马帝国军队踏上不列颠群岛那样残酷杀戮先住民,到岛屿上当主宰话语权力的主人,而只能基于仁政传统,采取战国“割地自保,不争王霸”的生存方略,与原住民和平共处地生存。于是,在中国文字的基础上产生了日本文字,在中国“吴服”影响中产生了日本和服,在中国饮食的同化作用下产生了日本料理。所以日本19世纪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第九章“日本文明的来源”中说:“把我国人民从野蛮世界中拯救出来,这不能不归功于佛教和儒学。尤其是近世以来儒学逐渐昌盛,排除了世俗神佛的荒谬之说,扫除了人们的迷信,其功绩的确很大。”②“如果过去我国没有儒学,也不可能有今天”③。因此,如果说大陆文化来源于各种文化的碰撞与妥协,那么,同化型的岛屿文化则来源于大陆优秀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征服与同化。只是到了科学技术使大航海成为一种可能,岛国经济以及岛国军事的独立才得以真正出现,脱离母体的岛屿文化才成为现实,甚至强大的大陆文化也只能望洋兴叹(如率先发起工业革命的不列颠之于保守顽固的欧洲大陆)。在此之前,岛屿文化难以在狭小、封闭的环境中以普遍的社会形式成熟起来,他们的文化不仅来源于大陆,而且他们若不继续从距离最近又较为发达的大陆文明中汲取养分,其文化的根基必然无法成长。
起源于一种普遍的事实,在这普遍的事实中,海南岛文化,显然属于普遍的同化型的岛屿文化,而不是个别的异化型的岛屿文化。有研究表明,如今广西南部的勾漏山,在远古时期直延伸到海南岛五指山;如今海南岛北部和广东的雷州半岛南部还分布有同样的玄武岩层:以前海南原始居民落笔洞人的牙齿,与河南(仰韶文化)、甘肃新石器时代人以及云南现代人的差别不大,不排除人类从大陆迁入海南岛的可能性。由此可见,海南岛是一个古老而典型的“大陆型岛屿”①。这种岛屿文明的性质,使得大陆人口的移入历史相当久远和持续。具言之,早在7000~3000年前,南方“骆越人”(百越族之一)便陆续移入海南岛,成为海南岛的先住民——黎族的祖先。并且早从秦始皇时期开始,至少由于三方面的原因,大陆中原文化便侵入和浸入海南文化之中,逐渐取黎族文化而代之,成为海南文化体系的主体。首先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的政治需要。在这种需要下,秦始皇统一岭南,设南海、桂林、象郡,海南岛属象郡边缘;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伏波将军路博德和楼船将军杨仆平服南越后,在海南岛设立珠崖、儋耳两郡,隶属交趾(越南)部刺史;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九年(43年),伏波将军马援平定交趾,往来南海,抚定珠崖,调立城郭。如此等等,直至隋文帝开皇十一年(591年),冼夫人招慰诸俚僚,十余州归附大陆政权,海南岛才结束了整体性的军事冲突和完成了行政建制,政治的同化才告完成。其次是大陆移民的必然结果。从汉代辟郡建制到隋代设县并邑之间,海南即有大陆人群移入。到了唐宋之际,随着航海业的发达,福建、广东的商人开始落籍海南。尤其是中原大陆战争频繁,导致大陆北方人群南迁,而闽、粤、桂诸地区的大批南方人群则继续南迁至海南岛,海南移民开始形成规模,并到明清二代,达到高潮。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移居海南的大陆人,唐以前仅有2万多人,唐代增至7万多人,南宋时增至10万多人,元代已达17万多人,明代高达50万人,清代中叶增加到217万人。其中,闽人150多万,中原人40多万,客家人20多万,而作为先住民的黎人,仅有20多万人。这种现在在海南人的姓氏中依然可觅其踪的移民运动,为海南岛形成同化型的岛屿文化,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最后是贬官文化的必然结果。唐宋时期,大陆中央政权派系斗争激烈,被称为“蛮荒之域”和“瘴疠之区”的海南成为流放贬谪官员的地方。人数之多(唐朝70余人,宋朝80余人)、职位之高(侍郎、尚书以上的高级官员达50余人)、影响之广、对贬地文化贡献之大,乃全国之最,并为世界文化史罕见。尤其重要的是,这些“独上高楼望帝京”的贬官们,均为中华封建帝国的政治文化精英,他们流贬到海南岛后,或寄情山水,或著文销愤,或开办学堂、教书课徒……因而也就成了大陆文化的自觉的传播者,在用先进的文化同化海南岛文化方面,居功至伟。其中的杰出代表当属苏东坡。苏东坡在贬谪中和镇的三年间,开辟儋州学府,自编讲义,自讲诗书,不遗余力地推行文化教育,培养了大批如姜唐佐、王宵、黎子云等饱学之士,益及全岛,大陆文化日兴,儒道精神日盛。这些精英,为海南岛文化体系创建了重要的主流话语。
如此一来,经过军事征服、人口移入和官员流贬,到了明清之际,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中华大陆文化已在政治体制、社会基础、核心价值观诸方面,基本完成了对海南岛文化的彻底同化,以及海南文化体系的创建。其同化的力度之大、程度之深、强度之固,非其他同化型岛屿所能比。
二
海南岛是个在政治体制、社会基础和核心价值观诸多方面被中华大陆文明深深同化的岛屿。和其他同化型岛屿所遭受的命运一样,在此过程中,海南岛也曾发生过黎族先住民的顽强抵抗。早在汉代,黎族就曾反抗官府强征“广幅布”而攻破郡城,杀死珠崖太守孙幸。而此后的黎汉冲突一直都时有时无,未能终止。即使海南文化兴盛时期的明代和海南文化普及时期的清代,亦复如此。但总体来看,深受大陆农业文明和儒家文化所熏陶的历代统治者,从隋明冼夫人奉众“归附”以后,一直在探讨平黎治黎的问题,并且尽力避免使用武力最终选择了以抚定为主,以讨平为辅的“文治”路线。他们或厚赏赐官;或诰令世袭,世为峒首;或设立社学、延聘教师;或实行“土官、土舍”制度,授以黎族统首各种自治权力。更有清代制定了“抚黎”章程《十二条》,提出了“据其心腹,通其险阻,令其向化”的治黎方针,在统治方法上不断进行改进,所以同化得比较温和,王化得比较彻底。除此之外,明清政府也加大了海南的投资开发力度,架设了一些桥梁,修了一些道路,完成了一些基础建设,遂使海南岛的土地开发、农业种植、工矿企业和对外贸易全面发展,黎汉关系明显改善,黎人汉化明显加强。甚至一些地方,黎族已基本融入汉族,出现了文化交流和联姻通婚,以及“无黎”之说(如“文昌无黎”)。也有一些汉人,“因近黎土,谙晓黎俗”、“利其山水田地,创为村峒,落土藉田”,逐渐同化于黎族之中。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明清二代的海南岛文化,全面吸收了中华大陆文明,形成了“海外衣冠胜事”,出现了一批杰出的文化学者。其中,尤以书院和科举考试为最。
海南的书院始之于宋代文豪苏东坡。明清时期,在东坡书院的基础上,海南书院蔚然兴起,达六十余所,以尚友书院、蔚文书院、琼台书院、溪北书院著名,云集了众多名儒、学者,其特殊的教育方式和优雅的书院建筑,对当时海南的教育以及文化均有重要影响,使海南进入了人才辈出的时代。据文献记载,海南从宋代开始参与中华帝国的科举考试,到明清两朝,不断涌现举人或进士。其中,宋代有举人13人,进士12人;明代则有举人595人,进士62人,文渊阁大学士1人,达到高峰;清代有举人157人,进士22人,虽逊于明代,但产生了当朝探花张岳崧,并得到了皇帝的手谕——“何地无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文化传播过程,并不是岛屿文化对大陆文化的被动接受,而是一种主动吸收及精神向往。所以,其间不仅有普遍的民间响应,还有特别的精英推动,还发生了明代名臣王弘诲“奏考回琼”的故事。由于海南岛孤悬海外,距中原和京师都非常遥远,所以每当科举大考时,主考官惧怕凶险,很少到琼督考,只是驻节雷州,行文调考。海岛学子不得不长途跋涉,劈波斩浪,冒险前去赴考,死伤颇多,以致发生了嘉靖三十六年一次覆没数百人的惨案。基于此,深感“天下儒生之远而苦者,未有如琼之甚者也”的王弘诲,便上奏疏请在海南岛增设考场,由琼州兵备道台兼提学考官,并且获得诏准。其推动海南岛屿文化靠拢大陆主流文化的“形而上”之心,跃然而出。
其实,海南岛民,或者说移居到海南岛的大陆人以及受其同化的先住民,他们向往和吸收中原文化的现象,不仅仅体现在书院和科举考试方
面,而且还发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大陆中原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宗法性,而宗法性又发展为对祖先世系的记载和认知,即来源于“孔氏家谱”的叙谱传统。这种海洋文明中较为罕见而且带有传宗接代意义的叙谱传统,在海南由来已久,而且十分普遍。遍布海南的宗庙祠堂,尤其是那些显然与妈祖庙不同的祠堂,充分说明了海南岛文化体系中大陆文化因子的影响。还有海南民居,海南传统主流民居不仅与北京主次分明、方正对称的四合院非常相似,而且堂屋比其他房屋宽敞高大,在院落中显得特别突出,堂屋中供奉着祖宗神位,是家族礼制的中心。过年过节,婚丧大典或生辰忌日时,家庭成员都会在这里设条行礼,出嫁的女儿回娘家也要在这里拜见父母,鲜明地体现了大陆中原文化循规蹈矩、祖先认同、家长权威的特点。
所有这些现象都足以说明,海南岛作为一个被大陆文化同化的岛屿,始终对其文化的母体持以吸收传承的态度。
三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曾区分过三种不同的地理环境,一是干燥的高地和高地上的广阔草原和平原;二是巨大河流所经过的平原流域;三是处在与海直接相连的沿海地区。第一种地区盛行畜牧业,第二种地区盛行农业,第三种地区则盛行商业。黑格尔说,海洋和河流使人们接近,山岳使人们分离,但“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补充说:“不过海洋使人们接近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到较高的阶段上;而在生产力较低的阶段……海洋却大大阻碍了被它所隔离开来的各个部落间的关系。”①直到生产力发展水平达到可以制造出安全可靠的海上交通工具以前,海洋一直是使人类分割封闭的因素。只有当可以保证较为安全地在海上航行的轮船出现之后,欧洲才打破了氏族血缘集团以及封建主的有效控制,形成平等自由的观念和民主政体;海洋才不再使各民族分割成或大或小的生活单元,居住在地中海地带的各民族之间才得以有了更为频繁的交往,并促进了国际贸易以及资本主义的发展,才出现了反对封建专制的资产阶级革命及其民主政治的代表——英国。作为一个岛屿国家,英国近代崛起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而其中与时俱进的宪政体制(三权分立)的形成与完善,无疑是最重要的结构性和制度性支撑。近代英国正是借此而引领时代潮流,先消灭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又打败了“海上马车夫”荷兰,并在工业革命中迅速成为欧洲强国的。因此,如果说农业文化创造了专制国家,那么,近代英国岛的文化,拥有一个包括海南岛在内的所有东方岛屿文化所普遍缺乏的体制性特点,即由开放而非封闭、不确定而非确定、多元而非大统的海洋所产生的自由平等意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民主制度—宪政精神、法律制度—契约精神、私有财产制度一个人主义精神。这与自给自足,重农轻商、讲求宗法约束之下的海南岛文化,大异其趣。
但是近代英国与西方的海洋文化,尤其与古代地中海的岛屿或半岛文化之间还存在另一种历史关系。古代地中海的这些小岛和半岛,山地丘陵较多,土地也较贫瘠,适合种植葡萄树和橄榄树之类的经济作物,但不适合进行大规模的粮食作物的栽培,这意味着它不可能为文明的发育提供足够的内部资源,只有从战争和贸易中获取必需的外部资源,并建立相应的商业文化。于是,古代地中海海洋文明便在航海和贸易中早就形成了一种思维模式,只要通过武力扩张,建立海外殖民地,控制地中海沿岸,就能攫取大量财富,实现强国梦想。古希腊之于特洛伊战争,古罗马之于埃及征伐,均为此例。延续这种海洋文化的传统,不列颠岛屿文化便具有了突出的扩张主义、重商主义和物质享受主义的色彩。具言之,大不列颠岛系由诸多岛屿构成,隔海峡与欧洲大陆相望,是一个领土面积狭小的岛国。在古代历史中,地中海的罗马帝国扩张入侵过这里,欧洲大陆的条顿人扩张征服过这里,北欧“蛮夷部落”维京海盗也肆虐骚扰过这里,导致从欧洲早期移居而来的先住民凯尔特人,一个个消亡在山野丛林之中。而且,取凯尔特人而代之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在近代全球化的过程中,随着圈地运动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达与本岛资源的衰竭,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后先进的政治制度的形成,随着航海浪潮中强大的海军的创建,以及宗教改革后英国清教徒强烈的个人奋斗进取精神的张扬,又秉承着这种扩张精神,开始成立殖民公司,甚至展开殖民战争,向殖民地倾销商品,同时掠夺殖民地的廉价原料,到海外进行不平等的贸易,获得了财富的流入,获得了原料和工业品市场,一举成为著名的“日不落帝国”。由此可见,领先于欧洲近代化进程的英国岛的文化,是通过征服与开拓殖民地来实现其重商主义的。而之所以必然如此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资源的贫乏短缺。
与海洋性质的岛屿文化不同,海南岛文化显然更具有农业文化的性质。而能够如此的原因之一,也在于海南岛资源极为丰富,人口却不众多,发展空间巨大,并无地中海诸岛以及“圈地运动”后英国那种因为空间狭小或资源紧缺所产生的社会压力,或者说,没有扩张主义和重商主义基础。首先,海南岛有1830公里的海岸线,近海物产极为丰富,完全能够靠海吃海,靠水吃水;其次,岛上又有大片的热带雨林,生长着各种植物4200多种,包括椰子、胡椒、槟榔、腰果、沉香、香茅、剑麻等稀有特产,以及花梨、母生、子京、坡垒、苦梓、红椤等珍贵木材,完全能够立足本岛,靠山吃山;再次,海南岛全境34000平方公里,其中有大量的土地尚待开发,土地潜力很大,根本无须对外扩张。而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唐宋之际的海南人口不过10多万,清代中叶的人口仅仅200多万!总之,无论在移民潮之初,还是在移民潮之末,海南都是一个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的社会,是一个完全可以走农业开发道路的岛屿。事实也是如此,到了宋代,随着汉人增多、文化开化、航海发达,以槟榔、吉贝(棉布)和香料等农产品为主的海外贸易在海南甚为兴盛,其贸易对象是以广州、泉州、福州为主的大陆,兼有马来半岛。而到了明清时期,在大陆农业文明和农业技术的影响下,海南岛的开发更直接地体现在农业生产方面。或者说,海南岛作为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已臻于成熟,形成了大陆性质而非海洋性质的岛屿文化体系。
西方岛屿文化的海洋观,从其海神形象中可见一斑。在古希腊的神话体系中,脾气暴躁而贪婪成性的波塞冬是众神之王宙斯的哥哥,他与宙斯一同战胜了父亲克洛斯之后,一同分割世界,负责掌管海洋,以三叉戟主宰水域,在水上拥有无上的权威,能动摇大地,能呼唤或平息暴风雨,能轻易地令任何船只粉碎。但象征着他的圣兽海豚则又显示出海的宁静和波塞冬亲切的神性。更重要的是,波塞冬不仅神性广泛,而且野心勃勃,常与诸神交战,不满足于他所拥有的权力,具有强烈的侵略性和极大的野心。他密谋夺取宙斯天帝的宝座,但被宙斯发觉,放逐到地上受刑,帮助劳梅顿王修建特洛伊城。力量和权力以及在此基础上诞生的冒险和争霸意
识,是西方海神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唯其如此,爱琴海附近的希腊海员和渔民对他极为崇拜。他们认为,海洋的自然力非常强大,这个自然力中必有一种更强大并能够使其左右的力量,这个力量的化身就是令人崇敬的波塞冬。诚如研究者所说:“波塞冬是海洋的强者,他可以给人类制造种种灾难。从东方人的观点看,波塞冬是个恶神,但古代希腊人重视的不是善恶之辨,而是力量的比较。”①
与此不同,在以岛屿内陆为生活生产环境的海南黎族的宗教信仰中,有山神、地神、灶神、雷公神,就是没有海神;有植物崇拜、动物崇拜,就是没有海洋崇拜;有婚姻禁忌、丧葬禁忌、生育禁忌、做鬼禁忌,但却鲜有海洋禁忌。说明黎族虽然居住在海岛之上,却是一个农业民族。而在海南后来的移民文化中,虽有与海洋相关的宗教信仰,但与西方的海神精神相去甚远。其中的原因之一在于,作为其来源的中国大陆的海洋观相当保守,且具有农业文化的性质。在古代中国人看来,海洋是一个充满黑暗和恐怖的地方。“海”这个字“从水从晦”。晦便是晦暗,便是“晦昏无所睹”,即不可知。这与古代海神传说相辅相成。中国最早的四海海神包括东海海神禺虢、南海海神不廷胡余、西海海神弇兹、北海海神禺疆。他们都是珥两蛇,践两蛇,甚至人面鸟身,与蛇图腾密切相关。随着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四海龙王信仰渐取蛇图腾而代之,其神形成了大鱼或蛟龙。又由于佛教的传入,以及佛经中描述的西天来的兴云布雨、令诸众生、热恼消灭、“无边法力”的特点,无量诸大龙王自然同中国原有的龙蛇形早期海神相融合,名正言顺地取代了原始海神,享用渔民舟子的香火。从此以后,中国东西南北四海全部由四海龙王接管,其成为海中之王,水族统帅和海洋世界的最高统治者。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陆的民间传说中,人格化了的龙王既有为民造福的形象,也有与民为害的事迹。神话小说《封神榜》《西游记》,戏曲杂剧《柳毅传书》《张羽煮海》中,都有善恶不同的龙王出现。尤其是《西游记》中面对孙悟空时战战兢兢地献上金箍棒、黄金甲的龙王,更是几近于小丑。但其原型——不同于大陆龙王传说的海南海龙王则是一位护佑平安、拯救灾难的正神。说明海南先民对潮起潮落、碧波万顷以及水患无穷的南海,不能做出解释,还不具备认识海洋和征服海洋的能力,他们只能抱着一种敬畏的心理来看待海洋,祭祀海神,祈求海神。于是具有“广徕天下财利”和“广利生民”之意的南海广利王,在海南的民间便演变成海龙王和海龙王庙,成为民间崇拜对象。
更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海龙王之外,海南还从大陆引进并创造了一系列女性海神,首先就是著名的妈祖。妈祖的神形像东海女神观世音一样,慈眉善目,和蔼可亲,但又与东海女神观世音有所不同。作为东海女神,观世音是由佛教中的菩萨转化而来,妈祖则是由人死后的魂灵转化而来。妈祖姓林名默,福建莆田人。相传妈祖性情和顺,热心助人,洞晓天文气象,能够“预知休咎事”,有“神女”“龙女”之称。她羽化成仙后,传说身着红装飞翔在海上,每当风高浪险时,“涛雨济民”“挂席泛槎”“化草救商”“降伏二神”“圣泉救疫”,等等,屡屡显灵,被尊为“妈祖”,被宋元明清历代帝王先后封为“顺济夫人”“灵惠夫人”“天妃”“天后”“天上圣母”等,是历代船工、海员、旅客、商人和渔民共同信奉的神祗,影响遍及包括海南在内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妈祖崇拜在海南相当悠久。宋元之际,大量移入海南的福建船民,先是在船上设神主牌位香案各自祭拜,后来在岸上分区位集中祭拜并形成“天后庙”或“天妃庙”。据日本学者小叶田淳《海南岛史》记载,元代的海南岛即建有“天后庙”,而且发展很快。据考证,整个元代,海南岛的妈祖庙仅有5座,明清两代却增加了42座,遍布琼州府的13个州县;数量最多的是文昌县,达11座之多,其次是万宁,有7座①。海南妈祖崇拜之盛,可见一斑。属于这类女性海神的还有来自大陆佛教的观世音菩萨,来自海南本土的水尾圣娘、泰华仙妃和三江晶信夫人,等等。这些女性海神之所以能够与男性的海龙王并驾齐驱甚至备受海南岛民崇拜,在于她们个个慈眉善目,不像海龙王那样怪异狰狞,具有东方的古典美;也在于她们温和慈祥,大慈大悲,乐于拯救苦难,救渔夫于狂风巨浪之中,救岛民于生老病死之中。而且无处不在,有求必应,一呼即灵。体现着男性海神所缺乏的关怀和关爱,更为一般渔夫舟子所接受和膜拜。
总而言之,虽然海南和西方宗教中都有海神崇拜,但性质大不相同。西方海神波塞冬体现了征服、冲突的海洋文化精神,其中那充满紧张对立关系的力量与权力,吸引着人们在精神层面上信仰崇拜;而海南的“海龙王”和“妈祖”,作为正神和善神,他们体现的都是天人合一的大陆农业文化精神,其中那正义与善良,吸引人们在实践层面上祈求乃至迷信,以对付不可知的“恶”。这再次说明,海南和中国沿海地区一样,虽然有着漫长的海岸线,靠海、吃海、用海、观海,海洋文化历史悠久且内涵丰富,但受到黄河文化的深刻制约,有着明显的农业性质。如果把英国式的岛屿文化称为竞争、扩张性质的海洋商业文化,那么海南岛文化则可称为服从、保守性质的海洋农业文化。
综上比较,海南岛作为一个被中华大陆农业文化所持续而深刻同化的岛屿,其文化中既不存在去大陆化的倾向,也不存在扩张主义的传统;既没有东方岛屿文化的狭隘性,也没有西方岛屿文化的冲突性;既缺乏大河文化的宏大性(所以海南古代文学中少有重大题材的叙事文学),也缺乏海洋文化的民主性(因为在海南古代生活中更具话语霸权的不是制度而是宗法),具有自己独立而特殊的文化根性。这种根性,属于非常值得研究的“蓝色的农业文化”。①
关于海南岛文化根性的若干思考(二)
闫广林
一
从社会根性的视角来看,海南是一种多元的历史组合,黎、汉、苗、回四个民族,不同时期先后移居海南并形成了海南社会的基本结构。而从文化根性的视角来看,海南文化形成则更为复杂。这是因为:除极少数富裕的长老能够用金钱或牛马向汉族、黎族地主换得少量土地作为私有产业外,大部分苗人基本上都是租种汉族、黎族地主的山岭。苗族是一个没有文字、没有土地的佃种与游耕民族。而作为一个人数同样不多、居住又分散的族群,海南回族一直群体聚居,自然形成村落,使用自己的语言,拥有自己的宗教,属于一个迄今仍然未被同化的民族。所以,苗族文化和回族文化对于海南文化根性的形成,未能产生主体作用。对海南文化根性产生主体作用的,是先住民的黎族文化、后来者大陆文化尤其是闽南文化,以及给海南带来佛教和基督教信仰的外来文化。但海南文化与这些构成元素又有所不同。
首先是黎族文化。虽然早在宋代就有“熟黎”之说,而到了明代,在靠近汉族的黎族地区的汉化已很普遍,虽然黎族诚实守信、勤劳俭朴、敬老爱幼、团结互助、热情好客的传统,对海南文化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其深山丛林的生活环境,船型屋的居住方式,“峒”的社会组织,“合亩制”的生产方式,黎锦、文身、树皮布和盘条制陶等工艺形式,鼻箫、山歌等艺术形式,以及节日、出生、结婚、死亡、生病等仪式规则,还有100多种的一系列与鬼文化相关的禁忌辟邪法术,以及“道公”“娘母”习俗,并没有在海南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被海南社会所普遍接受,而成为地方性知识的主体。个中原因,应与地理环境导致的文化封闭有关。诚如学者司徒尚纪分析:“至岛内部,山高林密,瘴疠袭人,为少数民族所居,汉人难以进入,多数地区来往稀少,处于分割、阻绝状态。如‘秦以水德王,其数用六。今琼人行使铜钱,犹用六数,以六文为一钱,六十文为一两,六百文为一贯。又田禾以六把为半担,十二把为一担,亦用六数,皆秦旧俗也’。黎族至今传统计算方法仍然如此。鸡卜、钻木取火、文身、不落夫家、夜寮以及古越族一些自然、神灵崇拜等习俗,在大陆上已经消失或残存,但在海南却长期传承,显示海南文化少受外来文化因素冲击,一旦形成或从岛外传入,只要没有强大因素影响,即能长期保存下来。”①
其次是外来文化。海南文化与域外文化的交流始于唐宋,到了明清时期,由于生活贫困、战乱饥荒、海盗掠卖以及经商贸易等原因,移居境外的海南人逐渐增多至数百万。而且在家园情结的推动下,这些华侨、华人在寻根觅祖、回报乡里的同时,也为海南引进了佛教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对海南岛的地方性知识,尤其是建筑和饮食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海南的骑楼。作为一种外廊式的建筑,骑楼艺术历史久远,甚至可以追溯至古希腊的“帕特农神庙”。随着华侨群体的形成,闯南洋的商人将南洋的骑楼样式带入了海口以及海南岛东南沿海的各大乡镇,形成了繁华的商业群和独特的景观线,形成了既有浓厚的西方建筑风格,又有南洋装饰风格,还明显受到印度和阿拉伯文化影响的骑楼艺术。可谓多姿多彩,合而为一。但不可忽视的是,海南骑楼中的中国元素,尤其是外墙浮雕上那精美的百鸟朝凤、双龙戏珠、海棠花、蜡梅花等中国传统的雕刻艺术,以及窗楣、柱子、墙面造型、腰线、阳台、栏杆、雕饰,等等,居功至伟。这种中西合璧的复合风格表明,海南文化已经使外来的诸种文化中国化、海岛化了;同时也表明,外来文化之于海南岛,影响作用不小决定作用不大,缺少文化支配的权力。
再次,作为孤悬海外的小岛,海南岛的文化根性也与大陆文化不尽相同。当然,由移民和贬流官员传播而来的大陆文化是海南岛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构成要素。海南岛以儒为主、以道为辅,以仁为主、以自然为辅,以中和中庸为主、以天人合一为辅的文化,与大陆文化也具有同宗同源的关系。但由于大陆文化在本质上是温带文化、内陆文化和原住民文化,所以也不能取热带、海岛和移民的海南文化而代之。例如“大一统”。从秦汉开始,中国大陆的宗法统治就逐渐被中央集权式的官僚等级制所取代,形成了一套成熟而严格的“三省六部制”政治制度,以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核心价值观,还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伦理,“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道德。显然,大陆文化的这种社会控制和人身约束能力,足以让孤悬海外的海南叹为观止。海南不是广袤的大陆,不是黑格尔所说的人类文明起源的温带,而是一个小岛,一个热带岛,一个从大陆文化中移民而来的岛屿。这个岛屿上的文化如同这个岛屿上的环境一样,植物丰富多样,有的在换叶、有的在开花、有的正处在生长阶段,难以看到某种野果成片地出现,难以看到一种树木一统天下的局面,一种集权的基础。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当推闽南岭南文化。海南学者符永光认为:“五代十国至宋代是我国北方向南方大举移民的第二次高峰,其时移民的方向多从中原往东南沿海诸省大流动,尤其是福建省,以至于形成了人稠地狭的局面。于是,宋代闽人(包括落籍闽南的中原人)开始迁移广东、海南岛乃至东南亚各国。大批的有意识或松散式的移民,沿着粤东的潮汕平原南下,他们跨越珠江三角洲,经粤西、雷州半岛直至海南岛,这是沿着陆路来的移民。而自闽南沿海从水路乘船直达海南岛者,大多在岛北至岛东部的琼山、文昌至琼海一线登陆,形成了宋代闽南人向海南岛移民的第一次高潮,也是海南方言以闽南方言为母语基础的开始。”①此外,经海南学者对海南112个姓氏205位迁琼先祖的调查,表明海南各姓先祖来自于全国各地,其中有65个姓氏123位先祖来自福建,占60%;来自莆田的迁琼先祖就有90位,占44%。②因此有“琼者莆之枝叶、莆者琼之本根”之说,甚至有学者将海南与潮汕和台湾一起,列入“泛闽南文化”。③的确,海南文化中诸多元素如方言、祠堂、牌坊、舞狮、琼剧,尤其是祭祖风俗和妈祖崇拜,均与闽南文化密切相关。但尽管如此,闽南文化仍与作为地方知识的海南文化不尽相同,那宫殿式的“古大厝”建筑,那悬丝傀儡、普度仪式、南音文化,在文化移植过程中不是被改造过了就是被过滤掉了。或者说,作为热带海岛和移民社会的海南,在接受闽南文化的同时使之本岛化了。例如屋顶正脊的建筑。有专家指出,闽南岭南传统民居屋顶正脊多呈弧形曲线,向两端翘起成燕尾之型;琼北民居简化了正脊的形式,两端用脊吻以强调立体感;脊吻形式与闽南岭南的龙凤豪华造型也不一样,多用草尾、祥云图案。在山墙建造方面,闽南岭南较多用镬耳山墙,常以此来显示富贵富有,而琼北屋顶多作硬山顶,多为人字山墙,装饰也较前两者更加简约明快。“这体现了海南人谦虚、低调的生活态度和质朴的情感。”④这种谦虚、低调的特点体现在思想文化方面,就是对大陆儒家文化的不同态度。实际上,大陆儒家文化在闽南文化的发展史上,经常被草根阶层消极地抵制着,甚至出现了一个叛逆的反儒教思想家李贽。但海南却不同,他对儒家文化一直践行着一条全盘接受和全面归化的道路。甚至可以说,唐宋以来的海南文化史,就是一部儒家文化的接交史。
海南军坡节最初与岭南文化中的冼夫人崇拜有关。冼夫人的军队最先驻在新坡镇,人们在安居乐业之后,为感激冼夫人而举行模仿当年出军仪式的活动,故此得名。后来,“军坡”活动融进了更为丰富的内容,军坡节成了海南凌驾于地方道德观和其他民俗文化之上的最主要的神道节,所拜祭的对象也逐渐演变成当地曾经存在过的杰出“峒主”“境主”或者“祖先”及其生日,亦即“公期”和“婆期”。所以军坡节虽然多集中在阳春二三月,但却没有统一的日子。文昌文城镇是正月十三,海口新坡镇是二月初六,定安定城镇是二月十二,屯昌屯城镇是二月二十五,文昌东郊镇甚至每年有两期。而有些乡镇,既有共同的军坡节,各村还有各自的公期;既供奉较大的神祖“大公”,又供奉各自的神祖“小公”。多元性、多神性和不充分性的特征相当突出,说明在移民社会的公共意识里,只要具备足够的道德威望和能力,包括祖先在内的任何领袖都可以成为他们崇拜的神。所以海南人从一个地方搬家到另一个地方居住以后,就会立即放弃原来的军坡节,而改成新居住地的军坡节,原来拜祭的神也随即放弃,而改拜新居住地的神。凡此种种,均与崇尚境主的闽南文化密切相关,而与移民性质尤其是贬官色彩并不十分突出的岭南文化相去渐远。至于军坡节中颇具道教神秘色彩的各类“穿杖”节目,更与崇高性质的岭南巾帼英雄(谯国夫人、岭南圣母)大异其趣。
文化有意识形态和非意识形态之分,意识形态是想象性的“社会意识”或价值系统,是一个社会非正式约束的核心,或者说是社会中每个人的思想、信仰和行为都受其支配的准则和规范。而且,这种已经被某个群体所接受的体系性的社会意识融于生活特别是成为习惯时,就会成为集体无意识,使之自觉遵守并持之以恒。即所谓“道在伦常之中”和“日用而不知”。美国当代著名的人类学家吉尔兹认为,人类所赖以塑型的意识形态,就社会决定因素而言,存有利益论和张力论两种研究路径。在前者看来,意识形态是一种面具或武器;而对后者来说,意识形态则是病症和处方。在前一种可能性中,人们追逐权力,所以应在争取优越的斗争的背景中加以考察;而在后一种背景下,人们逃离焦虑,则应在修正社会心理失衡的漫长努力背景中来进行考察。由此可见,与更具革命性质的利益关系不同,张力关系既是一种充满对抗性的紧张关系,又是一种富有吸引力的合作关系,而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的海南文化,与其说是权力关系下的意识形态,毋宁说是蓝色的热带海岛文化和大陆的农业文化之间张力关系下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表明,受到狭小性和边缘性的地理条件的限制,古代海南不可能独立创造出自己的文化体系,只能步入一条吸收性的道路,从大陆吸收文化元素,但孤立的海岛生存又使他所吸收的诸多元素在这里汇成现世主义的文化品格。
二
同样是岛屿文化,但英伦理想国的归宿是理性,日本理想国的归宿是神道,海南理想国中的归宿是至尊至善并超越一切批判视野的祖先。祖先崇拜是海南岛的精神支柱和文化灵魂;以此为支点,海南历史不自觉地建构起了一个亲情和人情的社会。
其实,作为海南的先住民,黎族就是一个祖先信仰的民族。只不过,黎族的祖先信仰不是崇拜,而是敬畏,原始宗教性质的敬畏。原始宗教的发生原理在于,人们以集体的力量和简陋的工具与自然界做斗争时,一方面逐步认识到人们的生产活动与某些自然现象的联系;另一方面又对许多诸如风雨、雷电、日月、死亡、生育等自然现象和人类自身的现象进行万物有灵的朴素理解,认为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存在于自然之中。于是,敬畏与崇拜、恐惧与希望交织在一起,各种禁忌和巫术油然而生。黎族亦复如此。具言之,相信“灵魂不灭”的黎族人历来就认为,生命生时灵魂附于躯体,死后灵魂独立存在,或栖附于其他物体,或往来于阴阳两界间,或游离于亡者的村峒住所近处,成为鬼魂。人们只能用巫术的方式来敬畏,或请鬼公、娘母“作鬼”来驱邪,或以作法的方式来消灾避难。而且在黎族鬼魂体系中,“祖先鬼”是最大的鬼,和雷公鬼一样可怕,比其他鬼还要令人敬畏。即所谓:天上怕雷公,人间怕禁公,地下怕祖公。所以黎族便形成了诸多严厉的祖先禁忌文化,如平日禁忌提及祖先的名字,唯恐触怒祖先而招致灾难。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习俗在汉族文化的影响下,特别是在道教文化的影响下,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即从“鬼”向“神”的转变,并呈现巫道结合的特点。在这种转变中,“祖先鬼”已经淡化了对家人施以各种灾祸的能力,并有了“神”的内容和保护家人平安、牲畜繁殖、庄家丰收的“善”的意义。于是,黎族对“祖先鬼”由畏而敬,祭祀性质由恐惧而祈福,宗教目的也有了敬祖尊先、慎终追远的大陆人伦礼仪和道德情怀。
与黎族原始的祖先崇拜不同,海南汉人的祖先崇拜因移民的原因而明显呈现宗族化的特点。宗族观念是中国历史上盛行了几千年的文化观念,但对海南来说,似乎要特别突出一些。所以如此的原因在于,海南岛是个移民岛,从中原和闽粤以及广西南下驻琼的大批移民多以同姓同宗聚族而居,规模较大且人口较多的村落一村一姓,反之则一村多姓。这种宗族性质的村落组织是海南社会的基本结构,并使得社会成员产生并保持了祖先崇拜的传统,自觉和不自觉地在与祖先的关系中确定自己的位置和等级;使得他们相当重视血缘和宗姓关系,比较缺乏天下意识和终极关怀;使得他们固守于某一村落,对外部世界缺乏好奇心和交往动力,形成了保守主义的文化品格。一言以蔽之,祖先崇拜早已成为海南宗亲文化的历史起点,而宗亲文化也早已成为海南地方文化的逻辑起点。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孤悬海外,长期闭锁,远离中国政治的中心,因为较少受到大陆那样由于战争征伐、权力斗争、改朝换代等重大事件的革命性冲击,所以这种以祖先崇拜为中心的宗亲关系及其文化,在海南得到了更加纯粹的继承和更加顽强的坚守。以至于可以说,祖先崇拜已成为海南岛的文化根性之一。在这种崇拜中,所有家族成员都必须与自己的祖先建立起一种想象性关系,与社会建立起一种话语权力,并通过一系列的方式予以隐喻或实现。
首先是民居。海南主流民居是大陆四合院文化的延续,但又有自己的特色,诸如郁郁葱葱的居住环境、“龙翅”和“云公”的屋顶建筑、四面通风的结构设计、俗称“飘廊”的挡风遮雨功能,等等。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更具祖先崇拜意义的“堂屋”文化。大陆四合院的“四”字表示东南西北四面,“合”则表示围在一起的意思。也就是说,四合院是由四面的房屋或围墙圈成的一个封闭空间;只要关上大门,四合院内便形成一个独立自足的小世界,而中堂便是这世界的中心。在这个中心中敬奉着不同的神位。其中,观音位于左方,以凸显其地位,其余神明位阶不分上下并设于右方,而祖先牌位往往被安放在神位中最低的位阶,不能超越于诸神明之上。①与此相应的是,在这个中心中还会悬挂着一些书画作品,喜欢精英文化的挂诗词字画,喜欢世俗文化的挂“福、禄、寿”,官宦人家挂激励子孙的对联,而经商人家则多用吉祥如意、恭喜发财的对子。如此多元的文化元素在中堂这个小世界中构建了一个礼仪文化空间,而祖先崇拜文化仅居其一,尚未达到唯我独尊的高度。海南民居特别是民居中的“堂屋”则有所不同,虽然在这里也有其他元素存在,但却更集中地体现了祖先认同主题——“屋”。因此在选址上,“屋”只能选在自己的祖地,不能占用其他的土地;在动土之前,要请来风水先生给“屋”看风水定阴阳,定良辰吉日;在“起屋”之时,要邀请同宗同族成员,一同祭祀土地爷,祭祀祖先;在新房建好之时,还要举行“进屋”仪式,宴请前来贺喜的三亲六戚、左邻右舍。而从建筑格局来看,海南之“屋”的祖先崇拜主题更为突出。海南传统民居系由“正屋”和“横屋”两部分组成。“正屋”的主体是堂屋,堂屋的主体是客厅,客厅里设有三殿堂,供奉祖先神位和道德格训。年时节下,生辰忌日,婚丧大典,在此设祭行礼;贵客临门,在此接待;女儿回娘家在此拜见父母;甚至上年纪的老人,也会守在客厅以待归天。他们认为,如果在屋外逝世,就成了孤魂野鬼,以后必须做佛招魂,方能上得灵位,与列祖列宗一起接受在世亲人的祭拜。对于海南人来说,堂屋是家园和家族的象征,是祖先崇拜的外在表现,只有儿子或者长子才能继承。所以在海南方言中,“屋”字涵盖了“家”“室”“房”的意义,“有屋有头”就是说有产有业、有根有基,光宗耀祖。一字之中,包含着血脉相承、薪火相传的隐喻。
其次是宗祠。宗祠或称家庙、祠堂,是本姓氏奉祀祖先神位的建筑,也是血亲村落最重要的建筑,有着很强的神灵色彩和精神家园、血缘纽带的意义。中国大陆的姓氏宗祠文化很早就与郡望——门阀文化联系在一起,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政治生活。“郡”是行政区划,“望”是名门望族,“郡望”表示某一地域的名门大族。这些高门大姓一般地说由家族人物的地位、权威和声望自然造成,一旦形成则显赫无比,十分威严,并世代传承,成为所谓“门阀”,亦即门第阀阅。有时官方还做明确规定,宣称某姓为望族大姓,具体划分姓族等级,确定门阀序列以及特权。而与高门望族相比,门第较低,家世不显的家族则被称为“寒门”“庶族”。他们虽然也有一定的土地、财产,其成员也有入仕的机会,但总的说来,其社会地位无法与门阀士族相比。其结果便是士庶不同。出身于名门望族的“衣冠子弟”,即便无才无德,也能列为上品优先入仕,得授清贵之职,而出身孤寒的庶族子弟,即便才德超群,总被列为下品,即使入仕,也只可能就任士族所不屑的卑微之职,以致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甚至“士庶之别,国之章也”。
政治色彩十分显然。而海南的姓氏宗祠则与政治基本无关。具言之,海南的姓氏宗祠都源于渡琼始祖的崇拜。尽管其中有的始祖来自内陆,有的来自闽南岭南;有的属于朝廷命官,有的属于朝廷贬官;有的避乱入琼,有的经商落籍;有的是迁居入琼者,有的是宦游来琼者;有的是举人进士,有的是武将出身,还有张氏宗祠的张岳崧为海南历史上唯一的探花。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除了曾氏宗祠以及符氏宗祠的始祖,或为中国历史上圣贤以及望族的后裔外,多数宗祠的始祖之所以成为始祖,并非其“郡望”身份而是其宗法力量和海南岛的生存环境所使然。因此,人们建设宗祠这种族人群落在精神层面的公共财产,并不是要获取和维护某种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而是要在这里敬奉祖先,记载祖训,举行祭祀仪式,保存全族的派系、行辈、婚姻及其历史渊源,让族人感受到本族变迁、发展的轨迹。春节、清明、中秋、冬至等重大节庆,以及凡是家有要事,如结婚生子等,一般都要来这里“告慰”先人。由此可见,作为祖先崇拜的一种存在形式,宗祠完全属于宗族血亲的圣殿,郡望性质的政治色彩及其权力意义并不明显。
最后是家谱。如果说宗祠是与姓氏有关的物质文化,那么家谱就是与姓氏有关的非物质文化,是以记载一个血亲家族的世系与事迹为主要内容的历史文献。而且,虽然许多欧洲国家都有家谱族谱的传统,甚至像意大利的罗伦佐家族那样,记载了该家族十分重要的历史贡献,但相比之下,中国家谱文化更加源远流长和普遍化。所以自夏商以来,中国不仅王室有家谱,诸侯及一些贵族也有家谱,政府还曾设专门机构进行家谱管理。屈原官居三闾大夫,其主要职掌就是掌管楚国昭、景、屈三族的三姓事务,编制三姓的家谱。相传荀子也曾编有《春秋公子血脉谱》,“血脉”二字生动形象地揭示了家谱的本质。直到清代,中国家谱文化依然十分发达,而且愈演愈烈。所以当时的著名史学家章学诚说过“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家乘谱牍,一家一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①把家谱与国史、方志相提并论。家谱如此重要的原因,在于其中的家规族训,不仅具有规范人生和教育子弟的道德功能,而且具有维系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加强文化认同的团结功能。所不同的是,古代海南“编户之民”很少,姓氏总量偏少,多集中在王、陈、符、李、黄、林、吴几大姓中,而且家谱文化的移民主题十分突出,均记载了渡琼始祖在海南的丰功伟绩。与此移民文化相对应的是,海南各宗姓之间和睦相处,并未形成生存地位上的士族与庶族的等级关系和紧张关系。因此使得海南的家谱文化各问其祖,各寻其根,各自进行自己慎终追远性质的文化认同,以通过祖先崇拜而获得最可靠、最永久的血脉依凭。即使在多姓的村落中,也无小说《白鹿原》中白鹿两姓那种充满恩怨的权力斗争。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随着历史的发展,海南的祖先崇拜从一个血亲现象演变成了一个社会现象。以至于可以说,整个海南就是个由祖先崇拜延伸而来的恩情世界,其中的子女与父母、兄弟与姐妹、宗亲与外戚、师生与朋友甚至所有的人,都因为生命或生存与恩情构成了一种或核心或紧密或松散的情义关系亦即社会秩序,而孝与忠则是维系这情义关系的基本义务和行为准则。规范之下,每个人都不再是单独的个人,而是这个情义世界的组成部分,并和邻近的人构成另一个情义世界。每个人都要明白自己的位置,并将“孝”和“忠”奉为必须履行的最高责任和准则。因此,他可以为“孝”去牺牲幸福和生命,也可能因为不忠而成为不义之人,受到社会的谴责与惩罚。这种无私的超功利的情义精神,体现了岛屿生存的团结需要,因为古代岛民只有依靠“群”的力量才能够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和发展。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说:“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①在这方面,特殊的地理环境,使义务和责任均成为行之有效的道德律令的海南岛,颇具“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性质。
三
当然,团结的需要是人类古代社会的普遍需要。在“日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的远古社会里,人类只有通过集体协作的方式才能生产和生活,而血亲组织是集体协作的不二选择。于是,以血亲为基础,以部落为形式,以集体主义为精神,自然而然地成了原始氏族社会的一个共同属性。一直到阶级诞生以后,家族—部落式的血亲组织才逐渐被国家这一更高级的社会组织形式所取代。后来的差异在于,古希腊的“梭伦变法”一举摧毁了氏族公社制度,并经由古罗马的继承,早已使西方的“族人”关系让位给“公民”关系,血亲制度让位给民主制度。而在农业中国,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血亲制度或者说宗法制度却世代相传,甚至还以伦理纲常和政治制度的形式获得了话语霸权,以至于发展成为“家族本位”的中国“伦理法系”精神。在这种精神的支配下,家长对家庭成员管理的“规矩”就是家法,家族对国家管理的规矩就是国法,甚至成为超越法律原则的一种意识形态。伍子胥为报父仇,叛国、投敌、弑君,实属罪大恶极,但在人们心中,他仍然是正面的英雄,原因就在于“杀父之仇,不共戴天”。随后,战国时期发生在各个诸侯国的“变法”运动,对代表家族利益的“家族本位”形成重大冲击。“变法”最重要的内容是“隆君”“重法”。“隆君”抬高了君主和国家的权威,变贵族(家族)制为君主制,变“家族本位”为“国家本位”;“重法”抬高了法律和制度的权威,变“礼治”为“法治”,变众家族之“家法”为君主独裁之“王法”。从此,“朕即国家,朕即法律”便成了不可置疑的绝对真理,家家户户也成了“天然的皇权主义者”。而且从汉武帝时期起,儒家容忍代表“国家本位”的专制皇权,法家也容忍代表“家族本位”的宗法伦理,中国社会开始从强调礼法对立转变为提倡礼法合一。例如二者结合的典范——《唐律》,其“十恶”中“谋反”“谋大逆”“谋叛”“大不敬”所维护的,显然是“国家本位”的专制皇权和中央集权体制,而“恶逆”“不孝”“不睦”“内乱”四条所维护的,则显然是“家族本位”。
海南的问题在于,无论从历时性还是从共时性的角度考察,都没有完成从“家族本位”向“国家本位”的转变,以至于各种由“家族本位”所产生的地方性的“习惯法”,在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中一直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历时性地来看,汉王朝在海南设置郡县,实行“遥领”;隋王朝赐冼夫人“临振县汤沐邑一千五百户”,认可了冯冼家族在海南岛的统治;唐王朝在崖州设都督府,又设琼州都督府统管全岛;宋元王朝海南先后隶属于广南西路、湖广行省、广西行省;称海南为“南溟奇甸”的明太祖朱元璋,在登基的第三年也就是1370年,海南隶属广东,把琼州升格为府,大修府城、州城、县城,调查户口,丈量土地。从此,海南才有了统一的治理结构,才不被看作蛮荒和流放之地,即所谓:“前代珠崖郡,今日少窜臣。”由此可见,直到中国封建政治文化十分发达和严格的明代,大陆对海南的“王化”才告完成。而且在此过程中,由于统治者对这块遥远边地的轻视,中央政府对海南的控制时断时续,海南的行政区划时弱时强,海南黎族百姓的造反活动时有时无,导致王权的霸权力量远不如大陆那么强大。所以王安石变差役法为免役法后,“天下无复有邮差为吏之州,独海南四州不行焉”。于是,神宗只好下诏,仅海南岛罢免役法而仍旧令服差役。①在此“梗化”的背景下,海南的基层社会组织的“自治”作用也就更加重要了。
共时性地来看,海南的村落组织可以分为:作为山区居民地点的抱或者番,作为比较原始的氏族部落组织的峒,作为苗族游居地点的山岭苗,作为回族居住区的羊栏,还有诸多汉族居住区,如以原籍名命名的东山、东坡、东阁、蓬莱、铺前,以军事移民命名的所、亭、屯、都、堡、营、台。而且峒有峒首,村有村老,亭有亭长,以血亲家族为核心的村落组织相当牢固。例如峒首。实际上,峒首已经握有超越氏族长老所有的军事和行政权力,是一个黎区的军事长官和行政长官,甚至政治领袖。在他的领导下,峒有自己的规矩,土地共有,共耕分收,抵御外辱,保卫家园。这种移民性质和家族性质结合而成的社会结构,更支持了地方“自治”及其习惯法。
习惯法是一种源于生产生活的地方性习俗、信仰、规范,一种与条文法相对应并具有普遍性和权威性的习惯做法。法国著名的比较法学家勒内·达维德认为:“中国人解决争端首先必须考虑‘情’,其次是‘礼’,最后是‘理’,只有最后才诉诸法。”“中国人民一般是在不用法的情况下生活的。……他们处理与别人的关系以是否合乎情理为准则。他们不要求什么权利,要的只是和睦相处下和谐。”①在这乡土社会、礼治秩序、长老统治方面,由于没有完成从“家族本位”向“国家本位”的转变,海南的状况似乎更为突出。
首先,习惯法就是海南先住民黎族中普遍存在的民间法。如前所述,在社会体制方面,黎族的基层组织为“峒”;峒的地域一般以山岭、河流为界,并且立碑、砌石或栽种树木作为标志。黎族百姓称呼他们的峒领为“奥雅”亦即“老人”,说明原始氏族社会的长老观念仍存在于民众意识之中。峒内成员的行为都有一定的规范,以世代相传的传统习惯为一切行动的准则,对峒的疆界和其他成员负有保卫保护的责任;如受到外峒人欺侮时,必须为其复仇,并共同负担械斗时的费用。诸如此类的行为,主要靠习惯法来维持。在法律方面,黎族传统习惯多是民法与刑法合二为一,司法大权掌握在峒长、哨官、头家手中,一般案件由头家处理,大的案件由哨官或峒长裁决,处理不了才上报县衙,交由条文法处理。而且在黎族习惯法中,对通奸处理较轻,对盗窃处理较重,对本村人处理较轻,对外村人处理较重,对峒里人处理较轻,对外峒人处理较重。穷人少罚,富人多罚,穷人无力赔偿,家族或氏族分担赔偿的责任。除此之外还罚牛、猪、鸡、酒、谷慰劳峒长和其他长老。在财产关系方面,峒管辖的范围神圣不可侵犯。峒内的土地、森林、河流未经许可,外人不能越界砍山开荒、采藤、伐木、打猎、捕鱼和居住等。或者须经本峒许可,还要上缴一定数额的物产给峒长,这些物产由峒长和峒长所居住的村庄的奥雅享用;村与村之间也不能越界砍山开荒、采藤、伐木、打猎、捕鱼,违者峒长负责仲裁,罚款赔偿。此外,婚姻家庭关系的各种规范也是黎族传统习惯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各地区各方言都有自己的婚俗,同一方言不同地区的婚俗也有差异。一般为一夫一妻制,多在本民族本方言内择偶,但严格遵守氏族社会族外婚制,即不同血缘集团才能通婚。如此等等,表明海南黎族社会是一个由习惯法所维系的地方自治社会。
在这方面,海南汉族社会与黎族社会大有异曲同工之趣。具言之,海南汉族不仅是一个血亲的社会,还是一个与“家族本位”密切相关的习惯法的社会。因为封建王朝只能把政权机构设立到州县,而将广大的乡村权力空间让渡给地方乡绅。这类人多属乡间长老,识字识历,有财有势,协调能力较强,因而受到普遍的拥戴,成了各种纠纷的仲裁者和可以同官府打交道的头面人物,人治与礼治的具体操作者。诚如日本学者小叶田淳所说,宋代海南,“长官是知县,有通判辅佐,镇有监镇官,乡有乡户,又设有称为耆户长等等的长老,关于警察催税等等,都听从长老的指圖”①。海南崖州的“父兄”就是如此。“父兄”既不领俸禄,也不问政务,只依“乡规民约”仲裁邻里纠纷,公正分家典田,主持婚丧礼仪。其势力范围或仅及族内,或波及全村,或四野六乡,乃至可以蓄养兵丁,缉捕盗贼,处死人犯。只要不触犯官威,便可相安无事。如对盗贼的惩治:着人将盗贼按到板凳上,或反手向后吊上榕树,用扁担或竹编狠狠抽打,还让早在一旁待命的歌手歌唱,进行讽刺挖苦,教育众人不可学坏。②所不同的是,海南汉族的习惯法不仅约定俗成,而且得到了勒石刻碑,以示标志。海南的乡规民约即是如此。具言之,海南的乡规民约所体现的习惯法,一般以禁碑为载体,这些禁碑既有“官府示禁”之碑,但更多的是“奉官示禁”之碑,且多立于约亭之中。所谓“约亭”,通常是乡村文人儒士吟诗作对、联谊交友之地,同时也是乡村士绅传达官府谕示、讨论重大事务的地方。禁碑放置约亭,既体现了乡民们的高度重视,又方便乡民接近禁碑,为禁约的内容能够深入人心奠定了基础。从名称可以看出,具有禁约性质的海南乡规民约,虽属民间行为,但须官府认可。一方面,包括立约原因和奖罚标准在内的禁约条文,须根据当地生产生活的实际情况,经过乡民们的充分酝酿和商议,再署上“首事”(即倡导人)及父老的名单呈报官府。另一方面,官府同意禁约。例如文昌龙楼镇的一块奉谕示禁之碑:
近来盗贼滋甚,此非风俗之偷,实由乡禁之不显耳。遍开名都,图皆有弭盗要策,独我处此举未备。今圆得云梯岭四面,遵圣谕联保以弭盗贼之条,称家捐资生息,以资巡×(碑文不清,以×代替,下同),严赏罚务,使游懒者警,狗盗风熄,将人皆托业农,有所储士,有所储立,见风俗还淳,则乡×之中,虽赏不窃矣,敬将条规开勒于石:窃盗家财衣服耕牛捉获者,赏钱乙千六百文,窃盗罚钱演大戏三本。窃盗家器物件捉获者,赏钱五百文,窃盗罚钱演小戏三本。窃盗田园物业捉获者,赏钱乙千五百文,窃盗罚钱演小戏六本。窃盗小六畜海子棠,乱砍青叶树木各物件者,随众议罚,捉者随众议赏。窝盗者与捉盗私和者,加倍议罚,有家当为盗者,任众重罚,捉者赏亦加,接贼者同窝论。凡捉盗者,俱要连状送出方准有赏,不得凭例,呈凶过甚……①
由此可见,海南古代的乡禁虽然不是政府法律,却具有法律的作用,而且具有自我保护的乡民自治的性质。所以在保护乡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农业生产和经商活动、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管束伤风败俗的行为、倡导黎汉团结的一般内容中,在“禁刀斧不得入山砍”“禁盗砍芦林竹木”“禁不得盗割竹笋”,以及禁赌、禁抢、禁盗的习惯条文之外,更以排他性的禁约警告邻近乡村,充分体现了“自治”性质。即“遍开名都,图皆有弭盗要策,独我处此举未备”。凡此“有上述行为之徒”,或被绑起来让父老杖打,然后游村示众;或由官府“以凭拿究,决不稍微宽待”。如此看来,海南古代社会秩序并不十分安定,乡民忧虑之下,便请求恩准勒石示禁,“家族本位”的性质显而易见,而“奉官示禁”一语,则清晰表明了禁碑乃是私权与公权的结合。于是,乡规民约因官府的认可成为国家在地方的民法或习惯“法”,国家管制因乡规民约实现其“法治”化,最大限度减少了国家法律的执行阻力。可谓相得益彰。
值得关注的是,人类历史上的许多国家和许多时期,都出现过地方自治的力量和现象。如中国大陆的乡绅集团以及乡绅自治,英伦岛屿的贵族集团以及庄园自治,日本列岛的大名以及领地自治。但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大陆的乡绅集团走上了既依附于专制皇权又以施仁义道德来约束官员的儒士道路,英伦贵族集团走上了一条既与国王斗争又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底层民众基本权利的绅士道路,日本列岛大名集团走上了一条既受幕府控制又有地方武装的军事道路,而海南的长老、父兄阶层却仍然停留在家族宗族的阶段,社会化和政治化的能力尚不发达,公权与私权、条文与习惯处于弱势平衡状态;在这里从来没有形成一个大陆式的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
四
西方文化,是一种典型的“罪感文化”,相信人人有原罪,人人有罪,所以强调忏悔和赎罪,希望借此来减轻自身的罪,从而得到心灵的安慰。日本文化是“耻感文化”,“重视耻辱感远胜于罪恶感”①。日本人的耻辱感,来源于他们对名誉的高要求,来源于他们敏感的脆弱的自尊心。“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最大的区别是在对待“罪”的态度上:前者只有耻辱感,而无罪恶感,哪怕干着的是十恶不赦的大罪恶;没有忏悔和赎罪之说,即使认识到自己的确犯了罪,也是如此。而中国文化,则是一种乐感文化。李泽厚认为,中国文化精神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罪感文化的乐感文化,它立足于此岸世界而强调自强不息、乐观积极的精神状态,尽管千辛万苦,也要乐于眺望未来。具有“乐行之,忧则违之”(《周易》)的乐天知命的乐生特点,相信只要前仆后继、百折不挠,就会否极泰来、柳暗花明。所谓:“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但乐感文化也有其消极的性质:由于讲究“实用理性”,讲究变通,导致中国人整体耻辱感、罪恶感的缺乏,“内心的自我约束力”的缺乏;导致形而上的终极追问能力的缺乏。蓝色的农业文明所哺育起来的张力性的海南意识形态,就是一种乐感文化,一种以人的现世性为本的乐感文化。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中江兆民曾经说:“我们日本从古代到现在,一直没有哲学。”②海南亦复如此。
当然,海南意识形态中也有形而上的“道”的追求,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浸润下,才产生了大陆主流文化中不普遍的“牌坊”文化和并不存在的“从道不从君”的思想。牌坊起源于汉代坊墙上的坊门,门上榜书坊名以为标记,宋以后随着里坊制的瓦解,坊门的原有功能消失,但坊门仍然脱离坊墙的形式独立存在,成为象征性的门,立于大街、桥梁的显要位置。经汉代的“榜其闾里”,唐宋的“树阙门闾”,至元明清已发展为“旌表建坊”,即对政绩、及弟、长寿、守节等进行表彰,具有了“道”的意义。据史料,海口市文山村,原有明代进士举人牌坊“折桂坊”“毓秀坊”“登科坊”“文魁坊”“科甲联芳坊”等多达15座,记载着文山古村周氏家族“文士接踵,官员济济”的盛况。而海口市攀丹村原有明代进士举人牌坊“青云坊”“天衢坊”“省魁坊”“进士第坊”等也多达11座,记载了攀丹村唐氏名门“累朝衣冠蝉联,英才辈出,代不乏人”的荣耀。以至于可以说,海南岛就是一个牌坊岛。①关于“从道不从君”的思想,海南更为突出。尽管大陆主流文化中也有谏官文化,也出现过名臣魏征,但他们在侍明君的立场下,常常谏言不露,“密陈所见,潜献所闻”,难以“从道不从君”,难以坚持守道精神、产生批判意识,而海瑞之所以备受争议,“大逆不道”,或许正是因为他的这种守道思想和行动与大陆文化的差异所致。他在户部云南司主事任上,目睹了皇帝的昏庸和朝政的腐败,深为天下百姓的安危而担忧,更为大明王朝的内忧外患而心急如焚。如果上疏劝谏,必然是死路一条;如果袖手旁观,又大失忠臣之道。终于列举事实,冒死为国家和百姓,上疏抨击皇帝,以实现他一生追求的“武死战,文死谏”的道德目标,将一份措辞十分激烈的《治安疏》呈给了皇帝。“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言人所不敢言”,“触人所不欲言”,震动朝野,惊动皇帝,险些丢掉身家性命。
但是,在海南意识形态基础上所成长起来的这种伦理道德和政治道德,少有终极关怀的意义。作为哲学智慧的终极关怀,是一种超越有限追求无限,以化解生存和死亡紧张关系的终极性思考。在实践理性的引领下,中国古代圣贤一般不去进行这种务虚的精神活动。即所谓的“道可道,非常道”(老子),“不知生,焉知死”(孔子),“以有涯随无涯,殆己”(庄子)。海南牌坊文化和海瑞思想中的“道”,亦复如此,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海南古代书院与大陆古代书院的一个重要差别,就是始终处于礼仪文化的教育层面,“以诗书礼乐之教,转移其风俗,变化其心”,普遍缺乏问天、问道的哲学内容,以及天下关怀的忧患意识。推而广之,海南文化重感觉,轻抽象;重经验,轻思辨;重道德,轻忧患。其结果便是,文化建构力度不强、主体地位不高、话语权力不大,始终未能与大陆主流文化之间形成一种对话关系,其话语权力与同属于中华文化子系统的闽南文化难以相提并论。闽南颇富文化底蕴,正如泉州文庙对联所说:“圣域津梁,理学渊源开石井;海滨邹鲁,诗书弦诵遍桐城。”根基于这个文化底蕴,朱熹创建的书院及其闽学,便因其形而上的思考而曾对中国古代思想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哲学贡献。如果说,宋儒革新了汉代以来的儒家道统学说,将儒家经学传统拓展为关于政道、经史、文章的文化学术,那么,闽学则由此转向文化的心性义理,成为性理之学或宋代新儒学中的新儒学,朱熹也成了继先秦孔孟、汉代董仲舒、唐代韩愈之后最伟大的儒学大师。如此重要的理论贡献,非海南文化所能企及。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注重世俗幸福的大陆农业文化,试图消解焦虑的海岛生存,远离政治中心的地缘环境,诸如此类的因素使追寻乐感乐生的现世倾向成为海南乐感文化的主流,进而从现世主义倾向发展成为现实主义精神,支配着历代海南人的价值观。
首先是安贫乐道的人生态度。这种在海南比较普遍的人生态度似乎与贬流文化相关。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安贫乐道、快意生存素来是中国重要的人文选择。海南亦复如此。那些被贬谪的精英们身处“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交无友,冬无碳,夏无寒泉”的“蛮荒”之地,有人壮志未酬,“独上高楼望帝京”(李德裕);有人黯然神伤,“白首何归,怅余生之无几”(赵鼎);但是已经不能兼济天下的流放者们,更多地像苏东坡那样,选择了独善其身的道路,安贫乐道,快意生存。诚如斯言:“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①于是,他怀着对老庄思想的浓厚兴趣,追随陶渊明,写了大量的和陶诗,办起了“载酒堂”,在海南过了三年的隐士生活,写下了大量的诗词文赋,给海南留下了“一蓑烟雨任平生”的精神遗产。
其次是闲适优游的人生情怀。诗是一种阐述心灵的文字,“感其况而述其心,发乎情而施乎艺也。”借此心灵文字,我们可以看到:“五指山光胜九华,版图曾奏汉王家。窠中老人多遗世,被里官闲早放衙。橄榄香回茶后美,蝤蛑鲙出酒余嘉。薰风座上羲皇客,一曲雍容咏天涯。”“地极南堧萃物华,竹垣深浅里人家。儿童总解藏私货,父老无由识县衙。藜子熟时村酒酽,甜茹拙处野肴嘉。东风不负凫鷖约,白首同归醉天涯。”①在诸多的心灵文字中,我们对海南文化之闲适优游的追求也可略见一斑。司马迁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奋(愤)之所为作也。”(《史记·太史公自序》)但唐宋以来海南的古代诗歌中,却鲜有“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的忧患意味,更多的是颇具老庄精神的咏物咏怀。如邢宥的《休归咏怀》:“脱却樊笼得自由,家园万里望琼州。花看晚节添幽兴,人忆同时觅旧游。一枕黑甜山舍午,半樽白泼水亭秋。归来已定栖身地,独愧君恩未应酬。”②
最后还有乐观主义的艺术传统。千古绝唱《梁山伯与祝英台》本来与《白蛇传》《孟姜女》《牛郎织女》一样,属于那种颇为悲惨的爱情故事,但流传到海南,却被本土化成了一个具有大团圆结局的喜剧——海南岛的《威尼斯商人》:马俊逼婚,祝英台誓死不从;梁山伯考中状元,被招驸马;金銮殿上梁山伯不从君命,被定欺君之罪;祝英台及时赶到,据理力争,皇帝倍受感动,特赐梁祝天地良缘。乐感文化不言而喻。在乐感文化的引领下,传统而普遍的海南琼剧,放弃悲剧性的宏大叙事,忽视权力斗争和死亡情节,一直围绕着优美的爱情主题,积淀着乐观主义的艺术传统。
1882年美国人香便文海南岛之行日期考
辛世彪
香便文(Benjamin Couch Henry,1850~1901),美国传教士,1873年来华,为岭南大学前身格致书院(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创办人之一,曾著有《基督教与中国》(The Cross and the Dragon)和《岭南纪行》(Ling-Nam)。①
1882年10月,香便文在早一年上岛传教的美籍丹麦裔传教士冶基善(CarlC.Jeremiassen,1847~1901)②的陪同下前往海南岛考察旅行,考察经过写在《岭南纪行》一书中,成为该书的后半部分(第17~27章)。这是西方人穿越黎区的最早记录,1868年史温侯(Robert Swinhoe,1836~1877)最远只到过琼中的岭门。③不过,香便文“海南纪行”这一部分内容已于1883年分为四篇率先发表,前三篇题为“海南几瞥”(Glimpses of Hainan),发表在上海出版的《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①末篇题为“海南纪行尾声”(The close of a journey through Hainan),刊载于香港出版的《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②这四篇文章收入《岭南纪行》时,只增加了两小段文字,其他内容几乎没有改动。
香便文在书中没有说明他在海南岛旅行的具体起止日期和总天数,给我们留下了一处疑问。“海南纪行”译注完成后,我觉得有必要弄清楚这些具体时间。本文根据他在书中每日行程的记录,结合所能找到的当时其他相关文献,考订1882年香便文海南岛之行的日期和时间,以供治近代史及基督教入华史者参考。以下所引文献皆为笔者翻译,但引文末括号内所标为原书页码。
一 现有的材料和记录
有关香便文海南岛之行时间的直接记述,主要有以下3项材料。
1.香便文在《岭南纪行》第17章中说,这次旅行时间是1882年10月和11月:
直到三年前,海南岛腹地的外壳才被真正打破,对外界开放。做这事的第一人是冶基善先生,一位丹麦绅士,现在献身向岛内民众做独立的传教工作。1882年4~5月,他做了徒步环岛游,探索在岛上旅行的可行性,他走过每一个地区都未受到侵扰,并证实那里的人很友善。这次由一个岛内外国人做的大范围旅行的记录,非常详细,令人充满兴趣。在过去的一年里,他已从岛北穿到岛南,再从东穿到西,在任何地方都未遇到特别的敌意。1882年10月和11月,我有幸跟这位先生一道做了大范围旅行,穿越了这个岛的腹地,我就把这次的旅行记录续上。(p.331)
2.《教务杂志》1882年11~12月号“传教士新闻”栏中说,香便文于1882年12月7日返回广州:①
广州。12月7日,传教士香便文从海南岛旅行归来,这次穿越之旅是在冶基善先生陪同下进行的。他们在所到之处获得当地居民的极大好感,既有说海南话的汉人,也包括土著部落。冶基善先生诊治了无数的病人。书籍很容易就被买走了,处处热情好客,对待旅行的客人也如此。我们希望读到香便文先生对海南岛及岛上居民考察的记录。
3.香便文在《基督教与中国》里说,他们在海南岛内旅行共计45天:②
两年前,我在冶基善先生陪同下去过海南,做了穿越该岛的大范围旅行。我在海南岛腹地度过了45天时间,在汉人和土著人中都住过,因此我可以基于个人的观察和经历,说一说海南岛人的性情以及如何在他们中间开展工作;我可以强调说,整个海南岛——无论沿海还是腹地,无论山区还是平原——似乎都向基督教工作完全敞开了。
以上3种材料综合在一起,并非从12月7日往前数45天即可得到香便文旅行的准确日期。首先,香便文说他在海南岛旅行是10月和11月,并没有把12月包括在内。其次,香便文说得很清楚,这45天是他在海南岛内旅行的时间,而不是往返海南岛的总时间,如果把12月7日作为旅行的最后一天,那他们登岛旅行的第一天就是1882年10月23日,可是香便文收集的植物标本清楚地记着,10月24日在临高收集到某些植物,根据《岭南纪行》中的记录推算,他们到达海口以后的第7天才进入临高县境内,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因此,接下来我们要靠两种材料加以考订。一是香便文书中每天行程的记录,每天从哪儿到哪儿,住在什么地方,这是最重要的内证材料。二是当时香港的植物学家汉斯博士(Dr.Henry Fletcher Hance,1827~1886)的文章,因为香便文把他在海南岛收集到的植物标本全部赠送给汉斯做研究,汉斯将这些标本分类整理,发表于专业杂志,每一种植物都注明了香便文收集的地点、日期等,这可以作为重要的旁证。
二 香便文行程的描述
香便文在书中虽然没有说到任何一天具体是几月几日,但他提供了两种重要的时间信息。一是每天的行止,住在哪儿,在那里待了几天,我们可以据此推算出旅行的总天数;二是有两处提到在某地过星期天,这可以帮助我们推算出当天是几月几日,进而推算出该日前后的具体日期。
1.从海口到儋州南丰
1882年10月的一天,香便文从香港乘船前往海口:
我们从香港到海口的旅行,是乘坐一艘破旧的小汽船,船舱就在蒸汽锅炉上面。……傍晚时分,我们在开阔的锚地抛锚,港口的弊端立时显现。……我们乘坐其中的一只小船,到将近午夜才上岸,离我们下大船已有5个小时。在这番遭罪的航行之后,我朋友清洁、宁静、舒适的住处,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解脱。(p.332)
此次随香便文一同来海南岛的还有几个说粤语的挑夫。从香港到海口,原文说海路有290英里,不管走了几天,这一段不算在45天之内,他们的行程是从登岛开始算起的。
接下来他们考察了海口及周边环境、历史人文风貌,并做旅行前的准备,但没有注明天数。他们在岛上的旅行是走西线,从东线返回,这一路都记着当晚住哪里、住了几天,可以据此排列推算日期。书中涉及的地名笔者都做过实地调查,多数地名都已考订出来。古今地名不一致的,在叙述中注明了原书所记历史地名,并用括弧标注今地名,有些暂时无法弄清楚的,则用音译名,叙述文字中用括弧标出原文。
第1天从海口出发,当晚住海口西部的龙山(荣山):
第一天徒步旅行17英里,止于“龙山村”(Lung-shan),村边有小溪流向大海,溪上有座石桥。(p.345)
次日住澄迈县城(老城),从荣山到老城只有5英里:
城里的居民有礼而淡然地迎接我们。我们包下了整个旅店,这样就觉得相对舒服些。(p.348)
第3天住澄迈森山(福山),女店主泼辣能干,丈夫是鸦片烟鬼:
我们住在镇上最好的客栈里。据我们观察,海南所有的客栈都是女人当家,这可能是她们自立的一个迹象。(p.352)
第4天住临高船肚(皇桐),这地方离福山大约6英里:
几英里之后,我们来到一个叫“船肚”(Shun-tó)的小市镇,在这里我们住了一家上等客栈,干净舒适,又很安静,后面还有一个隐蔽的门。(p.354)
第5天住临高县城(临城),考察城内古迹,登高山岭。第6天到临高美珠(波莲),因在此地诊治病人走不开,多住一天,一百多人得到诊治:
我们本打算次日一早动身,但是散集回去的人已经把我们到来的消息传开了,我朋友的医术在远近村庄都很有名。第二天早晨,我们的门口挤满了热切而焦急的人。……于是,我们舍出一天,给他们治病,锁上里面的门,让一个人守着,一次只许进几个人。(pp.359-360)
第8~10天住临高马停(美台),在这里休息并治病,从安息日(星期六)到星期一共3天,有清楚的时间标记。
尽管他们一再请求,我们还是拒绝了所有的邀请,动身前往“马停”(Ma-ting),离此地五英里远,我们希望去那里过一个安静的安息日。(p.360)
这一段说的依然是波莲,那天应该是星期五,由于治病太累,他们希望到下一站美台过安息日(星期六),休息一下;次日就是星期日,香便文和冶基善两位牧师要做礼拜。书中又说到,星期一美台有集市,他们详细考察了市场,并且卖掉了带来的一部分书,当天也治病,治疗的人比波莲多一半;由于病人多,次日凌晨才脱身。因此他们在美台共计待了3天。
第11天住临高和舍,次日亦在和舍考察:
我们沿着缓坡下山,走了一英里半后到达“和舍”(Wo-she)镇,我们要在这里休息两天。(p.365)
第13天住儋州那大,在这里治病、卖书,考察当地多种方言:
到了那大,我们发现正是繁忙开市的日子,街上挤满了赶时间专心做买卖的人。人的数量之多,商品交换速度之快,以及整个城镇的面貌,使人感觉这里是个繁华的地方。我们急于避开拥挤的人群,步行二十英里之后也很想休息一会儿,就走进了一家客栈。(p.372)
第14天到儋州南丰,原文说因下雨滞留一周,但具体停留几天没有说明。因此从南丰开始我们重新排列日期。
终于,耽搁了一周之后,天有些放晴,我们早晨就动身,希望天黑前能到达第一个黎村。(p.402)
2.从儋州南丰到海口
从南丰开始,第1天住志文(Chi-wan),因下雨滞留3天。
已经大半天过去了,我们全身湿透,筋疲力尽,又打着冷战。这里离镇上还有六英里,考虑到天黑下来,又阴沉沉的要下雨,全身衣服也是湿的,并且还可能找不到住处,我们就在“志文”(Chi-wán)村停下来,决定在这里过夜。幸好做了这样的决定,因为雨又下起来,在三天内不可能再往前走。(p.404)
三天之后,尽管浓重的雾气依然在山间萦绕,我们还是动身往黎村走。(p.406)
第4天住什满汀(Ta-man-teen),他们的到来在黎人中引起轰动:
什满汀(Ta-mán-teen)村距南丰十二英里,位于黎区内边缘地带,在汉人辖区几英里之外。……我们要求见村里的头人,马上有人送我们到他家。头人当时不在家,但我们被毫不犹豫地请了进去,像回到家里一样。他的妹妹担当起女主人的角色,麻利地拿来水、木柴及其他必需品。(p.410)
我们一行(共十四人)的到来,在镇上引起巨大的轰动,几乎所有的人都来看我们。(p.415)
第5天住白沙县东北部的番仑,番仑是大村,他们住其中的一个小村:
几分钟后来到一个小村子里,这就是那些被称为“番仑”(Fan-lun)的第一个村庄。年轻活泼的黎人把我们带到此地最好的房子,我们进去后,按照待客的礼数,这房子和里面的一切就属于我们了。(p.422)
第6天住福马(Fung-ma):
步行三英里之后,我们又经过了两个村子,都叫“福马”(Fung-ma),我们在第二个福马村停下休息。(p.435)
第7天到黎班,因下雨耽搁2天。此地离福马不远,俱在今白沙县细水乡合口村境内,因此第7天当天也应该算上:
到了黎班,人们带我们去的房子,虽然并不像我们离开的那座房子那样整洁吸引人,但也够大够舒适。(p.440)
因为下雨,我们在黎班耽搁了两天,但这并不妨碍附近村子的人成群结队来看我们。(p.443)
第9天住快丰(Kwai-fung),次日在那里过主日(礼拜天),这是第二个清楚的时间标记:
到达“快丰”(Kwai-fung)以后我们感到极大的轻松,这里是进入山谷以后的最后一个村庄。(p.454)
星期天是在村子里过的。尽管人们对我们的宗教活动表现出极大的尊重,但是我们发现,让他们理解其中的含义是困难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不懂他们的语言。(p.457)
第11天住琼中县红毛镇西北的打寒,这里的黎语跟白沙黎语不同:
休息一小时后我们继续上路,又翻过一道岭,走了一英里半路,到达“打寒”(Ta-hán)。……这里的人属于“干脚黎”(the Kon-keuk Les)部落,所讲方言与山岭那边的截然不同,我们的黎人挑夫只好讲海南话,这样他们才能听懂。房主和其他几个常跟汉人做生意的人,包括一个刚从海口回来的人,穿着汉服,但是大多数男人穿的衣服,如果可以称之为衣服,那就更为原始。(pp.460-461)
第12天到牙寒,住在一个汉族商人家里,他们的穿越计划即被此人破坏(详见附录):
我们来到“牙寒镇”(the town of Nga-han),它位于一条较大的溪流边上。我们的老黎人挑夫是我们在山岭那边遇到的一个鸦片烟鬼,他带我们去一个汉人家里,说是为了让我们住得更舒服些,但我们相信他是为了给自己弄一点鸦片。(p.464)
第13天他们到牙寒南边一个村子的黎头家里,请他帮助物色说当地方言的挑夫,遭拒后折回,住在牙寒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此村当为红毛镇的毛西:
黎头的村里没有可住之处,我们只好折回来,三次趟过宽阔的河流,在早晨路过的一个小村里过夜。(p.467)
第14天开始返回海口,但没有走老路,而是从红毛往北走,当日住水乖(Shui-kwai):
黎族老向导好像急匆匆要赶往下个歇脚的地方,我紧随其后,天黑前一个小时,我便到达一个叫“水乖”(Shui-kwai)的村子。尽管有前面的教训,但一进村子,老向导还是把我带进一户汉人家里。(p.476)
第15天到岭门,在岭门停留2天,经历了很多事情:
就这样,我们一次次在臭气熏天的泥潭里挣扎前行,又一次次在溪流里把全身冲洗干净,终于隐约看到了我们的目的地岭门镇。……我们找了一处相对干燥的地方休息,是一个建在主房上面的小阁楼,有点像鸡舍。(p.480)
经过两天半的休整,我们继续上路,穿过这片平原,直取东部的山脉。(p.489)
第18天离开岭门向北,住屯昌县乌坡镇:
在道路崎岖的平原上走了十英里,我们来到了一个海南话叫“乌坡”(Au-pó)的市镇。一天的交易已经结束,但还是有成群的人聚集围观我们。客栈大都客满,这时候有一大群人带着稻谷和货物住在店里。在一座小房子里,我们总算找到了一个安身之所;这房子没有门,但好奇围观的人比我们更欣赏它。(p.489)
第19天从乌坡经船埠坐船,一夜漂流到琼海嘉积,次日在嘉积考察集市,卖掉剩下的书和东西:
清晨,我们发现已经到了嘉积镇外的码头。从码头步行到客栈,我们差不多走了一英里,因此我们对镇子的规模有了一些概念。……我花了一整天时间逛街,带着大约三百册书和我们余下的所有东西,不费吹灰之力就处理掉了。(p.492)
第21天住定安县居丁镇,第22天从居丁到定安县城(定城),乘船连夜返回海口:
第一天我们走了二十五英里,在“居丁”(Kü-ting)镇落脚,次日中午抵达海口河。我们在这里乘船,连夜驶往海口,清晨到岸,在我朋友的住处吃早餐。(p.494)
以上从海口到南丰共走了14天,南丰以后共22天,合计36天,这是非常清楚的。需要考订的是他们在海口住了几天,在南丰住了几天,以及每一天的具体日期。
三 具体日期推算及旁证
1.日期推算
有四个时间标记可以参考:一是此次旅行在10~11月,二是在海南岛旅行共计45天,三是在美台的3天是从星期六到星期一,四是在快丰村的那一日是星期天。
我们把最后的一天(从居丁到海口)当作第45天,以快丰的那个星期日(倒数第13天)作为起点,在11月和12月初之间进行时间排列,发现那一天正好是1882年11月19日(光绪八年十月初九)。旅行的后半段时间就是11月18日(周六)晚上到达快丰,12月1日(周五)连夜返回海口。
然后从19日往前推,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时间标记,在美台正好是周六、周日、周一,这个不会变,这样他们滞留在南丰的时间就可以推算出来。他们于1882年10月28日(周六)当天到达美台(原文说从美珠到马停有5英里),31日(周二)离开美台前往和舍,当日及次日都住和舍。11月2日住那大。11月3日(周五)到达南丰,滞留6天,11月10日离开南丰到志文,后面的日期就都接上了。
最后,他们初到海口时待的时间也就清楚了,总共3天,具体日期是1882年10月18日至20日(周三到周五)。
这样,香便文一行是在1882年10月17日(星期二)晚上到达海口港,次日凌晨上岸。他们在海南岛旅行的时间是从1882年10月18日(星期三)算起,12月1日连夜赶路也就是12月2日(星期六)清晨到海口,不计12月2日当天,共45天。具体行程及大事记见附录。
有一个问题,《教务杂志》1882年11~12月号说香便文于1882年12月7日返回广州,这怎么解释?原来,香便文因为旅途的疲惫,加上从船埠到嘉积那一夜在船上受了风寒,11月30日到达会同(今琼海塔洋)后本想取道文昌回海口,但因发高烧,不得不乘坐轿子加紧赶回海口:
我们本打算先去文昌,再从那儿返回海口,但是嘉积河上那一夜漂流的恶果,在我身上转成了严重的打摆子发高烧,这病把我放倒了。我们只好抄最近、最便捷的路赶回去。几天后,我的朋友也同样病倒了,因此这次旅行的结尾并不如开始时那么令人愉快。从会同坐上轿子,我们直奔距离海口河(the Hoi-how river)最近的地点。(p.494)
接下来的几天香便文在海口养病、恢复,整理材料,于1882年12月7日回到广州。香便文对于坐船到海口港的情形已经表现得深恶痛绝,加上身体不适,情理上不可能立即从海口坐船折腾到广州。12月初这几天在香便文书中没有任何记录,自然也不可能算在穿越海南岛的旅行当中。而且根据书中的叙述推算,也没有超过45天的行程记录。
2.旁证材料
香便文是植物学爱好者,来海南之前就曾在广东北江、连州一带收集过很多植物标本,交给当时在香港的植物学家汉斯博士①做分类研究并且发表。香便文在海南岛旅行45天,收集到200种植物样本,都带回去交给了汉斯。汉斯将这些样本整理并做了植物学分类,发表在英国的《植物学报》(Journal of Botarey:British and Foreign)上,每一种都注明了香便文收集的地点、日期等。较重要的有如下几篇。
1883年的《中国植物志拾遗(八)》,包括植物品种100个,其中有香便文1882年在海南收集的5个。②1884年的《几种中国榛木科植物》,包括植物品种10个,其中有香便文1882年在海南收集的3个。③1885年的《中国植物志拾遗(九)》,包括植物品种59个,其中有香便文1882年在海南收集的13个。①1887年的《中国植物志拾遗(十)》,包括植物品种19个,其中有香便文1882年在海南收集的2个。②1885年的一篇短文《中国的四种番樱桃属植物》,③用拉丁语写成,所说的4个品种都是香便文收集的,其中有3个品种是在海南岛收集的。
这26种在海南岛收集的植物按汉斯原文标注的收集时间排列如下所示。
1.Jasminum ( Unifoliata) microcalyx,sp.nov.-1882 年10月19日香便文在海南海口(Hoi-hau)收集。
2.Gossypii sp.—1882年10月21日香便文在海南临高(Lam-ko)收集。
3.Loranthus ( cichlanthus) notothixoides,sp.nov.——1882年10月香便文在海南临高(Lam-ko)收集。
4.Helicteres spicata Colebr.Var.hainanensis.—1882年10月24日香便文在海南临高(Lam-ko)收集。
5.Anisochilus sinense,sp.nov.—1882年10月24日香便文在海南临高(Lam-ko)收集。
6.Pteris quadriaurum Retz. Var.—1882年10月24日香便文在海南什满汀(Ta-men-tin)收集。
7.Hygrophilia phlomoides N.abE.—1882年10月31日香便文在海南临高(Lam-ko)收集。
8.Ipomoea capitellata Choisy.—1882年10月31日香便文在海南和舍(Wo-chi)收集。
9.Ipomoea pileata Roxb.—1882年10月31日香便文在海南和舍(Wo-chi)收集。
10.Engenia (syzygium)Henryi.——1882年10月31日香便文在海南和舍(Wo-chi)收集。
11.Chailletia hainanensis,sp.nov.——1882年11月1日香便文在海南和舍(Wo-shi)收集。
12.Linociera(Ceranthus)Cambodiana Hance.——1882年11月1日香便文在海南临高和舍(Wo-shi)收集。
13.Suertia (Ophelia)vacillans Hance.——1882年11月6日香便文在海南南丰(Nam-fung)收集。
14.Kleinhoriahospital L.1882年11月7日香便文在海南收集。
15.Sphenodesma unguiculata Schauer.——1882年11月14日香便文在海南黎人区什满汀(Ta-men-tin)收集。
16.Thea bohea L.1882年11月14日香便文在海南黎人区什满汀(Ta-men-tai)收集。
17.Gomph Jiostemma Chinense Oliv.——1882年11月15日香便文在海南黎人区番仑(Fan-lrn)收集。
18.Quercus (Cyclobalanus) silvicolarum,sp.nov.1882年11月16日香便文在海南黎人区收集。
19.Diosspyros eriantha Champ.——1882年11月21日香便文在海南黎人区的红毛(Hung-mo)收集。
20.Plectraqnthus(Isodon,Euisodon)veronicifolius,sp.nov.1882年11月21日香便文在海南黎人区收集。
21.Eugenia(syzygium)myrsinifolia.——1882年11月21日香便文在海南黎人区的红毛(Hung-mo)收集。
22.Quercus(Pasania)litseifolia,sp.nov.——1882年11月22日香便文在海南黎人区的红毛(Hung-mo)收集。
23.Quercus (Pasania) Naiadarum,sp.nov.1882年11月26日香便文在海南黎人区的山脚下收集。
24.Melodorum ( Eumelodorum ) verrucosum Hook.fil.& Thomas.——1882年11月28日香便文在海南黎人区的红毛(Hung-mo)收集。
25.Eugenia(Syzygium) tephrodes.——1882年11月30日香便文在海南嘉积(Ka-chik)收集。26.Myrica(Morella)adenophora,sp.nov.——1882年11月香便文在海南定安(Ting-on)境内收集。
以上26条记录中,第3条和第26条没有注明具体日期,第14条、第18条和第23条没有注明具体收集地点。第1条,第4~5条,第7~13条,第15~17条,第19~22条,第25条,共计18条都与笔者考订的时间完全相合。其中第15和第16条在同一天,地点应该都是什满汀,“Ta-men-tai”当是“Ta-men-tin”之误。
1882年10月24日香便文从澄迈森山(福山)到临高船肚(皇桐),10月31日至11月1日在临高和舍,第3条说是10月在临高收集,应该说得过去。11月4-9日香便文一行滞留在南丰(当时属临高,今属儋州),因此第14条应该也是在南丰收集。第18条笼统地说11月16日在黎区收集,他们当天在黎区的福马到黎班之间行走。11月25~26日他们在岭门,这是黎区最北端,第23条也说得过去。第26条说11月在定安收集,当时的定安县范围很大,包括现在的琼中县全境和屯昌县一部分,可以是11月20日到27日的任何一天所经过的地方。因此这5条也不一定有问题。
问题出在第2条、第6条和第24条。据我考订,10月21日是香便文一行开始穿越旅行的第一天,从海口出发到龙山(荣山)过夜,行走17英里(27公里),4天后才到临高境内,10月21日无论如何不可能在临高。怀疑是香便文手写的标签“24”或“27”因看起来像“21”,被汉斯误认作10月21日。第6个标本说是香便文10月24日在什满汀收集的,这绝无可能,10月24日应该在临高境内,从这一天到什满汀还有近20天的路程,肯定是汉斯把标签弄错了。第24条说是11月28日在红毛峒收集,这个也没有可能。他们在11月23日离开红毛,当晚住在水乖,其地在琼中北部,当在今湾岭镇境内。11月28日这一天他们已经离开黎区了,更无可能在黎区的红毛。怀疑是汉斯把香便文手写标签“23”看成“28”,因此出错。
以上26条材料中,有3条怀疑是汉斯弄错了标签上的日期或地点,5条虽然没有具体时间或地点标记,但也未必有问题,其他18条都与考订出来的日期相合。汉斯的文章可以旁证香便文1882年海南岛之行的具体日期。
结语
我们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香便文没有在书中标注这次行程的具体日期,这本是轻而易举之事,也许他这样做是为了保证可读性,避免成为流水账似的日志或报告。香便文行文的简洁、流畅和优美令人称道,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记者出身的前缅甸殖民者司各特爵士(Sir James George Scott,1851~1935)是很能写作的人,但他的《法国与东京》(Franceand Tongkin,1885)①一书中关于海南岛的描写直接大段抄录香便文的文章,对其文笔大加赞叹,可见其价值和影响力。尽管如此,香便文记下了他们在旅途中的行止等相关信息,当时的教会文献也记载了这次旅行,汉斯博士的植物分类论文中更保留了香便文采集植物样本的时间、地点等。我们从内证和外证两方面的材料加以考订,得出1882年香便文海南岛之行的具体日期,应该是比较准确的。
附录 1882年10月18日至12月1日香便文一行海南岛旅行大事记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市场经济转化与产业化重构
——以海南为例
张军军
如何发展海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其在现代文明进程中快速消逝的本土文明得到良好的保护和传承,是海南省文化与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公益性保护与市场化开发相结合,政府主导、民间资本参与的多种样式的产业化经营,旅游文化园区、文化艺术品、民族性演艺等多元化开发模式,都将带动非遗融入现代理念,走可持续的发展与传承之路。在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大背景下,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市场开发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也必须看到,国际旅游岛的建设目标与海南非遗的保护之间存在一些内在的矛盾与冲突。那么,在国际旅游岛建设的市场经济背景下,如何做到海南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和构建旅游产业化之间理性沟通,使二者能够有机融合,最大限度地做到双赢?这一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一 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市场经济转化的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反映了一个民族、族群、社区和国家对自身特性的认同和自豪感,以及被世界认可的程度,是维系一个群体或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由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人们生产、生活方式及文化生态环境的变化,原生态的传统文化正在走向衰落,或走向变异。但世代劳动人民口传心授、约定俗成的活态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民族的根脉,也是现代文化发展的不竭源泉。
海南由于其地理位置,本土文化受现代文化冲击相对较小,很多地区都还保有原生态、古朴的自然状态。如距今6000多年的黎族制陶技艺、4000年历史的树皮布制作技艺、3000年历史的黎族文身,这些活态传承的技艺,在海南仍保存完好。但由于传承方式的局限,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现状堪忧,尤其是较为单一的项目,一旦传承人离世,绝活就成了绝唱,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如手工制陶的艺人全省不足10人,懂得黎族骨簪工艺的手艺人只有3人,临高人偶戏后继乏人。再如黎族打柴舞,全省只有三亚的一个村庄还完整存在,如果这个村庄打柴舞消失了,从此这个古老的舞蹈就在世界上消失了。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归根到底是对传承制度的创新性、传承环境的承接性和传承人的保护。
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程度,离不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程度和文化政策制定执行水平。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具有产业化潜质的项目走向市场,通过这一渠道可以使传统的文化项目获得生机,促进其有效传承的同时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国内有些城市将非遗项目的旅游市场开发与保护相结合,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如甘肃省环县道情皮影几十支队伍在全国各地演出,获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庆阳香包制作产业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民族文化在市场上特别是在旅游市场因特有的地域、文化、民族等优势,已经成为重要的旅游资源,是被开发和有效利用的热点。许多原本被抛弃的文化遗产不仅随着民族旅游文化的商品化而重获新生,而且正在成为独具地方特色的文化旅游资源。
其次,把非遗适度地通过市场化的形式融入当代生活,这样在资金的组合上,除了政府常态的财政“输血”外,带来了更多的资金渠道,从而开发非遗项目的自身“造血”功能。如海南以热带旅游为主题的“呀诺达”度假公园,将部分海南“非遗”项目纳入观光旅游中,成为海南岛特色品牌景区,年接待游客百万人次,单门票一项收入可达亿元,为技艺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资金与物质保障。
此外,将本地区的文化景观、本民族传统民间文化遗产、本土个性化的文化元素整合起来,构建相应的文化产业园区,已经成为世界上很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瞩目的议题。一个地区人们世代传习的精神文化因子经过时间的沉积、岁月的锻造,有机地融入这座城市的主体命脉,构成这座城市的精神源泉。将精神文化与文化产业相融合,打造适合本地区特点的文化产业园区,既是各地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举措,也是对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激发、重塑,形成产业化模式的市场动力。此举可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培育区域经济和城市经济新的增长点,对于扩大就业、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实力具有积极意义。
二 非遗项目在市场经济转化中存在的问题
(一)以利益为目的的商业化开发将失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
本真性(Authenticity),本意是真实而非虚假的、原本的而非复制的、忠实的而非虚伪的、神圣的而非亵渎的。①20世纪60年代,“本真性”或称为“原真性”被引入遗产保护领域,逐渐在世界范围内达成理解和共识。文化遗产的本真性来自原初可以流传的一切之整体,从物质形态上的持续、文化环境的“本体真实”,到它所经历的历史发展过程的见证,这一系列本真性的存在可以提高公众对文化遗产价值的认知度,防止“伪民俗”“伪遗产”。
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市场性开发相对滞后。21世纪初期,随着全国性文化旅游热潮的兴起,海南各地曾建起以打造地方民俗文化为旗号的大大小小的民俗风情园、黎村苗寨原始风情村等众多市场化行为的伪文化园区,极大地破坏了海南特有民族黎族及其原始黎族文化的本体真实性。如在海南的陵水、保亭、五指山等海南少数民族聚居区沿线,迅速仿建了许多少数民族居住村寨、粗制微缩原始景观。这些风情园、民俗村既没有文化赋予的生命内涵,又没有因时间的沉积而透出的历史厚重,相互间的同质化又导致了恶性竞争,暴露出很多市场性问题,其命运是以金钱的损失而落幕。这种只有民俗形,没有文化魂的伪民俗、伪遗产,最终破坏的是海南宝贵的文化资源,损害的是海南人民千百年来世代相传的文化印记。
(二)盲从性复制使“非遗”的可解读性遭到破坏,无法形成保护性开发
可解读性,指的是我们能够从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上辨识、解读出它的历史年轮、演变规律,尤其是内在的精神蕴涵。①非物质文化遗产蕴涵着一个民族传统文化最深厚的根源,保留着该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心理图腾和价值观念。在挖掘、开发、保护时,自然要格外重视其精神观念,即人和文化的关系。目的是使得所继承的事物具有真正的历史文化价值,而不是表现外在的文化形式,不能解读其内容。如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从农耕时代的祭神、蜡祭,发展到汉代出现的朝廷“众吏饮宴”、民间“华服盛饰”,演变到宋代出现的传递“拜年贴”、贴“门神”,到明代出现了年画的多样性。从其长期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出,春节无论是其功能、饮食、习俗,都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直到今天仍然能够解读出其延续的历史性变迁。再如,省级“非遗”项目海南传统节日“三月三”是黎族文化最具体、最典型的表现,也是黎族生产、生活、娱乐等整体民俗风貌的集中体现,是世人了解黎族文化和历史的窗口。近年来,海南本地进行了不同形式的市场性开发,政府“搭台唱戏”,但其中的舞台性表演、群众性会演、游人的即兴参与,反而掩盖了黎族在这一节庆里原有的传统民俗、仪式、庆典、传说等及其历史发展脉络,以及其具有的原始神秘性。结果,并没有给当地带来更多的经济收入,同时也破坏了这一节庆的可解读性,更无从谈起对“非遗”的保护性。
三 国际旅游岛背景下海南非遗项目的产业化重构
(一)海南国际旅游岛开发与非遗保护之间的内在矛盾
旅游开发与非遗保护之间虽然有利益结合点,但其根本性的目标还是不同的。国际旅游岛的建设要将海南特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纳入现代性的观光产业中来,就必须对此加以改造,以适应人们猎奇式观看的需求。在这种改造的过程中,难免将现代人的思维方式纳入其中,使那些能够与旅游开发相配套的项目为适应旅游开发的需求,削足适履,变成一种表演,从而破坏了其核心的文化价值;此外,这种为了适应旅游而进行的开发,也将使一些无法被改造成为视觉体验产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淘汰出局。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本身不存在商业目标,它完全站在对人类文明、文化方式延留的立场上,对项目的评价有其独立的尺度与价值体系,以项目的独特性与不可再生性为选取标准。非物质文化是在特定的文化生态场景、语境中发生、发展的,失去了这样的场景和语境,单独把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传承人保存下来,这虽然也很重要,但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背景和基础。然而,这一套体系却难以与旅游开发的市场经济相一致。我们可以将非遗项目与旅游开发之间的关系分为三种。
第一,二者有着高度的关联性。这方面的项目得到了海南各级政府与旅游开发组织的高度重视,如前述的呀诺达等项目,由于形成了良性循环,既获得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也在客观上避免了这些项目陷于失传的危险中。
第二,二者关联性不大,未得到良好开发。如黎族的骨簪工艺。黎族的骨簪,不仅是精美的饰品,而且反映了黎族的一段历史,记录了黎族的一位英雄,但由于市场开发不善,未能成为旅游工艺品,而使传承人越来越少,目前懂得制作的只有3人。与此同时,原本具有旅游表演项目潜质的黎族传统打柴舞,由于未得到相应重视而无人开发,截至目前只在三亚的一个村庄得以保存,如果打柴舞在这个村庄消失,那么就意味着后人只能从图片上找寻这一古老舞蹈的踪迹了……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缺乏旅游开发的潜力,或者未能被开发成为旅游产品而被冷落,进而面临失传的危险。
第三,二者存在矛盾或冲突。出于旅游开发的需要,对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人为改造,使遗产失掉了原有的意义与风貌。如海口府城古老传统的“换花节”,作为民俗类项目入选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①本地政府也有意要将这一传统习俗传承下去,形成品牌的力量。近几年的换花节虽然形式仍然延续,举办模式也由民间自发变成了政府主办,活动内容也不断外延,还增添了花展、灯展、舞狮、游艺娱乐等内容,但人们对该节日的期待却有衰减之势。
旅游是“看”的经济,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存在商业目标。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建设,使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旅游的产业化虽然对非现代的文化提供了资金支持等保护,但又迫使一些传统文化因“被看”而被改造进而破坏了其文化承载。海南是国内的重要旅游地区,又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较多的地区。尤其是2010年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开发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之后,旅游开发一路走热,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申请与实施保护迎来关键时期。二者之间的关系既有一致性,又充满了矛盾,实际上体现了现代社会的内在矛盾与冲突。
(二)非遗项目与旅游产业构建之间的结合点
有学者从旅游业的角度将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划分为五种资源类型,即观赏型、参与型、体验型、深层型、辅助型。②从视觉特征吸引旅游者、行动上融入体会人文风貌、精神上享有更深层文化内涵等范畴进行了旅游资源的划分。海南现有的89项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中,涵盖了传统手工技艺、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文学、民俗、戏剧、杂技、民间美术、文化空间等,其中一半以上属于观赏型、参与型、体验型的旅游文化资源。如濒临失传的手工制陶、龙被技艺;黎族特有的织锦、树皮衣制作技艺;传统民俗节庆“三月三”、军坡节;海南传统的琼剧、临高人偶戏;极富地方特色的崖州民歌、儋州调声;传统民间舞蹈打柴舞、招龙舞;黎族古民居船型屋、干栏式建筑等,这些既是海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又是具有极强的旅游开发价值的地域文化资源。这对于正在进行的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开发与建设,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资源财富。
旅游业围绕人们本能性的心理体验,满足人们好奇与陌生化的心理体验需求。因此,发展旅游业除了自然奇观之外,很大程度上需要提供给游客与其日常感官体验不一致的“奇观”。这种奇观一方面是物质性的,另一方面则是文化性的。尤其是在今天全球的现代性生产与消费体系抹平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差异化的时代,寻找与这种现代性的日常生活方式不同的文化体验,成为旅游的一个重要目标。旅游产业根据工业化的原则,将这种异域性的文化差异转变成为可供人们观赏的奇观。这就要求对一些不符合现代社会的文化加以包装与改造,使之成为人们进行工业化观赏的消费产品。而这正是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产业的结合点。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看不到,或者正在消失的“奇观”,它本身是一种陌生化的看点,能够为现代生活中的人们提供一种体验,并使之形成旅游产业所需要的市场,这是非遗与旅游业能达成一致的原因。这种需求可以为保护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资金和保护动力。如前文提到,国内一些非遗项目将旅游与保护相结合,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一方面通过走入市场,使传统的文化项目获得生机,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以热带原生态旅游为主题的海南呀诺达度假公园,将黎族织锦、文身等纳入观光项目,为技艺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资金与物质保障。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企业将黎族织锦开发成为工艺品与旅游纪念品,逐渐形成产业化运营模式,在获得市场的同时,也使这项手工技艺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和传承。
(三)非遗保护与旅游产业之间的双赢
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台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政府行为限定为: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总政策;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主管机构;编制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奖励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机构;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鼓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工作;制定法律法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等。这一规定,明确了政府与社会团体以及旅游企业之间的关系,体现出政府的主导作用。
首先,各级政府需要分辨非遗中能与旅游文化结合的点,并按它们之间不同的关系、不同项目区别对待和处理。对于具有旅游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鼓励个人与企业进行产业化开发,从而获得更多的资金与社会资源来对它们进行保护,进而提升旅游的深度,形成良性循环。如对黎锦、花梨木雕,以及一些村镇能够与旅游结合的公期等项目,可以采取与旅游结合的方式获得更好的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借此使古老的技艺和民俗得以传承,避免因缺乏资金与积极性而失传。找到非遗能够被“看”的一面,借助现代媒体力量吸引人来看,为旅游产业服务。如对于黎族骨簪制作这样的项目,应挖掘其潜在的旅游资源,通过帮扶其扩大市场的方式使之与旅游工艺品市场相结合,引导更多的民间艺人参与进来。否则,单纯依靠政府人为保护的方式,一旦资金、保护方式出现问题,这种技艺可能就永久性失传。
与旅游经济相矛盾或者相冲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则需要以政府力量为主导进行抢救和保护。首先需要厘清哪些是无旅游价值却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然后重点投入资金进行保护。如钻木取火、一些与原始宗教相关的黎族歌舞、口头传说等既无实用价值,又暂时难以对游客产生吸引力,这就需要政府层面进行抢救式的保护,一方面需要投入资金,另一方面保留影像资料。对于无旅游市场的民间技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则采取政府专项资金保护扶持的方式给予传承人经济支持。
其次,引导社会对非主流的生存方式与价值观给予充分的尊重与理解,保护民间独立性的生活方式与生存方式的存在空间,在现代化进程中能够更好地保留文化的多元性和差异性。这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所在,也能为旅游产业的未来发展提供更加充分的后续资源,在这点上保护与提供二者是一致的。针对海南现今的情况,可以考虑通过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方式将二者结合起来。“文化生态保护区是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对历史积淀丰厚、存续状态良好、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特色和价值的文化形态进行整体性保护,以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而划定的特定区域。”①
在海南未来的发展中,正视旅游开发与非遗保护之间的矛盾,在思考中不局限于现代性的思维方式,使“看”与“被看”都以全方位的视角来进行,这才能为日后海南的社会发展留下充足的空间。在这一过程中,需鼓励的是“看”的兴趣刺激旅游产业发展,但需避免“看”的过程对“被看”物的破坏。笔者希望海南能够成为一个永远有可“看”之处的旅游岛,也希望那些“被看”的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恒久地得到保护与传承。
四 从文化溯源的视角挖掘市场经济下海南非遗的地方承载
因阿诗玛而声名远播的云南石林;因白蛇传说而重新修缮的雷峰塔;滕王阁、岳阳楼、黄鹤楼因王勃、范仲淹、崔颢的诗句而千古传世,这些都因其合理有效的发掘,重塑了承载着浓厚地域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激活了非遗这一古老的文化元素构成,从而更好地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如何在发展中拓宽文化的传承渠道,在开发中体现文化的价值,在市场化的进程中构建文化的精神内涵,是当下必须关注的问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中,首先不能丢的是文化存在的根源,非遗本身的文化溯源要始终与现实生活的需求站在同一水平线上,否则“非遗”就变得“夹生”了。
海南府城正月十五日的换花节,原为“换香节”,俗称“驳香”,是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日海口市琼山地区具有历史特色的民间节日,起源于唐代贞观元年(627年),宋元时一直盛行,距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上的元宵节,府城居民在街上“换香”,意味着香火不绝,象征真实、祥和、喜庆、友好和爱慕,除此之外,民间还有挂灯、换香摘青的风俗。这些民俗形式实际上都是由元宵节演化而来,清咸丰《琼山县志》等史书均有记载:元宵节之夜满城妇女尽到总镇衙前,折取榕叶,谓之偷青。或燃香城门祝之,以祈有子。孩儿则摩总镇衙前两旁石狮,以祈平安。好事者悬迷灯于门首,游人聚观,测中者酬以笔墨烟草。①琼山府城镇曾为琼州府官方的驻地,每年农历“元宵节”都要举行灯会。脚下穿着新履的居民纷纷出门上街赏灯,由于当时没有路灯,人们为了夜行方便,手里都拿一把点燃的香烛用以照明,路遇没有香的人便送他几枝,有时偶遇朋友,也用香烛互相交换,互相说几句祝福的话语,换完香烛后不少人感到心中的夙愿已传到佛祖那里,便开始心满意足地踏上归路。一些人兴致勃勃,还特意从路边摘些青枝绿叶带回家,寓意一种蓬勃向上、乐观豁达的精神,由此演变成了海南人民之间一种传递心中情感的特殊方式。直到1984年,琼山政府考虑到燃香的安全性以及其本身附带封建迷信色彩,于是将这一近千年的民间换香习俗改为换花,希望能以花为媒继续传递祝福、友谊和爱情。但这种改变失掉了传统民俗性,其中寓意被置换,影响了民众参与的积极性。如今,人们手中的“香”换成了“花”,而这“花”多是“玫瑰花”,不产自海南,大多从云南空运到海南。人来人往、换花如潮的大街上,已经很少有纯朴的海南人自愿相互交换手中物、互道祝福的温馨场面了。在换花节上常常看到,一些小伙子从姑娘手中野蛮抢花的镜头,换花已经缺失了海南韵味。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节日、一种海南独特民俗、一份珍贵的海南本土文化的遗产,就这样变得不伦不类了。从换花节产生发展的脉络上可知,其原本的社会功能是娱乐、交友、祝福,而随着人们生活的变化、文化需求的变迁,这些原有的功能存在空间日益变大、渠道拓宽了,民众可以在更多的时间、地点里有选择地从事类似活动,又何必要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里重复性参与这种毫无创意的活动呢?由此可见,换花节这一节日习俗的变迁有其内在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如果不解风情地在发展中一味地简单复制、盲目恢复、粗暴改造,不仅会有损节日自身的民俗内涵,而且会加速其走向相反方向,甚至用我们的双眼看着它有一天消失殆尽。如今的“换花节”,虽然仍在延续这一节庆形式,内容也在不断丰富,但人们对“换花节”的期待却大有衰减之势,究其原因不得不从文化的传承错位进行分析。
在传承与发展换花节这一问题上,笔者认为没有必要原模原样的生搬硬套,非要照葫芦画瓢空留这套“外衣”,而是要在保有其文化内涵上做文章。把这一天作为纪念海南整体民俗文化的节日来组织运作,把更多的海南民俗拓展进来,打造一个富有海南地方文化品位、民间文化特色、民族文化精髓的品牌,集娱乐、和谐、诚信、交融、互动于一体的富有参与性的民俗活动,创造新的社会功能,使之世代传承。同时,一些非遗项目为了与开发挂钩,让媒体过度宣传、对比炒作、失实夸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实中的存在,使部分地方政府、百姓错误地认为“非遗”可以变成“摇钱树”,能成为地方的“标志性景观”,导致很多非遗项目遭到人为破坏。“如果把非物质文化比为鱼的话,那么特定的生态环境就是它的生命之水。水之不存,鱼将不再,二者是无法分割的。”①
海南学者将海南划分为五大文化区域,即以海口为中心的琼北历史文化区;以五指山为中心的黎苗族历史文化区;以三亚天涯海角和崖城镇为中心的历史文化区;以文昌、万宁为中心的沿海文化区;以儋州为中心的西部历史文化区。②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所在的区域文化紧密相关,构成了有机的整体,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所在城市的文化形象内涵。在进行非遗的市场化运作时,如果单纯地为了开发而进行简单的形态语境的还原,为了市场效益而进行文化元素的复制,忽略其文化的原真性,那么将失去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的本真形态及其历史价值的可解读性,同时失去的还将是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承载。
附注
该文属于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名称:海南岛文化根性研究;项目编号:HNSK11-49。
闫广林,博士,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原院长,退休教授,硕士生导师。
①葛绥成:《世界文化地理》,中华书局,1946,第1~2页。
① 王桐龄:《东洋史》,商务印书馆,1926,第8~10页。
②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92,第145~146页。
③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92,第149页。
①黄晶:《三亚落笔洞古人类牙齿化石——中国最南端古人类生存印记》,《海南日报》2008年10月14日。
① 何梓焜:《普列汉诺夫哲学思想述评》,中山大学出版社,1987,第151页。
①徐晓望:《妈祖的子民——闽台海洋文化研究》,学林出版社,1999,第407页。
① 陈耿:《盛行海南700年的妈祖文化》,《海南日报》2007年3月19日。
①宋正海:《中国传统海洋文化中的大陆文化影响》,《中国海洋文化研究》,海洋出版社2005,第11~16页。
该文属于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名称:海南岛文化根性研究;项目编号:HNSK11-49。
闫广林,博士,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原院长,退休教授,硕士生导师。
①司徒尚纪、李燕:《海南文化特质、类型和历史地位初探》,周伟民主编《琼粤地方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海南出版社,2002,第530页。
①符水光:《海南文化发展概观》,海南出版社,2010,弟84~85贝。
②张玉:《海南传统节庆饮食文化研究》,《文化纵横》2010年第9期。
③《潮汕文化属泛闽南文化》,《东南快报》2004年12月23日。
④单憬岗:《海南近代建筑的绚烂绽放》,《海南日报》2010年5月31日。
① 文锦堂:《古宅中堂位之谜》,《信息时报》2009年9月21日。
① 王燕飞:《家谱与方志关系小议》,《江苏图书馆学报》2002年第6期,第28页。
①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中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第36页。
①小叶田淳:《海南岛史》,学林出版社,1979,第46页。
① 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第487页。
①小叶田淳:《海南岛史》,学海出版社,1979,第38页。
②张跃虎:《朱崖田野上的华夏魂:琼南乡土社会之履历沧桑》,广东旅游出版社,2009第188~189页。
① 王俞春、陈耿:《海南禁约乡规(1857—1988)》,《天涯》2005年第2期,第95页。
①本尼迪克特:《菊花与刀》,马小鹤、孙志民、朱理胜译,九州出版社,2005,第159页。
②中江兆民:《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商务印书馆,1982,第15页。
① 《穿越岁月风尘的古牌坊》,《海南日报》2009年8月3日。
①苏轼:《试笔自书》,《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第2549页。
① 邢宥:《湄丘集》,海南出版社,2006,第29页。
② 邢宥:《湄丘集》,第31页。
*辛世彪,博士,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副教授。
①Henry,B.C.,Ling-Nam,or Interior Views of Southern China,Including Explorations in the Island of Hainan,London,1886.书名直译是《岭南,或华南腹地览胜,包括在迄今未涉足的海南岛考察》,本人译为《岭南纪行》,后半部分译为《海南纪行》(原书第17~27章)。
②冶基善为美籍丹麦裔传教士。冶基善于1869年来华,任粤海军舰长,缉拿珠三角一带的海盗。1881年辞职进入海南岛做独立传道人,1882年4~5月先行考察探索了黎区一些地方,同年10月陪同香便文进人黎区。
③Swinhoe,Robert,“Narrative of an Exploring Visit to Hainan.”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871-1872):41-91.
① Henry,B.C.,“Glimpses of Hainan”,The ChineseRecorder,Vol.14,Shanghai,pp.165-185,pp.302-324,pp.335-365,1883.这三篇文章的内容分别是《岭南纪行》第17~18章、第19~21章、第22~24章。
②佛山市Henry,B.C.,“The Close of a Journey through Hainan”,The China Review, or notes & querieson the Far East,Vo1.12,No.2(1883 Sep.),pp.109-124.本篇内容即《岭南纪行》第25~27章。参看辛世彪中译文《海南纪行尾声》,载《海南历史文化》2010年第1期,南方出版社,第211~239页。
①“Missionary News”,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ionary Journal,Vol.13,American Presbytery Mission Press,Shanghai,1882,p.469.
②Henry,B.C.,The Cross and the Dragon,or Lightinthe Broad East,New York,1885,p.473.
①汉斯博士(Dr.Henry Fletcher Hance,1827~1886),英国外交官和植物分类学家。1844年被派往香港做领事官员,1881年在广州附近的黄埔任副领事,1886年调任厦门代理领事并逝于厦门,上任仅仅几周时间。他利用业余时间研究香港等地的植物,成为华南植物学方面的权威,著名博物学家史温侯(Robert Swinhoe)对他极为推崇。有意思的是,作为植物分类学家,汉斯本人很少长途跋涉做调查,他主要通过通信方式,收集别人采集 到的植物标本,然后加以鉴定分类。汉斯最主要的成果是给George Bentham的《香港植物志》(Flora Hongkongensis: A description of the flowering plants and ferns of the island of HongAwig,1861)做的增补,名叫《香港植物志补编》(Flora Honkongensis: A compendi-ous supplemeraf fo Mr.Beratham’s description of the plants of Hongkong,1872)。汉斯收集分类
的植物标本多达22437种。香便文收集的海南岛植物标本全部赠送给汉斯做研究了。
②H.F.Hance,“Spicilegia Florae Sinensis:Diagnoses of New and Habitats of Rare or Hitherto Un-recorded Chinese Plants (VⅢ)”,Journal of Botany:British and Foreign, Vol.21,Oct.1883,pp.295-299;Nov.1883,pp.321-324;Dec.1883,p.355-359.
③H.F.Hance,“Some Chinese Corylaceae”,Journal of Botany:British and Foreign,Vol.22,Aug.1884,pp.227-231.
①H.F.Hance,“Spicilegia Florae Sinensis : Diagnoses of New and Habitats of Rare or Hitherto Unrecorded Chinese Plants (IX)” ,Journal of Botany: firitish and Foreign ,Vol.23,Nov.1885,pp. 321-330.
②H.F.Hance,“Spicilegia Florae Sinensis: Diagnoses of New and Habitats of Rare or Hitherto Un-recorded Chinese Plants (X)”,Journal of Botany :British and Foreign, Vol.25,Jan.1887,pp.12-14.
③H.F.Hance,“Eugenias Quattuor Novas Sinenses” , Journal of Botany: British and Foreign,Vol.23,Jan. 1885,pp.7-8.
① Scott,Sir James George,France and Tongkin: A Narrative of the Campaign of 1884 and the Oc-cupation of Further India,London,1885.
本文为海南省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国际旅游岛背景下——海南非遗的开发与文化承载问题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HNSK(Z)12-74。
张军军,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①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第323页。
① 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第330页。
① 海南省人民政府文件,琼府〔2007〕49号,2010年6月,http://www.hainan.gov.cn/data/hnzb/2007/09/1120/。
② 张捷:《区域民俗文化的旅游资源的类型及旅游业价值研究——九寨沟藏族民俗文化与江苏吴文化民俗旅游资源比较研究之一》,《人文地理》1997年第3期。
①周和平:《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与探索》,《求是》2010年第4期。
① 洪余祥:《琼山县志》,海南出版社,2003,第101页。
①贺学君:《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思考》,《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②阎根齐:《海南历史文化——建设国际旅游岛的命脉》,《新东方》2009年第7期。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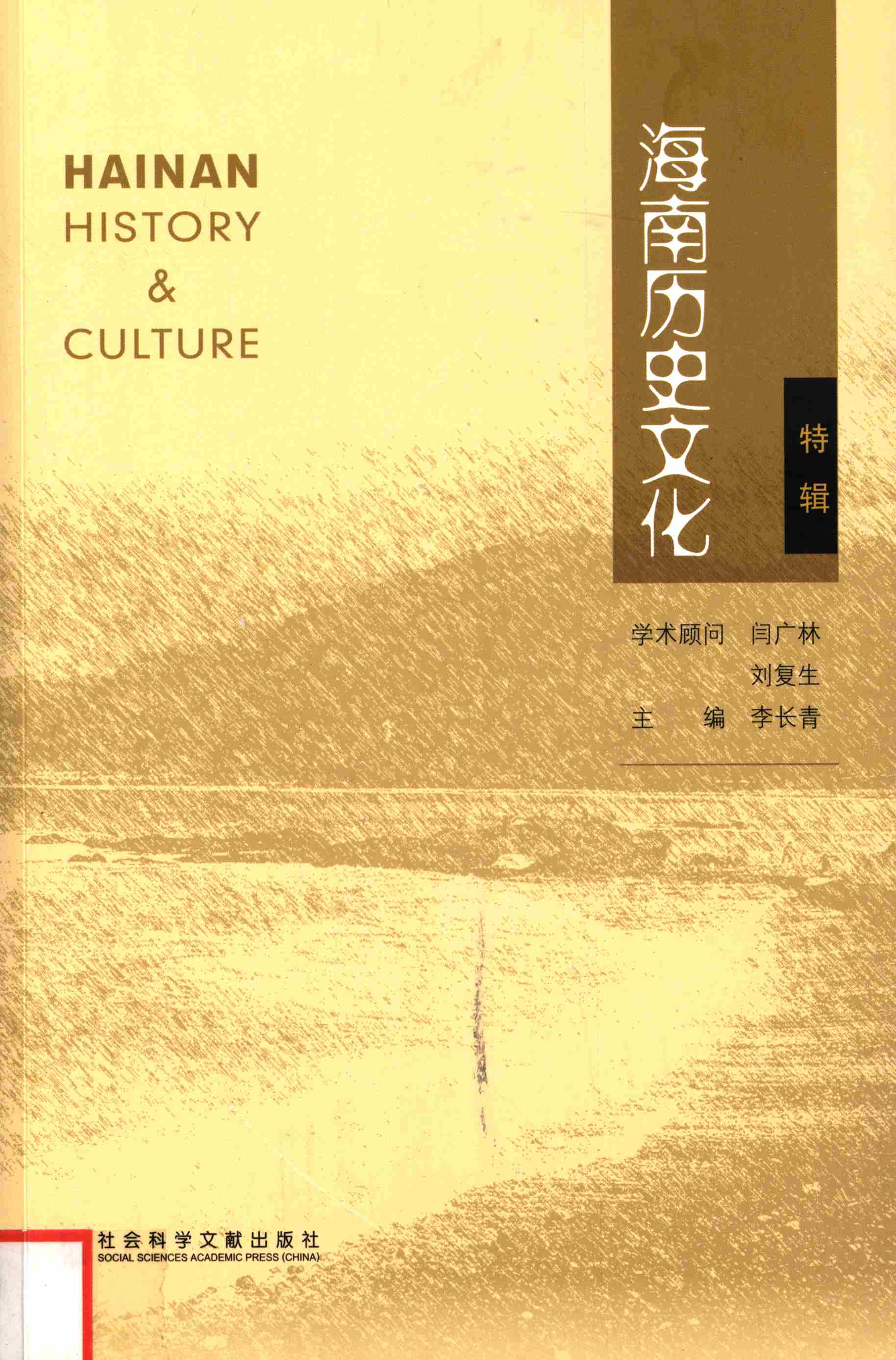
《海南历史文化.特辑》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本书设有历史渊源、文化嬗变、黎族研究、地方文化、移民文化、历史人物、海洋文化”七个栏目。收录了《海南史前考古概述》《1882年美国人香便文海南岛之行日期考》《黎族文身的抢救性保护与合理利用》《三亚历史上的族群和多元一体文化》《从地名看海南移民文化》等文章。
阅读
相关地名
海南省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