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创建仲田岭革命根据地
| 内容出处: | 《三亚海棠湾乡土人文录》 图书 |
| 唯一号: | 200120020230004184 |
| 颗粒名称: | 第三章 创建仲田岭革命根据地 |
| 分类号: | D267.4 |
| 页数: | 17 |
| 页码: | 93-109 |
| 摘要: | 本文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在仲田岭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背景、斗争经历和组织建设情况,并阐述了“肃反”左倾路线对革命事业的负面影响以及在战略转移中的重要作用。 |
| 关键词: | 仲田岭 革命根据地 斗争 |
内容
仲田岭是我陵崖党组织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根据地,坚持23年红旗不倒。山岭不算高,却被誉为“小小井冈山”、“小延安”。
第一节 仲田岭状貌
仲田岭,位于三亚市海棠湾镇西部,崖县(三亚市)、陵水、保亭三县边界甘什岭山脉分界的正中,古称峡岭。两岭对峙如门,巍峨雄壮,中间仄径深约60多米,海拔约800米,方圆约100多公里。向东眺望,便见汹涌澎湃的大海。北、西、南三面山深林密,相互环扣,逶迤连绵,直连吊罗山、扎南岭山脉,绿波万顷,辽阔苍茫。岭门有一个方圆约4000米,宽为800米,积雨面积为60多亩的自然山塘,古来为军事关隘,易守难攻,有优越的回旋余地。东南沿海有30多个汉族村庄,群山脚下散居着30多个黎族山寨,汉黎居民共有两万多人。1927年11月,藤桥武装暴动前,岭脚下的仲田村、北山村、岭脚塘村已建立仲田党支部和农会、妇会等组织,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
第二节 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
三亚(崖县)藤桥暴动胜利后,因受“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路线的影响,没有及时组织红军、农军去发展、巩固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而是让武装力量跟随东路红军进攻城市,造成藤桥武装力量大大削减,从而导致了暴动胜利后,遭敌人反扑,几经受挫,革命走向了低潮。200多名红军和500多名农军,从藤桥苏维埃保卫战中脱围转上仲田岭时,仅存区委委员占行诚和红军排长陈儒充带领陈保卿、陈贤德、黎学林等16人。1928年夏,原中共崖县委委员张开泰,从保亭营事件中突围后,带着枪伤,艰苦跋涉十多天到了陵水,几经周折后潜回仲田岭,终于同岭上坚持斗争的同志们会合,使大家在绝境中增强了信心,充满了希望。
由于暴动队伍受挫,力量薄弱,致使海棠湾苏区人民群众遭受敌人的大肆摧残,军田村、风塘村、仲田村,被扣上“共村”帽子,敌人纵火烧村,强迫军田村搬入椰子园村,由叛徒朱仁高监控。风塘村迁入新村,由反动民团团长蒙燕章管制。仲田村迁入岭脚塘村,村民的一切行动,都受到敌人的严密监管。敌军四出搜捕,严密封锁,红色老区乌云密布,红军与群众联系不上。一部分人心情沉重,情绪低落,对革命信心不足。突围上山的同志生活极为艰苦,十多人一个月也吃不上一口稀粥,只好摸鱼虾,捉小鸟,掏蚁卵,挖山茨,采野菜,摘野果充饥。
秋天,台风多,风雨大。在狂风暴雨之下,居住的茅屋片草不留,大家只好挨挤在大树底下。衣服破了,采野葵叶,扒樟树皮,抽麻丝一针一线织成雨衣,暂且防雨御寒。原始的热带雨林,树高林密,遮人耳目,难辨四季,只能从雨量的大小和湿度来判断时节。有时听到风摇树响,雨珠像瓢泼一样冲下来,叫人睁不开眼睛,好像匪兵追来,使人神经过敏,一阵紧张。
冬天,虽然无冰雪,但细雨濛濛,寒气凛冽,到处都是湿漉漉的,难以找到一块干燥的地方。由于夜间寒冷,难以抵挡,战士们采取钻木取火,围着篝火一边取暖一边打瞌睡。有一天中午,同志们分头去采山果时,忽然发现敌军从两路上山搜查。张开泰决定分两组向西、向北山腰疏散隐蔽。占行诚因小腿长疮行走困难,爬上一峰跌倒了,眼看敌兵快要追上来,同志们只好拼命地轮流背他翻过西峰,终于转危为安。在敌人围困的日子里,同志们忍受着难以想像的艰难困苦。他们一方面要同敌人作斗争,一方面要同自然困境搏斗,一方面要战胜饥饿、病伤。有人身上长满疮,有人因营养不良水肿,有人因病重倒下了。张开泰同志十分爱护战士们,他身先士卒,亲自采野稻、挖山薯、掏鸟蛋、捉鱼虾、筛蚁卵,并将它们混在一起捣成一团,然后用枇杷叶包扎好,涂上泥巴,再用火烙熟分发给同志们吃。他还采来山艾叶拧成绳条,用于燃烟驱蚊,采来珍珠草挤成汁用于治痢疾,采来“牛大力”煮水当茶饮,帮助大家恢复体力。张开泰带头吃苦,关心部下,使大家十分感动,大家互助鼓励,打起精神,顽强地坚持斗争。
仲田岭山前水塘西面的一块大石上(后称为第一岗),一株万年青树从石缝中挺立而起,远瞧像在水泊梁山上飘扬的“替天行道”的紫黄色旗帜。张开泰把队伍从深山转移到此处,面水背山地坚持革命斗争。
仲田岭的处境虽然艰难,但因有张开泰同志的带头作用,英明果敢,同志们又能团结友爱,顽强不屈,使得这场革命斗争充满了光明和希望。占行诚时常哼起“武松打虎上山冈”的琼剧小调。张开泰带领大家唱革命歌曲,激活斗志。张开泰经常组织文化学习,讲梁山水泊故事,讲革命道理,鼓励大家说:“琼崖特委一定在找我们,群众不会忘记我们。只要我们坚定信念,坚持到底,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他还说:“共产党人从入党那刻起,就把生命交给党,交给人民了,为了伟大的理想,为了给牺牲的同志报仇,我们一定要与仲田岭共存亡,仲田岭就是我们胜利的希望……”
王鸣亚联合王昭夷的匪兵几次搜山都没有发现红军的踪迹,认为张开泰及他的红军都完蛋了,便逐渐解除戒严。风塘、军田、仲田村民重新搬回老村建房居住,渐渐恢复了往日的生机。由于长时间没有联系上乡村群众,大家都心感不安。张开泰、占行诚和陈儒充等商议,认为照此下去,是自己把自己孤立起来,只能被动挨打。有人说不如冲出去同敌人决一死战,为死去的同志报仇,死也光荣。张开泰很冷静,他认为仇是要报的,但不能轻易去送死,能活下来就是要保存力量,就是要继续高高举起暴动的革命红旗,坚持斗争到最后胜利。现在革命尚有力量,那些被打散的红军、农军必然隐潜在各地,红色村庄虽然被摧毁了,但是各地的党组织决不会被敌人完全打垮,找到他们就会有希望。张开泰将大家分成四个小组,从四个方向观察敌情。占行诚带领的小组在通往甘什村的西边,发现甘什岭至南林峒一带有敌兵巡逻。陈儒充等三人摸到东侧岭门处观察,发现仲田老村已被敌人烧毁,群众在山塘前坡建起新村庄。约有十多个团丁驻扎在仲田新村,他们来回于山塘北面巡逻防守,不准群众上山收挖山兰、番薯。陈儒充等三人乘机潜入山兰园,拾到一个陶罐,摘一些山兰稻穗,挖点番薯,带回驻地。大家一起分析观察到的敌情,认为敌人还没有摸清我们的情况,如果莽撞行动,就会暴露自己,正好上敌人的当,陷入敌人的圈套,决定暂时不派员下山。夜间,他们趁黑摸到山兰园,摘些山兰稻穗,挖些地瓜,还找到了一些盐巴。他们用火把山兰稻谷烘干,在石片上磨出米粒,用土罐当锅煮粥充饥。十多人在仲田岭上度过了6个多月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生活,在海棠湾人民的支持下,终于走出了低谷。
第三节 仲田岭燃起熊熊之火
农历还是己巳年(民国十八年)十二月下旬,新历已跨进公元1929年2月。临近春节,王鸣亚决心对仲田岭进行一次大清剿,派100多名团丁,配合王昭夷黎兵100多人,从山前山后两路上山搜剿,强迫仲田村民10人带路。敌兵不清楚山上是否有红军,不敢深入。贪生怕死的团丁,到了山脚就胡乱鸣枪,当官的为了保命,下令草草收兵,报告王鸣亚说岭上全被搜过了,没发现“共匪”。原仲田村年轻的中共党员农军自卫队副队长黎亚吉,他凭经常巡山打猎的经验,从山兰园里挖薯的迹象来断定红军一定在山上。于是,他乘机避开敌人的视线逃入仲田岭,在铁门坎吹口哨为信号,寻找红军。张开泰在一峰石崖深处窥视,发现是黎亚吉,马上跟他接头。张开泰向黎亚吉了解乡村情况。黎亚吉说:“敌人太凶残了,连日来日日闻枪声,夜夜见火光。移村封村,不准村民外出,连犁田、插秧也派兵监视,群众敢怒不敢言。”听了黎亚吉的汇报后,张开泰心情非常沉重,心里思忖,想要打开局面,必须下山,找到上级党组织,并争取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于是,张开泰决定由自己北上找特委,安排占行诚、陈儒充下村打探消息,其余的同志留在山上观察动静,坚持斗争。在黎亚吉的引路下,张开泰翻山越岭,绕道到了后海渔村,找到1927年入党的中共党员林师泽,林师泽用船把张开泰送到北营港。在万宁县城,经过苦苦的探访,张开泰终于遇上琼崖特委派来联络工作的朱运泽同志,得知特委已转移到母瑞山。朱运泽对张开泰说:“特委指示,目前在海南岛的国民党军队正在换防,要求各地的同志,要抓住新军队入琼尚未站稳脚跟之前的有利时机,迅速恢复各级党组织,扩充我军力量,发动群众掀起第二次土地革命高潮。”占行诚、陈儒充也找到分散隐蔽的王传录、蒙传良、林诗润、罗中兴、王文贵、黎学江、符大尧等同志,带他们到山上与同志们会合。
张开泰返回仲田岭,见到失散的蒙传良、林诗润、王文贵等50多名同志时,高兴得热泪盈眶。他们互相拥抱,高唱着《国际歌》,洪亮的歌声在山谷里回荡着。张开泰向大家讲述了遇见特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朱运泽同志的经过,并决定根据特委的指示精神,恢复中共崖三区委,建立根据地,开展持久的敌后斗争。大家一致赞同,选举张开泰为区委书记,委员占行诚、蒙传良、林诗润、王文贵、陈儒充。同时,恢复崖三区苏维埃政府,选举林诗润为主席,委员陈保卿、蒙传良、王文贵、祝兴礼、陈贤德。成立崖三区农会,主席蒙传良。成立区团委,团委书记罗中兴,副书记陈保标,委员罗中邦、罗中华、王卷颜、黄乐民。
国民党崖县县长王鸣亚的反动民团,因长时间封锁搜山找不到红军踪影,渐渐放松了戒严。中共崖三区委、苏区政府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派员分别下到各乡村,重新开展活动,动员潜伏的军政人员上山,壮大武装力量。由于敌人的摧残,部分群众心有余悸,不敢接触我们的同志,开展活动遇到了困难。为了尽快打开局面,中共崖三区委派员秘密潜回风塘村,杀掉了土豪恶霸蒙庆贵及反动分子符文兴,灭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给人民群众壮了胆。这一行动,缴获步枪1支,找回隐藏的步枪2支、粉枪5支。张开泰派老红军王传录回军田村以他家作为交通联络站,其任务:第一是联系、接头,使失散的同志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并尽快带送上仲田岭革命根据地;第二是组织购买粮食、日用品等物资,支持仲田岭革命根据地;第三是收集敌人情报,并及时报送;第四是把村骨干组织起来,秘密进行斗争;第五是对来联系但不认识的人,要搞清来历,才带上山。张开泰安排谢文山同志负责同王传录接头,化装成卖糖果的货郎挑担下到军田等村叫卖,把分散隐蔽各地的革命同志带上山。通过军田交通联络站,我方先后找到特委派来的林鸿蛟、高球、符致雄等7位同志。接着,我方又设立土福湾、扛牛、仕榴、后海4个联络站。负责人分别是林诗润、李仕刚、叶亚山、杨秀山。张开泰和林鸿蛟多次下军田村、白田土村,把风塘、洪李邻近村庄的农会骨干召集到白土田村召开各种会议,帮助原农会和农军干部家属和革命烈属消除恐惧心理,通过努力,军田、风塘、洪李、椰子园等村民众重新树立起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的信任。
仲田岭革命根据地的建立,革命声势不断扩大,使敌人惊恐不安。1929年5月,时值张开泰母亲病重,敌人利用这一时机到处张贴招降布告,诱惑说:“张开泰先生,你母亲在病中常叫你的名字,十分想念你,家乡的父老乡亲都希望你回来见上一面。如果你能回来,我们决不伤害你,你要什么都可以解决。”张开泰同志看到了布告,想到病危的母亲,想到父亲过早离开人世,母亲年轻轻就守寡,带着兄妹四人过着贫苦的生活。他很想去见母亲最后一面,却又考虑到,仲田岭革命根据地需要他。他想,同志们需要他,这个母亲是会理解的,为了革命他化悲痛为力量,坚守在战斗岗位上。
张开泰、林鸿蛟深入到赤田、南土岭等黎族村庄找到共产党员苏运祥、陈文会,共同宣传发动群众,恢复党组织,建立起高土村联络站。张开泰和林鸿蛟还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潜入国民党龙江民团驻地,在敌人眼皮下,于新村召开党员、骨干会议,恢复党的组织,从而再次渐渐地打开了斗争的局面。
1929年7月,区委派区团委书记罗中兴和苏区委员王文贵利用过去他们曾在山村当过教师的有利条件,到保亭地区搞黎民运动,组建农会和兵变工作。罗中兴和王文贵组织他们教过的学生,通过他们深入宣传发动,黎族人民群众逐渐有所觉悟,消除了民族隔阂。原在叛徒王昭夷手下当兵的王德录、王德祥兄弟俩深明大义,反戈一击,带领40多名少数民族兄弟携带武器起义,投奔仲田岭革命根据地,收编为苏区自卫大队,任命王德录为队长。
为武装队伍,开展对敌斗争,区委派员从农村中找回藤桥起义挫折撤退时埋藏的步枪3支、粉枪5支,重建起红军连60人,连长林诗润,副连长陈儒充。有了枪杆子,有了武装队伍,群众看到了希望,看到了革命的曙光,支持革命的信心增强了。后海、风塘、军田、仲田、庄头、大灶、下丈等村,在党支部的发动下,群众自觉收粮,捐物资支持红军。后海交通站长、革命堡垒户杨秀山,活动于各渔船,收集布料、咸鱼、盐巴等物资,源源不断地送上仲田岭。
仲田岭名声大扬,王鸣亚惶惶不可终日。他虚张声势恐吓说,要踏平仲田岭,消灭“共匪”。他派500多名县民团乡丁,分别驻扎于甘什村、南林村、龙江村,对汉族村庄推行“五家联保”、“出村领证,回村收证”等高压措施,贴出“五杀”公告:“参共者杀,见共不报者杀,窝藏共匪者杀,通共者杀,支持共匪者杀。”他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杀害我革命老区群众30多名。在白色恐怖下,群众不敢随便走动,我党的工作又陷入了艰难境地。根据地人民在敌人的高压下,吸取了起义受挫折的教训,琢磨出用智慧同敌人周旋。如石姆龙村革命堡垒户王达明,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利用下地干活为名,用牛粪掩盖粮食,用牛车拉上宝福田洋藏于石穴,仲田联络站长黎亚辉接到通知,星夜带领运粮队将粮食运送到我军驻地。白土田村革命母亲黎金銮在环境十分恶劣的情况下,毅然挺身而出,担当起运粮队的妇女队长和通讯联络工作。仲田村十多户村民受尽了敌人的百般摧残,对国民党反动派恨之入骨,在黎亚吉的带领下,全村自愿离开家园,搬进仲田岭深山种山兰、玉米和砍竹笋支持革命,并同红军并肩作战。群众的热忱,大大地鼓舞了红军战士们的革命斗志。
1930年5月,红军从灶子村甲长黄道全口中了解到,藤桥保甲团龙江分团副团长黄守宇带领团丁到灶子村收月饷的消息。抓住这一歼灭敌人的有利时机,区委派陈贤德、陈保卿带领12名红军战士在灶子和新村交叉路口埋伏,打死3个保甲兵,缴获3支步枪,团丁不敢抵抗溃逃。同年10月,区委获悉风塘村土豪蒙庆贵的儿子蒙燕安是龙江保甲团的一个小头目,看中同村女青年陈亚梅。于是,派区团委副书记陈保标去做陈亚梅的思想工作,要她保持与蒙燕安的恋爱关系,探听反动民团的行动情况。同年12月,陈亚梅从蒙燕安口中得知龙江民团副团长王仕贤于12月24日带队上藤桥市的消息。我军提前埋伏在石姆龙村前龙坡塘公路边,消灭了保甲团丁十多名,缴获了12支步枪,王仕贤当场被击毙,其余团丁仓惶逃命。
打一仗,长一智。中共崖三区委根据形势的需要,果断地提出“日伏夜击,个别吃掉,消灭小股,开展策反,壮大队伍,震慑敌人,夺取胜利”的战略思想。1931年初春,区委派风塘村团支书占道和潜入藤桥保甲团当兵做内应。同年端午节前一天,根据掌握的情报,乘着藤桥市民开展龙舟比赛活动,乘着敌人麻痹时,张开泰率领56名武装人员化装成市民,通过内应,奇袭保甲团,将其全部歼灭,缴获60多支步枪和10支短枪,以及粮食和物资。这一战役,威震陵崖保边区,对搞黎民运动创造了条件。经过宣传教育,仲田岭附近的赤田、南土岭、田湾等村庄的黎族群众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民团的反动面目,主动向我党我军靠拢。
为把仲田岭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党政军民一齐动手挖战壕,彻垒石,在交通要道挖暗沟安竹箭,吊竹排箭,挂吊枪,设陷阱,决心把敢于来犯的敌人葬在山底。仲田岭似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吓得敌人胆战心惊。伪县长王鸣亚恼羞成怒,虚张声势,叫嚷“一个月消灭共匪”。他四出搜刮民财,招兵买马,利用叛徒陈贤光(风塘村人,人称精仔),当游击队长,加强防守藤桥地区。
为惩治叛徒,振我军威,1930年8月的一天傍晚,张开泰组织40多人分三小队攻打藤桥守敌。一队化装成渔民,从藤桥合口港扛着鱼虾,登岸插入区公所;一队扮成龙江民团乡丁,从西桥直插入市内;一队由张开泰带领10人扮成卖山货的苗民,先到市中心,乘着夜幕,点火为号。从三个交叉点集中火力,扑向守敌,敌人晕头转向,胡乱鸣枪,引起敌军打敌军。我军乘机集中火力消灭守敌20多人,缴获步枪十多支和一批子弹,胜利而归。
为不断扩大战果,动摇敌军军心,扩大红色区域,造就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1931年7月,张开泰派苏区政府委员双枪英雄王文贵带领5名自卫队员到红花、罗逢黎村开展工作。当时,该地区由苏打虎为首的12名“山猫”(土匪类)统治。他们经常打村劫舍。当听到汉人带队入村建立农会时,他担心被吃掉。7月的一天傍晚,“山猫”向王鸣亚告密,王鸣亚派县团丁一小队8名配合“山猫”,乘我不备之机,下村偷袭我工作组,王文贵在激战中不幸负伤被捕,惨遭杀害,砍头示众,尸体被藏在水沟里。王文贵同志的警卫员跑回仲田岭向区委报告,张开泰接到王文贵同志牺牲的噩耗后,怒发冲冠,立即带领20名红军战士赶到罗逢,彻底消灭了这帮为非作歹的“山猫”,在群众的协助下找到王委员的头颅带回安葬。张开泰发动群众,铲除敌人的余党,培养骨干,建立起农会和乡人民政府。张开泰回到仲田岭驻地,派苏区政府主席林诗润至陵水县城,同已打入驻陵水县城国民党海军陆战队第五连当排长的共产党员陈平联系,共同开展策反活动,争取到该连副连长陈国霖的支持,将敌连长打死,率领全连90多名士兵起义,开上仲田岭。区委根据特委的指示,将这支起义军改编为琼崖红军第三营,营长陈平,副营长陈国霖。同年8月8日,陈平带兵配合自卫队进攻藤桥,击毙守敌20多人,缴获步枪13支,子弹1000多发。接着攻打陵水县中区秀峰民团,不经一打,全部投降,缴获步枪40余支,俘虏反动民团团长和大土豪。接着,我军以突如其来的速度包围袭击陵水县政府,敌人惊慌失措,仓促撤离县城。我军占领县城,打开牢狱,救出30多名群众,军威大振。区委为了扩大影响,在仲田岭召开2000多名群众参加的祝捷大会。会后,区委在仲田、北山、南土岭等黎族村庄挑选出思想进步的青壮年,建立起2支共有30人的运输队,配合仲田岭部队作战。还派员到甘什村、南林峒、南旦一带开展宣传发动工作,把曾经一度被王昭夷控制的村庄变成红色根据地,使仲田岭同陵水县、保亭县红色区域连成一片。
第四节 中共陵崖县委在仲田岭成立
为更加有利于指导崖县、陵水、保亭各地党组织开展工作,掀起第二次土地革命高潮,琼崖特委决定崖县、陵水两县合并。在特委委员王伯伦的指导下,于1931年10月,在崖县三区仲田岭革命根据地成立中共陵崖县委员会,书记王克礼,委员张开泰、王伯伦、廖仕英、王玉花(妇女主任),秘书林鸿蛟。陵崖县委辖管陵水县、崖县、保亭县毛政弓、加答弓和五弓、七弓地区。
县委成立后,派共产党员李亚光、黄光焘等30余名农军骨干到琼崖特委驻地母瑞山领回50支步枪,特委还派90名青年骨干到仲田岭,组成红军第五连,由张开泰任连长。加强对县自卫队200人,两个运输队30人,各乡村自卫队500多人的培训,不断提高战斗力。在县委领导下,以红军连为主力,自卫队配合,把仲田岭根据地周围残存的龙江、南土岭民团据点彻底拔掉。在军田、番园、风塘、北山、仲田等乡苏维埃政权已巩固的基础上,又新建起8个乡苏维埃政府。此时,陵水县苏维埃政府也迁驻仲田岭。陵崖县委办起苏区学校,设立小卖部(消费部),有咸鱼盐巴等日杂物资出售。干部家属都驻进仲田岭苏区。人多志气旺,县委和崖三区委号召大家动手,开展生产运动,办起军政学校、医院、制衣厂、兵工厂和军政农场,养牛十多只,养猪十多头,养三鸟200多只,垦荒种水稻200多亩,还种山兰、玉米、花生、香蕉等作物。仲田岭革命根据地成为了琼西南的革命摇篮,成为有志青年向往的“小小井冈山”,也称“小延安”。
为更好地指导陵崖保地区各级党组织的工作,中共陵崖县委向辖区党组织,发出第1号、第2号通告和告团丁书,动员国民党士兵认清形势,弃暗投明,以进一步打击国民党反动派。①
革命形势向前发展,斗争就显得更加激烈。1931年秋,陵崖县委炊事班班长冯德明带领5名同志到藤桥市买菜。当挑菜回到泮水田洋时被国民党民团包围,5名同志全部被捕杀害。同年秋的某一天,张开泰带陈保标到海棠湾石姆龙村召开党员、农会干部会议,传达县委的通告,了解藤桥的敌情,布置收粮筹款工作。刚要进村时,他们遇到国民党伪乡长蒙国才和他的乡丁(张与蒙同是风塘村人),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双方展开了一场激战。战斗中张开泰被子弹擦破了一块头皮,顿时鲜血直流。蒙国才见状大喜,高喊:“谁抓住共匪头子张开泰,赏大洋200块。”匪兵闻讯,蜂拥而上。情况万分危急,开泰急中生智,脱下上衣,用上衣紧紧捆住尖刀,然后用力向敌兵抛去,敌兵以为是手榴弹,连忙伏倒在地,开泰、保标乘此潜入山林,安全脱险,回到仲田岭驻地,经治疗很快恢复。
迅速把仲田岭革命烽火燃遍陵崖大地,掀起第二次土地革命高潮是中共陵崖县委的中心任务。1932年1月21日,中共陵崖县委在仲田岭召开全陵崖苏维埃代表大会。大会由张开泰主持,王克礼作报告。大会期间,我方组织上千名干部群众游行示威,在武装的护卫下,队伍从仲田岭游行到军田、番园、洪李、风塘村。人们手举钩镰、斧头、小红旗,吹着军号,一路高呼:“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进攻苏区!”“被压迫的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官僚军阀!”“反对压迫剥削,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各村群众在村路口摆设开水、椰子水热情接待游行队伍。革命的浪潮感召陵、崖、保边区,许多青年纷纷上仲田岭,投身革命。藤桥市女青年王玉连,男朋友黄荣益在藤桥区保甲团当兵,她规劝他认清形势,弃暗投明,不要为国民党反动派卖命。黄接受女友的劝导,同好友林道华一起,各带一支七九式步枪和200发子弹,奔上仲田岭参加红军。黄荣益在椰子寨战役中光荣牺牲,留下英名。
中共陵崖县委在苏区代表会议前后,为鼓舞各级党组织的斗志,继之发出“决议”和“通告”。(见三亚市委党史研究室《崖县革命史资料汇编》)
陵崖苏维埃代表大会结束后,县委书记王克礼带领红军连两个排到陵水大里地区开展工作,由张开泰主持县委的全面工作。张开泰指派蒙传良到莺歌海找林克泽,检查县委“通告”和“决议”的实施情况,传达县委的指示,要求他抓紧恢复崖城、保平、港门、水南、红塘等地区党的组织活动,抓紧领导渔民开展对敌斗争和发展党员工作,不断壮大党组织的力量,扩大党的影响。张开泰在林鸿蛟的协助下,组织军民加固防御工事,办好军政学校培训军政干部,建立医院、制衣厂,建立起10个粮食物资仓库。革命影响非常之深广,群众的革命热情十分高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父送子、妻送夫、夫妻双双上战场和国民党民团士兵纷纷弃暗投明的动人事迹,从而使仲田岭革命根据地的红色区域扩大到了崖、陵、保周边各个村庄并连成一片,使仲田岭形成了“山已森严壁垒坚”的堡垒。
第五节 “肃反”左倾路线导致革命走向低潮
1932年初,中国工农红军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在福建打败了蔡廷锴的部队,从缴获敌人的文件中,发现我们内部有“AB”团组织,这些文件转到了海南。琼崖特委先抓了冯勋等人,开展了全琼的“肃反”清查“AB”分子运动。同年8月,特委从机要室派林诗耀以巡视员身份到陵崖抓“肃反”运动。在红军连长王贻起和一个排长护送下,林诗耀上仲田岭见到王克礼、张开泰、林鸿蛟等同志,传达了特委关于开展“肃反”运动的指示,指出陵崖存在40余名社党,并圈出一批干部名单,把县团委书记廖仕英,县妇联会主任王玉花,红军连指导员林才尤,排长欧朝庆及黎学林、陈保卿、占行诚、占行周、占行亲等当AB分子杀害,许多红军战士也被无故解除武装,勒令离队,干部家属也被遣散,有些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害怕被株连,偷偷逃离。县自卫队和运输队被迫散伙,回村不敢上山。群众也被吓得不敢接近红军。500多人的革命武装,最后仅存30多人,武装力量大大削弱,许多干部战士在心灵上蒙上了一层阴影,对革命的前途产生了怀疑。沸腾的仲田岭陷入沉思中。
1932年7月,广东军阀陈济棠派遣他的警卫旅和一个空军中队,由旅长陈汉光带领来琼配合地方武装,执行蒋介石的反共内战方针,大举向苏区和红军进行围剿。10月,陈汉光派其飞机配合步兵围剿陵水县太平峒至大里一带革命根据地。时值中共陵崖县委书记王克礼出差大里指导工作,被叛徒黄大忠(原大里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出卖,带敌围剿,不幸壮烈牺牲。红军30多人阵亡,红军连长王贻超等12人被捕到陵水县城英勇就义。有十多名红军冲出重围,隐蔽深山。陵崖县委书记王克礼牺牲的噩耗传来,在仲田岭的中共陵崖县委负责人张开泰和琼崖特委派来抓“肃反”工作的林诗耀,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赶到大里,四处寻找,从六弓潜入吊罗山大里乡一带,找到脱险的十多名战士,带回仲田岭根据地。
陈汉光和崖县伪县长王鸣亚闻悉陵崖县委的情况后,下令军队和地方民团分兵驻扎仲田岭周围的村庄,实行移民并村政策,仲田岭战火纷飞,硝烟弥漫。敌人围剿封锁,贴出五杀公告:“当匪者杀,投共者杀,见共不报者杀,济共者杀,藏共者杀。”来自内部“左”倾的伤害以及外部敌对势力的清剿,形势极端严峻,处境十分恶劣,革命又一次走向低潮。
第六节 实行战略转移,挺进崖西南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封锁,陵崖县委和红军的力量显得十分薄弱。在危急关头,县委委员张开泰同志毅然担起挽救陵崖的沉重担子。他同林诗耀商量在危难中寻找出路的办法。经研究认为,崖西南的莺歌海和昌感地区有几股地方力量互相牵制割据,王鸣亚的势力不敢伸到那里去,敌人力量较薄弱,且有我们的同志在那里活动,如林克泽同志在莺歌海当党支部书记。据此,县委决定,为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实行战略转移,挺进崖西南。为安全转移,先由交通员黄初乙带林诗耀下去联系。诗耀在莺歌海找到林克泽后,三人一起返回仲田岭。经再次商定,除留下部分当地同志坚持斗争外,队伍分两批撤离。第一批20多人,由林克泽、林鸿蛟(又名林豪,县委秘书)、林诗润带领转移;第二批十多人,由张开泰、林诗耀、王国栋带领转移。他们于1933年4月到达莺歌海,与当地的武装会合。县委决定将所有的武装力量,合编为琼崖工农红军第五连,连长陈文光,副连长陈世德,林鸿蛟为指导员。红五连和陵崖县委一起,以尖锋岭为据点,在琼崖西南一带开展武装斗争。在林克泽的配合下,张开泰、林诗耀到崖城、保港、保平等地活动,同当时在保平活动的何赤、吴金琪联系上,一起开展工作。后回莺歌海指挥红五连开展对敌斗争。琼崖工农红军第五连成立不久,获悉王鸣亚的走私船停泊在望楼港海边,就星夜赶到埋伏袭击,缴获敌人七九式步枪14支,左轮手枪2支,6门铜炮,50箱鸦片和200块光洋等物资。王鸣亚气急败坏,叫嚣要彻底消灭张开泰这帮“共匪”。他同陈汉光互相勾结,狼狈为奸。陈汉光旅和王鸣亚的反动民团共1000多名兵丁,对尖锋岭地区进行围剿,严密封锁出入山区的通道,隔断部队与群众的联系,企图把红军困死在山上。党政干部和红军战士,自力更生,克服困难,顽强地坚持斗争。但因形势严峻,环境恶劣,又找不到上级党组织,张开泰领导的陵崖县委果断地作出决定:红五连化整为零,分散到仲田岭、六弓峒、莺歌海、望楼港和感恩县的新村、板桥墟等地,以从事某种职业作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张开泰、林诗耀各出25块光洋买下新村一个荒废了的盐田,和林克泽一起带领20多名战士,一起做盐工。张开泰还以卖瓜子作掩护,在板桥一带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一天,二排长陈天贵和两个班长经不起艰苦斗争的考验,串通一气,偷走两支驳壳手枪出逃。张开泰、林诗耀、林鸿蛟、林克泽、林诗润经研究认为:不能待在新村港盐田了,必须离开这里,分散隐蔽,中共陵崖县委被迫解体。时值1934年初,大家推选张开泰、林诗耀北上找琼崖特委,从仲田岭来的12名战士由林诗润、王国栋带领,携带武器潜回仲田岭或陵水县六峒。盐田工作交林克泽负责。张开泰、林诗耀北上在文昌、琼山、万宁、儋州等地都找不到特委,俩人都不死心,分工张开泰重返感恩盐田,林诗耀在琼山以教师身份继续开展秘密联络活动。张开泰回到盐田后,又以卖瓜子生意做掩护,在感恩北黎一带开展联络活动,所到村庄大家都亲热地称呼他为“瓜子老板”。
1933年初,陵崖县委和红军撤离后,仲田岭革命根据地,无时不遭受敌人的围剿。在岭上坚持斗争的自卫队,在共产党员中共崖三区团委书记罗中兴、陈保标,中队长黎亚吉等的领导下,采取了白天在村中劳动,夜间集中研究,组织群众开展反对“移民并村”的斗争,终于粉碎了敌人企图消灭我苏区和红军的阴谋。1934年7月,林诗润从感恩县带回的12名红军战士,回到陵水县傲盆村时遭敌人打散。林诗润潜回藤桥岭头坡村老家,因国民党崖县东三区反动区长梁英标告密被捕送到崖城监狱。1936年初,张开泰再次北上找特委,3月以教书做掩护,在陵水县山村教书。一天,他正在上课,被到村里来探情报的叛徒李亚来认出,立即赶到英州炮楼向敌军报告,并亲自带领国民党联防队的匪兵将张开泰拘捕投进陵水县陵城监狱。敌人每星期提审两次,严刑拷打,用烧红的铁铲烫,用辣椒水往鼻子里灌,使用“坐飞机”、上“老虎凳”等酷刑,迫他承认是“共匪”头子张开泰。不管敌人用怎么的酷刑,张开泰都坚定地说:“我是教书先生,名叫吴伯雄,琼山县人。我不是共产党,也不认识共产党。”敌人又拉来叛徒李亚来同他对质,指着张开泰大叫:“张开泰,你不是琼山县的吴伯雄,你是崖县藤桥区风塘村的张开泰,中共陵崖地区的党委书记。”张开泰睁大眼睛怒视他,叛徒李亚来低下头,柔声地说:“开泰兄,大势已去了,硬挺着对你有什么好处,还不如痛痛快快承认,还有官做呢。”面对叛徒指控,张开泰毫不心慌,做好了牺牲的思想准备,示意叛徒走近他的身边,狠狠向他脸上唾口水。5月,张开泰又被押到崖县崖城监狱。在狱中和林诗润一起组织狱友开展斗争。1937年10月底,双手沾满了陵崖革命人民和共产党人鲜血的王昭夷,因敌人内部矛盾引起“狗咬狗”而被捕,也投进崖城监狱。开泰获悉后,就同林诗润等同志商议惩治这个叛徒的方法。一次利用放风的机会,出其不意地将麻袋套住这个作恶多端的叛徒,将其狠狠揍了一顿,被打昏迷,狱役发现抬走。总算为当年“保亭营血案”殉难的同志们出了一口气。后因被告密,林诗润同志在监狱中被敌人杀害。张开泰同志于1940年由党组织营救出狱,回到革命队伍中来,领导人民继续开展对敌斗争。
第七节 在仲田岭恢复和创建的基层
党政军群组织建制
(按时间顺序排列)
一、恢复中共崖三区委
书记:张开泰(1929.春—1929.秋)
委员:陈保辉(1929.秋—1931.秋)
罗玉山(1931.秋—1933.春)
蒙传良(兼秘书1929.秋—1933.春)
陈育奇(1929.秋—1933.春)
中共崖三区委直属党支部21个
军田党支部、风塘一党支部、洪李党支部、藤桥党支部、龙楼党支部、风塘二党支部、椰子园党支部、庄头党支部、大灶党支部、新村党支部、番园党支部、灶子沙牛六党支部、下丈党支部、田尾党支部、仲田党支部、田岸党支部、大茅半岭党支部、赤田党支部、土福湾党支部、南头岭党支部、北山党支部。
二、1929年7月恢复充实的崖三区苏维埃政府
主席:林诗润(1929.7—1933.春)
委员:祝兴礼(1929.7—1933.春)
王文贵(1929.7—1933.春)
龙道学(1929.7—1933.春)
陈贤德(1929.7—1933.春)
罗亚宝(1929.7—1933.春)
黎光昭(1929.7—1933.春)
下属乡苏维埃政府
红埠乡苏维埃政府
乡长:李翠刚(1929.12—1933.3)
三灶乡苏维埃政府
乡长:欧振经(1929.12—1933.3)
赤峰乡苏维埃政府
乡长:罗南昌(1929.12—1933.3)
三、共青团崖三区委员会
书记:罗中兴(1929—1932)
陈保标(1929.春—1933.春)
四、崖三区妇女协会
主任:黄国英(女,1929.春—1933.春)
(一)中共陵崖县委
书记:王克礼(1931.秋—1932.12)
负责人:张开泰(1932.12—1934.春)
委员:王克礼(1931.秋—1932.12)
张开泰(1931.秋—1934.春)
王伯伦(1931.秋—)
林豪(1931.秋—1934.春)
廖仕英(1931.秋—1932.夏)
巡视员:林木光(林诗耀,1932.秋—1934.春)
秘书:林豪(1931.秋—1933.春)
共青团陵崖县委员会
书记:廖仕英(1931.秋—1932.夏)
陵崖县妇女协会主任:王玉花(1931.秋—1932.夏)
(二)县委直属下级地方党组织
崖县地区:中共崖三区委
中共崖西区委
陵水地区:中共中东区委
中共北区委
中共西区委
中共南区委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崖县党组织演变情况表
重建的红军连(80人)
连长:林诗润(1929.冬—1931.夏)
副连长:陈儒充(1929.冬—1931年.夏)
六个交通联系站:
军田站:负责人:王传录
土福湾:负责人:林诗润
扛牛站:负责人:李仕刚
仕榴站:负责人:叶亚山
后海站:负责人:杨秀山
傲牛岭站:负责人:李亚来
中共陵崖县委组建的红军第五连(90人)
连长:陈文光(1931—1932.夏)
副连长:陈世德(1931—1932)
指导员:林木(林鸿蛟)(1931—1932.夏)
县政府自卫大队:
队长:陈保卿(1931—1932.夏)
副队长:黎亚吉(1931—1932.夏)
党代表:林诗润(1931—1932.夏)
第一节 仲田岭状貌
仲田岭,位于三亚市海棠湾镇西部,崖县(三亚市)、陵水、保亭三县边界甘什岭山脉分界的正中,古称峡岭。两岭对峙如门,巍峨雄壮,中间仄径深约60多米,海拔约800米,方圆约100多公里。向东眺望,便见汹涌澎湃的大海。北、西、南三面山深林密,相互环扣,逶迤连绵,直连吊罗山、扎南岭山脉,绿波万顷,辽阔苍茫。岭门有一个方圆约4000米,宽为800米,积雨面积为60多亩的自然山塘,古来为军事关隘,易守难攻,有优越的回旋余地。东南沿海有30多个汉族村庄,群山脚下散居着30多个黎族山寨,汉黎居民共有两万多人。1927年11月,藤桥武装暴动前,岭脚下的仲田村、北山村、岭脚塘村已建立仲田党支部和农会、妇会等组织,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
第二节 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
三亚(崖县)藤桥暴动胜利后,因受“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路线的影响,没有及时组织红军、农军去发展、巩固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而是让武装力量跟随东路红军进攻城市,造成藤桥武装力量大大削减,从而导致了暴动胜利后,遭敌人反扑,几经受挫,革命走向了低潮。200多名红军和500多名农军,从藤桥苏维埃保卫战中脱围转上仲田岭时,仅存区委委员占行诚和红军排长陈儒充带领陈保卿、陈贤德、黎学林等16人。1928年夏,原中共崖县委委员张开泰,从保亭营事件中突围后,带着枪伤,艰苦跋涉十多天到了陵水,几经周折后潜回仲田岭,终于同岭上坚持斗争的同志们会合,使大家在绝境中增强了信心,充满了希望。
由于暴动队伍受挫,力量薄弱,致使海棠湾苏区人民群众遭受敌人的大肆摧残,军田村、风塘村、仲田村,被扣上“共村”帽子,敌人纵火烧村,强迫军田村搬入椰子园村,由叛徒朱仁高监控。风塘村迁入新村,由反动民团团长蒙燕章管制。仲田村迁入岭脚塘村,村民的一切行动,都受到敌人的严密监管。敌军四出搜捕,严密封锁,红色老区乌云密布,红军与群众联系不上。一部分人心情沉重,情绪低落,对革命信心不足。突围上山的同志生活极为艰苦,十多人一个月也吃不上一口稀粥,只好摸鱼虾,捉小鸟,掏蚁卵,挖山茨,采野菜,摘野果充饥。
秋天,台风多,风雨大。在狂风暴雨之下,居住的茅屋片草不留,大家只好挨挤在大树底下。衣服破了,采野葵叶,扒樟树皮,抽麻丝一针一线织成雨衣,暂且防雨御寒。原始的热带雨林,树高林密,遮人耳目,难辨四季,只能从雨量的大小和湿度来判断时节。有时听到风摇树响,雨珠像瓢泼一样冲下来,叫人睁不开眼睛,好像匪兵追来,使人神经过敏,一阵紧张。
冬天,虽然无冰雪,但细雨濛濛,寒气凛冽,到处都是湿漉漉的,难以找到一块干燥的地方。由于夜间寒冷,难以抵挡,战士们采取钻木取火,围着篝火一边取暖一边打瞌睡。有一天中午,同志们分头去采山果时,忽然发现敌军从两路上山搜查。张开泰决定分两组向西、向北山腰疏散隐蔽。占行诚因小腿长疮行走困难,爬上一峰跌倒了,眼看敌兵快要追上来,同志们只好拼命地轮流背他翻过西峰,终于转危为安。在敌人围困的日子里,同志们忍受着难以想像的艰难困苦。他们一方面要同敌人作斗争,一方面要同自然困境搏斗,一方面要战胜饥饿、病伤。有人身上长满疮,有人因营养不良水肿,有人因病重倒下了。张开泰同志十分爱护战士们,他身先士卒,亲自采野稻、挖山薯、掏鸟蛋、捉鱼虾、筛蚁卵,并将它们混在一起捣成一团,然后用枇杷叶包扎好,涂上泥巴,再用火烙熟分发给同志们吃。他还采来山艾叶拧成绳条,用于燃烟驱蚊,采来珍珠草挤成汁用于治痢疾,采来“牛大力”煮水当茶饮,帮助大家恢复体力。张开泰带头吃苦,关心部下,使大家十分感动,大家互助鼓励,打起精神,顽强地坚持斗争。
仲田岭山前水塘西面的一块大石上(后称为第一岗),一株万年青树从石缝中挺立而起,远瞧像在水泊梁山上飘扬的“替天行道”的紫黄色旗帜。张开泰把队伍从深山转移到此处,面水背山地坚持革命斗争。
仲田岭的处境虽然艰难,但因有张开泰同志的带头作用,英明果敢,同志们又能团结友爱,顽强不屈,使得这场革命斗争充满了光明和希望。占行诚时常哼起“武松打虎上山冈”的琼剧小调。张开泰带领大家唱革命歌曲,激活斗志。张开泰经常组织文化学习,讲梁山水泊故事,讲革命道理,鼓励大家说:“琼崖特委一定在找我们,群众不会忘记我们。只要我们坚定信念,坚持到底,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他还说:“共产党人从入党那刻起,就把生命交给党,交给人民了,为了伟大的理想,为了给牺牲的同志报仇,我们一定要与仲田岭共存亡,仲田岭就是我们胜利的希望……”
王鸣亚联合王昭夷的匪兵几次搜山都没有发现红军的踪迹,认为张开泰及他的红军都完蛋了,便逐渐解除戒严。风塘、军田、仲田村民重新搬回老村建房居住,渐渐恢复了往日的生机。由于长时间没有联系上乡村群众,大家都心感不安。张开泰、占行诚和陈儒充等商议,认为照此下去,是自己把自己孤立起来,只能被动挨打。有人说不如冲出去同敌人决一死战,为死去的同志报仇,死也光荣。张开泰很冷静,他认为仇是要报的,但不能轻易去送死,能活下来就是要保存力量,就是要继续高高举起暴动的革命红旗,坚持斗争到最后胜利。现在革命尚有力量,那些被打散的红军、农军必然隐潜在各地,红色村庄虽然被摧毁了,但是各地的党组织决不会被敌人完全打垮,找到他们就会有希望。张开泰将大家分成四个小组,从四个方向观察敌情。占行诚带领的小组在通往甘什村的西边,发现甘什岭至南林峒一带有敌兵巡逻。陈儒充等三人摸到东侧岭门处观察,发现仲田老村已被敌人烧毁,群众在山塘前坡建起新村庄。约有十多个团丁驻扎在仲田新村,他们来回于山塘北面巡逻防守,不准群众上山收挖山兰、番薯。陈儒充等三人乘机潜入山兰园,拾到一个陶罐,摘一些山兰稻穗,挖点番薯,带回驻地。大家一起分析观察到的敌情,认为敌人还没有摸清我们的情况,如果莽撞行动,就会暴露自己,正好上敌人的当,陷入敌人的圈套,决定暂时不派员下山。夜间,他们趁黑摸到山兰园,摘些山兰稻穗,挖些地瓜,还找到了一些盐巴。他们用火把山兰稻谷烘干,在石片上磨出米粒,用土罐当锅煮粥充饥。十多人在仲田岭上度过了6个多月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生活,在海棠湾人民的支持下,终于走出了低谷。
第三节 仲田岭燃起熊熊之火
农历还是己巳年(民国十八年)十二月下旬,新历已跨进公元1929年2月。临近春节,王鸣亚决心对仲田岭进行一次大清剿,派100多名团丁,配合王昭夷黎兵100多人,从山前山后两路上山搜剿,强迫仲田村民10人带路。敌兵不清楚山上是否有红军,不敢深入。贪生怕死的团丁,到了山脚就胡乱鸣枪,当官的为了保命,下令草草收兵,报告王鸣亚说岭上全被搜过了,没发现“共匪”。原仲田村年轻的中共党员农军自卫队副队长黎亚吉,他凭经常巡山打猎的经验,从山兰园里挖薯的迹象来断定红军一定在山上。于是,他乘机避开敌人的视线逃入仲田岭,在铁门坎吹口哨为信号,寻找红军。张开泰在一峰石崖深处窥视,发现是黎亚吉,马上跟他接头。张开泰向黎亚吉了解乡村情况。黎亚吉说:“敌人太凶残了,连日来日日闻枪声,夜夜见火光。移村封村,不准村民外出,连犁田、插秧也派兵监视,群众敢怒不敢言。”听了黎亚吉的汇报后,张开泰心情非常沉重,心里思忖,想要打开局面,必须下山,找到上级党组织,并争取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于是,张开泰决定由自己北上找特委,安排占行诚、陈儒充下村打探消息,其余的同志留在山上观察动静,坚持斗争。在黎亚吉的引路下,张开泰翻山越岭,绕道到了后海渔村,找到1927年入党的中共党员林师泽,林师泽用船把张开泰送到北营港。在万宁县城,经过苦苦的探访,张开泰终于遇上琼崖特委派来联络工作的朱运泽同志,得知特委已转移到母瑞山。朱运泽对张开泰说:“特委指示,目前在海南岛的国民党军队正在换防,要求各地的同志,要抓住新军队入琼尚未站稳脚跟之前的有利时机,迅速恢复各级党组织,扩充我军力量,发动群众掀起第二次土地革命高潮。”占行诚、陈儒充也找到分散隐蔽的王传录、蒙传良、林诗润、罗中兴、王文贵、黎学江、符大尧等同志,带他们到山上与同志们会合。
张开泰返回仲田岭,见到失散的蒙传良、林诗润、王文贵等50多名同志时,高兴得热泪盈眶。他们互相拥抱,高唱着《国际歌》,洪亮的歌声在山谷里回荡着。张开泰向大家讲述了遇见特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朱运泽同志的经过,并决定根据特委的指示精神,恢复中共崖三区委,建立根据地,开展持久的敌后斗争。大家一致赞同,选举张开泰为区委书记,委员占行诚、蒙传良、林诗润、王文贵、陈儒充。同时,恢复崖三区苏维埃政府,选举林诗润为主席,委员陈保卿、蒙传良、王文贵、祝兴礼、陈贤德。成立崖三区农会,主席蒙传良。成立区团委,团委书记罗中兴,副书记陈保标,委员罗中邦、罗中华、王卷颜、黄乐民。
国民党崖县县长王鸣亚的反动民团,因长时间封锁搜山找不到红军踪影,渐渐放松了戒严。中共崖三区委、苏区政府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派员分别下到各乡村,重新开展活动,动员潜伏的军政人员上山,壮大武装力量。由于敌人的摧残,部分群众心有余悸,不敢接触我们的同志,开展活动遇到了困难。为了尽快打开局面,中共崖三区委派员秘密潜回风塘村,杀掉了土豪恶霸蒙庆贵及反动分子符文兴,灭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给人民群众壮了胆。这一行动,缴获步枪1支,找回隐藏的步枪2支、粉枪5支。张开泰派老红军王传录回军田村以他家作为交通联络站,其任务:第一是联系、接头,使失散的同志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并尽快带送上仲田岭革命根据地;第二是组织购买粮食、日用品等物资,支持仲田岭革命根据地;第三是收集敌人情报,并及时报送;第四是把村骨干组织起来,秘密进行斗争;第五是对来联系但不认识的人,要搞清来历,才带上山。张开泰安排谢文山同志负责同王传录接头,化装成卖糖果的货郎挑担下到军田等村叫卖,把分散隐蔽各地的革命同志带上山。通过军田交通联络站,我方先后找到特委派来的林鸿蛟、高球、符致雄等7位同志。接着,我方又设立土福湾、扛牛、仕榴、后海4个联络站。负责人分别是林诗润、李仕刚、叶亚山、杨秀山。张开泰和林鸿蛟多次下军田村、白田土村,把风塘、洪李邻近村庄的农会骨干召集到白土田村召开各种会议,帮助原农会和农军干部家属和革命烈属消除恐惧心理,通过努力,军田、风塘、洪李、椰子园等村民众重新树立起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的信任。
仲田岭革命根据地的建立,革命声势不断扩大,使敌人惊恐不安。1929年5月,时值张开泰母亲病重,敌人利用这一时机到处张贴招降布告,诱惑说:“张开泰先生,你母亲在病中常叫你的名字,十分想念你,家乡的父老乡亲都希望你回来见上一面。如果你能回来,我们决不伤害你,你要什么都可以解决。”张开泰同志看到了布告,想到病危的母亲,想到父亲过早离开人世,母亲年轻轻就守寡,带着兄妹四人过着贫苦的生活。他很想去见母亲最后一面,却又考虑到,仲田岭革命根据地需要他。他想,同志们需要他,这个母亲是会理解的,为了革命他化悲痛为力量,坚守在战斗岗位上。
张开泰、林鸿蛟深入到赤田、南土岭等黎族村庄找到共产党员苏运祥、陈文会,共同宣传发动群众,恢复党组织,建立起高土村联络站。张开泰和林鸿蛟还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潜入国民党龙江民团驻地,在敌人眼皮下,于新村召开党员、骨干会议,恢复党的组织,从而再次渐渐地打开了斗争的局面。
1929年7月,区委派区团委书记罗中兴和苏区委员王文贵利用过去他们曾在山村当过教师的有利条件,到保亭地区搞黎民运动,组建农会和兵变工作。罗中兴和王文贵组织他们教过的学生,通过他们深入宣传发动,黎族人民群众逐渐有所觉悟,消除了民族隔阂。原在叛徒王昭夷手下当兵的王德录、王德祥兄弟俩深明大义,反戈一击,带领40多名少数民族兄弟携带武器起义,投奔仲田岭革命根据地,收编为苏区自卫大队,任命王德录为队长。
为武装队伍,开展对敌斗争,区委派员从农村中找回藤桥起义挫折撤退时埋藏的步枪3支、粉枪5支,重建起红军连60人,连长林诗润,副连长陈儒充。有了枪杆子,有了武装队伍,群众看到了希望,看到了革命的曙光,支持革命的信心增强了。后海、风塘、军田、仲田、庄头、大灶、下丈等村,在党支部的发动下,群众自觉收粮,捐物资支持红军。后海交通站长、革命堡垒户杨秀山,活动于各渔船,收集布料、咸鱼、盐巴等物资,源源不断地送上仲田岭。
仲田岭名声大扬,王鸣亚惶惶不可终日。他虚张声势恐吓说,要踏平仲田岭,消灭“共匪”。他派500多名县民团乡丁,分别驻扎于甘什村、南林村、龙江村,对汉族村庄推行“五家联保”、“出村领证,回村收证”等高压措施,贴出“五杀”公告:“参共者杀,见共不报者杀,窝藏共匪者杀,通共者杀,支持共匪者杀。”他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杀害我革命老区群众30多名。在白色恐怖下,群众不敢随便走动,我党的工作又陷入了艰难境地。根据地人民在敌人的高压下,吸取了起义受挫折的教训,琢磨出用智慧同敌人周旋。如石姆龙村革命堡垒户王达明,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利用下地干活为名,用牛粪掩盖粮食,用牛车拉上宝福田洋藏于石穴,仲田联络站长黎亚辉接到通知,星夜带领运粮队将粮食运送到我军驻地。白土田村革命母亲黎金銮在环境十分恶劣的情况下,毅然挺身而出,担当起运粮队的妇女队长和通讯联络工作。仲田村十多户村民受尽了敌人的百般摧残,对国民党反动派恨之入骨,在黎亚吉的带领下,全村自愿离开家园,搬进仲田岭深山种山兰、玉米和砍竹笋支持革命,并同红军并肩作战。群众的热忱,大大地鼓舞了红军战士们的革命斗志。
1930年5月,红军从灶子村甲长黄道全口中了解到,藤桥保甲团龙江分团副团长黄守宇带领团丁到灶子村收月饷的消息。抓住这一歼灭敌人的有利时机,区委派陈贤德、陈保卿带领12名红军战士在灶子和新村交叉路口埋伏,打死3个保甲兵,缴获3支步枪,团丁不敢抵抗溃逃。同年10月,区委获悉风塘村土豪蒙庆贵的儿子蒙燕安是龙江保甲团的一个小头目,看中同村女青年陈亚梅。于是,派区团委副书记陈保标去做陈亚梅的思想工作,要她保持与蒙燕安的恋爱关系,探听反动民团的行动情况。同年12月,陈亚梅从蒙燕安口中得知龙江民团副团长王仕贤于12月24日带队上藤桥市的消息。我军提前埋伏在石姆龙村前龙坡塘公路边,消灭了保甲团丁十多名,缴获了12支步枪,王仕贤当场被击毙,其余团丁仓惶逃命。
打一仗,长一智。中共崖三区委根据形势的需要,果断地提出“日伏夜击,个别吃掉,消灭小股,开展策反,壮大队伍,震慑敌人,夺取胜利”的战略思想。1931年初春,区委派风塘村团支书占道和潜入藤桥保甲团当兵做内应。同年端午节前一天,根据掌握的情报,乘着藤桥市民开展龙舟比赛活动,乘着敌人麻痹时,张开泰率领56名武装人员化装成市民,通过内应,奇袭保甲团,将其全部歼灭,缴获60多支步枪和10支短枪,以及粮食和物资。这一战役,威震陵崖保边区,对搞黎民运动创造了条件。经过宣传教育,仲田岭附近的赤田、南土岭、田湾等村庄的黎族群众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民团的反动面目,主动向我党我军靠拢。
为把仲田岭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党政军民一齐动手挖战壕,彻垒石,在交通要道挖暗沟安竹箭,吊竹排箭,挂吊枪,设陷阱,决心把敢于来犯的敌人葬在山底。仲田岭似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吓得敌人胆战心惊。伪县长王鸣亚恼羞成怒,虚张声势,叫嚷“一个月消灭共匪”。他四出搜刮民财,招兵买马,利用叛徒陈贤光(风塘村人,人称精仔),当游击队长,加强防守藤桥地区。
为惩治叛徒,振我军威,1930年8月的一天傍晚,张开泰组织40多人分三小队攻打藤桥守敌。一队化装成渔民,从藤桥合口港扛着鱼虾,登岸插入区公所;一队扮成龙江民团乡丁,从西桥直插入市内;一队由张开泰带领10人扮成卖山货的苗民,先到市中心,乘着夜幕,点火为号。从三个交叉点集中火力,扑向守敌,敌人晕头转向,胡乱鸣枪,引起敌军打敌军。我军乘机集中火力消灭守敌20多人,缴获步枪十多支和一批子弹,胜利而归。
为不断扩大战果,动摇敌军军心,扩大红色区域,造就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1931年7月,张开泰派苏区政府委员双枪英雄王文贵带领5名自卫队员到红花、罗逢黎村开展工作。当时,该地区由苏打虎为首的12名“山猫”(土匪类)统治。他们经常打村劫舍。当听到汉人带队入村建立农会时,他担心被吃掉。7月的一天傍晚,“山猫”向王鸣亚告密,王鸣亚派县团丁一小队8名配合“山猫”,乘我不备之机,下村偷袭我工作组,王文贵在激战中不幸负伤被捕,惨遭杀害,砍头示众,尸体被藏在水沟里。王文贵同志的警卫员跑回仲田岭向区委报告,张开泰接到王文贵同志牺牲的噩耗后,怒发冲冠,立即带领20名红军战士赶到罗逢,彻底消灭了这帮为非作歹的“山猫”,在群众的协助下找到王委员的头颅带回安葬。张开泰发动群众,铲除敌人的余党,培养骨干,建立起农会和乡人民政府。张开泰回到仲田岭驻地,派苏区政府主席林诗润至陵水县城,同已打入驻陵水县城国民党海军陆战队第五连当排长的共产党员陈平联系,共同开展策反活动,争取到该连副连长陈国霖的支持,将敌连长打死,率领全连90多名士兵起义,开上仲田岭。区委根据特委的指示,将这支起义军改编为琼崖红军第三营,营长陈平,副营长陈国霖。同年8月8日,陈平带兵配合自卫队进攻藤桥,击毙守敌20多人,缴获步枪13支,子弹1000多发。接着攻打陵水县中区秀峰民团,不经一打,全部投降,缴获步枪40余支,俘虏反动民团团长和大土豪。接着,我军以突如其来的速度包围袭击陵水县政府,敌人惊慌失措,仓促撤离县城。我军占领县城,打开牢狱,救出30多名群众,军威大振。区委为了扩大影响,在仲田岭召开2000多名群众参加的祝捷大会。会后,区委在仲田、北山、南土岭等黎族村庄挑选出思想进步的青壮年,建立起2支共有30人的运输队,配合仲田岭部队作战。还派员到甘什村、南林峒、南旦一带开展宣传发动工作,把曾经一度被王昭夷控制的村庄变成红色根据地,使仲田岭同陵水县、保亭县红色区域连成一片。
第四节 中共陵崖县委在仲田岭成立
为更加有利于指导崖县、陵水、保亭各地党组织开展工作,掀起第二次土地革命高潮,琼崖特委决定崖县、陵水两县合并。在特委委员王伯伦的指导下,于1931年10月,在崖县三区仲田岭革命根据地成立中共陵崖县委员会,书记王克礼,委员张开泰、王伯伦、廖仕英、王玉花(妇女主任),秘书林鸿蛟。陵崖县委辖管陵水县、崖县、保亭县毛政弓、加答弓和五弓、七弓地区。
县委成立后,派共产党员李亚光、黄光焘等30余名农军骨干到琼崖特委驻地母瑞山领回50支步枪,特委还派90名青年骨干到仲田岭,组成红军第五连,由张开泰任连长。加强对县自卫队200人,两个运输队30人,各乡村自卫队500多人的培训,不断提高战斗力。在县委领导下,以红军连为主力,自卫队配合,把仲田岭根据地周围残存的龙江、南土岭民团据点彻底拔掉。在军田、番园、风塘、北山、仲田等乡苏维埃政权已巩固的基础上,又新建起8个乡苏维埃政府。此时,陵水县苏维埃政府也迁驻仲田岭。陵崖县委办起苏区学校,设立小卖部(消费部),有咸鱼盐巴等日杂物资出售。干部家属都驻进仲田岭苏区。人多志气旺,县委和崖三区委号召大家动手,开展生产运动,办起军政学校、医院、制衣厂、兵工厂和军政农场,养牛十多只,养猪十多头,养三鸟200多只,垦荒种水稻200多亩,还种山兰、玉米、花生、香蕉等作物。仲田岭革命根据地成为了琼西南的革命摇篮,成为有志青年向往的“小小井冈山”,也称“小延安”。
为更好地指导陵崖保地区各级党组织的工作,中共陵崖县委向辖区党组织,发出第1号、第2号通告和告团丁书,动员国民党士兵认清形势,弃暗投明,以进一步打击国民党反动派。①
革命形势向前发展,斗争就显得更加激烈。1931年秋,陵崖县委炊事班班长冯德明带领5名同志到藤桥市买菜。当挑菜回到泮水田洋时被国民党民团包围,5名同志全部被捕杀害。同年秋的某一天,张开泰带陈保标到海棠湾石姆龙村召开党员、农会干部会议,传达县委的通告,了解藤桥的敌情,布置收粮筹款工作。刚要进村时,他们遇到国民党伪乡长蒙国才和他的乡丁(张与蒙同是风塘村人),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双方展开了一场激战。战斗中张开泰被子弹擦破了一块头皮,顿时鲜血直流。蒙国才见状大喜,高喊:“谁抓住共匪头子张开泰,赏大洋200块。”匪兵闻讯,蜂拥而上。情况万分危急,开泰急中生智,脱下上衣,用上衣紧紧捆住尖刀,然后用力向敌兵抛去,敌兵以为是手榴弹,连忙伏倒在地,开泰、保标乘此潜入山林,安全脱险,回到仲田岭驻地,经治疗很快恢复。
迅速把仲田岭革命烽火燃遍陵崖大地,掀起第二次土地革命高潮是中共陵崖县委的中心任务。1932年1月21日,中共陵崖县委在仲田岭召开全陵崖苏维埃代表大会。大会由张开泰主持,王克礼作报告。大会期间,我方组织上千名干部群众游行示威,在武装的护卫下,队伍从仲田岭游行到军田、番园、洪李、风塘村。人们手举钩镰、斧头、小红旗,吹着军号,一路高呼:“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进攻苏区!”“被压迫的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官僚军阀!”“反对压迫剥削,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各村群众在村路口摆设开水、椰子水热情接待游行队伍。革命的浪潮感召陵、崖、保边区,许多青年纷纷上仲田岭,投身革命。藤桥市女青年王玉连,男朋友黄荣益在藤桥区保甲团当兵,她规劝他认清形势,弃暗投明,不要为国民党反动派卖命。黄接受女友的劝导,同好友林道华一起,各带一支七九式步枪和200发子弹,奔上仲田岭参加红军。黄荣益在椰子寨战役中光荣牺牲,留下英名。
中共陵崖县委在苏区代表会议前后,为鼓舞各级党组织的斗志,继之发出“决议”和“通告”。(见三亚市委党史研究室《崖县革命史资料汇编》)
陵崖苏维埃代表大会结束后,县委书记王克礼带领红军连两个排到陵水大里地区开展工作,由张开泰主持县委的全面工作。张开泰指派蒙传良到莺歌海找林克泽,检查县委“通告”和“决议”的实施情况,传达县委的指示,要求他抓紧恢复崖城、保平、港门、水南、红塘等地区党的组织活动,抓紧领导渔民开展对敌斗争和发展党员工作,不断壮大党组织的力量,扩大党的影响。张开泰在林鸿蛟的协助下,组织军民加固防御工事,办好军政学校培训军政干部,建立医院、制衣厂,建立起10个粮食物资仓库。革命影响非常之深广,群众的革命热情十分高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父送子、妻送夫、夫妻双双上战场和国民党民团士兵纷纷弃暗投明的动人事迹,从而使仲田岭革命根据地的红色区域扩大到了崖、陵、保周边各个村庄并连成一片,使仲田岭形成了“山已森严壁垒坚”的堡垒。
第五节 “肃反”左倾路线导致革命走向低潮
1932年初,中国工农红军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在福建打败了蔡廷锴的部队,从缴获敌人的文件中,发现我们内部有“AB”团组织,这些文件转到了海南。琼崖特委先抓了冯勋等人,开展了全琼的“肃反”清查“AB”分子运动。同年8月,特委从机要室派林诗耀以巡视员身份到陵崖抓“肃反”运动。在红军连长王贻起和一个排长护送下,林诗耀上仲田岭见到王克礼、张开泰、林鸿蛟等同志,传达了特委关于开展“肃反”运动的指示,指出陵崖存在40余名社党,并圈出一批干部名单,把县团委书记廖仕英,县妇联会主任王玉花,红军连指导员林才尤,排长欧朝庆及黎学林、陈保卿、占行诚、占行周、占行亲等当AB分子杀害,许多红军战士也被无故解除武装,勒令离队,干部家属也被遣散,有些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害怕被株连,偷偷逃离。县自卫队和运输队被迫散伙,回村不敢上山。群众也被吓得不敢接近红军。500多人的革命武装,最后仅存30多人,武装力量大大削弱,许多干部战士在心灵上蒙上了一层阴影,对革命的前途产生了怀疑。沸腾的仲田岭陷入沉思中。
1932年7月,广东军阀陈济棠派遣他的警卫旅和一个空军中队,由旅长陈汉光带领来琼配合地方武装,执行蒋介石的反共内战方针,大举向苏区和红军进行围剿。10月,陈汉光派其飞机配合步兵围剿陵水县太平峒至大里一带革命根据地。时值中共陵崖县委书记王克礼出差大里指导工作,被叛徒黄大忠(原大里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出卖,带敌围剿,不幸壮烈牺牲。红军30多人阵亡,红军连长王贻超等12人被捕到陵水县城英勇就义。有十多名红军冲出重围,隐蔽深山。陵崖县委书记王克礼牺牲的噩耗传来,在仲田岭的中共陵崖县委负责人张开泰和琼崖特委派来抓“肃反”工作的林诗耀,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赶到大里,四处寻找,从六弓潜入吊罗山大里乡一带,找到脱险的十多名战士,带回仲田岭根据地。
陈汉光和崖县伪县长王鸣亚闻悉陵崖县委的情况后,下令军队和地方民团分兵驻扎仲田岭周围的村庄,实行移民并村政策,仲田岭战火纷飞,硝烟弥漫。敌人围剿封锁,贴出五杀公告:“当匪者杀,投共者杀,见共不报者杀,济共者杀,藏共者杀。”来自内部“左”倾的伤害以及外部敌对势力的清剿,形势极端严峻,处境十分恶劣,革命又一次走向低潮。
第六节 实行战略转移,挺进崖西南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封锁,陵崖县委和红军的力量显得十分薄弱。在危急关头,县委委员张开泰同志毅然担起挽救陵崖的沉重担子。他同林诗耀商量在危难中寻找出路的办法。经研究认为,崖西南的莺歌海和昌感地区有几股地方力量互相牵制割据,王鸣亚的势力不敢伸到那里去,敌人力量较薄弱,且有我们的同志在那里活动,如林克泽同志在莺歌海当党支部书记。据此,县委决定,为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实行战略转移,挺进崖西南。为安全转移,先由交通员黄初乙带林诗耀下去联系。诗耀在莺歌海找到林克泽后,三人一起返回仲田岭。经再次商定,除留下部分当地同志坚持斗争外,队伍分两批撤离。第一批20多人,由林克泽、林鸿蛟(又名林豪,县委秘书)、林诗润带领转移;第二批十多人,由张开泰、林诗耀、王国栋带领转移。他们于1933年4月到达莺歌海,与当地的武装会合。县委决定将所有的武装力量,合编为琼崖工农红军第五连,连长陈文光,副连长陈世德,林鸿蛟为指导员。红五连和陵崖县委一起,以尖锋岭为据点,在琼崖西南一带开展武装斗争。在林克泽的配合下,张开泰、林诗耀到崖城、保港、保平等地活动,同当时在保平活动的何赤、吴金琪联系上,一起开展工作。后回莺歌海指挥红五连开展对敌斗争。琼崖工农红军第五连成立不久,获悉王鸣亚的走私船停泊在望楼港海边,就星夜赶到埋伏袭击,缴获敌人七九式步枪14支,左轮手枪2支,6门铜炮,50箱鸦片和200块光洋等物资。王鸣亚气急败坏,叫嚣要彻底消灭张开泰这帮“共匪”。他同陈汉光互相勾结,狼狈为奸。陈汉光旅和王鸣亚的反动民团共1000多名兵丁,对尖锋岭地区进行围剿,严密封锁出入山区的通道,隔断部队与群众的联系,企图把红军困死在山上。党政干部和红军战士,自力更生,克服困难,顽强地坚持斗争。但因形势严峻,环境恶劣,又找不到上级党组织,张开泰领导的陵崖县委果断地作出决定:红五连化整为零,分散到仲田岭、六弓峒、莺歌海、望楼港和感恩县的新村、板桥墟等地,以从事某种职业作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张开泰、林诗耀各出25块光洋买下新村一个荒废了的盐田,和林克泽一起带领20多名战士,一起做盐工。张开泰还以卖瓜子作掩护,在板桥一带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一天,二排长陈天贵和两个班长经不起艰苦斗争的考验,串通一气,偷走两支驳壳手枪出逃。张开泰、林诗耀、林鸿蛟、林克泽、林诗润经研究认为:不能待在新村港盐田了,必须离开这里,分散隐蔽,中共陵崖县委被迫解体。时值1934年初,大家推选张开泰、林诗耀北上找琼崖特委,从仲田岭来的12名战士由林诗润、王国栋带领,携带武器潜回仲田岭或陵水县六峒。盐田工作交林克泽负责。张开泰、林诗耀北上在文昌、琼山、万宁、儋州等地都找不到特委,俩人都不死心,分工张开泰重返感恩盐田,林诗耀在琼山以教师身份继续开展秘密联络活动。张开泰回到盐田后,又以卖瓜子生意做掩护,在感恩北黎一带开展联络活动,所到村庄大家都亲热地称呼他为“瓜子老板”。
1933年初,陵崖县委和红军撤离后,仲田岭革命根据地,无时不遭受敌人的围剿。在岭上坚持斗争的自卫队,在共产党员中共崖三区团委书记罗中兴、陈保标,中队长黎亚吉等的领导下,采取了白天在村中劳动,夜间集中研究,组织群众开展反对“移民并村”的斗争,终于粉碎了敌人企图消灭我苏区和红军的阴谋。1934年7月,林诗润从感恩县带回的12名红军战士,回到陵水县傲盆村时遭敌人打散。林诗润潜回藤桥岭头坡村老家,因国民党崖县东三区反动区长梁英标告密被捕送到崖城监狱。1936年初,张开泰再次北上找特委,3月以教书做掩护,在陵水县山村教书。一天,他正在上课,被到村里来探情报的叛徒李亚来认出,立即赶到英州炮楼向敌军报告,并亲自带领国民党联防队的匪兵将张开泰拘捕投进陵水县陵城监狱。敌人每星期提审两次,严刑拷打,用烧红的铁铲烫,用辣椒水往鼻子里灌,使用“坐飞机”、上“老虎凳”等酷刑,迫他承认是“共匪”头子张开泰。不管敌人用怎么的酷刑,张开泰都坚定地说:“我是教书先生,名叫吴伯雄,琼山县人。我不是共产党,也不认识共产党。”敌人又拉来叛徒李亚来同他对质,指着张开泰大叫:“张开泰,你不是琼山县的吴伯雄,你是崖县藤桥区风塘村的张开泰,中共陵崖地区的党委书记。”张开泰睁大眼睛怒视他,叛徒李亚来低下头,柔声地说:“开泰兄,大势已去了,硬挺着对你有什么好处,还不如痛痛快快承认,还有官做呢。”面对叛徒指控,张开泰毫不心慌,做好了牺牲的思想准备,示意叛徒走近他的身边,狠狠向他脸上唾口水。5月,张开泰又被押到崖县崖城监狱。在狱中和林诗润一起组织狱友开展斗争。1937年10月底,双手沾满了陵崖革命人民和共产党人鲜血的王昭夷,因敌人内部矛盾引起“狗咬狗”而被捕,也投进崖城监狱。开泰获悉后,就同林诗润等同志商议惩治这个叛徒的方法。一次利用放风的机会,出其不意地将麻袋套住这个作恶多端的叛徒,将其狠狠揍了一顿,被打昏迷,狱役发现抬走。总算为当年“保亭营血案”殉难的同志们出了一口气。后因被告密,林诗润同志在监狱中被敌人杀害。张开泰同志于1940年由党组织营救出狱,回到革命队伍中来,领导人民继续开展对敌斗争。
第七节 在仲田岭恢复和创建的基层
党政军群组织建制
(按时间顺序排列)
一、恢复中共崖三区委
书记:张开泰(1929.春—1929.秋)
委员:陈保辉(1929.秋—1931.秋)
罗玉山(1931.秋—1933.春)
蒙传良(兼秘书1929.秋—1933.春)
陈育奇(1929.秋—1933.春)
中共崖三区委直属党支部21个
军田党支部、风塘一党支部、洪李党支部、藤桥党支部、龙楼党支部、风塘二党支部、椰子园党支部、庄头党支部、大灶党支部、新村党支部、番园党支部、灶子沙牛六党支部、下丈党支部、田尾党支部、仲田党支部、田岸党支部、大茅半岭党支部、赤田党支部、土福湾党支部、南头岭党支部、北山党支部。
二、1929年7月恢复充实的崖三区苏维埃政府
主席:林诗润(1929.7—1933.春)
委员:祝兴礼(1929.7—1933.春)
王文贵(1929.7—1933.春)
龙道学(1929.7—1933.春)
陈贤德(1929.7—1933.春)
罗亚宝(1929.7—1933.春)
黎光昭(1929.7—1933.春)
下属乡苏维埃政府
红埠乡苏维埃政府
乡长:李翠刚(1929.12—1933.3)
三灶乡苏维埃政府
乡长:欧振经(1929.12—1933.3)
赤峰乡苏维埃政府
乡长:罗南昌(1929.12—1933.3)
三、共青团崖三区委员会
书记:罗中兴(1929—1932)
陈保标(1929.春—1933.春)
四、崖三区妇女协会
主任:黄国英(女,1929.春—1933.春)
(一)中共陵崖县委
书记:王克礼(1931.秋—1932.12)
负责人:张开泰(1932.12—1934.春)
委员:王克礼(1931.秋—1932.12)
张开泰(1931.秋—1934.春)
王伯伦(1931.秋—)
林豪(1931.秋—1934.春)
廖仕英(1931.秋—1932.夏)
巡视员:林木光(林诗耀,1932.秋—1934.春)
秘书:林豪(1931.秋—1933.春)
共青团陵崖县委员会
书记:廖仕英(1931.秋—1932.夏)
陵崖县妇女协会主任:王玉花(1931.秋—1932.夏)
(二)县委直属下级地方党组织
崖县地区:中共崖三区委
中共崖西区委
陵水地区:中共中东区委
中共北区委
中共西区委
中共南区委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崖县党组织演变情况表
重建的红军连(80人)
连长:林诗润(1929.冬—1931.夏)
副连长:陈儒充(1929.冬—1931年.夏)
六个交通联系站:
军田站:负责人:王传录
土福湾:负责人:林诗润
扛牛站:负责人:李仕刚
仕榴站:负责人:叶亚山
后海站:负责人:杨秀山
傲牛岭站:负责人:李亚来
中共陵崖县委组建的红军第五连(90人)
连长:陈文光(1931—1932.夏)
副连长:陈世德(1931—1932)
指导员:林木(林鸿蛟)(1931—1932.夏)
县政府自卫大队:
队长:陈保卿(1931—1932.夏)
副队长:黎亚吉(1931—1932.夏)
党代表:林诗润(1931—1932.夏)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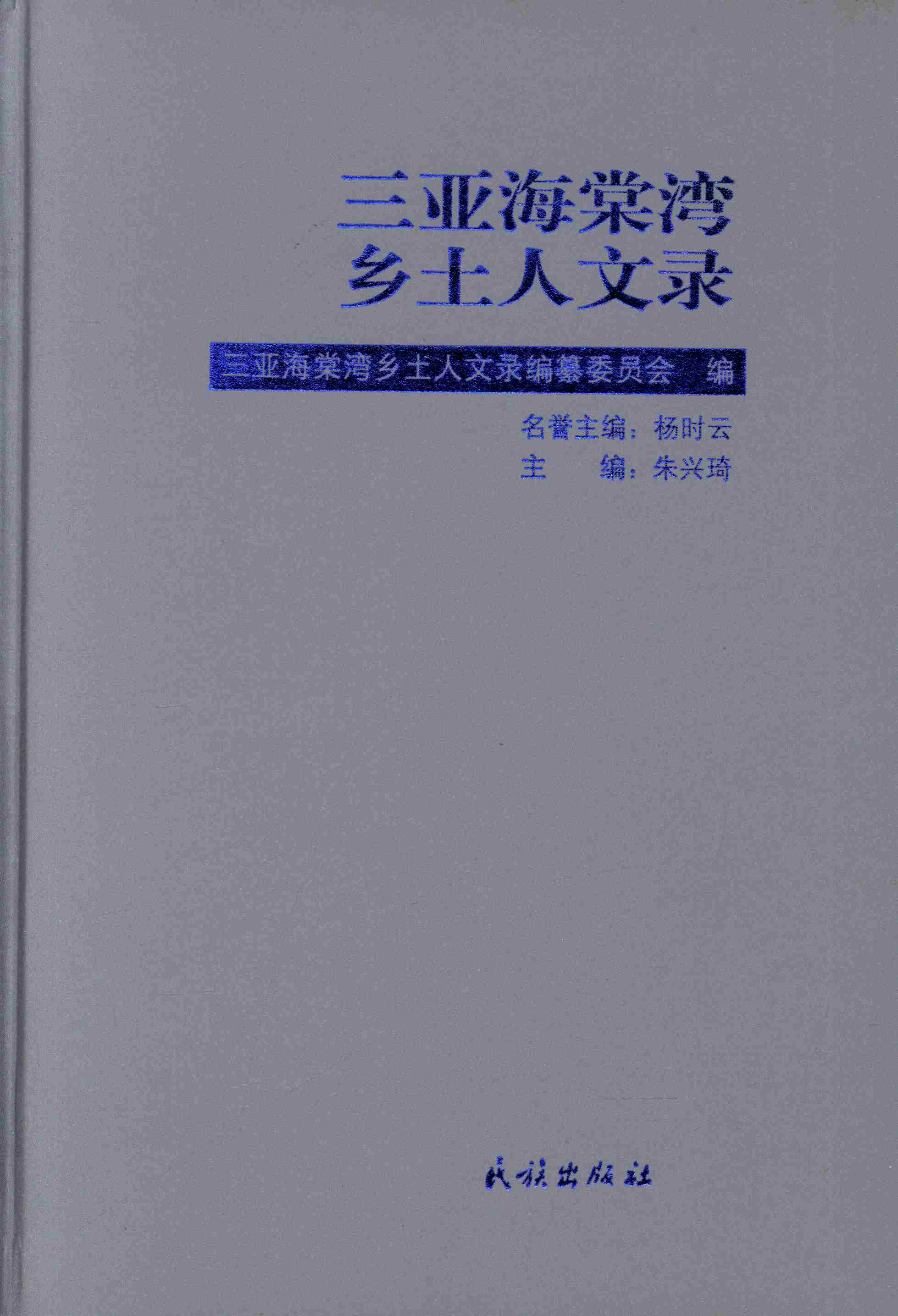
《三亚海棠湾乡土人文录》
出版者:民族出版社
本书分为建制沿革、自然资源、乡土浩气、赤胆忠魂、民族民俗民娱、乡貌新姿、乡土名士录八编,介绍了三亚海棠湾区域、建制沿革、古迹、商旅、地质与地貌、气候、地产与特产、黎族人民抗日斗争等内容。
阅读
相关地名
三亚市海棠湾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