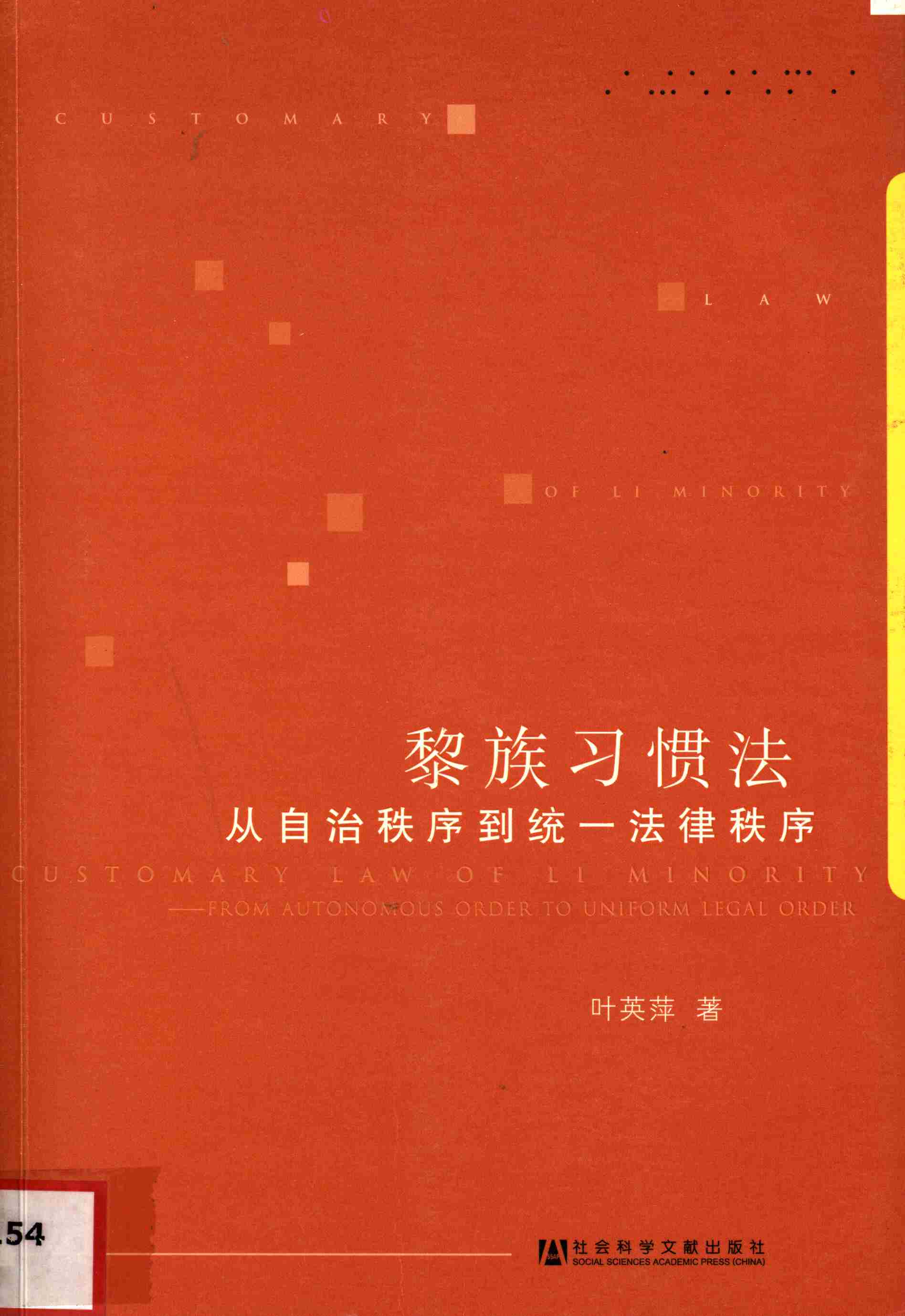内容
黎峒中的峒首职位并非男性权威长辈的特权,文献中有明确提及女性任峒首的情形。而且女性峒首可以将自己的位置传给女性继承人继续担任。“峒中有王二娘者,黎之酋也,夫之名不闻,家饶于财,善用其众,力能制服群黎,朝廷赐封宜人。琼管有令于黎峒,必下王宜人,无不帖然。二娘死,女亦能继其业。”①清代史料中记载了黎族地区在过去发生内部纠纷的时候,只要有妇女出面干预或者调解,就可以平息下来。如张庆长《黎岐纪闻》:“(黎人)……一语言不合,辄持弓矢标枪相向,势不可当,有妇人从中间之,即立解。”《广东新语》、《黎岐纪闻》、《峒溪纤志》、《琼黎一览》、《琼崖黎岐风俗图说》第三十三图等书,都曾记载过去一些地区的黎族当内部发生纠纷时,只要妇女出面干预或调解,就可息兵解仇。《琼州海黎图》以生动形象的图画描绘了妇女解决纠纷的作用:一名男子手拿弓箭,与另一名持刀男子打斗,一位妇女上前劝解。该图右上角的文字介绍说:“黎性悍而质直,间有同类,一语不合,辄操戈矢相向,得妇人架中一劝,随亦解释。”②这样的史料记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黎人社会母权制度的残余。
根据在保亭县“合亩制”地区的调查,以前毛枝峒和毛道峒发生械斗,最后达成和解协议时,双方还要各派寡妇一人为代表,举行一种传统的和解仪式,黎语称“蕊岔”,在汉语中也叫做“给眼”。举行仪式时,双方先后于一碗清水中,拿起两个铜钱抹对方的眼,然后被抹眼的人接过铜钱,往脑后抛掉。经过这个重归于好的仪式后,他们相信若有反悔食言者眼睛会变瞎。①该案在《黎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具体记载道:清末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合亩制”地区毛枝峒和毛道峒发生械斗时,最终达成和解协议,双方各派出寡妇一人为代表,举行一种传统的和解仪式,黎语叫“蕊岔”。在谈判时,毛道代表带了一个老寡妇,毛枝代表也找一老寡妇作陪。毛道的老妇来到门前时,毛枝老妇站在门内,手托清水一碗,碗内放一个铜钱,门前的旁边,置一个破水缸。毛道老妇从碗内拿出铜钱,抹毛枝老妇的双眼,口念“毛道打死你们的人,你们不要朦眼,要开开眼,以后好来往,好做亲戚”等语,念毕把钱放回碗中;毛枝老妇再拿出铜钱来抹毛道老妇双眼,口念“毛枝打死你们的人,要你们的牛,你们也不要朦眼,要开开眼,以后好来往,也可以做亲戚”,念毕把钱交给毛道老妇,毛道老妇把钱丢在背后,接着毛枝老妇把那碗水倒掉,用右手按水缸,口念前语,毛道老妇亦如此做。进屋后两个老妇对坐,中间放鸡、猪、牛肉各一碗,酒两碗,毛道老妇倒些酒在地上念:“不要朦眼,毛道人好来毛枝,毛枝人好去毛道,子子孙孙做好亲戚”;毛枝老妇亦如此做。然后毛道老妇撕一些鸡肉丢在地上,再念前语,毛枝老妇也如此做。她们做毕,开始吃酒,那三碗肉只能给两个寡妇吃。谈判,则由代表进行。谈判完毕,双方代表各拿出一枝箭并在一起,先由毛道代表在近箭头处砍1刀,再由毛枝代表在近箭头处砍1刀,然后再在另一边的中间各砍1刀,最后折断箭头,表示今后不互相射杀打仗,各执断箭为凭。喝完了酒,毛道代表带牛颈和装水的碗、小水缸回去,到半路把碗和水缸丢掉。②
从上述史料和案例的阐述可以看出,虽然黎族血族复仇、械斗比较普遍,但妇女在氏族械斗和血族纠纷中起到了一种特殊的调解作用。黎族妇女在纠纷解决中确实具有的化解矛盾的作用,以及她化解矛盾的方法与效力,与黎民对妇女地位的尊崇、古老的宗教禁忌是难以分开的。
综上,黎族习惯法解决纠纷的方式,基本上是在权威和首领主导下的协商解决,而械斗则是纠纷解决机制中最有效的暴力手段,且是双方最终通过谈判实现妥协与媾和的重要阶段。习惯法不同于现代国家法,具有强大的国家实力作为法律实现的后盾,实现习惯法的力量本源在于绝大多数群众自发的遵守和支持,而遵守和支持在根本上取决于内容的合理性。习惯法的形成、改变乃至消亡都是在润物无声的状态下完成的,它没有专门的制定组织,也没有固定的立法程序,民众自觉的遵守就是其形成的标志。以黎族习惯法为例,当黎族人民自觉遵守历代传承的行为规范时,习惯法是隐藏在生活中的,如果不去提炼和凝结,我们甚至无法发现其客观存在形式。但纠纷的发生往往是对习惯法的稳定和权威最直接的震撼,如果原有的习惯被违背,而无法恢复到原有状态,破坏固有法律秩序的行为人不受到应有责罚,那么就很难说黎族内部形成了严格意义上的习惯法。习惯法中纠纷解决机制的本质在同单位内,是发动社会单元内全体群众的力量,在权威和首领的指导下,对违背习惯法的行为进行公议,使违法者成为单位内大众的对立面。在生产力不发达的黎族地区,这种对立事实意味着生存空间的丧失,进而使违法者承受巨大的社会压力,主动改正,力求和解。而一旦和平方式无法解决问题,则利用全单位的力量共同暴力解决。而在不同组织之间的纠纷解决机制,最终转化为实力的比拼,而由于双方武力的震慑,通常可以将械斗转化为谈判,避免更多的暴力与流血。
暂且不讨论该机制的合理性,根据笔者对资料的分析和实际走访调查得到的情况来看,上述纠纷解决机制确实具有明显的效果,黎族习惯法和其所维护的自治秩序也在该机制的护航下,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被保存与传承,实现了黎族的延续与发展。
根据在保亭县“合亩制”地区的调查,以前毛枝峒和毛道峒发生械斗,最后达成和解协议时,双方还要各派寡妇一人为代表,举行一种传统的和解仪式,黎语称“蕊岔”,在汉语中也叫做“给眼”。举行仪式时,双方先后于一碗清水中,拿起两个铜钱抹对方的眼,然后被抹眼的人接过铜钱,往脑后抛掉。经过这个重归于好的仪式后,他们相信若有反悔食言者眼睛会变瞎。①该案在《黎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具体记载道:清末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合亩制”地区毛枝峒和毛道峒发生械斗时,最终达成和解协议,双方各派出寡妇一人为代表,举行一种传统的和解仪式,黎语叫“蕊岔”。在谈判时,毛道代表带了一个老寡妇,毛枝代表也找一老寡妇作陪。毛道的老妇来到门前时,毛枝老妇站在门内,手托清水一碗,碗内放一个铜钱,门前的旁边,置一个破水缸。毛道老妇从碗内拿出铜钱,抹毛枝老妇的双眼,口念“毛道打死你们的人,你们不要朦眼,要开开眼,以后好来往,好做亲戚”等语,念毕把钱放回碗中;毛枝老妇再拿出铜钱来抹毛道老妇双眼,口念“毛枝打死你们的人,要你们的牛,你们也不要朦眼,要开开眼,以后好来往,也可以做亲戚”,念毕把钱交给毛道老妇,毛道老妇把钱丢在背后,接着毛枝老妇把那碗水倒掉,用右手按水缸,口念前语,毛道老妇亦如此做。进屋后两个老妇对坐,中间放鸡、猪、牛肉各一碗,酒两碗,毛道老妇倒些酒在地上念:“不要朦眼,毛道人好来毛枝,毛枝人好去毛道,子子孙孙做好亲戚”;毛枝老妇亦如此做。然后毛道老妇撕一些鸡肉丢在地上,再念前语,毛枝老妇也如此做。她们做毕,开始吃酒,那三碗肉只能给两个寡妇吃。谈判,则由代表进行。谈判完毕,双方代表各拿出一枝箭并在一起,先由毛道代表在近箭头处砍1刀,再由毛枝代表在近箭头处砍1刀,然后再在另一边的中间各砍1刀,最后折断箭头,表示今后不互相射杀打仗,各执断箭为凭。喝完了酒,毛道代表带牛颈和装水的碗、小水缸回去,到半路把碗和水缸丢掉。②
从上述史料和案例的阐述可以看出,虽然黎族血族复仇、械斗比较普遍,但妇女在氏族械斗和血族纠纷中起到了一种特殊的调解作用。黎族妇女在纠纷解决中确实具有的化解矛盾的作用,以及她化解矛盾的方法与效力,与黎民对妇女地位的尊崇、古老的宗教禁忌是难以分开的。
综上,黎族习惯法解决纠纷的方式,基本上是在权威和首领主导下的协商解决,而械斗则是纠纷解决机制中最有效的暴力手段,且是双方最终通过谈判实现妥协与媾和的重要阶段。习惯法不同于现代国家法,具有强大的国家实力作为法律实现的后盾,实现习惯法的力量本源在于绝大多数群众自发的遵守和支持,而遵守和支持在根本上取决于内容的合理性。习惯法的形成、改变乃至消亡都是在润物无声的状态下完成的,它没有专门的制定组织,也没有固定的立法程序,民众自觉的遵守就是其形成的标志。以黎族习惯法为例,当黎族人民自觉遵守历代传承的行为规范时,习惯法是隐藏在生活中的,如果不去提炼和凝结,我们甚至无法发现其客观存在形式。但纠纷的发生往往是对习惯法的稳定和权威最直接的震撼,如果原有的习惯被违背,而无法恢复到原有状态,破坏固有法律秩序的行为人不受到应有责罚,那么就很难说黎族内部形成了严格意义上的习惯法。习惯法中纠纷解决机制的本质在同单位内,是发动社会单元内全体群众的力量,在权威和首领的指导下,对违背习惯法的行为进行公议,使违法者成为单位内大众的对立面。在生产力不发达的黎族地区,这种对立事实意味着生存空间的丧失,进而使违法者承受巨大的社会压力,主动改正,力求和解。而一旦和平方式无法解决问题,则利用全单位的力量共同暴力解决。而在不同组织之间的纠纷解决机制,最终转化为实力的比拼,而由于双方武力的震慑,通常可以将械斗转化为谈判,避免更多的暴力与流血。
暂且不讨论该机制的合理性,根据笔者对资料的分析和实际走访调查得到的情况来看,上述纠纷解决机制确实具有明显的效果,黎族习惯法和其所维护的自治秩序也在该机制的护航下,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被保存与传承,实现了黎族的延续与发展。
附注
①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二《海外黎蛮》条,周伟民、唐玲玲辑纂点校《历代文人笔记中的海南》,海南出版社,2006,第19页。
② 《琼州海黎图》第十五幅画,参见谭爱萍《黎族画卷古籍——<琼州海黎图>点校》,海南省民族研究所《拂拭历史尘埃——黎族古籍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第133页。
① 参见《黎族简史》的有关章节,也可参见邢关英《黎族——民族知识从书》,民族出版社,2004,第31页。
② 参见广东省编辑组编《黎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出版社,1986,第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