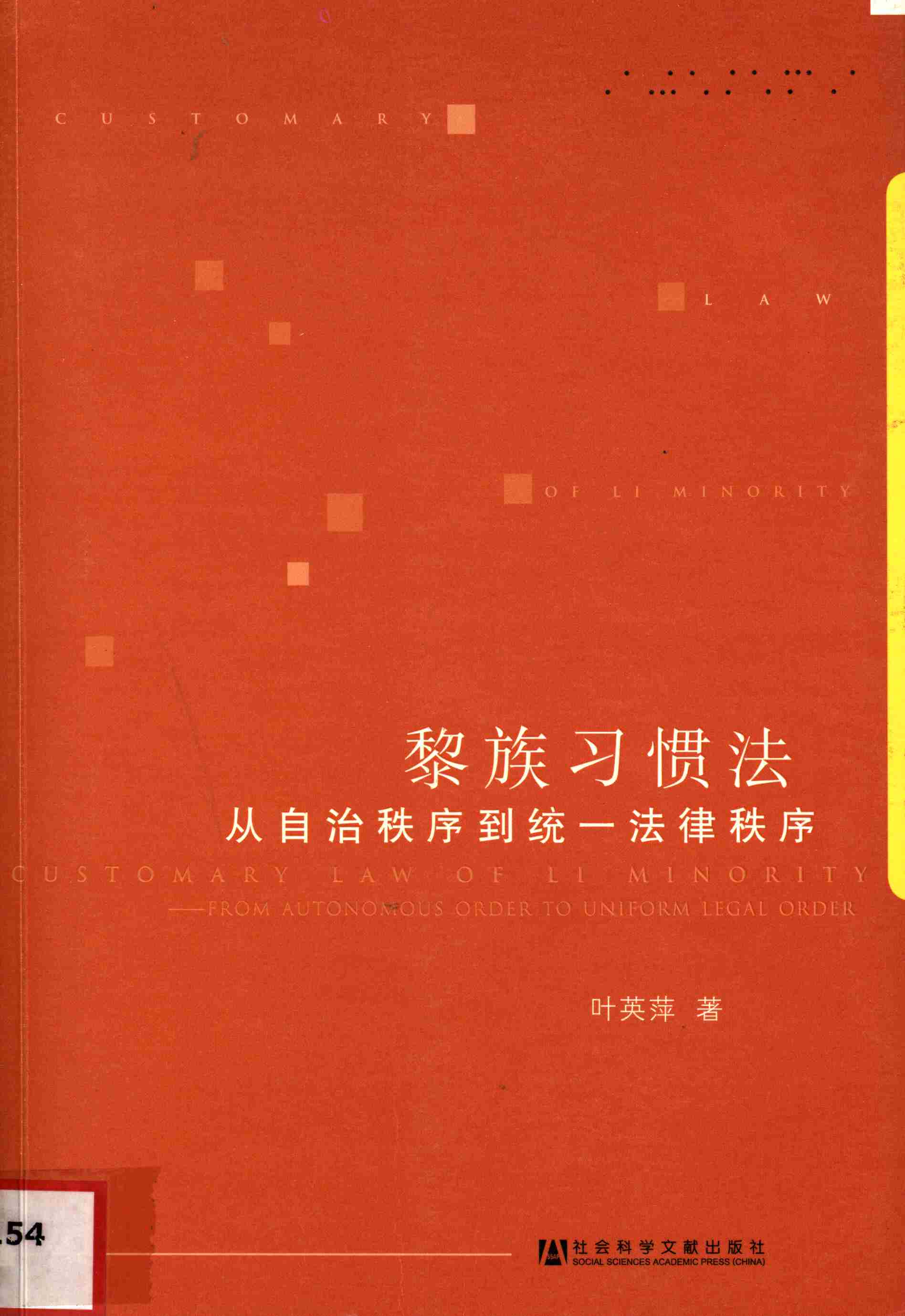内容
早在公元前2世纪秦并六国中国便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由此,中国的疆域、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便由中华各民族共同开发、共同创造,其中也包括中华法制文明。作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它凝聚着少数民族的法律智慧,吸纳了少数民族优秀的法文化成果,是各民族的法律文化与法制经验相互交流与吸收的结果。各个少数民族在中华法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少数民族的习惯法与民间法,同样构成并丰富了中华法系的内涵。
根据古文献记载,夏商周三代通行的奴隶制“五刑”是由三苗的刑制发展而来。西晋至南北朝时期,一些少数民族相继在广大的中原地区建立了政权,为适应统治广大中原地区的需要,结合本民族的传统,制定了适用范围不同的法律。特别是鲜卑族统治的北魏时期,较为重视法制建设,迅速由习惯法过渡到成文法阶段,并在汉族思想家和律学家的帮助下,以“齐之以法,示之以礼”①为指导思想,在太和五年(公元481年)颁布了著名的《太和律》。隋唐时期,中华法系成为相邻国家和地区的母法,而建立在祖国边陲的吐蕃、突厥、南诏等地方民族政权,各自都有着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体系,唐朝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法律和习俗持认同态度。《唐律疏议》在处理化外人相犯时提出了这样的原则:“诸化外人,同类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唐朝统治者开明的民族观念和民族政策,使得各民族关系更为和谐。在宋朝统治期间,契丹族、党项族、女真族先后崛起,建立了辽、西夏、金等国,这些国家分别制定了既吸收中原地区传统法律文化,又具有各民族特色的辽《《重熙新定条例》、金《泰和律义》、西夏《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等。元朝的法制在传承唐宋律、金律并参以国制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某种创新精神和民族特色的一代法制。清朝作为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政权,以“参汉酌金”的立法路线,制定封建国家的典章制度,同时还注重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专门性立法,诸如《理藩院则例》、《回疆则例》、《西藏章程》、《《苗疆条例》等等,代表了民族立法的成就,对于稳定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起到了重要作用。
少数民族的习惯法、民间法是中华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建立地方性的独立政权的少数民族毕竟是少数,而建立全国性政权的少数民族也仅有元、清两朝的蒙古族与满洲族。绝大部分少数民族依然固守在世代生活的一隅之地,遵循着传统的习俗和共同推崇的权威规则,维持着社会的秩序,调整着生产与生活,使民族的生命得以延续和发展。这些民族的生产与生活如何有序进行,相互间的矛盾与纠纷如何解决,对财产的侵犯与人身的伤害如何制裁,等等,都需要依靠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有些是成文的习惯法,有些是不成文的习俗。这些习惯法与习俗虽然简单疏陋,却世代相传,具有很高的权威与约束力,发挥着对该族内部各方面的规范作用。事实上,国家制定的大法难以覆盖的角落,习惯法、民间法、家族法,或者其他的风俗习惯都对建立与维持一定的秩序发挥了重要的乃至主要的作用,这是我们研究中华法文化所不可忽视的。例如,彝族存在于格言和谚语之中的习惯法,被人们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世代承袭,内含彝族的微观秩序,以及婚姻、家庭、继承、契约关系的规范,家支头人据以行使刑赏处罚大权,维持彝族社会的延续和发展。羌族习惯法是羌人公认并且被视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一些习惯、惯例和通行的做法,其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土司、刑事、财产、婚姻、家庭、继承、诉讼等诸多方面。其表现形式既有口耳相传的民歌民谣、民间谚语、民间传说等口碑资料,也有石刻碑文、家谱族规、文书契约、诉讼档案等文献资料。苗族习惯法是以鼓社强制力保证实现,对危害社会秩序的各类违法犯罪,轻则罚款、罚畜,重则要驱逐出村寨,甚至活埋、沉水、杀人祭祖。清朝统治中后期,在苗疆立法中准许按照苗族习惯法“苗例”,处理人命斗殴一类刑事案件。藏族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刑事、民事、行政等世俗法律、伦理道德法律、宗教法规以及各种部落习惯法,这些法律在中央政府立法的统领下,发挥着重要的调整作用,构成了藏族独具特色的法律文化。蒙古族自古就有许多世代相传的“yusun”(蒙古语音译“约孙”),被长期奉行和遵守。“约孙”具有“理”、“道理”的含义,通常汉译为“习惯”,元代又译为“体例”,其义为道理、规矩、缘故,即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法规,是蒙古族评判是非的标准、调整社会关系的准则。
少数民族习惯法与民间法的数量是庞大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少数民族社会起着重要的调整作用。它们的存在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特别是经过了漫长的岁月,无论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习惯法、民间法,都沉积了少数民族的法律意识、法律智慧与法律创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法文化。而纷繁多样的少数民族法文化又都融入以汉族为主体的法文化中,如同涓涓细流汇入长江一样,最终形成了丰富多彩、多元一体的中华法文化。
韦伯在论中国传统皇权治理模式时说:“出了城墙以外,统辖权威的有效性便大大地减弱,乃至消失。”①这个论断虽然稍嫌绝对,却揭示了一个现象:在乡土中国,存在着王法难以到达的统辖真空。一般偏僻地域犹且如此,更何况在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地区呢?因此,全面研究中华法文化也需要探究在少数民族地区起实际作用的法律渊源;需要了解少数民族的生活秩序中,法与情、法与理是如何统一的;尤其需要掌握具有共同性的法律意识的生成、发展及其应用。早在1984年,我在《再论中华法系的若干问题》②一文中,提出中华法系的特点之一就是融合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各民族的法律意识和法律原则,中华法系是中华各民族法律智慧的结晶,并倡导学界开展对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多年来,学术界尤其是法律史学界一大批学者积极参与少数民族法制史的调查与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黎族,一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古老民族,其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华民族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黎族虽偏隅海天之间,千百年来,却为华夏文明的历史长卷增添了绚丽多彩的光辉篇章,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黎族的纺织技术经元初女纺织家黄道婆带入了中原,推动了中国纺织技术的进步。黎族的习惯法同其他少数民族习惯法一样,也为黎族地区的社会管理,黎族人民的生活、生产发挥了重要的规范作用。目前关于黎族文化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可关于黎族习惯法却少见系统的学术研究。
叶英萍教授撰写的《黎族习惯法:从自治秩序到统一法律秩序》,为我国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做出了新的贡献,该著作是迄今为止很少见的一篇很有分量的学术论著。黎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关于黎族法制史既缺乏系统研究和文字记载,学界关注也很少,因此,研究工作十分困难。为撰写此著作,她较长时期深入黎族聚居地区进行调查,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对其进行了认真的系统分析和研究,因而所提出的观点均有资料支撑。该著作以法律秩序为主线,分别从黎族习惯法的历史流变、内容与运行的角度,分析了黎族习惯法的秩序价值,其中关于黎族法制史的历史分期,黎族习惯法的团体主义、平等互助、诚实守信以及本分处事等特点的论述,很有新意,所总结的黎族法制的流变与规律极具理论价值,对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和谐与团结也具有现实意义。总之,从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研究的角度来说,这部著作具有新资料、新内容、新结构和新观点的特点,是一部极具价值的黎族法制史研究著作。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即将出版这部关于黎族习惯法的学术著作,是对我国少数民族法制的一大贡献;作为英萍同志的导师,看到她的成果能够得到社会的承认,我十分高兴,特予作序,以资鼓励。
2012.3.18
根据古文献记载,夏商周三代通行的奴隶制“五刑”是由三苗的刑制发展而来。西晋至南北朝时期,一些少数民族相继在广大的中原地区建立了政权,为适应统治广大中原地区的需要,结合本民族的传统,制定了适用范围不同的法律。特别是鲜卑族统治的北魏时期,较为重视法制建设,迅速由习惯法过渡到成文法阶段,并在汉族思想家和律学家的帮助下,以“齐之以法,示之以礼”①为指导思想,在太和五年(公元481年)颁布了著名的《太和律》。隋唐时期,中华法系成为相邻国家和地区的母法,而建立在祖国边陲的吐蕃、突厥、南诏等地方民族政权,各自都有着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体系,唐朝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法律和习俗持认同态度。《唐律疏议》在处理化外人相犯时提出了这样的原则:“诸化外人,同类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唐朝统治者开明的民族观念和民族政策,使得各民族关系更为和谐。在宋朝统治期间,契丹族、党项族、女真族先后崛起,建立了辽、西夏、金等国,这些国家分别制定了既吸收中原地区传统法律文化,又具有各民族特色的辽《《重熙新定条例》、金《泰和律义》、西夏《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等。元朝的法制在传承唐宋律、金律并参以国制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某种创新精神和民族特色的一代法制。清朝作为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政权,以“参汉酌金”的立法路线,制定封建国家的典章制度,同时还注重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专门性立法,诸如《理藩院则例》、《回疆则例》、《西藏章程》、《《苗疆条例》等等,代表了民族立法的成就,对于稳定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起到了重要作用。
少数民族的习惯法、民间法是中华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建立地方性的独立政权的少数民族毕竟是少数,而建立全国性政权的少数民族也仅有元、清两朝的蒙古族与满洲族。绝大部分少数民族依然固守在世代生活的一隅之地,遵循着传统的习俗和共同推崇的权威规则,维持着社会的秩序,调整着生产与生活,使民族的生命得以延续和发展。这些民族的生产与生活如何有序进行,相互间的矛盾与纠纷如何解决,对财产的侵犯与人身的伤害如何制裁,等等,都需要依靠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有些是成文的习惯法,有些是不成文的习俗。这些习惯法与习俗虽然简单疏陋,却世代相传,具有很高的权威与约束力,发挥着对该族内部各方面的规范作用。事实上,国家制定的大法难以覆盖的角落,习惯法、民间法、家族法,或者其他的风俗习惯都对建立与维持一定的秩序发挥了重要的乃至主要的作用,这是我们研究中华法文化所不可忽视的。例如,彝族存在于格言和谚语之中的习惯法,被人们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世代承袭,内含彝族的微观秩序,以及婚姻、家庭、继承、契约关系的规范,家支头人据以行使刑赏处罚大权,维持彝族社会的延续和发展。羌族习惯法是羌人公认并且被视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一些习惯、惯例和通行的做法,其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土司、刑事、财产、婚姻、家庭、继承、诉讼等诸多方面。其表现形式既有口耳相传的民歌民谣、民间谚语、民间传说等口碑资料,也有石刻碑文、家谱族规、文书契约、诉讼档案等文献资料。苗族习惯法是以鼓社强制力保证实现,对危害社会秩序的各类违法犯罪,轻则罚款、罚畜,重则要驱逐出村寨,甚至活埋、沉水、杀人祭祖。清朝统治中后期,在苗疆立法中准许按照苗族习惯法“苗例”,处理人命斗殴一类刑事案件。藏族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刑事、民事、行政等世俗法律、伦理道德法律、宗教法规以及各种部落习惯法,这些法律在中央政府立法的统领下,发挥着重要的调整作用,构成了藏族独具特色的法律文化。蒙古族自古就有许多世代相传的“yusun”(蒙古语音译“约孙”),被长期奉行和遵守。“约孙”具有“理”、“道理”的含义,通常汉译为“习惯”,元代又译为“体例”,其义为道理、规矩、缘故,即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法规,是蒙古族评判是非的标准、调整社会关系的准则。
少数民族习惯法与民间法的数量是庞大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少数民族社会起着重要的调整作用。它们的存在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特别是经过了漫长的岁月,无论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习惯法、民间法,都沉积了少数民族的法律意识、法律智慧与法律创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法文化。而纷繁多样的少数民族法文化又都融入以汉族为主体的法文化中,如同涓涓细流汇入长江一样,最终形成了丰富多彩、多元一体的中华法文化。
韦伯在论中国传统皇权治理模式时说:“出了城墙以外,统辖权威的有效性便大大地减弱,乃至消失。”①这个论断虽然稍嫌绝对,却揭示了一个现象:在乡土中国,存在着王法难以到达的统辖真空。一般偏僻地域犹且如此,更何况在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地区呢?因此,全面研究中华法文化也需要探究在少数民族地区起实际作用的法律渊源;需要了解少数民族的生活秩序中,法与情、法与理是如何统一的;尤其需要掌握具有共同性的法律意识的生成、发展及其应用。早在1984年,我在《再论中华法系的若干问题》②一文中,提出中华法系的特点之一就是融合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各民族的法律意识和法律原则,中华法系是中华各民族法律智慧的结晶,并倡导学界开展对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多年来,学术界尤其是法律史学界一大批学者积极参与少数民族法制史的调查与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黎族,一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古老民族,其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华民族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黎族虽偏隅海天之间,千百年来,却为华夏文明的历史长卷增添了绚丽多彩的光辉篇章,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黎族的纺织技术经元初女纺织家黄道婆带入了中原,推动了中国纺织技术的进步。黎族的习惯法同其他少数民族习惯法一样,也为黎族地区的社会管理,黎族人民的生活、生产发挥了重要的规范作用。目前关于黎族文化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可关于黎族习惯法却少见系统的学术研究。
叶英萍教授撰写的《黎族习惯法:从自治秩序到统一法律秩序》,为我国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做出了新的贡献,该著作是迄今为止很少见的一篇很有分量的学术论著。黎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关于黎族法制史既缺乏系统研究和文字记载,学界关注也很少,因此,研究工作十分困难。为撰写此著作,她较长时期深入黎族聚居地区进行调查,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对其进行了认真的系统分析和研究,因而所提出的观点均有资料支撑。该著作以法律秩序为主线,分别从黎族习惯法的历史流变、内容与运行的角度,分析了黎族习惯法的秩序价值,其中关于黎族法制史的历史分期,黎族习惯法的团体主义、平等互助、诚实守信以及本分处事等特点的论述,很有新意,所总结的黎族法制的流变与规律极具理论价值,对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和谐与团结也具有现实意义。总之,从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研究的角度来说,这部著作具有新资料、新内容、新结构和新观点的特点,是一部极具价值的黎族法制史研究著作。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即将出版这部关于黎族习惯法的学术著作,是对我国少数民族法制的一大贡献;作为英萍同志的导师,看到她的成果能够得到社会的承认,我十分高兴,特予作序,以资鼓励。
2012.3.18
附注
① (北齐)魏收:《魏书·刑法志》。
① 〔德〕马克斯·韦伯著《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第109页。
② 张晋藩:《再论中华法系的若干问题》,《政法论坛》198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