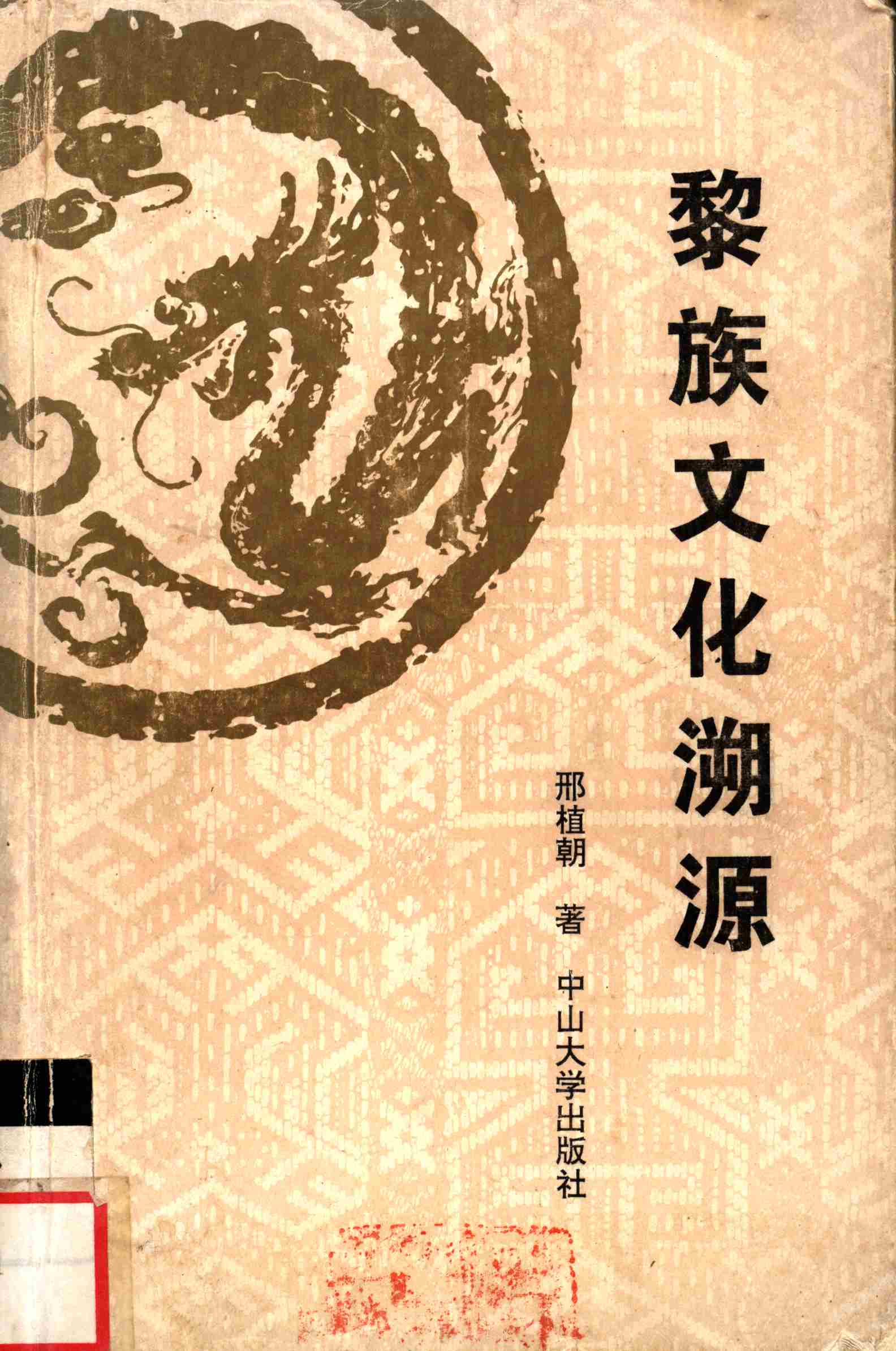内容
黎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有着悠久历史的少数民族,它跟其它的少数民族一样,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心理特征,而其心理特征是在历史的凝聚、沉淀和演变中形成的,是受不同历史时期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所制约的。虽然,黎族的心理演变不一定与生产力的发展平行,但是,它的构成和演变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层次,复合型的。
环境衍化性格:黎族的警戒心理
一个民族心理结构的形成与演变,是与他们的特定的生活环境紧密相关的。黎族所具有的独特的警戒心理,在很大程度上发源于他们羁留于
其中的险恶的自然环境与社会氛围。
早在三千年前,黎族的先民就居住在孤悬海外的孤岛上,最初他们定居在海滨平原地区,凭借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从事农、牧、渔业生产,辛勤地开拓着自己的生活空间。至今,海南岛的沿海各地有部分市镇村寨的名称如“北黎”“抱X”“抱ⅩⅩ”就带有黎语的色彩,这说明,这些地方依然残留着黎族先民耕耘改造自然的痕迹。但是,后来由于自然灾害的袭击,异族的侵扰,特别是历代统治者在政治上以所谓的“羁縻政策”,制造民族压迫,挑起民族纠纷;军事上实行野蛮的武力镇压和征讨。据史料记载,仅元朝统治的九十年间,元朝统治者的“征黎”就不下十次之多,其中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即一二九一至一二九四年)阔里吉斯和朱斌等统兵深入五指山区“征黎”,在五指山、黎母山、尖峰岭等地刻石作纪念,至今残留在乐东县尖峰岭下的“大元军马下营”的巨型石刻,就是这一次血腥历史的见证。此外,他们对黎族人民还实行强制的超经济剥削。到了鸦片战争以后,反动统治者们对黎族人民的烧杀掠夺更为惨重。由于上述原因,黎民不得不逃进深山老林,最后游居五指山腹地,在深山恶水,台风干旱虫蛇野兽等自然灾害的无规则的侵袭面前,黎族人民由于尚未掌握一定的科学技术,因而只能接受无常的命运以及命运的打击。个人和群体的力量既单薄,又孱弱。所以,环境的乖戾与莫测的变动,久而久之,就会给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群体输入,培育出一类文化生理型的原始心态,即社会人类学意义上的警戒心理。这是其一。另一方面,社会政治环境中的仇杀气氛,他民族一而再,再而三的围剿与征伐,也诱发和强化了黎族的警戒心理,但因为同属人类的不同民族,在力与力,心智与心智的抗衡方面,黎族子弟在连绵的戈斗中尚能偶或取胜,这在另一种意义上便又形成了民族的暴力情绪的反弹,即慓悍精神,好斗尚武意识的张扬。
从黎族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历程看,黎族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相当落后的。解放前,他们使用的工具是极为简陋的,他们用钻木取火的方法,在大森林里进行原始的“砍倒烧光”(即“砍山栏”)的刀耕火种生产。随着历史的进一步的发展,黎族的社会文化结构发生了某些变化,靠近沿海汉族的地区,黎族原始社会渐趋瓦解,未经过奴隶制社会就直接过渡到了封建社会,社会生产力也得到一定的发展。但是,从总体上看,尤其是从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看,还是极为缓慢的,特别是那些与汉族接触较少的黎聚居区——五指山腹地的黎峒、黎寨,到解放前夕还保留着“合亩制”的原始组织,仍可看到黎族历史上父系氏族制的某些残余。甚至到了今天,这些地区还保留着“刀耕火种”“不落夫家”和“翁堂沃工”(黎话,其意是大家一起做工”)等原始残余形式和生产特点。本来黎族的这种落后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与整个民族的生存与振兴是相矛盾的。但是,就是因为这种矛盾的逼迫所导致的警戒心理的作用,这个民族的群体凝聚力又特别之强,成员之间的“归属感”与向心力与其它少数民族一样,都显得非常突出,极具性格力度。他们常以一个“峒”或一个“寨”为整体,进行生产、文化、抗暴、排拒外来侵扰等活动。在这一高度的群居性、凝聚性的“部落式”社会文化结构的框架里,也自然会产生出属于群体的领袖、权威以及英雄。他或者他们凭依个人的智慧、武艺、力量等等,形成众望所归的气氛,并不矢人心地为群体的团结、繁盛、发展而有节制地或无限地使用自己的权威。这些被选中而成为头领的人物也受到了整个群体的成员的特别尊重,即使在五指山上乌云压顶,大地鲜血横流的岁月里,他们都紧跟头人去冒险和抗争。这突出表现在抵御外来侵扰和反对历代反动统治者的斗争中。
自有史以来,黎族人民就从来未停歇过这种大规模的对外来侵征的排拒和战斗,再加之地理环境的作用,以至于在他们的民族精神中也内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懔悍和尚武意识。在黎族社会里,男子汉从小就练出一手好枪法和过硬的刀术,所以,爱好刀枪是黎族社会里的一种良好的习气,是勇敢者和力量的特征。因此,黎族男子汉无论到外乡访亲探友参加生产劳动,还是节日集会,他们都无不扛枪挂刀,不同支系的黎族还有不同的装束。如“合亩”制地区的杞人,白沙县的润人,他们出征时,头缠红布巾,胸前挂着装火药和火喼用的红布褂,腰间还扎一条红腰带,扛枪佩长尖刀,英姿威武。反过来,这种被环境驱使塑造而衍化成的个体——群体的凝聚性,尚武精神,警戒性,特殊的自然社会应激机制,又给他们的抗暴历史、反压迫反欺凌反侵掠的历史,增添了辉煌而豪?的层次。据史料记载,从宋朝到元朝期间,黎族人民的大规模的斗争就有十八次之多,遍及全岛沿海州县。明清两代,黎族人民的斗争规模更大,以弘治十四年(一九0一年)儋州七坊垌(今白沙县七坊区)符南蛇领导的起义声势最大,“三州十县闻风响应”震撼了全岛。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黎族人民的革命斗争开始走上新的道路。以黎族领袖王国兴为首领导的白沙起义,其声势更为浩大,斗争更加艰苦,影响更加深远,是黎族历次起义所不可比拟的。在全国少数民族革命斗争史上所占有的地位也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仅为琼崖革命斗争创建五指山根据地打下良好的基础,而且为整个海南的革命斗争提供了一个广阔而又坚实的大后方。但是,应该指出的是,整个黎族的抗暴史、革命史、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滞留在民族斗争的社会文化层次。这因为,其一,民族的反抗道路从来都是从自身的被压迫被欺虐的经历、感受出发,而本能性地反弹形成的;其二,黎族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使他们只能从本民族的特定立场,特殊境遇出发去采取行动,并且多少有点被迫的性质。从本质上,渴望结束剑弩的岁月,流徙的生活,渴望安居乐业是这个民族更迫切的要求。正是这两重的困难,要求和平与不得和平的矛盾,使得黎族人民对自然、社会格外富于警戒意识。
然而,这种警戒心理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一方面呈现了以上所阐述的对自然与社会的激烈抗衡。另一方面又体现出对命运的不可知心态,以及在这种心态支配下对恶势力(自然与社会)的畏惧与祈求。这一特征集中表现在面对自然的威胁时的图腾崇拜。无论是上山“砍柴栏园”、“插秧下种”还是“上山伐木”“放狗围猎”“向天求雨”等,都无不举行隆重的宗教仪式。黎族人民认为在人间除了有祖先鬼之外,还有雷公鬼、山鬼、地鬼、灶鬼、天狗鬼等,而这些大量的“鬼”又几乎都成了种族的自然崇拜物。所以,每进行一项生产活动,他们都要十分虔诚地祈求天地和大自然的保护。
原型文化遗态:图腾崇拜及其变形
在我国除汉族以外的五十多个少数民族中,黎族算是发育比较成熟的民族之一。根植于它极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所以,黎族的文化心理也呈现出原始的滞后和古朴的虔诚的特点。至今为止,居住在深山之中的黎胞仍然认为他们所崇拜的植物、动物图腾就是自己本民族或本支系的始祖。在黎族的宗教和社会生活里,图腾崇拜的观念起着相当大的支配作用。如果没有很大程度的感情上的虔诚意识,没有与之相应的原始——自然氛围,显然是很难不打破这种滞后、朴拙、甚至驳杂粗陋的精神信仰的。
有些人类学家认为,黎族唯一崇拜的图腾动物是狗,他们认为,黎族对衍生而来的动物狗,特别遵重和保护。这确实有根据。黎族无论那一支系(赛、杞、润、侾美孚)都爱狗,把养狗看得比养猪还重要。史料记载,过去的黎民是不随便杀狗的,也不吃狗肉,即使杀狗祭鬼神,也不许在房屋里煮。平时对意外死亡的狗,要举行隆重的埋葬仪式,特别是侾黎,还取下祭神时杀的狗的牙齿,用绳子绑住挂在胸前做护身符。但是根据多年的考证,黎族除了对狗有着深厚的感情外,他们对牛、青蛙、鱼的感情也是相当突出的,每年七月或十月份,黎族就要为“牛”选定特别的日子做为“牛日”。“鱼”和“青蛙”在黎家的心目中也是“吉祥”和“有福气”的象征。此外,还有植物图腾。黎民对诸如红、白藤树叶、木棉树、芭蕉树等等,均有着同样特殊的感情,有的不仅是象征物、护身符,而且当作其中禁忌的标志。由于图腾崇拜在黎族所占的位置是如此重要。有人甚至利用黎族先民崇拜祖宗这样的心理编造一套“祖先鬼”的咒语,把“祖先鬼”(黎语“tingputpau”)作为最大的鬼,要黎民杀牛祭拜,故黎族地区有所谓“天上怕雷公,地下怕祖宗,人间怕禁公”的说法。黎族是以崇拜同一图腾,同一个血缘聚居在一起的,他们的头人几乎都懂得念祖宗的咒语,于是,无形中头人就成为当然的“真理”的化身,无论是生产劳动,上山打猎还是出征,他们都带领着全体黎民进行要求祖宗保佑的各种宗教活动,而祖宗崇拜实际上成为头人们统率部落人民的精神支柱。就象弗雷泽曾经说过的,在澳大利亚的牙利部落中,一个以某种植物的种子为图腾形象的氏族的头人,被他的人民说成就是产生这种种子的植物本身一样。为此,黎族先民对他们的头人是极其崇拜的,对他们头人所提出的问题可以说是一呼百应的。
这样一来,正是这种特殊的宗教文化情绪,使黎族社会的凝聚性,公众精神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铺厉。很久以来,在黎族聚居的村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即使谷仓从不上锁,丰收季节硕果累累也从不发生盗窃现象。而这种对图腾,对“头人”的尊崇心态,又起到了调节黎族社会人际关系的杠杆作用。天神就是意志,头人就是一切,而作为“头人”首领,由于要带领大家抗拒无时无刻不潜存着的各种威胁的责任,所以要求众人的服从和团结就成为了所有“头人”的第一使命。加之黎族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主观上也迫使黎民们必须团结和谐,互相帮助。
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黎、汉民族之间的多种政治融合,经济渗透以及文化的影响,特别是由于进入现、当代社会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历史上最具有大文化意识的政治集团开始对黎族社会实行政治导向,经济扶植,文化促进的方针,使之在非常迅速的程度和非常之广的规模上,改造和转变了黎胞的传统信仰,即图腾崇拜。使他们的精神境界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然而,黎胞的几千年积淀而成的对待人与事物的虔诚心理都作为一种良善的道德传统保留下来,只不过转向到对新的,进步的政治集团——中国共产党的执着认同。解放前后几十年来,黎胞们对共产党的虔诚与敬颂最突出地反映在他们所创作的数以万计的大量的民歌、民间故事上。
冲击与融汇:黎族的模仿心理溯源
文字语言代表着一个民族的灵魂。保持民族文化传统的最有效的载体,除了世代相传的神话、习俗、舞蹈、传说等等之外,最主要的便是文字。没有文字,连神话传说这样的口语历史也会变得不完整,不系统。在缺乏本民族文字的情况下,一个民族的发展是很缓慢的,有些问题甚至会被中断而无法延续和继承下去。就象五彩缤纷的花朵,如果没有花枝和根系的支撑,便将很快凋萎。黎族就是一个没有自身文字的民族。它之所以能够以结构发音比较成熟,形态比较完整的面目发展至今,主要是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独特无二的地理环境以及滞后发展的社会经济制度——即原始社会的“合亩制”,封建时代的“村落共同体”等等的杂揉与拼接。而非现、当代科技文明的冲击。
但是,冲击迟早要到来。只要一个民族欲求发展,欲求经济与文化的共同繁荣,这个民族就必须自觉或被迫地接受现、当代文明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冲击,与之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要与代表着现、当代文明的他民族发生经济上和精神上的多层次、多方位、多格局的融汇。在这个剧烈的摩擦与冲突,同化与反同化的过程中,冲突双方都以不同的方式实现了互补,也以自身特性的部分丧失作为代价。但是,常常的情形是,没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或者语言文字比较落后的民族,自身特性的消融也比较迅速,这样一来,在其社会心理的演变程式中,也呈现出两重态征:一是逆反与排拒,一是模仿与认同。而模仿心理又普遍地植根于整个年轻一代的价值追求,思维方式,以及生活形态的诸方面。
大量的史实证明,黎族文学艺术的发展,几乎都是模仿汉族文学、向汉族学习的。甚至黎族民间文学的发展与演变都带有模仿的痕迹。随着汉、黎族人民日益频繁的交往,黎族学习模仿汉族口头文学的机会越来越多,他们把汉族民间流传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董永的故事》、《牛郎织女》等作品作为他们演唱的内容。虽然,黎族口头文学家们已根据黎族人民的观念和美学观加以修饰,但是,原作的面目仍然保留着。又如黎族民歌的加工与修饰问题。原来黎歌的“比”“兴”很少,经过黎汉文化交流后,黎族民歌的“比兴”便大大地加强了,有的黎歌甚至与海南方言合流。另外从当代文学发展方面来看,黎族虽然已经有了以龙敏为首的一支作家队伍,但是,他们都以汉语言文学为基础,所以,尽管他们极力去摄取民族生活中的浪花,捕捉时代的信息,汲取黎族神奇瑰丽的传统故事为素材,千方百计地反映本民族人民的生活,把握本民族精神的流向。可是,从作品里看,人们不难发现,他们在整个创作过程中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评判却都是从汉语言文学中脱胎而出的。
此外,从黎族妇女的纹身,男子汉的服饰以及他们居住房屋上的演变也证明了这一点。从外观上看,无论沿海的黎族还是与汉杂居在一起的黎族。他们的衣着和生活实量有许多方面是模仿汉族的,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姑娘们连绣面纹身这一带有图腾崇拜、祖宗崇拜含义的习俗都不坚持了,她们模仿汉族姑娘们的穿戴,上衣改穿汉族的女装。而男子汉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几乎全都改穿汉族服装。黎族目前的住房建筑有好几种,其中高架船形屋是黎族现有房屋中最原始的一种,是历史上记载的最原始的所谓“干栏”建筑,后来演变为离地仅半公尺的铺地式船形房屋。随着黎汉的交往,黎族人民又模仿汉族的金字形汉式房屋建造,在受汉族影响较大的外围地区,如三亚市、陵水等县的黎族聚居地,他们的住房不仅从形式上与附近汉族相同(金字形,门向一边开)质料也从纯植物性改为泥糊墙,甚至红砖墙瓦盖顶。最为突出的例子是文化教育。据调查研究,黎族学校的文字教育几乎百分之百是以汉字为基础,这和有自己文字的其它民族如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的教育格局便大不相同。而这样以来,凡是接受过一定程度教育的黎族青少年,都很快学会了引用汉语言文字进行交流,用汉语进行思维的习惯。普通话在黎族同胞中的普及率远远超出许多民族地区的普及率。
从上述的实例,我们可以看到黎胞对先进的科学技术文明的积极模仿和认同心理是非常突出的,拒外意识比较弱。也正由于此,才形成了黎族社会生产力发展相对落后,文化教育水平相对超前的独特景观。但我们完全可以相信,文化教育水平、科学技术水平的进一步发展,也一定能够对黎胞的生产力水平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其潜力绝不可低估。
从模仿到自强:黎族的振兴心理发端
一个民族从弱小到壮大,从落后到繁荣,在心
理历程上必然要经过这样几个环节:蒙昧时期的封闭——体现在经济形态、宗教文化、社会关系等各方面。都极其重视强化本民族各个个体的纵向的“朝内转”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拒斥外向——横向的社会交流与比较。这个环节大约要经历很长时期,直到封闭的大门被先进的生产力打破为止,这样才会进入第二环节而开化时期的融合与模仿——以横向文明与先进的文化类型作为参照系,在价值判断,生活方式,行为形态等方面尽量与之认同和沟通。但认同与沟通的方式这时期主要体现为模仿,随着模仿程度在量与质上的不断加深和类型化,第三个环节即开放时期便开始了——这一时期虽也呈现横向移植。但横向的他民族的经济文化形态又逐渐退居到陪衬、借鉴的地位,本民族的主体生命力趋于旺盛,独立的自主发展的意识日趋高涨,具体反映到黎族社会里的便是强烈的振兴心理。
黎族的振兴心理发端于近代。西方列强包括他们的军舰、商船在海南的侵入,既给黎胞的生存困境雪上加霜,又刺激了黎族社会欲图改变生存困境的精神冲动。在此之前,虽然有长达几千年的汉族文化的袭扰和汉族反动统治集团的不断地围剿,但毕竟由于交通、传播系统等等的不发达,这种袭扰与围剿尚不足以撼动黎族社会的自尊意识。固本意知,只是在小范围如沿海平原等区域造成了某些方面的模仿气氛。还是帝国主义的洋枪,大炮以及附着于其上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生产力,撼醒了一部分黎胞的精神世界,使他们成为最早的民族的文明振兴的先驱者,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为了反抗外族入侵,驱逐帝国主义的洋枪大炮。一些黎胞在政治上率先成熟起来,他们自觉与中国共产党实行政治、军事的接壤,从而一致对外。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变得明达、开放、而且高度自信。当他们发现,正是中国共产党可以而且能够给黎族社会带来繁荣与发展的希望时,他们便自觉地将自身置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追求在统一与和平的旗帜下振兴民族大业。如黎族领袖王国兴、王玉锦等。另一方面,便是极少数的黎胞开始接受微弱的商品意识,从事小商小贩活动等等。如民国初年,黎族已有个别富裕人家办庙经商,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保亭市(今保城镇)就有六家黎族经营的商店。随着沿海城镇的贸易发展,国民党时期,近沿海的黎民有的已经挑着零星的土产品上街摆卖。
然而,黎族的振兴心理的真正和全面的勃兴,黎族社会的划时代发展的最大契机,应当说是在解放后的四十年历程,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近十年,以黎族的文化振兴,科技振兴与经济振兴为主导的全面振兴活动动得到了普遍的推演。以文化振兴为例,众所周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黎族文学的形式除了单调的口头文学,其它文学形式几乎是空的。但是,到了新的时期,黎族便涌现了以龙敏、王海为代表的第一批黎族作家,他们创作出一批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品,民族的振兴心理在他们的作品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在他们的作品里,人们看到原来以物换物,以草结计算的黎族,在农村商品经济的冲击下,终于露出了商品交换的幼芽。特别是作品里那一幅幅意趣盎然的山区市景的画面描写,五颜六色的摊棚画廊,都无不告诉了人们,在党的路线政策的指引下,边疆黎寨的商品经济出现了兴旺发达的景象和黎家那充满着时代气息的多彩多姿的生活及蓬勃向上的生机。此外,美术界还涌现了黎族女画家陈桂花。体育界出了黎族运动员吉泽标、王金玲。他们在全国和国际比赛中都争到了名次。以科技开发为例,解放前,黎族的农业经济是相当落后,其耕作是很粗陋的。解放后,他们购进大批铁制农具。普遍推广使用铁犁铁耙,中耕器7890一、打谷机、打谷桶、风拒等农业机具,改变了原始的刀耕火种,牛踩田,手捻稻等落后的耕作方法,并通过兴修水利,扩大水稻田的种植面积,大力开展以合理密植为中心的农业技术改革,促进了粮食生产的发展。到了六十年代,随着黎族地区水利灌溉条件的逐步改善,各地又认真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全面开展改良土壤,改革品种,改变植期,改善灌溉条件,改进栽培技术,推广科学种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贯彻落实,黎族地区普遍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学科学、学技术的热情高涨。原来的民族自治县都普遍建立了农科所,农技站和农科组,基本上形成了四级农科网。据1980年后的不完全统计,现有的七个民族自治县除了健全四级农科网外,还建立了六十七个农村基层科普协会,建立一千八百三十六个农业技术联系户,有的地方还建立科技咨询服务公司和开办科技夜校,有力地促进了黎族人民走科学致富的道路。黎族聚居地的白沙县,就有9个自然专业学会,会员共530人,每个乡镇有科普协会,57%的村委会建立科普分会,40%的自然村建立科普小组,拥有会员1200多人,每个乡镇还建立起文化、技术业余学校,全县初步建成比较完整的农村科普网络。特别是海南办大特区后,原来只是“一间芽房三石灶,一条野藤挂家当,一把钩刀砍大山,一碗谷种养全家”的黎族,竞然涌现出不少的企业家,原来只靠自然经济为生的黎族,现在也盛行贸易经商活动。黎族聚居的一些市镇,如通什、保亭市、营根、什运、毛阳等,有许多商店摊贩就是黎胞经营的,原来黎家自酿的“山栏酒”,现在已成为商品销售岛内外,黎族妇女织绣的〓裙也引起了国内外游客的注目。文化的振兴、科技的振兴与经济的振兴,给黎族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这种振兴心理又一次在鞭策着他们,为加快开发建设而作出新的努力。
当然,在此同时,黎族老一辈人的心目中,还存在着多多少少的自卑消极心理,他们不愿意打破旧的坛坛罐罐,生怕黎族的一切都被汉族同化了,所以,对新生事物的接受和学习仍显得迟滞,这不仅需要时间的推动才能改变,也需要空间上的文化心理结构的不断拓宽。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黎族的文化心理特征主要由警戒意识,虔诚意识、模仿意识和振兴意识等共同因素而构成。其中警戒意识和虔诚意识根源于民族纵向历史传统。受制约于世代聚居的险恶莫测的自然氛围和不断遭受侵扰,困厄的社会政治氛围。而警戒意识又派生出了民族的凝聚力和尚武精神;虔诚意识则变形于原形的图腾崇拜的泛神式信仰。
模仿意识与振兴意识相反,它们的形成,完全是横向比较和民族间经济文化政治甚至军事形态的相互交叉融汇的结果。正是在与他民族尤其是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科学技术文明的外来民族的相互交流以至于冲突的过程中,一个封闭的民族才会逐渐走向开化和开放,一个落后的民族才会依赖于模仿进而依赖于自我唤醒自我振兴的方式以图富强,以图繁盛。这基本上是民族交流史上的最基本的定则。黎族也不例外。只不过,黎族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得更加滞后,但却更加迅速猛烈,并且更加自觉罢了。
环境衍化性格:黎族的警戒心理
一个民族心理结构的形成与演变,是与他们的特定的生活环境紧密相关的。黎族所具有的独特的警戒心理,在很大程度上发源于他们羁留于
其中的险恶的自然环境与社会氛围。
早在三千年前,黎族的先民就居住在孤悬海外的孤岛上,最初他们定居在海滨平原地区,凭借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从事农、牧、渔业生产,辛勤地开拓着自己的生活空间。至今,海南岛的沿海各地有部分市镇村寨的名称如“北黎”“抱X”“抱ⅩⅩ”就带有黎语的色彩,这说明,这些地方依然残留着黎族先民耕耘改造自然的痕迹。但是,后来由于自然灾害的袭击,异族的侵扰,特别是历代统治者在政治上以所谓的“羁縻政策”,制造民族压迫,挑起民族纠纷;军事上实行野蛮的武力镇压和征讨。据史料记载,仅元朝统治的九十年间,元朝统治者的“征黎”就不下十次之多,其中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即一二九一至一二九四年)阔里吉斯和朱斌等统兵深入五指山区“征黎”,在五指山、黎母山、尖峰岭等地刻石作纪念,至今残留在乐东县尖峰岭下的“大元军马下营”的巨型石刻,就是这一次血腥历史的见证。此外,他们对黎族人民还实行强制的超经济剥削。到了鸦片战争以后,反动统治者们对黎族人民的烧杀掠夺更为惨重。由于上述原因,黎民不得不逃进深山老林,最后游居五指山腹地,在深山恶水,台风干旱虫蛇野兽等自然灾害的无规则的侵袭面前,黎族人民由于尚未掌握一定的科学技术,因而只能接受无常的命运以及命运的打击。个人和群体的力量既单薄,又孱弱。所以,环境的乖戾与莫测的变动,久而久之,就会给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群体输入,培育出一类文化生理型的原始心态,即社会人类学意义上的警戒心理。这是其一。另一方面,社会政治环境中的仇杀气氛,他民族一而再,再而三的围剿与征伐,也诱发和强化了黎族的警戒心理,但因为同属人类的不同民族,在力与力,心智与心智的抗衡方面,黎族子弟在连绵的戈斗中尚能偶或取胜,这在另一种意义上便又形成了民族的暴力情绪的反弹,即慓悍精神,好斗尚武意识的张扬。
从黎族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历程看,黎族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相当落后的。解放前,他们使用的工具是极为简陋的,他们用钻木取火的方法,在大森林里进行原始的“砍倒烧光”(即“砍山栏”)的刀耕火种生产。随着历史的进一步的发展,黎族的社会文化结构发生了某些变化,靠近沿海汉族的地区,黎族原始社会渐趋瓦解,未经过奴隶制社会就直接过渡到了封建社会,社会生产力也得到一定的发展。但是,从总体上看,尤其是从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看,还是极为缓慢的,特别是那些与汉族接触较少的黎聚居区——五指山腹地的黎峒、黎寨,到解放前夕还保留着“合亩制”的原始组织,仍可看到黎族历史上父系氏族制的某些残余。甚至到了今天,这些地区还保留着“刀耕火种”“不落夫家”和“翁堂沃工”(黎话,其意是大家一起做工”)等原始残余形式和生产特点。本来黎族的这种落后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与整个民族的生存与振兴是相矛盾的。但是,就是因为这种矛盾的逼迫所导致的警戒心理的作用,这个民族的群体凝聚力又特别之强,成员之间的“归属感”与向心力与其它少数民族一样,都显得非常突出,极具性格力度。他们常以一个“峒”或一个“寨”为整体,进行生产、文化、抗暴、排拒外来侵扰等活动。在这一高度的群居性、凝聚性的“部落式”社会文化结构的框架里,也自然会产生出属于群体的领袖、权威以及英雄。他或者他们凭依个人的智慧、武艺、力量等等,形成众望所归的气氛,并不矢人心地为群体的团结、繁盛、发展而有节制地或无限地使用自己的权威。这些被选中而成为头领的人物也受到了整个群体的成员的特别尊重,即使在五指山上乌云压顶,大地鲜血横流的岁月里,他们都紧跟头人去冒险和抗争。这突出表现在抵御外来侵扰和反对历代反动统治者的斗争中。
自有史以来,黎族人民就从来未停歇过这种大规模的对外来侵征的排拒和战斗,再加之地理环境的作用,以至于在他们的民族精神中也内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懔悍和尚武意识。在黎族社会里,男子汉从小就练出一手好枪法和过硬的刀术,所以,爱好刀枪是黎族社会里的一种良好的习气,是勇敢者和力量的特征。因此,黎族男子汉无论到外乡访亲探友参加生产劳动,还是节日集会,他们都无不扛枪挂刀,不同支系的黎族还有不同的装束。如“合亩”制地区的杞人,白沙县的润人,他们出征时,头缠红布巾,胸前挂着装火药和火喼用的红布褂,腰间还扎一条红腰带,扛枪佩长尖刀,英姿威武。反过来,这种被环境驱使塑造而衍化成的个体——群体的凝聚性,尚武精神,警戒性,特殊的自然社会应激机制,又给他们的抗暴历史、反压迫反欺凌反侵掠的历史,增添了辉煌而豪?的层次。据史料记载,从宋朝到元朝期间,黎族人民的大规模的斗争就有十八次之多,遍及全岛沿海州县。明清两代,黎族人民的斗争规模更大,以弘治十四年(一九0一年)儋州七坊垌(今白沙县七坊区)符南蛇领导的起义声势最大,“三州十县闻风响应”震撼了全岛。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黎族人民的革命斗争开始走上新的道路。以黎族领袖王国兴为首领导的白沙起义,其声势更为浩大,斗争更加艰苦,影响更加深远,是黎族历次起义所不可比拟的。在全国少数民族革命斗争史上所占有的地位也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仅为琼崖革命斗争创建五指山根据地打下良好的基础,而且为整个海南的革命斗争提供了一个广阔而又坚实的大后方。但是,应该指出的是,整个黎族的抗暴史、革命史、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滞留在民族斗争的社会文化层次。这因为,其一,民族的反抗道路从来都是从自身的被压迫被欺虐的经历、感受出发,而本能性地反弹形成的;其二,黎族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使他们只能从本民族的特定立场,特殊境遇出发去采取行动,并且多少有点被迫的性质。从本质上,渴望结束剑弩的岁月,流徙的生活,渴望安居乐业是这个民族更迫切的要求。正是这两重的困难,要求和平与不得和平的矛盾,使得黎族人民对自然、社会格外富于警戒意识。
然而,这种警戒心理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一方面呈现了以上所阐述的对自然与社会的激烈抗衡。另一方面又体现出对命运的不可知心态,以及在这种心态支配下对恶势力(自然与社会)的畏惧与祈求。这一特征集中表现在面对自然的威胁时的图腾崇拜。无论是上山“砍柴栏园”、“插秧下种”还是“上山伐木”“放狗围猎”“向天求雨”等,都无不举行隆重的宗教仪式。黎族人民认为在人间除了有祖先鬼之外,还有雷公鬼、山鬼、地鬼、灶鬼、天狗鬼等,而这些大量的“鬼”又几乎都成了种族的自然崇拜物。所以,每进行一项生产活动,他们都要十分虔诚地祈求天地和大自然的保护。
原型文化遗态:图腾崇拜及其变形
在我国除汉族以外的五十多个少数民族中,黎族算是发育比较成熟的民族之一。根植于它极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所以,黎族的文化心理也呈现出原始的滞后和古朴的虔诚的特点。至今为止,居住在深山之中的黎胞仍然认为他们所崇拜的植物、动物图腾就是自己本民族或本支系的始祖。在黎族的宗教和社会生活里,图腾崇拜的观念起着相当大的支配作用。如果没有很大程度的感情上的虔诚意识,没有与之相应的原始——自然氛围,显然是很难不打破这种滞后、朴拙、甚至驳杂粗陋的精神信仰的。
有些人类学家认为,黎族唯一崇拜的图腾动物是狗,他们认为,黎族对衍生而来的动物狗,特别遵重和保护。这确实有根据。黎族无论那一支系(赛、杞、润、侾美孚)都爱狗,把养狗看得比养猪还重要。史料记载,过去的黎民是不随便杀狗的,也不吃狗肉,即使杀狗祭鬼神,也不许在房屋里煮。平时对意外死亡的狗,要举行隆重的埋葬仪式,特别是侾黎,还取下祭神时杀的狗的牙齿,用绳子绑住挂在胸前做护身符。但是根据多年的考证,黎族除了对狗有着深厚的感情外,他们对牛、青蛙、鱼的感情也是相当突出的,每年七月或十月份,黎族就要为“牛”选定特别的日子做为“牛日”。“鱼”和“青蛙”在黎家的心目中也是“吉祥”和“有福气”的象征。此外,还有植物图腾。黎民对诸如红、白藤树叶、木棉树、芭蕉树等等,均有着同样特殊的感情,有的不仅是象征物、护身符,而且当作其中禁忌的标志。由于图腾崇拜在黎族所占的位置是如此重要。有人甚至利用黎族先民崇拜祖宗这样的心理编造一套“祖先鬼”的咒语,把“祖先鬼”(黎语“tingputpau”)作为最大的鬼,要黎民杀牛祭拜,故黎族地区有所谓“天上怕雷公,地下怕祖宗,人间怕禁公”的说法。黎族是以崇拜同一图腾,同一个血缘聚居在一起的,他们的头人几乎都懂得念祖宗的咒语,于是,无形中头人就成为当然的“真理”的化身,无论是生产劳动,上山打猎还是出征,他们都带领着全体黎民进行要求祖宗保佑的各种宗教活动,而祖宗崇拜实际上成为头人们统率部落人民的精神支柱。就象弗雷泽曾经说过的,在澳大利亚的牙利部落中,一个以某种植物的种子为图腾形象的氏族的头人,被他的人民说成就是产生这种种子的植物本身一样。为此,黎族先民对他们的头人是极其崇拜的,对他们头人所提出的问题可以说是一呼百应的。
这样一来,正是这种特殊的宗教文化情绪,使黎族社会的凝聚性,公众精神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铺厉。很久以来,在黎族聚居的村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即使谷仓从不上锁,丰收季节硕果累累也从不发生盗窃现象。而这种对图腾,对“头人”的尊崇心态,又起到了调节黎族社会人际关系的杠杆作用。天神就是意志,头人就是一切,而作为“头人”首领,由于要带领大家抗拒无时无刻不潜存着的各种威胁的责任,所以要求众人的服从和团结就成为了所有“头人”的第一使命。加之黎族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主观上也迫使黎民们必须团结和谐,互相帮助。
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黎、汉民族之间的多种政治融合,经济渗透以及文化的影响,特别是由于进入现、当代社会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历史上最具有大文化意识的政治集团开始对黎族社会实行政治导向,经济扶植,文化促进的方针,使之在非常迅速的程度和非常之广的规模上,改造和转变了黎胞的传统信仰,即图腾崇拜。使他们的精神境界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然而,黎胞的几千年积淀而成的对待人与事物的虔诚心理都作为一种良善的道德传统保留下来,只不过转向到对新的,进步的政治集团——中国共产党的执着认同。解放前后几十年来,黎胞们对共产党的虔诚与敬颂最突出地反映在他们所创作的数以万计的大量的民歌、民间故事上。
冲击与融汇:黎族的模仿心理溯源
文字语言代表着一个民族的灵魂。保持民族文化传统的最有效的载体,除了世代相传的神话、习俗、舞蹈、传说等等之外,最主要的便是文字。没有文字,连神话传说这样的口语历史也会变得不完整,不系统。在缺乏本民族文字的情况下,一个民族的发展是很缓慢的,有些问题甚至会被中断而无法延续和继承下去。就象五彩缤纷的花朵,如果没有花枝和根系的支撑,便将很快凋萎。黎族就是一个没有自身文字的民族。它之所以能够以结构发音比较成熟,形态比较完整的面目发展至今,主要是因为他们赖以生存的独特无二的地理环境以及滞后发展的社会经济制度——即原始社会的“合亩制”,封建时代的“村落共同体”等等的杂揉与拼接。而非现、当代科技文明的冲击。
但是,冲击迟早要到来。只要一个民族欲求发展,欲求经济与文化的共同繁荣,这个民族就必须自觉或被迫地接受现、当代文明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冲击,与之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要与代表着现、当代文明的他民族发生经济上和精神上的多层次、多方位、多格局的融汇。在这个剧烈的摩擦与冲突,同化与反同化的过程中,冲突双方都以不同的方式实现了互补,也以自身特性的部分丧失作为代价。但是,常常的情形是,没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或者语言文字比较落后的民族,自身特性的消融也比较迅速,这样一来,在其社会心理的演变程式中,也呈现出两重态征:一是逆反与排拒,一是模仿与认同。而模仿心理又普遍地植根于整个年轻一代的价值追求,思维方式,以及生活形态的诸方面。
大量的史实证明,黎族文学艺术的发展,几乎都是模仿汉族文学、向汉族学习的。甚至黎族民间文学的发展与演变都带有模仿的痕迹。随着汉、黎族人民日益频繁的交往,黎族学习模仿汉族口头文学的机会越来越多,他们把汉族民间流传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董永的故事》、《牛郎织女》等作品作为他们演唱的内容。虽然,黎族口头文学家们已根据黎族人民的观念和美学观加以修饰,但是,原作的面目仍然保留着。又如黎族民歌的加工与修饰问题。原来黎歌的“比”“兴”很少,经过黎汉文化交流后,黎族民歌的“比兴”便大大地加强了,有的黎歌甚至与海南方言合流。另外从当代文学发展方面来看,黎族虽然已经有了以龙敏为首的一支作家队伍,但是,他们都以汉语言文学为基础,所以,尽管他们极力去摄取民族生活中的浪花,捕捉时代的信息,汲取黎族神奇瑰丽的传统故事为素材,千方百计地反映本民族人民的生活,把握本民族精神的流向。可是,从作品里看,人们不难发现,他们在整个创作过程中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评判却都是从汉语言文学中脱胎而出的。
此外,从黎族妇女的纹身,男子汉的服饰以及他们居住房屋上的演变也证明了这一点。从外观上看,无论沿海的黎族还是与汉杂居在一起的黎族。他们的衣着和生活实量有许多方面是模仿汉族的,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姑娘们连绣面纹身这一带有图腾崇拜、祖宗崇拜含义的习俗都不坚持了,她们模仿汉族姑娘们的穿戴,上衣改穿汉族的女装。而男子汉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几乎全都改穿汉族服装。黎族目前的住房建筑有好几种,其中高架船形屋是黎族现有房屋中最原始的一种,是历史上记载的最原始的所谓“干栏”建筑,后来演变为离地仅半公尺的铺地式船形房屋。随着黎汉的交往,黎族人民又模仿汉族的金字形汉式房屋建造,在受汉族影响较大的外围地区,如三亚市、陵水等县的黎族聚居地,他们的住房不仅从形式上与附近汉族相同(金字形,门向一边开)质料也从纯植物性改为泥糊墙,甚至红砖墙瓦盖顶。最为突出的例子是文化教育。据调查研究,黎族学校的文字教育几乎百分之百是以汉字为基础,这和有自己文字的其它民族如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的教育格局便大不相同。而这样以来,凡是接受过一定程度教育的黎族青少年,都很快学会了引用汉语言文字进行交流,用汉语进行思维的习惯。普通话在黎族同胞中的普及率远远超出许多民族地区的普及率。
从上述的实例,我们可以看到黎胞对先进的科学技术文明的积极模仿和认同心理是非常突出的,拒外意识比较弱。也正由于此,才形成了黎族社会生产力发展相对落后,文化教育水平相对超前的独特景观。但我们完全可以相信,文化教育水平、科学技术水平的进一步发展,也一定能够对黎胞的生产力水平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其潜力绝不可低估。
从模仿到自强:黎族的振兴心理发端
一个民族从弱小到壮大,从落后到繁荣,在心
理历程上必然要经过这样几个环节:蒙昧时期的封闭——体现在经济形态、宗教文化、社会关系等各方面。都极其重视强化本民族各个个体的纵向的“朝内转”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拒斥外向——横向的社会交流与比较。这个环节大约要经历很长时期,直到封闭的大门被先进的生产力打破为止,这样才会进入第二环节而开化时期的融合与模仿——以横向文明与先进的文化类型作为参照系,在价值判断,生活方式,行为形态等方面尽量与之认同和沟通。但认同与沟通的方式这时期主要体现为模仿,随着模仿程度在量与质上的不断加深和类型化,第三个环节即开放时期便开始了——这一时期虽也呈现横向移植。但横向的他民族的经济文化形态又逐渐退居到陪衬、借鉴的地位,本民族的主体生命力趋于旺盛,独立的自主发展的意识日趋高涨,具体反映到黎族社会里的便是强烈的振兴心理。
黎族的振兴心理发端于近代。西方列强包括他们的军舰、商船在海南的侵入,既给黎胞的生存困境雪上加霜,又刺激了黎族社会欲图改变生存困境的精神冲动。在此之前,虽然有长达几千年的汉族文化的袭扰和汉族反动统治集团的不断地围剿,但毕竟由于交通、传播系统等等的不发达,这种袭扰与围剿尚不足以撼动黎族社会的自尊意识。固本意知,只是在小范围如沿海平原等区域造成了某些方面的模仿气氛。还是帝国主义的洋枪,大炮以及附着于其上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生产力,撼醒了一部分黎胞的精神世界,使他们成为最早的民族的文明振兴的先驱者,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为了反抗外族入侵,驱逐帝国主义的洋枪大炮。一些黎胞在政治上率先成熟起来,他们自觉与中国共产党实行政治、军事的接壤,从而一致对外。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变得明达、开放、而且高度自信。当他们发现,正是中国共产党可以而且能够给黎族社会带来繁荣与发展的希望时,他们便自觉地将自身置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追求在统一与和平的旗帜下振兴民族大业。如黎族领袖王国兴、王玉锦等。另一方面,便是极少数的黎胞开始接受微弱的商品意识,从事小商小贩活动等等。如民国初年,黎族已有个别富裕人家办庙经商,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保亭市(今保城镇)就有六家黎族经营的商店。随着沿海城镇的贸易发展,国民党时期,近沿海的黎民有的已经挑着零星的土产品上街摆卖。
然而,黎族的振兴心理的真正和全面的勃兴,黎族社会的划时代发展的最大契机,应当说是在解放后的四十年历程,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近十年,以黎族的文化振兴,科技振兴与经济振兴为主导的全面振兴活动动得到了普遍的推演。以文化振兴为例,众所周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黎族文学的形式除了单调的口头文学,其它文学形式几乎是空的。但是,到了新的时期,黎族便涌现了以龙敏、王海为代表的第一批黎族作家,他们创作出一批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品,民族的振兴心理在他们的作品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在他们的作品里,人们看到原来以物换物,以草结计算的黎族,在农村商品经济的冲击下,终于露出了商品交换的幼芽。特别是作品里那一幅幅意趣盎然的山区市景的画面描写,五颜六色的摊棚画廊,都无不告诉了人们,在党的路线政策的指引下,边疆黎寨的商品经济出现了兴旺发达的景象和黎家那充满着时代气息的多彩多姿的生活及蓬勃向上的生机。此外,美术界还涌现了黎族女画家陈桂花。体育界出了黎族运动员吉泽标、王金玲。他们在全国和国际比赛中都争到了名次。以科技开发为例,解放前,黎族的农业经济是相当落后,其耕作是很粗陋的。解放后,他们购进大批铁制农具。普遍推广使用铁犁铁耙,中耕器7890一、打谷机、打谷桶、风拒等农业机具,改变了原始的刀耕火种,牛踩田,手捻稻等落后的耕作方法,并通过兴修水利,扩大水稻田的种植面积,大力开展以合理密植为中心的农业技术改革,促进了粮食生产的发展。到了六十年代,随着黎族地区水利灌溉条件的逐步改善,各地又认真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全面开展改良土壤,改革品种,改变植期,改善灌溉条件,改进栽培技术,推广科学种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贯彻落实,黎族地区普遍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学科学、学技术的热情高涨。原来的民族自治县都普遍建立了农科所,农技站和农科组,基本上形成了四级农科网。据1980年后的不完全统计,现有的七个民族自治县除了健全四级农科网外,还建立了六十七个农村基层科普协会,建立一千八百三十六个农业技术联系户,有的地方还建立科技咨询服务公司和开办科技夜校,有力地促进了黎族人民走科学致富的道路。黎族聚居地的白沙县,就有9个自然专业学会,会员共530人,每个乡镇有科普协会,57%的村委会建立科普分会,40%的自然村建立科普小组,拥有会员1200多人,每个乡镇还建立起文化、技术业余学校,全县初步建成比较完整的农村科普网络。特别是海南办大特区后,原来只是“一间芽房三石灶,一条野藤挂家当,一把钩刀砍大山,一碗谷种养全家”的黎族,竞然涌现出不少的企业家,原来只靠自然经济为生的黎族,现在也盛行贸易经商活动。黎族聚居的一些市镇,如通什、保亭市、营根、什运、毛阳等,有许多商店摊贩就是黎胞经营的,原来黎家自酿的“山栏酒”,现在已成为商品销售岛内外,黎族妇女织绣的〓裙也引起了国内外游客的注目。文化的振兴、科技的振兴与经济的振兴,给黎族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这种振兴心理又一次在鞭策着他们,为加快开发建设而作出新的努力。
当然,在此同时,黎族老一辈人的心目中,还存在着多多少少的自卑消极心理,他们不愿意打破旧的坛坛罐罐,生怕黎族的一切都被汉族同化了,所以,对新生事物的接受和学习仍显得迟滞,这不仅需要时间的推动才能改变,也需要空间上的文化心理结构的不断拓宽。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黎族的文化心理特征主要由警戒意识,虔诚意识、模仿意识和振兴意识等共同因素而构成。其中警戒意识和虔诚意识根源于民族纵向历史传统。受制约于世代聚居的险恶莫测的自然氛围和不断遭受侵扰,困厄的社会政治氛围。而警戒意识又派生出了民族的凝聚力和尚武精神;虔诚意识则变形于原形的图腾崇拜的泛神式信仰。
模仿意识与振兴意识相反,它们的形成,完全是横向比较和民族间经济文化政治甚至军事形态的相互交叉融汇的结果。正是在与他民族尤其是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科学技术文明的外来民族的相互交流以至于冲突的过程中,一个封闭的民族才会逐渐走向开化和开放,一个落后的民族才会依赖于模仿进而依赖于自我唤醒自我振兴的方式以图富强,以图繁盛。这基本上是民族交流史上的最基本的定则。黎族也不例外。只不过,黎族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得更加滞后,但却更加迅速猛烈,并且更加自觉罢了。
相关地名
海南岛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