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黎情
| 内容出处: | 《历代史志中的海棠湾》 图书 |
| 唯一号: | 200120020230003648 |
| 颗粒名称: | 第一节 黎情 |
| 分类号: | K28 |
| 页数: | 9 |
| 页码: | 334-342 |
| 摘要: | 本节介绍了海南岛三亚地区的黎族先民,包括其迁徙历史、文化特征、风俗习惯和社会组织等方面的特点。文章中还对黎族婚姻制度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
| 关键词: | 黎族 发展史 海棠湾 |
内容
海棠湾的黎族先民
《三亚史》
黎族先民的迁徙
在三亚原始社会时期,黎族远古祖先的迁徙南来是陆续进行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岭南古越族的一支,以及以后的百越民族及其骆越人先后跨海迁徙而来,在适应当地的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下,从事生产活动并定居下来,经过较长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逐渐形成具有共同地域文化特征的黎族先民。
较早的黎族先民迁徙
在距今3000—4000年前后,黎族远古祖先就已越过琼州海峡迁徙到海南岛。到达三亚地区的黎族先民,主要活动在今宁远河中上游沿岸一带。这里发现的河头、卡巴岭、沟口、大弄、二弄、高村、大茅、从毛、二毛等原始文化遗址,应是当时黎族先民活动后留下的遗迹。这些遗址大都分布在河流两岸近旁的坡地上,相距并不太远,有的还很近,表明当时黎族先民生活在宁远河沿岸地区,居住地是相对集中的。此外,在三亚藤桥河沿岸及邻近南海边的沙坡上也发现了走马园、长枕、东方红和亚龙湾等遗址,虽在分布上比较稀疏,但也表明这里曾是黎族先民活动的地方。与三亚相邻的陵水县发现的石贡、移辇、桥山等新石器时代遗址,都位于邻近南海的沙丘坡上,其分布范围达1万~2万平方米以上,这也是黎族先民在此生活居住时面积比较大的原始聚落遗迹。
按:这则史料说明,远古时代,海棠湾已有黎族先人在此生息。
《史记》卷四三世家第一三
赵世家第十三
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请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圣人观乡而顺宜,因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夫剪发文身,错臂左衽,《索隐》错臂亦文身,谓以丹青错画其臂。孔衍作“右臂左衽”,谓右袒其臂也。瓯越之民也。《索隐》刘氏云:“今珠崖、儋耳谓之瓯人,是有瓯越。”《正义》按:属南越,故言瓯越也。《舆地志》云:“交趾,周时为骆越,秦时曰西瓯,文身断发避龙”。则西瓯又在番吾之西。南越及瓯骆皆芈姓也。《世本》云“越,芈姓也,与楚同祖”是也。黑齿雕题,《集解》刘逵曰:“以草染齿,用白作黑。”郑玄曰:“雕文谓刻其肌,以青丹涅之。”去冠秫绌,《集解》徐广曰:“《战国策》作‘秫缝’,绌亦缝紩之别名也。秫者,綦针也。古字多假借,故作‘秫绌’耳。此盖言其女功针缕之粗拙也。又一本作‘鲑冠黎鲽也。”大吴之国也。
《汉书》卷九帝纪第九
元帝纪
珠崖郡山南县反,博谋群臣。待诏贾捐之以为宜弃珠崖,救民饥馑。师古曰:“谷不熟为饥,蔬不熟为馑。蔬,菜也。”乃罢珠崖。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第八下
地理志下(节选)
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师古曰:“著时从头而贯之。”男子耕农,种禾稻纻麻,女子桑蚕织绩。亡马与虎,民有五畜,师古曰:“牛、羊、豕、鸡、犬。”山多麈麖。师古曰:“麈似鹿而大,麖似鹿而小。麈音主,麖音京。”兵则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为镞。师古曰:“镞,矢锋,音子木反。”自初为郡县,吏卒中国人多侵陵之,故率数岁壹反。元帝时,遂罢弃之。
《后汉书》卷八六列传第七六
南蛮传
楚子称霸,朝贡百越。秦并天下,威服蛮夷,始开领外,置南海、桂林、象郡。汉兴,尉佗自立为南越王,传国五世。《前书》南粤王赵佗,真定人也。秦时为南海尉。佗孙胡,胡子婴齐,婴齐子兴也。至武帝元鼎五年,遂灭之,分置九郡,交趾刺史领焉。其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上,东西千里,南北五百里。其渠帅贵长耳,皆穿而缒之,垂肩三寸。武帝末,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蛮不堪役,遂攻郡杀幸。幸子豹合率善人还复破之,自领郡事,讨击余党,连年乃平。豹遣使封还印绶,上书言状,制诏即以豹为珠崖太守。即,就也。威政大行,献命岁至。中国贪其珍赂,渐相侵侮,故率数岁一反。元帝初元三年,遂罢之。凡立郡六十五岁。
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纳贾捐之言,而下诏曰:“珠崖背畔,今议者或曰可讨,或日弃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则欲诛之。通于时变,复忧万民。夫万民之饥与远蛮之不讨,何者为大?宗庙之祭,凶年犹有不备,况避不嫌之辱哉。今关东大困,无以相赡,又当动兵,非但劳民而已。其罢珠崖郡。”此元帝所以发德音也。夫恤民救急,虽成郡列县,尚犹弃之,况障塞之外,未尝为民居者乎。
《三国志》卷三〇《魏书》第三〇
东夷传附倭传(节选)
其风俗不淫,男子皆露紒,以木绵招头。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妇人被发屈紒,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种禾稻、紵麻,蚕桑、缉绩,出细紵、缣绵。其地无牛马虎豹羊鹊。兵用矛、楯、木弓。
《三国志》卷五三《吴书》第八
薛综传(节选)
珠崖除州县嫁娶,皆须八月引户,人民集会之时,男女自相可适,乃为夫妻,父母不能止。交趾糜泠、九真都庞二县,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为俗,长吏恣听,不能禁制。日南郡男女裸体,不以为羞。由此言之,可谓虫豸,有腼面目耳。然而土广人众,阻险毒害,易以为乱,难使从治。县官羁縻,示令威服,田户之租赋,裁取供办,贵致远珍名珠、香药、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鹦鹉、翡翠、孔雀、奇物、充备宝玩,不必仰其赋入,以益中国也。然在九甸之外,长吏之选,类不精覈。
《梁书》卷五四列传第四八
东夷传·倭传(节选)
物产略与儋耳、朱崖同。地温暖,风俗不淫。男女皆露紒。富贵者以锦绣杂采为帽,似中国胡公头。食饮用笾豆。其死,有棺无槨,封土作冢。人性皆嗜酒。俗不知正岁,多寿考,多至八九十,或至百岁。其俗女多男少,贵者至四五妻,贱者犹两三妻。妇人无淫妒。无盗窃,少诤讼。若犯法,轻者没其妻子,重则灭其宗族。
《岭外代答》宋·周去非
海外黎蛮
海南有黎母山,内为生黎,去州县远,不供赋役;外为熟黎,耕省地,供赋役,而各以所迩隶于四军州,生黎质直犷悍,不受欺触,本不为人患。熟黎多湖广、福建之奸民也,狡悍祸贼,外虽供赋于官,而阴结生黎以侵省地,邀掠行旅、居民,官吏经由村峒,多舍其家。峒中有王二娘者,黎之酋也,夫之名不闻。家饶于财,善用其众,力能制服群黎,朝廷赐封宜人,琼管有令于黎峒,必下王宜人,无不帖然。二娘死,女亦能继其业。昔崇宁中,王祖道经略广西,抚定黎贼九百七峒,结丁口六万四千,开通道路一千二百馀里,自以为汉唐以来所不臣之地,皆入版图,官僚皆受厚赏。淳熙元年,五指山生黎峒首王仲期,率其旁十八峒、丁口一千八百二十人归化。诸峒首王仲文等八十一人诣琼管公参,就显应庙斫石歃血,约誓改过,不复抄掠。琼管犒遣归峒。
大抵黎俗多猜。客来不遽见之,而于隙间察客俨然不动,然后遣奴出布席。客即席坐,移时,主乃出见,不交一谈。少焉置酒,先以恶秽味尝客,客忍食不疑,则喜,继以牛酒。否则遣客。其亲故聚会,椎鼓歌舞,三杯后请去备,犹以弓刀置身侧也。性好雠杀,谓之作拗。遇亲戚之仇,即械系之,要牛酒银尊,谓之赎命。婚姻以折箭为信。商旅在其家,黎女有不洁者,父母反对邻里夸之。其亲死,杀牛以祭,不哭不饭,唯食生牛肉。其葬也,舁榇而行,前一人以鸡子掷地,不破即吉地也。居处皆栅屋。土产名香、槟榔、椰子、小马、翠羽、黄蜡、苏木、吉贝之属,四州军征商,以为岁计,商贾多贩牛以易香。黎装椎髻、徒跣、裸袒,而腰缭吉贝,首珥银钗,或铜或锡,首或以绛帛彩帛包髻,或戴小花笠,或加鸡尾,而皆簪银篦二枝,亦有着短织花裙者。崇宁中王祖道抚定黎峒,其酋亦有补官,今其孙尚服锦袍银束带,盖其先世所受赐而服之云。黎人执黎弓,垂箭莆,戴兜鍪,佩黎刀。刀刃长二尺,而柄甚长,以白角片长尺许如鸡尾为靶子饰兜鍪,织藤为之。其妇人高髻绣面,耳带铜环,垂坠到肩。衣裙皆吉贝,五色烂然。无有袴襦,徒系裙数重。裙制:四围合缝,以足穿之,而系诸腰。群浴于川。黎人半能汉语,十百为群,变服入州县墟市,人莫辨焉。日将晚,或吹牛角为声,则纷纷聚会,结队而归,始知其为黎也。
《桂海虞衡志》宋·范成大
黎
黎,海南四郡,坞上蛮也。坞直雷州,由徐闻渡,半日至。坞之中,有黎母山,居民环居四傍,号黎人。内为生黎,外为熟黎。山极高,常在雾霭中,黎人自鲜识之。久晴,海氛清廓时,或见翠尖浮半空下,犹洪濛也。山水分四郡,熟黎所居已阻深,生黎之巢深邃,外人不复迹。黎母之巅,则虽生黎亦不能至。相传其上有人,寿考逸乐,不与世接,虎豹守险,无路可攀。但觉水泉甘美绝异尔。蛮去省地远,不供赋役者名生黎;耕作省地供赋役者名熟黎。各以所迩,分隶四郡。皆椎髻跣足,插银铜锡钗,腰缭花布,执长靶刀、长鞘弓、长荷枪,跬步不舍去。熟黎能汉语,变服入州县圩市,日晚鸣角结队以归。妇人绣面,高髻,钗上加铜环,耳坠垂肩。衣裙皆五色吉贝,无裤襦,但系裙数重,制四围合缝,以足穿而系之。群于川,先去上衣,自濯,乃濯足,渐升其裙至顶,以身串入水,浴则裙复自顶而下,身亦出水。绣面乃其吉礼,女年将及笄,置酒会亲属女伴,自施针笔,涅为极细虫蛾花卉,而以淡粟纹遍其馀地,谓之绣面,女婢获则否。女工纺织,得中国彩帛,拆取色丝,和吉贝织花,所谓黎锦、黎单及鞍搭类,精粗有差。居处架木两重,上以自居,下以畜牧。婚姻折箭为定,聚会亦椎鼓舞歌。亲死不哭,不粥饭,惟食生牛肉,以为哀痛之至。葬则舁榇而行,令一人前行,以鸡子掷地,鸡子不破处,即为吉穴。客来未相识,主人先于隙间窥之。客俨然矜庄,始遣奴布席于地,客即坐。又移时,主人乃出,对坐不交一谈。少焉,置酒,先以恶臭秽味尝客,客食不疑,则喜,继设中酒,遂相亲。否则遣客,不复与交。会饮未尝舍刀,三杯后各请弛备,虽解器械,犹置身傍也。一语不相能,则起而相戕。性喜仇杀,谓之捉拗。所亲为人所杀后,见仇家人及其洞中种类,皆擒取,以荔枝木械之,要牛酒银瓶乃释,谓之赎命。土产沉水、蓬莱诸香,漫山悉槟榔、椰子木,亦产小马,翠羽、黄蜡之属。与省地商人博易,甚有信而不受欺绐。商人有信,则相与如至亲,借贷有所不吝。岁望其一来,不来则数数念之,或负约不至,自一钱以上,虽数十年后,其同郡人擒之,以为质,枷其项,关以横木,俟前负者来偿,乃释。负者或远或死,无辜被系,累岁月至死乃已。复伺其同郡人来,亦枷系之。被系家人往负债之家,痛诟责偿,或乡党率敛为偿始解。凡负钱一缗,次年倍责两缗,倍至十年乃止。本负一缗,十年为千缗,以故人不敢负其一钱。客或误杀其一鸡,则鸣鼓告众,责偿曰:某客杀我一鸡,当偿一斗。一斗者,雌雄各一也。一雄为钱三十,一雌五十。一斗每生十子,五为雄,五为雌,一岁四产十鸡,并种,当为六斗,六斗当生六十鸡。以此倍计,展转十年乃已。误杀其一鸡,虽富商亦偿不足。客其家,无敢损动其一毫。闽商值风水,荡去其资,多入黎地,耕种不归。官吏及省民经由村洞,必舍其家,恃以安。熟黎之地,始是州县。大抵四郡各占坞之一陲,其中黎地不可得,亦无路通。珠崖在坞南陲,既不可取径,则复桴海,循坞而南,所谓再涉鲸波也。四郡之人,多黎姓,盖其裔族,而今黎人乃多姓王。生黎质直犷悍,不受欺触,不服王化,亦不出为人患。熟黎贪狡,湖广、福建之奸民亡命杂焉,侵轶省界,常为四郡患。有王二娘者,琼州熟黎之酋,有夫而名不闻,家饶财,善用众,能制服群黎,朝廷封宜人。琼管有号令,必下王宜人,无不帖然。二娘死,女能继之。其馀三郡,强名小垒,实不及江浙间一村落。县邑或为黎人据其厅事治所,遣人说谢,始得还。前后边吏,惴不敢言。淳熙元年十月,五指山生黎洞首王仲期,率其傍人十洞丁口千八百二十归化,仲期与诸洞首王仲文等八十一人诣琼管司,琼管司受之,以例诣显应庙研石歃血,约誓改过,不复钞掠,犒赐遣归。琼守图其形状衣制上经略司,髻露者以绛帛约髻根,或以彩帛包髻,或戴小花笠,皆簪二银篦,或加雉尾,衣花织短衫,系花襈裙,悉跣足,是其盛饰也。惟王居则青布红锦袍,束带,麻鞋,自云祖父宣和中尝纳土补官,赐锦袍云。(录存佚文,见《文献通考》卷三三一、四裔考八)
《琼崖志略》
黎族
性情
黎人生性朴直,绝少机械心。对于同村同弓同峒之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一家有事,全部尽力以援。事成之后,不取报酬。食尽,则群赴他村食之;又尽,则又赴他村,皆无彼此之别。黎头之于黎众亦极平等,劳动、生活与众共之,众亦因其德望,愿听指挥。无专制之形迹,有共和之精神。遇有变故,黎头发号司令,全弓服从。一弓有难,则传矢他弓,附者自刻一符号痕迹于其上,则又传之他弓,订期并举,同赴为首之弓,宰牛剧饮。既食其杯酒片肉,即有必死之决心。其有不赴者,则于事后群起而攻之。对于外来孤客,能尽地主之谊,待之无异家人。若与之联为同庚,执待犹为亲切。平素寡诺重信,来往贸易不欺,亦不受人欺。约定之后,至死不悖。有时无力偿负,辄不惜一切,或冒险出劫以予之。因其性质如此,故遇有仇怨,或彼此误会,其报复对待之手段,亦甚残酷,必致其人于死而后已。犷悍之名,由此而得。实则黎人天性纯朴,有太古之遗风,极易共事。较之常人,有过之无不及也。
风俗习惯
琼崖土著四族,杂居于腹地各处,无一定之区域,且历时久远,每有小部落移地迁居者,故不能以地理强为划分。然约而言之,则侾族所居较近海岸,伎族所居最为深邃,黎则处于二者之间。苗人性喜居山,又多迁徙,散在各处,无固定住所。至于黎中之三差、四差,则仅于崖县见之。四差系唐代乡贤李德裕、邢宥之子孙,避世入山,渐化为黎,现时尚存有李德裕之遗物。侾中之西侾则多居于崖县西部及感、昌二属,为他处所无。各族之间交通虽不甚频繁,然接近之地则往来甚密,缔结婚姻,久而久之,间有相互同化之点,故彼此风俗习惯不尽同,而不尽不同也。
组织
黎境土地肥沃,户口无多,生活简陋,嗜好绝无,彼此之间鲜有冲突。其社会之组织,因此极为简单。峒有峒首,村有头目,略如家族之有家长族长而已。其尤简者,则并此而无之。历时既久,黎汉之关系,日渐趋于复杂,而黎患之声遂盈于耳。每次大征之后,必创为种种制度以束缚黎人,想藉之预防后患。干百年来,黎患屡起,制度亦屡变。清光绪间,冯子材平黎之时,将黎峒组织大加修改,于抚黎局下设黎团总长,统辖全属黎境。黎团总长之下有总管,总辖全峒。峒中黎户十家为排,排有排长;三排为甲,甲有甲长;三甲为保,保有保正保副。保正保副理军政,总管理民政,亦有总管兼理军政者。是等黎酋,有世袭者,有公举由官加委者。
衣食住
黎人饮食甚为简便,无碗筷,以叶包饭,以手掇食。佐膳品用南瓜、叶、野菜、草菰,和盐煮之。米之外,并加番薯合煮为粥。视猪牛肉为佳肴,必于婚丧礼及祈祷之日始得而尝之。黎人衣着,男子下身皆以布一方遮蔽,上身全裸,杂于人中,恬不为怪。至其住处,则多架屋,以木为柱,以竹为梁,张以巨叶,上加茆草。两檐垂地,两端筑泥为墙,正中各凿二户。二户之外,别置窗棂。二户不能同时并开,否则必召灾祲,故室内光线极其暗淡。室内布置,大都以竹编为床,上面睡人,下则睡畜。又有编竹与藤为屋底,离地二尺许,敷以草席,坐卧其上。
婚姻
黎族男女之间极其自由,生活单简,经济不相依赖。女至十五六岁,其父母辄为另建小屋于僻静之地,任其独居,随意结交,父母绝不过问。设或生子女,即留作日后之嫁装,多子则曰多装,所嫁之夫家亦不以为嫌,惟主祭不用之耳。春秋佳日,择地集会,男女齐集,唱歌互答,彼此相悦,即可合婚。婚姻不避同姓。聘礼用牛一二头至十余头不等。无子者,嫁后三日即回小屋,每逢岁节辄来往夫家数日,必俟生子后,乃永住夫家。俗以最后之子为嫡。举行婚礼时,九代亲属男女各持牛猪鸡酒前来庆贺,女家亦遣陪嫁者数十人送新妇过门,即为成礼。礼毕设宴,男女宾客相对聚饮,尽欢而散。席中男女宾客互相戏谑,本夫在座,亦不干预。如有不愿其妻交他人者,则须预劝其妻不来,惟来否之权,仍操之妻。兄死而弟未聚,则嫂问弟愿留己否,不留及无弟者,均即归宁。
嗜好
黎人嗜好极少,然亦不能绝无。最好者为米酒,载饮载歌,欢呼啸傲,虽无佳肴,其乐无极。当其饮酒之时,无论若何重大事件,亦置之不问。次于酒者为狩猎。深山旷野,每多麋鹿、山猪、山马等兽,农暇无事,辄荷枪围猎。倘有所获,则以其肉为脯,留供庆吊之用,皮筋茸角则鬻之于山客。留腮骨及牙齿悬挂屋中,作为纪念。以悬骨之多寡,表其人之勇懦,及枪术之优劣。富者爱好古代铜鼓铜锣,以鼓缘锣柄有虾蟆形者为上品,真伪新旧均有考证。每鼓或锣之价,可值数牛至十余牛不等。若有四虾蟆以上者,则非百牛不办矣。
武器
时武器尚弓矢,以木为弓,以藤竹为弦,铁簇无羽而有钩,中者辄入骨不能拔。苗人则用弩箭,以毒药敷箭端,中者必死。清末火器渐次流入,弓矢之用日见减少,所用前膛枪、大急枪,有力者家置一杆至数杆不等。此项枪枝黎人不能自制,必向外间购买,每枪一杆及子弹若干以数牛易之。出入携带,弹鸟击兽,习成惯技,发必有中。其出入之径路有数处,就中以岭门及白沙方面为交通较便,来往极众。
丧葬
四黎之中,苗俗多用火葬风葬,黎、伎、侾则用土葬。棺用佳木,而各地形式不同。有刳整木为棺者,有以板为之者。有掘地作长方形,而于上下四方列板为墙,置尸其中,以土掩盖者。倘人死而棺木未备,则由其亲属入山访佳木,而陈尸室中而待,迟至十余日不能葬。亲死不哭,准食生牛肉以表哀痛。第八日奠祭,名曰“作八”。邀亲戚中熟悉死者之历史者一二人,报告死者之祖先及其本身经历,与债权务关系,俾众周知。远近男女亲戚,必以牛、羊、酒、米、纸灯、鼓吹来奠。礼毕聚饮。每逢亲死,辄留祭牛顶角,悬钉柱端,以作纪念。悬角多者,表示家世甚旧。
《三亚史》
黎族先民的迁徙
在三亚原始社会时期,黎族远古祖先的迁徙南来是陆续进行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岭南古越族的一支,以及以后的百越民族及其骆越人先后跨海迁徙而来,在适应当地的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下,从事生产活动并定居下来,经过较长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逐渐形成具有共同地域文化特征的黎族先民。
较早的黎族先民迁徙
在距今3000—4000年前后,黎族远古祖先就已越过琼州海峡迁徙到海南岛。到达三亚地区的黎族先民,主要活动在今宁远河中上游沿岸一带。这里发现的河头、卡巴岭、沟口、大弄、二弄、高村、大茅、从毛、二毛等原始文化遗址,应是当时黎族先民活动后留下的遗迹。这些遗址大都分布在河流两岸近旁的坡地上,相距并不太远,有的还很近,表明当时黎族先民生活在宁远河沿岸地区,居住地是相对集中的。此外,在三亚藤桥河沿岸及邻近南海边的沙坡上也发现了走马园、长枕、东方红和亚龙湾等遗址,虽在分布上比较稀疏,但也表明这里曾是黎族先民活动的地方。与三亚相邻的陵水县发现的石贡、移辇、桥山等新石器时代遗址,都位于邻近南海的沙丘坡上,其分布范围达1万~2万平方米以上,这也是黎族先民在此生活居住时面积比较大的原始聚落遗迹。
按:这则史料说明,远古时代,海棠湾已有黎族先人在此生息。
《史记》卷四三世家第一三
赵世家第十三
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请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圣人观乡而顺宜,因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夫剪发文身,错臂左衽,《索隐》错臂亦文身,谓以丹青错画其臂。孔衍作“右臂左衽”,谓右袒其臂也。瓯越之民也。《索隐》刘氏云:“今珠崖、儋耳谓之瓯人,是有瓯越。”《正义》按:属南越,故言瓯越也。《舆地志》云:“交趾,周时为骆越,秦时曰西瓯,文身断发避龙”。则西瓯又在番吾之西。南越及瓯骆皆芈姓也。《世本》云“越,芈姓也,与楚同祖”是也。黑齿雕题,《集解》刘逵曰:“以草染齿,用白作黑。”郑玄曰:“雕文谓刻其肌,以青丹涅之。”去冠秫绌,《集解》徐广曰:“《战国策》作‘秫缝’,绌亦缝紩之别名也。秫者,綦针也。古字多假借,故作‘秫绌’耳。此盖言其女功针缕之粗拙也。又一本作‘鲑冠黎鲽也。”大吴之国也。
《汉书》卷九帝纪第九
元帝纪
珠崖郡山南县反,博谋群臣。待诏贾捐之以为宜弃珠崖,救民饥馑。师古曰:“谷不熟为饥,蔬不熟为馑。蔬,菜也。”乃罢珠崖。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第八下
地理志下(节选)
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师古曰:“著时从头而贯之。”男子耕农,种禾稻纻麻,女子桑蚕织绩。亡马与虎,民有五畜,师古曰:“牛、羊、豕、鸡、犬。”山多麈麖。师古曰:“麈似鹿而大,麖似鹿而小。麈音主,麖音京。”兵则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为镞。师古曰:“镞,矢锋,音子木反。”自初为郡县,吏卒中国人多侵陵之,故率数岁壹反。元帝时,遂罢弃之。
《后汉书》卷八六列传第七六
南蛮传
楚子称霸,朝贡百越。秦并天下,威服蛮夷,始开领外,置南海、桂林、象郡。汉兴,尉佗自立为南越王,传国五世。《前书》南粤王赵佗,真定人也。秦时为南海尉。佗孙胡,胡子婴齐,婴齐子兴也。至武帝元鼎五年,遂灭之,分置九郡,交趾刺史领焉。其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上,东西千里,南北五百里。其渠帅贵长耳,皆穿而缒之,垂肩三寸。武帝末,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蛮不堪役,遂攻郡杀幸。幸子豹合率善人还复破之,自领郡事,讨击余党,连年乃平。豹遣使封还印绶,上书言状,制诏即以豹为珠崖太守。即,就也。威政大行,献命岁至。中国贪其珍赂,渐相侵侮,故率数岁一反。元帝初元三年,遂罢之。凡立郡六十五岁。
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纳贾捐之言,而下诏曰:“珠崖背畔,今议者或曰可讨,或日弃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则欲诛之。通于时变,复忧万民。夫万民之饥与远蛮之不讨,何者为大?宗庙之祭,凶年犹有不备,况避不嫌之辱哉。今关东大困,无以相赡,又当动兵,非但劳民而已。其罢珠崖郡。”此元帝所以发德音也。夫恤民救急,虽成郡列县,尚犹弃之,况障塞之外,未尝为民居者乎。
《三国志》卷三〇《魏书》第三〇
东夷传附倭传(节选)
其风俗不淫,男子皆露紒,以木绵招头。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妇人被发屈紒,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种禾稻、紵麻,蚕桑、缉绩,出细紵、缣绵。其地无牛马虎豹羊鹊。兵用矛、楯、木弓。
《三国志》卷五三《吴书》第八
薛综传(节选)
珠崖除州县嫁娶,皆须八月引户,人民集会之时,男女自相可适,乃为夫妻,父母不能止。交趾糜泠、九真都庞二县,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为俗,长吏恣听,不能禁制。日南郡男女裸体,不以为羞。由此言之,可谓虫豸,有腼面目耳。然而土广人众,阻险毒害,易以为乱,难使从治。县官羁縻,示令威服,田户之租赋,裁取供办,贵致远珍名珠、香药、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鹦鹉、翡翠、孔雀、奇物、充备宝玩,不必仰其赋入,以益中国也。然在九甸之外,长吏之选,类不精覈。
《梁书》卷五四列传第四八
东夷传·倭传(节选)
物产略与儋耳、朱崖同。地温暖,风俗不淫。男女皆露紒。富贵者以锦绣杂采为帽,似中国胡公头。食饮用笾豆。其死,有棺无槨,封土作冢。人性皆嗜酒。俗不知正岁,多寿考,多至八九十,或至百岁。其俗女多男少,贵者至四五妻,贱者犹两三妻。妇人无淫妒。无盗窃,少诤讼。若犯法,轻者没其妻子,重则灭其宗族。
《岭外代答》宋·周去非
海外黎蛮
海南有黎母山,内为生黎,去州县远,不供赋役;外为熟黎,耕省地,供赋役,而各以所迩隶于四军州,生黎质直犷悍,不受欺触,本不为人患。熟黎多湖广、福建之奸民也,狡悍祸贼,外虽供赋于官,而阴结生黎以侵省地,邀掠行旅、居民,官吏经由村峒,多舍其家。峒中有王二娘者,黎之酋也,夫之名不闻。家饶于财,善用其众,力能制服群黎,朝廷赐封宜人,琼管有令于黎峒,必下王宜人,无不帖然。二娘死,女亦能继其业。昔崇宁中,王祖道经略广西,抚定黎贼九百七峒,结丁口六万四千,开通道路一千二百馀里,自以为汉唐以来所不臣之地,皆入版图,官僚皆受厚赏。淳熙元年,五指山生黎峒首王仲期,率其旁十八峒、丁口一千八百二十人归化。诸峒首王仲文等八十一人诣琼管公参,就显应庙斫石歃血,约誓改过,不复抄掠。琼管犒遣归峒。
大抵黎俗多猜。客来不遽见之,而于隙间察客俨然不动,然后遣奴出布席。客即席坐,移时,主乃出见,不交一谈。少焉置酒,先以恶秽味尝客,客忍食不疑,则喜,继以牛酒。否则遣客。其亲故聚会,椎鼓歌舞,三杯后请去备,犹以弓刀置身侧也。性好雠杀,谓之作拗。遇亲戚之仇,即械系之,要牛酒银尊,谓之赎命。婚姻以折箭为信。商旅在其家,黎女有不洁者,父母反对邻里夸之。其亲死,杀牛以祭,不哭不饭,唯食生牛肉。其葬也,舁榇而行,前一人以鸡子掷地,不破即吉地也。居处皆栅屋。土产名香、槟榔、椰子、小马、翠羽、黄蜡、苏木、吉贝之属,四州军征商,以为岁计,商贾多贩牛以易香。黎装椎髻、徒跣、裸袒,而腰缭吉贝,首珥银钗,或铜或锡,首或以绛帛彩帛包髻,或戴小花笠,或加鸡尾,而皆簪银篦二枝,亦有着短织花裙者。崇宁中王祖道抚定黎峒,其酋亦有补官,今其孙尚服锦袍银束带,盖其先世所受赐而服之云。黎人执黎弓,垂箭莆,戴兜鍪,佩黎刀。刀刃长二尺,而柄甚长,以白角片长尺许如鸡尾为靶子饰兜鍪,织藤为之。其妇人高髻绣面,耳带铜环,垂坠到肩。衣裙皆吉贝,五色烂然。无有袴襦,徒系裙数重。裙制:四围合缝,以足穿之,而系诸腰。群浴于川。黎人半能汉语,十百为群,变服入州县墟市,人莫辨焉。日将晚,或吹牛角为声,则纷纷聚会,结队而归,始知其为黎也。
《桂海虞衡志》宋·范成大
黎
黎,海南四郡,坞上蛮也。坞直雷州,由徐闻渡,半日至。坞之中,有黎母山,居民环居四傍,号黎人。内为生黎,外为熟黎。山极高,常在雾霭中,黎人自鲜识之。久晴,海氛清廓时,或见翠尖浮半空下,犹洪濛也。山水分四郡,熟黎所居已阻深,生黎之巢深邃,外人不复迹。黎母之巅,则虽生黎亦不能至。相传其上有人,寿考逸乐,不与世接,虎豹守险,无路可攀。但觉水泉甘美绝异尔。蛮去省地远,不供赋役者名生黎;耕作省地供赋役者名熟黎。各以所迩,分隶四郡。皆椎髻跣足,插银铜锡钗,腰缭花布,执长靶刀、长鞘弓、长荷枪,跬步不舍去。熟黎能汉语,变服入州县圩市,日晚鸣角结队以归。妇人绣面,高髻,钗上加铜环,耳坠垂肩。衣裙皆五色吉贝,无裤襦,但系裙数重,制四围合缝,以足穿而系之。群于川,先去上衣,自濯,乃濯足,渐升其裙至顶,以身串入水,浴则裙复自顶而下,身亦出水。绣面乃其吉礼,女年将及笄,置酒会亲属女伴,自施针笔,涅为极细虫蛾花卉,而以淡粟纹遍其馀地,谓之绣面,女婢获则否。女工纺织,得中国彩帛,拆取色丝,和吉贝织花,所谓黎锦、黎单及鞍搭类,精粗有差。居处架木两重,上以自居,下以畜牧。婚姻折箭为定,聚会亦椎鼓舞歌。亲死不哭,不粥饭,惟食生牛肉,以为哀痛之至。葬则舁榇而行,令一人前行,以鸡子掷地,鸡子不破处,即为吉穴。客来未相识,主人先于隙间窥之。客俨然矜庄,始遣奴布席于地,客即坐。又移时,主人乃出,对坐不交一谈。少焉,置酒,先以恶臭秽味尝客,客食不疑,则喜,继设中酒,遂相亲。否则遣客,不复与交。会饮未尝舍刀,三杯后各请弛备,虽解器械,犹置身傍也。一语不相能,则起而相戕。性喜仇杀,谓之捉拗。所亲为人所杀后,见仇家人及其洞中种类,皆擒取,以荔枝木械之,要牛酒银瓶乃释,谓之赎命。土产沉水、蓬莱诸香,漫山悉槟榔、椰子木,亦产小马,翠羽、黄蜡之属。与省地商人博易,甚有信而不受欺绐。商人有信,则相与如至亲,借贷有所不吝。岁望其一来,不来则数数念之,或负约不至,自一钱以上,虽数十年后,其同郡人擒之,以为质,枷其项,关以横木,俟前负者来偿,乃释。负者或远或死,无辜被系,累岁月至死乃已。复伺其同郡人来,亦枷系之。被系家人往负债之家,痛诟责偿,或乡党率敛为偿始解。凡负钱一缗,次年倍责两缗,倍至十年乃止。本负一缗,十年为千缗,以故人不敢负其一钱。客或误杀其一鸡,则鸣鼓告众,责偿曰:某客杀我一鸡,当偿一斗。一斗者,雌雄各一也。一雄为钱三十,一雌五十。一斗每生十子,五为雄,五为雌,一岁四产十鸡,并种,当为六斗,六斗当生六十鸡。以此倍计,展转十年乃已。误杀其一鸡,虽富商亦偿不足。客其家,无敢损动其一毫。闽商值风水,荡去其资,多入黎地,耕种不归。官吏及省民经由村洞,必舍其家,恃以安。熟黎之地,始是州县。大抵四郡各占坞之一陲,其中黎地不可得,亦无路通。珠崖在坞南陲,既不可取径,则复桴海,循坞而南,所谓再涉鲸波也。四郡之人,多黎姓,盖其裔族,而今黎人乃多姓王。生黎质直犷悍,不受欺触,不服王化,亦不出为人患。熟黎贪狡,湖广、福建之奸民亡命杂焉,侵轶省界,常为四郡患。有王二娘者,琼州熟黎之酋,有夫而名不闻,家饶财,善用众,能制服群黎,朝廷封宜人。琼管有号令,必下王宜人,无不帖然。二娘死,女能继之。其馀三郡,强名小垒,实不及江浙间一村落。县邑或为黎人据其厅事治所,遣人说谢,始得还。前后边吏,惴不敢言。淳熙元年十月,五指山生黎洞首王仲期,率其傍人十洞丁口千八百二十归化,仲期与诸洞首王仲文等八十一人诣琼管司,琼管司受之,以例诣显应庙研石歃血,约誓改过,不复钞掠,犒赐遣归。琼守图其形状衣制上经略司,髻露者以绛帛约髻根,或以彩帛包髻,或戴小花笠,皆簪二银篦,或加雉尾,衣花织短衫,系花襈裙,悉跣足,是其盛饰也。惟王居则青布红锦袍,束带,麻鞋,自云祖父宣和中尝纳土补官,赐锦袍云。(录存佚文,见《文献通考》卷三三一、四裔考八)
《琼崖志略》
黎族
性情
黎人生性朴直,绝少机械心。对于同村同弓同峒之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一家有事,全部尽力以援。事成之后,不取报酬。食尽,则群赴他村食之;又尽,则又赴他村,皆无彼此之别。黎头之于黎众亦极平等,劳动、生活与众共之,众亦因其德望,愿听指挥。无专制之形迹,有共和之精神。遇有变故,黎头发号司令,全弓服从。一弓有难,则传矢他弓,附者自刻一符号痕迹于其上,则又传之他弓,订期并举,同赴为首之弓,宰牛剧饮。既食其杯酒片肉,即有必死之决心。其有不赴者,则于事后群起而攻之。对于外来孤客,能尽地主之谊,待之无异家人。若与之联为同庚,执待犹为亲切。平素寡诺重信,来往贸易不欺,亦不受人欺。约定之后,至死不悖。有时无力偿负,辄不惜一切,或冒险出劫以予之。因其性质如此,故遇有仇怨,或彼此误会,其报复对待之手段,亦甚残酷,必致其人于死而后已。犷悍之名,由此而得。实则黎人天性纯朴,有太古之遗风,极易共事。较之常人,有过之无不及也。
风俗习惯
琼崖土著四族,杂居于腹地各处,无一定之区域,且历时久远,每有小部落移地迁居者,故不能以地理强为划分。然约而言之,则侾族所居较近海岸,伎族所居最为深邃,黎则处于二者之间。苗人性喜居山,又多迁徙,散在各处,无固定住所。至于黎中之三差、四差,则仅于崖县见之。四差系唐代乡贤李德裕、邢宥之子孙,避世入山,渐化为黎,现时尚存有李德裕之遗物。侾中之西侾则多居于崖县西部及感、昌二属,为他处所无。各族之间交通虽不甚频繁,然接近之地则往来甚密,缔结婚姻,久而久之,间有相互同化之点,故彼此风俗习惯不尽同,而不尽不同也。
组织
黎境土地肥沃,户口无多,生活简陋,嗜好绝无,彼此之间鲜有冲突。其社会之组织,因此极为简单。峒有峒首,村有头目,略如家族之有家长族长而已。其尤简者,则并此而无之。历时既久,黎汉之关系,日渐趋于复杂,而黎患之声遂盈于耳。每次大征之后,必创为种种制度以束缚黎人,想藉之预防后患。干百年来,黎患屡起,制度亦屡变。清光绪间,冯子材平黎之时,将黎峒组织大加修改,于抚黎局下设黎团总长,统辖全属黎境。黎团总长之下有总管,总辖全峒。峒中黎户十家为排,排有排长;三排为甲,甲有甲长;三甲为保,保有保正保副。保正保副理军政,总管理民政,亦有总管兼理军政者。是等黎酋,有世袭者,有公举由官加委者。
衣食住
黎人饮食甚为简便,无碗筷,以叶包饭,以手掇食。佐膳品用南瓜、叶、野菜、草菰,和盐煮之。米之外,并加番薯合煮为粥。视猪牛肉为佳肴,必于婚丧礼及祈祷之日始得而尝之。黎人衣着,男子下身皆以布一方遮蔽,上身全裸,杂于人中,恬不为怪。至其住处,则多架屋,以木为柱,以竹为梁,张以巨叶,上加茆草。两檐垂地,两端筑泥为墙,正中各凿二户。二户之外,别置窗棂。二户不能同时并开,否则必召灾祲,故室内光线极其暗淡。室内布置,大都以竹编为床,上面睡人,下则睡畜。又有编竹与藤为屋底,离地二尺许,敷以草席,坐卧其上。
婚姻
黎族男女之间极其自由,生活单简,经济不相依赖。女至十五六岁,其父母辄为另建小屋于僻静之地,任其独居,随意结交,父母绝不过问。设或生子女,即留作日后之嫁装,多子则曰多装,所嫁之夫家亦不以为嫌,惟主祭不用之耳。春秋佳日,择地集会,男女齐集,唱歌互答,彼此相悦,即可合婚。婚姻不避同姓。聘礼用牛一二头至十余头不等。无子者,嫁后三日即回小屋,每逢岁节辄来往夫家数日,必俟生子后,乃永住夫家。俗以最后之子为嫡。举行婚礼时,九代亲属男女各持牛猪鸡酒前来庆贺,女家亦遣陪嫁者数十人送新妇过门,即为成礼。礼毕设宴,男女宾客相对聚饮,尽欢而散。席中男女宾客互相戏谑,本夫在座,亦不干预。如有不愿其妻交他人者,则须预劝其妻不来,惟来否之权,仍操之妻。兄死而弟未聚,则嫂问弟愿留己否,不留及无弟者,均即归宁。
嗜好
黎人嗜好极少,然亦不能绝无。最好者为米酒,载饮载歌,欢呼啸傲,虽无佳肴,其乐无极。当其饮酒之时,无论若何重大事件,亦置之不问。次于酒者为狩猎。深山旷野,每多麋鹿、山猪、山马等兽,农暇无事,辄荷枪围猎。倘有所获,则以其肉为脯,留供庆吊之用,皮筋茸角则鬻之于山客。留腮骨及牙齿悬挂屋中,作为纪念。以悬骨之多寡,表其人之勇懦,及枪术之优劣。富者爱好古代铜鼓铜锣,以鼓缘锣柄有虾蟆形者为上品,真伪新旧均有考证。每鼓或锣之价,可值数牛至十余牛不等。若有四虾蟆以上者,则非百牛不办矣。
武器
时武器尚弓矢,以木为弓,以藤竹为弦,铁簇无羽而有钩,中者辄入骨不能拔。苗人则用弩箭,以毒药敷箭端,中者必死。清末火器渐次流入,弓矢之用日见减少,所用前膛枪、大急枪,有力者家置一杆至数杆不等。此项枪枝黎人不能自制,必向外间购买,每枪一杆及子弹若干以数牛易之。出入携带,弹鸟击兽,习成惯技,发必有中。其出入之径路有数处,就中以岭门及白沙方面为交通较便,来往极众。
丧葬
四黎之中,苗俗多用火葬风葬,黎、伎、侾则用土葬。棺用佳木,而各地形式不同。有刳整木为棺者,有以板为之者。有掘地作长方形,而于上下四方列板为墙,置尸其中,以土掩盖者。倘人死而棺木未备,则由其亲属入山访佳木,而陈尸室中而待,迟至十余日不能葬。亲死不哭,准食生牛肉以表哀痛。第八日奠祭,名曰“作八”。邀亲戚中熟悉死者之历史者一二人,报告死者之祖先及其本身经历,与债权务关系,俾众周知。远近男女亲戚,必以牛、羊、酒、米、纸灯、鼓吹来奠。礼毕聚饮。每逢亲死,辄留祭牛顶角,悬钉柱端,以作纪念。悬角多者,表示家世甚旧。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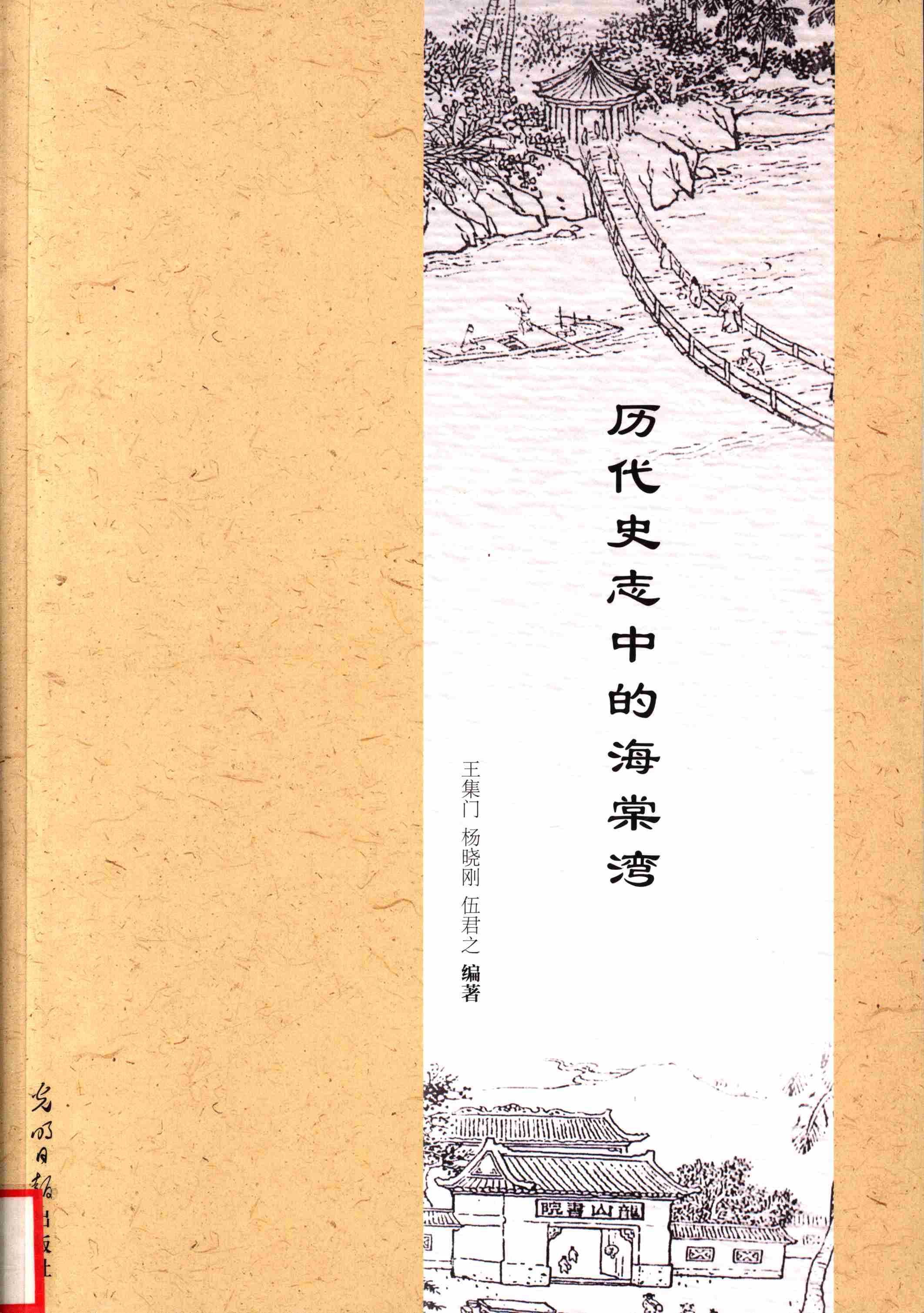
《历代史志中的海棠湾》
出版者:光明日报出版社
《历代史志中的海棠湾》,是对历朝历代正史及地方志书中涉及海棠湾的地理历史事实进行辑录。编辑原则包括涉及海棠湾的一切相关内容均要辑录,对于重复内容视情况删减,以整个三亚的史事为线索突出海棠湾的史事,不选择创作而是编辑历史书籍内容。本书按人文地理、手工业、工业、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商贸、旅游业、教育、文化、民族关系、人物、艺文等篇章分门别类进行编排。所辑录的史料加上现行标点符号,一律改用现行简化字。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