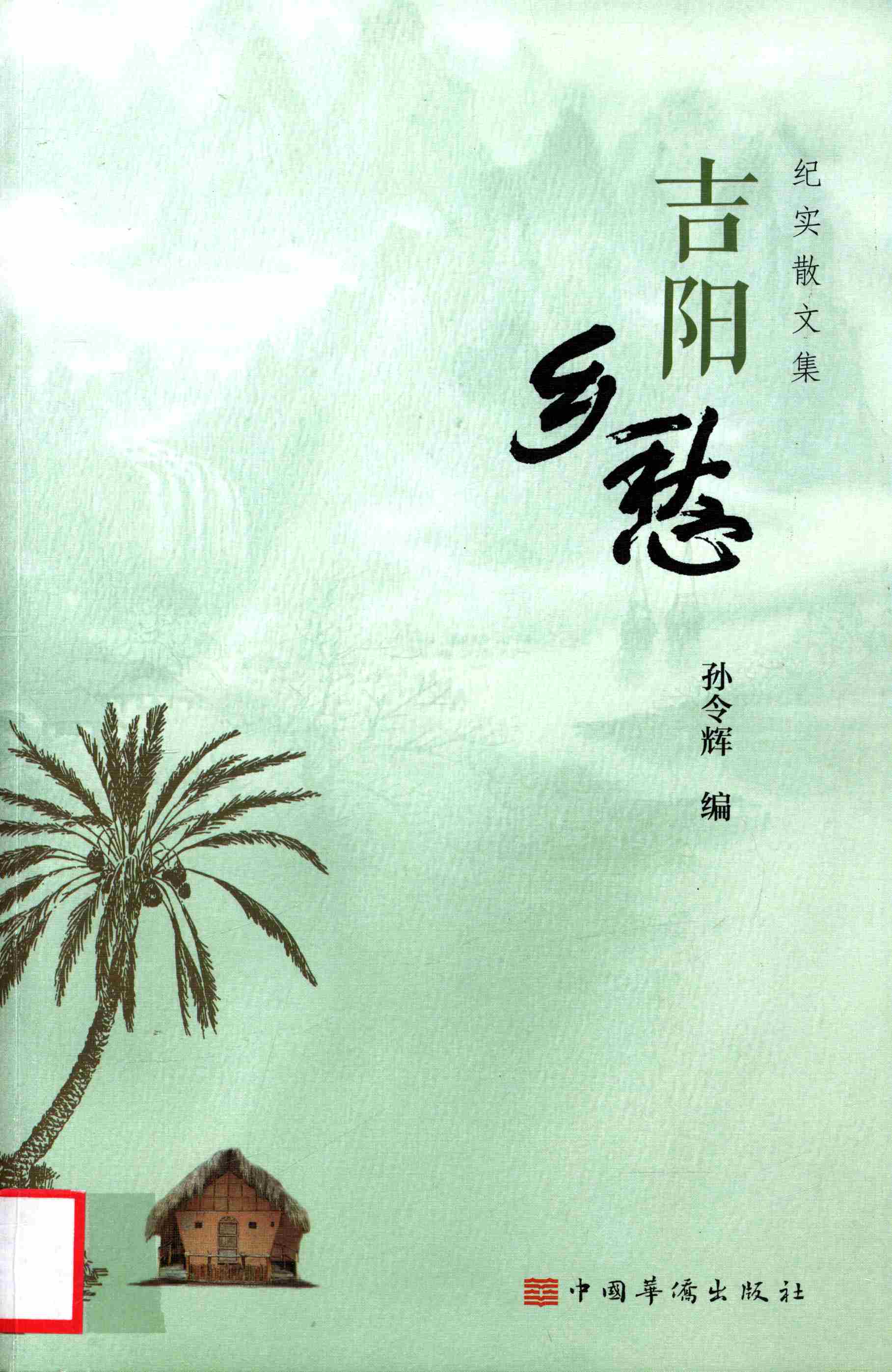内容
黄泥岭的记忆
吴强
位于三亚市吉阳区东南的黄泥岭山麓脚下,有个世外桃源般的小山村——田独村。这里有炊烟接青天,落日下云涌的山水迷人景色,更有黎歌四溢的醉人风情。
村落环山倚水,座落在市级水源保护区颂和水库库区边。随着弯弯曲曲的碎石小路,一座陡峭的山崖耸立在面前,这就是黄泥岭。山中云雾缭绕,绿树红花,一阵阵花香扑鼻而来,弯曲舒展的小溪从山谷中汇入水库,那淡淡的水雾,如薄薄的轻纱,在夕阳的映照下,像一条绿色的绸带,明镜一样的水面顿时漾起了一道道波纹。小溪边草地上开着五颜六色的野花,一到山下,就嗅到那芳香扑鼻的香味,仿佛走进了童话般的梦幻世界。碧蓝的天空点缀着几朵云彩,蓝天白云、青山绿水组成了一幅优美的画面。
当绯红的晚霞在天边渐渐褪尽后,夜色朦胧的面纱笼罩着大地,远处的灯开始跳入眼帘。灯光在迷离的夜雾里像眼睛一闪一闪的,重叠在一起连成了一簇,合成一片,一会工夫,整个村落变成一片闪烁的光海,让人眼花缭乱。千变万化的灯把新农村的夜装饰得如此妩媚,沿着鹅卵石小路,这带着光的库区,那披着光的山岭,诠释了田独村现有的繁华。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楼,是黎家蒸蒸日上二的写意;是全体村民在村委会班子的带领下,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的幸福。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黄泥岭山麓下的田独村,同样是人杰地灵的好地方,每每谈论起人物,村民们都会竖起拇指,津津乐道地说起刘保乐家庭的故事。
在村里堪称是邻里和睦的好家庭,刘保乐家庭并不富裕,夫妇平时省吃俭用,勤勤恳恳地工作赚钱,供在广东读大学的女儿学费。但是,当看到周围哪家有困难,都会极力帮助他们。住在村头的一位大姐,是村里的贫困户,家里没有稳定的收入,生活困难。有一次她生病了,医疗费开销很大。当刘保乐知道这件事后,把平时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550元帮她垫付了医疗费。村里帮他们申请低保,但总是被刘保乐婉言谢绝,他说自己还有能力工作赚钱,养活家庭,把低保留给更需要的人。村里平时只要谁家有小事大事,谁家结婚摆酒的、丧事的、盖房子的都叫他,他都会尽力帮忙。刘保乐乐于助人的品行,受到大家的敬重。刘保乐是个有头脑的人,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爱动脑子,喜欢接受新鲜事物和新知识,平时闲着的时候,就到村文化室去借与农业有关的科普书籍来看。在参加了市送文化下乡的活动中,他学到了创业理论技巧和蔬菜瓜果的种植技术。他开始利用自己的一亩多田地种植青瓜和豆角,赚了一些钱,维持家里的日常开销和支付孩子读书的费用。刘保乐一家也热心公益事业,女儿在学校里时常参加志愿者活动,去海边拾垃圾,去敬老院照顾孤寡老人等。刘保乐家庭尊老爱幼,家庭和睦,热爱公益事业,有爱心,深受村民们的爱戴,是新时代涌现出来的模范家庭。
新农村的时代变迁,让人刮目相看,山岭后的风景,令人流连忘返。黄泥岭岁月记忆中,也留下一段抹不去的历史悲情。殊不知,它曾经历过6年的生死磨砺;殊不知,它也曾受到人间炼狱般的苦难。田独村最为出名的,便是闻名已久的铁矿万人坑。这里是田独铁矿旧址,现存直径300米、深50米的矿井运矿矿桥、日军营房、仓库等。离矿井东50米有一片长约100米、宽50米的坡地,掩埋着当年劳苦矿工的累累白骨。这就是日寇侵华掠夺资源杀害同胞的历史见证。1939年2月,日军侵占海南岛,发现田独铁矿资源,日本政府便授命“石原株式会社”投资开发。通过敌伪机关的合证公司,在上海、广州、香港、澳门、汕头、厦门等沦陷城市,采取强迫、诱骗手段,据不完全统计,先后从大陆各地抓来有68批,每批300—500人,共有两万五千余人。日寇掠夺田独铁矿6年中,病死、饿死、打死、烧死、活埋、枪毙的矿工数以万计。
田独万人坑,是日军侵华时期杀害和奴役近万名矿工的罪恶遗址。1986年,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田独万人坑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海南建省后,三亚市人民政府列为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这里已成为阶级斗争、民族解放斗争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活教材。
黄泥岭见证了这段历史,同样见证田独村的华丽转身,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互融合,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相互碰撞,诠释了“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心境。如果想达到新的高度,领略山岭后的风景,那么请翻越这座山岭,让苍劲顽强的树,峥嵘林立的石,变幻莫测的风,澄清洁净的云,构成黄泥岭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画卷!山麓脚下田独村这颗深埋的明珠终于发出璀璨的光芒。
田独万人坑
孙令辉
一天,凭《请把窗户打开》《阿婆的槟榔》《陵水谣》等影片,获国内外奖项的导演江流打电话给我,说对“田独万人坑”感兴趣,要创作一部小说,拍一部电影,需要了解相关史实。这通电话着实让我感动,但我对这段历史知之甚少,趁此机会邀请江导、田独村苏书记等一起,来了一次田野调查。
吉阳区田独村颂和路、新红路、福海苑二路三岔路口,两排民居逼仄出一块尺形空地,“田独万人坑”就坐落在这块空地上。空地不大,被一条砖墙围挡。与民居并排的西墙,开了一个小门,“田独万人坑简介”“海南省文物保护单位——田独万人坑”花岗岩牌匾分立两侧。空地内有一新一旧、一高一矮两座碑。新碑正对小门,高8米,白色碑身镌刻“田独万人坑死难矿工纪念碑”12个大字,系三亚市人民政府2001年修建。新碑左侧,一座约2米高、水泥浇筑的旧碑,上刻“日寇时期受迫害死亡工友纪念碑”,为海南铁矿田独矿区1958年4月5日立。空地寂寥,碑石无言,芳草萋萋。碑前遗存一些残香剩烛、枯干花束,说明这里有人常来祭拜。人们没有因年代远去而忘却这段往事,让这个孤寂的荒冢多了些许人性的温度。
我们来到一个黄土坡,站在坡上环顾四周,东南边一抹青山连绵起伏,北面是水库和村庄,西面新建安置区高楼林立。坡下一个深深的水塘,墨绿色的水面比一个足球场还大。苏书记指着水塘,说这里原叫独田岭,与黄泥岭、竹落岭相连。独田岭蕴藏铁矿,日军侵占三亚后对其大肆开采,整个山岭被挖成了深水塘。在水库边,当年日军修筑的碉堡残迹尚存。苏书记介绍,颂和水库就是万人坑遗址。20世纪50年代,村民挖土造坝,挖出一堆白骨,后来,驻地部队又挖了好多天,挖出来的白骨摆满了整个坡地,令人毛骨悚然
“田独万人坑,是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日寇奴役和杀害近万名矿工的罪恶遗址。在日寇掠夺田独铁矿的六年中,一大批被抓自朝鲜、印度、台湾、香港等地和我省各市县的劳工先后在这里被折磨和劳役致死,现颂和水库范围就是当年掩埋死难矿工的地方。”
“田独万人坑简介”文字虽少,但字字沥血。每一个字,仿佛一只只惊恐、怨恨的瞳眼,发着幽幽的绿光。为了进一步整理这段历史,我们开始了多方的寻访。
据《崖州志》载:“独田岭,在榆林港西南铁炉坡。上有石高三尺,广五尺,刻龟蛇图,详《金石》……岭东南面蕴藏丰富的铁矿石,这里有个小黎村,村名为田独”田独有铁矿,我们祖先早探明,且尝试过开挖,未果。日军1939年2月侵占三亚,8月份便对该铁矿进行开采,可见,日本人对田独,甚至海南岛矿产资源相当了解,觊觎已久。这在日本人编著的《海南岛》(台湾总督府调查课)、《海南岛读本》(南支调查会)、《实用海南岛指南》(日本东亚地理调查会)等书籍均有记载,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譬如,对田独铁矿的描述很详细:“位于崖县三亚红泥岭靠近榆林港的田独村,品位优质,且水运便利,经营条件好。”
《三亚史》载,田独铁矿蕴藏量约500万吨,日本石原株式会社分三期开采,从1939年8月至1944年1月共盗矿270万吨。这一数据出自日本大藏省管理局编印的《关于日本人在海外活动的历史调查——海南岛篇》(第122—123页)。期间,日军修建一条石碌至三亚铁路,通过这条交通线源源不断地将从田独和石碌掠夺的矿石,经安由港装船载往日本。
昌江石碌铁矿档案室现存日本人河野司编著的《海南岛石碌铁山开发志》孤本。河野司系日本侵华时期在石碌开矿负责人,1982年6月19日,他带领日本旅行团一行20人,由海南区外事办唐科长陪同参观石碌铁矿,将该书赠送铁矿档案室。书中大量文字、图片,其中一部分是关于田独铁矿的,都是日本人在海南岛犯下滔天罪行的实证。
在海南省党史研究室,《海南铁矿劳工口述史》《海南省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等史料,阅后令人触目惊心,义愤填膺。从上海、广东、台湾、香港、澳门、朝鲜等沦陷区以及海南本岛,诱骗或强制征用的劳工,被关在集中营一样的茅屋里,囚徒一般被日军、工头押着从事种种繁重体力劳动。随意毒打、折磨、刑罚甚至处死的惨状,穿越八十多年时光隧道,电影蒙太奇般浮现在眼前。能逃脱日军魔掌的劳工,至今皆先后故去了。据一位已故老矿工朱恩留下的口述记录:1942年底,他从香港来田独铁矿,同来的一共有530多人,到了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仅剩37人。田独村二组村民李永光,他的父亲就是田独铁矿的一名劳工。李永光小时候常听父亲讲述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并且铭记于心。得知我们的来意,近90岁的老人李永光,挥动那因岁月侵蚀而发抖的双手,欲说不能,声泪俱下,泣不成声。
寻访得知,“田独万人坑”仅仅是日军侵琼制造的惨绝人寰的一处墓坑。《海南省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记载,日军在海南岛制造的惨案、血案213桩,“万人坑”“千人墓”“百人墓”等有18处,被夷为废墟的“无人村”有476个。日军在田独铁矿采矿6年之久,被枪杀、活埋、烧死、打死和饿死、病死的劳工共计1.2万人。距离田独村不远的南丁村,有一座朝鲜人墓坑,埋葬的就是当年田独铁矿惨死的朝鲜籍劳工。后来一韩国商人将“墓坑”遗址建成“中国海南岛朝鲜人慰灵墓”,立碑刻字,每年都有一批韩国人来这里凭吊,追忆亲人,寄托哀思。
重提旧事,控诉罪恶,不是为了激起仇恨;铭记历史,不忘过去,方能让亡魂安息,让后人砥砺前行。将致力于“田独万人坑纪念园”的推进工作,使之成为一处教育基地,还历史于朗朗乾坤。
田独铁矿,一段无法忘却的记忆
王娜
灰色,这里到处是灰色。
灰色的门,灰色的路,灰色的草,围着那灰色的碑。
碑上有文:田独万人坑死难矿工纪念碑。
1939—1945。
1939年2月,侵华日军从琼州海峡北部的滘尾湾出发,穿过海峡进入三亚湾,先后占领三亚街、三亚港、榆林、崖州。位于榆林港东北12公里处的田独铁矿,进入日军视线。
一年前,1937年隆冬,亚太地区的一个中心城市,距离田独2000多公里的六朝古都南京,爆发了大屠杀。
一年后,1940年早春,东欧的一个小城,距田独7000多公里,在波兰最美丽的古城克拉科夫一侧,只有4万人的奥斯维辛,开始了变成承载400多万条生命的炼狱之路。
再从奥斯维辛一路向东,穿过燃烧在二战战火中的欧亚大陆,回到热带岛屿海南的最南端。这里比冬无严寒、夏无酷热的波兰更加舒适宜人。这里富含露天铁矿的小镇田独,也笼罩在了血色之中。
一艘艘船,在夜幕中卸下了它的乘客——一队又一队的青壮年;一辆辆车,卸下了它的乘客——同样是一队队的青壮年。
他们从广东、香港、台湾、东南亚、朝鲜、印度……从澄迈、乐东、陵水、三亚、田独……来到这片丛林环绕、充满热带风情的土地。有人以为正如招工时承诺的一般,可以“一年之后,合同期满,送回原籍”,他们或许可以注意到这是个美丽的地方,而更多的人,则是被抓而来,在他们眼中,一切都是灰色的恐惧……
这些都是七十多年前的旧事了,被囚于此的矿工们掘矿时扬起的绝望烟尘,早已在过往消散殆尽。
而今,久居三亚的人们,可能并不知晓,沿着熟悉的榆亚路到吉阳大道行进至亚龙湾站路口,右转进田独路后,在颂和水库旁,有这样一个死神曾无数次残酷降临的地方,一个上万名矿工命失于此的地方。
这是一段远去的记忆,正如纪念碑旁的丛丛冬日枯草一样,已从血色变成了灰色,再慢慢变成透明的颜色
当并未忘记这段记忆的人们来到这里,局促的砖墙在四面围挡,外侧是自建民居房和小小的饭店,寂寞的枯草在地上默默生长,越过四围砖墙铺盖下来的是枯黄的芭蕉叶,萧瑟。这萧瑟,促使着人们去追溯身边的这份灰色的沉重。
田独铁矿,据《三亚市志》记载:位于田独村东黄泥岭西北山麓,总储量500万吨左右,工业品位高达63%,有害成分很小,属优质铁矿。
铁矿石,维持战争机器的重要资源,可以生产钢材,用于造船、枪械、坦克、大炮……资源匮乏的日本,在美国为控制其在东南亚扩张采取了系列资源禁运之后,更加急于寻找资源支持。
田独铁矿,开始被掠夺性开采。
对矿,是毁灭性开采;对人,同样是毁灭性利用。
可能,已经没有“人”了,无数更甚动物世界的杀戮在每天上演。
所以这座铁矿曾被叫作红山矿,因为“满山满地的血红色,整座山都是血腥味。”一位见证人这样讲述。
今天,人们站在蓄满水的巨大矿坑旁,周围是草地、山林和高楼,恍惚以为这是个鱼塘、这是个小小的湖。微风拂过,舒适惬意,却不知这足有50米深的水底,曾有过多少无辜矿工的哀泣,这许多的水,是否是他们泪聚而成。
那无数绝望的血泪中,可能只有一个小小的期望——能如动物一般活着就好。这是奢望,到1945年被光复时,达到这个小小期望的幸存者已寥寥。
据史料记载,日本海南海军特务部从各地强抽一大批青壮年男子到田独、石碌等矿区充当各种苦役。这些矿工每天要干14个小时重活,规定每天每人挖矿石8吨,完不成任务不给饭吃,还要遭受毒打。沉重的苦役折磨着矿工,忍受不了而逃跑的被抓回来后立即枪毙,病了的被活埋,患传染病的被抬出去活活烧死。从1940年日本开始盗采铁矿到1944年1月因盟军飞机封锁海域难以运出而停产,四年多的时间里,累死、病死、饿死、烧死、活埋、枪毙的矿工近万人,矿山共计被盗掘约270万吨。
如此,能如动物一般活着就好。
7000公里外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在1945年被苏联红军解放后,幸存者们并无欢呼激动,“绝大部分被解放的人,都是一脸茫然。然后有的人就趴在地上,一路攀爬,站不起来。”奥斯维辛幸存者、意大利籍化学家和作家普利莫·莱维,在《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一书中如此描述和记载。
他说,所有从那个集中营活过来的人,都觉得有一种洗刷不去的耻辱感。原因之一,就是那是一段动物般的不能称为“人”的日子。
动物一般地活着,随时都会死去,这是什么样的感觉?
如今的人们都知道为“人”的感觉。自由安心地走在街头,吃想吃的东西,去想去的地方,见想见的人,我们可能已经超越了马斯洛人类需求五层次理论中的生存和安全需求,开始在尊重和自我实现的层面苦苦追寻。
可怕的和痛苦的记忆,是安心生活中难以触碰的角落,也终会变为面目不清的模糊灰色。只是,打开搜索引擎就可看到的那些遍布中国数不清的“万人坑”和惨案,在这矿坑,在老铁路,在八所、屯昌、万福村、天烛坡、石马村等地方,还留着深深伤痕。
当我们走过田独死难矿工的纪念碑,走过碑侧村民们留下的根根残香,在地球另一侧的华盛顿,每年有200万人走过被称为美国“哭墙”的黑色大理石越战纪念碑;在侵华口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每年有逾800万人走过长长的“哭墙”;在德国柏林大屠杀纪念馆,孩子们在2711块水泥墩组成的迷宫方阵间奔跑,大人们在石碑间沉思;在奥斯维辛殉难者纪念博物馆,每年亦有200多万人走过……
田独死难矿工纪念碑所象征和所代表的,其实是人们美好生活中的另一种重量,是三亚不该忘记的那些事情中的重要一页。
所以请记住,在这椰风海韵中,还有这个承载着无限沉重的小小角落。
田独万人坑的劳工祭
吴强
越过时间和山水,我们来到这里,沿着一级一级台阶,向前寻找。长揖,敬献,表达忆念和告慰,脚下的这方厚重而实在的土地里,许多人深埋于斯,己近百年。历史的寻踪,是一抹凄惨的光影,是一朵凋残的野花,曾经的呐喊、呻吟演绎着颠沛流离、血泪悲情的劳工祭。
时光回到那年,一个承载负重和艰辛、苦难和眼泪,深含绝望和忧伤的黑暗年代。1939年1月13日,日本天皇不顾国际公法,召开卫前会议作出侵占琼崖的决定,1月19日,发布攻陷海口及附近重要地域的命令。从2月3日起,日本陆海空军入侵海南岛领海领空,2月10日占领海口,2月14日凌晨占领三亚、榆林。火光、血、沉闷的滚雷、啸叫的风、淫雨,如墨低垂的浓云,及满山的哀歌和悲哭,没有人不会簌簌地发抖。踏进了由鲜血和骸骨汇成的血水中,不断泛起带有骷髅花纹的气泡,踏起的烟尘,越来越近。
日军占领海南岛之后,便加速对海南岛资源的掠夺,他们迫不及待地派海军特务部北浦大佐带领工程技术人员进行海南岛资源勘探,发现了优质的田独铁矿。日本海南株式会社和石原株式会社通过敌伪机关的合证公司,从朝鲜、香港、印度,还有海南岛各县的汉族、黎族青壮年,采取强迫诱骗的手段先后抓来在田独、安由地区开采矿石及各种苦役的劳工有一万多人。这些劳工,似沙丘中的蚂蚁,沉溺于沙海中,重压下精神萎缩和意志溃散,尝尽了人生的苦头。日寇在田独村东南侧约数百米处的一片平坦荒坡上,建有20幢用茅草竹木搭起排列成行的大工棚。工棚里用竹子捆扎了两排对称的大通铺,每幢住劳工200名,编为4个班。月光混着煤油灯透过茅屋间隙染进来,乌黑斑驳的霉点布满整个工棚,充满陈腐霉味。每个人深陷灰气,人间的哀乐,曾在里面浮游。阴暗与悲凄的命运,那是心灵的腐烂,悲剧在浑然不察中上演。
遍野都是丛生的荆棘和树木,远处群山的倒影、朝霞和夕阳,还有满天星斗,抬起头,极目而望,是生生不息的大地阡陌,一切美丽丰绕的家园,充满灵感和梦想,而如今灾祸、野蛮、暴虐开始了。从此,客死他乡,再也回不去,故乡不可见,云水空如一。日寇把所有劳工集中在田独的矿山上,放火烧山,清除残枝,开始挖矿石,装运矿石。每天劳动时间长达14个小时,每天的伙食就两个饭团,几只发烂的咸鱼仔。因吃不饱,跑不动,常被日本监工打得皮开肉绽。劳工们被蹂躏得伤痕累累,受尽屈辱,留下恐惧,令人战栗,用无法言喻的惊心动魄,在哀鸣里得以残存。
多少人想从夜幕里偷出一条回乡之路。在田独铁矿当劳工的,有些人忍受不了日军监工的棍棒毒打,只得想办法逃脱虎口。1942年4月间,保亭县一位黎族劳工,因不堪忍受日军监工的毒打,所以就乘机逃跑。不幸被日军监工追捕逮住了,押至一片荒坡上,挖了一个大土坑,驱赶所有的劳工都前来这里观看日军监工对这位逃亡的劳工行刑。荒草沿路蔓生,周围是深陷于地平线下的广袤荒地,越陷越深的坡,好像走在世界尽头,一切都安静极了。天是空旷遥远的灰色,一个粗暴野蛮的日本监工,手中的刀在军裤上来回摩擦,眯着小眼,把刀举在空中,薄薄的刀刃在阳光下闪着精光,面目狰狞,暴躁又狂野地逼视眼前的劳工,狠狠地往他的脖子砍去。头颅立即滚落地上,鲜血像喷泉一样从断颈处喷出来,鲜血汩汩流出,染红了路边的无名草。劳工们都被惊吓得呆若木鸡,浑身发抖。像晴空炸响霹雳,心被劈开一刀,瞥见深渊的恐惧,好似汹涌的大河里漂流了漫长的岁月,终于被波浪冲到沙滩上,有些眩晕,有些漂浮,回忆梦的最后一幕。
这是一群十足的弱者,一个悲剧的角色,遭受欺凌、屈辱和不公,亳无尊严可言,虽然反抗,也会变得无可奈何。惨遭日寇荼毒,新鬼嚎哭,世道黑暗,余生只好如飞鸟一般无枝可依,夺我魂魄,苟全于奔走之间,去沉默地流下热泪。
野蛮不仅仅指劳工营的杀戮,更是充满惨绝人寰的侵略性。日寇每天上午把已咽气或未咽气的劳工全部堆叠其上,再铺满干木柴,浇上汽油,点火烧尸,臭气四处横溢。未咽气的劳工哀号不绝,一名未咽气的广东劳工,被日军监工抬进焚人坑里焚烧时,衣衫褴褛的他惨叫一声从焚人坑里跳出来,又被监工抓住再投扔进熊熊的大火里,只剩下一副光秃秃的骨架。他发出的惨叫声使人毛骨悚然,尖叫声伴着尘土混成一团,瞳孔无声明灭,仿佛笼罩全世界所有暗影,如宣纸一滴淡墨留存长久。那天大雨滂沱,窒息如影随形,一盏独自闪耀在漆黑夜晚的煤油灯,在疯长的杂草乱藤里,照出面目可憎、行同狗豨的日本人。那一坑留下的悲伤和泪水,那些在屠刀下悄无声息的死亡,只有亲历者才能明白。一生如此,犹如在黑暗深处寻找光明,犹如夏虫趋光向它奔去,一生都试图进入生活的纵深,试图与群体平等交流,发出人生有死,若死得其所,夫复何恨!
劳工们吃的是猪狗饭,干的是牛马活,住的是破顶断壁的茅草棚,睡的是竹架分成两层通连的太平铺,穿的是破麻袋和浑灰纸袋,每天要干14小时的重活,规定每天每人挖8吨矿石,完不成任务不给饭吃,还要遭受毒打。沉重的苦役,折磨着这些累死累活的劳工,致使他们经常昏倒在工地;忍受不了逃跑的被抓回来打得死去活来;病了的当作怠工,不给医治,活活埋掉;患上痢疾或症疾说是传染病,抬出去活活烧死,烧不完的尸骸被狗噬、兽咬、鸟啄,残骨遍野,臭气熏天,惨不忍睹。日本侵略者恃强凌弱,开采田独铁矿6年多,被抓来服苦役而病死、饿死、烧死、活埋、枪毙的矿工有一万人之多他们统统被埋在田独铁矿附近的一块矿地上,这里后人称之为“万人坑”(现今的颂和水库里,因水库蓄水,焚人坑被大水淹没)。
1958年4月,为纪念被日军迫害死亡的田独铁矿劳工,由海南铁矿田独矿区在田独村东侧颂和水库大坝旁,用水泥砌筑一座“日寇时期受迫害死亡工友纪念碑”黄泥岭不会忘记,那碑上的劳工祭文。
吴强
位于三亚市吉阳区东南的黄泥岭山麓脚下,有个世外桃源般的小山村——田独村。这里有炊烟接青天,落日下云涌的山水迷人景色,更有黎歌四溢的醉人风情。
村落环山倚水,座落在市级水源保护区颂和水库库区边。随着弯弯曲曲的碎石小路,一座陡峭的山崖耸立在面前,这就是黄泥岭。山中云雾缭绕,绿树红花,一阵阵花香扑鼻而来,弯曲舒展的小溪从山谷中汇入水库,那淡淡的水雾,如薄薄的轻纱,在夕阳的映照下,像一条绿色的绸带,明镜一样的水面顿时漾起了一道道波纹。小溪边草地上开着五颜六色的野花,一到山下,就嗅到那芳香扑鼻的香味,仿佛走进了童话般的梦幻世界。碧蓝的天空点缀着几朵云彩,蓝天白云、青山绿水组成了一幅优美的画面。
当绯红的晚霞在天边渐渐褪尽后,夜色朦胧的面纱笼罩着大地,远处的灯开始跳入眼帘。灯光在迷离的夜雾里像眼睛一闪一闪的,重叠在一起连成了一簇,合成一片,一会工夫,整个村落变成一片闪烁的光海,让人眼花缭乱。千变万化的灯把新农村的夜装饰得如此妩媚,沿着鹅卵石小路,这带着光的库区,那披着光的山岭,诠释了田独村现有的繁华。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楼,是黎家蒸蒸日上二的写意;是全体村民在村委会班子的带领下,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的幸福。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黄泥岭山麓下的田独村,同样是人杰地灵的好地方,每每谈论起人物,村民们都会竖起拇指,津津乐道地说起刘保乐家庭的故事。
在村里堪称是邻里和睦的好家庭,刘保乐家庭并不富裕,夫妇平时省吃俭用,勤勤恳恳地工作赚钱,供在广东读大学的女儿学费。但是,当看到周围哪家有困难,都会极力帮助他们。住在村头的一位大姐,是村里的贫困户,家里没有稳定的收入,生活困难。有一次她生病了,医疗费开销很大。当刘保乐知道这件事后,把平时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550元帮她垫付了医疗费。村里帮他们申请低保,但总是被刘保乐婉言谢绝,他说自己还有能力工作赚钱,养活家庭,把低保留给更需要的人。村里平时只要谁家有小事大事,谁家结婚摆酒的、丧事的、盖房子的都叫他,他都会尽力帮忙。刘保乐乐于助人的品行,受到大家的敬重。刘保乐是个有头脑的人,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爱动脑子,喜欢接受新鲜事物和新知识,平时闲着的时候,就到村文化室去借与农业有关的科普书籍来看。在参加了市送文化下乡的活动中,他学到了创业理论技巧和蔬菜瓜果的种植技术。他开始利用自己的一亩多田地种植青瓜和豆角,赚了一些钱,维持家里的日常开销和支付孩子读书的费用。刘保乐一家也热心公益事业,女儿在学校里时常参加志愿者活动,去海边拾垃圾,去敬老院照顾孤寡老人等。刘保乐家庭尊老爱幼,家庭和睦,热爱公益事业,有爱心,深受村民们的爱戴,是新时代涌现出来的模范家庭。
新农村的时代变迁,让人刮目相看,山岭后的风景,令人流连忘返。黄泥岭岁月记忆中,也留下一段抹不去的历史悲情。殊不知,它曾经历过6年的生死磨砺;殊不知,它也曾受到人间炼狱般的苦难。田独村最为出名的,便是闻名已久的铁矿万人坑。这里是田独铁矿旧址,现存直径300米、深50米的矿井运矿矿桥、日军营房、仓库等。离矿井东50米有一片长约100米、宽50米的坡地,掩埋着当年劳苦矿工的累累白骨。这就是日寇侵华掠夺资源杀害同胞的历史见证。1939年2月,日军侵占海南岛,发现田独铁矿资源,日本政府便授命“石原株式会社”投资开发。通过敌伪机关的合证公司,在上海、广州、香港、澳门、汕头、厦门等沦陷城市,采取强迫、诱骗手段,据不完全统计,先后从大陆各地抓来有68批,每批300—500人,共有两万五千余人。日寇掠夺田独铁矿6年中,病死、饿死、打死、烧死、活埋、枪毙的矿工数以万计。
田独万人坑,是日军侵华时期杀害和奴役近万名矿工的罪恶遗址。1986年,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田独万人坑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海南建省后,三亚市人民政府列为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这里已成为阶级斗争、民族解放斗争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活教材。
黄泥岭见证了这段历史,同样见证田独村的华丽转身,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互融合,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相互碰撞,诠释了“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心境。如果想达到新的高度,领略山岭后的风景,那么请翻越这座山岭,让苍劲顽强的树,峥嵘林立的石,变幻莫测的风,澄清洁净的云,构成黄泥岭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画卷!山麓脚下田独村这颗深埋的明珠终于发出璀璨的光芒。
田独万人坑
孙令辉
一天,凭《请把窗户打开》《阿婆的槟榔》《陵水谣》等影片,获国内外奖项的导演江流打电话给我,说对“田独万人坑”感兴趣,要创作一部小说,拍一部电影,需要了解相关史实。这通电话着实让我感动,但我对这段历史知之甚少,趁此机会邀请江导、田独村苏书记等一起,来了一次田野调查。
吉阳区田独村颂和路、新红路、福海苑二路三岔路口,两排民居逼仄出一块尺形空地,“田独万人坑”就坐落在这块空地上。空地不大,被一条砖墙围挡。与民居并排的西墙,开了一个小门,“田独万人坑简介”“海南省文物保护单位——田独万人坑”花岗岩牌匾分立两侧。空地内有一新一旧、一高一矮两座碑。新碑正对小门,高8米,白色碑身镌刻“田独万人坑死难矿工纪念碑”12个大字,系三亚市人民政府2001年修建。新碑左侧,一座约2米高、水泥浇筑的旧碑,上刻“日寇时期受迫害死亡工友纪念碑”,为海南铁矿田独矿区1958年4月5日立。空地寂寥,碑石无言,芳草萋萋。碑前遗存一些残香剩烛、枯干花束,说明这里有人常来祭拜。人们没有因年代远去而忘却这段往事,让这个孤寂的荒冢多了些许人性的温度。
我们来到一个黄土坡,站在坡上环顾四周,东南边一抹青山连绵起伏,北面是水库和村庄,西面新建安置区高楼林立。坡下一个深深的水塘,墨绿色的水面比一个足球场还大。苏书记指着水塘,说这里原叫独田岭,与黄泥岭、竹落岭相连。独田岭蕴藏铁矿,日军侵占三亚后对其大肆开采,整个山岭被挖成了深水塘。在水库边,当年日军修筑的碉堡残迹尚存。苏书记介绍,颂和水库就是万人坑遗址。20世纪50年代,村民挖土造坝,挖出一堆白骨,后来,驻地部队又挖了好多天,挖出来的白骨摆满了整个坡地,令人毛骨悚然
“田独万人坑,是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日寇奴役和杀害近万名矿工的罪恶遗址。在日寇掠夺田独铁矿的六年中,一大批被抓自朝鲜、印度、台湾、香港等地和我省各市县的劳工先后在这里被折磨和劳役致死,现颂和水库范围就是当年掩埋死难矿工的地方。”
“田独万人坑简介”文字虽少,但字字沥血。每一个字,仿佛一只只惊恐、怨恨的瞳眼,发着幽幽的绿光。为了进一步整理这段历史,我们开始了多方的寻访。
据《崖州志》载:“独田岭,在榆林港西南铁炉坡。上有石高三尺,广五尺,刻龟蛇图,详《金石》……岭东南面蕴藏丰富的铁矿石,这里有个小黎村,村名为田独”田独有铁矿,我们祖先早探明,且尝试过开挖,未果。日军1939年2月侵占三亚,8月份便对该铁矿进行开采,可见,日本人对田独,甚至海南岛矿产资源相当了解,觊觎已久。这在日本人编著的《海南岛》(台湾总督府调查课)、《海南岛读本》(南支调查会)、《实用海南岛指南》(日本东亚地理调查会)等书籍均有记载,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譬如,对田独铁矿的描述很详细:“位于崖县三亚红泥岭靠近榆林港的田独村,品位优质,且水运便利,经营条件好。”
《三亚史》载,田独铁矿蕴藏量约500万吨,日本石原株式会社分三期开采,从1939年8月至1944年1月共盗矿270万吨。这一数据出自日本大藏省管理局编印的《关于日本人在海外活动的历史调查——海南岛篇》(第122—123页)。期间,日军修建一条石碌至三亚铁路,通过这条交通线源源不断地将从田独和石碌掠夺的矿石,经安由港装船载往日本。
昌江石碌铁矿档案室现存日本人河野司编著的《海南岛石碌铁山开发志》孤本。河野司系日本侵华时期在石碌开矿负责人,1982年6月19日,他带领日本旅行团一行20人,由海南区外事办唐科长陪同参观石碌铁矿,将该书赠送铁矿档案室。书中大量文字、图片,其中一部分是关于田独铁矿的,都是日本人在海南岛犯下滔天罪行的实证。
在海南省党史研究室,《海南铁矿劳工口述史》《海南省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等史料,阅后令人触目惊心,义愤填膺。从上海、广东、台湾、香港、澳门、朝鲜等沦陷区以及海南本岛,诱骗或强制征用的劳工,被关在集中营一样的茅屋里,囚徒一般被日军、工头押着从事种种繁重体力劳动。随意毒打、折磨、刑罚甚至处死的惨状,穿越八十多年时光隧道,电影蒙太奇般浮现在眼前。能逃脱日军魔掌的劳工,至今皆先后故去了。据一位已故老矿工朱恩留下的口述记录:1942年底,他从香港来田独铁矿,同来的一共有530多人,到了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仅剩37人。田独村二组村民李永光,他的父亲就是田独铁矿的一名劳工。李永光小时候常听父亲讲述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并且铭记于心。得知我们的来意,近90岁的老人李永光,挥动那因岁月侵蚀而发抖的双手,欲说不能,声泪俱下,泣不成声。
寻访得知,“田独万人坑”仅仅是日军侵琼制造的惨绝人寰的一处墓坑。《海南省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记载,日军在海南岛制造的惨案、血案213桩,“万人坑”“千人墓”“百人墓”等有18处,被夷为废墟的“无人村”有476个。日军在田独铁矿采矿6年之久,被枪杀、活埋、烧死、打死和饿死、病死的劳工共计1.2万人。距离田独村不远的南丁村,有一座朝鲜人墓坑,埋葬的就是当年田独铁矿惨死的朝鲜籍劳工。后来一韩国商人将“墓坑”遗址建成“中国海南岛朝鲜人慰灵墓”,立碑刻字,每年都有一批韩国人来这里凭吊,追忆亲人,寄托哀思。
重提旧事,控诉罪恶,不是为了激起仇恨;铭记历史,不忘过去,方能让亡魂安息,让后人砥砺前行。将致力于“田独万人坑纪念园”的推进工作,使之成为一处教育基地,还历史于朗朗乾坤。
田独铁矿,一段无法忘却的记忆
王娜
灰色,这里到处是灰色。
灰色的门,灰色的路,灰色的草,围着那灰色的碑。
碑上有文:田独万人坑死难矿工纪念碑。
1939—1945。
1939年2月,侵华日军从琼州海峡北部的滘尾湾出发,穿过海峡进入三亚湾,先后占领三亚街、三亚港、榆林、崖州。位于榆林港东北12公里处的田独铁矿,进入日军视线。
一年前,1937年隆冬,亚太地区的一个中心城市,距离田独2000多公里的六朝古都南京,爆发了大屠杀。
一年后,1940年早春,东欧的一个小城,距田独7000多公里,在波兰最美丽的古城克拉科夫一侧,只有4万人的奥斯维辛,开始了变成承载400多万条生命的炼狱之路。
再从奥斯维辛一路向东,穿过燃烧在二战战火中的欧亚大陆,回到热带岛屿海南的最南端。这里比冬无严寒、夏无酷热的波兰更加舒适宜人。这里富含露天铁矿的小镇田独,也笼罩在了血色之中。
一艘艘船,在夜幕中卸下了它的乘客——一队又一队的青壮年;一辆辆车,卸下了它的乘客——同样是一队队的青壮年。
他们从广东、香港、台湾、东南亚、朝鲜、印度……从澄迈、乐东、陵水、三亚、田独……来到这片丛林环绕、充满热带风情的土地。有人以为正如招工时承诺的一般,可以“一年之后,合同期满,送回原籍”,他们或许可以注意到这是个美丽的地方,而更多的人,则是被抓而来,在他们眼中,一切都是灰色的恐惧……
这些都是七十多年前的旧事了,被囚于此的矿工们掘矿时扬起的绝望烟尘,早已在过往消散殆尽。
而今,久居三亚的人们,可能并不知晓,沿着熟悉的榆亚路到吉阳大道行进至亚龙湾站路口,右转进田独路后,在颂和水库旁,有这样一个死神曾无数次残酷降临的地方,一个上万名矿工命失于此的地方。
这是一段远去的记忆,正如纪念碑旁的丛丛冬日枯草一样,已从血色变成了灰色,再慢慢变成透明的颜色
当并未忘记这段记忆的人们来到这里,局促的砖墙在四面围挡,外侧是自建民居房和小小的饭店,寂寞的枯草在地上默默生长,越过四围砖墙铺盖下来的是枯黄的芭蕉叶,萧瑟。这萧瑟,促使着人们去追溯身边的这份灰色的沉重。
田独铁矿,据《三亚市志》记载:位于田独村东黄泥岭西北山麓,总储量500万吨左右,工业品位高达63%,有害成分很小,属优质铁矿。
铁矿石,维持战争机器的重要资源,可以生产钢材,用于造船、枪械、坦克、大炮……资源匮乏的日本,在美国为控制其在东南亚扩张采取了系列资源禁运之后,更加急于寻找资源支持。
田独铁矿,开始被掠夺性开采。
对矿,是毁灭性开采;对人,同样是毁灭性利用。
可能,已经没有“人”了,无数更甚动物世界的杀戮在每天上演。
所以这座铁矿曾被叫作红山矿,因为“满山满地的血红色,整座山都是血腥味。”一位见证人这样讲述。
今天,人们站在蓄满水的巨大矿坑旁,周围是草地、山林和高楼,恍惚以为这是个鱼塘、这是个小小的湖。微风拂过,舒适惬意,却不知这足有50米深的水底,曾有过多少无辜矿工的哀泣,这许多的水,是否是他们泪聚而成。
那无数绝望的血泪中,可能只有一个小小的期望——能如动物一般活着就好。这是奢望,到1945年被光复时,达到这个小小期望的幸存者已寥寥。
据史料记载,日本海南海军特务部从各地强抽一大批青壮年男子到田独、石碌等矿区充当各种苦役。这些矿工每天要干14个小时重活,规定每天每人挖矿石8吨,完不成任务不给饭吃,还要遭受毒打。沉重的苦役折磨着矿工,忍受不了而逃跑的被抓回来后立即枪毙,病了的被活埋,患传染病的被抬出去活活烧死。从1940年日本开始盗采铁矿到1944年1月因盟军飞机封锁海域难以运出而停产,四年多的时间里,累死、病死、饿死、烧死、活埋、枪毙的矿工近万人,矿山共计被盗掘约270万吨。
如此,能如动物一般活着就好。
7000公里外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在1945年被苏联红军解放后,幸存者们并无欢呼激动,“绝大部分被解放的人,都是一脸茫然。然后有的人就趴在地上,一路攀爬,站不起来。”奥斯维辛幸存者、意大利籍化学家和作家普利莫·莱维,在《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一书中如此描述和记载。
他说,所有从那个集中营活过来的人,都觉得有一种洗刷不去的耻辱感。原因之一,就是那是一段动物般的不能称为“人”的日子。
动物一般地活着,随时都会死去,这是什么样的感觉?
如今的人们都知道为“人”的感觉。自由安心地走在街头,吃想吃的东西,去想去的地方,见想见的人,我们可能已经超越了马斯洛人类需求五层次理论中的生存和安全需求,开始在尊重和自我实现的层面苦苦追寻。
可怕的和痛苦的记忆,是安心生活中难以触碰的角落,也终会变为面目不清的模糊灰色。只是,打开搜索引擎就可看到的那些遍布中国数不清的“万人坑”和惨案,在这矿坑,在老铁路,在八所、屯昌、万福村、天烛坡、石马村等地方,还留着深深伤痕。
当我们走过田独死难矿工的纪念碑,走过碑侧村民们留下的根根残香,在地球另一侧的华盛顿,每年有200万人走过被称为美国“哭墙”的黑色大理石越战纪念碑;在侵华口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每年有逾800万人走过长长的“哭墙”;在德国柏林大屠杀纪念馆,孩子们在2711块水泥墩组成的迷宫方阵间奔跑,大人们在石碑间沉思;在奥斯维辛殉难者纪念博物馆,每年亦有200多万人走过……
田独死难矿工纪念碑所象征和所代表的,其实是人们美好生活中的另一种重量,是三亚不该忘记的那些事情中的重要一页。
所以请记住,在这椰风海韵中,还有这个承载着无限沉重的小小角落。
田独万人坑的劳工祭
吴强
越过时间和山水,我们来到这里,沿着一级一级台阶,向前寻找。长揖,敬献,表达忆念和告慰,脚下的这方厚重而实在的土地里,许多人深埋于斯,己近百年。历史的寻踪,是一抹凄惨的光影,是一朵凋残的野花,曾经的呐喊、呻吟演绎着颠沛流离、血泪悲情的劳工祭。
时光回到那年,一个承载负重和艰辛、苦难和眼泪,深含绝望和忧伤的黑暗年代。1939年1月13日,日本天皇不顾国际公法,召开卫前会议作出侵占琼崖的决定,1月19日,发布攻陷海口及附近重要地域的命令。从2月3日起,日本陆海空军入侵海南岛领海领空,2月10日占领海口,2月14日凌晨占领三亚、榆林。火光、血、沉闷的滚雷、啸叫的风、淫雨,如墨低垂的浓云,及满山的哀歌和悲哭,没有人不会簌簌地发抖。踏进了由鲜血和骸骨汇成的血水中,不断泛起带有骷髅花纹的气泡,踏起的烟尘,越来越近。
日军占领海南岛之后,便加速对海南岛资源的掠夺,他们迫不及待地派海军特务部北浦大佐带领工程技术人员进行海南岛资源勘探,发现了优质的田独铁矿。日本海南株式会社和石原株式会社通过敌伪机关的合证公司,从朝鲜、香港、印度,还有海南岛各县的汉族、黎族青壮年,采取强迫诱骗的手段先后抓来在田独、安由地区开采矿石及各种苦役的劳工有一万多人。这些劳工,似沙丘中的蚂蚁,沉溺于沙海中,重压下精神萎缩和意志溃散,尝尽了人生的苦头。日寇在田独村东南侧约数百米处的一片平坦荒坡上,建有20幢用茅草竹木搭起排列成行的大工棚。工棚里用竹子捆扎了两排对称的大通铺,每幢住劳工200名,编为4个班。月光混着煤油灯透过茅屋间隙染进来,乌黑斑驳的霉点布满整个工棚,充满陈腐霉味。每个人深陷灰气,人间的哀乐,曾在里面浮游。阴暗与悲凄的命运,那是心灵的腐烂,悲剧在浑然不察中上演。
遍野都是丛生的荆棘和树木,远处群山的倒影、朝霞和夕阳,还有满天星斗,抬起头,极目而望,是生生不息的大地阡陌,一切美丽丰绕的家园,充满灵感和梦想,而如今灾祸、野蛮、暴虐开始了。从此,客死他乡,再也回不去,故乡不可见,云水空如一。日寇把所有劳工集中在田独的矿山上,放火烧山,清除残枝,开始挖矿石,装运矿石。每天劳动时间长达14个小时,每天的伙食就两个饭团,几只发烂的咸鱼仔。因吃不饱,跑不动,常被日本监工打得皮开肉绽。劳工们被蹂躏得伤痕累累,受尽屈辱,留下恐惧,令人战栗,用无法言喻的惊心动魄,在哀鸣里得以残存。
多少人想从夜幕里偷出一条回乡之路。在田独铁矿当劳工的,有些人忍受不了日军监工的棍棒毒打,只得想办法逃脱虎口。1942年4月间,保亭县一位黎族劳工,因不堪忍受日军监工的毒打,所以就乘机逃跑。不幸被日军监工追捕逮住了,押至一片荒坡上,挖了一个大土坑,驱赶所有的劳工都前来这里观看日军监工对这位逃亡的劳工行刑。荒草沿路蔓生,周围是深陷于地平线下的广袤荒地,越陷越深的坡,好像走在世界尽头,一切都安静极了。天是空旷遥远的灰色,一个粗暴野蛮的日本监工,手中的刀在军裤上来回摩擦,眯着小眼,把刀举在空中,薄薄的刀刃在阳光下闪着精光,面目狰狞,暴躁又狂野地逼视眼前的劳工,狠狠地往他的脖子砍去。头颅立即滚落地上,鲜血像喷泉一样从断颈处喷出来,鲜血汩汩流出,染红了路边的无名草。劳工们都被惊吓得呆若木鸡,浑身发抖。像晴空炸响霹雳,心被劈开一刀,瞥见深渊的恐惧,好似汹涌的大河里漂流了漫长的岁月,终于被波浪冲到沙滩上,有些眩晕,有些漂浮,回忆梦的最后一幕。
这是一群十足的弱者,一个悲剧的角色,遭受欺凌、屈辱和不公,亳无尊严可言,虽然反抗,也会变得无可奈何。惨遭日寇荼毒,新鬼嚎哭,世道黑暗,余生只好如飞鸟一般无枝可依,夺我魂魄,苟全于奔走之间,去沉默地流下热泪。
野蛮不仅仅指劳工营的杀戮,更是充满惨绝人寰的侵略性。日寇每天上午把已咽气或未咽气的劳工全部堆叠其上,再铺满干木柴,浇上汽油,点火烧尸,臭气四处横溢。未咽气的劳工哀号不绝,一名未咽气的广东劳工,被日军监工抬进焚人坑里焚烧时,衣衫褴褛的他惨叫一声从焚人坑里跳出来,又被监工抓住再投扔进熊熊的大火里,只剩下一副光秃秃的骨架。他发出的惨叫声使人毛骨悚然,尖叫声伴着尘土混成一团,瞳孔无声明灭,仿佛笼罩全世界所有暗影,如宣纸一滴淡墨留存长久。那天大雨滂沱,窒息如影随形,一盏独自闪耀在漆黑夜晚的煤油灯,在疯长的杂草乱藤里,照出面目可憎、行同狗豨的日本人。那一坑留下的悲伤和泪水,那些在屠刀下悄无声息的死亡,只有亲历者才能明白。一生如此,犹如在黑暗深处寻找光明,犹如夏虫趋光向它奔去,一生都试图进入生活的纵深,试图与群体平等交流,发出人生有死,若死得其所,夫复何恨!
劳工们吃的是猪狗饭,干的是牛马活,住的是破顶断壁的茅草棚,睡的是竹架分成两层通连的太平铺,穿的是破麻袋和浑灰纸袋,每天要干14小时的重活,规定每天每人挖8吨矿石,完不成任务不给饭吃,还要遭受毒打。沉重的苦役,折磨着这些累死累活的劳工,致使他们经常昏倒在工地;忍受不了逃跑的被抓回来打得死去活来;病了的当作怠工,不给医治,活活埋掉;患上痢疾或症疾说是传染病,抬出去活活烧死,烧不完的尸骸被狗噬、兽咬、鸟啄,残骨遍野,臭气熏天,惨不忍睹。日本侵略者恃强凌弱,开采田独铁矿6年多,被抓来服苦役而病死、饿死、烧死、活埋、枪毙的矿工有一万人之多他们统统被埋在田独铁矿附近的一块矿地上,这里后人称之为“万人坑”(现今的颂和水库里,因水库蓄水,焚人坑被大水淹没)。
1958年4月,为纪念被日军迫害死亡的田独铁矿劳工,由海南铁矿田独矿区在田独村东侧颂和水库大坝旁,用水泥砌筑一座“日寇时期受迫害死亡工友纪念碑”黄泥岭不会忘记,那碑上的劳工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