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深处炼红心
| 内容出处: | 《崖县知青史料专辑·中册》 图书 |
| 唯一号: | 200120020230001680 |
| 颗粒名称: | 大山深处炼红心 |
| 分类号: | F323.6 |
| 页数: | 9 |
| 页码: | 320-328 |
| 摘要: | 本文讲述了1975年31名男女知青离开家乡,前往雅亮五七农场建设的艰辛历程。他们在路上遇到了种种困难,但得到了当地人的帮助。到达农场后,他们开始修缮茅草屋、砍毛竹、割茅草、砍木材等工作,为建设新农场做出自己的贡献。 |
| 关键词: | 知青 雅亮五七农场 艰辛历程 |
内容
引子
1975年9月1日上午,崖县三亚镇委办公楼前骤然热闹起来,来自三亚镇各街道居委会、下属单位的31名男女知青,一个个肩上挎着背包,胸前佩着红花,在家人的陪同以及欢送群众的簇拥下,陆续汇聚到这里。三亚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欢送大会”,今天在这里隆重举行。9时许,镇领导发表了简短有力、热情洋溢的讲话后,随着一声响亮的“出发”号令,挂在树上长长的鞭炮被点燃了,霎时,鞭炮声、掌声、锣声、鼓声响成一片,令所有在场者心潮澎湃。在欢送亲人闪着泪花的目光注视下,知青们先后登上了前来接送的“解放牌”大卡车。
跋涉
卡车拐上县城中心大道解放路后,开始加速行驶,目的地是距城区50多公里、位于雅亮公社辖区的三亚镇雅亮五七农场。卡车驶出城区后,就进入沙土路。车轮驰过之处,不时扬起阵阵尘土。途经天涯公社马岭村口,跑了一段“排骨路”(即路面成搓板状),便进入了山区公路,路面崎岖不平。进入育才、雅亮地段后,路况愈见险恶,时而盘旋而上,时而临渊而行。时值雨后初晴,路面泥泞不堪,极易打滑,稍有不慎就有危险。司机自是集中精力,小心翼翼,我们头晕目眩,心惊肉跳。因车身摇晃,站立不稳,有不少人晕车了,呕吐连连。
中午12时左右,来到雅亮公社驻地附近的雅亮河边(处宁远河上游),卡车就开不过去了,大家只得下车。河上那座40多米长的旧木桥,修建于20世纪50年代初,平时车辆和行人正常通过,只因雅亮地区几天来连下暴雨,山洪暴发,导致平日温顺的河水猛涨,水流湍急,已漫过桥面约70厘米,河面成了天堑,来往车辆均被阻隔。我们站在河岸边,望着浪花翻滚的河水,不禁眉头紧锁,心里犯愁:这下可怎么办啊!
忽听河对岸有人大声呼喊:“知青们,你们别着急,站在河边等着我们!”原来是雅亮公社领导闻讯,派出几位熟悉路桥情况的公社干部前来迎接,当地黎苗族同胞也划竹排前来支援,我们扬手向来者频频致意。他们高挽裤脚,沿着河水漫过的木桥,涉水来到我们身边,做出如下安排:男知青从木桥上涉水过河,女知青原地待命,以竹排接应过河。在他们的指导和协助下,23名男知青沿着木桥站成纵队,先把大家的一件件行李,依次从各人头顶上传递过去。再手拉着手,跟在他们身后,一步步走向河对岸。
接着,两位黎族大叔将竹排划了过来。一条竹排长约4米、宽约2米,除了两名排夫可乘坐6人,8名女知青分为两批接送。第一批4名女知青还算顺利,只用10多分钟便抵达对岸。第二批可就不那么幸运了,竹排划到河心时,一排浪头打过来,被撞出几米远。女知青的衣服、头发被溅起的浪花打湿了,人吓得浑身颤抖,忙蹲下身子用双手死死抠住竹排缝隙,生怕掉入水中。在这危急关头,只见两位排夫从容镇定,一边鼓励女知青沉着冷静,不要慌乱,一边拿紧竹篙,熟练摆渡,不久也将第二批女知青安全送上岸,两岸观看者先前提到嗓子眼的心才放了下来。
再往前便是羊肠小道,我们只好安步当车。时值仲秋,山里潮湿,雨后泥泞,加之过河时衣服已被打湿,我们一边哆嗦着身子,一边在坑坑洼洼、弯弯曲曲的小路上艰难前行,大约走了近3个小时,终于到达三亚镇雅亮五七农场。场长符文山、会计孙鸿雄,以及各街道居委会派驻的几名老场员,跟我们亲切握手,表示热烈欢迎。一阵寒暄过后便安排住宿,31位男女知青分别住在3栋旧茅草房里。当晚,场里把饲养多时的鸡鸭杀了几只,又在附近采摘了一些野菜熬汤,热情款待了我们。符场长和老场员的盛情,驱散了我们一路来的疲惫和寒意。这一夜,知青们睡得很踏实。
扎根
三亚镇雅亮五七农场所在地,为崖县五七干校原址,是崖县为落实毛泽东主席的“五·七指示”而建立的。由于交通不便、环境较差,崖县五七干校建成不久,就搬到荔枝沟公社落笔洞新址。三亚镇接下原址建立了雅亮五七农场,作为自己的生产基地,并从本镇各街道居委会抽调人员为场员。同样由于交通、环境因素,还有劳动艰苦、生活困难,不少人员先后离场,只剩下符场长和几位场员留守。这里群山环抱,山脉连绵,有一座高大巍峨的山峰叫雅亮岭。在雅亮岭东边的山脉间,一条白练似的河流蜿蜒流淌,这便是被称为崖县母亲河的宁远河上游支流雅亮河。五七农场场部就坐落在雅亮岭脚下与雅亮河之间的一块面积约30多亩的山坳里。
第二天一早,符场长便召集全体知青交代工作任务:“眼下咱们农场只有3间茅草屋,由于风吹雨淋,年久失修,现已破旧不堪,无法满足大家生活、工作的需要。场里决定,除了对原有的3间破旧茅草屋进行全面修缮外,再新盖6栋茅草屋。先安居后乐业嘛。因此,这段时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盖房子。”符场长接着做具体安排:男知青负责砍伐毛竹;女知青负责割茅草。吃完早餐后,男女知青就在符场长和另两位场员的带领下,背着军用水壶,拿上砍刀、镰刀和扁担等工具,分头向雅亮岭的纵深处进发。
雅亮岭山高林密、地势险峻,并且山雾浓、瘴气重,常有毒蛇猛兽出没。然而,大家并未被恶劣环境所吓退,一心要为建设新农场尽一份力量,人人热情高涨,个个干劲十足。由于毛竹生长较为分散,我们便将每处砍下的先放在下山路口,待收工时再搬到山脚下的雅亮河边集中。接着,将脚拇指大小的毛竹,按每40支一捆、每五六捆一排的做法,扎成四五个竹排,每个竹排派两个人撑竿“押送”,随雅亮河水顺流而漂。虽是初次“放排”,而且沿途不时遇到急流险滩、河石拦路等险情,但“排夫们”毫无惧色,信心满怀,驾驭竹排顺利漂过几公里的流程,安全到达场部附近的下游河口。然后再将竹排拆开,两个人合抬一捆,将所有毛竹搬回场部。女知青那边也是巾帼不让须眉,不顾自己皮娇肉嫩、身单体薄,将割下的茅草用藤条扎成一捆捆,每人两捆挑回场部。毛竹、茅草备齐后,我们又在附近山林砍伐盖房所需的木材。经过连续10多天的艰苦奋战,终将盖房所需材料备齐,接下来投入到盖房屋、搭床铺的紧张劳动中。
一个多月后,在场部一处空旷园地上,“矗立”起6间崭新的茅草屋,其中较大一间约60平方米,专供场部办公、会议之用,原先那3间茅草屋也旧貌换新颜。全场34名新老场员的居住问题,以及农场办公、会议场所问题,自此得到解决。由于条件所限,我们的茅草屋和竹架床还相当简陋,可这毕竟是自己的劳动成果,大家都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和骄傲。
五七农场地处深山,那时不通电话,与外界无法联系,给农场的工作和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场部经与雅亮公社邮电所、雅亮公社广播站联系,决定利用农村有线广播线路安装电话,但人家要求我们自己备料及埋设电线杆。于是,场部从31名知青中挑选十几人组成作业队,由李忠富带队砍伐适用木材作为电线杆,还负责挖坑及埋设。从农场到雅亮公社的路程约4公里多,如何选择竖杆路线及埋设电线杆,视具体情况而定。每根间距30至50米,总需100多根,这对于没有任何经验的我们,不啻一项异常“浩繁”的工程。
用做电线杆的木材,长度4米左右,尾径10厘米以上,材质要求不高。一般是竖杆到哪里,就在哪里附近砍伐木材。但靠近线路两边,符合标准的树木并不多,常常要往远山去寻找、砍伐,还要搬运到埋设现场。砍下木材后,通常是两个人抬着走,粗重的甚至三四个人合力,在忽高忽低、忽左忽右、弯弯曲曲的山间小道,行走很艰难。遇上较陡的山坡还好办,将木材顺势滚下去,或小心拖下坡。在这些日子里,大家跟着队长李忠富早出晚归,肩膀磨破了皮,手掌磨出水泡,但大家毫无怨言,用碘酒一抹、纱布一包,又继续下去。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努力,我们完成了电线杆埋设工作,有关方面也抓紧架线及安装电话,电话线终于接通了!当符场长第一个拨通电话总机,从话筒里传来话务员清晰而亲切的声音时,场部办公室响起了知青们经久不息的掌声。
依照场部的计划,还要建造一个水泥篮球场、一张水泥乒乓球台、一间水泥砌石猪圈,需要若干数量的水泥、钢筋,大量的石子、河沙。由于知青安置经费有限,农场没有经济来源,实现计划困难重重,场部特此向三亚镇汇报情况,请求解决钢筋水泥。农场原是三亚镇的生产基地,因条件太差留不住人,现在有了知青到来,他们非常重视,很快答应下来。距场部几百米处有一条山溪,经过日积月累,溪滩上的河沙、石子、石头相当充足,知青们主动要求担当采集、挑运重任。每天带上铁锤、钢钎、铁锨、扁担、箩筐等工具,去溪边挖沙拾石,破击大石,再挑回场部。由于不通车路,三亚镇支持的钢筋水泥只能运到雅亮公社,知青们便徒步前往,硬是用肩膀将10多吨水泥和几扎钢筋或抬或扛运回来。人心齐,泰山移。一个月后,一个像模像样的篮球场、一张中规中矩乒乓球台、一间可饲养十几头猪的猪圈,逐一呈现在人们面前。往日空落落、冷清清的场部,忽然间变得“丰富多彩”起来,每天傍晚都热闹非凡。
然而,还有一块“心病”仍然在折磨着我们,那就是每天不可或缺的生活用水问题。到达五七农场后的几个月里,吃用的水要到300多米外的雅亮河去挑回,洗澡也要结伴而去。有一条弯曲小路通往,下雨时泥泞不堪,徒手走路尚且艰难。无风无雨时河水还算干净,若逢风雨天气,上游的枯枝败叶、废渣腐物一齐涌下,就变得非常混浊。这时挑水回来,要待其沉淀澄清,除去杂质后,方可使用。况且这种“过滤”后的水质也不卫生,吃用后容易造成肠胃不适。考虑到以上因素,我们想就近挖一口可供吃用的水井。其时适逢镇领导陈昌爱(大家都叫“陈镇长”)在农场蹲点,她赞同这个想法,并答应打井经费、所需建材由镇里给予解决。有了陈主任的“金口”承诺,加上水泥等材料很快送到,大家打井的信心更足了。
经过反复比较,选址离厨房不远,拟挖1.5米直径的大井,事不宜迟,说干就干。陈主任亲自“坐镇”指挥,由较有经验的李忠富、林秋祥和张和弟等人组成挖井小组,一边在平地挖地沟预制混凝土井圈,一边在选定位置开挖井土。刚开始,挖掘进度还算顺利,可挖到3米深后,就碰到了岩石层,土石结构坚硬。用十字镐挖、钢钎撬,成效有限,李忠富决定用土炮炸。几声炮响过后,把炸塌的土石装入箩筐,再吊出井外,挖掘进度加快。挖到8米深的时候,井底有泉水不断涌出,正在井底作业的林秋祥、张和弟喜出望外,精神倍增。出现过一次意外,幸得他两人“命大福大”,总算有惊无险。当时井底掘出一块大卵石,重约百斤,两人合力抬入大箩筐,让井口上的人拉动滑轮吊上去。然而,就在箩筐吊离井底6米后,谁也没有想到:箩筐一头当吊钩的铁丝突然断开,大卵石“嘭”的一声砸下去,贴着林秋祥、张和弟的脊梁落地,距脚后跟不足两厘米,把所有在场的人惊得目瞪口呆!如此石头若砸在人身上,后果将不堪设想!
其间天气变化无常,工作时断时续,所以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经过一番团结协作、连续奋战,一口直径1.5米、深9米的水井终于落成了,水井荡漾着清冽、甘爽、纯净的井水,从此五七农场汲水于河、滤水而饮的日子就成为历史。
拓业
居住、饮水问题得到解决后,五七农场便全面进入了“开疆拓土”、艰苦创业的新阶段。按场部的部署,31名知青中除两名伙夫、两名猪倌留场外,其余都上后山去开荒垦地。山区不似平原,所谓“后山”,简直就是一个荆棘丛生、藤蔓缠绕、荒草疯长、残根盘踞的“蛮荒王国”,隐约可见蛇鼠、蚊虫、野禽等遁迹其间。在接下来的披荆斩棘、锄草挖树的征战中,手臂划破、脚掌穿刺等等“流血”事件已成家常便饭,毒蛇滋扰、蚊虫叮咬更是司空见惯。
一天,有“急先锋”之称的林秋祥、张秋弟在劈砍一丛棘蓬时,意外捣破了一个蜜蜂窝。眨眼间,成百上千只蜜蜂犹如一团乌云死死罩在我们的头顶上,见人就咬,吓得大伙抱着头四处乱跑,不少人当场被蜜蜂蜇得鼻青眼肿、疼不堪言。最令人深感恐怖的当推山蚂蟥。这玩意不像水蚂蟥那样易于辨认。它长得又细又小,很不起眼,且隐蔽性特强。它若待在枝丫上一动不动,像极了一根山刺,可一闻到人气味或血腥味,便从四处集拢而来,悄无声息黏在人身上,吸起血来贪婪得吓人。一次,一位女知青的裤腿不知何时钻进了几条山蚂蟥,直到收工回宿舍准备洗脚时,才发现几条圆鼓鼓的山蚂蟥正紧紧地黏在小腿上,吓得她又叫又跳。后来在男知青的帮助下,才把这几条山蚂蟥弄死。
雅亮岭山区,夏季高温多雨,闷热潮湿,冬季温和少雨,偶有寒潮。我们顶着炎炎烈日,在地表发烫、石头冒烟的荒地上,饱受煎熬,挥汗如雨;又冒着瑟瑟寒风,在雾气缭绕、寒露沾衣的山坳里,胼手胝足,奋战不已。还要应对各种突如其来的“不测风云”,诸如台风、暴雨、阵雨、寒潮等等。然而,所有这一切,是一道道的人生阶梯,需要我们历练和跨越!次年秋季的某日,一场风雨连着下了许多天,肆虐的山洪倾泻而下,农场与外界连接的唯一山路给冲垮了,往后山的小径也被冲得沟壑纵横,雅亮河水连日暴涨,五七农场几乎成了“孤岛”。在那段日子里,场部的伙食“库存”几近掏空,大家天天喝着地瓜粥,啃着咸菜、萝卜干。但我们始终保持乐观和自信,耐心等待风过雨停,再整装列队,重返战场。
经过将近一年的艰苦奋斗,我们开垦出了300多亩肥沃的土地。在较为平缓的50多亩土地上,种植了甘蔗、番薯、花生、芭蕉等短期经济作物;在靠近水源的平坦地段,特别留出10多亩好地,用以种植山兰稻和蔬菜,以解决自身的生活之需;另外,在坡度较高的250亩土地上,准备种植橡胶树,以收“以短养长、多种经营”之效。
种橡胶必须有橡胶籽,要培育橡胶苗。我们了解到橡胶林正处落籽时节,就到附近的立才农场、一山之隔的乐东县保国农场联系捡拾橡胶籽事宜,对方知道我们是知青,均表示大力支持。场部便指派张秋弟、叶发健、王春琳、王文肖等知青兵分两路,一路直指立才农场,一路翻山越岭前往保国农场,要求务必完成任务。树龄为4年的橡胶树即可结果,每个果中含3至4颗大的带棕色斑点的种子,果实自动裂开,种子即散落,时间多在下午。由于橡胶籽种仁有煮熟食用、压榨食用油、用做牲畜饲料等用途,收购价每斤5分钱,所以成了垦区农场众多学生及家属的一项“副业”,连队附近的橡胶树种子很少有剩落,得到较深的林段去捡。
为了早日完成任务,两路知青努力克服困难,不论白天黑夜,吃住都在橡胶林里。每天拂晓至日落西山,带着麻袋不停歇地到各处林段巡行捡拾,晚上披着大衣、抱着身子蜷缩在大树底下,还得提防被蛇鼠蚊虫叮咬。用石头垒起炉灶,每天三顿都是简单用餐,就用自带的铁锅煮些米粥,伴菜是豆腐乳或萝卜干。中午困了,就轮番打个盹。艰辛的汗水没有白流,历经10多天的苦熬死守,两路知青分别捡回了几大麻袋的橡胶籽,圆满地完成了肩负的任务。
在我们的精心培育和细心呵护下,苗圃场里呈现一派生机。另外,也从立才农场求援到一批芽接橡胶苗,都在5个多月后种植下去。只见一株株橡胶苗青翠娇嫩、摇曳生姿,仿佛一曲曲优美动听的童谣,在250多亩土地上快乐地吟唱。
苦炼
在大山里,在荒地上,在各种生产劳动场景中,我们与天斗、与地斗、与各种意想不到的艰难困苦斗。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常常与生存环境斗、与疾病伤痛斗,在内心世界与自己斗。
那时,我们居住的是相当简陋的茅草屋,睡的是凹凸不平、吱呀作响的“竹竿床”。住处四周杂草丛生、阴暗潮湿。这种环境极易招致毒蛇、蜈蚣、蝎子、蚊子等害虫。某晚,知青张秋弟半夜起来小解,刚出门,忽觉脚下有一软乎乎的东西在蠕动,赶忙用手电筒一照,只见一条眼镜蛇正在他的脚底下挣扎。原来是他穿的“山屐”(一种用木板和胶皮制作的拖鞋)恰巧踩在眼镜蛇的头上,吓得他大叫一声,跳到一旁。舍友闻声跳将下床,冲出门外,操起木棍当场将这条眼镜蛇打死。一天早上,知青王春琳起床后取下挂在篱笆壁上的衣服正准备穿上,猛然感到手背被什么东西狠狠地螫了一下,痛得他“哎哟”大叫一声,慌忙将衣服一甩,只见一只手指头大小的蝎子“扑”地掉在床头上。
经过了这一连串的“惊吓”之后,场部决定对茅草屋重新进行修葺。我们先将竹片墙体拆掉,改用黏土裹稻草糊成墙体,然后将房顶稀松破损的地方,重新用茅草加厚压牢,并对门窗加固补实,还在住处四周洒上石灰粉以驱虫杀菌。果然,经过我们这么一弄,蛇蝎蚊虫就很少“光顾”“寒舍”了。
当时崖县有几个高疟区,雅亮公社便是其中之一。我们身处的五七农场,正好就在高疟区域之中。在我们工作、生活的几年时间里,全场31名知青,除了王春琳和林海福外,其余29个人都曾不同程度地患过疟疾病,严重时一天竟同时病倒七八个人,还有不少知青治愈后又反复发作。由于场部缺医少药,一些病情严重的知青,我们就用毛竹当抬竿、藤条当床网,自制担架抬到3公里外的雅亮公社卫生院。某晚,知青李英武忽然全身发冷,高烧不退,很快便陷入昏迷状态。见情况危急,大家将他抬上担架,由10名知青连夜护送,就往雅亮公社卫生院赶。由于夜雾迷茫,山路险恶,担架较沉,行走相当困难。当时两个人在前边打着手电筒开道,中间4个人抬担架,后边4个人作为“替补”,也打着手电筒给前边的人照明。将李英武(还有一次是颜海浪)送到雅亮公社卫生院时,大伙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在那段岁月,在那段山路,大家伙还真的是你抬过我,我背过你,你慰问过我,我探望过你。一次集体甘蔗园失火,知青吉秋弟奋勇扑救,不慎被大火烧伤,晕倒在甘蔗园里。知青们闻讯奋不顾身舍命相助,冲进火海硬是把吉秋弟从死神手中抱了出来。当时吉秋弟已是浑身伤痕,不省人事。我们10多名知青轮番抬着他,从农场火速赶路送到雅亮卫生院。由于抢救及时,吉秋弟躲过了死神的魔爪。
在五七农场,我们不仅仅挥洒着热汗,而且还时时激荡着赤诚的兄弟情义。是啊,在远离亲人、远离家乡的大山深处,我们时时刻刻经受着各种磨难,在不可预知的命运和挑战面前,我们每一个个体是多么的脆弱和无助,或许正是有了知青间这种兄弟般的团结、互助、和睦相处、患难与共,才让我们在面对一个又一个恶浪似的困厄的摔打、撕扯时,犹能一次又一次地顽强地站立起来!
在五七农场,全年几乎没有节假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除了有时打一下篮球和乒乓球,没别的文娱活动。知青们每天吃完早餐就上工地劳动,往往下午收工后,吃完晚饭已黄昏,大多人很快就钻进被窝做“南柯一梦”。能给大家带来些许乐趣的,唯有窗外不时传来的各种不知名的飞禽走兽的叫声。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枯燥、单调、寂寞的山区生活,无时不在挑战着知青们的心理承受极限。于是,厌倦、思家、消极的情绪,如同疟疾病源般悄然在知青群中蔓延。
场领导一边积极做好知青安抚工作,一边及时向三亚镇做了汇报。镇里对农场反映的情况非常重视,迅速派出干部前往农场蹲点,与知青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了解知青们的思想动态,并对个别知青“有的放矢”地进行思想教育工作,稳定他们的思想情绪。当时崖县委副书记符木生和团县委书记符玉花也在“1975届毕业生上山下乡一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先后来到五七农场,探望和慰问我们。三亚镇也派出医疗队定期到农场为知青们作身体检查。为了更好地改善和丰富知青们的文化娱乐生活,三亚镇还从有限的财政经费中拨出专款,为农场购置了娱乐器材、图书、象棋、扑克等。毋庸置疑,组织和领导的教育、关怀与体贴,极大地鼓舞和鞭策了知青们,使知青们的思想、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也重新燃起知青们对山区生活、对个人前途的信心和追求之火。
自此,每天收工后,在球场上,在运动器材旁,随处可见知青们奔跑的身影、矫健的英姿;晚上作息前,借着昏黄的煤油灯光,知青们或看书,或下棋,或打扑克。文娱生活活跃起来了,知青们的精神面貌也随之发生了喜人的变化。几个热衷于文体活动的骨干分子还发起成立了文艺体工队,由能编会导、多才多艺的林海福任队长。队员们白天劳动,晚上便借着朦胧的月光在球场上进行训练或排练节目,不辞辛苦,不计报酬。农闲时,文艺体工队便走出农场前往雅亮中学、附近农场进行篮球、排球比赛,或携带自编自导的文艺节目为周边的雅亮村、青法村、东方红村等黎苗同胞演出。知青们的一场场球赛、一场场演出,为农场的伙伴们、为当地的黎苗同胞们奉上一道道丰盛的精神美餐!
沉寂的五七农场活跃了!农场主人翁的心活泛了!
后记
当年我们31名知青,听从党和祖国的召唤,从县城来到堪称崖县所有知青点中最偏僻、最边远的崖县三亚镇雅亮五七农场,前后历经五度春秋、五载风雨。从手不能提、肩不能挑、思想幼稚、意志薄弱的小知青,“蝶变”为直面苦难、敢于担当、心志成熟、信念坚定的大青年,我们为成长付出了坚守和无悔,我们为五七农场的发展壮大贡献了青春和热血。5年间,知青林海福、余秋英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30%的知青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其中团员王春琳多次被评为崖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先后出席过共青团崖县、共青团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共青团海南行政区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是的,我们未必都能为祖国和人民书写多么辉煌的历史篇章。然而,我们因曾经在那个年代,在那座大山深处,为后人留下一串串堪值缅怀的足印而感到自豪。
口述:王春琳 文永四 张秋弟 林海福 叶发建 简贤贵 王文肖 李忠富
整理:陈垂华 陈斌
1975年9月1日上午,崖县三亚镇委办公楼前骤然热闹起来,来自三亚镇各街道居委会、下属单位的31名男女知青,一个个肩上挎着背包,胸前佩着红花,在家人的陪同以及欢送群众的簇拥下,陆续汇聚到这里。三亚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欢送大会”,今天在这里隆重举行。9时许,镇领导发表了简短有力、热情洋溢的讲话后,随着一声响亮的“出发”号令,挂在树上长长的鞭炮被点燃了,霎时,鞭炮声、掌声、锣声、鼓声响成一片,令所有在场者心潮澎湃。在欢送亲人闪着泪花的目光注视下,知青们先后登上了前来接送的“解放牌”大卡车。
跋涉
卡车拐上县城中心大道解放路后,开始加速行驶,目的地是距城区50多公里、位于雅亮公社辖区的三亚镇雅亮五七农场。卡车驶出城区后,就进入沙土路。车轮驰过之处,不时扬起阵阵尘土。途经天涯公社马岭村口,跑了一段“排骨路”(即路面成搓板状),便进入了山区公路,路面崎岖不平。进入育才、雅亮地段后,路况愈见险恶,时而盘旋而上,时而临渊而行。时值雨后初晴,路面泥泞不堪,极易打滑,稍有不慎就有危险。司机自是集中精力,小心翼翼,我们头晕目眩,心惊肉跳。因车身摇晃,站立不稳,有不少人晕车了,呕吐连连。
中午12时左右,来到雅亮公社驻地附近的雅亮河边(处宁远河上游),卡车就开不过去了,大家只得下车。河上那座40多米长的旧木桥,修建于20世纪50年代初,平时车辆和行人正常通过,只因雅亮地区几天来连下暴雨,山洪暴发,导致平日温顺的河水猛涨,水流湍急,已漫过桥面约70厘米,河面成了天堑,来往车辆均被阻隔。我们站在河岸边,望着浪花翻滚的河水,不禁眉头紧锁,心里犯愁:这下可怎么办啊!
忽听河对岸有人大声呼喊:“知青们,你们别着急,站在河边等着我们!”原来是雅亮公社领导闻讯,派出几位熟悉路桥情况的公社干部前来迎接,当地黎苗族同胞也划竹排前来支援,我们扬手向来者频频致意。他们高挽裤脚,沿着河水漫过的木桥,涉水来到我们身边,做出如下安排:男知青从木桥上涉水过河,女知青原地待命,以竹排接应过河。在他们的指导和协助下,23名男知青沿着木桥站成纵队,先把大家的一件件行李,依次从各人头顶上传递过去。再手拉着手,跟在他们身后,一步步走向河对岸。
接着,两位黎族大叔将竹排划了过来。一条竹排长约4米、宽约2米,除了两名排夫可乘坐6人,8名女知青分为两批接送。第一批4名女知青还算顺利,只用10多分钟便抵达对岸。第二批可就不那么幸运了,竹排划到河心时,一排浪头打过来,被撞出几米远。女知青的衣服、头发被溅起的浪花打湿了,人吓得浑身颤抖,忙蹲下身子用双手死死抠住竹排缝隙,生怕掉入水中。在这危急关头,只见两位排夫从容镇定,一边鼓励女知青沉着冷静,不要慌乱,一边拿紧竹篙,熟练摆渡,不久也将第二批女知青安全送上岸,两岸观看者先前提到嗓子眼的心才放了下来。
再往前便是羊肠小道,我们只好安步当车。时值仲秋,山里潮湿,雨后泥泞,加之过河时衣服已被打湿,我们一边哆嗦着身子,一边在坑坑洼洼、弯弯曲曲的小路上艰难前行,大约走了近3个小时,终于到达三亚镇雅亮五七农场。场长符文山、会计孙鸿雄,以及各街道居委会派驻的几名老场员,跟我们亲切握手,表示热烈欢迎。一阵寒暄过后便安排住宿,31位男女知青分别住在3栋旧茅草房里。当晚,场里把饲养多时的鸡鸭杀了几只,又在附近采摘了一些野菜熬汤,热情款待了我们。符场长和老场员的盛情,驱散了我们一路来的疲惫和寒意。这一夜,知青们睡得很踏实。
扎根
三亚镇雅亮五七农场所在地,为崖县五七干校原址,是崖县为落实毛泽东主席的“五·七指示”而建立的。由于交通不便、环境较差,崖县五七干校建成不久,就搬到荔枝沟公社落笔洞新址。三亚镇接下原址建立了雅亮五七农场,作为自己的生产基地,并从本镇各街道居委会抽调人员为场员。同样由于交通、环境因素,还有劳动艰苦、生活困难,不少人员先后离场,只剩下符场长和几位场员留守。这里群山环抱,山脉连绵,有一座高大巍峨的山峰叫雅亮岭。在雅亮岭东边的山脉间,一条白练似的河流蜿蜒流淌,这便是被称为崖县母亲河的宁远河上游支流雅亮河。五七农场场部就坐落在雅亮岭脚下与雅亮河之间的一块面积约30多亩的山坳里。
第二天一早,符场长便召集全体知青交代工作任务:“眼下咱们农场只有3间茅草屋,由于风吹雨淋,年久失修,现已破旧不堪,无法满足大家生活、工作的需要。场里决定,除了对原有的3间破旧茅草屋进行全面修缮外,再新盖6栋茅草屋。先安居后乐业嘛。因此,这段时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盖房子。”符场长接着做具体安排:男知青负责砍伐毛竹;女知青负责割茅草。吃完早餐后,男女知青就在符场长和另两位场员的带领下,背着军用水壶,拿上砍刀、镰刀和扁担等工具,分头向雅亮岭的纵深处进发。
雅亮岭山高林密、地势险峻,并且山雾浓、瘴气重,常有毒蛇猛兽出没。然而,大家并未被恶劣环境所吓退,一心要为建设新农场尽一份力量,人人热情高涨,个个干劲十足。由于毛竹生长较为分散,我们便将每处砍下的先放在下山路口,待收工时再搬到山脚下的雅亮河边集中。接着,将脚拇指大小的毛竹,按每40支一捆、每五六捆一排的做法,扎成四五个竹排,每个竹排派两个人撑竿“押送”,随雅亮河水顺流而漂。虽是初次“放排”,而且沿途不时遇到急流险滩、河石拦路等险情,但“排夫们”毫无惧色,信心满怀,驾驭竹排顺利漂过几公里的流程,安全到达场部附近的下游河口。然后再将竹排拆开,两个人合抬一捆,将所有毛竹搬回场部。女知青那边也是巾帼不让须眉,不顾自己皮娇肉嫩、身单体薄,将割下的茅草用藤条扎成一捆捆,每人两捆挑回场部。毛竹、茅草备齐后,我们又在附近山林砍伐盖房所需的木材。经过连续10多天的艰苦奋战,终将盖房所需材料备齐,接下来投入到盖房屋、搭床铺的紧张劳动中。
一个多月后,在场部一处空旷园地上,“矗立”起6间崭新的茅草屋,其中较大一间约60平方米,专供场部办公、会议之用,原先那3间茅草屋也旧貌换新颜。全场34名新老场员的居住问题,以及农场办公、会议场所问题,自此得到解决。由于条件所限,我们的茅草屋和竹架床还相当简陋,可这毕竟是自己的劳动成果,大家都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和骄傲。
五七农场地处深山,那时不通电话,与外界无法联系,给农场的工作和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场部经与雅亮公社邮电所、雅亮公社广播站联系,决定利用农村有线广播线路安装电话,但人家要求我们自己备料及埋设电线杆。于是,场部从31名知青中挑选十几人组成作业队,由李忠富带队砍伐适用木材作为电线杆,还负责挖坑及埋设。从农场到雅亮公社的路程约4公里多,如何选择竖杆路线及埋设电线杆,视具体情况而定。每根间距30至50米,总需100多根,这对于没有任何经验的我们,不啻一项异常“浩繁”的工程。
用做电线杆的木材,长度4米左右,尾径10厘米以上,材质要求不高。一般是竖杆到哪里,就在哪里附近砍伐木材。但靠近线路两边,符合标准的树木并不多,常常要往远山去寻找、砍伐,还要搬运到埋设现场。砍下木材后,通常是两个人抬着走,粗重的甚至三四个人合力,在忽高忽低、忽左忽右、弯弯曲曲的山间小道,行走很艰难。遇上较陡的山坡还好办,将木材顺势滚下去,或小心拖下坡。在这些日子里,大家跟着队长李忠富早出晚归,肩膀磨破了皮,手掌磨出水泡,但大家毫无怨言,用碘酒一抹、纱布一包,又继续下去。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努力,我们完成了电线杆埋设工作,有关方面也抓紧架线及安装电话,电话线终于接通了!当符场长第一个拨通电话总机,从话筒里传来话务员清晰而亲切的声音时,场部办公室响起了知青们经久不息的掌声。
依照场部的计划,还要建造一个水泥篮球场、一张水泥乒乓球台、一间水泥砌石猪圈,需要若干数量的水泥、钢筋,大量的石子、河沙。由于知青安置经费有限,农场没有经济来源,实现计划困难重重,场部特此向三亚镇汇报情况,请求解决钢筋水泥。农场原是三亚镇的生产基地,因条件太差留不住人,现在有了知青到来,他们非常重视,很快答应下来。距场部几百米处有一条山溪,经过日积月累,溪滩上的河沙、石子、石头相当充足,知青们主动要求担当采集、挑运重任。每天带上铁锤、钢钎、铁锨、扁担、箩筐等工具,去溪边挖沙拾石,破击大石,再挑回场部。由于不通车路,三亚镇支持的钢筋水泥只能运到雅亮公社,知青们便徒步前往,硬是用肩膀将10多吨水泥和几扎钢筋或抬或扛运回来。人心齐,泰山移。一个月后,一个像模像样的篮球场、一张中规中矩乒乓球台、一间可饲养十几头猪的猪圈,逐一呈现在人们面前。往日空落落、冷清清的场部,忽然间变得“丰富多彩”起来,每天傍晚都热闹非凡。
然而,还有一块“心病”仍然在折磨着我们,那就是每天不可或缺的生活用水问题。到达五七农场后的几个月里,吃用的水要到300多米外的雅亮河去挑回,洗澡也要结伴而去。有一条弯曲小路通往,下雨时泥泞不堪,徒手走路尚且艰难。无风无雨时河水还算干净,若逢风雨天气,上游的枯枝败叶、废渣腐物一齐涌下,就变得非常混浊。这时挑水回来,要待其沉淀澄清,除去杂质后,方可使用。况且这种“过滤”后的水质也不卫生,吃用后容易造成肠胃不适。考虑到以上因素,我们想就近挖一口可供吃用的水井。其时适逢镇领导陈昌爱(大家都叫“陈镇长”)在农场蹲点,她赞同这个想法,并答应打井经费、所需建材由镇里给予解决。有了陈主任的“金口”承诺,加上水泥等材料很快送到,大家打井的信心更足了。
经过反复比较,选址离厨房不远,拟挖1.5米直径的大井,事不宜迟,说干就干。陈主任亲自“坐镇”指挥,由较有经验的李忠富、林秋祥和张和弟等人组成挖井小组,一边在平地挖地沟预制混凝土井圈,一边在选定位置开挖井土。刚开始,挖掘进度还算顺利,可挖到3米深后,就碰到了岩石层,土石结构坚硬。用十字镐挖、钢钎撬,成效有限,李忠富决定用土炮炸。几声炮响过后,把炸塌的土石装入箩筐,再吊出井外,挖掘进度加快。挖到8米深的时候,井底有泉水不断涌出,正在井底作业的林秋祥、张和弟喜出望外,精神倍增。出现过一次意外,幸得他两人“命大福大”,总算有惊无险。当时井底掘出一块大卵石,重约百斤,两人合力抬入大箩筐,让井口上的人拉动滑轮吊上去。然而,就在箩筐吊离井底6米后,谁也没有想到:箩筐一头当吊钩的铁丝突然断开,大卵石“嘭”的一声砸下去,贴着林秋祥、张和弟的脊梁落地,距脚后跟不足两厘米,把所有在场的人惊得目瞪口呆!如此石头若砸在人身上,后果将不堪设想!
其间天气变化无常,工作时断时续,所以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经过一番团结协作、连续奋战,一口直径1.5米、深9米的水井终于落成了,水井荡漾着清冽、甘爽、纯净的井水,从此五七农场汲水于河、滤水而饮的日子就成为历史。
拓业
居住、饮水问题得到解决后,五七农场便全面进入了“开疆拓土”、艰苦创业的新阶段。按场部的部署,31名知青中除两名伙夫、两名猪倌留场外,其余都上后山去开荒垦地。山区不似平原,所谓“后山”,简直就是一个荆棘丛生、藤蔓缠绕、荒草疯长、残根盘踞的“蛮荒王国”,隐约可见蛇鼠、蚊虫、野禽等遁迹其间。在接下来的披荆斩棘、锄草挖树的征战中,手臂划破、脚掌穿刺等等“流血”事件已成家常便饭,毒蛇滋扰、蚊虫叮咬更是司空见惯。
一天,有“急先锋”之称的林秋祥、张秋弟在劈砍一丛棘蓬时,意外捣破了一个蜜蜂窝。眨眼间,成百上千只蜜蜂犹如一团乌云死死罩在我们的头顶上,见人就咬,吓得大伙抱着头四处乱跑,不少人当场被蜜蜂蜇得鼻青眼肿、疼不堪言。最令人深感恐怖的当推山蚂蟥。这玩意不像水蚂蟥那样易于辨认。它长得又细又小,很不起眼,且隐蔽性特强。它若待在枝丫上一动不动,像极了一根山刺,可一闻到人气味或血腥味,便从四处集拢而来,悄无声息黏在人身上,吸起血来贪婪得吓人。一次,一位女知青的裤腿不知何时钻进了几条山蚂蟥,直到收工回宿舍准备洗脚时,才发现几条圆鼓鼓的山蚂蟥正紧紧地黏在小腿上,吓得她又叫又跳。后来在男知青的帮助下,才把这几条山蚂蟥弄死。
雅亮岭山区,夏季高温多雨,闷热潮湿,冬季温和少雨,偶有寒潮。我们顶着炎炎烈日,在地表发烫、石头冒烟的荒地上,饱受煎熬,挥汗如雨;又冒着瑟瑟寒风,在雾气缭绕、寒露沾衣的山坳里,胼手胝足,奋战不已。还要应对各种突如其来的“不测风云”,诸如台风、暴雨、阵雨、寒潮等等。然而,所有这一切,是一道道的人生阶梯,需要我们历练和跨越!次年秋季的某日,一场风雨连着下了许多天,肆虐的山洪倾泻而下,农场与外界连接的唯一山路给冲垮了,往后山的小径也被冲得沟壑纵横,雅亮河水连日暴涨,五七农场几乎成了“孤岛”。在那段日子里,场部的伙食“库存”几近掏空,大家天天喝着地瓜粥,啃着咸菜、萝卜干。但我们始终保持乐观和自信,耐心等待风过雨停,再整装列队,重返战场。
经过将近一年的艰苦奋斗,我们开垦出了300多亩肥沃的土地。在较为平缓的50多亩土地上,种植了甘蔗、番薯、花生、芭蕉等短期经济作物;在靠近水源的平坦地段,特别留出10多亩好地,用以种植山兰稻和蔬菜,以解决自身的生活之需;另外,在坡度较高的250亩土地上,准备种植橡胶树,以收“以短养长、多种经营”之效。
种橡胶必须有橡胶籽,要培育橡胶苗。我们了解到橡胶林正处落籽时节,就到附近的立才农场、一山之隔的乐东县保国农场联系捡拾橡胶籽事宜,对方知道我们是知青,均表示大力支持。场部便指派张秋弟、叶发健、王春琳、王文肖等知青兵分两路,一路直指立才农场,一路翻山越岭前往保国农场,要求务必完成任务。树龄为4年的橡胶树即可结果,每个果中含3至4颗大的带棕色斑点的种子,果实自动裂开,种子即散落,时间多在下午。由于橡胶籽种仁有煮熟食用、压榨食用油、用做牲畜饲料等用途,收购价每斤5分钱,所以成了垦区农场众多学生及家属的一项“副业”,连队附近的橡胶树种子很少有剩落,得到较深的林段去捡。
为了早日完成任务,两路知青努力克服困难,不论白天黑夜,吃住都在橡胶林里。每天拂晓至日落西山,带着麻袋不停歇地到各处林段巡行捡拾,晚上披着大衣、抱着身子蜷缩在大树底下,还得提防被蛇鼠蚊虫叮咬。用石头垒起炉灶,每天三顿都是简单用餐,就用自带的铁锅煮些米粥,伴菜是豆腐乳或萝卜干。中午困了,就轮番打个盹。艰辛的汗水没有白流,历经10多天的苦熬死守,两路知青分别捡回了几大麻袋的橡胶籽,圆满地完成了肩负的任务。
在我们的精心培育和细心呵护下,苗圃场里呈现一派生机。另外,也从立才农场求援到一批芽接橡胶苗,都在5个多月后种植下去。只见一株株橡胶苗青翠娇嫩、摇曳生姿,仿佛一曲曲优美动听的童谣,在250多亩土地上快乐地吟唱。
苦炼
在大山里,在荒地上,在各种生产劳动场景中,我们与天斗、与地斗、与各种意想不到的艰难困苦斗。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常常与生存环境斗、与疾病伤痛斗,在内心世界与自己斗。
那时,我们居住的是相当简陋的茅草屋,睡的是凹凸不平、吱呀作响的“竹竿床”。住处四周杂草丛生、阴暗潮湿。这种环境极易招致毒蛇、蜈蚣、蝎子、蚊子等害虫。某晚,知青张秋弟半夜起来小解,刚出门,忽觉脚下有一软乎乎的东西在蠕动,赶忙用手电筒一照,只见一条眼镜蛇正在他的脚底下挣扎。原来是他穿的“山屐”(一种用木板和胶皮制作的拖鞋)恰巧踩在眼镜蛇的头上,吓得他大叫一声,跳到一旁。舍友闻声跳将下床,冲出门外,操起木棍当场将这条眼镜蛇打死。一天早上,知青王春琳起床后取下挂在篱笆壁上的衣服正准备穿上,猛然感到手背被什么东西狠狠地螫了一下,痛得他“哎哟”大叫一声,慌忙将衣服一甩,只见一只手指头大小的蝎子“扑”地掉在床头上。
经过了这一连串的“惊吓”之后,场部决定对茅草屋重新进行修葺。我们先将竹片墙体拆掉,改用黏土裹稻草糊成墙体,然后将房顶稀松破损的地方,重新用茅草加厚压牢,并对门窗加固补实,还在住处四周洒上石灰粉以驱虫杀菌。果然,经过我们这么一弄,蛇蝎蚊虫就很少“光顾”“寒舍”了。
当时崖县有几个高疟区,雅亮公社便是其中之一。我们身处的五七农场,正好就在高疟区域之中。在我们工作、生活的几年时间里,全场31名知青,除了王春琳和林海福外,其余29个人都曾不同程度地患过疟疾病,严重时一天竟同时病倒七八个人,还有不少知青治愈后又反复发作。由于场部缺医少药,一些病情严重的知青,我们就用毛竹当抬竿、藤条当床网,自制担架抬到3公里外的雅亮公社卫生院。某晚,知青李英武忽然全身发冷,高烧不退,很快便陷入昏迷状态。见情况危急,大家将他抬上担架,由10名知青连夜护送,就往雅亮公社卫生院赶。由于夜雾迷茫,山路险恶,担架较沉,行走相当困难。当时两个人在前边打着手电筒开道,中间4个人抬担架,后边4个人作为“替补”,也打着手电筒给前边的人照明。将李英武(还有一次是颜海浪)送到雅亮公社卫生院时,大伙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在那段岁月,在那段山路,大家伙还真的是你抬过我,我背过你,你慰问过我,我探望过你。一次集体甘蔗园失火,知青吉秋弟奋勇扑救,不慎被大火烧伤,晕倒在甘蔗园里。知青们闻讯奋不顾身舍命相助,冲进火海硬是把吉秋弟从死神手中抱了出来。当时吉秋弟已是浑身伤痕,不省人事。我们10多名知青轮番抬着他,从农场火速赶路送到雅亮卫生院。由于抢救及时,吉秋弟躲过了死神的魔爪。
在五七农场,我们不仅仅挥洒着热汗,而且还时时激荡着赤诚的兄弟情义。是啊,在远离亲人、远离家乡的大山深处,我们时时刻刻经受着各种磨难,在不可预知的命运和挑战面前,我们每一个个体是多么的脆弱和无助,或许正是有了知青间这种兄弟般的团结、互助、和睦相处、患难与共,才让我们在面对一个又一个恶浪似的困厄的摔打、撕扯时,犹能一次又一次地顽强地站立起来!
在五七农场,全年几乎没有节假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除了有时打一下篮球和乒乓球,没别的文娱活动。知青们每天吃完早餐就上工地劳动,往往下午收工后,吃完晚饭已黄昏,大多人很快就钻进被窝做“南柯一梦”。能给大家带来些许乐趣的,唯有窗外不时传来的各种不知名的飞禽走兽的叫声。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枯燥、单调、寂寞的山区生活,无时不在挑战着知青们的心理承受极限。于是,厌倦、思家、消极的情绪,如同疟疾病源般悄然在知青群中蔓延。
场领导一边积极做好知青安抚工作,一边及时向三亚镇做了汇报。镇里对农场反映的情况非常重视,迅速派出干部前往农场蹲点,与知青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了解知青们的思想动态,并对个别知青“有的放矢”地进行思想教育工作,稳定他们的思想情绪。当时崖县委副书记符木生和团县委书记符玉花也在“1975届毕业生上山下乡一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先后来到五七农场,探望和慰问我们。三亚镇也派出医疗队定期到农场为知青们作身体检查。为了更好地改善和丰富知青们的文化娱乐生活,三亚镇还从有限的财政经费中拨出专款,为农场购置了娱乐器材、图书、象棋、扑克等。毋庸置疑,组织和领导的教育、关怀与体贴,极大地鼓舞和鞭策了知青们,使知青们的思想、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也重新燃起知青们对山区生活、对个人前途的信心和追求之火。
自此,每天收工后,在球场上,在运动器材旁,随处可见知青们奔跑的身影、矫健的英姿;晚上作息前,借着昏黄的煤油灯光,知青们或看书,或下棋,或打扑克。文娱生活活跃起来了,知青们的精神面貌也随之发生了喜人的变化。几个热衷于文体活动的骨干分子还发起成立了文艺体工队,由能编会导、多才多艺的林海福任队长。队员们白天劳动,晚上便借着朦胧的月光在球场上进行训练或排练节目,不辞辛苦,不计报酬。农闲时,文艺体工队便走出农场前往雅亮中学、附近农场进行篮球、排球比赛,或携带自编自导的文艺节目为周边的雅亮村、青法村、东方红村等黎苗同胞演出。知青们的一场场球赛、一场场演出,为农场的伙伴们、为当地的黎苗同胞们奉上一道道丰盛的精神美餐!
沉寂的五七农场活跃了!农场主人翁的心活泛了!
后记
当年我们31名知青,听从党和祖国的召唤,从县城来到堪称崖县所有知青点中最偏僻、最边远的崖县三亚镇雅亮五七农场,前后历经五度春秋、五载风雨。从手不能提、肩不能挑、思想幼稚、意志薄弱的小知青,“蝶变”为直面苦难、敢于担当、心志成熟、信念坚定的大青年,我们为成长付出了坚守和无悔,我们为五七农场的发展壮大贡献了青春和热血。5年间,知青林海福、余秋英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30%的知青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其中团员王春琳多次被评为崖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先后出席过共青团崖县、共青团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共青团海南行政区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是的,我们未必都能为祖国和人民书写多么辉煌的历史篇章。然而,我们因曾经在那个年代,在那座大山深处,为后人留下一串串堪值缅怀的足印而感到自豪。
口述:王春琳 文永四 张秋弟 林海福 叶发建 简贤贵 王文肖 李忠富
整理:陈垂华 陈斌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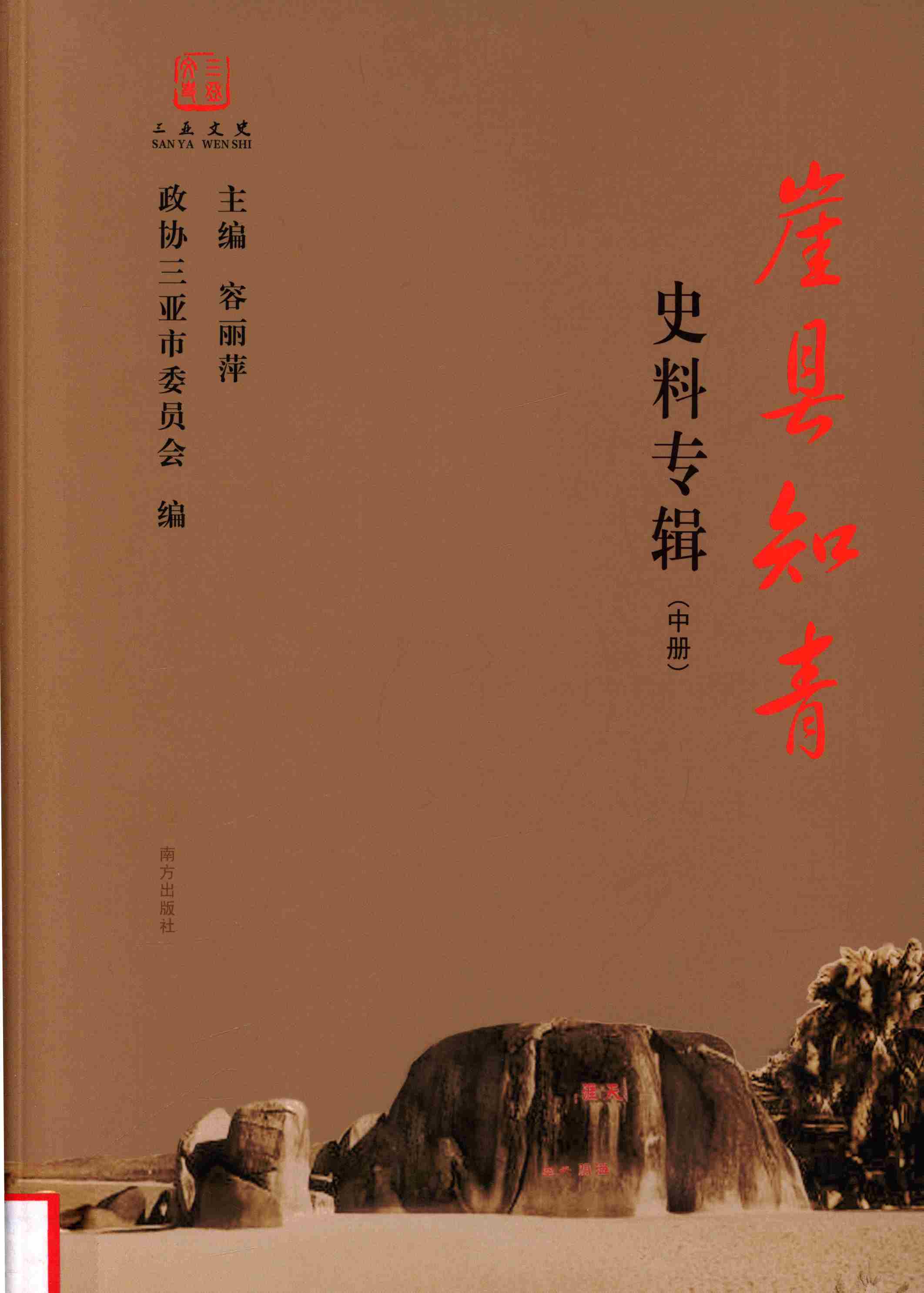
《崖县知青史料专辑·中册》
出版者:南方出版社
本书共有83篇文稿:崖县抱龙林场(20篇)、崖县三亚林场(2篇)、林旺猪场(3篇)、海螺农场(2篇)4处安置点27篇知青回忆录;藤桥(4篇)、林旺(2篇)、田独(13篇)、红沙(4篇)、荔枝沟(6篇)、羊栏(8篇)、天涯(1篇)、育才(6篇)、雅亮(3篇)、崖城(5篇)、水上(2篇)、保港(2篇)12个公社安置点56篇知青回忆录。
阅读
相关人物
王春琳
责任者
相关地名
崖县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