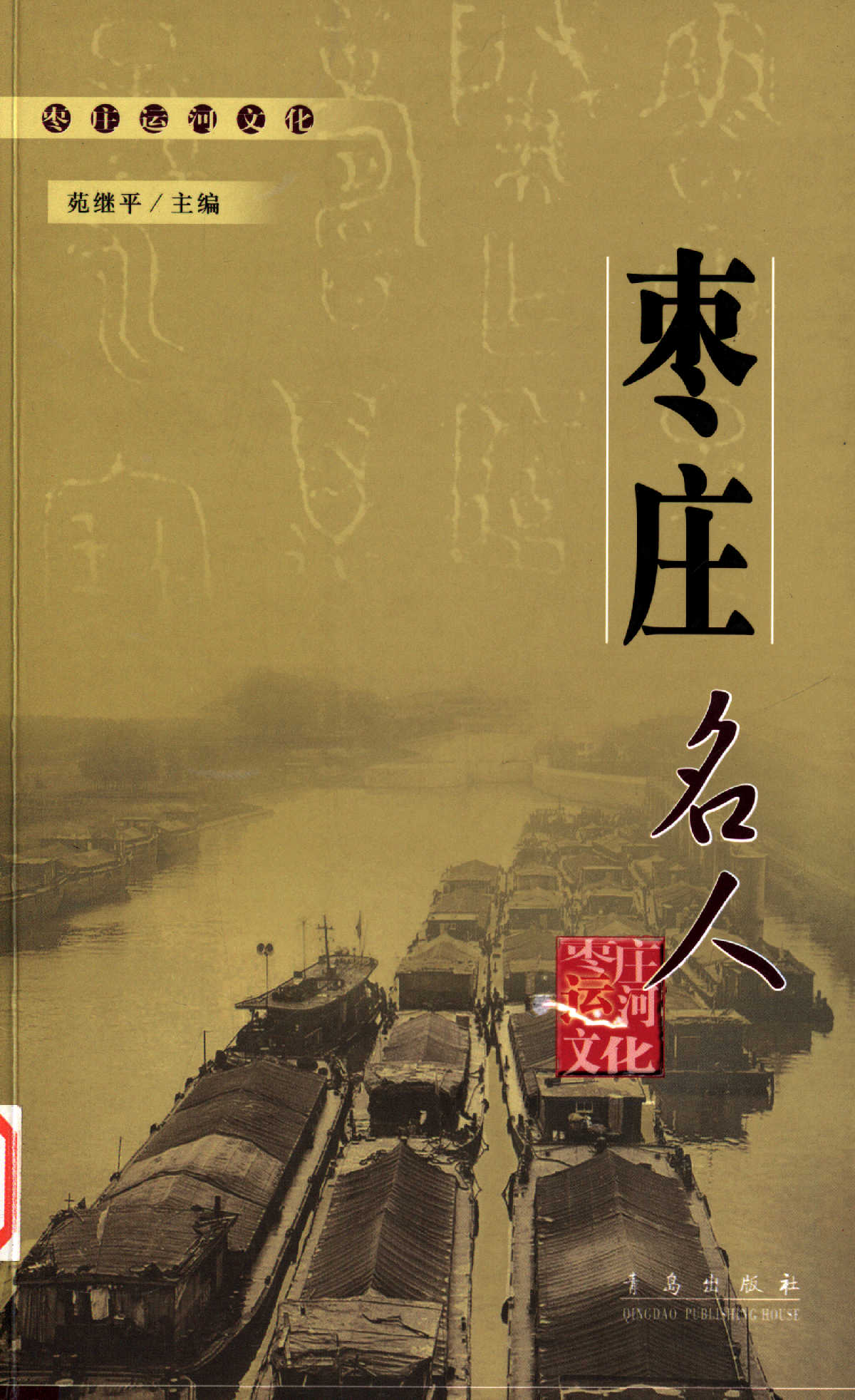刘位钧
| 知识出处: | 《枣庄名人》 |
| 唯一号: | 151030020220000541 |
| 人物姓名: | 刘位钧 |
| 人物异名: | 刘子衡 |
| 文件路径: | 1510/01/object/PDF/151010020220000010/001 |
| 起始页: | T00164_00.pdf |
| 性别: | 男 |
| 出生年: | 1903年 |
| 卒年: | 1981年 |
| 籍贯: | 滕州 |
传略
刘子衡(1903至1981年)原名刘位钧,滕州城关杏花村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析证诸子、衡量百家的学者,被尊称为“布衣大师'刘子衡生于一个佃农家庭。自幼聪明放达,9岁便入私塾读四书五经。1924年春,刘子衡考入山东省立第二师范(曲阜二师)。当时的校长是山东的马列主义早期传播者之一范铭枢先生。范铭枢在学校大力推荐进步书刊,积极传播革命思想。在这种氛围中,学生们关注时事,思想活跃,进步思潮弥漫校园。图书馆员辛成智和学生杨荫鸿、张观成等,建立了学校里的第一个中共党支部。刘子衡与学生中的共产党员王泽新、刘德荣、张化恪、张育东等,交往甚密。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救国之事,并参加了震惊全国的“五卅运动”。1928年,济南发生“五•三”惨案后,国民党省党部派员进驻曲阜二师。中共党员王泽新等人由于活动频繁,引人注意而被捕。刘子衡作为学生代表挺身而出,到兖州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说理。国民党反动派怕事态扩大,只好答应把被捕的学生全部释放。由于刘子衡善于斗争,主持公道,受到同学信赖。改组学生会时,他被一致推举为学术部长,后来改任学生会主席。此时的学生会,实际已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学生组织。
1927年,刘子衡参与主持公演了话剧《子见南子》。该剧主要反映了孔子周游列国到卫国会见卫灵公夫人南子的故事。
没想到触怒了孔氏家族,认为剧中孔子拜倒于南子石榴裙下,是对孔子的侮辱。孔氏家族上告中央教育部门,加上个别外国新闻记者的推波助澜,于是就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子见南子》案。事件发生以后,国民党当局要停演这出戏。但在共产党领导下,师生奋起反抗,获得了全国各地的热烈声援,还得到了鲁迅先生的大力支持。此次斗争,被后人称为“五•四”青年学生运动的继续。这场斗争,最后以校长宋还吾被撤职,刘子衡等人被开除,大批进步学生被迫离校而告结束。而刘子衡在这场斗争中初试锋芒、崭露头角,显示了他超群的胆略与才华,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注意。
1929年,刘子衡到济南,考入国立青岛大学补习班。他因学业优异、见解独到,深受该校筹委会主任蔡元培的赏识。刘子衡在青岛大学学习期间,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对我国东北的侵略战争,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结果被迫休学。回到他阔别多年的家乡,在滕县师范任国文教员。他教授的是国文知识,同时向学生传授救国思想。授课之余,潜心研究学问。他博览强记,勤于经史,旁及佛道,尤长于《周易》和诸子研究,有“三玄专家”之美称。国民党党政军要员也经常邀请他讲学。
他曾应邀到南京给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讲学。林森本来要求刘子衡为其解读《周易》,推测自然和社会的变化。但在讲学过程中,刘子衡根据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讲了另一个题目:“俱立则治,共同抗日,则民族可兴;偏立则乱,内战不休,则国家必亡”。时而讲历史,进而讲国情;时而讲政治,时而又讲时局,总把抗日救国道理,贯穿于讲学内容之中。他巧妙地对蒋介石所谓的“攘夕卜必先安内”反动政策,进行了有力批驳。刘子衡借给冯玉祥讲《易经》之机,点出他多次失败的原因,是缺少正确的政治方针和知人善任之明。“《易》者,变也; 要随‘时’而变,审时度势,掌握住时机,才能成就大事。当此民族危亡之秋,正英雄大展抱负之时,应重振张家口抗日精神,不为一时名利所羁绊,联合真实抗日之朋友,‘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以完成抗日救国大业,自可名垂青史。”这些观点,冯玉祥极为钦服。在为柏烈武、冯玉祥讲学时,何应钦等国民党要人,也闻讯前来听讲。“刘大师”的名字开始在国民党军政界传播开来。“七•七”事变后,形势日益严峻。11月上海陷落,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刘子衡随冯玉祥到徐州,会见李宗仁,指出“坚决抗战,则民族可兴;不坚决抗战,则国家必亡。”并说: “此次战役,必定获胜;将军建功,在此一举。”这些话,为台儿庄大战的胜利,点出伏笔。
1939年初,刘子衡到西安讲学。先后为顾希平、董介生、胡宗南等西安军政官员和大专学校师生举办讲座。对胡等主要讲经学、子学;对师生主要做学术讲演、宣传和鼓动抗日。在给胡、顾、董等讲学时,随时借题发挥,激发其爱国热情,提高全民族团结一致对敌的觉悟。当时,胡宗南住下马陵,院内有董仲舒的墓,墓前石刻有一幅对联:“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当给胡宗南等人讲董仲舒“天人相与”学说时,提到这副对联,他说:“这对联是恭维董仲舒的,其实董并未做到。他是计利计功的。我认为应改为‘正其谊亦谋其利,明其道亦计其功’才对。就我们当前来说,就是要明晓民族大义,外无私产,内无私心,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战,谋求抗战的彻底胜利。‘明其道’、‘计其功就是明白抗战的正确战略方针,去创建复兴中华民族的丰功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