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心血付管城
| 内容出处: | 《郯城文史资料第十六辑》 图书 |
| 唯一号: | 150020020220012315 |
| 颗粒名称: | 一生心血付管城 |
| 分类号: | J03 |
| 页数: | 22 |
| 页码: | 313-334 |
| 摘要: | 韩烽老师生于1925年,卒于1975年,山东泰安人,中国美术家协会山东分会会员。1952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学院艺术系,来郯城工作后,先后在马头一中、郯城三中任教,1970年调入县文化馆从事美术创作工作。他为郯城的美术教育事业、美术创作、普及工作做了很大贡献。从街头矗立的巨幅“主席像”、鼓舞人心、振奋斗志的宣传画,各种类型、各种政治内容的展览,到大批判专栏,宣传橱窗,各类会议的宣传标语;从县城到乡村,到处都有他的笔迹。 |
| 关键词: | 文艺工作者 韩烽 |
内容
韩烽老师生于1925年,卒于1975年,山东泰安人,中国美术家协会山东分会会员。1952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学院艺术系,来郯城工作后,先后在马头一中、郯城三中任教,1970年调入县文化馆从事美术创作工作。他为郯城的美术教育事业、美术创作、普及工作做了很大贡献。从街头矗立的巨幅“主席像”、鼓舞人心、振奋斗志的宣传画,各种类型、各种政治内容的展览,到大批判专栏,宣传橱窗,各类会议的宣传标语;从县城到乡村,到处都有他的笔迹。他只要工作需要,水彩画、中国画、连环画、宣传画,山水、人物、花卉、翎毛、漫画、雕塑、木刻、插图无不涉猎。他对书法的各种书体,乃至美术字,刻板漏印无不精通。他的作品何止万计,十万计,可是他身后却没能留下多少作品,但他那高尚的人格,认真、勤恳的工作态度;渊博的学识及对同事,对学生的谦和,在人们心中永不泯灭,使他所热爱,所从事的美术事业薪火相传。
五十年代初期,韩烽老师在郯城是唯一接受过大学正规美术教育的、艺术素养全面的青年教师。他兴趣广泛、朝气蓬勃,喜欢篮球、排球,爱好吹打弹拉等音乐活动,象一个文化使者,在基层、在学校、在学生中间传播着艺术的种子,影响、带动了一大批人。早在五、六十年代,他就将郯城的学生培养、输送到浙江美术学院、山东艺术学院等高等艺术学府深造,他的学生现在很多都是教授、副教授。他的子女在他的影响下,也都传承他的衣钵,有的在本县从事美术宣传工作,有的在高等艺术院校任教授、研究生导师。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讲是个“教书匠”。调到县文化馆,也是个极普通的美术干部。1975年,他病逝时“文革”还未结束,极左路线还在扭曲着人性,没有吹鼓手,没有哀乐,只有几个年幼的子女领着他的灵柩。但灵柩的后边,却是自发的送葬队伍及一条长长的花圈长龙。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那些平淡的日子,却显示着他的不平凡。许多机关、学校、农村在悼念他,同事、好友、学生在悼念他,这是一首无声的颂歌;他的棺木悄悄埋在郯城的土地上,但在人们心目中却矗立着无形的丰碑。
我认识韩烽老师是在1965年秋,暑假开学之后。当时在马头一中的高中部搬到了郯城三中。我做为郯城三中刚升入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并不了解这些变故,只是懵懵懂懂看到校园里多了许多人高马大的“大学生”。后来学校成立“课外美术活动小组”,班主任就推荐了我。韩老师就是“美术小组”的任课老师和直接组织、倡导者。我当时刚十四岁,人长的矮小,生的老实,看到韩老师高高的个子,背微躬,瘦削的脸上尽管老是有笑容,但我心里老是很害怕。美术小组活动、上课就在操场东侧的艺体教研组,两间房子中还有体育、音乐老师在里面办公。美术组活动是每天下午课后,别的同学都在操场活动,而我们十几个学生则静悄悄集合在一起开始上课。美术组好多人都是随韩老师从马头一中高中部来的学生,是我眼中的“大人”,其中有几个正准备考大学的学生。韩老师讲的第一课由于我过于紧张,又坐在远处角落,加上操场上同学的嘈杂声,我几乎没听见,因此也没有太多的印象,但是从此开始了从未见过的写生、速写训练。同学们围在一起,互相画,韩老师只要有时间,就随大家一起画,或者在室内踱来踱去。我很小的时候喜欢“小画书”(连环画),喜欢照着上面的人物乱画,由于我有临摹连环画的基本功,写生时的抓型能力经常受到韩老师的表扬,胆也越来越大。正是在老师的鼓励下,我的绘画兴趣愈来愈浓,与美术结下了不解之缘,美术成了我的终生爱好、半生职业。
1965年底,省里举办一个少年美术作品征稿活动,韩老师反复启发我们每人构思一幅画,要全凭自己想像。先是用铅笔画小稿,定题材,围绕着要表现的情节,韩老师还带我们去搜集素材。当时郯三中紧挨的古城墙栽满了桃树,老师带着我们去桃林写生,又到实验室写生化学实验器材。这次活动虽小,但在我心中留下深刻印象,这种正规的创作方法、步骤奠定了我在以后的美术创作活动中的基本知识与能力。美术小组的活动持续了几个月,到文革开始便自动结束了。
文革开始后学校成立了“漫画小组”,可能是韩老师的推荐,我被吸收进去。组内整个气氛比较沉闷,韩老师脸上已少有笑容,同室的其他老师也都板着脸,说话及进出的声音都很小。由于漫画组大多都是老师,再加上当时的政治气氛,我就更加拘谨,连气都不敢大声出。开始画的内容是揭发出来本校几位“黑帮”的历史及“罪行”,其形式是连环漫画、流水作业式。我和韩老师一组,先是韩老师用铅笔起完草稿,然后指导着我着颜色,基本是单线平涂。韩老师边示范边小声地教我怎样画,使我了解了颜色的调配及画面色彩的搭配,什么样的人物,穿什么服装,什么颜色。知道了人物脸部和衣物有凹凸、阴阳、表里之分。着完色后,再由韩老师勾墨线,统一定稿。几天以后,韩老师就让我根据批判材料的文字(角本)自己构思起草。大批判材料许多都是很抽象的,有许多事情是一个初中生根本不理解和不知道的,还得--请教韩老师。
一天,我在着色整理漫画作品时,看到一个黑伞下面,掩藏几个“牛鬼蛇神”,一个人的身边明明写着“韩烽”二字,我大惊失色,偷偷看韩老师一眼,他仍在平静的做着手边的事情。现在想起来,韩老师由于出身问题,已经承受着沉重的思想压力,还不厌其烦、手把手教我这样一个笨孩子,这需要什么样的心境和耐力。正是有了这一段训练,我的创作能力、表现能力,尤其是想象力的发挥和表现手法的多样,成稿的速度、效率都引得老师和同行的赞许。年纪轻轻的我就在县里展露头角、小有名气了。可惜的是在那个年代,才华都用到了无限反复的政治运动中。我作为一个年轻学生,把一切都当作画来画。象韩老师一辈人,特别是象他那样的知识分子,是怎样的违心和痛苦。后来形势更乱,学校造反派战斗队越来越多,校长、书记都成了被批判、被画的对象,官办的漫画小组解了体。韩烽老师也被地区、县里调出搞展览。剩下几位老师研究怎样用"三合板”刻印“主席像”搞红海洋、语录台之类。没人再给我安排具体任务,我乐得回到同学中间,开会、喊口号,反正不上课是很高兴的。打牌、下军棋、下河洗澡、摸鱼逍遥起来,也就再也没有见过韩老师。1968年我被机械厂招工,当了学徒。有一天,厂里突然通知我到县里帮忙,我到县委小礼堂报到,原来是韩老师受命筹备“一打三反”展览。他是从大街上批判栏知道我的下落,并推荐了我,从此开始了与韩老师的长期接触,直到他去世。
“一打三反”展览是县里组建了一个展览班子,已经筹备了很长时间。原班人马都是从教育、乡镇抽调的,有些人的绘画水平太差。为了把这次展览办成高规格的,县里才把韩老师调过来,进行突击加工。重新抽调的人员中间,韩老师既是老师,又是年长者,工作又负责任,实际上成了核心人物,成了头。韩老师就组织抽调的人员对原来的内容、版面、文字重新进行调整、更换。多年不见,这时韩老师已没有文革初期那种沉闷情绪,接触的多了,在他身上发现了更多的和蔼可亲、可敬之处。当时负责展览美术部分的,象季相玉、朱利和、李瑞东、徐敏生等都是20多岁,对韩老师都是执师生之礼。他在青年人中间有说有笑,同和他年龄相仿的刘春辉等人,也时时幽上一默,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展览的文字内容专门由文字组负责,多有揭露某人男女作风问题(这是国人臭人的方式)。一般的表现方法都是画男女搂抱在一起,或画在窗上投过男女相拥的黑影。记得韩老师画的则是垂下的蚊帐,床前摆着两双鞋,其中一只男鞋压在一只女鞋的上面。人物没有出现,“此时无人胜有人”其含蓄的表现手法,引起大家的称赞。有一次,韩老师画一个“坏”女人,老是画的不坏,正在改来改去,李瑞东嘻笑着在一旁说:“韩老师把人画的和你一样老实,怎么能坏起来呢?”于是他拿过笔来,将她的眼珠画的朝一侧斜视,画上的女人顿显的风流,大家都调笑道:“还是瑞东有生活!”。我们几个人画到兴致高时,还哼上几段样板戏。尽管任务很重,是突击性的,经常加夜班,在韩老师带动下,还是按时完成了任务。除了把展览馆全部布置完毕,还画了一部分漫画,到街头、集市巡回展出。这期间接触人多了,我了解了美术原来还有这么多画种,有众多流派,见识与水平有了很大提高。韩老师指出:“你有临摹小人的基本功,又有扎实的写生速写能力,从事人物画有别人不可比拟的条件,但也不能光画小人,对山水、树木都要掌握,毛笔字也不能忽视。”他拿出一本碑拓字贴,让我临写,并鼓励说:“字无百日功,只要写就比不写强,先写写楷书,再写写隶书。” 可惜当时没能领会老师的教诲,碑帖拿回家放在枕边,“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直到今日,字也没练成。后来韩老师调到文化馆,又因工作关系抽调我随他一起参加了几次活动。
当时推行的是“三结合”创作方法。《一部脱谷机》是我县青年农民作者的一篇小说,后改编为连环画《麦场风波》。美术创作任务由韩烽老师、八零三矿工人吕顺旗担任。我随韩、吕到农村搜集创作素材,画了大量的农村场景,劳动工具,车、马、牛、羊、树木、村舍等等,锻炼提高了我的写生能力,了解了一本书、一幅画的创作产生过程。一本连环画近200幅独立的画面,集中在文化馆画正稿,老是脱不开繁杂的零星任务和众多的来访者。领导就让韩老师与吕顺旗搬到八零三矿,住下来潜心搞好创作,不料一天夜里,因派性发生了械斗,连矿区的围墙也被推倒,紧急中矿长让韩老师赶快离开,避免受到牵连,发生危险。仓惶中韩老师只身一人连夜回到县城,衣物都丢到矿上。特别是损失了许多珍贵的美术资料让韩老师心痛不已,加上受到惊吓又深夜奔波几十里路,使他的身心都受到很大的伤害。一九七三年冬天领导安排到何围子生产队帮助画村史教育展览,当时天气非常寒冷,韩老师已是肝病缠身,他完全可以推辞也应该请假,可是他还是接受了这个任务。每天早出晚归忙工作,早饭后骑自行车到何围子,照样深入农户、田间地头搜集素材。记得其中有反映村里地富分子破坏农田建设和鱼塘的内容,韩老师就带我到地头认真画了机井、水泵、抽水机、养鱼池等景物道具。年方二十的我,血气方刚,体会不到韩老师病弱之体,在田间跨水渠、迈田埂是特别吃力。中午饭在村里吃,生产队拿出上等菜,记得是和豆腐块一样大小、白花花的肥肉膘子一盆,韩老师根本吃不下,几乎没有动筷子。晚上,回家的路上,韩老师的身体已经疲惫不堪,走走停停,距家十里的路程走了近一个小时。我以极慢的速度缓缓前行,时而停下来等着韩老师,回头看到:寒风中,夕阳下,韩老师吃力的骑着自行车,一件灰色的呢子大衣,一条长长的围巾,仍顶不住晚风的侵袭,郯马路两旁高高的白杨树,在凛冽的寒风中颤抖着,偶尔飘零着几片枯黄的树叶,暮色中,有几只归巢的寒鸦在枝头掠过。残照中他那萎缩的身影,显得瘦弱无助,怎么也想象不到,眼前这样一位老人曾是一米八五的个子、学校教工篮球队的主力运动员。我心中突然涌起一种莫名的悲壮,眼睛不觉有些湿润。
后来,全省在郯城召开“沼气现场会”,紧急抽调韩老师、李瑞东、朱利和、季相玉和我。除了布置会场,绘制幻灯外,重点布置招待所会议室、招待室等,韩老师不但要总体协调、布置、安排具体分工,自己还要绘制一幅大型山水画。别人都年轻力壮,分工之后大家都分头行动,会议室只剩下韩老师和我。当时宣纸只有四尺的,画大画要分几张拼接,没有毛毡,下面铺报纸。记得韩老师画的是一幅小青绿山水画,尺寸约在5平方米。小青绿画法更须反复勾勒、皴擦、点染,需要作者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夜深了白炽灯光下韩老师聚精会神地作画,整个会议室内只有他的抽烟声、喘息声,笔与纸的摩擦声,静的似乎听得到灯发光的声音。我只能帮助作些辅助工作,待作品完成后再帮助裱画上版、装饰定框。一时插不上手,忍不住哈欠连天,韩老师就让我先休息一会。开始我还硬撑着陪他,后来实在熬不住就睡在一旁。等我醒来,韩老师正坐在联椅上低垂着头休息,苍白的脸上充满精疲力竭的神色,旁边是刚刚完成的一幅秀丽的画作,地上满是烟蒂。我请韩老师抓紧去睡一会,他只是苦笑着摇摇头,抽了几口烟后又起身统篇调整,收拾画面,落款盖章。天亮了,人渐渐多了起来,又有许多想不到的未尽事宜安排下来。两天一夜下来,韩老师脚肿的连鞋都无法穿・。现场会如期召开了,韩老师却躺在了病床上。
韩老师失去工作能力了,我仍按习惯到他家去,他有时躺在床上与我交谈几句,有时起身到书箱拿出《美术》《世界名画》等给我翻阅,或者给我纸笔、颜料到文化馆展览室临摹画。我当时不喜欢国画,热衷于水粉、油画,临过汤小铭的《女委员》,朱乃正的《新门巴》,董辰生的《红灯记》、《黄继光》等作品。有时我画的入了迷,忘记了时间,韩老师总是留下我吃饭,临的好,和原作神似的,有点滴进步,韩老师病弱的脸上总是露出笑容,给予肯定,不足之处给予指点,有时我流露出苦恼,韩老师耐心地给予启发、教诲,并常以他自己举例说:“画到一个阶段,总要面临一个台阶,越过这个陡坡,水平和境界就有一个提升和飞跃。”并多次鼓励我坚持下去,将来推荐我考浙江美术学院。
后来我因厂里工作忙和个人事务多,很少再到韩老师家中,对韩老师的境况知之不多。可是,韩老师知道我要结婚了,亲自画了一幅山水中堂,裱好并配上隶书对联,临近喜期专程让师母连同一件绸子袄面送给我,连我喜房、大门的喜联,都是他亲自用红纸写好派人送来的。我叫他老师,是因为他的职业是老师,教过我美术课。我未向他行过拜师之礼,也从未送过礼,以我的才能,悟性远不够其学生这种资格。他对我这个美术爱好者无微不至的关怀,体现了一个专业美术工作者,甘做铺路石,甘为孺子牛的精神。
据我所知,韩老师的入室弟子并不多,但是他的学生却很多很多,在实际工作中受到他精心指导、言传身教的美术工作者、爱好者数不胜数。即使他在家养病休息,许多从农村、工矿前来求教、看画的人也不少,他都硬撑起来,耐心热情接待,将自己的书法、美术资料借给他们,困难的还赠画赠笔。有的痴迷者简直象个神经病,坐在家中不走,韩老师还要强扶病体,搭上时间陪着,谈到吃饭时间还要招待。有些人借走的资料干脆就不送还了,韩老师从不计较。他脸上一直都是和蔼可亲,宽容宽厚的笑容,从没流露出丝毫的厌倦。
在家中,韩老师是个慈父,对孩子从不打骂。即使有了过失,最多用一个“贼”字,算是责骂。他对子女的学习要求严格,经常检查他们的作业并指导他们进行美术基础训练。吕顺旗是山艺毕业,受过规范的基础训练,当时借调在文化馆。忙完任务之余,韩老师总是组织我们几个人在一起画画素描、速写,也是一种互相学习。只要孩子在家,总是把孩子叫过来一起画,“感受感受”。潜移默化中使孩子幼小的心灵受到艺术的感染与熏陶。他在病重期间仍指导小儿子菊声创作作品参加全省的一次展览,表现的题材是一个老干部在夜间查巡。当时菊声刚十四岁,为了帮助他画准人物动态,韩老师支撑着病体为他做模特,摆个手举罩子灯的动作让他写生,还为儿子刻了一方小图章,加盖在画面上。记得一年春节,他亲自为小女儿笑梅扎制一个很大的花鼓灯,并在灯上题诗作画,专门画了女儿最喜欢的梅花,题上女儿的名字。小笑梅爱不释手,等不到天黑就关上房门,点着灯笼四处乱照。红红的烛光照亮室内,孩子们欢笑嬉闹,感染了每个人。
韩老师比较爱干净,最不能容忍苍蝇。而他在文化馆的宿舍与村民临墙,村民将厕所和粪池建在靠文化馆一侧,除冬天外其余时间苍蝇到处飞。当时又无纱门、纱窗,韩老师手中总拿着一个硕大的苍蝇拍,有时正说着话就突然站起来,去拍打苍蝇。他的许多作品都是在这种环境中酝酿、创作出来的。韩老师为了创作表现“沂水东调工程”的大幅国画,他多次到东调工程深入生活,画了大量的速写。为了表现“战天斗地、人山人海”的场面,作品中刻画了推车、拉车、挖土等等人物,形态各异,何止百千。在创作国画《喜看稻菽千重浪》时,为将伟人毛泽东与农民的形象刻画得更为准确、传神,反复修改,其创作态度严谨使我们这些年轻人为之动容。当时由于政治的需要,创作受表现内容的约束及表现形式的羁绊,多突出“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和“革命新生事物”,韩老师常流露出为自己不是学人物画的而遗憾。为弥补自己这方面的不足,适应工作需要,他不耻下问,常常向身边的年轻人学习请教。他常戴着花镜或手拿放大镜仔细研究印刷并不精良的宣传画册,以探求其中的技法。
在我的印象当中,韩老师在工作上对组织服从、对领导尊重、对同事谦让,凡是安排的事从来没说过“不”。他住在文化馆一间半旧房里,不论公事私事,许多人找不到办公室,找不到领导,就都找到他的门上。是工作他都接受,即使在他病重期间,考虑到别人家远、有孩子、有家务,许多工作和烦杂的事务他都承担下来。韩老师不是党员,也不是领导干部,在那种特定环境下,在有些人眼中还有“问题”,但他那虚怀若谷的长者风度、宽厚的为人,他一生心血付管城的工作态度和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奉献精神,直到今天仍是值得我们学习、推崇的。
在我的心目中,韩老师既是一个严格的老师,又是一个和蔼的长者,一个可亲可敬的人。对于他的其他方面了解甚少,在他去世多年后我才知道,他是全临沂地区屈指可数的中国美术家协会山东分会的会员,是山东省著名画家、教育家、山东艺术学院院长于希宁先生的高徒。在山师学习期间是学校的高才生,曾任班长。毕业后,响应党的号召,满腔热血来到沂蒙地区郯城县工作。他主攻山水画,青绿、浅绛无不擅长;花卉颇具吴昌硕、潘天寿等大家气度,对金石、书法也有很高的造诣。家属在农村教学,几个子女小时家累较重,为了不误工作,上班时都将孩子锁在家里,或将孩子放在堆了沙子的缸里。调到县文化馆后,更是一心一意扑在全县的美术工作中,他当时正值中年,上有年迈的二老,下有几个少不更事的子女,任劳任怨,忍辱负重,其苦其累,可想而知。但是由于我年轻,作为学生、同事对此一无所知,没能对老师有一点帮助或回报。每每想起,悔愧之情无以言表。早想写写韩烽老师,自己虽在他身边多年,但当时太年轻又不是善于用心用脑之人,加上文笔太差,怕一旦成文,有损韩老师的形象。而今自己也是年过五十之人了,事隔二、三十年,但老师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总觉得不向后人诉说老师的事情,难了自己的心愿,尽管所记这些只是几件平凡之事。张宏亮
五十年代初期,韩烽老师在郯城是唯一接受过大学正规美术教育的、艺术素养全面的青年教师。他兴趣广泛、朝气蓬勃,喜欢篮球、排球,爱好吹打弹拉等音乐活动,象一个文化使者,在基层、在学校、在学生中间传播着艺术的种子,影响、带动了一大批人。早在五、六十年代,他就将郯城的学生培养、输送到浙江美术学院、山东艺术学院等高等艺术学府深造,他的学生现在很多都是教授、副教授。他的子女在他的影响下,也都传承他的衣钵,有的在本县从事美术宣传工作,有的在高等艺术院校任教授、研究生导师。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讲是个“教书匠”。调到县文化馆,也是个极普通的美术干部。1975年,他病逝时“文革”还未结束,极左路线还在扭曲着人性,没有吹鼓手,没有哀乐,只有几个年幼的子女领着他的灵柩。但灵柩的后边,却是自发的送葬队伍及一条长长的花圈长龙。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那些平淡的日子,却显示着他的不平凡。许多机关、学校、农村在悼念他,同事、好友、学生在悼念他,这是一首无声的颂歌;他的棺木悄悄埋在郯城的土地上,但在人们心目中却矗立着无形的丰碑。
我认识韩烽老师是在1965年秋,暑假开学之后。当时在马头一中的高中部搬到了郯城三中。我做为郯城三中刚升入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并不了解这些变故,只是懵懵懂懂看到校园里多了许多人高马大的“大学生”。后来学校成立“课外美术活动小组”,班主任就推荐了我。韩老师就是“美术小组”的任课老师和直接组织、倡导者。我当时刚十四岁,人长的矮小,生的老实,看到韩老师高高的个子,背微躬,瘦削的脸上尽管老是有笑容,但我心里老是很害怕。美术小组活动、上课就在操场东侧的艺体教研组,两间房子中还有体育、音乐老师在里面办公。美术组活动是每天下午课后,别的同学都在操场活动,而我们十几个学生则静悄悄集合在一起开始上课。美术组好多人都是随韩老师从马头一中高中部来的学生,是我眼中的“大人”,其中有几个正准备考大学的学生。韩老师讲的第一课由于我过于紧张,又坐在远处角落,加上操场上同学的嘈杂声,我几乎没听见,因此也没有太多的印象,但是从此开始了从未见过的写生、速写训练。同学们围在一起,互相画,韩老师只要有时间,就随大家一起画,或者在室内踱来踱去。我很小的时候喜欢“小画书”(连环画),喜欢照着上面的人物乱画,由于我有临摹连环画的基本功,写生时的抓型能力经常受到韩老师的表扬,胆也越来越大。正是在老师的鼓励下,我的绘画兴趣愈来愈浓,与美术结下了不解之缘,美术成了我的终生爱好、半生职业。
1965年底,省里举办一个少年美术作品征稿活动,韩老师反复启发我们每人构思一幅画,要全凭自己想像。先是用铅笔画小稿,定题材,围绕着要表现的情节,韩老师还带我们去搜集素材。当时郯三中紧挨的古城墙栽满了桃树,老师带着我们去桃林写生,又到实验室写生化学实验器材。这次活动虽小,但在我心中留下深刻印象,这种正规的创作方法、步骤奠定了我在以后的美术创作活动中的基本知识与能力。美术小组的活动持续了几个月,到文革开始便自动结束了。
文革开始后学校成立了“漫画小组”,可能是韩老师的推荐,我被吸收进去。组内整个气氛比较沉闷,韩老师脸上已少有笑容,同室的其他老师也都板着脸,说话及进出的声音都很小。由于漫画组大多都是老师,再加上当时的政治气氛,我就更加拘谨,连气都不敢大声出。开始画的内容是揭发出来本校几位“黑帮”的历史及“罪行”,其形式是连环漫画、流水作业式。我和韩老师一组,先是韩老师用铅笔起完草稿,然后指导着我着颜色,基本是单线平涂。韩老师边示范边小声地教我怎样画,使我了解了颜色的调配及画面色彩的搭配,什么样的人物,穿什么服装,什么颜色。知道了人物脸部和衣物有凹凸、阴阳、表里之分。着完色后,再由韩老师勾墨线,统一定稿。几天以后,韩老师就让我根据批判材料的文字(角本)自己构思起草。大批判材料许多都是很抽象的,有许多事情是一个初中生根本不理解和不知道的,还得--请教韩老师。
一天,我在着色整理漫画作品时,看到一个黑伞下面,掩藏几个“牛鬼蛇神”,一个人的身边明明写着“韩烽”二字,我大惊失色,偷偷看韩老师一眼,他仍在平静的做着手边的事情。现在想起来,韩老师由于出身问题,已经承受着沉重的思想压力,还不厌其烦、手把手教我这样一个笨孩子,这需要什么样的心境和耐力。正是有了这一段训练,我的创作能力、表现能力,尤其是想象力的发挥和表现手法的多样,成稿的速度、效率都引得老师和同行的赞许。年纪轻轻的我就在县里展露头角、小有名气了。可惜的是在那个年代,才华都用到了无限反复的政治运动中。我作为一个年轻学生,把一切都当作画来画。象韩老师一辈人,特别是象他那样的知识分子,是怎样的违心和痛苦。后来形势更乱,学校造反派战斗队越来越多,校长、书记都成了被批判、被画的对象,官办的漫画小组解了体。韩烽老师也被地区、县里调出搞展览。剩下几位老师研究怎样用"三合板”刻印“主席像”搞红海洋、语录台之类。没人再给我安排具体任务,我乐得回到同学中间,开会、喊口号,反正不上课是很高兴的。打牌、下军棋、下河洗澡、摸鱼逍遥起来,也就再也没有见过韩老师。1968年我被机械厂招工,当了学徒。有一天,厂里突然通知我到县里帮忙,我到县委小礼堂报到,原来是韩老师受命筹备“一打三反”展览。他是从大街上批判栏知道我的下落,并推荐了我,从此开始了与韩老师的长期接触,直到他去世。
“一打三反”展览是县里组建了一个展览班子,已经筹备了很长时间。原班人马都是从教育、乡镇抽调的,有些人的绘画水平太差。为了把这次展览办成高规格的,县里才把韩老师调过来,进行突击加工。重新抽调的人员中间,韩老师既是老师,又是年长者,工作又负责任,实际上成了核心人物,成了头。韩老师就组织抽调的人员对原来的内容、版面、文字重新进行调整、更换。多年不见,这时韩老师已没有文革初期那种沉闷情绪,接触的多了,在他身上发现了更多的和蔼可亲、可敬之处。当时负责展览美术部分的,象季相玉、朱利和、李瑞东、徐敏生等都是20多岁,对韩老师都是执师生之礼。他在青年人中间有说有笑,同和他年龄相仿的刘春辉等人,也时时幽上一默,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展览的文字内容专门由文字组负责,多有揭露某人男女作风问题(这是国人臭人的方式)。一般的表现方法都是画男女搂抱在一起,或画在窗上投过男女相拥的黑影。记得韩老师画的则是垂下的蚊帐,床前摆着两双鞋,其中一只男鞋压在一只女鞋的上面。人物没有出现,“此时无人胜有人”其含蓄的表现手法,引起大家的称赞。有一次,韩老师画一个“坏”女人,老是画的不坏,正在改来改去,李瑞东嘻笑着在一旁说:“韩老师把人画的和你一样老实,怎么能坏起来呢?”于是他拿过笔来,将她的眼珠画的朝一侧斜视,画上的女人顿显的风流,大家都调笑道:“还是瑞东有生活!”。我们几个人画到兴致高时,还哼上几段样板戏。尽管任务很重,是突击性的,经常加夜班,在韩老师带动下,还是按时完成了任务。除了把展览馆全部布置完毕,还画了一部分漫画,到街头、集市巡回展出。这期间接触人多了,我了解了美术原来还有这么多画种,有众多流派,见识与水平有了很大提高。韩老师指出:“你有临摹小人的基本功,又有扎实的写生速写能力,从事人物画有别人不可比拟的条件,但也不能光画小人,对山水、树木都要掌握,毛笔字也不能忽视。”他拿出一本碑拓字贴,让我临写,并鼓励说:“字无百日功,只要写就比不写强,先写写楷书,再写写隶书。” 可惜当时没能领会老师的教诲,碑帖拿回家放在枕边,“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直到今日,字也没练成。后来韩老师调到文化馆,又因工作关系抽调我随他一起参加了几次活动。
当时推行的是“三结合”创作方法。《一部脱谷机》是我县青年农民作者的一篇小说,后改编为连环画《麦场风波》。美术创作任务由韩烽老师、八零三矿工人吕顺旗担任。我随韩、吕到农村搜集创作素材,画了大量的农村场景,劳动工具,车、马、牛、羊、树木、村舍等等,锻炼提高了我的写生能力,了解了一本书、一幅画的创作产生过程。一本连环画近200幅独立的画面,集中在文化馆画正稿,老是脱不开繁杂的零星任务和众多的来访者。领导就让韩老师与吕顺旗搬到八零三矿,住下来潜心搞好创作,不料一天夜里,因派性发生了械斗,连矿区的围墙也被推倒,紧急中矿长让韩老师赶快离开,避免受到牵连,发生危险。仓惶中韩老师只身一人连夜回到县城,衣物都丢到矿上。特别是损失了许多珍贵的美术资料让韩老师心痛不已,加上受到惊吓又深夜奔波几十里路,使他的身心都受到很大的伤害。一九七三年冬天领导安排到何围子生产队帮助画村史教育展览,当时天气非常寒冷,韩老师已是肝病缠身,他完全可以推辞也应该请假,可是他还是接受了这个任务。每天早出晚归忙工作,早饭后骑自行车到何围子,照样深入农户、田间地头搜集素材。记得其中有反映村里地富分子破坏农田建设和鱼塘的内容,韩老师就带我到地头认真画了机井、水泵、抽水机、养鱼池等景物道具。年方二十的我,血气方刚,体会不到韩老师病弱之体,在田间跨水渠、迈田埂是特别吃力。中午饭在村里吃,生产队拿出上等菜,记得是和豆腐块一样大小、白花花的肥肉膘子一盆,韩老师根本吃不下,几乎没有动筷子。晚上,回家的路上,韩老师的身体已经疲惫不堪,走走停停,距家十里的路程走了近一个小时。我以极慢的速度缓缓前行,时而停下来等着韩老师,回头看到:寒风中,夕阳下,韩老师吃力的骑着自行车,一件灰色的呢子大衣,一条长长的围巾,仍顶不住晚风的侵袭,郯马路两旁高高的白杨树,在凛冽的寒风中颤抖着,偶尔飘零着几片枯黄的树叶,暮色中,有几只归巢的寒鸦在枝头掠过。残照中他那萎缩的身影,显得瘦弱无助,怎么也想象不到,眼前这样一位老人曾是一米八五的个子、学校教工篮球队的主力运动员。我心中突然涌起一种莫名的悲壮,眼睛不觉有些湿润。
后来,全省在郯城召开“沼气现场会”,紧急抽调韩老师、李瑞东、朱利和、季相玉和我。除了布置会场,绘制幻灯外,重点布置招待所会议室、招待室等,韩老师不但要总体协调、布置、安排具体分工,自己还要绘制一幅大型山水画。别人都年轻力壮,分工之后大家都分头行动,会议室只剩下韩老师和我。当时宣纸只有四尺的,画大画要分几张拼接,没有毛毡,下面铺报纸。记得韩老师画的是一幅小青绿山水画,尺寸约在5平方米。小青绿画法更须反复勾勒、皴擦、点染,需要作者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夜深了白炽灯光下韩老师聚精会神地作画,整个会议室内只有他的抽烟声、喘息声,笔与纸的摩擦声,静的似乎听得到灯发光的声音。我只能帮助作些辅助工作,待作品完成后再帮助裱画上版、装饰定框。一时插不上手,忍不住哈欠连天,韩老师就让我先休息一会。开始我还硬撑着陪他,后来实在熬不住就睡在一旁。等我醒来,韩老师正坐在联椅上低垂着头休息,苍白的脸上充满精疲力竭的神色,旁边是刚刚完成的一幅秀丽的画作,地上满是烟蒂。我请韩老师抓紧去睡一会,他只是苦笑着摇摇头,抽了几口烟后又起身统篇调整,收拾画面,落款盖章。天亮了,人渐渐多了起来,又有许多想不到的未尽事宜安排下来。两天一夜下来,韩老师脚肿的连鞋都无法穿・。现场会如期召开了,韩老师却躺在了病床上。
韩老师失去工作能力了,我仍按习惯到他家去,他有时躺在床上与我交谈几句,有时起身到书箱拿出《美术》《世界名画》等给我翻阅,或者给我纸笔、颜料到文化馆展览室临摹画。我当时不喜欢国画,热衷于水粉、油画,临过汤小铭的《女委员》,朱乃正的《新门巴》,董辰生的《红灯记》、《黄继光》等作品。有时我画的入了迷,忘记了时间,韩老师总是留下我吃饭,临的好,和原作神似的,有点滴进步,韩老师病弱的脸上总是露出笑容,给予肯定,不足之处给予指点,有时我流露出苦恼,韩老师耐心地给予启发、教诲,并常以他自己举例说:“画到一个阶段,总要面临一个台阶,越过这个陡坡,水平和境界就有一个提升和飞跃。”并多次鼓励我坚持下去,将来推荐我考浙江美术学院。
后来我因厂里工作忙和个人事务多,很少再到韩老师家中,对韩老师的境况知之不多。可是,韩老师知道我要结婚了,亲自画了一幅山水中堂,裱好并配上隶书对联,临近喜期专程让师母连同一件绸子袄面送给我,连我喜房、大门的喜联,都是他亲自用红纸写好派人送来的。我叫他老师,是因为他的职业是老师,教过我美术课。我未向他行过拜师之礼,也从未送过礼,以我的才能,悟性远不够其学生这种资格。他对我这个美术爱好者无微不至的关怀,体现了一个专业美术工作者,甘做铺路石,甘为孺子牛的精神。
据我所知,韩老师的入室弟子并不多,但是他的学生却很多很多,在实际工作中受到他精心指导、言传身教的美术工作者、爱好者数不胜数。即使他在家养病休息,许多从农村、工矿前来求教、看画的人也不少,他都硬撑起来,耐心热情接待,将自己的书法、美术资料借给他们,困难的还赠画赠笔。有的痴迷者简直象个神经病,坐在家中不走,韩老师还要强扶病体,搭上时间陪着,谈到吃饭时间还要招待。有些人借走的资料干脆就不送还了,韩老师从不计较。他脸上一直都是和蔼可亲,宽容宽厚的笑容,从没流露出丝毫的厌倦。
在家中,韩老师是个慈父,对孩子从不打骂。即使有了过失,最多用一个“贼”字,算是责骂。他对子女的学习要求严格,经常检查他们的作业并指导他们进行美术基础训练。吕顺旗是山艺毕业,受过规范的基础训练,当时借调在文化馆。忙完任务之余,韩老师总是组织我们几个人在一起画画素描、速写,也是一种互相学习。只要孩子在家,总是把孩子叫过来一起画,“感受感受”。潜移默化中使孩子幼小的心灵受到艺术的感染与熏陶。他在病重期间仍指导小儿子菊声创作作品参加全省的一次展览,表现的题材是一个老干部在夜间查巡。当时菊声刚十四岁,为了帮助他画准人物动态,韩老师支撑着病体为他做模特,摆个手举罩子灯的动作让他写生,还为儿子刻了一方小图章,加盖在画面上。记得一年春节,他亲自为小女儿笑梅扎制一个很大的花鼓灯,并在灯上题诗作画,专门画了女儿最喜欢的梅花,题上女儿的名字。小笑梅爱不释手,等不到天黑就关上房门,点着灯笼四处乱照。红红的烛光照亮室内,孩子们欢笑嬉闹,感染了每个人。
韩老师比较爱干净,最不能容忍苍蝇。而他在文化馆的宿舍与村民临墙,村民将厕所和粪池建在靠文化馆一侧,除冬天外其余时间苍蝇到处飞。当时又无纱门、纱窗,韩老师手中总拿着一个硕大的苍蝇拍,有时正说着话就突然站起来,去拍打苍蝇。他的许多作品都是在这种环境中酝酿、创作出来的。韩老师为了创作表现“沂水东调工程”的大幅国画,他多次到东调工程深入生活,画了大量的速写。为了表现“战天斗地、人山人海”的场面,作品中刻画了推车、拉车、挖土等等人物,形态各异,何止百千。在创作国画《喜看稻菽千重浪》时,为将伟人毛泽东与农民的形象刻画得更为准确、传神,反复修改,其创作态度严谨使我们这些年轻人为之动容。当时由于政治的需要,创作受表现内容的约束及表现形式的羁绊,多突出“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和“革命新生事物”,韩老师常流露出为自己不是学人物画的而遗憾。为弥补自己这方面的不足,适应工作需要,他不耻下问,常常向身边的年轻人学习请教。他常戴着花镜或手拿放大镜仔细研究印刷并不精良的宣传画册,以探求其中的技法。
在我的印象当中,韩老师在工作上对组织服从、对领导尊重、对同事谦让,凡是安排的事从来没说过“不”。他住在文化馆一间半旧房里,不论公事私事,许多人找不到办公室,找不到领导,就都找到他的门上。是工作他都接受,即使在他病重期间,考虑到别人家远、有孩子、有家务,许多工作和烦杂的事务他都承担下来。韩老师不是党员,也不是领导干部,在那种特定环境下,在有些人眼中还有“问题”,但他那虚怀若谷的长者风度、宽厚的为人,他一生心血付管城的工作态度和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奉献精神,直到今天仍是值得我们学习、推崇的。
在我的心目中,韩老师既是一个严格的老师,又是一个和蔼的长者,一个可亲可敬的人。对于他的其他方面了解甚少,在他去世多年后我才知道,他是全临沂地区屈指可数的中国美术家协会山东分会的会员,是山东省著名画家、教育家、山东艺术学院院长于希宁先生的高徒。在山师学习期间是学校的高才生,曾任班长。毕业后,响应党的号召,满腔热血来到沂蒙地区郯城县工作。他主攻山水画,青绿、浅绛无不擅长;花卉颇具吴昌硕、潘天寿等大家气度,对金石、书法也有很高的造诣。家属在农村教学,几个子女小时家累较重,为了不误工作,上班时都将孩子锁在家里,或将孩子放在堆了沙子的缸里。调到县文化馆后,更是一心一意扑在全县的美术工作中,他当时正值中年,上有年迈的二老,下有几个少不更事的子女,任劳任怨,忍辱负重,其苦其累,可想而知。但是由于我年轻,作为学生、同事对此一无所知,没能对老师有一点帮助或回报。每每想起,悔愧之情无以言表。早想写写韩烽老师,自己虽在他身边多年,但当时太年轻又不是善于用心用脑之人,加上文笔太差,怕一旦成文,有损韩老师的形象。而今自己也是年过五十之人了,事隔二、三十年,但老师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总觉得不向后人诉说老师的事情,难了自己的心愿,尽管所记这些只是几件平凡之事。张宏亮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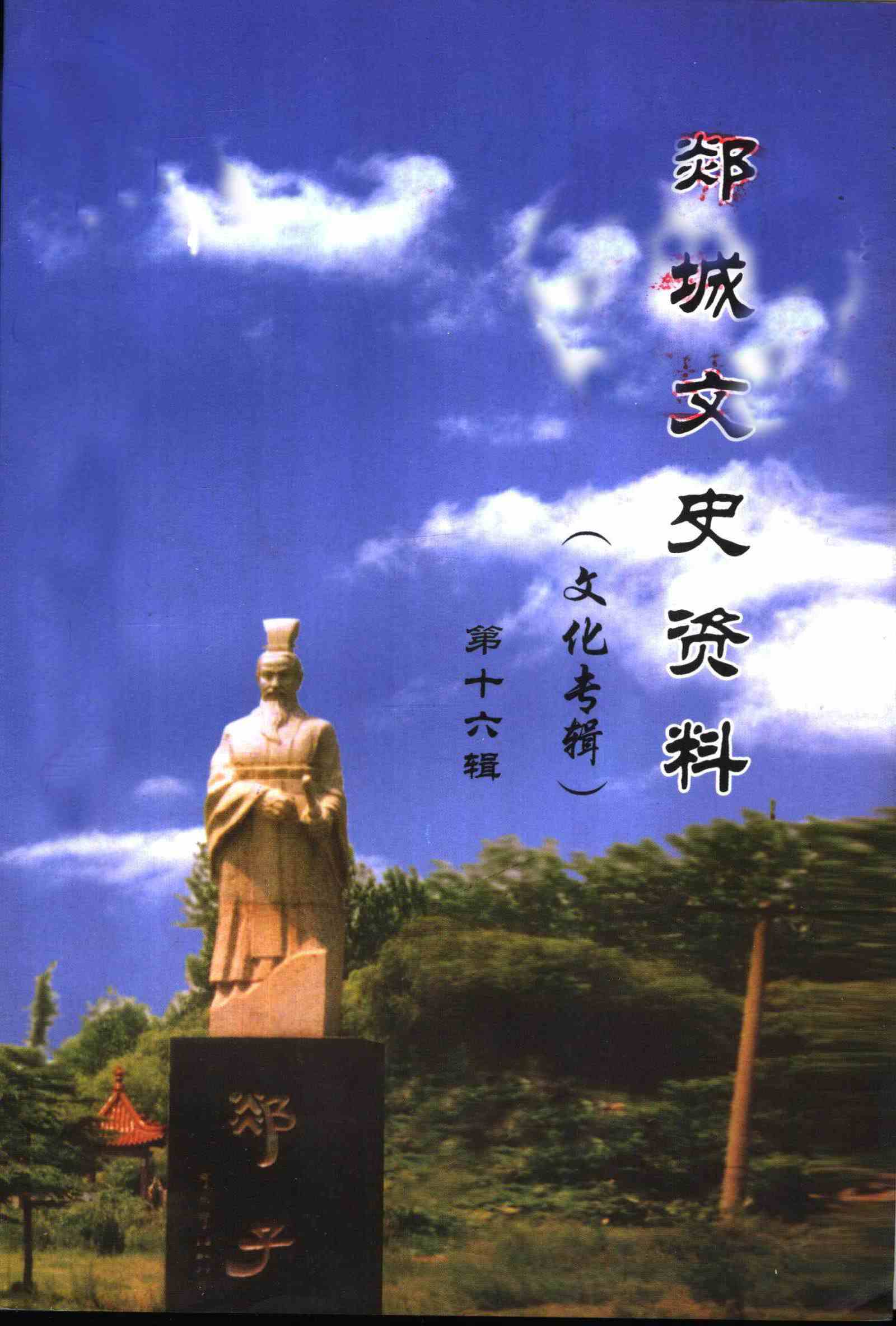
相关人物
张宏亮
责任者
相关地名
韩烽
相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