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文革''中美术活动二三事
| 内容出处: | 《郯城文史资料第十六辑》 图书 |
| 唯一号: | 150020020220012306 |
| 颗粒名称: | 忆“文革''中美术活动二三事 |
| 分类号: | F768.7 |
| 页数: | 14 |
| 页码: | 217-230 |
| 摘要: | 书法、美术在文革中象所有的文艺形式一样已经少有艺术可言,它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武器”被运用到了极至。“运动”提倡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主要载体是纸笔,至于后来动了拳头、棍棒,乃至枪炮,那是少数人背离了运动的“大方向”超越了“文斗”的范畴,自然不在此话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郯城爆发时,本人刚刚是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由于参加过学校美术组的学习训练,有一定的绘画基础,被学校文革领导小组吸收到漫画小组,随之参加了各种“大批判”运动。我所接触的还都是“秀才造反”,主要是 “拿起笔杆做刀枪,口诛笔伐打黑帮”。文革期间印刷和绘制的“主席像”是无以计数的。 |
| 关键词: | 工艺美术 美术活动 |
内容
书法、美术在文革中象所有的文艺形式一样已经少有艺术可言,它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武器”被运用到了极至。“运动”提倡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主要载体是纸笔,至于后来动了拳头、棍棒,乃至枪炮,那是少数人背离了运动的“大方向”超越了“文斗”的范畴,自然不在此话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郯城爆发时,本人刚刚是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由于参加过学校美术组的学习训练,有一定的绘画基础,被学校文革领导小组吸收到漫画小组,随之参加了各种“大批判”运动。我所接触的还都是“秀才造反”,主要是 “拿起笔杆做刀枪,口诛笔伐打黑帮”。在“要砸烂一个旧社会”的口号声中,一切艺术活动和艺术作品都是“封、资、修”的产物和糟粕,无知和狂热的人们砸文物,烧书籍,毁字画..,"大破大立”的作法是:靡靡之音必须消灭,但语录歌一定要唱响;古字画要烧毁但领袖像要画,大批判要搞,大字报要写,漫画要画。
漫画与大字报
“漫画”一词按照《辞海》的解释是“一种有讽刺性或幽默性的绘画”,是“通过夸张、比喻、象征、寓意等手法,表现为幽默、诙谐的画面”。“文革”时已化为名副其实的“武器”,成了最具生命力的画种。这种“大字报式的”漫画铺天盖地、尖锐无比、所向披靡,可以使生者死去,使死者遗臭万年。矛头所指大到国家主席,小到村街的地主、富农,即便是群众之间的争执,都可以此为武器。其揭露的内容包括祖宗八代、家庭出身、海外关系、生活作风、历史现行,无所不能。已无丝毫的幽默、诙谐可言。运动是在揭批北京“三家村”黑店声中拉开序幕,接着就是揭露本校的“黑帮”。当时郯城三中的几位老教师一夜之间被揪了出来,揭发的内容使我们大吃一惊:和蔼可亲、笑容可掬的先生、学究,原来是埋藏很深的叛徒、特务、地主、资本家,转眼成了青面獠牙的牛鬼蛇神。在他们的家中居然抄出海外来信、洋文报刊、光屁股女人的画像..紧接着无休止的批斗开始了。有的老师读书笔记、诗抄被揭发、上纲为对党、对社会不满的证据,记得有“怅望西风报闷恩,蓼红苇白断肠时”被画成翘首盼望蒋介石反攻大陆;“昨日黄土珑头埋白骨,今宵红绡帐底卧鸳鸯”成了个人生活腐朽作风败坏的铁证,某老师吃猪肉吐皮,某老师夏天穿裙子、冬天抹雪花膏,都做为资产阶级思想予以揭批,上了漫画大字报,成了人们饭前茶后的最好谈资。我作为一名十四岁的学生,只知道循规蹈矩地跟在师长后边做事,在别人起过稿的画面上涂颜色,根据编好的文字起草漫画,体会不到、观察不到许多老师人人自危,朝不保夕,互相提防,小心翼翼的心境,也理解不了这些大字报、漫画对这些老师和他的家人的伤害。
当时县城街道,主要集中在县政府至县委这条街,路两旁全部都是用粗席搭起来的大字报墙,供各组织、各派别的红卫兵在此大鸣大放。有的在大字报上注明“严禁覆盖,保留XXX”,有的干脆写上“永久保留”,其实根本没人听这一套的,本派别的还可互相照顾一下,不是一个观点的哪怕你刚刚贴上,笔墨未干,照盖不误。贴大字报的浆糊都是白面打的,来回贴层数多了,成了厚厚的面饼,猪都跑到大街上啃大字报。不过,这些免费的纸、笔和颜料,倒培养了一些美术骨干。现在细细想起来,仅就绘画手法,表现水平,当时郯城的漫画形式可分为三类:
一是“连环漫画”。这一类漫画的作者,大都是经过专门学校训练的,大多出自文化艺术界的专业人员和学校的美术教师之手。尽管是“大批判”但仍流露出“学院派”严谨的造型、勾线、用笔、用色。画的有艺术性,在当时起到“指导示范”作用。
二是“大字报漫画”。这一类作者大多是美术爱好者,有一定的绘画基础,与被批判对象没有个人恩怨,作为政治任务来完成,此类漫画以文字为主,画面尽量避免人身攻击,占大批判专栏的多数。
三是“谩骂式漫画”。这一类作者根本就不会画画,字写的又不好,心凶笔弱,画的不象画,内容也多不象话。好像出自在茅厕里画下流画的一类人之手,连生殖器官都表现的淋漓尽致,言词多粗鲁不堪,一旦贴出被众人所不齿。
所有的漫画都配有解说词,可称为“图文并茂。有些“才子”就来了诗配画,读起来朗朗上口。例如以批露某人生活作风的诗句,象:“相当初,俺老万,XX市里名声显,跳舞厅,流情汗,夜晚住上婊子院”。俗一点的象:“黑咕隆咚天,二人正交欢,忽听一声响,光腚朝外窜。"还有更粗野的诗文,在今天属“扫黄打非”之列,不再列举。漫画随着文革运动在文革初期形成一个高潮,在以后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批宋江”、“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后,直到粉碎“四人帮”漫画又形成一个小高潮。随着“文革”结束,这种大字报式的漫画才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红海洋”与“伟人像”
“文革”开始,为了大树特树“老人家”的绝对权威,在揭批刘、邓的同时,掀起了早请示、晚汇报、背语录、语言革命化的热潮。为了营造革命气氛,红宝书、红袖章、红旗帜、语录板等等,全部是红色的。凡是工矿、机关、学校、村街能用的墙壁上都刷上或喷上大红漆,用黄漆写上或印上“老人家”的话或语录。此外还要在最显眼的位置或砌高墙、或焊大型钢铁架,画上巨幅的主席像。在突出“老人家”的同时,而对刘、邓另一个司令部的安排,群众自然爱憎分明。紧接着在工厂、机关门前两个或几个草扎或泥塑的人形跪趴在地上,有雕塑能力的高手,还能把他们制成个人样,手艺差的干脆只整了几堆泥,写上刘、邓的名字。有的还塑上牛头马面,毒蛇乌龟也算是牛鬼蛇神一小撮。记得1969年,我的单位红旗机械厂,所有的墙面全部喷上红漆,地面连洒的红漆加铁锈到处红彤彤的。有一天我们工厂也想再塑几个泥人,找来了铸工及木工车间的高级师父,让我在纸上给画了样子,但师傅们刻制机械模型的手怎么也不能将泥整成人形,急得两手黄泥,满头大汗也没完成这个政治任务。后来听说,我的母校(三中)搞的好,我们几个去参观了一回。当时学校已经开始“复课闹革命”,重返学校发现不但校门口有泥人,连各个教室门前都塑了形态各异的刘、邓很象今天发达城市的群雕。我的一个同学很具有这方面的天资,在教室门旁弄了这么几尊,塑的形神兼备,造型准确,引得了同去的工人师傅啧啧称赞,我自愧不如,很长时间在工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文革期间印刷和绘制的“主席像”是无以计数的。京剧有八个样板,而美术只有一幅油画《去安源》,前几年拍卖会上拍出了天价。画“主席像”都是根据照片或印刷品打格子放大,但是有“问题”的人,画的技术再好是不允许插手这项神圣工作的。因为全县需要画像的地方太多,专职美术工作者远远不能满足“革命形式”的需求,许多业余画家应运而生。反正千篇一律,打格子放大、调好几种颜色涂上。当时厂里请来一个画伟人像的高手,我怀着敬畏的心情去拜望,一看原来是学校漫画组的同学,画技远不如我。和他交流心得很容易,有些颜色可以在墙上直接调和,他再三鼓励我画,我连连摇头。我是画漫画惯了,手练的不严谨,对此是退避三舍,从来不敢染指。文革中有一部分头脑很清醒的人,趁着别人打派仗,搞串联之机专门从事绘制“伟人像”,据说颇收入了一笔。看到别人拿钱眼热,也有一些人趁热下了海,一点美术常识都没有的也敢大显身手。当然这部分人专门深入基层,为贫下中农“服务”。画的有些走形,只要在“似与不似”之间总是有理由糊弄过去,将钱拿到手就走人。就有这么一位“画家”(姑且隐去大名)初入道时就栽了一个跟头。其实他是只能勉强画画结婚用的喜床板的水平,看到画伟人像生意好,就勇敢地加入这个行列,不久,在一个村为大队画了伟人像之后,贫下中农不但拒绝付款,还派民兵押着该“画家”在伟人像面前长跪不起,叩头请罪:“丑化了伟大领袖,罪该万死。”直到痛哭流涕,最后又请了高手来,重新画了一个“象”的,才算罢休。
其实画伟人像时是很艰苦的,画位一般都在数米以上,有的达十多米之高,不光是在高架上摇摇晃晃,心惊胆颤,还要反反复复爬下来爬上去的观察、修改、夏天烈日,冬天寒风,是一项重体力的高空作业,有点收入也无可厚非。
“三结合”美术创作活动
文革期间的美术创作,特别强调“三突出”,即所谓“主题先行”,“红、光、亮”。一度流行的“三结合”创作队伍,是指由工人、农民、军人及专业知识分子参加共同组成的创作班子。各级“革命委员会”都把这一活动当做政治任务,逢重大展览,都要经过县、地区、省逐级选拔,通过预展或草图观摩的形式,发现好的题材,选定重点作品,进行重点加工。一般是工人、农民等基层业余美术作者拿出有生活气息、“革命气概”的作品样稿,之后请专业画家进行修改、提炼。1969年在临沂的最高指示展览馆(现为临沂艺术馆),举办了文革中第一次草图观摩会,我县组织了十几个重点作者前去参观,大家都是骑自行车去的,而且当天打个来回。
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县里组织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深入农村体验生活创作活动,抽调了县文化馆、电影院及教育界的部分专业美术工作者,业余作者有八零三矿的顺旗同志和我,共十几个人。首先集中到了马头公社桑庄,在与社员一起劳动的过程中,发现并酝酿创作题材。有的构思了表现农民学唱样板戏;有试图表现田间地头学习语录、写语录板;我参加的这一组构思的内容是田间地头开展“大批判”的题材,几天下来基本形成了组画的形式。记得初到桑庄时,我们几位深入生活的“画家”在庄稼地头看到一伙社员围在一起召开学习讲用会。我们不注意会议的内容,只是在人群外走动,搜集素材或画速写,有条件的拍拍照片,有一个人静静坐在一旁,抽着旱烟袋,很入画。我们围上去,热情地请老人摆姿势,做模特,想把他的形象画下或拍下来。正弄得老头不知所措,旁边过来一个农民,悄悄告诉我们:“他是地主”声音虽然很小,但这句话就象在我们耳边响了一个炸雷,一个个大惊失色,拔腿四散,有的笑容还僵在脸上,有的嘴巴张的大大的,走了老远还没回过神来,真象遇到鬼一样。
回县后我们集中在文化馆内开始画草稿,我和徐敏锦同志为一组,重点负责《田间批判会》这幅油画。画幅大约为2米左右,画了十几个群情激昂的贫下中农,在庄稼地围着开批判大会,男女老幼都有,表情动态各异,很有些王式廓《血衣》的气概。画面上需要刻画一个青年农民,因我是工人,身高体壮,又长得工农形象,决定由我来做模特。为了追求真实,我光着膀子站在太阳地里,摆着姿势让徐敏锦画了好几天,大家都说很象我。这件作品后来送到地区,但因政治气候不稳定,老是通不过,多次修改。问题的关键是批判的对象反反复复地改动,先是根据当时流行作法,画的是批刘、邓泥塑像,后改为稻草人挂黑牌,但上级已否定了这种做法。画村里的地富又不典型,改来改去,大家都不耐烦了,也失去了信心,最后在地头上画了一本“论修养”交稿了事。但是这么多人围着一本书怒目圆睁,让人看了不伦不类,很有些狐假虎威的味道。后来我又参加了几次类似的创作、合作活动,都没有桑庄这次慎重,不再赘述。当时县里美术界的领头人物是韩烽老师,擅山水、花卉、书法,可惜英年早逝,1976年病逝时才49岁;当时才华横溢的李瑞东老师擅长国画人物、连环画,摄影、无线电无师自通,后调山东经济报社也是英年早逝,1994年病故,只有五十一岁,刚刚任报社的社长;田学文老师擅长国画花卉、书法自成一体,1996年病故,也是五十多岁;八零三矿的吕顺旗兄,是山东艺校的高才生,擅长水粉、水彩、油画,七十年代调回老家青岛,失去联系。现在仍居留在郯城的,当时风华正茂的年轻人都已退休,多数人仍笔耕不止,颇有建树。我当时是年龄最小的一个,而今已是五十有三,每每想起这些师长,感慨万端,今逢政协约稿,成此拙文,请健在的师友正之。
张宏亮
漫画与大字报
“漫画”一词按照《辞海》的解释是“一种有讽刺性或幽默性的绘画”,是“通过夸张、比喻、象征、寓意等手法,表现为幽默、诙谐的画面”。“文革”时已化为名副其实的“武器”,成了最具生命力的画种。这种“大字报式的”漫画铺天盖地、尖锐无比、所向披靡,可以使生者死去,使死者遗臭万年。矛头所指大到国家主席,小到村街的地主、富农,即便是群众之间的争执,都可以此为武器。其揭露的内容包括祖宗八代、家庭出身、海外关系、生活作风、历史现行,无所不能。已无丝毫的幽默、诙谐可言。运动是在揭批北京“三家村”黑店声中拉开序幕,接着就是揭露本校的“黑帮”。当时郯城三中的几位老教师一夜之间被揪了出来,揭发的内容使我们大吃一惊:和蔼可亲、笑容可掬的先生、学究,原来是埋藏很深的叛徒、特务、地主、资本家,转眼成了青面獠牙的牛鬼蛇神。在他们的家中居然抄出海外来信、洋文报刊、光屁股女人的画像..紧接着无休止的批斗开始了。有的老师读书笔记、诗抄被揭发、上纲为对党、对社会不满的证据,记得有“怅望西风报闷恩,蓼红苇白断肠时”被画成翘首盼望蒋介石反攻大陆;“昨日黄土珑头埋白骨,今宵红绡帐底卧鸳鸯”成了个人生活腐朽作风败坏的铁证,某老师吃猪肉吐皮,某老师夏天穿裙子、冬天抹雪花膏,都做为资产阶级思想予以揭批,上了漫画大字报,成了人们饭前茶后的最好谈资。我作为一名十四岁的学生,只知道循规蹈矩地跟在师长后边做事,在别人起过稿的画面上涂颜色,根据编好的文字起草漫画,体会不到、观察不到许多老师人人自危,朝不保夕,互相提防,小心翼翼的心境,也理解不了这些大字报、漫画对这些老师和他的家人的伤害。
当时县城街道,主要集中在县政府至县委这条街,路两旁全部都是用粗席搭起来的大字报墙,供各组织、各派别的红卫兵在此大鸣大放。有的在大字报上注明“严禁覆盖,保留XXX”,有的干脆写上“永久保留”,其实根本没人听这一套的,本派别的还可互相照顾一下,不是一个观点的哪怕你刚刚贴上,笔墨未干,照盖不误。贴大字报的浆糊都是白面打的,来回贴层数多了,成了厚厚的面饼,猪都跑到大街上啃大字报。不过,这些免费的纸、笔和颜料,倒培养了一些美术骨干。现在细细想起来,仅就绘画手法,表现水平,当时郯城的漫画形式可分为三类:
一是“连环漫画”。这一类漫画的作者,大都是经过专门学校训练的,大多出自文化艺术界的专业人员和学校的美术教师之手。尽管是“大批判”但仍流露出“学院派”严谨的造型、勾线、用笔、用色。画的有艺术性,在当时起到“指导示范”作用。
二是“大字报漫画”。这一类作者大多是美术爱好者,有一定的绘画基础,与被批判对象没有个人恩怨,作为政治任务来完成,此类漫画以文字为主,画面尽量避免人身攻击,占大批判专栏的多数。
三是“谩骂式漫画”。这一类作者根本就不会画画,字写的又不好,心凶笔弱,画的不象画,内容也多不象话。好像出自在茅厕里画下流画的一类人之手,连生殖器官都表现的淋漓尽致,言词多粗鲁不堪,一旦贴出被众人所不齿。
所有的漫画都配有解说词,可称为“图文并茂。有些“才子”就来了诗配画,读起来朗朗上口。例如以批露某人生活作风的诗句,象:“相当初,俺老万,XX市里名声显,跳舞厅,流情汗,夜晚住上婊子院”。俗一点的象:“黑咕隆咚天,二人正交欢,忽听一声响,光腚朝外窜。"还有更粗野的诗文,在今天属“扫黄打非”之列,不再列举。漫画随着文革运动在文革初期形成一个高潮,在以后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批宋江”、“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后,直到粉碎“四人帮”漫画又形成一个小高潮。随着“文革”结束,这种大字报式的漫画才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红海洋”与“伟人像”
“文革”开始,为了大树特树“老人家”的绝对权威,在揭批刘、邓的同时,掀起了早请示、晚汇报、背语录、语言革命化的热潮。为了营造革命气氛,红宝书、红袖章、红旗帜、语录板等等,全部是红色的。凡是工矿、机关、学校、村街能用的墙壁上都刷上或喷上大红漆,用黄漆写上或印上“老人家”的话或语录。此外还要在最显眼的位置或砌高墙、或焊大型钢铁架,画上巨幅的主席像。在突出“老人家”的同时,而对刘、邓另一个司令部的安排,群众自然爱憎分明。紧接着在工厂、机关门前两个或几个草扎或泥塑的人形跪趴在地上,有雕塑能力的高手,还能把他们制成个人样,手艺差的干脆只整了几堆泥,写上刘、邓的名字。有的还塑上牛头马面,毒蛇乌龟也算是牛鬼蛇神一小撮。记得1969年,我的单位红旗机械厂,所有的墙面全部喷上红漆,地面连洒的红漆加铁锈到处红彤彤的。有一天我们工厂也想再塑几个泥人,找来了铸工及木工车间的高级师父,让我在纸上给画了样子,但师傅们刻制机械模型的手怎么也不能将泥整成人形,急得两手黄泥,满头大汗也没完成这个政治任务。后来听说,我的母校(三中)搞的好,我们几个去参观了一回。当时学校已经开始“复课闹革命”,重返学校发现不但校门口有泥人,连各个教室门前都塑了形态各异的刘、邓很象今天发达城市的群雕。我的一个同学很具有这方面的天资,在教室门旁弄了这么几尊,塑的形神兼备,造型准确,引得了同去的工人师傅啧啧称赞,我自愧不如,很长时间在工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文革期间印刷和绘制的“主席像”是无以计数的。京剧有八个样板,而美术只有一幅油画《去安源》,前几年拍卖会上拍出了天价。画“主席像”都是根据照片或印刷品打格子放大,但是有“问题”的人,画的技术再好是不允许插手这项神圣工作的。因为全县需要画像的地方太多,专职美术工作者远远不能满足“革命形式”的需求,许多业余画家应运而生。反正千篇一律,打格子放大、调好几种颜色涂上。当时厂里请来一个画伟人像的高手,我怀着敬畏的心情去拜望,一看原来是学校漫画组的同学,画技远不如我。和他交流心得很容易,有些颜色可以在墙上直接调和,他再三鼓励我画,我连连摇头。我是画漫画惯了,手练的不严谨,对此是退避三舍,从来不敢染指。文革中有一部分头脑很清醒的人,趁着别人打派仗,搞串联之机专门从事绘制“伟人像”,据说颇收入了一笔。看到别人拿钱眼热,也有一些人趁热下了海,一点美术常识都没有的也敢大显身手。当然这部分人专门深入基层,为贫下中农“服务”。画的有些走形,只要在“似与不似”之间总是有理由糊弄过去,将钱拿到手就走人。就有这么一位“画家”(姑且隐去大名)初入道时就栽了一个跟头。其实他是只能勉强画画结婚用的喜床板的水平,看到画伟人像生意好,就勇敢地加入这个行列,不久,在一个村为大队画了伟人像之后,贫下中农不但拒绝付款,还派民兵押着该“画家”在伟人像面前长跪不起,叩头请罪:“丑化了伟大领袖,罪该万死。”直到痛哭流涕,最后又请了高手来,重新画了一个“象”的,才算罢休。
其实画伟人像时是很艰苦的,画位一般都在数米以上,有的达十多米之高,不光是在高架上摇摇晃晃,心惊胆颤,还要反反复复爬下来爬上去的观察、修改、夏天烈日,冬天寒风,是一项重体力的高空作业,有点收入也无可厚非。
“三结合”美术创作活动
文革期间的美术创作,特别强调“三突出”,即所谓“主题先行”,“红、光、亮”。一度流行的“三结合”创作队伍,是指由工人、农民、军人及专业知识分子参加共同组成的创作班子。各级“革命委员会”都把这一活动当做政治任务,逢重大展览,都要经过县、地区、省逐级选拔,通过预展或草图观摩的形式,发现好的题材,选定重点作品,进行重点加工。一般是工人、农民等基层业余美术作者拿出有生活气息、“革命气概”的作品样稿,之后请专业画家进行修改、提炼。1969年在临沂的最高指示展览馆(现为临沂艺术馆),举办了文革中第一次草图观摩会,我县组织了十几个重点作者前去参观,大家都是骑自行车去的,而且当天打个来回。
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县里组织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深入农村体验生活创作活动,抽调了县文化馆、电影院及教育界的部分专业美术工作者,业余作者有八零三矿的顺旗同志和我,共十几个人。首先集中到了马头公社桑庄,在与社员一起劳动的过程中,发现并酝酿创作题材。有的构思了表现农民学唱样板戏;有试图表现田间地头学习语录、写语录板;我参加的这一组构思的内容是田间地头开展“大批判”的题材,几天下来基本形成了组画的形式。记得初到桑庄时,我们几位深入生活的“画家”在庄稼地头看到一伙社员围在一起召开学习讲用会。我们不注意会议的内容,只是在人群外走动,搜集素材或画速写,有条件的拍拍照片,有一个人静静坐在一旁,抽着旱烟袋,很入画。我们围上去,热情地请老人摆姿势,做模特,想把他的形象画下或拍下来。正弄得老头不知所措,旁边过来一个农民,悄悄告诉我们:“他是地主”声音虽然很小,但这句话就象在我们耳边响了一个炸雷,一个个大惊失色,拔腿四散,有的笑容还僵在脸上,有的嘴巴张的大大的,走了老远还没回过神来,真象遇到鬼一样。
回县后我们集中在文化馆内开始画草稿,我和徐敏锦同志为一组,重点负责《田间批判会》这幅油画。画幅大约为2米左右,画了十几个群情激昂的贫下中农,在庄稼地围着开批判大会,男女老幼都有,表情动态各异,很有些王式廓《血衣》的气概。画面上需要刻画一个青年农民,因我是工人,身高体壮,又长得工农形象,决定由我来做模特。为了追求真实,我光着膀子站在太阳地里,摆着姿势让徐敏锦画了好几天,大家都说很象我。这件作品后来送到地区,但因政治气候不稳定,老是通不过,多次修改。问题的关键是批判的对象反反复复地改动,先是根据当时流行作法,画的是批刘、邓泥塑像,后改为稻草人挂黑牌,但上级已否定了这种做法。画村里的地富又不典型,改来改去,大家都不耐烦了,也失去了信心,最后在地头上画了一本“论修养”交稿了事。但是这么多人围着一本书怒目圆睁,让人看了不伦不类,很有些狐假虎威的味道。后来我又参加了几次类似的创作、合作活动,都没有桑庄这次慎重,不再赘述。当时县里美术界的领头人物是韩烽老师,擅山水、花卉、书法,可惜英年早逝,1976年病逝时才49岁;当时才华横溢的李瑞东老师擅长国画人物、连环画,摄影、无线电无师自通,后调山东经济报社也是英年早逝,1994年病故,只有五十一岁,刚刚任报社的社长;田学文老师擅长国画花卉、书法自成一体,1996年病故,也是五十多岁;八零三矿的吕顺旗兄,是山东艺校的高才生,擅长水粉、水彩、油画,七十年代调回老家青岛,失去联系。现在仍居留在郯城的,当时风华正茂的年轻人都已退休,多数人仍笔耕不止,颇有建树。我当时是年龄最小的一个,而今已是五十有三,每每想起这些师长,感慨万端,今逢政协约稿,成此拙文,请健在的师友正之。
张宏亮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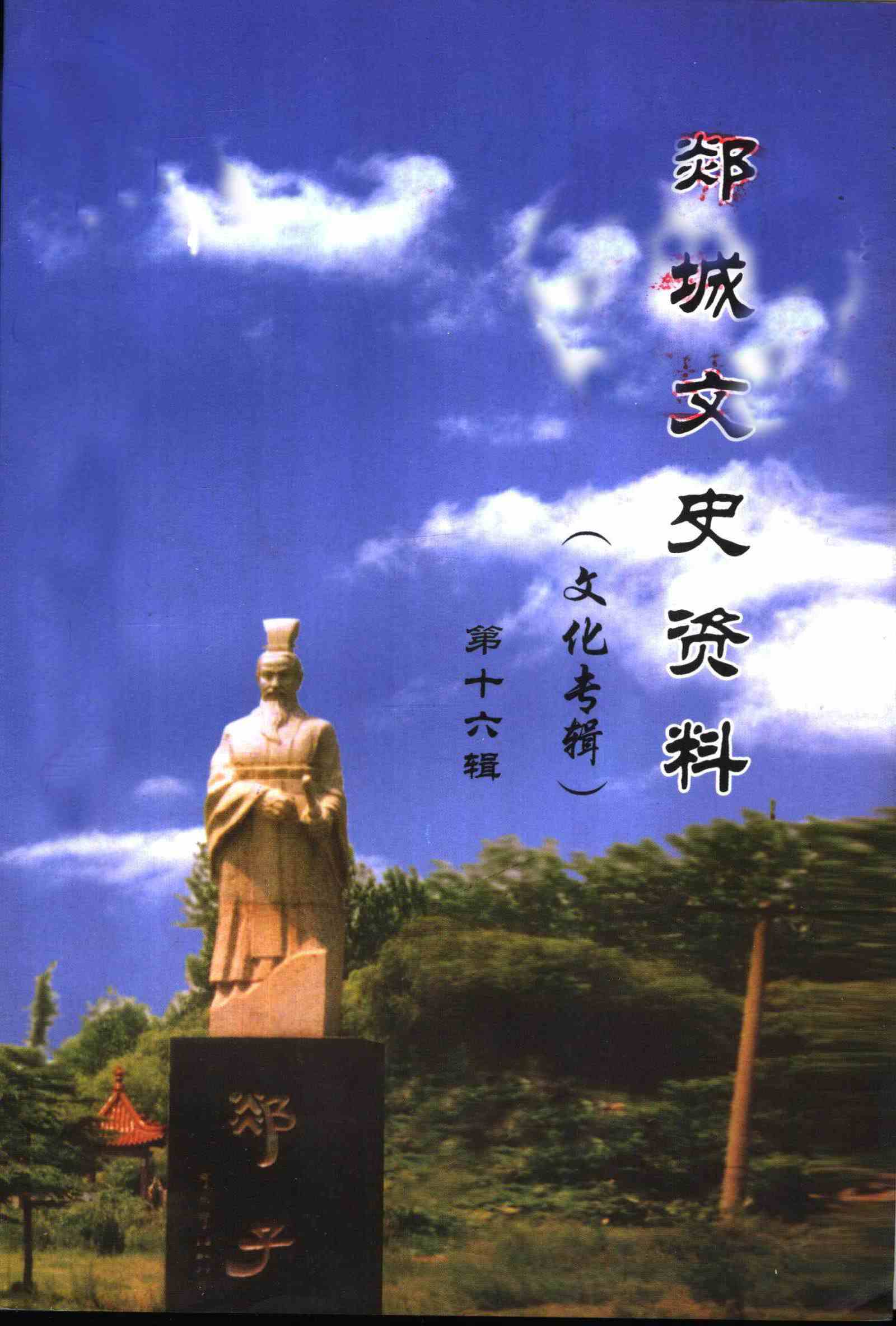
相关人物
张宏亮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