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言吾与中兴煤矿技术管理
| 内容出处: | 《山东文史集粹·科技卷》 图书 |
| 唯一号: | 150020020220007070 |
| 颗粒名称: | 朱言吾与中兴煤矿技术管理 |
| 分类号: | TD82-9 |
| 页数: | 8 |
| 页码: | 345-352 |
| 摘要: | 山东枣庄中兴煤矿公司是由二品衔办理津榆铁轨公司直隶候补道张莲芬于光绪二十四年正式筹建的。它是当时中国人自己经营的唯一能与“外煤”竞争的煤矿。它的历任总矿师大都是聘请的德国人,只有朱言吾是唯一的中国土生土长的总矿师,而且他任职的时间也最长,对煤矿技术发展的贡献较大,是我国早期煤炭工业颇有作为的人才。但高夫曼“原是五金矿师,于煤矿毫无历练”,于矿井测量一事尤不注意。约一小时后提出地面,两鸡安然无恙。这次惨重灾害,除造成数百名矿工的伤亡外,大井的设备和工程也遭到严重的破坏。此时正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因对钢铁的需要量增加,煤炭的需要量也大大增加。 |
| 关键词: | 山东 朱言吾 煤矿技术管理 |
内容
山东枣庄中兴煤矿公司是由二品衔办理津榆铁轨公司直隶候补道张莲芬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式筹建的。它是当时中国人自己经营的(即所谓商办)唯一能与“外煤”(包括外国人在中国投资开采的煤矿)竞争的煤矿。它的历任总矿师大都是聘请的德国人(如富里克、高夫曼、克礼柯等),只有朱言吾是唯一的中国土生土长的总矿师,而且他任职的时间也最长(1915~1928年),对煤矿技术发展的贡献较大,是我国早期煤炭工业颇有作为的人才。
朱言吾就任总矿师的经过
朱言吾,又名朱培元,江苏省江都县人,1881年生,毕业于南京实业学堂。民国2年(1913年)被中兴煤矿公司聘为副矿师。当时,该公司自筑的台枣运煤铁路和一号新式大井以及自备发电厂、机器修理厂等各项工程刚刚竣工投产,大批新式近代化机器设备源源来矿。除运煤铁路因有著名铁路工程师张拜庚负责管理而颇有秩序外,其他方面均无专职的技术人员。例如:自备发电厂的机器设备运抵枣庄后,因为无人管理,张莲芬只好与售货单位——德国人开办的西门子公司签订合同,以每人每月300银元的代价,雇用了他们推荐的德国电机师劳森和王根,来组织安装和进行生产管理。企业的经营管理和技术指挥,基本仍沿袭封建地主土窑旧制。张莲芬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在董事会同意后,不惜以高额薪金聘请了德国人高夫曼为总矿师,“冀图改良”,使管理能够适应生产技术的发展。但高夫曼“原是五金矿师,于煤矿毫无历练”,于矿井测量一事尤不注意。这位“洋矿师”虽专管大井工程,竟连一份准确的“详图”也没有。
枣庄煤田有近千年的开采历史,过去均是土法开采,所遗古井处处皆是,这些古井大都充满积水,一旦采煤打透,就会造成严重水灾。民国4年(1915年)2月1日,由于地质情况不明和高夫曼指挥失当,新大井北石门与原先废弃的土井打透了,发生了一起惨重的水灾。其经过是:在新大井西北方向,有两口废弃多年的小煤窑,窑内积水甚多。当工人在新东大巷挖煤时,即发现煤壁有水珠渗出,恐有水患,便向矿上报告。高夫曼虽也亲往现场查看,但是由于他对煤矿作业缺乏经验,再加平时又缺乏必要的勘测。因此,无法判断那两口废井延深的确切位置,只命人在渗水附近,修筑防水闸门两道,以作预防。他自以为作此部署,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所以当1月31日夜班在新东大巷工人再次向其报告工作面顶上有水流出时,他仍说“勿庸惊慌”,令工人继续往前工作。
2月1日早晨6时左右,废井内积水混着煤气(瓦斯)突然爆发,霎时间冲墙倒壁,随流涌出煤末约2000吨。700尺长的大巷东西之路塞满煤末约500尺。瓦斯在大巷内又与灯火相触,轰然爆炸,声如雷鸣,并且引起了熊熊大火。整个巷道浓烟滚滚,井口更是被乱木、铁车、煤末冲塞,以至罐笼不能升降,电泵也被淹没。当时在井下工作的共有矿工673人,因事起仓促,仅逃出12人,其余全被隔阻在井内。面对这种危急局面,高夫曼拿不出主意来。至于他原先所筑的两道水闸,因为既小又不坚固,早被大水冲得无影无踪了。
第二天,工人们建议,先用公鸡两只放在筐内,投入井下,测验煤气。约一小时后提出地面,两鸡安然无恙。始知井下风路还通,无大妨碍,但人心惶惶,受难家属更是牵挂亲人。
灾变后的第三天,水势稍退,矿上派人修理罐笼时,听到井下有人呼救,于是便立即报告了公司协理戴绪万(因经理张莲芬常住天津,此时又在病中,闻讯来得较晚,故一切事宜皆由戴主持)。在他的支持下,井上的工人冒着生命危险,纷纷下井抢救遇难工友。经过一天多的时间,才将塞满煤末、石块、乱木的大井挖出一条通道,把幸免于难的203名矿工救了上来。有458名矿工不幸遇难。
这次惨重灾害,除造成数百名矿工的伤亡外,大井的设备和工程也遭到严重的破坏。事故发生两个星期后,开始了灭火、排水、输风、清理维修巷道等各项抢险修复工作。这项工作,开始仍由高夫曼主持,他所采取的措施是用水灌注灭火。满以为经此一举,即可将火扑灭,再无蔓延之势。不料水高虽达火区,但因煤层太厚,浸渍未久,余烬尤存,至7月23日,火又复燃。高夫曼此时更急于求成,为了早日恢复矿井原来形象,便抛弃了用水灌注的计划,而改取“建筑高墙,兴砌碹工,并作种种粉糊,以为截断鲜风之用。”由于该处距离出风正道太近,再加上是久火之区,石层松落,焦缝分离,虽一再设防,终究无补于事。高夫曼至此,真是黔驴技穷,只好辞职回国一走了事。中兴煤矿公司便另聘朱言吾为总矿师,负责灭火排水工作。
全面规划 排水灭火 抢险修复新大井
朱言吾接任总矿师后,面临的第一个课题,就是排水灭火。为此,他接受高夫曼急于求成,结果欲速不达的教训,改而采取稳健的步骤,全面规化,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抢险修复工作。
1.灭火。由于火患区相距大井甚近(只50余尺),一旦余火再燃,公司的损失就会更大。因此,朱言吾先作了一部分灌注,又在其间兴筑14道水墙,隔断煤巷约500余尺,并放水1700余吨,火势才逐渐消灭。
2.排水。灾变之后,大井下面皆成积水之区,当时下山有抽水机两部,每分钟约可抽水一吨。当时估计,如果没有什么阻碍,3个月之内会把所有积水全部抽完。但是,由于水患下来时,各下山皆冲有积炭,棚木、铁道交错纵横,故抽水机向下移行,就必须先清理道途,才能节节而进。再加抽水机下行时,气、水两管均需接长,这就不得不耽延时日。直到10月25日,水才退至900尺大巷,尚有400余尺积水下山。而这些下山又都各不相通,必须一个一个进行排泄。因此时间更加拖长。再加原来大井灌水之时,各处煤墩均久浸水内,致使质体松动,棚木更移。四周旧井空隙又多,一旦地势倾斜,其煤震动,西段上山的积水又复下陷。有此种种困难,故一直到第二年(1916年)的8月,才将积水基本排除。
3.输风。灾变发生时,大井下面皆是废井涌下的积水,因而煤气甚浓。以后,浅近处虽然通风,情况略有好转,但深远处仍然不足。再加各处风门悉被冲毁,风向不能趋于一途。下山蒸气水机又开,回气升腾,风受潮湿则体重渐增,于是风量供给就更显不足了。致使各处工程均失去周转之力。高夫曼在任时,虽然扩大了回风道,并布置好各处风门,但是由于余火复燃,此道亦无济于事,因而条件更加恶劣。朱言吾只好“一面移安风扇,加添气管风量”;一面“开凿石门,另辟风路”,也是直到第二年8月,才一并告成。
4.清理、整修巷道。在抢险修复工程初期,公司所有人力、物力,悉为救火灌水之用,直到8月,水势下落以后,才开始着手于巷道的清理与整修工作。大井经此重创,当时的巷道情况极为恶劣,“若东大巷之尸骸狼藉,北石门之积水湍流,其他若东西水仓则积有煤气,不能通风,均足为进行之困难。”至于破坏情况,就更加严重。“以巷道言,则皆毁坏一空;以棚木言,则皆倒塌殆遍;以辘轳言,则皆飘落无存;以运道言,则皆歪斜欲陷。”要想恢复旧观,真是谈何容易。朱言吾督率全矿技术骨干,昼夜抢修,直到第二年8月,才基本完工。
组织设计施工 建设二号近代化大井
枣庄中兴煤矿公司这场惨重灾变,造成大井停产近半年,修复工程长达18个月,损失是相当大的。灾变后,公司于1916年11月在天津召开第六次股东会,对公司的组织机构进行了整顿。之后,又对企业的技术管理进行了改进,朱言吾继续担任总矿师。
此时正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因对钢铁的需要量增加,煤炭的需要量也大大增加。而这时各帝国主义国家又都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故我国的轻工业也得以迅速发展,特别是纺织业和面粉业发展得更快。轻重工业的发展,引起了煤炭价格的飞涨,而“洋煤”的入口量又大减,于是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环境中的中国煤矿,便获得了一个良好的发展机会。
这一时期,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又以上海、无锡、苏州、杭州一带最为迅速,因之这一地区的煤炭市场也特别活跃。但是这一地区并没有什么煤矿,从枣庄向南直到江浙,只有贾汪、淮南等几处小煤矿。而且这些煤矿又是在大战期间刚刚恢复发展起来的,不论产量和设备都远不能和枣庄中兴煤矿相比。因此,在长江下游这块广阔的市场上,枣庄中兴煤矿占了相当的优势。
为了适应当时形势的需要,中兴煤矿公司于民国9年(1920年)再度添招股本,筹备建设第二座大井。新大井从勘查、钻探、设计到施工,一切技术工作全部由朱言吾负责主持。在新大井的建设工程中,朱言吾进一步显露了他的才华,因而博得煤矿公司更加对他器重。他曾数次婉言辞谢公司对他的聘任,计划出国考察欧美的煤炭工业状况,但公司始终坚留不放。最后公司答允待新井竣工后,由公司资助他出洋考察,他才不得不接受聘任。
在新大井的建设工程中,困难是不少的。例如:为了选择好新大井的建设地点,朱言吾早在1917年春,就征得公司董事会同意,确定对周围煤层进行一次钻探。为此,他们于当年4月和美国纽约东方矿务公司协商借钻包打办法并签订合同。但该公司只有一具租机。合同只好规定以租机先行开工,另由中兴煤矿向美国订购一具新钻机(价格为美金4000余元)。5月下旬,第一批打钻人员由纽约来华。第二队也于6月携带新购钻机抵枣。可是打钻只进行到第二年1月31日,即遭“土匪”滋扰,打钻地点被围攻,洋技师等虽平安脱险,但也成了惊弓之鸟,吓得跑回天津(当时中兴煤矿总公司设在天津),说什么也不愿再返枣庄继续工作。中兴公司鉴于地方不靖,自己确实无力保护“外人”的安全,只好将原订打钻全同全部取消,而另筹接手办法。后来,他们找到一个名叫杨全的包工头子,与他签订试办合同,打钻工作方得继续下去。直到1920年5月,方才钻完朱言吾指定的田庄以东、小王庄以西的4个钻孔,为大井工程取得了相当丰富的资料。
1924年夏季,二号大井全部建成投产。大井井筒的直径为4.7米,深度287米,井口铁架高28米,附建煤楼3层,中层连接天桥,下层装置饰煤机及拣煤槽。绞车房位于井口南面,装有720千瓦之电绞车,用一寸半之钢丝绳提绞罐笼,每次提煤4车,每车容量660公斤,平均每50秒提煤一次,每日两班生产,可出煤2700吨。
新大井不仅工程、设备都比一号大井更加先进、雄伟,而且在当时还是整个华东地区的最大矿井。这座大井完全由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自己建造(机器设备是由德国引进的),这在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史上是罕见的。
第二大井竣工后,朱言吾即以为了“丰富阅历,增长知识”,赴欧美调查各国煤炭工业生产情况,“俾作他山攻玉”为由,于民国13年(1924年)8月辞去待遇优厚的中兴煤矿公司总矿师的职务,出国考察。中兴煤矿公司董事会为了感谢他对矿山建设做出的贡献,也恪守前言,并议决致送川资25000元予以资助。
经过一番简单准备,朱言吾及其随行人员(包括秘书和学员)即于当年10月4日从上海登轮起行。经南洋群岛锡兰,穿苏伊士运河,渡地中海,而后在法国的马赛登陆。他们抵欧后,先游览了意大利,然后至瑞士,再经奥地利而达德国,又由德国之鲁尔赴荷兰,复由比利时再转入法国,最后渡海抵英伦三岛。总计在欧洲逗留约3个半月,于第二年的2月中旬渡大西洋而达美国。他在美国又考查了一个多月,才由西海岸的温哥华乘船回国,4月9日抵达上海。此行共计费时6个月零5天,行程10余万里,调查欧美诸国煤矿30余座,工厂40余处。
朱言吾归国后,中兴煤矿公司又聘请他担任驻矿副经理兼总矿师,在他出国期间兼任总矿师的副经理张温卿为副矿师。直到民国17年(1928年),中兴煤矿公司聘请克礼柯为总矿师时,他才回南方定居,并曾一度被选为该公司的鉴察人。
朱言吾就任总矿师的经过
朱言吾,又名朱培元,江苏省江都县人,1881年生,毕业于南京实业学堂。民国2年(1913年)被中兴煤矿公司聘为副矿师。当时,该公司自筑的台枣运煤铁路和一号新式大井以及自备发电厂、机器修理厂等各项工程刚刚竣工投产,大批新式近代化机器设备源源来矿。除运煤铁路因有著名铁路工程师张拜庚负责管理而颇有秩序外,其他方面均无专职的技术人员。例如:自备发电厂的机器设备运抵枣庄后,因为无人管理,张莲芬只好与售货单位——德国人开办的西门子公司签订合同,以每人每月300银元的代价,雇用了他们推荐的德国电机师劳森和王根,来组织安装和进行生产管理。企业的经营管理和技术指挥,基本仍沿袭封建地主土窑旧制。张莲芬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在董事会同意后,不惜以高额薪金聘请了德国人高夫曼为总矿师,“冀图改良”,使管理能够适应生产技术的发展。但高夫曼“原是五金矿师,于煤矿毫无历练”,于矿井测量一事尤不注意。这位“洋矿师”虽专管大井工程,竟连一份准确的“详图”也没有。
枣庄煤田有近千年的开采历史,过去均是土法开采,所遗古井处处皆是,这些古井大都充满积水,一旦采煤打透,就会造成严重水灾。民国4年(1915年)2月1日,由于地质情况不明和高夫曼指挥失当,新大井北石门与原先废弃的土井打透了,发生了一起惨重的水灾。其经过是:在新大井西北方向,有两口废弃多年的小煤窑,窑内积水甚多。当工人在新东大巷挖煤时,即发现煤壁有水珠渗出,恐有水患,便向矿上报告。高夫曼虽也亲往现场查看,但是由于他对煤矿作业缺乏经验,再加平时又缺乏必要的勘测。因此,无法判断那两口废井延深的确切位置,只命人在渗水附近,修筑防水闸门两道,以作预防。他自以为作此部署,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所以当1月31日夜班在新东大巷工人再次向其报告工作面顶上有水流出时,他仍说“勿庸惊慌”,令工人继续往前工作。
2月1日早晨6时左右,废井内积水混着煤气(瓦斯)突然爆发,霎时间冲墙倒壁,随流涌出煤末约2000吨。700尺长的大巷东西之路塞满煤末约500尺。瓦斯在大巷内又与灯火相触,轰然爆炸,声如雷鸣,并且引起了熊熊大火。整个巷道浓烟滚滚,井口更是被乱木、铁车、煤末冲塞,以至罐笼不能升降,电泵也被淹没。当时在井下工作的共有矿工673人,因事起仓促,仅逃出12人,其余全被隔阻在井内。面对这种危急局面,高夫曼拿不出主意来。至于他原先所筑的两道水闸,因为既小又不坚固,早被大水冲得无影无踪了。
第二天,工人们建议,先用公鸡两只放在筐内,投入井下,测验煤气。约一小时后提出地面,两鸡安然无恙。始知井下风路还通,无大妨碍,但人心惶惶,受难家属更是牵挂亲人。
灾变后的第三天,水势稍退,矿上派人修理罐笼时,听到井下有人呼救,于是便立即报告了公司协理戴绪万(因经理张莲芬常住天津,此时又在病中,闻讯来得较晚,故一切事宜皆由戴主持)。在他的支持下,井上的工人冒着生命危险,纷纷下井抢救遇难工友。经过一天多的时间,才将塞满煤末、石块、乱木的大井挖出一条通道,把幸免于难的203名矿工救了上来。有458名矿工不幸遇难。
这次惨重灾害,除造成数百名矿工的伤亡外,大井的设备和工程也遭到严重的破坏。事故发生两个星期后,开始了灭火、排水、输风、清理维修巷道等各项抢险修复工作。这项工作,开始仍由高夫曼主持,他所采取的措施是用水灌注灭火。满以为经此一举,即可将火扑灭,再无蔓延之势。不料水高虽达火区,但因煤层太厚,浸渍未久,余烬尤存,至7月23日,火又复燃。高夫曼此时更急于求成,为了早日恢复矿井原来形象,便抛弃了用水灌注的计划,而改取“建筑高墙,兴砌碹工,并作种种粉糊,以为截断鲜风之用。”由于该处距离出风正道太近,再加上是久火之区,石层松落,焦缝分离,虽一再设防,终究无补于事。高夫曼至此,真是黔驴技穷,只好辞职回国一走了事。中兴煤矿公司便另聘朱言吾为总矿师,负责灭火排水工作。
全面规划 排水灭火 抢险修复新大井
朱言吾接任总矿师后,面临的第一个课题,就是排水灭火。为此,他接受高夫曼急于求成,结果欲速不达的教训,改而采取稳健的步骤,全面规化,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抢险修复工作。
1.灭火。由于火患区相距大井甚近(只50余尺),一旦余火再燃,公司的损失就会更大。因此,朱言吾先作了一部分灌注,又在其间兴筑14道水墙,隔断煤巷约500余尺,并放水1700余吨,火势才逐渐消灭。
2.排水。灾变之后,大井下面皆成积水之区,当时下山有抽水机两部,每分钟约可抽水一吨。当时估计,如果没有什么阻碍,3个月之内会把所有积水全部抽完。但是,由于水患下来时,各下山皆冲有积炭,棚木、铁道交错纵横,故抽水机向下移行,就必须先清理道途,才能节节而进。再加抽水机下行时,气、水两管均需接长,这就不得不耽延时日。直到10月25日,水才退至900尺大巷,尚有400余尺积水下山。而这些下山又都各不相通,必须一个一个进行排泄。因此时间更加拖长。再加原来大井灌水之时,各处煤墩均久浸水内,致使质体松动,棚木更移。四周旧井空隙又多,一旦地势倾斜,其煤震动,西段上山的积水又复下陷。有此种种困难,故一直到第二年(1916年)的8月,才将积水基本排除。
3.输风。灾变发生时,大井下面皆是废井涌下的积水,因而煤气甚浓。以后,浅近处虽然通风,情况略有好转,但深远处仍然不足。再加各处风门悉被冲毁,风向不能趋于一途。下山蒸气水机又开,回气升腾,风受潮湿则体重渐增,于是风量供给就更显不足了。致使各处工程均失去周转之力。高夫曼在任时,虽然扩大了回风道,并布置好各处风门,但是由于余火复燃,此道亦无济于事,因而条件更加恶劣。朱言吾只好“一面移安风扇,加添气管风量”;一面“开凿石门,另辟风路”,也是直到第二年8月,才一并告成。
4.清理、整修巷道。在抢险修复工程初期,公司所有人力、物力,悉为救火灌水之用,直到8月,水势下落以后,才开始着手于巷道的清理与整修工作。大井经此重创,当时的巷道情况极为恶劣,“若东大巷之尸骸狼藉,北石门之积水湍流,其他若东西水仓则积有煤气,不能通风,均足为进行之困难。”至于破坏情况,就更加严重。“以巷道言,则皆毁坏一空;以棚木言,则皆倒塌殆遍;以辘轳言,则皆飘落无存;以运道言,则皆歪斜欲陷。”要想恢复旧观,真是谈何容易。朱言吾督率全矿技术骨干,昼夜抢修,直到第二年8月,才基本完工。
组织设计施工 建设二号近代化大井
枣庄中兴煤矿公司这场惨重灾变,造成大井停产近半年,修复工程长达18个月,损失是相当大的。灾变后,公司于1916年11月在天津召开第六次股东会,对公司的组织机构进行了整顿。之后,又对企业的技术管理进行了改进,朱言吾继续担任总矿师。
此时正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因对钢铁的需要量增加,煤炭的需要量也大大增加。而这时各帝国主义国家又都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故我国的轻工业也得以迅速发展,特别是纺织业和面粉业发展得更快。轻重工业的发展,引起了煤炭价格的飞涨,而“洋煤”的入口量又大减,于是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环境中的中国煤矿,便获得了一个良好的发展机会。
这一时期,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又以上海、无锡、苏州、杭州一带最为迅速,因之这一地区的煤炭市场也特别活跃。但是这一地区并没有什么煤矿,从枣庄向南直到江浙,只有贾汪、淮南等几处小煤矿。而且这些煤矿又是在大战期间刚刚恢复发展起来的,不论产量和设备都远不能和枣庄中兴煤矿相比。因此,在长江下游这块广阔的市场上,枣庄中兴煤矿占了相当的优势。
为了适应当时形势的需要,中兴煤矿公司于民国9年(1920年)再度添招股本,筹备建设第二座大井。新大井从勘查、钻探、设计到施工,一切技术工作全部由朱言吾负责主持。在新大井的建设工程中,朱言吾进一步显露了他的才华,因而博得煤矿公司更加对他器重。他曾数次婉言辞谢公司对他的聘任,计划出国考察欧美的煤炭工业状况,但公司始终坚留不放。最后公司答允待新井竣工后,由公司资助他出洋考察,他才不得不接受聘任。
在新大井的建设工程中,困难是不少的。例如:为了选择好新大井的建设地点,朱言吾早在1917年春,就征得公司董事会同意,确定对周围煤层进行一次钻探。为此,他们于当年4月和美国纽约东方矿务公司协商借钻包打办法并签订合同。但该公司只有一具租机。合同只好规定以租机先行开工,另由中兴煤矿向美国订购一具新钻机(价格为美金4000余元)。5月下旬,第一批打钻人员由纽约来华。第二队也于6月携带新购钻机抵枣。可是打钻只进行到第二年1月31日,即遭“土匪”滋扰,打钻地点被围攻,洋技师等虽平安脱险,但也成了惊弓之鸟,吓得跑回天津(当时中兴煤矿总公司设在天津),说什么也不愿再返枣庄继续工作。中兴公司鉴于地方不靖,自己确实无力保护“外人”的安全,只好将原订打钻全同全部取消,而另筹接手办法。后来,他们找到一个名叫杨全的包工头子,与他签订试办合同,打钻工作方得继续下去。直到1920年5月,方才钻完朱言吾指定的田庄以东、小王庄以西的4个钻孔,为大井工程取得了相当丰富的资料。
1924年夏季,二号大井全部建成投产。大井井筒的直径为4.7米,深度287米,井口铁架高28米,附建煤楼3层,中层连接天桥,下层装置饰煤机及拣煤槽。绞车房位于井口南面,装有720千瓦之电绞车,用一寸半之钢丝绳提绞罐笼,每次提煤4车,每车容量660公斤,平均每50秒提煤一次,每日两班生产,可出煤2700吨。
新大井不仅工程、设备都比一号大井更加先进、雄伟,而且在当时还是整个华东地区的最大矿井。这座大井完全由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自己建造(机器设备是由德国引进的),这在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史上是罕见的。
第二大井竣工后,朱言吾即以为了“丰富阅历,增长知识”,赴欧美调查各国煤炭工业生产情况,“俾作他山攻玉”为由,于民国13年(1924年)8月辞去待遇优厚的中兴煤矿公司总矿师的职务,出国考察。中兴煤矿公司董事会为了感谢他对矿山建设做出的贡献,也恪守前言,并议决致送川资25000元予以资助。
经过一番简单准备,朱言吾及其随行人员(包括秘书和学员)即于当年10月4日从上海登轮起行。经南洋群岛锡兰,穿苏伊士运河,渡地中海,而后在法国的马赛登陆。他们抵欧后,先游览了意大利,然后至瑞士,再经奥地利而达德国,又由德国之鲁尔赴荷兰,复由比利时再转入法国,最后渡海抵英伦三岛。总计在欧洲逗留约3个半月,于第二年的2月中旬渡大西洋而达美国。他在美国又考查了一个多月,才由西海岸的温哥华乘船回国,4月9日抵达上海。此行共计费时6个月零5天,行程10余万里,调查欧美诸国煤矿30余座,工厂40余处。
朱言吾归国后,中兴煤矿公司又聘请他担任驻矿副经理兼总矿师,在他出国期间兼任总矿师的副经理张温卿为副矿师。直到民国17年(1928年),中兴煤矿公司聘请克礼柯为总矿师时,他才回南方定居,并曾一度被选为该公司的鉴察人。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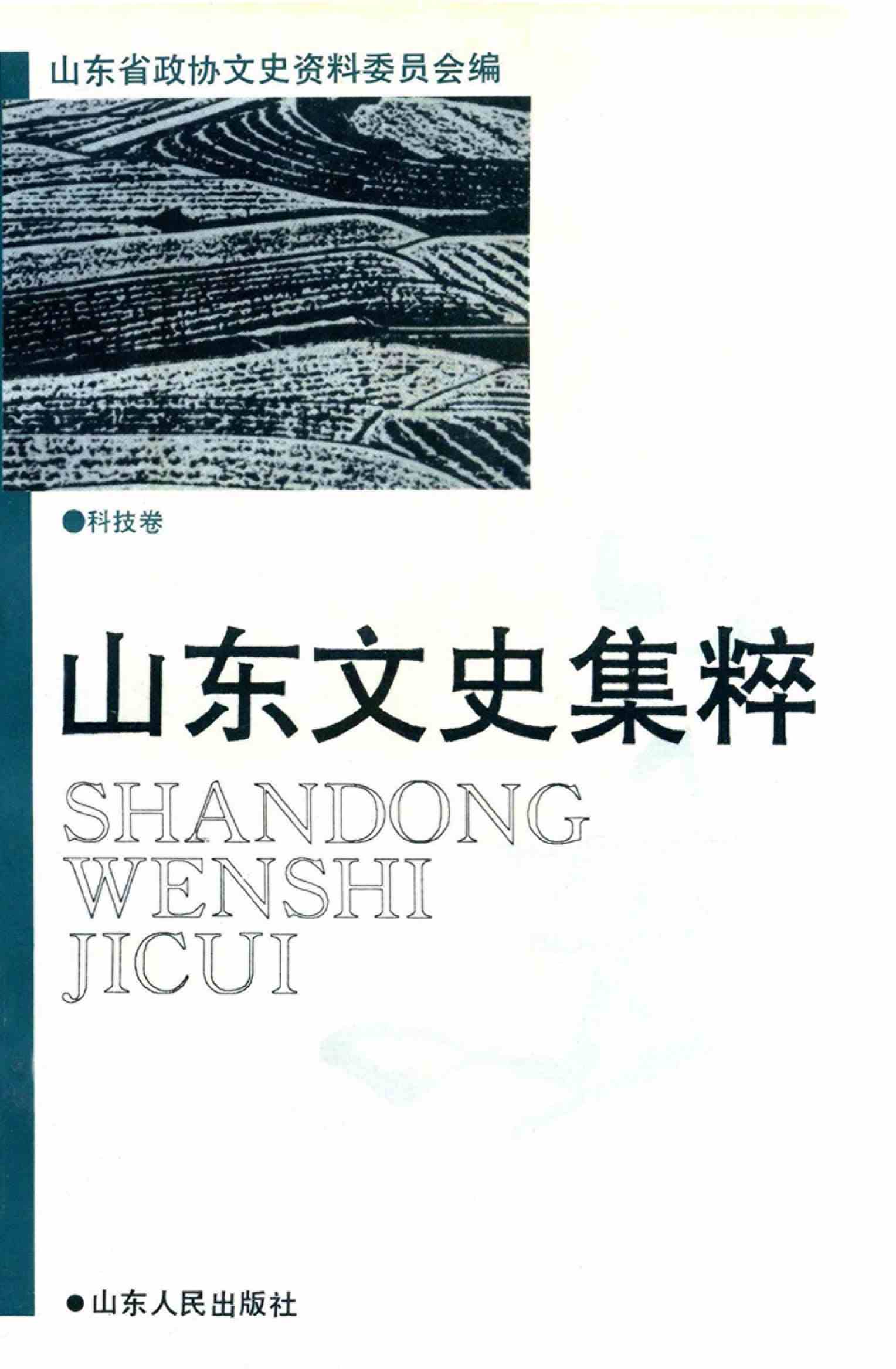
《山东文史集粹·科技卷》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本书收录了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丁肇中、著名科学家郭永怀烈士、杰出物理学家王淦昌、我国早期原子能物理专家王普博士、忆束星北教授、著名力学专家刘先志、著名航空工程专家丁履德、电子计算机专家王正、“西圣”孙学悟等多篇文章。
阅读
相关人物
苏任山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