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桥梁专家王洵才
| 内容出处: | 《山东文史集粹·科技卷》 图书 |
| 唯一号: | 150020020220007061 |
| 颗粒名称: | 铁路桥梁专家王洵才 |
| 分类号: | K826.1 |
| 页数: | 12 |
| 页码: | 273-284 |
| 摘要: | 王洵才,字幼泉,山东省牟平县养马岛镇马埠崖村人。父名汝奇,晚清秀才,素慕岳飞、韩世忠、文天祥之为人,取字景韩。景韩先生博通经籍,并擅医术,于本村私塾课读,兼行医济世。村邻求医问药者,往来不绝。他有子女6人,教书束修微薄,行医只收药费,难养8口之家,乃弃儒就业于合族开办的一个油坊,加上夫人缝补渔网之收入,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因受严父教诲,总角少年即怀读书报国之志。不幸14岁时,父亲一病不起。父故后依靠在朝鲜大使馆工作的兄长王瀛才资助,加之母亲勤俭持家,一家人得免饥寒之苦。1949年1月淮海战役后,国民党溃败南逃时,炸毁了淮河大桥。淮河大桥破坏严重,当时设备、材料不足,修复极为困难。 |
| 关键词: | 山东 铁路桥梁专家 王洵才 |
内容
含辛茹苦 孜孜求学
王洵才(1897—1977年),字幼泉,山东省牟平县养马岛镇马埠崖村人。父名汝奇,晚清秀才,素慕岳飞、韩世忠、文天祥之为人,取字景韩(景仰韩世忠之意)。景韩先生博通经籍,并擅医术,于本村私塾课读,兼行医济世。村邻求医问药者,往来不绝。他有子女6人,教书束修微薄,行医只收药费,难养8口之家,乃弃儒就业于合族开办的一个油坊,加上夫人缝补渔网之收入,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洵才自幼聪敏过人,7岁时于本村私塾就读,所学过目不忘。因受严父教诲,总角少年即怀读书报国之志。不幸14岁时,父亲一病不起。父故后依靠在朝鲜大使馆工作的兄长王瀛才资助,加之母亲勤俭持家,一家人得免饥寒之苦。洵才同志幼失父恃,辍学而不辍求知之志,一定要坚持上学读书,家兄无奈,于1911年把洵才同志送到烟台英法学校就读。英法学校除国文教师用汉语教学外,数理教师都是外国人,全用英语讲课,洵才只读过几年私熟,根本不懂外语,学习起来感到十分困难。也是天无绝人之路,洵才有个表兄叫黄善圃,在烟台经商,西学根底很深,英语娴熟。洵才每天晚上,每个星期天和每个假日,都去缠着黄善圃,学习英语,补习功课。第一年年终考试,国文全班第一,数理名列前茅。1914年,洵才考入北京汇文中学,高中毕业后,以优异成绩录取于国立唐山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专攻桥梁专业。在唐山读书4年,平时没请一天假,寒暑假也没回家一次,一来家庭贫寒,没有川资;二来勤奋攻读,也不愿抛废时光。
1920年由国家保送官费赴美留学,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系深造。就读三年,取硕士学位。1922年毕业后,在美利坚桥梁公司实习一年,米楼瓦城市工程局工作一年,企城承造工程公司工作一年。当时洵才风华正茂,风度翩翩而又才华横溢,在美国受到许多才女的爱慕和追求(洵才同志赴美前已经结婚,爱人孙希本,比洵才大4岁),洵才同志一一婉言辞去,明言已婚不能再娶。“糟糠之妻不能忘也”。在米楼瓦城市工程局和企城承造工程公司工作期间,洵才精明干练和诚信严谨的才能和作风,深得美方赞许,他们竞相以高职厚薪相挽留,但洵才不为名利地位所惑,只图报效桑梓,坚持拒绝,毅然启程回国。
在关键时刻的抉择
1925年冬,王洵才留美回国后,即到南京政府交通部报到,在交通部路政司工作了很短一段时间,正式分配在胶济铁路管理局工作,任工务员和帮工程司(当是工程师职务分三等:帮工程司、工程司、正工程司)。任帮工程司时,接受了设计施工城阳桥(城阳至韩漥,中经墨水河,高31米的上承钢板梁大桥,现属青岛市区)的任务,洵才详加勘测,胸有成竹,很快完成了设计任务。竣工后,中外专家评定,此桥设计遵重科学而别具一格,省工省料而坚牢度高,说明设计者根底深厚,才识不凡。城阳桥使用至今,60余年,安然无恙。洵才因此崭露了才华,由工务员、帮工程司直提升为胶济铁路第二工务段(胶济路分两工务段:第一工务段青岛至潍坊,第二工务段济南至潍坊)总段长、正工程司,旋即调任第一工务段总段长、正工程司。
1938年,日寇霸占了胶济铁路并控制了青岛。旬日后,即通知铁路工作人员到青岛指定地点报到。日本人按号叫人,逐一审查,叫到王洵才号数时,王洵才闭口不答。翻译官质问,洵才同志说:“中国人都有自己的名字,不叫名字叫号,是什么意思?”弄得翻译官面红耳赤。实际上,自日军铁蹄踏入青岛,洵才就寝食不安,深感异族入侵,国难当头,热血男儿当有所抉择。一是留在沦陷区,甘受凌辱,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一是去美国,高职厚薪,无虑温饱;一是去大后方,抵御外侮,精忠保国,走抗日道路。他选择了后者。在日本人通知报到的第二天深夜,他绕过了滋阳路(有日军看守),从定陶路后墙翻出,丢下病妻幼子,辗转去到了大后方重庆。
到重庆后,国民党交通部(部长曾养府,继任部长孙科)派王洵才去修滇缅铁路。滇缅铁路计划从昆明修到缅甸的密支那,在昆明设滇缅铁路工程局(局长杜振远,解放后在铁道部工作),王洵才任总工程司和桥梁股股长。
铺轨20多公里以后,缺钱短料。抗战时局紧张,瞬息万变,人心惶惶,滇缅铁路不得不报废停修。以后又修了几条公路。终因时局不稳,公路也被迫停工。王洵才同志接受了重庆中央大学的聘请,到该校工程系任教授。
1945年抗战胜利后,王洵才返回济南铁路局,任工务处长。这时,济南铁路局长陈舜耕多次动员王洵才加入国民党。王洵才对陈舜耕的说教,无动于衷,乃于1948年辞去济南铁路局工务处长职务,到北京大学工学院任土木工程系教授。解放前夕,又被调至前津浦区铁路局任工程处长兼总工程司。
1949年春,南京国民党政府,惶惶准备南逃,山东除青岛一隅,均获解放,津浦区铁路管理局只剩青岛至城阳30公里铁路,无路可管,形同虚设。这时,陈舜耕已调任台湾铁路局局长,邀王洵才到台湾与其共事。他思虑再三,决定跟共产党走!1949年3月,王洵才同志决然离开了南京,回到了青岛家中。
架桥铺路 不怕任重道远
1949年4月,中共城市工作部青岛工作委员会,派王恒珍(王洵才的大女儿,化名孙建平)与王洵才联系,争取王洵才及早参加人民铁路工作,王洵才欣然同意。6月2日,青岛解放,8月,王洵才同志亲赴济南,到铁路局报到供职。
1949年1月淮海战役后,国民党溃败南逃时,炸毁了淮河大桥。津浦路担负着南北交通运输的重要任务,尤其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百废俱兴,一刻千金,炸毁淮河大桥,无异于切断了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党中央和国务院非常焦急,周总理责成济南铁路局组织抢修,王洵才当时任济南铁路局顾问工程师,1949年调驻蚌埠,参与技术指导工作。淮河大桥破坏严重,当时设备、材料不足,修复极为困难。王洵才提出了修复方案,组织指导全体技术人员和广大职工(包括民工),克服了一道道技术难关,竟使破坏严重的淮河大桥提前一个月,于1950年5月1日完成修复任务。当时参加修复工作的苏联专家,对王洵才广博的土木建筑知识,非凡的技术水平和严密的组织能力,也深表钦佩。铁道部为王洵才记一等功。同年7月,王洵才擢任济南铁路管理局副局长(正局长赵锡纯同志)兼总工程师。当时国民经济还比较困难,抗美援朝也未结束,第五工程局只担负蓝烟一线的施工,压力不大。抗美援朝结束后,我国进入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时期,铁路建设的任务逐年加重。1955年除蓝烟路外,第五工程局还接受了杭州至宁波铁路的修建任务。1956年除完成了上述两线的配套工程并验收交付营业运输外,又承担了三项修建任务:一是供武汉钢铁公司运料的武昌——大冶铁路,二是供河南平顶山运煤炭的孟庙——平顶山线,三是为缓解陇海铁路压力的郑州——洛阳间的复线。看过的同志提出,第五工程局的担子太重了,是否向铁道部请示一下,减修几条路?王洵才总是动员大家:“现在的形势是一个人要顶几个人干,架桥铺路,何惧任重道远!”自1954年至1957年5月,4年多的时间,第五工程局的施工任务,由1条线路扩大为5条线路,由1省扩大为4省,点多线长,分布面广,再加上铁路建设的规章制度还未正式建立,通讯设备和其它工具设备相当落后,指挥困难,施工难度大,但年年提前完成任务,没有发生任何技术质量和工程安全事故。当然事业的成功,包括诸多因素,但不管怎么说,与集体施工的组织者、领导者、总工程师王洵才的指挥有方、组织得力是分不开的。
王洵才很善于把广博精深的土木建筑知识,运用于铁路建筑实践。他勘查路线、制定方案、组织施工稳健而求新,民主而善断,因地制宜,随时应变。1956年,河南平顶山支线设计,按原计划由临颖出岔,王洵才复勘后,重新制定了方案,提出了合理建议,由孟庙站出岔,缩短了运营里程,避开了颖河,免修大桥一座,铁道部采纳了这一建议。1953年至1957年修蓝烟铁路时,王洵才亲自勘测路线,对蓝村至莱阳一段,提出了改线建议。铁道部按这个建议施工,避开一条大河,免修两座桥梁,免凿一条隧道,为国家节省投资4000万元(当时旧值),获铁道部一等奖。
王洵才的身上还充分体现出惊人的毅力和吃苦耐劳的传统。1938年至抗战胜利前,洵才参加了滇缅铁路和南部边陲几条公路的修筑,虽受时局影响事倍功半或功亏一篑,但身为总工程司的王洵才的力并没有少出,事也没少费。滇缅铁路地处西南边陲之云贵高原,计划修筑1000多公里,要穿过南北走向的怒山、清水朗山、无量山、哀牢山、点莟山等大小几十座山脉,要跨过怒江、澜沧江、扎社江、龙川江等大大小小几百条河流,地理环境复杂,气候十分恶劣。王洵才与几个勘测人员,只用一辆吉普车,装载仪器、工具、行李和食物,翻山越岭,渡江涉水,穿越森林,主要靠两只脚一双手跋涉攀登。喝水,洗脸,吃饭兼用一个水桶。深山密林中有“瘴气”、“哑泉”和毒蛇猛兽,有的工作人员中了瘴气,似发虐疾,持久不退。有的喝了哑泉水,嗓子肿痛,发音不清。在勘测中没染病的很少,王洵才却安然无恙,他饶有风趣地向队员介绍“经验”:“我从小愿意和小朋友到家乡后山掀石头,捉蝎子,捉住以后,去掉毒针,生生吃掉,所以现在不染病,恐怕少年时吃蝎子收到的以毒攻毒之效吧。”滇缅铁路报废以后,又去勘测公路。在勘测中印公路线路时,有一天,他们仓惶跑回,人困马乏,狼狈不堪,有几个工作人员坚决不敢干了,也不讲明原因。后来才得知,他们勘测时,遇上了强盗,如不及早发现尽快逃脱,将被悉数擒捉。但洵才有个特点,只要他答应了的事,不论碰到什么困境,受到什么挫折,都要想方设法完成任务。中印公路的勘测尽管困难重重,也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治学严谨 务实求真
王洵才平时寡言守讷,不善言谈,更不会交际。他的头脑中装着两件事,一是做学问,一是干工作。他治学态度非常严谨,学习的内容也很广泛。凡是与土木工程有关的水文、地质、力学、气象学以至工业布局、矿产资源、人口问题以及新兴的交通地理学等等,无不深钻细研探幽发微,往往为一个数据(哪怕是小数点后的一个微差),通宵达旦反复验证,以澄是非。即使在家中休假,也大半是在读书、构图、计算、验证中度过的。他的记忆力强得惊人。技术人员向他求教学问,或帮后辈学习数理、外语,他能指出,这个问题在某书某卷某章某节上有详细说明。释疑解惑,兴会淋漓,侃侃而谈,连续几个小时毫无倦意。一涉及其它交际问题,往往是答非所问,心不在焉,有时把亲戚朋友弄得啼笑皆非,为此也常受家人埋怨。他时常这样解释:“船员以船为家,车务员以火车为家,看样子,我一生的心血,是要浇铸在土木工程上了!”在工作中王洵才同志非常重视实践,重视求实存真,常以“传闻不如亲见,视景不如察形”自戒和育人。
1954年,有人建议重建济南黄河铁桥(洛口至桑梓店),理由是此桥桥龄太长,原设计货载等级低,抗战时韩复榘败退时曾炸毁过,长期慢行使用,不适应大规模建设的需要,苏联专家也赞成重建。当时国家经济尚未完全恢复,财政还很困难,军事运输任务还很繁重,在这样情况下,济南铁桥是否需要重建?王洵才认为,一桥虽少,干系重大,不是济南铁路局可以决定的,也不是铁道部可以决定的,他几次登桥涉水进行检查,又认真阅读了原桥的图纸,然后作出了“济南黄河大桥可继续使用50年,并可撤销慢行,无须重建”的建议,并在建议中签了字。周总理看了这个建议后,亲自洵问了王洵才。国务院随即做出“济南铁桥继续使用,撤销慢行,暂不重建”的决定。
1957年汛期,黄河发生特大水灾,京广线郑州黄河大桥冲毁,全国南北两大交通动脉只剩津浦一线。如果济南黄河大桥再冲垮,全国南北交通中断,将会造成巨大损失。周总理指示济南铁路局,一定要加固济南黄河大桥,保证安全度过汛期。王洵才亲临现场,制定加固方案,立即付诸实施。周总理视察时,王洵才向周总理作了详细汇报。总理认为切实可行。由于加固得力,济南铁桥承载着南北运输的重担,经受着特大洪水的考验,安然度过汛期。直到1991年春,新的双线黄河大桥建成,原来的黄河大桥,才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自1954年起,王洵才被选为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第四届人大代表时,因年迈多病,恳请组织批准,另行遴选。1959年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时,在一次晚会上,总理与王洵才同志亲切交谈:“胶济路现在要不要修复线?”王洵才说:“按照现在的客流量和货运量,不需要修复线,单线完全能应付得了,修早了倒是浪费。”时隔不久,国务院作出了“胶济铁路暂不修复线”的决定。有的同志曾经善意地规劝过王洵才:“王局长如此直来直往,你就不怕犯“右”的错误?”王洵才笑道:“科学就是实事求是,搞科学的人,首先要做到‘彰非明是,捐私虑,效公益’,不能怕犯错误。”
建国后,政务院和铁道部酝酿修一座武汉长江大桥,连接武昌、汉阳、汉口三镇,并使京汉、粤汉两条铁路连成一线——京广线。建桥前政务院和铁道部召开了有全国著名桥梁专家参加的武汉长江大桥设计方案会议,全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王洵才、唐振绪等同志都参加了会议。会议上王洵才出示了他设计的武汉长江大桥结构图,此图不少部分为1955年正式施工建桥所采用。
1975年,铁道部决定胶济、蓝烟两线修复线,但有关资料已于内乱中丧失殆尽,于是派人到青岛铁路医院求教于住院养病的王洵才。当时王洵才已是78岁的高龄,离开岗位已经八九年了,但他仍将两线情况及修复线的重点、难点和应注意的问题,一一作了详细介绍,清晰明确,凿凿有据。两位访问者对老人精熟的业务,惊人的记忆力感叹不已,他们深有感触地说:“看王洵才同志的介绍,没有图纸也敢施工!”
廉洁奉公 为自己想得很少
王洵才同志担任铁路建设领导工作,前前后后50多年,在人、财、物等方面,应说是有“实权”的,但他一生廉洁自持,为自己想得很少很少。1952年开展“五反”运动时,王洵才担任工务段长和总工程师。所检查出来的问题是丢失了多少只铅笔和多用了几瓶浆糊。然而他对国家的贡献和对他人的照顾是不遗余力唯恐有所不周的。
1930年前后,王洵才在青岛齐东路买了一块地皮,准备利用在美国工作期间挣的钱盖幢住房。后来为了上下班方便,又与一个朋友在青岛火车站随近合买了一块地皮,由王洵才设计,按一个图纸各出3000元的造价,每人盖了一处住房。后来那个朋友又酌价卖给了王洵才。在任胶济路第二工务总段长和济南铁路局副局长时,长住济南,领导要给他安排住房。他认为很多职工缺房,自己在青岛有房,不应该给国家增加困难,坚持住招待所,步行上下班,不要公房。星期天、节假日来回跑青岛,过两地生活,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1954年,王洵才又以为,青岛住房紧张,国家压力太大,自己住不了那么多房,索性把那份闲房和齐东路的一块地皮,无偿地捐献给了国家。
1938~1940年,王洵才同志任滇缅铁路工程司时,有个老铁路工人的女儿,读书十分聪明,但老铁路工人收入微薄,无力供给女儿上大学。王洵才同志得知后,慷然资助,让其女儿考上大学,调西南公路总局工作,仍按月给老工人寄钱,直到他女儿大学毕了业。老铁路工人非要把女儿给王洵才做二房不可,并要女儿跪下给王洵才磕头。洵才说:“我已有妻室子女,不能再娶,为你女儿略尽绵薄,是让她求学深造,报效祖国,若非如此,就失去我的本意了。”洵才为人十分谦逊,不论自己为国家为人民做了多少贡献,都觉得这是应该做的,不值一提。他在修复淮河大桥时立了一等功,从来没对人提过,当时了解的几个人已调他职或成故人,年轻人谁也不知道。直到他停止了呼吸,济南铁路局为他写悼词时,才从铁道部转来的档案中查阅得知。
历尽坎坷 不坠鸿鹄之志
在史无前例的大内乱中,一场意料不到的灾难降临到王洵才同志的头上。一开始他就被当做“反动技术权威”、“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进行“严格审查”和“重点批判”。王洵才当时已属古稀之年,常感心虚力衰且患严重的关节炎病,这样的一位老专家、学者,不可避免地遭受了种种折磨、迫害,蒙受了不白之冤。多亏王老心胸豁达,相信“是非自有公论”,“历史会做出见证”,沉着应变,泰然处之,没有就此垮了下去。
王洵才有三个子女。大女儿王恒珍,1941年在青岛高考,以全市总分第一的成绩,录取于北京大学官费读书。在北大就读期间,参加了党的地下组织,积极开展学生运动,引起了特务的注意。在北大修业三年半,在党组织的指示下离开北大到青岛工委(驻胶南县灵山卫区),做地下工作。1967年内乱鼎沸,无辜受到批判。次女王恍珍,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1946年冬参加革命,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回国后在母校执教,“文革”时受到牵连。儿子王兆拓,1948年受业于北大工学院,同年入党,后转入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后,分配到国家计委城市规划局工作,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在摧残文化的“大革命”中,被冠以种种罪名,横加折磨,1967年4月冤愤而死。王洵才的夫人孙希本同志,勤劳贤惠而又通情达理,抗战期间,王洵才同志远离青岛去大后方供职,孙希本同志留家中操持家务,抚养子女,与王洵才同志音信隔绝,生活无接济,备受艰辛。在日寇封锁经济时,靠做咸菜、酱油维持生活。大女儿做地下工作时,以自家为联络点,希本同志甘当风险,多方支持。1967年男人受牵连,子女受株连,听到儿子死去的噩耗,一病不起,于同年11月,离开了人世。
王洵才晚年,丧妻失子,哀死伤离,本人受审查(日夜有两个人监视),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但他仍有一个坚强的信念:一定要坚持下去,待问题弄清后,再为国家效力。造反派没完没了的审查,始终也没能查出什么政治问题,1971年,王洵才同志才发了工资。
年龄不饶人,王老的身体长期超负荷运转,又经受了十年内乱这样的折磨,旧病未去,又增新疾,不得不住院治疗。治疗一段时间以后,病情似有好转,但困境并没有解除,老妻和儿子都离开了人世,两个女儿都在北京工作。儿子死了以后,儿媳改嫁,青岛的住房,也不能由自己做主,垂暮之年,哪能没个归宿。这时组织上派人到医院看望,并征求王老以后的休养意见。80高龄的王洵才同志,提笔写了4条意见:第一要坚持工作;第二要到济南科协搞科研;第三要到疗养院边工作边疗养;第四到北京住女儿家。青岛分局请示了济南铁路局。济南铁路局考虑王洵才同志年事已高,不能再继续工作了,批准了第四条意见,让王洵才同志到北京女儿家养老。但王老对他毕生进行的铁路建设事业,仍然恋恋不舍,看到铁路局的批示,不无感慨。耄耋之年且患重病,反复要求工作,一再申明,“离开了工作,岂不成了废人!”
1977年7月21日,王洵才同志旧病又发,于北京医院去世。
半个多世纪以来,王洵才同志以毕生心血,浇铸土木工程,成绩卓然,举世共见。他把个人正大的宗旨、超人的才智和非凡的毅力,全部倾注于祖国的伟大建设事业。他勤奋严谨务实求真的优良作风,他廉洁奉公舍己为人的美德,他默默奉献不图虚名的高尚情操,他历尽坎坷,不坠鸿鹄之志、报效祖国之心老而弥笃的宽阔胸襟,处处感人肺腑,催人泪下。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王洵才同志确实是我们向往、学习的最好师表、楷模。
王洵才(1897—1977年),字幼泉,山东省牟平县养马岛镇马埠崖村人。父名汝奇,晚清秀才,素慕岳飞、韩世忠、文天祥之为人,取字景韩(景仰韩世忠之意)。景韩先生博通经籍,并擅医术,于本村私塾课读,兼行医济世。村邻求医问药者,往来不绝。他有子女6人,教书束修微薄,行医只收药费,难养8口之家,乃弃儒就业于合族开办的一个油坊,加上夫人缝补渔网之收入,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洵才自幼聪敏过人,7岁时于本村私塾就读,所学过目不忘。因受严父教诲,总角少年即怀读书报国之志。不幸14岁时,父亲一病不起。父故后依靠在朝鲜大使馆工作的兄长王瀛才资助,加之母亲勤俭持家,一家人得免饥寒之苦。洵才同志幼失父恃,辍学而不辍求知之志,一定要坚持上学读书,家兄无奈,于1911年把洵才同志送到烟台英法学校就读。英法学校除国文教师用汉语教学外,数理教师都是外国人,全用英语讲课,洵才只读过几年私熟,根本不懂外语,学习起来感到十分困难。也是天无绝人之路,洵才有个表兄叫黄善圃,在烟台经商,西学根底很深,英语娴熟。洵才每天晚上,每个星期天和每个假日,都去缠着黄善圃,学习英语,补习功课。第一年年终考试,国文全班第一,数理名列前茅。1914年,洵才考入北京汇文中学,高中毕业后,以优异成绩录取于国立唐山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专攻桥梁专业。在唐山读书4年,平时没请一天假,寒暑假也没回家一次,一来家庭贫寒,没有川资;二来勤奋攻读,也不愿抛废时光。
1920年由国家保送官费赴美留学,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系深造。就读三年,取硕士学位。1922年毕业后,在美利坚桥梁公司实习一年,米楼瓦城市工程局工作一年,企城承造工程公司工作一年。当时洵才风华正茂,风度翩翩而又才华横溢,在美国受到许多才女的爱慕和追求(洵才同志赴美前已经结婚,爱人孙希本,比洵才大4岁),洵才同志一一婉言辞去,明言已婚不能再娶。“糟糠之妻不能忘也”。在米楼瓦城市工程局和企城承造工程公司工作期间,洵才精明干练和诚信严谨的才能和作风,深得美方赞许,他们竞相以高职厚薪相挽留,但洵才不为名利地位所惑,只图报效桑梓,坚持拒绝,毅然启程回国。
在关键时刻的抉择
1925年冬,王洵才留美回国后,即到南京政府交通部报到,在交通部路政司工作了很短一段时间,正式分配在胶济铁路管理局工作,任工务员和帮工程司(当是工程师职务分三等:帮工程司、工程司、正工程司)。任帮工程司时,接受了设计施工城阳桥(城阳至韩漥,中经墨水河,高31米的上承钢板梁大桥,现属青岛市区)的任务,洵才详加勘测,胸有成竹,很快完成了设计任务。竣工后,中外专家评定,此桥设计遵重科学而别具一格,省工省料而坚牢度高,说明设计者根底深厚,才识不凡。城阳桥使用至今,60余年,安然无恙。洵才因此崭露了才华,由工务员、帮工程司直提升为胶济铁路第二工务段(胶济路分两工务段:第一工务段青岛至潍坊,第二工务段济南至潍坊)总段长、正工程司,旋即调任第一工务段总段长、正工程司。
1938年,日寇霸占了胶济铁路并控制了青岛。旬日后,即通知铁路工作人员到青岛指定地点报到。日本人按号叫人,逐一审查,叫到王洵才号数时,王洵才闭口不答。翻译官质问,洵才同志说:“中国人都有自己的名字,不叫名字叫号,是什么意思?”弄得翻译官面红耳赤。实际上,自日军铁蹄踏入青岛,洵才就寝食不安,深感异族入侵,国难当头,热血男儿当有所抉择。一是留在沦陷区,甘受凌辱,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一是去美国,高职厚薪,无虑温饱;一是去大后方,抵御外侮,精忠保国,走抗日道路。他选择了后者。在日本人通知报到的第二天深夜,他绕过了滋阳路(有日军看守),从定陶路后墙翻出,丢下病妻幼子,辗转去到了大后方重庆。
到重庆后,国民党交通部(部长曾养府,继任部长孙科)派王洵才去修滇缅铁路。滇缅铁路计划从昆明修到缅甸的密支那,在昆明设滇缅铁路工程局(局长杜振远,解放后在铁道部工作),王洵才任总工程司和桥梁股股长。
铺轨20多公里以后,缺钱短料。抗战时局紧张,瞬息万变,人心惶惶,滇缅铁路不得不报废停修。以后又修了几条公路。终因时局不稳,公路也被迫停工。王洵才同志接受了重庆中央大学的聘请,到该校工程系任教授。
1945年抗战胜利后,王洵才返回济南铁路局,任工务处长。这时,济南铁路局长陈舜耕多次动员王洵才加入国民党。王洵才对陈舜耕的说教,无动于衷,乃于1948年辞去济南铁路局工务处长职务,到北京大学工学院任土木工程系教授。解放前夕,又被调至前津浦区铁路局任工程处长兼总工程司。
1949年春,南京国民党政府,惶惶准备南逃,山东除青岛一隅,均获解放,津浦区铁路管理局只剩青岛至城阳30公里铁路,无路可管,形同虚设。这时,陈舜耕已调任台湾铁路局局长,邀王洵才到台湾与其共事。他思虑再三,决定跟共产党走!1949年3月,王洵才同志决然离开了南京,回到了青岛家中。
架桥铺路 不怕任重道远
1949年4月,中共城市工作部青岛工作委员会,派王恒珍(王洵才的大女儿,化名孙建平)与王洵才联系,争取王洵才及早参加人民铁路工作,王洵才欣然同意。6月2日,青岛解放,8月,王洵才同志亲赴济南,到铁路局报到供职。
1949年1月淮海战役后,国民党溃败南逃时,炸毁了淮河大桥。津浦路担负着南北交通运输的重要任务,尤其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百废俱兴,一刻千金,炸毁淮河大桥,无异于切断了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党中央和国务院非常焦急,周总理责成济南铁路局组织抢修,王洵才当时任济南铁路局顾问工程师,1949年调驻蚌埠,参与技术指导工作。淮河大桥破坏严重,当时设备、材料不足,修复极为困难。王洵才提出了修复方案,组织指导全体技术人员和广大职工(包括民工),克服了一道道技术难关,竟使破坏严重的淮河大桥提前一个月,于1950年5月1日完成修复任务。当时参加修复工作的苏联专家,对王洵才广博的土木建筑知识,非凡的技术水平和严密的组织能力,也深表钦佩。铁道部为王洵才记一等功。同年7月,王洵才擢任济南铁路管理局副局长(正局长赵锡纯同志)兼总工程师。当时国民经济还比较困难,抗美援朝也未结束,第五工程局只担负蓝烟一线的施工,压力不大。抗美援朝结束后,我国进入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时期,铁路建设的任务逐年加重。1955年除蓝烟路外,第五工程局还接受了杭州至宁波铁路的修建任务。1956年除完成了上述两线的配套工程并验收交付营业运输外,又承担了三项修建任务:一是供武汉钢铁公司运料的武昌——大冶铁路,二是供河南平顶山运煤炭的孟庙——平顶山线,三是为缓解陇海铁路压力的郑州——洛阳间的复线。看过的同志提出,第五工程局的担子太重了,是否向铁道部请示一下,减修几条路?王洵才总是动员大家:“现在的形势是一个人要顶几个人干,架桥铺路,何惧任重道远!”自1954年至1957年5月,4年多的时间,第五工程局的施工任务,由1条线路扩大为5条线路,由1省扩大为4省,点多线长,分布面广,再加上铁路建设的规章制度还未正式建立,通讯设备和其它工具设备相当落后,指挥困难,施工难度大,但年年提前完成任务,没有发生任何技术质量和工程安全事故。当然事业的成功,包括诸多因素,但不管怎么说,与集体施工的组织者、领导者、总工程师王洵才的指挥有方、组织得力是分不开的。
王洵才很善于把广博精深的土木建筑知识,运用于铁路建筑实践。他勘查路线、制定方案、组织施工稳健而求新,民主而善断,因地制宜,随时应变。1956年,河南平顶山支线设计,按原计划由临颖出岔,王洵才复勘后,重新制定了方案,提出了合理建议,由孟庙站出岔,缩短了运营里程,避开了颖河,免修大桥一座,铁道部采纳了这一建议。1953年至1957年修蓝烟铁路时,王洵才亲自勘测路线,对蓝村至莱阳一段,提出了改线建议。铁道部按这个建议施工,避开一条大河,免修两座桥梁,免凿一条隧道,为国家节省投资4000万元(当时旧值),获铁道部一等奖。
王洵才的身上还充分体现出惊人的毅力和吃苦耐劳的传统。1938年至抗战胜利前,洵才参加了滇缅铁路和南部边陲几条公路的修筑,虽受时局影响事倍功半或功亏一篑,但身为总工程司的王洵才的力并没有少出,事也没少费。滇缅铁路地处西南边陲之云贵高原,计划修筑1000多公里,要穿过南北走向的怒山、清水朗山、无量山、哀牢山、点莟山等大小几十座山脉,要跨过怒江、澜沧江、扎社江、龙川江等大大小小几百条河流,地理环境复杂,气候十分恶劣。王洵才与几个勘测人员,只用一辆吉普车,装载仪器、工具、行李和食物,翻山越岭,渡江涉水,穿越森林,主要靠两只脚一双手跋涉攀登。喝水,洗脸,吃饭兼用一个水桶。深山密林中有“瘴气”、“哑泉”和毒蛇猛兽,有的工作人员中了瘴气,似发虐疾,持久不退。有的喝了哑泉水,嗓子肿痛,发音不清。在勘测中没染病的很少,王洵才却安然无恙,他饶有风趣地向队员介绍“经验”:“我从小愿意和小朋友到家乡后山掀石头,捉蝎子,捉住以后,去掉毒针,生生吃掉,所以现在不染病,恐怕少年时吃蝎子收到的以毒攻毒之效吧。”滇缅铁路报废以后,又去勘测公路。在勘测中印公路线路时,有一天,他们仓惶跑回,人困马乏,狼狈不堪,有几个工作人员坚决不敢干了,也不讲明原因。后来才得知,他们勘测时,遇上了强盗,如不及早发现尽快逃脱,将被悉数擒捉。但洵才有个特点,只要他答应了的事,不论碰到什么困境,受到什么挫折,都要想方设法完成任务。中印公路的勘测尽管困难重重,也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治学严谨 务实求真
王洵才平时寡言守讷,不善言谈,更不会交际。他的头脑中装着两件事,一是做学问,一是干工作。他治学态度非常严谨,学习的内容也很广泛。凡是与土木工程有关的水文、地质、力学、气象学以至工业布局、矿产资源、人口问题以及新兴的交通地理学等等,无不深钻细研探幽发微,往往为一个数据(哪怕是小数点后的一个微差),通宵达旦反复验证,以澄是非。即使在家中休假,也大半是在读书、构图、计算、验证中度过的。他的记忆力强得惊人。技术人员向他求教学问,或帮后辈学习数理、外语,他能指出,这个问题在某书某卷某章某节上有详细说明。释疑解惑,兴会淋漓,侃侃而谈,连续几个小时毫无倦意。一涉及其它交际问题,往往是答非所问,心不在焉,有时把亲戚朋友弄得啼笑皆非,为此也常受家人埋怨。他时常这样解释:“船员以船为家,车务员以火车为家,看样子,我一生的心血,是要浇铸在土木工程上了!”在工作中王洵才同志非常重视实践,重视求实存真,常以“传闻不如亲见,视景不如察形”自戒和育人。
1954年,有人建议重建济南黄河铁桥(洛口至桑梓店),理由是此桥桥龄太长,原设计货载等级低,抗战时韩复榘败退时曾炸毁过,长期慢行使用,不适应大规模建设的需要,苏联专家也赞成重建。当时国家经济尚未完全恢复,财政还很困难,军事运输任务还很繁重,在这样情况下,济南铁桥是否需要重建?王洵才认为,一桥虽少,干系重大,不是济南铁路局可以决定的,也不是铁道部可以决定的,他几次登桥涉水进行检查,又认真阅读了原桥的图纸,然后作出了“济南黄河大桥可继续使用50年,并可撤销慢行,无须重建”的建议,并在建议中签了字。周总理看了这个建议后,亲自洵问了王洵才。国务院随即做出“济南铁桥继续使用,撤销慢行,暂不重建”的决定。
1957年汛期,黄河发生特大水灾,京广线郑州黄河大桥冲毁,全国南北两大交通动脉只剩津浦一线。如果济南黄河大桥再冲垮,全国南北交通中断,将会造成巨大损失。周总理指示济南铁路局,一定要加固济南黄河大桥,保证安全度过汛期。王洵才亲临现场,制定加固方案,立即付诸实施。周总理视察时,王洵才向周总理作了详细汇报。总理认为切实可行。由于加固得力,济南铁桥承载着南北运输的重担,经受着特大洪水的考验,安然度过汛期。直到1991年春,新的双线黄河大桥建成,原来的黄河大桥,才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自1954年起,王洵才被选为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第四届人大代表时,因年迈多病,恳请组织批准,另行遴选。1959年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时,在一次晚会上,总理与王洵才同志亲切交谈:“胶济路现在要不要修复线?”王洵才说:“按照现在的客流量和货运量,不需要修复线,单线完全能应付得了,修早了倒是浪费。”时隔不久,国务院作出了“胶济铁路暂不修复线”的决定。有的同志曾经善意地规劝过王洵才:“王局长如此直来直往,你就不怕犯“右”的错误?”王洵才笑道:“科学就是实事求是,搞科学的人,首先要做到‘彰非明是,捐私虑,效公益’,不能怕犯错误。”
建国后,政务院和铁道部酝酿修一座武汉长江大桥,连接武昌、汉阳、汉口三镇,并使京汉、粤汉两条铁路连成一线——京广线。建桥前政务院和铁道部召开了有全国著名桥梁专家参加的武汉长江大桥设计方案会议,全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王洵才、唐振绪等同志都参加了会议。会议上王洵才出示了他设计的武汉长江大桥结构图,此图不少部分为1955年正式施工建桥所采用。
1975年,铁道部决定胶济、蓝烟两线修复线,但有关资料已于内乱中丧失殆尽,于是派人到青岛铁路医院求教于住院养病的王洵才。当时王洵才已是78岁的高龄,离开岗位已经八九年了,但他仍将两线情况及修复线的重点、难点和应注意的问题,一一作了详细介绍,清晰明确,凿凿有据。两位访问者对老人精熟的业务,惊人的记忆力感叹不已,他们深有感触地说:“看王洵才同志的介绍,没有图纸也敢施工!”
廉洁奉公 为自己想得很少
王洵才同志担任铁路建设领导工作,前前后后50多年,在人、财、物等方面,应说是有“实权”的,但他一生廉洁自持,为自己想得很少很少。1952年开展“五反”运动时,王洵才担任工务段长和总工程师。所检查出来的问题是丢失了多少只铅笔和多用了几瓶浆糊。然而他对国家的贡献和对他人的照顾是不遗余力唯恐有所不周的。
1930年前后,王洵才在青岛齐东路买了一块地皮,准备利用在美国工作期间挣的钱盖幢住房。后来为了上下班方便,又与一个朋友在青岛火车站随近合买了一块地皮,由王洵才设计,按一个图纸各出3000元的造价,每人盖了一处住房。后来那个朋友又酌价卖给了王洵才。在任胶济路第二工务总段长和济南铁路局副局长时,长住济南,领导要给他安排住房。他认为很多职工缺房,自己在青岛有房,不应该给国家增加困难,坚持住招待所,步行上下班,不要公房。星期天、节假日来回跑青岛,过两地生活,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1954年,王洵才又以为,青岛住房紧张,国家压力太大,自己住不了那么多房,索性把那份闲房和齐东路的一块地皮,无偿地捐献给了国家。
1938~1940年,王洵才同志任滇缅铁路工程司时,有个老铁路工人的女儿,读书十分聪明,但老铁路工人收入微薄,无力供给女儿上大学。王洵才同志得知后,慷然资助,让其女儿考上大学,调西南公路总局工作,仍按月给老工人寄钱,直到他女儿大学毕了业。老铁路工人非要把女儿给王洵才做二房不可,并要女儿跪下给王洵才磕头。洵才说:“我已有妻室子女,不能再娶,为你女儿略尽绵薄,是让她求学深造,报效祖国,若非如此,就失去我的本意了。”洵才为人十分谦逊,不论自己为国家为人民做了多少贡献,都觉得这是应该做的,不值一提。他在修复淮河大桥时立了一等功,从来没对人提过,当时了解的几个人已调他职或成故人,年轻人谁也不知道。直到他停止了呼吸,济南铁路局为他写悼词时,才从铁道部转来的档案中查阅得知。
历尽坎坷 不坠鸿鹄之志
在史无前例的大内乱中,一场意料不到的灾难降临到王洵才同志的头上。一开始他就被当做“反动技术权威”、“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进行“严格审查”和“重点批判”。王洵才当时已属古稀之年,常感心虚力衰且患严重的关节炎病,这样的一位老专家、学者,不可避免地遭受了种种折磨、迫害,蒙受了不白之冤。多亏王老心胸豁达,相信“是非自有公论”,“历史会做出见证”,沉着应变,泰然处之,没有就此垮了下去。
王洵才有三个子女。大女儿王恒珍,1941年在青岛高考,以全市总分第一的成绩,录取于北京大学官费读书。在北大就读期间,参加了党的地下组织,积极开展学生运动,引起了特务的注意。在北大修业三年半,在党组织的指示下离开北大到青岛工委(驻胶南县灵山卫区),做地下工作。1967年内乱鼎沸,无辜受到批判。次女王恍珍,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1946年冬参加革命,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回国后在母校执教,“文革”时受到牵连。儿子王兆拓,1948年受业于北大工学院,同年入党,后转入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后,分配到国家计委城市规划局工作,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在摧残文化的“大革命”中,被冠以种种罪名,横加折磨,1967年4月冤愤而死。王洵才的夫人孙希本同志,勤劳贤惠而又通情达理,抗战期间,王洵才同志远离青岛去大后方供职,孙希本同志留家中操持家务,抚养子女,与王洵才同志音信隔绝,生活无接济,备受艰辛。在日寇封锁经济时,靠做咸菜、酱油维持生活。大女儿做地下工作时,以自家为联络点,希本同志甘当风险,多方支持。1967年男人受牵连,子女受株连,听到儿子死去的噩耗,一病不起,于同年11月,离开了人世。
王洵才晚年,丧妻失子,哀死伤离,本人受审查(日夜有两个人监视),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但他仍有一个坚强的信念:一定要坚持下去,待问题弄清后,再为国家效力。造反派没完没了的审查,始终也没能查出什么政治问题,1971年,王洵才同志才发了工资。
年龄不饶人,王老的身体长期超负荷运转,又经受了十年内乱这样的折磨,旧病未去,又增新疾,不得不住院治疗。治疗一段时间以后,病情似有好转,但困境并没有解除,老妻和儿子都离开了人世,两个女儿都在北京工作。儿子死了以后,儿媳改嫁,青岛的住房,也不能由自己做主,垂暮之年,哪能没个归宿。这时组织上派人到医院看望,并征求王老以后的休养意见。80高龄的王洵才同志,提笔写了4条意见:第一要坚持工作;第二要到济南科协搞科研;第三要到疗养院边工作边疗养;第四到北京住女儿家。青岛分局请示了济南铁路局。济南铁路局考虑王洵才同志年事已高,不能再继续工作了,批准了第四条意见,让王洵才同志到北京女儿家养老。但王老对他毕生进行的铁路建设事业,仍然恋恋不舍,看到铁路局的批示,不无感慨。耄耋之年且患重病,反复要求工作,一再申明,“离开了工作,岂不成了废人!”
1977年7月21日,王洵才同志旧病又发,于北京医院去世。
半个多世纪以来,王洵才同志以毕生心血,浇铸土木工程,成绩卓然,举世共见。他把个人正大的宗旨、超人的才智和非凡的毅力,全部倾注于祖国的伟大建设事业。他勤奋严谨务实求真的优良作风,他廉洁奉公舍己为人的美德,他默默奉献不图虚名的高尚情操,他历尽坎坷,不坠鸿鹄之志、报效祖国之心老而弥笃的宽阔胸襟,处处感人肺腑,催人泪下。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王洵才同志确实是我们向往、学习的最好师表、楷模。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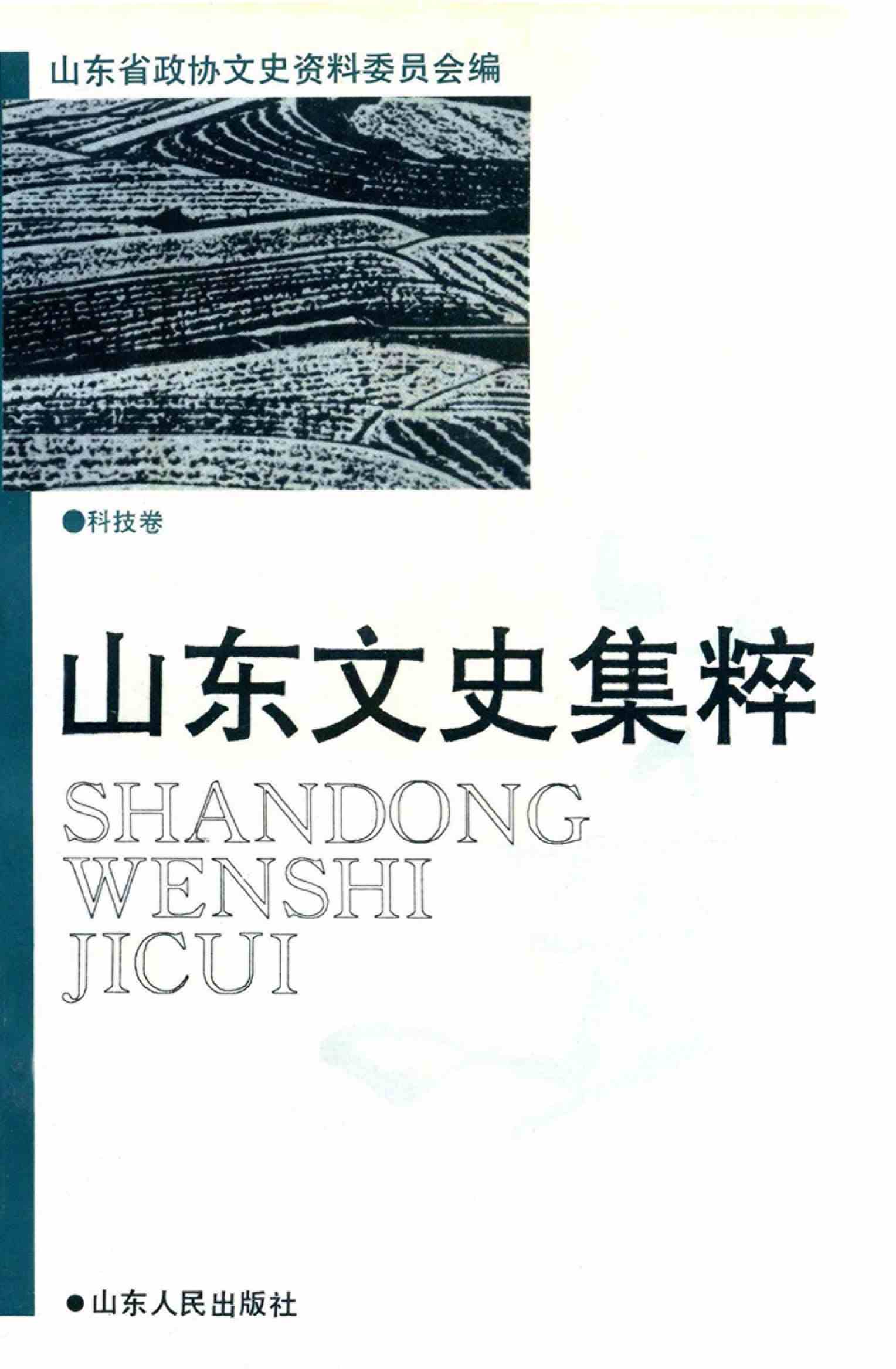
《山东文史集粹·科技卷》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本书收录了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丁肇中、著名科学家郭永怀烈士、杰出物理学家王淦昌、我国早期原子能物理专家王普博士、忆束星北教授、著名力学专家刘先志、著名航空工程专家丁履德、电子计算机专家王正、“西圣”孙学悟等多篇文章。
阅读
相关人物
曲言训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