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行星预测天气的奠基人栾来宗
| 内容出处: | 《山东文史集粹·科技卷》 图书 |
| 唯一号: | 150020020220007051 |
| 颗粒名称: | 以行星预测天气的奠基人栾来宗 |
| 分类号: | K826.14 |
| 页数: | 11 |
| 页码: | 218-228 |
| 摘要: | 栾来宗,寒亭区双杨店镇华疃村人,1857年出生于一个中等农民家庭,本天性聪颖,又十年寒窗,成为当地儒林的佼佼者。他虽孜孜好学,但不是为了仕途求进,而是把毕生精力用之于施惠当代,造福后人。他的一生,给当地人们留下了许多久为传颂的佳话,特别力排吞噬穷人的丧葬旧习,义举“仁义周济会”,这一办丧从简、街坊互助之举,一直为众乡里称道,此文不尽详述。他辛勤的汗水,为“以行星运动作超长期天气预报”开辟了道路。这比1984年2月29日塔斯社发布的消息——“苏联科学家查明地球气候受大小行星的影响”早了百年。正是它的为害才使栾来宗萌发了济世救民的愿望。 |
| 关键词: | 山东 天气 栾来宗 |
内容
栾来宗,寒亭区双杨店镇华疃村人,1857年出生于一个中等农民家庭,本天性聪颖,又十年寒窗,成为当地儒林的佼佼者。他虽孜孜好学,但不是为了仕途求进,而是把毕生精力用之于施惠当代,造福后人。他的一生,给当地人们留下了许多久为传颂的佳话,特别力排吞噬穷人的丧葬旧习,义举“仁义周济会”(俗名架子会),这一办丧从简、街坊互助之举,一直为众乡里称道,此文不尽详述。要介绍的乃是他那为济世救民而献身终生的精神和留下的业绩:他除了当过三年塾师之外,竟然以40年之久,埋头于对奇旱大涝的探索,写下《天文农事》一书,直到临终,留下遗嘱,事业着子孙相继。他辛勤的汗水,为“以行星运动作超长期天气预报”开辟了道路。这比1984年2月29日塔斯社发布的消息——“苏联科学家查明地球气候受大小行星的影响”早了百年。
天文农时
栾来宗的家乡华疃,位于白浪河西岸。这条白浪河,纵贯潍县南北,旧社会是条害河,旱了无水,涝时泛滥,不知给两岸人民带来过多少次灾难。正是它的为害才使栾来宗萌发了济世救民的愿望。
他出生的清咸丰七年(1857年),是一个特大干旱年。据传这一年的小麦,连种子也没收回来,农民用糖菜度了过来。他也就因营养不足而致体形瘦弱。长大后写下了“生不遇时”这一憾事。到1876年,碰上光绪二年大旱,他记下了“赤地千里,野无青苗,树皮食尽,新坟相连”的惨象。1888年,又遇上了一场罕见的洪水,那是“自六月三十日,大雨倾泻三昼夜,七月初三,七河交流,暴雨洪水,弥连九天,潍北广域,尽成泽国……惨无甚于此者”。他曾想“何日盼得西门豹,根治白浪不起蛟”。这只不过是空想,自己知道没有能力使官府体察民间疾苦,治理河患。
他思索:如果对旱涝灾害有所先知,做到防患于未然就好了。他认为岐伯、孔丘、孙武、诸葛亮等,皆是我国历史上能预知天气的人物,他们知识渊博,能测风雨,可惜方法都没有传下来。特别是对于未来一年的旱涝,并没有人事先可以知道。几千年来,天下农民,仍然是“庄稼不收年年种,种地在人收靠天”。对此事,他怀疑起来:古人能知风雨,今人为什么不能;就是古人不能完全预知旱涝,今人难道不该有所突破!风、雨、阴、晴,这些自然现象,就真的不能揭开个中奥秘吗?带着这个问题,20岁上,他开始了自己的追求:“问三光(日月星)以究旱涝根源”。他想:太阳是天气变化的总根,它的光热不变,那每年蒸发的水汽总量就不变,落下的雨水总量也该是一样多。不落于此地,必落于他处。有一现象值得深思:雨涝之秋,连四十天不开晴,是什么力量把水汽一个劲地向这里引来;干旱之年,又数月点滴不流,又是什么力量总把水汽赶走?绝没有上帝、龙王,那这股“力量”到底是什么呢?
《书经》有云:“箕星好风,毕星好雨;月之从星,则以风雨”,这说法被他通过验证所否定。他发现雨涝年份,月亮经过毕星附近时有雨,远离毕星时同样有雨;旱年,月从毕无雨,不从亦无雨。这说明毕星不是雨星。同样,有风无风与月从箕星毫无关系。《黄帝内经》云:“岁金太过,燥气流行,上应太白。”但他发现这颗金星并不是光主旱,而且也主涝。“六十甲子,天道循环”的说法,也被他否了。不错,他从先人得知上一个“丁己”年(1797年)是山东大旱年,他出生的那个“丁己”年,又是个大旱年,可是再看其他干支相同年份,并没有这种周期。于是得出初步结论:那些不动的二十八宿,箕、毕、翼、轸等恒星,都不可能影响天气。
他开始了一条崭新的思路:“风、雨、阴、晴,总根是太阳,太阳虽无变化,可是它的家族成员——行星月亮却变换无常,天气之变,会不会是太阳系全“家”所使?如果找到行星布局相同的年份,而天气也一样的话,旱涝之谜也就解开了。”
他花费不知多少个日日夜夜,计算出五大行星需经过四易甲子——237年才有共同周期。使他惊喜的是,历史上有名的明崇祯特大干旱和清光绪特大干旱。竟然正是这大周期的循环。这使他欣喜欲狂:“只要记录下240年的天象,配以每年的天气,岂不是有了预知旱涝的依据!”(周期年份不会绝对相同,因为还有月球,行星大周期不包括它)。就是这一信念,使他毅然地献出了自己的一生。在他撰写《天文农时》一书中,开头序言是这样的: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农为本,农以时为天。播种得时,丰收之基,失时则空劳。孟子曰:‘勿夺农时,五谷不可胜食’。为知天时,伏羲氏完阴阳、画八卦,神农氏定八节,夏修历书,尽应寒署往还,季节交替,留传后世,指导稼穑。然天有异常之变,水旱之灾,自古至今,不知其源。
“以吾之见,唯太阴,五星之千变,可应天气之万化,具天象与天气之记载,两者相对,可得天象似则天气亦似之实据,五星满周期之日,即功业告成之时……然此数代人相继方可期……至诚之道,可先知。至诚者,实埋也,唯此以诚,而穷天之异变规律,后自预测如神,天终可知也……斯诚,纵求之不中,亦不远矣!”
在《天文农时》的首篇,栾来宗辩证地指出:“……古之知者,皆以天动而地静,孔子亦曰北辰居其中而众星拱之,此天动也。世人信之,眼见为实也。今之知者曰,地亦球,周转而成昼夜,航海者证之,日月食证之,故明者信而不疑……。凡事愈索愈明,既知旧说不可过泥,亦当知新说不可全信,前日之是可为今日之非,今日之是焉知不成后日之非?学者宜自勉,宇宙真理之阐发尚待于后来者,望后人勿泥前人迷时之见而不前。”
在第二篇《论阴阳变化之理》中,他指出“前人以日为太阳,月为太阴。视之,日为火,月为冰;试之,日出暖,月出寒;分之,日月形同而性异,故曰阴阳合而万物生。今人已知,地亦球,太阳以极热之火,熔地球之寒,则阳气下降,水气上升,而致气象万千。故阴阳之合,应属气象之始。气象虽源于日,古人测风雨而不言日,盖因日运有常而无变也……”,在本篇中他大胆地否定了古人“箕星好风,毕星好雨”的论点,指出:“箕毕二星者,二十八宿之属也,毕居于赤道之北,箕居其南。毕夏日之所在,箕冬日之所在,日从毕为夏,月复从之则雨;日从箕为冬,月复从之则风。此日、月同位故耳。古人不知南夏即北冬,故谬曰从毕则雨,从箕则风……”。
在第三篇《论二十八宿与五星之分》中,栾来宗进而阐述了只有月球和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可影响地球的原由。
他指出“恒星之属,其位于黄、白、赤三道之间者,日、月经、望之近,实是远矣,与日月之运行无干系,皆不能定旱涝,测风雨……。唯五星运行于黄白二道之间,有迟速、有逆顺、有近远、有聚分,五星虽少,如五音之变不可胜听,如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以应天气,故有变而少常也。知常者易,知变者难,五星定旱涝,犹如弈之分胜负,虽决于一子,众子关焉……”
他接着在第四篇《论五行与五星》中列举了大量收集到的史料和自己多年观测到的数据,进一步说明和论证自己的观点。他指出:“日、月、五星犹如棋势,势成则旱涝定……应以全球为一体,夏冬有彼此,此夏则彼冬;旱涝亦有彼此,此涝则彼旱……”。在第五篇《论六十花甲子与天气周期》中,他指明,“木、土、水三星会合周期近乎甲子更迭,实则59年;太阴之行,有18年循环;五星布局,有237年周期……”在本篇最后,他提出这样一段话,以激励后人,“大旱之年,良田变赤地;大涝之秋,家园尽泽国。云之集聚,何力所为?唯五星之势应之……大周记录齐全之时,是非自明,故用五论。望后人遇难而勿退,有成而不满,盈坷而后进,到诚而后神。”
《天文农时》一书的六至十篇论五谷,最后两篇论树、园,主要是对各类农作物种植,收获时令和其对于旱涝适应性能的论述。
栾来宗的另一血汗结晶,便是对历年天象、天气、物候和农作物丰欠的记录,内容浩繁;在星象方面,以黄道十二官为标志,记下了金、火、木、土四星各时期的位置,以恒星结合月影长短测定了各年度月亮回归方位;物候方面,记录着每年杏花开放、白杨吐穗、蜜蜂蝙蝠等出洞日期,天气异变时的动物征兆,如丁螳掩洞、蚂蚁搬家、蛇过道等。至于天气记录,尤为详尽:晴、阴、风、雨、雷、电、雹、雾、霜、霰,大小不漏,时间、程度、风向,一一标明,前后计30余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择贤托孤
栾来宗深知,要记录240年的天象和天气,没有几代人以至十几代人艰苦不懈的努力,是不可能完成的。这又是一项只可埋头苦干而无半点实惠的事情,除了靠自家子孙,根本不能求助于外人,因不会有人甘愿葬送一生精力。就是靠子孙相继,没有恒心也难以实现。所以他在《天文农时》的序言第五篇中,反复地强调了“诚”字。他在自己的书斋前,亲手栽下一棵特殊的小树,以象征比拟自己的事业。这棵树俗名刺松,特点是生长极慢,但不弯不曲,不论墙遮屋挡,风吹雨打,总是笔直地向着天空伸展。象一个不急不躁,不屈不挠,坚韧不拔的英雄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栾来宗赋诗日:“南山移奇株,北国定新居,人厌性偏迟,独爱志不屈。嘱我后世人,相伴续天书,参透其中妙,教民稼五谷。四迭甲子过,阳侯祝融出,天时共地利,自见千钟粟”。现在,这棵百岁小树,已碗口粗细,高三丈余,虽处在残垣败壁、荒草瓦砾之中,依然铮骨铁躯,直刺苍穹。顶端衬着小小树冠,很象一支即将离弦的箭,去刺探宇宙的奥秘。
着子孙继承他的事业,第一步就走不通了。他生有三女一子,旧社会女孩子捞不着读书,不能够传给她们,自然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天偏不作美,儿子栾佃照一年年长大,不愿老守田园,看上经商这一行当。栾来宗几度规劝,终不能使之就范,最后被儿子质问得无言以对:“亏尔满腹经伦,一辈子少吃缺穿,眼看爷爷留下的家当要折腾净了,自己受熬煎不算,莫非叫俺们晚辈要着吃?”也确象儿子所说,栾来宗一生埋头于“天文农时”,并没有用在实处,过的日子是入不敷出,致使家底日薄,幸亏儿子能干,14岁当家支撑门面,以此要儿子也搞“天文农时”的事,被顶得理穷词屈,只好一声长叹!
1926年3月,他的孙子出世了。这孩子一颗大脑袋,两个眼珠子溜溜转。性格殊异,直到6个月,家人很少见他的笑脸。有时两眼盯上什么,任凭旁人怎么逗惹,也不理睬。栾来宗对这孩子爱如掌珠,每日里比孩子的妈妈抱的时候还要多。一家人只觉得爷爷拿着小孙孙比自己的命还急,又哪里知道,他已经把事业的希望全寄托在这第三代人身上了。他开始为这隔代人做“铺路”工作:用白纸糊了书房的天棚和四壁,天棚上画了星图,作了详尽的标记;四壁则画了祖国和世界地图。特别对当时的十八行省,编成歌谣,在孙孙咿呀学语的时候,便当做儿歌教唱。
1927年,栾来宗一场大病,卧床不起,百般调理,病情还是一天天加重,自知去日无多,于是盘算起如何把“事业”传给孙子的事来。孙孙栾巨庆尚不懂事,儿子佃照对此事向来持反对态度,只因礼教约束,表面上不过问、不干涉,实则他认为这是毫无意义的蠢事。栾来宗知道,若自己一旦下世,这“事业”肯定被他抛弃理葬,决不会叫后人干下去。要孙子能真正懂事,起码得十几年,那这十多年的岁月又如何处理?他苦思冥想,决定选择贤人相托。他把那些曾跟自己的读书的学生,在脑海里逐一进行了筛选,终于认定了一个可委托者——栾德修。
栾德修并没跟他念书,只是常随其族兄栾自修到栾来宗这里坐坐,听他谈论经书,天长日久,也算有了师生之谊。栾来宗发现他有与众不同的性格:沉默寡言,喜怒不形于色,处事老成持重;口无废语,语出必行,行必有成,以此对他十分器重。现在已是个塾师。栾来宗把他叫到床前,支开伺侯的家人,眼含热泪,向“弟子”倾吐衷肠:
“我少读圣贤之书,立志效法先哲,为世人做点好事,但岁月易逝,时不我待,今行将入木,余事未了——死不足惜,唯心中难平:举办的‘仁义周济会’,虽众乡里赞同,但反对者仍大有人在,若无牵头之人,恐难持久,此事唯‘无愧我心’而已。我所死不瞑目的并不是‘架子会’,而是……”说着他指了指顶棚上的星图和四壁的地图,述说了这些东西的来历后言道:“我已责令佃照,必将这顶棚和墙上的图保留二十年”。说到这里,他强撑起身子,拉开床前抽屉,拿出了手抄本《天文农时》及附书,以震颤的声音继续说了下去:
“这是我四十年的心血,上面记录了历年的星象、天气和适合种植的农作物。这只是个开端,完成它便是我到这世界年来的夙愿。这不是件容易事,得靠好几代人无偿地付出代价,才能有希望完成。
“奇旱大涝,有根有源,并非不可知之事。我经四十年探知,天气异变,乃是日、月、行星的布局而决定的。”栾德修听着,象啃木梨般茫然,不知如何回答。栾来宗继续说:“你不必忧惑,我不打算让你把这些事全弄明白,因为你没有必要无端地耗费精力,这是一项看不见因、摸不着果的事,我只能让我的子孙后代去干。此事我从不向人们讲,也不会有人相信。以五星测天与圣人论背道而驰(孔子以恒星),诬圣人言罪当死,故不能向人透露。”说到这里,栾来宗语气益加庄重:“今召你来,只一事相托,望念师生之谊答应我,烦你把此书保存,待浅亨(其孙栾巨庆的乳名)懂事,再转交给他,并告诉他我已呕心沥血大半生,为之开了个头,要他在这无形的长城上筑起一段,再传下去,直到……”
他几乎是字字泪,句句血,向着弟子述说了半天。栾德修被他那诚恳的态度和信任心情所感动,已决心完成业师所托。
栾来宗稍稍休息一会,又一次挣扎着坐着,握了栾德修的手:“向闻,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遗憾的就是不能亲传小孙,这百年大事,只能靠你了!”说罢,泪如雨下。栾德修见老师一再嘱托,知道这个老人为此事仍忧心忡忡,不禁双膝跪于床前,挥泪发誓:“师父放心,弟子决不会使你失望——你安心疗养身子吧,待痊愈之日,我再来领取教诲。”
“不,我不行了”栾来宗道,“现在你就把书拿去,珍藏起来,待十年之后,再让它出世。”说着从床头柜里抽出一个包袱,慢慢地把书包了起来,双手捧着递了过去。栾德修象接婴儿般的小心,含泪接了过来。此时此刻,师徒两颗心已经融在一起了。栾来宗仍余言未尽,那炽热期待的目光瞅着徒弟,好一会又开口说:“天已不早,你该走了。浅亨方满周岁,难度未来。我已经告诉佃照待懂事,就送他去你的塾中。你要看着他长大,教他成材。但愿苍天保佑,使他能象庭前那棵树一样正直坚强。如不成器,可留书以另待后来人!你回去吧!”说着挥了挥手,躺在床上闭目不再言语,他实在已精疲力竭。
不久,他带着“死而未已”的心,离开人世伴星月去了。
后记
民国28年(1939年)农历九月十四日,夜阑人静,华疃二村一幢曾是私塾的书房里,又是一师一徒在接续12年前的故事。师傅是栾德修,徒弟便是栾来宗的孙子栾巨庆。老人语重心长地向着未满十四岁的孩子叙述了他爷爷的往事。栾巨床听罢心潮起伏,久久难平,不知说什么才好,最后从他口中斩钉截铁般地吐出了几个字:“我知道了!”说罢擦了擦眼泪,从业师手中接过了《天文农时》。
他做为一个接力者踏上征途,不过,他没有按照爷爷指引的路走,因为那太慢了,他觉得一生只做个记录者,只为无形长城加几块“砖石”太少了。也许是历史不断的原因,他比爷爷更聪明,他悟出了一个道理:何必要等上240年?既然月亮、行星都有一定的运行规律,向前推算不是一样吗?向上算出它们各个时期的方位,对照历史的天气,以验证二者关系,岂不是一条捷径!他的路走对了。
一年、两年、十几年、几十年,他为了探索、验证,自食其力走过大江南北、塞外中原,当过搬运工、推车夫、伐木人;为向专家求教,他闯过13个大专院校。十年动乱时期,他被打成“专政对象”,被投进过监狱,用血汗凝成的数据、资料被七次没收,连爷爷的遗书统统被付之一炬。这曾一度使人痛不欲生,可一旦想到“诚”字,更使他咬紧牙关,迎着险阻,攀登、向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在内蒙古林业局、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等单位支持下,以他为首成立了天文气象研究小组,他们搜集和整理了1000多年的天文、气象史料。历史事实证明了栾来宗当年对“天气有59年小周期和237年大周期”的论断是正确的。更可喜者,栾巨床从中找出了行星方位影响地球的“对应区”,他于1983年写出了世界上第一部以天文预报天气的学术专著——《行星与长期天气预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人民日报》、《文汇报》、《工人日报》、《科技日报》等先后报道了他的事迹。
“对应区”的发现,随之揭开了一连串的不解之谜:“地震、太阳黑子竟也是与行星方位有关”。对此,《中国科技报》(今《科技日报》)一一做了报道。1987年8月2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特登载了“栾巨庆以行星研究太阳活动”的消息。1988年4月,一部40万字的论著——《星体与长期天气地震预报》出版了。该书参加了1988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图书展销会。
栾来宗的首创,栾巨庆的继往开来,不敢说已完善无缺,而只能仍算是开端。想来,广大气象工作者有必要以此作为参考,进一步探索,攻克长期天气预报这一堡垒,用之农事,用之于社会主义建设。届时,栾来宗九泉有知,当为这造福于亿万人类的功业,提前告成而含笑地下。
天文农时
栾来宗的家乡华疃,位于白浪河西岸。这条白浪河,纵贯潍县南北,旧社会是条害河,旱了无水,涝时泛滥,不知给两岸人民带来过多少次灾难。正是它的为害才使栾来宗萌发了济世救民的愿望。
他出生的清咸丰七年(1857年),是一个特大干旱年。据传这一年的小麦,连种子也没收回来,农民用糖菜度了过来。他也就因营养不足而致体形瘦弱。长大后写下了“生不遇时”这一憾事。到1876年,碰上光绪二年大旱,他记下了“赤地千里,野无青苗,树皮食尽,新坟相连”的惨象。1888年,又遇上了一场罕见的洪水,那是“自六月三十日,大雨倾泻三昼夜,七月初三,七河交流,暴雨洪水,弥连九天,潍北广域,尽成泽国……惨无甚于此者”。他曾想“何日盼得西门豹,根治白浪不起蛟”。这只不过是空想,自己知道没有能力使官府体察民间疾苦,治理河患。
他思索:如果对旱涝灾害有所先知,做到防患于未然就好了。他认为岐伯、孔丘、孙武、诸葛亮等,皆是我国历史上能预知天气的人物,他们知识渊博,能测风雨,可惜方法都没有传下来。特别是对于未来一年的旱涝,并没有人事先可以知道。几千年来,天下农民,仍然是“庄稼不收年年种,种地在人收靠天”。对此事,他怀疑起来:古人能知风雨,今人为什么不能;就是古人不能完全预知旱涝,今人难道不该有所突破!风、雨、阴、晴,这些自然现象,就真的不能揭开个中奥秘吗?带着这个问题,20岁上,他开始了自己的追求:“问三光(日月星)以究旱涝根源”。他想:太阳是天气变化的总根,它的光热不变,那每年蒸发的水汽总量就不变,落下的雨水总量也该是一样多。不落于此地,必落于他处。有一现象值得深思:雨涝之秋,连四十天不开晴,是什么力量把水汽一个劲地向这里引来;干旱之年,又数月点滴不流,又是什么力量总把水汽赶走?绝没有上帝、龙王,那这股“力量”到底是什么呢?
《书经》有云:“箕星好风,毕星好雨;月之从星,则以风雨”,这说法被他通过验证所否定。他发现雨涝年份,月亮经过毕星附近时有雨,远离毕星时同样有雨;旱年,月从毕无雨,不从亦无雨。这说明毕星不是雨星。同样,有风无风与月从箕星毫无关系。《黄帝内经》云:“岁金太过,燥气流行,上应太白。”但他发现这颗金星并不是光主旱,而且也主涝。“六十甲子,天道循环”的说法,也被他否了。不错,他从先人得知上一个“丁己”年(1797年)是山东大旱年,他出生的那个“丁己”年,又是个大旱年,可是再看其他干支相同年份,并没有这种周期。于是得出初步结论:那些不动的二十八宿,箕、毕、翼、轸等恒星,都不可能影响天气。
他开始了一条崭新的思路:“风、雨、阴、晴,总根是太阳,太阳虽无变化,可是它的家族成员——行星月亮却变换无常,天气之变,会不会是太阳系全“家”所使?如果找到行星布局相同的年份,而天气也一样的话,旱涝之谜也就解开了。”
他花费不知多少个日日夜夜,计算出五大行星需经过四易甲子——237年才有共同周期。使他惊喜的是,历史上有名的明崇祯特大干旱和清光绪特大干旱。竟然正是这大周期的循环。这使他欣喜欲狂:“只要记录下240年的天象,配以每年的天气,岂不是有了预知旱涝的依据!”(周期年份不会绝对相同,因为还有月球,行星大周期不包括它)。就是这一信念,使他毅然地献出了自己的一生。在他撰写《天文农时》一书中,开头序言是这样的: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农为本,农以时为天。播种得时,丰收之基,失时则空劳。孟子曰:‘勿夺农时,五谷不可胜食’。为知天时,伏羲氏完阴阳、画八卦,神农氏定八节,夏修历书,尽应寒署往还,季节交替,留传后世,指导稼穑。然天有异常之变,水旱之灾,自古至今,不知其源。
“以吾之见,唯太阴,五星之千变,可应天气之万化,具天象与天气之记载,两者相对,可得天象似则天气亦似之实据,五星满周期之日,即功业告成之时……然此数代人相继方可期……至诚之道,可先知。至诚者,实埋也,唯此以诚,而穷天之异变规律,后自预测如神,天终可知也……斯诚,纵求之不中,亦不远矣!”
在《天文农时》的首篇,栾来宗辩证地指出:“……古之知者,皆以天动而地静,孔子亦曰北辰居其中而众星拱之,此天动也。世人信之,眼见为实也。今之知者曰,地亦球,周转而成昼夜,航海者证之,日月食证之,故明者信而不疑……。凡事愈索愈明,既知旧说不可过泥,亦当知新说不可全信,前日之是可为今日之非,今日之是焉知不成后日之非?学者宜自勉,宇宙真理之阐发尚待于后来者,望后人勿泥前人迷时之见而不前。”
在第二篇《论阴阳变化之理》中,他指出“前人以日为太阳,月为太阴。视之,日为火,月为冰;试之,日出暖,月出寒;分之,日月形同而性异,故曰阴阳合而万物生。今人已知,地亦球,太阳以极热之火,熔地球之寒,则阳气下降,水气上升,而致气象万千。故阴阳之合,应属气象之始。气象虽源于日,古人测风雨而不言日,盖因日运有常而无变也……”,在本篇中他大胆地否定了古人“箕星好风,毕星好雨”的论点,指出:“箕毕二星者,二十八宿之属也,毕居于赤道之北,箕居其南。毕夏日之所在,箕冬日之所在,日从毕为夏,月复从之则雨;日从箕为冬,月复从之则风。此日、月同位故耳。古人不知南夏即北冬,故谬曰从毕则雨,从箕则风……”。
在第三篇《论二十八宿与五星之分》中,栾来宗进而阐述了只有月球和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可影响地球的原由。
他指出“恒星之属,其位于黄、白、赤三道之间者,日、月经、望之近,实是远矣,与日月之运行无干系,皆不能定旱涝,测风雨……。唯五星运行于黄白二道之间,有迟速、有逆顺、有近远、有聚分,五星虽少,如五音之变不可胜听,如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以应天气,故有变而少常也。知常者易,知变者难,五星定旱涝,犹如弈之分胜负,虽决于一子,众子关焉……”
他接着在第四篇《论五行与五星》中列举了大量收集到的史料和自己多年观测到的数据,进一步说明和论证自己的观点。他指出:“日、月、五星犹如棋势,势成则旱涝定……应以全球为一体,夏冬有彼此,此夏则彼冬;旱涝亦有彼此,此涝则彼旱……”。在第五篇《论六十花甲子与天气周期》中,他指明,“木、土、水三星会合周期近乎甲子更迭,实则59年;太阴之行,有18年循环;五星布局,有237年周期……”在本篇最后,他提出这样一段话,以激励后人,“大旱之年,良田变赤地;大涝之秋,家园尽泽国。云之集聚,何力所为?唯五星之势应之……大周记录齐全之时,是非自明,故用五论。望后人遇难而勿退,有成而不满,盈坷而后进,到诚而后神。”
《天文农时》一书的六至十篇论五谷,最后两篇论树、园,主要是对各类农作物种植,收获时令和其对于旱涝适应性能的论述。
栾来宗的另一血汗结晶,便是对历年天象、天气、物候和农作物丰欠的记录,内容浩繁;在星象方面,以黄道十二官为标志,记下了金、火、木、土四星各时期的位置,以恒星结合月影长短测定了各年度月亮回归方位;物候方面,记录着每年杏花开放、白杨吐穗、蜜蜂蝙蝠等出洞日期,天气异变时的动物征兆,如丁螳掩洞、蚂蚁搬家、蛇过道等。至于天气记录,尤为详尽:晴、阴、风、雨、雷、电、雹、雾、霜、霰,大小不漏,时间、程度、风向,一一标明,前后计30余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择贤托孤
栾来宗深知,要记录240年的天象和天气,没有几代人以至十几代人艰苦不懈的努力,是不可能完成的。这又是一项只可埋头苦干而无半点实惠的事情,除了靠自家子孙,根本不能求助于外人,因不会有人甘愿葬送一生精力。就是靠子孙相继,没有恒心也难以实现。所以他在《天文农时》的序言第五篇中,反复地强调了“诚”字。他在自己的书斋前,亲手栽下一棵特殊的小树,以象征比拟自己的事业。这棵树俗名刺松,特点是生长极慢,但不弯不曲,不论墙遮屋挡,风吹雨打,总是笔直地向着天空伸展。象一个不急不躁,不屈不挠,坚韧不拔的英雄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栾来宗赋诗日:“南山移奇株,北国定新居,人厌性偏迟,独爱志不屈。嘱我后世人,相伴续天书,参透其中妙,教民稼五谷。四迭甲子过,阳侯祝融出,天时共地利,自见千钟粟”。现在,这棵百岁小树,已碗口粗细,高三丈余,虽处在残垣败壁、荒草瓦砾之中,依然铮骨铁躯,直刺苍穹。顶端衬着小小树冠,很象一支即将离弦的箭,去刺探宇宙的奥秘。
着子孙继承他的事业,第一步就走不通了。他生有三女一子,旧社会女孩子捞不着读书,不能够传给她们,自然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天偏不作美,儿子栾佃照一年年长大,不愿老守田园,看上经商这一行当。栾来宗几度规劝,终不能使之就范,最后被儿子质问得无言以对:“亏尔满腹经伦,一辈子少吃缺穿,眼看爷爷留下的家当要折腾净了,自己受熬煎不算,莫非叫俺们晚辈要着吃?”也确象儿子所说,栾来宗一生埋头于“天文农时”,并没有用在实处,过的日子是入不敷出,致使家底日薄,幸亏儿子能干,14岁当家支撑门面,以此要儿子也搞“天文农时”的事,被顶得理穷词屈,只好一声长叹!
1926年3月,他的孙子出世了。这孩子一颗大脑袋,两个眼珠子溜溜转。性格殊异,直到6个月,家人很少见他的笑脸。有时两眼盯上什么,任凭旁人怎么逗惹,也不理睬。栾来宗对这孩子爱如掌珠,每日里比孩子的妈妈抱的时候还要多。一家人只觉得爷爷拿着小孙孙比自己的命还急,又哪里知道,他已经把事业的希望全寄托在这第三代人身上了。他开始为这隔代人做“铺路”工作:用白纸糊了书房的天棚和四壁,天棚上画了星图,作了详尽的标记;四壁则画了祖国和世界地图。特别对当时的十八行省,编成歌谣,在孙孙咿呀学语的时候,便当做儿歌教唱。
1927年,栾来宗一场大病,卧床不起,百般调理,病情还是一天天加重,自知去日无多,于是盘算起如何把“事业”传给孙子的事来。孙孙栾巨庆尚不懂事,儿子佃照对此事向来持反对态度,只因礼教约束,表面上不过问、不干涉,实则他认为这是毫无意义的蠢事。栾来宗知道,若自己一旦下世,这“事业”肯定被他抛弃理葬,决不会叫后人干下去。要孙子能真正懂事,起码得十几年,那这十多年的岁月又如何处理?他苦思冥想,决定选择贤人相托。他把那些曾跟自己的读书的学生,在脑海里逐一进行了筛选,终于认定了一个可委托者——栾德修。
栾德修并没跟他念书,只是常随其族兄栾自修到栾来宗这里坐坐,听他谈论经书,天长日久,也算有了师生之谊。栾来宗发现他有与众不同的性格:沉默寡言,喜怒不形于色,处事老成持重;口无废语,语出必行,行必有成,以此对他十分器重。现在已是个塾师。栾来宗把他叫到床前,支开伺侯的家人,眼含热泪,向“弟子”倾吐衷肠:
“我少读圣贤之书,立志效法先哲,为世人做点好事,但岁月易逝,时不我待,今行将入木,余事未了——死不足惜,唯心中难平:举办的‘仁义周济会’,虽众乡里赞同,但反对者仍大有人在,若无牵头之人,恐难持久,此事唯‘无愧我心’而已。我所死不瞑目的并不是‘架子会’,而是……”说着他指了指顶棚上的星图和四壁的地图,述说了这些东西的来历后言道:“我已责令佃照,必将这顶棚和墙上的图保留二十年”。说到这里,他强撑起身子,拉开床前抽屉,拿出了手抄本《天文农时》及附书,以震颤的声音继续说了下去:
“这是我四十年的心血,上面记录了历年的星象、天气和适合种植的农作物。这只是个开端,完成它便是我到这世界年来的夙愿。这不是件容易事,得靠好几代人无偿地付出代价,才能有希望完成。
“奇旱大涝,有根有源,并非不可知之事。我经四十年探知,天气异变,乃是日、月、行星的布局而决定的。”栾德修听着,象啃木梨般茫然,不知如何回答。栾来宗继续说:“你不必忧惑,我不打算让你把这些事全弄明白,因为你没有必要无端地耗费精力,这是一项看不见因、摸不着果的事,我只能让我的子孙后代去干。此事我从不向人们讲,也不会有人相信。以五星测天与圣人论背道而驰(孔子以恒星),诬圣人言罪当死,故不能向人透露。”说到这里,栾来宗语气益加庄重:“今召你来,只一事相托,望念师生之谊答应我,烦你把此书保存,待浅亨(其孙栾巨庆的乳名)懂事,再转交给他,并告诉他我已呕心沥血大半生,为之开了个头,要他在这无形的长城上筑起一段,再传下去,直到……”
他几乎是字字泪,句句血,向着弟子述说了半天。栾德修被他那诚恳的态度和信任心情所感动,已决心完成业师所托。
栾来宗稍稍休息一会,又一次挣扎着坐着,握了栾德修的手:“向闻,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遗憾的就是不能亲传小孙,这百年大事,只能靠你了!”说罢,泪如雨下。栾德修见老师一再嘱托,知道这个老人为此事仍忧心忡忡,不禁双膝跪于床前,挥泪发誓:“师父放心,弟子决不会使你失望——你安心疗养身子吧,待痊愈之日,我再来领取教诲。”
“不,我不行了”栾来宗道,“现在你就把书拿去,珍藏起来,待十年之后,再让它出世。”说着从床头柜里抽出一个包袱,慢慢地把书包了起来,双手捧着递了过去。栾德修象接婴儿般的小心,含泪接了过来。此时此刻,师徒两颗心已经融在一起了。栾来宗仍余言未尽,那炽热期待的目光瞅着徒弟,好一会又开口说:“天已不早,你该走了。浅亨方满周岁,难度未来。我已经告诉佃照待懂事,就送他去你的塾中。你要看着他长大,教他成材。但愿苍天保佑,使他能象庭前那棵树一样正直坚强。如不成器,可留书以另待后来人!你回去吧!”说着挥了挥手,躺在床上闭目不再言语,他实在已精疲力竭。
不久,他带着“死而未已”的心,离开人世伴星月去了。
后记
民国28年(1939年)农历九月十四日,夜阑人静,华疃二村一幢曾是私塾的书房里,又是一师一徒在接续12年前的故事。师傅是栾德修,徒弟便是栾来宗的孙子栾巨庆。老人语重心长地向着未满十四岁的孩子叙述了他爷爷的往事。栾巨床听罢心潮起伏,久久难平,不知说什么才好,最后从他口中斩钉截铁般地吐出了几个字:“我知道了!”说罢擦了擦眼泪,从业师手中接过了《天文农时》。
他做为一个接力者踏上征途,不过,他没有按照爷爷指引的路走,因为那太慢了,他觉得一生只做个记录者,只为无形长城加几块“砖石”太少了。也许是历史不断的原因,他比爷爷更聪明,他悟出了一个道理:何必要等上240年?既然月亮、行星都有一定的运行规律,向前推算不是一样吗?向上算出它们各个时期的方位,对照历史的天气,以验证二者关系,岂不是一条捷径!他的路走对了。
一年、两年、十几年、几十年,他为了探索、验证,自食其力走过大江南北、塞外中原,当过搬运工、推车夫、伐木人;为向专家求教,他闯过13个大专院校。十年动乱时期,他被打成“专政对象”,被投进过监狱,用血汗凝成的数据、资料被七次没收,连爷爷的遗书统统被付之一炬。这曾一度使人痛不欲生,可一旦想到“诚”字,更使他咬紧牙关,迎着险阻,攀登、向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在内蒙古林业局、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等单位支持下,以他为首成立了天文气象研究小组,他们搜集和整理了1000多年的天文、气象史料。历史事实证明了栾来宗当年对“天气有59年小周期和237年大周期”的论断是正确的。更可喜者,栾巨床从中找出了行星方位影响地球的“对应区”,他于1983年写出了世界上第一部以天文预报天气的学术专著——《行星与长期天气预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人民日报》、《文汇报》、《工人日报》、《科技日报》等先后报道了他的事迹。
“对应区”的发现,随之揭开了一连串的不解之谜:“地震、太阳黑子竟也是与行星方位有关”。对此,《中国科技报》(今《科技日报》)一一做了报道。1987年8月2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特登载了“栾巨庆以行星研究太阳活动”的消息。1988年4月,一部40万字的论著——《星体与长期天气地震预报》出版了。该书参加了1988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图书展销会。
栾来宗的首创,栾巨庆的继往开来,不敢说已完善无缺,而只能仍算是开端。想来,广大气象工作者有必要以此作为参考,进一步探索,攻克长期天气预报这一堡垒,用之农事,用之于社会主义建设。届时,栾来宗九泉有知,当为这造福于亿万人类的功业,提前告成而含笑地下。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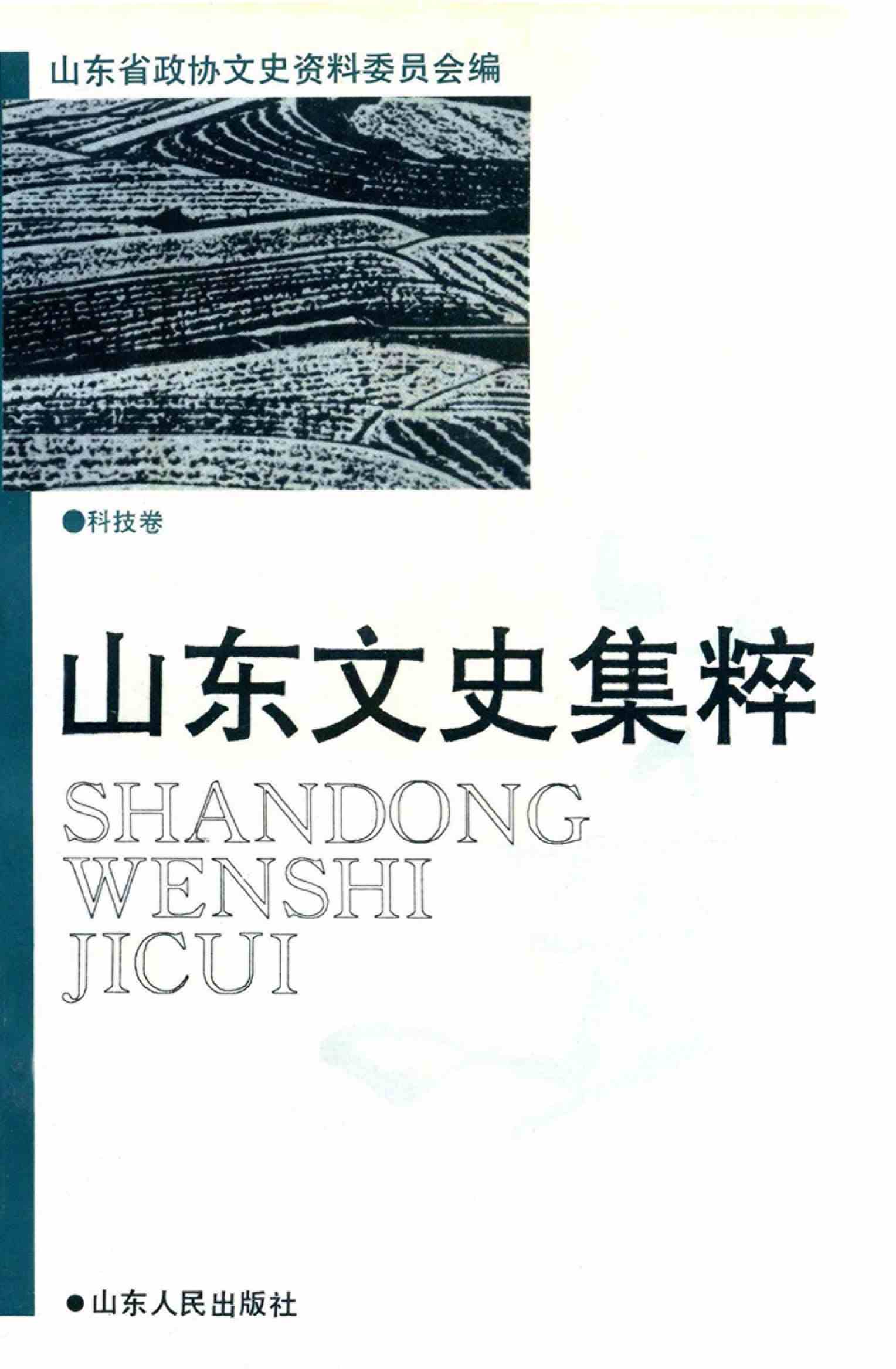
《山东文史集粹·科技卷》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本书收录了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丁肇中、著名科学家郭永怀烈士、杰出物理学家王淦昌、我国早期原子能物理专家王普博士、忆束星北教授、著名力学专家刘先志、著名航空工程专家丁履德、电子计算机专家王正、“西圣”孙学悟等多篇文章。
阅读
相关人物
陶波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