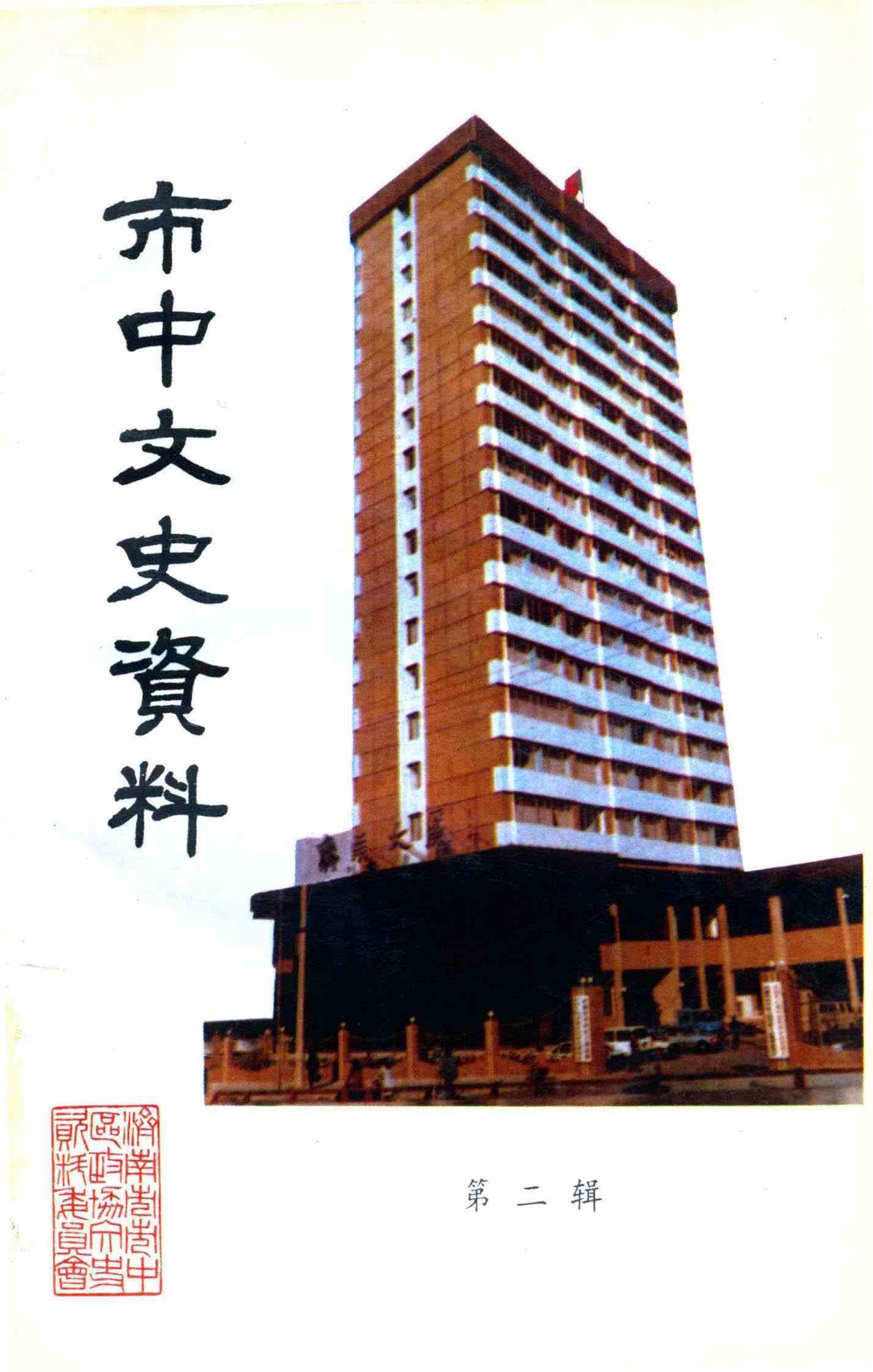内容
我演唱山东快书已经60多年了,被称作“杨派”,总算有了一些影响。10余年来,不断接到一些热心听众和快书圈内朋友们来信,询问我的家世和学世情况,对于快书艺术的演唱体会与见解,以及对快书未来的展望等等。在这里我对过去做些回顾思考,算是回答。
一、我的家世和艺术根基
我原籍山东省利津县城里杨家胡同。因为穷,祖父杨吉业带全家来到济南。开始在黄河渡口卖粥,日子过得十分艰难。那时父亲杨凤山和我叔杨凤岐,都才十几岁,先是跟“拉洋片”的帮忙,在赶集赶会的时候,结识了唱“武老二”的名家卢同武。卢非常喜欢我父亲,我父亲向他提出拜师学艺,他不许,而是代师收徒作为师弟,但演唱技艺由他亲自传授,并同样收了俺叔。从此奠定了我们这个快书世家的根基。1957年7月,在山东省曲目工作会上,听老前辈杨教常,以及周同宾、傅永昌、宋宗科一起谈论快书的历史,才知道我父辈的师爷爷就是“武老二”创始人傅汉章,叔师祖就是号称“三钧不敌”的老赵震,他的师父是魏玉河,绰号魏傻子,唱起来一股劲儿,专爱唱大回头。父亲的师兄弟还有卢同文、杜永春两人。山东快书历史不算长,我父亲、叔父才是第三代传人。
我父亲个头不高,人称“杨大辫子”。说“武老二”时,斜披大皮袄,大辫子往脖颈上一盘,唱起来口正脆火,赶劲解气,动作洒利,一个飞脚能踢到鼻子尖,钢板的嘟噜,能打几分钟,满彩!那时济南趵突泉、国货商场的书场茶社,已不像以前那么红火,随着商埠的开辟,南岗子(新市场)成了说书的重点活动场所。我父亲特别是叔叔又与崔金林结拜,学了相声、魔术,就在南门里撂地。后来置了大棚,成了当时驰名济南书坛的“荀、杨、黄”三大将之一。荀是荀春盛,唱京口落子;黄是黄春元(绰号黄六牙)唱木板大鼓;杨就是我父杨凤山。三大将名震济南,各有绝活。我婶子和父亲一个姓张的徒弟(铁路搬运工)都说过:“你父亲买卖真红火,一场书说下来,面袋子装铜子儿自己扛不动,雇人往家扛。”
还听我叔叔、婶子说,当我父亲在新市场干得正响时,从徐州来了个唱“武老二”的姓戚的,他听了我父亲两天书,没在济南摆场。我父亲去店里拜望过他,还领到家里来过。后来听傅永昌说:“那就是戚永立,当时在徐州正红。听说济南红了杨凤山,想来对买卖。看了两场,你老头儿又去店里看他,二人谈得投机,南北两员大将成了朋友。”
当时商埠刚开,岗子南边还是个杀人场。杀人就得从岗子南门路过。这天父亲正在说书,杀人的路过,观众都去看热闹。场子被搅了,父亲也挤到路边去看,谁想要斩的犯人听过我父亲的书,正摇摇晃晃地唱着二黄往前走,一眼看到我父亲,就大声喳呼:“杨大辫子,下辈子再听你的‘武老二’了!”一句话祸从天降,官员误认为我父亲是他的同伙,绑上带走了。书词公会赶紧出面去保,可万恶的军阀能错抓却不轻放,押他陪决后才释放回家,回家后一连病了半个月就去世了。
父亲死后三个月我才降生到这个世界上。不久生母带我被人拐跑,后经叔叔、婶子打官司,才把我这棵独根苗争回来。四五岁我就跟着叔叔上地,学了相声《训徒》、《大上寿》等小段。快书也是叔叔手把手教的,学了《大闹马家店》、《石家庄》等和一些小段儿。那年我才5岁,学不会就被一脚踹老远。年小学活不多,却是实授。那年冬,我叔叔又病故了,我一个6岁的孩子,过早地挑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我上地抡个早,婶子给我敛钱,靠着长辈的人缘,谁都可怜我小,挣的钱倒还可以糊口。这期间,父亲姓张的徒弟,不断照顾我,教全了我《石家庄》和《十字坡》。生活逼迫我非得认真学艺不可,不然就没有饭吃。所以自小用心,不只是摹仿,主要是用脑子。我生性腼腆,干这个本不够料儿,简直是逼出来的。
作为我生活中又一转折,是12岁那年被高福来骗到了乡下。开始为他当兄弟,后来又说是他徒弟,最后变成了他的奴隶。张口就骂,抬手就打,百般虐待。我跟他走遍了平阴、东阿、高唐、恩县、夏津、武城、在平、博平等地,替他挣了不少钱,他和姘头吃香的喝辣的,打了我还不给饭吃,老百姓实在看不过去,要揍他,吓得他连夜推车跑了。我只好一个人流浪,想挣钱回济南,曾跟辛三和学做擦床工;又跟杨会文卖过明药,在曲阜圣人门前干得挺红火,挣钱也不少,可又被他连行李也拐跑了。我气得病倒在曲阜,好心的房东大娘在小屋里给我搭了个铺,每天给口吃的,这样我总算活过来了。20天后病刚好,我就下地帮她收秋。后来,我到过泗水、兖州、邹县、滕县、徐州等地说书。转到1939年夏天,才回到济南。
回济南后,先在吴平江地上与他“合穴”,后来自己又到西市场、劝业场干过。在乡下的那一段,高福来人品虽坏,但在艺术上给我不少熏陶。特别是撂地摔打,唱不住人不行,这是一段难得的锻炼啊!尤其是得以深入地接触农村生活,接触质朴憨厚的山东农民,也接触了各类江湖先人,使我懂得了什么叫说书,如何才能说好书,这是我以后进行艺术创造的基础。这叫受几年苦终生受用。在济南,我与高元钧兄相识,格外投缘。还一块到章丘去说过相声。当时小报上就登过“高大鼻子和杨小麻子合说相声”的消息。那时我们到一块就探讨艺术,讨论过适应城市听众需要改说“清口”的问题。
杨家的快书(当然包括我)虽然渊源于卢同武,但应当说我的老师很多。我还得到过于传宾的传授,邱永春的指点,高福来的影响尤其不容忽视。此外,吴平江、周同宾、傅永昌、高元钧诸好友,都曾给我许多帮助,相互切磋过技艺。还有济南方言相声界的前辈崔金林和吴景春等,也都给过指点和熏陶。
这一切都是我的艺术根基。古人说“汇百川而为沧海”,我虽然不过是沧海中的一个小水珠,但道理却是一个。集众家之长,能根据个人具体条件加以创造,在实践中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
二、艺术上的发展与追求
我开始学唱“武老二”,因手小拿不住钢板,就敲着玉子击点演唱。那时不打过门,一股劲地赶着唱。年龄小讨人喜欢,勉强敛几个钱。我还有个姐姐叫杨大妮,她和叔叔都是打着竹板钢板演唱,点法很简单,一连串的“当滴各当滴”打着唱,别看简单,这是我们初学的基础。
被高福来骗到乡下以后,为了招来观众跟他学打四页板,赶集赶会一直这么干,倒挺火爆。重回济南后,感到在城市竹板打得太响不大文明,第二年到西市场演出,我就改成常用的钢板加大竹板了,可打的点儿还是四页板的。在大城市演出跟在乡里田间地头、集市会场确实不同,观众情况复杂,而且文化层次高得多。有一次,一个老太太指着鼻子说我:“小孩儿唱得不孬,就是不说人话!”这对我刺激太大了,咱一个大活人怎么不说人话呢?再使“荤口”就觉着不是味儿,矮人一等。1940年到劝业场说书时我就改了“清口”。结果收入增加了,因为陆续增加了女观众。看来说书非得适应听众,适应环境不可。从这种意义上讲,是听众创造了“武老二”,也创造了它的“清口”。
当时我唱“武老二”,身穿干净的派立司大褂(或纺绸小褂),青绸灯笼裤,脚下礼服呢便鞋,讲究个排场、率气。在乡下唱“武老二”,光一只膀,像高福来那样一场下来,拍得胸膛发紫,我进济南在吴平江地上唱时就改了。这也是适应观众,属于演出形式方面的改进。
作为一个演员我自知,个人天赋条件不算好,可我出身于快书世家,爱这一行几乎到了生死难分的程度,条件再差我也得干出个样儿来。当然我也有有利的一面:自小见得多,练就的基本功非常扎实,可怎么能让听众喜爱呢?我遭难时乡亲们对我的真诚爱护给了我很大启发,那就是爱观众,以心换心,带着最饱满的热情说给他们听。那怕是唱《贴报单》、《一窝刘》之类耍嘴皮的节目,也要对观众有真情,自然会使人感到亲切。说书必须动情,前辈们常说:“唱动人心才是书。”演员想要唱动听众的心,必须自己先有情,有恰当地表现人物的情感。整个说书过程都应该是演员情感的运动,基本功再好,也不能单纯耍弄技巧。否则,他就成不了艺术家,到头来不过是个说书匠。
参加工作之后,接触文艺界人士多了,特别是两次赴朝鲜慰问志愿军,与许多知名艺术家共同生活,同台演出,所受启发教育十分深刻。认识到一个艺术家,在自己的艺术创造与艺术境界上必须有所追求,不能糊里糊涂说一辈子糊涂书。多少年来我经常想:自己的艺术追求是什么呢?总结演出经验,结合反复实践,我初步归纳出“风格纯朴,表演自然,语言流畅,内涵厚实”16个字。这16个字做到确实不易,但是我的努力方向就是我艺术追求的目标。
说书靠一个“情”字贯穿,不故意卖弄技巧。例如打起板来不见掌声决不停止,甚至以摇头晃屁股,冲观众龇牙裂嘴种种丑态哗众取宠,这怎么行?一切从书中故事发展需要出发,从书中人物性格出发,老老实实地给观众讲故事;同时顺情入理地去表演,不搞外插花的邪门歪道,不以炫耀自己的技术长处为目的,演出风格自然朴实,不能像高福来那样唱着唱着就拿倒立,围着场子走,逼着观众喝采;再不就借武打场面故意卖弄拳脚架式,忘了自己是在说书,这是表演中的不自然。表演自然不是要技巧,因为艺术讲究美,是对生活的加工提炼。看来道理简单,厚厚的一层窗户纸却不容易戳破。如唱《鲁达除霸》金大姐诉苦一段,用个情绪悲切的姑娘声音就可以了,用不着几次大抽泣,更不能耍包袱儿,否则破坏了整体节奏就是自己下绊子。卢同武老先生唱《飞云浦》,表示在桥上滚翻厮打,既有抡背又打飞脚,技巧很高,用得恰当。因为符合故事和人物需要,表演也就自然。有人说我动作小,我不以为然。我觉得动作不在大小,而在用得是否恰当。该打飞脚我也照打不误,如唱《十字坡》,武松扔褥套,孙二娘来接,翻身打飞脚,正落在板上,伸手唱“抓住褥套挺手脖,连着颤合两颤合”。混然一体,非常协调。
声乐家演唱讲究声情并茂。山东快书有节奏有辙韵,也是语言的夸张与延伸,应当以情带声。快慢迟疾,抑扬顿挫,整个节奏和语气声调的处理都得靠这个“情”字。我的贯口其实并不快,是入情入理地讲故事给观众听,而不是表现自己嘴皮子多么灵巧,赶快夺字多么熟练,一口气能唱多少句,一段《贴报单》能要多少掌声。有人说:“杨立德有啥,不就是唱得甜美!”其实这个“甜”字来之不易呀!得时刻不忘自己说书是给观众听的。要始终有情,还得敢于突破一股劲追求“泼”的习惯唱法,观众听着甜才会感到美。让听众有美感是说书人的根本追求。所以我要从情节内容和人物出发,该粗就粗,该细就细,该快则快,该慢则慢。力求流畅绝不故意停顿,或是一惊一乍,去制造一些人为的效果。
任何成熟的艺术都有一定的表现程式,山东快书当然也不例外。但它远不如京剧那么固定、成熟。程式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在艺术实践中固定下来的,某些演出习惯不能看作是程式。同时,程式虽说固定,但又不能一成不变。必须顺应时代需要,不断丰富创造。用唱武松的一套来唱《抓俘虏》是不行的。艺术造诣再高也得在前进中不断变化。停滞不前是会葬送这门艺术的,广采博收才能不断发展自己的艺术。传统快书表现规律与手法要认真掌握,不然就会扔掉快书的特点,但不能走向程式化。如何表现要随内容和人物的变化而变化。
说快书必须以说唱为主,首先得唱得解气。我在乡下演唱,演晚场常常没有灯,表演哪能看得见?但照样坐一场院人。这时我才领悟到他们听书主要是听故事这个道理。怎么办?首先得保证口齿清楚,要像山东大鼓那样字清句浊,不能吐词不清,“钝刀子割肉”。演唱节奏要紧凑,打板粘糊,尽量减少中间空隙。最重要的还是声音化装,说快书要装谁像谁,哼、啊、哎、噢之类语气词要随时填充。我的快书语句简练,不拖泥带水,唱起来力求流畅动听,主要就是这么来的。
但是,演出毕竟是白天或在灯下的时候多,因此光唱好还不行,还得加上表演。位置摆得很清楚,快书表演是辅助性的,起个锦上添花的作用,动作不宜过多、过于琐碎,更不应喧宾夺主,要“点到为止。”说书主要靠与观众交流,靠调动他们的想象进入故事,点不到起不了调动想象力的作用,点过了令人生厌,会起相反的作用,说书讲究的是精、气、神,只要抓住要表演的人物的神态神气,一闪就成,动作做多了影响观众想象,想要表现得厚实些,反而浅薄了。一个故事、一个人物里面都藏着许多值得回味思考的东西,咱引个头儿,让观众去想他才觉得有意思。这样说书人才能与观众水乳交融。要相信观众比咱聪明。
“包袱”的使用也一样,我起先学的相声,深知它的重要。不过相声靠的就是“包袱儿”;说快书当然也需要它,但主要的却是故事。然而不能一味追求包袱儿,说什么越炸越火越好。我觉着啥时候也不应忘记自己是一个说书的,书里的“内里噱”一定要使好,只要不冷场就行,没有必要硬找一些外插花的笑料儿。笑声不断看似效果好,实际上影响观众思考。只要有几个“包袱儿”,场子里静,观众听完有点回味的东西,演出就很成功。
三、衷心愿望——团结、前进
山东快书自清光绪十九年(1893),傅汉章首演于曲阜林门会,才150年。这期间,虽然出现过赵震、吴洪钧、李合钧、卢同武、卢同文、马玉恒、邱永春、戚永立、杨凤山等著名艺人,但由于主要在农村演出,虽然艺术上各有特点,还没有分过什么流派。随着进入城市,走上舞台,以及表演水平的提高,演出队伍的扩大,尤其是艺术风格差异日见明显。高元钧首先亮出“高派”旗帜,1981年在青岛召开了“高派山东快书演唱会”,较深入地总结了他的艺术经验和特点。当然这是件大好事。相比较而存在吧,一些观众就把我的快书称作“杨派”。1989年济南市文化局又为我举行了从艺60周年的纪念活动,还总结了“杨派”山东快书的经验和特点。我除了感谢党和政府,以及文艺界的朋友之外,感到是一个非常有力的鞭策,因为我从来都认为艺无止境,自己的水平、贡献还差得远,没想过能称起什么派,这一庆祝纪念,反倒使我更感到肩头上的担子重了。会上高元钧兄说我们是一派,我认为有道理。如果从演出场所讲,我们是进入城市走向舞台的一派。当时张军同志写文章提到山东广大农村,还活跃着于传宾(于小辫儿)所创造的竹板快书“于派”,但一直被某些研究者所忽视。
不论哪一派,既然被看成山东快书的一个流派,就必须认真总结。我清楚自己这一派的特点和不足,应该努力去发展提高。还必须清楚认识到仅是一派昌盛还不够,应该站在全省、全国的高度,从山东快书整体出发,加强理论研究,艺术交流,发扬各自的优点而又同时得到发展提高。以求得整个山东快书的发展提高,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作者杨立德,中国曲协会员,山东省文联委员,山东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1990年离休。1994年病逝)
一、我的家世和艺术根基
我原籍山东省利津县城里杨家胡同。因为穷,祖父杨吉业带全家来到济南。开始在黄河渡口卖粥,日子过得十分艰难。那时父亲杨凤山和我叔杨凤岐,都才十几岁,先是跟“拉洋片”的帮忙,在赶集赶会的时候,结识了唱“武老二”的名家卢同武。卢非常喜欢我父亲,我父亲向他提出拜师学艺,他不许,而是代师收徒作为师弟,但演唱技艺由他亲自传授,并同样收了俺叔。从此奠定了我们这个快书世家的根基。1957年7月,在山东省曲目工作会上,听老前辈杨教常,以及周同宾、傅永昌、宋宗科一起谈论快书的历史,才知道我父辈的师爷爷就是“武老二”创始人傅汉章,叔师祖就是号称“三钧不敌”的老赵震,他的师父是魏玉河,绰号魏傻子,唱起来一股劲儿,专爱唱大回头。父亲的师兄弟还有卢同文、杜永春两人。山东快书历史不算长,我父亲、叔父才是第三代传人。
我父亲个头不高,人称“杨大辫子”。说“武老二”时,斜披大皮袄,大辫子往脖颈上一盘,唱起来口正脆火,赶劲解气,动作洒利,一个飞脚能踢到鼻子尖,钢板的嘟噜,能打几分钟,满彩!那时济南趵突泉、国货商场的书场茶社,已不像以前那么红火,随着商埠的开辟,南岗子(新市场)成了说书的重点活动场所。我父亲特别是叔叔又与崔金林结拜,学了相声、魔术,就在南门里撂地。后来置了大棚,成了当时驰名济南书坛的“荀、杨、黄”三大将之一。荀是荀春盛,唱京口落子;黄是黄春元(绰号黄六牙)唱木板大鼓;杨就是我父杨凤山。三大将名震济南,各有绝活。我婶子和父亲一个姓张的徒弟(铁路搬运工)都说过:“你父亲买卖真红火,一场书说下来,面袋子装铜子儿自己扛不动,雇人往家扛。”
还听我叔叔、婶子说,当我父亲在新市场干得正响时,从徐州来了个唱“武老二”的姓戚的,他听了我父亲两天书,没在济南摆场。我父亲去店里拜望过他,还领到家里来过。后来听傅永昌说:“那就是戚永立,当时在徐州正红。听说济南红了杨凤山,想来对买卖。看了两场,你老头儿又去店里看他,二人谈得投机,南北两员大将成了朋友。”
当时商埠刚开,岗子南边还是个杀人场。杀人就得从岗子南门路过。这天父亲正在说书,杀人的路过,观众都去看热闹。场子被搅了,父亲也挤到路边去看,谁想要斩的犯人听过我父亲的书,正摇摇晃晃地唱着二黄往前走,一眼看到我父亲,就大声喳呼:“杨大辫子,下辈子再听你的‘武老二’了!”一句话祸从天降,官员误认为我父亲是他的同伙,绑上带走了。书词公会赶紧出面去保,可万恶的军阀能错抓却不轻放,押他陪决后才释放回家,回家后一连病了半个月就去世了。
父亲死后三个月我才降生到这个世界上。不久生母带我被人拐跑,后经叔叔、婶子打官司,才把我这棵独根苗争回来。四五岁我就跟着叔叔上地,学了相声《训徒》、《大上寿》等小段。快书也是叔叔手把手教的,学了《大闹马家店》、《石家庄》等和一些小段儿。那年我才5岁,学不会就被一脚踹老远。年小学活不多,却是实授。那年冬,我叔叔又病故了,我一个6岁的孩子,过早地挑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我上地抡个早,婶子给我敛钱,靠着长辈的人缘,谁都可怜我小,挣的钱倒还可以糊口。这期间,父亲姓张的徒弟,不断照顾我,教全了我《石家庄》和《十字坡》。生活逼迫我非得认真学艺不可,不然就没有饭吃。所以自小用心,不只是摹仿,主要是用脑子。我生性腼腆,干这个本不够料儿,简直是逼出来的。
作为我生活中又一转折,是12岁那年被高福来骗到了乡下。开始为他当兄弟,后来又说是他徒弟,最后变成了他的奴隶。张口就骂,抬手就打,百般虐待。我跟他走遍了平阴、东阿、高唐、恩县、夏津、武城、在平、博平等地,替他挣了不少钱,他和姘头吃香的喝辣的,打了我还不给饭吃,老百姓实在看不过去,要揍他,吓得他连夜推车跑了。我只好一个人流浪,想挣钱回济南,曾跟辛三和学做擦床工;又跟杨会文卖过明药,在曲阜圣人门前干得挺红火,挣钱也不少,可又被他连行李也拐跑了。我气得病倒在曲阜,好心的房东大娘在小屋里给我搭了个铺,每天给口吃的,这样我总算活过来了。20天后病刚好,我就下地帮她收秋。后来,我到过泗水、兖州、邹县、滕县、徐州等地说书。转到1939年夏天,才回到济南。
回济南后,先在吴平江地上与他“合穴”,后来自己又到西市场、劝业场干过。在乡下的那一段,高福来人品虽坏,但在艺术上给我不少熏陶。特别是撂地摔打,唱不住人不行,这是一段难得的锻炼啊!尤其是得以深入地接触农村生活,接触质朴憨厚的山东农民,也接触了各类江湖先人,使我懂得了什么叫说书,如何才能说好书,这是我以后进行艺术创造的基础。这叫受几年苦终生受用。在济南,我与高元钧兄相识,格外投缘。还一块到章丘去说过相声。当时小报上就登过“高大鼻子和杨小麻子合说相声”的消息。那时我们到一块就探讨艺术,讨论过适应城市听众需要改说“清口”的问题。
杨家的快书(当然包括我)虽然渊源于卢同武,但应当说我的老师很多。我还得到过于传宾的传授,邱永春的指点,高福来的影响尤其不容忽视。此外,吴平江、周同宾、傅永昌、高元钧诸好友,都曾给我许多帮助,相互切磋过技艺。还有济南方言相声界的前辈崔金林和吴景春等,也都给过指点和熏陶。
这一切都是我的艺术根基。古人说“汇百川而为沧海”,我虽然不过是沧海中的一个小水珠,但道理却是一个。集众家之长,能根据个人具体条件加以创造,在实践中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
二、艺术上的发展与追求
我开始学唱“武老二”,因手小拿不住钢板,就敲着玉子击点演唱。那时不打过门,一股劲地赶着唱。年龄小讨人喜欢,勉强敛几个钱。我还有个姐姐叫杨大妮,她和叔叔都是打着竹板钢板演唱,点法很简单,一连串的“当滴各当滴”打着唱,别看简单,这是我们初学的基础。
被高福来骗到乡下以后,为了招来观众跟他学打四页板,赶集赶会一直这么干,倒挺火爆。重回济南后,感到在城市竹板打得太响不大文明,第二年到西市场演出,我就改成常用的钢板加大竹板了,可打的点儿还是四页板的。在大城市演出跟在乡里田间地头、集市会场确实不同,观众情况复杂,而且文化层次高得多。有一次,一个老太太指着鼻子说我:“小孩儿唱得不孬,就是不说人话!”这对我刺激太大了,咱一个大活人怎么不说人话呢?再使“荤口”就觉着不是味儿,矮人一等。1940年到劝业场说书时我就改了“清口”。结果收入增加了,因为陆续增加了女观众。看来说书非得适应听众,适应环境不可。从这种意义上讲,是听众创造了“武老二”,也创造了它的“清口”。
当时我唱“武老二”,身穿干净的派立司大褂(或纺绸小褂),青绸灯笼裤,脚下礼服呢便鞋,讲究个排场、率气。在乡下唱“武老二”,光一只膀,像高福来那样一场下来,拍得胸膛发紫,我进济南在吴平江地上唱时就改了。这也是适应观众,属于演出形式方面的改进。
作为一个演员我自知,个人天赋条件不算好,可我出身于快书世家,爱这一行几乎到了生死难分的程度,条件再差我也得干出个样儿来。当然我也有有利的一面:自小见得多,练就的基本功非常扎实,可怎么能让听众喜爱呢?我遭难时乡亲们对我的真诚爱护给了我很大启发,那就是爱观众,以心换心,带着最饱满的热情说给他们听。那怕是唱《贴报单》、《一窝刘》之类耍嘴皮的节目,也要对观众有真情,自然会使人感到亲切。说书必须动情,前辈们常说:“唱动人心才是书。”演员想要唱动听众的心,必须自己先有情,有恰当地表现人物的情感。整个说书过程都应该是演员情感的运动,基本功再好,也不能单纯耍弄技巧。否则,他就成不了艺术家,到头来不过是个说书匠。
参加工作之后,接触文艺界人士多了,特别是两次赴朝鲜慰问志愿军,与许多知名艺术家共同生活,同台演出,所受启发教育十分深刻。认识到一个艺术家,在自己的艺术创造与艺术境界上必须有所追求,不能糊里糊涂说一辈子糊涂书。多少年来我经常想:自己的艺术追求是什么呢?总结演出经验,结合反复实践,我初步归纳出“风格纯朴,表演自然,语言流畅,内涵厚实”16个字。这16个字做到确实不易,但是我的努力方向就是我艺术追求的目标。
说书靠一个“情”字贯穿,不故意卖弄技巧。例如打起板来不见掌声决不停止,甚至以摇头晃屁股,冲观众龇牙裂嘴种种丑态哗众取宠,这怎么行?一切从书中故事发展需要出发,从书中人物性格出发,老老实实地给观众讲故事;同时顺情入理地去表演,不搞外插花的邪门歪道,不以炫耀自己的技术长处为目的,演出风格自然朴实,不能像高福来那样唱着唱着就拿倒立,围着场子走,逼着观众喝采;再不就借武打场面故意卖弄拳脚架式,忘了自己是在说书,这是表演中的不自然。表演自然不是要技巧,因为艺术讲究美,是对生活的加工提炼。看来道理简单,厚厚的一层窗户纸却不容易戳破。如唱《鲁达除霸》金大姐诉苦一段,用个情绪悲切的姑娘声音就可以了,用不着几次大抽泣,更不能耍包袱儿,否则破坏了整体节奏就是自己下绊子。卢同武老先生唱《飞云浦》,表示在桥上滚翻厮打,既有抡背又打飞脚,技巧很高,用得恰当。因为符合故事和人物需要,表演也就自然。有人说我动作小,我不以为然。我觉得动作不在大小,而在用得是否恰当。该打飞脚我也照打不误,如唱《十字坡》,武松扔褥套,孙二娘来接,翻身打飞脚,正落在板上,伸手唱“抓住褥套挺手脖,连着颤合两颤合”。混然一体,非常协调。
声乐家演唱讲究声情并茂。山东快书有节奏有辙韵,也是语言的夸张与延伸,应当以情带声。快慢迟疾,抑扬顿挫,整个节奏和语气声调的处理都得靠这个“情”字。我的贯口其实并不快,是入情入理地讲故事给观众听,而不是表现自己嘴皮子多么灵巧,赶快夺字多么熟练,一口气能唱多少句,一段《贴报单》能要多少掌声。有人说:“杨立德有啥,不就是唱得甜美!”其实这个“甜”字来之不易呀!得时刻不忘自己说书是给观众听的。要始终有情,还得敢于突破一股劲追求“泼”的习惯唱法,观众听着甜才会感到美。让听众有美感是说书人的根本追求。所以我要从情节内容和人物出发,该粗就粗,该细就细,该快则快,该慢则慢。力求流畅绝不故意停顿,或是一惊一乍,去制造一些人为的效果。
任何成熟的艺术都有一定的表现程式,山东快书当然也不例外。但它远不如京剧那么固定、成熟。程式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在艺术实践中固定下来的,某些演出习惯不能看作是程式。同时,程式虽说固定,但又不能一成不变。必须顺应时代需要,不断丰富创造。用唱武松的一套来唱《抓俘虏》是不行的。艺术造诣再高也得在前进中不断变化。停滞不前是会葬送这门艺术的,广采博收才能不断发展自己的艺术。传统快书表现规律与手法要认真掌握,不然就会扔掉快书的特点,但不能走向程式化。如何表现要随内容和人物的变化而变化。
说快书必须以说唱为主,首先得唱得解气。我在乡下演唱,演晚场常常没有灯,表演哪能看得见?但照样坐一场院人。这时我才领悟到他们听书主要是听故事这个道理。怎么办?首先得保证口齿清楚,要像山东大鼓那样字清句浊,不能吐词不清,“钝刀子割肉”。演唱节奏要紧凑,打板粘糊,尽量减少中间空隙。最重要的还是声音化装,说快书要装谁像谁,哼、啊、哎、噢之类语气词要随时填充。我的快书语句简练,不拖泥带水,唱起来力求流畅动听,主要就是这么来的。
但是,演出毕竟是白天或在灯下的时候多,因此光唱好还不行,还得加上表演。位置摆得很清楚,快书表演是辅助性的,起个锦上添花的作用,动作不宜过多、过于琐碎,更不应喧宾夺主,要“点到为止。”说书主要靠与观众交流,靠调动他们的想象进入故事,点不到起不了调动想象力的作用,点过了令人生厌,会起相反的作用,说书讲究的是精、气、神,只要抓住要表演的人物的神态神气,一闪就成,动作做多了影响观众想象,想要表现得厚实些,反而浅薄了。一个故事、一个人物里面都藏着许多值得回味思考的东西,咱引个头儿,让观众去想他才觉得有意思。这样说书人才能与观众水乳交融。要相信观众比咱聪明。
“包袱”的使用也一样,我起先学的相声,深知它的重要。不过相声靠的就是“包袱儿”;说快书当然也需要它,但主要的却是故事。然而不能一味追求包袱儿,说什么越炸越火越好。我觉着啥时候也不应忘记自己是一个说书的,书里的“内里噱”一定要使好,只要不冷场就行,没有必要硬找一些外插花的笑料儿。笑声不断看似效果好,实际上影响观众思考。只要有几个“包袱儿”,场子里静,观众听完有点回味的东西,演出就很成功。
三、衷心愿望——团结、前进
山东快书自清光绪十九年(1893),傅汉章首演于曲阜林门会,才150年。这期间,虽然出现过赵震、吴洪钧、李合钧、卢同武、卢同文、马玉恒、邱永春、戚永立、杨凤山等著名艺人,但由于主要在农村演出,虽然艺术上各有特点,还没有分过什么流派。随着进入城市,走上舞台,以及表演水平的提高,演出队伍的扩大,尤其是艺术风格差异日见明显。高元钧首先亮出“高派”旗帜,1981年在青岛召开了“高派山东快书演唱会”,较深入地总结了他的艺术经验和特点。当然这是件大好事。相比较而存在吧,一些观众就把我的快书称作“杨派”。1989年济南市文化局又为我举行了从艺60周年的纪念活动,还总结了“杨派”山东快书的经验和特点。我除了感谢党和政府,以及文艺界的朋友之外,感到是一个非常有力的鞭策,因为我从来都认为艺无止境,自己的水平、贡献还差得远,没想过能称起什么派,这一庆祝纪念,反倒使我更感到肩头上的担子重了。会上高元钧兄说我们是一派,我认为有道理。如果从演出场所讲,我们是进入城市走向舞台的一派。当时张军同志写文章提到山东广大农村,还活跃着于传宾(于小辫儿)所创造的竹板快书“于派”,但一直被某些研究者所忽视。
不论哪一派,既然被看成山东快书的一个流派,就必须认真总结。我清楚自己这一派的特点和不足,应该努力去发展提高。还必须清楚认识到仅是一派昌盛还不够,应该站在全省、全国的高度,从山东快书整体出发,加强理论研究,艺术交流,发扬各自的优点而又同时得到发展提高。以求得整个山东快书的发展提高,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作者杨立德,中国曲协会员,山东省文联委员,山东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1990年离休。1994年病逝)
相关人物
杨立德
责任者
相关地名
杨立德
相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