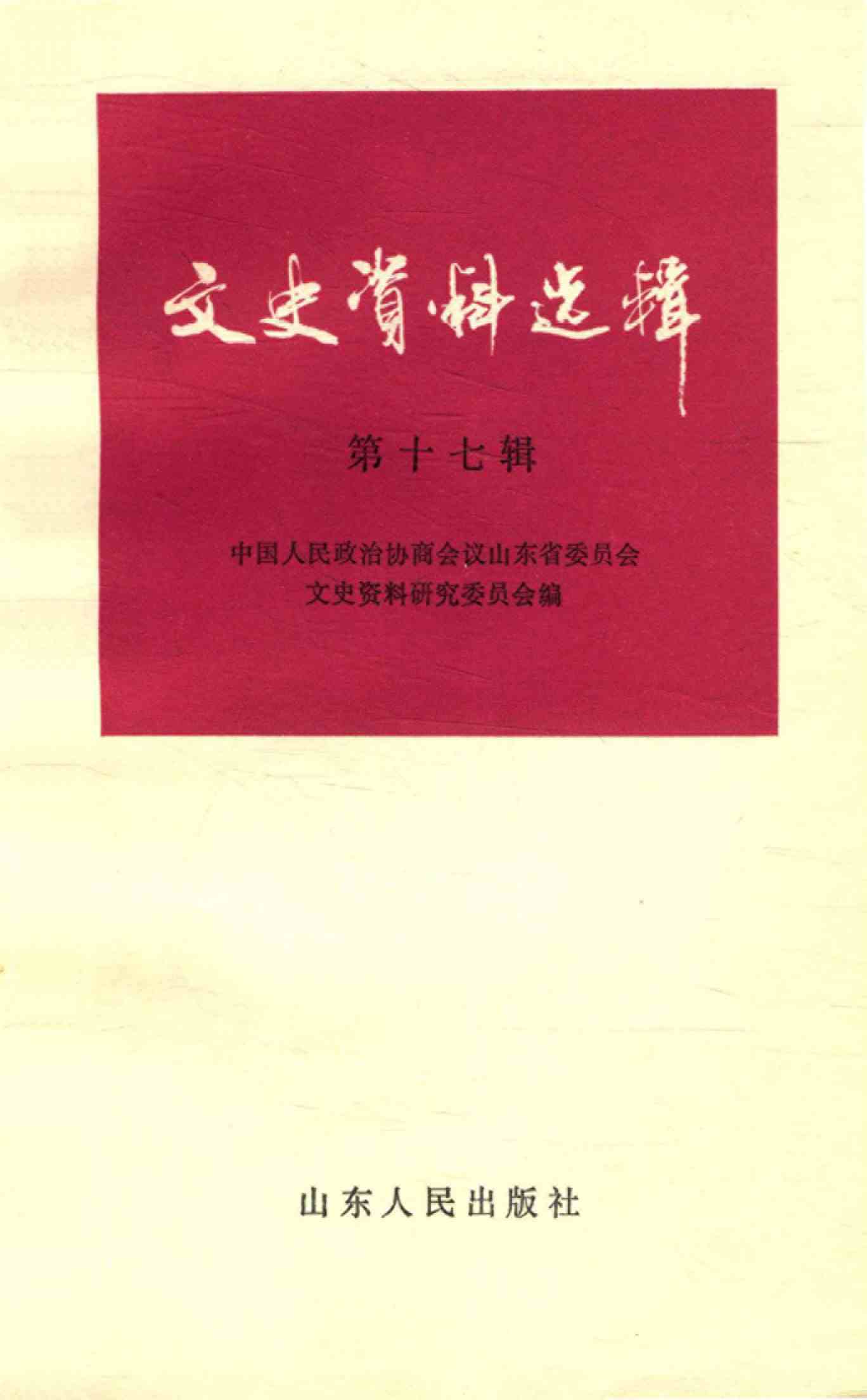内容
我今年六十八岁,是烟台塑料三厂的工人。担任烟台市政协委员,山东省天主教爱国会常委。
我老家是泰安城西南安驾庄。母亲因为手残,和家中只有七分地的父亲结了婚,婚后因生活没法维持,逃荒来到烟台,一九一三年十二月生了我。在外混了七、八年,父亲得了病,没法维持生活,又返回老家。我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姐姐,一九二四年我十一岁时,母亲刚生下小妹妹,父亲病重没钱医治,就去世了。母亲和俺姐妹三人,穷得吃不上饭,便以讨饭为生。住的两间房子破漏不堪,没钱修,加上孤儿寡母受不了叔叔的欺侮,母亲横了横心,于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八日,领着我们到济南逃荒。走到白马山正碰上北伐军和军阀张宗昌的军队打仗,炮弹在头上飞,路上乱七八糟躺着很多死尸,母亲领着我们一边快走,一边口里祷念着:“老天保佑”。走到离济南不远时,又碰上日本兵,攻打刚进入济南的北伐军。我们脸发秽垢,一身破烂,走到洪家楼天主教堂,外国人比划着叫俺们去东关修女院,母亲对俺说:“那不是咱去的地方,有我这口气,咱不入那个院。”就领俺姊妹三人,白天伸着残手沿街讨饭乞生,晚上宿在两军打仗时垒的小土屋里。遇到卍字会发放救济粮,俺也去要点。就这样维持了两年。直到十六岁的姐姐嫁了人,得到八十元“彩礼”,才赁了一间放煤炭的小屋安了个家。那年,母亲患痢疾、发皮汗(疟疾),卧床不起,我和小妹瘦得皮包骨头,彩礼钱慢慢花光了,万般无奈,母亲才叫姐姐找了一辆东洋车,拉着她,带着我和妹妹,投奔了东关天主教修女院。外国修女便把母亲送到贫民医院里,把小妹送到小孩屋,把我送到孤儿院,这三处都在一个大院里。当时贫民医院有病人二十多个,孤儿院有孤儿一百三十多个,小孩屋有五、六岁以下的孩子三十多个。
姐姐的婆婆家也住在东关,和修女院同在一条马路上,相距一里左右,姐姐有时做点饭给母亲送去,我和小妹妹看着母亲整日躺在床上,母亲哭,我俩也哭。母亲好不容易挣扎了一个多月,看看不行了,就对外国修女说:“把这两个孩子交给您吧!老家他叔叔来要,不要给他”。不几天母亲就去世了。
在老家时姐姐体弱多病,妹妹小,家里重活累活全是我干。十五岁到了孤儿院后,做鞋、缝衣、照顾小的孤儿,什么活都让我做。在这期间,修女教我念经,又讲“天主十诫”“教会四规”给我听。第二年我正式入教,入教时,进行“圣洗”,神甫念完了经后,将“圣水”倾注在我的额项上,表示洗去“原罪”和“本罪”。领洗后成了正式教徒,一切按照教会的要求去做。十八岁时,一位姓张的修女,把我分配到伙房干活。
当时孤儿院有个规定,女孩子到了十七、八岁,由院里指定跟一位男人结婚,自己不能选择,在结婚前夕或当夜才能看到给指定的男人。我十八岁时,院长也给我找了个没见面的男人,订了婚。一天姓张的修女对我说:“看你这么好的孩子,当个修女吧!结婚,有什么意思?!”自己想想,可也是,看看母亲遭的那个罪,还不如当个修女好,经过再三考虑,我决定不结婚了,请姓张的修女告诉院长,把那门亲事退了。
我干活的伙房,与孤儿院在一个院内。一天,小妹妹来找我,说饿得慌,我给了她一个窝窝头和三头蒜。这事,被一个姓徐的中国修女知道了,告诉了外国修女院长,第三天院长把我叫了去,说我向着自己家的人,别人看了很气愤,不能再在伙房干了。便把我调到另一个大院,帮另一个修女喂鸡,喂兔子,喂羊。
当时我难过的哭了。穷人难为人,自己白干活,不给一分钱;自己管做饭,小妹妹伸着手要了一点,就算犯了规。从此,下了决心,手中无钱无物,再不见她。一直两年没见小妹妹,我是多么想念她啊!后来听说她得了肺病,很想我,临死时,二院长外国修女告诉我,叫我去看看,我手中当时还是一分钱没有,狠了狠心,没有去。
我姐姐住的尽管距修女院很近,但我手中老是一分钱没有,她家有老人,我不能空着手去,也一直没有去看她。
我十九岁时,那位姓张的修女,又叫我入一种会,这个会的名字叫“玛丽亚传教修女会”。会中分三等人:一等是有学问的;二等是学问不够的,三等是大姑。当时院长是德国人,中国姓姓徐。我向她正式提出要求入会。院长问我:“你为什么要当修女?”我说:“我看修女好。”院长说:“光看修女好不行,还要知道当修女是为了传道,救人灵魂,不论分配你干什么活,都是为了传教,每个要求入会的人,要许‘三愿’”。又问:“你知道‘三愿’是什么吗?”我说:“不全知道”。她说:“‘三愿’是:神贫(绝财,个人不得拥有任何财产),贞洁(绝色,永不结婚),听命(绝意,绝对服从长上的命令),这些你能做到吗?”我说:“能。”从这之后,又把我分配到残老伙房干活,这里有女残三十多人,男残四十多人,共七十多人,由我一人做饭,还给了一个烧锅炉的。为了表示虔诚,从此我任劳任怨,埋头苦干,每天忙个不停。
二十岁时,又把我分配到潍县修女院做饭。这个修女院设在坊子,听说是一九〇八年德籍神甫瓦利刚创建的。当时有十八个修女,有六个教师,我一人做二十四个人的饭,做了两年,看我干的不错,定为大姑。(介于一般教友与正式修女之间),发了“小愿”——十字架。十字架是代表耶稣临死时,钉在十字架上的苦像。我胸前挂一个二寸左右小的;床头上挂一个一尺左右大的,象征耶稣随时都在自己身边,要永远跟耶稣吃苦、行善,不做坏事。
当个大姑我并不甘心,我一心要当个修女。一天,管全国修女院的总头法国修女,来到潍县,我向她要求当正式修女,一位姓孙的中国老修女,也帮着我说话。一九三七年,我二十二岁时被送到“烟台初学院”,它是训练一般入会的初级训练机构,是要当正式修女必须经过的步骤。听说这个初学院是我国修女院中历史最早的,是在中法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即一八八六年四月由驻罗马的法籍总长姆姆玛琍得拉帕逊派了六名法国修女来筹办的。进入初学院,证明自己很快就要成为正式修女了,心中很高兴,可是到了烟台,又不叫我马上进“初学院”,先派我到大麻疯医院照顾病人。这个医院在烟台大海阳河二十三号安多尼修女院中(现烟台三中地址),是一九〇六年由法籍省长姆姆玛得伦得玛兹初创,到一九二八年又扩建成的,有四十五个床位,病人多时还要加床,我去时工作人员只有一名姓魏的意大利修女,病人有二十多个,有的脚趾烂了,有的手指烂了,有的满脸满身都肿了。听说过去有一个印度修女,因给麻疯病人治病被传染,最后也和麻疯病人住在一起,越看越害怕,越想越害怕。但自己发过誓,愿意“绝意”,绝对服从命令,必须经得起考验。这样,每天给病人擦洗、换药,侍候他们,只在接触病人时,根据魏修女的要求,经常用酒精消消毒,拿他们的东西时,不直接用手拿,用镊子捏,夹子夹。
我到这个医院时,正是日本鬼子侵占烟台的时候。第二年,警察局实行麻疯病人登记,病人怕被日本鬼子烧死,纷纷离开医院。
在麻疯病院干活的同时,英国修女院长,也分配我到贫民医院干活。贫民医院与麻疯病院是同时成立的,而且同在一个院内。来看病的全是穷人,有好多人因为缺衣服穿,身上披着麻袋片,很脏,其中不少是抽大烟、扎吗啡的。重病号也能住院,雇了个男工人侍候他们,人手不够时,就叫轻病号侍候重病号,并干些杂活。这里有个小药房,小门诊。药,多是些简单的常用药,贵重药品很少;门诊也没有正式大夫,只能看些临时小病。后来来了一个正式大夫,又增加了一个西班牙修女当护士,后因经费不足,大夫又调到别处去了。
我在这里干了三年,印象最深的是一九三八年日本鬼子侵占烟台的那一个多月。四月四日晚上,从西郊进来一支部队(以后听说是我党领导的胶东二支队),半夜,市内枪声不断,早晨五点,一开门,看到在院门口躺着一位伤员,子弹从前肋骨打进去,从后背穿出来,血直流,我请求英国修女院长抢救他,院长说:“他是你们中国人,为抵抗外来侵略受了伤,可以”。可是贫民医院为条件所限,不能动外科手术,只给他换了换药,他流血过多,又不能给他水喝。我向院长要了一个水果罐头,打开后一匙一匙喂着他,他当时脑子还清醒,他说:“老家是日照,家有父母,为了抵抗日本侵略,加入了部队,夜袭‘道台衙门’时受伤,撤退时战友们把我抬到医院门口”。又说:“看样子我是不行了,这里有我一个叔叔,在通伸住,是拉洋车的,请你给我捎个口信”。中午,我按照他说的地址,请那位男工人偷偷地给他叔送了个信。这天二鬼子来了两次,要马上把他抬走。我说:“这里是慈善医院,他伤得这么重,不抢救反而抬走,天主是不允许的”。我还说:“同是中国人,他为国负伤,你们怎么能忍心?!”说得二鬼子脸红了,最后我答应他们等治好了再说。他因伤了肺,纱布贴上就被气泡冲开,医治无效,第二天八点死去。
伤员的死,使我联想起:一九二八年日本侵略军,在济南枪杀中国人,相隔正好十年,他们又到烟台来枪杀中国人了,我暗暗祈祷天主惩罚这些恶魔。
一九三九年,我二十五岁了,才进了“初学院”(当时在烟台山东路十三号,现交际处招待所),同法国学校住在一个院内。但在“初学院”我仍被分配在厨房干活,管厨房的是个老修女,美国人,有四十多岁。还有六个工作人员。就餐人员有初学院四十多人,法国学校的学生四十多人,还有二十多个修女,共一百多人。这里的教员全是修女,学生也全是女的,多是本地外国领事馆和外侨的孩子,又因烟台气候良好,上海、哈尔滨、青岛各地的外籍儿童,也有来此上学的,初办时只有三十多人,以后多达一百余人。一九四五年第一次解放烟台时,外籍学生大多数离烟,学校结束。吃饭的就只剩“初学院”的人了。
到初学院,头一年穿上白衣服、白鞋。衣服是里外三层,里面是粗布衬衣,二层是连衣裙,腰间束一条带子,带子尽头在腰旁有三个疙瘩结,象征许的“三愿”。穿衣时扣在三个环子上,起个腰带作用。外面再套一个大斗篷式的拖地长袍子,头上戴着黑色包头巾。因为这是修女服装,四季都得穿着。夏季不论天气多么热,都不准脱,不准把胳臂、腿露在外面。
第三年(一九四一年),又把我分配到威海修女院做饭。这里有十四个修女,加上大夫、老师共十八人。厨房由我全面负责。因我脾气直,曾与管发东西的外国修女二院长发生过争执,一次,发的地瓜烂得不少,她告诉我做油炸地瓜饼,我说地瓜不够,不能做,她火了,与我吵了起来。当时院长是个德国修女,她找院长,我也找院长。到了第三年头,我该发大愿(成为正式修女的仪式)了,却为这么一件事,延长了我的考验期,又把我调回烟台“初学院”,继续做了两年饭。以后又调到法国医院,还是做饭。这个医院在崇实街四号(现市立医院地址)修女院中。这个修女院,连同这个医院最初是由法籍主教常明德购置地皮,一八九〇年由法籍省长姆姆玛得伦得帕兹开设的一个小型门诊所,一九一七年由德籍修女郝培叶扩建,一九三七年才逐步建成的。郝培叶既是修女院院长,又是医院院长。因建筑时曾得到法国政府的捐助,所以定名为“法国医院”。这里有中籍大夫一人,外籍护士二人,中籍护士八人,工人八人。设有小型的司药室、化验室、手术室、爱克司光室、助产室、公务房,有床位六十五张。在这里干了一年,我三十一岁,到一九四五年烟台第一次解放,“初学院”要搬到青岛时,才给我发了“大愿”。
发“大愿”时,举行了隆重的仪式。神甫做完“弥撒”,把“大愿”的信物——一只银戒指,交给院长,院长给我戴在左手中指上,又给我戴上刺冠(用一种带刺的花枝做成圈状戴在头上),表示永远跟耶稣受苦。同时剪去了长发,表示永不结婚。发“大愿”前结婚还可以,发“大愿”后再结婚就有罪了。这只银戒指,没有接缝,外面刻着“耶稣、玛琍亚、约瑟”字样,里面刻着做首饰店的店名。
有钱人批准当修女,要对修会进行捐献,一般的得交三百元。因我是孤儿,下等人,没有钱,所以只得熬。从十九岁我正式提出要求当修女,直到三十一岁,整整十二年才批准了。
在这些年中和当正式修女以后,因为必须做到“三愿”,自己没有自主的权利,一切听老修女的支配,叫干什么就得干什么,说这是“神”的意思,不准打折扣。一进“初学院”就给我编了号码——八五九六,所有的生活用品,如衣服、毛巾、衬裤、鞋等上面都有这个号码。修女院分工很细,衣服脏了有专人洗,不准自己洗,若不经请示批准,自己洗了就是犯罪。不管自己犯了什么“罪”,都得当众跪在院长面前告解、痛悔、表示永不再犯。每人夏天一身白衣,冬天一身毛衣、毛裤,没有棉衣;床上只有一个草褥子、一个褥单、一个床单、一床被。大多数修女是一个人一个小房间,我与另外两个修女同住一间比较大一点的房子。每人床前一个布帘子,在宿舍和平日不准随便说话和聊天,互相只知道姓。我长期没有自己的名字,“领洗”入教后叫我“梁巴丽亚”,正式当修女后,改叫“巴亚利德”,说这是一个外国主教名字,他后来成了圣人,遭罪死去,叫我效仿他,也叫这个名字。我现在的名字梁淑贞,是在烟台解放后才新用的。
这里每天早晨五点起床,五点半进教堂,先念“本分经”,再默想全书半小时,再望“弥撒”领“圣体”。六点半早饭,十一点半午饭,六点晚饭,九点半熄灯,都是统一打钟。饭后都各人上自己工作岗位。每天午饭、晚饭后,在会议室统一休息半小时,院长坐在当中,大家围坐在一起说说话。但每人手中都拿着零活,边说边干,没有一个闲着的。到了半小时,院长摇小铃,这就是告诉不准再说话了,开始上晚课,念经祈祷天主。
修女院的饭食,早晨一般没有菜,有时有奶,有时大麦面饭一人一碗;中午一人一盘菜,一盘水果(每盘一两个);晚饭每人一盘菜,一小碗汤(甜的),饭管饱。日本鬼子在时,粮食困难,外面领橡子面,修女院中也吃橡子面。修女院中对教会所定的大小“斋期”,执行的很严。教会规定:星期五为“占礼六”,是小斋日,这天可以吃冷血动物的肉,如鱼、虾类;忌吃热血动物的肉,如牛、猪、羊、鸡、鸭等。此外,还有“大斋日”和“空心斋”。一年有四次“大斋日”,这一天只准吃一顿素餐;“空心斋”是从每次领“圣体”前的子夜起,到次日清晨领完“圣体”止,不准喝水、吃东西,空腹领完“圣体”后,方可饮食。
修女院还规定两人谈话必须到指定的地点,在走廊两头挂着可以谈话的牌子,别处不准谈话。谈话时不准高声,进屋与长上讲话也有规定的一定地点,不准靠前也不准靠后;院长找你训话,要跪在那里听。还规定访亲友或亲友来访,必须由院长指定专人陪同,不准个人单独行动。
象这样生活和工作的“初学院”,虽然开始进的多,但成功的很少。和我一起发白衣的五人,最后只有两人成了修女;和我一起入“初学院”的四名外国人:俄国人两名,英国人、葡萄牙人各一名,成功的才只一人。没当上修女的,都回青岛当一般的教友去了。
修女院的经费来源,与天主教会经费来源是一样的,除由罗马总会转拨和教友捐献外,尚有五个来源:
工厂生产的利润。教会有绣花工厂三处:崇实街十八号,一九一〇年创建,女工初二十余人,多时达一百余人,一九四四年结束;张家窑街三十三号,一九三四年创建,女工六十余人,一九四二年结束;大海阳河西崖二十三号,一九一〇年创建,女工最多达一百余人,一九四三年结束。这些工厂,当时都很赚钱。还有印书馆一所,在海岸街二十五号,是一九〇八年法籍李神甫所创,工人最多时四十多人,为教会印宣传品,也对外营业赚钱。一九三九年以后,有些工人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被日本宪兵队发觉,一九四二年负责人陈东河被害,印刷厂被迫关闭。
土地生产收入。教会在烟台共有土地一百七十一亩,其中:菜园、葡萄园三十八亩,沙窝地一百零三亩;荒地三十亩。
学校收学生的学费。教会在烟台开办收学费的学校有五所:崇德女中(爱德街二号)一九三〇年创办,一九四八年停办,学生最多时五百余人;崇正男子中学(大马路一三七号)一九一三年创办,一九四八年停办,学生最多时二百余人;崇正小学(东升街二十八号)一九一四年创办,一九四八年停办,学生最多时达一千余人;崇德女子小学(崇实街十八号)一九一八年创办,一九四八年停办,学生最多时二百五十多人;法国小学(又名方济各外国儿童学校)一八九〇年建立,一九四五年结束,学生最多时有一百多人。这些学校,学费很高。如崇正中学,学生每学期学费八元,一九四六年改收苞米,每学期六十斤,多于当时教师的月工资。
再如法国医院看病、卖药、治病、收病人住院,和教会房屋出租都有一定的收入。据烟台第二次解放后统计,教会的楼房出租的占百分之五十六点一四;平房出租的占百分之二十九点三五。
我当修女前后,大部分时间是做饭,粮、菜有人买回来,做什么样的饭菜有人告诉,我只管做,没有管过财务,也很少与外界接触。一九五二年外国人走时,我三十八岁,在这二十四年中,除身上穿的和睡觉、吃饭用的编号的衣物以外,自己一无所有,确实做到了“神贫”、“绝财”。外国人临走时,留给我们这些苦干了二十几年的人,每人一百万元钱。我二十四年来,头一次得到钱。当时币制还未改革,一万元顶现在一元,票面上哪是百元,哪是千元,哪是万元,我都不认得。
外国人走后,中国修女和大姑们,凡是乐意而且能够从事社会职业的,人民政府都作了安置。其中有五个老、残人不愿到恤养院,我只好留下来照顾她们,种着修女院中的四亩地,维持大家的生活,大家就把我看成是什么院长了。一九五五年前后,因城市建设需要征用这四亩地,老、残人由民政局给予救济。一九六二年二月,根据我的要求,政府给我安排了工作。我省吃俭用,工资花不了就存入银行,现在已经储蓄两千多元。在修女院二十四年没看一次电影,现在,有时我一天看两场,别人给我起了个外号叫“电影迷”。解放后,我和姐姐也多次见面,她的八个孩子,有的在部队,有的在公社,有的在医院,有的在生产队,生活都很好。
现在,我这个老修女,也成了国家的主人,参与了国家大事和宗教事务的研究和管理工作。当初,外国人走的时候,我还担心日子没法过,事实证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摆脱了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役和束缚,日子过的是越来越好,如果,我的父亲、母亲、妹妹能活到现在,亲眼看看今天,那该是多么高兴啊!
我老家是泰安城西南安驾庄。母亲因为手残,和家中只有七分地的父亲结了婚,婚后因生活没法维持,逃荒来到烟台,一九一三年十二月生了我。在外混了七、八年,父亲得了病,没法维持生活,又返回老家。我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姐姐,一九二四年我十一岁时,母亲刚生下小妹妹,父亲病重没钱医治,就去世了。母亲和俺姐妹三人,穷得吃不上饭,便以讨饭为生。住的两间房子破漏不堪,没钱修,加上孤儿寡母受不了叔叔的欺侮,母亲横了横心,于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八日,领着我们到济南逃荒。走到白马山正碰上北伐军和军阀张宗昌的军队打仗,炮弹在头上飞,路上乱七八糟躺着很多死尸,母亲领着我们一边快走,一边口里祷念着:“老天保佑”。走到离济南不远时,又碰上日本兵,攻打刚进入济南的北伐军。我们脸发秽垢,一身破烂,走到洪家楼天主教堂,外国人比划着叫俺们去东关修女院,母亲对俺说:“那不是咱去的地方,有我这口气,咱不入那个院。”就领俺姊妹三人,白天伸着残手沿街讨饭乞生,晚上宿在两军打仗时垒的小土屋里。遇到卍字会发放救济粮,俺也去要点。就这样维持了两年。直到十六岁的姐姐嫁了人,得到八十元“彩礼”,才赁了一间放煤炭的小屋安了个家。那年,母亲患痢疾、发皮汗(疟疾),卧床不起,我和小妹瘦得皮包骨头,彩礼钱慢慢花光了,万般无奈,母亲才叫姐姐找了一辆东洋车,拉着她,带着我和妹妹,投奔了东关天主教修女院。外国修女便把母亲送到贫民医院里,把小妹送到小孩屋,把我送到孤儿院,这三处都在一个大院里。当时贫民医院有病人二十多个,孤儿院有孤儿一百三十多个,小孩屋有五、六岁以下的孩子三十多个。
姐姐的婆婆家也住在东关,和修女院同在一条马路上,相距一里左右,姐姐有时做点饭给母亲送去,我和小妹妹看着母亲整日躺在床上,母亲哭,我俩也哭。母亲好不容易挣扎了一个多月,看看不行了,就对外国修女说:“把这两个孩子交给您吧!老家他叔叔来要,不要给他”。不几天母亲就去世了。
在老家时姐姐体弱多病,妹妹小,家里重活累活全是我干。十五岁到了孤儿院后,做鞋、缝衣、照顾小的孤儿,什么活都让我做。在这期间,修女教我念经,又讲“天主十诫”“教会四规”给我听。第二年我正式入教,入教时,进行“圣洗”,神甫念完了经后,将“圣水”倾注在我的额项上,表示洗去“原罪”和“本罪”。领洗后成了正式教徒,一切按照教会的要求去做。十八岁时,一位姓张的修女,把我分配到伙房干活。
当时孤儿院有个规定,女孩子到了十七、八岁,由院里指定跟一位男人结婚,自己不能选择,在结婚前夕或当夜才能看到给指定的男人。我十八岁时,院长也给我找了个没见面的男人,订了婚。一天姓张的修女对我说:“看你这么好的孩子,当个修女吧!结婚,有什么意思?!”自己想想,可也是,看看母亲遭的那个罪,还不如当个修女好,经过再三考虑,我决定不结婚了,请姓张的修女告诉院长,把那门亲事退了。
我干活的伙房,与孤儿院在一个院内。一天,小妹妹来找我,说饿得慌,我给了她一个窝窝头和三头蒜。这事,被一个姓徐的中国修女知道了,告诉了外国修女院长,第三天院长把我叫了去,说我向着自己家的人,别人看了很气愤,不能再在伙房干了。便把我调到另一个大院,帮另一个修女喂鸡,喂兔子,喂羊。
当时我难过的哭了。穷人难为人,自己白干活,不给一分钱;自己管做饭,小妹妹伸着手要了一点,就算犯了规。从此,下了决心,手中无钱无物,再不见她。一直两年没见小妹妹,我是多么想念她啊!后来听说她得了肺病,很想我,临死时,二院长外国修女告诉我,叫我去看看,我手中当时还是一分钱没有,狠了狠心,没有去。
我姐姐住的尽管距修女院很近,但我手中老是一分钱没有,她家有老人,我不能空着手去,也一直没有去看她。
我十九岁时,那位姓张的修女,又叫我入一种会,这个会的名字叫“玛丽亚传教修女会”。会中分三等人:一等是有学问的;二等是学问不够的,三等是大姑。当时院长是德国人,中国姓姓徐。我向她正式提出要求入会。院长问我:“你为什么要当修女?”我说:“我看修女好。”院长说:“光看修女好不行,还要知道当修女是为了传道,救人灵魂,不论分配你干什么活,都是为了传教,每个要求入会的人,要许‘三愿’”。又问:“你知道‘三愿’是什么吗?”我说:“不全知道”。她说:“‘三愿’是:神贫(绝财,个人不得拥有任何财产),贞洁(绝色,永不结婚),听命(绝意,绝对服从长上的命令),这些你能做到吗?”我说:“能。”从这之后,又把我分配到残老伙房干活,这里有女残三十多人,男残四十多人,共七十多人,由我一人做饭,还给了一个烧锅炉的。为了表示虔诚,从此我任劳任怨,埋头苦干,每天忙个不停。
二十岁时,又把我分配到潍县修女院做饭。这个修女院设在坊子,听说是一九〇八年德籍神甫瓦利刚创建的。当时有十八个修女,有六个教师,我一人做二十四个人的饭,做了两年,看我干的不错,定为大姑。(介于一般教友与正式修女之间),发了“小愿”——十字架。十字架是代表耶稣临死时,钉在十字架上的苦像。我胸前挂一个二寸左右小的;床头上挂一个一尺左右大的,象征耶稣随时都在自己身边,要永远跟耶稣吃苦、行善,不做坏事。
当个大姑我并不甘心,我一心要当个修女。一天,管全国修女院的总头法国修女,来到潍县,我向她要求当正式修女,一位姓孙的中国老修女,也帮着我说话。一九三七年,我二十二岁时被送到“烟台初学院”,它是训练一般入会的初级训练机构,是要当正式修女必须经过的步骤。听说这个初学院是我国修女院中历史最早的,是在中法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即一八八六年四月由驻罗马的法籍总长姆姆玛琍得拉帕逊派了六名法国修女来筹办的。进入初学院,证明自己很快就要成为正式修女了,心中很高兴,可是到了烟台,又不叫我马上进“初学院”,先派我到大麻疯医院照顾病人。这个医院在烟台大海阳河二十三号安多尼修女院中(现烟台三中地址),是一九〇六年由法籍省长姆姆玛得伦得玛兹初创,到一九二八年又扩建成的,有四十五个床位,病人多时还要加床,我去时工作人员只有一名姓魏的意大利修女,病人有二十多个,有的脚趾烂了,有的手指烂了,有的满脸满身都肿了。听说过去有一个印度修女,因给麻疯病人治病被传染,最后也和麻疯病人住在一起,越看越害怕,越想越害怕。但自己发过誓,愿意“绝意”,绝对服从命令,必须经得起考验。这样,每天给病人擦洗、换药,侍候他们,只在接触病人时,根据魏修女的要求,经常用酒精消消毒,拿他们的东西时,不直接用手拿,用镊子捏,夹子夹。
我到这个医院时,正是日本鬼子侵占烟台的时候。第二年,警察局实行麻疯病人登记,病人怕被日本鬼子烧死,纷纷离开医院。
在麻疯病院干活的同时,英国修女院长,也分配我到贫民医院干活。贫民医院与麻疯病院是同时成立的,而且同在一个院内。来看病的全是穷人,有好多人因为缺衣服穿,身上披着麻袋片,很脏,其中不少是抽大烟、扎吗啡的。重病号也能住院,雇了个男工人侍候他们,人手不够时,就叫轻病号侍候重病号,并干些杂活。这里有个小药房,小门诊。药,多是些简单的常用药,贵重药品很少;门诊也没有正式大夫,只能看些临时小病。后来来了一个正式大夫,又增加了一个西班牙修女当护士,后因经费不足,大夫又调到别处去了。
我在这里干了三年,印象最深的是一九三八年日本鬼子侵占烟台的那一个多月。四月四日晚上,从西郊进来一支部队(以后听说是我党领导的胶东二支队),半夜,市内枪声不断,早晨五点,一开门,看到在院门口躺着一位伤员,子弹从前肋骨打进去,从后背穿出来,血直流,我请求英国修女院长抢救他,院长说:“他是你们中国人,为抵抗外来侵略受了伤,可以”。可是贫民医院为条件所限,不能动外科手术,只给他换了换药,他流血过多,又不能给他水喝。我向院长要了一个水果罐头,打开后一匙一匙喂着他,他当时脑子还清醒,他说:“老家是日照,家有父母,为了抵抗日本侵略,加入了部队,夜袭‘道台衙门’时受伤,撤退时战友们把我抬到医院门口”。又说:“看样子我是不行了,这里有我一个叔叔,在通伸住,是拉洋车的,请你给我捎个口信”。中午,我按照他说的地址,请那位男工人偷偷地给他叔送了个信。这天二鬼子来了两次,要马上把他抬走。我说:“这里是慈善医院,他伤得这么重,不抢救反而抬走,天主是不允许的”。我还说:“同是中国人,他为国负伤,你们怎么能忍心?!”说得二鬼子脸红了,最后我答应他们等治好了再说。他因伤了肺,纱布贴上就被气泡冲开,医治无效,第二天八点死去。
伤员的死,使我联想起:一九二八年日本侵略军,在济南枪杀中国人,相隔正好十年,他们又到烟台来枪杀中国人了,我暗暗祈祷天主惩罚这些恶魔。
一九三九年,我二十五岁了,才进了“初学院”(当时在烟台山东路十三号,现交际处招待所),同法国学校住在一个院内。但在“初学院”我仍被分配在厨房干活,管厨房的是个老修女,美国人,有四十多岁。还有六个工作人员。就餐人员有初学院四十多人,法国学校的学生四十多人,还有二十多个修女,共一百多人。这里的教员全是修女,学生也全是女的,多是本地外国领事馆和外侨的孩子,又因烟台气候良好,上海、哈尔滨、青岛各地的外籍儿童,也有来此上学的,初办时只有三十多人,以后多达一百余人。一九四五年第一次解放烟台时,外籍学生大多数离烟,学校结束。吃饭的就只剩“初学院”的人了。
到初学院,头一年穿上白衣服、白鞋。衣服是里外三层,里面是粗布衬衣,二层是连衣裙,腰间束一条带子,带子尽头在腰旁有三个疙瘩结,象征许的“三愿”。穿衣时扣在三个环子上,起个腰带作用。外面再套一个大斗篷式的拖地长袍子,头上戴着黑色包头巾。因为这是修女服装,四季都得穿着。夏季不论天气多么热,都不准脱,不准把胳臂、腿露在外面。
第三年(一九四一年),又把我分配到威海修女院做饭。这里有十四个修女,加上大夫、老师共十八人。厨房由我全面负责。因我脾气直,曾与管发东西的外国修女二院长发生过争执,一次,发的地瓜烂得不少,她告诉我做油炸地瓜饼,我说地瓜不够,不能做,她火了,与我吵了起来。当时院长是个德国修女,她找院长,我也找院长。到了第三年头,我该发大愿(成为正式修女的仪式)了,却为这么一件事,延长了我的考验期,又把我调回烟台“初学院”,继续做了两年饭。以后又调到法国医院,还是做饭。这个医院在崇实街四号(现市立医院地址)修女院中。这个修女院,连同这个医院最初是由法籍主教常明德购置地皮,一八九〇年由法籍省长姆姆玛得伦得帕兹开设的一个小型门诊所,一九一七年由德籍修女郝培叶扩建,一九三七年才逐步建成的。郝培叶既是修女院院长,又是医院院长。因建筑时曾得到法国政府的捐助,所以定名为“法国医院”。这里有中籍大夫一人,外籍护士二人,中籍护士八人,工人八人。设有小型的司药室、化验室、手术室、爱克司光室、助产室、公务房,有床位六十五张。在这里干了一年,我三十一岁,到一九四五年烟台第一次解放,“初学院”要搬到青岛时,才给我发了“大愿”。
发“大愿”时,举行了隆重的仪式。神甫做完“弥撒”,把“大愿”的信物——一只银戒指,交给院长,院长给我戴在左手中指上,又给我戴上刺冠(用一种带刺的花枝做成圈状戴在头上),表示永远跟耶稣受苦。同时剪去了长发,表示永不结婚。发“大愿”前结婚还可以,发“大愿”后再结婚就有罪了。这只银戒指,没有接缝,外面刻着“耶稣、玛琍亚、约瑟”字样,里面刻着做首饰店的店名。
有钱人批准当修女,要对修会进行捐献,一般的得交三百元。因我是孤儿,下等人,没有钱,所以只得熬。从十九岁我正式提出要求当修女,直到三十一岁,整整十二年才批准了。
在这些年中和当正式修女以后,因为必须做到“三愿”,自己没有自主的权利,一切听老修女的支配,叫干什么就得干什么,说这是“神”的意思,不准打折扣。一进“初学院”就给我编了号码——八五九六,所有的生活用品,如衣服、毛巾、衬裤、鞋等上面都有这个号码。修女院分工很细,衣服脏了有专人洗,不准自己洗,若不经请示批准,自己洗了就是犯罪。不管自己犯了什么“罪”,都得当众跪在院长面前告解、痛悔、表示永不再犯。每人夏天一身白衣,冬天一身毛衣、毛裤,没有棉衣;床上只有一个草褥子、一个褥单、一个床单、一床被。大多数修女是一个人一个小房间,我与另外两个修女同住一间比较大一点的房子。每人床前一个布帘子,在宿舍和平日不准随便说话和聊天,互相只知道姓。我长期没有自己的名字,“领洗”入教后叫我“梁巴丽亚”,正式当修女后,改叫“巴亚利德”,说这是一个外国主教名字,他后来成了圣人,遭罪死去,叫我效仿他,也叫这个名字。我现在的名字梁淑贞,是在烟台解放后才新用的。
这里每天早晨五点起床,五点半进教堂,先念“本分经”,再默想全书半小时,再望“弥撒”领“圣体”。六点半早饭,十一点半午饭,六点晚饭,九点半熄灯,都是统一打钟。饭后都各人上自己工作岗位。每天午饭、晚饭后,在会议室统一休息半小时,院长坐在当中,大家围坐在一起说说话。但每人手中都拿着零活,边说边干,没有一个闲着的。到了半小时,院长摇小铃,这就是告诉不准再说话了,开始上晚课,念经祈祷天主。
修女院的饭食,早晨一般没有菜,有时有奶,有时大麦面饭一人一碗;中午一人一盘菜,一盘水果(每盘一两个);晚饭每人一盘菜,一小碗汤(甜的),饭管饱。日本鬼子在时,粮食困难,外面领橡子面,修女院中也吃橡子面。修女院中对教会所定的大小“斋期”,执行的很严。教会规定:星期五为“占礼六”,是小斋日,这天可以吃冷血动物的肉,如鱼、虾类;忌吃热血动物的肉,如牛、猪、羊、鸡、鸭等。此外,还有“大斋日”和“空心斋”。一年有四次“大斋日”,这一天只准吃一顿素餐;“空心斋”是从每次领“圣体”前的子夜起,到次日清晨领完“圣体”止,不准喝水、吃东西,空腹领完“圣体”后,方可饮食。
修女院还规定两人谈话必须到指定的地点,在走廊两头挂着可以谈话的牌子,别处不准谈话。谈话时不准高声,进屋与长上讲话也有规定的一定地点,不准靠前也不准靠后;院长找你训话,要跪在那里听。还规定访亲友或亲友来访,必须由院长指定专人陪同,不准个人单独行动。
象这样生活和工作的“初学院”,虽然开始进的多,但成功的很少。和我一起发白衣的五人,最后只有两人成了修女;和我一起入“初学院”的四名外国人:俄国人两名,英国人、葡萄牙人各一名,成功的才只一人。没当上修女的,都回青岛当一般的教友去了。
修女院的经费来源,与天主教会经费来源是一样的,除由罗马总会转拨和教友捐献外,尚有五个来源:
工厂生产的利润。教会有绣花工厂三处:崇实街十八号,一九一〇年创建,女工初二十余人,多时达一百余人,一九四四年结束;张家窑街三十三号,一九三四年创建,女工六十余人,一九四二年结束;大海阳河西崖二十三号,一九一〇年创建,女工最多达一百余人,一九四三年结束。这些工厂,当时都很赚钱。还有印书馆一所,在海岸街二十五号,是一九〇八年法籍李神甫所创,工人最多时四十多人,为教会印宣传品,也对外营业赚钱。一九三九年以后,有些工人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被日本宪兵队发觉,一九四二年负责人陈东河被害,印刷厂被迫关闭。
土地生产收入。教会在烟台共有土地一百七十一亩,其中:菜园、葡萄园三十八亩,沙窝地一百零三亩;荒地三十亩。
学校收学生的学费。教会在烟台开办收学费的学校有五所:崇德女中(爱德街二号)一九三〇年创办,一九四八年停办,学生最多时五百余人;崇正男子中学(大马路一三七号)一九一三年创办,一九四八年停办,学生最多时二百余人;崇正小学(东升街二十八号)一九一四年创办,一九四八年停办,学生最多时达一千余人;崇德女子小学(崇实街十八号)一九一八年创办,一九四八年停办,学生最多时二百五十多人;法国小学(又名方济各外国儿童学校)一八九〇年建立,一九四五年结束,学生最多时有一百多人。这些学校,学费很高。如崇正中学,学生每学期学费八元,一九四六年改收苞米,每学期六十斤,多于当时教师的月工资。
再如法国医院看病、卖药、治病、收病人住院,和教会房屋出租都有一定的收入。据烟台第二次解放后统计,教会的楼房出租的占百分之五十六点一四;平房出租的占百分之二十九点三五。
我当修女前后,大部分时间是做饭,粮、菜有人买回来,做什么样的饭菜有人告诉,我只管做,没有管过财务,也很少与外界接触。一九五二年外国人走时,我三十八岁,在这二十四年中,除身上穿的和睡觉、吃饭用的编号的衣物以外,自己一无所有,确实做到了“神贫”、“绝财”。外国人临走时,留给我们这些苦干了二十几年的人,每人一百万元钱。我二十四年来,头一次得到钱。当时币制还未改革,一万元顶现在一元,票面上哪是百元,哪是千元,哪是万元,我都不认得。
外国人走后,中国修女和大姑们,凡是乐意而且能够从事社会职业的,人民政府都作了安置。其中有五个老、残人不愿到恤养院,我只好留下来照顾她们,种着修女院中的四亩地,维持大家的生活,大家就把我看成是什么院长了。一九五五年前后,因城市建设需要征用这四亩地,老、残人由民政局给予救济。一九六二年二月,根据我的要求,政府给我安排了工作。我省吃俭用,工资花不了就存入银行,现在已经储蓄两千多元。在修女院二十四年没看一次电影,现在,有时我一天看两场,别人给我起了个外号叫“电影迷”。解放后,我和姐姐也多次见面,她的八个孩子,有的在部队,有的在公社,有的在医院,有的在生产队,生活都很好。
现在,我这个老修女,也成了国家的主人,参与了国家大事和宗教事务的研究和管理工作。当初,外国人走的时候,我还担心日子没法过,事实证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摆脱了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役和束缚,日子过的是越来越好,如果,我的父亲、母亲、妹妹能活到现在,亲眼看看今天,那该是多么高兴啊!
相关人物
梁淑贞
责任者
相关地名
山东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