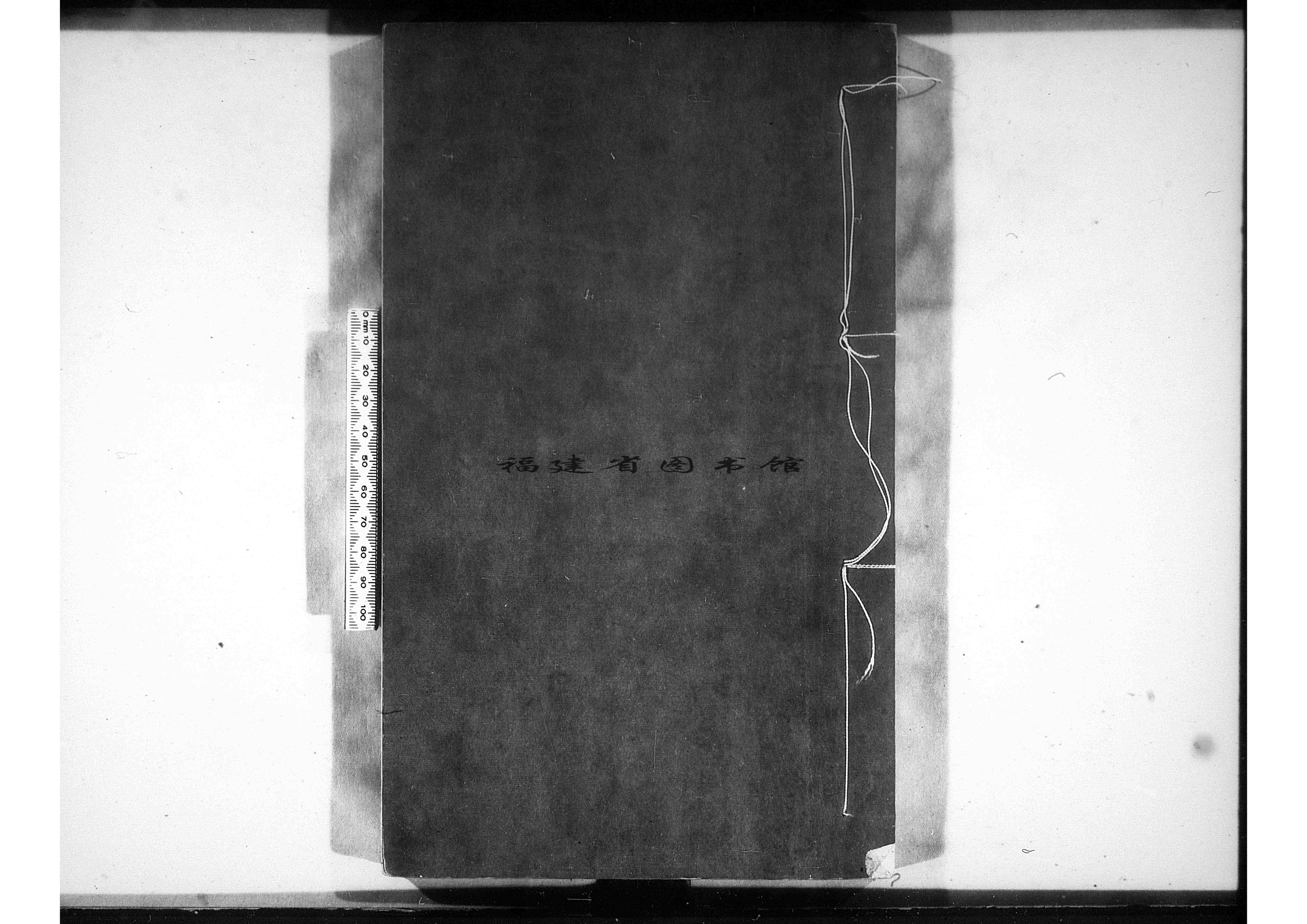内容
大学举吾十有五章来教云立是物格知至而意诚心
正之效不止是用功处不惑知命是意诚心正而所知
日进不已之验以至于耳顺则所知又至极而精熟矣
淳窃疑夫立者确然坚固不可移夺固非真知不能然
此时便谓物巳格知巳至恐莫失之大快否又事物之
理精微眇忽未至于灼然皆无疑惑万理根原来处未
洞见天命流行全体安得谓之知巳至曰所知日进不
巳则是面前犹有可进歩又安得全谓之至而耳顺又
云所知至极而精熟又何言之重复也而集注于耳顺
条方云知之至又何也凡此皆浅见未喻抑此之旨在
圣人分上言则圣人合下本是生知义理本是昭著自
儿童知巳至极本无疑惑天命全体本无蔽隔当入大
学则亦漫勘验其所以然随众做些小致知格物工夫
虽做此工夫而与众超越云云若以学者为学之序言
则自其志学时方一一做致知格物工夫以考察夫义
理积十五年之功至于确然有立时是亦真有所知然
后能然未可便谓物巳格知巳至
细思此意只得做学者事看而圣人所说则是他自见得
有略相似处今窥测它不得也正如曾子借忠恕两字發
明一贯之妙今岂可谓圣人必待施诸巳而不愿然后勿
施于人也然曾子所借犹有迹之可拟此则全不可知但
学者当以此自考耳
来孔文子章云此章固因论谥而人有一善之
可称圣人亦必取之此天地之量也淳谓自圣人平心
泛论人物言之则凡有一善之可称虽元恶大憝亦必
取之如天地之量无所不容自学者精考人物言之则
圣人所取之善当实体以为法而其不善则亦当知所
以自厉
大概是如此然不必说得太过却觉张皇无㴠蓄意思
再思可矣再字未详如何方是一畨思如何方是再畨
思
事到面前便断置了是一畨思断置定了更加审订是第
二畨思
桓魋其如予何匡人其如予何公伯寮其如命何来教
云三皆必其不能为害之辞与不得巳而听命以自
安者不同淳竊谓三语皆是必其不能为害之辞此便
是圣人乐天知命处见定志确断然以理自信绝无疑
忌顾虑之意虽曰命而实在主于理浑不见有天人之
辨彼不得巳而听命以自安者本不顾夫理义之当如
何但以事势无可奈何遂委之命以自遣而实未能自
信乎命与圣人之所谓命者自不同程子所谓命为中
人设即此等所谓命耳故在圣人分上则此等命不足
道也是则圣人之所谓命与常人之所谓命者事同而
情异焉不审是否【圣人所谓命者莫非理】
上二语是圣人自处处验之巳然而知其决不能害巳也
下一语是为子服景伯等言知其有命而未知其命之如
何但知公伯寮之无如此何耳
来教论夷齐云以天下之公义裁之则天伦重而父命
轻以人子之分言之则又不可分轻重但各认取自家
不便利处退后一歩便是伯夷叔齐得之矣淳详此竊
谓诸侯継世再問子路清禱
大概是如此但推得太支蔓如云祷尔于上下神祗只是
引此古语以明有祷之理非谓𣣔祷于皇天后土也
又尝疑集注曰圣人未尝有过无善可迁其素行固巳
合于神明故曰丘之祷久矣夫自其论圣人所以无事
于祷者其义固如此然此一句乃圣人自语也圣人之
意岂有谓我未尝有过无善可迁其素行固巳合于神
明哉不审此问少曲折更何如
圣人固有不居其圣时节又有直截担当无所推譲时节
如天生德于予未丧斯文之類盖诚有不可揜者
小学载𢈔黔娄父病毎夕稽颡北辰求以身代数日而
愈果有此应之之理否
祷是正礼自合有应不可谓知其无是理而姑为之
来教云窹寐者心之动静也有思无思者又动中之动
静也有夣无夣者又静中之动静也但窹阳而寐阴窹
清而寐浊窹有主而寐无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于窹
而言之淳思此竊谓人生具有阴阳之气神发于阳魄
根于阴心也者则丽阴阳而乘其气无间于动静即神
之所会而为魄之主也昼则阴伏藏而阳用事阳主动
故神运魄随而为窹夜则阳伏藏而阴主静故魄定神
蛰而为寐神之运故虚灵知觉之体烨然呈露有苗裔
之可寻如一阳万物之有春意焉此心之寂感所以
为有生神之蛰故虚灵知觉之体沉然潜隱悄无踪迹
如纯坤之月万物之生性不可窥其朕焉此心之寂感
所以不若窹之妙而于寐也为无主然其中实未尝泯
而有不可测者存呼之则应惊之则觉则是亦未尝无
主而未尝不妙也故自其大分言之窹阳而寐阴而心
之所以为动静也细而言之窹之有思者又动中之动
而为阳之阳也无思者又动中之静而为阳之阴也寐
之有夣者又静中之动而为阴之阳也无夣者又静中
之静而为阴之阴也又错而言之则思之有善与恶者
又动中之动阳明阴浊也无思而善应与妄应者又动
中之静阳明阴浊也夣之有正与邪者又静中之动阳
明阴浊也无夣而易觉与难觉者又静中之静阳明阴
浊也一动一静循环交错圣人与众人则同而所以为
阳明阴浊则异圣人于动静无不一于清明纯粹之主
而众人则杂焉而不齐然则人之学力所系于此亦可
以验矣
得之
宰予昼寝【云云】予虽非颜闵之伦而在圣门亦英才高
弟皆圣人所深属意者而予懈怠如此故【云云】
学者自是不可懈怠非有巳前许多说话也
又前段云吾軄分巳脩而吾事业巳毕乎吾生巳足而
吾将俯仰无愧乎【云云】
义理无穷若自谓四事都了而可以自安则虽不昼寝而
巳为懈怠矣此假大支蔓语气颇似张无垢更冝收敛就
亲切处看此事可否两言而决耳何用如此说作耶
仁者先难而后获先难克巳也既曰仁者则安得有巳
私恐此仁者字非指仁人而言语脉犹曰所谓仁云者
必先难后獲乃可谓之仁
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语意正如此
仁者虽巳无私然安敢自谓巳无私来示数卷此一様
病痛时时有之
又集注曰先其事之所难而后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
也此处下心字是如何岂此处便巳是仁者之心耶抑
求仁而其心当如是也晓此字未彻
仁者之心如是故求仁者之心亦当如之
又吕氏四句正是解此意四句然不惮所难为一句似
亦只说得先难意而后獲意思不切如何
当时本欲只用吕说后见其有此未备故别下语又惜其
语非它说所及故存之于后耳
述而第三十二章既以为之不厌诲人不倦自许而第
二章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集注又谓皆我所不能有或
者疑圣人之意不应如此相反欲以第二章亦为自许
之词而何有于我哉只谓其何但我有此众人皆能如
此庶前后意不相背淳为说以破之曰圣人之言各随
所在而发未尝参差挿杂当其有称夫子以圣且仁者
故夫子辞之而不敢当因退而就夫为之不厌诲之不
倦以自处此是为谦之意是辞髙而就卑也及人以学
而不厌诲人不倦二事归之夫子则又辞之以我所未
尝有此时为谦之意是辞其有能以就无能也二处之
言虽相袭而意之所主各自不同
不居仁圣巳为谦矣以学不厌诲不倦为无有又谦之谦
也至于事父兄公卿一节则又谦谦之谦也盖圣人只见
义理无穷而自巳有未到处是以其言毎下而益见其高
也
论语或问说桓魋匡人不能违天害巳处
此问病处亦与昼寝章相類
圣人既知天生德于我决无可害之理矣而避患又必
周详谨密者何耶【云云此身为天地附托至重云云】
患之当避自是理合如此众人亦然不必圣人为然也
君子坦荡荡坦荡二字只相连俱就气象说只是胸懐
平坦寛广否抑坦字就理说由循理平坦然后胸懐寛
广也
只合连说看下文对句可见
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集注云盛德之容中正和
平阴阳合德竊尝因其言而分之以上三截为阳而下
三截为阴似乎有合然又以上三截为阴而下三截为
阳亦自有合未知所决抑圣人浑是一元气之会无间
可得而指学者强为之形容如且以其说自分三才而
言则温然有和之可挹而不可屈夺则人之道也俨然
有威之可畏而不暴于物则天之道也恭顺卑下而恬
然无所不安则地之道也自阳根阴而言则温者阳之
和厉者阴之严威者阳之震不猛者阴之顺恭者阳之
主安者阴之定自阴根阳而言则温者阴之柔厉者阳
之刚威者阴之惨不猛者阳之舒恭者阴之肃安者阳
之健盖浑然无适而非中正和平之极不可得而偏指
者也
此说推得亦好
㤗伯之事集注【云云】当时商室虽衰天命时勢犹未也
大王乃萌是心睥睨于其下岂得不谓之邪志㤗伯固
譲为成父之邪志且自㓗其身而以所不欲者推之后
人何以为至德集注所谓岂无至公之说又果何如
翦商乃诗语不从亦是左氏所记当时必有所据看书中
说肇基王迹中庸言武王纉太王王季文王之绪则可见
矣此圣贤处事之变不可拘以常法处而太伯之譲则是
守常而不欲承当此事者也其心即夷齐之心而事之难
处则有甚焉尚以成父之邪志责之误矣
以能问于不能章集注采尹氏㡬于无我㡬字只就从
事一句可见邪抑并前五句皆可见邪犯而不校亦未
能无校此可见非圣人事
颜子正在着力不着力之间非但此处可见又只就从事
上看便分明不湏更说无校之云也
笃信好学犹笃行之云不是两字并言既笃而又信否
集注云笃厚而力也何谓厚而力只是其心加隆重于
此而又恳切于为之既不轻信而又不苟信否
笃信只是信得牢固不走作耳未有不轻信苟信之意不
轻不苟却在好学上见
㤗伯第十六章苏氏有是德无是德之说所谓德者是
原于天命之性否
德字只是说人各有长处不必便引到天命之性处也
恫而不愿愿字何训或谓谨愿则有不放纵之意或谓
愿悫则有朴实之意二说各不同不审其义果如何第
十七篇鄊原章亦引荀子愿悫之说
二说无甚不同鄊人无甚见识其所谓愿未必真愿乃卑
陋而随俗之人耳
集注又曰侗无知倥倥无能竊意侗者同也于物同然
一律瞑无识别是犹是也非犹是也倥者空也倥而又
倥是表里俱倥无寸长之实
此亦因旧说以字义音韵推之恐或然耳此類只合大概
看不湏苦推究也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集注云言以是为善非谓必欲如
是也竊谓善者㣲有未穏善者则有嘉善之意此不厌
但不嫌远而已盖圣人平日简淡
以下文推之圣人凡事子细初无简淡之意若如所说则
记者当云脍不厌粗食不厌粝乃为正理不应反作如此
说也
不得其酱不食集注云恶其不备也竊疑恶字太重似
见圣人有意处
恶其不备非恶其味之不羙但忘其贪味不苟食耳
集注中仲尼不易为夫子何也若如中庸第二章所辨
则恐在当时为可耳
不曾如此理会恐亦不湏如此理会也中庸或问乃为近
年有以此疑中庸非子思之作者故及之耳
文之为说大要只是有文理可观之谓盖凡义理之载
于经籍而存乎事物之间与夫见于威仪华采而为盛
德之辉光形于礼乐制度而为斯道之显及所引为有
文理之可观者皆是【云云】
物相杂故曰文如前所说是也如下面分别诸说则恐未
然如曰则以学文何以见其不为威仪华采礼乐制度耶
大学疑或问云人物之生莫不得其所以生者以为一
身之主近改物字作類字竊意類字意不重叠而字似
少开不若只依物字
向来改此類字盖为下文专说人之明德故不可下物字
若作物字即湏更分别人与物之所以异乃为全备近巳
如此改之矣
或问云既真知所止则其必得所止若巳无甚间隔竊
疑若巳字辞旨恐未明白欲改作亦非有甚间隔
若字意自分明未是真无间隔也
格物章或问云其所以精微要妙不可测度者乃在其
真积力久心通黙识之中此句晓之未详
此处细看当时下语不精今已改定
或问又曰所谓豁然贯通者又非见闻思虑之可及也
此句晓之未详不审此只是方其正一一格物时犹可
勉励用工夫以格之如所谓豁然贯通处則必真积之
久从容涵泳优㳺纯熟不期而自到非彊探力可擬
議以至耶抑是既到豁然贯通地位便是真知透彻【云】
【云】若于此而犹用力思索便是沛然自得
前说只以文义推可见何待如此致疑耶
或问所引书降衷以下八言虽皆所以证夫理而其相
次莫亦有序否尝试推之降衷自天赋于人而言秉彛
自人禀于天而言衷者理之至善而无妄也彛则理之
一定而有常也常即善之所为因有是善故能常衷者
綂言彛则指定言此二句方举其大纲而下文则详之
天地之中綂言天地间实理浑然大中无所偏倚为万
邦之极而万物之生莫不以是为枢纽也此比所谓衷
则又加确矣天命之性指是理降而在人为赋生之全
体而性则实即夫天理之中而非有二者是二言者一
言天一言自天而人又所以兼明夫天赋于人而详其
降衷之意也仁义之心仁义乃即天命之性指其实理
而心则包具焉以为体而主于身者也此比所谓彛则
又加实矣天然自有之中又细言是理之散于事物之
间莫不各有当然一定之则无过无不及皆天之所为
而非人之力者而其实又不外于其心此二句又就性
而言合衷彝而结之盖万物虽各有当然无过不及之
理然揔其根源之所自则只是一大本而同为一理也
此理人物所共由天地间所公共所以谓之道而其体
则綂会于吾之性非泛然事物之间而不根于其内也
竊疑此下更冝以周子所谓无极而太极以包天人事
物体用动静内外终始一贯为说似于八言之下其意
尤为圎也而不之取不审何也
当时只以古今为次第未有此意周子语意差远故不得
引以为证恐𨚫费注解也
延平格物之说原其意亦自程子说中得之【云云】又尝
疑前面反复论难专以程说为主盖不可以复加矣至
此假引延平说则又曰有非他说所能及未易以口舌
争其辞似抑扬低昻有左程右李别立一家之意
它说是指门人说语意自明何疑之有
传言谨独正就诚意著工夫处说或问又就意巳诚之
后说夫意之诚者既无所不尽真能慊快充足仰不愧
俯不怍到此地位其勢决然自不能巳矣而犹曰不敢
弛其谨独之劳焉所以防虑省察使其日新又新而不
至于间断何也恐此时所谓独与向时所谓谨独者大
不同
两说不见其不同但说到此恰好着力不可间斷耳
絜矩或问云各得其分不相侵越广狭长短平均如一
此四句晓之未详
所恶乎左便是左边人侵了自家左边界分而我恶之故
我亦不以此待右边人而不侵他右边之左如此方得左
边界分分明又以所恶乎右者度之方得右边界分分明
上下前后亦莫不然则四至所向皆得均平而界分方整
无偏广偏狭之病矣
作新民是成王封康叔之语而或问中曰武王何也
此书序之误五峰先生尝言之旧有一假辨此后以非所
急而去之但看此与酒诰两篇只说文王而不及武王又
曰朕其弟小子封又曰乃寡兄朂【武王自称犹今人云劣兄】则可见矣
【周公初基一节是错简】
又杂疑中庸序曰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
心人心只是就形气上平说天生如此未是就人为上
说然上文又曰或生于形气之私乃却下私字何也私
恐或渉人为私欲处说似与上智不能无人心句不相
合不审如何
如饥饱寒燠之類皆生于吾之血气形体而它人无与焉
所谓私也亦未便是不好但不可一向徇之耳
程子曰人无父母生日当倍悲痛如先生旧时亦尝有
寿母生朝及大硕人生朝与向日贺高倅词恐非先生
笔不审又何也岂在人子自已言则非其所冝而为父
母待亲朋则其情又有不容已处否然恐为此则是人
子以礼律身而以非礼事其亲以非礼待于人也其义
如何
此等事是力量不足放过了处然亦或有不得巳者其情
各不同也
程子以心使心之说竊谓此二心字只以人心道心判
之自明白盖上心字即是道心专以理义言之也下心
字即是人心而以形气言之也以心使心则是道心为
一身之主而人心为聴命也不审是否
亦是如此然观程先生之意只是说自作主宰耳
贫者举事有费财之浩瀚者不能不计度繁约而为之
裁处此与正义不谋利意相妨否竊恐谋利者是作这
一事更不看道理合当如何只论利便于巳与不利便
于巳得利便则为之不得则不为若贫而费财者只是
目下恐口足不相应因斟酌裁处而归之中其意自不
同否
当为而力不及者量宜处乃是义也力可为而计费吝惜
则是谋利而非义矣
中庸尚綗条以为巳立心明之象不审如何以为巳立
心明之象莫是有羙在其中只要自温好不用人知否
【象字疑下同】
此说得之然更宜详味
正之效不止是用功处不惑知命是意诚心正而所知
日进不已之验以至于耳顺则所知又至极而精熟矣
淳窃疑夫立者确然坚固不可移夺固非真知不能然
此时便谓物巳格知巳至恐莫失之大快否又事物之
理精微眇忽未至于灼然皆无疑惑万理根原来处未
洞见天命流行全体安得谓之知巳至曰所知日进不
巳则是面前犹有可进歩又安得全谓之至而耳顺又
云所知至极而精熟又何言之重复也而集注于耳顺
条方云知之至又何也凡此皆浅见未喻抑此之旨在
圣人分上言则圣人合下本是生知义理本是昭著自
儿童知巳至极本无疑惑天命全体本无蔽隔当入大
学则亦漫勘验其所以然随众做些小致知格物工夫
虽做此工夫而与众超越云云若以学者为学之序言
则自其志学时方一一做致知格物工夫以考察夫义
理积十五年之功至于确然有立时是亦真有所知然
后能然未可便谓物巳格知巳至
细思此意只得做学者事看而圣人所说则是他自见得
有略相似处今窥测它不得也正如曾子借忠恕两字發
明一贯之妙今岂可谓圣人必待施诸巳而不愿然后勿
施于人也然曾子所借犹有迹之可拟此则全不可知但
学者当以此自考耳
来孔文子章云此章固因论谥而人有一善之
可称圣人亦必取之此天地之量也淳谓自圣人平心
泛论人物言之则凡有一善之可称虽元恶大憝亦必
取之如天地之量无所不容自学者精考人物言之则
圣人所取之善当实体以为法而其不善则亦当知所
以自厉
大概是如此然不必说得太过却觉张皇无㴠蓄意思
再思可矣再字未详如何方是一畨思如何方是再畨
思
事到面前便断置了是一畨思断置定了更加审订是第
二畨思
桓魋其如予何匡人其如予何公伯寮其如命何来教
云三皆必其不能为害之辞与不得巳而听命以自
安者不同淳竊谓三语皆是必其不能为害之辞此便
是圣人乐天知命处见定志确断然以理自信绝无疑
忌顾虑之意虽曰命而实在主于理浑不见有天人之
辨彼不得巳而听命以自安者本不顾夫理义之当如
何但以事势无可奈何遂委之命以自遣而实未能自
信乎命与圣人之所谓命者自不同程子所谓命为中
人设即此等所谓命耳故在圣人分上则此等命不足
道也是则圣人之所谓命与常人之所谓命者事同而
情异焉不审是否【圣人所谓命者莫非理】
上二语是圣人自处处验之巳然而知其决不能害巳也
下一语是为子服景伯等言知其有命而未知其命之如
何但知公伯寮之无如此何耳
来教论夷齐云以天下之公义裁之则天伦重而父命
轻以人子之分言之则又不可分轻重但各认取自家
不便利处退后一歩便是伯夷叔齐得之矣淳详此竊
谓诸侯継世再問子路清禱
大概是如此但推得太支蔓如云祷尔于上下神祗只是
引此古语以明有祷之理非谓𣣔祷于皇天后土也
又尝疑集注曰圣人未尝有过无善可迁其素行固巳
合于神明故曰丘之祷久矣夫自其论圣人所以无事
于祷者其义固如此然此一句乃圣人自语也圣人之
意岂有谓我未尝有过无善可迁其素行固巳合于神
明哉不审此问少曲折更何如
圣人固有不居其圣时节又有直截担当无所推譲时节
如天生德于予未丧斯文之類盖诚有不可揜者
小学载𢈔黔娄父病毎夕稽颡北辰求以身代数日而
愈果有此应之之理否
祷是正礼自合有应不可谓知其无是理而姑为之
来教云窹寐者心之动静也有思无思者又动中之动
静也有夣无夣者又静中之动静也但窹阳而寐阴窹
清而寐浊窹有主而寐无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于窹
而言之淳思此竊谓人生具有阴阳之气神发于阳魄
根于阴心也者则丽阴阳而乘其气无间于动静即神
之所会而为魄之主也昼则阴伏藏而阳用事阳主动
故神运魄随而为窹夜则阳伏藏而阴主静故魄定神
蛰而为寐神之运故虚灵知觉之体烨然呈露有苗裔
之可寻如一阳万物之有春意焉此心之寂感所以
为有生神之蛰故虚灵知觉之体沉然潜隱悄无踪迹
如纯坤之月万物之生性不可窥其朕焉此心之寂感
所以不若窹之妙而于寐也为无主然其中实未尝泯
而有不可测者存呼之则应惊之则觉则是亦未尝无
主而未尝不妙也故自其大分言之窹阳而寐阴而心
之所以为动静也细而言之窹之有思者又动中之动
而为阳之阳也无思者又动中之静而为阳之阴也寐
之有夣者又静中之动而为阴之阳也无夣者又静中
之静而为阴之阴也又错而言之则思之有善与恶者
又动中之动阳明阴浊也无思而善应与妄应者又动
中之静阳明阴浊也夣之有正与邪者又静中之动阳
明阴浊也无夣而易觉与难觉者又静中之静阳明阴
浊也一动一静循环交错圣人与众人则同而所以为
阳明阴浊则异圣人于动静无不一于清明纯粹之主
而众人则杂焉而不齐然则人之学力所系于此亦可
以验矣
得之
宰予昼寝【云云】予虽非颜闵之伦而在圣门亦英才高
弟皆圣人所深属意者而予懈怠如此故【云云】
学者自是不可懈怠非有巳前许多说话也
又前段云吾軄分巳脩而吾事业巳毕乎吾生巳足而
吾将俯仰无愧乎【云云】
义理无穷若自谓四事都了而可以自安则虽不昼寝而
巳为懈怠矣此假大支蔓语气颇似张无垢更冝收敛就
亲切处看此事可否两言而决耳何用如此说作耶
仁者先难而后获先难克巳也既曰仁者则安得有巳
私恐此仁者字非指仁人而言语脉犹曰所谓仁云者
必先难后獲乃可谓之仁
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语意正如此
仁者虽巳无私然安敢自谓巳无私来示数卷此一様
病痛时时有之
又集注曰先其事之所难而后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
也此处下心字是如何岂此处便巳是仁者之心耶抑
求仁而其心当如是也晓此字未彻
仁者之心如是故求仁者之心亦当如之
又吕氏四句正是解此意四句然不惮所难为一句似
亦只说得先难意而后獲意思不切如何
当时本欲只用吕说后见其有此未备故别下语又惜其
语非它说所及故存之于后耳
述而第三十二章既以为之不厌诲人不倦自许而第
二章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集注又谓皆我所不能有或
者疑圣人之意不应如此相反欲以第二章亦为自许
之词而何有于我哉只谓其何但我有此众人皆能如
此庶前后意不相背淳为说以破之曰圣人之言各随
所在而发未尝参差挿杂当其有称夫子以圣且仁者
故夫子辞之而不敢当因退而就夫为之不厌诲之不
倦以自处此是为谦之意是辞髙而就卑也及人以学
而不厌诲人不倦二事归之夫子则又辞之以我所未
尝有此时为谦之意是辞其有能以就无能也二处之
言虽相袭而意之所主各自不同
不居仁圣巳为谦矣以学不厌诲不倦为无有又谦之谦
也至于事父兄公卿一节则又谦谦之谦也盖圣人只见
义理无穷而自巳有未到处是以其言毎下而益见其高
也
论语或问说桓魋匡人不能违天害巳处
此问病处亦与昼寝章相類
圣人既知天生德于我决无可害之理矣而避患又必
周详谨密者何耶【云云此身为天地附托至重云云】
患之当避自是理合如此众人亦然不必圣人为然也
君子坦荡荡坦荡二字只相连俱就气象说只是胸懐
平坦寛广否抑坦字就理说由循理平坦然后胸懐寛
广也
只合连说看下文对句可见
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集注云盛德之容中正和
平阴阳合德竊尝因其言而分之以上三截为阳而下
三截为阴似乎有合然又以上三截为阴而下三截为
阳亦自有合未知所决抑圣人浑是一元气之会无间
可得而指学者强为之形容如且以其说自分三才而
言则温然有和之可挹而不可屈夺则人之道也俨然
有威之可畏而不暴于物则天之道也恭顺卑下而恬
然无所不安则地之道也自阳根阴而言则温者阳之
和厉者阴之严威者阳之震不猛者阴之顺恭者阳之
主安者阴之定自阴根阳而言则温者阴之柔厉者阳
之刚威者阴之惨不猛者阳之舒恭者阴之肃安者阳
之健盖浑然无适而非中正和平之极不可得而偏指
者也
此说推得亦好
㤗伯之事集注【云云】当时商室虽衰天命时勢犹未也
大王乃萌是心睥睨于其下岂得不谓之邪志㤗伯固
譲为成父之邪志且自㓗其身而以所不欲者推之后
人何以为至德集注所谓岂无至公之说又果何如
翦商乃诗语不从亦是左氏所记当时必有所据看书中
说肇基王迹中庸言武王纉太王王季文王之绪则可见
矣此圣贤处事之变不可拘以常法处而太伯之譲则是
守常而不欲承当此事者也其心即夷齐之心而事之难
处则有甚焉尚以成父之邪志责之误矣
以能问于不能章集注采尹氏㡬于无我㡬字只就从
事一句可见邪抑并前五句皆可见邪犯而不校亦未
能无校此可见非圣人事
颜子正在着力不着力之间非但此处可见又只就从事
上看便分明不湏更说无校之云也
笃信好学犹笃行之云不是两字并言既笃而又信否
集注云笃厚而力也何谓厚而力只是其心加隆重于
此而又恳切于为之既不轻信而又不苟信否
笃信只是信得牢固不走作耳未有不轻信苟信之意不
轻不苟却在好学上见
㤗伯第十六章苏氏有是德无是德之说所谓德者是
原于天命之性否
德字只是说人各有长处不必便引到天命之性处也
恫而不愿愿字何训或谓谨愿则有不放纵之意或谓
愿悫则有朴实之意二说各不同不审其义果如何第
十七篇鄊原章亦引荀子愿悫之说
二说无甚不同鄊人无甚见识其所谓愿未必真愿乃卑
陋而随俗之人耳
集注又曰侗无知倥倥无能竊意侗者同也于物同然
一律瞑无识别是犹是也非犹是也倥者空也倥而又
倥是表里俱倥无寸长之实
此亦因旧说以字义音韵推之恐或然耳此類只合大概
看不湏苦推究也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集注云言以是为善非谓必欲如
是也竊谓善者㣲有未穏善者则有嘉善之意此不厌
但不嫌远而已盖圣人平日简淡
以下文推之圣人凡事子细初无简淡之意若如所说则
记者当云脍不厌粗食不厌粝乃为正理不应反作如此
说也
不得其酱不食集注云恶其不备也竊疑恶字太重似
见圣人有意处
恶其不备非恶其味之不羙但忘其贪味不苟食耳
集注中仲尼不易为夫子何也若如中庸第二章所辨
则恐在当时为可耳
不曾如此理会恐亦不湏如此理会也中庸或问乃为近
年有以此疑中庸非子思之作者故及之耳
文之为说大要只是有文理可观之谓盖凡义理之载
于经籍而存乎事物之间与夫见于威仪华采而为盛
德之辉光形于礼乐制度而为斯道之显及所引为有
文理之可观者皆是【云云】
物相杂故曰文如前所说是也如下面分别诸说则恐未
然如曰则以学文何以见其不为威仪华采礼乐制度耶
大学疑或问云人物之生莫不得其所以生者以为一
身之主近改物字作類字竊意類字意不重叠而字似
少开不若只依物字
向来改此類字盖为下文专说人之明德故不可下物字
若作物字即湏更分别人与物之所以异乃为全备近巳
如此改之矣
或问云既真知所止则其必得所止若巳无甚间隔竊
疑若巳字辞旨恐未明白欲改作亦非有甚间隔
若字意自分明未是真无间隔也
格物章或问云其所以精微要妙不可测度者乃在其
真积力久心通黙识之中此句晓之未详
此处细看当时下语不精今已改定
或问又曰所谓豁然贯通者又非见闻思虑之可及也
此句晓之未详不审此只是方其正一一格物时犹可
勉励用工夫以格之如所谓豁然贯通处則必真积之
久从容涵泳优㳺纯熟不期而自到非彊探力可擬
議以至耶抑是既到豁然贯通地位便是真知透彻【云】
【云】若于此而犹用力思索便是沛然自得
前说只以文义推可见何待如此致疑耶
或问所引书降衷以下八言虽皆所以证夫理而其相
次莫亦有序否尝试推之降衷自天赋于人而言秉彛
自人禀于天而言衷者理之至善而无妄也彛则理之
一定而有常也常即善之所为因有是善故能常衷者
綂言彛则指定言此二句方举其大纲而下文则详之
天地之中綂言天地间实理浑然大中无所偏倚为万
邦之极而万物之生莫不以是为枢纽也此比所谓衷
则又加确矣天命之性指是理降而在人为赋生之全
体而性则实即夫天理之中而非有二者是二言者一
言天一言自天而人又所以兼明夫天赋于人而详其
降衷之意也仁义之心仁义乃即天命之性指其实理
而心则包具焉以为体而主于身者也此比所谓彛则
又加实矣天然自有之中又细言是理之散于事物之
间莫不各有当然一定之则无过无不及皆天之所为
而非人之力者而其实又不外于其心此二句又就性
而言合衷彝而结之盖万物虽各有当然无过不及之
理然揔其根源之所自则只是一大本而同为一理也
此理人物所共由天地间所公共所以谓之道而其体
则綂会于吾之性非泛然事物之间而不根于其内也
竊疑此下更冝以周子所谓无极而太极以包天人事
物体用动静内外终始一贯为说似于八言之下其意
尤为圎也而不之取不审何也
当时只以古今为次第未有此意周子语意差远故不得
引以为证恐𨚫费注解也
延平格物之说原其意亦自程子说中得之【云云】又尝
疑前面反复论难专以程说为主盖不可以复加矣至
此假引延平说则又曰有非他说所能及未易以口舌
争其辞似抑扬低昻有左程右李别立一家之意
它说是指门人说语意自明何疑之有
传言谨独正就诚意著工夫处说或问又就意巳诚之
后说夫意之诚者既无所不尽真能慊快充足仰不愧
俯不怍到此地位其勢决然自不能巳矣而犹曰不敢
弛其谨独之劳焉所以防虑省察使其日新又新而不
至于间断何也恐此时所谓独与向时所谓谨独者大
不同
两说不见其不同但说到此恰好着力不可间斷耳
絜矩或问云各得其分不相侵越广狭长短平均如一
此四句晓之未详
所恶乎左便是左边人侵了自家左边界分而我恶之故
我亦不以此待右边人而不侵他右边之左如此方得左
边界分分明又以所恶乎右者度之方得右边界分分明
上下前后亦莫不然则四至所向皆得均平而界分方整
无偏广偏狭之病矣
作新民是成王封康叔之语而或问中曰武王何也
此书序之误五峰先生尝言之旧有一假辨此后以非所
急而去之但看此与酒诰两篇只说文王而不及武王又
曰朕其弟小子封又曰乃寡兄朂【武王自称犹今人云劣兄】则可见矣
【周公初基一节是错简】
又杂疑中庸序曰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
心人心只是就形气上平说天生如此未是就人为上
说然上文又曰或生于形气之私乃却下私字何也私
恐或渉人为私欲处说似与上智不能无人心句不相
合不审如何
如饥饱寒燠之類皆生于吾之血气形体而它人无与焉
所谓私也亦未便是不好但不可一向徇之耳
程子曰人无父母生日当倍悲痛如先生旧时亦尝有
寿母生朝及大硕人生朝与向日贺高倅词恐非先生
笔不审又何也岂在人子自已言则非其所冝而为父
母待亲朋则其情又有不容已处否然恐为此则是人
子以礼律身而以非礼事其亲以非礼待于人也其义
如何
此等事是力量不足放过了处然亦或有不得巳者其情
各不同也
程子以心使心之说竊谓此二心字只以人心道心判
之自明白盖上心字即是道心专以理义言之也下心
字即是人心而以形气言之也以心使心则是道心为
一身之主而人心为聴命也不审是否
亦是如此然观程先生之意只是说自作主宰耳
贫者举事有费财之浩瀚者不能不计度繁约而为之
裁处此与正义不谋利意相妨否竊恐谋利者是作这
一事更不看道理合当如何只论利便于巳与不利便
于巳得利便则为之不得则不为若贫而费财者只是
目下恐口足不相应因斟酌裁处而归之中其意自不
同否
当为而力不及者量宜处乃是义也力可为而计费吝惜
则是谋利而非义矣
中庸尚綗条以为巳立心明之象不审如何以为巳立
心明之象莫是有羙在其中只要自温好不用人知否
【象字疑下同】
此说得之然更宜详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