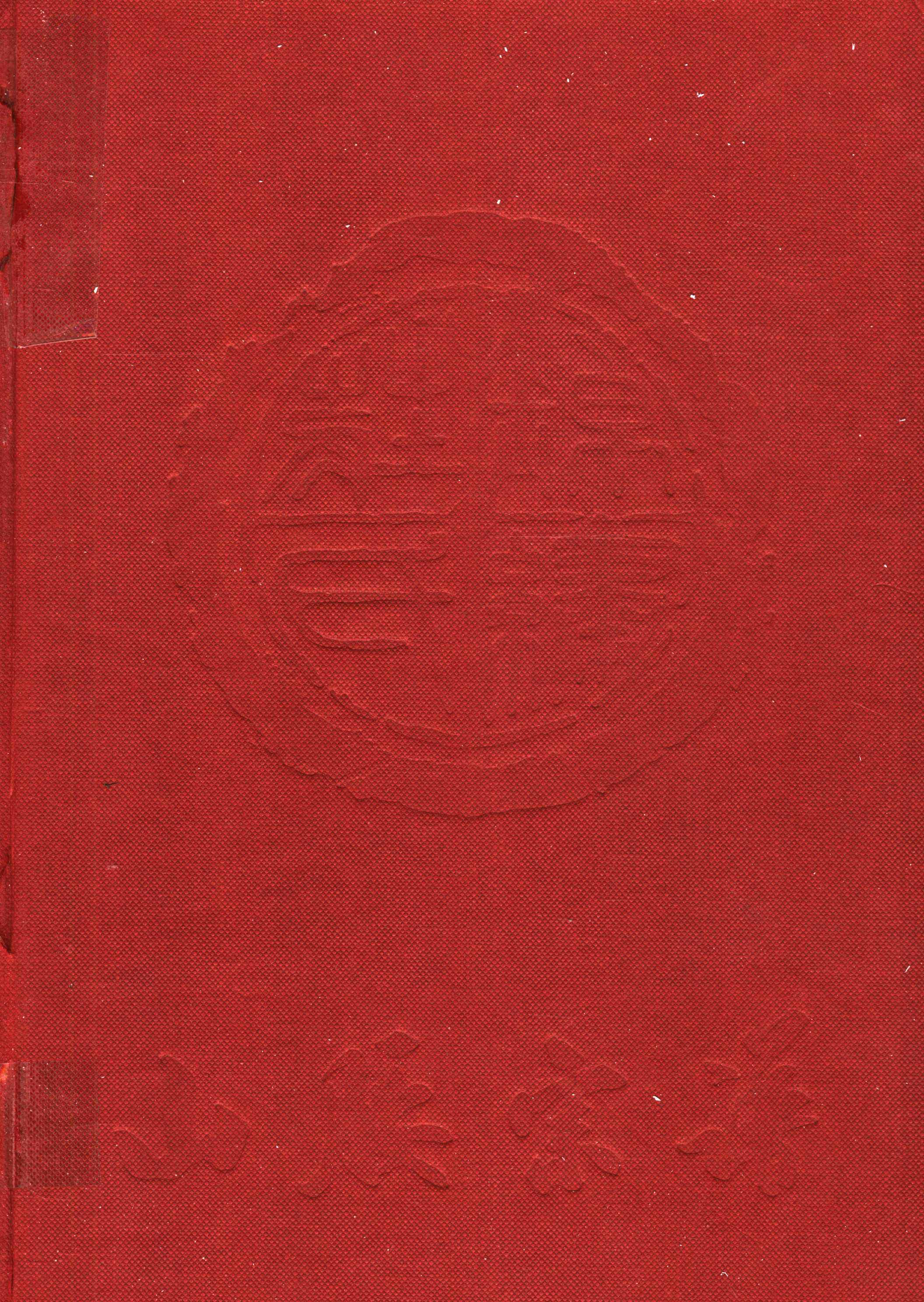第十二章 结语与思考
| 内容出处: | 《福建族谱》 图书 |
| 唯一号: | 131020020210010867 |
| 颗粒名称: | 第十二章 结语与思考 |
| 分类号: | K820.9 |
| 页数: | 9 |
| 页码: | 325-333 |
| 摘要: | 通过考察福建族谱的演化过程及其社会特征,我们似可得出以下基本结论。换言之,理念与实际是不相吻合的。而这种不相吻合的状况,随着宋元以来福建民间修纂族谱的不断发展,呈现出有所加剧的趋向。特别是清代以来,福建族谱中塑祖造神、联宗合流的现象大量出现,促使许多族谱突破家族的界限,而走向社会化的联络。强调以纯洁血缘传承为核心的原则,是凝聚家族内部团结的必不可少的联系纽带;而族谱的塑祖造神、联宗合流又是扩大家族影响,加强家族与社会联系的必然产物。福建的族规,无论是大型的宗谱或是小型的简易族谱,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大环境下的产物。 |
| 关键词: | 福建省 族谱 演化过程 |
内容
通过考察福建族谱的演化过程及其社会特征,我们似可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一、族谱作为中国家族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所标榜的敬宗收族和以纯洁血缘传承为核心的修纂原则,与族谱修纂的具体操作实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换言之,理念与实际是不相吻合的。而这种不相吻合的状况,随着宋元以来福建民间修纂族谱的不断发展,呈现出有所加剧的趋向。特别是清代以来,福建族谱中塑祖造神、联宗合流的现象大量出现,促使许多族谱突破家族的界限,而走向社会化的联络。
强调以纯洁血缘传承为核心的原则,是凝聚家族内部团结的必不可少的联系纽带;而族谱的塑祖造神、联宗合流又是扩大家族影响,加强家族与社会联系的必然产物。因此,原则与实际的不相吻合,不但未能导致福建家族制度的瓦解,相反地,成了维系明清以来福建家族社会正常运转与不断演进的两大要素,二者互为促进,相辅相成,共同推进明清以来福建家族制度的扩展,以及以家族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民间基层社会组织联系的加强。从而使家族制度能够不断适应时代的变化,历久不衰。尤其是在近百年来激烈的社会变迁中,家族制度几经挫折,往往死灰复燃,似乎具有跨时代的生命魅力,值得深思。
虽然福建族谱修纂中原则与实际的相互背离与相辅相成的特征表现得较为明显,但从文化继承的角度上看,这种特征实际上是中国文化实质、政治制度在族谱修纂中的一种折射而已。我们的祖先们、圣贤们,很早就为中国社会的演进创造了一整套近乎完善的文化观念、道德标准和标榜“爱民勤政”的政治官僚制度。 但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儒家道德标准与政治腐败的现实总是相依相伴、难分难解,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种道德标准的完善与社会政治的背离和相互配合,维系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长期延续。
二、就一般情景而言,福建各家族族谱的修纂,越是煞有其事,规模堂皇,长篇累卷,联宗合谱,其中假冒的现象就越严重。而那些弱族微房、贫民小姓修纂的族谱,由于受经济条件、社会地位和文化修养的限制,往往比较切乎家族的真实历史。福建 《梁氏合修族谱》载清同治年间徐伯舫夫子的修谱议论,颇道出了福建民间修纂族谱的这一事实:令族修谱,恐先代失稽,寄函请裁,可谓办事认真。然考之往牒,不一例。有称宗谱者,合天下同姓而联之于一本。由近溯远,由亲及疏,条分缕析,此最繁重。究不能考核真实,亦惟是附会牵合、夸张门户而已。有称族谱者,则就本族支祖以来,系其世次,序其长幼,别其尊卑,此欧阳文忠公、苏文忠公始创谱法也。若家谱则仅及三世、五世而止,此朱子、程子家礼遗意也。鄙见广修宗谱则太繁,其失也诬;仅修家谱則太简,其失也略。谱事当从欧、苏为是,法良意美。令族在闽浦历年既久,子孙亦蒸蒸繁衍,则自修为一族合修族谱,义亦至当。古人固有以大宗祖为始祖者,亦有以世祖中之显达者为始祖,如孔孟颜曾诸大族,各宗先圣先贤是也;如王之祖太原,郭之祖汾阳,即贵族之祖安定皆是也。至论族谱之例,则当以本支始迁之祖为始祖,始祖以上世次中有迁居别处者,来则合之,不来则于迁去名下注明迁居某处,故绝者亦据实真书,其他或传闻未确、征信无凭者,但系其名于本支之下,注云:后嗣未详,缺疑俟考。此欧、苏所定谱例也。故欧公著谱,自始祖议下及其身仅十五世,中间阙者二代;苏公族谱,则始祖以下世次皆疑,存疑,惟最近三代支派详明。二公皆前代名儒,所著谱法如是,必有卓见巨识,可法后世。今之修谱者,莫不自为取法,冒虚名而失真意,往往师心自用,不能系者牵强系之,不能合者附会合之。是谓自诬其祖,合族转为乱族。[1]不仅如此,那些小型简易族谱与大型宗谱相比较,各自所标榜的修谱原则和约束族人的家法、族规也不尽相同。大休言之,小型族谱所制定的家法、族规等原则,比较接近于家族及基层社会的实际问题,而大型宗谱等所制定的规条,则往往沦为空泛教条。这里试举泉州《新榜吴氏家谱》的《黄龙族规》和汀州邱、吴等家族族谱的族规为例,做一比较。
《新榜吴氏家谱》仅有一册,为清末民初手写本,现藏泉州市历史研究会资料室,家谱中所载《黄龙族规》如下:一、吾族一片平原,前人遍植荔枝,正为祖宗坟茔、子孙庐舍,树其屏藩。各乡无碍隙地,未栽者不妨多栽,既栽之后,不许擅自砍伐,若擅自砍伐,将红柴充公,本人押到 祠戒饬,斫工议罚。或因起盖厝宅,宜先报绅董蹈勘,果于厝场有碍,始听掘起再栽,若有不肖绅耆,受树主私贿,许其斫伐,察出重罚,终身不准入祠。而祖宗亦阴谴之。
一、孝悌为人伦之本,凡忤逆不孝,殴兄辱嫂者,人人得而诛之,不准入祠,而为兄当友其弟,为嫂宜和妯娌,不得恃长横恣。
一、淫乱为万恶之首,或有子蒸父妾,叔乱侄妇,侄奸叔母,兄收弟妇,弟纳兄妻者,是为乱伦,宜绝其嗣,亲服中罪加三等。
一、耆老为乡里表率,不但有齿,还须有德,德之一字,最无限量,但为房长为乡长,均当约束子侄,使子侄循分安业,便是乡房长之德。若子侄不遵约束,可听绅耆处置;若党子侄为恶,行事不正经,便不成人,与未成丁者,概不列为五老。
一、吾宗聚族而居,当念一本之亲,笃宗族以昭雍睦,不可因微嫌细故,顿起争端。有以横逆相加者,登投绅耆理论,毋速我讼。亦不得划毁五谷果木夺牛破屋等情,违者以犯族规公罚。
一、族人有能教督子孙,由科举学堂出仕者,身后从祀功德龛。若孝于亲,友于兄弟,修祖宗祠墓谱牒,以及一切公益义举,卓有声绩,亦准入祠,诸绅衿着为之报官请旌,以示鼓励。
一、妇人不幸夫死,不得借招夫养子之名,坏乱伦纪。若甘心守节,女德委实可嘉者,诸绅衿着为之请旌,采入谱牒, 以垂不朽。
在这则族规里,所涉及的内容不外是家族内部的尊卑长幼、和睦相处以及坟茔庐舍祠堂管理的实际问题,从这些内容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吴氏家族对于家族内部事务的具体操作规范,同时还可以了解到在清末民初的泉州地方,尚残存诸如“弟收兄妇”等等的古代收继婚遗俗。这些资料对于研究清末民初时期福建的民间基层社会,弥足珍贵。反观邱、吴等大型族谱的族规记载,情景就大不一样。他们引用“朱子箴铭八字”来制定家训、族规,[2]兹抄引邱氏家族的八字族训如下:孝,竹有孝笋,鸟有慈鸟,人灵于物,尚其省诸!养志于微,养体于著,和气蛇容,无间朝暮。
弟,为兄则友,为弟则恭,友恭之风,家道其隆。梨枣推让,枕被与其,王粲王祥,百禄是总。
忠,忠臣不二,志在致君。忠士无邪,信以与人。尽己之心,竭己之力,仰不愧天,攸往咸吉。
信,有言必践,信在言前,信近于义,行则罔愆。循物无违,以实之谓,感及豚鱼,配义者气。
礼,雍雍在宫,肃肃在庙,能敬与和,道其神妙。先王 制礼,小大由之,诗人所戒,相鼠茅鸥。
义,行事合宜,是之谓义。贫者廉贞,富者行济。行则相助,居则相亲,仁心义质,可以成人。
廉,何以为廉,曰有分辨。乐羊拾遗,为妻所贱,绳枢〓牖,原宪不忧,凡百君子,知命何求。
耻,圣贤教人,惟耻为大,屋漏神明,无欺则泰。秉无三惑,震有四知,中夜怵惕,可以为师。[3]通篇族训,皆为儒家口吻。虽然十分堂皇,但实际是空洞无物,不着边际。
福建的族规,无论是大型的宗谱或是小型的简易族谱,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大环境下的产物。但由于地区性的差别和各个具体家族的不同情况,不同地区的各个家族及其族谱所受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程度应当有所不同。从上引的两则族规中可以看出,那些小型族谱的修谱理念和操作原则,可能比较朴实无华,比较关注于家族及其周围社会的具体问题,它所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相对少些,更富有个案上的特点。而那些大型的宗谱,修撰者大多为地方士绅等读书人,族规中所标榜的规范原则与中国传统文化所标榜的伦理道德标准,差别较少,如出一辙。这样也就逐渐淹没了作为单独家族的个性文化特点。必须指出的是,这里所讲的个性淹没,仅仅是指口号原则而已,实际上,族谱中的口号原则越是响亮,越是与儒家“孝悌仁义、崇功报德”的口号相吻合,族谱的造假成份可能越多。回到原先的话题:原则与实际是相互背离而又相辅相成的。
三、从整体上讲,福建的家族制度和族谱文化与全国其他地区基本相同。但由于福建家族的形成和发展历史与其他地区不尽相同,门第相高、讲求实力、强欺弱、众暴寡的现象长期存在于福建民间家族社会里。[4]由此而形成的族谱文化,同样更具有夸张和炫耀的特点。这一点在我们前面所论述的粉饰族谱、塑祖造神和渊源合流等等方面得到了充分的证实。讲求家族实力、强欺弱、众暴寡的福建家族社会与夸张炫耀的族谱文化的相互结合,不能不对福建地区的家族心理和人文性格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比如,长期的移民开发造就了福建特别是沿海地区家族和人民富有开拓冒险进取的性格,从唐宋以来的海内外贸易,到明清时期私人海上走私活动和海盗行为,以至清代以来大量人口的海外移民和开发台湾,都充分地体现了福建沿海人民的这种冒险进取的开拓精神。 但从另一方面看,福建人的地域观念、集团宗派观念,以及闻名全国的家族械斗、乡族械斗、地域械斗(如客家人与非客家人的械斗,台湾称为分类械斗),这些都是不容否认的存在事实。而这 种家族心理和人文性格,无疑是与福建的家族社会和族谱文化的 相互结合,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反观闽北地区的族谱,夸张炫耀的成份相对少些,这一带割据对抗的家族心理相对淡薄,人文性格也比较淳朴、保守,这二者的差别也是值得重视的。
从史学研究的现状看,由于数十年来学者比较重视于生产关系的研究,人们一贯忽略了对不同地区不同社会氛围之间的人文性格的研究。笔者认为,不同地区、不同社会间的人文性格差别是实际存在的,因而也是不能忽视的。就整体而言,全国各地都奉行同样的文化观念和道德标准,都遵守着共同的政治制度,但福建与其他省份相比,福建沿海地区与闽北地区、客家地区相比,甚至于漳州与泉州、福州与兴化等更小范围内的地区相比,都或多或少存在着某些人文格的差别。这种差别虽然不能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结构,但区域性的差别,不仅体现了区域间的不同特点,同时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结构增添了更加斑烂多样的色彩。四、最后,我们还要郑重指岀的是,虽然福建族谱存在着原 则与实际不相吻合、假造冒托、夸张炫耀等等方面的显著特点,但这并不影响福建族谱的整体学术价值。因为我们对于族谱的考察和运用,不应当局限在单一的角度,而是应当进行多学科、多角度的综合考察。比如,族谱中对于祖先史实的假造冒托,这本来 是传统史学研究中最为忌讳的问题,但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族谱中的这种现象,恰好是证实家族组织及其制度实质的不可多得 的资料。有的同志指出,谱牒学的外延应该是从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民族学、考古学、民俗学、宗教学、法学、教育学、经济学、伦理学、人才学、遗传学等众多学科的视角出发, 对中国家谱作综合地、主体地、全面地研究。[5]这种看法是正确的。
我们打开了考察和运用族谱的视野,族谱的重大学术价值也就丰富多姿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它不仅为宗法制度、家族社会 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第一手资料,而且还对经济史、人口史、教育史、民族史、民俗史、宗教史、华侨史、妇女史等诸多方面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它所蕴藏的取之不竭的资料,有待于学人们的深入发掘。
然而,我们并不能因为族谱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而忽视对于族谱资料的鉴别取舍。因为族谱毕竟是私家所记,不受任何社会和公众约束,主观随意性很大。因此,我们在运用族谱资料时,应当实事求是,有所鉴别,有所选择。那种随意摘取族谱中的某些人物或历史事件的记载,不顾其余,动辄有“新观点”、 “新发现”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也是不严肃的。史学前辈谭其谭在运用谱牒研究湖南移民史时指岀:“谱牒之不可靠者,官阶也, 爵秩也,帝王作之祖,名人作之宗也。而内地移民史所需求于谱牒者,则并不在乎此,在乎其族姓之何时自何地转徙而来,…… 故谱牒不可靠,然惟此种材料,则为可靠也。”[6]谭先生对于运用谱牒资料的审慎态度,是值得钦佩和效法的。
如何正确而又高效地运用族谱资料,这本身就是一门严肃而又高深的学问,需要有志的学人们去努力开拓,不断进取。但是,始终如一地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审慎的科学态度,却是学人们的共同追求。笔者祝愿在有志学人们的不懈努力下,福建族谱乃至中国族谱、中国传统社会的研究,健康发展、硕果累累。
一、族谱作为中国家族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所标榜的敬宗收族和以纯洁血缘传承为核心的修纂原则,与族谱修纂的具体操作实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换言之,理念与实际是不相吻合的。而这种不相吻合的状况,随着宋元以来福建民间修纂族谱的不断发展,呈现出有所加剧的趋向。特别是清代以来,福建族谱中塑祖造神、联宗合流的现象大量出现,促使许多族谱突破家族的界限,而走向社会化的联络。
强调以纯洁血缘传承为核心的原则,是凝聚家族内部团结的必不可少的联系纽带;而族谱的塑祖造神、联宗合流又是扩大家族影响,加强家族与社会联系的必然产物。因此,原则与实际的不相吻合,不但未能导致福建家族制度的瓦解,相反地,成了维系明清以来福建家族社会正常运转与不断演进的两大要素,二者互为促进,相辅相成,共同推进明清以来福建家族制度的扩展,以及以家族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民间基层社会组织联系的加强。从而使家族制度能够不断适应时代的变化,历久不衰。尤其是在近百年来激烈的社会变迁中,家族制度几经挫折,往往死灰复燃,似乎具有跨时代的生命魅力,值得深思。
虽然福建族谱修纂中原则与实际的相互背离与相辅相成的特征表现得较为明显,但从文化继承的角度上看,这种特征实际上是中国文化实质、政治制度在族谱修纂中的一种折射而已。我们的祖先们、圣贤们,很早就为中国社会的演进创造了一整套近乎完善的文化观念、道德标准和标榜“爱民勤政”的政治官僚制度。 但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儒家道德标准与政治腐败的现实总是相依相伴、难分难解,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种道德标准的完善与社会政治的背离和相互配合,维系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长期延续。
二、就一般情景而言,福建各家族族谱的修纂,越是煞有其事,规模堂皇,长篇累卷,联宗合谱,其中假冒的现象就越严重。而那些弱族微房、贫民小姓修纂的族谱,由于受经济条件、社会地位和文化修养的限制,往往比较切乎家族的真实历史。福建 《梁氏合修族谱》载清同治年间徐伯舫夫子的修谱议论,颇道出了福建民间修纂族谱的这一事实:令族修谱,恐先代失稽,寄函请裁,可谓办事认真。然考之往牒,不一例。有称宗谱者,合天下同姓而联之于一本。由近溯远,由亲及疏,条分缕析,此最繁重。究不能考核真实,亦惟是附会牵合、夸张门户而已。有称族谱者,则就本族支祖以来,系其世次,序其长幼,别其尊卑,此欧阳文忠公、苏文忠公始创谱法也。若家谱则仅及三世、五世而止,此朱子、程子家礼遗意也。鄙见广修宗谱则太繁,其失也诬;仅修家谱則太简,其失也略。谱事当从欧、苏为是,法良意美。令族在闽浦历年既久,子孙亦蒸蒸繁衍,则自修为一族合修族谱,义亦至当。古人固有以大宗祖为始祖者,亦有以世祖中之显达者为始祖,如孔孟颜曾诸大族,各宗先圣先贤是也;如王之祖太原,郭之祖汾阳,即贵族之祖安定皆是也。至论族谱之例,则当以本支始迁之祖为始祖,始祖以上世次中有迁居别处者,来则合之,不来则于迁去名下注明迁居某处,故绝者亦据实真书,其他或传闻未确、征信无凭者,但系其名于本支之下,注云:后嗣未详,缺疑俟考。此欧、苏所定谱例也。故欧公著谱,自始祖议下及其身仅十五世,中间阙者二代;苏公族谱,则始祖以下世次皆疑,存疑,惟最近三代支派详明。二公皆前代名儒,所著谱法如是,必有卓见巨识,可法后世。今之修谱者,莫不自为取法,冒虚名而失真意,往往师心自用,不能系者牵强系之,不能合者附会合之。是谓自诬其祖,合族转为乱族。[1]不仅如此,那些小型简易族谱与大型宗谱相比较,各自所标榜的修谱原则和约束族人的家法、族规也不尽相同。大休言之,小型族谱所制定的家法、族规等原则,比较接近于家族及基层社会的实际问题,而大型宗谱等所制定的规条,则往往沦为空泛教条。这里试举泉州《新榜吴氏家谱》的《黄龙族规》和汀州邱、吴等家族族谱的族规为例,做一比较。
《新榜吴氏家谱》仅有一册,为清末民初手写本,现藏泉州市历史研究会资料室,家谱中所载《黄龙族规》如下:一、吾族一片平原,前人遍植荔枝,正为祖宗坟茔、子孙庐舍,树其屏藩。各乡无碍隙地,未栽者不妨多栽,既栽之后,不许擅自砍伐,若擅自砍伐,将红柴充公,本人押到 祠戒饬,斫工议罚。或因起盖厝宅,宜先报绅董蹈勘,果于厝场有碍,始听掘起再栽,若有不肖绅耆,受树主私贿,许其斫伐,察出重罚,终身不准入祠。而祖宗亦阴谴之。
一、孝悌为人伦之本,凡忤逆不孝,殴兄辱嫂者,人人得而诛之,不准入祠,而为兄当友其弟,为嫂宜和妯娌,不得恃长横恣。
一、淫乱为万恶之首,或有子蒸父妾,叔乱侄妇,侄奸叔母,兄收弟妇,弟纳兄妻者,是为乱伦,宜绝其嗣,亲服中罪加三等。
一、耆老为乡里表率,不但有齿,还须有德,德之一字,最无限量,但为房长为乡长,均当约束子侄,使子侄循分安业,便是乡房长之德。若子侄不遵约束,可听绅耆处置;若党子侄为恶,行事不正经,便不成人,与未成丁者,概不列为五老。
一、吾宗聚族而居,当念一本之亲,笃宗族以昭雍睦,不可因微嫌细故,顿起争端。有以横逆相加者,登投绅耆理论,毋速我讼。亦不得划毁五谷果木夺牛破屋等情,违者以犯族规公罚。
一、族人有能教督子孙,由科举学堂出仕者,身后从祀功德龛。若孝于亲,友于兄弟,修祖宗祠墓谱牒,以及一切公益义举,卓有声绩,亦准入祠,诸绅衿着为之报官请旌,以示鼓励。
一、妇人不幸夫死,不得借招夫养子之名,坏乱伦纪。若甘心守节,女德委实可嘉者,诸绅衿着为之请旌,采入谱牒, 以垂不朽。
在这则族规里,所涉及的内容不外是家族内部的尊卑长幼、和睦相处以及坟茔庐舍祠堂管理的实际问题,从这些内容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吴氏家族对于家族内部事务的具体操作规范,同时还可以了解到在清末民初的泉州地方,尚残存诸如“弟收兄妇”等等的古代收继婚遗俗。这些资料对于研究清末民初时期福建的民间基层社会,弥足珍贵。反观邱、吴等大型族谱的族规记载,情景就大不一样。他们引用“朱子箴铭八字”来制定家训、族规,[2]兹抄引邱氏家族的八字族训如下:孝,竹有孝笋,鸟有慈鸟,人灵于物,尚其省诸!养志于微,养体于著,和气蛇容,无间朝暮。
弟,为兄则友,为弟则恭,友恭之风,家道其隆。梨枣推让,枕被与其,王粲王祥,百禄是总。
忠,忠臣不二,志在致君。忠士无邪,信以与人。尽己之心,竭己之力,仰不愧天,攸往咸吉。
信,有言必践,信在言前,信近于义,行则罔愆。循物无违,以实之谓,感及豚鱼,配义者气。
礼,雍雍在宫,肃肃在庙,能敬与和,道其神妙。先王 制礼,小大由之,诗人所戒,相鼠茅鸥。
义,行事合宜,是之谓义。贫者廉贞,富者行济。行则相助,居则相亲,仁心义质,可以成人。
廉,何以为廉,曰有分辨。乐羊拾遗,为妻所贱,绳枢〓牖,原宪不忧,凡百君子,知命何求。
耻,圣贤教人,惟耻为大,屋漏神明,无欺则泰。秉无三惑,震有四知,中夜怵惕,可以为师。[3]通篇族训,皆为儒家口吻。虽然十分堂皇,但实际是空洞无物,不着边际。
福建的族规,无论是大型的宗谱或是小型的简易族谱,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大环境下的产物。但由于地区性的差别和各个具体家族的不同情况,不同地区的各个家族及其族谱所受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程度应当有所不同。从上引的两则族规中可以看出,那些小型族谱的修谱理念和操作原则,可能比较朴实无华,比较关注于家族及其周围社会的具体问题,它所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相对少些,更富有个案上的特点。而那些大型的宗谱,修撰者大多为地方士绅等读书人,族规中所标榜的规范原则与中国传统文化所标榜的伦理道德标准,差别较少,如出一辙。这样也就逐渐淹没了作为单独家族的个性文化特点。必须指出的是,这里所讲的个性淹没,仅仅是指口号原则而已,实际上,族谱中的口号原则越是响亮,越是与儒家“孝悌仁义、崇功报德”的口号相吻合,族谱的造假成份可能越多。回到原先的话题:原则与实际是相互背离而又相辅相成的。
三、从整体上讲,福建的家族制度和族谱文化与全国其他地区基本相同。但由于福建家族的形成和发展历史与其他地区不尽相同,门第相高、讲求实力、强欺弱、众暴寡的现象长期存在于福建民间家族社会里。[4]由此而形成的族谱文化,同样更具有夸张和炫耀的特点。这一点在我们前面所论述的粉饰族谱、塑祖造神和渊源合流等等方面得到了充分的证实。讲求家族实力、强欺弱、众暴寡的福建家族社会与夸张炫耀的族谱文化的相互结合,不能不对福建地区的家族心理和人文性格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比如,长期的移民开发造就了福建特别是沿海地区家族和人民富有开拓冒险进取的性格,从唐宋以来的海内外贸易,到明清时期私人海上走私活动和海盗行为,以至清代以来大量人口的海外移民和开发台湾,都充分地体现了福建沿海人民的这种冒险进取的开拓精神。 但从另一方面看,福建人的地域观念、集团宗派观念,以及闻名全国的家族械斗、乡族械斗、地域械斗(如客家人与非客家人的械斗,台湾称为分类械斗),这些都是不容否认的存在事实。而这 种家族心理和人文性格,无疑是与福建的家族社会和族谱文化的 相互结合,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反观闽北地区的族谱,夸张炫耀的成份相对少些,这一带割据对抗的家族心理相对淡薄,人文性格也比较淳朴、保守,这二者的差别也是值得重视的。
从史学研究的现状看,由于数十年来学者比较重视于生产关系的研究,人们一贯忽略了对不同地区不同社会氛围之间的人文性格的研究。笔者认为,不同地区、不同社会间的人文性格差别是实际存在的,因而也是不能忽视的。就整体而言,全国各地都奉行同样的文化观念和道德标准,都遵守着共同的政治制度,但福建与其他省份相比,福建沿海地区与闽北地区、客家地区相比,甚至于漳州与泉州、福州与兴化等更小范围内的地区相比,都或多或少存在着某些人文格的差别。这种差别虽然不能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结构,但区域性的差别,不仅体现了区域间的不同特点,同时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结构增添了更加斑烂多样的色彩。四、最后,我们还要郑重指岀的是,虽然福建族谱存在着原 则与实际不相吻合、假造冒托、夸张炫耀等等方面的显著特点,但这并不影响福建族谱的整体学术价值。因为我们对于族谱的考察和运用,不应当局限在单一的角度,而是应当进行多学科、多角度的综合考察。比如,族谱中对于祖先史实的假造冒托,这本来 是传统史学研究中最为忌讳的问题,但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族谱中的这种现象,恰好是证实家族组织及其制度实质的不可多得 的资料。有的同志指出,谱牒学的外延应该是从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民族学、考古学、民俗学、宗教学、法学、教育学、经济学、伦理学、人才学、遗传学等众多学科的视角出发, 对中国家谱作综合地、主体地、全面地研究。[5]这种看法是正确的。
我们打开了考察和运用族谱的视野,族谱的重大学术价值也就丰富多姿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它不仅为宗法制度、家族社会 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第一手资料,而且还对经济史、人口史、教育史、民族史、民俗史、宗教史、华侨史、妇女史等诸多方面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它所蕴藏的取之不竭的资料,有待于学人们的深入发掘。
然而,我们并不能因为族谱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而忽视对于族谱资料的鉴别取舍。因为族谱毕竟是私家所记,不受任何社会和公众约束,主观随意性很大。因此,我们在运用族谱资料时,应当实事求是,有所鉴别,有所选择。那种随意摘取族谱中的某些人物或历史事件的记载,不顾其余,动辄有“新观点”、 “新发现”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也是不严肃的。史学前辈谭其谭在运用谱牒研究湖南移民史时指岀:“谱牒之不可靠者,官阶也, 爵秩也,帝王作之祖,名人作之宗也。而内地移民史所需求于谱牒者,则并不在乎此,在乎其族姓之何时自何地转徙而来,…… 故谱牒不可靠,然惟此种材料,则为可靠也。”[6]谭先生对于运用谱牒资料的审慎态度,是值得钦佩和效法的。
如何正确而又高效地运用族谱资料,这本身就是一门严肃而又高深的学问,需要有志的学人们去努力开拓,不断进取。但是,始终如一地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审慎的科学态度,却是学人们的共同追求。笔者祝愿在有志学人们的不懈努力下,福建族谱乃至中国族谱、中国传统社会的研究,健康发展、硕果累累。
附注
注释:[1]《梁氏合修族谱》卷之一,《徐伯舫夫子覆函文》。
[2]闽西《渤海吴氏族谱》卷之首,《家训》。
[3]上杭《丘氏族谱》卷一,《族训》。
[4]参见拙著《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第一章,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 年5月版。
[5] 参见欧阳宗书:《中国家谱》第136页,新华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6] 谭其骧先生的原文载燕京大学《史学年报》第四期,转引自罗香林《客家源流考》三,《注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