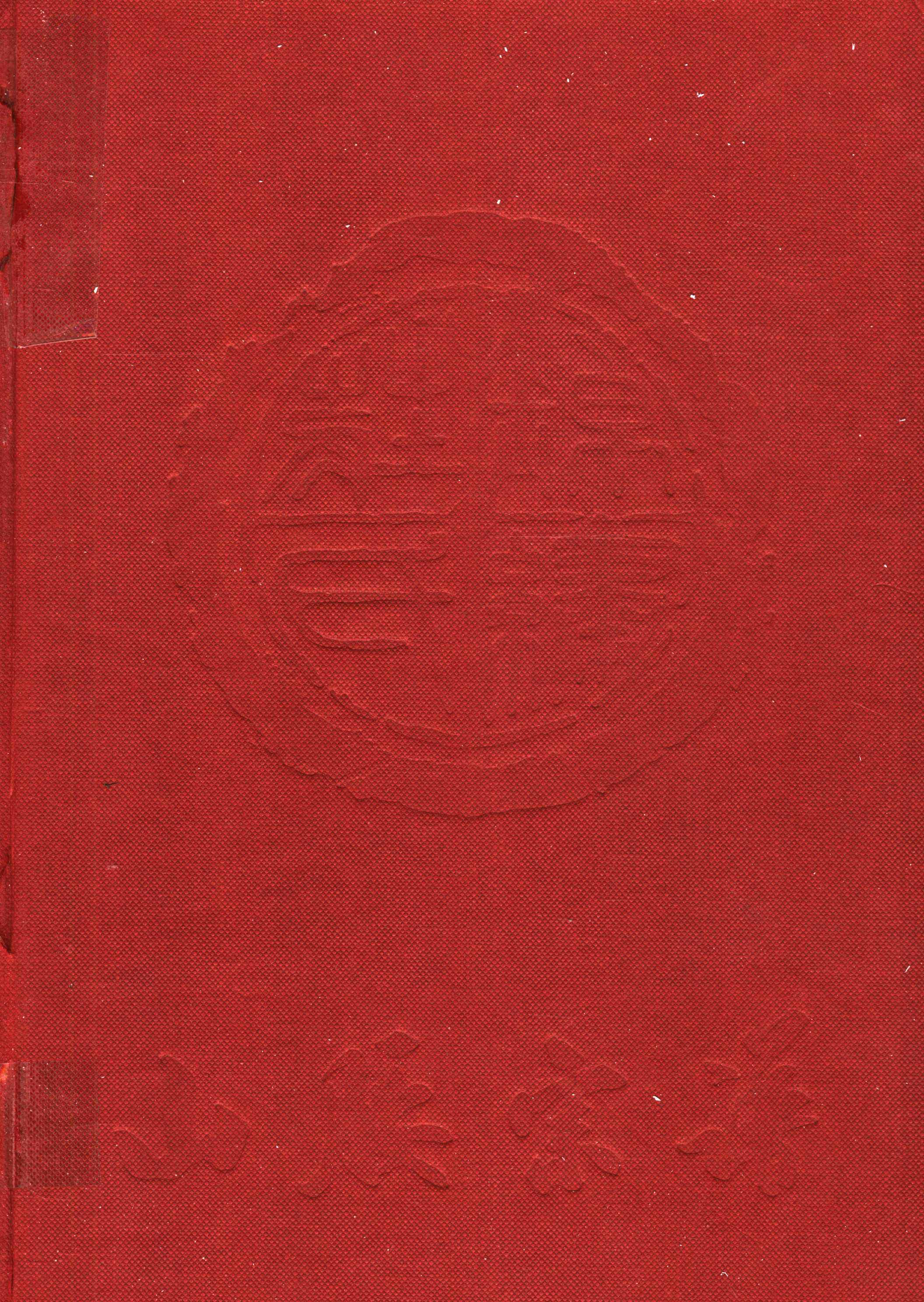第四章 原则的训诫与标榜
| 内容出处: | 《福建族谱》 图书 |
| 唯一号: | 131020020210010847 |
| 颗粒名称: | 第四章 原则的训诫与标榜 |
| 分类号: | K820.9 |
| 页数: | 17 |
| 页码: | 52-69 |
| 摘要: | 福建民间家族修撰族谱的基本原则,主要是通过族规和修谱凡例体现出来。虽然福建各家族的族规和修谱凡例不尽相同,但这些族规和修谱凡例所共同强调的一个核心精神,就是敬宗收族和慎终追远。它一方面注重血亲传统的纯洁性与传承性,另一方面则通过这种血亲传统的追寻,达到联络族众、壮大宗族势力的现实目的。福建民间家族的族规、家法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且各个家族所制定的族规、家法内容不一、形式多样,但其中有一点却是必不可少,具有普遍性的,那就是强调孝祖先、重续嗣、睦宗族。人之百行,莫大于孝,家庭中有善事父母,克供子职者理合褒嘉,呈请给匾,以旌孝行。今与子姓约尚敬礼之,毋或敢忽。凡我族人尚笃亲亲之谊,方不愧为望族。 |
| 关键词: | 福建省 族谱 训诫 |
内容
福建民间家族修撰族谱的基本原则,主要是通过族规和修谱凡例体现出来。虽然福建各家族的族规和修谱凡例不尽相同,但这些族规和修谱凡例所共同强调的一个核心精神,就是敬宗收族和慎终追远。它一方面注重血亲传统的纯洁性与传承性,另一方面则通过这种血亲传统的追寻,达到联络族众、壮大宗族势力的现实目的。
福建民间家族的族规、家法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且各个家族所制定的族规、家法内容不一、形式多样,但其中有一点却是必不可少,具有普遍性的,那就是强调孝祖先、重续嗣、睦宗族。这里,试举连城《文川李氏七修族谱》所载的宗规训戒为例:祖训一训孝顺父母。人之百行,莫大于孝,家庭中有善事父母,克供子职者理合褒嘉,呈请给匾,以旌孝行。一训敬老尊贤。高年硕望,模范具焉,国家且有优待之典,族姓可无推崇之文?今与子姓约尚敬礼之,毋或敢忽。
一训和睦亲族。子姓蕃衍皆祖宗一脉分形之人,忍膜外视乎?凡我族人尚笃亲亲之谊,方不愧为望族。
一训勤读诗书。报国荣亲,诗书之泽甚大。凡我子姓有志诵读者,品行文章着力砥励,或列黉序或掇巍科,非特宗祖有光,亦副族人之望。
一训诚实正业。农工商贾各有专业,敦本务实乃克有成。凡我子姓宜执其业,实其职者方为克家令嗣。
一训早完钱粮。钱粮为惟正之供,输纳实臣民之分,凡我族人宜各早完,毋累亲族。
族戒一戒不孝不友。五伦之大,孝友为先,倘明发有亏天显罔念,甚不足挂齿,维我众人定以不孝不友之罪罪之。
一戒挖卖祖坟。宅兆安厝,祖先之灵爽所栖也,俗有不肖之徒以卖坟墓为生涯,忍心害理,莫此为甚。倘子姓蹈此恶习,众削其图谱,呈官重惩,永不许入祠与祭。
一戒为匪乱伦。淫乱一事,律载五刑,况灭伦坏纪,尤禽兽不如。子姓倘犯此禁,削其图谱,拒其与祭,家法所在!决无轻纵。
一戒承充隶卒。隶卒世所共耻,以是人而列谱系与祠祭, 岂不玷祖宗而坏家风,倘有误践者,宜亲房令从正业,如固执迷,图谱槟黜。
一戒欺祖霸尝。祖宗尝田,完粮办祭所从出也。如有抗欠、借端欺霸以致祭祀不敷、钱粮贻累,情同悖祖,众共攻之。
一戒酗酒打架。家燕合欢,礼法所在。若酒酣耳热攘臂逞凶,乱我笾豆,礼法奚存?长少虽异,均当惩戒。[1]上引文川李氏家族训戒共有十二条,除了 “勤读诗书”,“诚实正业”,“早完钱粮”这三条是强调族人各安其业、为族争光之外,其余的九条,都是劝戒族人必须孝敬为先,和宗睦族,这也就是通常所讲的“敬宗收族”。这种情况不仅仅是李氏家族如此,福建民间其他家族所制定的族规、家范一类,大体上也是以“敬祖宗”、 “重宗长”、“禁犯上”、“睦宗党”、“重师友”、“重继嗣”、“重血脉”、“安灵墓”、“凛国教”、“恤患难”、“急相助”、“禁欺凌”、 “禁乱伦”、“禁争讼”、“惩小忿”等为主要内容。这些“敬宗”、 “收族”的族规内容,构成了家族内部团结和维系宗族延继不断的两大要素。而这两大要素,又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的基础上,抛弃了血缘关系上的尊卑次序观念,所有的家族组织和制度便无从讲起。正因为如此,慎终追远、水源木本便成了福建各地家族族谱所要努力体现的精神典范。许多家族的族谱都强调“敬祖宗而明绪体,辨昭穆而明亲疏,不为不重”,[2]“夫自一人之身分而至于千百人之身,由一人之世传而至千百年之世,……人不忘祖宗也,使人不弃宗族”,[3]“祖宗功德之流泽长矣,夫人道之大在亲亲,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族谱)列时代之后先,以考氏族之真伪,俾后嗣子孙得了然于寸楮间,斯诚仁人孝子之用心乎! ”[4]如果说族规、家范中所强调的“敬宗”、“收族”精神只是福建各家族修撰族谱时的指导原则,那么各家族所制定的“修谱凡例”则是这种指导原则的具体化表现。我们先来看看泉州《蓬岛郭氏家谱》所载的修谱凡例。泉州蓬岛郭氏家族开基于南宋时,到民国时期已繁衍二十余代,族众达万余人。该族首修族谱于明末崇祯年间,清朝嘉庆年间再次重修,至光绪庚寅年(公元1890年)由举人郭大彬及郭崇勋三修,延至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由郭治懋、郭朝麟等主持四修。该家族在首修族谱时,已经制定了修谱凡例,在二修时进行补充,修谱凡例已达二十一条之多,这二十一条谱例被称为“旧例”,兹摘录如下:…… 一谱系以宗派为重,最宜详慎。凡为人后者,于本生父母之名下必书,重所生也,旁注出嗣与某人为后,著其实也。至为所后者则书曰嗣子某,正名以定其志也。或随母嫁出及为他姓子者,削不书,不以混宗派也。其已殁者不议也。至螟蛉之子例宜注养字,著其别,以戒将来。第吾族抱养之人难以查明,姑就其名下载之,宽既往也。
一妇人年三十以内守节,艰苦备尝,有子成立者俱宜表而出之。……一生卒年月必书,其有不书者阚不知也,娶某氏亦即书于本名之下。元配、附配、继妻,虽无子必书,记嫡体也。妾有子则书,重嗣续也。妻妾俱有子各著其所出,妾无子者不书。……一妇人夫死他适者,于夫名下系不书,示与庙绝也。记所生之子几人,注妣某氏岀者,示无母之子也。侧室他适者,虽有子不书。
一图考五世为一图,六世一提图,画以五本缀以一,乔梓纵,棣萼横,仿欧阳文忠公之例,分之各一太极,合之同一太极。按图考之了然,则心目以广稽世系之详明,则孝友以森,周穷恤孤、尊贤敬老之心至矣。
一始祖德昭公支派详明,昭穆不紊,因派开房,因房再辟各派,各条宗支嗣续世系名字生卒配葬科第事迹皆备焉。…….[5]从这些例条中可以看出,郭氏家族在修谱时十分重视血缘的纯洁性,举凡嫡出、别出,出嗣、过继以及改适等等,都进行了相应的规定,以保证家庭血缘不致混乱。至光绪庚寅十六年(公元1890 年)三修时,该家族又增立了十六条谱例。除了重申旧例的各条注意事项外,还特别对进一步维护血缘的纯洁性作了补充规定:一我族人众其出嗣者则书之曰某某出嗣,又书之曰嗣子某某,以示别也。而独此抱养之子未及详注,与亲生之子无异也。兹除从前不知外,及今现知者一概加以养字,庶不致有鱼诛之混。
一我姓族大丁多,贤愚不一,其有移花接柳者一概革归原配,以为整顿风俗起见,不得谓秉笔之过于苛也。[6]到了民国年间郭氏家族进行四修族谱时,再次对旧谱例进行修改, 并称之为“新谱例”。新谱例对各种收养、招赘关系虽略有变通,但对于修谱时的血缘认可依然是十分严格的。新谱例共有七条,依次如下:一私生子必不入谱,兹奉官令变通办法,另设附谱以示区别。其母生,削去娶字;死,削去妣字,子削去名字行,于名下书养字,此条仅限夫死之后适行之。
一夫死重赘本姓,字行同者,男削去字行,妇削娶为取,削妣为比。所生子书养字,而存其名字行。赘异姓夫者,夫不入谱,母子同此例。赘异姓妇者,予书养,父不削字行。其字行不同者,奉官令收入附谱,男削去名字行,妇削去娶妣, 所生之子与父同。惟赘夫若有正娶妻之子,则仍列正谱。
一娶本族妇,男妇书法与重赞者同例,惟所生之子准与普通无异。
一苗养幼媳经载前谱,迨后长大而改配其父之兄弟及族人者,妇于前夫名次下书改适,其后夫及妇书法无论如何,与娶本族妇字行相同者同例,惟所生之子得与普通无异,若前夫既完婚生子者不得援议。
一兄夺弟妇,弟占兄嫂,叔夺侄妇,侄占叔母,为牍伦伤化之极,义不入谱,令亦聊纪其生卒葬于附谱。
一定议以上五条断自光绪庚寅年(按:公元1890年)男妇尚在,或所生之子未卒者适行之。
一赘同姓之妇,旧谱有仍书在前夫之后者,有互相详略者,有于后夫之后空书娶氏生卒年月日时者。兹订概归前夫,其空书者悉删去之。惟赘生之子不论归夫归妇,旧谱概书养子,今亦概书养子,不复置议。[7]经过三次对谱例的增订,郭氏家族对于以血缘为核心的修谱规定可谓详尽。这种情况不仅郭氏家族如此,福建其他家族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奉行着这种以血缘为核心的旨在敬宗收族的修谱原则。特别是对于血缘混乱,继嗣不明的现象,尤为明禁。龙岩《谢氏族谱》在修谱凡例中强调“谱内承继为后,并无紊乱昭穆,亦无抱养他姓之子以及随母来之子,所以明世次锄非种也。……娼优隶卒例禁,后嗣不得与考。倘族中有此等不肖子侄,不特败坏家风,抑且害及子孙。一俟查出,公革不贷。”[8]建阳《麻沙刘氏族谱》的修谱条约规定:“螟蛉宜禁,以杜乱宗也。……吾族新修谱牒,螟蛉之子悉行削去,以警族人不继本宗,而继异姓者。倘再蹈此弊,必严行惩罚。”[9]浦城《渤海西吴宗谱》的《族禁》云: “禁非种承祧,非类之异种宜锄,不特抱养他族,明属篡宗,即为姑娣侧生,终非同姓。”[10]闽北《余氏宗谱》亦称“禁非种承祧,本是联枝,何用寄生之草;苟非艾乾,必除当道之兰。艰于嗣者每畏亲房得其家财,昧天理者,必喜外姓承其宗祧。私情易起,默地难欺。若或产出姑娣,未全非类;惟有抱血他族,乃属乱宗,祭不使与,谱亦宜差”。[11] 为了维护家族血缘世系的纯洁和高贵,福建许多家族在严禁血缘乱宗的同时,还规定族人必须立身有道,不得沦为奴仆娼优等贱民,不得从事低贱的行业。如闽西《吴氏族谱》规定“子姓有不孝不友,非为乱伦以及娼优隶卒有玷宗风者,不许编入谱内,并不许春秋与祭。……凡族人有潜养异姓人子以混宗支者,例不得录。有随母改适冒从他姓,及出继异姓为人后者,例应〓书。俟其还本归宗,再行补订。”[12]闽北《余氏宗谱》的族禁云:“士农工商皆君子立身之道,娼优隶卒乃人生不齿之徒,即使迫于饥寒、谋生乏术,亦应念及祖父,何容改节以贻羞。……名既有玷,谱岂容登?”[13]永安《余氏族谱》的《谱禁》云:“一禁委身贱役。力田读书,居世应有恒产;为商攻技,凭人各擅其长,徒手耗食固当惩,贱役无良尤必饬。盖一身充入,百恶俱呈。状貌狰狞,曾禽兽之大若,爪牙鹰猛,肆戚友而俱伤,甚而借势杀人,鬻形制命。 ……今与宗党约,如敢委身贱役玷辱宗祊,定即视若路人,不准入庙与祭。”[14]正因为福建民间各家族在修撰族谱时,都十分强调以血缘为核心旨在敬宗收族的编纂原则,标榜本宗本族血缘的纯洁性。因此,一旦出现血缘混宗而危及本家族的社会地位时,有些家族便无法宽容,从而发生辨宗清源的对抗事件,甚至诉讼于政府。
惠安县《龙山骆氏族谱》,记载有明代万历年间骆氏家族的混宗及其抗争情况,即为一例。
惠安骆氏家族大致在宋末元初之际,“自光州固始避乱入闽,暂住云头村”,置有田宅产业,其肇基始祖为“必腾公”,仅生一男:“讳天佑,字孚仲”[15]骆天佑又生四子,长一麒,次一麟,三一凤,四一鸿,分为四房。以后族众不断繁衍,人口日益增多,到了明代嘉靖、万历年间,俨然成为惠安的大族之一。
骆必腾携家从河南迁居惠安时,有随迁养男黄来保、杨成安、朱长安等四人。“当播迁之始,与四仆同济时难,爰收入籍”,允其姓骆。后来二世祖骆天佑又率领族众徙居惠安县二十二都玉埕里,为了照看开基祖业和先人坟墓,便将“旧置田地庄舍在云头下洋者,尽付三养男等掌管”[16]。骆氏家族在玉埋里定居后,黄、杨、朱三姓养男虽与主人异居两地,但其主人与养男的隶属关系依然世代存在,每当骆氏家族春秋大祭之日,玉埕里的骆氏族众来到云头下洋扫祭,黄、杨、朱等养男后裔“岁供牲、纸,共应门役”。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明代中期,未有变更,“盖三百余年,里叟邻孩喙能道说也”[17]。
但是到了嘉靖、万历年间,骆氏家族这种历经三百多年的主人与养男的族属关系发生了变化。这个时期,正是福建沿海人民从事海上私人贸易最为活跃的时期,骆氏家族的黄姓养男后裔黄乾育兄弟,跟随安海商人冒险海上,从事走私贸易,取得成功,“一旦骤富”。于是,他们不甘屈服于“养男”为仆的社会地位,于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出揭乱宗”,出资请人撰刻先人墓志,修纂自家的《骆氏族谱》,把自己祖先养男的成份,跃居骆氏主人之上,声称始祖骆必腾生有二子,长天保,为(养男)乾育之派;次天佑,为玉埕里一派。同时,黄乾育等人运用自己的经济力量,出资重贿,拉拢和分化地方乡邻以至他们原先的主人,以求得其中一部分人的同情和支持。骆氏宗族中的一部分族人,有的“受贿于叛仆,而假族谱以供其变”,有的则亲密往来,兄弟相称,承认其为族伯的地位。黄乾育葬父时,又有族人“往吊以金纸,后为颁志铭”,主家之人“反拜于养男之墓”。黄氏养男还利用其 “富贾”的实力,广泛结交官府和地方士绅,他们盛请文人名士, “并拜云头祠宇”,以叙通家,重金聘请官宦“代笔志铭”,并试图联姻于泉州的林黄二大姓。
惠安骆氏家族由养男引起的混宗事件,已经危及骆氏家族的社会地位。于是,骆氏家族在士绅骆日升等人的倡议下,联合起来,与黄姓养男进行辨宗清源的抗争,该族谱载有《忿词》、《辨章》、《揭帖》等,兹引《忿词》如下:忿词惠安二十二都玉埕里立忿词,户长骆瑗因世仆乱宗,名分倒置,姑述其概,伴览观者得辨玉石,庶本宗世系不至为他姓所紊乱也。始祖必腾公原自光州固始避乱入闽,暂住云头村, 仅生一男,讳天佑、字孚仲,旋僻处,遂卜玉埕里后居焉。今乡贡骆廷炜、荣授教谕骆纶、廩生骆惟翰、奉训大夫骆惟怀、生员骆希谟、天锡、惟佐、惟仪、惟朝、惟仁、惟祯、趋庭、趋敬、廷晨、廷煌、廷炫、廷瞻、日升等皆正派也。祖有随迁养男黄来保、杨成安、朱长安,俱收入籍,共支户役。祖虑世远,仆奴乘主,严厉传家,族谱称载详悉。仍将云头建立田地付来保等耕种,岁供牲纸,而以旧筑庄舍令世居焉。即今骆乾育、号安峰者,正黄来保之裔也。始无立锥之地,为桶匠治生,妻陈来定女;弟乾佐娶贺庆福女,二姓皆白崎村郭、李之仆佃也,世代村落,五尺通晓。伊叔成贯怜育无依, 送跟安海商人为奴,颇得厚利,遂带货物往广,交接倭船,将弟乾佐为质,对银二千余两,约货填送。讵育见财忘义,弃弟不赎,被倭带去,经今未回,诈称身故。以此积奸致富,遂逞雄猾,渺视主仆分谊。今春葬父,谋地占害。掇采谱记糟粕,耸惑宦家代笔志铭,将伊始祖来保改作天保,冒称吾祖必腾公长子,而抑天祐次之,以此欺瞒亲友,炫耀缙绅,识者咸切齿之。夫以来保之后裔孙子,至今称主称仆,尊卑森严,惟育移居晋邑,欺众弗察,遂蒙虎尘,乘主蔑伦,实甚可恶,神人共愤。岂不知族类子姓班班诸记,纵奸诡百出,焉能以一旦之骤富而混数百年之黑白哉,第忿闻风轻信,未袭成例,谨将乾育世仆事由遍告诸士大夫君子,共扶正气,众口交槟乱宗罪恶,知所警戢,而晋之乡宦误听缔亲者,亦不可因财而忘贵贱之羞。若吾惠邑,则人人睹记不待辨矣。[18] 骆氏宗族在强烈攻击乱宗奴仆黄乾育的同时,亦加强了本宗族内部的控制,在族长和生员们的倡议下,阖族立下《倡义稿》,以加强族内的血缘团结和对乱宗事件的抗争。该《倡义稿》略云: 止公议户长骆以成、房长炳乡等为健奴乘主事 ,凡我同族子姓兄弟,苟存一念笃祖敬宗之意、传子贻孙之谋者,皆当目击心忿,以本月初六日齐到泉城东门二郎庙,同往乾育家正名,并带所刻主仆情由遍粘街坊,庶晋邑士大夫君子览观者亦得共愤而切齿之。今我宗族凡有同行者各书其名字于左,以凭届期会集,倘嗜利忘义,甘心事仆,不敢出一言以相攻正者,皆非我族类。生何面目入家庙,死何面目见先人于地下乎?自此以后槟而不齿。其向义出头之人,俱刻名字列之主仆扁额,永挂祠宇,以垂不朽,使远代后裔得有考据以定名分云。
公议条款一主仆混乱,乃通族之羞,非一人私愤。其公费等钱除养子孙外,照依派盐丁数均出,如有恃顽不出者会众同取。
一首议之人非生端喜事,以前辈尊长不敢劳烦,故不得已而任其责,如或后日生端,报施首议之人,族众誓约壮心共御,使后之向义者有所激励云。
一凡同宗子姓兄弟,既议之后,如再因财利之交而忘良贱之分者,查实会众鸣鼓而攻,以为后之戒。
一举议正名系祖宗重事,如有倡为不必较以阻后生之行,此事得罪祖宗,永不许入家庙。[19]通过这次乱宗与辨宗事件,骆氏家族与黄(骆)乾育后裔彻底决裂,至今两个家族各传衍派下子孙甚众,而两个家族仍各以正宗瞒氏自称,各有谱牒为证。据云清代康熙年间中过武进士的惠安骆俨,便是黄(骆)乾育的后裔。
清代乾隆年间武平县李氏家族发生了一起窜改祖先名字的事件,起因是该家族每年祭祀时有分胙的礼仪,乾隆戊子(公元1768 年)轮充经营尝谷分菲的李公杨,私下把族谱内的前辈名号篡改,造成宗绪混乱,该族谱有《禁窜改谱名记》云: 按阅家谱,有各房上祖诸先辈积锱经营置买各庄等处田亩,再立秋祭尝,聊尽报本追远之义,厥后公众列名登刻族谱,俟秋祭时誉单读祝,配祀宗祠,仝受千百年之血食,安得一旦而泯。且设班次轮收尝谷,买办牲仪等物,择八月十五为期堂祭,随同赴坟再祭,祭毕旋祠,遵照谱版名次颁胙各壹斤,并现存绅衿胙各壹觔,已遵百十余载,无敢欺心妄念。不意于乾隆戊子(按:公元1768年)七月,有本裔公杨者充收尝谷,弥缝莫知,八月十五致祭时,检谱查明擅将乏嗣之君华公改刻纶章名字,又长寿公改刻宗挺,君太公改刻五昌,继霖公改刻光渭,腾吾公改光斌。以上五位前代配祀本祠,勿今灭名,不列祝文,从此被窜改之祖,竟作无祀之魂灵,人心安否?又幣绅衿胙仅发三分之二,掩人耳目。噫! 欺祖藐宗,倾坏前模,谁能含忍?故通族会议,若不急为纠正,将来效尤愈炽。遂联名具呈县主陈讳步云,旋得公杨之父纶章到祠面恳伯叔,直认前愆,愿将私行刳去前代祖名,仍令梓人照旧补转原名,所欠绅士胙肉按名补足发清。斯时念属同宗,姑从宽宥。倘日后有横行射利售买并毁前辈名号者,通族同攻出族,将胙一并扣除,以杜效尤,藉以上慰先灵,下警强悍,方全一本同枝之谊,绵千载不坠之举。[20]这次窜改祖先名号事件,虽然于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以李公杨受谴责而告终,但到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又有一些族人企图再行改写,该族谱复记云:“原谱《禁窜改谱名记》,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冬重修族谱检齐谱版完刷已将告竣,竟被不肖裔故意偷匿,希图复蹈前辙,侵灭上祖名迹,并将各房世系谱版匿去数块,实可痛恨。阖族公正伯叔爰酌议仍将原订载悉行照旧补刻,其一切费用,权将阖族壬子年(按:公元1792年)春祭颁发绅胙每斤扣减二两五钱以为补刻工资。”[21]这起事件如此反复,起因虽为窜改祖先名号,导致族内血缘世系的混乱,但其背后,却不能不包含着家族内部不同房派之间的矛盾因素在内。
泉州府郭氏家族在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四修族谱时,也发生了一起因赘子混宗而引起的修谱争执,双方僵持至官府公堂,诉讼于舆论,轰动一时。《蓬岛郭氏家谱》特辟《外纪》一节,专记其事始末。
蓬岛郭氏家族的混宗争执,其起因据云是“有楼上派礽贵赘子名烈者,其身家不清,竟敢屡次到谱局要挟,强迫欲改为心远派云柱子,妄图紊乱宗支。谱局因开族众大会,众皆以前谱煌煌,不敢滥允。烈遂明目张胆煽惑无识之徒十余辈为党羽,冒称是伊房亲,同声附和,肆言烈派不改,伊等决不愿合修族谱,数次贻书,请脱离关系。”[22] 郭烈等提出与谱局脱离关系试图另修别谱时,“势成破裂”,双方开始走上正面的对抗。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闰六月廿四日谱局召开族众大会,通过两条决议,“一议决对楼上派烈,一致以族众对付,二议决朝宝函请(归宗)不能照准移越乱添”[23]。于是,双方决定呈词当地驻军旅部,请官府裁决。阳历八月十九日,谱局以郭治懋等人为首,正式向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陈旅长呈送诉词。二十一日,郭烈、郭朝炎等人亦呈词陈旅长,反控谱局郭治懋等,该反控呈词略云: 具状郭朝炎,住南安十二都蓬岛乡,为藉索不遂,以伪继伪,请饬警拘案押,令更正以维昭穆,以重谱例事。窃炎乡第三次所修家谱,伪谬舛错,昭穆不明,指不胜屈,查检便详。……第三次之谱,系乡先邑庠郭治政所修之谱,此人品行邪正,各都人士周知,尽可查证,炎系侄辈,未便誉毁。此次重修谱系,系郭治懋主笔,郭重安校对。当发起续修之日,懋、安二人亦经开会宣告,凡治政前修舛错之条,决励行更正,初意非不光明正大。迨本年古历三月间,懋、安欲藉修谱发财,懋阴令安向炎私索八十金,炎不许。懋、安遂将治政所谬修炎作族兄郭新贵之子认为义例无差,公然印刷宣告。……初烈且与贵系族兄弟之称,何得指炎为贵子,况贵与炎各出一派,尤懋、安二人及通乡所共知。贵为楼上派, 炎为甲田派……。懋、安二人董谱事,明知治政前谱之伪,于提倡续修时乡众集会日既更正改前谱伪载炎为贵子之条,固索怫意而变前议,致动炎房公愤,公函抗议。懋、安二人终以谱权在手,居奇欺压,且横宣告炎同派书辞背谬,使炎置系统诸无伦次之列,何以为人,何以齿于邻里。[24]郭朝炎反控词上呈之后,谱局郭治懋等复上辨诉状词如下: 据恳请旅长先生保护系统慎重昭穆恩迅执行万世戴德谨状。……具诉呈南安十二都蓬岛乡民郭治懋……等为叛父不遂,捏谎攻毁,诉恳察申,以存公道,以正谱例事。窃维谱所以正纲常而明昭穆,必据实编修,方足以昭信后世。近来风俗不古,有夫死而招赘生子者,于谱例不无阻碍,惟变通办法修谱或并收入,不轻为削去,而稍示区别,此亦不忍伤宗族和气,甚不得已之苦衷。敝族于光绪庚寅年庠生郭治政所修之谱固不敢称善本,然昭穆分明而支派不紊,谱内载楼上派廿三世缵烈乃俨父初贵入赘心远派廿一世云柱卒后之孀妻所生之予,修谱时柱父永汝视如赘疣,割与初贵.。此次续修谱乘,烈直欲〓父派而归母派,谓伊不欲无母,然亦岂可无父,烈母明明赘贵为夫,烈、自当终身以贵为父,乃竟称欲改汉顺昭穆,实则改更不顺昭穆,此可改,何事不可改? ..惟此次修谱乃众力合作,事事须开会议决,似此绝续攸关,昭穆不顺,若徇私滥允,则烈谓前修为伪谱,实今修乃真伪谱,茂等将得罪于祖宗并得罪于族人。无己沥诉并呈旧谱七本,恳乞旅长公明察核申办,以重谱牒而儆愚顽,幽明均戴。切叩。[25] 双方正式呈词于驻军旅部之后,有些地方士绅及族内公亲劝说双方调和解决,公推(永春县)陈县长等联名“具公亲禀声请销案,时诸公即令两造渐回,事可告一段落”,不料驻军旅长欲树其威,不准撤诉,最后由旅长判定:“凡属昭穆不清者一概削去,另修副谱。”终于导致双方分裂,各修各谱,郭朝炎等人于十月二十四日在厦门《民国日报》刊登启事,宣布谱局所修之谱为伪谱,所谓 “本年为第四次重修,本房复依理提出修改,彼辈一味顽强不理, 藉词欺人。邀之公评,亦置不顾。本房为此无可奈何,爰公决否认,以重谱义。此后该谱倘或编就,断不能认为正谱也。”此则启事刊登之后,谱局郭治懋等随即亦在厦门《民国日报》上登一反驳启事,声称“本局天职依议决案积极进行。彼荫之捏谎诬蔑,固无损于此次之族谱,无辨驳之必要。但事经外现,窃恐各界未明真由,被其瞒骗,淆乱是非,爰将荫之阴恶及其荒谬之黑点和盘揭出,登诸报端,俾众同知焉。”[26] 上举三个例子,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福建民间家族在撰修族谱时对于血缘统绪的重视。但是我们还不能不看到,在这三起以纠正乱宗为名号的背后,蕴含着家族内部各房派企图控制族权、争夺社会地位的实质。每当家族的血缘世系出现人为的混乱并且危及家族的社会地位和族内统治权的归属时,血缘纯正的原则往往成了攻击异己最有效的旗号;而当血缘混宗现象没有影响到家族的社会地位和族内控制权的稳定时,甚至这种血缘混宗现象有助于提高本家族的社会地位和声望,那么血缘的混宗也就常常被各家族所熟视无睹、司空见惯。因此,就福建族谱的整体情况而言,以血缘为核心的敬宗收族固然是每个家族在修撰族谱时所不断强调的原则,但是这种原则的标榜与实际的操作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上举的三个例子,在福建的族谱中毕竟相当少见,而各家族人为的造祖联宗却成了明清以来福建族谱带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现象。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逐次论及。
福建民间家族的族规、家法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且各个家族所制定的族规、家法内容不一、形式多样,但其中有一点却是必不可少,具有普遍性的,那就是强调孝祖先、重续嗣、睦宗族。这里,试举连城《文川李氏七修族谱》所载的宗规训戒为例:祖训一训孝顺父母。人之百行,莫大于孝,家庭中有善事父母,克供子职者理合褒嘉,呈请给匾,以旌孝行。一训敬老尊贤。高年硕望,模范具焉,国家且有优待之典,族姓可无推崇之文?今与子姓约尚敬礼之,毋或敢忽。
一训和睦亲族。子姓蕃衍皆祖宗一脉分形之人,忍膜外视乎?凡我族人尚笃亲亲之谊,方不愧为望族。
一训勤读诗书。报国荣亲,诗书之泽甚大。凡我子姓有志诵读者,品行文章着力砥励,或列黉序或掇巍科,非特宗祖有光,亦副族人之望。
一训诚实正业。农工商贾各有专业,敦本务实乃克有成。凡我子姓宜执其业,实其职者方为克家令嗣。
一训早完钱粮。钱粮为惟正之供,输纳实臣民之分,凡我族人宜各早完,毋累亲族。
族戒一戒不孝不友。五伦之大,孝友为先,倘明发有亏天显罔念,甚不足挂齿,维我众人定以不孝不友之罪罪之。
一戒挖卖祖坟。宅兆安厝,祖先之灵爽所栖也,俗有不肖之徒以卖坟墓为生涯,忍心害理,莫此为甚。倘子姓蹈此恶习,众削其图谱,呈官重惩,永不许入祠与祭。
一戒为匪乱伦。淫乱一事,律载五刑,况灭伦坏纪,尤禽兽不如。子姓倘犯此禁,削其图谱,拒其与祭,家法所在!决无轻纵。
一戒承充隶卒。隶卒世所共耻,以是人而列谱系与祠祭, 岂不玷祖宗而坏家风,倘有误践者,宜亲房令从正业,如固执迷,图谱槟黜。
一戒欺祖霸尝。祖宗尝田,完粮办祭所从出也。如有抗欠、借端欺霸以致祭祀不敷、钱粮贻累,情同悖祖,众共攻之。
一戒酗酒打架。家燕合欢,礼法所在。若酒酣耳热攘臂逞凶,乱我笾豆,礼法奚存?长少虽异,均当惩戒。[1]上引文川李氏家族训戒共有十二条,除了 “勤读诗书”,“诚实正业”,“早完钱粮”这三条是强调族人各安其业、为族争光之外,其余的九条,都是劝戒族人必须孝敬为先,和宗睦族,这也就是通常所讲的“敬宗收族”。这种情况不仅仅是李氏家族如此,福建民间其他家族所制定的族规、家范一类,大体上也是以“敬祖宗”、 “重宗长”、“禁犯上”、“睦宗党”、“重师友”、“重继嗣”、“重血脉”、“安灵墓”、“凛国教”、“恤患难”、“急相助”、“禁欺凌”、 “禁乱伦”、“禁争讼”、“惩小忿”等为主要内容。这些“敬宗”、 “收族”的族规内容,构成了家族内部团结和维系宗族延继不断的两大要素。而这两大要素,又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的基础上,抛弃了血缘关系上的尊卑次序观念,所有的家族组织和制度便无从讲起。正因为如此,慎终追远、水源木本便成了福建各地家族族谱所要努力体现的精神典范。许多家族的族谱都强调“敬祖宗而明绪体,辨昭穆而明亲疏,不为不重”,[2]“夫自一人之身分而至于千百人之身,由一人之世传而至千百年之世,……人不忘祖宗也,使人不弃宗族”,[3]“祖宗功德之流泽长矣,夫人道之大在亲亲,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族谱)列时代之后先,以考氏族之真伪,俾后嗣子孙得了然于寸楮间,斯诚仁人孝子之用心乎! ”[4]如果说族规、家范中所强调的“敬宗”、“收族”精神只是福建各家族修撰族谱时的指导原则,那么各家族所制定的“修谱凡例”则是这种指导原则的具体化表现。我们先来看看泉州《蓬岛郭氏家谱》所载的修谱凡例。泉州蓬岛郭氏家族开基于南宋时,到民国时期已繁衍二十余代,族众达万余人。该族首修族谱于明末崇祯年间,清朝嘉庆年间再次重修,至光绪庚寅年(公元1890年)由举人郭大彬及郭崇勋三修,延至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由郭治懋、郭朝麟等主持四修。该家族在首修族谱时,已经制定了修谱凡例,在二修时进行补充,修谱凡例已达二十一条之多,这二十一条谱例被称为“旧例”,兹摘录如下:…… 一谱系以宗派为重,最宜详慎。凡为人后者,于本生父母之名下必书,重所生也,旁注出嗣与某人为后,著其实也。至为所后者则书曰嗣子某,正名以定其志也。或随母嫁出及为他姓子者,削不书,不以混宗派也。其已殁者不议也。至螟蛉之子例宜注养字,著其别,以戒将来。第吾族抱养之人难以查明,姑就其名下载之,宽既往也。
一妇人年三十以内守节,艰苦备尝,有子成立者俱宜表而出之。……一生卒年月必书,其有不书者阚不知也,娶某氏亦即书于本名之下。元配、附配、继妻,虽无子必书,记嫡体也。妾有子则书,重嗣续也。妻妾俱有子各著其所出,妾无子者不书。……一妇人夫死他适者,于夫名下系不书,示与庙绝也。记所生之子几人,注妣某氏岀者,示无母之子也。侧室他适者,虽有子不书。
一图考五世为一图,六世一提图,画以五本缀以一,乔梓纵,棣萼横,仿欧阳文忠公之例,分之各一太极,合之同一太极。按图考之了然,则心目以广稽世系之详明,则孝友以森,周穷恤孤、尊贤敬老之心至矣。
一始祖德昭公支派详明,昭穆不紊,因派开房,因房再辟各派,各条宗支嗣续世系名字生卒配葬科第事迹皆备焉。…….[5]从这些例条中可以看出,郭氏家族在修谱时十分重视血缘的纯洁性,举凡嫡出、别出,出嗣、过继以及改适等等,都进行了相应的规定,以保证家庭血缘不致混乱。至光绪庚寅十六年(公元1890 年)三修时,该家族又增立了十六条谱例。除了重申旧例的各条注意事项外,还特别对进一步维护血缘的纯洁性作了补充规定:一我族人众其出嗣者则书之曰某某出嗣,又书之曰嗣子某某,以示别也。而独此抱养之子未及详注,与亲生之子无异也。兹除从前不知外,及今现知者一概加以养字,庶不致有鱼诛之混。
一我姓族大丁多,贤愚不一,其有移花接柳者一概革归原配,以为整顿风俗起见,不得谓秉笔之过于苛也。[6]到了民国年间郭氏家族进行四修族谱时,再次对旧谱例进行修改, 并称之为“新谱例”。新谱例对各种收养、招赘关系虽略有变通,但对于修谱时的血缘认可依然是十分严格的。新谱例共有七条,依次如下:一私生子必不入谱,兹奉官令变通办法,另设附谱以示区别。其母生,削去娶字;死,削去妣字,子削去名字行,于名下书养字,此条仅限夫死之后适行之。
一夫死重赘本姓,字行同者,男削去字行,妇削娶为取,削妣为比。所生子书养字,而存其名字行。赘异姓夫者,夫不入谱,母子同此例。赘异姓妇者,予书养,父不削字行。其字行不同者,奉官令收入附谱,男削去名字行,妇削去娶妣, 所生之子与父同。惟赘夫若有正娶妻之子,则仍列正谱。
一娶本族妇,男妇书法与重赞者同例,惟所生之子准与普通无异。
一苗养幼媳经载前谱,迨后长大而改配其父之兄弟及族人者,妇于前夫名次下书改适,其后夫及妇书法无论如何,与娶本族妇字行相同者同例,惟所生之子得与普通无异,若前夫既完婚生子者不得援议。
一兄夺弟妇,弟占兄嫂,叔夺侄妇,侄占叔母,为牍伦伤化之极,义不入谱,令亦聊纪其生卒葬于附谱。
一定议以上五条断自光绪庚寅年(按:公元1890年)男妇尚在,或所生之子未卒者适行之。
一赘同姓之妇,旧谱有仍书在前夫之后者,有互相详略者,有于后夫之后空书娶氏生卒年月日时者。兹订概归前夫,其空书者悉删去之。惟赘生之子不论归夫归妇,旧谱概书养子,今亦概书养子,不复置议。[7]经过三次对谱例的增订,郭氏家族对于以血缘为核心的修谱规定可谓详尽。这种情况不仅郭氏家族如此,福建其他家族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奉行着这种以血缘为核心的旨在敬宗收族的修谱原则。特别是对于血缘混乱,继嗣不明的现象,尤为明禁。龙岩《谢氏族谱》在修谱凡例中强调“谱内承继为后,并无紊乱昭穆,亦无抱养他姓之子以及随母来之子,所以明世次锄非种也。……娼优隶卒例禁,后嗣不得与考。倘族中有此等不肖子侄,不特败坏家风,抑且害及子孙。一俟查出,公革不贷。”[8]建阳《麻沙刘氏族谱》的修谱条约规定:“螟蛉宜禁,以杜乱宗也。……吾族新修谱牒,螟蛉之子悉行削去,以警族人不继本宗,而继异姓者。倘再蹈此弊,必严行惩罚。”[9]浦城《渤海西吴宗谱》的《族禁》云: “禁非种承祧,非类之异种宜锄,不特抱养他族,明属篡宗,即为姑娣侧生,终非同姓。”[10]闽北《余氏宗谱》亦称“禁非种承祧,本是联枝,何用寄生之草;苟非艾乾,必除当道之兰。艰于嗣者每畏亲房得其家财,昧天理者,必喜外姓承其宗祧。私情易起,默地难欺。若或产出姑娣,未全非类;惟有抱血他族,乃属乱宗,祭不使与,谱亦宜差”。[11] 为了维护家族血缘世系的纯洁和高贵,福建许多家族在严禁血缘乱宗的同时,还规定族人必须立身有道,不得沦为奴仆娼优等贱民,不得从事低贱的行业。如闽西《吴氏族谱》规定“子姓有不孝不友,非为乱伦以及娼优隶卒有玷宗风者,不许编入谱内,并不许春秋与祭。……凡族人有潜养异姓人子以混宗支者,例不得录。有随母改适冒从他姓,及出继异姓为人后者,例应〓书。俟其还本归宗,再行补订。”[12]闽北《余氏宗谱》的族禁云:“士农工商皆君子立身之道,娼优隶卒乃人生不齿之徒,即使迫于饥寒、谋生乏术,亦应念及祖父,何容改节以贻羞。……名既有玷,谱岂容登?”[13]永安《余氏族谱》的《谱禁》云:“一禁委身贱役。力田读书,居世应有恒产;为商攻技,凭人各擅其长,徒手耗食固当惩,贱役无良尤必饬。盖一身充入,百恶俱呈。状貌狰狞,曾禽兽之大若,爪牙鹰猛,肆戚友而俱伤,甚而借势杀人,鬻形制命。 ……今与宗党约,如敢委身贱役玷辱宗祊,定即视若路人,不准入庙与祭。”[14]正因为福建民间各家族在修撰族谱时,都十分强调以血缘为核心旨在敬宗收族的编纂原则,标榜本宗本族血缘的纯洁性。因此,一旦出现血缘混宗而危及本家族的社会地位时,有些家族便无法宽容,从而发生辨宗清源的对抗事件,甚至诉讼于政府。
惠安县《龙山骆氏族谱》,记载有明代万历年间骆氏家族的混宗及其抗争情况,即为一例。
惠安骆氏家族大致在宋末元初之际,“自光州固始避乱入闽,暂住云头村”,置有田宅产业,其肇基始祖为“必腾公”,仅生一男:“讳天佑,字孚仲”[15]骆天佑又生四子,长一麒,次一麟,三一凤,四一鸿,分为四房。以后族众不断繁衍,人口日益增多,到了明代嘉靖、万历年间,俨然成为惠安的大族之一。
骆必腾携家从河南迁居惠安时,有随迁养男黄来保、杨成安、朱长安等四人。“当播迁之始,与四仆同济时难,爰收入籍”,允其姓骆。后来二世祖骆天佑又率领族众徙居惠安县二十二都玉埕里,为了照看开基祖业和先人坟墓,便将“旧置田地庄舍在云头下洋者,尽付三养男等掌管”[16]。骆氏家族在玉埋里定居后,黄、杨、朱三姓养男虽与主人异居两地,但其主人与养男的隶属关系依然世代存在,每当骆氏家族春秋大祭之日,玉埕里的骆氏族众来到云头下洋扫祭,黄、杨、朱等养男后裔“岁供牲、纸,共应门役”。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明代中期,未有变更,“盖三百余年,里叟邻孩喙能道说也”[17]。
但是到了嘉靖、万历年间,骆氏家族这种历经三百多年的主人与养男的族属关系发生了变化。这个时期,正是福建沿海人民从事海上私人贸易最为活跃的时期,骆氏家族的黄姓养男后裔黄乾育兄弟,跟随安海商人冒险海上,从事走私贸易,取得成功,“一旦骤富”。于是,他们不甘屈服于“养男”为仆的社会地位,于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出揭乱宗”,出资请人撰刻先人墓志,修纂自家的《骆氏族谱》,把自己祖先养男的成份,跃居骆氏主人之上,声称始祖骆必腾生有二子,长天保,为(养男)乾育之派;次天佑,为玉埕里一派。同时,黄乾育等人运用自己的经济力量,出资重贿,拉拢和分化地方乡邻以至他们原先的主人,以求得其中一部分人的同情和支持。骆氏宗族中的一部分族人,有的“受贿于叛仆,而假族谱以供其变”,有的则亲密往来,兄弟相称,承认其为族伯的地位。黄乾育葬父时,又有族人“往吊以金纸,后为颁志铭”,主家之人“反拜于养男之墓”。黄氏养男还利用其 “富贾”的实力,广泛结交官府和地方士绅,他们盛请文人名士, “并拜云头祠宇”,以叙通家,重金聘请官宦“代笔志铭”,并试图联姻于泉州的林黄二大姓。
惠安骆氏家族由养男引起的混宗事件,已经危及骆氏家族的社会地位。于是,骆氏家族在士绅骆日升等人的倡议下,联合起来,与黄姓养男进行辨宗清源的抗争,该族谱载有《忿词》、《辨章》、《揭帖》等,兹引《忿词》如下:忿词惠安二十二都玉埕里立忿词,户长骆瑗因世仆乱宗,名分倒置,姑述其概,伴览观者得辨玉石,庶本宗世系不至为他姓所紊乱也。始祖必腾公原自光州固始避乱入闽,暂住云头村, 仅生一男,讳天佑、字孚仲,旋僻处,遂卜玉埕里后居焉。今乡贡骆廷炜、荣授教谕骆纶、廩生骆惟翰、奉训大夫骆惟怀、生员骆希谟、天锡、惟佐、惟仪、惟朝、惟仁、惟祯、趋庭、趋敬、廷晨、廷煌、廷炫、廷瞻、日升等皆正派也。祖有随迁养男黄来保、杨成安、朱长安,俱收入籍,共支户役。祖虑世远,仆奴乘主,严厉传家,族谱称载详悉。仍将云头建立田地付来保等耕种,岁供牲纸,而以旧筑庄舍令世居焉。即今骆乾育、号安峰者,正黄来保之裔也。始无立锥之地,为桶匠治生,妻陈来定女;弟乾佐娶贺庆福女,二姓皆白崎村郭、李之仆佃也,世代村落,五尺通晓。伊叔成贯怜育无依, 送跟安海商人为奴,颇得厚利,遂带货物往广,交接倭船,将弟乾佐为质,对银二千余两,约货填送。讵育见财忘义,弃弟不赎,被倭带去,经今未回,诈称身故。以此积奸致富,遂逞雄猾,渺视主仆分谊。今春葬父,谋地占害。掇采谱记糟粕,耸惑宦家代笔志铭,将伊始祖来保改作天保,冒称吾祖必腾公长子,而抑天祐次之,以此欺瞒亲友,炫耀缙绅,识者咸切齿之。夫以来保之后裔孙子,至今称主称仆,尊卑森严,惟育移居晋邑,欺众弗察,遂蒙虎尘,乘主蔑伦,实甚可恶,神人共愤。岂不知族类子姓班班诸记,纵奸诡百出,焉能以一旦之骤富而混数百年之黑白哉,第忿闻风轻信,未袭成例,谨将乾育世仆事由遍告诸士大夫君子,共扶正气,众口交槟乱宗罪恶,知所警戢,而晋之乡宦误听缔亲者,亦不可因财而忘贵贱之羞。若吾惠邑,则人人睹记不待辨矣。[18] 骆氏宗族在强烈攻击乱宗奴仆黄乾育的同时,亦加强了本宗族内部的控制,在族长和生员们的倡议下,阖族立下《倡义稿》,以加强族内的血缘团结和对乱宗事件的抗争。该《倡义稿》略云: 止公议户长骆以成、房长炳乡等为健奴乘主事 ,凡我同族子姓兄弟,苟存一念笃祖敬宗之意、传子贻孙之谋者,皆当目击心忿,以本月初六日齐到泉城东门二郎庙,同往乾育家正名,并带所刻主仆情由遍粘街坊,庶晋邑士大夫君子览观者亦得共愤而切齿之。今我宗族凡有同行者各书其名字于左,以凭届期会集,倘嗜利忘义,甘心事仆,不敢出一言以相攻正者,皆非我族类。生何面目入家庙,死何面目见先人于地下乎?自此以后槟而不齿。其向义出头之人,俱刻名字列之主仆扁额,永挂祠宇,以垂不朽,使远代后裔得有考据以定名分云。
公议条款一主仆混乱,乃通族之羞,非一人私愤。其公费等钱除养子孙外,照依派盐丁数均出,如有恃顽不出者会众同取。
一首议之人非生端喜事,以前辈尊长不敢劳烦,故不得已而任其责,如或后日生端,报施首议之人,族众誓约壮心共御,使后之向义者有所激励云。
一凡同宗子姓兄弟,既议之后,如再因财利之交而忘良贱之分者,查实会众鸣鼓而攻,以为后之戒。
一举议正名系祖宗重事,如有倡为不必较以阻后生之行,此事得罪祖宗,永不许入家庙。[19]通过这次乱宗与辨宗事件,骆氏家族与黄(骆)乾育后裔彻底决裂,至今两个家族各传衍派下子孙甚众,而两个家族仍各以正宗瞒氏自称,各有谱牒为证。据云清代康熙年间中过武进士的惠安骆俨,便是黄(骆)乾育的后裔。
清代乾隆年间武平县李氏家族发生了一起窜改祖先名字的事件,起因是该家族每年祭祀时有分胙的礼仪,乾隆戊子(公元1768 年)轮充经营尝谷分菲的李公杨,私下把族谱内的前辈名号篡改,造成宗绪混乱,该族谱有《禁窜改谱名记》云: 按阅家谱,有各房上祖诸先辈积锱经营置买各庄等处田亩,再立秋祭尝,聊尽报本追远之义,厥后公众列名登刻族谱,俟秋祭时誉单读祝,配祀宗祠,仝受千百年之血食,安得一旦而泯。且设班次轮收尝谷,买办牲仪等物,择八月十五为期堂祭,随同赴坟再祭,祭毕旋祠,遵照谱版名次颁胙各壹斤,并现存绅衿胙各壹觔,已遵百十余载,无敢欺心妄念。不意于乾隆戊子(按:公元1768年)七月,有本裔公杨者充收尝谷,弥缝莫知,八月十五致祭时,检谱查明擅将乏嗣之君华公改刻纶章名字,又长寿公改刻宗挺,君太公改刻五昌,继霖公改刻光渭,腾吾公改光斌。以上五位前代配祀本祠,勿今灭名,不列祝文,从此被窜改之祖,竟作无祀之魂灵,人心安否?又幣绅衿胙仅发三分之二,掩人耳目。噫! 欺祖藐宗,倾坏前模,谁能含忍?故通族会议,若不急为纠正,将来效尤愈炽。遂联名具呈县主陈讳步云,旋得公杨之父纶章到祠面恳伯叔,直认前愆,愿将私行刳去前代祖名,仍令梓人照旧补转原名,所欠绅士胙肉按名补足发清。斯时念属同宗,姑从宽宥。倘日后有横行射利售买并毁前辈名号者,通族同攻出族,将胙一并扣除,以杜效尤,藉以上慰先灵,下警强悍,方全一本同枝之谊,绵千载不坠之举。[20]这次窜改祖先名号事件,虽然于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以李公杨受谴责而告终,但到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又有一些族人企图再行改写,该族谱复记云:“原谱《禁窜改谱名记》,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冬重修族谱检齐谱版完刷已将告竣,竟被不肖裔故意偷匿,希图复蹈前辙,侵灭上祖名迹,并将各房世系谱版匿去数块,实可痛恨。阖族公正伯叔爰酌议仍将原订载悉行照旧补刻,其一切费用,权将阖族壬子年(按:公元1792年)春祭颁发绅胙每斤扣减二两五钱以为补刻工资。”[21]这起事件如此反复,起因虽为窜改祖先名号,导致族内血缘世系的混乱,但其背后,却不能不包含着家族内部不同房派之间的矛盾因素在内。
泉州府郭氏家族在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四修族谱时,也发生了一起因赘子混宗而引起的修谱争执,双方僵持至官府公堂,诉讼于舆论,轰动一时。《蓬岛郭氏家谱》特辟《外纪》一节,专记其事始末。
蓬岛郭氏家族的混宗争执,其起因据云是“有楼上派礽贵赘子名烈者,其身家不清,竟敢屡次到谱局要挟,强迫欲改为心远派云柱子,妄图紊乱宗支。谱局因开族众大会,众皆以前谱煌煌,不敢滥允。烈遂明目张胆煽惑无识之徒十余辈为党羽,冒称是伊房亲,同声附和,肆言烈派不改,伊等决不愿合修族谱,数次贻书,请脱离关系。”[22] 郭烈等提出与谱局脱离关系试图另修别谱时,“势成破裂”,双方开始走上正面的对抗。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闰六月廿四日谱局召开族众大会,通过两条决议,“一议决对楼上派烈,一致以族众对付,二议决朝宝函请(归宗)不能照准移越乱添”[23]。于是,双方决定呈词当地驻军旅部,请官府裁决。阳历八月十九日,谱局以郭治懋等人为首,正式向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陈旅长呈送诉词。二十一日,郭烈、郭朝炎等人亦呈词陈旅长,反控谱局郭治懋等,该反控呈词略云: 具状郭朝炎,住南安十二都蓬岛乡,为藉索不遂,以伪继伪,请饬警拘案押,令更正以维昭穆,以重谱例事。窃炎乡第三次所修家谱,伪谬舛错,昭穆不明,指不胜屈,查检便详。……第三次之谱,系乡先邑庠郭治政所修之谱,此人品行邪正,各都人士周知,尽可查证,炎系侄辈,未便誉毁。此次重修谱系,系郭治懋主笔,郭重安校对。当发起续修之日,懋、安二人亦经开会宣告,凡治政前修舛错之条,决励行更正,初意非不光明正大。迨本年古历三月间,懋、安欲藉修谱发财,懋阴令安向炎私索八十金,炎不许。懋、安遂将治政所谬修炎作族兄郭新贵之子认为义例无差,公然印刷宣告。……初烈且与贵系族兄弟之称,何得指炎为贵子,况贵与炎各出一派,尤懋、安二人及通乡所共知。贵为楼上派, 炎为甲田派……。懋、安二人董谱事,明知治政前谱之伪,于提倡续修时乡众集会日既更正改前谱伪载炎为贵子之条,固索怫意而变前议,致动炎房公愤,公函抗议。懋、安二人终以谱权在手,居奇欺压,且横宣告炎同派书辞背谬,使炎置系统诸无伦次之列,何以为人,何以齿于邻里。[24]郭朝炎反控词上呈之后,谱局郭治懋等复上辨诉状词如下: 据恳请旅长先生保护系统慎重昭穆恩迅执行万世戴德谨状。……具诉呈南安十二都蓬岛乡民郭治懋……等为叛父不遂,捏谎攻毁,诉恳察申,以存公道,以正谱例事。窃维谱所以正纲常而明昭穆,必据实编修,方足以昭信后世。近来风俗不古,有夫死而招赘生子者,于谱例不无阻碍,惟变通办法修谱或并收入,不轻为削去,而稍示区别,此亦不忍伤宗族和气,甚不得已之苦衷。敝族于光绪庚寅年庠生郭治政所修之谱固不敢称善本,然昭穆分明而支派不紊,谱内载楼上派廿三世缵烈乃俨父初贵入赘心远派廿一世云柱卒后之孀妻所生之予,修谱时柱父永汝视如赘疣,割与初贵.。此次续修谱乘,烈直欲〓父派而归母派,谓伊不欲无母,然亦岂可无父,烈母明明赘贵为夫,烈、自当终身以贵为父,乃竟称欲改汉顺昭穆,实则改更不顺昭穆,此可改,何事不可改? ..惟此次修谱乃众力合作,事事须开会议决,似此绝续攸关,昭穆不顺,若徇私滥允,则烈谓前修为伪谱,实今修乃真伪谱,茂等将得罪于祖宗并得罪于族人。无己沥诉并呈旧谱七本,恳乞旅长公明察核申办,以重谱牒而儆愚顽,幽明均戴。切叩。[25] 双方正式呈词于驻军旅部之后,有些地方士绅及族内公亲劝说双方调和解决,公推(永春县)陈县长等联名“具公亲禀声请销案,时诸公即令两造渐回,事可告一段落”,不料驻军旅长欲树其威,不准撤诉,最后由旅长判定:“凡属昭穆不清者一概削去,另修副谱。”终于导致双方分裂,各修各谱,郭朝炎等人于十月二十四日在厦门《民国日报》刊登启事,宣布谱局所修之谱为伪谱,所谓 “本年为第四次重修,本房复依理提出修改,彼辈一味顽强不理, 藉词欺人。邀之公评,亦置不顾。本房为此无可奈何,爰公决否认,以重谱义。此后该谱倘或编就,断不能认为正谱也。”此则启事刊登之后,谱局郭治懋等随即亦在厦门《民国日报》上登一反驳启事,声称“本局天职依议决案积极进行。彼荫之捏谎诬蔑,固无损于此次之族谱,无辨驳之必要。但事经外现,窃恐各界未明真由,被其瞒骗,淆乱是非,爰将荫之阴恶及其荒谬之黑点和盘揭出,登诸报端,俾众同知焉。”[26] 上举三个例子,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福建民间家族在撰修族谱时对于血缘统绪的重视。但是我们还不能不看到,在这三起以纠正乱宗为名号的背后,蕴含着家族内部各房派企图控制族权、争夺社会地位的实质。每当家族的血缘世系出现人为的混乱并且危及家族的社会地位和族内统治权的归属时,血缘纯正的原则往往成了攻击异己最有效的旗号;而当血缘混宗现象没有影响到家族的社会地位和族内控制权的稳定时,甚至这种血缘混宗现象有助于提高本家族的社会地位和声望,那么血缘的混宗也就常常被各家族所熟视无睹、司空见惯。因此,就福建族谱的整体情况而言,以血缘为核心的敬宗收族固然是每个家族在修撰族谱时所不断强调的原则,但是这种原则的标榜与实际的操作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上举的三个例子,在福建的族谱中毕竟相当少见,而各家族人为的造祖联宗却成了明清以来福建族谱带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现象。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逐次论及。
附注
注释:[1] 连城《文川李氏七修族谱》卷之首,《族戒》。
[2]安溪《清溪谢氏宗谱》,《伴读公示训》。
[3]《云程林氏家乘》卷十一,《补辑家范》。
[4]民国《何忘五修宗谱》卷一,《嘉靖甲寅志序》。
[5][6] [7] 民国《蓬岛郭氏家谱》卷一,上。
[8]《岩坪谢氏迁玉族谱》卷首,《凡例》。
[9]光绪建阳《麻沙刘氏族谱》卷首。
[10]浦城《渤海西吴宗谱》卷一。
[11][13]光绪《书林余氏重修宗谱》卷首,《族禁六款》。
[12] 闽西《渤海吴氏族谱》卷之首,《族规》。
[14]永安《余氏族谱》卷一,《谱禁八条》。
[15] 惠安《龙山骆氏族谱》,《大事记》。
[16] [17] [18] [19] 惠安《龙山骆氏族谱》,《大事记》。[20][21] 武平《城北李氏族谱》卷末(戊),《产业类》。
[22]《蓬岛郭氏家谱》卷一,上,《蓬岛郭氏四修族谱公序》。
[23][24] [25] [26]《蓬岛郭氏家谱》,《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