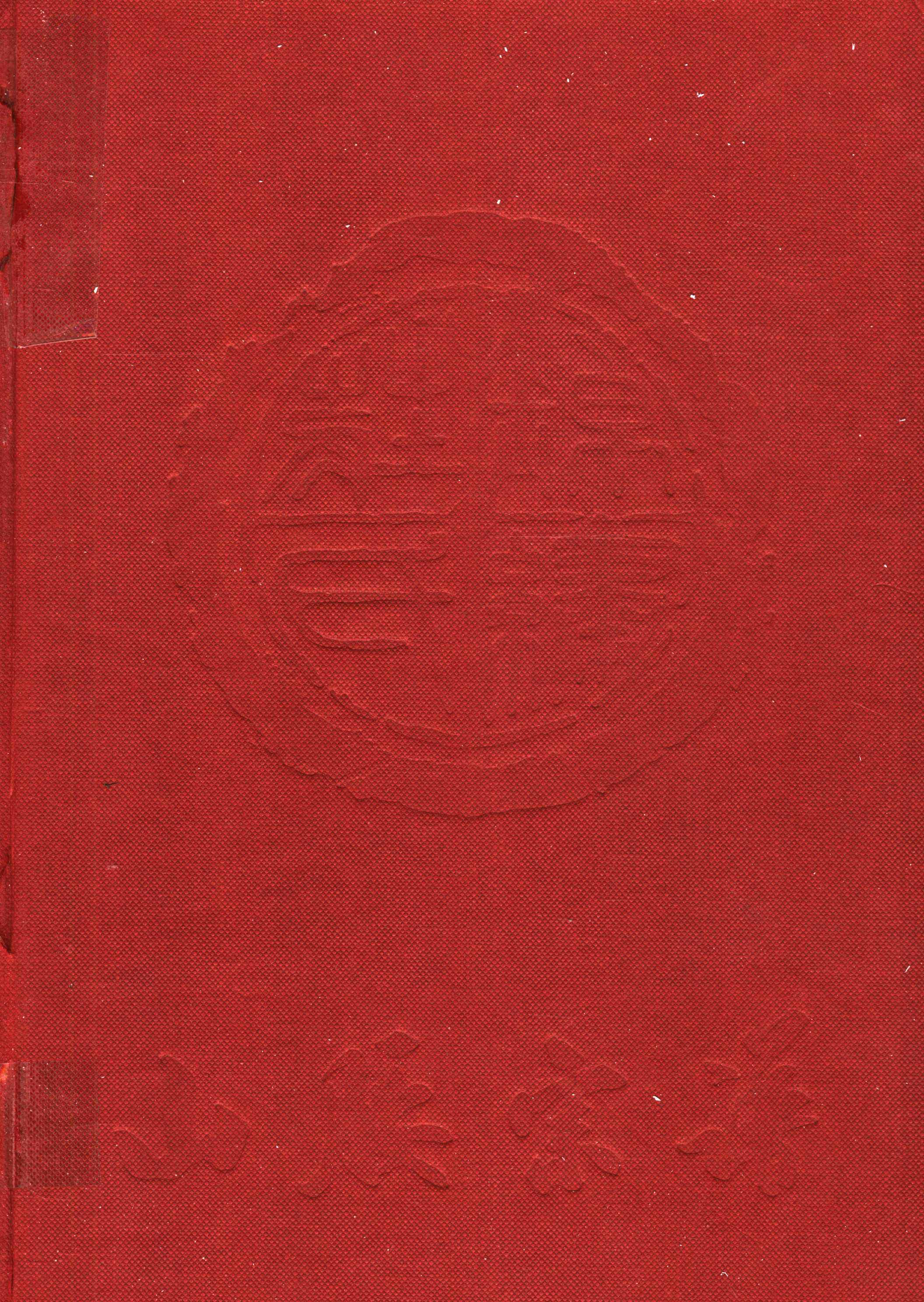内容
统谱(联谱),亦称统宗世谱、大成谱、通谱、总谱等。统谱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把分布于各地的同族各支派统编于一谱,这种统谱可称有直接血缘关系的同宗谱。如《罗氏大成谱》,以豫章罗氏为收谱对象,“豫章罗氏一世祖珠公,系秦武陵令君用公次子,字怀汉,号灵知,汉高祖时官治粟内史。惠帝三年(按:公元前192年)以直谏见斥,迁九江太守,遂籍豫章,为南迁始祖”[15]。故其后裔分衍于闽粤赣三省,统编《罗氏大成谱》。再如福建《朱氏通谱》,收谱对象限定于徽州朱氏(朱熹先祖)的后裔,凡自认为源出此脉者,均可被收入此通谱。
统谱的另一种形式,实际上是同一姓氏的联合谱,收进这种统谱的同姓人,其先祖并不一定都有直系的血关系。如晋江《董氏大成宗谱》,把天下各地董姓收入谱内,所谓“河间派,董仲舒迁居;临川派,董晋公扩源;湖溪派,董仲三金公;临湘派,董旭一公;云南派,董旭二公;广昌派,董谋公;浙江派,董思敬;广东派,董言公;……”[16]。 再如安溪《谢氏总谱》,除了收载泉州一带的谢氏族人外,也把南中国的许多谢氏均认为同宗而收载入谱,所谓“吾族得姓之始本姜姓,神农之后申伯,为周宣王之舅,受封于谢”,“申伯公所流而传哉,一本万殊,万殊一本,寻源溯流,自必由周而汉而晋而齐而梁而隋而唐而宋而元明,原原本本,班班可考矣。……吾谢英裔共培祖德,齐笃宗盟,广搜联络,大会成篇,爰订此血脉志,以为探祖问宗者循溯之基、会合之柄云”[17]。至于有些笼括全国同一姓氏的大统谱,其血缘关系更加稀疏,如民国时期撰修的《吴氏全国大统宗谱》,共收进吴氏各支派达“五百零三支”[18]。光绪年间编修的《章氏会谱》,“齐联福建江西两浙诸族,于世表外,著有郡县地望分支系图,于各族派别一览了然”[19]。
福建民间族谱虽然有以上种种类型,但从谱牒历史的发展轨迹来考察,这些类型的谱牒,并非同时出现的,而是大体经历了一个简易家谱——家谱、族谱、支谱、房谱细分化——宗谱、统谱等联宗合纂的演进过程。
宋元时期的福建族谱,现在虽然已不可见,但从当时福建民间修纂族谱推崇欧阳修和苏洵的谱图、谱式的情景来推测,则宋代福建的民间族谱,其体例和规模尚不至过于复杂[20]。
明代福建民间撰修的族谱,至今流传下来的也不多。但就笔者所见,其时族谱的修纂,还大多局限于一族一地,族谱的规模尚小,体例也比较简单不一,跨地域和跨家族的大型宗谱、统谱尚属少见。这里,试举泉州地区的陈、林二部族谱为例。
泉州《梅溪陈氏族谱》,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由该家族九世孙、进士陈学伊纂修。族谱共分上、下二卷。陈学伊在《前序》中写道:“余分责诸子弟检订旧谱,缀次新支,而裁之以独见,凡十年而始成新谱。谱凡上、下二卷,有总序,有义例,有世系图,有世传,有纶音,有年次,有外谱,有居室坟墓考,有祠堂记,有祭法,有大小宗祀田记,有义田公田记,有谱训,有立后解、家难考等纪。以万历丁亥之春缮写成书,告之家庙”[21]。虽然说陈学伊纂修的族谱包含了以上这么多内容,但我们翻阅该族谱时便可发现,陈学伊在记载这些内容时,都比较简单,远不如后代的族谱那样连篇累牍,因此整部族谱的篇幅不大,现传仅为抄本二册[22]。
同安《林氏族谱》,系明正德进士、名儒林希元所撰。该族谱为不分卷本,所载内容除世纪、世系图外,还有诸林宗派、得姓源流、家训、祭土地文、物产、麝圃垠等,记述也都比较简略,体例没有一定的规则。如其中《物产》一节,仅记如下数行文字:“物产者,可生之业,人所赖衣食以生者也。林氏散居四方,显晦贫富不一。予族居翔风里十三都为名族,田园虽少,犹足课子力耕,免于饥寒。自屯叟至予之孙完,凡六世,颇能克扩,不能悉书。姑即其关于门户之盛衰者书之,以示子孙,俾世守而勿失焉”[23]所以尽管族谱所包含的项目不少,但内容简略,总共不过薄薄的一小册。
以上两部族谱均修撰于明代嘉靖(公元1522——1566年)、万历(公元1573——1620年)年间的繁盛时期,作者又都是进士出身,但族谱的规模都比较小,体例的设计也颇为随心所欲。由花可以推见明代的福建民间族谱,一般都还比较简略。再如《兴化谷目村陈氏族谱》,明代崇祯年间撰修,仅有一册,分两部分:一为世系,一为传记,再无其他内容[24]。即使是福建的名族朱(熹)氏的族谱,其在明代万历庚申(公元1620年)撰修的《建安谱》,也比较简单。卷除了朱熹、真德秀的两篇序言和万历庚申修谱序外,正文共分十款:会元、尚像、世系、褒典、实录、象赞、丘陇、祠院、渊源、留题,整部族谱只有上下二册。
清代康、雍、乾时期(公元1662-1795年),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口增长以前所未有的势态发展。人口的迅速增长,一方面造成清代中后期生存环境的恶化,社会竞争日趋激烈,另一方面也加速了民间各家族的内部膨胀与扩散外迁。于是,原有的族谱规模和编写体例已不能适应这一时期社会与人口的急剧变迁。有经济能力和文化条件的强宗大族们,在清代兴起了修纂大型族谱的热潮。连城文川李氏家族自明至清历次纂修族谱的变化, 颇能反映这一趋向。该族谱载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文川城南李氏四刻族谱序》云:我祠族谱创自前明九世祖中孚公笔记,越正德丁丑(按:公元1517年),十二世元瑫公遂仿欧、苏氏例为合族总图、五世分宗图。迨万历己丑(按:公元1589年),十四世学诜公乃本黄氏族谱横图摹仿而增益之,即今所传之谱法是也。继此而十五世涵公等复于崇祯九年(按:公元1636年)起而续修,将缺者补、新者入,一时灿然称明备。厥后已历百有余载,诚有当续而无续者矣,纵各房间有私纂,然或详或略,不无互异。且从前俱系缮本,而别风淮雨亦未免传疑。至我朝乾隆丙辰(按:公元1736年),经十八代一韩公等取原本,采彼遗文,访诸故老,博览兼收,搜罗罔佚,始付诸剞劂,是为初刻。及庚寅(按:公元1770年)当再刻之期,亦曾十刻八九,究未完善。惟十九代德新公、大苏公等于嘉庆己未(按:公元1799年)间开局以为三刻,当是时,探讨无遗,校雠尽善,洵为一族之成书焉。嗣历三十载为道光己丑(按:公元1829年),时当四刻,众议续修。……于是在祠经理裔孙长房赞宗、德思,次房绣彩、名标,三房开乔、绍安,爰集三大房绅耆合议,众咸踊跃乐从。维时经众佥举在祠襄事,始终不惜勤劳,……而文学、世翰诸纪则命德恕一人总纂而校正之。但近来族大人繁,各逞意见,内中序传志铭虽不无冗杂失然,然揆其铺张扬励之心,要不失为尊亲之意,亦无恶也。……是役也,经始于甲辰(按:公元1844年)初秋,告竣于丙午(按:公元1846年)暮春,阅廿一月而蔵事,由总图世系至前后编,原止四十八卷,今增为五十余卷云。[25]从这篇序文中可以看出,连城文川李氏虽然早在明代中期就已开始撰写族谱,但其最初的形式只是“笔记”而已,正德、万历、崇祯年间虽然历经三修,但也仅是“将缺者补、新者入”,属于手抄缮本。一直到了清代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随着族人的繁衍和族谱的扩大,“始付诸剞劂,是为初刻”,其后每过三四十年重修重刻一次,至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已经四刻, 并且规模一次比一次增大,成了五十余卷、数十本之多的大型族谱。
连城文川李氏家族的修谱历程,大体能够反映清代福建民间家族的一般修谱演进情形。从民间家族修谱的作用看,族谱一方面固然是为了正本清源,团结与凝集族人,但另一方面,却也是家族向社会显示势力与地位的一种表现形式。而自明清以来,这后一种社会作用日益显示岀它的重要性。因此,民间在修纂大型族谱的基础上,对不同地域内的同姓族谱进行联纂,以及许多跨府县、跨省份的超大型宗谱、世谱、统谱等,也大都在清代陆续出现。
超地域的宗谱、联谱的出现,与士绅人物的社会活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一般的老百姓,既无充足的经济能力和活动机会,更不具备联合各族共襄大举的社会号召力。士绅人物则不同,他们在官场上一方面可以借助联宗统谱来加强自身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生命力,另一方面则因这些士绅人物有着较为广泛的社会交游和声望地位,修纂超地域的宗谱、联谱,自然非他们倡导不可。举福建的李姓为例。清代康熙年间,福建泉州安溪出了一位大学士李光地,号称“理学名臣”,福建其他地方的李氏家族多引以为荣。于是,许多李姓家族纷纷请李光地为族谱撰词作序,联宗认亲。其中,汀州李氏与泉州李氏本无联系,但自李光地始,两地李姓互认宗亲,视为同一血缘。汀州府《李氏族谱》载有李光地撰写的一篇序言云: 余巡抚山东时,有汀杭同宗兵部候推都司佥事友琦,因抵京谒选,便来署谒余。予见其气宇卓荦,举止从容,知其渐磨于诗礼者已深也。复细询其家世,则与吾同出陇西,实宋宰相纲公之后。予既友琦为之同宗,又见其雍然儒雅,大可人意,遂留住数月,不离左右。次年,予左迁,友琦亦返梓,自是相隔者数年。今岁孟秋七月,予仰邀皇上天恩,由吏部尚书协办,晋秩文华殿大学士。友琦不远数千里,挟其族人声卿、昆林等所编次儒溪李氏家谱副本,来京请序于余。 余于公暇,细为披阅。…… 余维天下之生也,蜂蚁之于君臣,虎狼之于父子,莫不有自然之经纶分梳合贯于其间,而无所〓乱,则人道大愈可知矣。宗法所以维人道也,谱法所以维宗法也。窃仰观而得知吾李之由来矣,…… 天下之李,举无非一人之分形矣。敢以吾居泉,友琦居汀,遂有异视哉! 吾愿友琦勉求,所以齐家之意,归以告族人,使咸知谱法之所系非小,则不远千里之辛苦,可以不负,即吾亦乐观其后云。[26] 汀州李氏士绅与李光地如此一联络,认定双方的祖先都是岀自唐李宗室。于是,这两地本来互不相干的李氏家族,冠冕堂皇地联宗起来。汀州李氏家族的士绅们舍近求远,不到近在本省的安溪去请李氏族人联宗写序,却不远数千里到北京勉求李光地作序,无非是为了借助李光地的名望而提高本家族的社会地位。这也正是清代福建民间家族大量出现认宗联谱现象的关键所在。
福建民间家族修纂族谱虽然大体存在着从简易家谱——大型族谱——跨地域的联宗统谱的演进过程,但这种演进必须具备相应的经济实力和族人的社会影响力。而许多一般的中、小家族,则往往无法做到这一点。因此,到清代后期和民国时期,福建各地族谱虽然不乏像《王氏宗谱》、《林氏宗谱》、《黄氏世谱》、《陈氏大宗谱》、《朱氏通谱》这样的大型宗谱和贯穿数十个支派的大联谱,册数达数十本、近百本之多。但同时也仍然存在着许多体例简易、规模较小的家谱、族谱。这种小型的家谱、族谱,或只记载本族的源流、迁移过程和罗列简单的世系表,或像记流水帐似的把列代祖先和后裔子孙的名字一一胪列。有些小型的族谱,并无严格的编撰规定,一部传藏的手写家谱,可以保存百年乃至数百年之久,前人草创之后,后代子孙一次又一次地在编末添上新近的世系。而有些小型族谱,又类似于家族的大事年表,在列代祖孙继传的世系之旁,偶尔随心所欲地记述一些与家族发展相关的事件。随着宋元以来人口的不断繁殖和家族的扩散外移,同一家族的支派、房头也越来越多,而那些分支出来的族人,在新居地形成新的家族之后,又开始撰写各自的族谱。因此,从数量上讲,这种规模小型、体例简约的族谱、家谱,仍然在福建族谱总量中占有多数。
统谱的另一种形式,实际上是同一姓氏的联合谱,收进这种统谱的同姓人,其先祖并不一定都有直系的血关系。如晋江《董氏大成宗谱》,把天下各地董姓收入谱内,所谓“河间派,董仲舒迁居;临川派,董晋公扩源;湖溪派,董仲三金公;临湘派,董旭一公;云南派,董旭二公;广昌派,董谋公;浙江派,董思敬;广东派,董言公;……”[16]。 再如安溪《谢氏总谱》,除了收载泉州一带的谢氏族人外,也把南中国的许多谢氏均认为同宗而收载入谱,所谓“吾族得姓之始本姜姓,神农之后申伯,为周宣王之舅,受封于谢”,“申伯公所流而传哉,一本万殊,万殊一本,寻源溯流,自必由周而汉而晋而齐而梁而隋而唐而宋而元明,原原本本,班班可考矣。……吾谢英裔共培祖德,齐笃宗盟,广搜联络,大会成篇,爰订此血脉志,以为探祖问宗者循溯之基、会合之柄云”[17]。至于有些笼括全国同一姓氏的大统谱,其血缘关系更加稀疏,如民国时期撰修的《吴氏全国大统宗谱》,共收进吴氏各支派达“五百零三支”[18]。光绪年间编修的《章氏会谱》,“齐联福建江西两浙诸族,于世表外,著有郡县地望分支系图,于各族派别一览了然”[19]。
福建民间族谱虽然有以上种种类型,但从谱牒历史的发展轨迹来考察,这些类型的谱牒,并非同时出现的,而是大体经历了一个简易家谱——家谱、族谱、支谱、房谱细分化——宗谱、统谱等联宗合纂的演进过程。
宋元时期的福建族谱,现在虽然已不可见,但从当时福建民间修纂族谱推崇欧阳修和苏洵的谱图、谱式的情景来推测,则宋代福建的民间族谱,其体例和规模尚不至过于复杂[20]。
明代福建民间撰修的族谱,至今流传下来的也不多。但就笔者所见,其时族谱的修纂,还大多局限于一族一地,族谱的规模尚小,体例也比较简单不一,跨地域和跨家族的大型宗谱、统谱尚属少见。这里,试举泉州地区的陈、林二部族谱为例。
泉州《梅溪陈氏族谱》,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由该家族九世孙、进士陈学伊纂修。族谱共分上、下二卷。陈学伊在《前序》中写道:“余分责诸子弟检订旧谱,缀次新支,而裁之以独见,凡十年而始成新谱。谱凡上、下二卷,有总序,有义例,有世系图,有世传,有纶音,有年次,有外谱,有居室坟墓考,有祠堂记,有祭法,有大小宗祀田记,有义田公田记,有谱训,有立后解、家难考等纪。以万历丁亥之春缮写成书,告之家庙”[21]。虽然说陈学伊纂修的族谱包含了以上这么多内容,但我们翻阅该族谱时便可发现,陈学伊在记载这些内容时,都比较简单,远不如后代的族谱那样连篇累牍,因此整部族谱的篇幅不大,现传仅为抄本二册[22]。
同安《林氏族谱》,系明正德进士、名儒林希元所撰。该族谱为不分卷本,所载内容除世纪、世系图外,还有诸林宗派、得姓源流、家训、祭土地文、物产、麝圃垠等,记述也都比较简略,体例没有一定的规则。如其中《物产》一节,仅记如下数行文字:“物产者,可生之业,人所赖衣食以生者也。林氏散居四方,显晦贫富不一。予族居翔风里十三都为名族,田园虽少,犹足课子力耕,免于饥寒。自屯叟至予之孙完,凡六世,颇能克扩,不能悉书。姑即其关于门户之盛衰者书之,以示子孙,俾世守而勿失焉”[23]所以尽管族谱所包含的项目不少,但内容简略,总共不过薄薄的一小册。
以上两部族谱均修撰于明代嘉靖(公元1522——1566年)、万历(公元1573——1620年)年间的繁盛时期,作者又都是进士出身,但族谱的规模都比较小,体例的设计也颇为随心所欲。由花可以推见明代的福建民间族谱,一般都还比较简略。再如《兴化谷目村陈氏族谱》,明代崇祯年间撰修,仅有一册,分两部分:一为世系,一为传记,再无其他内容[24]。即使是福建的名族朱(熹)氏的族谱,其在明代万历庚申(公元1620年)撰修的《建安谱》,也比较简单。卷除了朱熹、真德秀的两篇序言和万历庚申修谱序外,正文共分十款:会元、尚像、世系、褒典、实录、象赞、丘陇、祠院、渊源、留题,整部族谱只有上下二册。
清代康、雍、乾时期(公元1662-1795年),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口增长以前所未有的势态发展。人口的迅速增长,一方面造成清代中后期生存环境的恶化,社会竞争日趋激烈,另一方面也加速了民间各家族的内部膨胀与扩散外迁。于是,原有的族谱规模和编写体例已不能适应这一时期社会与人口的急剧变迁。有经济能力和文化条件的强宗大族们,在清代兴起了修纂大型族谱的热潮。连城文川李氏家族自明至清历次纂修族谱的变化, 颇能反映这一趋向。该族谱载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文川城南李氏四刻族谱序》云:我祠族谱创自前明九世祖中孚公笔记,越正德丁丑(按:公元1517年),十二世元瑫公遂仿欧、苏氏例为合族总图、五世分宗图。迨万历己丑(按:公元1589年),十四世学诜公乃本黄氏族谱横图摹仿而增益之,即今所传之谱法是也。继此而十五世涵公等复于崇祯九年(按:公元1636年)起而续修,将缺者补、新者入,一时灿然称明备。厥后已历百有余载,诚有当续而无续者矣,纵各房间有私纂,然或详或略,不无互异。且从前俱系缮本,而别风淮雨亦未免传疑。至我朝乾隆丙辰(按:公元1736年),经十八代一韩公等取原本,采彼遗文,访诸故老,博览兼收,搜罗罔佚,始付诸剞劂,是为初刻。及庚寅(按:公元1770年)当再刻之期,亦曾十刻八九,究未完善。惟十九代德新公、大苏公等于嘉庆己未(按:公元1799年)间开局以为三刻,当是时,探讨无遗,校雠尽善,洵为一族之成书焉。嗣历三十载为道光己丑(按:公元1829年),时当四刻,众议续修。……于是在祠经理裔孙长房赞宗、德思,次房绣彩、名标,三房开乔、绍安,爰集三大房绅耆合议,众咸踊跃乐从。维时经众佥举在祠襄事,始终不惜勤劳,……而文学、世翰诸纪则命德恕一人总纂而校正之。但近来族大人繁,各逞意见,内中序传志铭虽不无冗杂失然,然揆其铺张扬励之心,要不失为尊亲之意,亦无恶也。……是役也,经始于甲辰(按:公元1844年)初秋,告竣于丙午(按:公元1846年)暮春,阅廿一月而蔵事,由总图世系至前后编,原止四十八卷,今增为五十余卷云。[25]从这篇序文中可以看出,连城文川李氏虽然早在明代中期就已开始撰写族谱,但其最初的形式只是“笔记”而已,正德、万历、崇祯年间虽然历经三修,但也仅是“将缺者补、新者入”,属于手抄缮本。一直到了清代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随着族人的繁衍和族谱的扩大,“始付诸剞劂,是为初刻”,其后每过三四十年重修重刻一次,至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已经四刻, 并且规模一次比一次增大,成了五十余卷、数十本之多的大型族谱。
连城文川李氏家族的修谱历程,大体能够反映清代福建民间家族的一般修谱演进情形。从民间家族修谱的作用看,族谱一方面固然是为了正本清源,团结与凝集族人,但另一方面,却也是家族向社会显示势力与地位的一种表现形式。而自明清以来,这后一种社会作用日益显示岀它的重要性。因此,民间在修纂大型族谱的基础上,对不同地域内的同姓族谱进行联纂,以及许多跨府县、跨省份的超大型宗谱、世谱、统谱等,也大都在清代陆续出现。
超地域的宗谱、联谱的出现,与士绅人物的社会活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一般的老百姓,既无充足的经济能力和活动机会,更不具备联合各族共襄大举的社会号召力。士绅人物则不同,他们在官场上一方面可以借助联宗统谱来加强自身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生命力,另一方面则因这些士绅人物有着较为广泛的社会交游和声望地位,修纂超地域的宗谱、联谱,自然非他们倡导不可。举福建的李姓为例。清代康熙年间,福建泉州安溪出了一位大学士李光地,号称“理学名臣”,福建其他地方的李氏家族多引以为荣。于是,许多李姓家族纷纷请李光地为族谱撰词作序,联宗认亲。其中,汀州李氏与泉州李氏本无联系,但自李光地始,两地李姓互认宗亲,视为同一血缘。汀州府《李氏族谱》载有李光地撰写的一篇序言云: 余巡抚山东时,有汀杭同宗兵部候推都司佥事友琦,因抵京谒选,便来署谒余。予见其气宇卓荦,举止从容,知其渐磨于诗礼者已深也。复细询其家世,则与吾同出陇西,实宋宰相纲公之后。予既友琦为之同宗,又见其雍然儒雅,大可人意,遂留住数月,不离左右。次年,予左迁,友琦亦返梓,自是相隔者数年。今岁孟秋七月,予仰邀皇上天恩,由吏部尚书协办,晋秩文华殿大学士。友琦不远数千里,挟其族人声卿、昆林等所编次儒溪李氏家谱副本,来京请序于余。 余于公暇,细为披阅。…… 余维天下之生也,蜂蚁之于君臣,虎狼之于父子,莫不有自然之经纶分梳合贯于其间,而无所〓乱,则人道大愈可知矣。宗法所以维人道也,谱法所以维宗法也。窃仰观而得知吾李之由来矣,…… 天下之李,举无非一人之分形矣。敢以吾居泉,友琦居汀,遂有异视哉! 吾愿友琦勉求,所以齐家之意,归以告族人,使咸知谱法之所系非小,则不远千里之辛苦,可以不负,即吾亦乐观其后云。[26] 汀州李氏士绅与李光地如此一联络,认定双方的祖先都是岀自唐李宗室。于是,这两地本来互不相干的李氏家族,冠冕堂皇地联宗起来。汀州李氏家族的士绅们舍近求远,不到近在本省的安溪去请李氏族人联宗写序,却不远数千里到北京勉求李光地作序,无非是为了借助李光地的名望而提高本家族的社会地位。这也正是清代福建民间家族大量出现认宗联谱现象的关键所在。
福建民间家族修纂族谱虽然大体存在着从简易家谱——大型族谱——跨地域的联宗统谱的演进过程,但这种演进必须具备相应的经济实力和族人的社会影响力。而许多一般的中、小家族,则往往无法做到这一点。因此,到清代后期和民国时期,福建各地族谱虽然不乏像《王氏宗谱》、《林氏宗谱》、《黄氏世谱》、《陈氏大宗谱》、《朱氏通谱》这样的大型宗谱和贯穿数十个支派的大联谱,册数达数十本、近百本之多。但同时也仍然存在着许多体例简易、规模较小的家谱、族谱。这种小型的家谱、族谱,或只记载本族的源流、迁移过程和罗列简单的世系表,或像记流水帐似的把列代祖先和后裔子孙的名字一一胪列。有些小型的族谱,并无严格的编撰规定,一部传藏的手写家谱,可以保存百年乃至数百年之久,前人草创之后,后代子孙一次又一次地在编末添上新近的世系。而有些小型族谱,又类似于家族的大事年表,在列代祖孙继传的世系之旁,偶尔随心所欲地记述一些与家族发展相关的事件。随着宋元以来人口的不断繁殖和家族的扩散外移,同一家族的支派、房头也越来越多,而那些分支出来的族人,在新居地形成新的家族之后,又开始撰写各自的族谱。因此,从数量上讲,这种规模小型、体例简约的族谱、家谱,仍然在福建族谱总量中占有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