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移民人数、成份及迁徙原因
| 内容出处: | 《闽台关系族谱资料选编》 图书 |
| 唯一号: | 131020020210001143 |
| 颗粒名称: | 二、移民人数、成份及迁徙原因 |
| 分类号: | K810.2 |
| 页数: | 10 |
| 页码: | 4-13 |
| 摘要: | 大陆向台湾的移民,历来以闽人居多;闽人之中,又以泉、 漳二府各县为最。据1926年的调查,全台湾汉族居民共三百七十五万一千入,祖籍福建者达三百一十余万,占百分之八十三强。其中,泉州府各县占百分之四十四点八,漳州府各县占百分之三十五点一。据吴壮达《台湾的开发》一书的分析,形成这种地域来源特殊集中的主要原因,乃在于地理位置的接近和历史关系的密切,尤其是明末清初郑芝龙、郑成功对台湾的开发,以及后来历时逾二百年的闽台合治制度。我们仅从七十余部族谱中发现的迁台者姓名,巳近四千人之多。而这尚未包括那些笼统记载“族人分居台湾”,“此派子孙均移住台湾”,以及近代的一些统计数字。此次移民之主要成份,显系沿海一带饥民。 |
| 关键词: | 移民 人数 台湾 |
内容
大陆向台湾的移民,历来以闽人居多;闽人之中,又以泉、 漳二府各县为最。据1926年的调查,全台湾汉族居民共三百七十五万一千入,祖籍福建者达三百一十余万,占百分之八十三强。 其中,泉州府各县占百分之四十四点八,漳州府各县占百分之三十五点一。据吴壮达《台湾的开发》一书的分析,形成这种地域来源特殊集中的主要原因,乃在于地理位置的接近和历史关系的密切,尤其是明末清初郑芝龙、郑成功对台湾的开发,以及后来历时逾二百年的闽台合治制度。
我们仅从七十余部族谱中发现的迁台者姓名,巳近四千人之多。其中,晋江《玉山林氏宗谱》和《安溪参内二房黄氏族谱》, 均达一千人左右,说明移民人数确实很多。而这尚未包括那些笼统记载“族人分居台湾”,“此派子孙均移住台湾”,以及近代的一些统计数字。表格中数字,也包括那些在台出生的移民后代在内。从族谱记载可以知道,乾、嘉之前,移民的大多数系新自大陆迁徙而来;道光之后,新移民巳渐少,而原移民生传子女,则迅速增加, 成为多数。虽然,这个数字距历代移民的总数,相去甚远,但它所表现的从郑芝龙时期到清乾、嘉时期移民人数逐步发展的趋势, 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在台湾移民史上,明末郑芝龙据台时期、清初郑成功复台以后的郑氏政权时期和清政府统一台湾以后的康、雍、乾、嘉时期,是三个最重要的时期。史学界把这三个时期出现的大陆人民大批迁移台湾进行开发的情况,称为三次移民高潮。
第一次移民高潮明天启间,以颜思齐、郑芝龙为首的海上资本集团占据台湾北港时,适值福建沿海患旱,泉、漳一带贫民竞相奔往,人数不下三千余。崇祯元年郑芝龙归降明政府,又值福建饥荒,郑氏在福建巡抚熊文灿的支持下,即招集沿海灾区饥民数万入移台开垦。“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船舶载至台湾,令其芟舍开垦荒土为田。厥土惟上上,秋成所获,倍于中土。”这是破天荒第一次有组织的向台湾移民,郑芝龙对开发台湾的重大贡献,其功绩实不可泯灭。
此次移民之主要成份,显系沿海一带饥民。据族谱记载,晋观的开发大军。因此,在郑氏政权存在的短短二十三年中,台湾人口激增,开垦面积迅速扩大,社会经济飞跃发展起来了。
这支开发大军的主体,仍然是福建沿海的泉、漳各县人民。 从数量上看,除了郑氏部队外,更为大量的还是被迫“迁界”的入民。自顺治末年起,清政府为禁绝沿海人民对郑成功的支援, 开始实行野蛮的“迁界”政策,下令北起辽东,南至广东,所有各省沿海三十里居民一律迁居内地,并严禁船只出海,于沿海地区发兵戍守,犯者处死。这种极端残酷的政策,使沿海人民遭受了一场空前悲惨的大劫难。据族谱记载:“(晋江县东石郭岑村)迨至大清顺治庚子十七年 (1660),兵燹,迁都,门庭鞠为茂草,堂阶尽属秽荒,父子兄弟,流离失所。”(《东石汾阳郭氏族谱》)“(晋江县衙口乡)辛丑顺治十八年(1661)秋,沿海迁界,颠沛流离,虽至亲不能相保。”(《温陵浔海施氏大宗族谱》)“(晋江县石壁乡)际播迁之日,厥居拆毁,荒村灶冷。亲而壮者,散于四方;疏而老者,丧于沟壑。” “(林姓)子姓散处四方者,不知凡几。”(《玉山林氏宗谱》)“(同安县集美村)清朝康熙二年(1663),被大兵进剿,(陈姓)阖族裔孙数千口,失散越国者,不知去向。”(《同安集美陈氏族谱》)“(漳浦县沙岗村)继以清初郑国姓凭海为巢穴,本朝以迁界绝其交接,(蒲姓)宗族居址皆属海滨地区,是以流离逃散。”(《诏安蒲氏家谱》)此种惨况,见诸族谱,实难枚举。于是,无家可归的广大沿海居民,一部分被迫迁徙内地,一部分出洋东南亚国家谋生,一部分则渡过海峡,参加到郑氏政权开发台湾的行列中去。据史学家估计,当时来自大陆的移民当不下二十万之多。
族谱所反映的这一移民趋势,不惟人数比前增加,且多数均来自上述沿海地区的“界外”村镇(其中安海颜、黄二姓十三名,占27%。据《安海志》载,当时安海“迁界”最惨,除龙山寺外,余尽废墟),正说明“迁界”乃造成第二次移民高潮的重要社会原因之一。
从有限的资料中,我们至少还可以看出如下一些情况:移民携眷同往者五人,在台婚娶者四人。如东石郭岑村郭一星(乳名四,号厚斋)偕室吴氏;郭一程(乳名双,号毅斋)偕室林氏、继室吴氏同往,说明台湾妇女在逐渐增多。
移民有举家迁徙者,如永宁高祐。谱云:"九世公祐,生崇祯甲申年(1646),卒庚寅年(1710)o娶蔡氏。生男一。甲辰年(1664),搬住台湾。”(《永宁霁霞高氏家谱》)移民有携眷往台后又孤身到南洋去,而卒于异国者,如永宁高印柱。谱云:“九世印柱,生崇祯戊寅年(1638),卒康熙辛巳年 (1701),殁于番邦。娶陈氏,生崇祯癸未(1643),葬在台湾。”(《永宁霁霞高氏家谱》)族谱记载移民的死葬地点,有:鬼仔山(一人)、台湾府演武亭前(一人)、台湾大南门外下林仔(三人)、郡东门外观音亭(一人)、承天府演武亭山(一人)、洲仔尾(一人)、凤山伶舍埠(二人)、凤山庄槺榔林(一人)、诸罗赤山(一人)、 淡水北势湖海岛(一人)。表明这时期的移民均集中在西部沿海一带,而以台南为多。
-第三次移民高潮1683年郑氏政权结束以后,政治上统一的局面,给海峡两岸的各种联系和台湾的进一步开发都带来了新的积极的因素。尽管清政府在初期采取了一系列严厉而愚蠢的限制政策,但大陆人民,尤其是一水之隔的福建人民,还是相继不绝地涌向彼岸去。一场由南到北、由西到东的垦殖运动,在台湾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这次规模空前的移民高潮,在康、雍年间, 已能见到最初的浪头,至乾、嘉年间,则达到最高峰。据《台湾通史》的估计,到嘉庆十六年(1811),全台湾的汉族人口巳超过二百万。
族谱资料在如下几个方面,为这一时期的移民运动,提供了很好的说明:一是移民人数。七十余部族谱所载,从康熙二十二年(1683) 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移民达一千六百人,约占总人数的一半以上。(无生年未统计者除外)其中,康、雍时期一百八十人,乾、嘉时期一千四百人,其发展趋势十分明显。再从迁台人数最多的晋江石壁乡林姓来看,该族于郑氏政权时往台者二人, 康、雍时三十二人,乾、嘉时即增至二百九十人。安溪参内黄姓的情况亦如是:郑氏政权时三人,康、雍时二十四人,乾、嘉时遂遽增至二百人。这种情况甚为普遍。还有一些族姓,如晋江永宁鳌西林姓、泉州龙笋曾姓等,甚至是到了乾隆后期,才开始他们的迁台史的。
为什么这次移民运动,在康、雍时期的半个多世纪中,发展速度尚如此之缓慢?这完全是由于清政府统一台湾以后实行的所谓“为防台而治台”的错误方针导致的。我们知道,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五十八年(1719)和雍正七年(1729),清政府曾三次严申禁令,企图堵绝沿海人民偷渡入台。此禁令又经乾隆初年的三行三弛,至乾隆二十五(1760)以后,在移民运动的冲击下,限制政策始归于失败。这就是为什么此次移民高潮会迟至乾、嘉时期,认真地说是乾隆中期以后才真正形成的重要原因。我们还注意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清政府开放台湾鹿港与泉州蜡江港对渡,五十七年(1792)又开放淡水河口的八里岔与蚶江及福州五虎门对口通航,这个措施,不仅对闽台经济关系的进_步密切,而且对移民高潮的迅速形成,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蚶江港开放以后,很快便成为泉州对台交通的中心,一时 “大小商渔,往来利涉,其视鹿仔港,直户庭耳”,因而出现了 “群趋若鹫”的局面。(《新建蜡江海防官署碑记》)禁令之废弛,蚶江之开放,大大有利移民的迁徙活动。在晋江县南部,尤其是蚶江附近农村,迁台人数所以会特别多,这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兹就该县几部主要族谱记载的迁台大约人数列表于下,以资说明:二是移民特点。兄弟相率,夫妻同往,甚至举家迁徙现象的普遍出现,是这时期移民运动的特点之一。在各姓族谱中都能找到这样的记载。以安溪县参内黄姓为例:该姓从康熙末年以后移居台湾的族人中,父子同往者计二十九,兄弟同往者计十七(人数不等),夫妇同往者四十四对,全家同往者三十家。这种情况说明台湾的开垦所给予劳动者的利益,越来越吸引着大陆失掉土地或缺乏土地的人们。就参内黄姓而言,人多地少,始终是这里的一个严重问题,因而他们只有往台湾和南洋去寻找出路。(此时期参内黄姓往南洋者,也多至数百人)单身移民往台后娶妻、建立家庭现象的普遍出现,是这时期移民运动的又一特点。以晋江东石蔡氏长房三延科派迁移台湾的族人为例:从乾隆年间开始,在台娶妻者八十人,在台继娶者九人。
“世构,号纯朴,往台南路竹仔港汕岸顶居住。生乾隆二十四年(1759),卒嘉庆十八年(1813) 。在台娶三块厝许氏女,名澄娘,号纯慈。生乾隆三十四年(1769),卒道光十一年(1831),墓葬坎脚。生男四。”“文荣,号惠良。住布袋嘴庄。生乾隆四十一年(1776), 卒道光二十五年(1845)。先娶龙蚊郑氏女,名座娘;继娶新庄刘氏女,名密娘。承男一。”“文挺,住鹿港庄。在唐先娶苏氏女,名俭娘,早殁; 在台再娶某氏女,名溅娘。生男一。”“章蜡,号章纯。生嘉庆十八年(1813),卒同治二年 (1863),在台身故,葬五股。娶下村乡张却娘,又在台娶侧室陈香炽。养男四,生男一。”这说明,早期那种妇女奇缺、移民性别不平衡的状态,至此时已经结束。而移民家庭的建立,则使农业生产的发展,有了一个更坚实的基础。
三是移民成份。随着迁台人数的发展,移民的成份也复杂起来了。当然,农民始终是移民大军的主体,对此族谱虽不特别注明,但完全可以判断。除此之外,在族谱资料中,尚可看到商人、官吏、士兵、知识分子、城市平民、医生、店员、手工业者、僧侣等等,也都参加到移民的行列中来。他们构成了台湾社会的各个阶层,其意义无疑也是十分重要的。
下表数字,系根据族谱有注明身份者统计的,这里着重分析一下知识分子移台问题。康熙二十二年(1683) 清政府统一台湾后,始立府、县学,岁科试以取生员。定例府学岁进文武童各二十名,科进文童二十名,癝膳二十名,增广如之。县学定额稍减。但因草莱初辟,文化落后,故入泮较为容易。这给那些屡困科场的大陆诺县(尤其是泉、漳二府)学子们,带来了获取秀才资格的好机会,于是东渡求进学者,十分普遍。晋江县林宏礼(字孙敬,号省庵,官名名世。生康熙十九年,卒乾隆二十年)即为典型一例。他少年时“迨屡试晋水,久困莫售,……爰喟然叹曰:‘……何不可遨游东宁,聊托一试?' 于是登堂拜别,羁迹台湾,凡御史观风月课,以逮府县两试,其夺矛试艺,几于累牍。果也,文宗吴昌祚公岁取入泮。”(《玉山林氏宗谱》)又南安蓬岛郭姓移居台湾的家族,从十九世至二十三世,约当十八、十九世纪的一百多年中,共有十九人在台湾进学为秀才。(《蓬岛郭氏家谱》)不少移民于台湾进秀才后,即转回原籍,参加乡试。如晋江县从乾隆元年<1736)至二十年(1765),共有十名举人是台湾的秀才考中的。(《晋江县志》)龙溪县从康熙三十二年(1693) 至乾隆十六年(1751),也有十六名贡生原是台湾秀才。(《龙溪县志》)闽台文化关系之密切,于此可见一斑。
尚须指出,不少知识分子渡台任塾师,以及一些清廉的学官,对于传播文化知识,发展教育事业,都曾做过贡献。这方面地志记载颇多,兹引族谱中两例以作补充:清末著名状元、晋江人吴鲁的儿子吴钟善(光绪癸卯经济特科,廷试二等),曾应林姓之聘,渡台课授经文,并在台刊印其父的《正气研斋汇稿》及《百哀诗》。(吴增撰《清故徵君顽陀吴君墓志铭》)福州人陈平皋于嘉庆十二年(1817)调任台湾嘉义县学,见 “台地赌风甚炽,樗蒲辈藉学宫为逋逃薮,胥斗因而滋奸”,即 “令尽驱博徒,整肃学规,悉除陋习,分毫无所取,以故去任而行橐萧然”。(福州《颍州陈氏族谱》〉
我们仅从七十余部族谱中发现的迁台者姓名,巳近四千人之多。其中,晋江《玉山林氏宗谱》和《安溪参内二房黄氏族谱》, 均达一千人左右,说明移民人数确实很多。而这尚未包括那些笼统记载“族人分居台湾”,“此派子孙均移住台湾”,以及近代的一些统计数字。表格中数字,也包括那些在台出生的移民后代在内。从族谱记载可以知道,乾、嘉之前,移民的大多数系新自大陆迁徙而来;道光之后,新移民巳渐少,而原移民生传子女,则迅速增加, 成为多数。虽然,这个数字距历代移民的总数,相去甚远,但它所表现的从郑芝龙时期到清乾、嘉时期移民人数逐步发展的趋势, 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在台湾移民史上,明末郑芝龙据台时期、清初郑成功复台以后的郑氏政权时期和清政府统一台湾以后的康、雍、乾、嘉时期,是三个最重要的时期。史学界把这三个时期出现的大陆人民大批迁移台湾进行开发的情况,称为三次移民高潮。
第一次移民高潮明天启间,以颜思齐、郑芝龙为首的海上资本集团占据台湾北港时,适值福建沿海患旱,泉、漳一带贫民竞相奔往,人数不下三千余。崇祯元年郑芝龙归降明政府,又值福建饥荒,郑氏在福建巡抚熊文灿的支持下,即招集沿海灾区饥民数万入移台开垦。“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船舶载至台湾,令其芟舍开垦荒土为田。厥土惟上上,秋成所获,倍于中土。”这是破天荒第一次有组织的向台湾移民,郑芝龙对开发台湾的重大贡献,其功绩实不可泯灭。
此次移民之主要成份,显系沿海一带饥民。据族谱记载,晋观的开发大军。因此,在郑氏政权存在的短短二十三年中,台湾人口激增,开垦面积迅速扩大,社会经济飞跃发展起来了。
这支开发大军的主体,仍然是福建沿海的泉、漳各县人民。 从数量上看,除了郑氏部队外,更为大量的还是被迫“迁界”的入民。自顺治末年起,清政府为禁绝沿海人民对郑成功的支援, 开始实行野蛮的“迁界”政策,下令北起辽东,南至广东,所有各省沿海三十里居民一律迁居内地,并严禁船只出海,于沿海地区发兵戍守,犯者处死。这种极端残酷的政策,使沿海人民遭受了一场空前悲惨的大劫难。据族谱记载:“(晋江县东石郭岑村)迨至大清顺治庚子十七年 (1660),兵燹,迁都,门庭鞠为茂草,堂阶尽属秽荒,父子兄弟,流离失所。”(《东石汾阳郭氏族谱》)“(晋江县衙口乡)辛丑顺治十八年(1661)秋,沿海迁界,颠沛流离,虽至亲不能相保。”(《温陵浔海施氏大宗族谱》)“(晋江县石壁乡)际播迁之日,厥居拆毁,荒村灶冷。亲而壮者,散于四方;疏而老者,丧于沟壑。” “(林姓)子姓散处四方者,不知凡几。”(《玉山林氏宗谱》)“(同安县集美村)清朝康熙二年(1663),被大兵进剿,(陈姓)阖族裔孙数千口,失散越国者,不知去向。”(《同安集美陈氏族谱》)“(漳浦县沙岗村)继以清初郑国姓凭海为巢穴,本朝以迁界绝其交接,(蒲姓)宗族居址皆属海滨地区,是以流离逃散。”(《诏安蒲氏家谱》)此种惨况,见诸族谱,实难枚举。于是,无家可归的广大沿海居民,一部分被迫迁徙内地,一部分出洋东南亚国家谋生,一部分则渡过海峡,参加到郑氏政权开发台湾的行列中去。据史学家估计,当时来自大陆的移民当不下二十万之多。
族谱所反映的这一移民趋势,不惟人数比前增加,且多数均来自上述沿海地区的“界外”村镇(其中安海颜、黄二姓十三名,占27%。据《安海志》载,当时安海“迁界”最惨,除龙山寺外,余尽废墟),正说明“迁界”乃造成第二次移民高潮的重要社会原因之一。
从有限的资料中,我们至少还可以看出如下一些情况:移民携眷同往者五人,在台婚娶者四人。如东石郭岑村郭一星(乳名四,号厚斋)偕室吴氏;郭一程(乳名双,号毅斋)偕室林氏、继室吴氏同往,说明台湾妇女在逐渐增多。
移民有举家迁徙者,如永宁高祐。谱云:"九世公祐,生崇祯甲申年(1646),卒庚寅年(1710)o娶蔡氏。生男一。甲辰年(1664),搬住台湾。”(《永宁霁霞高氏家谱》)移民有携眷往台后又孤身到南洋去,而卒于异国者,如永宁高印柱。谱云:“九世印柱,生崇祯戊寅年(1638),卒康熙辛巳年 (1701),殁于番邦。娶陈氏,生崇祯癸未(1643),葬在台湾。”(《永宁霁霞高氏家谱》)族谱记载移民的死葬地点,有:鬼仔山(一人)、台湾府演武亭前(一人)、台湾大南门外下林仔(三人)、郡东门外观音亭(一人)、承天府演武亭山(一人)、洲仔尾(一人)、凤山伶舍埠(二人)、凤山庄槺榔林(一人)、诸罗赤山(一人)、 淡水北势湖海岛(一人)。表明这时期的移民均集中在西部沿海一带,而以台南为多。
-第三次移民高潮1683年郑氏政权结束以后,政治上统一的局面,给海峡两岸的各种联系和台湾的进一步开发都带来了新的积极的因素。尽管清政府在初期采取了一系列严厉而愚蠢的限制政策,但大陆人民,尤其是一水之隔的福建人民,还是相继不绝地涌向彼岸去。一场由南到北、由西到东的垦殖运动,在台湾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这次规模空前的移民高潮,在康、雍年间, 已能见到最初的浪头,至乾、嘉年间,则达到最高峰。据《台湾通史》的估计,到嘉庆十六年(1811),全台湾的汉族人口巳超过二百万。
族谱资料在如下几个方面,为这一时期的移民运动,提供了很好的说明:一是移民人数。七十余部族谱所载,从康熙二十二年(1683) 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移民达一千六百人,约占总人数的一半以上。(无生年未统计者除外)其中,康、雍时期一百八十人,乾、嘉时期一千四百人,其发展趋势十分明显。再从迁台人数最多的晋江石壁乡林姓来看,该族于郑氏政权时往台者二人, 康、雍时三十二人,乾、嘉时即增至二百九十人。安溪参内黄姓的情况亦如是:郑氏政权时三人,康、雍时二十四人,乾、嘉时遂遽增至二百人。这种情况甚为普遍。还有一些族姓,如晋江永宁鳌西林姓、泉州龙笋曾姓等,甚至是到了乾隆后期,才开始他们的迁台史的。
为什么这次移民运动,在康、雍时期的半个多世纪中,发展速度尚如此之缓慢?这完全是由于清政府统一台湾以后实行的所谓“为防台而治台”的错误方针导致的。我们知道,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五十八年(1719)和雍正七年(1729),清政府曾三次严申禁令,企图堵绝沿海人民偷渡入台。此禁令又经乾隆初年的三行三弛,至乾隆二十五(1760)以后,在移民运动的冲击下,限制政策始归于失败。这就是为什么此次移民高潮会迟至乾、嘉时期,认真地说是乾隆中期以后才真正形成的重要原因。我们还注意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清政府开放台湾鹿港与泉州蜡江港对渡,五十七年(1792)又开放淡水河口的八里岔与蚶江及福州五虎门对口通航,这个措施,不仅对闽台经济关系的进_步密切,而且对移民高潮的迅速形成,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蚶江港开放以后,很快便成为泉州对台交通的中心,一时 “大小商渔,往来利涉,其视鹿仔港,直户庭耳”,因而出现了 “群趋若鹫”的局面。(《新建蜡江海防官署碑记》)禁令之废弛,蚶江之开放,大大有利移民的迁徙活动。在晋江县南部,尤其是蚶江附近农村,迁台人数所以会特别多,这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兹就该县几部主要族谱记载的迁台大约人数列表于下,以资说明:二是移民特点。兄弟相率,夫妻同往,甚至举家迁徙现象的普遍出现,是这时期移民运动的特点之一。在各姓族谱中都能找到这样的记载。以安溪县参内黄姓为例:该姓从康熙末年以后移居台湾的族人中,父子同往者计二十九,兄弟同往者计十七(人数不等),夫妇同往者四十四对,全家同往者三十家。这种情况说明台湾的开垦所给予劳动者的利益,越来越吸引着大陆失掉土地或缺乏土地的人们。就参内黄姓而言,人多地少,始终是这里的一个严重问题,因而他们只有往台湾和南洋去寻找出路。(此时期参内黄姓往南洋者,也多至数百人)单身移民往台后娶妻、建立家庭现象的普遍出现,是这时期移民运动的又一特点。以晋江东石蔡氏长房三延科派迁移台湾的族人为例:从乾隆年间开始,在台娶妻者八十人,在台继娶者九人。
“世构,号纯朴,往台南路竹仔港汕岸顶居住。生乾隆二十四年(1759),卒嘉庆十八年(1813) 。在台娶三块厝许氏女,名澄娘,号纯慈。生乾隆三十四年(1769),卒道光十一年(1831),墓葬坎脚。生男四。”“文荣,号惠良。住布袋嘴庄。生乾隆四十一年(1776), 卒道光二十五年(1845)。先娶龙蚊郑氏女,名座娘;继娶新庄刘氏女,名密娘。承男一。”“文挺,住鹿港庄。在唐先娶苏氏女,名俭娘,早殁; 在台再娶某氏女,名溅娘。生男一。”“章蜡,号章纯。生嘉庆十八年(1813),卒同治二年 (1863),在台身故,葬五股。娶下村乡张却娘,又在台娶侧室陈香炽。养男四,生男一。”这说明,早期那种妇女奇缺、移民性别不平衡的状态,至此时已经结束。而移民家庭的建立,则使农业生产的发展,有了一个更坚实的基础。
三是移民成份。随着迁台人数的发展,移民的成份也复杂起来了。当然,农民始终是移民大军的主体,对此族谱虽不特别注明,但完全可以判断。除此之外,在族谱资料中,尚可看到商人、官吏、士兵、知识分子、城市平民、医生、店员、手工业者、僧侣等等,也都参加到移民的行列中来。他们构成了台湾社会的各个阶层,其意义无疑也是十分重要的。
下表数字,系根据族谱有注明身份者统计的,这里着重分析一下知识分子移台问题。康熙二十二年(1683) 清政府统一台湾后,始立府、县学,岁科试以取生员。定例府学岁进文武童各二十名,科进文童二十名,癝膳二十名,增广如之。县学定额稍减。但因草莱初辟,文化落后,故入泮较为容易。这给那些屡困科场的大陆诺县(尤其是泉、漳二府)学子们,带来了获取秀才资格的好机会,于是东渡求进学者,十分普遍。晋江县林宏礼(字孙敬,号省庵,官名名世。生康熙十九年,卒乾隆二十年)即为典型一例。他少年时“迨屡试晋水,久困莫售,……爰喟然叹曰:‘……何不可遨游东宁,聊托一试?' 于是登堂拜别,羁迹台湾,凡御史观风月课,以逮府县两试,其夺矛试艺,几于累牍。果也,文宗吴昌祚公岁取入泮。”(《玉山林氏宗谱》)又南安蓬岛郭姓移居台湾的家族,从十九世至二十三世,约当十八、十九世纪的一百多年中,共有十九人在台湾进学为秀才。(《蓬岛郭氏家谱》)不少移民于台湾进秀才后,即转回原籍,参加乡试。如晋江县从乾隆元年<1736)至二十年(1765),共有十名举人是台湾的秀才考中的。(《晋江县志》)龙溪县从康熙三十二年(1693) 至乾隆十六年(1751),也有十六名贡生原是台湾秀才。(《龙溪县志》)闽台文化关系之密切,于此可见一斑。
尚须指出,不少知识分子渡台任塾师,以及一些清廉的学官,对于传播文化知识,发展教育事业,都曾做过贡献。这方面地志记载颇多,兹引族谱中两例以作补充:清末著名状元、晋江人吴鲁的儿子吴钟善(光绪癸卯经济特科,廷试二等),曾应林姓之聘,渡台课授经文,并在台刊印其父的《正气研斋汇稿》及《百哀诗》。(吴增撰《清故徵君顽陀吴君墓志铭》)福州人陈平皋于嘉庆十二年(1817)调任台湾嘉义县学,见 “台地赌风甚炽,樗蒲辈藉学宫为逋逃薮,胥斗因而滋奸”,即 “令尽驱博徒,整肃学规,悉除陋习,分毫无所取,以故去任而行橐萧然”。(福州《颍州陈氏族谱》〉
附注
以生年加二十年为迁台时间。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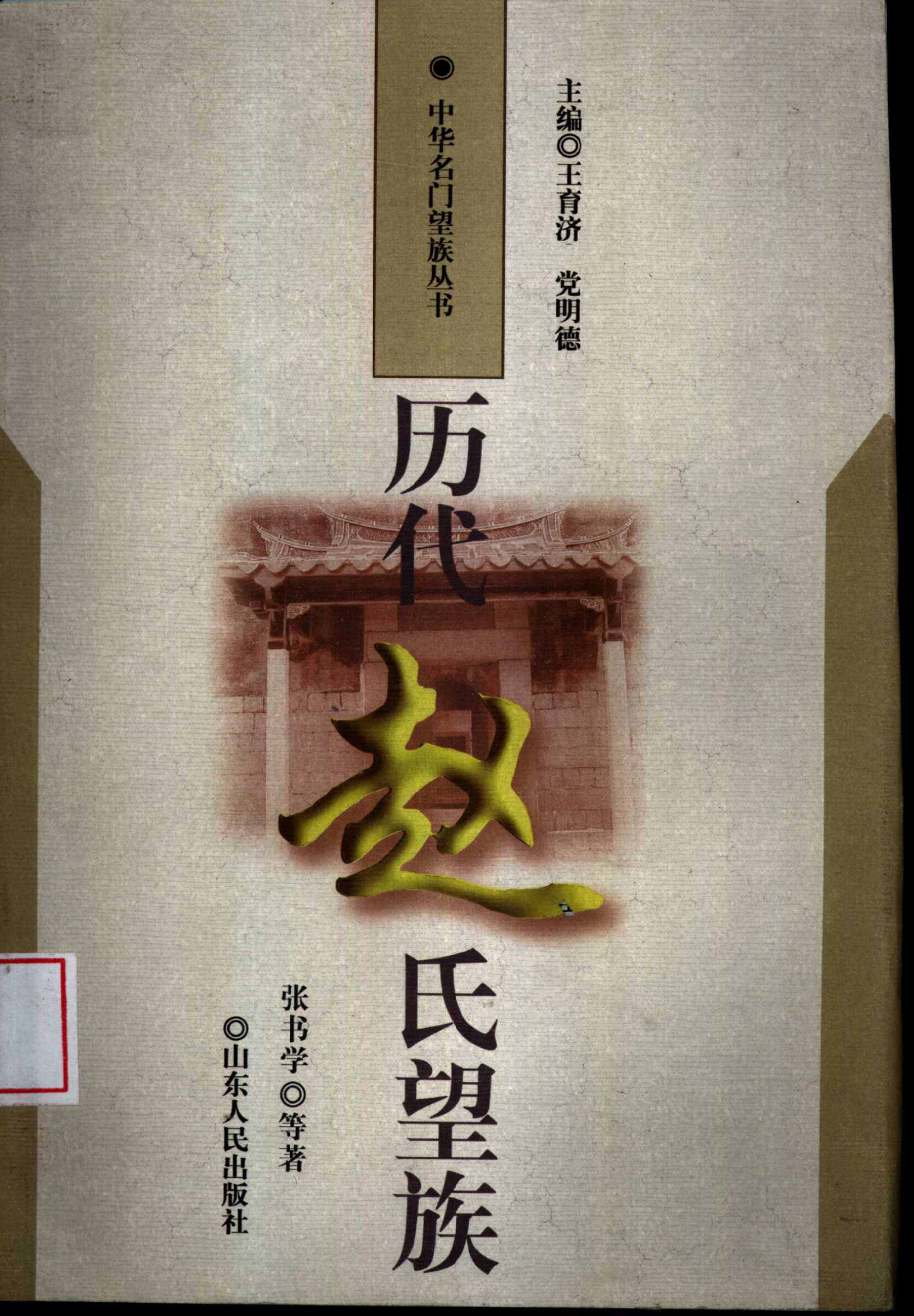
《闽台关系族谱资料选编》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本书考究有些姓氏在台湾的开基年代时,不应忘记他们先辈的足迹来到此地的时间,不知还要早多少年!早期的开拓者,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往往不带眷属,单入匹马,于荆棘丛莽中苦斗一生。这种情况,直至清初康、雍时代,犹甚普遍。从族谱看,移民携眷同往或在台婚娶者,在康、雍之前,占的比例很小,因而又形成这么一种情况: 被认定为某姓之开基祖者,跟他同时甚至更早往台者,还有很多。
阅读
相关地名
福建省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