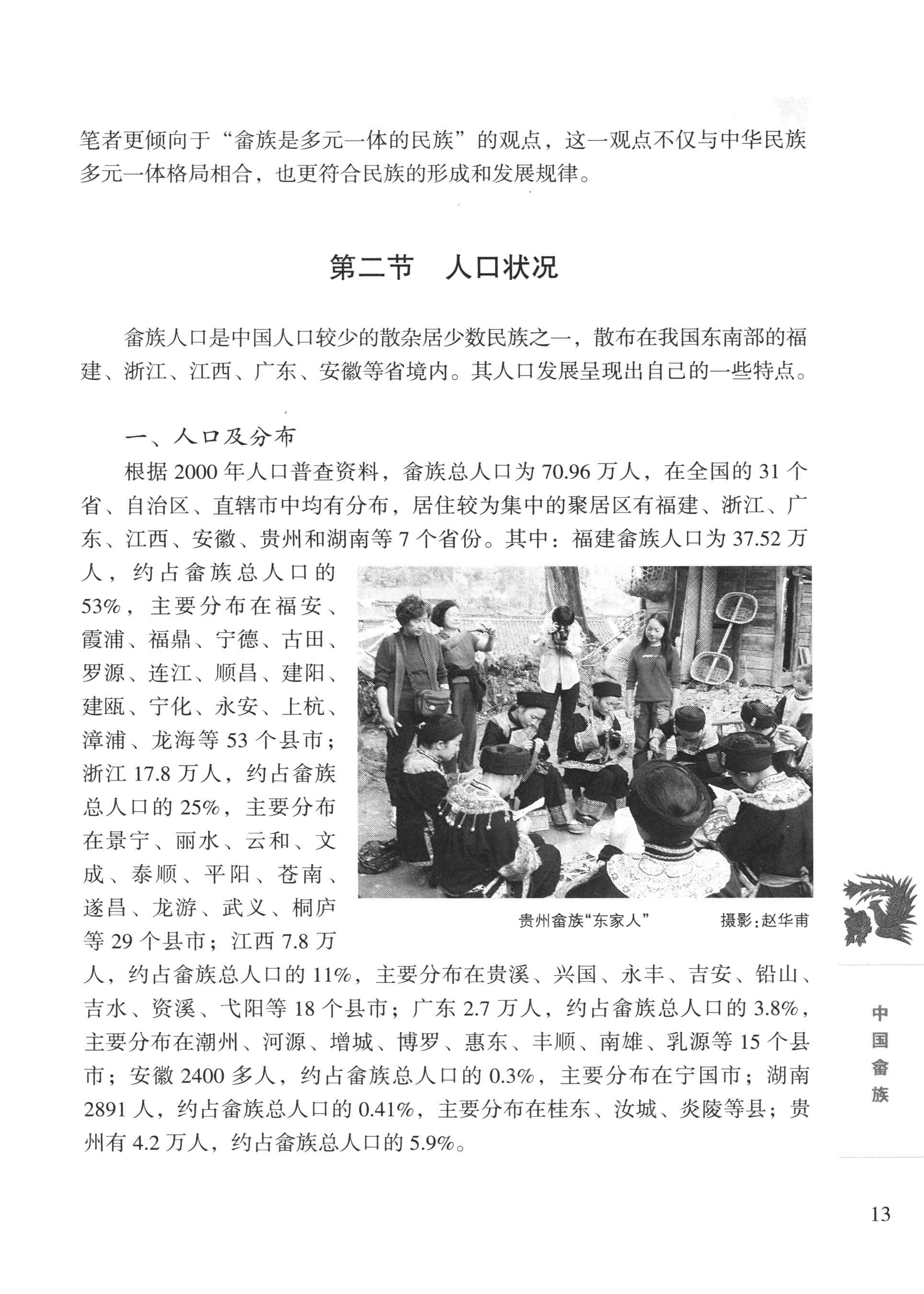第一章 畲族概况
内容
畲族自称“山哈”,是分布在我国东南部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安徽等省的少数民族。人口70余万,以闽东、浙南分布最为集中。早在隋唐时期,畲族就在闽、粤、赣交界的广袤山区聚居,以刀耕火种、耕山狩猎为生。唐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畲族从以凤凰山为中心的闽、粤、赣山区大量外迁,辗转于东南数省,至清代中后期形成了今天的分布格局。畲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自己的文字,通用汉文字。新中国成立后,畲族的民族成分得到确认,在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关照下,目前畲族地区建有1个民族自治县、45个民族乡。
第一节 族称族源
畲族是我国东南沿海的一个古老民族,至迟在6世纪末7世纪初,畲族先民就聚居在闽、粤、赣交界的广大地区,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人类共同体。
一、族称
畲族的族称有自称和他称两种。闽东、浙南一带畲族自称为“山哈”,“哈”在畲语中意为客人,“山哈”是山里客人的意思。贵州一带的畲族则自称“哈萌”,“萌”意为“人”,也就是说畲族自称是“客人”。畲族自称为“客”,与他们居住的环境、迁徙历史有关。畲族原分布在闽、粤、赣三省结合部的广大地区,元明清时期从原住地陆续迁徙到闽东、浙南、赣东等地山区半山区。先来为主,后来为客,先来的汉人就把这些后来的畲民当做客人。此外,畲族家谱中还有“瑶人”或“瑶家”的别称。
“畲族”“輋民”是汉族对“山哈”的他称。在汉文古籍中,“畲”字的出现和使用相当早。在《诗经》中有“新畲”,在《周易》中有“甾畲”,其意均为将荒地开垦成为可以种植的畲田。汉语中的“畲”字有两种读音:读作yú(余)时,指刚开垦的新田;读作shē(奢)时,其含义为用火烧去地里的杂草,然后种植农作物,刘克庄《漳州谕畲》说“畲,刀耕火耘”,即为此意。唐末衡山南岳玄泰禅师记述的“畲山儿”,虽没有明指是一个族群,但其以斫山烧畲为生,具有今年斫了一坡,明年又斫另一坡的不断转徙的特点,其特征都与畲民相符,可以认作是文献中以“畲”来指称这群山地民族的最早史例。①“畲”字被衍化为明确的族群称谓,则是始于南宋刘克庄的《漳州谕畲》。刘克庄在《漳州谕畲》中说: “畲民不悦(役),畲田不税,其来久矣。”可见最迟到南宋时期,畲族先民已经被人称为畲民了。畲族为什么被称为“畲”? 《龙泉县志》说: “(民)以畲名,其善田者也。”看来,畲族先民到处开荒种地的游耕经济生活,确实给当地的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宋末元初,各地畲民组织义军,加入抗元斗争的行列,《元史》中又出现“畲军”“畲丁”等名称。明清时期,闽、浙各地方志以“畲民”“畲人”和“畲客”等称呼畲族是非常普遍的。
文献记载中对畲族以“輋”相称也相当早,大约出现在12~13世纪。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02“梅州”条记载的“山客輋”,是文献上以“輋”作为畲族族称的正式记载。其时间比刘克庄所记早了三四十年。而《宋史》卷419《许应龙传》所载“山斜”,指的也是畲民。这一“山斜(畲)”作为畲民的专称约略与梅州的“山客輋”同时,也比刘克庄《漳州谕畲》早了30多年。文天祥《知潮州寺丞东岩先生洪公行状》说:“潮与漳、汀接壤,盐寇輋民群聚。”这大概也是关于“輋民”的较早记载。
“輋”是广东汉人创造的俗字,音读作she。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说:“粤人以山林中结竹木障覆居息为輋。”显然,以“輋”字作族称是侧重于居住形式,指在山里搭棚而居的人群。 “輋”的含义虽与“畲”有差异,但“畲民”和“輋民”并不是指两个不同的民族,也不是指同一民族的两个不同经济发展阶段,而是分别指分布在不同区域的同一群体。前者指福建畲族,后者指广东、江西畲族。这种称呼的差异,主要是由于汉族文人对闽、粤、赣畲族经济生活观察的侧重点不同而产生的。明清时期,闽、浙各地方志以“畲民”“畲人”和“畲客”等称畲族的非常普遍,粤、赣各地方志以“輋户”“輋蛮”和“山輋”等称畲族的也比比皆是。
清代以来,由于许多人不了解畲民的民族成分,还有以“苗族”“瑶族”“瑶僮”“畲傜”和“苗民”等称呼畲族的。如民国年间的福建地方政府文件中,就以“苗族”称连江、寿宁、周宁、长泰、宁化、南平、闽侯、罗源、柘荣、光泽等地的盘、蓝、雷、钟四姓畲族,但宁德第一二区、福鼎、福安、顺昌等地的盘、蓝、雷、钟四姓群众则被称为“畲族”。甚至在1956年畲族被确认为一个单一民族后,南平、长泰、宁化等县的政府公文中,仍将当地畲族称为“苗族”。①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史书对畲族族称的记载是相当混乱的,称呼也因时因地而异。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实行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畲民根据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要求确定族称。1953年8月,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派出以施联朱为组长的畲族民族识别调查研究小组,到浙江景宁及福建罗源、漳平等地做了为期3个月的畲民识别调查。通过缜密的民族识别,1956年12月,国务院正式确认畲族为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并确定将“畲族”作为这个民族的正式族称。
二、族源
根据畲族族谱及民间相传,畲族始祖是盘瓠。盘瓠与高辛帝的三公主结为夫妻后,生下三儿一女:长子盘自能,次子蓝光辉,三子雷巨佑,四女招婿钟志深, “盘、蓝、雷、钟”后来成为畲族四大姓。畲族的发祥地被认为在广东潮州市凤凰山,其他各省的畲族都是由凤凰山迁徙而去,凤凰山成了畲族崇拜祖先的圣地。粤、闽、浙、皖、赣等省畲族中有着“广东路上有祖坟”的传说,其始祖原居住深山,以狩猎为生,后不幸被山羊所伤,死于丛林中,葬在广东潮州凤凰山上。
在学术界,关于畲族来源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大致主要有“武陵蛮”说、“东夷”说、“河南夷”说、“越人”后裔说、“南蛮”说、“闽人”后裔说等几种不同说法。
一是“武陵蛮”说。这种观点以施联朱为代表,主张畲、瑶同源于汉晋时代长沙的“武陵蛮”(又称“五溪蛮”)。他们注意到畲族和大部分瑶族都家喻户晓地流传有盘瓠传说,传说的内容与汉晋时代分布在长江中下游的“武陵蛮”所流传的盘瓠传说大同小异,据此认为畲、瑶两族与“武陵蛮”有密切的渊源关系。瑶族中自称为“勉”的“盘瓠瑶”(或称“盘瑶”“板瑶”“顶板瑶”“过山瑶”)与自称为“门”的“山子瑶”,人口约占瑶族总人口的一半以上,也崇信盘瓠传说。
持畲族源于“武陵蛮”观点的学者人数较多,可佐证的材料比较丰富。他们提出畲族、瑶族同源于武陵蛮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史籍的记载。史籍多称瑶族和畲族本是“五溪蛮”盘瓠之后,畲、瑶两族不仅有相同的反映原始图腾崇拜的盘瓠传说,而且有许多相同的习俗,在史籍上也往往是畲、瑶并称,甚至说畲族就是瑶族。直到清代,畲、瑶还是混用,往往称畲族为“瑶人”。畲族族谱记载亦有自称为“瑶户”“瑶人子孙”等。现在分布在广东海丰、惠阳、增城、博罗的畲族仍称自己为“粤瑶”,在海丰、惠阳的汉人称他们为“畲民”,但在增城却被汉人称为“山瑶”。
第二,两族都具有相同的姓氏。传说畲族有盘、蓝、雷、钟四大姓,但实际上除广东增城县有几十个盘姓畲族外,其他地区未见盘姓。福建霞浦县畲族族谱中有一段对盘姓兄弟失散的解释:相传唐光启二年(886年),盘、蓝、雷、钟、李等姓畲族360余丁口,从闽王王审知由海道来闽,至连江马鼻道登岸后,徙居罗源大坝头。盘王碧一船被风漂流,不知去向,故盘姓在畲族中失传。畲族传说中的大哥盘姓留在广东,但在瑶族中盘姓却很多,也有蓝、雷等姓氏。 第三,两族至今仍都保存一种汉文文书。汉文文书在瑶人中称《过山榜》,在畲人中称《开山公据》,两者内容大同小异,都同样记载着具有原始图腾崇拜性质的盘瓠传说,此外还记述封建皇帝赐给他们券牒,准许他们租种山地,不纳粮租,不服徭役等特权,但不得到平原上耕种,不得与汉人通婚。
第四,在语言方面,虽然99%以上的畲族操接近于汉语客家方言的语言,但居住在广东惠阳、海丰、增城、博罗一带的畲族却操瑶族“布努”语。《潮州府志》也记载今天讲客家话的广东凤凰山的畲族,在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一种与今天海丰、惠阳、增城、博罗一带畲族的“布努”语很相似的语言。
第五,在歌调方面,虽然有不少地方的畲族民歌类似客家的山歌调,但福建宁德地区却存在着完全不同于客家山歌的四种畲族传统的基本音调(福宁调、福鼎调、霞浦调、罗连调),这四种基本调和自称“勉”的瑶族和“布努瑶”的基本调有惊人的类似之处。过山瑶唱的民歌传统基本调是“拉发调”,拉发调中长调的“跟声”唱法与畲族的二声部合唱“双条落”有许多类似之处。瑶族的拉发调又和福建罗源、连江等县畲族的“罗连调”在音调(包括音列、调式、节奏)的基本特点是相一致的。
根据上述种种的理由,从而推断畲、瑶同源于汉晋时代“南蛮”中包括长沙“武陵蛮”在内的一支,他们之间的历史渊源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二是“东夷”说。潘光旦教授生前第一个提出“畲族源于东夷中的徐夷”的设想。他把长沙“武陵蛮”的渊源关系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生活在淮河和黄河之间的“东夷”里靠西南的一支“徐夷”。他认为“徐夷”与苗、瑶、畲都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后来向长江流域活动进入五岭山脉中的一部分,就是发展为今天的瑶族;一部分从五岭山脉向东在江西、福建、浙江的山区里和汉族杂居融合而成为畲族;另一部分曾定居在洞庭湖一带,即后来进入湘西和贵州的苗族。
施联朱、张崇根等人后来也在畲、瑶同源于“武陵蛮”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把畲族渊源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生活在淮河与黄河之间的“东夷”里靠西南的一支“徐夷”,认为畲族和大部分瑶族同源于“武陵蛮”,而“武陵蛮”是“东夷”迁居鄂、湘西部地区后,融合了其他民族成分而形成的。他们从先秦氏族的迁徙、神话传说、考古资料及文化特点等方面,论证了“武陵蛮”中的一支“诞”(即“莫瑶”)是由“东夷”族群迁到湘西、鄂西后,融合了三苗、氐羌(犬戎)的成分而形成的。到唐宋之际,“莫瑶”在迁徙过程中,又分别发展形成新的族体——畲族、瑶族,有一部分加入苗族中。
还有一些学者对高辛氏和“东夷”、畲族的文化遗产作了比较,如人死洞葬,拾骨重葬,丧葬以歌代哭,结婚时男女不对拜,喜唱山歌,对本族人说“山哈”话,自称为“徐家人”,称中土汉人为“阜佬”,称土著汉人为“闽家人”,爱狗,流传“一犬九命”的故事,传颂“凤凰鸟”,结婚时正门横楣上写“凤凰到此”四个字的横联等,说明高辛帝喾、东夷、徐夷、畲族具有极其密切的渊源关系。 三是“越人”后裔说。蒋炳钊等则力主畲族乃古代越人的后裔。此说根据史籍中关于古越人和今天畲族在分布地域上的对照、民间传说和历史记载的偶同或从族称义、音的演变去推论以及畲、越具有共同的盘瓠传说,共同的生产方式、生产水平和共同的风俗习惯等,认为畲族乃古越人的后裔。在“越人”后裔说中,又有许多不同的具体说法,如认为畲族乃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或范蠡的子孙;有的认为畲族是我国秦汉时代的越人后裔;还有认为畲族是源于汉晋时代的“山越”,特别是与汉高祖十年(公元前197年)封地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的越人后裔南海王织有密切的渊源关系,等等。
四是“南蛮”说。王克旺、雷耀铨等人认为畲族乃“蛮”或“南蛮”的一支,但不是“武陵蛮”,畲族的历史渊源绝不迟于“武陵蛮”;他们认为盘瓠传说的范围包括《搜神记》中所说的“今即梁汉、巴蜀、武陵、长沙、庐江郡夷是也”,相当于今天大半个中国南部,而不仅流传于“武陵蛮”中;畲族和瑶族并没有共同的族源,他们的迁徙路线也没有混杂和交叉现象;畲族是广东的土著民族。
五是“闽人”后裔说。陈元煦认为畲族无论生计方式、图腾还是操持的语言,都与古越人毫无共同之处,因此畲族不可能是“越族之苗裔”。他认为闽、越乃我国南方的两个古老民族,闽族系福建土著,越族乃福建的客族,畲族先民应为“福建土人”“古闽人”。
六是“河南夷”说。肖孝正、钟玮奇等通过大量的畲族族谱的研究,认为高辛氏是皇帝正妻雷祖的长子,畲族的祖先龙麒则是高辛氏的第五个妻子刘君秀的儿子。龙麒后来生三男一女,分别为盘、蓝、雷、钟(女婿)四姓,四姓的郡望分别为“南阳” (盘姓)、“汝南”(蓝姓)、“冯翌”(雷姓)、“颍川” (钟姓),都在河南境内。因此认为畲族源于古代河南“夷”人的一支,是属于高辛氏近亲的一支氏族部落。
七是“多元一体”说。针对畲族源于武陵蛮、越人、闽人、南蛮、河南夷等单一族源的观点,谢重光则提出“多元一体”新说。认为畲族族源主要包含百越后裔、南迁武陵蛮和入畲而被畲化了的汉人三大部分,畲族是多元一体的民族。
总之,关于畲族的来源,目前仍是一个悬案,尚无定论。就个人来说,笔者更倾向于“畲族是多元一体的民族”的观点,这一观点不仅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相合,也更符合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规律。
第二节 人口状况
畲族人口是中国人口较少的散杂居少数民族之一,散布在我国东南部的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安徽等省境内。其人口发展呈现出自己的一些特点。 一、人口及分布 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畲族总人口为70.96万人,在全国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均有分布,居住较为集中的聚居区有福建、浙江、广东、江西、安徽、贵州和湖南等7个省份。其中:福建畲族人口为37.52万人,约占畲族总人口的53%,主要分布在福安、霞浦、福鼎、宁德、古田、罗源、连江、顺昌、建阳、建瓯、宁化、永安、上杭、漳浦、龙海等53个县市;浙江17.8万人,约占畲族总人口的25%,主要分布在景宁、丽水、云和、文成、泰顺、平阳、苍南、遂昌、龙游、武义、桐庐等29个县市;江西7.8万人,约占畲族总人口的11%,主要分布在贵溪、兴国、永丰、吉安、铅山、吉水、资溪、弋阳等18个县市;广东2.7万人,约占畲族总人口的3.8%,主要分布在潮州、河源、增城、博罗、惠东、丰顺、南雄、乳源等15个县市;安徽2400多人,约占畲族总人口的0.3%%,主要分布在宁国市;湖南2891人,约占畲族总人口的0.41%,主要分布在桂东、汝城、炎陵等县;贵州有4.2万人,约占畲族总人口的5.9%。
二、人口的演变
在1956年以前,虽然汉族文献中有大量“畲民”“畲瑶”“畲军”等记载,但畲族只是一个自在的族群,并没有获得国家的承认。而且由于社会上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民族歧视,畲族人很多都隐瞒自己的民族成分。因此,虽然早在唐代,蓝万兴、蓝奉高等领导的畲民起义军就曾屡挫唐军,体现了强劲的实力,但新中国成立前的畲族人口一直是一个谜。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推行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经过科学的民族识别,畲族人口经历了几次较快的增长时期。一是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经过民族调查和民族识别,闽东、浙南、广东等地大量畲族人民恢复民族成分,成为畲族人口增长的第一个高潮;二是20世纪80年代,闽西、赣南、珠三角等地又有一批畲族人民恢复民族成分,构成畲族人口增长的第二次高潮;三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贵州恢复黔东南4万多居民的畲族身份,成为畲族人口增长的又一个小高潮。
改革开放以来,畲族人口发展进入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不论在降低人口自然增长率、优化人口结构、改善人口素质等方面都取得了新的进展,正朝着人口现代化方向演进。1982年畲族人口为37.20万人,1990年达到63.47万人,净增加26.27万人,平均每年增长3.28万人,平均每年递增6.91%;2000年畲族人口达70.96万,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增加了7.49万人,增长率为1 1.80%,平均年增长率1.08%。其增长率表面看来是相当高的,但这种增长主要是通过社会增长(指更改民族成分和民族通婚子女选报为畲族人口数值)来支撑的,自然增长率并不高。以1982~1990年畲族人口的高增长率为例,自然增长仅占15.5%,社会增长达84.5%。
三、人口结构
1.畲族人口的性别与年龄结构
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畲族总人口中男性为38.10万人,女性为32.66万人,性别比为1 15∶97;在1999年11月1日~2000年10月31日,出生婴儿性别比为104∶70,这表明畲族社会有着较明显的男女不平等观念;从各年龄段的人口比例看,少年儿童人口(0~14岁)比重为26.36%,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比重为66.35%,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占7.29%,与1990年相比,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下降了5.59个百分点,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老年人口比重分别增加了3.87个和1.72个百分点。
2.畲族人口的文化结构
在畲族15岁及以上的52.25万人口中,文盲人口有6.17万人,占1 1.81%,其中男性成人文盲率为7.44%,女性成人文盲率为16.96%。文盲人口比1990年减少了6.51万人,文盲率下降了17.55%%。6岁及以上的65.54万人口中,受过小学以上(含小学)教育的占86.98%,受过初中以上(含初中)教育的占37.26%,受过高中及中专以上教育的占8.67%,受过大专、大学教育的占1.78%。平均受教育年数6.67年,比10年前增加1.41年。
3.畲族人口的劳动力就业水平与职业结构
从劳动力就业水平来看,2000年在畲族15岁及以上人口中,劳动力为39.01万人,其中从业人口37.69万,失业人口1.32万,劳动参与率为77.09%,就业率为74.49%,失业率为3.37%。从业人口中,从事第一产业的占71.64%,从事第二产业的占14.55%,从事第三产业的占13.81%。
从职业结构来看,2000年畲族从事脑力劳动工作的占全部从业人口的比率为6.45%,从事城市体力劳动的比率为21.46%,从事农村体力劳动的比率为72.09%。具体地说,担任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占从业人口的比率为0.84%,担任技术工作的占3.92%,办事员占1.68%,商业人员和服务员的比率为6.67%,从事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作的比率为14.76%,从事农林牧渔工作的占72.09%,从事其他工作的比率为0.03%。
4.畲族人口的城镇化水平
2000年,畲族人口中有城镇人口16.63万人,占总人口的23.44%;乡村人口54.33万人,占总人口的76.56%。与10年前相比,畲族城镇人口比率提高了13.95个百分点。
5.畲族人口的出生率与死亡率
1999年11月1日~2000年10月31日期间,全国畲族出生人口为7410人,总计生育率为1.29%,全国畲族死亡人口为4277人,其中男性2618人,女性1659人。粗死亡率为6.05‰,其中男性为6.89‰,女性为5.07‰,婴儿死亡率为27.75‰,预期寿命为72.41岁。
第三节 历史沿革
学术界对畲族的来源,尚无定论。但一般认为至迟到隋唐时代,畲族先民已经活跃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带的广大区域。古代畲族是山地游耕民族,从隋唐以来辗转迁徙于东南各省,历经1000多年,逐渐形成今天的分布格局。其历程大致可以分为隋唐时期、宋元时期、明清时期、近现代时期和新中国时期五个发展阶段。
一、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畲族先民被称为“蛮獠”,出没于闽、粤、赣三省交界的九龙江以西的广大山区。唐以前,这里还是化外之地,到处深林丛莽,畲族先民是这里的主要居民。
为反抗唐王朝对闽、粤、赣交界地区的控制,唐代畲族先民不断地开展武装斗争,这就是史书所谓的“蛮獠啸聚”。唐总章二年(669年),闽、粤交界地区的畲民举行暴动,并曾击败由岭南行军总管陈政率领的近4000唐军,迫使其退守九龙山待援;仪凤二年(677年),苗自成、雷万兴领导的畲民起义军攻陷潮阳县城,一时闽、粤震动。苗自成、雷万兴起义后被陈元光所镇压,大量畲民逃亡隐匿到更为偏僻的山林,但反抗并没有停止。陈元光意识到光靠武力镇压不是办法,因此向朝廷请求“置州县,以控岭表”。垂拱二年(686年),朝廷采纳陈元光建议,于十二月增置漳州郡,下辖漳浦、怀恩两县,并以陈元光为州刺史。为缓和社会矛盾,陈元光一方面加强生产建设,另一方面对畲民采取恩威并施的策略,在镇压反抗的畲民的同时,下令开山取道,派人将逃散的畲民诱抚出来,划地建立“唐化里”,专门收容归附的土著居民,还在经济上给予优待,使散移各处的畲族先民纷纷“归附”。随之大量汉民迁入,使“苗人散处之乡”变为“民獠杂处”之地。但陈元光的政策看来并没有得到畲族先民的普遍支持,景云二年(711年)十一月,雷万兴、苗自成之子又在潮州率领畲民起事,并率众潜抵岳山,仓促率轻骑抵御的陈元光被蓝奉高刀伤腰部,重伤而死。陈元光死后,因其开发漳州的卓著功勋,被后世尊为“开漳圣王”。
汀州则在开元二十四年(736年)设置。因不满王氏(王潮、王审知、王延翰)集团的统治和歧视,唐昭宗乾宁元年(894年),发生了以畲民为主的“黄连峒蛮二万围汀州”事件,结果被王潮部将李承勋击破。黄连峒蛮被镇压后,闽西的土著势力受到沉重打击,很久不能恢复元气。此后直到北宋末年,大规模的蛮獠武装反抗斗争较少。
整个隋唐时期,畲族先民主要在潮(州)漳(州)汀(州)一带活动。他们和汉族(特别是客家先民)一起,拓荒垦殖,使林木荫翳、荆棘丛生的荒地,“渐成村落,拓地千里”,山区得到开发,生产得到发展。这一时期畲民较远距离的迁徙发生在唐昭宗景福元年(892年),王潮、王审知攻取福州时, “平湖洞及滨海蛮夷皆以兵船助之”,这段往事也体现在闽、浙两地各姓畲族的谱牒中。学者一般认为,平湖洞及滨海蛮夷是畲族先民中杂有夷蜑成分较多的部分。这些随船而住的畲民后来在闽东的连江、罗源登岸,并陆续迁往闽东、浙南诸地,成为当地最早的畲族移民。
二、宋元时期
两宋时期,虽然高宗绍兴年间,有赣、闽、粤边“汀、虔、潮、惠山寇为乱”;理宗绍定、端平年间,闽西和赣南又爆发了晏头陀和陈三枪为首的“寇变”;孝宗隆兴年间长汀县葛畲的寇乱及光宗绍熙中上杭县峒寇结他峒为乱等事件,这些以畲族为主的武装斗争,最终导致不少畲民逃亡、流徙,但畲族的活动地域基本上仍在原有的聚居区内。刘克庄的《漳州谕畲》对宋代闽南畲族地区政治、经济有比较典型、详细的描述。宋末元初和元代,闽、粤、赣交界地区的畲民也参加到风起云涌的抗元斗争之中,由于连年战乱,各地畲军、畲兵的征战调动和戍城、屯田,造成畲族的迁徙路线错综复杂,迁徙的范围也随之扩大。总体来说,这个时期的移民相当部分属于军事性质的移民,最有代表性的是陈吊眼、许夫人、钟明亮等多支抗元畲军于漳州、潮州、泉州、汀州、赣州等处的转战屯守移民。
陈吊眼于至元十三年(1276年)自漳浦举义后,一路攻城掠地,由漳浦、漳州、安溪进抵泉州,配合文天祥、张世杰共讨蒲寿庚,大批畲民随军参战。与此同时,潮州畲族民妇许夫人也率诸峒畲户起兵,由潮州、云霄、诏安到达漳浦,在漳浦与陈吊眼会师后挥师泉州。后陈、许义军遭元军镇压失利,被迫退守漳浦千壁岭。此时黄华在闽北揭竿而起,抗击元军。许夫人又亲率畲军取道元军势力较弱的漳浦、漳州、汀州、南平、邵武一线,转战闽北,汇入黄华的义军队伍,抗击元军达十年之久。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钟明亮在广东循州举义,他们转战于漳州、汀州、赣州等地,得到泉州、龙溪、汀州、南平、赣州、吉安等地畲民的热烈响应,一时“拥兵十万,声摇数郡”。各路起义失败后,元朝政府“令于南诏黎、畲各立屯田……及将所招陈吊眼等余党入屯,与军人相参耕种,为户汀州屯一千五百二十五名、漳州屯一千五百一十三名”;又“诏福建黄华畲军有恒产者放为民,无恒产与妻子者,编为守城军”。随着各路义军的转战和战后元廷的安置,参战的畲民也随之播迁闽南、闽西、闽北、赣南等各地。
宋元时期,畲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比唐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汉族地主和封建官吏对畲民进行繁重的赋税征收,土地掠夺也随之加重,畲民丧失了赖以生存的资源,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入元以来,元朝统治者更是强占长汀路畲民的土地作为赐地,使畲民无以为生,这是导致畲民积极投身抗元运动、福建成为抗元斗争最为激烈的省份之一的重要原因。在日益加强的封建势力的分化统治下,宋元时期畲族内部开始出现明显的阶级分化。如刘克庄《漳州谕畲》记载,南宋时期的漳州“西九畲酋长相继受招”和“南畲三十余所酋长,各籍户口三十余家,愿为版籍民”。《元史》也记载元初畲军中“有恒产”和“无恒产者”之区别。
三、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是畲族大量迁往汉族地区和形成目前的“大分散,小聚居”分布格局的重要历史时段。与宋元时期相比,这个时期畲族的迁徙活动频繁,迁徙路线复杂,迁徙范围更为广泛,几乎遍及闽、粤、赣、浙、皖、湘、贵等省山区,基本形成了今天畲族的分布格局。这个时期畲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活相对比较安定,其迁移主要是基于畲族山地游耕的传统而非军事性质。这种迁徙的速度缓慢,迁徙的方式以家庭或家族中若干成员为单位徐徐而行,迁徙的取向是相对地广人稀的汉族地区。概而言之,广东畲族多迁至福建、浙江,福建畲族多迁至江西、浙江,浙江畲族多迁至安徽,而江西畲族则迁至湖南、贵州。
明清时期,畲区的封建社会已经确立,其社会经济状况和当地汉族基本一致。这个时期的畲族经过长期的动荡和迁徙以后,已基本稳定在闽、浙、粤、赣、皖、贵、湘等省的广大山区,对各地山区的开发(尤其对闽东、浙南山区的开发)作出了重要贡献。当畲族迁到闽东、浙南时,自然条件较好的平坝地方已多为汉人开垦,畲民只能在山谷冈麓地带开山劈岭,建造田园。有水源之处开为梯田,仰赖雨水的山地,辟为旱田。据浙江地方史志记载,浙西南景宁、云和的土地就多为畲民所开垦。此外,明代闽西南还有一批以种菁为业的畲民,迁徙到莆田、永泰、古田、罗源等山区以种菁为生。明代福建菁以量多质好闻名全国,畲族的贡献是巨大的。
经过几个世纪的长途跋涉,畲族终于在闽、粤、赣、浙、皖、贵、湘等省的广大山区找到了定居点,到清代基本稳定下来,停止迁徙。畲族地区的社会生产力获得了较大发展,通过耕种自己的少量土地或租种汉人的土地,畲民由此进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完全结束了传统的刀耕火种的游耕农业生活。
四、近现代时期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居住在东南沿海的畲族也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逐步地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命运中。在资本主义列强的炮舰威迫下,清政府被迫开放福州、温州等通商口岸,列强的大量商品源源不断地经由水陆交通输至福州口岸附近的闽东和温州口岸附近的浙南畲乡,对畲族社会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使其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走上崩溃的道路。如机制洋纱洋布的输入,排斥了农民手工纺织的土纱土布,使在畲族家庭手工业中占重要地位的手工纺织业遭到极大破坏。质好价廉的洋靛的输入,使种菁为生的畲民的生活受到巨大冲击,大量种菁为业的畲民不得不另谋生路。鸦片的输入更是危害巨大,清政府为加强税收剥削,竟强迫畲、汉农民种植鸦片,闽东许多畲民被迫将良田改种罂粟,造成农业生产的严重破坏。
畲族地区的经济生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剥削关系依旧保存下来,绝大部分土地仍然集中在汉族地主手中。而广大贫苦畲民或向汉族地主租佃土地,承受高额的地租剥削;或流入城市,终年出卖劳动力,变成游民无产者,生活陷入朝不保夕的境地。他们为了求生存、得解放,整个近现代时期,始终同汉族人民一起,支持太平天国运动,反洋教,发动新军起义,组织农民自卫军,展开如火如荼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经受了斗争的洗礼。
大革命时期,彭湃领导的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中就有畲民参加,与广东相邻的闽西、赣南的畲族地区也有畲族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土地革命时期,闽、浙、赣等广大的畲族地区都燃起了革命的火焰,畲族人民打土豪分田地,成立了工农武装政权。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册中,写下畲族革命的壮丽篇章。今天在上杭县汀江河畔辟为博物馆的临江楼陈列室中107位长征战士中有8名是畲族。闽东是畲族主要聚居区,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畲族地区成为党和红军的可靠的根据地,在1938年北上抗日的新四军三支队六团中有畲族指战员218人。该县还出现两名共和国的将军蓝庭辉、雷钦。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新中国的诞生,为了民族解放事业,畲族人民贡献出热血和生命。
五、新中国成立以后
1949年以后,畲族地区陆续获得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并展开了一系列的民族调查和民族识别,1956年12月,国务院正式确认畲族为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
经过50年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使畲乡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生活日渐安定,经济收入稳步提高,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各项事业不断发展,畲族社会已进入全新的历史征程。
第四节 生态资源
畲族广泛分布于长江以南的闽、浙、赣、粤、皖、湘、贵各省的山区,境内山林密布,层峦叠嶂,沟壑纵横,气候优越,生态条件得天独厚,堪称镶嵌在南中国版图上的“绿色明珠”。 一、气候条件优越畲族地区的气候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受海洋性气候的影响很大,光热充足,雨量充沛,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多在13℃~20℃,年降水量一般在800~1600毫米。因境内地形复杂,海拔高度悬殊,气候垂直差异明显。一般冬季比较寒冷,霜期短,下雪少。但各地畲族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又有一定的差异。闽东畲族最多的福安市,年平均气温16℃~18℃,无霜期260~270天,年降雨量在1540~1700毫米。
这种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为农业和林业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因此在畲族山区,谷物、茶叶、红薯等亚热带作物的种植久负盛名,香菇、竹笋等也是畲族山区重要的林产品。
二、地形地貌复杂
畲族分布的地区,山脉纵横交错,峰峦起伏,丘陵密布,地势大致自西北向东南沿海倾斜,山脉由东北西南走向。主要有闽、赣两省边境的武夷山、玳瑁山、仙霞岭、杉岭等。武夷山为福建第一名山,主峰黄岗山海拔高2158米。浙江东南部有雁荡、括苍、洞宫诸山。广东有罗浮、莲花、凤凰诸山。此外,还有闽北的鹫峰山和闽东的太姥山等。多山峦叠嶂,奇峰险谷,花岗岩地貌、丹霞地貌发达,为著名的游览胜地。
畲族地区溪流回绕,溪水多集诸山两侧之水,从深山峡谷中跌宕奔流出来,汇入闽江、瓯江、汀江。闽江源于武夷山,流经福州,注入东海。瓯江源于龙泉溪,汇丽水大溪与青田小溪后,流经温州,注入东海。汀江发源于武夷山南麓的东南一侧的宁化县治平乡,流经长汀、武平、上杭、永定4县,经永定出境进入广东与梅江汇合后称韩江。各条江河支流多、流域面积广,为畲族地区的水运交通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这些河流穿越深沟峡谷,跌宕奔涌,落差都很大,蕴含的水力资源也十分丰富。目前闽江、瓯江、汀江都进行了多级水利开发,为闽、浙地区包括畲区在内的城乡社会发展输送了大量清洁能源。
三、生物资源呈多样性
畲族地区林区面积大,森林覆盖率高,树木种类多,常见的有松、杉、樟、楠、柏、桉、青冈栎、泡桐、竹等,也有世界稀有的珍贵树种栓皮栎、檫树、红豆杉和柳杉等。木材蓄积量以松、杉为最大。景宁畲族自治县是浙江省重点林业基地之一,森林资源特别丰富,植被有针叶林、阔叶林、针阔混交林、竹林、灌木丛等5种类型,乔木、灌木、草木层次齐全。据不完全统计,景宁县的木本植物有1552种,其中有利用价值的就有1469种。用材林有松、杉、杂木等,经济林有厚朴、茶叶、油桐、油茶、柑橘、乌桕、雪梨等。闽北、闽东的武夷山、戴云山、太姥山等山脉,森林密布,也是我国重要的林区之一,素有“绿色金库”之美称。武夷山区还保留有大片的南方铁杉、小叶黄杨、武夷玉山竹等珍稀植物群落,几乎囊括了中国亚热带所有的亚热带原生性常绿阔叶林和岩生性植被群落。有许多珍贵的珍奇树种,如成片的高山矮林、铁杉林以及香榧、亮叶水青冈、红叶甘钧、响叶杨、北方银杏、花榈木、南方肉桂、黄杨木、红豆杉、鹅掌楸等。
畲族山区的林间动物资源也十分丰富。仅景宁畲族自治县,野生动物就有国家一类保护动物黑麂、白颈长尾雉、云豹、金雕、短尾猴等44种。全县共有脊椎动物31目78科272种。其中:兽类8目20科48种,鸟类15目40科162种,爬行类3目9科30种,两栖类2目5科18种,鱼类3目4科40多种。而在武夷山自然保护区中有哺乳动物100余种,占全国同类动物总数的1/4;鸟类400余种,占全国总数的近1/3,堪称是“鸟的王国”。两栖和爬行动物100余种,崇安髭蟾、蝾螈、三港雨蛙、大头平胸龟、丽棘蜥等均为世界罕见的特有种,所以这里被誉为研究“亚洲两栖和爬行动物的钥匙”。鱼类也有30余种,新近还发现一个新种——武夷厚唇鱼。武夷山自然保护区中昆虫的丰富程度也是我国其他地区少有的,全国昆虫32个目,保护区采到的就占31目,估计可达2万余种之多。保护区内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动物有华南虎、白颈长尾雉、金猫、大灵猫、穿山甲、猕猴、云豹、毛冠鹿、短尾猴、小灵猫、黄腹角雉、鬣羚等57种。
四、矿产资源较丰富
畲族山区地下矿藏有铁、煤、金、铜、钼、明矾、石墨、石膏、硫磺、滑石、云母石、瓷土以及其他多种有色金属。有的储量相当丰富,如业已探明的景宁畲族自治县的包山、敕木山铁矿,总储量为400万吨;三枝树的钼矿,储藏量达1万多吨。浙江武义、永康的萤石矿的储量也都很大。闽东畲族地区目前已探明的金属、非金属矿产就有20多种,其中钼精矿、高岭土、辉绿岩等矿产储量相当丰富。这些矿产都是国家的珍贵宝藏,它们的开发,将为畲族地区的发展带来坚实的物质保障。
第五节 语言文字
畲族内部有自己的交流语言,但各地又有所差别,没有自己的文字,通用汉文。畲族历史上曾经有过一种共同的语言——古畲语,但在与汉、瑶、苗等民族的长期杂居相处的过程中,这种语言逐渐演变、分化成了现代畲族使用的三种语言:惠东畲语、福安畲语与贵州畲语。 一、古畲语 早在隋唐时代,闽、粤、赣结合部就已经形成了相当广阔的畲族聚居区,从当时畲民的多次军事行动来看,这里聚居的畲族人口数量是相当庞大的。这些畲族先民用以交流的语言,就是古畲语。随着汉人,特别是客家先民的大量迁入和畲民的流徙,这种古畲语便在民族交融中逐渐消失。但在今天畲族使用的畲语中,我们仍可以发现一些古畲语“底层”的痕迹。虽然我们很难凭这些痕迹勾勒古畲语的全貌,但我们可以确信,现代畲语正是古畲语在融合客家方言和其他地方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
二、惠东方言
惠东畲语是居住于广东莲花山区、罗浮山区的惠东、海丰、博罗、增城4个县共1200多自称“活聂” (山人)的畲族所使用的语言。这种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跟瑶族布努语炯奈话比较接近。
毛宗武、蒙朝吉等认为,历史上畲族先民曾使用过一种语言,后来绝大部分畲族因长期与汉族客家人交错杂居,便逐渐放弃了自己的语言,改用汉语客家话进行交流;而居住在莲花山区和罗浮山区的这一小部分畲族,因“深居崇山峻岭,很少与外界接触”,则没有放弃自己的语言。因此,现在的惠东畲语就是被保留下来的古畲语。①
这个观点受到不少质疑。蓝周根、雷先根就反对关于“畲族放弃了自己的语言,改用汉语客家方言交际”的观点,他们认为现在绝大多数畲族使用的接近汉语客家方言的语言就是畲族的民族语言。②朱洪、姜永兴等也认为,“罗浮山、莲花山的畲语明显受到瑶语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延至凤凰山则又消失殆尽。”“这是瑶文化对罗浮山、莲花山畲族的渗透以及两个民族在粤中的交融关系而造成,故罗浮山、莲花山的畲语是否就是畲族的原生型语言,值得进一步研究。”③而雷阵鸣更认为惠东畲族相传的原籍、族谱记载的盘瓠传说、语言的系属等都与瑶族接近,而且他们一直都自称是瑶族、瑶人,因此惠东畲族究竟是畲族还是瑶族都有待商榷,更不宜将惠东畲语定性为畲族的原生语言。
这些质疑显然是有一定道理的。惠东畲语与讲炯奈话瑶族相似到可以无障碍通话的程度,却与其他绝大多数畲族的语言毫无相同之处,把它定位为畲族原生型语言,确实有商榷的必要。 三、福安畲语 福安畲语是除广东的惠东4县和贵州畲族外,其他分布在福建、浙江、江西、安徽等省以及广东的潮州、丰顺等地的畲族所共同使用的语言。由于福安畲语和客家话存在许多相似性,曾有一些学者认为闽、浙、赣等地畲族讲的福安畲语就是客家话。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特别是畲族学者开始质疑这种观点。一方面是因为福安畲语和客家话之间确实存在着差别,另一方面,则是福安畲语和客家话都是古中原汉语和古畲语在闽、粤、赣结合部畲族和客家交错聚居的广大地区,长期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下形成的。在隋唐至宋元的漫长时间里,这个地区的畲族和客家谁都不存在绝对的强势,也就不可能形成一种文化吞并另一种文化的问题。说畲族人放弃本民族语言,改用客家话交流的观点是很难站得住脚的。客家话之所以区别于中原汉语,就在于它本身就融入了大量畲语成分。
有学者认为,福安畲语是由古畲语演变而来的。从古畲语到福安畲语,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是宋元时期,古畲语与中原汉语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形成类似客家话的畲语;第二阶段是明清时期,这种类似客家话的畲语与畲族新居地的汉语方言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形成现在的福安畲语。因此,虽然福安畲语与汉语客家话接近,但两者是有区别的。福安畲语有其自身的特点,如它的语音声母单纯,韵母发达,声调复杂,变调现象较普遍,音节多。其词汇分虚、实两大类11种,实词尤为丰富,构词特点:多单音词,多转借和引申词,多偏正倒置词,保留不少古汉语词汇和词素。1994年福建省民委对罗源畲语100个常用词作了分析,其中粤语占14个,客家话占13个,闽南、潮州语占6个,福州语占43个,其余24个不属上述语类。其语法特点是以特定的语序、虚词和语感来表情达意,具有民族性、稳固性和一致性。畲语还有一些带有传统性和稳固性的隐语,起助趣、避讳、盘问作用。
因受当地汉语方言的影响,福安畲语所属的各地畲语事实上存在着差别,一般又分为福安方言片区、丽水方言片区、连罗方言片区、顺昌方言片区和华安方言片区等5个方言片区。①
四、贵州畲语
贵州畲语是分布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麻江县、凯里市,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福泉市和都匀市的畲族所使用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惠水次方言。贵州畲语的使用人口4.2万,约占畲族总人口的5.9%。
贵州畲族先祖多是元末和明洪武年间,或奉旨征讨、迁徙,或避祸而迁入贵州,但仍保持着本民族的语言。据1982年贵州省民族识别办公室语言组对畲族语言的调查,贵州畲族虽没有文字,但在其聚居的乡镇,男女老幼都说畲语,散居的畲族在社交活动中基本上用汉语。
贵州畲语的语音有闭塞音、塞擦音、塞边音等,分不带鼻冠音和带鼻冠音两种。贵州畲族语与汉语在音节分类、性质分类、结构分类方面基本相同,但语法和语义有很大差别。对于贵州畲语的形成,目前还没有系统的研究。比较大的可能是,元末明初,一群讲类似客家话的福安畲语的畲族因战乱或避祸,由江西迁入贵州定居,在之后数百年的时间里,他们与讲苗语惠水方言的当地苗人、瑶人长期杂居共处。在经济、生产、生活、婚姻等的长期互动过程中,出于需要,他们逐渐将这种语言与自己原来的畲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现在的贵州畲语。
除上述畲语人群外,闽西上杭、长汀等地的3万多畲族人所讲的语言与当地汉族的客家话已没有区别。
第六节 民族区域自治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为解决民族问题,推动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发展而采取的重要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成功施行,改变了过去少数民族受歧视的状况,使少数民族真正当家做了主人。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中国少数民族依法自主地管理本民族事务,民主地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保证了中国各民族不论大小都享有平等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权利。
一、畲族区域自治概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便开始着手解决历史遗留的一系列民族问题。根据中央的安排,在畲族聚居的福建、浙江、广东、江西和安徽各省各级人民政府都逐步设立和健全了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事务处和民族事务科等机构,专门负责管理包括畲族在内的少数民族事务,并着手筹划民族识别问题。
1952年,福建省人民政府派出工作组到闽东福安县仙洋岭村进行民族调查。1 952年7月8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畲族福安县仙岭洋村调查情况》,这是福建省第一份关于畲族的专门调查报告。报告阐述了“根据共同纲领精神,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问题,为畲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进行了先期的准备。同年9月11日,仙岩乡畲族农民雷霖其成为福建省第一位进京的畲族代表。1953年2月,福安县人民政府遵照1952年政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的精神,在第十一区畲族聚居的仙岩乡建立新中国成立后福建省第一个畲族自治政府——畲族仙岩乡自治区人民政府,这也是畲族管理本民族事务的第一次尝试。
1953年8月,以施联朱为组长的畲族民族识别调查研究小组开始奔赴浙江景宁,福建罗源、漳平等地进行为期3个月的畲民识别调查。1956年12月,国务院正式确认畲族为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畲族从此有了自己正式的、合法的民族身份。
遵照1955年国务院的《关于建立民族乡若干问题的指示》,从1957年开始,福建、浙江等省在畲族聚居的若干区域成立区人民政府管辖下的畲族乡人民委员会。仅1957年7月~10月,福安县就先后成立了仙岩、竹岭、燕洋、王溪、东南、凤洋、蓝山、碧后、茶洋、山岭、半岭、长山、林洋等13个畲族乡。到1958年底,畲族人口最集中的闽东北和浙西南就先后成立了50个畲族乡人民委员会。畲族乡中畲族人口在50%以上,正副乡长、乡政委员、乡人民代表的畲族比例都在70%以上。
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大量的畲族乡委员会被取消。1983年国务院发出《关于建立民族乡的通知》,开始对民族乡进行规范化工作。遵照通知精神,从1984年起,闽、粤、浙、赣、皖等省重新在畲族聚居地区陆续建立畲族乡人民政府。到目前为止,全国共建有畲族乡(镇)45个,其中福建17个,浙江18个,江西8个,广东和安徽各1个。畲族乡内的畲族人口占畲族总人口的30%,各畲族乡(镇)乡(镇)长均由畲族担任。
1984年6月30日,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这是中国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的一个畲族自治县。
二、景宁畲族自治县简介
景宁畲族自治县隶属浙江省丽水市,地处浙江省南部,东邻青田县、文成县,南衔泰顺县和福建省的寿宁县,西接庆元县、龙泉市,北毗云和县、东北连丽水市。全境南北长58.8公里,东西宽73.3公里,总面积1949.98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0.4万亩,山地面积269万亩,辖5个镇19个乡283个行政村。景宁全县有汉、畲、苗、藏、彝、回、侗、黎等8个少数民族,总人口17.9万人,其中畲族人口1.78万人。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驻鹤溪镇,是全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华东地区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属浙江省经济欠发达地区。
景宁畲族自治县境西周时属越,春秋仍属越地。三国时属临海郡,隋开皇九年(589年)废永嘉、临海二郡,置处州设立括苍县(含景宁地域)。明景泰三年(1452年)巡抚孙原员以“山谷险远,矿徒啸聚”为由始置景宁县。1949年5月12日景宁城解放,5月21日建立景宁县人民政府。1952年丽水专区撤销,改属温州专区。1960年景宁县并入丽水县。1962年划丽水县原云和县、景宁县辖地置云和县,属温州专区。1963年5月丽水地区复设,辖云和县(含景宁),1984年6月30日经国务院批准,析云和县原景宁县地域建立景宁畲族自治县。1985年4月22日,即畲族传统的“三月三”节,县人民政府在驻地鹤溪镇举行盛会,庆祝我国第一个畲族自治县正式成立。
景宁县境内峰峦叠嶂,沟壑纵横,洞宫山脉自西南向东北延伸,贯穿全境。县境溪涧众多,主要属瓯江、飞云江两大水系。境内山川起伏,巨大的海拔落差,使景宁的溪涧、河流蕴藏了极为丰富的水力资源。景宁县十分重视水力资源开发,把发展农村小水电作为振兴景宁经济,实现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战略重点,目前全县已建成各类电站100多座,装机容量20多万千瓦,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农村水电之乡”。
景宁县属亚热带季风区,温暖湿润,雨量充沛,四季分明。境内物产丰富,有植物178科,691属,1552余种;脊椎动物31目,78科,272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44种);有20余种矿产资源,钼矿的储量居浙江省之首。这里还是惠明茶的原产地,人工栽培香菇的发源地,同时也是浙江省的黑木耳、厚朴、茯苓生产的重点基地之一。
景宁畲族文化丰富多彩,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有优美动人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粗犷朴实、奔放刚健的舞蹈,富有哲理的谚语,工艺精巧的刺绣编织等,尤以民歌为胜。新中国成立前,民歌、传说故事多口头流传,也有手抄本。新中国成立后,经发掘整理,艺术水平大有提高。畲族自治县建立后,文化活动内容更广泛,形式更多样。1984年8月,浙江省第一次畲族文化工作会议在景宁举行。1987年6月,景宁畲族自治县政府与省博物馆联合在杭州举办畲族文物展览。1987年和1990年,丽水电视台先后摄制畲乡专题片《畲乡风情》《畲乡风》,在中央电视台、浙江电视台播放。1992年12月,首届景宁畲乡文化节在鹤溪镇举行,展现了丰富的畲族文化。2009年3月28日,景宁畲族自治县被国家文化部授予“中华民族艺术之乡”的荣誉称号。
第一节 族称族源
畲族是我国东南沿海的一个古老民族,至迟在6世纪末7世纪初,畲族先民就聚居在闽、粤、赣交界的广大地区,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人类共同体。
一、族称
畲族的族称有自称和他称两种。闽东、浙南一带畲族自称为“山哈”,“哈”在畲语中意为客人,“山哈”是山里客人的意思。贵州一带的畲族则自称“哈萌”,“萌”意为“人”,也就是说畲族自称是“客人”。畲族自称为“客”,与他们居住的环境、迁徙历史有关。畲族原分布在闽、粤、赣三省结合部的广大地区,元明清时期从原住地陆续迁徙到闽东、浙南、赣东等地山区半山区。先来为主,后来为客,先来的汉人就把这些后来的畲民当做客人。此外,畲族家谱中还有“瑶人”或“瑶家”的别称。
“畲族”“輋民”是汉族对“山哈”的他称。在汉文古籍中,“畲”字的出现和使用相当早。在《诗经》中有“新畲”,在《周易》中有“甾畲”,其意均为将荒地开垦成为可以种植的畲田。汉语中的“畲”字有两种读音:读作yú(余)时,指刚开垦的新田;读作shē(奢)时,其含义为用火烧去地里的杂草,然后种植农作物,刘克庄《漳州谕畲》说“畲,刀耕火耘”,即为此意。唐末衡山南岳玄泰禅师记述的“畲山儿”,虽没有明指是一个族群,但其以斫山烧畲为生,具有今年斫了一坡,明年又斫另一坡的不断转徙的特点,其特征都与畲民相符,可以认作是文献中以“畲”来指称这群山地民族的最早史例。①“畲”字被衍化为明确的族群称谓,则是始于南宋刘克庄的《漳州谕畲》。刘克庄在《漳州谕畲》中说: “畲民不悦(役),畲田不税,其来久矣。”可见最迟到南宋时期,畲族先民已经被人称为畲民了。畲族为什么被称为“畲”? 《龙泉县志》说: “(民)以畲名,其善田者也。”看来,畲族先民到处开荒种地的游耕经济生活,确实给当地的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宋末元初,各地畲民组织义军,加入抗元斗争的行列,《元史》中又出现“畲军”“畲丁”等名称。明清时期,闽、浙各地方志以“畲民”“畲人”和“畲客”等称呼畲族是非常普遍的。
文献记载中对畲族以“輋”相称也相当早,大约出现在12~13世纪。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02“梅州”条记载的“山客輋”,是文献上以“輋”作为畲族族称的正式记载。其时间比刘克庄所记早了三四十年。而《宋史》卷419《许应龙传》所载“山斜”,指的也是畲民。这一“山斜(畲)”作为畲民的专称约略与梅州的“山客輋”同时,也比刘克庄《漳州谕畲》早了30多年。文天祥《知潮州寺丞东岩先生洪公行状》说:“潮与漳、汀接壤,盐寇輋民群聚。”这大概也是关于“輋民”的较早记载。
“輋”是广东汉人创造的俗字,音读作she。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说:“粤人以山林中结竹木障覆居息为輋。”显然,以“輋”字作族称是侧重于居住形式,指在山里搭棚而居的人群。 “輋”的含义虽与“畲”有差异,但“畲民”和“輋民”并不是指两个不同的民族,也不是指同一民族的两个不同经济发展阶段,而是分别指分布在不同区域的同一群体。前者指福建畲族,后者指广东、江西畲族。这种称呼的差异,主要是由于汉族文人对闽、粤、赣畲族经济生活观察的侧重点不同而产生的。明清时期,闽、浙各地方志以“畲民”“畲人”和“畲客”等称畲族的非常普遍,粤、赣各地方志以“輋户”“輋蛮”和“山輋”等称畲族的也比比皆是。
清代以来,由于许多人不了解畲民的民族成分,还有以“苗族”“瑶族”“瑶僮”“畲傜”和“苗民”等称呼畲族的。如民国年间的福建地方政府文件中,就以“苗族”称连江、寿宁、周宁、长泰、宁化、南平、闽侯、罗源、柘荣、光泽等地的盘、蓝、雷、钟四姓畲族,但宁德第一二区、福鼎、福安、顺昌等地的盘、蓝、雷、钟四姓群众则被称为“畲族”。甚至在1956年畲族被确认为一个单一民族后,南平、长泰、宁化等县的政府公文中,仍将当地畲族称为“苗族”。①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史书对畲族族称的记载是相当混乱的,称呼也因时因地而异。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实行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畲民根据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要求确定族称。1953年8月,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派出以施联朱为组长的畲族民族识别调查研究小组,到浙江景宁及福建罗源、漳平等地做了为期3个月的畲民识别调查。通过缜密的民族识别,1956年12月,国务院正式确认畲族为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并确定将“畲族”作为这个民族的正式族称。
二、族源
根据畲族族谱及民间相传,畲族始祖是盘瓠。盘瓠与高辛帝的三公主结为夫妻后,生下三儿一女:长子盘自能,次子蓝光辉,三子雷巨佑,四女招婿钟志深, “盘、蓝、雷、钟”后来成为畲族四大姓。畲族的发祥地被认为在广东潮州市凤凰山,其他各省的畲族都是由凤凰山迁徙而去,凤凰山成了畲族崇拜祖先的圣地。粤、闽、浙、皖、赣等省畲族中有着“广东路上有祖坟”的传说,其始祖原居住深山,以狩猎为生,后不幸被山羊所伤,死于丛林中,葬在广东潮州凤凰山上。
在学术界,关于畲族来源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大致主要有“武陵蛮”说、“东夷”说、“河南夷”说、“越人”后裔说、“南蛮”说、“闽人”后裔说等几种不同说法。
一是“武陵蛮”说。这种观点以施联朱为代表,主张畲、瑶同源于汉晋时代长沙的“武陵蛮”(又称“五溪蛮”)。他们注意到畲族和大部分瑶族都家喻户晓地流传有盘瓠传说,传说的内容与汉晋时代分布在长江中下游的“武陵蛮”所流传的盘瓠传说大同小异,据此认为畲、瑶两族与“武陵蛮”有密切的渊源关系。瑶族中自称为“勉”的“盘瓠瑶”(或称“盘瑶”“板瑶”“顶板瑶”“过山瑶”)与自称为“门”的“山子瑶”,人口约占瑶族总人口的一半以上,也崇信盘瓠传说。
持畲族源于“武陵蛮”观点的学者人数较多,可佐证的材料比较丰富。他们提出畲族、瑶族同源于武陵蛮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史籍的记载。史籍多称瑶族和畲族本是“五溪蛮”盘瓠之后,畲、瑶两族不仅有相同的反映原始图腾崇拜的盘瓠传说,而且有许多相同的习俗,在史籍上也往往是畲、瑶并称,甚至说畲族就是瑶族。直到清代,畲、瑶还是混用,往往称畲族为“瑶人”。畲族族谱记载亦有自称为“瑶户”“瑶人子孙”等。现在分布在广东海丰、惠阳、增城、博罗的畲族仍称自己为“粤瑶”,在海丰、惠阳的汉人称他们为“畲民”,但在增城却被汉人称为“山瑶”。
第二,两族都具有相同的姓氏。传说畲族有盘、蓝、雷、钟四大姓,但实际上除广东增城县有几十个盘姓畲族外,其他地区未见盘姓。福建霞浦县畲族族谱中有一段对盘姓兄弟失散的解释:相传唐光启二年(886年),盘、蓝、雷、钟、李等姓畲族360余丁口,从闽王王审知由海道来闽,至连江马鼻道登岸后,徙居罗源大坝头。盘王碧一船被风漂流,不知去向,故盘姓在畲族中失传。畲族传说中的大哥盘姓留在广东,但在瑶族中盘姓却很多,也有蓝、雷等姓氏。 第三,两族至今仍都保存一种汉文文书。汉文文书在瑶人中称《过山榜》,在畲人中称《开山公据》,两者内容大同小异,都同样记载着具有原始图腾崇拜性质的盘瓠传说,此外还记述封建皇帝赐给他们券牒,准许他们租种山地,不纳粮租,不服徭役等特权,但不得到平原上耕种,不得与汉人通婚。
第四,在语言方面,虽然99%以上的畲族操接近于汉语客家方言的语言,但居住在广东惠阳、海丰、增城、博罗一带的畲族却操瑶族“布努”语。《潮州府志》也记载今天讲客家话的广东凤凰山的畲族,在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一种与今天海丰、惠阳、增城、博罗一带畲族的“布努”语很相似的语言。
第五,在歌调方面,虽然有不少地方的畲族民歌类似客家的山歌调,但福建宁德地区却存在着完全不同于客家山歌的四种畲族传统的基本音调(福宁调、福鼎调、霞浦调、罗连调),这四种基本调和自称“勉”的瑶族和“布努瑶”的基本调有惊人的类似之处。过山瑶唱的民歌传统基本调是“拉发调”,拉发调中长调的“跟声”唱法与畲族的二声部合唱“双条落”有许多类似之处。瑶族的拉发调又和福建罗源、连江等县畲族的“罗连调”在音调(包括音列、调式、节奏)的基本特点是相一致的。
根据上述种种的理由,从而推断畲、瑶同源于汉晋时代“南蛮”中包括长沙“武陵蛮”在内的一支,他们之间的历史渊源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二是“东夷”说。潘光旦教授生前第一个提出“畲族源于东夷中的徐夷”的设想。他把长沙“武陵蛮”的渊源关系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生活在淮河和黄河之间的“东夷”里靠西南的一支“徐夷”。他认为“徐夷”与苗、瑶、畲都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后来向长江流域活动进入五岭山脉中的一部分,就是发展为今天的瑶族;一部分从五岭山脉向东在江西、福建、浙江的山区里和汉族杂居融合而成为畲族;另一部分曾定居在洞庭湖一带,即后来进入湘西和贵州的苗族。
施联朱、张崇根等人后来也在畲、瑶同源于“武陵蛮”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把畲族渊源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生活在淮河与黄河之间的“东夷”里靠西南的一支“徐夷”,认为畲族和大部分瑶族同源于“武陵蛮”,而“武陵蛮”是“东夷”迁居鄂、湘西部地区后,融合了其他民族成分而形成的。他们从先秦氏族的迁徙、神话传说、考古资料及文化特点等方面,论证了“武陵蛮”中的一支“诞”(即“莫瑶”)是由“东夷”族群迁到湘西、鄂西后,融合了三苗、氐羌(犬戎)的成分而形成的。到唐宋之际,“莫瑶”在迁徙过程中,又分别发展形成新的族体——畲族、瑶族,有一部分加入苗族中。
还有一些学者对高辛氏和“东夷”、畲族的文化遗产作了比较,如人死洞葬,拾骨重葬,丧葬以歌代哭,结婚时男女不对拜,喜唱山歌,对本族人说“山哈”话,自称为“徐家人”,称中土汉人为“阜佬”,称土著汉人为“闽家人”,爱狗,流传“一犬九命”的故事,传颂“凤凰鸟”,结婚时正门横楣上写“凤凰到此”四个字的横联等,说明高辛帝喾、东夷、徐夷、畲族具有极其密切的渊源关系。 三是“越人”后裔说。蒋炳钊等则力主畲族乃古代越人的后裔。此说根据史籍中关于古越人和今天畲族在分布地域上的对照、民间传说和历史记载的偶同或从族称义、音的演变去推论以及畲、越具有共同的盘瓠传说,共同的生产方式、生产水平和共同的风俗习惯等,认为畲族乃古越人的后裔。在“越人”后裔说中,又有许多不同的具体说法,如认为畲族乃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或范蠡的子孙;有的认为畲族是我国秦汉时代的越人后裔;还有认为畲族是源于汉晋时代的“山越”,特别是与汉高祖十年(公元前197年)封地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的越人后裔南海王织有密切的渊源关系,等等。
四是“南蛮”说。王克旺、雷耀铨等人认为畲族乃“蛮”或“南蛮”的一支,但不是“武陵蛮”,畲族的历史渊源绝不迟于“武陵蛮”;他们认为盘瓠传说的范围包括《搜神记》中所说的“今即梁汉、巴蜀、武陵、长沙、庐江郡夷是也”,相当于今天大半个中国南部,而不仅流传于“武陵蛮”中;畲族和瑶族并没有共同的族源,他们的迁徙路线也没有混杂和交叉现象;畲族是广东的土著民族。
五是“闽人”后裔说。陈元煦认为畲族无论生计方式、图腾还是操持的语言,都与古越人毫无共同之处,因此畲族不可能是“越族之苗裔”。他认为闽、越乃我国南方的两个古老民族,闽族系福建土著,越族乃福建的客族,畲族先民应为“福建土人”“古闽人”。
六是“河南夷”说。肖孝正、钟玮奇等通过大量的畲族族谱的研究,认为高辛氏是皇帝正妻雷祖的长子,畲族的祖先龙麒则是高辛氏的第五个妻子刘君秀的儿子。龙麒后来生三男一女,分别为盘、蓝、雷、钟(女婿)四姓,四姓的郡望分别为“南阳” (盘姓)、“汝南”(蓝姓)、“冯翌”(雷姓)、“颍川” (钟姓),都在河南境内。因此认为畲族源于古代河南“夷”人的一支,是属于高辛氏近亲的一支氏族部落。
七是“多元一体”说。针对畲族源于武陵蛮、越人、闽人、南蛮、河南夷等单一族源的观点,谢重光则提出“多元一体”新说。认为畲族族源主要包含百越后裔、南迁武陵蛮和入畲而被畲化了的汉人三大部分,畲族是多元一体的民族。
总之,关于畲族的来源,目前仍是一个悬案,尚无定论。就个人来说,笔者更倾向于“畲族是多元一体的民族”的观点,这一观点不仅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相合,也更符合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规律。
第二节 人口状况
畲族人口是中国人口较少的散杂居少数民族之一,散布在我国东南部的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安徽等省境内。其人口发展呈现出自己的一些特点。 一、人口及分布 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畲族总人口为70.96万人,在全国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均有分布,居住较为集中的聚居区有福建、浙江、广东、江西、安徽、贵州和湖南等7个省份。其中:福建畲族人口为37.52万人,约占畲族总人口的53%,主要分布在福安、霞浦、福鼎、宁德、古田、罗源、连江、顺昌、建阳、建瓯、宁化、永安、上杭、漳浦、龙海等53个县市;浙江17.8万人,约占畲族总人口的25%,主要分布在景宁、丽水、云和、文成、泰顺、平阳、苍南、遂昌、龙游、武义、桐庐等29个县市;江西7.8万人,约占畲族总人口的11%,主要分布在贵溪、兴国、永丰、吉安、铅山、吉水、资溪、弋阳等18个县市;广东2.7万人,约占畲族总人口的3.8%,主要分布在潮州、河源、增城、博罗、惠东、丰顺、南雄、乳源等15个县市;安徽2400多人,约占畲族总人口的0.3%%,主要分布在宁国市;湖南2891人,约占畲族总人口的0.41%,主要分布在桂东、汝城、炎陵等县;贵州有4.2万人,约占畲族总人口的5.9%。
二、人口的演变
在1956年以前,虽然汉族文献中有大量“畲民”“畲瑶”“畲军”等记载,但畲族只是一个自在的族群,并没有获得国家的承认。而且由于社会上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民族歧视,畲族人很多都隐瞒自己的民族成分。因此,虽然早在唐代,蓝万兴、蓝奉高等领导的畲民起义军就曾屡挫唐军,体现了强劲的实力,但新中国成立前的畲族人口一直是一个谜。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推行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经过科学的民族识别,畲族人口经历了几次较快的增长时期。一是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经过民族调查和民族识别,闽东、浙南、广东等地大量畲族人民恢复民族成分,成为畲族人口增长的第一个高潮;二是20世纪80年代,闽西、赣南、珠三角等地又有一批畲族人民恢复民族成分,构成畲族人口增长的第二次高潮;三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贵州恢复黔东南4万多居民的畲族身份,成为畲族人口增长的又一个小高潮。
改革开放以来,畲族人口发展进入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不论在降低人口自然增长率、优化人口结构、改善人口素质等方面都取得了新的进展,正朝着人口现代化方向演进。1982年畲族人口为37.20万人,1990年达到63.47万人,净增加26.27万人,平均每年增长3.28万人,平均每年递增6.91%;2000年畲族人口达70.96万,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增加了7.49万人,增长率为1 1.80%,平均年增长率1.08%。其增长率表面看来是相当高的,但这种增长主要是通过社会增长(指更改民族成分和民族通婚子女选报为畲族人口数值)来支撑的,自然增长率并不高。以1982~1990年畲族人口的高增长率为例,自然增长仅占15.5%,社会增长达84.5%。
三、人口结构
1.畲族人口的性别与年龄结构
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畲族总人口中男性为38.10万人,女性为32.66万人,性别比为1 15∶97;在1999年11月1日~2000年10月31日,出生婴儿性别比为104∶70,这表明畲族社会有着较明显的男女不平等观念;从各年龄段的人口比例看,少年儿童人口(0~14岁)比重为26.36%,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比重为66.35%,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占7.29%,与1990年相比,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下降了5.59个百分点,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老年人口比重分别增加了3.87个和1.72个百分点。
2.畲族人口的文化结构
在畲族15岁及以上的52.25万人口中,文盲人口有6.17万人,占1 1.81%,其中男性成人文盲率为7.44%,女性成人文盲率为16.96%。文盲人口比1990年减少了6.51万人,文盲率下降了17.55%%。6岁及以上的65.54万人口中,受过小学以上(含小学)教育的占86.98%,受过初中以上(含初中)教育的占37.26%,受过高中及中专以上教育的占8.67%,受过大专、大学教育的占1.78%。平均受教育年数6.67年,比10年前增加1.41年。
3.畲族人口的劳动力就业水平与职业结构
从劳动力就业水平来看,2000年在畲族15岁及以上人口中,劳动力为39.01万人,其中从业人口37.69万,失业人口1.32万,劳动参与率为77.09%,就业率为74.49%,失业率为3.37%。从业人口中,从事第一产业的占71.64%,从事第二产业的占14.55%,从事第三产业的占13.81%。
从职业结构来看,2000年畲族从事脑力劳动工作的占全部从业人口的比率为6.45%,从事城市体力劳动的比率为21.46%,从事农村体力劳动的比率为72.09%。具体地说,担任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占从业人口的比率为0.84%,担任技术工作的占3.92%,办事员占1.68%,商业人员和服务员的比率为6.67%,从事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作的比率为14.76%,从事农林牧渔工作的占72.09%,从事其他工作的比率为0.03%。
4.畲族人口的城镇化水平
2000年,畲族人口中有城镇人口16.63万人,占总人口的23.44%;乡村人口54.33万人,占总人口的76.56%。与10年前相比,畲族城镇人口比率提高了13.95个百分点。
5.畲族人口的出生率与死亡率
1999年11月1日~2000年10月31日期间,全国畲族出生人口为7410人,总计生育率为1.29%,全国畲族死亡人口为4277人,其中男性2618人,女性1659人。粗死亡率为6.05‰,其中男性为6.89‰,女性为5.07‰,婴儿死亡率为27.75‰,预期寿命为72.41岁。
第三节 历史沿革
学术界对畲族的来源,尚无定论。但一般认为至迟到隋唐时代,畲族先民已经活跃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带的广大区域。古代畲族是山地游耕民族,从隋唐以来辗转迁徙于东南各省,历经1000多年,逐渐形成今天的分布格局。其历程大致可以分为隋唐时期、宋元时期、明清时期、近现代时期和新中国时期五个发展阶段。
一、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畲族先民被称为“蛮獠”,出没于闽、粤、赣三省交界的九龙江以西的广大山区。唐以前,这里还是化外之地,到处深林丛莽,畲族先民是这里的主要居民。
为反抗唐王朝对闽、粤、赣交界地区的控制,唐代畲族先民不断地开展武装斗争,这就是史书所谓的“蛮獠啸聚”。唐总章二年(669年),闽、粤交界地区的畲民举行暴动,并曾击败由岭南行军总管陈政率领的近4000唐军,迫使其退守九龙山待援;仪凤二年(677年),苗自成、雷万兴领导的畲民起义军攻陷潮阳县城,一时闽、粤震动。苗自成、雷万兴起义后被陈元光所镇压,大量畲民逃亡隐匿到更为偏僻的山林,但反抗并没有停止。陈元光意识到光靠武力镇压不是办法,因此向朝廷请求“置州县,以控岭表”。垂拱二年(686年),朝廷采纳陈元光建议,于十二月增置漳州郡,下辖漳浦、怀恩两县,并以陈元光为州刺史。为缓和社会矛盾,陈元光一方面加强生产建设,另一方面对畲民采取恩威并施的策略,在镇压反抗的畲民的同时,下令开山取道,派人将逃散的畲民诱抚出来,划地建立“唐化里”,专门收容归附的土著居民,还在经济上给予优待,使散移各处的畲族先民纷纷“归附”。随之大量汉民迁入,使“苗人散处之乡”变为“民獠杂处”之地。但陈元光的政策看来并没有得到畲族先民的普遍支持,景云二年(711年)十一月,雷万兴、苗自成之子又在潮州率领畲民起事,并率众潜抵岳山,仓促率轻骑抵御的陈元光被蓝奉高刀伤腰部,重伤而死。陈元光死后,因其开发漳州的卓著功勋,被后世尊为“开漳圣王”。
汀州则在开元二十四年(736年)设置。因不满王氏(王潮、王审知、王延翰)集团的统治和歧视,唐昭宗乾宁元年(894年),发生了以畲民为主的“黄连峒蛮二万围汀州”事件,结果被王潮部将李承勋击破。黄连峒蛮被镇压后,闽西的土著势力受到沉重打击,很久不能恢复元气。此后直到北宋末年,大规模的蛮獠武装反抗斗争较少。
整个隋唐时期,畲族先民主要在潮(州)漳(州)汀(州)一带活动。他们和汉族(特别是客家先民)一起,拓荒垦殖,使林木荫翳、荆棘丛生的荒地,“渐成村落,拓地千里”,山区得到开发,生产得到发展。这一时期畲民较远距离的迁徙发生在唐昭宗景福元年(892年),王潮、王审知攻取福州时, “平湖洞及滨海蛮夷皆以兵船助之”,这段往事也体现在闽、浙两地各姓畲族的谱牒中。学者一般认为,平湖洞及滨海蛮夷是畲族先民中杂有夷蜑成分较多的部分。这些随船而住的畲民后来在闽东的连江、罗源登岸,并陆续迁往闽东、浙南诸地,成为当地最早的畲族移民。
二、宋元时期
两宋时期,虽然高宗绍兴年间,有赣、闽、粤边“汀、虔、潮、惠山寇为乱”;理宗绍定、端平年间,闽西和赣南又爆发了晏头陀和陈三枪为首的“寇变”;孝宗隆兴年间长汀县葛畲的寇乱及光宗绍熙中上杭县峒寇结他峒为乱等事件,这些以畲族为主的武装斗争,最终导致不少畲民逃亡、流徙,但畲族的活动地域基本上仍在原有的聚居区内。刘克庄的《漳州谕畲》对宋代闽南畲族地区政治、经济有比较典型、详细的描述。宋末元初和元代,闽、粤、赣交界地区的畲民也参加到风起云涌的抗元斗争之中,由于连年战乱,各地畲军、畲兵的征战调动和戍城、屯田,造成畲族的迁徙路线错综复杂,迁徙的范围也随之扩大。总体来说,这个时期的移民相当部分属于军事性质的移民,最有代表性的是陈吊眼、许夫人、钟明亮等多支抗元畲军于漳州、潮州、泉州、汀州、赣州等处的转战屯守移民。
陈吊眼于至元十三年(1276年)自漳浦举义后,一路攻城掠地,由漳浦、漳州、安溪进抵泉州,配合文天祥、张世杰共讨蒲寿庚,大批畲民随军参战。与此同时,潮州畲族民妇许夫人也率诸峒畲户起兵,由潮州、云霄、诏安到达漳浦,在漳浦与陈吊眼会师后挥师泉州。后陈、许义军遭元军镇压失利,被迫退守漳浦千壁岭。此时黄华在闽北揭竿而起,抗击元军。许夫人又亲率畲军取道元军势力较弱的漳浦、漳州、汀州、南平、邵武一线,转战闽北,汇入黄华的义军队伍,抗击元军达十年之久。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钟明亮在广东循州举义,他们转战于漳州、汀州、赣州等地,得到泉州、龙溪、汀州、南平、赣州、吉安等地畲民的热烈响应,一时“拥兵十万,声摇数郡”。各路起义失败后,元朝政府“令于南诏黎、畲各立屯田……及将所招陈吊眼等余党入屯,与军人相参耕种,为户汀州屯一千五百二十五名、漳州屯一千五百一十三名”;又“诏福建黄华畲军有恒产者放为民,无恒产与妻子者,编为守城军”。随着各路义军的转战和战后元廷的安置,参战的畲民也随之播迁闽南、闽西、闽北、赣南等各地。
宋元时期,畲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比唐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汉族地主和封建官吏对畲民进行繁重的赋税征收,土地掠夺也随之加重,畲民丧失了赖以生存的资源,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入元以来,元朝统治者更是强占长汀路畲民的土地作为赐地,使畲民无以为生,这是导致畲民积极投身抗元运动、福建成为抗元斗争最为激烈的省份之一的重要原因。在日益加强的封建势力的分化统治下,宋元时期畲族内部开始出现明显的阶级分化。如刘克庄《漳州谕畲》记载,南宋时期的漳州“西九畲酋长相继受招”和“南畲三十余所酋长,各籍户口三十余家,愿为版籍民”。《元史》也记载元初畲军中“有恒产”和“无恒产者”之区别。
三、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是畲族大量迁往汉族地区和形成目前的“大分散,小聚居”分布格局的重要历史时段。与宋元时期相比,这个时期畲族的迁徙活动频繁,迁徙路线复杂,迁徙范围更为广泛,几乎遍及闽、粤、赣、浙、皖、湘、贵等省山区,基本形成了今天畲族的分布格局。这个时期畲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活相对比较安定,其迁移主要是基于畲族山地游耕的传统而非军事性质。这种迁徙的速度缓慢,迁徙的方式以家庭或家族中若干成员为单位徐徐而行,迁徙的取向是相对地广人稀的汉族地区。概而言之,广东畲族多迁至福建、浙江,福建畲族多迁至江西、浙江,浙江畲族多迁至安徽,而江西畲族则迁至湖南、贵州。
明清时期,畲区的封建社会已经确立,其社会经济状况和当地汉族基本一致。这个时期的畲族经过长期的动荡和迁徙以后,已基本稳定在闽、浙、粤、赣、皖、贵、湘等省的广大山区,对各地山区的开发(尤其对闽东、浙南山区的开发)作出了重要贡献。当畲族迁到闽东、浙南时,自然条件较好的平坝地方已多为汉人开垦,畲民只能在山谷冈麓地带开山劈岭,建造田园。有水源之处开为梯田,仰赖雨水的山地,辟为旱田。据浙江地方史志记载,浙西南景宁、云和的土地就多为畲民所开垦。此外,明代闽西南还有一批以种菁为业的畲民,迁徙到莆田、永泰、古田、罗源等山区以种菁为生。明代福建菁以量多质好闻名全国,畲族的贡献是巨大的。
经过几个世纪的长途跋涉,畲族终于在闽、粤、赣、浙、皖、贵、湘等省的广大山区找到了定居点,到清代基本稳定下来,停止迁徙。畲族地区的社会生产力获得了较大发展,通过耕种自己的少量土地或租种汉人的土地,畲民由此进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完全结束了传统的刀耕火种的游耕农业生活。
四、近现代时期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居住在东南沿海的畲族也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逐步地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命运中。在资本主义列强的炮舰威迫下,清政府被迫开放福州、温州等通商口岸,列强的大量商品源源不断地经由水陆交通输至福州口岸附近的闽东和温州口岸附近的浙南畲乡,对畲族社会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使其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走上崩溃的道路。如机制洋纱洋布的输入,排斥了农民手工纺织的土纱土布,使在畲族家庭手工业中占重要地位的手工纺织业遭到极大破坏。质好价廉的洋靛的输入,使种菁为生的畲民的生活受到巨大冲击,大量种菁为业的畲民不得不另谋生路。鸦片的输入更是危害巨大,清政府为加强税收剥削,竟强迫畲、汉农民种植鸦片,闽东许多畲民被迫将良田改种罂粟,造成农业生产的严重破坏。
畲族地区的经济生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剥削关系依旧保存下来,绝大部分土地仍然集中在汉族地主手中。而广大贫苦畲民或向汉族地主租佃土地,承受高额的地租剥削;或流入城市,终年出卖劳动力,变成游民无产者,生活陷入朝不保夕的境地。他们为了求生存、得解放,整个近现代时期,始终同汉族人民一起,支持太平天国运动,反洋教,发动新军起义,组织农民自卫军,展开如火如荼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经受了斗争的洗礼。
大革命时期,彭湃领导的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中就有畲民参加,与广东相邻的闽西、赣南的畲族地区也有畲族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土地革命时期,闽、浙、赣等广大的畲族地区都燃起了革命的火焰,畲族人民打土豪分田地,成立了工农武装政权。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册中,写下畲族革命的壮丽篇章。今天在上杭县汀江河畔辟为博物馆的临江楼陈列室中107位长征战士中有8名是畲族。闽东是畲族主要聚居区,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畲族地区成为党和红军的可靠的根据地,在1938年北上抗日的新四军三支队六团中有畲族指战员218人。该县还出现两名共和国的将军蓝庭辉、雷钦。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新中国的诞生,为了民族解放事业,畲族人民贡献出热血和生命。
五、新中国成立以后
1949年以后,畲族地区陆续获得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并展开了一系列的民族调查和民族识别,1956年12月,国务院正式确认畲族为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
经过50年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使畲乡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生活日渐安定,经济收入稳步提高,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各项事业不断发展,畲族社会已进入全新的历史征程。
第四节 生态资源
畲族广泛分布于长江以南的闽、浙、赣、粤、皖、湘、贵各省的山区,境内山林密布,层峦叠嶂,沟壑纵横,气候优越,生态条件得天独厚,堪称镶嵌在南中国版图上的“绿色明珠”。 一、气候条件优越畲族地区的气候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受海洋性气候的影响很大,光热充足,雨量充沛,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多在13℃~20℃,年降水量一般在800~1600毫米。因境内地形复杂,海拔高度悬殊,气候垂直差异明显。一般冬季比较寒冷,霜期短,下雪少。但各地畲族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又有一定的差异。闽东畲族最多的福安市,年平均气温16℃~18℃,无霜期260~270天,年降雨量在1540~1700毫米。
这种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为农业和林业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因此在畲族山区,谷物、茶叶、红薯等亚热带作物的种植久负盛名,香菇、竹笋等也是畲族山区重要的林产品。
二、地形地貌复杂
畲族分布的地区,山脉纵横交错,峰峦起伏,丘陵密布,地势大致自西北向东南沿海倾斜,山脉由东北西南走向。主要有闽、赣两省边境的武夷山、玳瑁山、仙霞岭、杉岭等。武夷山为福建第一名山,主峰黄岗山海拔高2158米。浙江东南部有雁荡、括苍、洞宫诸山。广东有罗浮、莲花、凤凰诸山。此外,还有闽北的鹫峰山和闽东的太姥山等。多山峦叠嶂,奇峰险谷,花岗岩地貌、丹霞地貌发达,为著名的游览胜地。
畲族地区溪流回绕,溪水多集诸山两侧之水,从深山峡谷中跌宕奔流出来,汇入闽江、瓯江、汀江。闽江源于武夷山,流经福州,注入东海。瓯江源于龙泉溪,汇丽水大溪与青田小溪后,流经温州,注入东海。汀江发源于武夷山南麓的东南一侧的宁化县治平乡,流经长汀、武平、上杭、永定4县,经永定出境进入广东与梅江汇合后称韩江。各条江河支流多、流域面积广,为畲族地区的水运交通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这些河流穿越深沟峡谷,跌宕奔涌,落差都很大,蕴含的水力资源也十分丰富。目前闽江、瓯江、汀江都进行了多级水利开发,为闽、浙地区包括畲区在内的城乡社会发展输送了大量清洁能源。
三、生物资源呈多样性
畲族地区林区面积大,森林覆盖率高,树木种类多,常见的有松、杉、樟、楠、柏、桉、青冈栎、泡桐、竹等,也有世界稀有的珍贵树种栓皮栎、檫树、红豆杉和柳杉等。木材蓄积量以松、杉为最大。景宁畲族自治县是浙江省重点林业基地之一,森林资源特别丰富,植被有针叶林、阔叶林、针阔混交林、竹林、灌木丛等5种类型,乔木、灌木、草木层次齐全。据不完全统计,景宁县的木本植物有1552种,其中有利用价值的就有1469种。用材林有松、杉、杂木等,经济林有厚朴、茶叶、油桐、油茶、柑橘、乌桕、雪梨等。闽北、闽东的武夷山、戴云山、太姥山等山脉,森林密布,也是我国重要的林区之一,素有“绿色金库”之美称。武夷山区还保留有大片的南方铁杉、小叶黄杨、武夷玉山竹等珍稀植物群落,几乎囊括了中国亚热带所有的亚热带原生性常绿阔叶林和岩生性植被群落。有许多珍贵的珍奇树种,如成片的高山矮林、铁杉林以及香榧、亮叶水青冈、红叶甘钧、响叶杨、北方银杏、花榈木、南方肉桂、黄杨木、红豆杉、鹅掌楸等。
畲族山区的林间动物资源也十分丰富。仅景宁畲族自治县,野生动物就有国家一类保护动物黑麂、白颈长尾雉、云豹、金雕、短尾猴等44种。全县共有脊椎动物31目78科272种。其中:兽类8目20科48种,鸟类15目40科162种,爬行类3目9科30种,两栖类2目5科18种,鱼类3目4科40多种。而在武夷山自然保护区中有哺乳动物100余种,占全国同类动物总数的1/4;鸟类400余种,占全国总数的近1/3,堪称是“鸟的王国”。两栖和爬行动物100余种,崇安髭蟾、蝾螈、三港雨蛙、大头平胸龟、丽棘蜥等均为世界罕见的特有种,所以这里被誉为研究“亚洲两栖和爬行动物的钥匙”。鱼类也有30余种,新近还发现一个新种——武夷厚唇鱼。武夷山自然保护区中昆虫的丰富程度也是我国其他地区少有的,全国昆虫32个目,保护区采到的就占31目,估计可达2万余种之多。保护区内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动物有华南虎、白颈长尾雉、金猫、大灵猫、穿山甲、猕猴、云豹、毛冠鹿、短尾猴、小灵猫、黄腹角雉、鬣羚等57种。
四、矿产资源较丰富
畲族山区地下矿藏有铁、煤、金、铜、钼、明矾、石墨、石膏、硫磺、滑石、云母石、瓷土以及其他多种有色金属。有的储量相当丰富,如业已探明的景宁畲族自治县的包山、敕木山铁矿,总储量为400万吨;三枝树的钼矿,储藏量达1万多吨。浙江武义、永康的萤石矿的储量也都很大。闽东畲族地区目前已探明的金属、非金属矿产就有20多种,其中钼精矿、高岭土、辉绿岩等矿产储量相当丰富。这些矿产都是国家的珍贵宝藏,它们的开发,将为畲族地区的发展带来坚实的物质保障。
第五节 语言文字
畲族内部有自己的交流语言,但各地又有所差别,没有自己的文字,通用汉文。畲族历史上曾经有过一种共同的语言——古畲语,但在与汉、瑶、苗等民族的长期杂居相处的过程中,这种语言逐渐演变、分化成了现代畲族使用的三种语言:惠东畲语、福安畲语与贵州畲语。 一、古畲语 早在隋唐时代,闽、粤、赣结合部就已经形成了相当广阔的畲族聚居区,从当时畲民的多次军事行动来看,这里聚居的畲族人口数量是相当庞大的。这些畲族先民用以交流的语言,就是古畲语。随着汉人,特别是客家先民的大量迁入和畲民的流徙,这种古畲语便在民族交融中逐渐消失。但在今天畲族使用的畲语中,我们仍可以发现一些古畲语“底层”的痕迹。虽然我们很难凭这些痕迹勾勒古畲语的全貌,但我们可以确信,现代畲语正是古畲语在融合客家方言和其他地方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
二、惠东方言
惠东畲语是居住于广东莲花山区、罗浮山区的惠东、海丰、博罗、增城4个县共1200多自称“活聂” (山人)的畲族所使用的语言。这种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跟瑶族布努语炯奈话比较接近。
毛宗武、蒙朝吉等认为,历史上畲族先民曾使用过一种语言,后来绝大部分畲族因长期与汉族客家人交错杂居,便逐渐放弃了自己的语言,改用汉语客家话进行交流;而居住在莲花山区和罗浮山区的这一小部分畲族,因“深居崇山峻岭,很少与外界接触”,则没有放弃自己的语言。因此,现在的惠东畲语就是被保留下来的古畲语。①
这个观点受到不少质疑。蓝周根、雷先根就反对关于“畲族放弃了自己的语言,改用汉语客家方言交际”的观点,他们认为现在绝大多数畲族使用的接近汉语客家方言的语言就是畲族的民族语言。②朱洪、姜永兴等也认为,“罗浮山、莲花山的畲语明显受到瑶语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延至凤凰山则又消失殆尽。”“这是瑶文化对罗浮山、莲花山畲族的渗透以及两个民族在粤中的交融关系而造成,故罗浮山、莲花山的畲语是否就是畲族的原生型语言,值得进一步研究。”③而雷阵鸣更认为惠东畲族相传的原籍、族谱记载的盘瓠传说、语言的系属等都与瑶族接近,而且他们一直都自称是瑶族、瑶人,因此惠东畲族究竟是畲族还是瑶族都有待商榷,更不宜将惠东畲语定性为畲族的原生语言。
这些质疑显然是有一定道理的。惠东畲语与讲炯奈话瑶族相似到可以无障碍通话的程度,却与其他绝大多数畲族的语言毫无相同之处,把它定位为畲族原生型语言,确实有商榷的必要。 三、福安畲语 福安畲语是除广东的惠东4县和贵州畲族外,其他分布在福建、浙江、江西、安徽等省以及广东的潮州、丰顺等地的畲族所共同使用的语言。由于福安畲语和客家话存在许多相似性,曾有一些学者认为闽、浙、赣等地畲族讲的福安畲语就是客家话。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特别是畲族学者开始质疑这种观点。一方面是因为福安畲语和客家话之间确实存在着差别,另一方面,则是福安畲语和客家话都是古中原汉语和古畲语在闽、粤、赣结合部畲族和客家交错聚居的广大地区,长期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下形成的。在隋唐至宋元的漫长时间里,这个地区的畲族和客家谁都不存在绝对的强势,也就不可能形成一种文化吞并另一种文化的问题。说畲族人放弃本民族语言,改用客家话交流的观点是很难站得住脚的。客家话之所以区别于中原汉语,就在于它本身就融入了大量畲语成分。
有学者认为,福安畲语是由古畲语演变而来的。从古畲语到福安畲语,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是宋元时期,古畲语与中原汉语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形成类似客家话的畲语;第二阶段是明清时期,这种类似客家话的畲语与畲族新居地的汉语方言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形成现在的福安畲语。因此,虽然福安畲语与汉语客家话接近,但两者是有区别的。福安畲语有其自身的特点,如它的语音声母单纯,韵母发达,声调复杂,变调现象较普遍,音节多。其词汇分虚、实两大类11种,实词尤为丰富,构词特点:多单音词,多转借和引申词,多偏正倒置词,保留不少古汉语词汇和词素。1994年福建省民委对罗源畲语100个常用词作了分析,其中粤语占14个,客家话占13个,闽南、潮州语占6个,福州语占43个,其余24个不属上述语类。其语法特点是以特定的语序、虚词和语感来表情达意,具有民族性、稳固性和一致性。畲语还有一些带有传统性和稳固性的隐语,起助趣、避讳、盘问作用。
因受当地汉语方言的影响,福安畲语所属的各地畲语事实上存在着差别,一般又分为福安方言片区、丽水方言片区、连罗方言片区、顺昌方言片区和华安方言片区等5个方言片区。①
四、贵州畲语
贵州畲语是分布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麻江县、凯里市,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福泉市和都匀市的畲族所使用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惠水次方言。贵州畲语的使用人口4.2万,约占畲族总人口的5.9%。
贵州畲族先祖多是元末和明洪武年间,或奉旨征讨、迁徙,或避祸而迁入贵州,但仍保持着本民族的语言。据1982年贵州省民族识别办公室语言组对畲族语言的调查,贵州畲族虽没有文字,但在其聚居的乡镇,男女老幼都说畲语,散居的畲族在社交活动中基本上用汉语。
贵州畲语的语音有闭塞音、塞擦音、塞边音等,分不带鼻冠音和带鼻冠音两种。贵州畲族语与汉语在音节分类、性质分类、结构分类方面基本相同,但语法和语义有很大差别。对于贵州畲语的形成,目前还没有系统的研究。比较大的可能是,元末明初,一群讲类似客家话的福安畲语的畲族因战乱或避祸,由江西迁入贵州定居,在之后数百年的时间里,他们与讲苗语惠水方言的当地苗人、瑶人长期杂居共处。在经济、生产、生活、婚姻等的长期互动过程中,出于需要,他们逐渐将这种语言与自己原来的畲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现在的贵州畲语。
除上述畲语人群外,闽西上杭、长汀等地的3万多畲族人所讲的语言与当地汉族的客家话已没有区别。
第六节 民族区域自治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为解决民族问题,推动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发展而采取的重要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成功施行,改变了过去少数民族受歧视的状况,使少数民族真正当家做了主人。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中国少数民族依法自主地管理本民族事务,民主地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保证了中国各民族不论大小都享有平等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权利。
一、畲族区域自治概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便开始着手解决历史遗留的一系列民族问题。根据中央的安排,在畲族聚居的福建、浙江、广东、江西和安徽各省各级人民政府都逐步设立和健全了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事务处和民族事务科等机构,专门负责管理包括畲族在内的少数民族事务,并着手筹划民族识别问题。
1952年,福建省人民政府派出工作组到闽东福安县仙洋岭村进行民族调查。1 952年7月8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畲族福安县仙岭洋村调查情况》,这是福建省第一份关于畲族的专门调查报告。报告阐述了“根据共同纲领精神,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问题,为畲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进行了先期的准备。同年9月11日,仙岩乡畲族农民雷霖其成为福建省第一位进京的畲族代表。1953年2月,福安县人民政府遵照1952年政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的精神,在第十一区畲族聚居的仙岩乡建立新中国成立后福建省第一个畲族自治政府——畲族仙岩乡自治区人民政府,这也是畲族管理本民族事务的第一次尝试。
1953年8月,以施联朱为组长的畲族民族识别调查研究小组开始奔赴浙江景宁,福建罗源、漳平等地进行为期3个月的畲民识别调查。1956年12月,国务院正式确认畲族为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畲族从此有了自己正式的、合法的民族身份。
遵照1955年国务院的《关于建立民族乡若干问题的指示》,从1957年开始,福建、浙江等省在畲族聚居的若干区域成立区人民政府管辖下的畲族乡人民委员会。仅1957年7月~10月,福安县就先后成立了仙岩、竹岭、燕洋、王溪、东南、凤洋、蓝山、碧后、茶洋、山岭、半岭、长山、林洋等13个畲族乡。到1958年底,畲族人口最集中的闽东北和浙西南就先后成立了50个畲族乡人民委员会。畲族乡中畲族人口在50%以上,正副乡长、乡政委员、乡人民代表的畲族比例都在70%以上。
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大量的畲族乡委员会被取消。1983年国务院发出《关于建立民族乡的通知》,开始对民族乡进行规范化工作。遵照通知精神,从1984年起,闽、粤、浙、赣、皖等省重新在畲族聚居地区陆续建立畲族乡人民政府。到目前为止,全国共建有畲族乡(镇)45个,其中福建17个,浙江18个,江西8个,广东和安徽各1个。畲族乡内的畲族人口占畲族总人口的30%,各畲族乡(镇)乡(镇)长均由畲族担任。
1984年6月30日,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这是中国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的一个畲族自治县。
二、景宁畲族自治县简介
景宁畲族自治县隶属浙江省丽水市,地处浙江省南部,东邻青田县、文成县,南衔泰顺县和福建省的寿宁县,西接庆元县、龙泉市,北毗云和县、东北连丽水市。全境南北长58.8公里,东西宽73.3公里,总面积1949.98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0.4万亩,山地面积269万亩,辖5个镇19个乡283个行政村。景宁全县有汉、畲、苗、藏、彝、回、侗、黎等8个少数民族,总人口17.9万人,其中畲族人口1.78万人。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驻鹤溪镇,是全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华东地区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属浙江省经济欠发达地区。
景宁畲族自治县境西周时属越,春秋仍属越地。三国时属临海郡,隋开皇九年(589年)废永嘉、临海二郡,置处州设立括苍县(含景宁地域)。明景泰三年(1452年)巡抚孙原员以“山谷险远,矿徒啸聚”为由始置景宁县。1949年5月12日景宁城解放,5月21日建立景宁县人民政府。1952年丽水专区撤销,改属温州专区。1960年景宁县并入丽水县。1962年划丽水县原云和县、景宁县辖地置云和县,属温州专区。1963年5月丽水地区复设,辖云和县(含景宁),1984年6月30日经国务院批准,析云和县原景宁县地域建立景宁畲族自治县。1985年4月22日,即畲族传统的“三月三”节,县人民政府在驻地鹤溪镇举行盛会,庆祝我国第一个畲族自治县正式成立。
景宁县境内峰峦叠嶂,沟壑纵横,洞宫山脉自西南向东北延伸,贯穿全境。县境溪涧众多,主要属瓯江、飞云江两大水系。境内山川起伏,巨大的海拔落差,使景宁的溪涧、河流蕴藏了极为丰富的水力资源。景宁县十分重视水力资源开发,把发展农村小水电作为振兴景宁经济,实现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战略重点,目前全县已建成各类电站100多座,装机容量20多万千瓦,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农村水电之乡”。
景宁县属亚热带季风区,温暖湿润,雨量充沛,四季分明。境内物产丰富,有植物178科,691属,1552余种;脊椎动物31目,78科,272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44种);有20余种矿产资源,钼矿的储量居浙江省之首。这里还是惠明茶的原产地,人工栽培香菇的发源地,同时也是浙江省的黑木耳、厚朴、茯苓生产的重点基地之一。
景宁畲族文化丰富多彩,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有优美动人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粗犷朴实、奔放刚健的舞蹈,富有哲理的谚语,工艺精巧的刺绣编织等,尤以民歌为胜。新中国成立前,民歌、传说故事多口头流传,也有手抄本。新中国成立后,经发掘整理,艺术水平大有提高。畲族自治县建立后,文化活动内容更广泛,形式更多样。1984年8月,浙江省第一次畲族文化工作会议在景宁举行。1987年6月,景宁畲族自治县政府与省博物馆联合在杭州举办畲族文物展览。1987年和1990年,丽水电视台先后摄制畲乡专题片《畲乡风情》《畲乡风》,在中央电视台、浙江电视台播放。1992年12月,首届景宁畲乡文化节在鹤溪镇举行,展现了丰富的畲族文化。2009年3月28日,景宁畲族自治县被国家文化部授予“中华民族艺术之乡”的荣誉称号。
附注
①谢重光、张春兰:《畲族文化研究的新收获——2009年全国畲族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宁德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①陈永成:《福建畲族档案资料选编》,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
①毛宗武、蒙朝吉:《畲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6年。
②蓝周根: 《畲族有自己的语言》,载《畲族研究论文集》,民族出版社,1987年;雷先根:《畲语刍义》,载《畲族历史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
③朱洪、姜永兴:《广东畲族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①参阅《中国民族文化大观·畲族篇》,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60~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