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畲族服饰在当代社会中的嬗变与动因
| 内容出处: | 《浙闽地区畲族服饰比较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920020230005642 |
| 颗粒名称: | 第六章 畲族服饰在当代社会中的嬗变与动因 |
| 分类号: | TS941.742.883 |
| 页数: | 9 |
| 页码: | 179-187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畲族传统服饰在当代社会中发生了嬗变,主要原因包括穿着场合变化、外观形材变化、工艺技术变化和着装心态变化。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使得畲族传统服饰从日常生活中逐渐蜕变为节庆和表演场合的着装。服饰外观方面,颜色和装饰面积增大,制作材料也发生了变化,传统手工艺被机器工艺所代替。此外,着装心态的变化也对服饰产生了影响,畲族服饰更多地用作表演和特殊场合的装束,而不是为自己的日常穿着。 |
| 关键词: | 畲族服饰 嬗变 动因 浙闽地区 |
内容
第一节 畲族传统服饰在当代社会中的嬗变
一 穿着场合变化
在畲族的历史发展中,畲族服饰是畲民日常生活和各种节庆、祭祀及重要活动的装束,贯穿于畲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同场合有不同的民族服饰习惯。随着现代文明的介入,畲乡经济发展迅速,同时很多畲族青壮年离开山村进城求学、打工,畲族人民逐渐接受了新的生活方式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主流服饰,而传统畲族服饰则逐渐蜕变为节庆和表演场合的着装。这种变化最先由畲族青年和男子开始,留守在家的老年妇女则坚守传统服饰的最后一块阵地,所以在田野调查中,越是交通闭塞的山村传统服饰保持得相对越好,而在浙南景宁的东弄村、双后岗村一带,由于距离县城较近,公路和公交巴士都已修到村口,这一带的畲族男女老少平时基本都是现代服饰装束,仅在三月三等大型节庆活动或民族歌会、畲族婚嫁表演时才穿戴民族服饰,浙江省桐庐县莪山畲族乡由于属于杭州市辖区,经济水平较高,当地人从商开厂的较多,日常生活中的畲族服饰文化保持得相对较少。另一方面,这种变化和该畲族地区人口的稠密程度成反比,畲族人口越稀少的地方相应的服饰文化抗击外来冲击的能力越弱小,受到的冲击越明显。福建闽东畲族人口密集,畲族杂散居的村镇相互距离不远,在这些地区尚能遇到极少在日常生活中仍保留民族服饰的老人,且畲族老年妇女中传统发髻的保持率较高;而闽北、闽西、闽南的畲族人口稀少,分布地区成零星散落装,所以这些地区的服饰受汉族影响最大,平时已几乎无人穿着畲族传统服饰,仅在组织大型民族活动时穿着新制作的民族服饰进行表演,而且这些新畲服普遍存在工艺粗糙、形制混乱的缺点。
潘宏立①认为畲族群众日常服饰的改装进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男子改装,最迟至清末,畲族男装完成了汉化的过程,梳长辫子穿长袍马褂,后这种清朝官服的样式被延续作为畲族婚礼中男子的服饰装扮。第二阶段是清末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这一阶段女性服饰发生改变,景宁及闽东的大部分妇女开始接受汉族服饰,且发饰也发生改变,闽北光泽、漳平等地从这时起不梳民族发髻。第三阶段是1949年后,改装呈加速状态,首先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至1958年“大跃进”时期,在民族平等政策下大部分畲族地区实现了日常生活改装,然后是“大跃进”至“文化大革命”期间,畲汉文化进一步交融,政治运动影响下一批老旧服饰被销毁,最后是“文化大革命”后至今,其速度和规模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几乎所有的畲族村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这种穿着场合变化是随着现代文明和经济发展的影响逐步形成的,以宁德八都乡猴盾村为例: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青年妇女几乎天天穿民族服装,到80年代,女青年只有外出做客时才穿民族服装,到80年代中后期,日常生活中已不穿民族服饰了。在福鼎硖门瑞云村,大约从1978年前后开始改装,连结婚也有穿普通的现代服装的(现在畲族结婚服装形式多样,有穿传统服饰的,也有穿西式礼服的)。
所以,畲族服饰这种穿着场合的变化是随着畲民生活方式的变化而产生的,现代生活中畲族传统服饰的穿着从贯穿生活的各个方面蜕变为表演服装则是畲族服饰在当代社会中发生的最大的变化。
二 外观形材变化
社会经济发展一方面使畲民生活节奏加快,打破了以往以山地耕猎为主的经济生活模式,工作之余人们花费在服饰手工艺上的时间转而用在各种娱乐休闲活动中,家庭自制服装已经基本退出了畲民生活,民族服饰的主要来源是裁缝定做和购买成衣。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及现代服装纺织技术的提升使服装面辅料也产生了变化,以往常用的棉麻材料被现代化纤材料和丝绸材料所取代,服装上很多费时费工的彩带、镶滚、刺绣手工也被机织花边和机器刺绣替代。
相对于穿着场合变化而言,服饰外观式样、造型以及制作材料的变化是畲族服饰本身发生的重要变化。由于伴随社会经济发展而使畲族服饰的穿着场合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使畲族服饰从满足日常生活需求的日常服饰转变为以满足展示需求为主的表演服饰,这种转变必然使服饰向更为华丽、隆重的方向发展。在服饰外观上表现为色彩脱离了传统的衣尚青蓝转而选择艳丽明朗的大红大绿,服装上的装饰面积增大,发饰等也尽量往华丽的方向发展。比如传统罗源老年妇女所梳凤凰髻为蓝色绒绳缠绕,且头顶的发桃不像青年妇女那么高耸,较为矮小,衣襟的花边也仅有边口处有带状边饰,并非像青年女装铺开至肩部那么夸张。但在现代表演服饰中,几乎所有的罗源式服饰均以青年已婚女子的造型为蓝本,头顶为高耸的红色发桃。很多民族服饰的制作材料也由原先的棉麻质地改为化纤面料,一些镶边、彩带等传统手工被现代机织花边所取代,其色彩、光泽、质地等均与传统样式有较大差异。另外,由于各民族间文化交流的增强以及信息沟通的便捷,各民族服饰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交流互通,由此也产生了民族服饰元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并对服饰的外观形制产生了影响。在这种影响下,畲族服饰的外观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在新制作的一些畲族服饰中杂糅了一些其他民族服饰中的元素,如北方民族的毛边、苗族的百褶裙和花片裙。
作为畲族服饰中典型性和标志性最强的头饰,在外观形材上的变化更大,除了一些畲民家庭中保存的老式凤冠外,在众多表演和活动中广大畲族女子所戴的都是改装过的简易凤冠,以红黑毛线缠绕而成,做成头箍戴在头上(见图6-1)。
三 工艺技术变化
传统畲族服饰中一些传统工艺逐渐式微,主要表现为彩带在年青一代中的传承比例急剧下降,在很多新制的畲族服饰中都采用机织花边代替传统手织彩带,有的是按照彩带上的字符纹样进行电脑绣花制成,更多的甚至直接用市场上买来的花卉图案花边充当彩带。另外,服装中原来层层叠加的镶滚工艺的运用逐渐减少,手工刺绣被机绣代替。景宁式女子服装中“兰观衫”的花边以及男子服装门襟领圈处的边缘装饰都是通过不同色彩的面料以镶嵌或镶拼的手法制作而成的,但现在的新制作的服装上这些镶边都以花边代替了,仅在服装本料上以市场购买的成品花边简单车缝在边缘位置,女装的花边装饰部位也出于简化工艺的目的由原来的锁骨处直角转弯镶边改为绕领圈一周满镶,或从肩缝处开始不做弯角直接顺延至腋下。
花边是现在各民族新制作的民族服饰中大量用到的装饰辅件,都喜欢用它替代本民族原有的边缘装饰,殊不知这种改镶边为花边的工艺手法看似工艺更简单并且使服装更加华丽,但传统工艺和形制的流失反而使服装失去了民族特性,这或许正是服饰认知调查中很多人认为看到身着畲族服饰的人,能认出是少数民族但不能确定是畲族的原因之一。不论技术如何发展,丧失了传统工艺的雕琢,工业化、规模化生产出的服饰制品和传统服饰相比只能说是形似而神失。传统服饰制作者(有时是穿着者本人)在制作时是怀揣着对生活的美好祝福和愿景的,在现代服饰生产中则有一种误区,认为花边和鲜艳的色彩就是民族服饰的符号,单纯以强烈的色彩对比和大量的花边引起视觉刺激,反而丧失了传统工艺的精致与含蓄。
四 着装心态变化
民族服饰是民族情感和审美心理的一种物化的表现,民族服饰所传达的是一种族群认同、祖先文化和一定经济生活环境下的审美观,畲族先民们穿着民族服饰、佩戴带有民族图腾意味的头饰冠戴之时是怀着对祖先的信仰和崇拜之情的。例如,旧时畲民对于自己的服装制式是非常敏感且固守的。何子星在提到畲民自织的凤冠上裹的红布时说:“其他一布,名为畲客帽布;彼族甚敬重之”①。笔者在田野工作中走访畲族村中上了年纪的畲族老人时,当她们珍而重之地拿出压箱底的凤冠珠饰给我们展示时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这种对民族服饰的谨慎与敬重。然而在现代社会,随着民族间的混杂居、自由通婚、语言一致等民族政策的实施,畲族青年中首先破除了封建迷信的鬼神思想,对于宗族观念普遍产生了淡化情绪,民族固守意识和民族自我意识也逐渐淡化。服饰审美情感与社会主流意识趋同,对于着装心态也由固守民族服饰观念转而追求时尚、舒适、便捷以及符合当下流行的审美观。当代畲民穿着民族服饰更多是为了一种民俗表演性质的展示,换言之,他们的服饰不是为自己而穿,而是为了满足观赏者的需求甚至仅仅作为一种特殊场合的“工作服”而穿。一些民俗表演中部分畲族服饰的穿着者可能并不是畲族,而是进行表演的汉族人,他们对于服装所传达的民族情感更加淡漠。由此,民族服饰进一步蜕化到工作表演装的定位,对工作服能心怀敬意已属不易,遑论其原始的祖先崇拜与信仰了。这种着装心态的转变是畲族服饰在当代社会中最重要的变化,因为服饰的物质表现实体是基于穿着服饰的人的审美观念和着装心理上的产物。当着装心态发生变化时,服饰也必然受其影响发生外观改变以迎合新的着装心理。
第二节 导致畲族服饰发生嬗变的因素
一 文化濡化与涵化的自然结果
文化濡化和文化涵化是社会学和人类学中的概念,分别代表文化传递的两种基本模式。“文化濡化”是指一种“主动态”,强调从文化中学习到价值与规划,其重要作用在于保持文化传递的连贯性;“文化涵化”是指一个群体如社会、国家、族群,尤其是一个部落因接触而接受另外一个群体的文化特征和社会模式的过程,强调外来文化的价值与规范,其重要作用在于保持文化传递的变迁性,其涵化深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的差异性。民族服饰不可能一成不变,它必然随着社会发展和民族发展而产生相应的演进,民族服饰文化也随着民族文化的变迁而发生变化,畲族服饰在当代社会中的嬗变就是文化濡化和文化涵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文化濡化”概念的核心是人及人的文化获得和传承机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承和文化濡化方式,有时候可以是通过族群个体主观习得的一种技艺、认知或相关文化传统,有时候是身处该民族的文化环境中耳濡目染获得的一种文化传承。“文化涵化”则表现为族群在民族发展中主动或被动地接受另一个群体的文化,在畲族发展历史上,畲汉文化交融的结果体现在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包括服饰形制与装饰特征,这种主动对异文化的接受与认同一般是对相较本民族的现代化程度更高、经济实力更强、生产方式更先进的群体的效仿。例如,明清时期随着各地畲族聚居地的稳定形成,畲民的主体部分逐渐由游耕向定耕转变,在各地服饰样式上均主动接受了汉族服装的基本形制,男装逐渐与汉族相同,女装的衣襟开口等也与清朝女子上衣相仿,甚至在清王朝结束后还将清朝官服的样式保留下来成为男子婚礼服的装束,当属畲族人民主动接受和融合主流文化在服饰上的典型映射。另一方面,这种文化涵化也有部分是被动接受的,主要是源自一些汉族政权的强制改装政策,在很长一段时期,如何引导畲民汉化曾是民国时期民族学研究的议题。如民国时期在景宁曾强制推行畲民服饰汉化制度,许多畲民妇女进城是摘掉凤冠,出城后再将凤冠戴上。对于这种强制改装政策,德国学者史图博曾从民族文化保护角度提出过忧虑和反对。著名历史学家王桐龄认为少数民族与汉民族间主要通过杂居、杂婚、更名、改姓、养子、易服色、变更语言文字和尊重道德伦理这八种方式来实现同化①,这八种方式是文化涵化与濡化的具体表现方式。在现代畲乡,这种文化上的濡化和涵化仍在交替作用,推动着畲族服饰文化的变迁。
现代社会中,受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冲击,畲族传统服饰工艺技术的主动传承呈现衰减状态,但民族环境下一些传统习俗、传说等仍继续对畲族年青一代进行着潜移默化的濡化作用。在本书撰写过程中进行的畲族服饰认知调查分析里,畲族聚居地的青少年学生中对于畲族服饰文化和传统手工艺的认知程度明显要高于普通民众中的调查数据,正是这种文化濡化的一种体现。由于缺乏主动性,这种濡化并不能对民族服饰文化进行完整的传承,而是随着传承代数在逐级衰减,比如景宁县彩带传人蓝延兰在对彩带字符图案的描述中,1999年的资料显示其能织造并说明寓意的符号有65个,而2009年笔者采访之时,她只能准确回忆起其中17个字符图案的含义。汉文化对畲族文化的涵化作用在经济高速发展、畲汉生活环境持平的当代社会更为明显。虽然我国实行民族平等的政策,尤其在文化发展方面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婚姻及丧葬习俗,但仍然难以阻止文化涵化的脚步。广大畲族人民对现代化生活方式的追求和对强势经济体和先进生产方式的学习不自觉地加速了文化涵化的速度。
文化的濡化与涵化是任何一个民族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的文化变迁现象,这种变迁是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的自然现象,民族服饰就是在这两者交错作用下逐步发展演化的,畲族服饰也不例外,当代畲族服饰产生的一些变化正是文化濡化与文化涵化共同作用的自然结果。
二社会经济文化的介入性影响
介入是一种外来的干预,医学中很早就提出了“介入”治疗的概念,指在一定的设备辅助下将专用医疗器械插入人体特定部位检查、治疗疾病的方法,是一种直接的治疗手段。社会经济文化对畲族服饰的介入式影响则是指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对畲民日常状态的一种渗透与改变,这种渗透和改变借由社会经济文化的跨越式发展对服饰现象和服饰文化产生干预,使之产生超越自身发展速度的突变。民族服饰发展过程中由于濡化和涵化共同作用下产生的渐变式发展是正常的演进状态,但是当代社会经济文化对畲族服饰发展产生的介入式影响则会给民族服饰带来跳跃式的巨大变化,这种突变表现为服饰外观的突然性改变(民族服饰在短时期内从族群主体成员的日常生活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现代服饰装束),民族服饰工艺被本民族青年摒弃且在服饰中的使用由于现代工艺的侵入而大量衰减。这种突变如果失去控制任由发展,很有可能给民族服饰文化带来灭顶之灾。全球化初期的经济文化一体化大潮是导致这种介入性影响的最主要因素。在生产力(以科学技术为核心)和普遍交往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人类实践活动不断地跨越时间、空间、制度、文化的障碍,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人、物质、信息之间普遍联系、达成共识与共同行动,并最终实现个体与全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这就是全球化的过程和趋势,文化的民族性和全球性的矛盾即普遍文化价值与民族文化个性的矛盾是全球化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①。然而在欧美等全球化进程更深入的西方国家早已认识到这种文化侵蚀的危害,各国有识之士奔走呼吁要警惕全球化对文化个性的消弭,从这个角度来说全球化强化了人民对民族文化个性发展的关注。
全球化带来了交通的便捷、信息的通达、经济的互通与文化的融合,同时也给历史上相对封闭的少数民族地区带来了社会经济文化的突变,这种跨越式的发展能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是也容易给民族文化发展带来震荡和断层,使民族服饰面临一次从材质、款式到服用习俗、心理的全面激变。
三 民族情感与民族认同的弱化
民族情感是对自己民族所特有的一种纯粹的真挚感情,民族认同即是一个族群的民族意识,是一个民族对自身历史、现状和未来,特别是所处环境的全面、客观的了解和认识。民族情感与民族认同是散落各地的畲族族民仍能维系民族服饰文化统一性的重要因素,强烈的民族情感使各地畲族固守本民族的服饰装束,服饰上特有的装饰、图案、色彩和样式成为外化的祖系认同标志,各地畲族在碰面时可以凭此辨认对方的民族身份,并可以通过服饰外观形成一种认同感,辨识出对方是否同族同支。但是在现代社会的冲击下,这种民族情感和民族认同已经不是那么强烈和纯粹。一方面由于民族平等政策的实施,各民族间呈现开放、和谐的局面,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原来的各种民族冲突减小到最弱,旧时畲族原本坚守的族内通婚制度也在畲汉文化交融的进程中逐渐瓦解,民族的自我意识和排他性也在这个过程中被弱化了。这种退化直接表现为不再坚持原有的民族服饰样式,日常生活中减少甚至不再穿着,对本族不同地区的服饰也无法辨认。
四 宗教信仰与祖先崇拜的淡化
祖先崇拜是原始宗教极为普遍的一种信仰形式,是维系族群成员情感的重要纽带。在畲族历史上长期频繁的迁徙中历经搬迁与动荡,无论家具行装如何删减,始终携带着代表家族祖先的香炉,甚至因为无法过稳定的定居生活修建祠堂而将香炉、祖杖放在扁担上形成“祖担”挑着走,这说明畲族是一个有着高度民族凝集力,非常注重祖先和宗族信仰的民族。除了祖先崇拜外,畲族的巫术崇拜和诸神信仰孕育下的民俗服饰习俗和宗族祭祀服饰、人生礼俗服饰、日常服饰共同构成了畲族服饰的全貌。然而随着社会结构和经济模式的转变,不仅畲族,包括汉族在内的国人宗教信仰和祖先崇拜似乎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淡化,全球化使各民族之间生活方式及文化上的差异日渐趋同,宗族祭祀活动举办不像以前那么频繁,一些巫术和仪礼民俗成为民族风情旅游表演展示的内容。宗教信仰的集体缺失是当代社会的普遍状况,而文化融合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也冲淡了畲民的祖先崇拜情结,一些青年畲民对于盘瓠传说和民族的奋斗发展历程也不甚清楚。这种宗教信仰与祖先崇拜的淡化使畲族青年对民族服饰的固守意识也逐渐弱化,而为了适应现代生活节奏进行的改装以及从众心理也致使民族服饰逐渐退出畲民日常生活的舞台。
一 穿着场合变化
在畲族的历史发展中,畲族服饰是畲民日常生活和各种节庆、祭祀及重要活动的装束,贯穿于畲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同场合有不同的民族服饰习惯。随着现代文明的介入,畲乡经济发展迅速,同时很多畲族青壮年离开山村进城求学、打工,畲族人民逐渐接受了新的生活方式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主流服饰,而传统畲族服饰则逐渐蜕变为节庆和表演场合的着装。这种变化最先由畲族青年和男子开始,留守在家的老年妇女则坚守传统服饰的最后一块阵地,所以在田野调查中,越是交通闭塞的山村传统服饰保持得相对越好,而在浙南景宁的东弄村、双后岗村一带,由于距离县城较近,公路和公交巴士都已修到村口,这一带的畲族男女老少平时基本都是现代服饰装束,仅在三月三等大型节庆活动或民族歌会、畲族婚嫁表演时才穿戴民族服饰,浙江省桐庐县莪山畲族乡由于属于杭州市辖区,经济水平较高,当地人从商开厂的较多,日常生活中的畲族服饰文化保持得相对较少。另一方面,这种变化和该畲族地区人口的稠密程度成反比,畲族人口越稀少的地方相应的服饰文化抗击外来冲击的能力越弱小,受到的冲击越明显。福建闽东畲族人口密集,畲族杂散居的村镇相互距离不远,在这些地区尚能遇到极少在日常生活中仍保留民族服饰的老人,且畲族老年妇女中传统发髻的保持率较高;而闽北、闽西、闽南的畲族人口稀少,分布地区成零星散落装,所以这些地区的服饰受汉族影响最大,平时已几乎无人穿着畲族传统服饰,仅在组织大型民族活动时穿着新制作的民族服饰进行表演,而且这些新畲服普遍存在工艺粗糙、形制混乱的缺点。
潘宏立①认为畲族群众日常服饰的改装进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男子改装,最迟至清末,畲族男装完成了汉化的过程,梳长辫子穿长袍马褂,后这种清朝官服的样式被延续作为畲族婚礼中男子的服饰装扮。第二阶段是清末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这一阶段女性服饰发生改变,景宁及闽东的大部分妇女开始接受汉族服饰,且发饰也发生改变,闽北光泽、漳平等地从这时起不梳民族发髻。第三阶段是1949年后,改装呈加速状态,首先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至1958年“大跃进”时期,在民族平等政策下大部分畲族地区实现了日常生活改装,然后是“大跃进”至“文化大革命”期间,畲汉文化进一步交融,政治运动影响下一批老旧服饰被销毁,最后是“文化大革命”后至今,其速度和规模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几乎所有的畲族村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这种穿着场合变化是随着现代文明和经济发展的影响逐步形成的,以宁德八都乡猴盾村为例: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青年妇女几乎天天穿民族服装,到80年代,女青年只有外出做客时才穿民族服装,到80年代中后期,日常生活中已不穿民族服饰了。在福鼎硖门瑞云村,大约从1978年前后开始改装,连结婚也有穿普通的现代服装的(现在畲族结婚服装形式多样,有穿传统服饰的,也有穿西式礼服的)。
所以,畲族服饰这种穿着场合的变化是随着畲民生活方式的变化而产生的,现代生活中畲族传统服饰的穿着从贯穿生活的各个方面蜕变为表演服装则是畲族服饰在当代社会中发生的最大的变化。
二 外观形材变化
社会经济发展一方面使畲民生活节奏加快,打破了以往以山地耕猎为主的经济生活模式,工作之余人们花费在服饰手工艺上的时间转而用在各种娱乐休闲活动中,家庭自制服装已经基本退出了畲民生活,民族服饰的主要来源是裁缝定做和购买成衣。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及现代服装纺织技术的提升使服装面辅料也产生了变化,以往常用的棉麻材料被现代化纤材料和丝绸材料所取代,服装上很多费时费工的彩带、镶滚、刺绣手工也被机织花边和机器刺绣替代。
相对于穿着场合变化而言,服饰外观式样、造型以及制作材料的变化是畲族服饰本身发生的重要变化。由于伴随社会经济发展而使畲族服饰的穿着场合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使畲族服饰从满足日常生活需求的日常服饰转变为以满足展示需求为主的表演服饰,这种转变必然使服饰向更为华丽、隆重的方向发展。在服饰外观上表现为色彩脱离了传统的衣尚青蓝转而选择艳丽明朗的大红大绿,服装上的装饰面积增大,发饰等也尽量往华丽的方向发展。比如传统罗源老年妇女所梳凤凰髻为蓝色绒绳缠绕,且头顶的发桃不像青年妇女那么高耸,较为矮小,衣襟的花边也仅有边口处有带状边饰,并非像青年女装铺开至肩部那么夸张。但在现代表演服饰中,几乎所有的罗源式服饰均以青年已婚女子的造型为蓝本,头顶为高耸的红色发桃。很多民族服饰的制作材料也由原先的棉麻质地改为化纤面料,一些镶边、彩带等传统手工被现代机织花边所取代,其色彩、光泽、质地等均与传统样式有较大差异。另外,由于各民族间文化交流的增强以及信息沟通的便捷,各民族服饰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交流互通,由此也产生了民族服饰元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并对服饰的外观形制产生了影响。在这种影响下,畲族服饰的外观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在新制作的一些畲族服饰中杂糅了一些其他民族服饰中的元素,如北方民族的毛边、苗族的百褶裙和花片裙。
作为畲族服饰中典型性和标志性最强的头饰,在外观形材上的变化更大,除了一些畲民家庭中保存的老式凤冠外,在众多表演和活动中广大畲族女子所戴的都是改装过的简易凤冠,以红黑毛线缠绕而成,做成头箍戴在头上(见图6-1)。
三 工艺技术变化
传统畲族服饰中一些传统工艺逐渐式微,主要表现为彩带在年青一代中的传承比例急剧下降,在很多新制的畲族服饰中都采用机织花边代替传统手织彩带,有的是按照彩带上的字符纹样进行电脑绣花制成,更多的甚至直接用市场上买来的花卉图案花边充当彩带。另外,服装中原来层层叠加的镶滚工艺的运用逐渐减少,手工刺绣被机绣代替。景宁式女子服装中“兰观衫”的花边以及男子服装门襟领圈处的边缘装饰都是通过不同色彩的面料以镶嵌或镶拼的手法制作而成的,但现在的新制作的服装上这些镶边都以花边代替了,仅在服装本料上以市场购买的成品花边简单车缝在边缘位置,女装的花边装饰部位也出于简化工艺的目的由原来的锁骨处直角转弯镶边改为绕领圈一周满镶,或从肩缝处开始不做弯角直接顺延至腋下。
花边是现在各民族新制作的民族服饰中大量用到的装饰辅件,都喜欢用它替代本民族原有的边缘装饰,殊不知这种改镶边为花边的工艺手法看似工艺更简单并且使服装更加华丽,但传统工艺和形制的流失反而使服装失去了民族特性,这或许正是服饰认知调查中很多人认为看到身着畲族服饰的人,能认出是少数民族但不能确定是畲族的原因之一。不论技术如何发展,丧失了传统工艺的雕琢,工业化、规模化生产出的服饰制品和传统服饰相比只能说是形似而神失。传统服饰制作者(有时是穿着者本人)在制作时是怀揣着对生活的美好祝福和愿景的,在现代服饰生产中则有一种误区,认为花边和鲜艳的色彩就是民族服饰的符号,单纯以强烈的色彩对比和大量的花边引起视觉刺激,反而丧失了传统工艺的精致与含蓄。
四 着装心态变化
民族服饰是民族情感和审美心理的一种物化的表现,民族服饰所传达的是一种族群认同、祖先文化和一定经济生活环境下的审美观,畲族先民们穿着民族服饰、佩戴带有民族图腾意味的头饰冠戴之时是怀着对祖先的信仰和崇拜之情的。例如,旧时畲民对于自己的服装制式是非常敏感且固守的。何子星在提到畲民自织的凤冠上裹的红布时说:“其他一布,名为畲客帽布;彼族甚敬重之”①。笔者在田野工作中走访畲族村中上了年纪的畲族老人时,当她们珍而重之地拿出压箱底的凤冠珠饰给我们展示时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这种对民族服饰的谨慎与敬重。然而在现代社会,随着民族间的混杂居、自由通婚、语言一致等民族政策的实施,畲族青年中首先破除了封建迷信的鬼神思想,对于宗族观念普遍产生了淡化情绪,民族固守意识和民族自我意识也逐渐淡化。服饰审美情感与社会主流意识趋同,对于着装心态也由固守民族服饰观念转而追求时尚、舒适、便捷以及符合当下流行的审美观。当代畲民穿着民族服饰更多是为了一种民俗表演性质的展示,换言之,他们的服饰不是为自己而穿,而是为了满足观赏者的需求甚至仅仅作为一种特殊场合的“工作服”而穿。一些民俗表演中部分畲族服饰的穿着者可能并不是畲族,而是进行表演的汉族人,他们对于服装所传达的民族情感更加淡漠。由此,民族服饰进一步蜕化到工作表演装的定位,对工作服能心怀敬意已属不易,遑论其原始的祖先崇拜与信仰了。这种着装心态的转变是畲族服饰在当代社会中最重要的变化,因为服饰的物质表现实体是基于穿着服饰的人的审美观念和着装心理上的产物。当着装心态发生变化时,服饰也必然受其影响发生外观改变以迎合新的着装心理。
第二节 导致畲族服饰发生嬗变的因素
一 文化濡化与涵化的自然结果
文化濡化和文化涵化是社会学和人类学中的概念,分别代表文化传递的两种基本模式。“文化濡化”是指一种“主动态”,强调从文化中学习到价值与规划,其重要作用在于保持文化传递的连贯性;“文化涵化”是指一个群体如社会、国家、族群,尤其是一个部落因接触而接受另外一个群体的文化特征和社会模式的过程,强调外来文化的价值与规范,其重要作用在于保持文化传递的变迁性,其涵化深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的差异性。民族服饰不可能一成不变,它必然随着社会发展和民族发展而产生相应的演进,民族服饰文化也随着民族文化的变迁而发生变化,畲族服饰在当代社会中的嬗变就是文化濡化和文化涵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文化濡化”概念的核心是人及人的文化获得和传承机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承和文化濡化方式,有时候可以是通过族群个体主观习得的一种技艺、认知或相关文化传统,有时候是身处该民族的文化环境中耳濡目染获得的一种文化传承。“文化涵化”则表现为族群在民族发展中主动或被动地接受另一个群体的文化,在畲族发展历史上,畲汉文化交融的结果体现在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包括服饰形制与装饰特征,这种主动对异文化的接受与认同一般是对相较本民族的现代化程度更高、经济实力更强、生产方式更先进的群体的效仿。例如,明清时期随着各地畲族聚居地的稳定形成,畲民的主体部分逐渐由游耕向定耕转变,在各地服饰样式上均主动接受了汉族服装的基本形制,男装逐渐与汉族相同,女装的衣襟开口等也与清朝女子上衣相仿,甚至在清王朝结束后还将清朝官服的样式保留下来成为男子婚礼服的装束,当属畲族人民主动接受和融合主流文化在服饰上的典型映射。另一方面,这种文化涵化也有部分是被动接受的,主要是源自一些汉族政权的强制改装政策,在很长一段时期,如何引导畲民汉化曾是民国时期民族学研究的议题。如民国时期在景宁曾强制推行畲民服饰汉化制度,许多畲民妇女进城是摘掉凤冠,出城后再将凤冠戴上。对于这种强制改装政策,德国学者史图博曾从民族文化保护角度提出过忧虑和反对。著名历史学家王桐龄认为少数民族与汉民族间主要通过杂居、杂婚、更名、改姓、养子、易服色、变更语言文字和尊重道德伦理这八种方式来实现同化①,这八种方式是文化涵化与濡化的具体表现方式。在现代畲乡,这种文化上的濡化和涵化仍在交替作用,推动着畲族服饰文化的变迁。
现代社会中,受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冲击,畲族传统服饰工艺技术的主动传承呈现衰减状态,但民族环境下一些传统习俗、传说等仍继续对畲族年青一代进行着潜移默化的濡化作用。在本书撰写过程中进行的畲族服饰认知调查分析里,畲族聚居地的青少年学生中对于畲族服饰文化和传统手工艺的认知程度明显要高于普通民众中的调查数据,正是这种文化濡化的一种体现。由于缺乏主动性,这种濡化并不能对民族服饰文化进行完整的传承,而是随着传承代数在逐级衰减,比如景宁县彩带传人蓝延兰在对彩带字符图案的描述中,1999年的资料显示其能织造并说明寓意的符号有65个,而2009年笔者采访之时,她只能准确回忆起其中17个字符图案的含义。汉文化对畲族文化的涵化作用在经济高速发展、畲汉生活环境持平的当代社会更为明显。虽然我国实行民族平等的政策,尤其在文化发展方面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婚姻及丧葬习俗,但仍然难以阻止文化涵化的脚步。广大畲族人民对现代化生活方式的追求和对强势经济体和先进生产方式的学习不自觉地加速了文化涵化的速度。
文化的濡化与涵化是任何一个民族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的文化变迁现象,这种变迁是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的自然现象,民族服饰就是在这两者交错作用下逐步发展演化的,畲族服饰也不例外,当代畲族服饰产生的一些变化正是文化濡化与文化涵化共同作用的自然结果。
二社会经济文化的介入性影响
介入是一种外来的干预,医学中很早就提出了“介入”治疗的概念,指在一定的设备辅助下将专用医疗器械插入人体特定部位检查、治疗疾病的方法,是一种直接的治疗手段。社会经济文化对畲族服饰的介入式影响则是指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对畲民日常状态的一种渗透与改变,这种渗透和改变借由社会经济文化的跨越式发展对服饰现象和服饰文化产生干预,使之产生超越自身发展速度的突变。民族服饰发展过程中由于濡化和涵化共同作用下产生的渐变式发展是正常的演进状态,但是当代社会经济文化对畲族服饰发展产生的介入式影响则会给民族服饰带来跳跃式的巨大变化,这种突变表现为服饰外观的突然性改变(民族服饰在短时期内从族群主体成员的日常生活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现代服饰装束),民族服饰工艺被本民族青年摒弃且在服饰中的使用由于现代工艺的侵入而大量衰减。这种突变如果失去控制任由发展,很有可能给民族服饰文化带来灭顶之灾。全球化初期的经济文化一体化大潮是导致这种介入性影响的最主要因素。在生产力(以科学技术为核心)和普遍交往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人类实践活动不断地跨越时间、空间、制度、文化的障碍,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人、物质、信息之间普遍联系、达成共识与共同行动,并最终实现个体与全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这就是全球化的过程和趋势,文化的民族性和全球性的矛盾即普遍文化价值与民族文化个性的矛盾是全球化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①。然而在欧美等全球化进程更深入的西方国家早已认识到这种文化侵蚀的危害,各国有识之士奔走呼吁要警惕全球化对文化个性的消弭,从这个角度来说全球化强化了人民对民族文化个性发展的关注。
全球化带来了交通的便捷、信息的通达、经济的互通与文化的融合,同时也给历史上相对封闭的少数民族地区带来了社会经济文化的突变,这种跨越式的发展能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是也容易给民族文化发展带来震荡和断层,使民族服饰面临一次从材质、款式到服用习俗、心理的全面激变。
三 民族情感与民族认同的弱化
民族情感是对自己民族所特有的一种纯粹的真挚感情,民族认同即是一个族群的民族意识,是一个民族对自身历史、现状和未来,特别是所处环境的全面、客观的了解和认识。民族情感与民族认同是散落各地的畲族族民仍能维系民族服饰文化统一性的重要因素,强烈的民族情感使各地畲族固守本民族的服饰装束,服饰上特有的装饰、图案、色彩和样式成为外化的祖系认同标志,各地畲族在碰面时可以凭此辨认对方的民族身份,并可以通过服饰外观形成一种认同感,辨识出对方是否同族同支。但是在现代社会的冲击下,这种民族情感和民族认同已经不是那么强烈和纯粹。一方面由于民族平等政策的实施,各民族间呈现开放、和谐的局面,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原来的各种民族冲突减小到最弱,旧时畲族原本坚守的族内通婚制度也在畲汉文化交融的进程中逐渐瓦解,民族的自我意识和排他性也在这个过程中被弱化了。这种退化直接表现为不再坚持原有的民族服饰样式,日常生活中减少甚至不再穿着,对本族不同地区的服饰也无法辨认。
四 宗教信仰与祖先崇拜的淡化
祖先崇拜是原始宗教极为普遍的一种信仰形式,是维系族群成员情感的重要纽带。在畲族历史上长期频繁的迁徙中历经搬迁与动荡,无论家具行装如何删减,始终携带着代表家族祖先的香炉,甚至因为无法过稳定的定居生活修建祠堂而将香炉、祖杖放在扁担上形成“祖担”挑着走,这说明畲族是一个有着高度民族凝集力,非常注重祖先和宗族信仰的民族。除了祖先崇拜外,畲族的巫术崇拜和诸神信仰孕育下的民俗服饰习俗和宗族祭祀服饰、人生礼俗服饰、日常服饰共同构成了畲族服饰的全貌。然而随着社会结构和经济模式的转变,不仅畲族,包括汉族在内的国人宗教信仰和祖先崇拜似乎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淡化,全球化使各民族之间生活方式及文化上的差异日渐趋同,宗族祭祀活动举办不像以前那么频繁,一些巫术和仪礼民俗成为民族风情旅游表演展示的内容。宗教信仰的集体缺失是当代社会的普遍状况,而文化融合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也冲淡了畲民的祖先崇拜情结,一些青年畲民对于盘瓠传说和民族的奋斗发展历程也不甚清楚。这种宗教信仰与祖先崇拜的淡化使畲族青年对民族服饰的固守意识也逐渐弱化,而为了适应现代生活节奏进行的改装以及从众心理也致使民族服饰逐渐退出畲民日常生活的舞台。
附注
①潘宏立:《福建畲族服饰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1985年,第111页。
①何子星:《畲民问题》,《东方杂志》1933年,第30卷第13号。
①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3—5页。
①邹广文、常晋芳:《全球化进程中的人》,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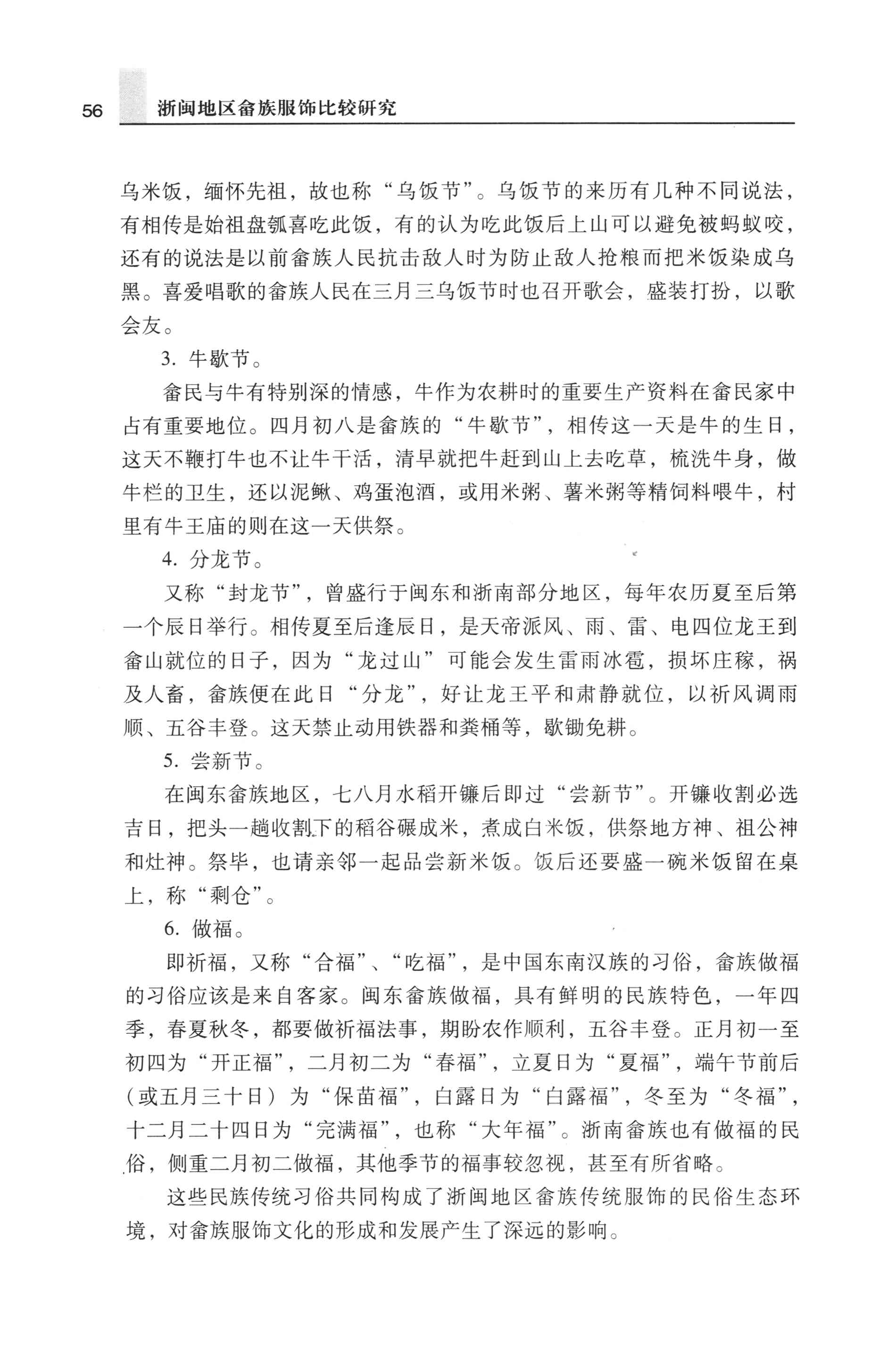
《浙闽地区畲族服饰比较研究》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从畲族历史上的迁徙路径和居住地的自然人文环境入手,通过田野调査对服饰文物资料进行收集和测量,进而对浙闽两地畲族传统服饰的形制外观、审美习俗进行比较,明晰各地服饰特征的异同和关联,总结了五种典型的服饰样式,揭示了服饰演化的脉络性特征,结合民族文化背景分析其审美文化内涵和承载媒介。在此基础上对当代社会对畲族服饰的认知现状进行调查,分析畲族服饰的嬪变及其动因,提出了对畲族服饰遗产进行固态保护与活态传承的观点。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