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浙闽地区畲族服饰审美比较
| 内容出处: | 《浙闽地区畲族服饰比较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920020230005621 |
| 颗粒名称: | 第一节 浙闽地区畲族服饰审美比较 |
| 分类号: | TS941.742.883 |
| 页数: | 12 |
| 页码: | 136-147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畲族服饰审美是在宗教信仰、祖先崇拜和生活环境的影响下形成的,体现了历代畲族先民积淀下来的民族审美观。审美主体既是服饰美的创造者,又是欣赏者,通过造型选择、色彩搭配、图案喜好和意蕴表达等方式塑造和选择服饰美。 |
| 关键词: | 畲族服饰 审美比较 浙闽地区 |
内容
审美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特殊形式,指人与世界(社会和自然)形成一种无功利的、形象的和情感的关系状态①。审美是一种主观的心理活动,它受制于客观因素,审美主体所处的时代背景会对人们的评判标准起到很大的影响。每个时代或阶段,人们所处的环境,或多或少都会对审美观造成影响。在畲族服饰的审美中,畲民是审美的主体,他们既是服饰美的创造者,又是欣赏者,他们的宗教信仰、祖先崇拜以及所处的生活环境、时代背景都会对服饰的审美起到一定的影响。在这些因素影响下,他们会结合个人喜好,从造型的选择、色彩的搭配、图案的喜好和意蕴的表达上对本民族服饰进行美的塑造和选择,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畲族传统服饰外观正是历代畲族先民一代代沉淀下来的民族审美观下的产物。
一 造型之美
浙闽畲族服饰在造型上有自己的民族特点,浙江、福建两省境内的畲族服饰在整体造型上由于同根同源的文化与族群认同,存在一定的共性,在局部造型上又由于民族迁徙与各自的分化发展而存在一定的地域特色。由于畲族男子服饰与汉族相同,故本书以女子服饰特征来分析其造型之美。
(一)整体造型的共性
对整体造型影响最直接的是民族始祖传说。由于各地畲族在对盘瓠始祖传说上的高度认同,对于盘瓠的崇拜也贯穿于服饰的整体。盘瓠乃高辛皇后耳中取出一条金龙所变龙犬,高辛皇帝赐名龙麒(期),号称盘瓠。故畲族历史上是以犬为图腾的。之后由于受汉文化中对犬形象态度的影响而引入凤凰崇拜,依托三公主嫁衣的传说认为其女装来自凤凰形象,但犬图腾在服饰整体造型上留下的印记是难以磨灭的。所以在整体造型上,两地畲族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拟物——此处的“物”为动物,主要是对犬和凤的模拟。这两种动物在形态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都是由头部、躯干和尾部构成的,所以经过服饰演化,对头部和尾部的解释具有一定的共通性。
畲族各地的女子装扮以凤凰为名,有凤首、凤身、凤尾的说法(旧时称狗头冠,对应为狗头、狗身、狗尾),这种传统的凤冠在景宁地区保持得较好,福建诸地出于劳作和日常生活便利等原因,仅在婚丧礼服中保留原始凤冠,平日则以凤凰髻代替。在服装上以绚烂的刺绣和花边形成对凤凰(或曰五彩龙犬)五彩身体的描摹。瑶族一些地区(如福安)的衣服大身前后片有明显的不等长设计,后裾明显长于前裾3—7厘米,畲民解释为祖先保留下来的习惯。依据潘宏立的观点,这很可能是对源于犬图腾下后裾略长盖住尾巴的传说。在各地畲族中拦腰作为一个始终保持下来的服饰配件,除罗源式的腰带是在后腰打结外,其他地方畲族腰带的打结方式都是两根侧带绕过后腰后在前中心处打结,且尾端加上流苏穗子,悬垂下来有尺余,主体色为白色的彩带在蓝黑色裙面的拦腰上显得尤为出挑。据《后汉书》对盘瓠后代服饰“制裁皆有尾形”的记载,这种腰带与福鼎式腋下留出的两条飘带都被认为是“尾形”的象征。而华丽的罗源装由于拦腰装饰繁复,腰带系于后中心,腰间蓝底白花,两端镶花边的腰带垂于后腰,更被认为是凤凰的五彩尾饰。
可见,在畲族女子服饰的整体造型上,犬图腾和凤凰崇拜的印记非常明显,凤凰崇拜应衍生自盘瓠传说中五彩龙麒的犬图腾,它们在服饰整体造型上表现为高耸的首冠、五彩的身体和下垂腰带象征的尾饰。不论何种式样,畲族女子服饰均遵循以上整体造型,体现出一种动物拟态之美(见图4-1)。
(二)局部造型的特性
畲族女装造型简单,以右衽大襟衫为上装,除罗源装为交领外,其余均为立领大襟衫,为传统平面裁剪,连袖,领口和大襟处多有刺绣或镶边装饰,袖口多有相应装饰与之呼应,形成节奏感。除罗源式外,各地服饰中以蓝黑色为主,白色主调的腰带在前中心打结并垂下尾穗,形成T字形,随人体的活动而摇摆,非常醒目。
罗源式服装的装饰最为绚丽,以大量条状镶绲花边的重复拼接形成块面装饰。袖口、拦腰边缘的镶绲与肩领部进行呼应,由于大量的花边和镶绲使服装上相应的装饰部位硬挺,穿上身后能保持挺括的造型。腰带于背后打结,垂于尾部,既保持了正面装饰的统一性又丰富了背后的视觉效果,加上头顶高耸的凤冠,显得穿着者修长挺拔。福安式服装较为朴素,通过边缘镶边对款式结构进行强调,衣襟呈直角造型,右侧服斗靠近侧缝处的三角印上的绣花和拦腰左右上方的花篮绣花相互呼应,使整体风格简单但不单调。霞浦和福鼎的上衣胸襟线条下凹成弧线,胸襟处的绣花以动物、花鸟为主,造型质朴,非常出彩。景宁式虽然服装样式较为普通,但珠冠的造型秀美华丽,畲族女子在高挑的冠首和垂挂的珠串及璎珞装点下别具民族风情。
二 色彩之美
(一)源出同宗,衣尚青蓝
各地畲族服饰皆喜用青蓝色或黑色,这种习俗源自畲民善于种菁。菁即靛蓝,是一种具有三千多年历史的还原染料。战国时期荀况的千古名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就源于当时的染蓝技术。这里的“青”是指青色,“蓝”则指制取靛蓝的蓝草。明清时期开始,各地畲区不仅普及种菁制靛,而且技术上佳,量多质优,所种之菁用于染布,其色鲜艳,经久不褪,所以畲民地区对自种自染的靛蓝衣料应用相当普遍。另一方面,由于畲民大多从事耕猎活动,日常劳作非常辛苦,男女皆然,青蓝色的服饰经久耐脏,适合劳作时穿着。故而各地畲民不论男女均喜着青蓝色服装。蓝靛色彩丰富,《通志》曰“蓝三种:蓼蓝染绿;大蓝如芥,染碧;槐蓝如槐,染青,三蓝皆可作淀,色成胜母,故曰青出于蓝,而青于蓝”。以青蓝、青黑色为主调的畲族日常服饰看似朴实,配以月白或大红镶边,衬托出穿着者或淡雅,或奔放的形象,盛装时绚丽的刺绣和花边在蓝黑色服饰的基调下反衬得越发艳丽(见图4-2)。
(二)五色斑斓,各不相同
各地畲族服饰上的用色崇尚五色斑斓,但随着用色部位、用色面积的不同,形成浓艳素雅各不相同的服色风格。
从整体色彩上来看,福安式和景宁式比较朴素淡雅,罗源式最为花哨绚丽,霞浦式和福鼎式整体大方沉稳,细节精致华美。畲族服饰不似绣工繁复装饰华丽的苗族女装,在动荡迁徙的民族发展历程中养成了畲族人民沉稳、朴实的性格,畲民服装以蓝黑色为本料,喜欢在边缘镶绲装饰和彩绣上使用红色布条和丝线,从而形成鲜明的色彩对比。比如福安式上衣的红色边缘绲边,肋下必镶嵌象征半枚金印的红布,精美的还在上面绣上凤鸟或花卉图案,老年妇女的亦有仅做简单的边缘装饰而不绣花鸟图案的。福安和景宁的拦腰腰头均为宽约2寸的大红色棉布。罗源装大量镶嵌的花边和“捆只颜”绲边也是以红、白为基调,由于花边间隔细腻,远观即形成视觉上的色彩空间混合效果,成为粉色调,衬托在底色为蓝黑色的服装本料和黑色短裙(短裤)上,大花配素黑的色彩搭配在华丽外平添一丝沉稳。霞浦和福鼎的衣襟绣花基本是以大红、玫红色图案为主,间或掺杂一些金黄、牙白、水绿色作调和,整体色彩感觉是在蓝黑色服装本料上凸显出红色的绣花块面。另外,凤冠上的色彩也是以红色为主,冠首裹以红布,珠饰则有白色、绿色、蓝色等多种颜色的“五色椒珠”。
可见,畲族女子服饰的主色为黑底红饰的基调,在诸如镶绲、刺绣等装饰细节上采用红色为主,夹杂五色斑斓的绚丽色彩,大红、玫红、水绿、靛蓝、牙白、金黄、鹅黄等色彩丰富了装饰的细节,与《后汉书》中所载盘瓠后代“好五色衣服”、“衣裳斑斓”的描述相吻合,服饰色彩鲜艳明朗,在大量运用对比色时采用白色勾边,黑色压底的配色手法,有时掺入金线作为装饰,无意中竟和现代色彩美学的配色原色相符。同时,暖色基调的各种边缘装饰与图案在青蓝色服装基底上形成强烈的反差与对比,体现了一种稳重、端庄的审美特点(见图4-3)。
三 图案之美
畲族服饰上有很多图案装饰,这些图案主要通过服装和饰品两个部分来呈现。服装上主要借助绣花和彩带编织工艺来表现,在饰品上则通过各种银簪、银笄和银牌、胸挂等饰品上的錾刻图案来表现。浙闽地区畲族服饰图案题材来源于日常生活、传说和戏剧故事,表现形式主要以刺绣、錾刻为主,按照图案表现的内容来分可以分为动物、植物、人物、几何和字符四大类别。其中动物图案中的龙凤图案是畲族服饰装饰图案中非常重要的部分。龙形图案主要来自畲族始祖盘瓠是高辛皇后耳中取出的金龙,化为五色龙犬,被赐名“龙麒”。凤鸟纹则源自由畲族始祖婆“三公主”及广东凤凰山祖地的传说和崇拜,亦受到汉文化龙凤吉祥寓意和东夷凤鸟崇拜的综合影响。由于族源崇拜的影响,龙凤图案在各地畲族服饰中被频繁使用,是绣花和银器上常见的装饰图案。
由于福建地区的服饰中绣花运用较浙江地区广泛、频繁,所以图案形式也较浙江地区更为多样和丰富,常见花鸟虫鱼、人物故事、几何文字等图案题材。浙江地区畲族服饰常服中绣花运用较少,图案主要以花鸟、几何文字为主。下面从图案题材入手,对畲族服饰常见图案进行分类论述。
(一)动物图案
动物图案是常见的服饰装饰图案,表现题材多为祥瑞动物。
1.龙凤图案。
龙凤是畲族服饰中最常见的一种图案题材(见图4-4),尤其是凤凰图案,这与畲族服装中源于始祖婆“三公主”的凤凰装有着直接的关系。正因为这种凤凰崇拜意识,在畲族女子服装的衣襟、领口、拦腰等装饰部位频繁出现凤凰的形象。龙纹的运用则多以某种固定的构图形式出现,比如和凤纹一起体现龙凤呈祥的寓意,或两条龙形成二龙戏珠的条状装饰,应用于领座部位。凤纹也经常和植物图案里的牡丹同时出现,表现富贵吉祥的寓意。由于畲族文化里并无龙图腾崇拜,始祖传说中盘瓠原为龙犬,但也并非纯粹的龙形。而凤凰崇拜是源自三公主嫁衣的典故,从收集到的资料来看,龙纹出现得较晚,且运用的频度和广度远不及凤纹。结合民族迁徙中畲汉文化交融的影响,这些龙凤呈祥、二龙戏珠的纹样应该是受到汉文化中龙凤图案的影响而产生的。虽然题材受到汉文化影响,但畲族服饰图案在表现形式上更加朴拙,尤其是凤凰形象的写实程度不高,而是加入了抽象、夸张的手法,形成拙中见巧的民族风格。凤纹除了在服装上经常出现,在畲族凤冠中象征凤身的银牌上也一般都錾刻有凤纹。
出于民族同源和祖先崇拜的缘故,以及各地畲汉交融的影响,龙凤图案是各地畲族服饰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一类装饰图案,尤其是凤纹。值得注意的是,畲族服饰图案中对龙凤形象并非盲目的膜拜,其中不乏一些将龙凤和人物结合的表达形式,将得道的仙人形象和龙凤放在同等的地位,如天官或道士形象骑龙驾凤的图案(见图4-11),表达了一种企盼求仙得道飞升的愿望。
2.其他动物图案。
龙凤图案乃是虚拟的瑞兽形象,畲族服饰中另有一些以生活中的动物为表现题材的图案(见图4-5),这些动物大都富有吉祥的寓意,和汉文化中常用的吉祥图案基本一致,如鱼代表年年有余、仙鹤、鹿竹代表长寿、喜鹊蝙蝠代表“喜”和“福”、象征爱情和美好的蝴蝶等。和汉族民间喜好一样,畲族儿童用品,尤其是童帽上特别喜欢用贴布绣的虎头纹样,且虎耳都做成立体的,像帽子上长了两个耳朵,一方面可以体现孩童虎头虎脑的可爱,一方面也有辟邪保佑儿童健康成长的含义。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独具畲族特色的动物,如雉鸡、松鼠等也是旧时服饰上喜用的装饰题材,根据畲民生活环境推测应该和常年的山地耕猎生活有关。但是在笔者对福鼎刺绣老师傅雷朝灏的交谈中得知,随着近年来畲民生活模式的改变以及外界审美意识的影响,鸡类形象已经不再受欢迎,松鼠的图案也很难见到。可见,生活环境的变迁对于服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服饰图案题材是直观反映民族生活环境的一面镜子,图案题材的变化也从一方面折射出生活方式的变化。
(二)植物图案
植物图案是服装中最常见的一种装饰题材,汉文化中喜用的象征高洁的梅兰松竹因其美好的寓意也常被使用(见图4-6),但单独运用的较少,梅花常和喜鹊组合出现,兰、松、竹图案则常与人物组合出现,兰花图案在外衣、拦腰上较少单独出现,仅单独运用在肚兜、荷包、帽子等配件上。
植物图案中尤以牡丹图案最为常见(见图4-7),这也是和畲族崇凤文化相关,凤纹的大量运用决定了牡丹作为搭配形象频繁出现,在上衣服斗胸襟绣花处一般和凤纹组合运用。在福安式和霞浦式拦腰中,拦腰裙面左右上方所用绣花为花盆或花篮造型的团花,尤以福安为甚,霞浦式拦腰中亦有将花卉与人物故事图案结合的。在花卉种类中,除了牡丹外,以荷花最常见,荷花常伴有莲藕和莲蓬造型,在肚兜等贴身服饰上亦有石榴的图案。莲藕、石榴均象征多子,故多运用在女性贴身肚兜上(见图4-8)。
畲族服饰中还有很多组合花卉图案(见图4-9),将各式花卉或凤鸟纹一起组合成盆花或花篮的形式,装饰在衣襟和拦腰裙面上(主要是福建地区的拦腰裙面,浙江地区的拦腰多为素色,无图案)。拦腰上以单独纹样的形式为主,在衣襟上则根据布局需要进行变化,形成角隅纹样或适合植物花卉图案还有一种最常见的运用方式,就是形成二方连续纹样对服装各个边口部位进行带状装饰。主要的构图骨架形式有波纹式和散点式两种,波纹式骨架除了简单的单波纹形式外还经常使用双波纹交叠的骨架形成复杂多变、生动而富有韵律感的图形。不同于汉族传统服饰纹样里求“全”避“破”的构图法则,畲族服饰纹样中散点式骨架构图时不拘泥于全幅图案的齐整性,常常截取图形的一个部分加以运用,多用于立领的领座图案或边缘装饰图案(见图4-10)。
(三)人物图案
人物图案是畲族服饰中较有特色的一种图案表现题材,表现的人物形象主要有仙道形象、文人场景和戏文故事几种类别(见图4-11)。仙道形象主要是骑着龙凤、麒麟等瑞兽的人物,有时亦会以道教八仙的形象为刺绣图案或银器錾刻图案,包括暗八仙图案(道教图案,将八仙手持的八件法器,即渔鼓、宝剑、花篮、笊篱、葫芦、扇子、阴阳板、横笛作为图案,因只采用神仙所执器物,不直接出现仙人,故称暗八仙,道教宫观常将这八件法器画成图案作为装饰)。文人场景则主要表现的是古代文人凭栏赏花、童子烹茶等场景。戏文故事则通过刺绣来表现一些民间传说戏文,比如白蛇传里断桥相会、祭塔救母等故事情节,福鼎式上衣胸襟绣花还常以头戴戏冠,手舞绸带的戏台人物形象作为图案。人物图案是畲族服饰装饰图案中较有特色的一个种类,除了刺绣的表现手法外,畲族童帽上钉缀着浮雕人物图像的银牌作为装饰,畲族人民通过多样的人物图案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四)几何字符图案
几何图案常见于服装的各个边缘修饰上,常通过刺绣工艺进行表现。比如福安式服装中边缘常用的马牙纹、罗源式服装和拦腰上常用的山字纹、柳条纹等(见图4-12)。几何图案造型简洁、线条明快,装饰效果简单朴素,有时与花卉、人物图案组合使用,构成块面装饰,形成丰富、完整的视觉效果。
字符图案主要包括文字类和符号类两种图案形式。文字类图案主要出现在童帽上,表达一种美好的祈愿和祝福。由于畲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文字图案均是以汉字为表达媒介,常在帽子前额处彩绣“福如东海”、“福禄祯祥”等吉祥文字(见图4-12),包括前文所述童帽顶和纽扣上的“福”字、罗源装后领的“囍”字等。符号类图案则以道教的八卦符号和佛教的“卍”字符号为主要表现内容,尤以八卦图案应用得更为广泛,在童帽、肚兜、荷包等服饰品上常通过彩绣的形式表现,也有錾刻在银牌或胸挂上的。“卍”字图案有时将其四角延伸、转折,形成几何图案。字符图案中还有一种很重要的类别是彩带上的字符,皆由45°角交叉构成,由于在前文彩带工艺部分已经详细分析过这些字符的造型和含义,此处不再赘述。
四 意蕴之美
受长期与汉族群众杂居的影响,不论福建还是浙江的畲族服饰装饰,均受汉文化中吉祥文化的影响,通过一些常用的吉祥图案寄托畲族人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同时结合本民族的图腾崇拜,表达了一种独特的意蕴之美。这种意蕴将畲族人民千年以来形成的民族风骨、情感和精神通过服饰的形式表达出来,通过吉祥图案表达对美的追求和憧憬,除了悦目之外还有“怡神怡情”的作用。虽然在吉祥图案的寓意上,受汉文化的影响比较明显,一些吉祥图案的题材和汉族传统图案相似,比如以凤凰牡丹寓意富贵红火,以松竹兰花表示清雅高洁,以松鹤鹿竹象征福寿绵长,以莲藕石榴象征多子,但在表现手法及形式语言的运用上畲族服饰更加奔放,图案造型质朴,线条生动,一些花卉和凤鸟的造型拙中见巧,表达了一种对自由和生命的热爱。此外,由于宗教信仰上受佛教和道教的浸染,还通过佛道常用的图形和服饰、冠戴来表达畲族人民崇神敬巫的民间信仰,比如佛教常用的宝莲、象征智慧与慈悲的“卍”字和道教的八卦、八仙图案成为畲族人民祈福避灾的一种精神寄托,常用于服饰图案装饰,而在祭祖服饰上则直接借用道教的服饰习俗。畲族服饰整体上构建的是一种衣服与人体的和谐之美,在服装与人体的关系上是贴合人体轮廓的,并无刻意的夸张或改变人体的结构、廓形。衣服的开襟、剪裁、结构等借鉴了汉族服饰,仅在边缘、服斗等处增加了装饰,从结构上来说体现的是一种顺应自然规则的朴素主义精神。
一 造型之美
浙闽畲族服饰在造型上有自己的民族特点,浙江、福建两省境内的畲族服饰在整体造型上由于同根同源的文化与族群认同,存在一定的共性,在局部造型上又由于民族迁徙与各自的分化发展而存在一定的地域特色。由于畲族男子服饰与汉族相同,故本书以女子服饰特征来分析其造型之美。
(一)整体造型的共性
对整体造型影响最直接的是民族始祖传说。由于各地畲族在对盘瓠始祖传说上的高度认同,对于盘瓠的崇拜也贯穿于服饰的整体。盘瓠乃高辛皇后耳中取出一条金龙所变龙犬,高辛皇帝赐名龙麒(期),号称盘瓠。故畲族历史上是以犬为图腾的。之后由于受汉文化中对犬形象态度的影响而引入凤凰崇拜,依托三公主嫁衣的传说认为其女装来自凤凰形象,但犬图腾在服饰整体造型上留下的印记是难以磨灭的。所以在整体造型上,两地畲族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拟物——此处的“物”为动物,主要是对犬和凤的模拟。这两种动物在形态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都是由头部、躯干和尾部构成的,所以经过服饰演化,对头部和尾部的解释具有一定的共通性。
畲族各地的女子装扮以凤凰为名,有凤首、凤身、凤尾的说法(旧时称狗头冠,对应为狗头、狗身、狗尾),这种传统的凤冠在景宁地区保持得较好,福建诸地出于劳作和日常生活便利等原因,仅在婚丧礼服中保留原始凤冠,平日则以凤凰髻代替。在服装上以绚烂的刺绣和花边形成对凤凰(或曰五彩龙犬)五彩身体的描摹。瑶族一些地区(如福安)的衣服大身前后片有明显的不等长设计,后裾明显长于前裾3—7厘米,畲民解释为祖先保留下来的习惯。依据潘宏立的观点,这很可能是对源于犬图腾下后裾略长盖住尾巴的传说。在各地畲族中拦腰作为一个始终保持下来的服饰配件,除罗源式的腰带是在后腰打结外,其他地方畲族腰带的打结方式都是两根侧带绕过后腰后在前中心处打结,且尾端加上流苏穗子,悬垂下来有尺余,主体色为白色的彩带在蓝黑色裙面的拦腰上显得尤为出挑。据《后汉书》对盘瓠后代服饰“制裁皆有尾形”的记载,这种腰带与福鼎式腋下留出的两条飘带都被认为是“尾形”的象征。而华丽的罗源装由于拦腰装饰繁复,腰带系于后中心,腰间蓝底白花,两端镶花边的腰带垂于后腰,更被认为是凤凰的五彩尾饰。
可见,在畲族女子服饰的整体造型上,犬图腾和凤凰崇拜的印记非常明显,凤凰崇拜应衍生自盘瓠传说中五彩龙麒的犬图腾,它们在服饰整体造型上表现为高耸的首冠、五彩的身体和下垂腰带象征的尾饰。不论何种式样,畲族女子服饰均遵循以上整体造型,体现出一种动物拟态之美(见图4-1)。
(二)局部造型的特性
畲族女装造型简单,以右衽大襟衫为上装,除罗源装为交领外,其余均为立领大襟衫,为传统平面裁剪,连袖,领口和大襟处多有刺绣或镶边装饰,袖口多有相应装饰与之呼应,形成节奏感。除罗源式外,各地服饰中以蓝黑色为主,白色主调的腰带在前中心打结并垂下尾穗,形成T字形,随人体的活动而摇摆,非常醒目。
罗源式服装的装饰最为绚丽,以大量条状镶绲花边的重复拼接形成块面装饰。袖口、拦腰边缘的镶绲与肩领部进行呼应,由于大量的花边和镶绲使服装上相应的装饰部位硬挺,穿上身后能保持挺括的造型。腰带于背后打结,垂于尾部,既保持了正面装饰的统一性又丰富了背后的视觉效果,加上头顶高耸的凤冠,显得穿着者修长挺拔。福安式服装较为朴素,通过边缘镶边对款式结构进行强调,衣襟呈直角造型,右侧服斗靠近侧缝处的三角印上的绣花和拦腰左右上方的花篮绣花相互呼应,使整体风格简单但不单调。霞浦和福鼎的上衣胸襟线条下凹成弧线,胸襟处的绣花以动物、花鸟为主,造型质朴,非常出彩。景宁式虽然服装样式较为普通,但珠冠的造型秀美华丽,畲族女子在高挑的冠首和垂挂的珠串及璎珞装点下别具民族风情。
二 色彩之美
(一)源出同宗,衣尚青蓝
各地畲族服饰皆喜用青蓝色或黑色,这种习俗源自畲民善于种菁。菁即靛蓝,是一种具有三千多年历史的还原染料。战国时期荀况的千古名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就源于当时的染蓝技术。这里的“青”是指青色,“蓝”则指制取靛蓝的蓝草。明清时期开始,各地畲区不仅普及种菁制靛,而且技术上佳,量多质优,所种之菁用于染布,其色鲜艳,经久不褪,所以畲民地区对自种自染的靛蓝衣料应用相当普遍。另一方面,由于畲民大多从事耕猎活动,日常劳作非常辛苦,男女皆然,青蓝色的服饰经久耐脏,适合劳作时穿着。故而各地畲民不论男女均喜着青蓝色服装。蓝靛色彩丰富,《通志》曰“蓝三种:蓼蓝染绿;大蓝如芥,染碧;槐蓝如槐,染青,三蓝皆可作淀,色成胜母,故曰青出于蓝,而青于蓝”。以青蓝、青黑色为主调的畲族日常服饰看似朴实,配以月白或大红镶边,衬托出穿着者或淡雅,或奔放的形象,盛装时绚丽的刺绣和花边在蓝黑色服饰的基调下反衬得越发艳丽(见图4-2)。
(二)五色斑斓,各不相同
各地畲族服饰上的用色崇尚五色斑斓,但随着用色部位、用色面积的不同,形成浓艳素雅各不相同的服色风格。
从整体色彩上来看,福安式和景宁式比较朴素淡雅,罗源式最为花哨绚丽,霞浦式和福鼎式整体大方沉稳,细节精致华美。畲族服饰不似绣工繁复装饰华丽的苗族女装,在动荡迁徙的民族发展历程中养成了畲族人民沉稳、朴实的性格,畲民服装以蓝黑色为本料,喜欢在边缘镶绲装饰和彩绣上使用红色布条和丝线,从而形成鲜明的色彩对比。比如福安式上衣的红色边缘绲边,肋下必镶嵌象征半枚金印的红布,精美的还在上面绣上凤鸟或花卉图案,老年妇女的亦有仅做简单的边缘装饰而不绣花鸟图案的。福安和景宁的拦腰腰头均为宽约2寸的大红色棉布。罗源装大量镶嵌的花边和“捆只颜”绲边也是以红、白为基调,由于花边间隔细腻,远观即形成视觉上的色彩空间混合效果,成为粉色调,衬托在底色为蓝黑色的服装本料和黑色短裙(短裤)上,大花配素黑的色彩搭配在华丽外平添一丝沉稳。霞浦和福鼎的衣襟绣花基本是以大红、玫红色图案为主,间或掺杂一些金黄、牙白、水绿色作调和,整体色彩感觉是在蓝黑色服装本料上凸显出红色的绣花块面。另外,凤冠上的色彩也是以红色为主,冠首裹以红布,珠饰则有白色、绿色、蓝色等多种颜色的“五色椒珠”。
可见,畲族女子服饰的主色为黑底红饰的基调,在诸如镶绲、刺绣等装饰细节上采用红色为主,夹杂五色斑斓的绚丽色彩,大红、玫红、水绿、靛蓝、牙白、金黄、鹅黄等色彩丰富了装饰的细节,与《后汉书》中所载盘瓠后代“好五色衣服”、“衣裳斑斓”的描述相吻合,服饰色彩鲜艳明朗,在大量运用对比色时采用白色勾边,黑色压底的配色手法,有时掺入金线作为装饰,无意中竟和现代色彩美学的配色原色相符。同时,暖色基调的各种边缘装饰与图案在青蓝色服装基底上形成强烈的反差与对比,体现了一种稳重、端庄的审美特点(见图4-3)。
三 图案之美
畲族服饰上有很多图案装饰,这些图案主要通过服装和饰品两个部分来呈现。服装上主要借助绣花和彩带编织工艺来表现,在饰品上则通过各种银簪、银笄和银牌、胸挂等饰品上的錾刻图案来表现。浙闽地区畲族服饰图案题材来源于日常生活、传说和戏剧故事,表现形式主要以刺绣、錾刻为主,按照图案表现的内容来分可以分为动物、植物、人物、几何和字符四大类别。其中动物图案中的龙凤图案是畲族服饰装饰图案中非常重要的部分。龙形图案主要来自畲族始祖盘瓠是高辛皇后耳中取出的金龙,化为五色龙犬,被赐名“龙麒”。凤鸟纹则源自由畲族始祖婆“三公主”及广东凤凰山祖地的传说和崇拜,亦受到汉文化龙凤吉祥寓意和东夷凤鸟崇拜的综合影响。由于族源崇拜的影响,龙凤图案在各地畲族服饰中被频繁使用,是绣花和银器上常见的装饰图案。
由于福建地区的服饰中绣花运用较浙江地区广泛、频繁,所以图案形式也较浙江地区更为多样和丰富,常见花鸟虫鱼、人物故事、几何文字等图案题材。浙江地区畲族服饰常服中绣花运用较少,图案主要以花鸟、几何文字为主。下面从图案题材入手,对畲族服饰常见图案进行分类论述。
(一)动物图案
动物图案是常见的服饰装饰图案,表现题材多为祥瑞动物。
1.龙凤图案。
龙凤是畲族服饰中最常见的一种图案题材(见图4-4),尤其是凤凰图案,这与畲族服装中源于始祖婆“三公主”的凤凰装有着直接的关系。正因为这种凤凰崇拜意识,在畲族女子服装的衣襟、领口、拦腰等装饰部位频繁出现凤凰的形象。龙纹的运用则多以某种固定的构图形式出现,比如和凤纹一起体现龙凤呈祥的寓意,或两条龙形成二龙戏珠的条状装饰,应用于领座部位。凤纹也经常和植物图案里的牡丹同时出现,表现富贵吉祥的寓意。由于畲族文化里并无龙图腾崇拜,始祖传说中盘瓠原为龙犬,但也并非纯粹的龙形。而凤凰崇拜是源自三公主嫁衣的典故,从收集到的资料来看,龙纹出现得较晚,且运用的频度和广度远不及凤纹。结合民族迁徙中畲汉文化交融的影响,这些龙凤呈祥、二龙戏珠的纹样应该是受到汉文化中龙凤图案的影响而产生的。虽然题材受到汉文化影响,但畲族服饰图案在表现形式上更加朴拙,尤其是凤凰形象的写实程度不高,而是加入了抽象、夸张的手法,形成拙中见巧的民族风格。凤纹除了在服装上经常出现,在畲族凤冠中象征凤身的银牌上也一般都錾刻有凤纹。
出于民族同源和祖先崇拜的缘故,以及各地畲汉交融的影响,龙凤图案是各地畲族服饰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一类装饰图案,尤其是凤纹。值得注意的是,畲族服饰图案中对龙凤形象并非盲目的膜拜,其中不乏一些将龙凤和人物结合的表达形式,将得道的仙人形象和龙凤放在同等的地位,如天官或道士形象骑龙驾凤的图案(见图4-11),表达了一种企盼求仙得道飞升的愿望。
2.其他动物图案。
龙凤图案乃是虚拟的瑞兽形象,畲族服饰中另有一些以生活中的动物为表现题材的图案(见图4-5),这些动物大都富有吉祥的寓意,和汉文化中常用的吉祥图案基本一致,如鱼代表年年有余、仙鹤、鹿竹代表长寿、喜鹊蝙蝠代表“喜”和“福”、象征爱情和美好的蝴蝶等。和汉族民间喜好一样,畲族儿童用品,尤其是童帽上特别喜欢用贴布绣的虎头纹样,且虎耳都做成立体的,像帽子上长了两个耳朵,一方面可以体现孩童虎头虎脑的可爱,一方面也有辟邪保佑儿童健康成长的含义。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独具畲族特色的动物,如雉鸡、松鼠等也是旧时服饰上喜用的装饰题材,根据畲民生活环境推测应该和常年的山地耕猎生活有关。但是在笔者对福鼎刺绣老师傅雷朝灏的交谈中得知,随着近年来畲民生活模式的改变以及外界审美意识的影响,鸡类形象已经不再受欢迎,松鼠的图案也很难见到。可见,生活环境的变迁对于服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服饰图案题材是直观反映民族生活环境的一面镜子,图案题材的变化也从一方面折射出生活方式的变化。
(二)植物图案
植物图案是服装中最常见的一种装饰题材,汉文化中喜用的象征高洁的梅兰松竹因其美好的寓意也常被使用(见图4-6),但单独运用的较少,梅花常和喜鹊组合出现,兰、松、竹图案则常与人物组合出现,兰花图案在外衣、拦腰上较少单独出现,仅单独运用在肚兜、荷包、帽子等配件上。
植物图案中尤以牡丹图案最为常见(见图4-7),这也是和畲族崇凤文化相关,凤纹的大量运用决定了牡丹作为搭配形象频繁出现,在上衣服斗胸襟绣花处一般和凤纹组合运用。在福安式和霞浦式拦腰中,拦腰裙面左右上方所用绣花为花盆或花篮造型的团花,尤以福安为甚,霞浦式拦腰中亦有将花卉与人物故事图案结合的。在花卉种类中,除了牡丹外,以荷花最常见,荷花常伴有莲藕和莲蓬造型,在肚兜等贴身服饰上亦有石榴的图案。莲藕、石榴均象征多子,故多运用在女性贴身肚兜上(见图4-8)。
畲族服饰中还有很多组合花卉图案(见图4-9),将各式花卉或凤鸟纹一起组合成盆花或花篮的形式,装饰在衣襟和拦腰裙面上(主要是福建地区的拦腰裙面,浙江地区的拦腰多为素色,无图案)。拦腰上以单独纹样的形式为主,在衣襟上则根据布局需要进行变化,形成角隅纹样或适合植物花卉图案还有一种最常见的运用方式,就是形成二方连续纹样对服装各个边口部位进行带状装饰。主要的构图骨架形式有波纹式和散点式两种,波纹式骨架除了简单的单波纹形式外还经常使用双波纹交叠的骨架形成复杂多变、生动而富有韵律感的图形。不同于汉族传统服饰纹样里求“全”避“破”的构图法则,畲族服饰纹样中散点式骨架构图时不拘泥于全幅图案的齐整性,常常截取图形的一个部分加以运用,多用于立领的领座图案或边缘装饰图案(见图4-10)。
(三)人物图案
人物图案是畲族服饰中较有特色的一种图案表现题材,表现的人物形象主要有仙道形象、文人场景和戏文故事几种类别(见图4-11)。仙道形象主要是骑着龙凤、麒麟等瑞兽的人物,有时亦会以道教八仙的形象为刺绣图案或银器錾刻图案,包括暗八仙图案(道教图案,将八仙手持的八件法器,即渔鼓、宝剑、花篮、笊篱、葫芦、扇子、阴阳板、横笛作为图案,因只采用神仙所执器物,不直接出现仙人,故称暗八仙,道教宫观常将这八件法器画成图案作为装饰)。文人场景则主要表现的是古代文人凭栏赏花、童子烹茶等场景。戏文故事则通过刺绣来表现一些民间传说戏文,比如白蛇传里断桥相会、祭塔救母等故事情节,福鼎式上衣胸襟绣花还常以头戴戏冠,手舞绸带的戏台人物形象作为图案。人物图案是畲族服饰装饰图案中较有特色的一个种类,除了刺绣的表现手法外,畲族童帽上钉缀着浮雕人物图像的银牌作为装饰,畲族人民通过多样的人物图案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四)几何字符图案
几何图案常见于服装的各个边缘修饰上,常通过刺绣工艺进行表现。比如福安式服装中边缘常用的马牙纹、罗源式服装和拦腰上常用的山字纹、柳条纹等(见图4-12)。几何图案造型简洁、线条明快,装饰效果简单朴素,有时与花卉、人物图案组合使用,构成块面装饰,形成丰富、完整的视觉效果。
字符图案主要包括文字类和符号类两种图案形式。文字类图案主要出现在童帽上,表达一种美好的祈愿和祝福。由于畲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文字图案均是以汉字为表达媒介,常在帽子前额处彩绣“福如东海”、“福禄祯祥”等吉祥文字(见图4-12),包括前文所述童帽顶和纽扣上的“福”字、罗源装后领的“囍”字等。符号类图案则以道教的八卦符号和佛教的“卍”字符号为主要表现内容,尤以八卦图案应用得更为广泛,在童帽、肚兜、荷包等服饰品上常通过彩绣的形式表现,也有錾刻在银牌或胸挂上的。“卍”字图案有时将其四角延伸、转折,形成几何图案。字符图案中还有一种很重要的类别是彩带上的字符,皆由45°角交叉构成,由于在前文彩带工艺部分已经详细分析过这些字符的造型和含义,此处不再赘述。
四 意蕴之美
受长期与汉族群众杂居的影响,不论福建还是浙江的畲族服饰装饰,均受汉文化中吉祥文化的影响,通过一些常用的吉祥图案寄托畲族人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同时结合本民族的图腾崇拜,表达了一种独特的意蕴之美。这种意蕴将畲族人民千年以来形成的民族风骨、情感和精神通过服饰的形式表达出来,通过吉祥图案表达对美的追求和憧憬,除了悦目之外还有“怡神怡情”的作用。虽然在吉祥图案的寓意上,受汉文化的影响比较明显,一些吉祥图案的题材和汉族传统图案相似,比如以凤凰牡丹寓意富贵红火,以松竹兰花表示清雅高洁,以松鹤鹿竹象征福寿绵长,以莲藕石榴象征多子,但在表现手法及形式语言的运用上畲族服饰更加奔放,图案造型质朴,线条生动,一些花卉和凤鸟的造型拙中见巧,表达了一种对自由和生命的热爱。此外,由于宗教信仰上受佛教和道教的浸染,还通过佛道常用的图形和服饰、冠戴来表达畲族人民崇神敬巫的民间信仰,比如佛教常用的宝莲、象征智慧与慈悲的“卍”字和道教的八卦、八仙图案成为畲族人民祈福避灾的一种精神寄托,常用于服饰图案装饰,而在祭祖服饰上则直接借用道教的服饰习俗。畲族服饰整体上构建的是一种衣服与人体的和谐之美,在服装与人体的关系上是贴合人体轮廓的,并无刻意的夸张或改变人体的结构、廓形。衣服的开襟、剪裁、结构等借鉴了汉族服饰,仅在边缘、服斗等处增加了装饰,从结构上来说体现的是一种顺应自然规则的朴素主义精神。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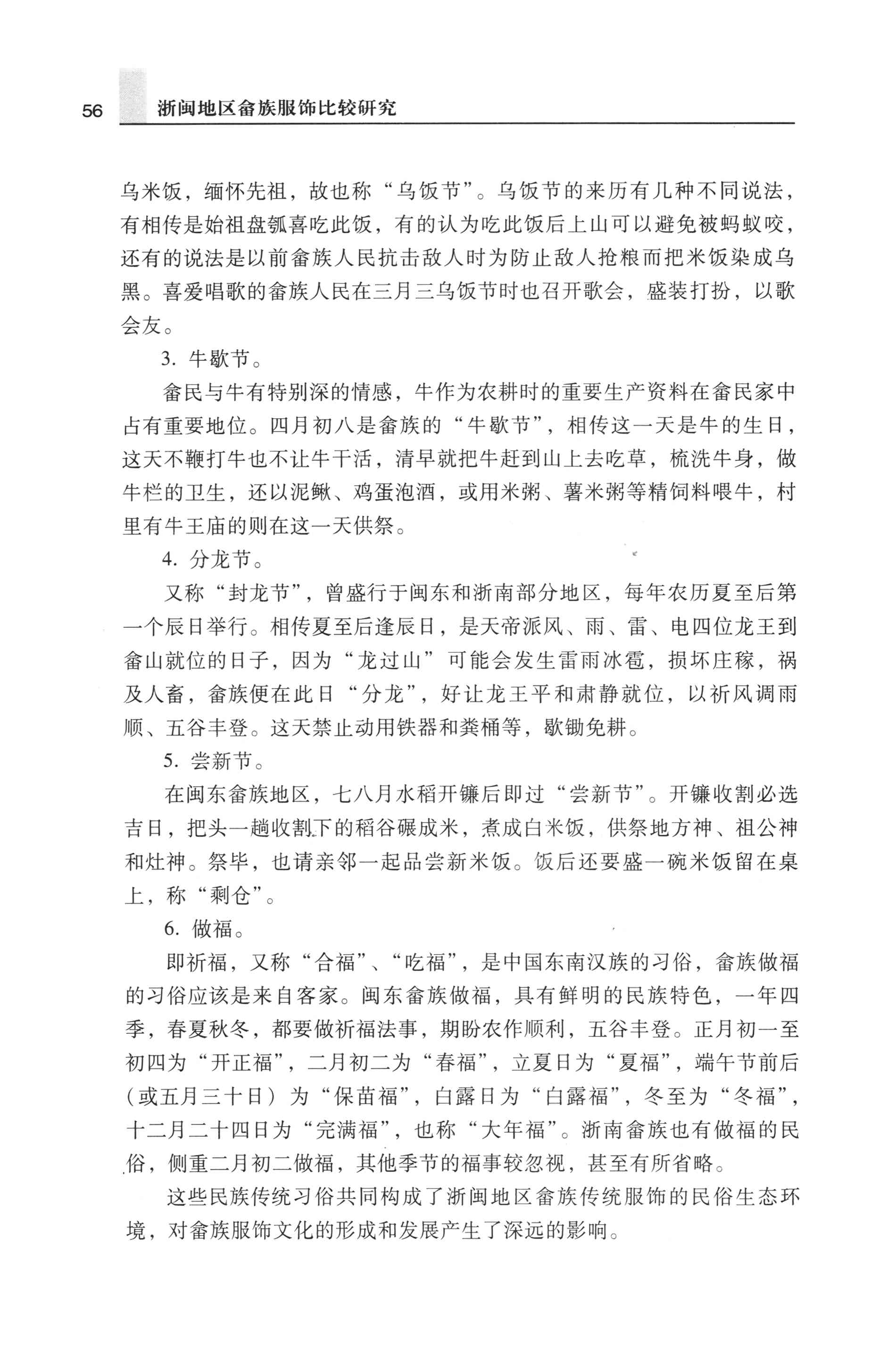
《浙闽地区畲族服饰比较研究》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从畲族历史上的迁徙路径和居住地的自然人文环境入手,通过田野调査对服饰文物资料进行收集和测量,进而对浙闽两地畲族传统服饰的形制外观、审美习俗进行比较,明晰各地服饰特征的异同和关联,总结了五种典型的服饰样式,揭示了服饰演化的脉络性特征,结合民族文化背景分析其审美文化内涵和承载媒介。在此基础上对当代社会对畲族服饰的认知现状进行调查,分析畲族服饰的嬪变及其动因,提出了对畲族服饰遗产进行固态保护与活态传承的观点。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