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夷夏”观念下的华南非汉族群格局
| 内容出处: | 《族群边缘:“畲”汉边界形成、发展与变迁的历史考察》 图书 |
| 唯一号: | 130920020230003772 |
| 颗粒名称: | 第二节 “夷夏”观念下的华南非汉族群格局 |
| 分类号: | K288.3 |
| 页数: | 8 |
| 页码: | 62-69 |
| 摘要: | 本文探讨了华夏化运动与宋代“畲”汉族群边界的形成。 |
| 关键词: | 华夏化运动 宋代 边界 |
内容
不同的自然生态造就了不同类型的区域文化,从而也塑造了具有不同文化特征的族群。不同族群在接触交往过程中,形成了对“他族”和“我族”(或者为“我群”和“你群”)②关系的认识,我们也将其称之为民族观或族群观。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形成了华夏与四夷关系的族群观念,并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一整套的观念体系,具体表现为“华夷之辨”“用夏变夷”“夷夏之防”等思想。这种族群观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其作为一种思想意识,长期影响着“华夏”与“诸夷”的族群关系。
一、华夏“异己观”的形成及其文化特性
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其文化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自然生态的制约,不同类型的自然生态造就了不同类型的文化,从而也塑造了不同的族群。自然地理学以秦岭至淮河一线为界,将中国划分为广义的华南区和华北区。由于南北方的自然地理的不同,这也造成了考古学意义上的南北区域在文化面貌、社会结构、发展阶段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也有学者将考古文化视为一个文化地理的概念。①中国自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以后,开始形成了区域的文化传统,而到了新石器时代时,已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各考古学者根据不同理论和方法,将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划分为不同区系。
从新石器时期的考古材料来看,由于经济形态的不同,华南区族群可以概分为两大集团,即苗蛮族群和百越族群。一般认为,前者的文化以(华夏)素面、绳纹灰陶(软陶)为特征,而后者的文化以印纹陶为特征;苗蛮族群的分布区以江汉平原为中心,南及洞庭湖平原,西达重庆东部,东与百越相接,北抵黄河中游;百越集团分布更为广阔,中国南方东南沿海各省区从商周到春秋直至秦汉,都是越族的分布区,在这些地区大量发现印纹陶,与汉文史料中所记载的越族活动地区相吻合,这说明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起到秦汉,东南沿海地区居住着具有共同文化特点的越民族群体。②
不同的自然生态,不仅塑造了不同的族群及其文化,还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文化心理和族群观念。从新石器时代后期开始,在考古学意义上的华北区,就逐渐形成了农耕区与游牧区的分野。这种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之间的生态边界,最终也导致了农耕民族文化与游牧民族文化的差别。③由于生态环境不同,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耕民族与长城线以外的游牧民族或半农半牧民族在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上出现了巨大的差异,进而在华夏族中形成了严格的“夷夏”观念,最后,中原地区比较有效地限制了边地民族实体、民族思想的南下或东进。这种中原文化对边地文化的排斥现象,体现在考古文化上,就是新石器时代以来的边地文化中常见中原文化的因素,而中原文化中少见边地文化的因素。④可见,早在新石器时代,古代华夏文明的边缘地带已经存在,有学者更是从考古发现材料,得出中国“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存在的结论。①
在不同族群文化长期遭遇时,各族群逐渐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异己观”,即如何看待其他族群,从而审视本族群。我国古代华夏族以“中国”称谓自己,这既是地理空间概念,也显示了“我群”为中心的文化观念认识②,是华夏族群认识和了解世界的基本参照点。与“中国”相类似的概念在古代亦称“华夏”“天下”“四海”等,与之对应的就是“四夷”(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或“五方之民”③,这种对他者形象的想象,其背后是一种文化霸权的体现。④总之,在华夏人地缘政治与文化视野中的诸夷,其根本性的区别是文化上的。正如学者指出:“华夏人以高水平的文化与文明自居,视夷狄野蛮落后,这就构成了华夷的界限,构造了‘用夏变夷’的思想文化体系。华夷之辨、华夷之防,构成了华与夷、天下与四海的主流历史意识。”⑤华夏与诸夷的关系,被认为是贯穿古代中国文化史、文明史始终的一个具有根本性的核心问题。
华夏族的这种“天下观”或“异己观”,使得其具有向外扩张的驱动性王明珂认为,秦汉以来形成的“英雄祖先历史心性”成为支持华夏认同最主要的历史心性,这决定了“华夏”的内在本质是“对外扩充边界资源及对内依阶序等差分配资源的群体”。⑥在这种历史心性下,产生了类似“英雄徙边”的各种传说,“它所创造的‘历史’隐喻着资源不足可借英雄之向外迁徙、征战、扩土及对内行阶序化资源分配来解决。华夏认同便在此历史心性下,通过‘历史’及受此记忆塑造的人们之言行,向各方、各个层面扩展其边缘……在战国时代以来经由攀附‘黄帝’或‘炎帝’及他们的后裔,以及通过‘正史’‘方志’与‘族谱’等文类,产生模式化之叙事文本,逐渐在两种‘华夏边缘’扩张——政治地理的华夏边缘,以及社会性的华夏边缘。”①在这许多的历史想象与建构之后,是真实与切要的资源垄断、分享与分配情境——“华夏”便是如此一个以“华夏边缘”排除外人,维护共同资源,并在华夏内部作阶序化资源分配的群体,“华夏帝国”是这些目的之实践工具。②
必须强调的是,在古代中国,史料文献的话语权始终掌握在主流(汉)文化圈手中。因此,关于非汉族群的记载,往往不能完全反映其真实或全貌,其中许多充满着想象与偏见。正如傅斯年、桑原骘藏所指出的,秦汉以后中国的地域问题主要是南北问题。③许多学者也指出,南方或该地族群所特有的如瘴气、蓄蛊、“南土卑湿”等特征,已经不是简单的疾病、风俗或气候的问题,更多的是观念问题,是主流文化圈的文化再创造。④随着南方各地区的渐次开发,瘴气、蓄蛊、“南土卑湿”等特征慢慢消失,显示的是族群边界的模糊化。⑤换句话说,在族群间存在严格的边界、族群文化尚未融合之时,一些类似气候、风俗,乃至族群的装饰、饮食、起居等可能成为相互嘲笑的把柄,目的就是把“我群”与“你群”区别开来,例如在中古之时就有“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⑥之说。而一个地方的文化由“野”变“文”,表现在服饰上,即所谓的“易椎髻为冠裳。”①
因此,在各种文献上,凡是与非汉民族有关的记载,大都带有蔑视的意味。以“溪洞”为例,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沅水》中记载:“武陵有五溪,谓雄溪、樠溪、潕溪、酉溪,辰溪其一焉。夹溪悉是蛮左所居,故谓此蛮五溪蛮也。”②古人以右为尊,以左为卑,“蛮左”显然是一种汉族对非汉民族的一种蔑称;再如宋代《岭外代答·外国门下》中载宋代钦州有“五类民”,其中俚人“史称俚獠者,此种自蛮峒出居,专事妖怪,若禽兽然。”③将“蛮”与“峒”合称,特指峒的属性是蛮夷之所;因为其“专事妖怪”,所以被蔑称为“禽兽”,恐怕是俚僚祀奉类似巫术的鬼神,被儒家正统认为是淫祀而加以排斥;宋代朱辅在《溪蛮丛笑》一书中描述西南地区仡佬村落称:“巢穴虽峙崄,中极宽广且以一处言之,仡佬有鸟落平(坪),言鸟飞不能尽也。周数十里皆腴田。凡平地曰平坦”。④这是典型的“山洞”特征,将其称为“巢穴”,显然是一种蔑称,体现了大汉族主义的民族观。可见,“山洞”不仅仅是一种居住地址,也不仅仅是一个聚落名称,还是一种对居住在该地区族群的一种蔑称。
总之,不同生态环境中形成了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在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中活动的族群,其文化特征必定不尽相同。不同文化特征的族群在接触过程中,形成了“异己”的观念,关于对“异己”的认识反过来也影响了族群之间的关系。
二、“夷夏之辨”视野下华南地区的非汉族群格局
古代华夏族关于南方族群的概念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迁。按照古代中国华夏族群观念,“中国”与“四夷”(东夷、西戍、南蛮、北狄)为“五方之民”,南方地区族群一般泛称为蛮。秦汉时期或更早,也将该地区族群泛称为越。明代学者章潢在《图书编》中写道:
秦并百郡,岭南有三郡。桂林,今广西地;南海,今广东地;象郡,今安南地也。夫自秦汉以来,所以为中国害者,北曰匈奴,南曰越然匈奴之势与南越不同,西北之国皆居中国边塞之外,有所限制,则彼不得越其界而入我内地也,惟越之地,在古种类实多,故有百越之名,曰南越,曰瓯越,曰闽越,曰东越,曰于越。其地非一处,其人非一种。①
北方民族泛称为胡(匈奴在古代归为“胡”),南方民族泛称为越,是秦汉以来的一种民族思想观。汉《古诗十九首》有“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②的记载,反映的正是当时的族群观念。以上材料也说明,即使是越族内部,因为种类繁多,称呼亦各异。隋唐以后,南方族群虽泛称为南蛮,但称呼仍然差别很大,如《隋书》说:“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疍,曰獽,曰俚,曰獠,曰狏,俱无君长,随山峒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③
唐代以后,在论述华南等地的非汉民族时,常将“深山的族群”和“水上的族群”并称,形成了一个表述的传统。如唐代刘禹锡称“闽有负海之饶,其民悍而俗鬼,居洞砦、家桴筏者,与华言不通。”④“居洞砦”指溪洞蛮夷,“家桴筏”则为水上疍民。唐代的韩愈也将这些居民合称为“林蛮峒疍”⑤;顾况《酬漳州张九使君》则写道:“薜鹿莫徭洞,网鱼卢亭洲。”“莫徭”根据刘禹锡记载,他们是一类“火种开山脊”⑥的畲田民族;卢亭则是水上居民⑦,“洞”(广义的山洞,即山中聚落)和“洲”(水边冲积地带)又分别代表两种族群所生活的地区。
这种表述影响后世对福建地区非汉民族的理解,如明初漳州府通判王祎在漳州时写下《清漳十咏》,其中一篇为:“近岁兵戎后,民风亦稍衰,番船收港少,畲酒入城迟。绿暗桄榔树,青悬橄榄枝,熏风荔子熟,旧数老杨妃。”①
作者为达到诗文的对仗工整,以“番船”对“畲酒”;但也说明了作者对漳州的族群印象中,在海为“番”,在山为“畲”的族群观念。再如清乾隆《龙溪县志》记载本地非汉居民:
南北之溪有水居之民焉,终岁舟,俗呼之曰泊水;穷山之内有蓝雷之族焉,不知其所始。姓蓝雷无土著,随山迁徙而种谷,三年土瘠则弃去,去则种竹偿之。无征税,无服役,以故俗呼之曰客,两家自为婚娶,朔望衣冠揖然,不读书,语言不通,不与世往来②
“蓝雷之族”与“泊水”应该就是后世所谓的畲与疍。到了民国时期,畲、疍仍是作为有异于当地居民的族群被记录,如民国《建德县志》称:“建德风俗之淳夙称于古,普通士夫之外别有渔户及畲客二种。其俗与地著(土著)稍异,县人均外视之。”③近代学者傅衣凌先生在《福建畲姓考》中写道:“在福建特殊部族中,畲与蜒实推巨擘,此两族其先盖同出于越。后乃辗转流布于今之闽浙赣三省边区,并深入于粤东,以其有居山、居水之异,爰分为二,实则一也。惟山居之民,在宋之前,多称为越、南蛮、峒蛮或洞僚,宋元之际,‘畲’名始渐通行。”④以上说明,各个时期的文献记载者注意到华南地区“山居”和“水居”非汉族群格局的存在。
关于南方非汉族群称呼变化不定,清人吴震方在《岭南杂记》中有深刻的理解,他写道:
獠即蛮之种,出自梁益之间,其在岭南,则隋唐时为患,然是时不言有猺,宋以后又不言獠,意其类合分无定,故随代异名。明通志凡山寇皆谓之獠,盖山寇亡命乌合,未必种传,无从究考。⑤
吴震方敏锐地观察到,每个朝代的非汉族群称呼不尽相同,其根本原因是“其类合分无定,故随代异名”,这种“合分无定”一方面由于族群融合导致族群实体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则与华夏族对非汉族群认知情况有关。正如郭志超先生所论:“中央王朝和中原人对周边少数民族的认识是随着王朝的开疆拓土和人口向周边的迁徙而增多的。大抵说来,以中原为中心,这种认识的半径的延长与时间成正比。并且,这种认识与半径长度成反比,对于越远之地的风物、族群,认识越模糊。”①另外,吴震方还指出,明代汉人将“山寇”都称之为“獠”,作者认为山寇并不一定都是“獠”的“种传”,无法考究这些乌合之众的具体族属。可见,吴氏的论述符合族群发展的客观实际,其论述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分辨族群时,不能单方面地强调该族群的血统因素,还应该分析其文化特征或社会身份,尤其要重视华夏族的族群对“异族”的认识观念。
一、华夏“异己观”的形成及其文化特性
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其文化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自然生态的制约,不同类型的自然生态造就了不同类型的文化,从而也塑造了不同的族群。自然地理学以秦岭至淮河一线为界,将中国划分为广义的华南区和华北区。由于南北方的自然地理的不同,这也造成了考古学意义上的南北区域在文化面貌、社会结构、发展阶段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也有学者将考古文化视为一个文化地理的概念。①中国自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以后,开始形成了区域的文化传统,而到了新石器时代时,已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各考古学者根据不同理论和方法,将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划分为不同区系。
从新石器时期的考古材料来看,由于经济形态的不同,华南区族群可以概分为两大集团,即苗蛮族群和百越族群。一般认为,前者的文化以(华夏)素面、绳纹灰陶(软陶)为特征,而后者的文化以印纹陶为特征;苗蛮族群的分布区以江汉平原为中心,南及洞庭湖平原,西达重庆东部,东与百越相接,北抵黄河中游;百越集团分布更为广阔,中国南方东南沿海各省区从商周到春秋直至秦汉,都是越族的分布区,在这些地区大量发现印纹陶,与汉文史料中所记载的越族活动地区相吻合,这说明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起到秦汉,东南沿海地区居住着具有共同文化特点的越民族群体。②
不同的自然生态,不仅塑造了不同的族群及其文化,还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文化心理和族群观念。从新石器时代后期开始,在考古学意义上的华北区,就逐渐形成了农耕区与游牧区的分野。这种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之间的生态边界,最终也导致了农耕民族文化与游牧民族文化的差别。③由于生态环境不同,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耕民族与长城线以外的游牧民族或半农半牧民族在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上出现了巨大的差异,进而在华夏族中形成了严格的“夷夏”观念,最后,中原地区比较有效地限制了边地民族实体、民族思想的南下或东进。这种中原文化对边地文化的排斥现象,体现在考古文化上,就是新石器时代以来的边地文化中常见中原文化的因素,而中原文化中少见边地文化的因素。④可见,早在新石器时代,古代华夏文明的边缘地带已经存在,有学者更是从考古发现材料,得出中国“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存在的结论。①
在不同族群文化长期遭遇时,各族群逐渐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异己观”,即如何看待其他族群,从而审视本族群。我国古代华夏族以“中国”称谓自己,这既是地理空间概念,也显示了“我群”为中心的文化观念认识②,是华夏族群认识和了解世界的基本参照点。与“中国”相类似的概念在古代亦称“华夏”“天下”“四海”等,与之对应的就是“四夷”(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或“五方之民”③,这种对他者形象的想象,其背后是一种文化霸权的体现。④总之,在华夏人地缘政治与文化视野中的诸夷,其根本性的区别是文化上的。正如学者指出:“华夏人以高水平的文化与文明自居,视夷狄野蛮落后,这就构成了华夷的界限,构造了‘用夏变夷’的思想文化体系。华夷之辨、华夷之防,构成了华与夷、天下与四海的主流历史意识。”⑤华夏与诸夷的关系,被认为是贯穿古代中国文化史、文明史始终的一个具有根本性的核心问题。
华夏族的这种“天下观”或“异己观”,使得其具有向外扩张的驱动性王明珂认为,秦汉以来形成的“英雄祖先历史心性”成为支持华夏认同最主要的历史心性,这决定了“华夏”的内在本质是“对外扩充边界资源及对内依阶序等差分配资源的群体”。⑥在这种历史心性下,产生了类似“英雄徙边”的各种传说,“它所创造的‘历史’隐喻着资源不足可借英雄之向外迁徙、征战、扩土及对内行阶序化资源分配来解决。华夏认同便在此历史心性下,通过‘历史’及受此记忆塑造的人们之言行,向各方、各个层面扩展其边缘……在战国时代以来经由攀附‘黄帝’或‘炎帝’及他们的后裔,以及通过‘正史’‘方志’与‘族谱’等文类,产生模式化之叙事文本,逐渐在两种‘华夏边缘’扩张——政治地理的华夏边缘,以及社会性的华夏边缘。”①在这许多的历史想象与建构之后,是真实与切要的资源垄断、分享与分配情境——“华夏”便是如此一个以“华夏边缘”排除外人,维护共同资源,并在华夏内部作阶序化资源分配的群体,“华夏帝国”是这些目的之实践工具。②
必须强调的是,在古代中国,史料文献的话语权始终掌握在主流(汉)文化圈手中。因此,关于非汉族群的记载,往往不能完全反映其真实或全貌,其中许多充满着想象与偏见。正如傅斯年、桑原骘藏所指出的,秦汉以后中国的地域问题主要是南北问题。③许多学者也指出,南方或该地族群所特有的如瘴气、蓄蛊、“南土卑湿”等特征,已经不是简单的疾病、风俗或气候的问题,更多的是观念问题,是主流文化圈的文化再创造。④随着南方各地区的渐次开发,瘴气、蓄蛊、“南土卑湿”等特征慢慢消失,显示的是族群边界的模糊化。⑤换句话说,在族群间存在严格的边界、族群文化尚未融合之时,一些类似气候、风俗,乃至族群的装饰、饮食、起居等可能成为相互嘲笑的把柄,目的就是把“我群”与“你群”区别开来,例如在中古之时就有“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⑥之说。而一个地方的文化由“野”变“文”,表现在服饰上,即所谓的“易椎髻为冠裳。”①
因此,在各种文献上,凡是与非汉民族有关的记载,大都带有蔑视的意味。以“溪洞”为例,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沅水》中记载:“武陵有五溪,谓雄溪、樠溪、潕溪、酉溪,辰溪其一焉。夹溪悉是蛮左所居,故谓此蛮五溪蛮也。”②古人以右为尊,以左为卑,“蛮左”显然是一种汉族对非汉民族的一种蔑称;再如宋代《岭外代答·外国门下》中载宋代钦州有“五类民”,其中俚人“史称俚獠者,此种自蛮峒出居,专事妖怪,若禽兽然。”③将“蛮”与“峒”合称,特指峒的属性是蛮夷之所;因为其“专事妖怪”,所以被蔑称为“禽兽”,恐怕是俚僚祀奉类似巫术的鬼神,被儒家正统认为是淫祀而加以排斥;宋代朱辅在《溪蛮丛笑》一书中描述西南地区仡佬村落称:“巢穴虽峙崄,中极宽广且以一处言之,仡佬有鸟落平(坪),言鸟飞不能尽也。周数十里皆腴田。凡平地曰平坦”。④这是典型的“山洞”特征,将其称为“巢穴”,显然是一种蔑称,体现了大汉族主义的民族观。可见,“山洞”不仅仅是一种居住地址,也不仅仅是一个聚落名称,还是一种对居住在该地区族群的一种蔑称。
总之,不同生态环境中形成了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在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中活动的族群,其文化特征必定不尽相同。不同文化特征的族群在接触过程中,形成了“异己”的观念,关于对“异己”的认识反过来也影响了族群之间的关系。
二、“夷夏之辨”视野下华南地区的非汉族群格局
古代华夏族关于南方族群的概念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迁。按照古代中国华夏族群观念,“中国”与“四夷”(东夷、西戍、南蛮、北狄)为“五方之民”,南方地区族群一般泛称为蛮。秦汉时期或更早,也将该地区族群泛称为越。明代学者章潢在《图书编》中写道:
秦并百郡,岭南有三郡。桂林,今广西地;南海,今广东地;象郡,今安南地也。夫自秦汉以来,所以为中国害者,北曰匈奴,南曰越然匈奴之势与南越不同,西北之国皆居中国边塞之外,有所限制,则彼不得越其界而入我内地也,惟越之地,在古种类实多,故有百越之名,曰南越,曰瓯越,曰闽越,曰东越,曰于越。其地非一处,其人非一种。①
北方民族泛称为胡(匈奴在古代归为“胡”),南方民族泛称为越,是秦汉以来的一种民族思想观。汉《古诗十九首》有“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②的记载,反映的正是当时的族群观念。以上材料也说明,即使是越族内部,因为种类繁多,称呼亦各异。隋唐以后,南方族群虽泛称为南蛮,但称呼仍然差别很大,如《隋书》说:“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疍,曰獽,曰俚,曰獠,曰狏,俱无君长,随山峒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③
唐代以后,在论述华南等地的非汉民族时,常将“深山的族群”和“水上的族群”并称,形成了一个表述的传统。如唐代刘禹锡称“闽有负海之饶,其民悍而俗鬼,居洞砦、家桴筏者,与华言不通。”④“居洞砦”指溪洞蛮夷,“家桴筏”则为水上疍民。唐代的韩愈也将这些居民合称为“林蛮峒疍”⑤;顾况《酬漳州张九使君》则写道:“薜鹿莫徭洞,网鱼卢亭洲。”“莫徭”根据刘禹锡记载,他们是一类“火种开山脊”⑥的畲田民族;卢亭则是水上居民⑦,“洞”(广义的山洞,即山中聚落)和“洲”(水边冲积地带)又分别代表两种族群所生活的地区。
这种表述影响后世对福建地区非汉民族的理解,如明初漳州府通判王祎在漳州时写下《清漳十咏》,其中一篇为:“近岁兵戎后,民风亦稍衰,番船收港少,畲酒入城迟。绿暗桄榔树,青悬橄榄枝,熏风荔子熟,旧数老杨妃。”①
作者为达到诗文的对仗工整,以“番船”对“畲酒”;但也说明了作者对漳州的族群印象中,在海为“番”,在山为“畲”的族群观念。再如清乾隆《龙溪县志》记载本地非汉居民:
南北之溪有水居之民焉,终岁舟,俗呼之曰泊水;穷山之内有蓝雷之族焉,不知其所始。姓蓝雷无土著,随山迁徙而种谷,三年土瘠则弃去,去则种竹偿之。无征税,无服役,以故俗呼之曰客,两家自为婚娶,朔望衣冠揖然,不读书,语言不通,不与世往来②
“蓝雷之族”与“泊水”应该就是后世所谓的畲与疍。到了民国时期,畲、疍仍是作为有异于当地居民的族群被记录,如民国《建德县志》称:“建德风俗之淳夙称于古,普通士夫之外别有渔户及畲客二种。其俗与地著(土著)稍异,县人均外视之。”③近代学者傅衣凌先生在《福建畲姓考》中写道:“在福建特殊部族中,畲与蜒实推巨擘,此两族其先盖同出于越。后乃辗转流布于今之闽浙赣三省边区,并深入于粤东,以其有居山、居水之异,爰分为二,实则一也。惟山居之民,在宋之前,多称为越、南蛮、峒蛮或洞僚,宋元之际,‘畲’名始渐通行。”④以上说明,各个时期的文献记载者注意到华南地区“山居”和“水居”非汉族群格局的存在。
关于南方非汉族群称呼变化不定,清人吴震方在《岭南杂记》中有深刻的理解,他写道:
獠即蛮之种,出自梁益之间,其在岭南,则隋唐时为患,然是时不言有猺,宋以后又不言獠,意其类合分无定,故随代异名。明通志凡山寇皆谓之獠,盖山寇亡命乌合,未必种传,无从究考。⑤
吴震方敏锐地观察到,每个朝代的非汉族群称呼不尽相同,其根本原因是“其类合分无定,故随代异名”,这种“合分无定”一方面由于族群融合导致族群实体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则与华夏族对非汉族群认知情况有关。正如郭志超先生所论:“中央王朝和中原人对周边少数民族的认识是随着王朝的开疆拓土和人口向周边的迁徙而增多的。大抵说来,以中原为中心,这种认识的半径的延长与时间成正比。并且,这种认识与半径长度成反比,对于越远之地的风物、族群,认识越模糊。”①另外,吴震方还指出,明代汉人将“山寇”都称之为“獠”,作者认为山寇并不一定都是“獠”的“种传”,无法考究这些乌合之众的具体族属。可见,吴氏的论述符合族群发展的客观实际,其论述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分辨族群时,不能单方面地强调该族群的血统因素,还应该分析其文化特征或社会身份,尤其要重视华夏族的族群对“异族”的认识观念。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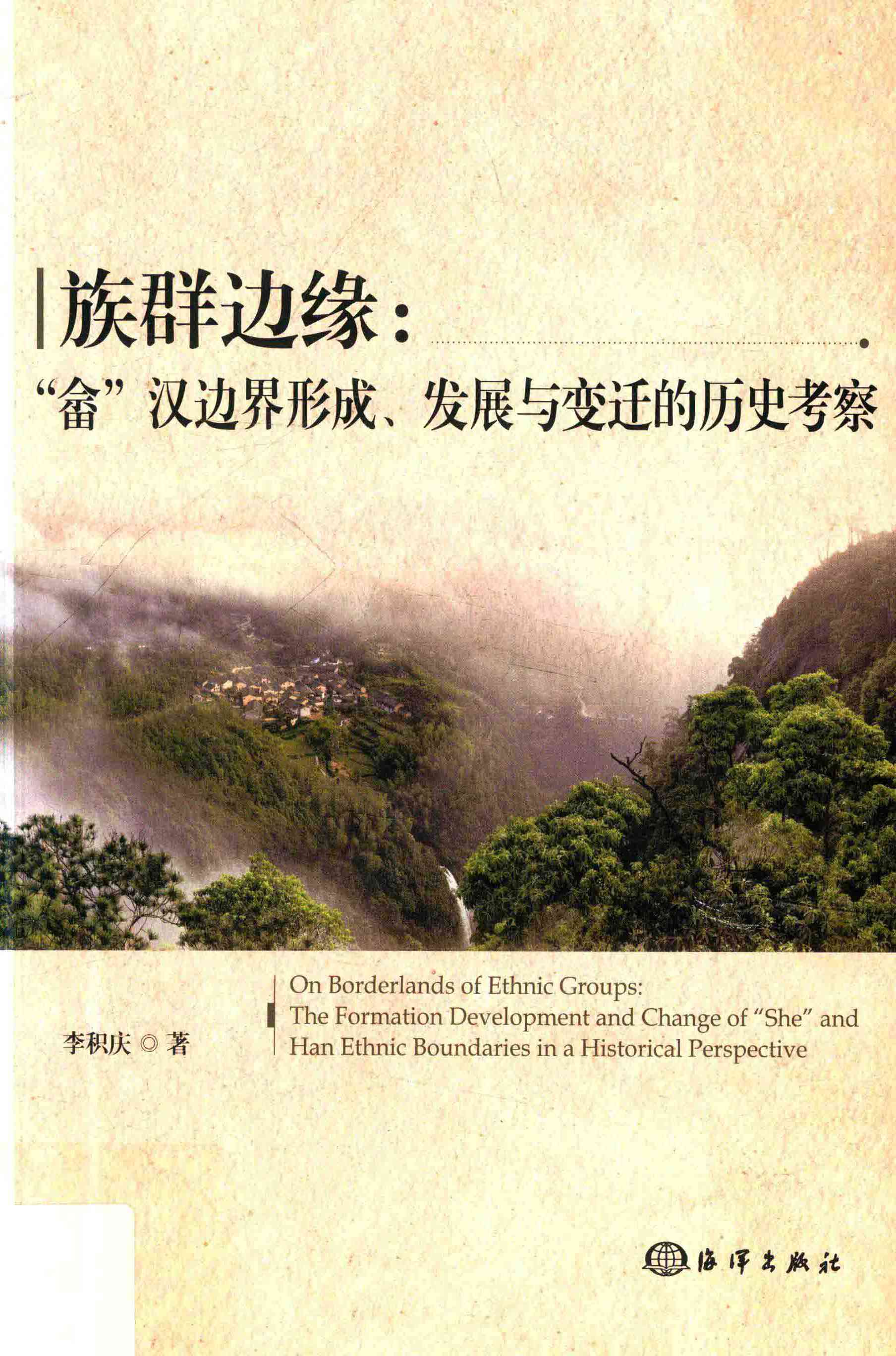
《族群边缘:“畲”汉边界形成、发展与变迁的历史考察》
出版者:海洋出版社
本书从族群边界的理论角度,重新审视畲族形成、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在承认族群客观历史文化的同时,重点研究历史上“他者”(主要是汉族)对“畲”的社会定义以及“自者”(主要为南方非汉族群)自我族群认同的过程,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现实意义。
阅读
相关地名
宁德市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