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华夏化运动与南方“山洞”地区的开发
| 内容出处: | 《族群边缘:“畲”汉边界形成、发展与变迁的历史考察》 图书 |
| 唯一号: | 130920020230003769 |
| 颗粒名称: | 第一节 华夏化运动与南方“山洞”地区的开发 |
| 分类号: | K288.3 |
| 页数: | 13 |
| 页码: | 50-62 |
| 摘要: | 本文探讨了华夏化运动与宋代“畲”汉族群边界的形成。 |
| 关键词: | 华夏化运动 宋代 边界 |
内容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华夏族就已经形成了东到海滨,南及长江中下游,西抵黄土高原的核心区域,并在此后很长的历史时间中,以类似“滚雪球”②的方式,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华夏化运动。华夏族对周围的“夷蛮戎狄”采取了两种策略:一是包进来,即“以夏变夷”;一是逐出去,赶到更远的地方。③唐代以后,文献中出现大量关于南方地区“山洞”开发的记载,这是华南地区“蛮夷”华夏化进程加快的重要表现之一。必须指出的是,“蛮夷”的华夏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渐进的、复杂而漫长的过程。
一、华夏化运动及其对“蛮夷”地区的影响
春秋战国以后,华南地区苗瑶语诸民族开始走上华夏化进程。最早完成华夏化进程的是位于长江中游的楚人,有史料证明,楚人建国时已经使用汉语和汉字,从而完成了从“蛮”到“夏”的文化认同的转变。①长江下游的吴人和越人也从长江下游的越族社会中分化出来。②罗新指出,先秦至秦汉时代,楚、吴、越三国或三个南方政治集团的华夏化是缓慢和逐渐扩散的过程,他用孤岛与海洋的关系比喻当时中国南方华夏化地区与非华夏地区③,但随着华夏化进程加快,孤岛与海洋的关系完成了逆转,也就是说非华夏地区只分布在一些山区之中,而其他平原地带均为华夏地区所占有。
秦汉时期,华夏族虽然已在江南和华南广大地区的政治、军事与文化取得稳固地位,然而各地的开发程度并不均衡。秦汉至六朝,福建相对封闭的自然生态和地理环境使得在先秦以前福建族群格局保持相对稳定状态。一般认为,在春秋之时福建地区生活着名为“七闽”④的土著居民,宋欧阳忞《舆地广记》卷三十四在论述福建路各州历代地理沿革均表述为“春秋时为七闽地”。⑤宋祝穆《方舆胜览》引《职方氏》注“七闽”云:“闽子孙分为七种,故曰七闽”。⑥朱维干认为:“七闽”指的是闽越之前的今福建和粤东潮州、梅州地区(可能还包括浙南的瓯江流域)的七大土著部落。⑦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早已存在“七闽”的称谓,一般认为是生活在闽浙的数个部族。在汉代,福建地区主要生活着闽越族,汉武帝时期,因“闽粤悍,数反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之间”。⑧史料称此次行动使得“东越地遂虚”,实际上直到唐代福建还有大量属于闽越族的土著居民。①
晋代以后,特别是“永嘉之乱”,北方汉人大批南渡,其中有一批汉人进入福建地区。东晋时期,南北分立,移入南方的中原士民在江南等地区设立了侨州、郡、县,地处边陲的福建并未置侨州、郡、县,但是北方移民也给当地社会带来影响,到了南朝梁,人口的增加促使政府又增设梁安一郡(陈时改为南安郡)和一批新设的县。
虽然有北方汉人移入福建,但在唐代以前,福建等中国东南地区仍被中原汉人视为“绝区”“瘴乡”或“蛮荒之地”,唐代诗人柳宗元曾赋诗描述当时的汀州、漳州、封州、连州等地均为“百粤文身地”②。另外,一些南方省区也是处于地旷人稀的蛮荒状态,明代工士性在《广志绎》写道:
孙吴立国建康,六代繁华,虽古今无比,然亦建康一隅而止,吴、越风气未尽开也……观孙吴治四十三州十重镇,并未及闽、越……岂非地旷人稀之故耶?至残唐钱氏立国,吴越五王继世,两浙始繁。王审知、李璟分据,八闽始盛。③
可见,直到唐五代以后,闽浙地区才开始“繁盛”起来。学术界一般认为,从唐代开始,中国经济重心开始向南转移,并在两宋完成这一历史过程。④闽浙地区的繁盛景象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一个体现。而这种经济社会的转型与“华夏化运动”所带来的地区开发和人口迁移是分不开的。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等学者均认为,北方汉人大量南迁,是南方经济崛起的重要原因。⑤而按照美国学者詹姆斯·李的研究,战国以后的政治形势和地理条件,一般有利于南下移民而不利于北上移民。①
二、唐宋时期南方“山洞”地区的开发
唐代以后,帝国加强对边陲地区的统治,唐代新一轮的“开山洞”设置新县运动说明了帝国政治势力深入南方边陲地区。以唐代福建为例,中原王朝加强对福建地区的开发,其中最重要的表现为唐开元年间“一州四县”的新置。而新县的设置在后世的一些志书中,常常表述为“开山洞置”。如《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九“福州”“汀州”条中有许多县的设置都有这样的记载:
汀州:“临汀。下。开元二十一年,福州长史唐循忠于潮州北、广州东、福州西光龙洞,检责得诸州避役百姓共三千余户,奏置州,因长汀溪以为名……管县三:长汀、沙、宁化。”
宁化县:“中下。西南至州六百里。本沙县地,开元二十二年开山洞置。县西与虔化县接。”
尤溪县:“中下。东南至州水路八百里。开元二十九年开山洞置。县东水路沿流至侯官,县西水路沂流至汀州龙岩县。”
古田县:“中下。东至州七百里。开元二十九年开山洞置。东与连江接界,(西)与沙县分界。”
永泰县:“中下。东北至州一百五十里。永泰二年观察使李承昭开山洞置。县东水路沿流至侯官,县西沂流至南安县,南北俱抵大山,并
无行路。”②
这一州四县开置的顺序分别为:汀州(733年)、宁化县(734年)、尤溪县(741年)、古田县(741年)、永泰县(766年)。一州四县空间相邻,在开置山洞的时间顺序呈现由闽西向闽江下游不断推进的趋势。日本学者佐竹靖彦认为:“据从唐初到唐中期这一时期的资料表明,这一阶段支持新县设置的是从华北入侵到福建的以土豪为中心的社会集团”③。
史料中出现的“开山洞置”,说明中原王朝承认了“山洞”地区非汉人群的土著地位。前文笔者已经对“山洞”进行考证,认为“山洞”在新石器时代为人类的居址之一,到了隋唐时期,逐渐演变成为南方非汉人群聚落称呼或族群泛称,其中体现了中原核心对地方边陲的文化阶序差别,包含着华夏人群相对于非华夏人群的心理优越感,汉人史籍中常将南方山洞地区的居民视为“蛮夷”北宋乐史在《太平寰宇记》记载汀州时称:“唐开元二十四年,开福、抚二州山洞置汀州。”①乾隆《汀州府志》对关于为何是开福、抚二州以及为何以山洞称之两个问题进行解释说:
唐时开福、抚二州山洞,置汀州。今考:州南境,旧为新罗县,隶泉州。北与石城、南丰、将乐、建宁、泰宁为邻。南丰隶抚州,而建、邵犹未郡,诸县所隶,非抚即福。时闽中只福、建、泉三郡尔。故以二州言,而四山崇峻,盘互交锁,其民狞犷,郡盗屡作,当时谓之山洞固宜。②
按照以上解释,由于汀州未设之时,其周围只有“福、抚”二州,而二者地理上“四山崇峻,盘互交锁”,人文上“其民狞犷,郡盗屡作”,因此被称为“山洞”。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华夏汉人眼里,山洞地区地势险要,居民野蛮未开化。另外也说明了至迟在唐开元年间,除了福州、抚州、泉州三郡之间的广大未设县区域,分布着大量的非汉人群,这些地区的汉人犹如孤岛点缀于非汉人群的海洋当中。所以《资治通鉴》记载汀州设郡161年后的乾宁元年(894年),发生“黄连峒蛮二万围汀州”的事件。此事件由时任福建观察使的王潮派部将李承勋“将万人击之,蛮解去,承勋追击之,至浆水口,破之。闽地略定。”③设郡治理100余年,峒蛮仍如此之多,可见未设郡时非汉人群在当地人口占较大比例。
另外,按照封建王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国家观念,“山洞”也是国家所有,虽然在客观上国家统治不到这些“山洞”地区,但由于“山洞”居民在主观上“不向王化”,未入版籍、不纳赋税,因而被认为是“逃户”“逋民”。就此而言,开山洞不仅意味着该更多的地区被开发,还象征着皇恩泽被天下,更多的“蛮夷”成为帝国子民。宋代的《太平寰宇记》载尤溪县:
其地与漳州龙岩县、汀州沙县及福州侯官县三处交界。山洞幽深,溪滩崄峻,向有千里,其诸境逃人,多投此洞。开元二十八年,经略使唐修忠使以书招谕其人,高伏等千余户请书版籍,因为县,人皆胥悦。①是否纳入版籍,是化内与化外的区别,也是区分山洞与百姓的重要标准之一。逃人,也称逋客,清代梁章钜在《称谓录》中称:“逋客,《山堂肆考》:‘逋客,避世之隐者也。’”②以上记载反映了两点:一是脱籍“逃人”投入“山洞”地区,成为化外之民;二是经朝廷“招谕”,地方逃户代表(很有可能是地方土豪)高伏等千余户要求进入国家版籍,成为编户齐民。国家通过奏置州县、检责户口、建立行政机构,对“山洞”地区进行开发。作者以“人皆胥悦”来形容新县建立后县民的喜悦情形,其中也包含着为王朝“开山洞”歌功颂德的成分。
再如民国《宁化县志》称宁化在“唐乾封二年乃改黄连峒为镇,开元十三年陞黄连镇为县”,并引旧志称:
开元十三年,福州长史唐循忠于潮州北界、福州西界检得避役百姓共三千余户,奏闻,复因居民罗令纪之请,因陞黄连镇为县。二十六年,开山峒,置汀州于新罗城。③
从宁化县的建置沿革,我们可以看到,宁化县经历了“峒”—“镇”—“县”的演变过程。从“峒”到“镇”,说明帝国首先加强对“山峒地区”采取军事措施,通过设立军事机构加强对非汉地区的控制和镇压;从“镇”升为“县”,行政机构提升一级,帝国在“山峒地区”统治更加深入,汉族势力以县城为中心逐渐扩张,并慢慢在非汉地区取得优势地位,特别是一些“避役”的汉人重新进入国家统治范围,以及“开山洞”时大量的蛮僚成为编户齐民④,这些原来被视为“化外之民”的人群在文化认同上均向汉文化发生转变,急剧扭转了“蛮”、汉在当地的族群格局。
因此,就“山洞”居民的成分而言,其中主要有非汉人群和“逃人”(大部分为避役的汉人)。另外,“山洞”中还有一个被称为“土豪”的特殊人群,主要为当地势力强大者。这些地方土豪常在“山洞”向化中起主导作用,如乾隆《古田县志》称:
古田属福州,唐开元以前尝为土豪所据,至开元十八年(740年)始建为县,有谢能者因古田亩开垦而居,故名古田……唐峒豪刘疆率林溢林希等向化,都督李亚邱遣参军杨楚畹招致,谢能等为刘氏开垦,始立邑于环峰复嶂间。①
在“山洞”成为新县、“逃人”成为编户齐民的同时,许多土著居民也慢慢完成身份的转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来的山洞地区的居民可能已经忘记本族“其来源之所自”了。如王象之《舆地纪胜》引宋代陈轩诗歌:“居人不记瓯闽事,遗迹空传福抚山,地有铜盐家自给,岁无兵盗戍长闲”②说明到了宋代,汀州居民安居乐业,此前的王朝在汀州开山洞已然成为遥远的往事,渐渐淡出当地居民的历史记忆,只不过偶尔从一些“遗迹”中才得以传闻。
在明清一些方志中,常将陈元光等人在闽、粤地区征伐“蛮夷”过程与开山洞联系起来。据史料载,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泉潮间蛮獠啸乱”③,陈元光“从父政戍闽,父没代领其众,以功授玉钤卫翊府左郎将。”④当时泉、潮交界地区,蛮夷甚多,史称龙溪县东部地区“两江(两江系指九龙江支流北溪与西溪,笔者注)夹峙,波涛激涌,两岸尽属蛮獠”⑤。永隆二年(681年),潮州盗起,陈元光军队“伐山开道,潜袭寇垒,俘馘万计,岭表悉平”,⑥唐廷晋升陈元光为正议大夫、岭南行军总管。陈元光还师移镇梁山一带,“阻盘陀诸山为寨,渐开西北诸山洞,拓地千里。”①文中所指的开“西北诸山洞”,实际上就是以华夏势力不断侵入非华夏族群势力范围的一个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唐代以后,朝廷持续对南方“山洞”地区进行开发,如在宋代神宗时,朝廷开启了大规模的“开梅山”行动,其本质是唐代“开山洞”政策的一种延续,均是朝廷加强对非汉民族地区经略,对当地的政治管理与社会控制。《宋史》卷四九四《蛮夷二·梅山峒》:
嘉祐末,知益阳县张颉收捕其桀黠符三等,遂经营开拓。安抚使吴中复以闻,其议中格。湖南转运副使范子奇复奏,蛮恃险为边患,宜臣属而郡县之。子奇寻召还,又述前议。熙宁五年,乃诏知潭州潘夙、湖南转运副使蔡烨、判官乔执中同经制章惇招纳之。惇遣执中知全州,将行,而大田三砦蛮犯境。又飞山之蛮近在全州之西,执中至全州,大田诸蛮纳款,于是遂檄谕开梅山,蛮徭争辟道路,以待得其地。东起宁乡县司徒岭,西抵邵阳白沙砦,北界益阳四里河,南止湘乡佛子岭。籍其民,得主、客万四千八百九户,万九千八十九丁。田二十六万四百三十六亩,均定其税,使岁一输。乃筑武阳、关硖二城,诏以山地置新化县,并二城隶邵州。自是,鼎、澧可以南至邵。②
从上文可以看出,应该是朝廷先对梅山地区进行“经营开拓”,而后梅山峒蛮“恃险为边患”,成为国家不稳定因素,于是朝廷下令“开梅山”。这种说法是官方的表述方式,实际上,按照族群边界的理论,所谓的“开梅山”就是汉族势力逐渐进入峒蛮地区,“开”字意味着疆域被“开边”、蛮族被“开化”。一是剿抚当地土著,有“诸蛮纳款”,即归顺降服;二是疆界被开发,在诸蛮“争辟道路”的配合下,开辟山洞的四至被界定;三是将当地土著编入版籍,并对土地收税;四是“以山地置新化县”,设置国家机构进行管理。这就是开山洞的基本过程。
“开梅山”始于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③,宋人晁补之《开梅山》对宋代此次事件进行描述,其文曰:
开梅山,梅山开自熙宁之五年。其初连峰上参天,峦崖盘崄阂群蛮。南北之帝凿混元,此山不圮藏云烟。跻攀鸟道出薈蔚,下视蛇脊相夤缘。相夤缘,穷南山。南山石室大如屋,黄闵之记盘瓠行迹今依然。高辛氏时,北有犬戎寇,国中下令购头首。妻以少女金盈斗,遍国无人有畜狗。厥初得之病耳妇,以盘覆瓠化而走。堪嗟吴将军,屈死狺狺口。帝皇下令万国同,事成违信道不容。竟以女妻之,狗乃负走逃山中,山崖幽绝不复人迹通。帝虽悲思深,往求辄遇雨与风更为独力之衣短后裾,六男六女相婚姻。木皮草实五色文,武溪赤髀皆子孙。侏离其声异言语,情黠貌痴喜安土,自以吾父有功母帝女,凌夷夏商间,稍稍病侵侮。周宣昔中兴,方叔几振旅。春秋绝笔逮战国,一负一胜安可数!迩来梅山恃险阻,黄茅竹箭霪雾雨。南人颠踣毙溪弩,据关守隘类穴鼠。一夫当其阨,万众莫能武。欲知梅山开,谁施神禹斧。大使身服儒,宾客盈幕府。檄传徭初疑,叩马卒欢舞。坦然无障塞,土石填溪渚。伊川被发祭,一变卒为虏。今虽关梁通,失制后谁御。开梅山,开山易,防獠难,不如昔人闭玉关。①
晁补之(1053—1110年),北宋著名文人,“苏门四学士”之一,曾任吏部员外郎、礼部郎中。其在《开梅山》一文中对朝廷经略山区进行描述与议论,其观点代表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理解。该文承袭黄闵《武陵记》、范晔《后汉书》关于“南山石室”“盘瓠传说”②的记载,借以证明梅山峒蛮与盘瓠之间的关系,学者也依据该文认定梅山峒蛮就是盘瓠蛮。③
另外,文章也反映了作者对开梅山持有矛盾的态度:一方面对朝廷开梅山持肯定态度,夸赞其“施神禹斧”,开辟障碍,填平溪渚,派驻“身服儒”的官员进行教化,当地百姓“叩马卒欢舞”;另一方面有对朝廷能否较好地在梅山地区守土防寇表示担心,因为梅山不仅地势险要,气候恶劣,而且群蛮负山险阻,叛变无常,“一变卒为虏”,“失制后”难以防守,为了“防獠”,最好如古人闭关守卫。①这种担心并非没有理由,《宋史·蛮夷传》就记载元祐时期蛮夷降而复叛的情况:
熙宁间,以章惇察访经制蛮事,诸溪峒相继纳土,愿为王民,始创城砦,比之内地。元祐(1086—1094年)初,诸蛮复叛,朝廷方务休息,乃诏谕湖南、北及广西路并免追讨,废堡砦,弃五溪诸郡县。崇宁间(1102—1106年),复议开边,于是安化上三州及思广诸峒蛮夷,皆愿纳土输贡赋,及令广西招纳左、右江四百五十余峒。②
从上文可知,朝廷对蛮夷地区的经略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反复的、长期的过程。这种反复的过程,似乎可以涨潮、退潮为比喻,即涨潮、退潮的潮水有进有退,但在潮汐力量的牵引下,潮水总体上是以前进的方向慢慢侵吞海滩。如果这个比喻恰当的话,那么汉族势力也像涨潮潮水,慢慢“侵吞”蛮夷的边界,这种边界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边界,还有文化上的边界,如文中提到的“愿为王民”“愿纳土输贡赋”就显示了蛮夷的国家认同。而随着教化进行,许多蛮夷的族群文化特征就与汉民渐渐的无特别大的差别了。
对于南方土著或非汉民族来讲,边陲地区的开发意味着国家对当地社会控制的加强,在钟姓畲民中流传着一些畲族的民间传说或许反映的正是这段史实。③根据闽西的一些钟氏畲族族谱记载,钟姓祖先经江西移居鄞江(长汀)白虎村,上杭树槐堂《颍川钟氏宗谱》记载道:
唐开抚、福山洞,于鄞江置汀州,以钟氏祖批黄氏之坟为刺史衙,以居宅为长汀县衙。钟氏难抗朝廷,故迁移南岭穽秋坑居住。幸刺史仁爱,以孝治天下民,泽及枯骨,有坟下废,递年清明前一日暂逊,府堂厅钟氏祭拜祖家。及礼公时,刺史酷虐,不容之祭,以致恭、宽、廉、敏、惠、节六公各迁移地方。曾将射箭坝以田施与开元寺,因塑逵公夫妇像于开元寺东阁堂,世代年年每日于香火祀奉。④
关于这个传说,该族谱摘录一段号称是南宋高宗十年(1140年)撰写的《逵公配马氏古迹谱序》,该文记载更为详细:
时因朝廷迁鄞江,祖坟葬为汀州府衙,迁宅住为长汀县衙,难杭(抗)朝廷,求有司递年祭赛,以展孝思。有知府马,仁政爱民,将箭射坝田六十亩作钟氏蒸尝,递年清明日逊府堂与钟家祭赛后数十年,又有知府姓许,不容祭扫,将钟氏一族百般刁难,即欲挖去祖坟挖开遂一油缸,有灯,又有碑文云:“许优许优,与尔无仇,数百年后,与我添油。”知府见此,遂添油而复葬之。兄弟七人见官府如此磨灭,将产业悉行出卖,悉舍入开元寺,兄弟迁徙他方。当天明誓云:“山有来龙水有源,此去代代产英雄,若有不认宗族者,天雷劈碎作灰尘。”后有知府李,以礼公兄弟舍田等项功德,题疏诏封礼公,为公望(塑)夫妇像于开元寺东廊阁下,号称南唐檀越主,世世配佛享记(祀)。当时恭、宽、敏移之虔州,恭公移龙南,宽公移信丰,敏公移零都赣县,惠、廉、节移之回龙河田等处,廉公移长汀县,节公移上杭县。世传穽丘有祖坟三穴,象形,坐西向东,前有河溪水为罗带,亦其始祖也。①
该传说在许多钟姓族谱中记载,蓝炯熹先生将其称为“白虎村传说”,该传说在闽南福佬人社区和闽西客家人社区中广泛流传,形成了大同小异的两个版本。②严格意义上讲,该传说不符合历史事实,且不说添油的神话成分以及舍田建寺的虚构成分,③序文号称撰写于南宋高宗十年(1140年),然而,汀州设府最早在明代,因此,“知府”的称谓不应在序文中出现。明清以后,民间修谱之风兴盛,该序文极有可能是在此期间伪托而作。
该传说显示了钟姓与当地政府斗争和妥协的一个过程:首先,钟姓原居住在汀州,朝廷开始对汀州进行治理,欲在钟姓祖坟上建府衙;其次,钟姓族人无法与朝廷对抗,只好顺从朝廷,朝廷也划出一定资产作为该族祭赛之用;再次,朝廷势力进一步扩大,以至于该族的祭扫权利都被剥夺;最后,钟姓族人只好将产业全部出卖,并舍入开元寺,兄弟几人迁徙他乡。
浦城村溪村《颍川堂钟氏宗谱》亦载有“许优添油”的故事,故事与上杭钟氏族谱大同小异,在一些细节上描写得更为详尽,该谱的“序”中写道:
嗣后许优莅任,每夜将公案推横,坟冢涌起。及询隶役,咸云古怪。因控开视,内现石碑,有灯偈云:许优与尔无仇,五百年后为我添油。随即示谕府中十三坊油户,各备十挑添之,未见盈溢,复各百挑增充,犹未敷足,众皆稽首叫苦方盈故从前太守每夜临寒食不能升堂理政,及清明必逊位。①
对比两则上述材料,二者均有类似诅咒的出现,或者说明本族子孙需认祖归宗,或者说明官员因为为难本族而遭到报应:除了许优添油外,此前的太守每夜临寒食不能升堂理政,到了清明必定逊位等。由于该传说的叙述主体为钟姓族人,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类似怨念的诅咒,实际上隐含着本族抵抗外来势力无果后,而采取的一种无可奈何的解释方式。
虽然不能以信史来看待流行于民间的“许优添油”传说,却可以由此追寻该传说出现的社会情境,即:随着国家对南方地区的开发和中原汉人南下,南迁汉人与畲族先民在土地等资源上存在着竞争关系。这种竞争的结果是,强势的汉族(官方)势力逼迫畲族先民退缩,直至分散各地。
我们还可以另外举上杭钟氏的一个例子,说明中央权力深入边陲给当地非汉人群带来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杭钟氏族谱的《颍川钟氏世系图》称,钟姓传至第九十五世时共有14个兄弟,因王安石变法而导致兄弟逃散,该世系图所附的文字写道:
天下姓钟皆同一脉。毅公十四兄弟因王安石余党仍在朝弄权,复行新法荼害,兄弟东逃西散,改姓流迁各省、府、县、乡,各流一处……十四兄弟遂改姓名住宁化,后各流地方。以上诸公后代都称为郎,故紊其名。因友文公兄弟阴灵在五凤楼救火,战败金,徽宗封为助国尊王。兄弟闻知,遂复为钟姓也。②
该段文字认为,正是由于北宋的王安石新政,迫使钟氏兄弟14人改姓流迁,此后子孙开始使用郎名;而钟姓后代恢复为钟姓主要是因为本族祖先有功并受封于朝廷。文中显然夸大了王安石新政对畲民家族的影响,另外阴灵救火出战也带有神话成分,其历史的真实性颇值得怀疑。正如此前所分析,这种传说的背后反映了一定的历史事实:随着朝廷对南方地区控制的加强,朝廷开始在南方地区施行政策,这引起了部分南方土著或非汉族群的反抗,一些畲民可能采取“逃离”的方式躲避朝廷的政策。该记载还显示了畲民对本族“郎名”由来背景的解释:华夏化进程给当地畲民族群社会带来冲击,导致畲民社会文化的变迁。①
一、华夏化运动及其对“蛮夷”地区的影响
春秋战国以后,华南地区苗瑶语诸民族开始走上华夏化进程。最早完成华夏化进程的是位于长江中游的楚人,有史料证明,楚人建国时已经使用汉语和汉字,从而完成了从“蛮”到“夏”的文化认同的转变。①长江下游的吴人和越人也从长江下游的越族社会中分化出来。②罗新指出,先秦至秦汉时代,楚、吴、越三国或三个南方政治集团的华夏化是缓慢和逐渐扩散的过程,他用孤岛与海洋的关系比喻当时中国南方华夏化地区与非华夏地区③,但随着华夏化进程加快,孤岛与海洋的关系完成了逆转,也就是说非华夏地区只分布在一些山区之中,而其他平原地带均为华夏地区所占有。
秦汉时期,华夏族虽然已在江南和华南广大地区的政治、军事与文化取得稳固地位,然而各地的开发程度并不均衡。秦汉至六朝,福建相对封闭的自然生态和地理环境使得在先秦以前福建族群格局保持相对稳定状态。一般认为,在春秋之时福建地区生活着名为“七闽”④的土著居民,宋欧阳忞《舆地广记》卷三十四在论述福建路各州历代地理沿革均表述为“春秋时为七闽地”。⑤宋祝穆《方舆胜览》引《职方氏》注“七闽”云:“闽子孙分为七种,故曰七闽”。⑥朱维干认为:“七闽”指的是闽越之前的今福建和粤东潮州、梅州地区(可能还包括浙南的瓯江流域)的七大土著部落。⑦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早已存在“七闽”的称谓,一般认为是生活在闽浙的数个部族。在汉代,福建地区主要生活着闽越族,汉武帝时期,因“闽粤悍,数反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之间”。⑧史料称此次行动使得“东越地遂虚”,实际上直到唐代福建还有大量属于闽越族的土著居民。①
晋代以后,特别是“永嘉之乱”,北方汉人大批南渡,其中有一批汉人进入福建地区。东晋时期,南北分立,移入南方的中原士民在江南等地区设立了侨州、郡、县,地处边陲的福建并未置侨州、郡、县,但是北方移民也给当地社会带来影响,到了南朝梁,人口的增加促使政府又增设梁安一郡(陈时改为南安郡)和一批新设的县。
虽然有北方汉人移入福建,但在唐代以前,福建等中国东南地区仍被中原汉人视为“绝区”“瘴乡”或“蛮荒之地”,唐代诗人柳宗元曾赋诗描述当时的汀州、漳州、封州、连州等地均为“百粤文身地”②。另外,一些南方省区也是处于地旷人稀的蛮荒状态,明代工士性在《广志绎》写道:
孙吴立国建康,六代繁华,虽古今无比,然亦建康一隅而止,吴、越风气未尽开也……观孙吴治四十三州十重镇,并未及闽、越……岂非地旷人稀之故耶?至残唐钱氏立国,吴越五王继世,两浙始繁。王审知、李璟分据,八闽始盛。③
可见,直到唐五代以后,闽浙地区才开始“繁盛”起来。学术界一般认为,从唐代开始,中国经济重心开始向南转移,并在两宋完成这一历史过程。④闽浙地区的繁盛景象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一个体现。而这种经济社会的转型与“华夏化运动”所带来的地区开发和人口迁移是分不开的。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等学者均认为,北方汉人大量南迁,是南方经济崛起的重要原因。⑤而按照美国学者詹姆斯·李的研究,战国以后的政治形势和地理条件,一般有利于南下移民而不利于北上移民。①
二、唐宋时期南方“山洞”地区的开发
唐代以后,帝国加强对边陲地区的统治,唐代新一轮的“开山洞”设置新县运动说明了帝国政治势力深入南方边陲地区。以唐代福建为例,中原王朝加强对福建地区的开发,其中最重要的表现为唐开元年间“一州四县”的新置。而新县的设置在后世的一些志书中,常常表述为“开山洞置”。如《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九“福州”“汀州”条中有许多县的设置都有这样的记载:
汀州:“临汀。下。开元二十一年,福州长史唐循忠于潮州北、广州东、福州西光龙洞,检责得诸州避役百姓共三千余户,奏置州,因长汀溪以为名……管县三:长汀、沙、宁化。”
宁化县:“中下。西南至州六百里。本沙县地,开元二十二年开山洞置。县西与虔化县接。”
尤溪县:“中下。东南至州水路八百里。开元二十九年开山洞置。县东水路沿流至侯官,县西水路沂流至汀州龙岩县。”
古田县:“中下。东至州七百里。开元二十九年开山洞置。东与连江接界,(西)与沙县分界。”
永泰县:“中下。东北至州一百五十里。永泰二年观察使李承昭开山洞置。县东水路沿流至侯官,县西沂流至南安县,南北俱抵大山,并
无行路。”②
这一州四县开置的顺序分别为:汀州(733年)、宁化县(734年)、尤溪县(741年)、古田县(741年)、永泰县(766年)。一州四县空间相邻,在开置山洞的时间顺序呈现由闽西向闽江下游不断推进的趋势。日本学者佐竹靖彦认为:“据从唐初到唐中期这一时期的资料表明,这一阶段支持新县设置的是从华北入侵到福建的以土豪为中心的社会集团”③。
史料中出现的“开山洞置”,说明中原王朝承认了“山洞”地区非汉人群的土著地位。前文笔者已经对“山洞”进行考证,认为“山洞”在新石器时代为人类的居址之一,到了隋唐时期,逐渐演变成为南方非汉人群聚落称呼或族群泛称,其中体现了中原核心对地方边陲的文化阶序差别,包含着华夏人群相对于非华夏人群的心理优越感,汉人史籍中常将南方山洞地区的居民视为“蛮夷”北宋乐史在《太平寰宇记》记载汀州时称:“唐开元二十四年,开福、抚二州山洞置汀州。”①乾隆《汀州府志》对关于为何是开福、抚二州以及为何以山洞称之两个问题进行解释说:
唐时开福、抚二州山洞,置汀州。今考:州南境,旧为新罗县,隶泉州。北与石城、南丰、将乐、建宁、泰宁为邻。南丰隶抚州,而建、邵犹未郡,诸县所隶,非抚即福。时闽中只福、建、泉三郡尔。故以二州言,而四山崇峻,盘互交锁,其民狞犷,郡盗屡作,当时谓之山洞固宜。②
按照以上解释,由于汀州未设之时,其周围只有“福、抚”二州,而二者地理上“四山崇峻,盘互交锁”,人文上“其民狞犷,郡盗屡作”,因此被称为“山洞”。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华夏汉人眼里,山洞地区地势险要,居民野蛮未开化。另外也说明了至迟在唐开元年间,除了福州、抚州、泉州三郡之间的广大未设县区域,分布着大量的非汉人群,这些地区的汉人犹如孤岛点缀于非汉人群的海洋当中。所以《资治通鉴》记载汀州设郡161年后的乾宁元年(894年),发生“黄连峒蛮二万围汀州”的事件。此事件由时任福建观察使的王潮派部将李承勋“将万人击之,蛮解去,承勋追击之,至浆水口,破之。闽地略定。”③设郡治理100余年,峒蛮仍如此之多,可见未设郡时非汉人群在当地人口占较大比例。
另外,按照封建王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国家观念,“山洞”也是国家所有,虽然在客观上国家统治不到这些“山洞”地区,但由于“山洞”居民在主观上“不向王化”,未入版籍、不纳赋税,因而被认为是“逃户”“逋民”。就此而言,开山洞不仅意味着该更多的地区被开发,还象征着皇恩泽被天下,更多的“蛮夷”成为帝国子民。宋代的《太平寰宇记》载尤溪县:
其地与漳州龙岩县、汀州沙县及福州侯官县三处交界。山洞幽深,溪滩崄峻,向有千里,其诸境逃人,多投此洞。开元二十八年,经略使唐修忠使以书招谕其人,高伏等千余户请书版籍,因为县,人皆胥悦。①是否纳入版籍,是化内与化外的区别,也是区分山洞与百姓的重要标准之一。逃人,也称逋客,清代梁章钜在《称谓录》中称:“逋客,《山堂肆考》:‘逋客,避世之隐者也。’”②以上记载反映了两点:一是脱籍“逃人”投入“山洞”地区,成为化外之民;二是经朝廷“招谕”,地方逃户代表(很有可能是地方土豪)高伏等千余户要求进入国家版籍,成为编户齐民。国家通过奏置州县、检责户口、建立行政机构,对“山洞”地区进行开发。作者以“人皆胥悦”来形容新县建立后县民的喜悦情形,其中也包含着为王朝“开山洞”歌功颂德的成分。
再如民国《宁化县志》称宁化在“唐乾封二年乃改黄连峒为镇,开元十三年陞黄连镇为县”,并引旧志称:
开元十三年,福州长史唐循忠于潮州北界、福州西界检得避役百姓共三千余户,奏闻,复因居民罗令纪之请,因陞黄连镇为县。二十六年,开山峒,置汀州于新罗城。③
从宁化县的建置沿革,我们可以看到,宁化县经历了“峒”—“镇”—“县”的演变过程。从“峒”到“镇”,说明帝国首先加强对“山峒地区”采取军事措施,通过设立军事机构加强对非汉地区的控制和镇压;从“镇”升为“县”,行政机构提升一级,帝国在“山峒地区”统治更加深入,汉族势力以县城为中心逐渐扩张,并慢慢在非汉地区取得优势地位,特别是一些“避役”的汉人重新进入国家统治范围,以及“开山洞”时大量的蛮僚成为编户齐民④,这些原来被视为“化外之民”的人群在文化认同上均向汉文化发生转变,急剧扭转了“蛮”、汉在当地的族群格局。
因此,就“山洞”居民的成分而言,其中主要有非汉人群和“逃人”(大部分为避役的汉人)。另外,“山洞”中还有一个被称为“土豪”的特殊人群,主要为当地势力强大者。这些地方土豪常在“山洞”向化中起主导作用,如乾隆《古田县志》称:
古田属福州,唐开元以前尝为土豪所据,至开元十八年(740年)始建为县,有谢能者因古田亩开垦而居,故名古田……唐峒豪刘疆率林溢林希等向化,都督李亚邱遣参军杨楚畹招致,谢能等为刘氏开垦,始立邑于环峰复嶂间。①
在“山洞”成为新县、“逃人”成为编户齐民的同时,许多土著居民也慢慢完成身份的转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来的山洞地区的居民可能已经忘记本族“其来源之所自”了。如王象之《舆地纪胜》引宋代陈轩诗歌:“居人不记瓯闽事,遗迹空传福抚山,地有铜盐家自给,岁无兵盗戍长闲”②说明到了宋代,汀州居民安居乐业,此前的王朝在汀州开山洞已然成为遥远的往事,渐渐淡出当地居民的历史记忆,只不过偶尔从一些“遗迹”中才得以传闻。
在明清一些方志中,常将陈元光等人在闽、粤地区征伐“蛮夷”过程与开山洞联系起来。据史料载,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泉潮间蛮獠啸乱”③,陈元光“从父政戍闽,父没代领其众,以功授玉钤卫翊府左郎将。”④当时泉、潮交界地区,蛮夷甚多,史称龙溪县东部地区“两江(两江系指九龙江支流北溪与西溪,笔者注)夹峙,波涛激涌,两岸尽属蛮獠”⑤。永隆二年(681年),潮州盗起,陈元光军队“伐山开道,潜袭寇垒,俘馘万计,岭表悉平”,⑥唐廷晋升陈元光为正议大夫、岭南行军总管。陈元光还师移镇梁山一带,“阻盘陀诸山为寨,渐开西北诸山洞,拓地千里。”①文中所指的开“西北诸山洞”,实际上就是以华夏势力不断侵入非华夏族群势力范围的一个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唐代以后,朝廷持续对南方“山洞”地区进行开发,如在宋代神宗时,朝廷开启了大规模的“开梅山”行动,其本质是唐代“开山洞”政策的一种延续,均是朝廷加强对非汉民族地区经略,对当地的政治管理与社会控制。《宋史》卷四九四《蛮夷二·梅山峒》:
嘉祐末,知益阳县张颉收捕其桀黠符三等,遂经营开拓。安抚使吴中复以闻,其议中格。湖南转运副使范子奇复奏,蛮恃险为边患,宜臣属而郡县之。子奇寻召还,又述前议。熙宁五年,乃诏知潭州潘夙、湖南转运副使蔡烨、判官乔执中同经制章惇招纳之。惇遣执中知全州,将行,而大田三砦蛮犯境。又飞山之蛮近在全州之西,执中至全州,大田诸蛮纳款,于是遂檄谕开梅山,蛮徭争辟道路,以待得其地。东起宁乡县司徒岭,西抵邵阳白沙砦,北界益阳四里河,南止湘乡佛子岭。籍其民,得主、客万四千八百九户,万九千八十九丁。田二十六万四百三十六亩,均定其税,使岁一输。乃筑武阳、关硖二城,诏以山地置新化县,并二城隶邵州。自是,鼎、澧可以南至邵。②
从上文可以看出,应该是朝廷先对梅山地区进行“经营开拓”,而后梅山峒蛮“恃险为边患”,成为国家不稳定因素,于是朝廷下令“开梅山”。这种说法是官方的表述方式,实际上,按照族群边界的理论,所谓的“开梅山”就是汉族势力逐渐进入峒蛮地区,“开”字意味着疆域被“开边”、蛮族被“开化”。一是剿抚当地土著,有“诸蛮纳款”,即归顺降服;二是疆界被开发,在诸蛮“争辟道路”的配合下,开辟山洞的四至被界定;三是将当地土著编入版籍,并对土地收税;四是“以山地置新化县”,设置国家机构进行管理。这就是开山洞的基本过程。
“开梅山”始于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③,宋人晁补之《开梅山》对宋代此次事件进行描述,其文曰:
开梅山,梅山开自熙宁之五年。其初连峰上参天,峦崖盘崄阂群蛮。南北之帝凿混元,此山不圮藏云烟。跻攀鸟道出薈蔚,下视蛇脊相夤缘。相夤缘,穷南山。南山石室大如屋,黄闵之记盘瓠行迹今依然。高辛氏时,北有犬戎寇,国中下令购头首。妻以少女金盈斗,遍国无人有畜狗。厥初得之病耳妇,以盘覆瓠化而走。堪嗟吴将军,屈死狺狺口。帝皇下令万国同,事成违信道不容。竟以女妻之,狗乃负走逃山中,山崖幽绝不复人迹通。帝虽悲思深,往求辄遇雨与风更为独力之衣短后裾,六男六女相婚姻。木皮草实五色文,武溪赤髀皆子孙。侏离其声异言语,情黠貌痴喜安土,自以吾父有功母帝女,凌夷夏商间,稍稍病侵侮。周宣昔中兴,方叔几振旅。春秋绝笔逮战国,一负一胜安可数!迩来梅山恃险阻,黄茅竹箭霪雾雨。南人颠踣毙溪弩,据关守隘类穴鼠。一夫当其阨,万众莫能武。欲知梅山开,谁施神禹斧。大使身服儒,宾客盈幕府。檄传徭初疑,叩马卒欢舞。坦然无障塞,土石填溪渚。伊川被发祭,一变卒为虏。今虽关梁通,失制后谁御。开梅山,开山易,防獠难,不如昔人闭玉关。①
晁补之(1053—1110年),北宋著名文人,“苏门四学士”之一,曾任吏部员外郎、礼部郎中。其在《开梅山》一文中对朝廷经略山区进行描述与议论,其观点代表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理解。该文承袭黄闵《武陵记》、范晔《后汉书》关于“南山石室”“盘瓠传说”②的记载,借以证明梅山峒蛮与盘瓠之间的关系,学者也依据该文认定梅山峒蛮就是盘瓠蛮。③
另外,文章也反映了作者对开梅山持有矛盾的态度:一方面对朝廷开梅山持肯定态度,夸赞其“施神禹斧”,开辟障碍,填平溪渚,派驻“身服儒”的官员进行教化,当地百姓“叩马卒欢舞”;另一方面有对朝廷能否较好地在梅山地区守土防寇表示担心,因为梅山不仅地势险要,气候恶劣,而且群蛮负山险阻,叛变无常,“一变卒为虏”,“失制后”难以防守,为了“防獠”,最好如古人闭关守卫。①这种担心并非没有理由,《宋史·蛮夷传》就记载元祐时期蛮夷降而复叛的情况:
熙宁间,以章惇察访经制蛮事,诸溪峒相继纳土,愿为王民,始创城砦,比之内地。元祐(1086—1094年)初,诸蛮复叛,朝廷方务休息,乃诏谕湖南、北及广西路并免追讨,废堡砦,弃五溪诸郡县。崇宁间(1102—1106年),复议开边,于是安化上三州及思广诸峒蛮夷,皆愿纳土输贡赋,及令广西招纳左、右江四百五十余峒。②
从上文可知,朝廷对蛮夷地区的经略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反复的、长期的过程。这种反复的过程,似乎可以涨潮、退潮为比喻,即涨潮、退潮的潮水有进有退,但在潮汐力量的牵引下,潮水总体上是以前进的方向慢慢侵吞海滩。如果这个比喻恰当的话,那么汉族势力也像涨潮潮水,慢慢“侵吞”蛮夷的边界,这种边界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边界,还有文化上的边界,如文中提到的“愿为王民”“愿纳土输贡赋”就显示了蛮夷的国家认同。而随着教化进行,许多蛮夷的族群文化特征就与汉民渐渐的无特别大的差别了。
对于南方土著或非汉民族来讲,边陲地区的开发意味着国家对当地社会控制的加强,在钟姓畲民中流传着一些畲族的民间传说或许反映的正是这段史实。③根据闽西的一些钟氏畲族族谱记载,钟姓祖先经江西移居鄞江(长汀)白虎村,上杭树槐堂《颍川钟氏宗谱》记载道:
唐开抚、福山洞,于鄞江置汀州,以钟氏祖批黄氏之坟为刺史衙,以居宅为长汀县衙。钟氏难抗朝廷,故迁移南岭穽秋坑居住。幸刺史仁爱,以孝治天下民,泽及枯骨,有坟下废,递年清明前一日暂逊,府堂厅钟氏祭拜祖家。及礼公时,刺史酷虐,不容之祭,以致恭、宽、廉、敏、惠、节六公各迁移地方。曾将射箭坝以田施与开元寺,因塑逵公夫妇像于开元寺东阁堂,世代年年每日于香火祀奉。④
关于这个传说,该族谱摘录一段号称是南宋高宗十年(1140年)撰写的《逵公配马氏古迹谱序》,该文记载更为详细:
时因朝廷迁鄞江,祖坟葬为汀州府衙,迁宅住为长汀县衙,难杭(抗)朝廷,求有司递年祭赛,以展孝思。有知府马,仁政爱民,将箭射坝田六十亩作钟氏蒸尝,递年清明日逊府堂与钟家祭赛后数十年,又有知府姓许,不容祭扫,将钟氏一族百般刁难,即欲挖去祖坟挖开遂一油缸,有灯,又有碑文云:“许优许优,与尔无仇,数百年后,与我添油。”知府见此,遂添油而复葬之。兄弟七人见官府如此磨灭,将产业悉行出卖,悉舍入开元寺,兄弟迁徙他方。当天明誓云:“山有来龙水有源,此去代代产英雄,若有不认宗族者,天雷劈碎作灰尘。”后有知府李,以礼公兄弟舍田等项功德,题疏诏封礼公,为公望(塑)夫妇像于开元寺东廊阁下,号称南唐檀越主,世世配佛享记(祀)。当时恭、宽、敏移之虔州,恭公移龙南,宽公移信丰,敏公移零都赣县,惠、廉、节移之回龙河田等处,廉公移长汀县,节公移上杭县。世传穽丘有祖坟三穴,象形,坐西向东,前有河溪水为罗带,亦其始祖也。①
该传说在许多钟姓族谱中记载,蓝炯熹先生将其称为“白虎村传说”,该传说在闽南福佬人社区和闽西客家人社区中广泛流传,形成了大同小异的两个版本。②严格意义上讲,该传说不符合历史事实,且不说添油的神话成分以及舍田建寺的虚构成分,③序文号称撰写于南宋高宗十年(1140年),然而,汀州设府最早在明代,因此,“知府”的称谓不应在序文中出现。明清以后,民间修谱之风兴盛,该序文极有可能是在此期间伪托而作。
该传说显示了钟姓与当地政府斗争和妥协的一个过程:首先,钟姓原居住在汀州,朝廷开始对汀州进行治理,欲在钟姓祖坟上建府衙;其次,钟姓族人无法与朝廷对抗,只好顺从朝廷,朝廷也划出一定资产作为该族祭赛之用;再次,朝廷势力进一步扩大,以至于该族的祭扫权利都被剥夺;最后,钟姓族人只好将产业全部出卖,并舍入开元寺,兄弟几人迁徙他乡。
浦城村溪村《颍川堂钟氏宗谱》亦载有“许优添油”的故事,故事与上杭钟氏族谱大同小异,在一些细节上描写得更为详尽,该谱的“序”中写道:
嗣后许优莅任,每夜将公案推横,坟冢涌起。及询隶役,咸云古怪。因控开视,内现石碑,有灯偈云:许优与尔无仇,五百年后为我添油。随即示谕府中十三坊油户,各备十挑添之,未见盈溢,复各百挑增充,犹未敷足,众皆稽首叫苦方盈故从前太守每夜临寒食不能升堂理政,及清明必逊位。①
对比两则上述材料,二者均有类似诅咒的出现,或者说明本族子孙需认祖归宗,或者说明官员因为为难本族而遭到报应:除了许优添油外,此前的太守每夜临寒食不能升堂理政,到了清明必定逊位等。由于该传说的叙述主体为钟姓族人,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类似怨念的诅咒,实际上隐含着本族抵抗外来势力无果后,而采取的一种无可奈何的解释方式。
虽然不能以信史来看待流行于民间的“许优添油”传说,却可以由此追寻该传说出现的社会情境,即:随着国家对南方地区的开发和中原汉人南下,南迁汉人与畲族先民在土地等资源上存在着竞争关系。这种竞争的结果是,强势的汉族(官方)势力逼迫畲族先民退缩,直至分散各地。
我们还可以另外举上杭钟氏的一个例子,说明中央权力深入边陲给当地非汉人群带来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杭钟氏族谱的《颍川钟氏世系图》称,钟姓传至第九十五世时共有14个兄弟,因王安石变法而导致兄弟逃散,该世系图所附的文字写道:
天下姓钟皆同一脉。毅公十四兄弟因王安石余党仍在朝弄权,复行新法荼害,兄弟东逃西散,改姓流迁各省、府、县、乡,各流一处……十四兄弟遂改姓名住宁化,后各流地方。以上诸公后代都称为郎,故紊其名。因友文公兄弟阴灵在五凤楼救火,战败金,徽宗封为助国尊王。兄弟闻知,遂复为钟姓也。②
该段文字认为,正是由于北宋的王安石新政,迫使钟氏兄弟14人改姓流迁,此后子孙开始使用郎名;而钟姓后代恢复为钟姓主要是因为本族祖先有功并受封于朝廷。文中显然夸大了王安石新政对畲民家族的影响,另外阴灵救火出战也带有神话成分,其历史的真实性颇值得怀疑。正如此前所分析,这种传说的背后反映了一定的历史事实:随着朝廷对南方地区控制的加强,朝廷开始在南方地区施行政策,这引起了部分南方土著或非汉族群的反抗,一些畲民可能采取“逃离”的方式躲避朝廷的政策。该记载还显示了畲民对本族“郎名”由来背景的解释:华夏化进程给当地畲民族群社会带来冲击,导致畲民社会文化的变迁。①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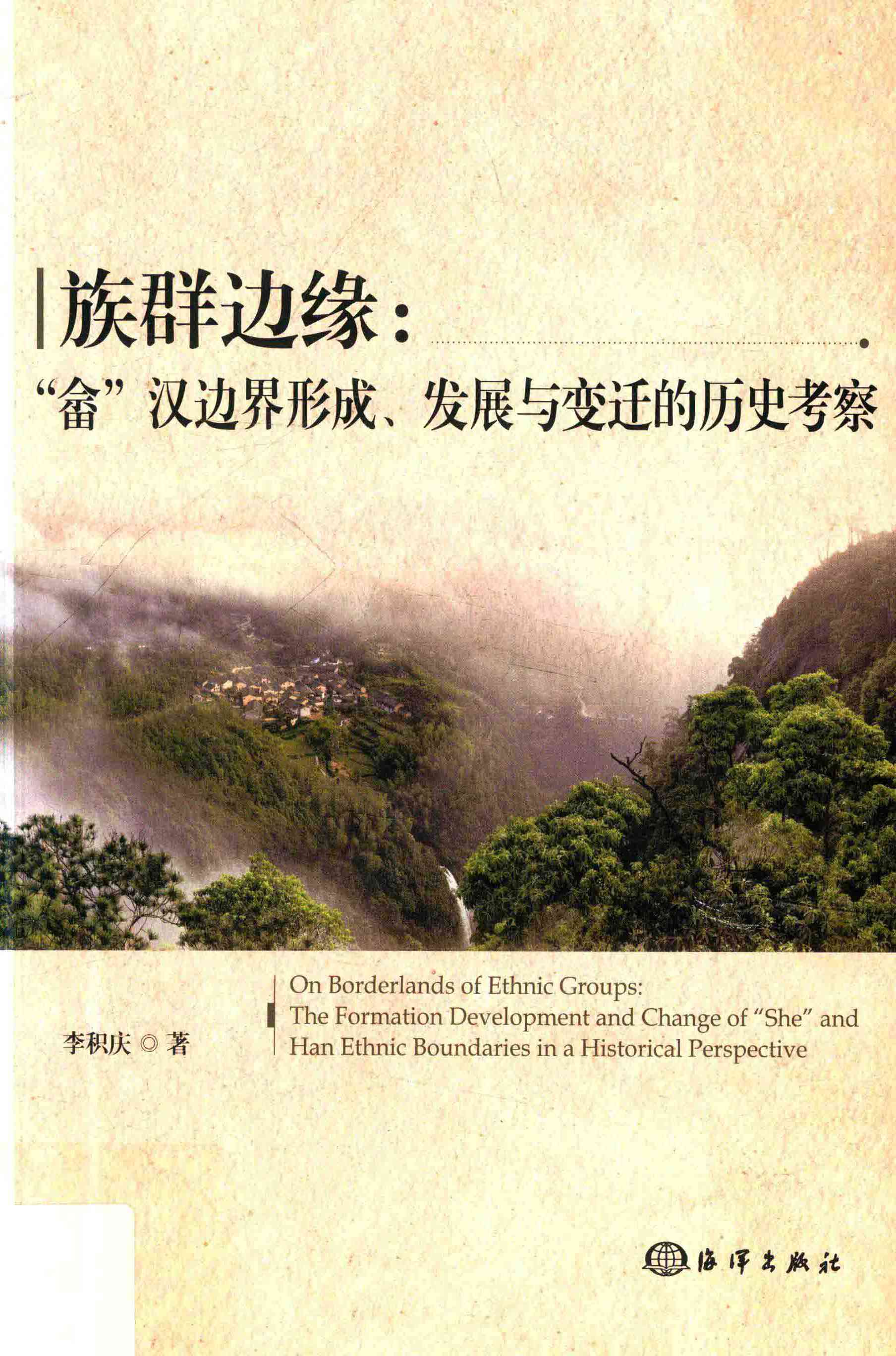
《族群边缘:“畲”汉边界形成、发展与变迁的历史考察》
出版者:海洋出版社
本书从族群边界的理论角度,重新审视畲族形成、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在承认族群客观历史文化的同时,重点研究历史上“他者”(主要是汉族)对“畲”的社会定义以及“自者”(主要为南方非汉族群)自我族群认同的过程,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现实意义。
阅读
相关地名
宁德市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