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华夏化运动与宋代“畲”汉族群边界的形成
| 内容出处: | 《族群边缘:“畲”汉边界形成、发展与变迁的历史考察》 图书 |
| 唯一号: | 130920020230003768 |
| 颗粒名称: | 第二章 华夏化运动与宋代“畲”汉族群边界的形成 |
| 分类号: | K288.3 |
| 页数: | 56 |
| 页码: | 50-105 |
| 摘要: | 本章探讨了在华夏化进程中,特别是在华夏民族观念下,中国南方地区族群格局变化的情况,着重论述了南宋时期畲汉族群边界形成的情况。 |
| 关键词: | 华夏化运动 宋代 边界 |
内容
春秋战国以来,华夏族不断向华夏核心区以外的“蛮夷”地区扩张,越来越多非华夏族群被卷入其中。随着华夏化进程的加快,南方的“蛮夷”边界向更边陲的地区移动,最后形成一个个非华夏族群的“孤岛”。①在这种族群互动中,中原华夏族对周边的非华夏人群认识加深,越来越多的“他者”族群被发现,并随着华夏化进程,其族群边界发生了漂移。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政治、文化(包括思想观念)因素在“畲”汉族群边界的界定中起了至关重要的重要作用。
第一节 华夏化运动与南方“山洞”地区的开发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华夏族就已经形成了东到海滨,南及长江中下游,西抵黄土高原的核心区域,并在此后很长的历史时间中,以类似“滚雪球”②的方式,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华夏化运动。华夏族对周围的“夷蛮戎狄”采取了两种策略:一是包进来,即“以夏变夷”;一是逐出去,赶到更远的地方。③唐代以后,文献中出现大量关于南方地区“山洞”开发的记载,这是华南地区“蛮夷”华夏化进程加快的重要表现之一。必须指出的是,“蛮夷”的华夏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渐进的、复杂而漫长的过程。
一、华夏化运动及其对“蛮夷”地区的影响
春秋战国以后,华南地区苗瑶语诸民族开始走上华夏化进程。最早完成华夏化进程的是位于长江中游的楚人,有史料证明,楚人建国时已经使用汉语和汉字,从而完成了从“蛮”到“夏”的文化认同的转变。①长江下游的吴人和越人也从长江下游的越族社会中分化出来。②罗新指出,先秦至秦汉时代,楚、吴、越三国或三个南方政治集团的华夏化是缓慢和逐渐扩散的过程,他用孤岛与海洋的关系比喻当时中国南方华夏化地区与非华夏地区③,但随着华夏化进程加快,孤岛与海洋的关系完成了逆转,也就是说非华夏地区只分布在一些山区之中,而其他平原地带均为华夏地区所占有。
秦汉时期,华夏族虽然已在江南和华南广大地区的政治、军事与文化取得稳固地位,然而各地的开发程度并不均衡。秦汉至六朝,福建相对封闭的自然生态和地理环境使得在先秦以前福建族群格局保持相对稳定状态。一般认为,在春秋之时福建地区生活着名为“七闽”④的土著居民,宋欧阳忞《舆地广记》卷三十四在论述福建路各州历代地理沿革均表述为“春秋时为七闽地”。⑤宋祝穆《方舆胜览》引《职方氏》注“七闽”云:“闽子孙分为七种,故曰七闽”。⑥朱维干认为:“七闽”指的是闽越之前的今福建和粤东潮州、梅州地区(可能还包括浙南的瓯江流域)的七大土著部落。⑦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早已存在“七闽”的称谓,一般认为是生活在闽浙的数个部族。在汉代,福建地区主要生活着闽越族,汉武帝时期,因“闽粤悍,数反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之间”。⑧史料称此次行动使得“东越地遂虚”,实际上直到唐代福建还有大量属于
闽越族的土著居民。①
晋代以后,特别是“永嘉之乱”,北方汉人大批南渡,其中有一批汉人进入福建地区。东晋时期,南北分立,移入南方的中原士民在江南等地区设立了侨州、郡、县,地处边陲的福建并未置侨州、郡、县,但是北方移民也给当地社会带来影响,到了南朝梁,人口的增加促使政府又增设梁安一郡(陈时改为南安郡)和一批新设的县。
虽然有北方汉人移入福建,但在唐代以前,福建等中国东南地区仍被中原汉人视为“绝区”“瘴乡”或“蛮荒之地”,唐代诗人柳宗元曾赋诗描述当时的汀州、漳州、封州、连州等地均为“百粤文身地”②。另外,一些南方省区也是处于地旷人稀的蛮荒状态,明代工士性在《广志绎》写道:
孙吴立国建康,六代繁华,虽古今无比,然亦建康一隅而止,吴、越风气未尽开也……观孙吴治四十三州十重镇,并未及闽、越……岂非地旷人稀之故耶?至残唐钱氏立国,吴越五王继世,两浙始繁。王审知、李璟分据,八闽始盛。③
可见,直到唐五代以后,闽浙地区才开始“繁盛”起来。学术界一般认为,从唐代开始,中国经济重心开始向南转移,并在两宋完成这一历史过程。④闽浙地区的繁盛景象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一个体现。而这种经济社会的转型与“华夏化运动”所带来的地区开发和人口迁移是分不开的。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等学者均认为,北方汉人大量南迁,是南方经济崛起的重要原因。⑤而按照美国学者詹姆斯·李的研究,战国以后的政治形势和地理条件,一般有利于南下移民
而不利于北上移民。①
二、唐宋时期南方“山洞”地区的开发
唐代以后,帝国加强对边陲地区的统治,唐代新一轮的“开山洞”设置新县运动说明了帝国政治势力深入南方边陲地区。以唐代福建为例,中原王朝加强对福建地区的开发,其中最重要的表现为唐开元年间“一州四县”的新置。而新县的设置在后世的一些志书中,常常表述为“开山洞置”。如《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九“福州”“汀州”条中有许多县的设置都有这样的记载:
汀州:“临汀。下。开元二十一年,福州长史唐循忠于潮州北、广州东、福州西光龙洞,检责得诸州避役百姓共三千余户,奏置州,因长汀溪以为名……管县三:长汀、沙、宁化。”
宁化县:“中下。西南至州六百里。本沙县地,开元二十二年开山洞置。县西与虔化县接。”
尤溪县:“中下。东南至州水路八百里。开元二十九年开山洞置。县东水路沿流至侯官,县西水路沂流至汀州龙岩县。”
古田县:“中下。东至州七百里。开元二十九年开山洞置。东与连江接界,(西)与沙县分界。”
永泰县:“中下。东北至州一百五十里。永泰二年观察使李承昭开山洞置。县东水路沿流至侯官,县西沂流至南安县,南北俱抵大山,并
无行路。”②
这一州四县开置的顺序分别为:汀州(733年)、宁化县(734年)、尤溪县(741年)、古田县(741年)、永泰县(766年)。一州四县空间相邻,在开置山洞的时间顺序呈现由闽西向闽江下游不断推进的趋势。日本学者佐竹靖彦认为:“据从唐初到唐中期这一时期的资料表明,这一阶段支持新县设置的是从华北入侵到福建的以土豪为中心的社会集团”③。
史料中出现的“开山洞置”,说明中原王朝承认了“山洞”地区非汉人群的土著地位。前文笔者已经对“山洞”进行考证,认为“山洞”在新石器时代为人类的居址之一,到了隋唐时期,逐渐演变成为南方非汉人群聚落称呼或族群泛称,其中体现了中原核心对地方边陲的文化阶序差别,包含着华夏人群相对于非华夏人群的心理优越感,汉人史籍中常将南方山洞地区的居民视为“蛮夷”
北宋乐史在《太平寰宇记》记载汀州时称:“唐开元二十四年,开福、抚二州山洞置汀州。”①乾隆《汀州府志》对关于为何是开福、抚二州以及为何以山洞称之两个问题进行解释说:
唐时开福、抚二州山洞,置汀州。今考:州南境,旧为新罗县,隶泉州。北与石城、南丰、将乐、建宁、泰宁为邻。南丰隶抚州,而建、邵犹未郡,诸县所隶,非抚即福。时闽中只福、建、泉三郡尔。故以二州言,而四山崇峻,盘互交锁,其民狞犷,郡盗屡作,当时谓之山洞固宜。②
按照以上解释,由于汀州未设之时,其周围只有“福、抚”二州,而二者地理上“四山崇峻,盘互交锁”,人文上“其民狞犷,郡盗屡作”,因此被称为“山洞”。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华夏汉人眼里,山洞地区地势险要,居民野蛮未开化。另外也说明了至迟在唐开元年间,除了福州、抚州、泉州三郡之间的广大未设县区域,分布着大量的非汉人群,这些地区的汉人犹如孤岛点缀于非汉人群的海洋当中。所以《资治通鉴》记载汀州设郡161年后的乾宁元年(894年),发生“黄连峒蛮二万围汀州”的事件。此事件由时任福建观察使的王潮派部将李承勋“将万人击之,蛮解去,承勋追击之,至浆水口,破之。闽地略定。”③设郡治理100余年,峒蛮仍如此之多,可见未设郡时非汉人群在当地人口占较大比例。
另外,按照封建王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国家观念,“山洞”也是国家所有,虽然在客观上国家统治不到这些“山洞”地区,但由于“山洞”居民在主观上“不向王化”,未入版籍、不纳赋税,因而被认为是“逃户”“逋民”。就此而言,开山洞不仅意味着该更多的地区被开发,还象征着皇恩泽被天下,更多的“蛮夷”成为帝国子民。宋代的《太平寰宇记》载尤溪县:
其地与漳州龙岩县、汀州沙县及福州侯官县三处交界。山洞幽深,溪滩崄峻,向有千里,其诸境逃人,多投此洞。开元二十八年,经略使唐修忠使以书招谕其人,高伏等千余户请书版籍,因为县,人皆胥悦。①是否纳入版籍,是化内与化外的区别,也是区分山洞与百姓的重要标准之一。逃人,也称逋客,清代梁章钜在《称谓录》中称:“逋客,《山堂肆考》:‘逋客,避世之隐者也。’”②以上记载反映了两点:一是脱籍“逃人”投入“山洞”地区,成为化外之民;二是经朝廷“招谕”,地方逃户代表(很有可能是地方土豪)高伏等千余户要求进入国家版籍,成为编户齐民。国家通过奏置州县、检责户口、建立行政机构,对“山洞”地区进行开发。作者以“人皆胥悦”来形容新县建立后县民的喜悦情形,其中也包含着为王朝“开山洞”歌功颂德的成分。
再如民国《宁化县志》称宁化在“唐乾封二年乃改黄连峒为镇,开元十三年陞黄连镇为县”,并引旧志称:
开元十三年,福州长史唐循忠于潮州北界、福州西界检得避役百姓共三千余户,奏闻,复因居民罗令纪之请,因陞黄连镇为县。二十六年,开山峒,置汀州于新罗城。③
从宁化县的建置沿革,我们可以看到,宁化县经历了“峒”—“镇”—“县”的演变过程。从“峒”到“镇”,说明帝国首先加强对“山峒地区”采取军事措施,通过设立军事机构加强对非汉地区的控制和镇压;从“镇”升为“县”,行政机构提升一级,帝国在“山峒地区”统治更加深入,汉族势力以县城为中心逐渐扩张,并慢慢在非汉地区取得优势地位,特别是一些“避役”的汉人重新进入国家统治范围,以及“开山洞”时大量的蛮僚成为编户齐民④,这些原来被视为“化外之民”的人群在文化认同上均向汉文化发生转变,急剧扭转了“蛮”、汉在当地的族群格局。
因此,就“山洞”居民的成分而言,其中主要有非汉人群和“逃人”(大部分为避役的汉人)。另外,“山洞”中还有一个被称为“土豪”的特殊人群,主要为当地势力强大者。这些地方土豪常在“山洞”向化中起主导作用,如乾隆《古田县志》称:
古田属福州,唐开元以前尝为土豪所据,至开元十八年(740年)始建为县,有谢能者因古田亩开垦而居,故名古田……唐峒豪刘疆率林溢林希等向化,都督李亚邱遣参军杨楚畹招致,谢能等为刘氏开垦,始立邑于环峰复嶂间。①
在“山洞”成为新县、“逃人”成为编户齐民的同时,许多土著居民也慢慢完成身份的转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来的山洞地区的居民可能已经忘记本族“其来源之所自”了。如王象之《舆地纪胜》引宋代陈轩诗歌:“居人不记瓯闽事,遗迹空传福抚山,地有铜盐家自给,岁无兵盗戍长闲”②说明到了宋代,汀州居民安居乐业,此前的王朝在汀州开山洞已然成为遥远的往事,渐渐淡出当地居民的历史记忆,只不过偶尔从一些“遗迹”中才得以传闻。
在明清一些方志中,常将陈元光等人在闽、粤地区征伐“蛮夷”过程与开山洞联系起来。据史料载,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泉潮间蛮獠啸乱”③,陈元光“从父政戍闽,父没代领其众,以功授玉钤卫翊府左郎将。”④当时泉、潮交界地区,蛮夷甚多,史称龙溪县东部地区“两江(两江系指九龙江支流北溪与西溪,笔者注)夹峙,波涛激涌,两岸尽属蛮獠”⑤。永隆二年(681年),潮州盗起,陈元光军队“伐山开道,潜袭寇垒,俘馘万计,岭表悉平”,⑥唐廷晋升陈元光为正议大夫、岭南行军总管。陈元光还师移镇梁山一带,“阻盘陀诸山为寨,渐开西北诸山洞,拓地千里。”①文中所指的开“西北诸山洞”,实际上就是以华夏势力不断侵入非华夏族群势力范围的一个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唐代以后,朝廷持续对南方“山洞”地区进行开发,如在宋代神宗时,朝廷开启了大规模的“开梅山”行动,其本质是唐代“开山洞”政策的一种延续,均是朝廷加强对非汉民族地区经略,对当地的政治管理与社会控制。《宋史》卷四九四《蛮夷二·梅山峒》:
嘉祐末,知益阳县张颉收捕其桀黠符三等,遂经营开拓。安抚使吴中复以闻,其议中格。湖南转运副使范子奇复奏,蛮恃险为边患,宜臣属而郡县之。子奇寻召还,又述前议。熙宁五年,乃诏知潭州潘夙、湖南转运副使蔡烨、判官乔执中同经制章惇招纳之。惇遣执中知全州,将行,而大田三砦蛮犯境。又飞山之蛮近在全州之西,执中至全州,大田诸蛮纳款,于是遂檄谕开梅山,蛮徭争辟道路,以待得其地。东起宁乡县司徒岭,西抵邵阳白沙砦,北界益阳四里河,南止湘乡佛子岭。籍其民,得主、客万四千八百九户,万九千八十九丁。田二十六万四百三十六亩,均定其税,使岁一输。乃筑武阳、关硖二城,诏以山地置新化县,并二城隶邵州。自是,鼎、澧可以南至邵。②
从上文可以看出,应该是朝廷先对梅山地区进行“经营开拓”,而后梅山峒蛮“恃险为边患”,成为国家不稳定因素,于是朝廷下令“开梅山”。这种说法是官方的表述方式,实际上,按照族群边界的理论,所谓的“开梅山”就是汉族势力逐渐进入峒蛮地区,“开”字意味着疆域被“开边”、蛮族被“开化”。一是剿抚当地土著,有“诸蛮纳款”,即归顺降服;二是疆界被开发,在诸蛮“争辟道路”的配合下,开辟山洞的四至被界定;三是将当地土著编入版籍,并对土地收税;四是“以山地置新化县”,设置国家机构进行管理。这就是开山洞的基本过程。
“开梅山”始于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③,宋人晁补之《开梅山》对宋代此次事件进行描述,其文曰:
开梅山,梅山开自熙宁之五年。其初连峰上参天,峦崖盘崄阂群蛮。南北之帝凿混元,此山不圮藏云烟。跻攀鸟道出薈蔚,下视蛇脊相夤缘。相夤缘,穷南山。南山石室大如屋,黄闵之记盘瓠行迹今依然。高辛氏时,北有犬戎寇,国中下令购头首。妻以少女金盈斗,遍国无人有畜狗。厥初得之病耳妇,以盘覆瓠化而走。堪嗟吴将军,屈死狺狺口。帝皇下令万国同,事成违信道不容。竟以女妻之,狗乃负走逃山中,山崖幽绝不复人迹通。帝虽悲思深,往求辄遇雨与风更为独力之衣短后裾,六男六女相婚姻。木皮草实五色文,武溪赤髀皆子孙。侏离其声异言语,情黠貌痴喜安土,自以吾父有功母帝女,凌夷夏商间,稍稍病侵侮。周宣昔中兴,方叔几振旅。春秋绝笔逮战国,一负一胜安可数!迩来梅山恃险阻,黄茅竹箭霪雾雨。南人颠踣毙溪弩,据关守隘类穴鼠。一夫当其阨,万众莫能武。欲知梅山开,谁施神禹斧。大使身服儒,宾客盈幕府。檄传徭初疑,叩马卒欢舞。坦然无障塞,土石填溪渚。伊川被发祭,一变卒为虏。今虽关梁通,失制后谁御。开梅山,开山易,防獠难,不如昔人闭玉关。①
晁补之(1053—1110年),北宋著名文人,“苏门四学士”之一,曾任吏部员外郎、礼部郎中。其在《开梅山》一文中对朝廷经略山区进行描述与议论,其观点代表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理解。该文承袭黄闵《武陵记》、范晔《后汉书》关于“南山石室”“盘瓠传说”②的记载,借以证明梅山峒蛮与盘瓠之间的关系,学者也依据该文认定梅山峒蛮就是盘瓠蛮。③
另外,文章也反映了作者对开梅山持有矛盾的态度:一方面对朝廷开梅山持肯定态度,夸赞其“施神禹斧”,开辟障碍,填平溪渚,派驻“身服儒”的官员进行教化,当地百姓“叩马卒欢舞”;另一方面有对朝廷能否较好地在梅山地区守土防寇表示担心,因为梅山不仅地势险要,气候恶劣,而且群蛮负山险阻,叛变无常,“一变卒为虏”,“失制后”难以防守,为了“防獠”,最好如古人闭关守卫。①这种担心并非没有理由,《宋史·蛮夷传》就记载元祐时期蛮夷降而复叛的情况:
熙宁间,以章惇察访经制蛮事,诸溪峒相继纳土,愿为王民,始创城砦,比之内地。元祐(1086—1094年)初,诸蛮复叛,朝廷方务休息,乃诏谕湖南、北及广西路并免追讨,废堡砦,弃五溪诸郡县。崇宁间(1102—1106年),复议开边,于是安化上三州及思广诸峒蛮夷,皆愿纳土输贡赋,及令广西招纳左、右江四百五十余峒。②
从上文可知,朝廷对蛮夷地区的经略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反复的、长期的过程。这种反复的过程,似乎可以涨潮、退潮为比喻,即涨潮、退潮的潮水有进有退,但在潮汐力量的牵引下,潮水总体上是以前进的方向慢慢侵吞海滩。如果这个比喻恰当的话,那么汉族势力也像涨潮潮水,慢慢“侵吞”蛮夷的边界,这种边界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边界,还有文化上的边界,如文中提到的“愿为王民”“愿纳土输贡赋”就显示了蛮夷的国家认同。而随着教化进行,许多蛮夷的族群文化特征就与汉民渐渐的无特别大的差别了。
对于南方土著或非汉民族来讲,边陲地区的开发意味着国家对当地社会控制的加强,在钟姓畲民中流传着一些畲族的民间传说或许反映的正是这段史实。③根据闽西的一些钟氏畲族族谱记载,钟姓祖先经江西移居鄞江(长汀)白虎村,上杭树槐堂《颍川钟氏宗谱》记载道:
唐开抚、福山洞,于鄞江置汀州,以钟氏祖批黄氏之坟为刺史衙,以居宅为长汀县衙。钟氏难抗朝廷,故迁移南岭穽秋坑居住。幸刺史仁爱,以孝治天下民,泽及枯骨,有坟下废,递年清明前一日暂逊,府堂厅钟氏祭拜祖家。及礼公时,刺史酷虐,不容之祭,以致恭、宽、廉、敏、惠、节六公各迁移地方。曾将射箭坝以田施与开元寺,因塑逵公夫妇像于开元寺东阁堂,世代年年每日于香火祀奉。④
关于这个传说,该族谱摘录一段号称是南宋高宗十年(1140年)撰写的《逵公配马氏古迹谱序》,该文记载更为详细:
时因朝廷迁鄞江,祖坟葬为汀州府衙,迁宅住为长汀县衙,难杭(抗)朝廷,求有司递年祭赛,以展孝思。有知府马,仁政爱民,将箭射坝田六十亩作钟氏蒸尝,递年清明日逊府堂与钟家祭赛后数十年,又有知府姓许,不容祭扫,将钟氏一族百般刁难,即欲挖去祖坟挖开遂一油缸,有灯,又有碑文云:“许优许优,与尔无仇,数百年后,与我添油。”知府见此,遂添油而复葬之。兄弟七人见官府如此磨灭,将产业悉行出卖,悉舍入开元寺,兄弟迁徙他方。当天明誓云:“山有来龙水有源,此去代代产英雄,若有不认宗族者,天雷劈碎作灰尘。”后有知府李,以礼公兄弟舍田等项功德,题疏诏封礼公,为公望(塑)夫妇像于开元寺东廊阁下,号称南唐檀越主,世世配佛享记(祀)。当时恭、宽、敏移之虔州,恭公移龙南,宽公移信丰,敏公移零都赣县,惠、廉、节移之回龙河田等处,廉公移长汀县,节公移上杭县。世传穽丘有祖坟三穴,象形,坐西向东,前有河溪水为罗带,亦其始祖也。①
该传说在许多钟姓族谱中记载,蓝炯熹先生将其称为“白虎村传说”,该传说在闽南福佬人社区和闽西客家人社区中广泛流传,形成了大同小异的两个版本。②严格意义上讲,该传说不符合历史事实,且不说添油的神话成分以及舍田建寺的虚构成分,③序文号称撰写于南宋高宗十年(1140年),然而,汀州设府最早在明代,因此,“知府”的称谓不应在序文中出现。明清以后,民间修谱之风兴盛,该序文极有可能是在此期间伪托而作。
该传说显示了钟姓与当地政府斗争和妥协的一个过程:首先,钟姓原居住在汀州,朝廷开始对汀州进行治理,欲在钟姓祖坟上建府衙;其次,钟姓族人无法与朝廷对抗,只好顺从朝廷,朝廷也划出一定资产作为该族祭赛之用;再次,朝廷势力进一步扩大,以至于该族的祭扫权利都被剥夺;最后,钟姓族人只好将产业全部出卖,并舍入开元寺,兄弟几人迁徙他乡。
浦城村溪村《颍川堂钟氏宗谱》亦载有“许优添油”的故事,故事与上杭钟氏族谱大同小异,在一些细节上描写得更为详尽,该谱的“序”中写道:
嗣后许优莅任,每夜将公案推横,坟冢涌起。及询隶役,咸云古怪。因控开视,内现石碑,有灯偈云:许优与尔无仇,五百年后为我添油。随即示谕府中十三坊油户,各备十挑添之,未见盈溢,复各百挑增充,犹未敷足,众皆稽首叫苦方盈故从前太守每夜临寒食不能升堂理政,及清明必逊位。①
对比两则上述材料,二者均有类似诅咒的出现,或者说明本族子孙需认祖归宗,或者说明官员因为为难本族而遭到报应:除了许优添油外,此前的太守每夜临寒食不能升堂理政,到了清明必定逊位等。由于该传说的叙述主体为钟姓族人,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类似怨念的诅咒,实际上隐含着本族抵抗外来势力无果后,而采取的一种无可奈何的解释方式。
虽然不能以信史来看待流行于民间的“许优添油”传说,却可以由此追寻该传说出现的社会情境,即:随着国家对南方地区的开发和中原汉人南下,南迁汉人与畲族先民在土地等资源上存在着竞争关系。这种竞争的结果是,强势的汉族(官方)势力逼迫畲族先民退缩,直至分散各地。
我们还可以另外举上杭钟氏的一个例子,说明中央权力深入边陲给当地非汉人群带来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杭钟氏族谱的《颍川钟氏世系图》称,钟姓传至第九十五世时共有14个兄弟,因王安石变法而导致兄弟逃散,该世系图所附的文字写道:
天下姓钟皆同一脉。毅公十四兄弟因王安石余党仍在朝弄权,复行新法荼害,兄弟东逃西散,改姓流迁各省、府、县、乡,各流一处……十四兄弟遂改姓名住宁化,后各流地方。以上诸公后代都称为郎,故紊其名。因友文公兄弟阴灵在五凤楼救火,战败金,徽宗封为助国尊王。兄弟闻知,遂复为钟姓也。②
该段文字认为,正是由于北宋的王安石新政,迫使钟氏兄弟14人改姓流迁,此后子孙开始使用郎名;而钟姓后代恢复为钟姓主要是因为本族祖先有功并受封于朝廷。文中显然夸大了王安石新政对畲民家族的影响,另外阴灵救火出战也带有神话成分,其历史的真实性颇值得怀疑。正如此前所分析,这种传说的背后反映了一定的历史事实:随着朝廷对南方地区控制的加强,朝廷开始在南方地区施行政策,这引起了部分南方土著或非汉族群的反抗,一些畲民可能采取“逃离”的方式躲避朝廷的政策。该记载还显示了畲民对本族“郎名”由来背景的解释:华夏化进程给当地畲民族群社会带来冲击,导致畲民社会文化的变迁。①
第二节 “夷夏”观念下的华南非汉族群格局
不同的自然生态造就了不同类型的区域文化,从而也塑造了具有不同文化特征的族群。不同族群在接触交往过程中,形成了对“他族”和“我族”(或者为“我群”和“你群”)②关系的认识,我们也将其称之为民族观或族群观。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形成了华夏与四夷关系的族群观念,并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一整套的观念体系,具体表现为“华夷之辨”“用夏变夷”“夷夏之防”等思想。这种族群观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其作为一种思想意识,长期影响着“华夏”与“诸夷”的族群关系。
一、华夏“异己观”的形成及其文化特性
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其文化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自然生态的制约,不同类型的自然生态造就了不同类型的文化,从而也塑造了不同的族群。自然地理学以秦岭至淮河一线为界,将中国划分为广义的华南区和华北区。由于南北方的自然地理的不同,这也造成了考古学意义上的南北区域在文化面貌、社会结构、发展阶段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也有学者将考古文化视为一个文化地理的概念。①中国自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以后,开始形成了区域的文化传统,而到了新石器时代时,已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各考古学者根据不同理论和方法,将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划分为不同区系。
从新石器时期的考古材料来看,由于经济形态的不同,华南区族群可以概分为两大集团,即苗蛮族群和百越族群。一般认为,前者的文化以(华夏)素面、绳纹灰陶(软陶)为特征,而后者的文化以印纹陶为特征;苗蛮族群的分布区以江汉平原为中心,南及洞庭湖平原,西达重庆东部,东与百越相接,北抵黄河中游;百越集团分布更为广阔,中国南方东南沿海各省区从商周到春秋直至秦汉,都是越族的分布区,在这些地区大量发现印纹陶,与汉文史料中所记载的越族活动地区相吻合,这说明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起到秦汉,东南沿海地区居住着具有共同文化特点的越民族群体。②
不同的自然生态,不仅塑造了不同的族群及其文化,还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文化心理和族群观念。从新石器时代后期开始,在考古学意义上的华北区,就逐渐形成了农耕区与游牧区的分野。这种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之间的生态边界,最终也导致了农耕民族文化与游牧民族文化的差别。③由于生态环境不同,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耕民族与长城线以外的游牧民族或半农半牧民族在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上出现了巨大的差异,进而在华夏族中形成了严格的“夷夏”观念,最后,中原地区比较有效地限制了边地民族实体、民族思想的南下或东进。这种中原文化对边地文化的排斥现象,体现在考古文化上,就是新石器时代以来的边地文化中常见中原文化的因素,而中原文化中少见边地文化的因素。④可见,早在新石器时代,古代华夏文明的边缘地带已经存在,有学者更是从考古发现材料,得出中国“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存在的结论。①
在不同族群文化长期遭遇时,各族群逐渐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异己观”,即如何看待其他族群,从而审视本族群。我国古代华夏族以“中国”称谓自己,这既是地理空间概念,也显示了“我群”为中心的文化观念认识②,是华夏族群认识和了解世界的基本参照点。与“中国”相类似的概念在古代亦称“华夏”“天下”“四海”等,与之对应的就是“四夷”(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或“五方之民”③,这种对他者形象的想象,其背后是一种文化霸权的体现。④总之,在华夏人地缘政治与文化视野中的诸夷,其根本性的区别是文化上的。正如学者指出:“华夏人以高水平的文化与文明自居,视夷狄野蛮落后,这就构成了华夷的界限,构造了‘用夏变夷’的思想文化体系。华夷之辨、华夷之防,构成了华与夷、天下与四海的主流历史意识。”⑤华夏与诸夷的关系,被认为是贯穿古代中国文化史、文明史始终的一个具有根本性的核心问题。
华夏族的这种“天下观”或“异己观”,使得其具有向外扩张的驱动性王明珂认为,秦汉以来形成的“英雄祖先历史心性”成为支持华夏认同最主要的历史心性,这决定了“华夏”的内在本质是“对外扩充边界资源及对内依阶序等差分配资源的群体”。⑥在这种历史心性下,产生了类似“英雄徙边”的各种传说,“它所创造的‘历史’隐喻着资源不足可借英雄之向外迁徙、征战、扩土及对内行阶序化资源分配来解决。华夏认同便在此历史心性下,通过‘历史’及受此记忆塑造的人们之言行,向各方、各个层面扩展其边缘……在战国时代以来经由攀附‘黄帝’或‘炎帝’及他们的后裔,以及通过‘正史’‘方志’与‘族谱’等文类,产生模式化之叙事文本,逐渐在两种‘华夏边缘’扩张——政治地理的华夏边缘,以及社会性的华夏边缘。”①在这许多的历史想象与建构之后,是真实与切要的资源垄断、分享与分配情境——“华夏”便是如此一个以“华夏边缘”排除外人,维护共同资源,并在华夏内部作阶序化资源分配的群体,“华夏帝国”是这些目的之实践工具。②
必须强调的是,在古代中国,史料文献的话语权始终掌握在主流(汉)文化圈手中。因此,关于非汉族群的记载,往往不能完全反映其真实或全貌,其中许多充满着想象与偏见。正如傅斯年、桑原骘藏所指出的,秦汉以后中国的地域问题主要是南北问题。③许多学者也指出,南方或该地族群所特有的如瘴气、蓄蛊、“南土卑湿”等特征,已经不是简单的疾病、风俗或气候的问题,更多的是观念问题,是主流文化圈的文化再创造。④随着南方各地区的渐次开发,瘴气、蓄蛊、“南土卑湿”等特征慢慢消失,显示的是族群边界的模糊化。⑤换句话说,在族群间存在严格的边界、族群文化尚未融合之时,一些类似气候、风俗,乃至族群的装饰、饮食、起居等可能成为相互嘲笑的把柄,目的就是把“我群”与“你群”区别开来,例如在中古之时就有“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⑥之说。而一个地方的文化由“野”变“文”,表现在服饰上,即所谓的“易椎髻为冠裳。”①
因此,在各种文献上,凡是与非汉民族有关的记载,大都带有蔑视的意味。以“溪洞”为例,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沅水》中记载:“武陵有五溪,谓雄溪、樠溪、潕溪、酉溪,辰溪其一焉。夹溪悉是蛮左所居,故谓此蛮五溪蛮也。”②古人以右为尊,以左为卑,“蛮左”显然是一种汉族对非汉民族的一种蔑称;再如宋代《岭外代答·外国门下》中载宋代钦州有“五类民”,其中俚人“史称俚獠者,此种自蛮峒出居,专事妖怪,若禽兽然。”③将“蛮”与“峒”合称,特指峒的属性是蛮夷之所;因为其“专事妖怪”,所以被蔑称为“禽兽”,恐怕是俚僚祀奉类似巫术的鬼神,被儒家正统认为是淫祀而加以排斥;宋代朱辅在《溪蛮丛笑》一书中描述西南地区仡佬村落称:“巢穴虽峙崄,中极宽广且以一处言之,仡佬有鸟落平(坪),言鸟飞不能尽也。周数十里皆腴田。凡平地曰平坦”。④这是典型的“山洞”特征,将其称为“巢穴”,显然是一种蔑称,体现了大汉族主义的民族观。可见,“山洞”不仅仅是一种居住地址,也不仅仅是一个聚落名称,还是一种对居住在该地区族群的一种蔑称。
总之,不同生态环境中形成了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在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中活动的族群,其文化特征必定不尽相同。不同文化特征的族群在接触过程中,形成了“异己”的观念,关于对“异己”的认识反过来也影响了族群之间的关系。
二、“夷夏之辨”视野下华南地区的非汉族群格局
古代华夏族关于南方族群的概念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迁。按照古代中国华夏族群观念,“中国”与“四夷”(东夷、西戍、南蛮、北狄)为“五方之民”,南方地区族群一般泛称为蛮。秦汉时期或更早,也将该地区族群泛称为越。明代学者章潢在《图书编》中写道:
秦并百郡,岭南有三郡。桂林,今广西地;南海,今广东地;象郡,今安南地也。夫自秦汉以来,所以为中国害者,北曰匈奴,南曰越然匈奴之势与南越不同,西北之国皆居中国边塞之外,有所限制,则彼不得越其界而入我内地也,惟越之地,在古种类实多,故有百越之名,曰南越,曰瓯越,曰闽越,曰东越,曰于越。其地非一处,其人非一种。①
北方民族泛称为胡(匈奴在古代归为“胡”),南方民族泛称为越,是秦汉以来的一种民族思想观。汉《古诗十九首》有“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②的记载,反映的正是当时的族群观念。以上材料也说明,即使是越族内部,因为种类繁多,称呼亦各异。隋唐以后,南方族群虽泛称为南蛮,但称呼仍然差别很大,如《隋书》说:“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疍,曰獽,曰俚,曰獠,曰狏,俱无君长,随山峒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③
唐代以后,在论述华南等地的非汉民族时,常将“深山的族群”和“水上的族群”并称,形成了一个表述的传统。如唐代刘禹锡称“闽有负海之饶,其民悍而俗鬼,居洞砦、家桴筏者,与华言不通。”④“居洞砦”指溪洞蛮夷,“家桴筏”则为水上疍民。唐代的韩愈也将这些居民合称为“林蛮峒疍”⑤;顾况《酬漳州张九使君》则写道:“薜鹿莫徭洞,网鱼卢亭洲。”“莫徭”根据刘禹锡记载,他们是一类“火种开山脊”⑥的畲田民族;卢亭则是水上居民⑦,“洞”(广义的山洞,即山中聚落)和“洲”(水边冲积地带)又分别代表两种族群所生活的地区。
这种表述影响后世对福建地区非汉民族的理解,如明初漳州府通判王祎在漳州时写下《清漳十咏》,其中一篇为:“近岁兵戎后,民风亦稍衰,番船收港少,畲酒入城迟。绿暗桄榔树,青悬橄榄枝,熏风荔子熟,旧数老杨妃。”①
作者为达到诗文的对仗工整,以“番船”对“畲酒”;但也说明了作者对漳州的族群印象中,在海为“番”,在山为“畲”的族群观念。再如清乾隆《龙溪县志》记载本地非汉居民:
南北之溪有水居之民焉,终岁舟,俗呼之曰泊水;穷山之内有蓝雷之族焉,不知其所始。姓蓝雷无土著,随山迁徙而种谷,三年土瘠则弃去,去则种竹偿之。无征税,无服役,以故俗呼之曰客,两家自为婚娶,朔望衣冠揖然,不读书,语言不通,不与世往来②
“蓝雷之族”与“泊水”应该就是后世所谓的畲与疍。到了民国时期,畲、疍仍是作为有异于当地居民的族群被记录,如民国《建德县志》称:“建德风俗之淳夙称于古,普通士夫之外别有渔户及畲客二种。其俗与地著(土著)稍异,县人均外视之。”③近代学者傅衣凌先生在《福建畲姓考》中写道:“在福建特殊部族中,畲与蜒实推巨擘,此两族其先盖同出于越。后乃辗转流布于今之闽浙赣三省边区,并深入于粤东,以其有居山、居水之异,爰分为二,实则一也。惟山居之民,在宋之前,多称为越、南蛮、峒蛮或洞僚,宋元之际,‘畲’名始渐通行。”④以上说明,各个时期的文献记载者注意到华南地区“山居”和“水居”非汉族群格局的存在。
关于南方非汉族群称呼变化不定,清人吴震方在《岭南杂记》中有深刻的理解,他写道:
獠即蛮之种,出自梁益之间,其在岭南,则隋唐时为患,然是时不言有猺,宋以后又不言獠,意其类合分无定,故随代异名。明通志凡山寇皆谓之獠,盖山寇亡命乌合,未必种传,无从究考。⑤
吴震方敏锐地观察到,每个朝代的非汉族群称呼不尽相同,其根本原因是“其类合分无定,故随代异名”,这种“合分无定”一方面由于族群融合导致族群实体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则与华夏族对非汉族群认知情况有关。正如郭志超先生所论:“中央王朝和中原人对周边少数民族的认识是随着王朝的开疆拓土和人口向周边的迁徙而增多的。大抵说来,以中原为中心,这种认识的半径的延长与时间成正比。并且,这种认识与半径长度成反比,对于越远之地的风物、族群,认识越模糊。”①另外,吴震方还指出,明代汉人将“山寇”都称之为“獠”,作者认为山寇并不一定都是“獠”的“种传”,无法考究这些乌合之众的具体族属。可见,吴氏的论述符合族群发展的客观实际,其论述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分辨族群时,不能单方面地强调该族群的血统因素,还应该分析其文化特征或社会身份,尤其要重视华夏族的族群对“异族”的认识观念。
第三节 畲族先民的族群来源与华夏族“异族”
概念的漂移
畲族的源流一直是畲族研究的重点,关于畲族的来源,各家众说纷纭,观点不一。②众多的观点中,又可以概括分为“土著说”“外来说”以及“多元说”三种。畲族的形成与发展应该是多源的,因为除了“多元说”外,“土著说”和“外来说”,都没有完全否认畲族来源的多源性③,只不过这些学说探讨多是“关于畲族的主源问题”,正如郭志超先生所说:“无论是溯源于五陵蛮,乃至东夷,还是溯源于越人,这些探讨多是关于畲族的主源问题,一般并不否认畲族的形成和发展是多源的。”④按照“多元说”观点,不论是外来的“盘瓠蛮”族群,还是闽粤土著,它们都只是形成畲族先民的一部分,这些族群与南迁汉人发生了较多的接触,互相融合后,最后在闽粤赣地区形成一个“具有稳定经济、文化特征和自我认同的新民族”,这个新民族就是畲族。①
畲族先民的族群成分具有多源性,历史上在华南地区生活着的众多非汉族群,诸如闽、越、莫徭、盘瓠(子孙)、山都木客、僚(獠)、疍(蜑)、畲(輋)、瑶(猺)②等,均是畲族先民的可能来源。这些族群在历史上因各种原因发生了变迁,一些学者通常以民族迁徙来解释这些非汉族群在某地存在或消亡的原因。③实际上,历史上一些族群的兴衰,不仅仅是族群实体人口迁移的结果,还可能是族群文化认同转变的结果。比如,一些原本文化特征存在较大差异的族群在交往过程中产生了民族融合,互相吸收各自文化,文化特征差异逐渐消失,文化认同也逐渐趋同,如历史上的许多少数民族汉化即是此例。另外,也存在一种可能:原本具有相同文化、文化认同差别不大的族群,由于坚持了不同的文化认同,从而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族群,历史上客家与畲族的分离即是此例,关于此,笔者在后文中将再作论述。
随着王朝势力进入边陲地区,唐宋以后的华南地区在族群格局和社会结构均发生了变化,占有政治文化优势的汉人逐渐扩大自己的族群势力范围,非汉人群的族群边界呈退缩状态,这种边界范围的变化不仅仅与非汉族群本身的兴衰有关,还与华夏人群心目中的异族概念向外漂移有关。王明珂通过研究发现,随着华夏的扩张,华夏边缘向外逐渐漂移,这种变迁过程借由两种手段:或者是华夏人群心目中的异族概念向外漂移,或者是非华夏人群假借华夏祖源记忆而成为华夏。④笔者以山都木客、蜑、盘瓠等族群为例,借以论证王氏之说。
一、族群格局虚幻与真实:以华安仙字潭研究为中心
1935年岭南大学黄仲琴教授发表了《汰溪古文》,开启了仙字潭石刻研究的学术领域。后世许多学者纷纷投入仙字潭石刻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成为福建古代民族考古的重要内容。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学者提出了仙字潭族属为七闽①、吴②、越③、番④、畲⑤、三苗支族后裔⑥等见解,与石刻主人发生族群关系的还有“古傣人”、夷等。由于仙字潭石刻本身对于研究华南地区族群的来源、迁徙及其文化、生活状况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加之梳理学术上与之有关的族群研究,对畲族乃至华南地区其他族群研究都有借鉴意义。因此,笔者以仙字潭石刻为研究视角,从中窥探福建乃至华南地区古代民族的若干概况。
早在1915年夏天,黄仲琴先生就乘船沿汰溪到达仙字潭实地考察,并参考大量文献后认为:“汰溪古文形有类似蝌蚪者,与近人法国牧师费亚所述苗文有相同之处,疑即古代蓝雷民族所用,为爨字,或苗文之一种。”⑦黄仲琴推断其为蓝雷畲民论据主要为:一是《唐书·舆地志》《漳州府志》《龙溪县志》《北溪纪胜》关于龙溪、柳营江等地理位置的记载;二是陈天定《北溪纪胜》关于“古称桃源,蓝雷所居”的记载;三是《平和县志》《罗源县志》猺民众“盘蓝雷”的记载;《漳州府志》《龙溪县志》、安溪《李氏家谱》讨平“洞蛮”“峒寇”苗、雷、蓝姓的记载;四是华安当地畲族分布:“今汰溪北之高层、新圩。南之归德彭水,山僻深处,犹有蓝雷遗种,自成村落,不与外人通婚,是其余胤。在唐尚盛,至今犹存,其势力远过汉之笮都诸夷。”⑧五是汰内本地乡人陈君关于古蓝雷石石蚵山洞古剑、古书传说以及汰内乡至今尚存有苗俗的巫术。黄仲琴最后推论,族群应是蓝雷族:“蓝雷钟系,或瑶、或苗,溯源不异,名称则淆,按闽南人对于蓝雷人,名之曰:‘蓝雷仔’。‘仔’者轻之之辞,盖弱小民族之称谓也。兹用其意,名本文所述之种族,曰‘蓝雷族’,以是地无盘姓也。”⑨由此可知,黄氏研究是根据文献、传说以及实地调查,目的就是为了追寻遥远的仙字潭石刻与畲族的联系。
黄仲琴教授是仙字潭石刻研究的开创者,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仙字潭石刻研究形成热潮,华安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先后于1984年和1988年整理出版两期《仙字潭古文字探索》①,共收录33篇相关学术论文;1990年,福建省考古博物馆学会编成《福建华安仙字潭摩崖石刻研究》②,收录29篇学术论文。在以往仙字潭石刻的研究中,各家学说观点不一,分歧较大。主要争论焦点在于:一是关于仙字潭石刻是文字或是岩画;二是关于仙字潭石刻的出现年代;三是关于仙字潭石刻的观念内涵;四是关于仙字潭石刻的民族族属问题,学术界已有学者对该研究进行综述③,兹不赘言。
关于仙字潭的记载,最早出自唐代张读《宣室志》,宋代《太平广记》收录该书。《宣室志》的作者张读,出生于官宦世家,系《朝野佥载》作者张鷟的玄孙。本文主要写唐代泉州一山边潭中有“蛟螭”,元和年间雷震山崩,石壁现字,有人请韩愈辨识的事。④之所以将韩愈与“蛟螭”联系在一起,是因为韩愈曾贬官于潮州,关心百姓疾苦,亲自撰写《祭鳄文》⑤后,“祝之夕,暴风震电起溪中,数日水尽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无鳄鱼患。”⑥因此,最后这些“泉人无有识”的蝌蚪篆书,在韩愈的解读下,成为“上帝责蛟螭”的内容。正如前文所分析,唐代以前,华南地区在自然生态上仍处于较原始状态,在开发自然过程中,人类在征服自然界时需克服许多困难,鳄鱼应该是其中一个例子,其他的还有大象、老虎等危险动物,或者人类将这些危险的事物投射到一些想象的事物中,如山都、木客等。到了明代,何乔远的《闽书》在记载了仙字潭所处地区“石铭里”时,引述了《宣室志》后,认为由于是“漳、泉接境,县南龙溪界域不分,古来争竞不决。”因雷雨山崩而形成几个分界的大字。⑦
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率先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①的观点,对中国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照《闽书》与《宣室志》关于“石铭里”的记载,我们也发现了文献的“层累性”。
其体现在:由“人—鳄”这对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矛盾演化为“漳—泉”界域纷争的区域社会关系的矛盾。按文中所称其矛盾主要源于“龙溪界域不分,古来争竞不决。”根据唐代《元和郡县图志》记载,龙溪县:“陈分晋安县置,属南安郡,后属闽州。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割属漳州。”②
《元和郡县图志》又载漳州:
本泉州地,垂拱二年(686年)析龙溪南界置,因漳水为名。初置于漳浦县西八十里。开元四年(716年)改移就李澳川,即今漳浦县东二百步旧城是。十二年,自州管内割属福州,二十二年又改属广州,二十八年又改属福州。乾元二年(759年)缘李澳川有瘴,遂权移州于龙溪县置,即今州理是也……管县三:龙溪,漳浦,龙岩。③
可见,《闽书》中所称“唐开元中,漳泉二州,分疆界不均”有一定的史实基础。自然地理条件是区域边界划分的首要因素。一些河流、山川成为天然的界线,成为一些地区分界的主要依据。按仙字潭处于九龙江上游的汰溪,明代陈天定在《北溪纪胜》(上四明施郡守稿并序)中写道:
北溪、九龙江,实郡右臂。唐镇府以前,插柳为营,渡江以后,揭鸿置塞外,设巡逻行台,渐次开辟,内犹山深林密,萑苻时警……初,玉钤将入龙潭,以山高涧窄,兵法所谓死地,先扎营于此,取道大山之巅,以瞰汰内。今山顶石磴尤存,揭鸿寨、营头亭在焉。④
史称陈元光“平蛮开郡……屯兵于泉州之龙溪,阻江为界,插柳为营……阴遣人沿溪而北,就上流缓处结筏连渡”⑤,其势力深入到“龙潭”以后,因为“山高涧窄”,扎营设寨,“以瞰汰内”,说明汰内(汰溪)地区处于陈元光势力与其他族群势力的交界处。按上述“大山之巅”的大山指的是位于龙溪与华安交界处的揭鸿岭。《全唐诗》收有唐代慕容韦《度揭鸿岭(漳州)》一首,其文曰:“闽越曾为塞,将军旧置营。我歌空感慨,西北望神京。”①据清代冯登府《闽中金石志》此诗出于漳州石刻,该书卷五称:“(唐代无年月的碑刻)慕容韦揭鸿塞诗刻,在龙溪岭脊。”②《舆地纪胜》则称此诗为:“唐慕容韦《葵岗岭》。”③另外在龙溪县与华安间有九龙山,是一座“岭极高峻”的大山,宋代王象之《舆地纪胜》载漳州九龙山:
《寰宇记》云“山下有水,名九龙水”,按《郡国志》云:“一名鬼侯山,北有金溪水,山中多山魈,一名羊化子”。④
可见龙溪与华安间山脉绵延,是地域之间的天然屏障。在仙字潭石刻中,有一处为后人(唐以后)用真书浅刻的文字,写着“营头至九龙山南安县界”十个汉字。可见,营头到九龙山的自然地理条件成为为漳、泉分界的重要因素。
造成“分疆界不均”,可能主要有政治区划与人文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仙字潭所在地区处于州(县)交界处;二是该地区可能存在数量不少的非汉人群即唐代以前泉漳“界域不分”是因为在龙溪地区,漳、泉政府控制能力有限,使得漳、泉政区边界飘忽不定。
一般来讲,历史上在各政区交界地区,地方政府的管控力度较弱根据唐代江南东道地理区划(见图2-1),九龙江上游的汰溪(今华安),处于泉、漳、汀三个州的交界处的附近。
明代陈天定的《北溪纪胜》(上四明施郡守稿并序)进一步说明了该区域的地理位置情况,其文写道:
梁天监间,有九龙群戏于此,故邑号龙溪,里名九龙,概称北溪。为游仙乡,宋末车驾南幸,乃改潭内为二十五都,潭外为二十三四都。大抵龙潭地处十字之中,直者为江,驾舟北入,可上宁洋;放棹南下,可抵海澄。横者为陆,循西列嶂通于南靖;徂东平畴,便驰长泰此潭以外之胜概也……地属溪之二十五都,上由永安北趋浦城出仙霞,西赴邵汀出光泽,南走天兴,每军兴多由龙潭掠舟以发。然大中小滩三十六,水石高下,不时险巇。初入小滩为马歧,唐将军牧马故处也稍上为汰口滩,汰水西汇大江,以小舟入,古称桃源洞,蓝雷所居,今号汰内。计入口十余里有平畴广原处,天宝之背,逾郡龙过脉,有间道,可通永丰司……石铭里在其东,属泰治。前行数里,居溪之西者为下樟,居溪之东者为热水地,出温泉……由此入,可缘石铭里,通泉之安溪治。①
从上可以看出,龙溪上通宁洋(漳平),下抵海澄,西列嶂通于南靖;东平畴驰长泰:再往北可通汀州、邵等地。而仙字潭所在之地“石铭里”处于漳州长泰,与泉州安溪交界,仙字潭所处的汰内盆地,三面环山,一面临江,扼安溪、龙岩交通之枢纽,有秦汉古道贯穿盆地南北,经过揭鸿岭、营头亭通往漳州(图2-2)
黄仲琴在《汰溪古文》中以推测汰溪流域附近古代可能有族群在这里居住,该文称:“汰溪之上为石蚵山。《龙溪县志》卷二云:‘石蚵山在城北四十里,高入云表,顶有粘蚵石,相传昔时海水所浸。’《志》说可证《山海经·海内南经》‘闽在海中’之语。闻之登其巅者,至今尚蚵壳弥望,既有贝类,可供食品,古代民族聚居其旁,亦理所固有也。”②
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在粤东闽南地区发现了商周时期的印纹陶文化遗存,其中以1974年在广东饶平浮滨、联饶发掘一些特征鲜明陶器和石器为最典型,③此后,地方考古工作者将此时期的闽南、粤东区域划为浮滨型文化时期④,该时期被学者认为是青铜器时代闽南地方文化最繁荣的阶段。①考古学同时还证明了九龙江流域的漳州地区,包括今天的龙溪、云霄、漳浦、南靖,平和、长泰、华安等地在商周时期有人类聚落的遗迹。②1986年,王振镛等人在华安汰内一带进行考古调查,并发现了数处青铜器时代文化遗存,在仙字潭南岸的小山丘上也采集到印纹硬陶片。③可见,在春秋以前,仙字潭地区生活着一定数量的古代族群。
唐垂拱二年(686年),朝廷在泉、潮二州之间设置漳州,这是汉人势力进入并控制漳州中心区域的一个表现。而在漳州周边一些偏远山区,仍生活着大量的非汉族群,这种现象直到南宋刘克庄时代还继续存在。一般来讲,在古代中国社会,政府通过控制区域内的人口,如将人口编入版籍,并对编户齐民征收赋税,从而实现地区的管理。而所谓的“失控”地区,常常是政府管理不到的偏远地区,这些地区或者是非汉族群,或者是“逋逃”的百姓。在唐代以前的龙溪,这里可能生活着一定数量的且政府管理不到位的非汉族群或“逋逃”百姓。随着漳州的设置以及龙溪县割属漳州,中央政府的权力由泉州至漳州,从北向南地渗透,并以漳州为据点加大周边(包括龙溪县)的控制,从而达到华夏化的过程。
通过以上分析,从“人鳄之争”到“界域纷争”实际上反映了不同时候文献关注点不同。其中也反映了在唐代以后,随着中央政府加强对南方地区的开发,原先矛盾焦点逐渐由生态矛盾转化为社会矛盾,这种矛盾是伴随着华夏化过程发生的,是华南地区族群开始整合的表现。
在清代道光年间,学者蔡永蒹④在《西山山杂记·仙字潭》一文中,引用了大量的文献材料,并根据自身考察见闻,对仙字潭进行详细的介绍。《西山杂记·仙字潭》一文分成三段,其文曰:
《闽中记》述:“南安郡西南有汰溪,古畲邦之域也。溪之上有摩崖镌蝌蚪之虫痕鸟迹,象形古篆文,自晋唐以来咸不之识焉。、晋邑欧阳詹,许谡、陈蟜、王玖、藩存实、杨在虎、谢谌、曾严、罗山甫莫能知晓焉,王翊为京兆令将拓本访之韩愈,都不之知也。武陵太守吴公瑾访之道士蔡明濬,云《古丹箓释义》:‘皇使盘瓠掌闽为七族:泉郡之畲家,三山之蜑户,剑川之高山,邵武之武夷,漳岩之龙门潭,漳郡之蓝太武,汀赣之客家,此即七闽也。七闽各有各之文字也仙字潭摩崖之石刻古文,是畲家、龙门、蓝太武三种古文,称之楔字,乃如飞云浮云焉,成舞女盘旋,武士挥刀,羽毛怪状矣。’”
《九鼎铭汉隶篆释义》云:“汰溪即古傣人之古乡,畲人有吴昱为君因争甲指之山,炎帝之世也,畲傣战争焉,傣君日超越被斩也,部众俘为馘矣,余走之滇粤。畲吴昱之世,正当炎帝之世也,洪崖先生亦此时人焉。”摩崖石刻乃商周之时畲人留伯所镌,其次露有汉文,乃汉明帝时楚王大夫少世坚摹古畲字篆刻,经畲吴昱战太君越庆功时,太母夫人称贺,太母者太姥也,摩石刻古文如舞女即蓝太武族翩翩起舞祝贺也,兽形古文龙门人之文也,余咸畲文耳”
余慕之往阅焉,此地原属南安,唐贞元时割界于武荣州漳也,后隶于华封。汰溪清碧,湾流潺潺,松青竹翠,面幽静也。古文不剥落,见者疑之矣,然则《闽中记》迄今亦千年矣,未可为不信也。据《古丹箓释义》云:“炎帝之世,傣君超越无道,畲吴昱战越,斩越首,俘越属,傣余越走滇。龙门、蓝太姥朝贺,洪崖刻石以纪事焉,盖迄于今五千载矣,古文若九鼎铭也,世之名家难识之矣。”宋《桑莲诗集》有汰溪诗,曰:“汰溪上古在南方,仙字奇书千古昂;韩愈难明斯怪字,书风书穗不成行。”《紫云诗集》:“仙字风云变化文,畲君伐越竟超群;傣溪陈迹万年事,摩石刻崖宝不乡。”《安仁诗抄》云:“傣人古国汰溪滨,吴越春秋炎帝人;镌石古文东汉刻,千年万载记荆榛。”《仁和诗集》云:“傣越畲吴史不存,惟看石刻古文言;当年争国斯溪地,纪事闽中有七番。”《青阳诗集》云:“畲王吴昱傣王番,太姥龙门蜑户藩;武口口口口口客,汰溪其地古闽蜿。”①
作者前两段主要引述《闽中记》《古丹箓释义》《九鼎铭汉隶篆释义》,后一段说明亲临现场查看,并引用《古丹箓释义》《桑莲诗集》《紫云诗集》《安仁诗抄》《仁和诗集》《青阳诗集》等文献,目的在于说明以下内容:其一,汰溪的古篆文内容晋唐时人都不识得,有个到京兆当长官的将拓本送到韩愈处,韩愈也不认识,这与张读《宣室志》所载内容有冲突;其二,有道士蔡明濬根据文献解读,认为仙字潭摩崖石刻是畲家、龙门、蓝太武三三种古文,又称楔字:其三,汰溪原来是“古傣人”居住的地方,后来在商周之时发生畲傣战争,傣人败逃滇粤。当时有蓝太武、龙门等部族前来祝贺,洪崖、畲人留伯刻石庆功,于是石刻上留下的是畲家、蓝太武、龙门三种古文;其四,当时福建有“七闽”,分别为:泉州的“畲家”,三山(福州)的“蜑户”,剑川(南平)的“高山”,邵武的“武夷”,漳岩(漳平龙岩一带)的“龙门潭”,漳郡(漳州)的“蓝太武”,汀赣(汀州、赣州一带)的“客家”,这七个族群(七闽)都为盘瓠所管辖。
《西山杂记·仙字潭》对古代福建的族群格局做了介绍,但是,其中有许多与史实存在不相符的情况,笔者拟对该文所反映的一些材料和观点进行辨析。
(一)蔡文所引的《闽中记》并非都出自于《闽中记》
蔡文称:“《闽中记》述‘南安郡西南有汰溪,古畲邦之域也’。”其并未指出《闽中记》何人所作。实际上,在唐代以前,福建先后出现关于两部名为《闽中记》的方志,宋代梁克家的《淳熙三山志》序中记载:
予领郡暇日,访无诸以来遗迹故俗。闻晋太康既置郡之一百一十三年,太守陶夔始有撰记,又四百五十六年至唐,郡人林谞复增为之,皆散佚无存者;独最后一百九十二年,本朝庆历三年,郡人林世程所作传于世,自言视前志颇究悉。①
东晋太元十九年(394年),陶夔担任晋安郡守②,随后撰成的福建首部方志《闽中记》。唐大中年间(847—860年),林谞修撰了另外一部《闽中记》,《八闽通志》载其事:“林谞,闽县人。博学,善讲贯,属文尤美。初尝俯从乡举,竟养高不仕,搜寻异闻,作《闽中记》十卷。”③以上两部《闽中记》均已散佚,后世仅存的佚文,散见于《太平寰宇记》和《三山志》等文献中。
蔡文所指的《闽中记》应为唐代林谞作《闽中记》。从南安郡设置时间年代看,可以排除东晋陶夔《闽中记》的可能性,该书比南安郡设置时间早了170余年。历史上有数个地名称为南安郡,按以上所称《闽中记》述南安郡之事,应该指的是福建境内的南安郡。宋代《舆地纪胜》记载:“南安郡,陈属闽州,在永定元年。后属丰州。光大元年(567年),陈文置南安郡……隋文平陈郡废属泉州。”①可见南安郡为南朝陈光大元年(567年)设置。其辖境相当于今晋江、九龙江、木兰溪三流域及同安等地,后于隋开皇九年(589年)废。其次,从文中记载的内容看,其提及的欧阳詹、韩愈等均属于唐代之人,因此,只能是唐代以后的文献记载唐代之事。然而,蔡永薕文中所引内容有些却非《闽中记》所载。首先,蔡文称:“《闽中记》述:南安郡西南有汰溪,古畲邦之域也。”如果按照文献以今溯古的表述方式,其潜台词似乎可以理解为:“《闽中记》述:(今)南安郡西南有汰溪,古畲邦之域也。”按此理解的话,《闽中记》或许在记载撰写时所发生的事。唐林谞作《闽中记》时,南安郡名已废止近300年。按“汰溪”位于九龙江上游,其时属龙溪县。唐代《元和郡县图志》载龙溪县隶属州郡变化为:“陈分晋安县置,属南安郡,后属闽州。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割属漳州。”②如果是林谞《闽中记》记载“汰溪”,合理的表述方式是:“漳州西北有汰溪”,而非“南安郡西南有汰溪”。
文中称汰溪是“古畲邦之域也”,这与史实不符。一般来讲,“畲”作为族群称谓,直到南宋后期的文献才有记载。因此,不论是东晋陶夔的《闽中记》,还是唐代林谞的《闽中记》,都不可能有此判断。
文中称“汀赣之客家”为“七闽”其中的一族,这也与史实不符。“客家”作为族群称谓不可能出现在唐代,谢重光先生认为,“客家”族群在移民过程中,由于族群间互相隔膜和互相歧视,产生了“客家”或“客民”“客仔”的称谓,这种称谓与“畲客”“山客”有渊源关系,其最早出现的时间大约明中叶嘉靖年间。③其他学者如曾祥委④、刘镇发⑤、刘丽川⑥也对“客家”称谓出现的时间进行讨论,其观点不一,但均认为“客家”出现于明清以后。⑦另外,客家在汀赣地区形成不可能早于唐代。
综上几点,可见蔡永薕所引的《闽中记》与事实出入较大,究其原因,第一是历史上的两部《闽中记》均已散佚,蔡永薕所引的《闽中记》可能非原著内容;蔡永薕在《西山杂记》写作过程中,除了引用古籍文献,还加入个人的想法,所谓的畲家、客家均有可能是作者根据传闻记载,当作《闽中记》内容。
(二)蔡文所称福建族群格局和族群关系与史实有误
首先,历史上的“七闽”并非蔡文所称的“七闽”。七闽,最早出现于《周礼·夏官·职方氏》,其文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贾公彦疏:“叔熊居濮如蛮,后子从分为七种,故谓之七闽。”一般认为,福建在春秋之时是七闽所居住的地方,宋欧阳忞《舆地广记》卷三十四在论述福建路各州历代地理沿革均表述为“春秋时为七闽地”。①宋祝穆《方舆胜览》引《职方氏》注“七闽”云:“闽子孙分为七种,故曰七闽”。②朱维干认为:“七闽”指的是闽越之前的今福建和粤东潮州、梅州地区(可能还包括浙南的瓯江流域)的七大土著部落。③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早已存在“七闽”的称谓,一般认为是生活在闽浙的数个部族。
其次,蔡文中所称的“皇使盘瓠掌闽为七族”中除了畲家、客家、蜑户在唐代以后有其民族实体,其他均为传说或传闻的部族。正如前文所论,畲家、客家不可能出现在唐代文献中。而实际上,“蜑”在魏晋南北朝时主要指西南非汉人群,直到隋唐以后才慢慢指南方非汉族群。“蜑户”作为族群称谓,直到宋代才出现,关于“蜑”的考证下节进一步论述。
再次,“武夷”“蓝太武”等古代部族是蔡永蒹根据文献材料进行整合,填充进“七闽”的概念中。“武夷”“蓝太武”都是传说中的部族。关于武夷的来源,有几种说法:一种“夷落”说,即闽地部族,宋代朱熹在《武夷图序》考证武夷君来源时说:“武夷君之名,著自汉世,祀以乾鱼,不知其何神也……颇疑前世,道阻未通、川雍未决时,夷落所居,而汉祀者即其君长。盖亦避世之土,为众所臣服,没而传以为仙也。”④朱熹怀疑,古时“道阻未通、川雍未决”时,武夷山地区为“夷落所居”,其君长就叫武夷君,武夷君可能是闽地氏族首领,死后被奉为仙;另外一种传说是彭祖居武夷山,生二子,长子名武,次子名夷,当地后裔就是武夷。
蓝太武也是传说中的部族。宋代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二八载:“太姥山三十六峰,在长溪县。王烈《蟠桃记》:‘尧时有老母,以蓝染为业,后得九转丹砂法,乘九色龙而仙。汉武时,名曰太姥山,凡有三十六奇。’”①
太姥山旧属长溪县,后属于福鼎县,乾隆《福宁府志》记载福鼎山川时称:“太姥山,在八都,旧名才山,相传尧时太姥业蓝处。”并注释曰:“汉武帝命东方朔授天下名山文,改母为姥。”②按古代太和大相通,“姥”与武、母同音,所以太姥,也称太武、大武、大母等。《舆地纪胜》又载:“大武山,蔡如松《十辨》云:‘去漳州二百八十里,东临大海,有大武山……大武夫人坛,古《图经》云:‘大武夫人者,闽中未有生人时,其神始开创土宇以居人也。’又名太武山。”③
《八闽通志》有相同记载,并称:“旧亦名大母山。”④传说中闽中还没有人类之时,大武夫人“拓土以居民”,类似某地的始祖。可见,蓝太武在福建许多地方都存在。卢美松先生据此认为,远古时期,闽东北存在着以太姥(母、武)为首领的母系氏族社会。太姥夫人的部族是闽族的先民,他们与后世的山越、畲族有渊源关系。⑤应该来讲,武夷、蓝太武是后世传说中福建古代的部族,传说的成分大于历史的真实。另外,关于“剑川之高山,漳岩之龙门潭”,其文献记载阙如。高山应该与现在所称的“高山族”没有直接关系,“高山族”的称谓是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大陆地区对台湾少数民族的称谓。1953年由国务院正式采用并公布高山族这一名称。⑥
笔者推论蔡文中提到的高山、龙门这两个部族应该同武夷、蓝太武一样,是传说或传闻中的族群。然而,在唐代以前历代文献关于福建民族记载,基本上以“闽”“越”“蛮”等称谓,基本上是泛称,这与中原汉人对福建非汉民族的认识过程是相符合的。而蔡文中所称的“七闽”分布于福建七个州(县)中,这在古代族群认识中是不可想象的。实际上,直到民国时期,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还认为福建人不好了解,他说:“吾侪研究中华民族,最难解者无过福建人。其骨骼肤色似皆与诸夏有异,然与荆、吴、苗、蛮、氐、羌诸族亦都不类。”①
笔者认为,蔡永蒹之所以将族群地域分得这么细,最大的可能是恰好汰溪处于漳泉交界,附近刚好有三个族群:泉郡之畲家、漳岩之龙门潭、漳郡之蓝太武,于是得出畲人打败傣人,龙门、蓝太武相贺,石刻上留下的是畲家、蓝太武、龙门三种古文的结论。
陈国强先生对《西山杂记》进行解读时曾指出,尽管《西山杂志》所载之事与史实不尽相符,但是“民间口碑传说往往是真实历史的反映,可提供我们研究史实的线索。”②王明珂也指出,一定文本的产生有其特定的社会情境和历史心然性。蔡永蒹《西山杂记》所载的族群情况,实际上,反映了明清以来知识分子对福建古代族群的认识,这种认识是基于一定历史的事实作为基础,即:历史上福建等地区存在着多种非汉族群,这些族群或许与畲族多多少少存在关系。
二、“山都”“木客”族群边界的移动
汉晋以来,文献记载闽粤赣地区还存在一些被称为“山都”“木客”的非汉族群。汀州等地被认为有“山都”“木客”存在,如《太平寰宇记》引《牛肃纪闻》云:“江东采访使奏于虔州南山洞中置汀州。州境五百里,山深,林木秀茂,以领长汀、黄连、杂罗三县,地多瘴疠,山都木客丛萃其中。”③
乾隆《汀州府志》论汀州地理气候时,引宋代《舆地纪胜》关于山都及其种类的描述,该文称:
郡距江、广,复岭重岗,旧传为山都所居(《舆地纪胜》云:造治初,砍大树千余,其树皆山都所居。有三种:下曰猪都,中曰人都,其高者为鸟都。即如人形而卑小,男、妇自为配偶。猪都皆身如猪;鸟都人首能言,闻其声不见其形;人都或时见形。当伐木时,有术者周元大,能禹步为厉术,以左合赤索围木而砍之。树仆,剖其中,三都皆不能化,执而煮之于镬内)。①
关于“山都”“木客”,陈国强认为“山都”“木客”既不同于越或山越,亦与畲族有别,而属于古老的南方“尼格利陀”即“小黑人”之种;②蒋炳钊将“山都”和“木客”视为一种古老土著民族,是属于古代越族的后裔。③黄向春认为前人的重点考证“山都”“木客”是或者不是某一“民族”或其族裔,而忽略了产生“山都”“木客”的历史背景,他认为“山都”“木客”是在一种特定的社会情境和话语氛围中所书写的,是人们将某种危险意识投射于某种“异类”,是想象之后的产物。④笔者认为,黄氏的论断颇有可取之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山都”“木客”常常具有一些异于常人的神异特征,另外,解释了随着中原王朝对南方族群认识的深入后,“山都”“木客”渐次消失。根据郭志超研究,“山都”见于方志、文集的准确记载,始于西晋,频见于唐宋,依稀见于明清。记载较多是赣南、闽西,其次是粤东。⑤靳阳春进一步研究,认为“山都”“木客”在闽粤赣文献出现时间顺序与中原王朝疆域的开拓时间顺序相一致。⑥随着中央政权在闽粤赣交界地区扩展,在唐以后,闽粤赣交界处的“山都”“木客”基本就消亡了。①从“山都”“木客”的记载情况,可以认为:西晋至唐,闽粤赣地区存在汉人与“山都”“木客”的族群边界,“山都”“木客”进入主流文化圈的视野与汉人边界扩张有关,这条族群边界呈现由北往南移动的趋势。
应该来说“山都”“木客”尽管带有神秘性,甚至有些类似于神话。在南方地区开发过程中,类似“山都”“木客”的形象在文献中仍多有出现。如《太平寰宇记》记载在尤溪幼山地区有一种类似狒狒,名为“山魅”“山魈”“山大人”的野人:
幼山,在县西北一百二十里。乃龙峡之地。孤峰上耸三十余里,周迴二百余里。山上有松、桧、竹、柏,其中有山魅,其形似人,生毛黑色,身长丈余,逢人而笑,口上唇盖眼,下唇盖胸,人见亦怪矣。或时遗下藤制草鞋,长二尺五寸,乡人所谓山大人。又云山魈,或野人也,尔雅云:“狒狒如人,被发迅走,食人。”即此也。②
除了官方史籍外,在民间传说中也常有类似“山都”“木客”的记载,如闽西一些族谱记载本族先人来到闽西时,曾受到一些“异物”“妖类”的困扰,光绪《上杭中都叶氏族谱·五郎公传》记载道:
(五郎)公生于元初,由汀州府长汀县官(馆)前湖坑徙至上杭中都古坊开基,为一世。尔时,林树阴翳,人烟稀少。凡虫蛇鸟兽、异物群妖类皆杂处于此,而人之受其害者不可胜道。其间有樟树妖精最为恶毒,每年要残食数人以肥其身,邻里相以悲啼,共叹何日能除此害。③
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叶姓族人迁徙到上杭时,此地应是比较蛮荒之地,不仅多有虫蛇鸟兽,而且“异物群妖”杂处,而樟树妖精因食人而成为祸害百姓最厉害的一种。这种类似神话的民间传说,其隐含的真实历史背景是:在华夏化进程中,外来移民在较为恶劣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中,与土著相遇并发生矛盾,这些外来的移民开始想象和建构“异类”,通过夸大文化差异的叙事方式,树立起一个“非人类”的对立面。
三、“蜑”族群边界的移动
“蜑”最初也称“诞”,后来还有蜒、疍、蛋等同音同义异体字。历史上专指长江流域蜑民和南方沿海地区蜑民,二者属于不同族属,没有血缘关系,“蜑”也与“蛮”合用,“蛮蜑”泛指各类非汉人族群。①作为族群名称,其最早出现于西南地区,时间不晚于汉代。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就载:“(涪陵郡)土地:山险水滩,人戆勇,多獽、蜑之民……汉时,赤甲军常取其民,蜀丞相亮亦发其劲卒三千人为连弩士。”②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蜑”用来泛指长江流域地区的非汉民族,如《隋书》说:“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疍,曰獽,曰俚,曰獠,曰狏,俱无君长,随山峒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③又称:“长沙郡又杂有夷蜒,名曰莫徭,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为名……武陵、巴陵、零陵、桂阳、澧阳、衡山、熙平皆同焉。”④
此时,南方一些非汉民族也被泛称为“蜑(蜒)”,如韩愈记载的“贞元末……岭外十三州之地,林蛮洞蜒,守条死要,不相渔劫,税节赋时,公私有余。”⑤再如柳宗元的《岭南节度飨军堂记》记载到:“延群僚……卉裳罽衣,胡夷蜑蛮,睢盱就列者千人以上。”⑥胡、夷、蛮、蜑均是非汉民族的泛称,这里的“蜑”主要指南方地区少数民族。
宋代许多文献开始用“蜑”来专称“水上居民”,如《后山谈丛》解释:“舟居谓之蜑人”⑦;《桂海虞衡志》则称:“蜑,海上水居蛮也。以舟楫为家,采海物为生,且生食之。”⑧《岭外代答》则称:“以舟为室,视水为陆,浮生江海者,蜑也。”⑨“蜑户”作为族群称谓,最早出现在北宋《太平寰宇记》中,其文称:“蜑户,(新会)县所管,生在江海,居于舟船,随潮往来,捕鱼为业,若居平陆,死亡即多,似江东白水郎也。”①
根据对“蛋”的出现时间、地点,以及其所指代的族群的不同,我们认为:随着中原地区汉人势力慢慢向边陲渗透,华夏边缘也由北往南移动,汉人常常以一些旧有的族称,用以称呼一些新发现的非汉族群。这些族称通常作为蔑称,中原华夏人以正统文化自居,对边陲非汉人群贴上标签,以此作为区分华夷的族群边界。
四、“盘瓠子孙”族群边界的移动
盘瓠,也作槃瓠,后世的畲族族谱中也有写作“盘匏”的。盘瓠传说是南方族群重要的研究内容,一些学者认为,正是因为有着共有的盘瓠信仰,使得畲族与苗、瑶等民族可能存在某种亲缘关系。②
盘瓠传说在广大南方地区分布,一方面是随着盘瓠蛮的南迁,盘瓠传说也由荆楚地区向西南、华南等地区传播;另一方面,华夏人群对其他非华夏人群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正如上文所述的“蛮”“蜑”也是一个不断被发现、被冠名的过程,有关“盘瓠”出现的时间与地区的开发顺序有着特定的关系。也就是说,盘瓠信仰固然与蛮族南迁有关系,也与华夏心目中“盘瓠”概念南移有关系。
关于盘瓠传说系统论述,最早见于南朝范晔的《后汉书·南蛮传》,其资料来源主要来自于东汉应劭的《风俗通》、曹魏鱼豢(生卒年待考,三国时期曹魏国郎中)的《魏略》、晋代干宝的《晋纪》及《搜神记》等书。近代以来,一些学者对盘瓠进行考证与解读,陈登原先生是其中一位较早对盘瓠研究的学者。他在《国史旧闻》第一册中“槃瓠”条详细考证了槃瓠的渊源流变,并在结尾处论述道:“槃瓠之说,虽曰生于东汉之季,起于荆湖之区,贵州、四川、云南、福建、浙江、广东、广西亦皆有之,是其分布,已达八省之多。若依《续云南通志》所谓‘楚、粤、黔皆有之’,则是湖北亦当有此传说。然则槃瓠一事,应劭初记,范晔集成,至于近世,尚不失为南方九省之大掌故也。至于此事,自属荒昧之记。如太昊蛇形,炎帝蛇首(原注:《北堂书钞》卷一),汤之先世,出于燕卵(原注:《诗·玄鸟篇》郑氏注),可知即在汉族,固亦往往而有,存而弗论可也。”①
在这段文字中,陈登原先生表达了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认为槃瓠之说起源于东汉的荆湖地区,至今在广大的南方地区仍流传着;二是认为槃瓠传说虽然荒诞不经,但即使是汉族,也流传着类似的、同样是异于常理的祖先传说。
实际上,盘瓠传说出现的时间可能早于东汉时期,最早出现的地点也非荆湖地区,而可能在中国的西北地区。晋代郭璞在为《山海经》作注时,将狗封国与盘瓠联系起来,他写道:“昔盘瓠杀戎王,高辛以美女妻之,不可以训,乃浮之会稽东海中,得三百里地封之,生男为狗,女为美人,是为狗封之国也。”②郭璞在其《玄中记》中也有狗封国氏与盘瓠之说的记载,与上述内容相近③。狗封国在《山海经》中又作犬封国,《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有人曰大行伯,把戈。其东有犬封国……犬封国曰犬戎国,状如犬。有一女子,方跪进柸食。”④
犬戎一般作为西北地区非华夏人群的称谓,而根据郭璞注释,“狗封之国”可能在“会稽东海中”,二者在方位上似乎存在矛盾。袁珂先生在《山海经校注》中作出解释称:“封、戎音近,故犬封国得称犬戎国。又‘犬封国’者,盖以犬立功受封而得国,即郭注所谓‘狗封国’也。伊尹四方令云:‘正西昆仑狗国。’淮南子墬形篇云:‘狗国在其(建木)东。’则狗国之传说实起源于西北然后始渐于东南也。”⑤
侯绍庄支持盘瓠传说最早起源于西北戎狄的观点,并指出:在春秋以前,盘瓠与江汉地区,特别是“武陵”或“五溪”地区居民的民族成分没有关系。⑥关于海上有“狗国”的传说,在后世的一些史料中仍有记载。如《梁书》记载道:
天监六年(507年),有晋安(晋安郡,晋武帝太康三年置,治在今福建闽侯县东北,笔者注)人渡海,为风所飘至一岛,登岸,有人居止。女则如中国,而言语不可晓;男则人身而狗头,其声如吠。①
而到了魏晋以后,文献中的盘瓠传说出现之地主要集中在长江中游地区如晋代干宝的《搜神记》称:“盘瓠死后,自相婚配,因为夫妇……即今梁、汉、巴、蜀、武陵、长沙、卢江郡蛮是也”。②干宝在《晋纪》中又称:“吴武陵蛮叛。武陵、长沙郡夷,盘瓠之后也,杂处五服,凭土阻险,每常为猱杂鱼肉而归以祭盘瓠。”③
郦道元《水经注》、范晔《后汉书》也均称武陵、长沙蛮夷为盘瓠之后。④盘瓠传说在汉魏以后已经从西北地区转移到长江中游的武陵、长沙等地区,说明在此之前,盘瓠之说可能经历了一个自西往东的一个变迁过程。
盘瓠传说的转移,有三种可能:一是长江中游等地区的“蛮”族与“犬封国”“犬戎国”有族源关系,作为一种文化传统随着族群的迁徙而向外流传;二是西部地区的“犬戎国”经过文化互动,将盘瓠传说直接传给武陵地区“蛮”族⑤;三是随着华夏化进程加深,中原华夏对南方“蛮”族有更深入的接触,从而将“盘瓠之后”这种非我族类概念转移到武陵地区,即盘瓠传说与华夏族群心目中异族概念的向外移动有关。王明珂还认为:“在魏晋时,湘西一些本地豪强由中国文献记忆中认识‘盘瓠’,因此以‘有功于中国’的盘瓠子孙自居。”⑥
汉晋以后,随着南方苗瑶语诸族华夏化进程加快①,华夏族群心目中的“盘瓠子孙”的地理人群范围往更南方扩延。南方非汉族群之所以自称是“盘瓠子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接受自身相对于汉的劣势族群地位”;另一方面“以此神圣化始祖来凝聚邻近各族群”。②唐宋以后,被称作“盘瓠子孙”的人群向南方扩延的趋势更加明显。王明珂认为,这些盘瓠子孙的在广大南方地区分布,并不是这些“蛮夷”往南迁徙,而是后来华夏开始称广西、贵州等地丘陵山地聚落人群为“猫”“猺”“獞”,并认为他们是由两湖扩散、迁移来的“盘瓠子孙”。③盘瓠种成为南方非汉族群的一种泛称,如南宋叶钱为《溪蛮丛笑》所作的序称:“五溪之蛮皆盘瓠种也……今有五:曰猫、曰猺、曰獠、曰獞、曰乞狫”。④
而从宋代开始,猫(苗)苗人、猫、猺等族群称号,也普遍被华夏族用来称呼南方各非汉人群。⑤如南宋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称:“猺本盘瓠之后,其地山溪高深,介于巴蜀、湖广间”。⑥清初的闵叙所著的《粤述》称:“百粤诸蛮,丑类至繁,然大要不出猺、獞二种,皆盘瓠后也”。⑦清康熙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诸蛮种落不一,皆古槃瓠之种也。”⑧可见,“盘瓠”传说不仅流传地域广,而且有多元的族群视其为共祖,有着相同的或相似的祖源记忆,许多文献将百越、诸蛮统称为盘瓠之后。而实际上,并非所有的南方蛮族均是盘瓠子孙,也并非所有具有盘瓠传说的族群均是盘瓠蛮南迁的结果。或许可以认为,将南方各蛮族视为盘瓠之后,只是华夏族民族观念在“异族”中的其中一个体现而已。如魏晋以后盘瓠在武陵地区盛行,明清以后,盘瓠传说在该地区反而不流行,而转向西南或东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这也说明华夏边缘漂移的可能性。
总之,盘瓠传说可能产生于战国以前的西北地区,汉晋以后转移到长江中游地区,唐宋明清以后广泛流传于南方各省区。关于这种变化,除了盘瓠子孙确实南迁外,汉人的认识或者南方少数民族借用盘瓠传说应该更值得信赖。
第四节 宋代“畲”汉族群边界的形成
族群边界既是自然生态、族群迁徙的客观结果,同时也是一个主观建构、文化再造的结果。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贴上族群标签,其目的在于通过对“他者”的建构来强化对“自我”的认同,从而实现资源的争夺①。宋代时期,“畲”汉边界形成,这种边界的划定,是“畲”汉人群集体意识的结果。
一、唐宋时期南方汉族文化认同的增强
在唐宋以后,关于南方地区“莫徭”“峒蛮”“蛮僚”的记载日益频繁见诸史料,这既体现华夏族对“他者”认识的加深,同时也是说明南方地区汉人意识的觉醒。这种意识的觉醒,体现在一些族群的形成与发展上,如谢重光先生指出,随着中原汉人的南迁,到了五代宋初,在漳、泉二州已经形成了福佬族群。②与中原汉人同时南迁的还有而五溪地区的盘瓠蛮,这些族群“向南又折而向东迁徙”③,逐渐分布于今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广大地区,并与闽越土著及南迁汉人产生互动与交流。以上三类族群被认为是组成畲族先民的重要来源。
南方地区汉人与非汉人群的互动,既有族群间的合作,又有族群间的冲突与对抗,唐宋的一些文献记载说明了这点。如《资治通鉴》记载道:“(昭宗景福元年)王潮以从弟彦福为军统、弟甚至为都监,将兵攻福州。民自请输米饷军,平湖洞及滨海蛮夷皆以兵船助之。”④
学者一般认为“平湖洞蛮夷”就是畲族先民⑤,滨海蛮夷则应为“蜑民”。这些“洞蛮”以兵和船的形式,为以王潮为代表的汉族势力提供了帮助。再如景福二年(893年),汀州盘瓠蛮酋“钟全慕举籍听命,岭海间群盗二十余辈皆降溃,潮乃尽有五州之地。”①则说明了一些蛮夷归顺了朝廷,成为中央王朝治理地方的合作者。这种合作间接地说明了南方汉族势力的逐渐增强。
南方汉族意识的觉醒还体现在当地汉人对祖居地的解释和建构上《太平寰宇记》在记载“永泰县”时称:“《晋安记》:‘东晋永嘉之乱,渡江衣冠士族多依于此,以求安堵’。当此之时必有县,后人或更改,图未甚详悉。”②
乐史根据《晋安记》的记载,对“晋人衣冠南渡”这一历史事实做出推论,认为当时南迁汉人在南方一些地区建立州县,只不过因为建置沿革变迁或记载不详而未能使县名存留于世。这种说法在宋代以后的南方地区颇为流行。“衣冠南渡”成为一种当地汉人祖源历史记忆,并作为文本在福建等地的文献中出现如乾隆《福州府志》引宋代路振的《九国志》称:“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黄、陈、郑、詹、邱、何、胡是也。”③《八闽通志》卷之三《地理》风俗引《建安志》称建宁府:“自五代乱离,江北士大夫、豪商巨贾,多逃难于此,故云云。”④
王明珂先生指出,一定的历史记忆产生于特定的社会情境中,而这种社会情境又与当时的历史心性息息相关。⑤因此我们认为,隋唐以后南方蛮族记载的增多以及汉人祖源地传说的建构,均是在南方地区汉人势力崛起这种社会情境中产生的。
唐宋或更早时期,华南地区处于帝国的边缘,这种边缘性不仅反映在政治地理上,更反映在文化阶序上。随着汉族势力在南方地区的增强,处于帝国边缘地区的南迁汉族或当地汉族土著为了提升自己的族群身份,往往对本族的历史进行建构。上述所举例子说明,当地汉人希望通过回忆或者建构类似“衣冠南渡”的历史来增强华夏认同,从而提升本地汉人的族群地位,并在资源竞争中取得优势。在汉人心目中,早在汉晋时期,本族群的祖先就来到包括福建在内广大南方地区,这进一步证明本地汉人在此地开发、经营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汉人增强文化认同主要通过两个手段:
一是建构自己的“汉人”身份。如帝国的华夏化进程中,地方土著积极向汉族或中原王朝靠拢,如积极协助政府在南方地区建立政治机构,“请书版籍”,成为政府的编户齐民后,意味着族群从“化外”向“化内”转变;再者就是通过“攀附”的手段对先祖进行建构,将本家族的迁居地、迁居祖先与中原发生联系,向本族和外界宣称“黄帝后裔”的中原正统身份。
二是与“蛮夷”划清界限。如在宋代开始,陈元光家族被描述为来自光州固始,且受命于朝廷“平蛮”的中原正统家族。一些非陈姓的汉人,通过建构本族为陈元光“部属”的历史记忆,说明本族与陈元光家族一样,均是中原正统身份。这种历史记忆间接反映了宋明以后,闽南等地区汉人意识的觉醒,他们希望通过将本族群与当地蛮夷截然区分,从而建构其本族非蛮的历史逻辑。
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的文献对陈元光记载甚多,陈元光因此被认为是开发漳州的重要人物,以致后来被人们尊奉为开漳圣王,成为流行于闽台诸省重要神明。而实际上,陈元光在唐代的形象与后世的形象相差较大,其中经历了一个历史人物建构的过程,而这种建构与闽南地区的汉族认同有特别大关系。唐代对陈元光的记载不多,目前所能发现的关于陈元光事迹的文献记载为张鷟的《朝野佥载》,其文称:“周岭南首领陈元光设客,令一袍袴行酒,光怒,令曳出,遂杀之。须臾,烂煮以食客,后呈其二手,客惧攫喉而吐。”①
作者张鷟的生卒年不详,但生活年代与陈元光相差不远,其所载的关于陈元光内容,纵使不一定是历史事实,至少反映了时人对陈元光其中一个印象的理解。作者将陈元光这种残暴的性格特征与岭南首领相联系,反映的是北方汉人对南方土著的印象。宋代《太平广记》在引用以上史料时,特意将其置于“酷暴”一节之中。②可以说,唐代时期对陈元光的记载不多,且较多为负面形象。从宋代起,漳州地区开始流传陈元光平贼立功的传说,并建庙对其奉祀。宋代漳州令吕璹有诗写道:“当年平贼立殊勋,时不族贤事忍闻?唐史无人修列传,漳江有庙祀将军。”③
前文已经说明,宋代时期福建等南方地区汉族意识逐渐增强,塑造陈元光平蛮的形象就是将本族群与“蛮”相区别,借以证明自己的正统身份,这应该是
陈元光形象塑造的滥觞。而后,到了明清时期,各种方志、族谱不断塑造陈元光的光辉事迹①,兹不赘述。
由此可见,从唐到宋,及至明清,陈元光的形象逐渐丰满,并以将军、儒士、神明等形象最终出现在人们面前,这是一种不断层累、“枝叶其说”的历史建构过程。这种建构的力量来源于闽南等地汉人文化认同的需要。
苏永前通过人类学视野对陈元光“开漳”传说进行分析,他认为该传说的叙事主体为闽南地区中原移民,而传说的产生与传播则是该族群文化认同的主观结果。这种认同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对自我的“圣化”和“神化”,另一方面是对他者的“非人化”与“妖魔化”。②由此可见,将本族与“蛮夷”区分开来,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证明本族群的纯正中原血统身份,这是一种主观认同的表现。
除了陈元光家族外,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为宁化巫罗俊家族。黄向春根据杨澜的《临汀汇考》中有关隋唐之际巫罗俊“请授田”的记载,说明当时出身“蛮夷”的地方豪酋通过与官府的相互利用与合作而进入正统社会的主体之中,成为南方汉人的重要来源及汉人社会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力量。③
黄氏所引的《临汀汇考》关于巫罗俊事迹的记载,基本上沿用李世熊修所纂的康熙《宁化县志》,较原文略有出入④。而巫罗俊的事迹则是来源于巫氏家谱,清代王捷南称:“明李世熊《答巫以侯书》辨巫罗俊事颇详。书言谱修于明初,旧志盖据巫氏谱也。”①除了《宁化县志》的记载外,巫罗俊不见于其前诸史籍。以明初族谱记隋唐之事,显然不能当做历史的真实。笔者推测,巫罗俊传说本质也同陈元光传说一样,都是对祖先的历史记忆的重构,目的在于创造与汉人正统性的连接。②
二、标签化与作为族群文化特征的“畲”
刘志伟通过对清代以后珠江三角洲沙田区和民田区研究后发现:二者“并不简单地只是土地自然形态的差别,实际上是在地方社会历史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经济关系、一种地方政治格局、一种身份的区分,甚至是一种‘族群’认同的标记。两个区域之间,除了自然形态的差异外,更存在一种独特的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③就此而言,畲田经济与农耕经济在某种程度上,也不仅仅是经济形态的区别,其中暗含着一种社会阶序、族群格局。确切地说,在华夏民族观念中,从事畲田的族群是不受王化的“非我”族群,而实行农业的则是王朝子民,二者存在着明显的“华夷之别”。将某一类族群归为“异类”,意味着其无法与华夏族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源享有同等地位。在唐宋时期,“畲”作为一种族群标签,充当了“异类称呼”的角色,这种贴标签的过程是伴随着华夏族的族群认知一起进行的。
在隋唐以前,由于南方开发缓慢,作为一种耕作方式“火耕”“水耨”等词语常用于表示一个地区经济落后、蛮荒化外、教化不及的状态。如《史记·平准书》载:“江南火耕水耨,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④《汉书·武帝纪》:“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⑤《汉书·地理志》又载:“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⑥,《盐铁论·通有》云:“荆、扬……伐木而树谷,燔莱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广而饶材。”①《晋书·食货志》:“江西良田,旷废未久,火耕水耨,为功差易。”②《隋书》:“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湿,无有蓄积之资。诸蛮陬俚洞,沾沐王化者。各随轻重,收其赎物,以裨国用。”③有的记载甚至直接将“火耕”“水耨”等耕作方式认为是蛮獠的习俗,如《唐大诏令集》载:“闻岭外诸州,居人与蛮獠同俗,火耕水耨。”④按照文中意思,“居人”相对于“蛮獠”,应该是汉人;“火耕水耨”是“蛮獠”的风俗,汉人在耕作方式上被同化了。
有的甚至引用春秋以前的休闲耕作制度来形容一个地方的未开发程度,如万历《古田县志》记载如下。
林谞《闽中记》:开元二十八年,都督李亚丘会溪峒逋民刘疆辈千余计归命向化,乃状其事以闻。越明年四月二日,命下允俞而始立邑,当环峰复嶂间,平陆三十五里,版垣墉高丈许,步三百周。树室辟户,张官置吏,子男之邦,周宏远规。先是,田畯锄芜敷菑,为厥疆亩,因著之名。⑤
林谞《闽中记》修于唐大中年间,是福州较早的一部方志,已散佚,林谞事迹见诸《八闽通志》⑥。林谞用“田畯锄芜敷菑,为厥疆亩,因著之名”来解释古田县名的由来,其中“田畯”“敷菑”“疆亩”的典故出自《诗经》《尚书》等文献,⑦均是春秋战国以前休闲耕作制生产及其管理的专用词语。林谞用典的寓意:或者是好古,用典溯及三代,言辞溢美;或者用以说明古田设县之前,该地“溪峒逋民”的生产方式仍很落后。
可见,主流文化圈时常将一个地方的开发程度与当地的农业方式联系起来,其中有一部分记载并不都符合史实,显示的是主流文化圈在“南北问题”上的文化偏见。唐宋以后出现的大量与“畬”有关的文学作品,并有许多与山区的非汉民族联系在一起,除了一部分写实、猎奇的功能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用“畬”来区别族群,如上述所说的莫徭、蛮、獠等。唐宋时期“畬田”农业与一些非汉族群的分布地区的高度重合,原本就带有“华夷有别”文化偏见的汉人将“畲”作为一种族群标签贴在某类族群身上。
如前所述,唐宋畲田区域逐渐缩小,刚好一些南方山林地带的非汉民族仍保存着这种古代农耕残存形态。如唐代刘禹锡之《莫猺蛮子诗》称莫徭实行刀耕火种,该诗写道:
莫徭自生长,名字无符籍。市易杂鲛人,婚姻通木客。星居占泉眼,火种开山春。夜渡千仭溪,含沙不能射。蛮语钩辀音,蛮衣斑斓布熏狸掘沙鼠,时节祠盘瓠。忽逢乘马客,恍若惊麕顾。腰斧上高山,意行无旧路。①
宋代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记载了一些被称为犵狑、犵獠、犵榄、山猺等非汉族群刀耕火种的习性:“辰、沅、靖州蛮有犵狑,有犵獠,有犵榄,有犵㺏,有山猺,俗亦土著,外愚内黠,皆焚山而耕,所种粟豆而已。食不足则猎野兽,至烧龟蛇啖之。”②
畲已然成为非汉族群一种特征,因此也为后来将一部分实施刀耕火种的族群称为“畲”埋下铺垫。饶宗颐先生在《潮州志》中曾对畲民来源进行考证,他说:“考畲民本山越孑遗……畲民山居,亦称山輋或山人……宋谓之畲或輋,以其民居山谷烧田为生,故以此名之。畲取义于田,輋取义于山。盖山越也称山民,后人专以山民呼之,寖失越名,以其居于近山之地,遂相呼曰輋。”③饶先生认为,畲民可能源于山越,只不过因为“山居”或“烧田”而被称为“輋”或“畲”,所谓“畲取义于田”“輋取义于山”。言下之意,“輋”和“畲”均为其他族群(主要是汉人)对“山越”的他称。如果这种推论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历史上与畲民有关的诸多称谓,如明清时期“棚民”“菁民”等,这些称谓的出现,与当时的生态语境和文化语境也是息息相关的。
当一个族群标签被贴上后,一些经济方式、经济作物也逐渐与该族群发生联系,这是文化再创造的结果。如出产于广东、福建等地区的稜(菱)禾,在宋代时并未完全与畲族有联系。《方舆胜览》对梅州程乡的菱禾进行了记载:“土产菱米,不知种之所自出,植于旱山,不假耒耜,不事灌溉,逮秋自熟,粒米粗粝。”①
而到了明清以后,稜禾(菱禾)均与畲族等非汉民族发生了联系,如明嘉靖《惠安县志》:“畬稻种出獠蛮,必深山肥润处伐木焚之,以益其肥,不二三年,地力耗薄,又易他处。近漳州人有业是者,常来赁山种之。”②清代《临汀汇考》称稜禾又叫畲米,分为两种,“畲客开山种树,掘烧乱草,乘土暖种之。分粘不粘两种,四月种九月收,六月八月雨泽和则熟。.”③清唐赞衮《台阳见闻录》称:“畬稻,种出獠蛮,晋江四十七都多种之。”④再如刀耕火种也打上了族群的烙印,《广东通志》:“畲蛮,岭海随在皆有之,以刀耕火种为名者也。”⑤
畲的最初形态除了经济形态,还有与“峒”有相类似的聚落或地名特征。在宋元,畲也被视为地区或聚落的名称,“畲”与“峒”一样,都有一个从“聚落”“地名”到“族群”含义转化的过程。笔者认为,这种转化有时候是可逆的,即:住在“畲洞”里的人被称为“畲民”,而畲民聚居的地方可能又被称为“畲洞”。实际上,南方的许多族群名称都经历了这种转化过程,如瑶,一般认为是由“莫徭”转化而来,因“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为名。”⑥再如僚(或獠),按郭璞的《史记·集解》解释为:“僚,猎也。”《索隐》引《尔雅》又云:“霄猎曰僚”。⑦清代梁绍献《南海县志》:
岭表溪洞之民,号为峒僚,古称山越。唐宋以来……其余不可羁縻者,则依山林而居,无酋长版籍,亦无年甲、姓名,以射生物为事,虫豸能蠕动,皆取食之,谓之山獠。①
可见,“僚”的原意与狩猎有关,许多南方非汉族群僻处山林,一般都具有狩猎技术,并有许多以此为主要生计来源。而华夏民族将这种族群印象特征化、标签化,慢慢地被用来泛指代古代南方非汉族群。因此,如果按生态语境——文化语境的角度,我们就可以更好地去理解一些族群称谓现象。
三、族群边界冲突与南宋“畲”族群称谓的出现
关丙胜指出:“古代族群边界首先是由自然生态环境营造和维持的,族群之间的边界就是自然生态之边界,当由自然生态决定的族群地理边界随着族群的发展而不断突破时,以占有更多生态资源为主要目的边界扩张势必使原本远离的族群因各自的扩张而发生边界冲突。”②在本章第一节,我们已经较为详细地说明了帝国经略后,给族群格局带来的变化。在福建地区,这种变化在南宋时期变得更为明显,族群的冲突更为严重。
朝廷对一些偏远的非汉人群所在地区,实行的是羁縻政策,在汀州,一般认为是畲民聚居的地区,在早期也是实行族群自治政策。如杨澜在《临汀汇考》中写道:“畲之在闽,所谓被之声教,疆以戎索也。”③这里引用了两个典故来说明畲民的政治管理情况:“被之声教”④说明畲民在礼乐教化,即文化上受到华夏文明的恩泽;“疆以戎索”⑤说明采用羁縻政治,由畲民自我管理。以上两个合起来说明畲族名义上受朝廷管辖,实际上是自我管理的一种状态。到了宋代,“畲”与汉之间族群开始冲突,并作为一种独特的族群进入汉人的视野中。南宋景定年间,刘克庄撰写的《漳州谕畲》,反映了“畲”汉族群扩张而发生边界冲突的情况,刘克庄在《漳州谕畲》开篇写道:
自国家定鼎吴会,而闽号近里,漳尤闽之近里,民淳而事简,乐土也。然炎绍以来,常驻军于是,岂非以其壤接溪峒,茆苇极目,林菁深阻,省民、山越,往往错居,先朝思患预防之意远矣。凡溪峒种类不一:曰蛮、曰猺、曰黎、曰蜑,在漳者曰畲。西畲隶龙溪,犹是龙溪人也。南畲隶漳浦,其地西通潮、梅,北通汀、赣,奸人亡命之所窟穴。①
由上可知当时族群边界冲突的原因:一是国家政治中心移到“吴会”(杭州),与浙江相邻的闽西南成为地理版图上“近里”,间接说明汉族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势力迫近漳州;二是漳州“壤接溪峒”,地理位置上接壤非汉地区,文中又说其地“西通潮、梅,北通汀、赣”,所指的“溪峒”应该是潮、梅、汀、赣等地,而宋代盘瓠蛮已广泛分布以上地区,其迁徙呈“向南又折而向东”的趋势,这种扩张趋势显然会遭遇漳州以东强大的汉族势力;三是此时的漳州已呈现出“省民、山越,往往错居”的状态,“先朝思患预防之意远矣”,说明“华夷”的地理边界已经被突破,族群间互动几率较大,官方出于军事防御考虑也好,出于“严夷夏之防”观念也好,总之漳州的边界冲突已然明显。
漳州汉民与“畲”民族群边界清晰,不仅体现在族称差别上,还体现在刘克庄书中所描述的族群间的巨大文化差异:畲民具有“长技止于机毒”“刀耕火耘”“崖栖谷汲”“猱升鼠伏”的生产生活习俗,“反复杰黠”“自称盘护孙”的社会心理和宗教信仰以及“畲民不悦(役)”“畲田不税”“有国者以不治治之”“贵豪辟产诛货”“官吏征求土物”的政治待遇。②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这么推论:“畲”、汉两大族群势力此时在一方或彼此扩张过程中,发生边界冲突,在各自文化认同的影响下,族群间的文化差异被放大,并带有文化偏见,如以“猱”“鼠”的动物习性来形容畲民的习惯等,而恰好掌握史料话语权的汉人士大夫代表刘克庄充当了这历史变化时刻的见证者。换言之,假如话语权掌握在“畲”的手中,其记载定然描述汉人种种负面形象,正如后世流传在畲民中的《高皇歌》所描述的一样。③
漳州“畲”、汉间的族群矛盾不是一开始就有的,直到北宋元丰年间,漳州社会比较安定。宋代王象之《舆地纪胜》载漳州风俗形胜时称:“元丰五年(1082年),郭祥正记云:‘闽之八州,漳最在南,民有田以耕,纺苎以为布,弗迫于衣食,乐善远罪,非七州之比也’云云。”①
而过了近200年的南宋刘克庄时代[按《漳州谕畲》于宋景定三年(1262年)],漳州的各族群间的矛盾开始紧张起来:漳州以东为福佬人的势力,潮、梅以西为广府人势力,汀、赣以北则是北方汉人的势力,而闽粤赣交界地区是“溪峒”(有一部分为“畲”)的族群势力。漳州、潮州当时都出现了“畲”“輋”的称呼,宋人蔡襄曾写道:“今来闽中,最急惟是贼盗群众与漳、潮之民为害。”②《宋史·许应龙传》记载:“距州(潮州)六七十里曰山斜,峒獠所聚,匄耕土田,不输赋,禁兵与哄,应龙平决之。”③山斜中的盗贼或“峒獠”应该与“畲”(輋)民有关,乾隆《潮州府志》记载宋宝祐五年(1257年)潮州知州洪天骥防御盐寇、輋民的事迹:
洪天骥,字逸仲,号东岩,晋江人。由朝散郎知潮州,治国事如家事,视民瘼如己疾,治无不为,为无不尽。潮与漳、汀接壤,盐寇、輋民群聚剽劫,历任以州兵单弱,山径多蹊不能讨。公应变设奇,降者相属,又于接境置屯,多者三百人,少者二百人,犄角为援。且严保伍之令,以澄其源,闻于朝并下之,漳汀仿此。④
可见,在南宋时期的漳州、潮州均有不少数量的畲民族群存在。与漳、潮相邻的汀州,在唐宋时期一直被认为是“畲猺”聚居地,如清代杨澜在《临汀汇考》中写道:“唐时,初置汀州,徙内地民居之,而本土之苗,仍杂处其间,今汀人呼为畬客。”⑤然而“畲”作为一个族群的具体记载却不是首先出现在汀州,而族群边界的理论恰好可以解释其原因。
从唐代以后,王朝在南方广置郡县,在政治上掀起了对福建地区的华夏化运动,中央王朝的势力开始深入边陲,帝国的“开山洞”正是这个运动的表征之一。两宋时期,中国经济完成重心南移,南宋偏安,福建与南宋政治中心相邻,这个时期的福建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都处于历史最发达时期。然而,在福建地区,各地汉族势力发展并不均衡,在开发较早、地理条件较优越的平原、盆地地区如福州、泉州、建州等地,经济文化发达;而开发较晚、地理条件较差的汀州、漳州等地区,仍被认为是“难治”地区,也是“盗贼渊薮”。
古人文人把唐代以前的漳州视为蛮荒之地。柳宗元(子厚)《登柳州城楼寄汀、漳、封、连四州刺史》云:“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轻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浸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粤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①
唐朝时期,漳、汀属江南道,封、连则属岭南道。柳宗元谪居柳州“共来百粤文身地”,都是与中原风土截然不同的地方,不仅仅是地理的隔绝,更多的是文化的隔阂。再如明人张燮在《清漳风俗考》认为在汉迁徙闽越到江淮以后,漳州是“羁縻瘴乡,声教尚阻”,他继而引用南朝沈怀远的诗句“阴崖猿昼啸,阳亩秔先熟。稚子练葛衣,樵人薛萝屋”,感叹漳州“萧索景象至今可覆案也。”②
唐宋时期的汀州也属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与福建其他地区相比,汀州的开发时间及进程与均较为滞后,直到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汀州才被奏置。有的文献将唐宋的汀州视为“穷处”“绝区”,如《舆地纪胜》载:“汀为州,在闽山之穷处,复嶂重峦,绵亘数百里,东接赣水,南邻百粤。闽部所隶八州,而汀为绝区。”③
《临汀汇考》也将汀州描述是“七闽穷处也,蕞尔一城,孑然于蛮风蜒雨中。”④《元一统志》引《广陵志》以诗的形式说明了汀州地理条件的险恶:“全闽形势数临汀,赣岭连疆似井径。江汇重渊锁地脉,山横华盖应天星。”⑤
此外,汀州内部蛮夷众多,周围山洞阻隔,北方中原(汉)文化未能在本地区占主导地位。《太平寰宇记》称汀州与建州交界的沙县:“自乾符后,土寇乱离,汉路阻隔”。①清代王捷南《闽中沿革表》则称:“……(汀州)其东北境,今长汀、宁化地毗连将乐、邵武一带,自是山洞盘互,道梗未通。”②按此前的理解,山洞应为非汉人群的聚居地,“山洞盘互”则间接说明当时“蛮夷”数量之多。《临汀汇考》则直接说明当时汀州为“峒民”“苗人”散处之地,其文曰:“长汀为光龙峒,宁化为黄连峒。峒者苗人散处之乡。大历后始郡县其巢窟,招集流亡,辟土殖谷而纳贡赋。”③
此外,历史上还曾发生“黄连峒蛮二万围汀州”④之事,该事件足见汀州非汉族群数量之多,汉文化在蛮夷文化中,犹如大海的孤岛。谢重光先生研究发现:南宋时期,虽然汀州城区及附近聚集较大数量人口,但汀州的“外邑”,特别是广大山区呈现出与郡城完全不同的文化面貌,经常表现为“一幅基本未开化的蛮夷景象”。⑤其实,闽粤赣地区这种政治中心与周边山区“华、夷”势力状态一直延续到元明时期,如明代李东阳在其《赣州府复修长沙营记》载:
眷兹南服,若赣、若惠、若潮、若汀、漳诸郡,衣冠文物与中州等,惟是万山蟠结,溪峒深阻,其风气郁而不畅,故其人所禀,颇多顽悍之质。⑥
在这种“蛮风蜒雨”中,作为掌握着史料话语权的汉人,把本族群与非汉族群区别开来的方法,就是把族群文化与中原联系起来,如庆元年间(1195—1200年)汀州教授陈一新在《跋赡学田碑》中写道:“闽有八郡,汀邻五岭,然风声气习颇类中州。”①这种不断强调“中原文化认同”的叙述模式,反映的是宋代以来,福建本土逐渐融入中原主流文化过程中的一种心理反弹,在表明自身文化历史渊源的同时,似乎更加强调其作为中原文化传承的正统性。②
而同时代的刘克庄描写漳州则称:“风烟绝不类中州”③,谢重光先生将《跋赡学田碑》与刘克庄诗对比后认为:“一说汀州颇类中州,一说漳州绝不类中州,可见在当时人眼中,汀、漳两州虽然境土相连,区域文化面貌和族群人文性格是迥然不同的。凡此都充分说明,宋代赣南、闽西确已形成彼此相似而与其他相邻地区迥异的独特区域文化风貌和独特族群人文性格。”④唐宋时期漳州与汀州族群格局有所不同。应该来说,汀州的非汉人群比例更高一些,如果以孤岛与海洋的关系去探讨不同地区华、夷的族群格局,那么,唐宋时期的汀州,汉人显然是处于孤岛的地位。
实际上,“畲”、汉间的边界是多重的,在族群边界冲突更明显的漳州族群边界更清晰,掌握史料话语权的汉族在本族群势力较强的漳州证明他者为“非”(汉),在本族群势力较弱的汀州证明自己为(汉),本质都是在维护族群认同总之,随着南宋时期“畲”、汉边界的划定,“畲”作为一个在文化特征迥异于汉人的特殊族群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在宋元时期的东南区域社会中扮演着区分人群的重要的角色。
第五节 小结
本章探讨了在华夏化进程中,特别是在华夏民族观念下,中国南方地区族群格局变化的情况,着重论述了南宋时期畲汉族群边界形成的情况。本章的主要论点有以下几点。
(1)华夏族不断向华夏核心区以外的“蛮夷”地区扩张,越来越多的非华夏族群被卷入其中。唐代以后,表现为南方各地区的“山洞”被开发,随之而产生的后果是越来越多的华夏族被纳入帝国统治范围,成为王朝的编户齐民。而一些未被“王化”的“蛮夷”,其边界只能向更边陲的地区移动,最后形成一个个漂在华夏族群“海洋”中的非华夏族群“孤岛”。随着华夏化进程加快,国家加强对边陲地区的开发,“开山洞”的政治意义在于,国家通过奏置州县、检责户口、建立行政机构,对“山洞”蛮夷地区进行控制,其文化意义在于,越来越多的非汉族群走向华夏化,成为帝国的子民。帝国对南方非汉民族地区的经略是漫长而复杂的过程,除了政治军事运动外,更多是对该地区采取文化教化。宋代以后,南方山洞成为一个个被汉族“海洋”包围的“孤岛”,并且随着华夏化进程的加快而逐渐消失,这在客观上显示了“畲”汉边界的移动情况。
(2)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华夏族形成“华夷之辨”的“天下观”或“异己观”,这种族群观念的心理优越性,使其具有向外扩张的驱动性。中原华夏族对周边的非华夏人群认识加深,越来越多的“他者”族群被发现,并随着华夏化进程,其族群边界发生了漂移。“华夏边缘”的漂移并非一定是华夏族人口实质性迁移,也与华夏族心目中“异族”边界的漂移有关,即一些原来存在于比较中心地区的“蛮夷”称谓,后来出现于边陲地区,有可能与华夏族的族群的认识有关。本章通过华夏族心目中“山都”“木客”“蜑”以及“盘瓠子孙”等族群边界的漂移,说明了影响族群形成的“他者性”问题,换言之,以上族群的发展与变迁,很大程度上与汉文化语境有关。在先秦之前的时代,闽粤地区的主要族群为百越,秦汉以后,来自鄂湘地区的荆蛮族群南移,东南地区的族群既多且杂,中原人常混淆不清,皆以未开化的蛮夷视之,出现了一些泛称,如蛮僚、峒僚等,实际上并非一个族群。随着族群接触的增多,对地方族群认识加深,汉人在主观上对这些蛮夷的族群分类也会更加详细。这种族群分类的细化,不仅仅是蛮夷本身自身演化分离的结果,还得从认识论的角度去分析其成因。
(3)在华夏中心族群观念和意识下,“畲”作为族群称谓应被认为是华夏异己观下的一种文化建构。把非汉民族以一定的特征联系起来,恰好一些仍维持古老农业形态的畲田方式的非汉族群被贴上“畲”的标签。然而正如文中所称,这种标签更多的是文化的标签,一些进入国家控制之内的“畲民”“峒民”不再被视为非汉民族;而原来一些可能是汉族的,因为“逋逃”或叛乱的,则被贴上“畲”或“峒”的标签,“畲”称谓的出现标志着“畲”汉边界的形成。两宋时期,中国经济完成重心南移,随着汉族势力在福建的扩张,其与“溪洞种类”在福建广东遭遇,“畲”作为一个族群称谓的记载,也最先出现在畲汉边界的漳州、潮州地区。
第一节 华夏化运动与南方“山洞”地区的开发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华夏族就已经形成了东到海滨,南及长江中下游,西抵黄土高原的核心区域,并在此后很长的历史时间中,以类似“滚雪球”②的方式,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华夏化运动。华夏族对周围的“夷蛮戎狄”采取了两种策略:一是包进来,即“以夏变夷”;一是逐出去,赶到更远的地方。③唐代以后,文献中出现大量关于南方地区“山洞”开发的记载,这是华南地区“蛮夷”华夏化进程加快的重要表现之一。必须指出的是,“蛮夷”的华夏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渐进的、复杂而漫长的过程。
一、华夏化运动及其对“蛮夷”地区的影响
春秋战国以后,华南地区苗瑶语诸民族开始走上华夏化进程。最早完成华夏化进程的是位于长江中游的楚人,有史料证明,楚人建国时已经使用汉语和汉字,从而完成了从“蛮”到“夏”的文化认同的转变。①长江下游的吴人和越人也从长江下游的越族社会中分化出来。②罗新指出,先秦至秦汉时代,楚、吴、越三国或三个南方政治集团的华夏化是缓慢和逐渐扩散的过程,他用孤岛与海洋的关系比喻当时中国南方华夏化地区与非华夏地区③,但随着华夏化进程加快,孤岛与海洋的关系完成了逆转,也就是说非华夏地区只分布在一些山区之中,而其他平原地带均为华夏地区所占有。
秦汉时期,华夏族虽然已在江南和华南广大地区的政治、军事与文化取得稳固地位,然而各地的开发程度并不均衡。秦汉至六朝,福建相对封闭的自然生态和地理环境使得在先秦以前福建族群格局保持相对稳定状态。一般认为,在春秋之时福建地区生活着名为“七闽”④的土著居民,宋欧阳忞《舆地广记》卷三十四在论述福建路各州历代地理沿革均表述为“春秋时为七闽地”。⑤宋祝穆《方舆胜览》引《职方氏》注“七闽”云:“闽子孙分为七种,故曰七闽”。⑥朱维干认为:“七闽”指的是闽越之前的今福建和粤东潮州、梅州地区(可能还包括浙南的瓯江流域)的七大土著部落。⑦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早已存在“七闽”的称谓,一般认为是生活在闽浙的数个部族。在汉代,福建地区主要生活着闽越族,汉武帝时期,因“闽粤悍,数反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之间”。⑧史料称此次行动使得“东越地遂虚”,实际上直到唐代福建还有大量属于
闽越族的土著居民。①
晋代以后,特别是“永嘉之乱”,北方汉人大批南渡,其中有一批汉人进入福建地区。东晋时期,南北分立,移入南方的中原士民在江南等地区设立了侨州、郡、县,地处边陲的福建并未置侨州、郡、县,但是北方移民也给当地社会带来影响,到了南朝梁,人口的增加促使政府又增设梁安一郡(陈时改为南安郡)和一批新设的县。
虽然有北方汉人移入福建,但在唐代以前,福建等中国东南地区仍被中原汉人视为“绝区”“瘴乡”或“蛮荒之地”,唐代诗人柳宗元曾赋诗描述当时的汀州、漳州、封州、连州等地均为“百粤文身地”②。另外,一些南方省区也是处于地旷人稀的蛮荒状态,明代工士性在《广志绎》写道:
孙吴立国建康,六代繁华,虽古今无比,然亦建康一隅而止,吴、越风气未尽开也……观孙吴治四十三州十重镇,并未及闽、越……岂非地旷人稀之故耶?至残唐钱氏立国,吴越五王继世,两浙始繁。王审知、李璟分据,八闽始盛。③
可见,直到唐五代以后,闽浙地区才开始“繁盛”起来。学术界一般认为,从唐代开始,中国经济重心开始向南转移,并在两宋完成这一历史过程。④闽浙地区的繁盛景象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一个体现。而这种经济社会的转型与“华夏化运动”所带来的地区开发和人口迁移是分不开的。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等学者均认为,北方汉人大量南迁,是南方经济崛起的重要原因。⑤而按照美国学者詹姆斯·李的研究,战国以后的政治形势和地理条件,一般有利于南下移民
而不利于北上移民。①
二、唐宋时期南方“山洞”地区的开发
唐代以后,帝国加强对边陲地区的统治,唐代新一轮的“开山洞”设置新县运动说明了帝国政治势力深入南方边陲地区。以唐代福建为例,中原王朝加强对福建地区的开发,其中最重要的表现为唐开元年间“一州四县”的新置。而新县的设置在后世的一些志书中,常常表述为“开山洞置”。如《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九“福州”“汀州”条中有许多县的设置都有这样的记载:
汀州:“临汀。下。开元二十一年,福州长史唐循忠于潮州北、广州东、福州西光龙洞,检责得诸州避役百姓共三千余户,奏置州,因长汀溪以为名……管县三:长汀、沙、宁化。”
宁化县:“中下。西南至州六百里。本沙县地,开元二十二年开山洞置。县西与虔化县接。”
尤溪县:“中下。东南至州水路八百里。开元二十九年开山洞置。县东水路沿流至侯官,县西水路沂流至汀州龙岩县。”
古田县:“中下。东至州七百里。开元二十九年开山洞置。东与连江接界,(西)与沙县分界。”
永泰县:“中下。东北至州一百五十里。永泰二年观察使李承昭开山洞置。县东水路沿流至侯官,县西沂流至南安县,南北俱抵大山,并
无行路。”②
这一州四县开置的顺序分别为:汀州(733年)、宁化县(734年)、尤溪县(741年)、古田县(741年)、永泰县(766年)。一州四县空间相邻,在开置山洞的时间顺序呈现由闽西向闽江下游不断推进的趋势。日本学者佐竹靖彦认为:“据从唐初到唐中期这一时期的资料表明,这一阶段支持新县设置的是从华北入侵到福建的以土豪为中心的社会集团”③。
史料中出现的“开山洞置”,说明中原王朝承认了“山洞”地区非汉人群的土著地位。前文笔者已经对“山洞”进行考证,认为“山洞”在新石器时代为人类的居址之一,到了隋唐时期,逐渐演变成为南方非汉人群聚落称呼或族群泛称,其中体现了中原核心对地方边陲的文化阶序差别,包含着华夏人群相对于非华夏人群的心理优越感,汉人史籍中常将南方山洞地区的居民视为“蛮夷”
北宋乐史在《太平寰宇记》记载汀州时称:“唐开元二十四年,开福、抚二州山洞置汀州。”①乾隆《汀州府志》对关于为何是开福、抚二州以及为何以山洞称之两个问题进行解释说:
唐时开福、抚二州山洞,置汀州。今考:州南境,旧为新罗县,隶泉州。北与石城、南丰、将乐、建宁、泰宁为邻。南丰隶抚州,而建、邵犹未郡,诸县所隶,非抚即福。时闽中只福、建、泉三郡尔。故以二州言,而四山崇峻,盘互交锁,其民狞犷,郡盗屡作,当时谓之山洞固宜。②
按照以上解释,由于汀州未设之时,其周围只有“福、抚”二州,而二者地理上“四山崇峻,盘互交锁”,人文上“其民狞犷,郡盗屡作”,因此被称为“山洞”。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华夏汉人眼里,山洞地区地势险要,居民野蛮未开化。另外也说明了至迟在唐开元年间,除了福州、抚州、泉州三郡之间的广大未设县区域,分布着大量的非汉人群,这些地区的汉人犹如孤岛点缀于非汉人群的海洋当中。所以《资治通鉴》记载汀州设郡161年后的乾宁元年(894年),发生“黄连峒蛮二万围汀州”的事件。此事件由时任福建观察使的王潮派部将李承勋“将万人击之,蛮解去,承勋追击之,至浆水口,破之。闽地略定。”③设郡治理100余年,峒蛮仍如此之多,可见未设郡时非汉人群在当地人口占较大比例。
另外,按照封建王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国家观念,“山洞”也是国家所有,虽然在客观上国家统治不到这些“山洞”地区,但由于“山洞”居民在主观上“不向王化”,未入版籍、不纳赋税,因而被认为是“逃户”“逋民”。就此而言,开山洞不仅意味着该更多的地区被开发,还象征着皇恩泽被天下,更多的“蛮夷”成为帝国子民。宋代的《太平寰宇记》载尤溪县:
其地与漳州龙岩县、汀州沙县及福州侯官县三处交界。山洞幽深,溪滩崄峻,向有千里,其诸境逃人,多投此洞。开元二十八年,经略使唐修忠使以书招谕其人,高伏等千余户请书版籍,因为县,人皆胥悦。①是否纳入版籍,是化内与化外的区别,也是区分山洞与百姓的重要标准之一。逃人,也称逋客,清代梁章钜在《称谓录》中称:“逋客,《山堂肆考》:‘逋客,避世之隐者也。’”②以上记载反映了两点:一是脱籍“逃人”投入“山洞”地区,成为化外之民;二是经朝廷“招谕”,地方逃户代表(很有可能是地方土豪)高伏等千余户要求进入国家版籍,成为编户齐民。国家通过奏置州县、检责户口、建立行政机构,对“山洞”地区进行开发。作者以“人皆胥悦”来形容新县建立后县民的喜悦情形,其中也包含着为王朝“开山洞”歌功颂德的成分。
再如民国《宁化县志》称宁化在“唐乾封二年乃改黄连峒为镇,开元十三年陞黄连镇为县”,并引旧志称:
开元十三年,福州长史唐循忠于潮州北界、福州西界检得避役百姓共三千余户,奏闻,复因居民罗令纪之请,因陞黄连镇为县。二十六年,开山峒,置汀州于新罗城。③
从宁化县的建置沿革,我们可以看到,宁化县经历了“峒”—“镇”—“县”的演变过程。从“峒”到“镇”,说明帝国首先加强对“山峒地区”采取军事措施,通过设立军事机构加强对非汉地区的控制和镇压;从“镇”升为“县”,行政机构提升一级,帝国在“山峒地区”统治更加深入,汉族势力以县城为中心逐渐扩张,并慢慢在非汉地区取得优势地位,特别是一些“避役”的汉人重新进入国家统治范围,以及“开山洞”时大量的蛮僚成为编户齐民④,这些原来被视为“化外之民”的人群在文化认同上均向汉文化发生转变,急剧扭转了“蛮”、汉在当地的族群格局。
因此,就“山洞”居民的成分而言,其中主要有非汉人群和“逃人”(大部分为避役的汉人)。另外,“山洞”中还有一个被称为“土豪”的特殊人群,主要为当地势力强大者。这些地方土豪常在“山洞”向化中起主导作用,如乾隆《古田县志》称:
古田属福州,唐开元以前尝为土豪所据,至开元十八年(740年)始建为县,有谢能者因古田亩开垦而居,故名古田……唐峒豪刘疆率林溢林希等向化,都督李亚邱遣参军杨楚畹招致,谢能等为刘氏开垦,始立邑于环峰复嶂间。①
在“山洞”成为新县、“逃人”成为编户齐民的同时,许多土著居民也慢慢完成身份的转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来的山洞地区的居民可能已经忘记本族“其来源之所自”了。如王象之《舆地纪胜》引宋代陈轩诗歌:“居人不记瓯闽事,遗迹空传福抚山,地有铜盐家自给,岁无兵盗戍长闲”②说明到了宋代,汀州居民安居乐业,此前的王朝在汀州开山洞已然成为遥远的往事,渐渐淡出当地居民的历史记忆,只不过偶尔从一些“遗迹”中才得以传闻。
在明清一些方志中,常将陈元光等人在闽、粤地区征伐“蛮夷”过程与开山洞联系起来。据史料载,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泉潮间蛮獠啸乱”③,陈元光“从父政戍闽,父没代领其众,以功授玉钤卫翊府左郎将。”④当时泉、潮交界地区,蛮夷甚多,史称龙溪县东部地区“两江(两江系指九龙江支流北溪与西溪,笔者注)夹峙,波涛激涌,两岸尽属蛮獠”⑤。永隆二年(681年),潮州盗起,陈元光军队“伐山开道,潜袭寇垒,俘馘万计,岭表悉平”,⑥唐廷晋升陈元光为正议大夫、岭南行军总管。陈元光还师移镇梁山一带,“阻盘陀诸山为寨,渐开西北诸山洞,拓地千里。”①文中所指的开“西北诸山洞”,实际上就是以华夏势力不断侵入非华夏族群势力范围的一个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唐代以后,朝廷持续对南方“山洞”地区进行开发,如在宋代神宗时,朝廷开启了大规模的“开梅山”行动,其本质是唐代“开山洞”政策的一种延续,均是朝廷加强对非汉民族地区经略,对当地的政治管理与社会控制。《宋史》卷四九四《蛮夷二·梅山峒》:
嘉祐末,知益阳县张颉收捕其桀黠符三等,遂经营开拓。安抚使吴中复以闻,其议中格。湖南转运副使范子奇复奏,蛮恃险为边患,宜臣属而郡县之。子奇寻召还,又述前议。熙宁五年,乃诏知潭州潘夙、湖南转运副使蔡烨、判官乔执中同经制章惇招纳之。惇遣执中知全州,将行,而大田三砦蛮犯境。又飞山之蛮近在全州之西,执中至全州,大田诸蛮纳款,于是遂檄谕开梅山,蛮徭争辟道路,以待得其地。东起宁乡县司徒岭,西抵邵阳白沙砦,北界益阳四里河,南止湘乡佛子岭。籍其民,得主、客万四千八百九户,万九千八十九丁。田二十六万四百三十六亩,均定其税,使岁一输。乃筑武阳、关硖二城,诏以山地置新化县,并二城隶邵州。自是,鼎、澧可以南至邵。②
从上文可以看出,应该是朝廷先对梅山地区进行“经营开拓”,而后梅山峒蛮“恃险为边患”,成为国家不稳定因素,于是朝廷下令“开梅山”。这种说法是官方的表述方式,实际上,按照族群边界的理论,所谓的“开梅山”就是汉族势力逐渐进入峒蛮地区,“开”字意味着疆域被“开边”、蛮族被“开化”。一是剿抚当地土著,有“诸蛮纳款”,即归顺降服;二是疆界被开发,在诸蛮“争辟道路”的配合下,开辟山洞的四至被界定;三是将当地土著编入版籍,并对土地收税;四是“以山地置新化县”,设置国家机构进行管理。这就是开山洞的基本过程。
“开梅山”始于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③,宋人晁补之《开梅山》对宋代此次事件进行描述,其文曰:
开梅山,梅山开自熙宁之五年。其初连峰上参天,峦崖盘崄阂群蛮。南北之帝凿混元,此山不圮藏云烟。跻攀鸟道出薈蔚,下视蛇脊相夤缘。相夤缘,穷南山。南山石室大如屋,黄闵之记盘瓠行迹今依然。高辛氏时,北有犬戎寇,国中下令购头首。妻以少女金盈斗,遍国无人有畜狗。厥初得之病耳妇,以盘覆瓠化而走。堪嗟吴将军,屈死狺狺口。帝皇下令万国同,事成违信道不容。竟以女妻之,狗乃负走逃山中,山崖幽绝不复人迹通。帝虽悲思深,往求辄遇雨与风更为独力之衣短后裾,六男六女相婚姻。木皮草实五色文,武溪赤髀皆子孙。侏离其声异言语,情黠貌痴喜安土,自以吾父有功母帝女,凌夷夏商间,稍稍病侵侮。周宣昔中兴,方叔几振旅。春秋绝笔逮战国,一负一胜安可数!迩来梅山恃险阻,黄茅竹箭霪雾雨。南人颠踣毙溪弩,据关守隘类穴鼠。一夫当其阨,万众莫能武。欲知梅山开,谁施神禹斧。大使身服儒,宾客盈幕府。檄传徭初疑,叩马卒欢舞。坦然无障塞,土石填溪渚。伊川被发祭,一变卒为虏。今虽关梁通,失制后谁御。开梅山,开山易,防獠难,不如昔人闭玉关。①
晁补之(1053—1110年),北宋著名文人,“苏门四学士”之一,曾任吏部员外郎、礼部郎中。其在《开梅山》一文中对朝廷经略山区进行描述与议论,其观点代表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理解。该文承袭黄闵《武陵记》、范晔《后汉书》关于“南山石室”“盘瓠传说”②的记载,借以证明梅山峒蛮与盘瓠之间的关系,学者也依据该文认定梅山峒蛮就是盘瓠蛮。③
另外,文章也反映了作者对开梅山持有矛盾的态度:一方面对朝廷开梅山持肯定态度,夸赞其“施神禹斧”,开辟障碍,填平溪渚,派驻“身服儒”的官员进行教化,当地百姓“叩马卒欢舞”;另一方面有对朝廷能否较好地在梅山地区守土防寇表示担心,因为梅山不仅地势险要,气候恶劣,而且群蛮负山险阻,叛变无常,“一变卒为虏”,“失制后”难以防守,为了“防獠”,最好如古人闭关守卫。①这种担心并非没有理由,《宋史·蛮夷传》就记载元祐时期蛮夷降而复叛的情况:
熙宁间,以章惇察访经制蛮事,诸溪峒相继纳土,愿为王民,始创城砦,比之内地。元祐(1086—1094年)初,诸蛮复叛,朝廷方务休息,乃诏谕湖南、北及广西路并免追讨,废堡砦,弃五溪诸郡县。崇宁间(1102—1106年),复议开边,于是安化上三州及思广诸峒蛮夷,皆愿纳土输贡赋,及令广西招纳左、右江四百五十余峒。②
从上文可知,朝廷对蛮夷地区的经略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反复的、长期的过程。这种反复的过程,似乎可以涨潮、退潮为比喻,即涨潮、退潮的潮水有进有退,但在潮汐力量的牵引下,潮水总体上是以前进的方向慢慢侵吞海滩。如果这个比喻恰当的话,那么汉族势力也像涨潮潮水,慢慢“侵吞”蛮夷的边界,这种边界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边界,还有文化上的边界,如文中提到的“愿为王民”“愿纳土输贡赋”就显示了蛮夷的国家认同。而随着教化进行,许多蛮夷的族群文化特征就与汉民渐渐的无特别大的差别了。
对于南方土著或非汉民族来讲,边陲地区的开发意味着国家对当地社会控制的加强,在钟姓畲民中流传着一些畲族的民间传说或许反映的正是这段史实。③根据闽西的一些钟氏畲族族谱记载,钟姓祖先经江西移居鄞江(长汀)白虎村,上杭树槐堂《颍川钟氏宗谱》记载道:
唐开抚、福山洞,于鄞江置汀州,以钟氏祖批黄氏之坟为刺史衙,以居宅为长汀县衙。钟氏难抗朝廷,故迁移南岭穽秋坑居住。幸刺史仁爱,以孝治天下民,泽及枯骨,有坟下废,递年清明前一日暂逊,府堂厅钟氏祭拜祖家。及礼公时,刺史酷虐,不容之祭,以致恭、宽、廉、敏、惠、节六公各迁移地方。曾将射箭坝以田施与开元寺,因塑逵公夫妇像于开元寺东阁堂,世代年年每日于香火祀奉。④
关于这个传说,该族谱摘录一段号称是南宋高宗十年(1140年)撰写的《逵公配马氏古迹谱序》,该文记载更为详细:
时因朝廷迁鄞江,祖坟葬为汀州府衙,迁宅住为长汀县衙,难杭(抗)朝廷,求有司递年祭赛,以展孝思。有知府马,仁政爱民,将箭射坝田六十亩作钟氏蒸尝,递年清明日逊府堂与钟家祭赛后数十年,又有知府姓许,不容祭扫,将钟氏一族百般刁难,即欲挖去祖坟挖开遂一油缸,有灯,又有碑文云:“许优许优,与尔无仇,数百年后,与我添油。”知府见此,遂添油而复葬之。兄弟七人见官府如此磨灭,将产业悉行出卖,悉舍入开元寺,兄弟迁徙他方。当天明誓云:“山有来龙水有源,此去代代产英雄,若有不认宗族者,天雷劈碎作灰尘。”后有知府李,以礼公兄弟舍田等项功德,题疏诏封礼公,为公望(塑)夫妇像于开元寺东廊阁下,号称南唐檀越主,世世配佛享记(祀)。当时恭、宽、敏移之虔州,恭公移龙南,宽公移信丰,敏公移零都赣县,惠、廉、节移之回龙河田等处,廉公移长汀县,节公移上杭县。世传穽丘有祖坟三穴,象形,坐西向东,前有河溪水为罗带,亦其始祖也。①
该传说在许多钟姓族谱中记载,蓝炯熹先生将其称为“白虎村传说”,该传说在闽南福佬人社区和闽西客家人社区中广泛流传,形成了大同小异的两个版本。②严格意义上讲,该传说不符合历史事实,且不说添油的神话成分以及舍田建寺的虚构成分,③序文号称撰写于南宋高宗十年(1140年),然而,汀州设府最早在明代,因此,“知府”的称谓不应在序文中出现。明清以后,民间修谱之风兴盛,该序文极有可能是在此期间伪托而作。
该传说显示了钟姓与当地政府斗争和妥协的一个过程:首先,钟姓原居住在汀州,朝廷开始对汀州进行治理,欲在钟姓祖坟上建府衙;其次,钟姓族人无法与朝廷对抗,只好顺从朝廷,朝廷也划出一定资产作为该族祭赛之用;再次,朝廷势力进一步扩大,以至于该族的祭扫权利都被剥夺;最后,钟姓族人只好将产业全部出卖,并舍入开元寺,兄弟几人迁徙他乡。
浦城村溪村《颍川堂钟氏宗谱》亦载有“许优添油”的故事,故事与上杭钟氏族谱大同小异,在一些细节上描写得更为详尽,该谱的“序”中写道:
嗣后许优莅任,每夜将公案推横,坟冢涌起。及询隶役,咸云古怪。因控开视,内现石碑,有灯偈云:许优与尔无仇,五百年后为我添油。随即示谕府中十三坊油户,各备十挑添之,未见盈溢,复各百挑增充,犹未敷足,众皆稽首叫苦方盈故从前太守每夜临寒食不能升堂理政,及清明必逊位。①
对比两则上述材料,二者均有类似诅咒的出现,或者说明本族子孙需认祖归宗,或者说明官员因为为难本族而遭到报应:除了许优添油外,此前的太守每夜临寒食不能升堂理政,到了清明必定逊位等。由于该传说的叙述主体为钟姓族人,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类似怨念的诅咒,实际上隐含着本族抵抗外来势力无果后,而采取的一种无可奈何的解释方式。
虽然不能以信史来看待流行于民间的“许优添油”传说,却可以由此追寻该传说出现的社会情境,即:随着国家对南方地区的开发和中原汉人南下,南迁汉人与畲族先民在土地等资源上存在着竞争关系。这种竞争的结果是,强势的汉族(官方)势力逼迫畲族先民退缩,直至分散各地。
我们还可以另外举上杭钟氏的一个例子,说明中央权力深入边陲给当地非汉人群带来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杭钟氏族谱的《颍川钟氏世系图》称,钟姓传至第九十五世时共有14个兄弟,因王安石变法而导致兄弟逃散,该世系图所附的文字写道:
天下姓钟皆同一脉。毅公十四兄弟因王安石余党仍在朝弄权,复行新法荼害,兄弟东逃西散,改姓流迁各省、府、县、乡,各流一处……十四兄弟遂改姓名住宁化,后各流地方。以上诸公后代都称为郎,故紊其名。因友文公兄弟阴灵在五凤楼救火,战败金,徽宗封为助国尊王。兄弟闻知,遂复为钟姓也。②
该段文字认为,正是由于北宋的王安石新政,迫使钟氏兄弟14人改姓流迁,此后子孙开始使用郎名;而钟姓后代恢复为钟姓主要是因为本族祖先有功并受封于朝廷。文中显然夸大了王安石新政对畲民家族的影响,另外阴灵救火出战也带有神话成分,其历史的真实性颇值得怀疑。正如此前所分析,这种传说的背后反映了一定的历史事实:随着朝廷对南方地区控制的加强,朝廷开始在南方地区施行政策,这引起了部分南方土著或非汉族群的反抗,一些畲民可能采取“逃离”的方式躲避朝廷的政策。该记载还显示了畲民对本族“郎名”由来背景的解释:华夏化进程给当地畲民族群社会带来冲击,导致畲民社会文化的变迁。①
第二节 “夷夏”观念下的华南非汉族群格局
不同的自然生态造就了不同类型的区域文化,从而也塑造了具有不同文化特征的族群。不同族群在接触交往过程中,形成了对“他族”和“我族”(或者为“我群”和“你群”)②关系的认识,我们也将其称之为民族观或族群观。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形成了华夏与四夷关系的族群观念,并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一整套的观念体系,具体表现为“华夷之辨”“用夏变夷”“夷夏之防”等思想。这种族群观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其作为一种思想意识,长期影响着“华夏”与“诸夷”的族群关系。
一、华夏“异己观”的形成及其文化特性
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其文化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自然生态的制约,不同类型的自然生态造就了不同类型的文化,从而也塑造了不同的族群。自然地理学以秦岭至淮河一线为界,将中国划分为广义的华南区和华北区。由于南北方的自然地理的不同,这也造成了考古学意义上的南北区域在文化面貌、社会结构、发展阶段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也有学者将考古文化视为一个文化地理的概念。①中国自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以后,开始形成了区域的文化传统,而到了新石器时代时,已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各考古学者根据不同理论和方法,将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划分为不同区系。
从新石器时期的考古材料来看,由于经济形态的不同,华南区族群可以概分为两大集团,即苗蛮族群和百越族群。一般认为,前者的文化以(华夏)素面、绳纹灰陶(软陶)为特征,而后者的文化以印纹陶为特征;苗蛮族群的分布区以江汉平原为中心,南及洞庭湖平原,西达重庆东部,东与百越相接,北抵黄河中游;百越集团分布更为广阔,中国南方东南沿海各省区从商周到春秋直至秦汉,都是越族的分布区,在这些地区大量发现印纹陶,与汉文史料中所记载的越族活动地区相吻合,这说明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起到秦汉,东南沿海地区居住着具有共同文化特点的越民族群体。②
不同的自然生态,不仅塑造了不同的族群及其文化,还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文化心理和族群观念。从新石器时代后期开始,在考古学意义上的华北区,就逐渐形成了农耕区与游牧区的分野。这种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之间的生态边界,最终也导致了农耕民族文化与游牧民族文化的差别。③由于生态环境不同,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耕民族与长城线以外的游牧民族或半农半牧民族在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上出现了巨大的差异,进而在华夏族中形成了严格的“夷夏”观念,最后,中原地区比较有效地限制了边地民族实体、民族思想的南下或东进。这种中原文化对边地文化的排斥现象,体现在考古文化上,就是新石器时代以来的边地文化中常见中原文化的因素,而中原文化中少见边地文化的因素。④可见,早在新石器时代,古代华夏文明的边缘地带已经存在,有学者更是从考古发现材料,得出中国“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存在的结论。①
在不同族群文化长期遭遇时,各族群逐渐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异己观”,即如何看待其他族群,从而审视本族群。我国古代华夏族以“中国”称谓自己,这既是地理空间概念,也显示了“我群”为中心的文化观念认识②,是华夏族群认识和了解世界的基本参照点。与“中国”相类似的概念在古代亦称“华夏”“天下”“四海”等,与之对应的就是“四夷”(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或“五方之民”③,这种对他者形象的想象,其背后是一种文化霸权的体现。④总之,在华夏人地缘政治与文化视野中的诸夷,其根本性的区别是文化上的。正如学者指出:“华夏人以高水平的文化与文明自居,视夷狄野蛮落后,这就构成了华夷的界限,构造了‘用夏变夷’的思想文化体系。华夷之辨、华夷之防,构成了华与夷、天下与四海的主流历史意识。”⑤华夏与诸夷的关系,被认为是贯穿古代中国文化史、文明史始终的一个具有根本性的核心问题。
华夏族的这种“天下观”或“异己观”,使得其具有向外扩张的驱动性王明珂认为,秦汉以来形成的“英雄祖先历史心性”成为支持华夏认同最主要的历史心性,这决定了“华夏”的内在本质是“对外扩充边界资源及对内依阶序等差分配资源的群体”。⑥在这种历史心性下,产生了类似“英雄徙边”的各种传说,“它所创造的‘历史’隐喻着资源不足可借英雄之向外迁徙、征战、扩土及对内行阶序化资源分配来解决。华夏认同便在此历史心性下,通过‘历史’及受此记忆塑造的人们之言行,向各方、各个层面扩展其边缘……在战国时代以来经由攀附‘黄帝’或‘炎帝’及他们的后裔,以及通过‘正史’‘方志’与‘族谱’等文类,产生模式化之叙事文本,逐渐在两种‘华夏边缘’扩张——政治地理的华夏边缘,以及社会性的华夏边缘。”①在这许多的历史想象与建构之后,是真实与切要的资源垄断、分享与分配情境——“华夏”便是如此一个以“华夏边缘”排除外人,维护共同资源,并在华夏内部作阶序化资源分配的群体,“华夏帝国”是这些目的之实践工具。②
必须强调的是,在古代中国,史料文献的话语权始终掌握在主流(汉)文化圈手中。因此,关于非汉族群的记载,往往不能完全反映其真实或全貌,其中许多充满着想象与偏见。正如傅斯年、桑原骘藏所指出的,秦汉以后中国的地域问题主要是南北问题。③许多学者也指出,南方或该地族群所特有的如瘴气、蓄蛊、“南土卑湿”等特征,已经不是简单的疾病、风俗或气候的问题,更多的是观念问题,是主流文化圈的文化再创造。④随着南方各地区的渐次开发,瘴气、蓄蛊、“南土卑湿”等特征慢慢消失,显示的是族群边界的模糊化。⑤换句话说,在族群间存在严格的边界、族群文化尚未融合之时,一些类似气候、风俗,乃至族群的装饰、饮食、起居等可能成为相互嘲笑的把柄,目的就是把“我群”与“你群”区别开来,例如在中古之时就有“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⑥之说。而一个地方的文化由“野”变“文”,表现在服饰上,即所谓的“易椎髻为冠裳。”①
因此,在各种文献上,凡是与非汉民族有关的记载,大都带有蔑视的意味。以“溪洞”为例,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沅水》中记载:“武陵有五溪,谓雄溪、樠溪、潕溪、酉溪,辰溪其一焉。夹溪悉是蛮左所居,故谓此蛮五溪蛮也。”②古人以右为尊,以左为卑,“蛮左”显然是一种汉族对非汉民族的一种蔑称;再如宋代《岭外代答·外国门下》中载宋代钦州有“五类民”,其中俚人“史称俚獠者,此种自蛮峒出居,专事妖怪,若禽兽然。”③将“蛮”与“峒”合称,特指峒的属性是蛮夷之所;因为其“专事妖怪”,所以被蔑称为“禽兽”,恐怕是俚僚祀奉类似巫术的鬼神,被儒家正统认为是淫祀而加以排斥;宋代朱辅在《溪蛮丛笑》一书中描述西南地区仡佬村落称:“巢穴虽峙崄,中极宽广且以一处言之,仡佬有鸟落平(坪),言鸟飞不能尽也。周数十里皆腴田。凡平地曰平坦”。④这是典型的“山洞”特征,将其称为“巢穴”,显然是一种蔑称,体现了大汉族主义的民族观。可见,“山洞”不仅仅是一种居住地址,也不仅仅是一个聚落名称,还是一种对居住在该地区族群的一种蔑称。
总之,不同生态环境中形成了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在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中活动的族群,其文化特征必定不尽相同。不同文化特征的族群在接触过程中,形成了“异己”的观念,关于对“异己”的认识反过来也影响了族群之间的关系。
二、“夷夏之辨”视野下华南地区的非汉族群格局
古代华夏族关于南方族群的概念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迁。按照古代中国华夏族群观念,“中国”与“四夷”(东夷、西戍、南蛮、北狄)为“五方之民”,南方地区族群一般泛称为蛮。秦汉时期或更早,也将该地区族群泛称为越。明代学者章潢在《图书编》中写道:
秦并百郡,岭南有三郡。桂林,今广西地;南海,今广东地;象郡,今安南地也。夫自秦汉以来,所以为中国害者,北曰匈奴,南曰越然匈奴之势与南越不同,西北之国皆居中国边塞之外,有所限制,则彼不得越其界而入我内地也,惟越之地,在古种类实多,故有百越之名,曰南越,曰瓯越,曰闽越,曰东越,曰于越。其地非一处,其人非一种。①
北方民族泛称为胡(匈奴在古代归为“胡”),南方民族泛称为越,是秦汉以来的一种民族思想观。汉《古诗十九首》有“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②的记载,反映的正是当时的族群观念。以上材料也说明,即使是越族内部,因为种类繁多,称呼亦各异。隋唐以后,南方族群虽泛称为南蛮,但称呼仍然差别很大,如《隋书》说:“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疍,曰獽,曰俚,曰獠,曰狏,俱无君长,随山峒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③
唐代以后,在论述华南等地的非汉民族时,常将“深山的族群”和“水上的族群”并称,形成了一个表述的传统。如唐代刘禹锡称“闽有负海之饶,其民悍而俗鬼,居洞砦、家桴筏者,与华言不通。”④“居洞砦”指溪洞蛮夷,“家桴筏”则为水上疍民。唐代的韩愈也将这些居民合称为“林蛮峒疍”⑤;顾况《酬漳州张九使君》则写道:“薜鹿莫徭洞,网鱼卢亭洲。”“莫徭”根据刘禹锡记载,他们是一类“火种开山脊”⑥的畲田民族;卢亭则是水上居民⑦,“洞”(广义的山洞,即山中聚落)和“洲”(水边冲积地带)又分别代表两种族群所生活的地区。
这种表述影响后世对福建地区非汉民族的理解,如明初漳州府通判王祎在漳州时写下《清漳十咏》,其中一篇为:“近岁兵戎后,民风亦稍衰,番船收港少,畲酒入城迟。绿暗桄榔树,青悬橄榄枝,熏风荔子熟,旧数老杨妃。”①
作者为达到诗文的对仗工整,以“番船”对“畲酒”;但也说明了作者对漳州的族群印象中,在海为“番”,在山为“畲”的族群观念。再如清乾隆《龙溪县志》记载本地非汉居民:
南北之溪有水居之民焉,终岁舟,俗呼之曰泊水;穷山之内有蓝雷之族焉,不知其所始。姓蓝雷无土著,随山迁徙而种谷,三年土瘠则弃去,去则种竹偿之。无征税,无服役,以故俗呼之曰客,两家自为婚娶,朔望衣冠揖然,不读书,语言不通,不与世往来②
“蓝雷之族”与“泊水”应该就是后世所谓的畲与疍。到了民国时期,畲、疍仍是作为有异于当地居民的族群被记录,如民国《建德县志》称:“建德风俗之淳夙称于古,普通士夫之外别有渔户及畲客二种。其俗与地著(土著)稍异,县人均外视之。”③近代学者傅衣凌先生在《福建畲姓考》中写道:“在福建特殊部族中,畲与蜒实推巨擘,此两族其先盖同出于越。后乃辗转流布于今之闽浙赣三省边区,并深入于粤东,以其有居山、居水之异,爰分为二,实则一也。惟山居之民,在宋之前,多称为越、南蛮、峒蛮或洞僚,宋元之际,‘畲’名始渐通行。”④以上说明,各个时期的文献记载者注意到华南地区“山居”和“水居”非汉族群格局的存在。
关于南方非汉族群称呼变化不定,清人吴震方在《岭南杂记》中有深刻的理解,他写道:
獠即蛮之种,出自梁益之间,其在岭南,则隋唐时为患,然是时不言有猺,宋以后又不言獠,意其类合分无定,故随代异名。明通志凡山寇皆谓之獠,盖山寇亡命乌合,未必种传,无从究考。⑤
吴震方敏锐地观察到,每个朝代的非汉族群称呼不尽相同,其根本原因是“其类合分无定,故随代异名”,这种“合分无定”一方面由于族群融合导致族群实体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则与华夏族对非汉族群认知情况有关。正如郭志超先生所论:“中央王朝和中原人对周边少数民族的认识是随着王朝的开疆拓土和人口向周边的迁徙而增多的。大抵说来,以中原为中心,这种认识的半径的延长与时间成正比。并且,这种认识与半径长度成反比,对于越远之地的风物、族群,认识越模糊。”①另外,吴震方还指出,明代汉人将“山寇”都称之为“獠”,作者认为山寇并不一定都是“獠”的“种传”,无法考究这些乌合之众的具体族属。可见,吴氏的论述符合族群发展的客观实际,其论述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分辨族群时,不能单方面地强调该族群的血统因素,还应该分析其文化特征或社会身份,尤其要重视华夏族的族群对“异族”的认识观念。
第三节 畲族先民的族群来源与华夏族“异族”
概念的漂移
畲族的源流一直是畲族研究的重点,关于畲族的来源,各家众说纷纭,观点不一。②众多的观点中,又可以概括分为“土著说”“外来说”以及“多元说”三种。畲族的形成与发展应该是多源的,因为除了“多元说”外,“土著说”和“外来说”,都没有完全否认畲族来源的多源性③,只不过这些学说探讨多是“关于畲族的主源问题”,正如郭志超先生所说:“无论是溯源于五陵蛮,乃至东夷,还是溯源于越人,这些探讨多是关于畲族的主源问题,一般并不否认畲族的形成和发展是多源的。”④按照“多元说”观点,不论是外来的“盘瓠蛮”族群,还是闽粤土著,它们都只是形成畲族先民的一部分,这些族群与南迁汉人发生了较多的接触,互相融合后,最后在闽粤赣地区形成一个“具有稳定经济、文化特征和自我认同的新民族”,这个新民族就是畲族。①
畲族先民的族群成分具有多源性,历史上在华南地区生活着的众多非汉族群,诸如闽、越、莫徭、盘瓠(子孙)、山都木客、僚(獠)、疍(蜑)、畲(輋)、瑶(猺)②等,均是畲族先民的可能来源。这些族群在历史上因各种原因发生了变迁,一些学者通常以民族迁徙来解释这些非汉族群在某地存在或消亡的原因。③实际上,历史上一些族群的兴衰,不仅仅是族群实体人口迁移的结果,还可能是族群文化认同转变的结果。比如,一些原本文化特征存在较大差异的族群在交往过程中产生了民族融合,互相吸收各自文化,文化特征差异逐渐消失,文化认同也逐渐趋同,如历史上的许多少数民族汉化即是此例。另外,也存在一种可能:原本具有相同文化、文化认同差别不大的族群,由于坚持了不同的文化认同,从而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族群,历史上客家与畲族的分离即是此例,关于此,笔者在后文中将再作论述。
随着王朝势力进入边陲地区,唐宋以后的华南地区在族群格局和社会结构均发生了变化,占有政治文化优势的汉人逐渐扩大自己的族群势力范围,非汉人群的族群边界呈退缩状态,这种边界范围的变化不仅仅与非汉族群本身的兴衰有关,还与华夏人群心目中的异族概念向外漂移有关。王明珂通过研究发现,随着华夏的扩张,华夏边缘向外逐渐漂移,这种变迁过程借由两种手段:或者是华夏人群心目中的异族概念向外漂移,或者是非华夏人群假借华夏祖源记忆而成为华夏。④笔者以山都木客、蜑、盘瓠等族群为例,借以论证王氏之说。
一、族群格局虚幻与真实:以华安仙字潭研究为中心
1935年岭南大学黄仲琴教授发表了《汰溪古文》,开启了仙字潭石刻研究的学术领域。后世许多学者纷纷投入仙字潭石刻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成为福建古代民族考古的重要内容。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学者提出了仙字潭族属为七闽①、吴②、越③、番④、畲⑤、三苗支族后裔⑥等见解,与石刻主人发生族群关系的还有“古傣人”、夷等。由于仙字潭石刻本身对于研究华南地区族群的来源、迁徙及其文化、生活状况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加之梳理学术上与之有关的族群研究,对畲族乃至华南地区其他族群研究都有借鉴意义。因此,笔者以仙字潭石刻为研究视角,从中窥探福建乃至华南地区古代民族的若干概况。
早在1915年夏天,黄仲琴先生就乘船沿汰溪到达仙字潭实地考察,并参考大量文献后认为:“汰溪古文形有类似蝌蚪者,与近人法国牧师费亚所述苗文有相同之处,疑即古代蓝雷民族所用,为爨字,或苗文之一种。”⑦黄仲琴推断其为蓝雷畲民论据主要为:一是《唐书·舆地志》《漳州府志》《龙溪县志》《北溪纪胜》关于龙溪、柳营江等地理位置的记载;二是陈天定《北溪纪胜》关于“古称桃源,蓝雷所居”的记载;三是《平和县志》《罗源县志》猺民众“盘蓝雷”的记载;《漳州府志》《龙溪县志》、安溪《李氏家谱》讨平“洞蛮”“峒寇”苗、雷、蓝姓的记载;四是华安当地畲族分布:“今汰溪北之高层、新圩。南之归德彭水,山僻深处,犹有蓝雷遗种,自成村落,不与外人通婚,是其余胤。在唐尚盛,至今犹存,其势力远过汉之笮都诸夷。”⑧五是汰内本地乡人陈君关于古蓝雷石石蚵山洞古剑、古书传说以及汰内乡至今尚存有苗俗的巫术。黄仲琴最后推论,族群应是蓝雷族:“蓝雷钟系,或瑶、或苗,溯源不异,名称则淆,按闽南人对于蓝雷人,名之曰:‘蓝雷仔’。‘仔’者轻之之辞,盖弱小民族之称谓也。兹用其意,名本文所述之种族,曰‘蓝雷族’,以是地无盘姓也。”⑨由此可知,黄氏研究是根据文献、传说以及实地调查,目的就是为了追寻遥远的仙字潭石刻与畲族的联系。
黄仲琴教授是仙字潭石刻研究的开创者,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仙字潭石刻研究形成热潮,华安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先后于1984年和1988年整理出版两期《仙字潭古文字探索》①,共收录33篇相关学术论文;1990年,福建省考古博物馆学会编成《福建华安仙字潭摩崖石刻研究》②,收录29篇学术论文。在以往仙字潭石刻的研究中,各家学说观点不一,分歧较大。主要争论焦点在于:一是关于仙字潭石刻是文字或是岩画;二是关于仙字潭石刻的出现年代;三是关于仙字潭石刻的观念内涵;四是关于仙字潭石刻的民族族属问题,学术界已有学者对该研究进行综述③,兹不赘言。
关于仙字潭的记载,最早出自唐代张读《宣室志》,宋代《太平广记》收录该书。《宣室志》的作者张读,出生于官宦世家,系《朝野佥载》作者张鷟的玄孙。本文主要写唐代泉州一山边潭中有“蛟螭”,元和年间雷震山崩,石壁现字,有人请韩愈辨识的事。④之所以将韩愈与“蛟螭”联系在一起,是因为韩愈曾贬官于潮州,关心百姓疾苦,亲自撰写《祭鳄文》⑤后,“祝之夕,暴风震电起溪中,数日水尽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无鳄鱼患。”⑥因此,最后这些“泉人无有识”的蝌蚪篆书,在韩愈的解读下,成为“上帝责蛟螭”的内容。正如前文所分析,唐代以前,华南地区在自然生态上仍处于较原始状态,在开发自然过程中,人类在征服自然界时需克服许多困难,鳄鱼应该是其中一个例子,其他的还有大象、老虎等危险动物,或者人类将这些危险的事物投射到一些想象的事物中,如山都、木客等。到了明代,何乔远的《闽书》在记载了仙字潭所处地区“石铭里”时,引述了《宣室志》后,认为由于是“漳、泉接境,县南龙溪界域不分,古来争竞不决。”因雷雨山崩而形成几个分界的大字。⑦
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率先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①的观点,对中国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照《闽书》与《宣室志》关于“石铭里”的记载,我们也发现了文献的“层累性”。
其体现在:由“人—鳄”这对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矛盾演化为“漳—泉”界域纷争的区域社会关系的矛盾。按文中所称其矛盾主要源于“龙溪界域不分,古来争竞不决。”根据唐代《元和郡县图志》记载,龙溪县:“陈分晋安县置,属南安郡,后属闽州。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割属漳州。”②
《元和郡县图志》又载漳州:
本泉州地,垂拱二年(686年)析龙溪南界置,因漳水为名。初置于漳浦县西八十里。开元四年(716年)改移就李澳川,即今漳浦县东二百步旧城是。十二年,自州管内割属福州,二十二年又改属广州,二十八年又改属福州。乾元二年(759年)缘李澳川有瘴,遂权移州于龙溪县置,即今州理是也……管县三:龙溪,漳浦,龙岩。③
可见,《闽书》中所称“唐开元中,漳泉二州,分疆界不均”有一定的史实基础。自然地理条件是区域边界划分的首要因素。一些河流、山川成为天然的界线,成为一些地区分界的主要依据。按仙字潭处于九龙江上游的汰溪,明代陈天定在《北溪纪胜》(上四明施郡守稿并序)中写道:
北溪、九龙江,实郡右臂。唐镇府以前,插柳为营,渡江以后,揭鸿置塞外,设巡逻行台,渐次开辟,内犹山深林密,萑苻时警……初,玉钤将入龙潭,以山高涧窄,兵法所谓死地,先扎营于此,取道大山之巅,以瞰汰内。今山顶石磴尤存,揭鸿寨、营头亭在焉。④
史称陈元光“平蛮开郡……屯兵于泉州之龙溪,阻江为界,插柳为营……阴遣人沿溪而北,就上流缓处结筏连渡”⑤,其势力深入到“龙潭”以后,因为“山高涧窄”,扎营设寨,“以瞰汰内”,说明汰内(汰溪)地区处于陈元光势力与其他族群势力的交界处。按上述“大山之巅”的大山指的是位于龙溪与华安交界处的揭鸿岭。《全唐诗》收有唐代慕容韦《度揭鸿岭(漳州)》一首,其文曰:“闽越曾为塞,将军旧置营。我歌空感慨,西北望神京。”①据清代冯登府《闽中金石志》此诗出于漳州石刻,该书卷五称:“(唐代无年月的碑刻)慕容韦揭鸿塞诗刻,在龙溪岭脊。”②《舆地纪胜》则称此诗为:“唐慕容韦《葵岗岭》。”③另外在龙溪县与华安间有九龙山,是一座“岭极高峻”的大山,宋代王象之《舆地纪胜》载漳州九龙山:
《寰宇记》云“山下有水,名九龙水”,按《郡国志》云:“一名鬼侯山,北有金溪水,山中多山魈,一名羊化子”。④
可见龙溪与华安间山脉绵延,是地域之间的天然屏障。在仙字潭石刻中,有一处为后人(唐以后)用真书浅刻的文字,写着“营头至九龙山南安县界”十个汉字。可见,营头到九龙山的自然地理条件成为为漳、泉分界的重要因素。
造成“分疆界不均”,可能主要有政治区划与人文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仙字潭所在地区处于州(县)交界处;二是该地区可能存在数量不少的非汉人群即唐代以前泉漳“界域不分”是因为在龙溪地区,漳、泉政府控制能力有限,使得漳、泉政区边界飘忽不定。
一般来讲,历史上在各政区交界地区,地方政府的管控力度较弱根据唐代江南东道地理区划(见图2-1),九龙江上游的汰溪(今华安),处于泉、漳、汀三个州的交界处的附近。
明代陈天定的《北溪纪胜》(上四明施郡守稿并序)进一步说明了该区域的地理位置情况,其文写道:
梁天监间,有九龙群戏于此,故邑号龙溪,里名九龙,概称北溪。为游仙乡,宋末车驾南幸,乃改潭内为二十五都,潭外为二十三四都。大抵龙潭地处十字之中,直者为江,驾舟北入,可上宁洋;放棹南下,可抵海澄。横者为陆,循西列嶂通于南靖;徂东平畴,便驰长泰此潭以外之胜概也……地属溪之二十五都,上由永安北趋浦城出仙霞,西赴邵汀出光泽,南走天兴,每军兴多由龙潭掠舟以发。然大中小滩三十六,水石高下,不时险巇。初入小滩为马歧,唐将军牧马故处也稍上为汰口滩,汰水西汇大江,以小舟入,古称桃源洞,蓝雷所居,今号汰内。计入口十余里有平畴广原处,天宝之背,逾郡龙过脉,有间道,可通永丰司……石铭里在其东,属泰治。前行数里,居溪之西者为下樟,居溪之东者为热水地,出温泉……由此入,可缘石铭里,通泉之安溪治。①
从上可以看出,龙溪上通宁洋(漳平),下抵海澄,西列嶂通于南靖;东平畴驰长泰:再往北可通汀州、邵等地。而仙字潭所在之地“石铭里”处于漳州长泰,与泉州安溪交界,仙字潭所处的汰内盆地,三面环山,一面临江,扼安溪、龙岩交通之枢纽,有秦汉古道贯穿盆地南北,经过揭鸿岭、营头亭通往漳州(图2-2)
黄仲琴在《汰溪古文》中以推测汰溪流域附近古代可能有族群在这里居住,该文称:“汰溪之上为石蚵山。《龙溪县志》卷二云:‘石蚵山在城北四十里,高入云表,顶有粘蚵石,相传昔时海水所浸。’《志》说可证《山海经·海内南经》‘闽在海中’之语。闻之登其巅者,至今尚蚵壳弥望,既有贝类,可供食品,古代民族聚居其旁,亦理所固有也。”②
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在粤东闽南地区发现了商周时期的印纹陶文化遗存,其中以1974年在广东饶平浮滨、联饶发掘一些特征鲜明陶器和石器为最典型,③此后,地方考古工作者将此时期的闽南、粤东区域划为浮滨型文化时期④,该时期被学者认为是青铜器时代闽南地方文化最繁荣的阶段。①考古学同时还证明了九龙江流域的漳州地区,包括今天的龙溪、云霄、漳浦、南靖,平和、长泰、华安等地在商周时期有人类聚落的遗迹。②1986年,王振镛等人在华安汰内一带进行考古调查,并发现了数处青铜器时代文化遗存,在仙字潭南岸的小山丘上也采集到印纹硬陶片。③可见,在春秋以前,仙字潭地区生活着一定数量的古代族群。
唐垂拱二年(686年),朝廷在泉、潮二州之间设置漳州,这是汉人势力进入并控制漳州中心区域的一个表现。而在漳州周边一些偏远山区,仍生活着大量的非汉族群,这种现象直到南宋刘克庄时代还继续存在。一般来讲,在古代中国社会,政府通过控制区域内的人口,如将人口编入版籍,并对编户齐民征收赋税,从而实现地区的管理。而所谓的“失控”地区,常常是政府管理不到的偏远地区,这些地区或者是非汉族群,或者是“逋逃”的百姓。在唐代以前的龙溪,这里可能生活着一定数量的且政府管理不到位的非汉族群或“逋逃”百姓。随着漳州的设置以及龙溪县割属漳州,中央政府的权力由泉州至漳州,从北向南地渗透,并以漳州为据点加大周边(包括龙溪县)的控制,从而达到华夏化的过程。
通过以上分析,从“人鳄之争”到“界域纷争”实际上反映了不同时候文献关注点不同。其中也反映了在唐代以后,随着中央政府加强对南方地区的开发,原先矛盾焦点逐渐由生态矛盾转化为社会矛盾,这种矛盾是伴随着华夏化过程发生的,是华南地区族群开始整合的表现。
在清代道光年间,学者蔡永蒹④在《西山山杂记·仙字潭》一文中,引用了大量的文献材料,并根据自身考察见闻,对仙字潭进行详细的介绍。《西山杂记·仙字潭》一文分成三段,其文曰:
《闽中记》述:“南安郡西南有汰溪,古畲邦之域也。溪之上有摩崖镌蝌蚪之虫痕鸟迹,象形古篆文,自晋唐以来咸不之识焉。、晋邑欧阳詹,许谡、陈蟜、王玖、藩存实、杨在虎、谢谌、曾严、罗山甫莫能知晓焉,王翊为京兆令将拓本访之韩愈,都不之知也。武陵太守吴公瑾访之道士蔡明濬,云《古丹箓释义》:‘皇使盘瓠掌闽为七族:泉郡之畲家,三山之蜑户,剑川之高山,邵武之武夷,漳岩之龙门潭,漳郡之蓝太武,汀赣之客家,此即七闽也。七闽各有各之文字也仙字潭摩崖之石刻古文,是畲家、龙门、蓝太武三种古文,称之楔字,乃如飞云浮云焉,成舞女盘旋,武士挥刀,羽毛怪状矣。’”
《九鼎铭汉隶篆释义》云:“汰溪即古傣人之古乡,畲人有吴昱为君因争甲指之山,炎帝之世也,畲傣战争焉,傣君日超越被斩也,部众俘为馘矣,余走之滇粤。畲吴昱之世,正当炎帝之世也,洪崖先生亦此时人焉。”摩崖石刻乃商周之时畲人留伯所镌,其次露有汉文,乃汉明帝时楚王大夫少世坚摹古畲字篆刻,经畲吴昱战太君越庆功时,太母夫人称贺,太母者太姥也,摩石刻古文如舞女即蓝太武族翩翩起舞祝贺也,兽形古文龙门人之文也,余咸畲文耳”
余慕之往阅焉,此地原属南安,唐贞元时割界于武荣州漳也,后隶于华封。汰溪清碧,湾流潺潺,松青竹翠,面幽静也。古文不剥落,见者疑之矣,然则《闽中记》迄今亦千年矣,未可为不信也。据《古丹箓释义》云:“炎帝之世,傣君超越无道,畲吴昱战越,斩越首,俘越属,傣余越走滇。龙门、蓝太姥朝贺,洪崖刻石以纪事焉,盖迄于今五千载矣,古文若九鼎铭也,世之名家难识之矣。”宋《桑莲诗集》有汰溪诗,曰:“汰溪上古在南方,仙字奇书千古昂;韩愈难明斯怪字,书风书穗不成行。”《紫云诗集》:“仙字风云变化文,畲君伐越竟超群;傣溪陈迹万年事,摩石刻崖宝不乡。”《安仁诗抄》云:“傣人古国汰溪滨,吴越春秋炎帝人;镌石古文东汉刻,千年万载记荆榛。”《仁和诗集》云:“傣越畲吴史不存,惟看石刻古文言;当年争国斯溪地,纪事闽中有七番。”《青阳诗集》云:“畲王吴昱傣王番,太姥龙门蜑户藩;武口口口口口客,汰溪其地古闽蜿。”①
作者前两段主要引述《闽中记》《古丹箓释义》《九鼎铭汉隶篆释义》,后一段说明亲临现场查看,并引用《古丹箓释义》《桑莲诗集》《紫云诗集》《安仁诗抄》《仁和诗集》《青阳诗集》等文献,目的在于说明以下内容:其一,汰溪的古篆文内容晋唐时人都不识得,有个到京兆当长官的将拓本送到韩愈处,韩愈也不认识,这与张读《宣室志》所载内容有冲突;其二,有道士蔡明濬根据文献解读,认为仙字潭摩崖石刻是畲家、龙门、蓝太武三三种古文,又称楔字:其三,汰溪原来是“古傣人”居住的地方,后来在商周之时发生畲傣战争,傣人败逃滇粤。当时有蓝太武、龙门等部族前来祝贺,洪崖、畲人留伯刻石庆功,于是石刻上留下的是畲家、蓝太武、龙门三种古文;其四,当时福建有“七闽”,分别为:泉州的“畲家”,三山(福州)的“蜑户”,剑川(南平)的“高山”,邵武的“武夷”,漳岩(漳平龙岩一带)的“龙门潭”,漳郡(漳州)的“蓝太武”,汀赣(汀州、赣州一带)的“客家”,这七个族群(七闽)都为盘瓠所管辖。
《西山杂记·仙字潭》对古代福建的族群格局做了介绍,但是,其中有许多与史实存在不相符的情况,笔者拟对该文所反映的一些材料和观点进行辨析。
(一)蔡文所引的《闽中记》并非都出自于《闽中记》
蔡文称:“《闽中记》述‘南安郡西南有汰溪,古畲邦之域也’。”其并未指出《闽中记》何人所作。实际上,在唐代以前,福建先后出现关于两部名为《闽中记》的方志,宋代梁克家的《淳熙三山志》序中记载:
予领郡暇日,访无诸以来遗迹故俗。闻晋太康既置郡之一百一十三年,太守陶夔始有撰记,又四百五十六年至唐,郡人林谞复增为之,皆散佚无存者;独最后一百九十二年,本朝庆历三年,郡人林世程所作传于世,自言视前志颇究悉。①
东晋太元十九年(394年),陶夔担任晋安郡守②,随后撰成的福建首部方志《闽中记》。唐大中年间(847—860年),林谞修撰了另外一部《闽中记》,《八闽通志》载其事:“林谞,闽县人。博学,善讲贯,属文尤美。初尝俯从乡举,竟养高不仕,搜寻异闻,作《闽中记》十卷。”③以上两部《闽中记》均已散佚,后世仅存的佚文,散见于《太平寰宇记》和《三山志》等文献中。
蔡文所指的《闽中记》应为唐代林谞作《闽中记》。从南安郡设置时间年代看,可以排除东晋陶夔《闽中记》的可能性,该书比南安郡设置时间早了170余年。历史上有数个地名称为南安郡,按以上所称《闽中记》述南安郡之事,应该指的是福建境内的南安郡。宋代《舆地纪胜》记载:“南安郡,陈属闽州,在永定元年。后属丰州。光大元年(567年),陈文置南安郡……隋文平陈郡废属泉州。”①可见南安郡为南朝陈光大元年(567年)设置。其辖境相当于今晋江、九龙江、木兰溪三流域及同安等地,后于隋开皇九年(589年)废。其次,从文中记载的内容看,其提及的欧阳詹、韩愈等均属于唐代之人,因此,只能是唐代以后的文献记载唐代之事。然而,蔡永薕文中所引内容有些却非《闽中记》所载。首先,蔡文称:“《闽中记》述:南安郡西南有汰溪,古畲邦之域也。”如果按照文献以今溯古的表述方式,其潜台词似乎可以理解为:“《闽中记》述:(今)南安郡西南有汰溪,古畲邦之域也。”按此理解的话,《闽中记》或许在记载撰写时所发生的事。唐林谞作《闽中记》时,南安郡名已废止近300年。按“汰溪”位于九龙江上游,其时属龙溪县。唐代《元和郡县图志》载龙溪县隶属州郡变化为:“陈分晋安县置,属南安郡,后属闽州。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割属漳州。”②如果是林谞《闽中记》记载“汰溪”,合理的表述方式是:“漳州西北有汰溪”,而非“南安郡西南有汰溪”。
文中称汰溪是“古畲邦之域也”,这与史实不符。一般来讲,“畲”作为族群称谓,直到南宋后期的文献才有记载。因此,不论是东晋陶夔的《闽中记》,还是唐代林谞的《闽中记》,都不可能有此判断。
文中称“汀赣之客家”为“七闽”其中的一族,这也与史实不符。“客家”作为族群称谓不可能出现在唐代,谢重光先生认为,“客家”族群在移民过程中,由于族群间互相隔膜和互相歧视,产生了“客家”或“客民”“客仔”的称谓,这种称谓与“畲客”“山客”有渊源关系,其最早出现的时间大约明中叶嘉靖年间。③其他学者如曾祥委④、刘镇发⑤、刘丽川⑥也对“客家”称谓出现的时间进行讨论,其观点不一,但均认为“客家”出现于明清以后。⑦另外,客家在汀赣地区形成不可能早于唐代。
综上几点,可见蔡永薕所引的《闽中记》与事实出入较大,究其原因,第一是历史上的两部《闽中记》均已散佚,蔡永薕所引的《闽中记》可能非原著内容;蔡永薕在《西山杂记》写作过程中,除了引用古籍文献,还加入个人的想法,所谓的畲家、客家均有可能是作者根据传闻记载,当作《闽中记》内容。
(二)蔡文所称福建族群格局和族群关系与史实有误
首先,历史上的“七闽”并非蔡文所称的“七闽”。七闽,最早出现于《周礼·夏官·职方氏》,其文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贾公彦疏:“叔熊居濮如蛮,后子从分为七种,故谓之七闽。”一般认为,福建在春秋之时是七闽所居住的地方,宋欧阳忞《舆地广记》卷三十四在论述福建路各州历代地理沿革均表述为“春秋时为七闽地”。①宋祝穆《方舆胜览》引《职方氏》注“七闽”云:“闽子孙分为七种,故曰七闽”。②朱维干认为:“七闽”指的是闽越之前的今福建和粤东潮州、梅州地区(可能还包括浙南的瓯江流域)的七大土著部落。③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早已存在“七闽”的称谓,一般认为是生活在闽浙的数个部族。
其次,蔡文中所称的“皇使盘瓠掌闽为七族”中除了畲家、客家、蜑户在唐代以后有其民族实体,其他均为传说或传闻的部族。正如前文所论,畲家、客家不可能出现在唐代文献中。而实际上,“蜑”在魏晋南北朝时主要指西南非汉人群,直到隋唐以后才慢慢指南方非汉族群。“蜑户”作为族群称谓,直到宋代才出现,关于“蜑”的考证下节进一步论述。
再次,“武夷”“蓝太武”等古代部族是蔡永蒹根据文献材料进行整合,填充进“七闽”的概念中。“武夷”“蓝太武”都是传说中的部族。关于武夷的来源,有几种说法:一种“夷落”说,即闽地部族,宋代朱熹在《武夷图序》考证武夷君来源时说:“武夷君之名,著自汉世,祀以乾鱼,不知其何神也……颇疑前世,道阻未通、川雍未决时,夷落所居,而汉祀者即其君长。盖亦避世之土,为众所臣服,没而传以为仙也。”④朱熹怀疑,古时“道阻未通、川雍未决”时,武夷山地区为“夷落所居”,其君长就叫武夷君,武夷君可能是闽地氏族首领,死后被奉为仙;另外一种传说是彭祖居武夷山,生二子,长子名武,次子名夷,当地后裔就是武夷。
蓝太武也是传说中的部族。宋代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二八载:“太姥山三十六峰,在长溪县。王烈《蟠桃记》:‘尧时有老母,以蓝染为业,后得九转丹砂法,乘九色龙而仙。汉武时,名曰太姥山,凡有三十六奇。’”①
太姥山旧属长溪县,后属于福鼎县,乾隆《福宁府志》记载福鼎山川时称:“太姥山,在八都,旧名才山,相传尧时太姥业蓝处。”并注释曰:“汉武帝命东方朔授天下名山文,改母为姥。”②按古代太和大相通,“姥”与武、母同音,所以太姥,也称太武、大武、大母等。《舆地纪胜》又载:“大武山,蔡如松《十辨》云:‘去漳州二百八十里,东临大海,有大武山……大武夫人坛,古《图经》云:‘大武夫人者,闽中未有生人时,其神始开创土宇以居人也。’又名太武山。”③
《八闽通志》有相同记载,并称:“旧亦名大母山。”④传说中闽中还没有人类之时,大武夫人“拓土以居民”,类似某地的始祖。可见,蓝太武在福建许多地方都存在。卢美松先生据此认为,远古时期,闽东北存在着以太姥(母、武)为首领的母系氏族社会。太姥夫人的部族是闽族的先民,他们与后世的山越、畲族有渊源关系。⑤应该来讲,武夷、蓝太武是后世传说中福建古代的部族,传说的成分大于历史的真实。另外,关于“剑川之高山,漳岩之龙门潭”,其文献记载阙如。高山应该与现在所称的“高山族”没有直接关系,“高山族”的称谓是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大陆地区对台湾少数民族的称谓。1953年由国务院正式采用并公布高山族这一名称。⑥
笔者推论蔡文中提到的高山、龙门这两个部族应该同武夷、蓝太武一样,是传说或传闻中的族群。然而,在唐代以前历代文献关于福建民族记载,基本上以“闽”“越”“蛮”等称谓,基本上是泛称,这与中原汉人对福建非汉民族的认识过程是相符合的。而蔡文中所称的“七闽”分布于福建七个州(县)中,这在古代族群认识中是不可想象的。实际上,直到民国时期,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还认为福建人不好了解,他说:“吾侪研究中华民族,最难解者无过福建人。其骨骼肤色似皆与诸夏有异,然与荆、吴、苗、蛮、氐、羌诸族亦都不类。”①
笔者认为,蔡永蒹之所以将族群地域分得这么细,最大的可能是恰好汰溪处于漳泉交界,附近刚好有三个族群:泉郡之畲家、漳岩之龙门潭、漳郡之蓝太武,于是得出畲人打败傣人,龙门、蓝太武相贺,石刻上留下的是畲家、蓝太武、龙门三种古文的结论。
陈国强先生对《西山杂记》进行解读时曾指出,尽管《西山杂志》所载之事与史实不尽相符,但是“民间口碑传说往往是真实历史的反映,可提供我们研究史实的线索。”②王明珂也指出,一定文本的产生有其特定的社会情境和历史心然性。蔡永蒹《西山杂记》所载的族群情况,实际上,反映了明清以来知识分子对福建古代族群的认识,这种认识是基于一定历史的事实作为基础,即:历史上福建等地区存在着多种非汉族群,这些族群或许与畲族多多少少存在关系。
二、“山都”“木客”族群边界的移动
汉晋以来,文献记载闽粤赣地区还存在一些被称为“山都”“木客”的非汉族群。汀州等地被认为有“山都”“木客”存在,如《太平寰宇记》引《牛肃纪闻》云:“江东采访使奏于虔州南山洞中置汀州。州境五百里,山深,林木秀茂,以领长汀、黄连、杂罗三县,地多瘴疠,山都木客丛萃其中。”③
乾隆《汀州府志》论汀州地理气候时,引宋代《舆地纪胜》关于山都及其种类的描述,该文称:
郡距江、广,复岭重岗,旧传为山都所居(《舆地纪胜》云:造治初,砍大树千余,其树皆山都所居。有三种:下曰猪都,中曰人都,其高者为鸟都。即如人形而卑小,男、妇自为配偶。猪都皆身如猪;鸟都人首能言,闻其声不见其形;人都或时见形。当伐木时,有术者周元大,能禹步为厉术,以左合赤索围木而砍之。树仆,剖其中,三都皆不能化,执而煮之于镬内)。①
关于“山都”“木客”,陈国强认为“山都”“木客”既不同于越或山越,亦与畲族有别,而属于古老的南方“尼格利陀”即“小黑人”之种;②蒋炳钊将“山都”和“木客”视为一种古老土著民族,是属于古代越族的后裔。③黄向春认为前人的重点考证“山都”“木客”是或者不是某一“民族”或其族裔,而忽略了产生“山都”“木客”的历史背景,他认为“山都”“木客”是在一种特定的社会情境和话语氛围中所书写的,是人们将某种危险意识投射于某种“异类”,是想象之后的产物。④笔者认为,黄氏的论断颇有可取之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山都”“木客”常常具有一些异于常人的神异特征,另外,解释了随着中原王朝对南方族群认识的深入后,“山都”“木客”渐次消失。根据郭志超研究,“山都”见于方志、文集的准确记载,始于西晋,频见于唐宋,依稀见于明清。记载较多是赣南、闽西,其次是粤东。⑤靳阳春进一步研究,认为“山都”“木客”在闽粤赣文献出现时间顺序与中原王朝疆域的开拓时间顺序相一致。⑥随着中央政权在闽粤赣交界地区扩展,在唐以后,闽粤赣交界处的“山都”“木客”基本就消亡了。①从“山都”“木客”的记载情况,可以认为:西晋至唐,闽粤赣地区存在汉人与“山都”“木客”的族群边界,“山都”“木客”进入主流文化圈的视野与汉人边界扩张有关,这条族群边界呈现由北往南移动的趋势。
应该来说“山都”“木客”尽管带有神秘性,甚至有些类似于神话。在南方地区开发过程中,类似“山都”“木客”的形象在文献中仍多有出现。如《太平寰宇记》记载在尤溪幼山地区有一种类似狒狒,名为“山魅”“山魈”“山大人”的野人:
幼山,在县西北一百二十里。乃龙峡之地。孤峰上耸三十余里,周迴二百余里。山上有松、桧、竹、柏,其中有山魅,其形似人,生毛黑色,身长丈余,逢人而笑,口上唇盖眼,下唇盖胸,人见亦怪矣。或时遗下藤制草鞋,长二尺五寸,乡人所谓山大人。又云山魈,或野人也,尔雅云:“狒狒如人,被发迅走,食人。”即此也。②
除了官方史籍外,在民间传说中也常有类似“山都”“木客”的记载,如闽西一些族谱记载本族先人来到闽西时,曾受到一些“异物”“妖类”的困扰,光绪《上杭中都叶氏族谱·五郎公传》记载道:
(五郎)公生于元初,由汀州府长汀县官(馆)前湖坑徙至上杭中都古坊开基,为一世。尔时,林树阴翳,人烟稀少。凡虫蛇鸟兽、异物群妖类皆杂处于此,而人之受其害者不可胜道。其间有樟树妖精最为恶毒,每年要残食数人以肥其身,邻里相以悲啼,共叹何日能除此害。③
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叶姓族人迁徙到上杭时,此地应是比较蛮荒之地,不仅多有虫蛇鸟兽,而且“异物群妖”杂处,而樟树妖精因食人而成为祸害百姓最厉害的一种。这种类似神话的民间传说,其隐含的真实历史背景是:在华夏化进程中,外来移民在较为恶劣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中,与土著相遇并发生矛盾,这些外来的移民开始想象和建构“异类”,通过夸大文化差异的叙事方式,树立起一个“非人类”的对立面。
三、“蜑”族群边界的移动
“蜑”最初也称“诞”,后来还有蜒、疍、蛋等同音同义异体字。历史上专指长江流域蜑民和南方沿海地区蜑民,二者属于不同族属,没有血缘关系,“蜑”也与“蛮”合用,“蛮蜑”泛指各类非汉人族群。①作为族群名称,其最早出现于西南地区,时间不晚于汉代。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就载:“(涪陵郡)土地:山险水滩,人戆勇,多獽、蜑之民……汉时,赤甲军常取其民,蜀丞相亮亦发其劲卒三千人为连弩士。”②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蜑”用来泛指长江流域地区的非汉民族,如《隋书》说:“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疍,曰獽,曰俚,曰獠,曰狏,俱无君长,随山峒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③又称:“长沙郡又杂有夷蜒,名曰莫徭,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为名……武陵、巴陵、零陵、桂阳、澧阳、衡山、熙平皆同焉。”④
此时,南方一些非汉民族也被泛称为“蜑(蜒)”,如韩愈记载的“贞元末……岭外十三州之地,林蛮洞蜒,守条死要,不相渔劫,税节赋时,公私有余。”⑤再如柳宗元的《岭南节度飨军堂记》记载到:“延群僚……卉裳罽衣,胡夷蜑蛮,睢盱就列者千人以上。”⑥胡、夷、蛮、蜑均是非汉民族的泛称,这里的“蜑”主要指南方地区少数民族。
宋代许多文献开始用“蜑”来专称“水上居民”,如《后山谈丛》解释:“舟居谓之蜑人”⑦;《桂海虞衡志》则称:“蜑,海上水居蛮也。以舟楫为家,采海物为生,且生食之。”⑧《岭外代答》则称:“以舟为室,视水为陆,浮生江海者,蜑也。”⑨“蜑户”作为族群称谓,最早出现在北宋《太平寰宇记》中,其文称:“蜑户,(新会)县所管,生在江海,居于舟船,随潮往来,捕鱼为业,若居平陆,死亡即多,似江东白水郎也。”①
根据对“蛋”的出现时间、地点,以及其所指代的族群的不同,我们认为:随着中原地区汉人势力慢慢向边陲渗透,华夏边缘也由北往南移动,汉人常常以一些旧有的族称,用以称呼一些新发现的非汉族群。这些族称通常作为蔑称,中原华夏人以正统文化自居,对边陲非汉人群贴上标签,以此作为区分华夷的族群边界。
四、“盘瓠子孙”族群边界的移动
盘瓠,也作槃瓠,后世的畲族族谱中也有写作“盘匏”的。盘瓠传说是南方族群重要的研究内容,一些学者认为,正是因为有着共有的盘瓠信仰,使得畲族与苗、瑶等民族可能存在某种亲缘关系。②
盘瓠传说在广大南方地区分布,一方面是随着盘瓠蛮的南迁,盘瓠传说也由荆楚地区向西南、华南等地区传播;另一方面,华夏人群对其他非华夏人群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正如上文所述的“蛮”“蜑”也是一个不断被发现、被冠名的过程,有关“盘瓠”出现的时间与地区的开发顺序有着特定的关系。也就是说,盘瓠信仰固然与蛮族南迁有关系,也与华夏心目中“盘瓠”概念南移有关系。
关于盘瓠传说系统论述,最早见于南朝范晔的《后汉书·南蛮传》,其资料来源主要来自于东汉应劭的《风俗通》、曹魏鱼豢(生卒年待考,三国时期曹魏国郎中)的《魏略》、晋代干宝的《晋纪》及《搜神记》等书。近代以来,一些学者对盘瓠进行考证与解读,陈登原先生是其中一位较早对盘瓠研究的学者。他在《国史旧闻》第一册中“槃瓠”条详细考证了槃瓠的渊源流变,并在结尾处论述道:“槃瓠之说,虽曰生于东汉之季,起于荆湖之区,贵州、四川、云南、福建、浙江、广东、广西亦皆有之,是其分布,已达八省之多。若依《续云南通志》所谓‘楚、粤、黔皆有之’,则是湖北亦当有此传说。然则槃瓠一事,应劭初记,范晔集成,至于近世,尚不失为南方九省之大掌故也。至于此事,自属荒昧之记。如太昊蛇形,炎帝蛇首(原注:《北堂书钞》卷一),汤之先世,出于燕卵(原注:《诗·玄鸟篇》郑氏注),可知即在汉族,固亦往往而有,存而弗论可也。”①
在这段文字中,陈登原先生表达了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认为槃瓠之说起源于东汉的荆湖地区,至今在广大的南方地区仍流传着;二是认为槃瓠传说虽然荒诞不经,但即使是汉族,也流传着类似的、同样是异于常理的祖先传说。
实际上,盘瓠传说出现的时间可能早于东汉时期,最早出现的地点也非荆湖地区,而可能在中国的西北地区。晋代郭璞在为《山海经》作注时,将狗封国与盘瓠联系起来,他写道:“昔盘瓠杀戎王,高辛以美女妻之,不可以训,乃浮之会稽东海中,得三百里地封之,生男为狗,女为美人,是为狗封之国也。”②郭璞在其《玄中记》中也有狗封国氏与盘瓠之说的记载,与上述内容相近③。狗封国在《山海经》中又作犬封国,《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有人曰大行伯,把戈。其东有犬封国……犬封国曰犬戎国,状如犬。有一女子,方跪进柸食。”④
犬戎一般作为西北地区非华夏人群的称谓,而根据郭璞注释,“狗封之国”可能在“会稽东海中”,二者在方位上似乎存在矛盾。袁珂先生在《山海经校注》中作出解释称:“封、戎音近,故犬封国得称犬戎国。又‘犬封国’者,盖以犬立功受封而得国,即郭注所谓‘狗封国’也。伊尹四方令云:‘正西昆仑狗国。’淮南子墬形篇云:‘狗国在其(建木)东。’则狗国之传说实起源于西北然后始渐于东南也。”⑤
侯绍庄支持盘瓠传说最早起源于西北戎狄的观点,并指出:在春秋以前,盘瓠与江汉地区,特别是“武陵”或“五溪”地区居民的民族成分没有关系。⑥关于海上有“狗国”的传说,在后世的一些史料中仍有记载。如《梁书》记载道:
天监六年(507年),有晋安(晋安郡,晋武帝太康三年置,治在今福建闽侯县东北,笔者注)人渡海,为风所飘至一岛,登岸,有人居止。女则如中国,而言语不可晓;男则人身而狗头,其声如吠。①
而到了魏晋以后,文献中的盘瓠传说出现之地主要集中在长江中游地区如晋代干宝的《搜神记》称:“盘瓠死后,自相婚配,因为夫妇……即今梁、汉、巴、蜀、武陵、长沙、卢江郡蛮是也”。②干宝在《晋纪》中又称:“吴武陵蛮叛。武陵、长沙郡夷,盘瓠之后也,杂处五服,凭土阻险,每常为猱杂鱼肉而归以祭盘瓠。”③
郦道元《水经注》、范晔《后汉书》也均称武陵、长沙蛮夷为盘瓠之后。④盘瓠传说在汉魏以后已经从西北地区转移到长江中游的武陵、长沙等地区,说明在此之前,盘瓠之说可能经历了一个自西往东的一个变迁过程。
盘瓠传说的转移,有三种可能:一是长江中游等地区的“蛮”族与“犬封国”“犬戎国”有族源关系,作为一种文化传统随着族群的迁徙而向外流传;二是西部地区的“犬戎国”经过文化互动,将盘瓠传说直接传给武陵地区“蛮”族⑤;三是随着华夏化进程加深,中原华夏对南方“蛮”族有更深入的接触,从而将“盘瓠之后”这种非我族类概念转移到武陵地区,即盘瓠传说与华夏族群心目中异族概念的向外移动有关。王明珂还认为:“在魏晋时,湘西一些本地豪强由中国文献记忆中认识‘盘瓠’,因此以‘有功于中国’的盘瓠子孙自居。”⑥
汉晋以后,随着南方苗瑶语诸族华夏化进程加快①,华夏族群心目中的“盘瓠子孙”的地理人群范围往更南方扩延。南方非汉族群之所以自称是“盘瓠子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接受自身相对于汉的劣势族群地位”;另一方面“以此神圣化始祖来凝聚邻近各族群”。②唐宋以后,被称作“盘瓠子孙”的人群向南方扩延的趋势更加明显。王明珂认为,这些盘瓠子孙的在广大南方地区分布,并不是这些“蛮夷”往南迁徙,而是后来华夏开始称广西、贵州等地丘陵山地聚落人群为“猫”“猺”“獞”,并认为他们是由两湖扩散、迁移来的“盘瓠子孙”。③盘瓠种成为南方非汉族群的一种泛称,如南宋叶钱为《溪蛮丛笑》所作的序称:“五溪之蛮皆盘瓠种也……今有五:曰猫、曰猺、曰獠、曰獞、曰乞狫”。④
而从宋代开始,猫(苗)苗人、猫、猺等族群称号,也普遍被华夏族用来称呼南方各非汉人群。⑤如南宋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称:“猺本盘瓠之后,其地山溪高深,介于巴蜀、湖广间”。⑥清初的闵叙所著的《粤述》称:“百粤诸蛮,丑类至繁,然大要不出猺、獞二种,皆盘瓠后也”。⑦清康熙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诸蛮种落不一,皆古槃瓠之种也。”⑧可见,“盘瓠”传说不仅流传地域广,而且有多元的族群视其为共祖,有着相同的或相似的祖源记忆,许多文献将百越、诸蛮统称为盘瓠之后。而实际上,并非所有的南方蛮族均是盘瓠子孙,也并非所有具有盘瓠传说的族群均是盘瓠蛮南迁的结果。或许可以认为,将南方各蛮族视为盘瓠之后,只是华夏族民族观念在“异族”中的其中一个体现而已。如魏晋以后盘瓠在武陵地区盛行,明清以后,盘瓠传说在该地区反而不流行,而转向西南或东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这也说明华夏边缘漂移的可能性。
总之,盘瓠传说可能产生于战国以前的西北地区,汉晋以后转移到长江中游地区,唐宋明清以后广泛流传于南方各省区。关于这种变化,除了盘瓠子孙确实南迁外,汉人的认识或者南方少数民族借用盘瓠传说应该更值得信赖。
第四节 宋代“畲”汉族群边界的形成
族群边界既是自然生态、族群迁徙的客观结果,同时也是一个主观建构、文化再造的结果。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贴上族群标签,其目的在于通过对“他者”的建构来强化对“自我”的认同,从而实现资源的争夺①。宋代时期,“畲”汉边界形成,这种边界的划定,是“畲”汉人群集体意识的结果。
一、唐宋时期南方汉族文化认同的增强
在唐宋以后,关于南方地区“莫徭”“峒蛮”“蛮僚”的记载日益频繁见诸史料,这既体现华夏族对“他者”认识的加深,同时也是说明南方地区汉人意识的觉醒。这种意识的觉醒,体现在一些族群的形成与发展上,如谢重光先生指出,随着中原汉人的南迁,到了五代宋初,在漳、泉二州已经形成了福佬族群。②与中原汉人同时南迁的还有而五溪地区的盘瓠蛮,这些族群“向南又折而向东迁徙”③,逐渐分布于今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广大地区,并与闽越土著及南迁汉人产生互动与交流。以上三类族群被认为是组成畲族先民的重要来源。
南方地区汉人与非汉人群的互动,既有族群间的合作,又有族群间的冲突与对抗,唐宋的一些文献记载说明了这点。如《资治通鉴》记载道:“(昭宗景福元年)王潮以从弟彦福为军统、弟甚至为都监,将兵攻福州。民自请输米饷军,平湖洞及滨海蛮夷皆以兵船助之。”④
学者一般认为“平湖洞蛮夷”就是畲族先民⑤,滨海蛮夷则应为“蜑民”。这些“洞蛮”以兵和船的形式,为以王潮为代表的汉族势力提供了帮助。再如景福二年(893年),汀州盘瓠蛮酋“钟全慕举籍听命,岭海间群盗二十余辈皆降溃,潮乃尽有五州之地。”①则说明了一些蛮夷归顺了朝廷,成为中央王朝治理地方的合作者。这种合作间接地说明了南方汉族势力的逐渐增强。
南方汉族意识的觉醒还体现在当地汉人对祖居地的解释和建构上《太平寰宇记》在记载“永泰县”时称:“《晋安记》:‘东晋永嘉之乱,渡江衣冠士族多依于此,以求安堵’。当此之时必有县,后人或更改,图未甚详悉。”②
乐史根据《晋安记》的记载,对“晋人衣冠南渡”这一历史事实做出推论,认为当时南迁汉人在南方一些地区建立州县,只不过因为建置沿革变迁或记载不详而未能使县名存留于世。这种说法在宋代以后的南方地区颇为流行。“衣冠南渡”成为一种当地汉人祖源历史记忆,并作为文本在福建等地的文献中出现如乾隆《福州府志》引宋代路振的《九国志》称:“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黄、陈、郑、詹、邱、何、胡是也。”③《八闽通志》卷之三《地理》风俗引《建安志》称建宁府:“自五代乱离,江北士大夫、豪商巨贾,多逃难于此,故云云。”④
王明珂先生指出,一定的历史记忆产生于特定的社会情境中,而这种社会情境又与当时的历史心性息息相关。⑤因此我们认为,隋唐以后南方蛮族记载的增多以及汉人祖源地传说的建构,均是在南方地区汉人势力崛起这种社会情境中产生的。
唐宋或更早时期,华南地区处于帝国的边缘,这种边缘性不仅反映在政治地理上,更反映在文化阶序上。随着汉族势力在南方地区的增强,处于帝国边缘地区的南迁汉族或当地汉族土著为了提升自己的族群身份,往往对本族的历史进行建构。上述所举例子说明,当地汉人希望通过回忆或者建构类似“衣冠南渡”的历史来增强华夏认同,从而提升本地汉人的族群地位,并在资源竞争中取得优势。在汉人心目中,早在汉晋时期,本族群的祖先就来到包括福建在内广大南方地区,这进一步证明本地汉人在此地开发、经营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汉人增强文化认同主要通过两个手段:
一是建构自己的“汉人”身份。如帝国的华夏化进程中,地方土著积极向汉族或中原王朝靠拢,如积极协助政府在南方地区建立政治机构,“请书版籍”,成为政府的编户齐民后,意味着族群从“化外”向“化内”转变;再者就是通过“攀附”的手段对先祖进行建构,将本家族的迁居地、迁居祖先与中原发生联系,向本族和外界宣称“黄帝后裔”的中原正统身份。
二是与“蛮夷”划清界限。如在宋代开始,陈元光家族被描述为来自光州固始,且受命于朝廷“平蛮”的中原正统家族。一些非陈姓的汉人,通过建构本族为陈元光“部属”的历史记忆,说明本族与陈元光家族一样,均是中原正统身份。这种历史记忆间接反映了宋明以后,闽南等地区汉人意识的觉醒,他们希望通过将本族群与当地蛮夷截然区分,从而建构其本族非蛮的历史逻辑。
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的文献对陈元光记载甚多,陈元光因此被认为是开发漳州的重要人物,以致后来被人们尊奉为开漳圣王,成为流行于闽台诸省重要神明。而实际上,陈元光在唐代的形象与后世的形象相差较大,其中经历了一个历史人物建构的过程,而这种建构与闽南地区的汉族认同有特别大关系。唐代对陈元光的记载不多,目前所能发现的关于陈元光事迹的文献记载为张鷟的《朝野佥载》,其文称:“周岭南首领陈元光设客,令一袍袴行酒,光怒,令曳出,遂杀之。须臾,烂煮以食客,后呈其二手,客惧攫喉而吐。”①
作者张鷟的生卒年不详,但生活年代与陈元光相差不远,其所载的关于陈元光内容,纵使不一定是历史事实,至少反映了时人对陈元光其中一个印象的理解。作者将陈元光这种残暴的性格特征与岭南首领相联系,反映的是北方汉人对南方土著的印象。宋代《太平广记》在引用以上史料时,特意将其置于“酷暴”一节之中。②可以说,唐代时期对陈元光的记载不多,且较多为负面形象。从宋代起,漳州地区开始流传陈元光平贼立功的传说,并建庙对其奉祀。宋代漳州令吕璹有诗写道:“当年平贼立殊勋,时不族贤事忍闻?唐史无人修列传,漳江有庙祀将军。”③
前文已经说明,宋代时期福建等南方地区汉族意识逐渐增强,塑造陈元光平蛮的形象就是将本族群与“蛮”相区别,借以证明自己的正统身份,这应该是
陈元光形象塑造的滥觞。而后,到了明清时期,各种方志、族谱不断塑造陈元光的光辉事迹①,兹不赘述。
由此可见,从唐到宋,及至明清,陈元光的形象逐渐丰满,并以将军、儒士、神明等形象最终出现在人们面前,这是一种不断层累、“枝叶其说”的历史建构过程。这种建构的力量来源于闽南等地汉人文化认同的需要。
苏永前通过人类学视野对陈元光“开漳”传说进行分析,他认为该传说的叙事主体为闽南地区中原移民,而传说的产生与传播则是该族群文化认同的主观结果。这种认同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对自我的“圣化”和“神化”,另一方面是对他者的“非人化”与“妖魔化”。②由此可见,将本族与“蛮夷”区分开来,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证明本族群的纯正中原血统身份,这是一种主观认同的表现。
除了陈元光家族外,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为宁化巫罗俊家族。黄向春根据杨澜的《临汀汇考》中有关隋唐之际巫罗俊“请授田”的记载,说明当时出身“蛮夷”的地方豪酋通过与官府的相互利用与合作而进入正统社会的主体之中,成为南方汉人的重要来源及汉人社会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力量。③
黄氏所引的《临汀汇考》关于巫罗俊事迹的记载,基本上沿用李世熊修所纂的康熙《宁化县志》,较原文略有出入④。而巫罗俊的事迹则是来源于巫氏家谱,清代王捷南称:“明李世熊《答巫以侯书》辨巫罗俊事颇详。书言谱修于明初,旧志盖据巫氏谱也。”①除了《宁化县志》的记载外,巫罗俊不见于其前诸史籍。以明初族谱记隋唐之事,显然不能当做历史的真实。笔者推测,巫罗俊传说本质也同陈元光传说一样,都是对祖先的历史记忆的重构,目的在于创造与汉人正统性的连接。②
二、标签化与作为族群文化特征的“畲”
刘志伟通过对清代以后珠江三角洲沙田区和民田区研究后发现:二者“并不简单地只是土地自然形态的差别,实际上是在地方社会历史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经济关系、一种地方政治格局、一种身份的区分,甚至是一种‘族群’认同的标记。两个区域之间,除了自然形态的差异外,更存在一种独特的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③就此而言,畲田经济与农耕经济在某种程度上,也不仅仅是经济形态的区别,其中暗含着一种社会阶序、族群格局。确切地说,在华夏民族观念中,从事畲田的族群是不受王化的“非我”族群,而实行农业的则是王朝子民,二者存在着明显的“华夷之别”。将某一类族群归为“异类”,意味着其无法与华夏族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源享有同等地位。在唐宋时期,“畲”作为一种族群标签,充当了“异类称呼”的角色,这种贴标签的过程是伴随着华夏族的族群认知一起进行的。
在隋唐以前,由于南方开发缓慢,作为一种耕作方式“火耕”“水耨”等词语常用于表示一个地区经济落后、蛮荒化外、教化不及的状态。如《史记·平准书》载:“江南火耕水耨,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④《汉书·武帝纪》:“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⑤《汉书·地理志》又载:“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⑥,《盐铁论·通有》云:“荆、扬……伐木而树谷,燔莱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广而饶材。”①《晋书·食货志》:“江西良田,旷废未久,火耕水耨,为功差易。”②《隋书》:“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湿,无有蓄积之资。诸蛮陬俚洞,沾沐王化者。各随轻重,收其赎物,以裨国用。”③有的记载甚至直接将“火耕”“水耨”等耕作方式认为是蛮獠的习俗,如《唐大诏令集》载:“闻岭外诸州,居人与蛮獠同俗,火耕水耨。”④按照文中意思,“居人”相对于“蛮獠”,应该是汉人;“火耕水耨”是“蛮獠”的风俗,汉人在耕作方式上被同化了。
有的甚至引用春秋以前的休闲耕作制度来形容一个地方的未开发程度,如万历《古田县志》记载如下。
林谞《闽中记》:开元二十八年,都督李亚丘会溪峒逋民刘疆辈千余计归命向化,乃状其事以闻。越明年四月二日,命下允俞而始立邑,当环峰复嶂间,平陆三十五里,版垣墉高丈许,步三百周。树室辟户,张官置吏,子男之邦,周宏远规。先是,田畯锄芜敷菑,为厥疆亩,因著之名。⑤
林谞《闽中记》修于唐大中年间,是福州较早的一部方志,已散佚,林谞事迹见诸《八闽通志》⑥。林谞用“田畯锄芜敷菑,为厥疆亩,因著之名”来解释古田县名的由来,其中“田畯”“敷菑”“疆亩”的典故出自《诗经》《尚书》等文献,⑦均是春秋战国以前休闲耕作制生产及其管理的专用词语。林谞用典的寓意:或者是好古,用典溯及三代,言辞溢美;或者用以说明古田设县之前,该地“溪峒逋民”的生产方式仍很落后。
可见,主流文化圈时常将一个地方的开发程度与当地的农业方式联系起来,其中有一部分记载并不都符合史实,显示的是主流文化圈在“南北问题”上的文化偏见。唐宋以后出现的大量与“畬”有关的文学作品,并有许多与山区的非汉民族联系在一起,除了一部分写实、猎奇的功能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用“畬”来区别族群,如上述所说的莫徭、蛮、獠等。唐宋时期“畬田”农业与一些非汉族群的分布地区的高度重合,原本就带有“华夷有别”文化偏见的汉人将“畲”作为一种族群标签贴在某类族群身上。
如前所述,唐宋畲田区域逐渐缩小,刚好一些南方山林地带的非汉民族仍保存着这种古代农耕残存形态。如唐代刘禹锡之《莫猺蛮子诗》称莫徭实行刀耕火种,该诗写道:
莫徭自生长,名字无符籍。市易杂鲛人,婚姻通木客。星居占泉眼,火种开山春。夜渡千仭溪,含沙不能射。蛮语钩辀音,蛮衣斑斓布熏狸掘沙鼠,时节祠盘瓠。忽逢乘马客,恍若惊麕顾。腰斧上高山,意行无旧路。①
宋代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记载了一些被称为犵狑、犵獠、犵榄、山猺等非汉族群刀耕火种的习性:“辰、沅、靖州蛮有犵狑,有犵獠,有犵榄,有犵㺏,有山猺,俗亦土著,外愚内黠,皆焚山而耕,所种粟豆而已。食不足则猎野兽,至烧龟蛇啖之。”②
畲已然成为非汉族群一种特征,因此也为后来将一部分实施刀耕火种的族群称为“畲”埋下铺垫。饶宗颐先生在《潮州志》中曾对畲民来源进行考证,他说:“考畲民本山越孑遗……畲民山居,亦称山輋或山人……宋谓之畲或輋,以其民居山谷烧田为生,故以此名之。畲取义于田,輋取义于山。盖山越也称山民,后人专以山民呼之,寖失越名,以其居于近山之地,遂相呼曰輋。”③饶先生认为,畲民可能源于山越,只不过因为“山居”或“烧田”而被称为“輋”或“畲”,所谓“畲取义于田”“輋取义于山”。言下之意,“輋”和“畲”均为其他族群(主要是汉人)对“山越”的他称。如果这种推论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历史上与畲民有关的诸多称谓,如明清时期“棚民”“菁民”等,这些称谓的出现,与当时的生态语境和文化语境也是息息相关的。
当一个族群标签被贴上后,一些经济方式、经济作物也逐渐与该族群发生联系,这是文化再创造的结果。如出产于广东、福建等地区的稜(菱)禾,在宋代时并未完全与畲族有联系。《方舆胜览》对梅州程乡的菱禾进行了记载:“土产菱米,不知种之所自出,植于旱山,不假耒耜,不事灌溉,逮秋自熟,粒米粗粝。”①
而到了明清以后,稜禾(菱禾)均与畲族等非汉民族发生了联系,如明嘉靖《惠安县志》:“畬稻种出獠蛮,必深山肥润处伐木焚之,以益其肥,不二三年,地力耗薄,又易他处。近漳州人有业是者,常来赁山种之。”②清代《临汀汇考》称稜禾又叫畲米,分为两种,“畲客开山种树,掘烧乱草,乘土暖种之。分粘不粘两种,四月种九月收,六月八月雨泽和则熟。.”③清唐赞衮《台阳见闻录》称:“畬稻,种出獠蛮,晋江四十七都多种之。”④再如刀耕火种也打上了族群的烙印,《广东通志》:“畲蛮,岭海随在皆有之,以刀耕火种为名者也。”⑤
畲的最初形态除了经济形态,还有与“峒”有相类似的聚落或地名特征。在宋元,畲也被视为地区或聚落的名称,“畲”与“峒”一样,都有一个从“聚落”“地名”到“族群”含义转化的过程。笔者认为,这种转化有时候是可逆的,即:住在“畲洞”里的人被称为“畲民”,而畲民聚居的地方可能又被称为“畲洞”。实际上,南方的许多族群名称都经历了这种转化过程,如瑶,一般认为是由“莫徭”转化而来,因“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为名。”⑥再如僚(或獠),按郭璞的《史记·集解》解释为:“僚,猎也。”《索隐》引《尔雅》又云:“霄猎曰僚”。⑦清代梁绍献《南海县志》:
岭表溪洞之民,号为峒僚,古称山越。唐宋以来……其余不可羁縻者,则依山林而居,无酋长版籍,亦无年甲、姓名,以射生物为事,虫豸能蠕动,皆取食之,谓之山獠。①
可见,“僚”的原意与狩猎有关,许多南方非汉族群僻处山林,一般都具有狩猎技术,并有许多以此为主要生计来源。而华夏民族将这种族群印象特征化、标签化,慢慢地被用来泛指代古代南方非汉族群。因此,如果按生态语境——文化语境的角度,我们就可以更好地去理解一些族群称谓现象。
三、族群边界冲突与南宋“畲”族群称谓的出现
关丙胜指出:“古代族群边界首先是由自然生态环境营造和维持的,族群之间的边界就是自然生态之边界,当由自然生态决定的族群地理边界随着族群的发展而不断突破时,以占有更多生态资源为主要目的边界扩张势必使原本远离的族群因各自的扩张而发生边界冲突。”②在本章第一节,我们已经较为详细地说明了帝国经略后,给族群格局带来的变化。在福建地区,这种变化在南宋时期变得更为明显,族群的冲突更为严重。
朝廷对一些偏远的非汉人群所在地区,实行的是羁縻政策,在汀州,一般认为是畲民聚居的地区,在早期也是实行族群自治政策。如杨澜在《临汀汇考》中写道:“畲之在闽,所谓被之声教,疆以戎索也。”③这里引用了两个典故来说明畲民的政治管理情况:“被之声教”④说明畲民在礼乐教化,即文化上受到华夏文明的恩泽;“疆以戎索”⑤说明采用羁縻政治,由畲民自我管理。以上两个合起来说明畲族名义上受朝廷管辖,实际上是自我管理的一种状态。到了宋代,“畲”与汉之间族群开始冲突,并作为一种独特的族群进入汉人的视野中。南宋景定年间,刘克庄撰写的《漳州谕畲》,反映了“畲”汉族群扩张而发生边界冲突的情况,刘克庄在《漳州谕畲》开篇写道:
自国家定鼎吴会,而闽号近里,漳尤闽之近里,民淳而事简,乐土也。然炎绍以来,常驻军于是,岂非以其壤接溪峒,茆苇极目,林菁深阻,省民、山越,往往错居,先朝思患预防之意远矣。凡溪峒种类不一:曰蛮、曰猺、曰黎、曰蜑,在漳者曰畲。西畲隶龙溪,犹是龙溪人也。南畲隶漳浦,其地西通潮、梅,北通汀、赣,奸人亡命之所窟穴。①
由上可知当时族群边界冲突的原因:一是国家政治中心移到“吴会”(杭州),与浙江相邻的闽西南成为地理版图上“近里”,间接说明汉族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势力迫近漳州;二是漳州“壤接溪峒”,地理位置上接壤非汉地区,文中又说其地“西通潮、梅,北通汀、赣”,所指的“溪峒”应该是潮、梅、汀、赣等地,而宋代盘瓠蛮已广泛分布以上地区,其迁徙呈“向南又折而向东”的趋势,这种扩张趋势显然会遭遇漳州以东强大的汉族势力;三是此时的漳州已呈现出“省民、山越,往往错居”的状态,“先朝思患预防之意远矣”,说明“华夷”的地理边界已经被突破,族群间互动几率较大,官方出于军事防御考虑也好,出于“严夷夏之防”观念也好,总之漳州的边界冲突已然明显。
漳州汉民与“畲”民族群边界清晰,不仅体现在族称差别上,还体现在刘克庄书中所描述的族群间的巨大文化差异:畲民具有“长技止于机毒”“刀耕火耘”“崖栖谷汲”“猱升鼠伏”的生产生活习俗,“反复杰黠”“自称盘护孙”的社会心理和宗教信仰以及“畲民不悦(役)”“畲田不税”“有国者以不治治之”“贵豪辟产诛货”“官吏征求土物”的政治待遇。②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这么推论:“畲”、汉两大族群势力此时在一方或彼此扩张过程中,发生边界冲突,在各自文化认同的影响下,族群间的文化差异被放大,并带有文化偏见,如以“猱”“鼠”的动物习性来形容畲民的习惯等,而恰好掌握史料话语权的汉人士大夫代表刘克庄充当了这历史变化时刻的见证者。换言之,假如话语权掌握在“畲”的手中,其记载定然描述汉人种种负面形象,正如后世流传在畲民中的《高皇歌》所描述的一样。③
漳州“畲”、汉间的族群矛盾不是一开始就有的,直到北宋元丰年间,漳州社会比较安定。宋代王象之《舆地纪胜》载漳州风俗形胜时称:“元丰五年(1082年),郭祥正记云:‘闽之八州,漳最在南,民有田以耕,纺苎以为布,弗迫于衣食,乐善远罪,非七州之比也’云云。”①
而过了近200年的南宋刘克庄时代[按《漳州谕畲》于宋景定三年(1262年)],漳州的各族群间的矛盾开始紧张起来:漳州以东为福佬人的势力,潮、梅以西为广府人势力,汀、赣以北则是北方汉人的势力,而闽粤赣交界地区是“溪峒”(有一部分为“畲”)的族群势力。漳州、潮州当时都出现了“畲”“輋”的称呼,宋人蔡襄曾写道:“今来闽中,最急惟是贼盗群众与漳、潮之民为害。”②《宋史·许应龙传》记载:“距州(潮州)六七十里曰山斜,峒獠所聚,匄耕土田,不输赋,禁兵与哄,应龙平决之。”③山斜中的盗贼或“峒獠”应该与“畲”(輋)民有关,乾隆《潮州府志》记载宋宝祐五年(1257年)潮州知州洪天骥防御盐寇、輋民的事迹:
洪天骥,字逸仲,号东岩,晋江人。由朝散郎知潮州,治国事如家事,视民瘼如己疾,治无不为,为无不尽。潮与漳、汀接壤,盐寇、輋民群聚剽劫,历任以州兵单弱,山径多蹊不能讨。公应变设奇,降者相属,又于接境置屯,多者三百人,少者二百人,犄角为援。且严保伍之令,以澄其源,闻于朝并下之,漳汀仿此。④
可见,在南宋时期的漳州、潮州均有不少数量的畲民族群存在。与漳、潮相邻的汀州,在唐宋时期一直被认为是“畲猺”聚居地,如清代杨澜在《临汀汇考》中写道:“唐时,初置汀州,徙内地民居之,而本土之苗,仍杂处其间,今汀人呼为畬客。”⑤然而“畲”作为一个族群的具体记载却不是首先出现在汀州,而族群边界的理论恰好可以解释其原因。
从唐代以后,王朝在南方广置郡县,在政治上掀起了对福建地区的华夏化运动,中央王朝的势力开始深入边陲,帝国的“开山洞”正是这个运动的表征之一。两宋时期,中国经济完成重心南移,南宋偏安,福建与南宋政治中心相邻,这个时期的福建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都处于历史最发达时期。然而,在福建地区,各地汉族势力发展并不均衡,在开发较早、地理条件较优越的平原、盆地地区如福州、泉州、建州等地,经济文化发达;而开发较晚、地理条件较差的汀州、漳州等地区,仍被认为是“难治”地区,也是“盗贼渊薮”。
古人文人把唐代以前的漳州视为蛮荒之地。柳宗元(子厚)《登柳州城楼寄汀、漳、封、连四州刺史》云:“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轻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浸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粤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①
唐朝时期,漳、汀属江南道,封、连则属岭南道。柳宗元谪居柳州“共来百粤文身地”,都是与中原风土截然不同的地方,不仅仅是地理的隔绝,更多的是文化的隔阂。再如明人张燮在《清漳风俗考》认为在汉迁徙闽越到江淮以后,漳州是“羁縻瘴乡,声教尚阻”,他继而引用南朝沈怀远的诗句“阴崖猿昼啸,阳亩秔先熟。稚子练葛衣,樵人薛萝屋”,感叹漳州“萧索景象至今可覆案也。”②
唐宋时期的汀州也属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与福建其他地区相比,汀州的开发时间及进程与均较为滞后,直到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汀州才被奏置。有的文献将唐宋的汀州视为“穷处”“绝区”,如《舆地纪胜》载:“汀为州,在闽山之穷处,复嶂重峦,绵亘数百里,东接赣水,南邻百粤。闽部所隶八州,而汀为绝区。”③
《临汀汇考》也将汀州描述是“七闽穷处也,蕞尔一城,孑然于蛮风蜒雨中。”④《元一统志》引《广陵志》以诗的形式说明了汀州地理条件的险恶:“全闽形势数临汀,赣岭连疆似井径。江汇重渊锁地脉,山横华盖应天星。”⑤
此外,汀州内部蛮夷众多,周围山洞阻隔,北方中原(汉)文化未能在本地区占主导地位。《太平寰宇记》称汀州与建州交界的沙县:“自乾符后,土寇乱离,汉路阻隔”。①清代王捷南《闽中沿革表》则称:“……(汀州)其东北境,今长汀、宁化地毗连将乐、邵武一带,自是山洞盘互,道梗未通。”②按此前的理解,山洞应为非汉人群的聚居地,“山洞盘互”则间接说明当时“蛮夷”数量之多。《临汀汇考》则直接说明当时汀州为“峒民”“苗人”散处之地,其文曰:“长汀为光龙峒,宁化为黄连峒。峒者苗人散处之乡。大历后始郡县其巢窟,招集流亡,辟土殖谷而纳贡赋。”③
此外,历史上还曾发生“黄连峒蛮二万围汀州”④之事,该事件足见汀州非汉族群数量之多,汉文化在蛮夷文化中,犹如大海的孤岛。谢重光先生研究发现:南宋时期,虽然汀州城区及附近聚集较大数量人口,但汀州的“外邑”,特别是广大山区呈现出与郡城完全不同的文化面貌,经常表现为“一幅基本未开化的蛮夷景象”。⑤其实,闽粤赣地区这种政治中心与周边山区“华、夷”势力状态一直延续到元明时期,如明代李东阳在其《赣州府复修长沙营记》载:
眷兹南服,若赣、若惠、若潮、若汀、漳诸郡,衣冠文物与中州等,惟是万山蟠结,溪峒深阻,其风气郁而不畅,故其人所禀,颇多顽悍之质。⑥
在这种“蛮风蜒雨”中,作为掌握着史料话语权的汉人,把本族群与非汉族群区别开来的方法,就是把族群文化与中原联系起来,如庆元年间(1195—1200年)汀州教授陈一新在《跋赡学田碑》中写道:“闽有八郡,汀邻五岭,然风声气习颇类中州。”①这种不断强调“中原文化认同”的叙述模式,反映的是宋代以来,福建本土逐渐融入中原主流文化过程中的一种心理反弹,在表明自身文化历史渊源的同时,似乎更加强调其作为中原文化传承的正统性。②
而同时代的刘克庄描写漳州则称:“风烟绝不类中州”③,谢重光先生将《跋赡学田碑》与刘克庄诗对比后认为:“一说汀州颇类中州,一说漳州绝不类中州,可见在当时人眼中,汀、漳两州虽然境土相连,区域文化面貌和族群人文性格是迥然不同的。凡此都充分说明,宋代赣南、闽西确已形成彼此相似而与其他相邻地区迥异的独特区域文化风貌和独特族群人文性格。”④唐宋时期漳州与汀州族群格局有所不同。应该来说,汀州的非汉人群比例更高一些,如果以孤岛与海洋的关系去探讨不同地区华、夷的族群格局,那么,唐宋时期的汀州,汉人显然是处于孤岛的地位。
实际上,“畲”、汉间的边界是多重的,在族群边界冲突更明显的漳州族群边界更清晰,掌握史料话语权的汉族在本族群势力较强的漳州证明他者为“非”(汉),在本族群势力较弱的汀州证明自己为(汉),本质都是在维护族群认同总之,随着南宋时期“畲”、汉边界的划定,“畲”作为一个在文化特征迥异于汉人的特殊族群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在宋元时期的东南区域社会中扮演着区分人群的重要的角色。
第五节 小结
本章探讨了在华夏化进程中,特别是在华夏民族观念下,中国南方地区族群格局变化的情况,着重论述了南宋时期畲汉族群边界形成的情况。本章的主要论点有以下几点。
(1)华夏族不断向华夏核心区以外的“蛮夷”地区扩张,越来越多的非华夏族群被卷入其中。唐代以后,表现为南方各地区的“山洞”被开发,随之而产生的后果是越来越多的华夏族被纳入帝国统治范围,成为王朝的编户齐民。而一些未被“王化”的“蛮夷”,其边界只能向更边陲的地区移动,最后形成一个个漂在华夏族群“海洋”中的非华夏族群“孤岛”。随着华夏化进程加快,国家加强对边陲地区的开发,“开山洞”的政治意义在于,国家通过奏置州县、检责户口、建立行政机构,对“山洞”蛮夷地区进行控制,其文化意义在于,越来越多的非汉族群走向华夏化,成为帝国的子民。帝国对南方非汉民族地区的经略是漫长而复杂的过程,除了政治军事运动外,更多是对该地区采取文化教化。宋代以后,南方山洞成为一个个被汉族“海洋”包围的“孤岛”,并且随着华夏化进程的加快而逐渐消失,这在客观上显示了“畲”汉边界的移动情况。
(2)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华夏族形成“华夷之辨”的“天下观”或“异己观”,这种族群观念的心理优越性,使其具有向外扩张的驱动性。中原华夏族对周边的非华夏人群认识加深,越来越多的“他者”族群被发现,并随着华夏化进程,其族群边界发生了漂移。“华夏边缘”的漂移并非一定是华夏族人口实质性迁移,也与华夏族心目中“异族”边界的漂移有关,即一些原来存在于比较中心地区的“蛮夷”称谓,后来出现于边陲地区,有可能与华夏族的族群的认识有关。本章通过华夏族心目中“山都”“木客”“蜑”以及“盘瓠子孙”等族群边界的漂移,说明了影响族群形成的“他者性”问题,换言之,以上族群的发展与变迁,很大程度上与汉文化语境有关。在先秦之前的时代,闽粤地区的主要族群为百越,秦汉以后,来自鄂湘地区的荆蛮族群南移,东南地区的族群既多且杂,中原人常混淆不清,皆以未开化的蛮夷视之,出现了一些泛称,如蛮僚、峒僚等,实际上并非一个族群。随着族群接触的增多,对地方族群认识加深,汉人在主观上对这些蛮夷的族群分类也会更加详细。这种族群分类的细化,不仅仅是蛮夷本身自身演化分离的结果,还得从认识论的角度去分析其成因。
(3)在华夏中心族群观念和意识下,“畲”作为族群称谓应被认为是华夏异己观下的一种文化建构。把非汉民族以一定的特征联系起来,恰好一些仍维持古老农业形态的畲田方式的非汉族群被贴上“畲”的标签。然而正如文中所称,这种标签更多的是文化的标签,一些进入国家控制之内的“畲民”“峒民”不再被视为非汉民族;而原来一些可能是汉族的,因为“逋逃”或叛乱的,则被贴上“畲”或“峒”的标签,“畲”称谓的出现标志着“畲”汉边界的形成。两宋时期,中国经济完成重心南移,随着汉族势力在福建的扩张,其与“溪洞种类”在福建广东遭遇,“畲”作为一个族群称谓的记载,也最先出现在畲汉边界的漳州、潮州地区。
附注
①罗新:《王化与山险——中古早期南方诸蛮历史命运之概观》,《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第4-20页。
②徐杰舜等学者提出“雪球”理论,用“雪球”比喻在春秋战国以来华夏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他们认为雪球“不仅在夏、商、周、楚,越诸族之间滚动,而且还在部分蛮、夷、戎、狄中滚动更重要的是在雪球的滚动中,各民族之间的界限逐渐消失,许多小雪球开始滚成一个大雪球”徐杰舜主编:《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页。
③费孝通等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21页。
①罗新:《王化与山险——中古早期南方诸蛮历史命运之概观》,《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第5页。
②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63-184页。
③罗新:《王化与山险——中古早期南方诸蛮历史命运之概观》,《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第5页。
④按《周礼·夏官·职方氏》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贾公彦疏:“叔熊居濮如蛮,后子从分为七种,故谓之七闽。”
⑤[宋]欧阳忞撰,李勇先,王小红校注:《舆地广记》,见《宋元地理志丛刊》,卷三十四《福建路》,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第1054-1070页。
⑥[宋]祝穆撰,施和金校:《方舆胜览》,卷十《福建路》,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63页。
⑦朱维干:《福建史稿》,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页。
⑧[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九五《闽越王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①谢重光先生推测,被迁徙的只能是闽越国的上层统治人物以及一部分军队而已,还有大量的普通民众留在当地。、参见谢重光:《畲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9-51页。
②[唐]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寄汀、漳、封、连四州刺史》,载[清]吴宜燮修,黄惠,李畴纂:《龙溪县志》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修,卷二十二《艺文》,第310页。
③[明]王士性撰,吕景琳点校:《广志绎》,卷一《方舆崖略》,元明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页。
④关于唐宋经济重心的南移,学术界多有讨论,参见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郑学檬,陈衍德:《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若干问题探讨》,《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4期:王大建,刘德增《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原因再探讨》,《文史哲》,1999年第3期等。
⑤参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2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94页;郭沫若:《中国史稿》第3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77页;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54页。
①[美]詹姆斯·李著,朱伦节译:《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与边界扩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0年第3期,第39页。
②[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九,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17、718、722、723页。
③[日]佐竹靖彦:《宋代福建地区的土豪型物资流通和庶民型物资流通》,载《佐竹靖彦史学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01页。
①[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000页。
②[清]曾曰瑛等修,李绂等纂:《汀州府志》,乾隆十七年(1752年)修,卷四十五《杂记·丛谈(附)》,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649页。
③[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五九,《唐纪》七五,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457页。
①[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000页。
②[清]梁章钜撰,王释非,许振轩点校:《称谓录》(校注本),卷二十四《布衣》,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56页。
③黎景曾,黄宗宪等修纂:《宁化县志》,卷一《疆域沿革》,民国十五年(1926年)刊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441页。
④谢重光先生认为,在黄连峒检括避役百姓与“开山峒”不完全相同,前者应是逃避贼役的汉人,后者可能有避役百姓,更多的可能是被强制为民的蛮僚。参见谢重光:《畲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0页。
①[清]辛竟可修,林咸吉等纂:《古田县志》,卷一《建置》,乾隆十六年(1751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24页。
②[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31福建路《汀州·诗》,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3798页
③[清]李维钰原本,沈定均续修,吴联熏增纂:《漳州府志》,卷二十四《宦绩·陈政》,据清光绪三年(1877年)芝山书院刻本影印,《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29.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481页。
④[明]罗青霄总纂,谢彬编纂:《漳州府志》,卷之四《漳州府·秩官志下·名宦·刺史陈元光》,明万历元年(1573年)年刻本,明代方志选第三辑,台北:学生书局,1965年,第67-68页。
⑤[清]陈寿祺等撰:《重纂福建通志》,卷八十五《关隘·龙溪柳营江把截所》,道光九年(1829年)修,同治十年(1871年)重刊本,台北: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8年,第1697页。
⑥[明]黄佐纂修:《广东通志》,卷第五十五《列传十二·人物二》,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刻本,广东历代方志集成,省部二,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辑,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1424页。
①[清]陈寿祺等撰:《重纂福建通志》,卷九《山川·漳浦梁山》,道光九年(1829年)修,同治十年(1871年)重刊本,台北: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8年,第320页。
②[元]脱脱:《宋史》,卷四九四《蛮夷二·梅山峒》,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③[清]陈寿祺等撰:《重纂福建通志》,卷一五《神宗纪》,道光九年(1829年)修,同治十年(1871年)重刊本,台北: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8年。
①[宋]晁补之撰:《鸡肋集钞》卷一,载[清]吴之振等选,管庭芬,蒋光煦补:《宋诗钞》(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l16页。
②黄闵《武陵记》已失传,《后汉书》李贤注保存其部分佚文:“黄闵《武陵记》曰:‘山高可万仞山半有槃瓠石室,可容数万人中有石床,槃瓠行迹。’今案:山窟前有石羊、石兽,古迹奇异尤多望石窟大如三闲屋,遥见一石仍似狗形,蛮俗相传,云是槃瓠像也。”详见:[南朝]范晔,[唐]李贤注:《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传·南蛮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③除了盘瓠蛮的特征外,晁补之诗中还将梅山峒蛮称为“傜”(见“幕府檄传傜初疑”句),谢重光先生推测其与历史上的“莫徭”有很大关系参见谢重光:《客家文化述论》,第69页。
①[宋]晁补之撰:《鸡肋集钞》一卷,第1116页
②[元]脱脱等撰:《宋史》,卷四百九十五《蛮夷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③按照知识考古学的观点,民间传说表面看来充满时间、空间错置与幻想的迷雾,但作为某种历史记忆的符号,它们的产生和流传过程恰恰是包含着丰富社会舆论与情境的一个历史真实。参见户华为:《虚构与真实——民间传说、历史记忆与社会史“知识考古”》,《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第162页。
④上杭树槐堂《颍川钟氏族谱》,清道光八年(1828年)手抄本,载《家族谱牒——畲族卷》(下),福州:海风出版社,2011年,第563页。
①上杭树槐堂《颍川钟氏族谱》,清道光八年(1828年)手抄本,载《家族谱牒——畲族卷》(下),福州:海风出版社.2011年,第556-557页
②关于钟姓肇居汀州白虎村的始祖及时间,不同族谱记载不完全相同,主要有二说:一说为东晋末年钟贤(妣黄氏、子钟朝)江西赣州徙居白虎村,如上杭树槐堂《颍川钟氏宗谱》(清道光八年本);或钟贤之子钟会同母从江西赣州徙居白虎村,如浦城村溪《颍川堂钟氏宗谱》(清光绪八年本)、松溪季源垅《钟氏宗谱》(民国三十三年本)、宁德市丹斗畲族村钟氏家谱等;另一说为唐末钟翱自江西赣州雩都迁入白虎村,如上杭《颍川郡坵辉钟氏族谱》(光绪三十一年本)等关于白虎村传说的版本又见蓝炯熹:《畲族家族文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52页。
③文中提到钟氏兄弟七人变卖产业,悉舍入开元寺,后被南唐檀越主,关于舍田这个传说,笔者认为这与谢重光先生所论的蓝文卿舍田宅建雪峰寺传说有相似之处,其背景应该在明代佛教严重世俗化与社会普遍佞佛风气下,钟氏宗族建构的一种历史记忆。于蓝文卿舍田宅建雪峰寺传说的考证,详见谢重光:《唐代经济史的一桩公案:蓝文卿舍田宅建雪峰寺传说辨伪》,《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3期,第116页。
①钟大荣修纂:浦城村溪村《颍川堂钟氏宗谱》,清光绪八年(1882年)刻本,载《家族谱牒——畲族卷》(上),福州:海风出版社,2010年,第430-431页。
②上杭树槐堂《颍川钟氏族谱》,清道光八年(1828年)手抄本,载《家族谱牒——畲族卷》(下),福州:海风出版社,2011年,第566-567页。
①关于“郎名”习俗来源,罗香林先生认为源于畲族,客家先民受其畲族;李默则认为“郎名”畲族与客家先民在闽粤赣边中形成的;董建辉则认为畲族与客家郎名发展演变线索大概为:避乱南迁的客家先民“迁徙到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带后,与当地土著畲民交错杂居,从而将郎名传播给了畲族。畲族在接受源自汉族的郎名之后,又根据其自身的文化传统,进行了部分改造,使郎名的使用更加规范,从而形成了畲族的郎名文化。在畲族与客家先民相互交融的过程中,畲族郎名文化中的部分因素,如通过法事仪式取得郎名等,又反过来影响了客家先民。”参见董建辉:《畲、客“郎名”探源——兼与李默先生商榷》,《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第76页。
②李济借用萨姆纳先生概念,“我群”指的是被中国的史学家们视为同类的文明人的群体而他们所谓的野蛮人,在我们看来便可以称作“你群”。参见李济:《中国民族的形成——一次人类学的探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页。
①王妙发:《黄河流域聚落论稿——从史前聚落到早期都市》,北京: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5页、
②印纹陶是一种在陶器表面印有各种几何形纹饰,质料较硬,且为泥质与夹砂质的陶器。这种陶器主要分布在福建、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台湾、广东等地。在福建及台湾发现的印纹陶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发现的印纹陶属于周代前后,其他地区发现者属自春秋战国一直延续至汉代。参见吕荣芳:《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特征之一:印纹陶》,《厦门大学学报》,1959年第1期,第45页;邓晓华:《论客家话的来源——兼论客畲关系》,《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第146页。
③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10页。
④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南方文明》,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年,第558-603页。
①童恩正认为,环绕着中原大地,从东北经阴山山脉、贺兰山脉、祁连山脉,至西南的四川西部通向云南西北部的横断山脉,这一北一南的两列山峰及其邻近的高地,在地理上呈半月形地带;这个地带从新石器时代后期直至铜器时代,生活期间的民族保留了共同的文化因素由此将其界定为“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这种边缘地带的形成,除了生态环境因素以外,因素是生态环境,中原文化对边地文化的排斥的社会文化心理也占很重要因素
②叶舒宪:《〈山海经〉与“文化他者”神话——形象学与人类学的分析》,《海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③《礼记王制》关于“五方之民”的记载:“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参见陈戍国撰:《礼记校注》,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83页。
④这种权威性如王一川指出:“‘中国’如‘夏’,位于世界体系的‘中心’(中央),享有号令天下的最高权威,而周围各国如‘夷’,位于这个体系的边缘,必须向‘中国’主子臣服与这种中国形象相似,还有‘万方之主’‘百鸟来朝’等经典形象。”参见王一川:《中国形象诗学》,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14页。
⑤张碧波,庄鸿雁:《华夷变奏:关于中华多元一体运动规律的探索》,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页。
⑥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45页。
①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31页。
②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44-245页
③傅斯年:《夷夏东西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39页;[日]桑原骘藏:《历史上所见之南北中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9-67页
④该类研究主要代表作有:龚胜生:《2000年来中国瘴病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地理学报》,48卷,1993年第4期;左鹏:《宋元时期的瘴疾与文化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张文:《地域偏见和族群歧视:中国古代瘴气与瘴病的文化学解读》,《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于赓哲:《蓄蛊之地——一项文化歧视符号的迁转流移》,《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于赓哲:《疾病、卑湿与中古族群边界》,《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等等。
⑤于赓哲:《疾病、卑湿与中古族群边界》,《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第65页。
⑥[汉]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437页。
①[清]陈汝咸修,林登虎纂:《漳浦县志》,卷三《风土志上》,据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修,民国十七年(1928年)翻印本影印,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专辑31,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31页。
②[北魏]郦道元著;谭属春,陈爱平点校:《水经注》卷三十七,《沅水》,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第544页。
③[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外国下·五民》,扬州:广陵书社,2003年,第117页。
④[宋]朱辅:《溪蛮丛笑》,《生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史部352地理类,第59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9页。
①[明]章潢:《图书编》,卷三十四《百粤总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98-699页
②杨效知:《古诗十九首鉴赏》,《行行重行行》,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83页。
③[唐]魏征:《隋书》,卷82《南蛮》,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④[唐]刘禹锡:《刘宾客文集》,卷三《唐故福建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使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赠左散骑常侍薛公神道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唐]韩愈著,钱仲联,马茂元校点:《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铭》,载《韩愈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66页。
⑥刘禹锡《莫猺蛮子诗》:“莫徭自生长,名字无符籍……星居占泉眼,火种开山春。”刘禹锡《莫猺蛮子诗》录在南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中。[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七十三《诗话前集》,四部丛刊初编216集部
⑦唐代刘恂《岭表录异》卷中则载:“卢亭者,卢循昔据广州,既败,余党奔如海岛,野居,唯食蠔蛎,叠壳为墙壁。”宋代《太平寰宇记》卷102,泉州风俗:“泉郎,即州之夷户,亦曰游艇子,即卢循之余。晋末,卢循寇暴,为刘裕所灭,遗种逃叛,散居山海,至今种类尚繁。”参见[唐]刘恂:《岭表录异》,扬州:广陵书社,2003年,第27页;[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102,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030页。
①[清]吴宜燮修,黄惠,李畴纂:《龙溪县志》,卷二十二《艺文》,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修,第310页,
②同①,第101页。
③王韧:《建德县志》,卷三《风俗志》,民国八年(1919年)刊本。
④傅衣凌:《福建畲姓考》,载《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70页。
⑤[清]吴震方:《岭南杂记》,丛书集成初编,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复印本),第28页。
①郭志超:《闽台民族史辨》,合肥:黄山书社,2006年,第106页。
②根据郭志超先生概括,目前关于畲族的来源学说大概可以分为六种:(1)畲族源于武陵蛮;(2)畲为越人后裔;(3)畲源于“南蛮”一支;(4)畲源于河南夷;(5)畲族源于武陵蛮与闽粤赣越人后裔以及客家及其先民的融合;(6)畲族中不同群体的不同来源参见郭志超:《闽台民族史辨》,合肥:黄山书社,2006年,第482-491页。
③如主张武陵蛮说的施联朱认为决不能因为畲族中可能多少包含有越人的成分或风俗习惯而得出畲族来源于山越的结论;而主张越族说的蒋炳钊认为畲族是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古越族的后裔,并不排斥在以后历史发展过程中包括迁入这一地区的其他民族。他认为民族间相互同化的现象在历史上是经常存在的,但这部分不是主要的。参见施联朱:《关于畲族来源与迁徙》,《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蒋炳钊:《关于畲族来源问题》,《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3期;郭志超:《闽台民族史辨》,合肥:黄山书社,2006年,第490页。
④郭志超:《闽台民族史辨》,合肥:黄山书社,2006年,第489页。
①谢重光:《客家文化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84页。
②文献记载中,对非汉族群名称多有歧视意义,常加上“犬”“虫”偏旁,笔者按原文引用
③如郭志超先生认为畲族在华南地区的出现,是迁徙造成的,他指出:“关于非南岛语族的苗瑶语族群,在中国东南百越地区,亦即原南岛语族地区的出现,是迁徙的结果。”参见郭志超:《畲族文化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出版社,2009年,第41-42页。
④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64页。
①弘礼:《福建古代闽族的摩崖文字》,《义物》,1960年第6期;陈存洗:《汰溪摩崖石刻年代问题》,《福建文博》,1989年第1、2期合刊;陈龙:《华安仙字潭摩崖的考古学考察》,《福建文博》,1989年第1、2期合刊。
②刘蕙荪:《福建华安汰溪图像文字初研》,《福建文博》,1982年第1期。
③石钟健:《论广西岩壁画和福建岩石刻的关系》,《学术论坛》,1978年第1期,第28-44页;林蔚文:《福建华安摩崖石刻试考》,《福建文博》,1984年第1期;林蔚文:《福建华安仙字潭摩崖石刻再探》,《美术史论》,1987年第2期;黄起云:《仙字潭摩崖石刻散考》,载福建省考古博物馆学会编:《福建华安仙字潭摩崖石刻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第120-134页。
④王铁藩:《台湾高山族和华安仙字潭图像文字》,《华侨日报》,1986年6月24日
⑤黄仲琴:《汰溪古文》,《岭南大学学报》四卷二期,1935年;林钊,曾凡:《华安汰内仙字潭摩崖的调查》,《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1期;万里云:《仙字潭摩崖石刻的族属、年代和内容》,载《福建华安仙字潭摩崖石刻研究》,第125-146页。
⑥曾五岳:《福建仙字潭摩崖石刻初议》,《中国文物报》,1988年8月26日
⑦黄仲琴:《汰溪古文》,《岭南大学学报》四卷二期,1935年,载《福建华安仙字潭摩崖石刻研究》,第16页。
①华安县政协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福建省华安县文化馆合编:《仙字潭古文字探索(一)》(华安文史资料第六辑),1984年7月;《仙字潭古文字探索(二)》(华安文史资料第十辑),1988年6月
②福建省考古博物馆学会编:《福建华安仙字潭摩崖石刻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
③关于仙字潭石刻研究综述,详见杨青林:《华安仙字潭摩崖石刻研究史考述》,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47-50页。
④[唐]张读《宣室志》,载[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三九二“韩愈”条,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130页。
⑤[唐]韩愈:《祭鳄文》,《韩吕黎全集》卷三十四,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第929页
⑥[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百七十六《韩愈》,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62-5263页。
⑦[明]何乔远:《闽书》,卷二十九《方域》,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01页。
①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0页。
②[唐]李吉甫,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21页。
③同②
④[明]陈天定:《北溪纪胜》,载[清]吴宜燮修,黄惠,李畴纂:《龙溪县志》清乾隆二十七年修,卷二十四《艺文》,第369-370页。
⑤[清]李维钰原本,沈定均续修,吴联熏增纂:《漳州府志》,卷四十《古迹》,据清光绪三年(1877年)芝山书院刻本影印。
①[唐]慕容韦:《度揭鸿岭(漳州)》,载[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七七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926页。
②[清]冯登府编:《闽中金石志》(第3册),卷五“慕容韦揭鸿塞诗刻”条,嘉业堂金石丛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4a页。
③[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30,福建路《漳州诗》,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3777页。
④[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30,福建路《漳州景物下》,第3770页。
①[明]陈天定:《北溪纪胜》,载[清]吴宜燮修,黄惠,李畴纂:《龙溪县志》清乾隆二十七年修,卷二十四《艺文》,第369-371页。
①根据樊万春:《仙字潭与仙人峰岩刻新探》制作,载《福建华安仙字潭摩崖石刻研究》,第248页
②黄仲琴:《汰溪古文》,载《福建华安仙字潭摩崖石刻研究》,第11-12页。
③1974年,广东饶平浮滨、联饶发掘了21座古墓,出土了包括竖条纹釉陶大口尊、圜凹底罐、深折腹豆等在内的一套特征鲜明的陶器组合,伴出凹刃锛、无阑戈等石器。参见干小莉:《九龙江流域商周时期古文化分期初探——兼谈浮滨类型的年代》,《考古学报》,2010年第1期,第21页。
④徐恒彬:《广东青铜器时代概论》,《广东出土先秦文物》,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84年;朱非素:《粤闽地区浮滨类型文化遗存的发现和探索》,《人类学论文选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
①王振镛:《略论华安仙字潭岩刻研究》,载《福建华安仙字潭摩崖石刻研究》,第232页。
②如考古调查发现,华安等地曾出土一批通体磨光、制作精细的仿铜石器,如圭形石戈和大型扁平石斧以及釉陶和几何印纹陶器。参见林钊:《福建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文化时期的考古概况》,《先秦史研究动态》,1986年3期。
③王振镛:《略论华安仙字潭岩刻研究》,载《福建华安仙字潭摩崖石刻研究》,第231页。
④蔡永蒹,福建晋江县东石人,他根据文献材料及自身见闻,在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写成《西山杂记》,全书凡12卷,系抄本,从未付梓。关于书名及内容,蔡永蒹称:“盖缘吾乡起有林西山先生,垂至宋淳熙有蔡元定亦曰西山先生,因之以为归结精华,曰《西山杂志》,文章之依据为上述诸古籍以及所辑录之诸碑及志书。”参见刘浩然:《蔡永蒹〈西山杂记〉》,载陈建才:《八闽掌故大全·艺文篇》,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35-136页。
①转引自陈国强:《西山杂记记汰溪摩崖石刻的几个问题》,载《福建华安仙字潭摩崖石刻研究》,92-97页。
①[宋]梁克家修纂:《淳熙三山志》,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福州:海风出版社,2000年,序第1页。
②同①,卷之二十《秩官类一》,第226页。
③[明]黄仲昭:弘治《八闽通志》卷六二,《人物·文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①[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三二,《福建路》,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3787-3788页。
②[唐]李吉甫,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21页。
③谢重光:《客家文化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52页。
④曾祥委:《试论“客家”》,载黄钰钊主编:《客从何来》,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7页。
⑤刘镇发:《“客家”:从他称到自称》,载黄钰钊主编:《客从何来》,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77-79页。
⑥刘丽川:《深圳客家研究》,海口:南方出版社,2002年,第15-16页。
⑦学术界出版南京师范大学本关于“客家”称谓正式出现的背景、时间,地域等问题的讨论,详见谢重光:《客家文化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40-252页。
①[宋]欧阳忞撰,李勇先,王小红校注:《舆地广记》(宋元地理志丛刊),卷三:十四《福建路》,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54-1070页。
②[宋]祝穆撰,施和金校:《方舆胜览》,卷十《福建路》,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63页。
③朱维干:《福建史稿》,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页。
④[宋]朱熹撰:《武夷图序》,载《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
①[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二八,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3660页
②[清]朱珪修,李拔纂:《福宁府志》,卷四《福鼎山川》,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修,光绪六年重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57页。
③[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三零《福建路·漳州古迹》,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3773页。
④[明]黄仲昭:弘治《八闽通志》,卷八《地理·山川·漳浦县》,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⑤卢美松:《太姥传说与畲族渊源》.载《畲族文化研究》(上册).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1-10页。
⑥《高山族简史》编写组:《高山族简史》(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页。
①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专集》第廿四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16页。
②陈国强:《(西山杂记)记汰溪摩崖石刻的几个问题》,载《福建华安仙字潭摩崖石刻研究》,第95页。
③[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二,《江南东道十四·汀州》,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034页。
①[清]曾曰瑛等修,李绂等纂:《汀州府志》,乾隆十七年修,卷六《风俗气候(附)》,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70-71页。
②陈国强:《福建的古民族——“木客”试探》,《厦门大学学报》,1963年第2期
③蒋炳钊:《古民族“山都木客”历史初探》,《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第87-94页。
④黄向春:《历史记忆与文化表述——明清以来闽江下游地区的族群关系与仪式传统》,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63页。
⑤郭志超:《闽粤赣交界地区原住民族的再研究》,《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第106-111页。
⑥靳阳春发现:闽粤赣地区记载最多的是赣南,时间最早是西晋郭璞对《山海经》中“枭阳国”注,稍晚依次是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和邓德明《南康记》,南朝齐祖冲之《述异记》,南朝陈顾野王《舆地志》,曹叔雅《庐陵异物志》;记载较少的是闽西和粤东,时间上记载闽西山都木客的《牛肃纪闻》又早于记载粤东山都木客的《太平寰宇记》。在闽粤赣交界地区,赣南是最早开发的,开拓基本趋势是从南向北,由西而东,稍晚开发的是粤东地区,开拓趋势是由沿海而山区,最晚开发的是闽西地区靳阳春:《宋元汀州经济社会发展与变迁》,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30-31页
①关于山都木客消亡的原因,谢重光先生认为:“部分的原因是汉人对山都一类‘鬼物’采取了仇杀、歼灭的方针,造成山都死亡率高,有的则逃到更僻远的深山中,不为人知;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与其他族群接触、交流,被同化了。一部分汉化成为客家,另一部分与南迁的武陵蛮同化成为畲族。”谢重光:《畲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5页。
②[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999页。
③光绪甲辰《上杭中都叶氏族谱》,卷一《五郎公传》。
①詹坚固:《试论蜑名变迁与蜑民族属》,《民族研究》,2012年第1期,第81页
②[晋]常璩:《华阳国志》,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③[唐]魏征:《隋书》,卷八二《南蛮》,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④[唐]魏征:《隋书》,卷三一《地理下》,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887页,
⑤[唐]韩愈:《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铭》,载[唐]韩愈著,钱仲联,马茂元校点:《韩愈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66页。
⑥[唐]柳宗元著,曹明纲标点:《柳宗元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20页
⑦[宋]陈师道撰,李伟国点校:《后山谈丛》,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77年。
⑧[宋]范成大撰:《桂海虞衡志》(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28页。
⑨[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外国下·蜑蛮》,扬州:广陵书社,2003年版,第94页。
①[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七《岭南道一·广州》,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021页。
②凌纯声:《畬民图腾文化的研究》,《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16本,1947年,第127-172页。
①陈登原:《国史旧闻》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0页
②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07页。
③郭璞的《玄中记》称:“狗封氏者:高辛氏有美女,未嫁。犬戎为乱,帝曰,有讨之者,妻以美女,封三百户。帝之狗名槃护(《御览》引作槃瓠),三月而杀犬戎,以其首来帝以为不可训民,乃妻以女流之,会稽东南二万一千里,得海中土。方三千里,(《御览》引千作百)而封之,生男为狗,生女为美女(《类聚》九十四)。封为狗民国。(《御览》九百五,亦见《路史·发挥二》引帝以二句作‘帝以女妻之不可教训流作浮美女作美人末句作是为犬封氏’。)”参见[晋]郭璞撰:《玄中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81页。
④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07、309页
⑤郭璞的《玄中记》称:“狗封氏者:高辛氏有美女,未嫁。犬戎为乱,帝曰,有讨之者,妻以美女,封三百户。帝之狗名槃护(《御览》引作槃瓠),三月而杀犬戎,以其首来。帝以为不可训民,乃妻以女流之,会稽东南二万一千里,得海中土。方三千里,(《御览》引千作百)而封之,生男为狗,生女为美女(《类聚》九十四)封为狗民国。(《御览》九百五,亦见《路史·发挥二》引帝以二句作‘帝以女妻之不可教训流作浮美女作美人末句作是为犬封氏’。)”参见[晋]郭璞撰:《玄中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10页。
⑥侯绍庄:《“盘瓠”源流考》,《贵州民族研究》,1981年第4期,第27页。
①[唐]姚思廉:《梁书》,卷五十四,列传第四十八《诸夷·东夷·扶桑国》,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560页。
②[晋]干宝撰,汪绍楹校注:《搜神记》,卷十四《盘瓠》,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68页。
③[晋]干宝:《晋纪》,载[清]汤球,黄乔治忠校注《众家编年体晋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97页。
④[北魏]郦道元著,谭属春,陈爱平点校:《水经注》,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南朝]范晔撰,[唐]李贤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⑤如侯绍庄先生认为盘瓠传说作为一种图腾崇拜,“在社会发展特别是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往往会被原属其他民族集团的人们所接受。所以,关于盘瓠传说民族归属的变化,就是由于戎狄的南迁和民族融合的结果”,他认为西周春秋以来,随着戎狄一些支系南迁,从而将盘瓠传说带入武陵地区,但认为盘瓠蛮并非该地区的族群主体。侯绍庄:《“盘瓠”源流考》,《贵州民族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1981年第4期,第24、27页。
⑥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61-162页。
①罗新指出,六朝以后,华夏化运动以前所未有的幅度和深度进行,在长江中游的苗瑶语诸族纷纷进入华夏化的历史进程。参见罗新:《王化与山险——中古早期南方诸蛮历史命运之概观》,载《历史研究》,2008年第6期,第4-5页。
②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33页。
③同②,第164页。
④[宋]朱辅:《蛮溪丛笑》,《说郛》卷五,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
⑤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64页。
⑥[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26页
⑦[清]闵叙:《粵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2-63页。
⑧[清]陈梦雷编:《古今图书集成》,卷1410《职方典》,上海中华书局缩印本,1934年。
①萧凤霞,刘志伟:《宗族、市场、盗寇与蛋民——明以后珠江三角洲的族群与社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1-13页
②谢重光:《客家文化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56页。
③谢重光先生认为盘瓠蛮的迁徙路线可能不止一条,根据史迹推寻至少有两条路线:一条路线大概由五溪入洞庭湖,溯湘江而南,先后进至衡州、连州等地,再沿湟水、武溪等河流南下粤中,经由粤东而进至闽南、闽西北;另有一条路线,则可能由湘入赣,再由赣入闽。同②,第66页。
④[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五九《唐纪》七五,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457页。
⑤谢重光认为,在闽南和莆仙方言中,“平湖”与“盘瓠”音近,“平湖洞”可能是“盘瓠洞”之讹。参见谢重光:《客家文化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75页。
①[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九十《闽一·司空世家》,“景福二年(893年)”条、
②[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995页。
③[宋]路振:《九国志》,载[清]徐景熹主修:《福州府志》,卷七五《外记》,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根据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刻本整理,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年
④[明]黄仲昭:弘治《八闽通志》,卷三《地理·风俗》引《建安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2页。
⑤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36页。
①[唐]张〓:《朝野佥载》,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5页。
②[宋]李昉:《太平广记》,卷二百六十七《酷暴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351小说家类,第1045册。
③[明]黄仲昭修纂:《八闽通志》,卷八十六《拾遗·漳州府》,明弘治四年(1491年)刻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24页。
①参见[明]罗青霄总纂,谢彬编纂:《漳州府志》卷四,《漳州府·秩官志下·名宦·刺史陈元光》,明万历元年(1573年)年刻本,第68页;[明]黄佐纂修:《广东通志》卷第五十五,《列传十二人物二》,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刻本,广东历代方志集成,省部二.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辑,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1423-1424页。[清]薛凝度修,吴文林纂:《云霄厅志》第十一卷,《宦绩》,第401-404页;[清]陈汝咸修,林登虎纂:《漳浦县志》卷十四.《宦志·刺史》,据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修,民国十七年(1928年)翻印本影印,第996-997页,《白石丁氏古谱》上册,《漳浦县志名宦卷》,漳州市方志办编,影印抄本,厦门大学古古籍室藏,第39a页。
②苏永前:《想象、权力与民间叙事——人类学视野中的陈元光“开漳”传说》,《民族文学研究》,2011年5期,第52-59页。
③黄向春:《“畲/汉”边界的流动与历史记忆的重构——以东南地方文献中的“蛮獠——畲”叙事为例》,《学术月刊》,2009年第6期,第139-140页。
④《宁化县志》称:“先是,隋大业之季,群雄并起。东海李子通率众渡淮,据江都,称吴帝。改元明政,遣使略闽地。其时土寇蜂举,黄连人巫罗俊者,年少负殊勇,就峒筑堡卫众,寇不敢犯,远近争附之罗俊因开山伐木,泛筏于吴,居奇获赢,因以观占时变,益鸠众辟土,武德四年,子通败死。时天下初定,黄连去长安天末,版籍疏脱。贞观三年,罗俊自诣行在上状,言黄连土旷齿繁,宜可授田征税。朝廷嘉之,因授巫罗俊一职,令归翦荒以自效。而罗俊所辟荒界,东至桐头岭,西至站岭,南至杉木堆,北至乌泥坑。乾封间乃改黄连为镇。”载[清]李世熊:《宁化县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页。
①巫罗俊除《宁化县志》此记载外,不见于其前诸史籍:参见[清]王捷南:《闽中沿革表》卷五,“长汀县”,道光十九年刻本。载陈支平主编:《台湾文献汇刊》第五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年
②黄向春:《“畲/汉”边界的流动与历史记忆的重构——以东南地方文献中的“蛮獠——畲”叙事为例》,《学术月刊》,2008年第6期,第145页。
③刘志伟认为,正是由于沙田区和民田区象征着不同的利益载体,因此两个地区的族群常常通过历史记忆来建构自己的身份,目的就是为了争取更多的资源。刘志伟:《地域空间中的国家秩序——珠江三角洲“沙田—民田”格局的形成》,《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14页。
④[汉]司马迁:《史记》卷六九,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186页。
⑤[汉]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第六》,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82页。
⑥[汉]班固:《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66页。
①[汉]恒宽:《盐铁论》上册,卷一《通有第三》,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41-42贞
②[唐]房玄龄:《晋书》,卷二六《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92页
③[唐]魏征:《隋书》,卷二四《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673-674页。
④[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一百九《禁岭南货卖男女敕》,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567页。
⑤《古田县志》,卷十二,万历年修,收入《万历福州府属县志》,福建文史丛书,北京:方志出版社,2007年,第187页。
⑥《八闽通志》:“林谞,闽县人博学,善讲贯,属文尤美。初尝俯从乡举,竟养高不仕,搜寻异闻,作《闽中记》十卷。”见[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六二《人物·文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⑦如《诗经·小雅·甫田》:“馌彼南亩,田畯至喜”;《诗经·小雅·信南山》“我疆我理,南东其亩”,“疆亩”即为划分疆界管理田亩之意;《尚书·梓材》“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陈修,为厥疆畎”参见葛培岭注译评:《诗经》,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91页、第189页;王世舜:《尚书译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75页。
①[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七十三《诗话前集》,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
②[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唐宋史料笔记》,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4页。
③饶宗颐:《潮州志》,新编第七册《民族志》,修于1946—1949年,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2005年重印,第3076页。
①[宋]祝穆:《方舆胜览》,卷三十六《梅州·土产》,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650页
②[明]莫尚简修,张岳纂:《惠安县志》,卷五《物产·谷属》,明嘉靖九年(1530年)刻本,天一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1年。
③[清]杨澜:《临汀汇考》,卷四《物产考》,第15a页。
④[清]唐赞衮辑:《台阳见闻录》卷下,《谷米·粳稻》,《台湾文献丛刊》第30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8年,第153页。
⑤[清]郝玉麟纂修:《广东通志》,卷之五十七《岭蛮志》,清雍正九年刻本,据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本影印。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辑,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1778页。
⑥[唐]魏征:《隋书》,卷三十一《地理下》,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887页。
⑦转引自朱洪,姜永兴:《广东畲族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3页。
①[清]梁绍献:《南海县志》,卷二十六《杂录下》,中国方志丛书,第50号,据道光十五年(1835年)刻本,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重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
②关丙胜:《边界缓冲区:催生新族群的温床》,《青海民族研究》,2009年第1期,第26页。
③[清]杨澜:《临汀汇考》,卷三《风俗考·畲民附》,第29b页。
④“被之声教”,可根据汉代班固《尚书·禹贡》所写:“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或唐代薛能《东都赋》中称:“穷览万国之有无,考声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烛幽。”
⑤“疆以戎索”出自《左传·定公四年》:“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杜预注:“大原近戎而寒,不与中国同,故自以戎法。”
①②[宋]刘克庄:《漳州谕畲》,载《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三,《记》,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
③《高皇歌》中阜老(或汉人)作为畲族的对立面而被描述,如:“千万男女莫作贱,莫嫁阜老做妻人。当初皇帝话言真,吩咐盘蓝四姓亲;女大莫去嫁阜老,阜老翻面便无情:皇帝圣旨吩咐其,养女莫嫁阜老去;几多阜老无情义,银两对重莫嫁其。皇帝圣旨话言是,受尽阜老几多气;养女若去嫁阜老,好似细细未养其。当初出朝在广东,盘蓝雷钟共祖宗;养女若去嫁阜老,就是除祖灭太公。”参见:施联珠,雷文先:《畲族历史与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88-390页。
①[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百三十《福建路》,《漳州风俗形胜》,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3766-3767页
②[宋]蔡襄:《莆阳居上蔡公文集》,卷十七《移福州乞依旧知泉州状》,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86,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47页。
③[元]脱脱:《宋史》卷四百一十九,《列传》第一百七十八《许应龙传》,第12554页。
④[清]周硕勋:《潮州府志》,卷三三《宦绩》,乾隆二十年(1755年)修,《中国方志丛书》第46号,据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重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
⑤[清]杨澜:《临汀汇考》,卷三《畲民附》,第29b页。
①[清]吴宜燮修,黄惠,李畴纂:《龙溪县志》,卷二十二《艺文》,第310页。
②[清]吴宜燮修,黄惠,李畴纂:《龙溪县志》,卷二十三《艺文》,第339页。
③[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三二《福建路·汀州风俗形胜》,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3787-3788页。
④[清]杨澜:《临汀汇考》,卷一《方域考》,第14a页。
⑤赵万里辑:《元一统志》,卷八《汀州路风俗形胜》,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631页。
①笔者所引的《太平寰宇记》是王文楚先生根据金陵书局本校勘,上文提到“汉路阻隔”,万历本、四库全书本、《嘉庆重修一统志·延平府》与引本同,但是宋版作“溪”。“漢”(汉)与“溪”字形相近,恐在传抄过程中,鲁鱼豕亥而发生错误按字面理解,“溪”路阻隔指的是地理交通受阻,说明在沙县一带存在“土寇”与汉人的地理边界;“汉”路阻隔,则说明闽西北间存在“土寇”与汉人族群边界。笔者推论:若按版本先后,宋版应更接近原本关于地理情况的描述,其后各版本欲将“汉”与“土”对应来写,表现的是“华夷有别”的民族观,反映了中国民族史深受大一统意识的影响。通过以上版本的修正,实际上也验证了族群边界演化的一个基本过程[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100,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999页、第2008页。
②[清]王捷捷南:《闽中沿革表》,卷五《长汀县》,道光十九年刻本,载陈支平主编:《台湾文献汇刊》第五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年。
③[清]杨澜:《临汀汇考》,卷一《方域考》,第14a页
④[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五九《唐纪》七五,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457页。
⑤根据谢重光先生研究,南宋时汀州,赣州城区一带虽然汇集了不少北方移民,由于北方移民文化的传播,在这两个郡城一带出现了类似于中原的语言风俗,但在汀、赣两州的广大乡村和山区,中原文化的传播还很微弱,梅州更是一派未开化景象参见谢重光:《宋代湘赣闽粤边区的社会变迁与民族新格局》,《宁德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第15页。
⑥[清]魏流等修,钟音鸿等纂:《赣州府志》,卷六十八《艺文志·明文》,中国方志从书华中地方第100号,据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刊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1238页。
①[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三二《福建路》,《汀州风俗形胜》,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3787-3788页。
②祁刚:《八至十八世纪闽东北开发之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第24页
③刘克庄在《木绵铺》中写道:“庵远人稀行未休,风烟绝不类中州。何须更问明朝路,才出南门极目愁。”参见[宋]刘克庄:《木绵铺》,载《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十五,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
④谢重光:《客家文化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11页。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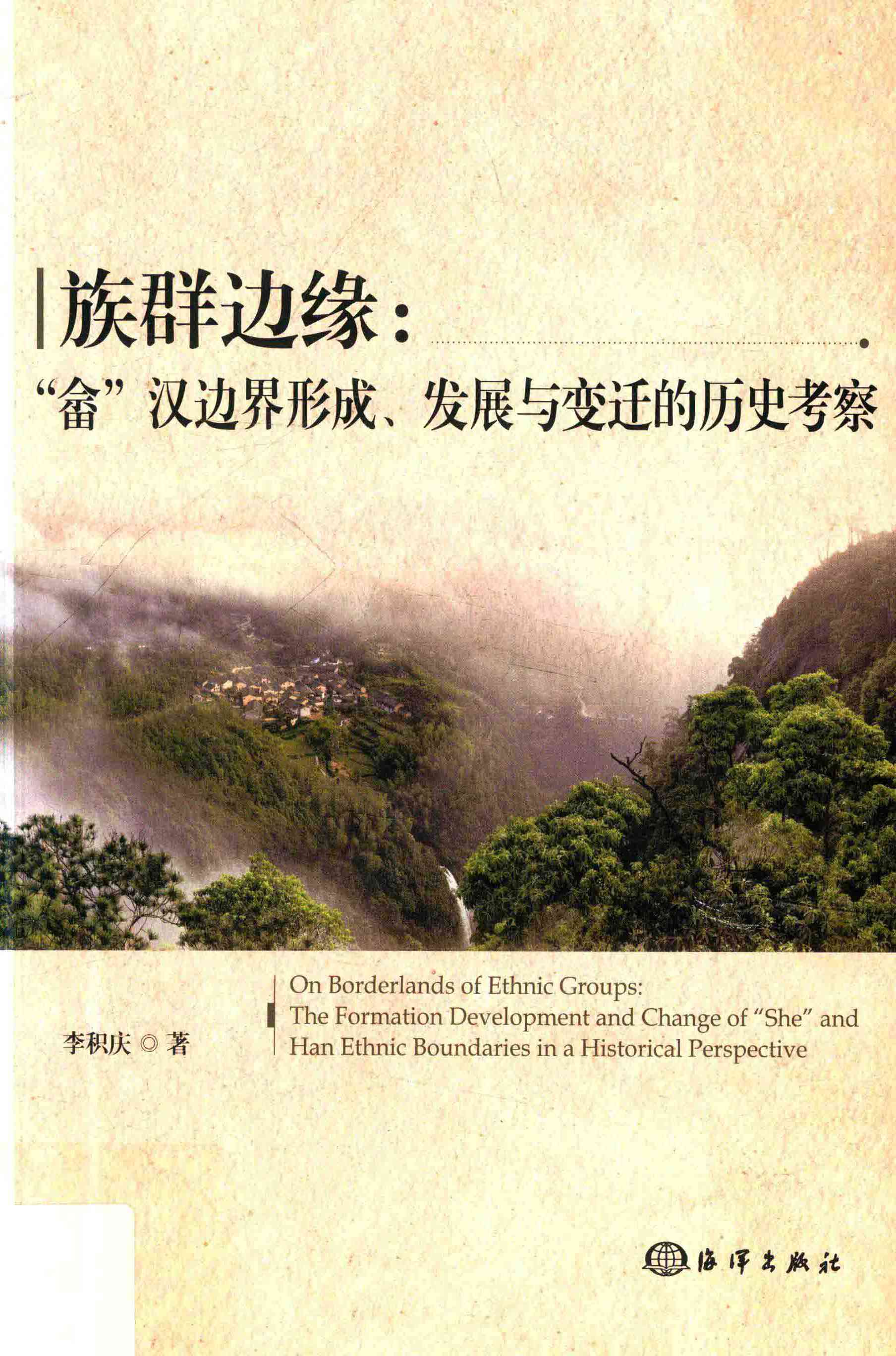
《族群边缘:“畲”汉边界形成、发展与变迁的历史考察》
出版者:海洋出版社
本书从族群边界的理论角度,重新审视畲族形成、发展、变迁的历史过程。在承认族群客观历史文化的同时,重点研究历史上“他者”(主要是汉族)对“畲”的社会定义以及“自者”(主要为南方非汉族群)自我族群认同的过程,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现实意义。
阅读
相关地名
宁德市
相关地名